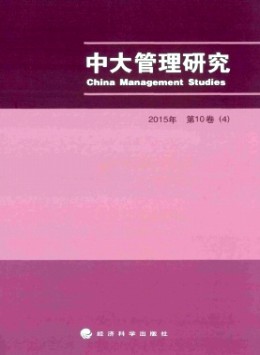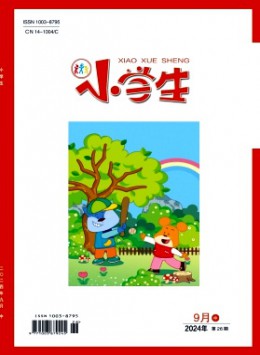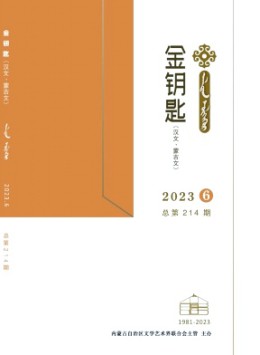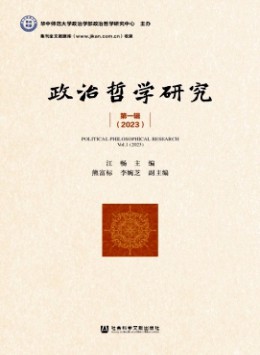多元系統理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多元系統理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偵探小說(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說中一個新的類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以翻譯偵探小說著稱的周桂笙說:“偵探小說,為我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周桂笙,1904:3)。作為中國翻譯小說的一種類型,偵探小說在近代譯介較早,1896年至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最早翻譯了柯南·道爾的四篇福爾摩斯探案,并刊載在《時務報》上,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隨后,許多外國偵探小說家如愛倫·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奧(MileGaboriau)、鮑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陸續被翻譯過來。到1911年左右,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一遍,其數量之多,用阿英的話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小說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據資料顯示,當時投身這股翻譯偵探小說熱潮的譯者有程小青、孫了紅、周桂笙、悉若等數十人,其中不乏林紓,周瘦鵑等翻譯大家。由此可見,域外小說中偵探小說的翻譯在當時尤其風靡。
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學者伊塔瑪·埃文一佐哈爾(Itama Even-Zohar)于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一種理論。該理論以俄國形式主義文藝理論為基礎,汲取了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
一 晚清偵探小說的譯介
晚清時期,翻譯活動明顯比創作活動活躍,“就翻譯書的數量,總有全數量的三分之一99(阿英,1980:180)。陳平原也認為,1896-1916年這20年間出版的小說“具體數字很難準確估計,但這20年小說出版中譯作占壓倒優勢,卻是明顯的事實(陳平原,1989:29)”。當時的翻譯文學在中國文學多元系統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發揮著比創作小說更為重要的影響。翻譯偵探小說作為當時翻譯小說的主流之一,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占據了主流的地位,其“數量之多(約占全部翻譯小說的四分之一)、范圍之廣(歐美偵探名家幾乎都有譯介)、速度之快(翻譯幾乎和西方偵探小說創作同步)”(郭延禮,1996:81)、影響之深在當時翻譯小說界可謂是名列前茅。
二 晚清偵探小說翻譯熱潮之緣由
在當時,偵探小說翻譯熱潮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本身的藝術內容與形式:它內容新穎,“給中國讀者提供了全新的閱讀體驗”(劉揚體,1997:281);另一方面,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背景都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偵探小說在當時的繁榮是晚清社會政治文化因素與譯作之間互動選擇的結果。
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三種條件下會在目的語的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下面我們將針對這三種條件分別探討分析。
1. 第一個條件——晚清時期新小說處于建立中
清朝末年,大多數具有改良意識的文人將文學作為政治改良和社會變革的手段,梁啟超等竭力倡導“文學救國”,提倡譯介西方小說,以作為開啟民智的工具。晚清偵探小說大量譯入以致形成偵探熱,大約是在1907年之后,到五四時期達到頂峰。由于當時中國所處的內外交困的歷史環境,人們痛感科學力量的偉大,“迫切想在政治小說中祈望新的民主體制,在科學小說中領略科技的魅力,在偵探小說中獲得公平法制”(張萍,2002:53),而且晚清時期正好是中國傳統的文學體系行將崩潰,而新文學體系又尚未完全確立之際(1919年爆發的五四為中國新文學體系真正確立的分水嶺),翻譯文學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承擔起了啟迪民智的作用。 2. 第二個條件——晚清小說處于弱小狀態
小說這一文學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學多元體系中一直是邊緣化的角色,屬于“小道”,寫小說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正是因為中國本土小說長期處于邊緣和弱勢的地位,它們不具備足夠的影響力來對翻譯小說進行限制和打壓,只能放任它們泛濫流行。
傳統小說的弱小使得它無法擔負起當時的社會環境賦予小說的任務——改良圖志;因此,梁啟超等人倡導“小說界革命”,正是要借助于域外小說的力量實現新文學的發展,從而改變國家的落后地位,翻譯文學在當時就一躍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主流,占主導地位。
3. 第三個條件——晚清傳統文學受到沖擊,處于轉折點
晚清翻譯小說的可以說是隨著“小說界革命”的興起而來臨的。梁啟超在1902年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飲冰,1989)。把小說視為“改良群治”,救國救民的關鍵,雖說只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延續,但前人多對此不甚重視,梁啟超等卻借此提倡小說。但是他們所提倡的新小說卻不是中國原有的古典小說,因為中國傳統小說為“中國群治****之總根源”(飲冰,1989)。至此,中國原有的傳統小說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真正意義上的新小說又尚未誕生,所以外來的翻譯小說自然進入了梁啟超等人的視野。要“改良群治”,自然要借助翻譯小說,因此域外小說變得身價百倍。在這股變革洪流中,原以詩詞歌賦為文學正宗的傳統文學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正在處于佐哈爾所說的何去何從的轉折關頭。當形式新穎、內容扣人心弦的外國偵探小說介紹到中國時,國內讀者的注意力為之吸引,促使了翻譯熱潮的產生。
第2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論文關鍵詞:新疆外宣英譯,多元系統理論,邊緣性,充分性,本土化
一、引言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 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二、理論簡介
多元系統理論是埃文· 佐哈爾與20世紀70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他認為語言、文學、政治、意識形態等是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的混合體,他們共同構成一個多元系統。這個多元系統是動態的、異質的、系統的。他描述了動態分層和系統產品,還強調系統的歷史性,不能把歷史事物錯誤的看作一系列互不相關的事件(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本土化,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英國當代翻譯理論家西奧·赫曼斯(2004)繼續發展了多遠系統理論,他認為圖里的規范提醒我們,譯文不可能與原文同一,譯者的介入無法避免,無法被清除。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隨后張南峰(2002)、謝天振(2002)、廖七一(2004)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張南峰教授認為“多遠系統理論是跳出文本外對翻譯進行研究”,謝天振教授評價說,“該理論對中國漢譯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辜正坤,劉宓慶結合該理論形成了新的翻譯理論假說。該理論擺脫了以往僅從語言學角度解讀翻譯的缺陷,翻譯活動推向了前臺,放在大的社會環境中進行探討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雖然有極個別的作品,如《福樂智慧》《江格爾》等被外譯,也是由他國人根據他們的需要節譯的。新疆外宣英譯在新疆翻譯史上處于邊緣地帶。
直至90年代,隨著國家倡導以開發新疆的旅游資源帶動全區的經濟發展,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福樂智慧》。隨著新疆英語教育和對外的發展,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新疆電視臺也有了自己的英語頻道,新疆各地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與2001年起本土化,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語言與翻譯》,《新疆大學學報》及全國其他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地名,新疆旅游,新疆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英譯初出茅廬,在中國外譯系統中還處于邊緣地帶,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新疆外宣英譯也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而發展起來。
2.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縱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中國發展新疆的以旅游為先鋒帶動全疆經濟發展(鄧新民,2000)的政策上。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和錯誤的解讀。如:though 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 Levinson,KienChristenson,1999)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而整句話更反映出他所在的意識形態對新疆心懷叵測的政治意圖。而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自己的家鄉的立場上清楚明了地給以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1998)。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譯者在進行外宣英譯時,應了解外國人對我國外宣英譯的普遍的態度.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我國讀者喜歡的華麗抒情性的文體,在外國人看來只能是減少傳播的清晰性和效果,甚至被認為是空洞和冗長,夸大宣傳。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 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本土化,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還不如直接告訴那一年的時間為好。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與漢語的隨后有一定的差別,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將讀者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薩義德),這樣就不能按照尤金·奈達所謂的“譯者必須完全滿足讀者的需求”來進行翻譯,而是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本土化的翻譯是楊憲益在英譯《紅樓夢》時保留的風格,他認為宣傳自己的文化就是要保留自己文化中最本質的東西。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本土化,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就要如實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其一來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的捏造,其二讓的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Xinjiang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a little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 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wells connected by 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unique landscape.(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還需處理好在原文與意識形態,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參考文獻]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11.1:53-72,1990.
[2]David Levinson,Kien Christenson,Xinjiang,Encyclopedia of Modern Asia, Volumn 6,1999.
[3]Toury ,G,DescriptiveTranslation Studies and Others[M] .
[4]陳世民.新疆現代翻譯史[M]. 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
[5]段連城.對外宣傳理論初探[M]. 中國建設出版社,1988.
[6]鄧新民.推動旅游發展,促進西部開發[J]. 旅游,2000,4.
[7]辜正坤.當代譯學建構理論略論[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姜秋霞.文學翻譯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作用關系研究[M].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
[9]廖七一.多遠系統[J]. 外國文學,2004,4.
[10]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11]熱扎克·買提尼亞孜.西域翻譯史[M]. 新疆大學出版社,1997.
[12]唐立久,崔保新.發現新疆[M].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13]謝天振.多元系統論[J]. 中國翻譯,2002.
[14]謝旭升.特色漢英翻譯教程[M]. 新疆大學出版社,2009.
[15]余言,向京.中國新疆事實與數字[M]. 五洲傳播出版社,2009.
[16]張南峰.多元系統論[J]. 中國翻譯,2002,4.
第3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關鍵詞:多元系統;局限性;自我擴展;辨析
中圖分類號:H0-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1)32-0208-01
埃文-佐哈爾( Itama Even - Zohar)的多元系統理論作為許多描述性翻譯理論的基礎被廣泛應用,研究者們也對其的局限性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梳理各家所謂局限性的同時,認真研讀多元系統理論,并且將其看作一個不斷發展的理論系統,從這一角度對它的局限性做一個辨析。
一、多元系統理論簡介
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直到90年代末,該理論才被真正介紹到中國學術界來。佐哈爾吸取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一般系統理論與文化符號學的積極因素,將翻譯文學視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子系統,客觀描述翻譯文學在主體文化中的接受與影響,以期有效揭示制約文學翻譯的規范與規律。
多元系統理論將翻譯研究從傳統的對文本進行孤立、靜止的對比中解放出來,不以價值判斷為準則對譯本進行研究,而是著重對翻譯實踐活動的描述、揭示和認識,是一種比較超脫的純學術研究;幫助我們更深刻地審視和理解文學翻譯,并讓我們看到了文化譯介過程背后的諸多因素;對翻譯文學的闡述也為我們研究翻譯文學提供了多個切入點,并對翻譯史上的一些現象作出了比較圓滿的解釋。還讓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學翻譯中的“充分性”問題。(謝天振:2003)
如上所示,多元系統理論在中國學術界傳播的過程中,研究者們認識到了其對翻譯研究的貢獻,而與之相對的,也有不少批評之聲出現。
二、多元系統理論局限性梳理
現在,我們來梳理一下對多元系統理論局限性的討論。根據各類資料,我們大致可以將對局限性的討論分為以下三類。
(一)忽視了譯者主體性
許多學者撰文指出,多元系統在解釋某些翻譯現象時顯示出不充分性,其原因在于忽略了譯者主體性。王東風在其文章中寫道:“這一理論只考慮了制約翻譯策略選擇的客觀文化因素,而忽視了作為翻譯主體的人的主觀能動性。”(王東風:2000,謝世賢:2002)。很多學者認為,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不僅僅由出發語文化在世界文化大系統里所處的地位決定,同時也深受譯者對譯語文化主觀判定的影響。(吳耀武, 張建青:2010)
例如,在清末民初,翻譯文學處于中國文學系統的中心地位,根據佐哈爾的理論,翻譯中應傾向于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然而梁啟超、嚴復、林紓等人在譯介外國小說時多采用歸化策略,譯作中多有刪節、改寫,并采用中國文學傳統形式和結構。1915年,龐德的《華夏集》問世,當時的中國尚處于半殖民社會,而美國則處于強勢地位,據佐哈爾理論,此時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為英文時,應采取歸化策略,而龐德作為處于強勢文化中的人,在譯介中國古詩時卻采用了歸化策略。
以上例子說明了多元系統在解釋翻譯現象時只考慮到了宏觀的客觀文化因素,忽略了譯者本身的詩學觀和主體性。
(二)對超文本因素關注不足
有人認為,在研究翻譯文學在文學系統中地位時,佐哈爾對影響經典與非經典、中心與邊緣,一級與二級的意識形態社會、政治等因素缺少深入分析。
正如根次勒所言,佐哈爾很少將文本與文本產生的“實際情形”聯系起來,而只是將文本與那些假設性的結構模式和抽象的概括加以關聯。因此超文學因素在佐哈爾的分析之中明顯缺場。(Genztler, 1993, 123)
(三)概括的簡單化、絕對化傾向
蘇珊?巴斯奈特認為佐哈爾對文學系統狀態的描述“有些粗糙”;赫曼斯認為佐哈爾對“弱小”、“邊緣”的評價性的陳述“并不明晰”,對系統演進的描述不僅非常抽象,而且給人決定論的感覺,似乎系統的演進是自主和周期性的。最后,佐哈爾將系統內部的變異完全局限于二元對立的因素,忽略了“所有那些模棱兩可、混雜、不穩定、流動易變和交叉……的因素”。(廖七一:2004)
三、多元系統理論局限性辨析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其局限性進行辨析:
(一)多元系統理論的立論原則
多元系統理論認為,各種社會符號現象,應視為系統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這些系統是由若干個不同的子系統組成的系統,子系統各有不同的行為,卻又相互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而運作。任何一個多元系統里面的現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須同整體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這個人類社會中最大的多元系統中的現象聯系起來觀察。(埃文-佐哈爾,張南峰譯,2002)也就是說,多元系統在本質上是“異質的”、“動態的”。佐哈爾強調,他創造“多元系統”這個術語,就是要明確表達動態的、異質的系統觀念,和共時主義劃清界限。(廖七一,2004)
第一,多元系統理論在歸納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的地位時也指出,翻譯文學自身也是有層次的,自身也有經典和非經典,中心與邊緣,一級和二級的不斷斗爭。“這意味著當一部分翻譯文學可能取得中心位置的時候,其余的翻譯文學仍處于相當邊緣的地位”。其異質性的理論本質本身就能很好地解釋由于譯者本身詩學觀和主體性,在同一社會同一時期出現不同翻譯選擇和策略的情況。
第二,多元系統理論在其立論和思維方式上也潛在地包含了大系統中相互影響的各種因素。佐哈爾在做出理論假設后,以文學系統為對象進行分析,他在《多元系統論》中說到,“必須承認,由于研究開放的系統比研究封閉的系統困難,十分詳盡的分析有可能做不到。”(埃文-佐哈爾,張南峰譯,2002)但這并不說明他將其他系統的影響排除在外。佐哈爾用以描述文學內部系統的規則也同樣適用于描述文學與超文學系統之間的互動關系。(廖七一,2004)
第三,如果對多元系統理論所強調的動態性多加關注,就應該認識到這一理論是將各系統的運動以及之間的張力和斗爭作為研究對象的,如經典化文化和非經典化文化之間的張力,動態的經典性,一級與二級模式的斗爭和相互轉化。
因此,佐哈爾是充分認識到系統內部和系統之間運動和變異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的,而出于理論論述的需要,對研究結果做出了歸約性的概括,并不能說多元系統理論本身屏蔽了各種現象的紛雜性。
(二)多元系統理論的自我擴展
多元系統理論的優點在于留下自我擴展的空間。
佐哈爾于一九七七年修正了多元系統假設,使其能進一步容納文學與社會內部的經濟因素之間的關系。(廖七一:2002)還有一些學者對系統概念進行了重要補充,如圖里、切斯特曼的翻譯規范,赫曼斯的操控理論和勒弗維爾的重寫概念(歸納了意識形態、贊助人和詩學三因素的制約),以及韋努蒂的文化翻譯觀(凸顯譯者主體性)。國內的香港學者張南峰也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精細版”,對佐哈爾多元系統理論中政治、意識形態、經濟、語言、文學和翻譯相互作用方面做出補充與完善,并在專著中演示了其應用。
四、結論
多元系統理論把翻譯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將翻譯與譯作所產生和被閱讀的文化語境、社會條件、政治等許多因素結合起來,為翻譯研究開拓廣闊的研究領域。(謝天振:2003)應該指出的是,在看待多元系統理論時,不僅僅將其看作單個人(Even-Zohar)的理論,而應視為一種動態發展、不斷完善的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1]埃文-佐哈爾.多元系統論[J].張南峰,譯.中國翻譯,2002,23:19-25.
[2]廖七一編著.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M].江蘇:譯林出版社,2002:59-65.
[2]廖七一.多元系統[J].外國文學,2004,(4):48-52.
[3]王東風.翻譯文學的文化地位與譯者的文化態度[J].中國翻譯,2000,(4):2-8.
[4]吳耀武,張建青.佐哈爾多元系統翻譯理論的批評性闡釋[J]. 外語教學,2010,(3):110-113.
第4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今天,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其中文學翻譯事業成為維系國家之間關系的有利保障,為了更好的促進國家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帶動經濟、文化、社會的發展,本文站在多元系統理論的視角下,對文學翻譯策略進行研究,下面我們就開始探究工作。
關鍵詞:
多元系統;文學翻譯;策略研究
一、多元系統論視角下對文學翻譯的概述
所謂“多元系統”就是指由社會各種相關系統共同構成的多元化系統模式,其中包括文學系統以及與文學相關的其他系統。在多元系統視角下,國內外的文學翻譯事業對其有了更好的應用,并且產生了一定的積極影響,為翻譯研究工作帶了有利的幫助。在多元系統理論的視角下,如果一個民族在文化方面具有強勢的地位,這就屬于強勢文化,而翻譯文學就相應的處于弱勢地位,在進行文學翻譯工作時多采用歸化式的研究策略,相反的如果一個民族在文化上處于弱勢地位,那么在翻譯文學中的強勢地位,要求翻譯人員采用異化式的翻譯策略。
二、多元系統論視角下關于文學翻譯策略的探究
文學翻譯策略針對翻譯工作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翻譯工作中應當遵守的翻譯原則和規范性方式,翻譯策略對翻譯工作有著一定的積極性作用,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文學翻譯策略也是一種行為方式。在翻譯的過程中,為了實現較好的翻譯效果,需要采取多樣性的文學翻譯策略,歸化式的翻譯策略和異化式的翻譯策略不是文學翻譯策略的全部,但卻占有較強的地位。下面我們來舉例說明歸化式翻譯策略和異化式翻譯策略。以《簡愛》為例,由于這本著作的優秀,先后被多個國家翻譯,但是不同的翻譯版本,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樣的,下面我們來列舉兩個翻譯的不同版本,通過對比說明多元系統論對翻譯策略的影響。首先我們來說異化式的文學翻譯策略,這種翻譯方式主要側重于譯文的貼切程度,使用這種方法在翻譯的過程中大量的保留了原本歐式風格,翻譯工作人員在注重原文語言風格的情況下,為讀者提供了一種來自異國的語言風格和情調,讓讀者有更貼切的感受;接下來我們說歸化式的翻譯策略,相對異化式翻譯方式,這種翻譯方式與其有很大的不同,它側重于行文的流暢程度,貼近中國文化中遣詞造句形式,這樣方便讀者進行閱讀,不僅看著舒服還有順暢感,這是一種典型的歸化式翻譯策略。
三、多元系統論的不足之處及對文學翻譯策略的啟示
以上我們對多元系統論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們來闡述一下多元系統論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從客觀的角度出發,西方文化具有強勢的地位,然而我們的中國文化卻處于劣勢的地位,在整個世界化的大系統內,中國文化沒有凸顯出自己的優勢。在佐哈爾的提出的多元系統論中,中國的翻譯文學理應處于中國文學多元系統匯的中心位置,翻譯工作者也應當相應的采用異化式的翻譯策略,但是就實際的情況來看,多元系統論存在自身的不足之處,它忽略了文學翻譯主體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地位,沒有較好的發揮自身的能動性作用。為了更好的促進文學翻譯工作的發展,下面我們講述幾點針對翻譯策略的啟示:
(1)在進行文學翻譯的過程中,僅僅應用一項翻譯策略是遠遠不夠的,為了更好增強翻譯效果,可以利用刪節、增評、加按語評注等方式來增強翻譯的效果。其中刪節是指有選擇地翻譯文本,大膽的刪去一些對文本無關系的部分,比如在一些書籍的題目上有所應用,《EvolutionandEthicsandOtherEssays》利用刪節的翻譯方式后就被簡便的翻譯成《天演論》;增評是指根據實際的翻譯需要,增加一些語句和翻譯內容,將增評性的文字添加到翻譯中,有效的表達出自己翻譯上的見解;加按語是指在翻譯的過程中在文章的結束部分或者是中間部分增加一些按語,為文學翻譯工作帶來一些便利,便于讀者更好的理解文章內容;評注的意思就是在翻譯的過程中,遇到一些難理解或者不好解釋的詞或語句,通過注釋的方式為讀者提供閱讀的方便,以上說的這四種方式都是增強翻譯效果的有效途徑,它們都屬于歸化式翻譯的范疇。
第5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文化學翻譯;對比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學翻譯學
翻譯的文化轉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討會。這次會議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統理論的學者與歐洲其他地區的學者集中到一起,會上Lefevere指出翻譯的目標應該是發展綜合性的能夠指導翻譯產出的理論,這種理論對文學與語言學翻譯理論的構建都有幫助,這一理論是動態的,不斷演變的,時刻接受實踐的檢驗,理論與實踐并行不悖,相得益彰,這一理論指導的翻譯實踐將會影響譯語文化的發展。Lefevere的這一言論奠定了翻譯研究下一個發展階段的基本原則,Lefevere言論的核心是反對傳統的評判式的翻譯立場,拒絕把翻譯研究單純定位于文學或語言學領域,這開辟了翻譯研究的獨立空間。最先在文化翻譯領域進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統理論學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創造了多元系統這一名稱。他指出,譯作與多元文學體系的關系不能簡單定位于次要與主要,或從屬與支配的關系,而是依據文學體系的具體情況而變化。
文化翻譯領域的另一學派――文學翻譯的操控學派在某種程度上與多元系統理論異曲同工。這一學派把翻譯定位于比較文學的一個下屬分支學科,其代表人物有荷蘭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國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學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經指出:“從目標文學的角度出發,所有的翻譯都隱含著為實現某一目的而對原文的某種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學操控學派一開始是和語言學翻譯學派針鋒相對的,不追求嚴格的對等而追求某種程度的操控。
概括來說,文化翻譯注重翻譯與譯語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關系,關注翻譯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在譯語社會中的巨大影響和作用。
與語言學翻譯觀相比,文化翻譯觀以譯文為重心,強調譯者的能動作用,重視文化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以及翻譯對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譯觀把關注的焦點轉移到翻譯的結果,把翻譯的結果放在社會文化語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側重文化交流與融合,并關注動態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譯文較為靈活,譯者的作用可以充分發揮。文化翻譯觀以雙語文化為取向,根據交流的需要,偏重譯語或原語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異性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性,積極進行交流與融合。
二、生態翻譯學
生態翻譯學是一個由中國學者首倡的翻譯研究的學問,是近年來在翻譯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構建的又一新穎嘗試。2001年以來,胡庚申教授通過其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及數十篇論文的深入論證,已基本確立起一套以生態學視角進行翻譯研究的話語表述方式、評估語言、評估方式和評估標準。
生態翻譯學的確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國翻譯》上發表的“生態翻譯學解讀”一文為標志;2010年11月在澳門舉行的“首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討會”,更是讓學者們看到生態翻譯學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生態翻譯學在不斷充實和完善。然而這一理論的出現和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順應各種趨向、適應翻譯研究各層次生態環境的成果。
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主張用整體、立體、動態的眼光看待翻譯行為,探討翻譯生態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發展基本規律,從生態視角描述和解釋翻譯活動和翻譯現象及其成因,是能夠對翻譯本體做出新解的翻譯理論范式。生態翻譯學的代表人物是清華大學的胡庚申教授。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 所謂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翻譯生態環境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生態翻譯學所遵循的翻譯原則一方面是“多維度適應”,另一方面是在多維度地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做出與翻譯生態環境相適應的“適應性選擇”,即概括為:“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具體來說,“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翻譯原則,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原則上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度地適應,繼而依此做出適應性地選擇轉換。生態翻譯學認為,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所謂“整合適應選擇度”,是指譯者產生譯文時,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維度適應”和繼而依此、并照顧到其他翻譯生態環境因素的“適應性選擇”程度的總和。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某譯品的“多維度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適應選擇度”也就越高。在翻譯的重心上,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以譯者為中心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的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具體來說,翻譯過程是譯者對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和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譯者為中心”是以突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為目的,以從譯者為視角對翻譯活動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為途徑,以彰顯譯者主體、發展譯者能力為特征,以譯者為終極關照的翻譯觀。“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使譯者真正成為“主宰”者,從而名正言順地由譯者來主導翻譯活動的全過程,以至“譯有所為”地創生譯文、影響譯語的文化和社會。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生態翻譯學在很多方面與文化學翻譯學存在一致性,是對文化翻譯學研究范式的繼承,但同時在很多方面,生態翻譯學又是對文化翻譯學的發展。生態翻譯學在理論基礎、基本理念、翻譯實質、翻譯過程、翻譯原則、翻譯方法和譯評標準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語言文化的范疇,把翻譯置于整個社會的大生態環境之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雖然生態翻譯學的發展才不過十幾年的時間,但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具有不同于傳統譯論的理論體系,并在不斷完善與發展。
參考文獻:
[1] 胡庚申.從譯文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應用例析[J].外語教學,2006,(4):50-55.
[2] 胡庚申.從術語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觀[J].上海翻譯,2008,(2):1-5.
[3] 孫紅梅.語言學翻譯觀與文化學翻譯觀之對比淺析[J].高等函授學報,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
第6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關鍵詞:翻譯規范、哈利波特與死亡圣器、大陸譯本、臺灣譯本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4)01-0000-01
1.引言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迅速發展起來。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統理論。他用一種描述性的以目標語為中心的,關注功能和系統的方法來進行翻譯研究。從此,翻譯研究開始從純理論研究走向文本描述。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Toury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的描寫翻譯研究理論。Toury(1995:21-112)認為,如果翻譯研究不想依靠語言學等其他學科并自身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那么它必須發展一種描寫性方法。Toury提出了著名的翻譯規范理論。它通過對譯者翻譯行為趨勢的描寫和研究來構筑翻譯研究的理論體系,并將其運用到翻譯實踐和翻譯相關活動中,作為理論指導。
本文選擇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和臺灣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第七本兩個版本作為文本分析對象,分別從三個翻譯規范的角度研究并比較了大陸和臺灣兩個中文譯本在各個層次上的翻譯規范。
2.預備規范
預備規范包括翻譯方針的選擇以及翻譯的直接程度,是翻譯行為開始前影響譯者的宏觀因素。
我們來看一下大陸的翻譯版本及其譯者。在哈利波特的前六本的譯本中,由于譯者在不斷變換,我們會發現譯作中出現主人公名字前后不一致、作品風格截然不同等問題。為了在作品風格和語言上達到高度一致,哈利波特系列小說第七本的翻譯決定交由翻譯經驗豐富的馬氏姐妹。由于馬愛新在國外,兩姐妹經常通過電話郵件等方式進行溝通,翻譯出來的第七本也大受歡迎。
臺灣系列譯本,前三本是由彭倩文所譯。彭倩文也翻譯過許多兒童文學作品,包括Peter Carey的Jack Maggs,Thomas Keneally的Schindler’s List等。后三本由彭倩文為首的團隊翻譯。
J.K.Rowling的哈利波特系列主要的受眾群體是兒童,所以原文語言淺顯易懂,簡單活潑,便于兒童理解和接受。因此,譯文的總體風格應與原文保持一致,采用平實簡單的語言,但又要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兩本譯文在這一點上都把握住了基本方向。
3.初始規范
初始規范是譯者自身的宏觀選擇,確定譯文究竟是傾向源語規范還是目的語規范,是更注重譯文充分性還是可接受性。
Example 1:
Lupin,greyer,more lined; …… and Mundungus Fletcher,small dirty and hangdog,with his droopy,basset hound’s eyes and matted hair.
馬譯:盧平,更加憔悴瘦削;……蒙頓格斯?弗萊奇,小個子,邋里邋遢,一副猥瑣樣,眼皮像短腿獵犬那樣耷拉著,頭發蓬亂糾結。
彭譯:路平頭發更白了,臉上的皺紋也更多了;……還有矮小骯臟、鬼鬼祟祟的蒙當葛?弗列契,一雙無精打采的短腿獵犬眼睛和一頭缺乏光澤的頭發。
在描寫Lupin的時候,“greyer,more linked”被分別翻譯成了“更加憔悴瘦削”和“頭發更白了,臉上的皺紋也更多了”。這樣看來,大陸版本的描寫稍顯抽象,臺灣版本的描寫更加具體形象,就更容易為年輕讀者們接受。
但在這里,我想指出的是同一譯者在翻譯同一部作品的過程中有可能從以源語規范為主轉換到以目的語規范為主,反之亦然。這就說明翻譯規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在考慮多種現實因素的情況下,可以不斷進行選擇。張南峰就曾指出:“翻譯等比較復雜的活動,可供選擇的行為比較多,例如一個詞或者句子怎么譯,甚至有無限的可能性”(2008:116)。總而言之,翻譯是一個靈活多變的過程,譯者也要具備隨機應變的能力。本文所討論的哈利波特第七本的兩個譯本在其所在地區都大受歡迎,可以說達到了可接受性和充分性的要求。
在翻譯開始前,預備規范和初始規范決定了譯者的宏觀策略。而在翻譯開始之后,則由操作規范影響譯者的微觀策略。
4.操作規范
操作規范涉及翻譯過程中具體翻譯策略的選擇,可分為結構規范和語篇規范,屬于影響翻譯作品的微觀因素。語篇規范包括語言規范和文學規范;結構規范主要是指譯者在翻譯中對原文本的增刪、搬移和重組。
譯者為了迎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通常會對原文本進行省譯、增譯和改譯。在JK羅琳創作這部作品的十年中,很多當年的小讀者都已經長大,同樣作品中的主人公們也長大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話,如果說第一本是一部兒童文學作品,那第七本就是一部青少年讀物。作品的內容也從歡快喜悅的魔法世界變成了與邪惡勢力作斗爭的危險經歷。第七本書的風格更加嚴肅沉郁。因而譯者也會采用更加正式的詞匯來描寫主人公,來敘述整個故事。
在結構規范上,譯者會根據目的與文化的習慣,對源語文本進行省譯、增譯和改譯。總體來說,目的語規范對譯者策略的選擇起著主要作用。
語篇規范包括文學規范和語言規范,前者主要指譯者決定用什么來翻譯某種體裁、某種文學作品,后者則包括一般的語言或文體規范。
Example 2:
‘Genius!’yelled Harry.
馬譯:“你太有才了!”哈利喊道。
彭譯:“真天才!”哈利喊道。
“你太有才了”這句話2007年春節聯歡晚會后變成了熱門詞匯。臺灣版譯成“真天才”,只是將意思平實地表達出來。可以說,馬譯在這里更加的本土化,不僅具有充分性也有可接受性,而彭譯只照顧到了后者。
在語篇規范上,臺灣版和大陸版譯本語法上盡量保持對源語文本的充分翻譯,以學習英語語言規范,完善漢語;另一方面為了內容的傳達以及譯文的可接受性起見,又無法擺脫漢語的語言規范,在一定程度上仍傾向目的語的語言規范。
5.小結
總的來說,大陸版本的中文譯本更加傾向于源語語言規范,比起可接受度來說更具充分性。相比而言,臺灣版本譯本以目標語語言規范為主,更具可接受性。但兩個譯本都比較忠實,譯者的意圖都得到了較好地實現。
翻譯研究正在從規范性翻譯研究走向描寫翻譯研究,規范性的翻譯研究更多的是微觀的研究,不夠全面。翻譯研究還應該有另一個視角,也就是宏觀的視角。兩者并不矛盾,兩者應該結合起來,這樣的翻譯研究才能揭示翻譯的全部。
References:
[1] Rowling,J.K.2007.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 Toury 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J].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3] 皇冠編譯組譯.哈利波特―死神的圣物[M].臺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7.
第7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關鍵詞]《紅樓夢》 生態翻譯學 適應 選擇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7-0064-02
作為四大古著之一,《紅樓夢》不僅有著深厚的文學價值,還是一本濃縮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目前學術界對《紅樓夢》英譯本比較認同的有兩部,一部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另一部則是大衛?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譯本(下文將分別簡稱為楊譯本和霍譯本)。縱觀幾十年來《紅樓夢》的英譯研究,筆者發現,學者們已運用了包括功能對等理論、譯者主體性理論、隱形話語權、接受理論、目的論、多元系統理論、認知語言學等各種翻譯理論對兩個譯本進行了比較研究。本文將從一種全新的翻譯分析維度——生態翻譯學視角出發,通過兩部譯本比較的方法,分析翻譯如何以譯者為中心,從譯者的主體性出發,通過多維度適應與選擇來產生譯文,概括出生態翻譯學在《紅樓夢》兩種英譯本中的策略體現其對文學翻譯評析的重要意義。
一、生態翻譯學
生態翻譯學是關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互動的整體性研究。翻譯生態環境的要素包括原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即翻譯生態學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原文—譯者—譯文”的體系,以譯者為中心,從譯者的主體性出發,譯者通過多維度適應與選擇來產生譯文。
譯者的中心地位體現為譯者在翻譯前和翻譯過程中均進行了適應與選擇。在翻譯前,譯者對原文的解讀便是一種適應,根據自己立下的翻譯目的,結合出版社的要求,適應性地選擇出自己的翻譯標準、策略和風格。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進行“三維”轉換——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在轉換中,譯者要充分發揮主體性,適應性的選擇最恰當,最能體現原文思想和靈魂的翻譯。
二、譯者在翻譯之前的適應與選擇
(一)譯者對原文的適應與選擇
譯者對原文的適應就是對原文整體結構上的理解把握。沒有對原文的理解,就談不上譯者適應性選擇出的翻譯標準和策略。在理解適應的基礎上,譯者作為橋梁,要把握原作創作的時代背景,“設身處地”考量作者的意圖。下面便以《紅樓夢》的英譯書名為例,分析楊憲益和霍克斯對這部巨作的適應與選擇。
楊將書名翻譯為:A Dream of Red Mansions,霍則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楊憲益保留書名中的“紅”,將“樓”翻譯為復數“mansions”,用詞精準。首先,“mansion”的釋義為“a large, stately house”, 符合原著里描寫的大院豪宅。更讓人拍案叫絕的是,譯者對小說內容及背景的準確把握,因為《紅樓夢》主要圍繞著榮寧二府,楊憲益則采用復數形式,可謂傳神。而為了避免西方讀者對“紅”產生誤解,深諳中西文化差異的霍克思取《石頭記》作為譯本主書名,作為補償措施,以《紅樓夢》為別名,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 also known a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巧妙融合兩者在封面上。這既適應譯語文化和譯文讀者需求又照顧到原著及作者意圖(此譯文書名出現在第一、二、五卷)。《紅樓夢》是章回體小說,故而只有分章沒有分卷,霍克思出于對原書內容邏輯上的適應與選擇,在翻譯時創造性地按照小說的內容自行分為五卷,并根據每卷具體內容另行命名。例如第一卷覆蓋原文第1~26回,譯本命名為“The Golden Days”。譯文五卷本的卷名既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系,增強了譯本可讀性,減輕了讀者閱讀負擔。
(二)對譯者翻譯目的的適應
譯者在翻譯原文時,均會帶有不同的翻譯目的。楊憲益翻譯《紅樓夢》旨在向逐漸開啟中西交流的西方人傳播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帶有政治任務的。霍克斯則純粹出于個人愛好。霍克斯是個性情中人,崇尚文學,尊重具有才華的文學家。他說《紅樓夢》“是一位偉大作家嘔心瀝血的結晶”,他嘔心泣血只譯完前80回,而把后40回的翻譯交由他的女婿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完成。面對蘊含文化特色的中英譯時“楊譯本情系文化,霍譯本面向讀者”:楊譯本忠實于原著,完整地傳達了中國文化的價值觀;霍譯本則更符合英文習慣,不拘泥于原作的字句結構,很好地融合了雅致與創新。
(三)對出版社要求的適應
應企鵝出版公司的邀請,漢學家霍克斯于上個世紀70年代著手翻譯《紅樓夢》。企鵝出版公司的一貫風格就是要求譯文有很強的可讀性,要通俗易懂。霍克思將自己的翻譯靈感和翻譯方法發揮到極致,被公認為是“學術成分較少、英語讀者更加喜歡”的譯本。
楊譯本的市場定位則針對專業讀者,讀者群體就沒有那么廣。戴乃迭1980年評價《紅樓夢》翻譯時則表示:“我們的靈活性太小了。有一位翻譯家,我們非常欽佩,名叫大衛?霍克斯。他就比我們更有創造性。我們太死板,讀者不愛看,因為我們偏于直譯。”
三、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適應與選擇
(一)語言維的適應與選擇
霍譯本語言地道,活潑生動,多采用意譯,更符合譯入語習慣,易于讀者接受;楊譯本語言正式,措辭精美,多采用直譯,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民族文化傳播。兩本譯本都可堪稱是翻譯史上的佳作。筆者將從以下三個方面分析兩個譯本。
1.章回目錄的翻譯
第8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摘要:吉迪恩?圖里,是特拉維夫學派的創始人。他提出了翻譯規范理論,認為譯者在整個翻譯過程中主要受到源語文化規范和目的語文化規范這兩種規范的制約,這兩種規則就像兩個端點,譯者則應該在這兩端間動態地選取自己應該采取的規則。本文是在翻譯規范理論的基礎上探討實際翻譯中譯者的地位以及其現實意義。
關鍵詞:翻譯規范;翻譯策略;譯者地位
1.引言
圖里的翻譯規范理論對翻譯過程中翻譯策略的選擇做了描述性的規范,在此基礎上突出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前的研究大多是從翻譯規范的角度對譯本進行比較得出其中的翻譯策略,而關于譯者地位的研究也層出不窮,二者相結合更能理清譯者主體地位的,從而使譯者能夠更清楚自己的作用和使命,對現實翻譯中譯者地位的界定有著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2.圖里翻譯規范理論
描述性翻譯是建立在多元系統理論之上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圖里的描述性翻譯研究,而他還提出了“翻譯規范”的概念。圖里認為,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通常受到以下三種規范的制約1)預備規范(preliminary norms)是譯者對翻譯政策的選擇,考慮文本的文學類型、學派等等,或者是考慮直接還是間接使用源語來翻譯;2)初始規范(initial norms)是譯者在翻譯前決定使用什么樣的翻譯政策和翻譯取向,選擇是偏向源語還是偏向目標語;3)操作規范(operational norms),是譯者在實際翻譯過程中的行為選擇。操作規范之下又分為(1)母體規范(matricial norms),是譯者翻譯過程中是否使用源語以及使用某種間接語言的形式,以及決定增刪的程度,是具體到實際翻譯層次方面的選擇;(2)文本語言規范(textual linguisitic norms),是影響譯者最終選擇代替源于材料的內容,包括具體的句子結構。篇章設計等等細節上的環節。這里所說的翻譯規范,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關于忠實還是通順之類的翻譯標準的規范,而指的是譯者在翻譯時所受到的不同方面的制約,這些制約主要反映源語譯入語的社會文化,從而直接影響著譯者的翻譯決定。圖里將以上幾個方面稱之為翻譯規范(norms),這也是本文理論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3.翻譯規范中對譯者作用的界定
從一般意義上看,規范的作用不言自明,如果失去規范,不僅會導致行為的隨意性,也會使社會中的個體陷入迷茫沒有目標和方向。同樣的,在翻譯過程中,規范始終貫穿翻譯始終,圖里認為,規范就是那些被反復使用且經常是優先使用的準則,它既不是絕對的規則,也不是模糊的界定。對于不符合翻譯規范的譯文,既沒有對其明確的評價標準,對讀者也是不負責任的,也無法實現原作的客觀展現。對于譯者而言,其譯本得到廣大讀者甚至是原作者的認可,就必須仔細斟酌,首先譯者就必須熟知翻譯規范,并且在此基礎上將翻譯規范應用到實際的翻譯過中,讓翻譯規范發揮作用,使最終的譯本得以實現其自身價值,同時也能完整地體現出譯者的能力和思路。基于以上總結的翻譯規范的特征和翻譯規范的重要性,我們可以看出,譯文文本規范與否,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是否遵循了翻譯規范的基本原則,是評價譯文好壞的重要標準,因為譯者采取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譯文質量。這就說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究竟采取什么樣的翻譯策略,遵循怎樣的翻譯規范,最終的衡量標準就是讓譯本得到受眾的認可。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中心的取向是翻譯過程以及翻譯操作如何進行,具體到翻譯中,就涉及到譯者使用何種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只要涉及的是翻譯過程問題,是翻譯行為問題,是翻譯操作問題,那么,譯者的主體作用就蘊含其中。由此說來,譯者的主體地位毫無疑問。
4.譯者主體地位的現實意義
在翻譯實踐中經常會出現不同的譯者翻譯同一文本,可是出現的效果卻大相徑庭,譯入語讀者的反應也相差很遠。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譯者有不同的傾向性,是根據不同的翻譯規范選擇的翻譯策略。最終的譯作達到的效果如何,主要是取決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采取何種翻譯規范下的翻譯策略,這也是譯者最核心的使命和任務,是譯者作為兩種語言轉換媒介的主要功能所在。能否夠處理好譯者與“規范”的關系將直接影響著譯文的成功與否,也直接影響譯文受眾得到的閱讀效果。譯者要想將翻譯作為生存和發展的技能,就應該搞好翻譯的基礎,提升譯者本身的翻譯能力。一旦譯者主體地位這個說法成立之后,相應地,譯者在翻譯時的智力勞動和主觀創造性會受到肯定,這就使譯者的自進一步加大,但是與此同時譯者的責任(Venuti,1995:290)也就更大了。譯者不僅需要自重,還需要自律,特別是需要他律,可見,建立對譯者的相應的制約機制也就很有必要了。從譯者角度而言,譯者自身必須提高自己的知識素養和翻譯技能,從而符合翻譯職業的要求,捕捉語言之間的微妙差異并用適當的翻譯策略彌補,使譯本能夠被受眾更好地接受。只有做到了這些,譯者才是得到了解放。
5.結語
譯者作為整個翻譯活動的主體,占據主體地位,在整個翻譯過程中創造性地發揮其主觀能動的作用,因而譯者的主體性貫穿于整個翻譯的過程。從客觀角度而言,翻譯相關產業應得到相應的法規的制約,譯者的權益也應該得到相應的保障;從主觀角度而言,作為譯者本身,應該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多方面鍛煉自己的技能,從翻譯規范實際出發,制定合理的翻譯策略,充分發揮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作用,讓翻譯規范這個理論在實際翻譯過程中發揮出應有的指導性作用,讓譯者的主體性發揮的更加合理。(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參考文獻:
[1]Toury,Gideon.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Tel Aviv: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1980
[2]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269-273
[3]趙寧.特拉維夫學派翻譯理論研究概論[J].上海科技翻譯,2001(3):51-54
[4]謝天振.翻譯研究新視野[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3
第9篇:多元系統理論范文
亞里士多德曾在《詩學》中將詩學定義為組成文學系統的文體、主題與文學手法的總和。雅格布森指出詩學即“文學性”,也就是使一個語言信息成為藝術品的因素。勒菲弗爾在《翻譯、改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操縱》(2004)一書中對詩學所下的定義是:詩學即文學觀念,包括兩大部分,一是文學手法、文體、主題、原型人物、情景與象征;二是文學在整個文學系統中的作用。根據查明建在《文化操縱與利用:意識形態與翻譯經典的建構》(2004)一文中對對翻譯文學經典的界定,翻譯文學經典被分成三類:一是指翻譯文學史上杰出的譯作,如朱生豪譯的莎劇、傅雷譯的《約翰?克里斯多夫》、楊必譯的《名利場》等;二是指翻譯過來的世界文學名著;三是指在譯入語文化語境下被經典化了的外國文學譯作。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第三種類型的翻譯文學經典,即譯者把外國文學的經典或非經典文本帶進譯入語的翻譯文學經典形式庫。譯者是翻譯文學的生產者,其在翻譯文學經典建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一部經典的外國文學作品,經過翻譯,可能會有不同的命運。或者在目的語中保留其在源語中的地位,成為經典;或者失去其在源語中的經典地位,無人問津。反之,一部非經典的外國文學作品,經過翻譯,也可能成為經典,進入目的語翻譯文學經典庫。當然,翻譯文學經典化的過程十分復雜,在這里,筆者主要探討譯者的詩學觀在翻譯文學經典建構中的重要作用。
2、傳統詩學觀與翻譯文學經典建構
20世紀初是中國翻譯史的大盛時期,在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下,一批優秀的學者開始通過翻譯引入大量西方著作。據粗略統計,在這一時期,有數千種西方著作被譯成中文,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科技、哲學、歷史和文學等領域。其中外國文學翻譯特別是翻譯小說數量最為驚人,據考證,有多達2500多種(郭延禮,1996)。而在著紛繁的翻譯事業中,涌現出的翻譯文學經典數不勝數。清末時期,傳統的詩學觀影響著廣大文人,特別是士大夫階層,文言翻譯仍然一統天下。嚴復是晚清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也是該時期影響力最大的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他在翻譯《天演論》時,在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信達雅”一說,一直被國內學者們津津樂道,稱其為翻譯界的金科玉律。其中,“雅”頗受爭議。嚴譯《原富》首二篇出版后,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二期上加以推薦,但對他的文體提出了批評,覺得美中不足的是嚴氏的譯筆太過淵雅,不利于“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然而嚴復在《譯例言》中明確表示“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為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嚴復的“雅”實指用漢以前的字法句法來翻譯如外國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中的“精理微言”,因為這種譯書的讀者多為士大夫等上層知識分子和文人,唯有投其所好,用古雅的文字來翻譯才能做到達意。嚴復的翻譯思想和他飽讀古文史書,受中國傳統文論啟發有很大關系。雖然他一生譯書不算太多,但都是經典文本,大多關乎啟迪民智,立國安邦的政治經濟類啟蒙書籍,史稱“嚴譯八經”。嚴復正是以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秉承個人信念,在翻譯中注入自己的詩學態度,主導著翻譯經典建構的方向。而另外一位清末時期重要的翻譯家就是林紓。林紓是一位不懂外文的翻譯家,盡管如此,他一生譯書頗多,達到180余本,共一千數百萬字,涉及11國文字。林譯作品因為誤讀、紕漏太多,從而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判。但如果我們審時度勢,結合當時的情況來看,或許我們可以更理智的看待林紓的翻譯策略,透視他的詩學觀。有學者(王秉欽,2004)發現,林氏的文學語言觀是二元的:既維護文言,又不排斥白話。用錢鐘書先生的話說,“林紓譯書所用的文體是他心目中以為較通俗、較隨便、富于彈性的文言。它雖然保留著若干‘古文’的成分,但卻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詞匯和句法上規矩不嚴密,收容量大。”林譯小說中不僅使用了大量白話口語,如:阿姨、妮子、老子等,還用了許多外來語,如:蜜月、安琪兒、咖啡、布丁等。不僅如此,林譯小說還通過借鑒外國文學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等創作方法,革新了近代小說的創作形式,打破了傳統章回體的舊格式,通過大量歐化句型的使用,使近代文學文體逐步向新文體過渡,為“五四”的興起開辟了道路。
3、近現代詩學觀與翻譯文學經典建構
晚清到五四是中國文化的文化的轉型期,也是中國文學的轉型期。晚清主流翻譯規范越來越遭到質疑,譯者們在翻譯策略、譯作形態、表現形式等方面都呈現出與傳統詩學觀念相背離的趨勢。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魯迅也為現代翻譯文學提出了大量不落俗套標新立異的翻譯思想和理論,并且貢獻了數量龐大的翻譯作品。據魯迅博物館的孫郁先生(2006)統計,從1903年到1936年,魯迅在他33年的翻譯生涯中翻譯介紹了近14個國家近百位外國作家的200多部作品,字數達500多萬字。在魯迅看來,要有新的文藝,沒有別的路,只能拿來域外的藝術。魯迅涉獵的域外話題極其廣闊,最初是科幻小說、科學史,后來是尼采與裴多菲的作品。不久又被安德烈夫、迦爾洵所吸引。他同代人的翻譯,大多以大人物的作品為對象,如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歌德等,而魯迅所譯介的都是小人物的作品,愛羅先珂、阿爾志巴綏夫、有島武郎、片上伸、理定等。魯迅譯介他們的文字,更多的是為了自己的內心,可以喚起一種內力的噴吐。那些外來的作品多少是反省本民族痼疾的,無論日本還是俄國,許多他喜歡的作家,都是思想界的斗士。在精神的高度和藝術的水準上,確有不凡之筆。在1909年《域外小說集》出版之前,魯迅的翻譯從選材到語言都難逃晚清之風。自那以后,魯迅的翻譯觀有了很大的轉變。翻譯策略由意譯轉向直譯,語言由文言轉向白話,文體由短篇文言轉向短篇小說等新文體形式。例如,在《一個青年的夢》中,魯迅采用會話文體譯成,這在當時的翻譯界是一種新的嘗試。盡管魯迅的翻譯詩學轉變遭到了許多學者的抨擊和質疑,但從先生義無反顧的還擊中我們不難看到其良苦用心。直譯是為了吸取外國語言中“新的表現法”,彌補中文文法本來的不足;采用白話是為了讓文學更接近群眾的語言;新文體的使用則是為了豐富文學表現手法,為文學發展注入新鮮的血液。魯迅以及一大批翻譯家們正是通過這種新詩學觀,指引中國翻譯文學發展的方向,構建翻譯文學經典。
相關文章閱讀
相關期刊推薦
精選范文推薦
- 1多元化戰略公司案例
- 2多元文化護理論文
- 3多元智能理論論文
- 4多元化經營戰略的分類
- 5多元化戰略
- 6多元化管理論文
- 7多元文化的價值
- 8多元化營銷策略
- 9多元化經營
- 10多元智能理論對教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