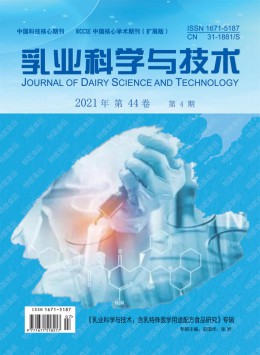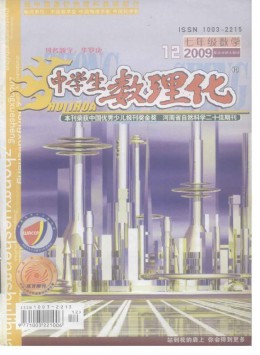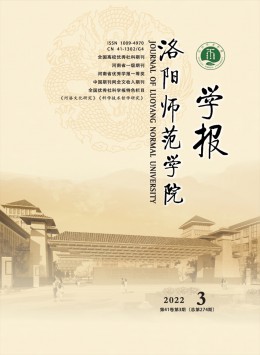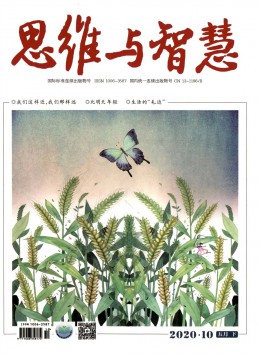簡明邏輯學導論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簡明邏輯學導論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簡明邏輯學導論范文
【關鍵詞】邏輯/廣義與狹義/一元論/多元論/工具主義
【正文】
一、廣義的邏輯與狹義的邏輯
什么是邏輯?要清楚明確地回答這一問題,要將各種各樣冠以“邏輯”的學科都統一在一個明確清晰的“邏輯”的定義之下,這是很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不妨先對邏輯發展史作一簡單考察。
在西方,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集其前人研究之大成,寫成了邏輯巨著《工具論》(由亞氏的六部著作編排而成:《范疇篇》、《解釋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論辯篇》、《辨謬篇》)。雖然在亞氏的著作中他并沒有明確地使用“邏輯”這一名稱,也沒有明確地以“邏輯”這一術語命名其學說,但是,歷史事實是,亞氏使形式邏輯從哲學、認識論中分化出來,形成了一門以推理為中心,特別是以三段論為中心的獨立的科學。因此,可以說,亞里士多德是形式邏輯的創始人。
亞氏之后,亞里士多德學派即逍遙學派和斯多葛學派都以不同形式發展了亞氏的形式邏輯理論——逍遙學派的德奧弗拉斯特和歐德慕給亞里士多德邏輯的推理形式增補了一些新的形式與內容,提出了命題邏輯問題,斯多葛學派克里西普斯等人則構造了一個與亞里士多德詞項邏輯不同的命題邏輯理論。
弗蘭西斯·培根是英國近代唯物主義哲學家,也是近代歸納邏輯的創始人,他在總結前人歸納法的基礎上,在批判了經院邏輯和亞里士多德邏輯之后,以其古典歸納邏輯名著《新工具》為標志,奠定了歸納邏輯的基礎。
18-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黑格爾等,對人類思維的辯證運動與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另一種新的思辯邏輯——辯證邏輯。
與此同時,以亞里士多德邏輯為基礎的形式邏輯在發展與變化中也進入了新的階段——數理邏輯階段。數理邏輯也稱符號邏輯,或謂狹義的現代邏輯,奠基人是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茲。他主張建立“表意的、普遍的語言”來研究思維問題,使推理的有效性可以用數學方法來進行。萊布尼茲的這些設想雖然在許多方面并未實現,但他提出的“把邏輯加以數學化”的偉大構想,對邏輯學發展的貢獻卻是意義深遠的,正如邏輯史家肖爾茲所說,“人們提起萊布尼茲的名字就好象在談到日出一樣。他使亞里士多德邏輯開始了‘新生’,這種新生的邏輯在今天的最完美的表現就是采作邏輯斯蒂形式的現代精確邏輯。”(注:肖爾茲著,張家龍譯:《簡明邏輯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0頁。)萊氏之后,經過英國數學家、哲學家、邏輯學家哈米爾頓、德摩根的研究,英國數學家布爾于1847年建立了邏輯代數,這是第一個成功的數理邏輯系統。1879年,德國數學家、邏輯學家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一種模仿算術語言構造的純思維的形式語言》這部88頁的著作中發表了歷史上第一個初步自足的、包括命題演算在內的謂詞演算公理系統,從而創建了現代數理邏輯。之后,英國哲學家、邏輯學家羅素和懷特海于1910年發表了三大卷的《數學原理》,建立了帶等詞的一階謂詞系統,從而使得數理邏輯成熟與發展起來。
上述數理邏輯,以兩個演算——命題演算與謂詞演算作為核心,被稱之為現代形式邏輯或狹義的現代邏輯。在當代,以現代邏輯為基礎,將現代邏輯應用于各個領域、各個學科,從而出現了廣義的各種各樣的現代邏輯分支。
從以上對古代、近代、現當代邏輯學說發展的簡單考察可以看出,邏輯的范圍是十分廣泛的。它至少包括了以亞里士多德邏輯為基礎的傳統演繹邏輯、以數理邏輯為核心及基礎的現代邏輯及其分支、歸納邏輯、辯證邏輯等等,而這些邏輯相互之間的特性又是十分不同甚至十分對立的。所以,要用一個明確的定義把這些歷史上所謂的邏輯都包含進去,確實是很難的。事實上,“邏輯”一詞是可以有不同的涵義的,邏輯可以有廣義與狹義之分。
英國邏輯學家哈克在談到邏輯的范圍時,認為邏輯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學科群,其分支主要包括如下:
1.傳統邏輯: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
2.經典邏輯:二值的命題演算與謂詞演算
3.擴展的邏輯: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認識論邏輯、優選邏輯、命令句邏輯、問題邏輯
4.異常的邏輯:多值邏輯、直覺主義邏輯、量子邏輯、自由邏輯
5.歸納邏輯(注:S.Haack:Philosophyoflog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4,221-231.)
在這里,哈克所謂的“擴展的邏輯”,是指在經典的命題演算與謂詞演算中增加一些相應的公理、規則及其新的邏輯算子,使其形式系統擴展到一些原為非形式的推演,由此而形成的不同于經典邏輯的現代邏輯分支;至于“異常的邏輯”,則是指其形成過程一方面使用與經典邏輯相同的詞匯,但另一方面,這些系統又對經典邏輯的公理與規則進行了限制甚至根本性的修改,從而使之脫離了經典邏輯的軌道的那些現代邏輯分支。“擴展的邏輯”與“異常的邏輯”統稱為“非經典邏輯”。
以哈克的上述分類為基礎,從邏輯學發展的歷史與現實來看,邏輯是有不同的涵義的,因此,邏輯的范圍是有寬有窄的:首先,邏輯指經典邏輯,即二值的命題演算與謂詞演算,不嚴格地,也可以叫數理邏輯,這是最“標準”、最“正統”的邏輯,也是最狹義的邏輯;其次,邏輯還包括現代非經典邏輯,不嚴格地,也可以叫哲學邏輯,即哈克所講的擴展的邏輯與異常的邏輯;再次,邏輯還包括傳統演繹邏輯,它是以亞里士多德邏輯為基礎的關于非模態的直言命題及其演繹推理的直觀理論,其主要內容一般包括詞項(概念)、命題、推理、證明特別是三段論等。此外,邏輯還可以包括歸納邏輯(包括現代歸納邏輯與傳統歸納法)、辯證邏輯。將邏輯局限于經典邏輯、非經典邏輯,這就是狹義的邏輯,而將邏輯包括傳統邏輯、歸納邏輯與辯證邏輯,則是廣義的邏輯。以這一取向為標準,狹義的邏輯基本上可以對應于“邏輯是研究推理有效性的科學,即如何將有效的推理形式從無效的推理形式中區分開來的科學”這一定義,而廣義的邏輯則可以基本上對應于“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邏輯基本規律及簡單的邏輯方法的科學”這一定義。
由此可見,邏輯學的發展是多層面的,站在不同的角度,就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考察邏輯學的不同層面及不同涵義:
(1)從現代邏輯的視野看,邏輯學的發展從古到今的過程是從傳統邏輯到經典邏輯再到非經典邏輯的過程。這一點上面已有論述,此不多說。
(2)從邏輯學兼具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的角度,可以確切地把邏輯分成純邏輯與應用邏輯兩大層面。可以說,純邏輯制定出一系列完全抽象的機械性裝置(例如公理與推導規則),它們只展示推理論證的結構而不與某一具體領域或學科掛鉤,是“通論”性的,而應用邏輯則是將純邏輯理論應用于某一領域或某一主題,從而將這一具體主題與純邏輯理論相結合而形成的特定的邏輯系統,它相當于邏輯的某一“分論”。在純邏輯這一層面,還可以分成理論邏輯與元邏輯,所謂元邏輯,是以邏輯本身為研究對象的元理論,是刻劃、研究邏輯系統形式面貌與形式性質的邏輯學科,它研究諸如邏輯系統的一致性、可滿足性、完全性等等。不言而喻,元邏輯之外的純邏輯部分,統稱為理論邏輯。以這種分法為基礎,如果說純邏輯是狹義的邏輯的話,則應用邏輯就是廣義的邏輯。
(3)從邏輯學對表達式意義的不同研究層次,可以把邏輯分成外延邏輯、內涵邏輯與語言邏輯。傳統邏輯與經典邏輯對語言表達式(詞或句子)意義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表達式的外延上,認為表達式的外延就是其意義(如認為詞的意義就是其所指,句子的意義就是其真值),因此,它們是外延邏輯。對表達式意義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其外延上,認為不僅要研究表達式的外延,也要研究表達式的內涵,這樣的邏輯就是內涵邏輯。可以看出,外延邏輯與內涵邏輯對表達式意義的研究都只是停留在語形或語義層面,而實際上,表達式總是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下使用的,因此,邏輯對語言表達式意義的研究還可以也應該深入到語言表達式的具體的使用中去,對其進行語用研究,這一考慮,就促成了所謂的自然語言邏輯或語言邏輯的研究。所謂自然語言邏輯,按我的理解,就是通過對自然語言的語形、語義與語用分析來研究自然語言中的推理的科學。因此,如果說狹義的邏輯是一種語形或語義邏輯、它們只研究語形或語義推理的話,則廣義的邏輯則是一種語用邏輯,它還要研究語用推理。
二、現代邏輯背景下的邏輯一元論、多元論與工具論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在當代,現代邏輯的發展呈現出多層次、全方位發展的態勢,邏輯學正在從單一學科逐步形成為由既相對獨立又有內在聯系的諸多學科組成的科學體系的邏輯科學。現代邏輯發展的這一趨勢,就使得一方面大量的、各種各樣的現代邏輯分支、各種各樣的邏輯系統不斷涌現,比如,既有作為經典邏輯的命題演算與謂詞演算,也有作為對經典邏輯的擴展或背離的非經典邏輯。另一方面,不同于傳統邏輯或經典邏輯所具有的直觀性,非經典邏輯系統越來越遠離直觀甚至在某些意義上與直觀相背。在這種背景下,邏輯學家就必然面臨如下需要回答的問題:
(1)邏輯系統有無正確與不正確之分?說一個邏輯系統是正確的或不正確的是什么意思?
(2)是否一定要期望一個邏輯系統成為總體應用的即可以應用于代表任何主題的推理的?或者說,邏輯可以是局部地正確,即在一個特定的討論區域內正確的嗎?
(3)經典邏輯與非經典邏輯特別是其中的異常邏輯之間的關系如何?它們是否是相互對立的?
對上述問題的不同回答,就區分出了關于邏輯的一元論、多元論與工具主義。
不管是一元論還是多元論,都認為邏輯系統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分,邏輯系統的正確與否依賴于“相對于系統本身的有效性或邏輯真理”與“系統外的有效性或邏輯真理”是否一致。如果某一邏輯系統中的有效的形式論證與那些在系統外的意義上有效的非形式論證相一致,并且那些在某一系統中邏輯地真的合式公式與那些在系統外的意義上也邏輯地真的陳述相一致,則該邏輯系統就是正確的,反之則為不正確的。以這一認識為基礎,一元論認為只有一個唯一地在此意義下正確的邏輯系統,而多元論則認為存在多個如此的邏輯系統。
工具主義則認為,談論一個邏輯系統是否正確或不正確是沒有意義的,不存在所謂正確或不正確的邏輯系統,“正確的”這個詞是不合適的。就工具主義來說,他們只允許這樣一個“內部”問題:一個邏輯系統是否是“完善的”(Sound)?即是說,邏輯系統的定理或語法地有效的論證是否全部地并且唯一地是在該系統內邏輯地真或有效的?(注:S.Haack:Philosophyoflog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P.4,221-231.)
多元論又可以分為總體多元論與局部多元論。局部多元論認為,不同的邏輯系統是由于應用于討論的不同領域而形成的,因此,局部多元論把系統外的有效性和邏輯真理從而也把邏輯系統的正確性看作是討論的一個特定領域,認為一個論證并不是無條件地有效的,而是在討論中有效的,所以,邏輯可以是局部地正確的,即在某一特定的討論區域內正確的。而總體多元論則持有與一元論相同的假定:邏輯原理可以應用于任何主題,因此,一個邏輯系統應該是總體應用的即可以應用于代表任何主題的推理的。
就經典邏輯與非經典邏輯特別是異常邏輯之間的關系而言,一元論者強迫人們在經典系統與異常系統中二者擇一,而多元論者則認為經典邏輯與擴展的邏輯都是正確的。因此,一元論者斷言經典邏輯與異常邏輯在是否正確地代表了系統外的有效論證或邏輯真理的形式上是相互對立的,而多元論者則認為經典邏輯與異常邏輯兩者在某一或其他途徑下的對立只是表面的。
就邏輯科學發展的現實而言,從傳統邏輯到經典邏輯再到非經典邏輯的道路,也是邏輯科學特別是邏輯系統發展由比較單一走向豐富多樣的過程。以傳統邏輯來說,它來自于人們的日常思維和推理的實際,可以說是對人們的日常思維特別是推理活動的概括和總結,因此,傳統邏輯的內容是比較直觀的,與現實也是比較吻合的。而經典邏輯是傳統邏輯的現展階段,是以形式化的方法對傳統邏輯理論特別是推理理論的新的研究,因此,與傳統邏輯一樣,經典邏輯的內容仍是具有直觀基礎的——經典邏輯的公理與定理大都可以在日常思維中找到相對應的思維與推理的實例予以佐證,人們對它們的理解與解釋也不會感到與日常思維特別是推理的實際過于異常。所以,在傳統邏輯與經典邏輯的層面,用“系統內的有效性”與“系統外的有效性”的一致來說明一個邏輯系統的正確性是合適的,這種說明的實質就是要求邏輯系統這種“主觀”的產物與思維的客觀實際相一致。
相對而言,在經典邏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非經典邏輯,它的直觀性、與人們日常思維特別是推理的吻合性就大大不如經典邏輯,甚至與經典邏輯背道而馳。以模態命題系統為例(應該說,相對而言,模態命題邏輯在非經典邏輯中是較為直觀的),如果說系統T滿足對模態邏輯系統的直觀要求,它所斷定的是沒有爭論的一些結論的話,則系統S4、S5就難以說具有直觀性以及與人們日常思維特別是推理的吻合性了:在系統S4和S5中都出現了模態算子的重疊,因而象pp、pp這樣的公式大量出現,而這些公式幾乎沒有什么直觀性。至于非經典邏輯中的直覺主義邏輯、多值邏輯,它們離人們的日常思維特別是推理的實際更遠,更顯得“反常”。同時,同一個領域比如模態邏輯或時態邏輯,由于方法和著眼點不同,可以構造出各種不同的系統。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學者作出邏輯系統無正確性可言、邏輯系統純粹只是人們思考的工具的工具主義結論也就不足為怪了。應該說,工具主義的觀點是有一定的可取之處的:它看到了邏輯系統特別是各種非經典邏輯系統遠離日常思維與推理和作為“純思維產物”的高度抽象性,看到了邏輯學家在建構各種邏輯系統時的高度的創造性或“主觀能動性”。但是,另一方面,從本質來看,工具主義的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可取的。它完全抹殺了邏輯系統建構的客觀基礎,否定了邏輯系統最終是人們特別是邏輯學家的主觀對思維實際、推理實際的反映。這種觀點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邏輯無用論,最終取消邏輯。這顯然是不符合邏輯科學發展的實際和邏輯科學的學科性質的。
而一元論對邏輯系統的“正確性”的理解過于狹窄,也過于嚴厲,這種觀點難以解釋在今天各種不同的邏輯系統之間相互并存、互為補充的現實。從本質上講,盡管任何邏輯系統都是邏輯學家構造出來的,但是,它們是有客觀基礎的——它總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類思維特別是推理實際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領域(否則,它就是沒有實際意義的,最終難以存在下去),所以,邏輯系統是有“正確”與“不正確”之分的——正確地反映了人類思維特別是推理實際的邏輯系統就是正確的,反之則是不正確的。應該說,這一點是一元論與多元論都可以同意的,但是,在承認這一說法的同時,還應該看到,“正確地反映人類思維特別是推理的實際”是可以有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層次的:邏輯系統對人類思維特別是推理實際的反映可以是比較普遍、一般的(比如傳統邏輯與經典邏輯),也可以是比較特殊、具體的(比如某些非經典邏輯系統,它所反映的就是相對于某一特定主題或領域的特定的思維與推理);邏輯系統對人類思維特別是推理實際的反映可以是比較直觀、與日常較為吻合的,也可以是相對來說較為抽象、遠離現實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邏輯系統的“正確性”是多樣的,不可絕對化和唯一化。所以,我認為,一元論堅持“只有一個正確的、唯一的邏輯”是不妥的,相反,多元論的觀點則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按哈克的分析把非經典邏輯分成“擴展的邏輯”與“異常的邏輯”的話,那么,很顯然,擴展的邏輯是以經典邏輯為基礎,將經典邏輯理論應用于某一領域或學科而形成的對經典邏輯的擴充,它們之間并不存在互斥、對立的情況,它們都可以是“正確的”。至于“異常的邏輯”,它的某些性質與特征確實可能與經典邏輯不同甚至相矛盾(例如在直覺主義邏輯、多值邏輯中排中律的失效等等),因此,它們有“對立”的地方,但就經典邏輯與某一異常邏輯分支相比而言,它們的對立或不一致只是在某些方面,而從整個系統的性質來看,它們的互通之處更多,因此,經典邏輯與某一異常邏輯分支之間的所謂“對立”之處,恰恰是該異常邏輯分支的獨特之處,也是它對某一問題的不同于經典邏輯的處理和解決之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對經典邏輯的意義不在于“否定”了經典邏輯的某些定理或規則,而在于對經典邏輯忽略了的或無法處理的地方進行了自己的獨特的處理。所以,經典邏輯與異常邏輯之間的“對立”是表面上的,其實質是它們之間的互補。
【參考文獻】
[1]陳波.邏輯哲學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2]馮棉,等.哲學邏輯與邏輯哲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
[3]桂起權.當代數學哲學與邏輯哲學入門[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
[4]楊百順.西方邏輯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5]江天驥,等.西方邏輯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第2篇:簡明邏輯學導論范文
解釋蘊涵完全拋開表層形式,只憑對語句語義的理解而進行。運用解釋蘊涵可以作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語
義鑒別是對單個語句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可將語句區分為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語義比較
是對多個語句間的語義關系進行認定,可將語義關系區分為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關鍵詞】語義蘊涵虛指蘊涵解釋蘊涵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同義關系矛盾關系
對立關系
***
運用現代語義理論對漢語語義進行分析是個新課題。
以語義場理論為代表的結構語義學派于30年代出現,是現代語義學興起的標志,但是無論德國的特里
爾(J·Trier)還是英國的烏爾曼(S·Ullmann),他們的語義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詞(或小于詞)一級上進
行。直到60年代卡茲(J·Katz)、福德(J·Fodor)創立“解釋語義學”和萊可夫(G·Lakoff)、麥考
萊(J·McCawley)創立“生成語義學”,現代語義學才開始了語句語義的全面研究。
現代語義理論引進我國始于80年代,近些年來已由“介紹”漸進到了“引用”,探索以現代語義學的
觀點和方法研究漢語,已現蓬勃態勢。特里爾的語義場及義素分析理論,已被引入漢語教材,成為了詞義理
論教學的一部分。
對漢語語句語義的探討則還遠遠不夠。
現代語義學的誕生是語言理論與邏輯理論“聯姻”的結果,對語詞語義、語句語義的解釋、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現代邏輯的方法和模型。“蘊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來對語句語義進行分析的一種邏輯方法
。
本文嘗試引鑒蘊涵理論,對漢語的語句語義進行探討分析。
一、語義蘊涵
對自然語言語義進行“蘊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邏輯蘊涵,邏輯蘊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論基礎上的。“
蘊涵,即‘p蘊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義是‘如果p不是假的,則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這就是邏輯上所稱的“實質蘊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題蘊涵一切真命題
,真命題為一切命題所蘊涵”這一“蘊涵怪論”。這里說的“真”、“假”并非語句所陳述的事實上的真假
,它與自然語言的語義并無直接聯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這種蘊涵理論當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來進行語義
分析。
“蘊涵”最基本、最簡單的關系是“p真必然q真”,避開抽象的純真值解釋,將“真”、“假”理解
為直觀的事實反映,即語句的具體內容,“蘊涵”也就可以應用于語義分析了。
為與邏輯學中的“實質蘊涵”相區別,擬將語義間的蘊涵關系稱為“語義蘊涵”。
語句是事實情況的反映,語句語義實際就是關于事物情況的各種“信息”。
“當語句‘p’在語義學上蘊涵語句‘q’時,語句‘p’所傳遞的信息包含著語句‘q’所傳遞的信
息。”[②]
這是對語義蘊涵最簡明的闡述。p的信息包含著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蘊涵關系自可成立。
設語句p為“王前是翻譯家”,語句q為“王前懂外語”,顯然,p的信息包含著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語句是真的,q語句必然也是真的,這就可以說,在語義上,語句p對語句q有蘊涵關系,或者說語句p
蘊涵語句q。
“一句陳述句的蘊涵命題就是離開任何語境可以從句子本身推理出來的那些命題;只要那個句子本身表
達一個真實的判斷,其蘊涵命題必定真實。”[③]
從這一闡述中,可以析出語義蘊涵應具有的條件:
(一)離開具體的語境,在同一個可能世界中進行討論,即排除語境因素,獨立分析語義,不涉及語用
問題。
(二)必須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關系。
為敘述方便,本文擬將語句p稱作“源語句”,將其所蘊涵的語句q稱作“蘊涵語句”。還要說明的是
,本文所稱的“語句”絕非語法意義的“句子”,它是語義單位,即語義學上所稱的“義句”,或者說是具
有邏輯意義的語句,即“命題”。文中所稱的“語詞”絕非語法意義的詞、詞組,它也是語義單位,即語義
學上所稱的“義位”、“義叢”,或者說是“概念”。
二、虛指蘊涵
虛指蘊涵是以語詞為操作對象的,即以一個不定指稱短語代替源語句中的各個成分,以形成多個蘊涵語
句。
“不定指稱短語”的結構為:“某+屬”,即由任指代詞“某”附加于源語句中語詞的屬概念之上而形
成。
設源語句為S,蘊涵語句分別為S1、S2、S3、S4……
源語句S:校長獎勵了三好學生。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某人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實施)某行為于三好學生。
S3:校長獎勵了某些人。
為確保虛指蘊涵嚴格可靠,應遵從下列兩條規則:
(一)不改變源語句的表層結構。
以虛指方式導出的蘊涵語句直接來自源語句的表層結構,各個蘊涵語句一般都不改變原有的語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稱短語所“置換”。
如上例的S與S1、S2、S3的短語結構均為:
SNp+Vp
VpV+Np
(注:TG理論中“”表“重寫”,并非蘊涵符號。)
以樹形圖顯示則更明顯:
(附圖[圖])
顯然,源語句與蘊涵語句具有著“同構”關系。
(二)進行置換的虛指短語必須與源語句成分的語義范圍同一。用于進行置換的短語是被限定的“屬”
,這里的“屬”,可以是一般意義上的“范疇”,如“人”、“物”、“行為”、“時間”、“地點”、“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長”的范疇。“屬”也可以是較為鄰近的“類”,比如采用“領導”、“學校
領導”也無不可。
無論“范疇”還是“類”,語義范圍都大于被置換語詞,以虛指語詞限定后范圍縮小,結果兩者語義相
等。如圖:
(附圖[圖])“某人”與“校長”指稱范圍相同,只是“實”、“虛”之別而已。
蘊涵語句是有序的,其順序是依著源語句表層結構“語符列”的順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順序便是依據著主語、謂語、賓語在表層結構中的語符位置。
蘊涵語句的這種有序性,對確認一個語句的語義具有著重要意義,其間音位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個置換成分的順序予以側重,就會構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從而可以傳遞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問。
S1:誰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對三好學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長獎勵了誰?
由重音模式轉移所形成的語義各異的蘊涵語句,構成了源語句S的全部語義,而S在無語境、無重音模
式的情況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語義。
重音模式與語境因素密切相關,由于語義蘊涵遵從著“無語境”的條件,所以這不是本文要深入討論的
問題。
虛指蘊涵的操作機制是對語句的表層結構進行“改造”,實際只是一種“語法義蘊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語句語義,當然也就無法應用于深入的語義分析。
三、解釋蘊涵
解釋蘊涵則是拋開語句的表層形式,完全憑借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和解釋以形成蘊涵語句。
憑借理解對語義進行解釋,是分析自然語言的慣用方式,“所有關于自然語言的論證有效地證明,依賴
于未經訓練的語言直覺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賴于邏輯理論的程度。”[④]進行語義解釋尤其要依賴“未經訓
練的語言直覺”能力。
任一語句的語義都是可以進行理解、進行解釋的,語句語義與其語義的解釋是不同的,前者是復合總體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體”。
源語句S:王工程師是劉師傅女兒的未婚夫。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王工程師是男性。
S2:王工程師未婚。
S3:劉師傅已婚。
S4:劉師傅有個女兒。S5:劉師傅女兒未婚。
S6:王工程師與劉師傅女兒已確定婚姻關系。
上列蘊涵語句是對S的語義進行分解的結果,進行這種分解的依據是純語義的,與表層結構無關,蘊涵
語句是完全憑借直覺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而形成。
源語句S分別蘊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蘊涵關系,可讀作“蘊涵”或“那么”。
這種蘊涵關系可以用側樹形圖表示:
(附圖[圖])
S是S1、S2、S3、S4語義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語義的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對語句語義的解釋不是任意的,源語句與蘊涵語句之間必須存有“p真必然q真”的關系,為此,下列
操作規則是必不可少的:
(一)蘊涵語句是不超出源語句語義的范圍,就是說所傳遞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語句,如“劉師傅是男的
”、“劉師傅女兒20多歲”等就不是源語句的蘊涵語句。
(二)不能導出與源語句相背的語句,如“劉師傅未婚”、“王工程師不認識劉師傅的女兒”等。
虛指蘊涵與解釋蘊涵都是對語句語義進行分解,但兩者大不相同,茲以下表進行對比:
虛指蘊涵解釋蘊涵
操作依據語詞語義語句語義
語形結構不改變改變
操作方式置換解釋
蘊涵本源表層結構深層結構
蘊涵性質語法的語義的
蘊涵語義范圍相等縮小
蘊涵語句組合有序無序
蘊涵語句數量定量不定量
語句語義的研究絕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之上,還應該對語句的語義性質及語句語義間的關系
予以認定,在這方面解釋蘊涵是最為可行、最為有效的分析方法。
語義認定可從“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兩個方面分述。
四、語義鑒別
語義鑒別是對語句自身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
依據語句的語義性質區分,有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
1.單義句
一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相互獨立并可以組合成完整語義,此句為單義句。
“相互獨立”是指蘊涵語句之間不重復、不交叉。“可以組合成完整語義”是指不含有語義相抵的不可
組合情況。
源語句S:甲的1號賽車榮獲了本屆越野賽的冠軍。
可以蘊涵下列語句:
S1:甲是賽車手。
S2:甲駕的是1號車。
S3:曾舉行越野賽。
S4:甲參加了本屆越野賽。
S5:1號車榮獲了冠軍。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語義,相互獨立,它們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語句的語義,彼此可以進行組合
、還原成源語句的完整語義,因此源語句為單義句。
2.歧義句
一個語句同時蘊涵多組語句,其間含有“異己”語句而無法進行組合、還原,此句為歧義句。
源語句S:我們見到了剛剛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語句可以蘊涵A、B兩組不同的語句。
A組:
A—S1:小王有個哥哥。
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
A—S3:我們見到了哥哥。
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A、B兩組語句都是S所蘊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與B—
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是兩組之間的“異己”語句,由于兩者的存在,兩組不可重新進行組合、還原,此可說源語句S是個歧義句。
歧義句的語義有如下特征:任一個語句組(A或B組)中引入另一組所含異己語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會出現矛盾,反而能組合成更為完整、更為明確的語義。
如A組S2的否定式為“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試將其引入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新組成的這組語句,不但可以進行組合,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義現象。
同理,B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組是如此。
3.重復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同一的語句,此句為重復句。
源語句S:處女之作《淚痕》是小李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蘊涵語句:
S1:小李寫了一部《淚痕》。
S2:《淚痕》是處女之作。
S3:《淚痕》是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顯然,S2與S3的語義是同一的。
重復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語義同一的語詞所造成,如“處女之作”與“第一部作品”。
這里說的“同一”是指語義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語詞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語義未必同一。
源語句S:那個老運動員很老。
蘊涵語句:
S1:那是個運動員。
S2:他是老運動員。
S3:他很老。
這組蘊涵語句中,S2與S3都用了“老”這一語詞,但語義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時間久長,
S3中的“老”是年歲高邁,因此源語句S不為重復句。
4.矛盾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不可共存的語句,此句為矛盾句。
源語句S: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我國歷來是統一的,分裂只是暫時的。
蘊涵語句:
S1: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
S2:我國歷來是統一的。
S3:我國曾有過分裂。
顯然,S2(歷來是統一的)與S3(并非歷來是統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論”是一種特殊的矛盾句。此類語句包含有“預設語義”,“預設”的語義與“顯現”的語義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論”的矛盾語義是極其隱含的,運用解釋蘊涵進行分析可以將其揭示出來。
源語句S:真實的判斷是不存在的。
蘊涵語句:
S1:真實判斷不存在。
S2:存在著一個真實判斷(該判斷)。
S2是言者默認的預設語義,S1是語句所顯現的語義,兩者不可共存。
五、語義比較
通過對不同語句的語義進行對比分析,以認定它們之間的語義關系,為語義比較。
大量的語句都是各自獨立的,它們的語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這些語句可稱為“獨立句”,這里不予
討論。
語句間的語義關系區分,有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1.同義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完全相同,這兩個語句為同義關系。
同義關系所傳遞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語句:
A—S:中國隊又一次榮獲冠軍。
B—S:中國隊再次奪魁。
C—S:中國隊衛冕成功。
上列三個語句都蘊涵著下列語句:
S1:中國隊曾獲得第一。
S2:中國隊本次又獲第一。
此類同義關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義語詞,因此它們的表層結構也大都無異,這是“同構”的同義關系
。
同義關系大都不是同構的,比如由核心句經“移動轉換”而生成的轉換句,表層結構就是不同的。
源語句:
A—S:秦國滅了趙國。
B—S:秦國把趙國滅了。
C—S:趙國被秦國滅了。
蘊涵語句:
S1:秦國曾與趙國交戰。
S2:秦國勝利了。
S3:趙國失敗了。
S4:趙國已不存在。
由“省略轉換”生成的轉換句,不但表層結構縮減,語義也有所省略,蘊涵語句的語義有了差異,不能
認為是同義關系。
源語句:
A—S:趙國被秦國滅了。
B—S:趙國被滅了。
語句B—S并不蘊涵S1、S2兩個語義,信息量減少了,A—S與B—S不是同義關系。2.矛盾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矛盾關系。
源語句:
A—S: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裝。
B—S: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而沒有褪色。
A—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B—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
A—S所蘊涵的S2與B—S所蘊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總量,即“是新款的”與“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這兩種情況外,別無其他情況。
矛盾關系語句之間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假。
(二)可以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真。矛盾關系語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別無其他情況,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為假,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真。
3.對立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對立關系。
源語句:
A—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中國產品。
B—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B—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與B—S所蘊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兩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即“是中國產品”
與“是韓國產品”只包含了信息總量中的部分信息。
對立關系語句有如下兩個特征:
(一)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真,可以推知“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假。
(二)不能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為真,對立關系語句所傳遞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這批
設備是中國產品”與“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還可以是其他國家產品),所以非此未必
為彼,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為假,就推不出“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真。
注釋:
①[英]羅素:《數理哲學導論》,轉引自[美]帕特里克·蘇佩斯《邏輯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頁。
②[日]末木剛博:《邏輯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頁。
③[英]尼爾·史密斯、[英]達埃德爾·威爾遜:《現代語言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
3年版,第163頁。
④[美]G·J·馬塞:《邏輯與語言學》,轉引自《邏輯與語言論集》,語文出版社,1986年版
第3篇:簡明邏輯學導論范文
關鍵詞: 科學史 科學知識社會學 內史 外史
abstract: since 1930s, most of changes and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ern history of science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division, and evalua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 about that problem, many chinese schola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nal history”, and, even some scholars who focus the “external history” would insis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however,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sk, the premise of these opinions and controversies is the opposi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t insists that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a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ask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is view of science, there is no such independent “internal history” that is free from any social factors. in that way, the demarcation of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is eliminated.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ssk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科學史中的“內史論”與“外史論”已經是科學史界和科學哲學界十分熟悉的概念。可以說,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構成了科學編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對其進行分析,對于一階的科學史研究來說,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從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簡稱ssk)的立場出發,指出這種劃分實際上是可以被消解的,而且這種消解又可以帶來科學觀和科學史觀上的新拓展。
一、科學史“內外史”之爭
在討論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內外史”劃分的消解之前,我們先且按傳統的標準和劃分方式對“內史論”與“外史論”的含義及“內外史”之爭做簡單的回顧與分析。
一般而言,科學史的“內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學本身的內部發展歷史。“內史論”(internalism)強調科學史研究只應關注科學自身的獨立發展,注重科學發展中的邏輯展開、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論的闡述、實驗的完成,以及理論與實驗的關系等等,關心科學事實在歷史中的前后聯系,而不考慮社會因素對科學發展的影響,默認科學發展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科學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則指社會等因素對科學發展影響的歷史。“外史論”(externalism)強調科學史研究應更加關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軍事••••••等環境對科學發展的影響,認為這些環境影響了科學發展的方向和速度,在研究科學史時,把科學的發展置于更復雜的背景中。[ ](p24)
從時間上來看,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科學史研究(包括薩頓的編年史研究在內)基本上都屬于“內史”范疇。直到20世紀30年代默頓和格森發表了有關著作之后,科學史研究才開始重視外部社會因素對于科學發展的影響,并逐漸形成了與傳統“內史”研究不同風格的編史傾向。這才出現了科學史的“外史”轉向,并引起了所謂的“內外史”之爭。
具體而言,“內外史”之爭的焦點在于外部社會因素是否會對科學的發展產生影響,或者說,在科學史的研究中,這些外部影響是否可被研究者忽略。其中,“內史論”者認為,科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內在發展邏輯,是不斷趨向真理的過程;科學內在的認知概念和認知內容不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且科學的真理性和內在發展邏輯往往使得其發展的速度和方向也不受外部因素的影響。相反,“外史論”者則堅持認為,盡管科學有其內在的概念和認知內容,但是科學發展的速度和方向,往往是社會因素作用的結果。在其看來,社會的、經濟的、宗教的、政治制度的和意識形態的因素,無一不對科學研究主題的變化和科學發展進程的快慢產生重要影響。
在20世紀30-40年代,因為格森和默頓等人的工作,“外史論”在科學史界逐漸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二戰后期直接源于坦納里、迪昂、邁耶遜、布魯內和黙茨格的法國傳統的觀念論綱領開始流行。正如科學史家薩克雷所說,由于觀念論的哲學性歷史占主導地位,在50-60年代的大部分時期,人們很自然地注意遠離任何對科學的社會根源的討論。即使出現這種討論,那也是發生在一個明確界定的領域,并由社會學家而非科學史家進行。[ ](p55)在這一時期,柯瓦雷關于伽利略和牛頓的經典研究奠定了觀念論科學史的主導地位。20世紀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外史論”在另一種意義上又重新發揮了影響,顯示出較為活躍的勢頭,這與科學哲學中歷史學派的出現不無關系。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知識社會學(ssk)的發展,對科學的社會學分析開始興起,其中,不但科學的形成過程和形式,連科學的內容也被納入了社會分析的范圍,科學知識的內容因其社會建構過程,也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科學既被看成是一種知識現象,更被看成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
可以說,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釋框架上的一些變化和爭論,大多是圍繞著界定、區分和評價“內史論”與“外史論”,是在這兩者彼此對立存在(雖然也有認為兩者可以綜合融通的看法)的前提下展開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內外史”研究的變化與爭論進行分析,可以窺見20世紀以來西方科學史研究側重點和范式變化的歷史脈絡。
二、國內學者的態度及其前提假定
對于西方科學史研究的“內外史”演變和爭論,國內學者的態度大抵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種是埋首于個人的具體研究,不去關心和討論這個編史學理論問題,但潛在地卻基本同意“內外史”的劃分,這類學者占大多數;另一種是對該問題做了專門的研究和討論,當然這些學者在人數上不是很多。在這類學者當中,通常極端的“內史論”和“外史論”都不被他們同意,他們從某種程度上堅持的二者的綜合運用。
具體而言,在第一類學者看來,具體的一階研究更為重要,討論“內外史”之爭問題往往是“空談理論”,對于實際的科學史研究沒有多大意義。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國內科學編史學研究相對來說一直是較為薄弱的環節,其價值和意義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不過,值得注意而且也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在這些一階的研究中,“內史”所占的比重遠遠超過“外史”。在許多學者看來,科學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科學史描述的就是科學自身發展的歷史和規律。少數“外史”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描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因素對科學發展的速度、形式的影響上,把社會因素作為科學發展的一個外在的背景環境來考慮,尚未觸及到社會因素對科學內容的建構與塑型的層面。
在第二類學者中,80年代末就已經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指出科學中的多數重大進展都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成的,認為在“內史”和“外史”之間必須保持必要的張力。[ ](p39-47)隨后一些學者較為系統地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科學史研究的“外史”轉向進行了專門研究。他們通過對國際科學史刊物isis自1913年到1992年的論文和書評進行的計量研究,發現科學史的確發生了從內史向外史的轉向,20世紀80年代之前以內史研究為主,80年代之后以外史研究為主。[ ](p128)此外,他們還就“內史”為何先于“外史”、“內史”為什么轉向“外史”、“內史”與“外史”的關系究竟如何進行了分析,總結了國外學者關于“內外史”問題的觀點,并認為“內外史”二者應該有機地結合起來。[ ](p27-32)其理由在于“極端的‘內史論’會使科學失去其賴以生存的社會動力和基礎,無法解釋科學的發生和發展;極端的‘外史論’又會使科學失去科學味,而顯得空洞。”[ ](p64)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學者雖然未對“內外史”問題進行專門研究,但從不同的關注角度出發,大多都認為科學史的“內史論”與“外史論”必須進行某種綜合。[ ](p14,p97-98)
無論是不去討論“內外史”問題,還是總結國外學者的觀點并主張“內外史”綜合,第一類學者和第二類學者都默認了“內史”與“外史”的劃分方式,且大多更為看重“內史”。如果對他們的觀點做深入分析,不難發現在背后支撐著這種劃分及側重的仍然是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這種科學觀認為,科學是對實在的揭示和反映,它的發展有其內在的邏輯規律,不受外在的社會因素的影響,科學的歷史是一系列新發現的出現,以及對既有觀察材料的歸納總結過程,是不斷趨向真理和進步的歷史。這種科學觀指導下的科學史研究就必須揭示出科學發展的這種“內在”發展邏輯,揭示科學的縱向的“進步”歷史。例如,有學者在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科學、科學史的發展來談“內史”先于“外史”的合理性時,提到“科學史一開始的首要任務就是對科學史事實在(包括科學家個人思想、科學概念及理論發展)的內部因素及產生機制的研究。而這一科學史事實在內部機制的研究構成了科學史區別于別的學科的特質和自身賴以存在的基石。也就是說內史研究是科學史的基礎和起點;”“外史是在內史研究的基礎上隨著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增大而非研究外史不可的地步時才逐漸從內史中生長出來的。”[5](p28)這些觀點大致包含了這么幾層含義:首先,科學史事實在內部蘊含了科學發展有其獨立于社會因素影響之外的內部機制、邏輯與規律;其次,對這些科學發展規律、機制及內部自主性的研究構成了科學史學科的特性;最后,注重科學內部理論概念等的自主發展的“內史”研究先于“外史”研究,“外史”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內史”的補充。盡管一些作者堅持一種“內外史”相結合的綜合論,但仔細分析起來,其“外史”仍然沒有取得與“內史”并重的位置。而且,其強調的“外史”研究也只是重視“分析科學發展的社會歷史背景如哲學、社會思潮、社會心理、時代精神以及非精神因素諸如科學研究制度、科學政策、科學管理、教育制度、特別是社會制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科學發展的阻礙或促進作用。”[5](p32)此外,從一些學者的總結性論文中可以發現,在那些圍繞著“李約瑟問題”而討論近代科學為什么沒有在中國產生的諸多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 ](p110-116)在這里,種種社會因素只被看成是科學活動的背景(盡管可能是非常重要乃至于決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其構成因素。因為在他們看來,科學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科學方法、程序以及科學結果的可檢驗性保證了科學本身的客觀性,對科學的歷史的研究,必然要以研究科學本身的內在邏輯發展為主要線索,科學史仍然是普遍的、抽象的、客觀的、價值中立的、有其獨立的內在發展邏輯科學活動的歷史。
由此可見,對“內史”與“外史”的傳統劃分的堅持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綜合”運用,都是以科學的的一種內在、客觀、理性及自主獨立發展為前提假定的,只有基于這樣的科學觀,才可能使得“內史”研究和“外史”研究分別得以成立,“內史”與“外史”的劃分才成為可能。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西方科學史界“內史論”與“外史論”的爭論之所以長期持續,原因可能恰恰在于這種科學觀本身。它使得研究者或者片面強調“內史”,完全否認“外史”研究的合法性;或者雖偏重“外史”,卻仍只將社會因素作為科學發展的背景來考察;或者雖強調“內外史結合”,卻仍以“內史”為主,“外史”為輔。要結束這種爭論,就必須在科學觀和科學史觀的層面進行超越。科學知識社會學正是基于對這一科學觀和前提假定的解構,消解了傳統的“內史”與“外史”的劃分。
三、科學知識社會學對“內外史”劃分的消解
科學知識社會學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初的英國,它以愛丁堡大學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愛丁堡學派,其主要代表人物為巴恩斯、布魯爾、夏平和皮克林等。ssk明確地把科學知識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探索和展示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變遷和發展的作用,并要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其中,巴恩斯和布魯爾提出了系統的關于科學的研究綱領,尤其是因果性、公平性、對稱性和反身性四條“強綱領”原則。除此之外,ssk的學者如謝廷娜、夏平和拉圖爾等,在這些綱領下做了大量成功的、具體的案例研究。
“愛丁堡學派”自稱其學科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是為了與早期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等人建立的“知識社會學”,以及當時占主流地位的默頓學派的“科學社會學”相區別。在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中,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知識是不能做社會學的分析的,因為它們只受內在的純邏輯因素的決定,它們的歷史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內在的因素。[ ](p68-69)在默頓的科學社會學中,科學是一種有條理的、客觀合理的知識體系,是一種制度化了的社會活動,科學的發展及其速度會受到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科學家必須堅持普遍性、共有性、無私利性等社會規范的約束。[ ](p267-278)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首先不贊成曼海姆將自然科學排除在社會學分析之外的做法,他們認為獨立于環境或超文化的所謂的理性范式是不存在的,因而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的分析不但可行而且必須,布魯爾對數學和邏輯學進行的社會學分析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p133-249)由此也可看到,ssk與默頓的科學社會學最重要的區別在于,它進一步將科學知識的內容納入社會學分析的范疇。在ssk看來,科學知識并非由科學家“發現”的客觀事實組成,它們不是對外在自然界的客觀反映和合理表達,而是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制造出來的局域知識。通過各種修辭學手段,人們將這種局域知識說成是普遍真理。科學知識實際上負載了科學家的認識和社會利益,它往往是由特定的社會因素塑造出來的。它與其他任何知識一樣,也是社會建構的產物。[9](p2)
ssk與傳統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的上述區別直接反映在其相關的科學史研究上,表現為對“內外史”的不同側重和消解。傳統知識社會學在自然科學史領域仍然堅持的是“內史”傳統,科學社會學雖然開始重視“外史”研究,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時至今日它只討論科學的社會規范、社會分層、社會影響、獎勵體系、科學計量學等,而不進入認識論領域去探討科學知識本身;在其看來,研究科學知識的生產環境和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是兩回事,后者超出了社會學家的探索范圍。[ ](p38-39)可見,傳統的科學觀在科學社會學那里仍沒有被打破,科學“內史”與“外史”的劃分依然存在,二者的界限依然十分清晰。但ssk卻堅持應當把所有的知識,包括科學知識,都當作調查研究的對象,主張科學知識本身必須作為一種社會產品來理解,科學探索過程直到其內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會化的。[12](p38)這樣一來,因為連科學知識的內容本身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獨立于社會因素影響之外的、那種純粹的所謂科學“內史”便不復存在,原來被認為是“內史”的內容實際上也受到了社會因素無孔不入的影響,從而,“內史”與“外史”的界限相應地也就被消解了。正如巴恩斯所說,柏拉圖主義對于科學而言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柯瓦雷本人的觀點也含糊不清。[ ](p150)又如布魯爾就開爾文勛爵對進化論的批判事件進行分析時指出的那樣,該事件表明了社會過程是內在于科學的,因而也不存在將社會學的分析局限在對科學的外部影響上的問題了。[ ](p6-7))。
ssk關于科學史的內在說明和外在說明問題也有直接的分析。其重要代表人物布魯爾在對“知識自主性”進行批判時,就對科學自身的邏輯、理性說明和外在的社會學、心理學說明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過討論。他指出,以往學者一般將科學的行為或信仰分為兩種類型:對或錯、真或假、理性或非理性,并往往援引社會學或心理學的原因來說明這些劃分中的后者,對于前者而言,則認為這些正確的、真的、理性的科學之所以如此發展,其原因就在于邏輯、理性和真理性本身,也即它是自我說明的。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往往認為這種內在的說明,比外在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說明更加具有優先性。[14](p9)
實際上,布魯爾所要批判的這種觀點代表著ssk理論出現之前,科學哲學和科學史領域里的某種介乎于傳統實證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之間的過渡性科學編史學思想。其中,拉卡托斯可以被看成是一位較具代表性的人物。一方面,他將科學史看成是在某種關于科學進步的合理性理論或科學發現的邏輯的理論的框架下的“合理重建”,是對其相應的科學哲學原則的某種史學例證和解釋,也就是說科學史是某種“重建”的過程,而非科學發展歷史的實證主義記錄或者某種具有邏輯必然性的歷史;另一方面,拉卡托斯又認為科學史的合理重建屬于一種內部歷史,其完全由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只有當實際的歷史與這種“合理重建”出現出入時,才需要對為什么會產生這一出入提供外部歷史的經驗說明。[ ](p163)也就說,科學發展仍然有其內在的邏輯性、理性和真理性,科學的內部歷史就是對這種邏輯性和合理性方面的內部證明,它具有某種邏輯必然性;而社會文化等方面因素仍然外在于科學的合理性和科學的邏輯發展,仍然外在于科學的“內部歷史”,是科學史家關注的次要內容。但這種歷史觀內在的悖論在于,那種純內史的合理重建,實際上又離不開科學史家潛在的理論預設,因而是不可能的。
正如布魯爾所說,考察和批判這種觀點的關鍵首先在于認識到,它們實際上是把“內部歷史”看成是自洽和自治的,在其看來,展示某科學發展的合理性特征本身就是為什么歷史事件會發生的充分說明;其次還在于認識到,這種觀點不僅認為其主張的合理重建是自治的,而且對于外部歷史或者社會學的說明而言,這種內部歷史還具有優先性,只有當內部歷史的范圍被劃定之后,外部歷史的范圍才得以明確。[14](p10)實際上,布魯爾強調科學知識本身的社會建構性,恰恰是基于對這種科學內部歷史的自治性和隨之而來的“內史”優先性假定的批判,而這一批判又導致了科學編史學上“內外史”界限的模糊和“內外史”劃分的消解。
四、其他相關分析與評論
ssk之于科學的社會學分析以及隨之可能帶來的科學史“內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引起了國內少數學者的注意,但他們對此所持的態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例如,有的學者認為,科學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和sts研究,就其個人看法,缺乏思想的深度,偏重了科學外部的社會性分析,如能注入科學思想的成分和哲理性的分析會更好些。[6](p63-64)此外,還有些學者肯定了ssk研究的價值,并從中看到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和默頓學派對待科學合理性和科學知識本性的態度的不同,但認為在一定意義上ssk是用相對主義消解了在科學理性旗幟下“內外史”觀點之爭。[ ](p47)實際上,認為社會學的分析缺乏深度,本身就是在對科學知識、科學理性與內在邏輯性不可做社會學分析的觀點的一種認可,并潛在地賦予社會學的“外史”研究以較低的地位。認為“內史”與“外史”的劃分必須存在,認為ssk對“內外史”之爭的消解來自于其相對主義的科學觀等等,實際上都反映了對傳統的科學理性、客觀性、價值中立性、真理性與實在性的堅守,這種堅守又意味著對科學內在的發展邏輯做“內史”考察是可能的,并且是第一位的。
然而,在國際學術背景中,后庫恩時期研究的整體趨勢確已開始走向了將“內史論”和“外史論”相結合的道路,只不過這種結合更多地是將“內史”與“外史”的界限逐漸模糊和消除。例如,除了ssk的理論可以消解傳統的“內史”與“外史”的劃分之外,類似地,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同樣可以對這一劃分進行解構。在女性主義者看來,并不是科學研究的結果被政治家誤用或濫用,而是社會政策的議程和價值已內在地包含于科學進程的選擇、科學問題的概念化理解以及科學研究的結果中。[ ](p81)因而,科學本身即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為此也就不存在著對科學內在獨立邏輯的某種真理性的挖掘,也不存在關于社會因素加于科學發展之上的某種作用關系的考察。正如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家哈丁所認為的,“內史論”與“外史論”之間的界限是人為的,兩者之間的共同特點是贊同純科學的認知結構是超驗的和價值中立的,以科學與社會的虛假分離為前提,因此他們并沒有為考察社會性別關系的變遷和延續對科學思想和實踐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留下認識論的空間。[17](p82)
這種整體趨勢在關于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中也有實際的體現。在李約瑟去世后,2000年,由研究中國科學史的美國權威學者席文負責編輯整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6卷“生物學與生物技術”第6分冊“醫學”得以出版,這是一個很有象征意義的事件。此卷此分冊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其它已經出版了的各卷各分冊有明顯的不同。席文將此書編成僅由李約瑟幾篇早期作品組成的文集。對于席文編輯處理李約瑟文稿的方式,學界當然存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席文的做法確也明顯地表現出他與李約瑟在研究觀念等方面的不同。他在為此書所寫的長篇序言中,系統地總結了李約瑟對中國科學技術史與醫學史的研究成果與問題,并對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做了全面的綜述,提出了諸多見解新穎的觀點。在他那篇重要的序言中,席文明確指出:“由于對相互關系之注重的革新,內部史和外部史漸漸隱退。在80年代,最有影響的科學史家,以及那些與他們接近的醫學史家,承認思想和社會關系的二分法使得人們不可能把任何歷史的境遇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p1-37)
“內史”與“外史”的劃分、“內史”與“外史”何者更為重要以及“內史”與“外史”二元劃分的消解,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科學觀,在這些不同的科學觀下又產生了科學史研究的不同范式和綱領。“內史”的研究傳統在柯瓦雷關于16、17世紀科學革命時期哥白尼、開普勒、牛頓等人的研究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外史”的研究方法則在18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科學技術的互動方面,找到了合適的落腳點;而ssk的案例研究則充分體現了打破“內外史”界限之后,對科學史進行新詮釋的巨大威力。盡管科學哲學領域對于ssk的“相對主義”、“反科學”以及圍繞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仍在持續,但在某種意義上講,對于科學史研究來說,ssk對“內外史”界限的消除也可以被看作是打通了“內史”和“外史”之間的壁壘,形成了一種統一的科學史。在這種新的范式下,科學史研究能夠大大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給予科學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以更為深入的分析和詮釋。
[1 ]劉兵.克麗奧眼中的科學[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
[2 ]吳國盛編.科學思想史指南[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
[3 ]邱仁宗. 論科學史中內在主義與外在主義之間的張力[j].自然辯證法通訊,1987,(1).
[4 ]魏屹東,邢潤川.國際科學史刊物isis(1913-1992年)內容計量分析[j].自然科學史研究,1995,(2).
[5 ]魏屹東. 科學史研究為什么從內史轉向外史[j].自然辯證法研究,1995,(11).
[6 ]魏屹東. 科學史研究的語境分析方法[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2,(5).
[7 ]江曉原.為什么需要科學史——《簡明科學技術史》導論[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4);肖運鴻.科學史的解釋方法[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4,(3).
[8 ]胡化凱. 關于中國未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的幾種觀點[j].大自然探索,1998,(3).
[9 ]趙萬里.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0 ] r.k.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11 ]大衛•布魯爾.知識和社會意象[m].艾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
[12]劉華杰.科學元勘中ssk學派的歷史與方法論述評.哲學研究[j].2000,(1).
[13 ]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m].魯旭東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14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15 ]伊•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m].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16 ]趙樂靜,郭貴春.科學爭論與科學史研究[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