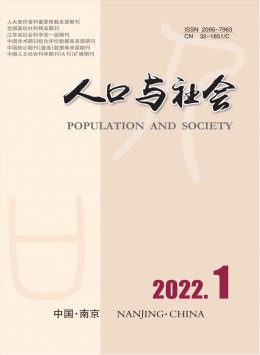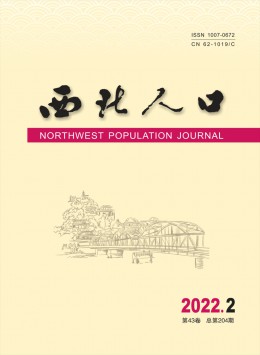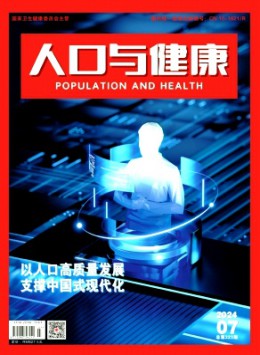人口流動的原因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人口流動的原因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影響因素
一、研究背景
伴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城市化的加速帶來了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遷移,在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下,就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流動人口階層,構成了轉型期社會第三元。與城市和農村常住人口相比,一方面流入城市的農民往往在觀念、行為方式上受城市的巨大沖擊,加之流動本身伴隨的生活不穩定和職業頻繁變更,其生育觀念和行為方式上有別于其家鄉人;但另一方面,農村文化在他們身上仍烙下印跡,制度限制又使得他們很難真正地融入城市社會,從而造成他們對城鄉兩種文化的雙重不適應,成為一個既游離于農村、城市之外又與兩者有緊密聯系的邊緣群體。因此,對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的分析必將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
二、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
(一)期望子女數
期望子女數是人們在一定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下對生育子女數的期望。絕大多數流動人口對于孩子數量的選擇傾向取決于其目前的經濟狀況。調查顯示,期望子女數為2個的比例高達52.60%,1個的為40.86%,3個及以上的為4.70%,不要孩子的比例只有1.84%。可見,大多數流動人口的期望子女數是1至2個,想要3個及以上的人數較少。流動人口的期望子女數在年齡上呈現出一定規律,即年齡越大,期望子女數越多;從性別來看,男性意愿子女數要多于女性。這種差異是由于女性是生育的直接承擔者,而且女性在養育子女上花費的時間遠多于男性;不同婚姻狀況的流動人口,意愿子女數也有較大差異。
(二)性別偏好
性別偏好是指人們期望生男孩還是生女孩,是人們對孩子性別的一種愿望和需求,即意愿生育性別。流動人口對孩子的性別預期呈現多元化的特點。據資料顯示,“兒女雙全”是農村流動人口最主要的理想子女性別結構,其次是男孩偏好,最后是無性別偏好和女孩偏好。城市中有別于農村的社會關系以及自我保障能力,弱化了男孩偏好存在的環境和經濟基礎,但是在流動人口中,男性偏好的程度還是相當高的,女性在短期內還是較難取代男性的繼嗣功能和經濟效用。但性別選擇已經開始呈現出理性的一面,女孩偏好或者沒有性別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漸增多。
(三)生育動機
生育動機即生育目的,指人們是出于何種目的而考慮生育。生育動機反映了人們對子女價值的判斷和看法,它一般包括傳宗接代、養兒防老和消除社會壓力等等。據資料顯示,農村育齡婦女中有接近三分之一認為養兒防老是她們生育子女的主要動機,將近四分之一的育齡婦女認為傳宗接代是其最主要的生育動機。相對于農村居民而言,流動人口受傳宗接代、養兒防老這些傳統思想的影響相對要弱些,但由于針對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等方面存在缺失現象,導致了生育動機方面,養兒防老、傳宗接代仍然占據主要位置。
三、農村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
影響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國家政策干預外,還有其他復雜多樣的影響因素在起作用。一般來說,主要包括個體層面的因素、家庭層面的因素和城市的社會融入因素。
(一)個體層面的因素
流動人口個體層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是否購買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流動人口個體因素會直接影響其生育觀念。年齡較大的流動人口受傳統生育文化影響較大,更希望傳宗接代、養兒防老;教育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也不言而喻,受教育水平高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注重自我發展”的現代型生育觀念;此外,有社會保險者晚年對子女的依賴度會有所降低,也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二)家庭層面的因素
家庭層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家里人口數、家庭人均收入等。家庭因素對個人生育決策有著很大的影響作用。大家庭一般是多代同堂,長輩容易將傳統的生育觀念滲透到晚輩中,同時又會以已有的多子女行為作為示范效應加以強化。所以一般來說,來自大家庭的人往往傾向于多生育,對男孩的偏好也較強。家庭收入高低對人們決定是否要孩子可能有不同影響,收入高可能未來通過孩子來養老的需求小,降低生育意愿,但同時,收入高者撫養孩子能力也更強,可能會傾向于多要孩子。
(三)城市的社會融入因素
社會融入因素主要考慮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情況、工作類型、流動時間等。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過程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相對穩定的職業、像樣的經濟收入及社會地位,這些條件使流動人口與流入地常住居民交往和參與流入地的社會生活成為可能,并促進他們接受與當地人相似的價值觀,包括生育意愿方面的觀點和看法。社會融入因素中的工作類型和居住類型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是顯著的,在公有制企業、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的流動人口意愿生育的子女數較其他工作類型的人要少;通過租房或自購房這種散居的方式在城市定居的流動人口較混居在宿舍工棚的人更傾向于少生。
四、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具有雙重性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工作和居住環境的改變,使他們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響,遠離了農村社區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與農村社區之間依然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還受到根深蒂固的農村生育文化的牽制。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生育意愿內部的變化是不同步的。期望子女數的變遷相對較快,性別偏好與生育動機變遷相對遲緩。在現有的戶籍制度下,流動人口要想徹底改變傳統的生育觀念,仍然具有很多困難。因此,政府政策未來改革的取向,需要通過戶籍制度和相關配套體制改革,在就學環境、居住條件、社會保障和工資待遇等方面逐漸為流動人口實現長久遷移創造條件,通過系統性的制度促進流動人口實現社會融和,從而實現健康的人口城市化。
參考文獻
[1]佟新.人口社會學(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王薇.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分析―以廣西宜州市農村流動人口調查為基礎[D].南開大學,2008.
[3]劉愛玉.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變遷及其影響[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8(5).
第2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國際資本流動;非價格因素;啟示
國際資本流動的成因可分為價格因素和非價格因素。價格因素的理論包括以利率差為成因的流量理論,以“利率-風險”為基礎的存量理論,貨幣現象的貨幣分析理論以及交易成本理論和危機模型等理論。非價格因素主要包括制度質量和人口結構。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和人口老年化的發展,非價格因素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本文將綜述國際資本流動的非價格性因素和對我國的啟示,這不僅有利于我國更好地管理好國際資本的流動,還對防止它們危害中國的金融安全和經濟穩定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非價格因素的文獻綜述
1.制度質量
制度質量與國際資本流動的關系應從“盧卡斯之謎”開始研究。“盧卡斯之謎”是指與資源應該從資本豐裕(收益率低)的國家向資本稀缺(收益率高)的國家流動的理論相反,在現實中更多的國際資本流向了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質量低下是“盧卡斯之謎”廣泛受到認可的解釋。制度質量低下主要指產權保護不力、政府債務違約和官員等。這些不良現象會使得發展中國家風險調整后的資本邊際報酬不高于甚至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因而導致國際資本逐漸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Alfaro等對解釋“盧卡斯之謎”不同的理論假說進行經驗分析,其中假說包括制度質量、人力資本和信息不對稱等。研究結果表明在1970-2000年間,制度質量低下指標解釋了52%的外商直接投資和證券資產的國際流動,這說明制度質量低下是解釋“盧卡斯之謎”的主要原因。
2.人口結構
人口結構的分析以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生命周期理論是指人會從一生整體上權衡消費,換句話說,即年輕和年老時消費大于儲蓄,甚至透支消費,而中年時則多儲蓄少消費。以生命周期理論為分析基礎的人口結構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具體表現如下:一是老年和少年人口占比大,撫養負擔會增大,從而需要減少儲蓄來滿足撫養需求。二是勞動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勞動人口減少,會導致投資回報下降,同時勞動人口的就業需求減少,從而導致投資需求下降。三是封閉經濟下,儲蓄率下降,投資率下降;開放經濟下,經常賬戶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緩沖工具,會打破國內儲蓄率與投資率之間的關聯,使得儲蓄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而如何流動取決于儲蓄和投資下降幅度的相對大小。大量實證分析證實人口結構對儲蓄的影響要大于對投資的影響。換句話說,當人口結構趨于成年時,儲蓄增加幅度大于投資增加幅度,經常賬戶余額上升;反之,當人口結構趨于老年時,儲蓄下降幅度大于投資下降幅度,經常賬戶余額下降。
從對我國的分析來看,簡永軍等通過基準模型的模擬,發現資本會由人口快速老齡化地區流向人口老齡化速度相對較慢的地區,我國人口的快速老齡化會使得我國向世界輸出大量的資本,我國扮演著“資本輸出”大國的角色,而美國則為最大的資本流入國。從對國際的分析來看,朱超等分析人口年齡結構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關系,發現總體上經常賬戶余額與人口撫養比的逆向相關,全球國際資本從成年國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國家。
雖然非價格因素越來越重要,值得研究,但非價格因素研究有難點,制度質量的衡量指標難以選擇,導致關于制度質量的實證鳳毛麟角;人口結構問題選取指標與模型困難,因而雖然有一些實證證明,但得出的結論并不一致。所以如何選擇指標和模型成為非價格因素的未來研究方向。
二、啟示
國際資本流動理論基于非價格因素的文獻綜述給我國以下啟示:
從制度質量上來看,我國需要規范產權制度、提高政府執政能力、嚴懲官員腐敗等,以提高我國制度質量,以穩定我國國際資本流動。
從人口結構上來看,我國要密切關注人口結構問題。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漸漸消失,我國可以采取推遲退休年齡的政策。這不僅可以解決人口老年化問題,還可以降低儲蓄率和經常項目順差,有利于管理好我國國際資本流動。
參考文獻:
[1]王永忠.國際資本流動悖論:一個文獻綜述[J].金融評論,2010,(04).
[2]Alfaro,L.Kalemli-Ozcan,S.and Volosovych,V.(2005):“Why Doesn't Capital Flow from Rich to Poor Countr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BE
R Working Paper, No. 11901.
[3]Kim,S.and J.W.Lee.Demographic Changes,Saving,and Current Acco
unt:An Analysis Based on a Panel VAR model[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8 (20): 236-56.
[4]簡永軍,周繼忠.人口老齡化、推遲退休年齡對資本流動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11,(02).
第3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一、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實證分析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西藏、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可見,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2)充分發揮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城鎮的聚集經濟功能,增強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步形成符合經濟規律和我國國情的現代化城市體系。這一體系的形成必須遵循客觀規律,而不能人為地“制造”。經驗表明,違背客觀規律而人為地制造的“經濟中心”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勞動力及人口由經濟落后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和聚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也是確定我國城市體系的布局和結構的主要依據。據此可以設想未來中國城市體系應當是:以現有大城市為中心輻射周邊城鎮形成數百個城市聚集體,以此為依托形成以東部及沿海地帶為重心、東中西部布局合理、規模不同的數十個城市化地帶。它是未來中國工商業中心和大多數人口。的聚居地。
第4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流動;二元經濟;戶籍制度;勞動力市場
中圖分類號:F323.6
勞動力流動是勞動者以改變就業形式、改善收入狀況等為導向的一種跨地域流動行為。在任何時期的任何國家,勞動力流動都是勞動力市場的一種常態。根據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推算,2010年農村就業勞動力達到1.55億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萬人,增長率為5.2%①。另據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達到1.59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高達44.2%②;2012年進城農民工數量則高達1.63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達到44.0% 。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是我國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現象。我國流動人口特別是鄉城流動人口規模之大,增長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我國的人口流動已成為“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活動 ”③。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歷史沿革
根據不同時期國家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的不同,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流動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以前的嚴格限制流動階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國處于計劃經濟階段,對勞動力流動嚴格控制,對勞動力實行有計劃的流動,不在計劃之內的流動被稱為“盲流”。在城鄉嚴重分割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由農村遷移到城鎮的途徑很少,只能通過城鎮企業有計劃的招工、子女上大學、部隊干部轉業等途徑來實現遷移。
第二階段,1980年以后勞動力流動開始恢復,進入允許遷移階段。隨著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向鄉鎮企業流動。而且從1984年開始,國家允許農村居民自帶口糧、自籌資金進城務工經商,這個政策極大地刺激了勞動力的流動,此時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快速增長時期。張曉建(1997)估計,1980年代末在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村勞動力達到了1500多萬人④。
第三階段,1990年代進入跨區域流動階段。進入1990年代,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時期,主要是由農村地區流向城鎮地區,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跨區域流動頻繁。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1995年出省的農村勞動力人數大約為2500~2800萬人⑤。
第四階段,2000年以后進入快速的大規模流動階段。從2000年開始國家實施了積極的遷移就業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對農民工進城的不合理限制,推進相關配套改革保障農民工權益,促進勞動力市場發育。這些鼓勵政策極大地激發了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流動:2002年末,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數量就突破1億人,達到1.05億人,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高達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進城務工人員數量一路攀升,占城鎮就業的比例也一直維持在40%以上。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規模
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從一個地區向另一個地區遷移、流動的過程。近年來,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特別是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流動引起了學者和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2006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指出,我國的流動人口達到總人口的10%以上,“我國目前正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規模最大的人口遷移活動,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遷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計,全國在城鎮就業的農村勞動力數量1995年為3600萬,1996年為4000萬,1997年達到4600萬,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京、津、滬三地的流動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達到20%~25%,廣州市甚至達到38%,這些流動人口50%以上是由農村遷移出來的。⑦《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數量達到1.45億人,比上一年增加492萬人,增長率為3.5%⑧。另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北京市外來流動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該比重甚至達到39%⑨。
根據1983-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相應年份人口統計數據以及其它資料整理出了我國1983-2012年的進城農民工數量及其占城鎮就業比例的數據,由于受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數據缺失。為了更直觀地描述進城農民工的數量及其占城鎮就業比例的變化趨勢,圖1給出了它們的變化曲線圖。從圖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國進城農民工數量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從1983年的200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萬人,同時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主要表現為:1983-1994年處于快速上升時期,主要原因是從1980年開始國家開始允許勞動力的鄉城遷移,農村勞動力流動開始恢復,且到了1990年代勞動力跨區域流動頻繁,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一個高漲時期;1995-1997年處于下降階段,原因是這段時間進城農民工由于在城鎮受到歧視等因素影響,部分勞動力開始回流到農村;1997年之后隨著國家對農民工權益保障力度的加強以及農民工工資的提高,農村居民進城務工的意愿和動力增強,進城農民工數量處于穩步上升階段。從圖1也可以看出,農民工占城鎮就業的比例總體上處于上升趨勢,從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變化的趨勢及階段性特征與進城農民工數量相類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變化趨勢。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進城農民工占城鎮就業的比例出現了下降趨勢并趨于穩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民工回鄉現象,但由于受國家實施的經濟刺激和就業調整政策影響,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農村外出就業人口逐漸恢復常態;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就業人數的增長,進城農民工數量的增長量相對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出現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導致能夠轉移到城鎮就業的農民工數量減少。有學者估算表明,現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并沒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艷(2007)利用反設事實法,通過估算農業中種植業和飼養業的勞動力需求數量,根據農村勞動力的不同轉移規模,估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和比例的三種不同情形,得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和比例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農村剩余勞動力50%左右是40歲以上的勞動力⑩。另據估算,我國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在9000萬人左右,與本世紀初相比大約減少了6000萬人,而且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以剩余時間的形式存在的,絕對意義上的剩余人口并沒有這么多!。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形式和特征
對我國來說,勞動力流動主要是指勞動力由農村向城鎮、由農業向非農業的轉移過程。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主要是城市工業部門以招工形式為主的有計劃的轉移。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戶籍管理的松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形式轉變為以就地轉移和跨區域轉移為主的轉移形式。所謂就地轉移,是指農村勞動力由農業向本地縣城的轉移,即鄉外縣內的流動。這種轉移形式在改革開放之初最為明顯,主要原因是農村副業、鄉鎮企業以及城市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所謂跨地區轉移,顧名思義,是指農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廣義上的跨地區轉移還包括跨縣流動,即縣外省內的流動。跨地區的勞動力轉移雖然開始時間較短,但已經成為當前或許未來一段時間內勞動力轉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的勞動力流動@達到26139萬人,其中就地轉移#達到3996萬人,跨地區轉移$達到22143萬人,分別占農村勞動力流動總人口的17.27%和84.71%。與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相比,就地轉移人口和跨地區轉移人口分別增長了71.37%%和82.89%⑨。另據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2011年農村外出就業人口中,跨省就業比重達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個百分點;縣外省內就業比重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個百分點;鄉外縣內就業比重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個百分點;2012年跨省就業比重為46.8%,縣外省內就業比重33.2%,鄉外縣內就業比重為20%,增減趨勢與2011年基本一致^。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勞動力跨地區轉移占總勞動力流動的比重和增長幅度大大超過就地轉移,已經成為勞動力流動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說的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的鄉城遷移,更準確地說是指勞動力跨地區的鄉城流動。
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為主
Zhao(1999)根據1995年四川省農村住戶調查數據的計算結果表明,男性占遷移人口的72%,而農村非遷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勞動力遷移的概率低4.7%&。根據2006年《我國農民工調研報告》,男性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體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顯示,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流動以男性為主的特征一直延續到現在,2012年的最新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男性農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壯年為主,且年齡有提高趨勢
Zhao(1999)使用的調查數據顯示,遷移人口的年齡比非遷移人口將近小10歲,且隨著年齡的增大,遷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2002年在全國12個省份所做的城鎮住戶和暫住戶調查數據分析結果表明,流動人口比城鎮人口年齡將近小6歲) 。2006年《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_平均年齡只有28.6歲,其中,16~20歲的農民工占18.3%,21~25歲占27.1%,26~30歲占15.9%,31~40歲占23.2%,40歲以上占15.5%+。2010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為33.8歲,其中,16~20歲占6.5%,21~30歲占35.9%,31~40歲占23.5%,41~50歲占21.2%,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數據表明: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7.3歲,其中,16~20歲占4.9%,21~30歲占31.9%,31~40歲占22.5%,41~50歲占25.6%,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進城農民工的平均年齡有了提高(2006年為28.6歲,2010年為33.8歲,2012年為37.3歲),且青壯年(21~40歲)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為66.2%,2010為59.4%,2012年為54.4%),這意味著40歲以上的外出農民工越來越多。主要是因為外出農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農民工收入增加額比上年同期減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個百分點^),且東、中、西部外出農民工收入趨同(2012年東、中、西部農民工月收入分別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壯年農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較高,在自己家鄉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價比的工作,也就是說,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農村非流動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農村住戶調查數據表明,遷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遷移人口,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遷移,但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這些人并不是選擇外出務工,而是就地占據基層資源,比如擔任村干部等職能崗位&。根據2006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4年外出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比重達到81.6%,比全國農村勞動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個百分點2。2012年的數據也是如此:外出農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農村非流動人口只占10.9%^。
4.勞動力流動的區域間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研究發現,在2000年,東部地區有65%的跨省勞動力遷移是發生在地區內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分別有84%和68%的跨省勞動力遷移到東部地區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沿海發達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內陸欠發達地區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這反映了我國的人口流動是從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遷移過程。此外,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水平呈現出區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據1992年的分省面板數據研究發現,西部和中部地區流動到東部地區的是技術工人、管理人員等人力資本較高的人員,而東部地區流動到中部的是非技術人員,很少有流動到西部地區的5。另據《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人數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占全國外出農民工的比重分別為17%和20.2%⑧。2012年的調查數據也證實了這一區域不平衡現象:外出農民工中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占42.6%,中部地區占31.4%,西部地區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外出農民工中在東部地區務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與2009年(62.5%)相比該數據已經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相反,在中西部務工的農民工比重有了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東中西部外出農民工收入趨同,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參保率低于城鎮居民
由于農民工在城鎮從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職業,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簽訂就業勞動合同6,從而導致外出農民工的社保參保率較低,且明顯低于城鎮居民參與水平。圖2反映了2012年城鎮居民和外出農民工社保參保率的差異。從圖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險”中,除了工傷保險外出農民工比城鎮居民參保率略高以外,其他類社會保險參保率城鎮居民均比農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為什么要比城鎮居民高,原因顯而易見,跟農民工從事的高風險行業密切相關。有調查數據顯示,2012年外出農民工中有60.7%從事制造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等安全事故高發的行業;從事這些行業的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也高達73.5%^。
(三)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
根據勞動力遷移的經典理論,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農村居民在城鎮就業的預期純收入
農村居民在決定是否向城鎮遷移時考慮的不僅是在城鎮就業的預期收入,還要考慮城鎮生活成本,包括貨幣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謂貨幣成本是指農村居民由農村遷移到城鎮所花費的交通費用、找工作花費的時間和金錢等;心理成本是指遠離親人,適應陌生環境所帶來的心理壓力等。如果預期收入與生活成本的凈值大于零,則選擇遷移,否則不遷移。
2.戶籍制度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決定是否遷移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戶籍制度,遷入地的戶籍管理越松或戶籍限制越少,勞動力流向該地的可能性越大。
3.遷移距離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遷移距離也是影響遷移的一個重要因素。遷移距離的遠近直接影響遷移者獲取勞動力市場信息的成本、回家鄉往返交通成本、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農村勞動力的遷移呈現出就近區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勞動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蘇、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廣東,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響我國勞動力跨地區流動、鄉城流動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發達地區居民人均收入較高,外出勞動力就較少;而內陸中、西部地區居民平均收入較低,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就較大。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較高,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較小;而農村居民平均收入較低,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就較大。
5.年齡因素
在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以青壯年為主,這與外出勞動力所從事的職業有關。農村的外出務工人員大多數從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職業”,這些職業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業,年齡成為從事這些職業的必需條件。另外,年齡越輕的人,遷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遷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長,從遷移中獲得的潛在收益的現值也越大。我國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16~25歲的勞動力占全部遷移人口的50%左右,16~35歲的勞動力占全部遷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狀況、子女上學、家庭贍養老人等問題,這些也是影響勞動力遷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發現,未婚人員遷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從于家庭的遷移,家庭中存在學齡孩子會降低遷移的可能性9。另外,隨著家庭規模的擴大,遷移的潛在成本會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遷移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資本存量就越高,從遷移中獲得的潛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對生活的追求越高,改變現狀的動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關政策建議
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國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既受經濟方面因素如農民工在城鎮的預期收入等的影響,又受城鄉之間不平等的因素如戶籍制度和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等的影響。因此,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是我國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現象和典型特征。要進一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既要增加農民工收入,又要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來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歧視和不平等,而農民工在城鎮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素質影響以外,很大程度上還受歧視性因素的影響(如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勞動力市場)。因此,要促進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就要從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兩大方面著手:
(一)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一個最主要因素。有學者的研究發現,本世紀初的戶籍制度改革對農民工流動的影響不大,主要是因為部分省市僅僅是統一了城鄉戶口稱謂,城鄉戶口所攜帶的實際差別并沒有消失0。因此,要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就必須要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在于剝離與戶籍相掛鉤的城鄉歧視性政策和一系列隱利,統籌城鄉居民的遷徙權-(陳光普,2013)。戶籍上所附加的各種福利政策人為地加大了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剝離與戶籍捆綁的社會福利,關鍵在于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戶籍觀念。
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離不開與戶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攜帶的社會保障制度,消除城鎮和農村地區在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等。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村勞動力的合理有序流動提供了制度保證: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盲目流動;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調動那些有能力轉變為城鎮“市民”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積極性;同時對于解決流動人口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子女上學等問題有重要作用。
在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會有很多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城鎮居民,而這些人的收入比城鎮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2002年全國12個省份的城鎮住戶和暫住戶調查數據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小時工資只有城鎮人口的61.67%),但比農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雖然這些務工人員成為城鎮居民會降低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邊際上降低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會更大,進而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比原來的更大。因此,在進行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為城鎮居民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過測算認為,當前的農民工工資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農民工工資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農民工在城鎮所受到的就業、工資以及社會保障方面的歧視;增加他們再教育和培訓的機會,增強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等。
(二)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根據前文的分析,勞動力市場的發育程度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重要影響,越完善的勞動力市場,或者說城鄉一體化程度越高的勞動力市場有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地區的流動。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現象仍然存在,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仍然很低。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不僅能矯正勞動力市場的資源配置扭曲,還能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進勞動力流動就要加快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我國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最主要表現是,城市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是指向具有城市戶籍的本地人提供就業崗位的勞動力市場;次要勞動力市場是指向外來農民工提供就業崗位的勞動力市場,這些就業崗位大多數是工作條件差、工資待遇低的崗位。造成我國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其它城鄉分割制度,如城鄉分割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這些制度阻礙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就業部門的自由轉移。戶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鎮勞動者優先獲得就業機會,而農村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劣勢地位;另一方面戶籍制度限制了農村流動人口在城鎮享受與城鎮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機會。因此,要培育和發展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勞動力由農村地區向城鎮地區的自由流動,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還需要建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就業制度,包括取消對進城農民工在就業工種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對勞動者的身份歧視,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信息網絡和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實行農民工社會保險與城鎮居民社會保險的相互銜接,以及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相互銜接和轉換。政府部門還應該把勞動力市場改革的重點從戶籍制度改革向就業制度、社會福利制度改革轉變,消除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所受到的各種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來促進和吸引農村勞動力從流動狀態向城鎮永久性居民轉變。
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的培育還離不開勞動力市場制度、各種規制和協調機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勞動立法、加強工會作用、建立勞動者權益保障機制等等。此外,政府職能要從以經濟干預為主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保護勞動者權益、降低勞動者所承受的就業風險,加大政府對勞動者的社會保護力度,同時發揮各類社會組織在建立、健全旨在保護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的社會保護機制方面的積極作用。
注釋:
①來源于2010年12月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
②來源于2011年和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③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力問題報告,NO.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④張小建:《中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啟示錄》,中國勞動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頁。
⑤來源于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公報。
⑥進城農民工數據來源于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城鎮就業數據來源于2002年《中國統計年鑒》。
⑦仲小敏:《世紀之交中國城市化道路問題的探討》,《科學經濟社會》2000年第1期,第38~42頁。
⑧參見國家統計局農村司:《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0年。
⑨來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公報。
⑩蔡昉、王美艷:《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事實的重新考察——一個反設事實法的應用》,《中國農村經濟》2007年第10期,第4~12頁。
!蔡昉等:《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頁。
@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計算得來的。
^來源于2012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
(來源于2010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數據。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調查年度內,在本鄉鎮地域以外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
+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
1來源于2010年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力問題報告,NO.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頁。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公報。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據《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2年外出農民工中簽訂勞動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陽、王美艷:《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孫文凱、白重恩、謝沛初:《戶籍制度改革對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經濟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頁。
-陳光普:《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的動態計量分析》,《經濟師》2013年第3期,第38頁。
=丁守海:《農民工工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一項實證研究》,《中國農村經濟》2006年第4期,第56~62頁。
參考文獻:
[1]蔡昉,都陽,王美艷.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治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蔡昉.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力問題報告,NO.7[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3]蔡昉,王美艷.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事實的重新考察——一個反設事實法的應用[J].中國農村經濟,2007(10):4-12.
[4]蔡昉,等.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2011[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
[5]陳光普.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因素的動態計量分析[J].經濟師,2013(3):38.
[6]丁守海.農民工工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一項實證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06(4):56-62.
[7]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8]孫文凱,白重恩,謝沛初.戶籍制度改革對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1 (1):35-40.
[9]張小建.中國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啟示錄[M].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7.
[10]仲小敏.世紀之交中國城市化道路問題的探討[J].科學經濟社會,2000(1):38-42.
[11]Cai Fang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J].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3(2).
[12]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J].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7 (2):8-16.
[13]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749-775.
[14]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C].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2006.
第5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農民流動 民工潮 農民工
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跨區流動,即“民工潮”,日漸成為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對此大規模的民工流動,國家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平安渡過,但現實中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流動的短暫時期內造成的交通運輸及相關社會影響,而在于這些勞動力在流入城市之后造成的社會后果和遠期效應。從這一點來看,目前的討論大部分注重現象的描述和流動利弊的分析,并未用社會學系統的觀點看問題。與許多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情況類似,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已是不可逆轉的現實問題。從輿論傾向看,理論界和民工流動地強調其利,而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政府與居民多重視其弊。事實上,不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操作上,現在該做的已不是利弊分析,而是必須著力研究政府和社會各個部門如何興利除弊,系統協調城市與民工的關系,使各種社會資源包括民工勞動力的配置趨于最優化,使與民工流動相關的社會利益分配失衡降低到最小。本文將深入細致地探討“民工潮”背后隱藏的社會問題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原因
1、我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農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動的必然性
(1)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人口眾多是我國最突出的國情,龐大的農村人口基數帶來巨大的就業壓力。
一方面,耕地逐年減少,農村就業彈性十分小;另一方面,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土地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下降。這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尋求其它就業渠道,從而出現了各種方式的流動。
(2)農業比較效益下降。由于農業比較收益下降,土地對農民的吸引力越來越小,再加上農民收入增長不前,各種收費增多,負擔沉重,這是“民工潮”的直接動因。人口問題和農業問題的交織已將許多農民推向城市,由此構成不發達省區“民工潮”的推力。
(3)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的內在要求。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在生產技術極為落后的農業基礎上開始的,建國后所走
的重型工業化道路使國家的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偏差越來越大,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更加突出了國民經濟的二元結構特點。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及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導致兩個明顯不同的階層的出現: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我國現階段正處于農業勞動力非農化時期。轉變二元結構格局,推進農業勞動力非農化,從而實現現代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2、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是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的根本原因
我國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發展政策,導致城鄉間經濟差距較大。農民在意識到了這一點后,產生了強烈的離土流動的傾向。就全國來看,農村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我國的中西部人口7.2億,集中了全國63%的人口。其中農村人口5.77億,占全國農村人口的64.4%,中西部農業勞動力占全國勞動力的76.2%,我國的勞動力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而且基本上是以從事農業為主。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大批農民從中西部流往東部地區,從內地奔向沿海,從農村涌向城市,形成了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
3、農民觀念的更新和寬松的政策促進了農民的流動
隨著改革的深化,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市場意識不斷增強,觀念不斷更新,眼界不斷開闊,沖出家園致富的愿望越來越強烈。加上不少地區把勞務輸出作為本地區經濟的一條途徑,注意加強引導、服務和組織,消除了農民外出打工的一些限制,所以,農民一般憑一張身份證就可走南闖北。
總之,我國現階段正處于二元結構向現代化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上述各種原因的存在決定了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是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必然過程。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
十幾年來,進城民工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作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在城市“苦、臟、累、險”行業中已成為主力軍;他們把勞動所得寄回家鄉,為當地經濟發展增加了大量資金;他們在城市學到了知識和技能,回鄉后成為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生力量;他們增加了城市與農村的聯系,加快了農村城市化進程。但大量農民流入城市,也給社會治安管理造成很多困難。由于他們沒有固定住所,沒有固定職業,較難以管理。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一些城鎮中,各種刑事犯罪多數是民工所為,有的地方甚至比重高達90%左右。
三、加強對農村流動人口的管理
1、提高認識水平,破除陳舊觀念
(1)必須充分認識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的客觀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性。尊重市場經濟下人口流動的規律性,從根本上轉變對流動人口自由擇業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不得侵犯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不能一提流動人口,就把他們同“盲流”和流竄犯罪分子聯系起來,隨意清理和遣返。對于已取得就業崗位的流動人口,不能肆意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克扣工資,甚至進行人身侮辱等。
(2)要克服城市自我保護意識,從市場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給農村剩余勞動力應有的地位。
(3)改革城鄉戶籍制度,打破戶口身份上的終身制和世襲制,實現人口遷移的自由。
2、加快和培育勞動力市場,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
為了減少人口流動的盲目性,必須加快建立和培育勞動力市場,引導勞動力合理流動。第一,應在交通便利的城市區建立區域性勞動力供求交易中心,為流動人口和用人單位提供公平競爭和雙向選擇的場所。第二,加強市場中介組織建設,如信息機構、職業介紹機構、職工培訓機構的建設,開展咨詢、職業介紹、培訓等系列化就業服務,以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盲目流動所帶來的風險。
3、規范政府管理行為,加強管理法規建設
(1)為加強流動人口的管理,一些地方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制定了許多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在指導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存在不少問題,必須進行認真的清理和完善,使之走上規范化、條理化和科學化的軌道。其中,凡是對流動人口管得太死、短期行為嚴重、存在歧視的政策條文應一律廢止;互相制約或不完善、不嚴密的政策條文應予調整和完善;徹底改變重收費輕管理的不良傾向。管理是政府行為,政府有相應的資金渠道,不能一提加強管理就同設卡收費和罰款聯系起來。當前農民負擔仍然沉重,即使他們外出打工掙幾個錢,也是血汗錢,來之不易,不能任意收取,對該收的費用、該辦的證卡,應力求合理、簡便、適合于流動人口的具體情況。
(2)加強市場規則建設。為了保證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平等競爭、公平交易和自由擇業的權利,必須加快市場規則的建設。對那些搞市場壟斷、歧視、侵犯自由權和契約權的不正當行為嚴加制裁。
第6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新城建設理論來源于西方城市規劃實踐,自霍華德提出建設“田園城市”的構想開始[1],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從北京推進新城建設的思路來看,更多地是希望實現沙里寧所言的“有機疏散”,即將大城市目前的擁擠區域,分解成若干個集中單元,并把這些單元有機組織成為“在活動上相互關聯的功能集中點”[2],這樣原來密集的城區分裂成一個一個的集鎮,他們彼此之間用綠化地帶隔離開來。北京市啟動新城建設不久,就有研究從城市發展階段理論出發,指出北京市目前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建設新城難以緩解中心城人口壓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為外來人口繼續向北京市遷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設過程中,順義、通州、亦莊等新城在短時間內的流動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對一些重點新城的建設進行了調查,發現重點新城建設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動人口。北京市政協相關專門委員會也組織開展了相關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協會議提案《關于統籌解決首都重點新城建設中人口問題的提案》(第2018號),呼吁重視新城建設中的人口規劃和管理問題。這些研究對于本文關注的問題已經做出了一些回答,筆者希望進一步結合初步的調查數據,一方面對這些結論進行一些實證檢驗,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來新城建設對于北京市人口規模及流動的實際效應方面有更多發現。在流動人口相關統計信息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筆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動人口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調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莊、順義與密云開展,主要通過地圖法進行抽樣,調查結束后通過再抽樣對樣本進行了篩選,最終有931位受訪者入樣。基于調查數據的分析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動人口的特征,尤其是與流動相關的特征,探討新城實有流動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機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動人口的流動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研判當前新城流動人口的未來流動趨勢。這一思路充分考慮了流動人口群體“是個內部差異性很大的異質性群體”[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關注流動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間的流動問題,從相對微觀的視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動問題。
調查數據顯示,受訪新城流動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調查對象的58.4%;平均年齡29歲,其中最小16歲,最大62歲;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離婚和喪偶者比例較低;農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為主,分別為39.7%和33%,大專和高職占10.4%。通過與北京全市范圍內的流動人口相關數據②比較可以初步發現,新城流動人口平均年齡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筆者首先考察了流動人口及家庭成員的流動情況。從調查數據來看,被調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齡為21歲,平均在外務工6年之余,平均到過2個城市,從事過2個工種。初步來看,北京新城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類型保持了一定的穩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們多屬于新生代農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與父母雙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動的趨勢較為明顯。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為20.6%。而有1個子女的流動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個子女的流動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個孩子在京的占20%。對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問卷中我們詢問其“是否打算將他們接到北京來讀書或工作”,結果顯示,38.6%被調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沒想過。將這些數據與已有調查數據比較可以發現,在有子女的流動人口群體中,就攜子女流動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對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斷,新城的流動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動人口更具有穩定居住的傾向。當然,不可忽視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動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調查數據顯示,新城區的流動人口絕大多數是從老家直接來新城區,占50.8%,其次是從北京其他郊區來到新城區,占18.2%,從中心城區和其他地方來的比例分別為15.6%和15.4%。分區縣來看(圖2),密云和亦莊流動人口來自北京中心城區的比例相對較大,分別為25%和18.8%,順義較低,為14.4%。圖2三個新城流動人口的來源分布(%)從流動原因來看,單位遷移、投奔親朋好友、提高相對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為主要的原因。不過,各區縣流動人口的流動原因則有一些差異,單位遷移是亦莊流動人口從北京中心城區或其他郊區縣來到亦莊的主要因素(25.3%),這自然與亦莊經濟開發區的產業集聚有關,不過從比例上來說仍然不高;而對密云流動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們從北京中心城區或其他郊區來到密云的重要原因,這一比例遠高于亦莊和順義,占16.7%。同時,投奔親友是流動人口在北京市范圍內流動的重要原因,各區縣的比例相當,都在25%左右。這一結果也與受訪者目前工作的獲得途徑相吻合,“家人、親戚朋友介紹”,及“同村、老鄉介紹”仍是流動人口獲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徑,分別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動人口的聚集與近年來新城建設是否存在必然聯系呢?調查考察了受訪者流動到新城的時間,發現2000年及以前來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來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體來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別占10.9%、16.0%和41.7%。這一分布至少證明新城建設與新城流動人口迅速增長是可能存在因果關系的。對于未來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調查者認為只要“工作機會好就去中心城區”,占45.5%,有37.2%的被調查者沒有計劃,17.3%的被調查者則“一直在尋找機會,遲早得去中心城區”。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動人口“一直尋找機會,遲早得去中心區”的比例最大,占31.2%,順義和亦莊的這一比例為17.8%和15.7%。綜合前文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密云的流動人口中,從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對高,同時有強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對高。結合前文關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的背后可能存在兩個重要的機制:其一,從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動人口中,存在大量的臨時性流動現象,相當數量的流動人口主要是迫于經濟壓力暫時流入生活成本較低的新城,他們一直在尋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機會;其二,對大量從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動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區—北京中心城”的發展與流動預期,新城只是他們到北京就業的過渡地。這些機制也可以從另外的一項數據得到印證。從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來看,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認為中心城區“發展機會更多”,占59.9%,其次為“城里更長見識”,占16.4%,而選擇“環境設施好”、“以后說起來也體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兒”的比例則很低,分別為7.2%、5.3%和1.3%。
為更好地了解新城區流動人口未來流動意愿,分析新城區流動人口的流動機制,我們對新城區流動人口流動意愿進行了Logistic回歸分析。我們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區”為因變量,該變量答案為二分變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歸分析法。我們以受教育程度、來京時間、來新城時間、來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為自變量,將性別、年齡、民族、戶口性質作為控制變量。其中,受教育程度為分類變量,分為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專、本科及以上;來新城之前所在地為二分變量,1=“北京其他區縣”,0=“其他省市”;性別為二分變量,1=“男性”,0=女性;民族為二分變量,1=“漢族”,0=“少數民族”;戶口性質為二分變量,1=“非農業戶口”,0=“農業戶口”;來京時間、來新城時間、收入水平、年齡為連續變量。各變量具體描述見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學者研究及前文對流動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以下假設:(1)受教育程度越高,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2)與從其他省市來到新城的流動人口相比,從北京市內城區遷往新城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再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3)來京時間越長,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4)年齡越大,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弱;(5)與女性相比,男性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6)與農業戶口相比,非農業戶口人們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4.3Logistic回歸結果分析我們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區”為因變量,將受教育程度、來京時間、來新城時間、來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別、年齡、民族、戶口性質均納入模型,利用SPSS軟件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表3所示為回歸分析結果。從Logistic回歸結果可以看出:與假設一樣,與從其他省市來到新城的流動人口相比,從北京市內遷往新城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再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對新城區流動人口流向中心城區的意愿有較為顯著的影響。與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專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專。與假設不同的是,來京時間越長,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弱,來京時間每增加一個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區的可能性減小0.4%。相反,來新城時間越長,希望流向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強,但是不強烈,來新城時間每增加一個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0.1%。對于控制變量,年齡、性別、戶口性質對因變量的影響性質同假設一致。年齡越大,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意愿越弱,年齡每增加一歲,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區的可能性降低了0.09%;與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20.8%;與農業戶口相比,非農業戶口人們更希望遷往北京市中心城區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第7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職業流動;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婦女
中圖分類號:F2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7-0123-02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職業對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國際勞工組織在2001年就業論壇上通過的《全球就業協議》明確提出:“工作是人們生活的核心。不僅是因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還是人們融入社會、實現自我以及為后代帶來希望的手段。” [1]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各地域差距比較大的國家,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婦女的職業流動與其他群體相比是否會存在差異呢?如果存在差異,我們又將如何改進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婦女的職業流動呢?這是筆者力圖去探究的主要問題。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和資料來源
(一)本研究的主要概念
1.職業流動。所謂職業流動,就是指尋找和變換工作的過程 [2] 。職業流動分為代內流動和代際流動,筆者將代內流動操作化為是否流動和流動次數兩個變量。對于代際流動,主要研究代際流動方向,筆者將代際流動方向分為兩種:向上流動和未向上流動。陸學藝認為,中國存在十種職業類型: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 [3]。前面的職業類型比后面的職業類型的社會經濟地位高,在代際流動方向中,筆者以父親職業為基準,如果個人目前的職業類型排在其父親的職業類型的前面,就認為是向上流動,否則就是未向上流動。
2.民族。趙利生認為,“民族是在變動著的社會體系中,以文化區分的,具有自我認同的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群體。”[4]中國有56個民族,根據研究的需要,在本研究中筆者將民族分為漢族和少數民族兩種類別。
3.區域。根據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的差異,中國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運用的是廣西的抽樣調查資料。廣西屬于西部地區,同時又是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人口總數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排名第一,廣西的少數民族人口有1 839萬,占全區人口總數的38%,因此比較具有代表性。資料來源于李文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廣西不同民族職業流動與就業培訓政策的比較研究》的數據庫 [5] 。數據庫的樣本容量為1 155份。其中少數民族婦女樣本278份,占樣本總量的24.1%,其他樣本877份,占樣本總量的75.9%。
二、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婦女職業流動狀況的實證分析
(一)職業是否流動
筆者對少數民族婦女樣本和其他樣本的職業是否流動分布情況進行描述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職業是否流動情況分布表 (人 %)
從表1的統計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少數民族婦女樣本有職業流動經歷的比例為60.1%,其他樣本為52.8%,少數民族婦女樣本有職業流動經歷的比例比其他樣本稍微高一點。能否說明少數民族婦女的職業流動比例比其他群體高呢?我們必須對其進行統計推論檢驗,由于群體類別和職業是否流動都屬于定類變量,因此,我們采用的是列聯表檢驗,統計檢驗結果顯示:其系數λ值為0.062,顯著性水平值Sig為0.038,小于0.05,表明職業是否流動與群體類別有關,也就是說少數民族婦女有職業流動經歷的比例要高于其他群體。
(二)職業流動強度
職業流動頻率統計的是勞動者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流動的平均次數,它反映了勞動者職業流動的強度。通過統計,樣本的職業流動強度情況(見表2):
表2 樣本的職業流動強度情況分布表(人 次)
從表2可以發現,總樣本的平均職業流動頻率為1.5次,少數民族婦女樣本的平均職業流動頻率為1.56次,其他樣本的平均職業流動頻率為1.48次,少數民族婦女樣本的平均職業流動頻率高于其他樣本。我們能否得出這個結論,少數民族婦女的平均職業流動頻率高于其他群體,這必須進行統計推論檢驗。由于群體類別屬于定類變量,職業流動次數屬于定距變量,我們對其進行方差分析,其F值為0.300,顯著性水平值Sig為0.584,大于0.05,因此,職業流動次數與群體類別無關,從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少數民族婦女和其他群體的職業流動強度不存在差異。
(三)職業流動方向
職業流動方向,筆者將其分為向上流動和未向上流動兩種。這主要是針對發生過職業流動的樣本,通過描述統計,樣本的職業流動方向分布狀況(見表3):
表3樣本的職業流動方向分布表 (人 %)
從表3可以看出,少數民族婦女樣本向上流動的比例為43.7%,其他樣本為50.8%,總樣本為48.9%,少數民族婦女樣本在職業流動中向上流動的比例低于其他樣本。對此,我們對其進行統計推論,由于群體類別和職業流動方向都屬于定類變量,因此,我們采用的是列聯表檢驗,統計檢驗結果顯示:其系數λ值為0.062,顯著性水平值Sig為0.140,大于0.05,表明職業流動方向與群體類別無關,少數民族婦女和其他群體在職業流動方向上不存在差異。
(四)職業流動原因
筆者把職業流動的原因歸納為三類,第一類為個人原因,比如:提高收入水平、獲得升遷機會、專業對口、實現自身價值、改善工作環境、個人興趣等;第二類為家庭原因,包括解決兩地分居問題、結婚生子、照顧家人、輔導孩子等;第三類為社會原因,比如:組織安排調動、原單位倒閉、下崗等。通過統計分析及其檢驗發現,關于職業流動的社會原因方面,少數民族婦女和其他群體之間不存在差異。但關于職業流動的個人原因和家庭原因方面,少數民族婦女和其他群體之間存在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其他群體比少數民族婦女更加重視提高收入水平。少數民族婦女樣本中把提高個人收入水平作為職業流動的主要原因的比例為36.0%,而其他樣本的比例為52.1%。通過列聯表檢驗發現:其系數λ值為0.146,顯著性水平值Sig為0.012,小于0.05,表明是否把提高收入水平作為職業流動的主要原因與群體類別相關,其他群體在職業流動時與少數民族婦女相比更加注重提高收入水平。二是其他群體比少數民族婦女更加重視實現自己的價值。少數民族婦女樣本中把實現自己的價值作為職業流動的主要原因的比例為24.7%,而其他樣本的比例為36.7%。通過列聯表檢驗顯示:其系數λ值為0.115,顯著性水平值Sig為0.046,小于0.05,表明是否把實現自己的價值作為職業流動的主要原因與群體類別相關,其他群體在職業流動時與少數民族婦女相比更加注重實現自己的價值。三是少數民族婦女和其他群體相比更加重視家人團聚。少數民族婦女樣本中把為了家人團聚作為職業流動的主要原因的比例為27.0%,而其他樣本的比例為15.8%。通過列聯表檢驗顯示:其系數λ值為0.128,顯著性水平值Sig為0.036,小于0.05,表明是否把為了家人團聚作為職業流動的主要原因與群體類別相關,少數民族婦女在職業流動時與其他群體相比更加注重家人團聚。
三、結論及對策
從上面的實證分析我們發現:少數民族婦女與其他群體相比在職業是否流動以及職業流動原因方面還存在差異,這給少數民族婦女的社會經濟地位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少數民族婦女的職業不夠穩定,職業收入比較低(統計結果顯示:少數民族婦女樣本的收入是其他樣本的61.8%,統計檢驗結果表明少數民族婦女和其他群體的職業收入存在差異),職業發展的前景不夠理想。而要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要綜合政府、社會、企業和個人等多方面的力量。首先,要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政策方面對少數民族婦女的職業流動方面給予關照與傾斜,提高他們的職業技能。在教育方面給予少數民族婦女更多的關注,少數民族婦女的教育水平與其他群體相比還存在較大的差距(統計分析與檢驗結果表明少數民族婦女的教育水平比其他群體低),我們要集合政府、社會和企業各方力量,為少數民族婦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乃至整個人力資本的提升創造有利的條件。其次,社會和企業要形成關注少數民族婦女職業流動的良好氛圍,在職業進入、職業待遇和職業流動方面給予少數民族婦女一定的傾斜政策。最后,少數民族婦女要提高自身的職業技能,轉變職業觀念,自覺主動地投身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錘煉自己,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逐漸消除少數民族婦女在職業流動方面的不利因素,在各地區、各民族和各性別之間創建和諧的就業和勞動關系,同時也為中國和諧民族關系的發展作出貢獻。
感謝李文華教授允許我使用他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廣西不同民族職業流動與就業培訓政策的比較研究》(批準號:04XSH003)的數據庫。
參考文獻:
[1]張小建,等.當代中國就業與勞動關系[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8:1-2.
[2]王春光.中國職業流動中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研究[J].中國人口科學,2003,(2).
第8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人口流動;城市發展;GIS;灰色關聯分析
一、引言
人口流動和大規模勞動力轉移是我國城鎮化的主體力量,人口再分布格局將直接影響各地城鎮化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后勁。經濟增長的初期,由于科學技術的制約,經濟的增長多取決于原始資源,如土地、資本、當地的勞動力以及區位等因素的影響,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傳統因素對經濟的影響作用開始減弱,而流動人口因素作為最活躍的經濟發展影響因素逐漸被人們所重視。
早在1954年,劉易斯就提出了“兩部門學說”,指的是工業部門與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差異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工業部門,并且這種的人口流動對兩者都有益。此外,1967年,戴爾?喬根森(D.W.Jogenson)的《過剩農業勞動力和兩重經濟發展》中指出農業發展出現剩余使得剩余人口向工業部門流動,促進工業的發展。兩者都是指出人口的流動對于城市工業的積極影響。這樣說明人口流動與城市發展有著正相關關系。
國內研究中,大多觀點是人口流動對經濟的增長和城市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原新、萬能(2007)指出人口流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未來,城市的發展必然要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相關問題,屆時,城市發展對流動人口的依賴程度會越來越高。紀韶、朱志勝(2014)認為人口的流動可以明顯的改善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和城市群內部的人口分布。段平忠(2008)指出人口的流動對我國地區經濟的收斂效應的影響很大,同時人口的流動對于地區的經濟增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這種促進作用是逐漸遞減的。杜小敏,陳建寶(2010)在研究中指出人口流動對我國經濟來說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在此基礎上,于瀟等(2013)進一步指出人口遷入與人口的凈遷入地的經濟發展有著最為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孫峰華等(2006)則是提出遷出人口的收入回流對地區資本積累和經濟建設的推動作用。王德(2003)和袁曉玲(2009)都認為人口流動能夠縮小地區的經濟差距,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段平忠(2011)經過一個動態的收斂框架下分析得出:越發達地區受人口流動的影響越小,越落后的地區,則其影響越大。這也說明,對于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江西來說,人口流動對其影響不可忽視。
二、江西省人口流擁奶氐
江西人口流動的特點是總體上流動人口規模加大。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江西省戶籍外出人口為368.03萬人,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江西省的戶籍外出人口增加到了578.74萬人,十年的平均增長速度為4.63%。流動方向上是農村流向城市。2000年,在所有流動人口中,農業人口占到了89.44%,到2010年,比重為86.69%。雖然略有下降,但還是占到了絕大部分,農業人口在人口流動中的主導地位沒有改變。類型上,流動熱口多為勞動人口。江西流動人口中,15歲到60歲的在90%以上,具體如表1。
在區域分布上則是有著明顯的差異性。2000年人口流出量較大的城市上饒和贛州的流出人口分別是828997人和991226人,最少的是新余,人數為670142人;就人口流入而言,最大的是省會城市南昌,人數為822589人,是新余流入人口的7.1倍。2010年,人口流出最大的城市仍是贛州,人數是人口流出最小城市鷹潭的9.7倍;人口流入方面,流入量最大的城市南昌的流入人口是鷹潭的10.8倍。
三、實證分析
第9篇:人口流動的原因范文
【關鍵詞】神農架林區;人口遷移;經濟發展;生態保護
1 神農架林區人口遷移流動特點分析
1.1 流動人口來源地
從神農架林區流動人口來源地來看,來自重慶、河南省的流動人口所占比重排在前二位,分別為44.70%、16.52%。由于神農架林區西與重慶市巫山縣毗鄰,其河南省的位置也相近,對于流動人口來說有一定的便利條件。從圖中也可以明顯看出,來自重慶市和河南省的流動人口數量明顯多于其他省份。寧夏、天津流向神農架林區的人口相對較少,所占比重都為0.09%。除此之外,遼寧省、吉林省等地區的流動人口也相對較少,所占比重均為0.18%。從遷移距離方面來看,這些省份相較遠,且大多數屬于北方地區,生活習慣等均與神農架林區有較大差距,遷移相對較少,這也符合遷移流動的一般規律。
1.2 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
從神農架林區省內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來看,具有初中學歷的流動人口所占比重最大,超過三分之一,達到40.27%,具有小學學歷的流動人口所占比重超過五分之一,達到22.47%,而具有高中歷的流動人口所占比重為19.54%,排在第三。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流動人口所占比重最低,僅為0.08%,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比重還不到五分之一。從性別來看,具有高中以下學歷的流動人口中,男性人口少于女性人口,而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學歷的流動人口中,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多出8.8%,即神農架林區流動人口中男性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于女性人口。
省際流動方面,同省內流動一樣,具有初中學歷的流動人口所占比重較大,達到48.54%,具有小學學歷的比重將近三分之一,達到31.35%,而具有高中學歷的流動人口所占比重為11.14%,位居第三。相比于省內,省際流動人口中沒有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流動人口,具有大專級以上學歷的流動人口比重僅為7.08%,明顯低于省內流動人口所占比重。
1.3 流動原因
從神農架林區流動人口流動原因來看,省內流動中,務工經商所占比重較大,為35.16%,工作調動和婚姻嫁娶的比重分別為22.10%和11.07%,排在第二、第三位。寄掛戶口的流動人口所占比重最小,僅為0.56%。
同省內流動情況有所不同,省際流動人口中,因為務工經商而流動所占比重最大,超過50%,婚姻嫁娶和隨遷家屬的比重排在第二、三位,分別為16.08%和9.63%。寄掛戶口所占比重最小,還不到1%。
2 人口遷移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效應分析
2.1正面效應
2.1.1流動人口有利于資本積累,為林區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無論是省內人口遷入還是省際人口遷入,流動人口對神農架林區經濟增長的貢獻都是巨大的。據最小二乘估計法得到的結果可知,神農架林區各鄉鎮的流動人口數量與當地經濟發展存在高度的正相關。作為流入人口大鎮的松柏鎮,其財政收入遠遠高于流入人口數量較少的九湖鄉,前者的財政收入約為后者的9.3倍。據對神農架林區計生委統計資料的研究分析發現,從神農架林區整個視角來看,雖然林區人口的遷入量不及遷出量,但流入人口的數量近三年來(2011~2013)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對林區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據神農架林區旅游委員會的經營情況快報:2010年林區旅游經濟總收入為75020.7萬元,同比增長36.37%。2011年旅游經濟總收入同比增長47.21%,基本保持著穩定增長趨勢。此外,流動人口不僅僅是人口本身的流動,同時也帶動了資本的流動,使資本向某一地區集中,形成資本集聚,促進林區經濟發展。
2.1.2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
根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從神農架林區流動人口流動原因來看,無論是省內流動人口還是省際流動人口,因為務工經商而流動所占比重都是最大的。流動人口在作為第二產業中主角的同時,由于自身的生理需求以及對生活服務設施、公共基礎設施的需求迫切地需要得到滿足,進而在很大程度上帶動了林區第三產業的發展。據神農架林區2010~2011年國民公報,2010年,全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23043萬元,按可比價計算增長速度為12.2%。其中:第一產業實現增加值14000萬元,同比增長4.8%;第二產業實現增加值48814萬元,同比增長7.9%,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60229萬元,同比增長17.0%。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的141∶40.8:45.1調整為11.4∶39.7∶48.9,到2011年調整為10.2∶41.4∶48.4。由此可見,第一產業的發展逐漸向第二產業讓步,第二產業繼續擴張,第三產業的增長趨勢逐漸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