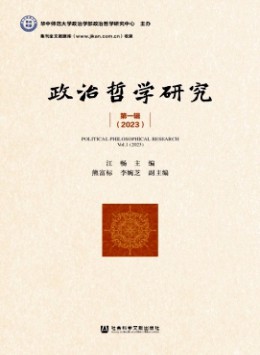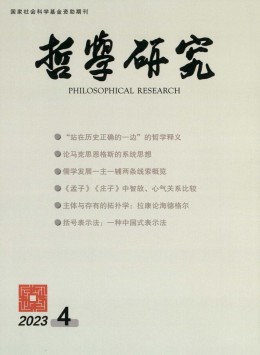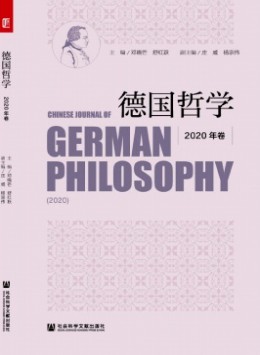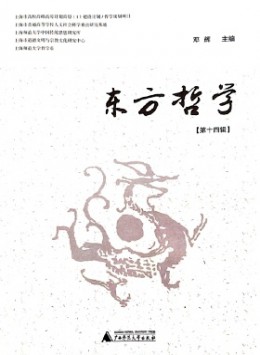哲學的基本范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哲學的基本范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一、中西哲學在內容上的相似性比照
在(〈中國哲學史》中,馮友蘭并沒給哲學一個明確的定義。他認為,欲知哲學為何物,只須指出其內容即可。哲學包括宇宙論、認識論、人生論,這是當時人們的共識。問題在于,馮先生對哲學三部分內容之間的關系的理解解并沒能有助于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解決。馮先生認為哲學的三部分內容是密切相關的。“宇宙論與人生論,相即不離,有密切之關系。一哲學之人生論,皆根據于其宇宙論。……哲學家中有以知識論證成其宇宙論者;有因研究人是什么而連帶及知識問題者。哲學中各部分皆互有關系也但問題是,宇宙論、認識論、人生論的統一,既可理解為一系哲學中三者的統一,也可理解為某位哲學家的哲學中三者的統一。馮友蘭似乎傾向于后一種理解,而在中國思想家普遍強于人生論,而弱于宇宙論和知識論的情況下,這種理解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理論上的困難。因為按照后一種統一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傳統學術,先秦思想家乃至大部分中國思想家的思想能否被列入中國哲學史就成了問題。馮友蘭自己也未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在〈〈中國哲學史》中說:吾人觀上述哲學之內容,可見西洋所謂哲學,與中國晉人所謂玄學,宋明人所謂道學,及清人所謂義理之學,其所研究之對象,頗可約略相當這段引文中并未提及諸子之學,如果馮友蘭要把諸子之學列入中國哲學史,就必須對他所理解的宇宙論、認識論、人生論相統一這一標準進行轉換。因為,“中國哲學的創始者孔子,及繼起者墨子,都是談論人生問題,而未嘗成立宇宙論系統。馮友蘭是如何進行這種轉換的呢?他在〈中國哲學史》的緒論中說:“由上述宇宙論與人生論之關系,亦可見一哲學家之思想皆為整個的。凡真正哲學系統,皆如枝葉扶疏之樹,其中各部,皆首尾貫徹,打成一片。(w這里,衡量一個思想家的思想是否為哲學思想的標準由宇宙論、認識論、人生論的統一,變成了“首尾一貫,打成一片”,也就是說,由一個內容上的標準變成了一個半形式上的標準。進行了這樣一層轉折之后,諸子之學進入中國哲學史才名正言順。例如,馮友蘭把孔子列入中國哲學史的理由是孔子以前,尚無有私人著述之事……哲學為哲學家之有系統的思想,須于私人著述中表現之……就其門人所記錄者觀之,孔子實有有系統的思想。由斯而言,貝lj在中國哲學史中,孔子實占開山之地位。從馮友蘭的這段話看來,他判定一種思想是否是哲學思想的標準變成了思想的系統性,但系統性更多的是一個形式標準,它只是哲學之為哲學的一個必要條件,我們并不能僅據此條件就說一個人的思想是哲學思想。這里,馮友蘭忽略了他所謂的系統性思想的初始意義是宇宙論、人生論、認識論的統一,從而模糊了這一標準的內涵。
張岱年也承認哲學包括宇宙論、認識論和人生論三個部分,但和馮友蘭不同的是,他認為每個哲學家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地研究所有問題。宇宙論的研究或人生論的研究或認識論的研究,都可以是哲學研究。“哲學之研究,實以探索最根本的問題為能事。不論何派哲學家,其主要工作,或在研究宇宙之根本原理(或世界事物之源流)或在探討人類生活之根本準則(或改造社會的道路)或在考察人類認識之根本規律(或科學知識之基礎)總而言之,凡關于自然世界、人類生活或人類認識之根本問題之研究,統謂之哲學。哲學家可以建立系統的哲學,“然哲學家之工作亦不必專以建立系統為務。有時專門問題之探索,個別概念范疇之剖析,較之建立一個一偏而空洞的系統更為重要。哲學家之工作,與其說是建立系統,不如說是探索問題,發闡原則,即僅就一部分根本問題而充分研究之。按照張岱年的這種觀點,先秦的諸子之學、魏晉的玄學、宋明清的道學或義理之學,都可順理成章地稱之為哲學。
張岱年雖認為每個哲學家不必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論、認識論、方法論,但他并不否認三者的統一。只是他所理解的統一不是某位哲學家那里三者的統一,而是一系哲學中三者的統一,這一點對解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也至關重要。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依賴兩方面的前提:一方面要確認一些中國學者的工作是哲學工作,另一方面要肯定中國傳統思想中有哲學。張岱年在確認了前者之后,著眼點放在了后者上。也就是說,他關注的是整個中國思想。馮友蘭認為中國哲學史研究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找出哲學家思想的形式系統,而張岱年則致力于找出整個中國哲學的形式系統,這從〈中國哲學大綱》的寫作體例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的學者可能沒有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論、認識論、人生論,但只要中國哲學在整體上具有這些方面的研究,那么從內容上講,就可以說中國有哲學。從整體上反思中國思想,是近代文化界的一個主題,張岱年的貢獻在于他梳理了整個中國哲學的形式系統。在這36個系統中,他分別敘述了中國哲學的三個部分(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的內容,具體地考察了各個部分的概念、命題的淵源流變,從而更加突出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在內容上的共性,進而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增添了證據。
二、中西哲學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比照
馮友蘭先生為解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把內容標準轉化為某種意義上的形式標準,但即使把衡量的標準形式化,也還不能完全解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因為在形式上,中西哲學也表現出很大的差異。照馮友蘭看來,中國哲學既無形式上的條理系統也不長于論證。前一個缺陷可以用中國哲學有實質上的系統來補救,但中國哲學弱于論證的缺點則不能不認真對待。馮友蘭非常強調論證之于哲學的重要性,認為若無論證,普通人的見解和哲學家的見解就無以區別,而中國哲學恰恰是在論證說明方面較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遜色。既然論證對哲學之為哲學至關重要,那么中國哲學疏于論證的缺點就絕不是無足輕重的,它實際上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戰。
馮友蘭對論證的強調是和對邏輯的強調分不開的。他認為哲學是說出一番道理來的道理。金岳霖認為,所謂“說出一個道理來”,就是以論理(即邏輯)的方式組織對于各問題的答案。強調邏輯是清華學派哲學家的一大特色,但邏輯并不止于論證。就形式邏輯的內容來看,它除了研究推理論證,還研究范疇和命題。張岱年和馮友蘭、金岳霖不同的是,他沒有把論證作為哲學在形式上的唯一標志,而是突出了哲學系統由哲學范疇和哲學命題所形成的形式上的特征,并進而從這些形式特征上考察了中西哲學的相似性。
首先,張岱年從“哲學是范疇之學”出發來肯定中國哲學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他認為哲學家研究的主要是范疇,哲學系統也就是范疇系統。哲學系統為何首先是范疇系統呢?這和張岱年對哲學的理解有關。張岱年認為哲學是探索最根本問題的學問,“哲學為根本問題之學,亦即事物基本類型之學,研究世界事物中之基本區別及其統一關系。哲學研究對象的上述特點,決定了哲學在形式上必然是范疇之學,“自古及今,哲學家之主要工作,或在創立概念范疇,或在詮釋概念范疇,或在厘清概念范疇,或提出若干重要概念范疇而特別表彰之,或統綜一切概念范疇而厘定其相互關系。另外,哲學系統都是理論系統,而理論系統都必以一個范疇或一組范疇為其最基本的范疇。哲學系統區別于其他理論系統的地方,即在于其所設定的基本范疇不同。
如果把哲學看成范疇之學,那么中國哲學的存在在形式上是沒有問題的。中國哲學也許缺少形式上的論證或條理系統,但就研究基本范疇這一點來說,中國傳統的諸子之學、義理之學等對性與天道、心物及理氣等范疇的研究都可以說是哲學研究。而且在這些研究中也不乏范疇系統,《中國哲學大綱》所展示的,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哲學的范疇系統。
其次,張岱年從哲學命題的特征上來論證中國哲學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前提之一其實是哲學的合法性,而哲學的合法性在近代卻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命題意義理論的沖擊。馮友蘭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理論的擠壓下,提出了一種特殊的命題一形上學命題。“形上學命題”是說到事實的,但只是形式地說。它不肯定也不證明“有某種事物存在”,而只是對于已存在的事實,作形式的解釋,所以雖然其說到事實,但也還是分析命題。馮友蘭所說的這種形上學命題,不能說中國傳統思想中沒有,但如果以有沒有這種命題去衡量中國傳統思想,恐怕能列入中國哲學史的思想家就寥寥無幾了,也就是說,馮友蘭所提出的形上學命題,雖不失為一種抵御邏輯實證主義對形上學攻擊的方法,但同時也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構成了威脅。
面對邏輯實證主義對形上學的攻擊,張岱年體現了和馮友蘭不同的思路。他根本不承認邏輯實證主義的命題意義標準,而是另起爐灶,提出了自己的命題意義理論。張岱年認為,哲學中有各種命題,“而為特色的哲學命題者,有三:一、統賅經驗事實命題,二、名言命題,三、基本價值準衡命題。統賅命題是關于宇宙之全部事實、或大部事實之命題,名言命題是關于符號或命題之命題,價值命題是關于理想或事實與理想之關系之命題。三種命題的意義(意謂)標準是不同的。統賅命題是事實命題,事實命題的意謂準衡為可驗,或在經驗上有征;名言命題之意謂準衡為可辨或可解;價值命題之意謂標準為可實踐或有實踐之可能。按照邏輯實證主義的標準,統賅命題和價值命題因無法驗證,所以是沒有意義的。而張岱年則認為,統賅命題是一種泛經驗命題,泛經驗命題雖非特殊經驗所能證成或否證,然而卻能為大部分經驗所證成或否證,并不是無意義的。至于價值命題,雖不能證實,卻可以實行,所以也不是無意義的。
張岱年對哲學命題的論列和對命題意義的厘定對解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張岱年的命題意義理論維護了哲學的合法性,進而也維護了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按照新實證論者的理解解哲學處理的是無意義的命題,根本就無存在之必要。而按照實用主義的標準,哲學是無用之學,也無存在的必要。哲學尚不能存在,遑論中國哲學?所以維護哲學的合法性也就是維護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前提。按照張岱年的命題意義理論,實用主義的錯誤在于把“有用”這個名言命題的意義標準引用到事實命題上,而新實證論的錯誤在于認為一切泛經驗命題及價值命題都無意義。其次,張岱年的命題意義理論為中國哲學在內容上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論支持。眾所周知,中國哲學三分之二的內容是人生論,人生論主要關乎實踐和價值領域。如果把哲學命題認定為馮友蘭所謂的形而上學命題,就很難說中國有哲學。所以要肯定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必須在意義理論上脫離邏輯實證主義的窠臼,為中國哲學中眾多的統賅命題和價值命題尋求意義支撐。
三、中西哲學在方法上的相似性比照
哲學的方法問題,對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也至關重要。如果哲學有其特有的方法,而在中國哲學中我們卻找不到這些方法,那么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就必將受到質疑。從方法上考察中西哲學,我們會發現二者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國哲學中沒有充分發展的歸納法和演繹法。其次,中國哲學比較強調體驗和踐履。最后,中國哲學較多關注了“為學之方’。面對中西哲學在方法上的諸多差異,如何溝通中西哲學,論證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就成了擺在哲學家們面前的重要問題。
在中國近代哲學史上,從開始,方法就受到特別的重視。認為哲學的核心就是方法。但和早期的馮友蘭對哲學方法和科學方法都沒加區別。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上卷中說,“科學方法,即是哲學方法,與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亦僅有程度上的差異,無種類上的差異。既然科學方法就是哲學方法,那么關鍵就是指出科學方法是什么,然后考察一下在中國哲學中有沒有這種方法。在那里,科學方法更多的是指歸納法,而馮友蘭早期強調的則主要是演繹邏輯的方法。但眾所周知,中國傳統學術中,既沒有充分發展的演繹法,也沒有充分發展的歸納法,這樣一來,中國哲學存在的合法性在方法上就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張岱年并不否認演繹法和歸納法的重要性,不過他認為這些都不是最適合哲學的方法,最適合哲學的方法是辯證法。“辯證法乃是考察事物之全貌以發現事物之變化規律之方法,亦即,考察一歷程之諸要素與其一切相互關系,以及其對于歷程以外之其他要素之一切關系,而尋求歷程之內在的變化根源,厘定歷程之發展規律,以達到對于歷程所含之諸現象之全面的理解。辯證法之所以是最適合哲學的方法,首先是由哲學的研究對象決定的,哲學研究的是宇宙大化的歷程及社會發展的歷程,這些都不是重復屢現的,因而演繹法和歸納法難以奏效。只有包含演繹和歸納而又高于演繹和歸納的辯證法才能勝任這一任務。其次,辯證法之所以是最適合哲學的方法,乃是因為哲學上許多問題的產生,源于各家的各執己見、蔽于一曲而不能會通。哲學要達到會通的認識,必須能夠解蔽,而最精的解蔽之術是辯證法。“辯證法以對立統一為基本準則,對于一切兩相對立者,概不忽略其一方,而各予以適宜之位置。凡有所見,必勘察其對立見解,凡有所斷,必考量其適用之限度,如此固能免于以偏該全、以畸為奇。
以辯證法為哲學的方法,可以解除中國哲學合法性在方法問題上遇到的困境。因為在中國傳統學術中,辯證法的發展是比較充分的,其運用也是比較自覺的。若以辯證法為哲學的根本方法,中國哲學就沒有無方法之虞。在這個問題上,張岱年的貢獻是不僅指出了辯證法是最適合哲學的方法,而且論證了中國傳統學術中這種方法的存在。他認為,辯證法的聯系和變化的觀點以及對事物運動變化規律的概括,可以用中國哲學中的兩個范疇一“反復’和“兩一”來涵蓋。“反復”、“兩一”是中國傳統思想中固有的觀念,老子早就提出、闡發過‘反復”的原則。而“兩一”的思想在張載的思想中已發展得非常成熟。中國哲學中的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
在方法問題上,中國哲學的另一問題是體驗、踐履及‘為學之方”的定位問題。張岱年的貢獻是把這些都納入到哲學方法論的框架之內,從而在方法論層面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張岱年認為,“哲學方法,就其為思維方法而言,實與科學方法并無根本不同。然而科學之范圍與哲學不盡相同,哲學所注意之方面,與科學不同,故哲學專門方法與科學專門方法,有其相對的不同。也認為,哲學于運用邏輯之際,有三種特殊的方法:一為體驗,二為解析,三為會通。其中體驗是哲學的首要的方法。“茲所謂體驗,謂以身驗之,或驗之于身。體即身體,驗即查驗。就身體之所經歷而慮察之,謂之體驗。就身體之所經歷而考察之,即就身體實際活動以考察之。
張岱年所謂的體驗即生活實踐,他認為,理論與實踐之一致或知行之一致是辯證法的一個根本要求,是從辯證法的基本原則引申出來的方法準則。它強調凡知識或理論須與行為和實踐相合,立說應以生活實踐為根據,并通過行動和實驗加以甄別。張岱年認為實踐的引入,使新唯物論在方法論上超越了新實在論。新實在論的邏輯分析以經驗自限,故既不能走出懷疑,也不能協符于生活。而辯證法強調實踐,故能不妄有所信,而又合于生活。
把實踐納入到哲學方法論的框架中對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解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哲學的特點之一就是強調踐履,強調知行合一,這和近代西方哲學是一個很大的不同。金岳霖在《中國哲學》一文中說,中國哲學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式人物,他的哲學要求他身體力行,他本人是實行他哲學的工具。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引用了金岳霖的這段話,并且認為,這是由中國哲學的特點造成的。“由于哲學的主題是內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學不但是要獲得這種知識,而且是要養成這種人格。哲學不但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體驗它。在馮和金那里,強調體驗或踐履是中國哲學的特色(西方近代再也沒有蘇格拉底式的人物了)是中西哲學無法溝通的相異點,而張岱年則不如此認為,他把體驗這一概念從中國傳統哲學中剝離出來,結合新唯物論的實踐觀,把它納入到哲學方法論的框架內,從而進一步從方法上論證了中國哲學的合法性。
第2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認知科學;語義;語法
現代語言學的研究表明,認知與語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語言的認知研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卻是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的,80年代中期以后其研究范圍擴展到了語言學中的許多領域,包括句法學、語義學、音系學、篇章分析等。1989年在德國召開的第一次國際認知語言學會議以及l990年創刊的《認知語言學》雜志,標志著認知語言學的學科地位得以確立。此后,認知語言學的發展非常迅猛,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認知的角度來研究語言。
一、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觀點
(一)認知語言學是認知科學發展的產物
認知語言學是認知科學的一部分,而認知科學是一門綜合科學,由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哲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學科組成的交叉學科,從多角度來探索思維的奧秘。人類思維的結晶是語言,語言是人類表達觀念和思想的方式之一,是認知系統的一部分,是人類體驗、文化、社會、風俗、環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認知語言學一方面運用認知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語言現象,另一方面又通過語言現象來揭示人的認知能力,把語言認知作為人的整體認知過程的一部分來把握。
(二)認知語言學研究中的范疇理論
“范疇化”(categorization)可以說是人類最重要最基本的一種認知活動,是指人類在演化的過程中對外界事物進行分類或歸類,使無序的世界變成有序的、分等級的范疇體系。這個過程(即范疇化的過程)就是認知,或者說是認知的第一個環節。范疇化使人類從千差萬別萬事萬物中看到相似性,并據此將可分辨差異的事物處理為相同的類別,從而形成概念。在此基礎上人類才能完成更復雜的認知活動,包括判斷和推理。認知的發生和發展是一個形成概念和范疇的過程,它是一種以主客互動為出發點對外界事物進行類屬劃分的心智過程[1]。正如Lakoff所言:“沒有范疇化的能力,我們根本不可能在外界或社會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發揮作用。”[2]
范疇化的現象很早便引起哲學家的注意,亞里士多德在《范疇篇》中系統論述了自己對范疇的觀點,經典范疇觀便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20世紀60年代以來,心理學和人類學研究對傳統的經典范疇觀提出了大量的反證。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提出了“家族相似”[3]的概念。維氏認為, 無法用一種共同的屬性來描述一個范疇中的全體成員,只是在成員與成員之間存在部分的相似性,并以這種相似性的交織聯結成范疇的整體;范疇的邊界是模糊的、開放的;范疇內的各個成員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維氏的“家族相似說”否認范疇的各個成員之間存在任何共同的本質, 向經典范疇觀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20世紀70年代起,“家族相似說”被引入語義范疇研究。觸發了哲學界、心理學界、語言學界對范疇化問題的重新審核。語言學家Labov和Rosch先后發表了他們對自然范疇的試驗研究結果,把具有“家族相似”的這些自然范疇稱為“原型范疇”[4-6]。一事物是否屬于該范疇, 不是看它是否具備該范疇成員所有的共同特性, 而是看它與其原型之間是否具有足夠的“家族相似性”。范疇化研究的巨大發展成為認知語言學得以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三)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
Lakoff和Johnson按照哲學的承諾和信念把認知科學劃分為兩大派: 第一代認知科學和第二代認知科學。第一代認知科學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客觀主義的認知觀代表了第一代認知科學的基本觀點,可概括為“所有的理性思維牽涉抽象符號的操作,這些符號只有通過與外界事物的規約才能獲得意義”[7]。思維僅是對抽象符號的機械運作,不受人體感知系統和運動系統的制約。人類的心智就是自然的一面鏡子,是外部世界的內部表征, 對自然作出客觀的、鏡像的反映。喬姆斯基的生成語言學是第一代認知科學在語言學領域的典型理論形態。
第二代認知科學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 信奉的是所謂非客觀主義的哲學,以體驗哲學為基礎。第二代認知科學堅決反對第一代認知科學的基本觀點,認為客觀主義認知觀忽視了人類認知最重要的一個特征,即人的生理基礎在形成概念和語言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體驗主義認知觀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8-9]:思維是不能脫離形體的。概念、范疇、心智來自身體經驗,那些不是來源于經驗的概念是運用隱喻、轉喻和心理意象的結果。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觀點與第二代認知科學一致。認知語言學家認為,語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認知能力的一部分,其描寫必須參照認知過程。語法、句法都不是獨立的,而是與語義、詞匯密不可分。語義不只是外部世界的客觀反映,還與人的主觀認識息息相關,是通過身體和想象力獲得的,而這種想象力也是不能脫離形體的,因為隱喻、轉喻和心理意象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這與客觀主義語義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體驗哲學是第一代認知科學與第二代認知科學的分水嶺, 兩者的劃分具有深遠意義, 能使我們更清楚地理解認知科學理論, 不至于將其間的不同流派混為一談。”[10]
二、認知語言學的主要流派
認知語言學不是一種單一的語言理論,而是代表一種研究范式,是多種認知語言理論的統稱,其特點是把人們的日常經驗看成是語言使用的基礎,著重闡釋語言和一般認知能力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些語言理論雖不相同,但對語言所持的基本假設都大同小異,都不同程度地認可上一節提到的基本觀點,只是在討論和關注的具體語言現象上有所差別。認知語言學主要理論方法有:Fillmore的框架語義學 (Frame Semantics),Langacker的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Lakoff等人的認知語義學(Cognitive Semantics)。
(一)框架語義學
框架語義學是認知語言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詞義及句法結構意義的一種方法。Fillmore指出:“框架語義學提供觀察詞語的一種特別方式,同時也努力描寫一種語言新詞的產生和已有詞語里新意義的增加,或將一段文章中各部分的意義組合到一起,從而形成整篇文章的意義所需要遵循的原則”[11]。在框架語義學中,詞義是用框架來描寫的,框架是一種概念系統或認知結構,要理解詞語的意義,就必須先具備概念結構即語義框架的知識。“一個“框架”作為在對語言意義的描寫中起作用的一個概念, 是跟一些激活性語境相一致的一個結構化的范疇系統”[11]。以Fillmore著名的“商業交易”框架為例。這一框架涉及的概念包括: 擁有、給予、交易、錢。這樣一個場景圖式中的元素包括:錢、商品、買方、賣方。其他元素還包括:價格、時間、找錢等。根據這些概念, 我們就可以對一系列詞語的意義、用法及語法結構進行對比描寫。例如,英語中的buy, sell, spend, cost, charge, price等等。如果我們把商業交易框架與其他框架進一步結合起來, 那么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描述和解釋像tip, bribe, fee, honorarium, taxes, tuition這樣的詞語。由此可見, 框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認知結構。語言框架為詞義的存在和使用提供了背景和動因。要理解詞義必須將其放置于人們的經驗與社會文化的習俗框架中,理解人們的經驗與社會習俗。
(二)認知語法
認知語法是Langacker的語言學理論及其研究方法,最初稱為“空間語法”(Space Grammar)。該理論為語法研究提供了一個迄今為止最全面詳盡的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和描述框架。認知語法對語法和語言意義的本質提出了新的理論[12]:
1.語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認知能力的一部分,因此語言不是一個自足的系統,對語言的描寫必須參照人的一般認知規律;
2.語法結構(或句法)并不構成一個自足的形式表征層次,它在本質上是象征性的,是語義結構的規約象征化(conventional symbolization);
3.句法不是語言的一個自足的組成部分, 句法(和詞法)在本質上和詞匯一樣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象征系統,句法分析不能脫離語義;
4.基本真值的形式邏輯用來描寫語義是不夠的,語義不僅僅是客觀的真值條件,還跟人的主觀認識密切相關。顯然,這些基本假設跟喬姆斯基生成語法的基本假設是針鋒相對的。
認知語法認為語言中只有三類單位:語音單位,語義單位,象征單位。語音單位和語義單位是構成象征單位的兩極,兩極之間的聯系是象征聯系。例如,英語單詞cat 作為一個象征單位就是[[CAT]/[cat]],其中大寫字母代表語義極,小寫字母代表語音極。象征單位是一種音義結合體,一定形式代表一定的意義,而且這種代表是約定俗成的。各種語法范疇和語法結構式都是象征單位,只有具體和抽象程度上的差別。語法研究不可能脫離語義。因此認知語法打破了詞匯和詞法、句法的界線,認為詞匯、詞法和句法構成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可借用象征關系對這一連續體作窮盡性描述。也就是說象征關系高度概括性使得認知語法能對語言不同層次作出統一性解釋。 (三)認知語義學
第3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一、亞里士多德的范疇論
(一)亞里士多德的范疇論的概述
“范疇”一詞來自古希臘語,由兩個詞復合而成:Kata+agora。該詞從構詞角度來看乃指“與集合或集會相對立”,那就意味著“分散”,“分解”,進一步引申,就是“劃分”,“分類”。在亞里士多德把這個詞引入哲學領域之前,它原本是一個法律術語。亞里士多德從法律中借用了這一術語, 第一次賦予了它以哲學意義,構造了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范疇表。而且,他還最先從詞語學p邏輯學p認識論和本體論等多方面對范疇進行了自覺的理論探討, 創立了系統的范疇理論。
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應該區分一個范疇的本質特性和它的偶然特征,前者是指使一個個體成為某范疇的一員的基本屬性,后者的存在與否則不能影響某實體是否為范疇的成員。以“人”為例,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這一范疇的本質特征是“兩足動物”,而其他諸如膚色p受教育程度等則屬于偶然特征。亞里士多德的范疇觀主要可以概括為:(1)范疇由一組充分必要條件決定;(2)范疇的所有特性均為二元的;(3)各范疇有自己界定清晰的邊界;(4)范疇的所有成員均地位平等。
(二)亞里士多德的范疇分類原則
亞里士多德在《范疇篇》構建起對事物(“是者”)本身進行分類的兩個原則:(1)表述主體;(2)在本體(即實體)中。然后根據這兩個原則將事物本身分為四類。
首先,我們來看兩個原則的含義。“表述主體”,在“B是A”這樣的判斷中,B是主詞,是主體,A是謂詞。是表述B的。以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來看,普遍的東西可以表述主體,個別的東西不能表述主體。這就是說,他以是否“表述主體”這一原則區分出普遍和個體。“在本體中”,“不在本體中”的東西就是本體自身。實際上,亞里士多德根據是否“在本體中”,即事物的獨立性,區分出本體和屬性。
這樣,我們再來看亞里士多德依據這兩條原則的肯否形式排列組合得到的四類事物。
表述主體,但不在本體中的事物,是普遍實體或第二實體,如“人”p“動物”等。在邏輯上表現為個別實體的屬p種,普遍實體表述個別實體,但不存在于個別實體之中,因為它自身也是實體。在本體中,但不表述主體的事物,是個別屬性或偶性,如“某個特殊的白色”。它們不能表述別的東西,因為它們只能做主體;它們可以存在于實體中,因為它們是屬性。表述主體,又在本體中的事物,是普遍屬性,如“知識”、“顏色”等。在邏輯上表現為個別屬性的種p屬。它們既能表述個別屬性,又存在于實體之中。不在本體,又不表述主體的事物,是個別實體或第一實體,如“個別的人”等。它們是永遠的主體,所以不表述其它東西,它們也是永遠的實體,所以不存在任何其它實體中。
(三)十大范疇的提出
從范疇分類原則可以得出,普遍屬性存在于普遍實體之中,個別屬性存在于個別實體之中;普遍屬性表述個別屬性,普遍實體表述個別實體。在這種關系中,普遍離不開個別,個別也離不開普遍。每一種個別總是隸屬于某種普遍的個別,沒有純粹的個別。由個別向普遍的上升不是一個無限的序列,而是一個有限的階梯。這個階梯的最底層乃是被學者稱為“零點實在”的個別實體和個別屬性。階梯的頂層就是最普遍的“是者”類型,即“范疇”,也就是邏輯上的“最大的種”或坐高的謂詞。亞里士多德把“是者”的階梯分為十種類型,即十大范疇。一種是由個別實體普遍實體……最普遍實體逐級而上的階梯,如由“蘇格拉底”“人”“動物”……“實體”;另外九種都是從個別屬性普遍屬性……最普遍儺災鴆繳仙的階梯。這九種屬性階梯分別是“數量”、“性質”、“關系”、“場所”、“時間”、“姿態”、“具有”、“活動”和“遭受”。這樣,十大范疇就提出來了。
二、認知語言學上的范疇等級結構
(一)認知語言學上的范疇論
20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在對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進行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在范疇化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原型”,從而建立了現代范疇理論-原理理論。我們也可以用四點來概括原型理論的范疇觀:1.原型理論不能通過一組充分必要條件來定義;2.特征是分等級的,原型范疇體現家族相似性結構;3.原型范疇體現成員隸屬度差異:4.有的原型模棱兩可,表明有的范疇邊界模糊。
(二)認知語言學上的范疇等級結構
在認知語言學上,把范疇分為三個等級,即為基本范疇p上位范疇和下屬范疇。認知科學發現,基本等級范疇是人類對事物進行區分最基本的心理等級,是認知的重要基點和參照點。在此層面上,人們的分類與客觀主義的自然分類最接近,人們處理自然的事物最有效p最成功。也就是在此層面上,人們區分事物最容易。
上位范疇是寄生于基本范疇之上的,因為它依賴基本范疇獲得完型和大部分屬性。上位范疇具有兩個功能:一是聚合功能,即集合下級范疇成員。構成范疇等級,二是突出所屬成員明顯的共有屬性。上位范疇依賴于基本等級范疇,所以成為寄生范疇。
下屬范疇是在基本范疇的基礎上的進一步切分,也是寄生范疇。只有當人們需要更加細致的區分時,才進行下屬范疇切分。下屬范疇語言也是晚于基本范疇詞語產生的。
三、亞里士多德的實體范疇觀與認知語言學上的范疇等級結構
我們在第一部分中,談到亞里士多德把“是者”的階梯分為十種類型,即十大范疇,其中一種是由個別實體普遍實體……最普遍實體逐級而上的階梯,如由“蘇格拉底”“人”“動物”……“實體”。
我們在第二部分中談到范疇等級結構,下屬范疇,突顯個別屬性,如獵狗p哈巴狗;基本范疇,多泛范疇屬性,如狗;上位范疇,起作概括屬性的作用,如犬科。這三等級范疇之間的關系是,上位范疇包括了基本范疇和下屬范疇,基本范疇包括了下屬范疇。它們之間的關系也可以用逐級而上的階梯來表示,如下屬范疇基本范疇上位范疇,具體的例子,如“獵狗p哈巴狗”“狗”“犬科”,如果對此例進行延伸一下,可以得到“獵狗p哈巴狗”“狗”“犬科”“動物”“物體”……“實體”。
通過比較發現,我們不難發現認知語言學上的三個的范疇等級結構之間的關系與亞里士多德的由個別實體普遍實體……最普遍實體逐級而上成階梯狀的實體范疇觀有極大的相似性。亞里士多德的范疇論是在2000多年前由他本人提出,而認知科學是最近才興起的一門學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認知語言學上的范疇等級結構師源自亞里士多德的實體范疇觀。
四、范疇理論對英語詞匯學習的影響
按照范疇理論,語言詞匯也可以分為三個范疇等級,即上位范疇詞匯p基本范疇詞匯和下屬范疇詞匯。其中上位范疇詞屬概括詞,沒有單一的完型,基本范疇詞由有單一的完型,而下屬范疇詞往往突顯事物的某一具體屬性,從而獲得更加具體的含義。在學習詞匯的過程中,要遵循學習規律,做到循序漸進,由簡單到復雜,由基本詞匯到上位范疇詞和下屬范疇詞,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將基本范疇詞匯作為學習的重點和首選,掌握基本范疇詞匯對詞匯學習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第4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摘要]馬克思的實踐觀,最是一種思維方式,是哲學的解釋原則和看待一切問題的思維邏輯。同時,馬克思的實踐觀點是對傳統主體概念的否定與解構,超越了傳統哲學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實現了主客同一。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的哲學革命的實質,以實踐這一本體的中介為基礎,超越了傳統唯物論與唯一心論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
一、實踐是一種思維方式
“實踐唯物論”、“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都是以實踐為核心范疇重新理解哲學的哲學理論,但在對實踐范疇的不同理解中卻蘊含著值得深入研究的學理上的區別。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為實踐,并以此為基礎來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學。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第一次提出了實踐的概念,實踐范疇的提出,標志著哲學天才世界觀的誕生。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公開以實踐作為“新唯物主義”的建構原則和全部哲學變革的出發點。他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納入到實踐的解釋框架中去理解,指出過去舊唯物主義的缺點在于:“對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義的缺點則是:“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_2J這段話充分表明了馬克思是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置于實踐這一全新的解釋原則之下,從實踐的觀點出發看待整個西方傳統哲學,去理解傳統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并且從這一角度闡明了自己的哲學與以往哲學的不同。
馬克思不僅從實踐觀點出發去看待整個哲學史,而且還進一步把所有的理論問題都歸結為實踐的問題。所以,馬克思認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J緊接著,馬克思又進一步指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_4J即便是觀念的東西,包括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也要從物質實踐來予以說明。這樣,實踐范疇便成為哲學的核心范疇,不僅社會物質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且社會精神生活在本質上也是實踐的,所以,馬克思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樣,實踐不僅成為馬克思理解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而且也成為馬克思理解所有哲學問題的思維方式。與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相比,實踐觀點作為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也就是哲學對待一切問題的思維邏輯。
從實踐的觀點出發去理解人的社會生活,并以人的實踐活動的觀點去批判“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這是“實踐唯物論”、“實踐本體論”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這三種解釋模式的共同之處,但是,“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所理解的實踐和所強調的實踐,是人的實踐活動本身,也就是從人的實踐活動的特性——諸如實踐活動的客觀性、歷史性、能動性、目的性等出發去解釋各種哲學問題。這就是說,在“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這里,實踐是一個被描述的對象,是一個實體性的哲學范疇,尚未構成一種哲學意義的解釋原則或思維方式。因此,“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既試圖把實踐作為核心范疇而貫穿于各種哲學問題之中,又無法把實踐作為解釋原則而重新解釋全部哲學問題。與“實踐唯物論”和“實踐本體論”不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所理解的實踐和所強調的實踐,是馬克思所說的“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也是把實踐觀點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來理解人、理解人與實踐的關系,從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學問題。正因為是把實踐的哲學意義理解為“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所以,這里的實踐既不是一種“實體”范疇,也不是客體意義上的“關系”范疇,而是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解釋原則。這種解釋原則,就是從“現實的個人”即“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出發,去理解和解釋全部哲學問題。因此,馬克思的實踐觀點是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哲學解釋原則的創新,這才是實踐觀點的真實意蘊。
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內涵
“思維方式是人們思維活動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評價客觀對象的基本依據和模式”5J。所以,觀點僅僅屬于哲學理論的個別表現,思維方式才代表哲學家思想的精神實質。理解哲學的思想實質,關鍵就在于理解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內涵。任何一種哲學,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維方式而與其他哲學相區別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哲學的精神實質,是否貫徹實踐觀點這種思維方式,是判定哲學與非哲學原則界限的基本依據。就哲學傳統而言,馬克思繼承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但是他的“新唯物主義”與傳統的唯物主義卻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個區別就在于馬克思提出的實踐觀點,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辯證法思想,這是因為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以實踐觀點為理論基礎的。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最根本之處就在于對人的本質進行了重新理解,把實踐看作人的存在方式,從而實現了從抽象的、虛幻的人到具體的、現實的人的轉換。所以,哲學的出發點就“是一些現實的個人,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包括他們得到的現成的和由他們自己的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生活條件”6J。作為哲學出發點的“現實的個人”與西方傳統哲學的“主體”概念有著本質的區別,傳統哲學的“主體”概念是以主客二分為前提的,而在馬克思的哲學中,實踐成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個抽象的主體,而成為“現實的個人”,從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達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學自笛卡爾以來,便形成了主體性哲學的傳統。康德在批判地總結傳統主體概念的基礎上,正式確立了哲學的主體性原則,把主體概念改造、規定為先驗主體或主體性。所以,在康德哲學那里,主體就是邏輯主體,是絕對的、先驗的自我或意識,而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學中,主體概念基本上僅僅是一個認識論的概念,而沒有進入存在論的領域。與康德關于主體的概念不同,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序言中明確地提出了“實體在本質上即是主體”的思想_7J,并且進一步指出:“活的實體,只當它是建立自身的運動時,或者說,只當它是自身轉化與其自己之間的中介時,它才真正是個現實的存在,或換個說法也一樣,它這個存在才真正是主體。”8j在黑格爾的哲學中,主體已經不再是笛卡爾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驗主體”,而是絕對的,“絕對即主體的概念”_9J。主體已經不僅僅是指認識論意義上的自我或意識,而且也是一種存在樣式,即一個在對抗過程中實現統一的自我發展過程,可見,黑格爾的主體概念已經真正地進入了存在論的領域。黑格爾堅決反對康德將現象與本體、主體與客體分裂的二元論,在絕對精神自身發展的過程中,黑格爾實現了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但是他卻將這個歷史過程視為精神自我實現的過程。所以,黑格爾的主體是一個最終超越歷史過程的主體,一個“純粹的概念神話”,黑格爾哲學是一種主體性哲學擴張的極致,是一種“理性的放蕩”。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體概念,但是后來他更多使用的是“現實的個人”或者“勞動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徹底地把“現實的個人”作為其理論的出發點,這樣,馬克思就從根本上超越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革新。這是因為“現實的個人”就是從事實踐活動的人,所以,馬克思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象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只存在于口頭上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象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真正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Ll0l。“現實的個人”是對傳統主體概念的瓦解與顛覆,是主客同一體,這與海德格爾把人稱之為“此在”所具有的意義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與傳統單純的、純粹的主體概念區別開來,無論是“現實的個人”還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是一種主客同一體,表達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與世界共在的性質。哲學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真實內涵就是從“現實的個人”出發,“現實的個人”就是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就是“他們的活動和他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所以,“現實的個人”就是一個主客同一體。雖然黑格爾強烈反對康德現象與物自體、主體與客體分裂的二元對立,也在努力地解決兩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絕對精神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實現了主客體的統一,但是主客體的統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對立為前提的,如果沒有主客二元對立,又怎么會有二者的統一?馬克思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從“現實的個人”或“實踐活動”出發,而“現實的個人”表明了人與世界的不可分,兩者是同一的,我們不能把人僅僅當作一個純粹的主體去看待。可見,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已經超越了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一種主客同一的思維模式。
三、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與馬克思的哲學變革
“思維方式的變化是根本性的變化,每一種代表時代精神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的出現,都具有某種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學的產生之所以能夠引起整個哲學理論觀點的革命性變革,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思維方式發生了轉換。哲學立足于實踐的觀點去理解一切哲學問題,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就成為哲學看待一切問題的邏輯原則。所以,與傳統哲學相比,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的哲學變革的實質。傳統的哲學爭論集中在“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上,這被恩格斯稱之為“哲學的基本問題”。由于傳統哲學不了解能夠把思維和存在統一起來的現實中介,所以,近代以來唯物論與唯心論在此問題上爭論不休,陷入了一種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而馬克思提出的實踐觀點,正好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的統一中介問題,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兩極對立,為哲學的發展開辟了全新的理論視域,并實現了哲學向生活世界的回歸。馬克思提出的實踐概念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它不僅解決了思維與存在統一的中介問題,更重要的是改變了哲學看待問題的基本觀念,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過去,人們看待哲學問題只是從或者物質或者精神的單一基礎出發,實踐作為人的目的性活動,它的含義則是雙重性的。而從物質和精神的統一關系出發,原來哲學中的許多理論觀念便都需要改變。所以,馬克思的哲學變革的實質就是思維方式的轉換,更確切地說,就是馬克思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的確立。
由于傳統哲學以主客二元對立為前提,所以,傳統唯物論和唯心論執著于“本原”問題上的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也就造成了思維方式上的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互不相容。黑格爾認為,消解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的抽象對立,克服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互不相容,必須訴諸于把它們統一起來的中介環節——概念的世界。雖然黑格爾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個抽象的、邏輯的中介環節,并不是一個現實的基礎,但是黑格爾“本體中介化”的道路卻為問題的解決指明了方向,整個西方哲學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礎上完成的,馬克思哲學當然也不例外。包括馬克思在內的整個西方哲學都試圖找到某種揚棄自然與精神、客觀與主觀抽象對立的中介環節,并以這個中介環節作為統一性原理實現一種哲學范式的轉換。現代西方哲學找到的中介是“語言”,馬克思找到的是“實踐”,馬克思不僅以實踐范疇去揚棄舊哲學中的自然本體與精神本體、客體性原則與主體性原則的抽象對立,而且也把實踐活動本身視為人與世界對立統一的根據,用實踐的觀點去解決全部哲學問題,這就是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從對立的兩極出發,并以抽象的兩極對立關系為基礎而形成的舊唯物論和唯心論,被“本體中介化”的現代西方哲學所取代。“本體中介化”的現代哲學,站在歷史主義的立場,排斥絕對確定性的追求。傳統哲學從對立的兩極去思考自然界與精神的關系問題,其實質是把人的自然屬性和精神屬性抽象地對立起來,從人的兩極存在去尋求人類本質。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現代西方哲學從中介出發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關系問題,其實質則是以人的歷史活動或生存活動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動具體地統一起來,從人的社會存在去尋求人類的本質。
第5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關鍵詞:古代本體論;近代認識論;現代語言轉向
一古代“本體論”哲學的存在
一般認為,哲學本體論是一種關于一般存在或存在自身的哲學學說,關于脫離具體存在的超驗存在的學說。作為一種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它是一種理論思維的沒有窮盡的指向性,其中,指向的是無限的終極關懷,主要目的是為了在浩瀚宇宙中獲得生存的歸屬感,古人通過存在寄希望在人的心靈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建立起某種終極穩定的聯系,希望尋求一個超感性絕對和歷史恒久的終極存在來實現生命的價值所在。“哲學本體論具有三重蘊涵,即:追尋作為‘世界統一性’的終極存在(存在論或狹義的本體論);反思作為‘知識統一性’的終極解釋(知識論或認識論);體認作為‘意義統一性’的終極價值(價值論或意義論)。”[1]古代的哲學家認為世界的本源是一種物質,比如,泰勒斯認為“水”是世界的本源,后來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又將“火”“氣”“種子”等視為當時的世界本源。由此可以得出,古代哲學家們提出的“始基”一詞,帶有一種經驗主義的色彩,而且是感性直觀的。相當一部分的思想觀念或者著名學說都是屬于最原始的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前者屬于存在論或本體論,后者屬于狹義宇宙論。古代本體論思維模式關注的是對知性的追根問底和本原的探索,即是將“物理”問題轉向“物理學之后”的頂端智慧的終極探索,希望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建構一個具有絕對真理價值意義的形而上學體系,因此,這也就確立起了一種知識形態的哲學探索框架和具有理性主義思想觀念的傳統文化,這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對人類的理性積累、科學知識的進步和社會文明的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和歷史價值。古代和近代有一種本體觀的形態叫“本質論”,這一理念認為本體是萬事萬物的內在本質和普遍的共相。比如柏拉圖的理念,絕對觀念等當作世界的本體,從中可以看出古近代對本體性的理解是本原性、本質性、基礎性的,然后它符合了形而上學的最基本的要求。人類的實踐活動具有理想性、現實性、有限性、指向性。人類實踐的本性是建立在理論思維的基礎之上的,總是渴望著能夠在最深層次的基礎上認識世界、把握和解釋世界,從而對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價值有一個明確的認識。
二近代“認識論”轉向的哲學存在
培根和笛卡爾是近代認識論哲學的開創人,在培根所有的理論哲學中,大部分的思想是他的知識方面的思想。雖然笛卡爾的所有哲學觀念中,知識學占的比重不大,但是他的經典著作中大部分是屬于知識學的。認識論轉向哲學是近代哲學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特別是近代哲學的重大的基本問題”;而且具體的指出,“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只是”在近代哲學中“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來”,“才獲得了它的完全的意義。”[2]近代哲學能夠確切的區分“意識外的存在”與“意識界的存在”,也就是明確區分了“客觀世界”和“意識內容”,這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從“內容”上去考察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因此,掌握近代哲學的基本特征對我們理解、掌握哲學基本問題的歷史前提、基本內涵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認識論轉向是相對于古代的本體論哲學而言的一個概念。認識論轉向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能夠自覺到了“思維和存在”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視為最基本的哲學“問題”來探討研究。也就是說,近代哲學所實現的哲學基本問題的“完全的意義”,主要是在“認識論”意義上來實現的。近代認識論思維模式把思維和存在視為探索存在問題的邏輯出發點,“思想”的主題地位得到了確立,它根本的價值就在于:以主體的人作為核心,在主客體之間探尋思想的客觀性和知識的確定性的根本依據,從而為人和世界的知識提供根本的保障。近代哲學產生了認識論的轉向,不管是唯理論也好,經驗論也罷,最后的目的所在都是為了探索認識與存在的關系,區別就在于兩者的研究方向、出發點不同而已。笛卡爾在他的《第一哲學沉思錄》開篇就明確的提出了“上帝和靈魂這兩個問題是應該用哲學的理由而不應該用神學的理由去論證的主要問題。”[3]洛克制定了經驗理論體系,即主體意識原理的理論。他說道:“在我們考察那類(知識的)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考察自己的能力,并且看看什么物象是我們的理解能夠解決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決的。”[4]對洛克而言,知識的問題本質就是人的理智能力的問題。
三現代西方“語言轉向”的哲學存在
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把語言問題視為哲學最基本的問題來研究,是從認識和存在的關系轉向了語言和存在的關系。這時的人類也頓悟到,思想觀念的經歷也即是語言的經歷,哲學的體驗感受也即是語言的游戲,因此,語言的這種意識使得語言問題在某個世紀主體化了,并且包含在語言中的語法、語義等受到了高度的重視。“所謂語言學轉向,指的是哲學接過語言學得對象為自己的對象,但哲學對語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結果等諸多方面都有別于語言學。”[5]現代西方哲學語言轉向包括了語言論的反思方式、存在論的反思方式和文化論的反思方式。而且了解語言轉向的基本內容對于我們認識研究哲學基本問題是非常有必要的。脫離對人類語言的考察進而直接斷言思維與存在的關系是現代西方哲學語言轉向所要批判的。并且關于哲學家們對人類意識和世界的相互關系的是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上的,這也是現代西方哲學語言轉向的必然要求,其實質是把語言作為研究思維和存在關系的基本出發點。現代西方哲學如此重視從哲學的角度來研究語言,主要原因在于形成了一種基本的共識,即世界在人的語言之中,盡管世界在人的意識之外;語言不僅是人類存在的消極界限,而且是人類存在的積極世界;通過對語言的反思達到“治療”傳統哲學的效果;既從批判傳統哲學和實現“哲學科學化”的角度去對待哲學語言轉向,而且更加深切地從“文化批判”和“人文研究”的角度去看待哲學語言轉向;語言相對于觀念而言,更具有廣闊的哲學反思價值尺度。語言學轉向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是哲學本身滅亡的救世主,化解了這場岌岌可危的劫難。而且這次轉向有它自身的客觀必然性,原因在于哲學從未消停過對存在的探索與追求。從這個角度來講,哲學不是對它的方向作了改變,而在于它遇到危險的時候能夠轉變思維方式,換一種介質繼續向前進。古代自然哲學為了往外尋求“始基”,而無法實現時,就轉化為認識存在的精神實質。現代語言哲學家們對諸如語言的原則、性質、規范等等進行了一系列的探討,力圖通過語言分析來創立一門既嚴格又清晰的工作語言。語言是一個紛繁復雜的系統,而它的意義則是更加的難以確定,對于相同的話,相同的信號系統,不同的人對于這些持有的看法和觀點是不一樣的。正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四西方哲學“存在”的理論缺陷
人是現實的存在,但是卻要尋求著超驗的存在,原因在于人對世界的認識總是處在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之中的。感性所把握的存在是經驗的,理性所把握的存在是超驗的存在。古代的本體論是人們在沒有經過認識和反思的情況下而直接的追問下,所以這種幻想只能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西方哲學史上的哲學家們都力圖通過對求知的方法來解決本體論的問題,但是古希臘的哲學家的研究重點在于本體論上,而不是在認識論方面,隨著認識論哲學的發展,探求存在本身為核心的本體論哲學模式,就被以反省人類認識為理論核心的認識論哲學模式所取代。近代西方哲學對于理性和主體的自我意識的思索,僅僅是看作能思的存在,過于局部地看重理性的認識,沒有意識到能思主體的價值所在,原因也在于人類判斷力、理解力的局限性、狹隘性,使得近代認識論不能走出思維主體的枷鎖。在認識論哲學中,存在與自我意識中的存在、世界和主體的人相脫離,使得對哲學的追問又陷進了古代本體論那種窘境。這表明,近代哲學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解存在的缺陷就在于脫離了人類的實踐活動及其發展歷史去回答“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由此,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6]進而,產生了新的革命性的“語言轉向”。現代西方哲學家他們并不是像傳統思想家們把語言視為具有邏輯和理性的東西,僅僅是看作生活經驗和非理性的東西,與此同時,否定了邏輯在語言活動中所起到的作用,比如,德里達在批判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時就把人的語言活動認為不是人的理性活動的一種認知活動,僅僅是一種非理性、非決定論的雜亂無序的活動。缺乏抽象的社會歷史性的實踐觀,例如,胡塞爾與哈貝馬斯等人的主體性關鍵是以種語言交往的形式為基礎的作為人的主體性的社會性,是一種抽象的經驗和精神交往的關系。“視域融合”作為伽達默爾解釋學的內容也主要體現在文本中的作者與讀者間的思想交流以及讀者閱讀文本的反思。所以,哲學語用學說明的語言意義不僅僅是來自于語言自身的要素以及結構框架,而且還來自于語言的使用等范疇之間的相互作用。
參考文獻
[1] 孫正聿.思想中的時代——當代哲學的理論自覺[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50.
[2]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20頁.
第6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一、巴門尼德的“存在”
巴門尼德他是愛利亞學派的主要代表。在他的哲理長詩一開篇,巴門尼德就借女神之口為眾人指點迷津,希望把人們從黑暗帶到光明中。我們的認識面對著兩條路,一條是“真理之路”,一條是“意見之路”。“真理之路”以“存在”為對象,“意見之路”則以“非存在”為對象。“非存在”不是不存在,而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自然事物。在巴門尼德看來,只有存在是可以思想和述說的,因為它與真理同行。因此,知識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存在之路。巴門尼德把以往的自然哲學都看作是“意見之路”,他現在做的是使哲學走上“真理之路”。希臘哲學從一開始就把尋求知識做為最高的理想,但是在自然哲學這一領域卻難以達到這個高度,因為它局限于感性的經驗和崇尚本原的無定性中,這使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為基礎的知識成為不可能。如果說以泰勒斯為首的自然哲學家所追問的是時間在先,那么巴門尼德則扭轉了哲學的方向,他追問的是邏輯上在先的本質,即“存在”。
巴門尼德關于哲學的研究與論述是希臘哲學的轉折點,即便它的意義直到蘇格拉底之后才得以顯現。巴門尼德他對哲學的貢獻有很多。第一,劃分了兩個世界。即現象世界與本質世界,這為以后西方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本方向。第二,將“存在”定為研究對象,這奠定了本體論的基礎;第三,區別于自然哲學家的武斷地判定與宣稱,他使用邏輯論證的方法,這使古希臘哲學開始向理論化系統化的方向發展;第四,關于“作為思想和作為存在是一回事情”這一命題確定了理論思維或者說思辨思維的基本形式。
但是,盡管巴門尼德的思想為后期西方哲學的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在當時卻并沒有被大多數哲學家所接受。他的思想在當時非常新穎、深刻,但與自然現象的千變萬化相抵牾,所以,他的思想就很難被同時期的哲學家們所接受與理解。
二、蘇格拉底的概念論
蘇格拉底對本體論哲學的貢獻在于他將巴門尼德所確定的一般的原則落到了實處,將它具體化為“是什么”的問題。
關于希臘哲學的基本問題其實是認識問題。在蘇格拉底登上哲學舞臺的時候,自然哲學其實就已經陷入了困境。而蘇格拉底用“德性即知識”來闡述獲得知識的可能性,而以“是什么”的問題講解獲得知識的具體途徑。
根據柏拉圖的記載,關于蘇格拉底的對話大多是以追問“是什么”為主題,例如,什么叫作勇敢,什么是節制,而什么又是正義等,但他追問的并不是具體的和特殊的事物,而是其本質。由此可見,蘇格拉底要求認識的是一事物成為其自身的本質,他所理解的知識是對事物普遍的本質認識。在柏拉圖記載的關于蘇格拉底與智者希庇亞討論美是什么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他們二者分別代表理性和感性,當蘇格拉底把哲學的問題集中在“是什么”上的時候,他就把哲學需要解決的問題確定在了怎樣從感覺經驗中歸納抽象普遍概念。
從表面看來,蘇格拉底的哲學主要是從邏輯學的意義上區別澄清與道德相關的某些概念,實際上它也是具有深刻的本體論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講,蘇格拉底所提出的“是什么”的問題,為整個西方哲學史確定了方向。同時,蘇格拉底對于概念定義的探索也促進了柏拉圖理論的產生,不過,他沒有將普遍存在的東西從特殊事物中抽離出來,而蘇格拉底的這種思想被稱為“概念論”。
由此可見,從巴門尼德到蘇格拉底,從“存在”到“概念論”,古希臘本體論的思路是越來越清晰了。
三、柏拉圖的“理念論”
柏拉圖繼續發展了巴門尼德的存在論以及蘇格拉底的概念論,在二者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本體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理念論。理念的基本定義是“由一種特殊性質所表明的類”,但它并非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作為世界萬物存在的實在。柏拉圖認為,每一類事物有一個理念,事物是多,理念為一,理念作為萬事萬物最根本的根據,是最完美的整體。因此,理念不會受到別的事物對其的影響,而且,理念和理念之間是沒有聯系的,因為理念是單獨的自身的存在,不依靠他物,不變為他物。個別事物是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而理念是永恒不變的,是必然的、絕對的存在。在理念與事物的關系之間,柏拉圖認為,理念是萬物的根據與原因,事物是理念的派生物。他通過兩種方式來證明理念的派生。
一是分有,一是模仿。分有即具體事物分有同名的理念,模仿則是造物主根據理念進行創造具體事物。二者的區別實際上是有無造物主的區別。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講,柏拉圖兩個世界的理論發展了巴門尼德的意見之路與真理之路的思想,不同之處在于,柏拉圖所謂的非存在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現象,因此,比巴門尼德的思想更有深度。
柏拉圖的思想涉及概念與事物的關系問題。他所說的理念論實際是為了解決知識的問題,但是他的兩個世界的劃分是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盡管后期柏拉圖對他的思想進行了一定的修正,但理念論的矛盾即可感世界與可知世界的對立是無法克服的。晚年的柏拉圖雖然苦于無法解決這兩個世界的關系問題,但是他認為就知識而言絕不能放棄理念論的立場,因而他更關注的是理念之間的關系問題,于是他嘗試進一步說明理念世界的統一性。
四、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
亞里士多德關于形而上學的論述是以“存在”作為他的研究對象的,他甚至把以“存在”為研究對象哲學叫做“第一哲學”,后世的人們經常由此出發來確定哲學對其他科學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在研 究應該如何認識“存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困境。而認識事物的關鍵在于能夠把握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能夠認識事物的“是什么”,而認識“存在”也應當如此。可是,在實際中我們卻不能夠像認識具體事物“是什么”那樣去認識存在“是什么”。因為認識一事物“是什么”其實就是給該事物下定義,而我們所謂的“下定義”就是通過形式邏輯“種加屬差”的方式對其做出規定。所以,我們無法認識存在“是什么”,只能夠認識存在是以怎樣的方式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的存在的“存在方式”。我們知道存在有兩種存在方式,即“偶然的存在方式”與“本然的存在方式”。舉例說明“這位老師是有德性的”,“這位老師長得很漂亮”,這些都是表述一位老師的“偶然的存在方式”,因為一位老師的“本然的存在方式”是具有她本該具備的知識技能,至于她有沒有德性,長得漂不漂亮,與身為老師沒有必然的聯系。也就是說,“本然的存在方式”就是存在本身必然所擁有的存在方式。于是,亞里士多德就將形而上學的任務確立在研究“存在”的本然的存在方式上,也稱之為“范疇”。
亞里士多德在《范疇篇》中提出了關于事物的十種描述方式,也就是十個范疇。這十個范疇是最基本的。在這十個范疇中,有一個范疇最重要,它就是“實體”。依據亞里士多德的規定,“實體”指的是事物的“是什么”,或者是事物的“是其所是”,相當于我們說的“本質”。亞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圖關于事物之外存在著分離的理念的觀點,他主張具體個別的事物是真實存在的。后來經過研究,亞里士多德意識到個別具體的事物還可以再分析,可以分為質料和形式。這就需要再追問在個別事物中,究竟是質料還是形式是第一實體?在具體事物中,質料是處于生滅變化中,因而是不可定義的,而真正定義的是事物中的形式。所以,“形式”是第一實體。
亞里士多德認為最高的實體善,唯有理性才能把握善,就其最完滿的狀態而言,理性與善是同一的,當然唯有神是這個同一。盡管我們把亞里士多德關于最高實體的學說稱為“神學”,但他所說的“神”并不是后來基督教的人格神,而是指最高的實體、最完滿的現實性、最高的目的。
從“具體事物”是“實體”,到“形式”是“第一實體”,再到“神”是“最高實體”,這是亞里士多德實體學說的發展歷程。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是與巴門尼德、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根本上是一脈相承的。
從巴門尼德將“存在”確定為哲學的研究對象,經過蘇格拉底再到柏拉圖對“是什么”的研究,再到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學,這個過程可以看作是古希臘哲學本體論的發展歷程,它為整個西方哲學定下了基調。古希臘時期涌現出了許多優秀的哲學家,他們的思想為西方哲學史留下了非常寶貴的哲學精神,為以后西方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是在這一時期,人們發現了哲學對人們生活的啟示,進而啟發人們的思維,為哲學發展帶來了更多機遇,西方哲學史是一部宏大的發展史,需要我們更加深入地進行研究和探討,得出更多優秀的成果,為哲學的發展增添一抹亮色。
參考文獻:
苗力田.古希臘哲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第7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一
傳統形而上學(第一哲學)的核心理論是“是態學”(die Ontologie)。柏拉圖說,在人的靈魂中有著哲學的因素。這種哲學的因素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試圖用“一”來統攝“多”,即對統一性甚至最高統一性的某種追求。在希臘哲學那兒,它經歷了從“宇宙學”(die Kosmologie)到“是態學”(die Ontologie)的轉變。前者所思考的,乃是紛紜復雜的現象背后是否有著某種統一的東西,其基本的發問方式可以規定為“它是由什么構成的?”或“它是從哪兒來的?”,它追問萬物產生于它又復歸于它的某種或某些“基質”、“本原”或“元素”。而后者打量世界的基本發問方式是“它是什么?”以及與之相關的“它是怎樣?”,它的核心是追問萬物的“所是”或“本質”。后者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即“第一哲學”所要思考的東西。
“它是什么?”(Was ist das?)這一打量世界的基本發問方式不僅催生了邏輯學和科學,更是導致了形而上學的產生。柏拉圖的理念論以及亞里士多德的范疇學說,都可以視為對這一問題的某種回應,都是對現象的某種拯救()。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一書中明確將“第一哲學”()①的研究對象規定為“是者作為是者”或“作為是者的是者”(),它也是“第一哲學家”(,《論靈魂》,403b.16.)所要加以探究的東西。他在該書的第四卷(Γ卷)、第六卷(Ε卷)和第十一卷(Κ卷)中反復指出,第一哲學的對象乃“是者作為是者”(),它研究“是者作為是者”(,)。例如:
溥林:否定形而上學,延展形而上學?“有一門科學,它研究是者作為是者以及那些就其自身就屬于它的東西。它不同于任何的特殊科學,因為其他那些科學中的任何一門都不普遍地思考是者作為是者,而是切取它的某個部分并研究該部分的屬性。”《形而上學》,1003a.21.
“因此,顯然有一門科學研究是者作為是者以及那些位于是者作為是者之中的東西;這同一門科學不僅研究各種所是而且研究那些屬于所是的東西,既研究前面所述的那些東西,也研究在先和在后、屬和種、整體和部分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形而上學》,1005a.13.
“哲學家的科學普遍地探究是者作為是者,而不是探究它的部分;而‘是者’在多重方式上而不是在一重方式上被言說。”《形而上學》,1060b.31.
這種學說在古代被稱為“關于是者的理論”()這一表達后來在拉丁語中被概念化為ontologia。現在一般認為ontologia一詞最早是由德國哲學家雅各布?洛哈德(Jacobus Lorhardus, 15611609)在《八藝》(Ogdoas Scholastica)一書中提出來的,他將它視為“形而上學”的同義詞。在該書中,他討論了八門學科:拉丁語法(Grammatices Latinae)、希臘語法(Grammatices Graecae)、邏輯學(Logices)、修辭學(Rhetorices)、天文學(Astronomices)、倫理學(Ethices)、物理學(Physices)、形而上學或是態學(Metaphysices, seu Ontolgia)。,研究“是者作為是者”乃是形而上學即第一哲學的任務Simplicius,In Aristotelis Categorias Commentarium, 9.2930.。對它的理解是把握形而上學和是態學的關鍵。關于這一點,亞里士多德本人也曾指出: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那總是被追問和總是讓人困惑的問題就是:‘是者’是什么。”《形而上學》,1028b.2.
基于形而上學打量世界的基本發問方式,凡是可以用“是”(Sein)加以發問和回答的,都是“是者”(das Seiende)。也正因為如此,亞里士多德才會說:“因此,我們也說不是者是不是者。”()《形而上學》,1003b.10.
我們認為,在傳統形而上學中(至少在亞里士多德那兒),并未如海德格爾那樣嚴格區分“是”(das Sein)和“是者”(das Seiende),也即是說,并未將和加以嚴格區分。是動詞的現在分詞的中性單數,前面加上中性冠詞,就可以成為一個名詞。這一名詞既可在動詞的意義上進行理解(是、是著),也可以在名詞的意義上理解(是著的東西、是者)。亞里士多德本人似乎并未嚴格區分“是”和“是者”;他在 “是”和“是者”這兩個意義上使用這一語詞,這既給后世的理解帶來極大的麻煩,也為一種新的哲學理解提供了可能后來海德格爾就嚴格區分了“是”(das Sein)和“是者”(das Seiende),并將之稱為一種“是態學上的差異”(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
當作物質名詞“是者”理解時,有復數形式;當作動詞“是”或“是著”理解時,亞里士多德有時使用替代表達。的否定形式是,它既可在動詞的意義上來理解,也可在名詞的意義上來理解。作動詞理解,則有替代形式(不是,不是著);作物質名詞理解,則有復數形式(不是者,非是者)。我們這兒選取《形而上學》第五卷(Δ卷)第七章中的一段話作為例證:
“‘是者’”(),有的被稱作根據偶然而來的‘是者’,而有的則被稱作根據自身而來的‘是者’。……根據自身而來的‘是’()如范疇表所表示的那么多;能說出多少范疇,‘是’()就有多少意指。在諸謂詞中,有的意指‘是什么’,有的意指‘質’,有的意指‘量’,有的意指‘相對物’,有的意指‘行動’或‘遭受’,有的意指‘地點’,有的意指‘時間’;‘是’()就意指著它們當中的某一個。因為人正在康復和人康復之間并無區別,人正在走或人正在切同人走或人切之間也無區別,就其他的情形而言也同樣如此。……此外,‘是’()和‘它是’()意指著是真的,而‘不是’()意指著不是真的而是假的,就肯定和否定而言同樣如此。……此外,在前述‘是’()和‘是者’()中,有的意指潛能上的‘是者’,有的意指現實上的‘是者’。”《形而上學》,1017a.7.
既然在“是者”()的四重含義中,只有范疇意義上的“是者”和潛能、現實意義上的“是者”屬于第一哲學的研究對象,而后者又體現在前者當中,因此,范疇理論就構成了第一哲學(形而上學)或是態學的核心內容,而在諸范疇中,“所是”()范疇最為重要,對它的討論又進一步成為第一哲學的核心所在:
“正如我們在前面關于一個語詞有多重含義那兒所指出的,‘是者’具有多重含義。因為它或者意指‘是什么’即‘這個’,或者意指‘質’,或者意指‘量’,或者意指這類謂詞中的其他某個。盡管‘是者’有如此多的含義,但顯然其中首要的‘是者’乃‘是什么’,因為它揭示的乃‘所是’(當我們問這個東西具有怎樣的質時,我們說它或者是善的,或者是惡的,而不說它是三肘長或是人。但當我們問它是什么時,我們不會說白的、熱的、三肘長的,而說人或神。),而其他的之所以被稱為是者,乃是因為要么是這種是者的‘量’,要么是它的‘質’,要么是它的某些情狀,要么是它的其他某種東西。”《形而上學》,1028a.10.
“‘首要的’具有多重含義,但‘所是’在各方面都是‘首要的’,無論是在邏各斯上,還是在認識和時間上。其他的范疇都不能獨立存在,唯有它能夠獨立存在。在邏各斯上它是首要的(因為在每一范疇的邏各斯中必然存在著‘所是’的邏各斯)。當我們知道人是什么,或者火是什么,而不是知道它們的‘質’、‘量’、‘地點’等時,我們認為我們最為充分地知道了它們;而且我們要知道這些東西中的每一個,也只有當我們認識到‘量’或‘質’是什么時才行。事實上,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總是被尋求并總是讓人感到困惑的東西,就是‘是者’是什么,即‘所是’是什么(因為一些人說它是‘一’,一些人則說它不只是‘一’,而是‘多’;一些人說它是有限的,一些人則說它是無限的);因此,對于我們來說,最根本的、首要的和唯一的問題就是考察這樣‘是著’的東西是什么。”《形而上學》,1028a.31.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諸范疇是不能彼此歸約的諸最高的屬。如果范疇之間的差異是最高屬上的差異,那位于每一范疇之下的屬、種也是不同的,它們彼此之間沒有隸屬關系。既然諸范疇都是最高的屬,那么,它們除了不能彼此歸約外,也不能歸約到某一更高屬之下。對此,亞里士多德給予了非常清楚的表達:
“那些原初載體不同的東西,被稱作是在屬上不同的東西,它們不能彼此歸約,也不能將兩者歸入到同一東西中;例如……以及那些歸入是者的不同范疇中的東西(因為一些是者意指‘是什么’,一些意指‘質’,有些意指前面所劃分出來的其他范疇)。它們不能彼此歸約,也不能一起歸入到某種‘一’中。”《形而上學》,1024b.9.
那么,有無比作為最高是者的范疇更高、更普遍、統攝它們的東西呢?有!那就是“是(者)”(/, das Seiende / das Sein)。根據前面所講,諸范疇也就是在其自身“是著”()的諸方式;“是(者)”雖然比它們的普遍性更高,但“是(者)”本身不是一種屬,即不是比諸范疇更高的、統攝它們的屬。也正因為如此,它不“同名同義地”()謂述諸范疇;而根據亞里士多德,范疇作為屬,“同名同義地”謂述位于其下的種直至個體:
“屬和種都是同名同義者。”( 《論題篇》,123a.2829.)
“屬同名同義地謂述一切種。”(《論題篇》,127b.67.)
“是(者)”(/)是最普遍的,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講就是它最為述說所有的東西。這又該作何理解呢?因為即使在古希臘語中,我們也發現,該詞除了大量出現在系表結構中外(當然也可以省略),還有大量的句子不會使用它。要理解這一點,還是只能回到亞里士多德那兒。在我們前面所引的《形而上學》第五卷(Δ卷)第七章中的那段話中,亞里士多德說道:“‘是’()就意指著它們當中的某一個。因為人正在康復和人康復之間并無區別,人正在走或人正在切同人走或人切之間也無區別,就其他的情形而言也同樣如此。”歷代注家面對這句話,都做出了相應的解釋,而托馬斯?阿奎那在其《〈形而上學〉注釋》(In XII libros Metaphysicorum Aristotelis Expositio)中的解釋最為清楚明白:
但是,由于有些進行謂述的語詞在其中顯然并未使用動詞“是”(例如我們說“人走路”,為了避免有人以為這些謂詞與“是”這個謂詞沒有關系,于是他接下來就排除了這種情況,他說:在所有這樣的謂詞中都有著某個東西意指著“是”。因為每一動詞都可歸為動詞“是”加分詞。因為說“人正在康復”和“人康復”并無區別,其他情形也同樣如此。因此,顯然謂詞有多少種樣式,“是者”就有多少種含義。Quia vero quaedam praedicantur, in quibus manifeste non apponitur hoc verbum est, ne credatur quod illae praedicationes non pertineant ad praedicationem entis, ut cum dicitur, homo ambulat, ideo consequenter hoc removet, dicens quod in omnibus huiusmodi praedicationibus significatur aliquid esse. Verbum enim quodlibet resolvitur in hoc verbum est, et participium. Nihil enim differt dicere, homo convalescens est, et homo convalescit, et sic de aliis. Unde patet quod quot modis praedicatio fit, tot modis ens dicitur. Thomas Aquinas, In XII libros Metaphysicorum Aristotelis Expositio, 893.
“是(者)”(/)雖是最普遍的,但卻不是統攝諸范疇的屬。亞里士多德本人不止一次講到這一點:
“‘是’不是任何東西的所是,因為‘是’不是屬。”(《后分析篇》,92b.13.)
“‘是’和‘一’都不可能是諸是者的一個屬。”(《形而上學》, 998b22.)
對此亞里士多德的理由主要有兩點:(1)一方面,無論是屬、種還是種差,都可以用“是”加以謂述,因為“是”謂述所有的“是者”;另一方面,就屬、種和種差之間的關系而言,屬在本質上不能謂述種差,因為種差是外在于屬的,正是通過它將屬劃分為種。因此,“是”不是屬。(2)如果“是”是屬,那么,就可以通過在它之外的種差將之劃分為種,但“是”的最高普遍性不同于范疇的最高普遍性,因為在它之外就是“無”,故“是”不是屬。參見:《論題篇》,144a.31;《形而上學》,998b.14。因而它不“同名同義地”()謂述所有的是者(當然包括諸范疇),而是“同名異義地”()謂述它們。關于這一點,珀爾菲琉斯(Porphyrius)在其《導論》(Isagoge)中也曾加以指出:
“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是(者)’并不是所有東西的一個共同的屬,所有的東西也不會因一個最高的屬而是同屬的。但是,正如亞里士多德在《范疇篇》中所做的那樣,十個最高的屬要被確定出來,它們就像十個最高的本原一樣。他說,即使有人將所有的東西都稱作‘是(者)’,那他也是在同名異義的意義上而不是在同名同義的意義上那樣稱它們。”Porphyrius, Isagoge sive quinque voces, 4,1.6.59.
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在“同名同義地”和“同名異義地”之外,進一步提出“類比地”()這一觀點,明確指出,“是(者)”的最高統一性乃是類比的統一性,而類比的統一性是最高的統一性。
“此外,一些東西在‘數目’上是‘一’,一些東西在‘種’上是‘一’,一些東西在‘屬’上是‘一’,一些東西在‘類比’上是‘一’。那些在‘數目’上是‘一’的,其質料是‘一’;那些在‘種’上是‘一’的,其定義是‘一’;那些在‘屬’上是‘一’的,指的是同一范疇形態適用它們;那些在‘類比’上是‘一’的,指的是具有如比例相同的那樣的關系。后面的情形總是跟隨著前面的情形。例如:凡在‘數目’上是‘一’的,在‘種’上也是‘一’;但在‘種’上是‘一’的,并不全都在‘數目’上是‘一’。凡在‘種’上是‘一’的,在‘屬’上也全都是‘一’;但在‘屬’上是‘一’的,并不全都在‘種’上是‘一’,而是在‘類比’上是‘一’。凡在‘類比’上是‘一’的,并不全都在‘屬’上是‘一’。”《形而上學》,1016b.311017a.3.
由于作為最普遍者的“是”()所具有的統一性是類比的統一性,故亞里士多德將它標示為一種無規定的東西,這種無規定的東西通過諸范疇方才獲得規定,而諸范疇自身也就是“是之規定”(Seinsbestimmungen)。根據亞里士多德,一方面我們的全部思維對象最終都會落入諸范疇之中;另一方面,也正是通過范疇,我們方能進行表象活動,方才能有思維的對象,各門具體的科學方才可能有自己的“基礎概念”,并基于這些基礎概念展開自己的活動。對范疇的思考屬于形而上學(第一哲學)的任務,它屬于對“是者”()的一般思考,即歸屬在對“是者作為是者”()的思考中。因此,亞里士多德才會說:“有一門科學,它研究是者作為是者以及那些就其自身就屬于它的東西。它不同于任何的特殊科學,因為其他那些科學中的任何一門都不普遍地思考是者作為是者,而是切取它的某個部分并研究該部分的屬性。”《形而上學》,1003a.21.而海德格爾在《是與時》第3節“是之問題在是態學上的優先性”中的那段話則是亞里士多德這段話的最好注腳:
“諸基本概念是這樣一些規定,在這些規定中,那為一門科學的所有專題對象給予奠基的專業領域得到了在先的并且引導著所有實證探索的理解。因此,只有在對專業領域自身進行一番相應的先行考察中,那些基本概念方才獲得其真正的顯示和‘確立’。然而,只要每一個這樣的領域都是從是者本身的畿域中贏得的,那么,這樣一種在先的、創造諸基本概念的研究就只能意味著就是者之是的基本情狀對是者進行解釋。這種研究必須走到實證科學的前面;它也能夠這樣做。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工作就是其明證。對諸科學的這種奠基從根本上有別于跟在后面跛行的‘邏輯’――邏輯不過是根據一門科學的‘方法’來探索這門科學的某種偶然情況而已。對諸科學的奠基在下述意義上是生產性的邏輯:它仿佛先行跳進某一特定的是之領域,首先就這一領域的是之情狀將該領域展開出來,并讓贏得的諸結構作為對追問的各種透徹指示供諸實證科學使用。例如,在哲學上的首要東西既不是某種關于歷史學之概念構造的理論,也不是關于歷史學上的認識的理論,也不是關于作為歷史學之對象的歷史的理論,而是就真正歷史的是者之歷史性對真正歷史的是者進行闡釋。同樣,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之積極成果在于著手清理出那屬于一般的自然的東西,而不在于得出了某種關于認識的‘理論’。他的先驗邏輯是關于是之領域-自然的先天實事邏輯。”(SZ,S.1011)
三
無論是范疇(die Kategorien)還是“生存論規定”(die Existenzialien),都是“是之規定”(Seinsbestimmungen),它們都是在是態學上(ontologisch)對“是者”的一般規定。只不過前者適用于非此是式的是者,而后者乃是對“此是”(Dasein)這種獨特是者的規定。根據海德格爾的思路,《是與時》一書的最終目的是要擬定出“是之意義”(der Sinn von Sein),而臨時目標則是對作為進行是之理解的視域的“時間”(Zeit)進行闡釋。而這一視域是從一種獨特的是者,即“此是”(Dasein)那兒顯現出來的。
因此,一方面,所有“是態學”(Ontologie)所追問的都是“是者”(das Seiende)之“是”(Sein),而“是”自身不是某種“是者”(海德格爾語),“是”具有多重含義(亞里士多德語),因此,對于它只能擬定出它的“意義”(Sinn),從而生出“基礎是態學”(Fundamentalontologie)。另一方面,既然“時間”是進行“是之理解”的視域,而它又是從“此是”(Dasein)這種是者那兒給出的,故需要對這種是者進行是態學上的分析,從而生起“此是之分析學”(Daseinsanalytik / Analytik des Daseins)。于是,“基礎是態學”和“此是之分析學”具有了一種內在的關聯,對此,海德格爾曾反復加以指出:
“因此,所有其他的是態學所源出的基礎是態學,必須在生存論上的此是之分析學中去尋找。”(SZ,S.13)
“現在已經顯明:一般此是的是態學上的分析學本身就構成了基礎是態學,因而此是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它就是那要在原則上事先就其是而加以詢問的是者。”(SZ,S.14)
“因此,對作為是的是(Sein als solches)進行闡釋這一基礎是態學的任務就包含有對是之時態性進行清理。是之意義問題的具體答案只有在對時態性的整個問題的闡述中給出。”(SZ,S.19)
“就實事而言,現象學就是關于是者之是的科學――是態學。在前面已經給出了的關于是態學之任務的說明中,生起了某種基礎是態學之必要性,它將是態學-是態上的獨特是者,即此是作為課題,從而將自己帶到了主要問題即一般的是之意義問題的面前。”(SZ,S.37)
“那直逼操心現象的關于此是的分析學,應準備好基礎是態學的整個問題,即一般的是之意義問題。”(SZ,S.183)
“在繼續探索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對迄今為了一般的是之意義這一基礎是態學問題所進行的闡釋進行一種回顧性的、細致的占有。”(SZ,S.196)
傳統形而上學所給出的范疇就是對是者的一般的“是之規定”,它們也適用于“此是”嗎?顯然不行!傳統形而上學中的范疇只能適用于非此是式的是者(das nicht daseinsm-ige Seiende),它們無法規定“此是”。而海德格爾在《是與時》中首先要從事的,恰恰是要對“此是”進行是態學上的一般規定――他將之命名為“生存論規定”(Existenzial / pl. Existenzialien),這些一般規定蘊含在“操心結構”(Sorgestruktur)中,而操心結構的源始統一性在于時間性。“時間性在每一種綻出中都整體地將自己時間化,也就是說,生存、實際性和沉淪之結構整體的整體性――即操心結構的統一性,奠基在時間性之每一當前完整的時間化那綻出的統一性之上。”(SZ,S.350)當然,即使這樣,也并未完成該論文所設定的目的:“時間性將被展示出來,作為我們稱為此是的那種是者的是之意義。這一證明必須在對那暫時展示出來的作為時間性的諸樣式的此是之諸結構的重新闡釋中得到檢驗。然而,將此是解釋為時間性,那關于一般的是之意義這一主導問題的答案,并未隨之就已經給出。但是,贏得該答案的地基或許已經被準備好了。”(SZ,S.17)
無論是諸范疇(Kategorien)還是諸“生存論規定”(Existenzialien),都是“是之規定”(Seinsbestimmtheit),都只能放在整個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中來把握。康德將他的三個著名問題歸于“人是什么?”(Was ist der Mensch?)這一問題之下,并將對該問題的回答視為其哲學的頂峰;而在海德格爾看來,這一基于傳統形而上學而來的發問本身就是成問題的,所有的范疇都是規定不住作為“此是”(Dasein)的“人”的,因為對于他怎么能以“是什么”的方式加以追問呢,因為這種是者的“本質”(Wesen)在于它的“去-是”(Zu-sein)和“能是”(Seinknnen)。因此,海德格爾說:
第8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價值問題自古以來就是哲學家研究和爭論的重點問題,不同學者的研究結構和研究視野具有一定的差別。具體來說,生活中的美丑與好壞問題就屬于價值哲學的研究范疇。古希臘哲學和近代西方哲學視野下,哲學家多在美學和倫理學的名義下進行研究與分析,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征。但這種研究視角具有較大的局限性,沒有一個相對穩定和完善的研究范疇,研究范式相對模糊,研究結果的準確度和可信度不高。隨著近代倫理學和美學的不斷發展成熟,價值論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其研究方法更為先進,研究過程更為嚴密,研究思路更為清晰明確,價值論已經初現端倪。
到了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以經驗論知識為基礎,就事實與價值的標準進行了科學合理的區分,他認為“是”與“應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知識概念,其本質風格也存在差異,同時在進行認知研究時,研究者無法根據前者的合理性去推導后者。休謨的這種價值區分標準得到了包括康德在內的哲學家的一致肯定。同時,康德在進行價值研究時,立足于二元認識論和道德哲學的具體理論,提出了“事實的知識”和“價值的事實”兩個概念。在他看來,事實的知識屬于經驗世界范疇,而價值的知識則屬于先驗世界的范疇,同時價值的知識是出于先驗的理性領域發展起來的,是一種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知識。而德國哲學家洛采繼承了這種劃分理論,并將其擴展至世界的劃分當中,劃分了世界的具體領域。他認為世界是由事實的領域、普遍規律的領域以及價值的領域組成。其中,普遍規律的領域又主要表現為普遍的因果規律,即一些規律都是因果作用的產物;價值的領域包括善、美、神圣思想以及其各自體現的意義。在這三個構成領域當中,價值的領域居于首要地位,直接決定著其他兩個領域的發展。同時,其他兩個領域所包含的內容是價值領域實現其最終發展目標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洛采首次將價值論研究提升到哲學研究的首位,這是價值論發展的一次里程碑,具有標志性意義,對后世的研究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因此,洛采在西方被稱為價值哲學之父,他直接影響了西方價值哲學的產生和發展。
價值哲學作為一種全新哲學被人們認識和了解則起源于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文德爾班的新價值哲學。文德爾班在繼承和發展前人價值哲學的基礎上,立足具體的研究實際,逐步建立起自己獨具特色的價值論框架。它將傳統倫理學、美學、哲學的研究視角進行了有機融合,提出了具有包含性的統一范疇,有利于價值研究活動的進一步開展和完善。同時,價值哲學的產生也是哲學在面對危機所采取的自救行動。到了十九世紀后期,西方哲學由近代哲學向現代哲學轉變,其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研究視角都有了相應的變化,呈現出過渡期的不穩定性和沖突性。在這一時期,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哲學體系已經逐漸解體,傳統的啟蒙思想和形而上學的理性思辨被人們逐漸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自然科學在這一階段大行其道,受到了人們的一致認可和推崇。同時,伴隨著傳統理性主義哲學體系的瓦解,哲學研究變得雜亂無章,其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向無法有效明確。文德爾班認為哲學研究陷入了一種絕望的境地,需要優秀的哲學家去拯救。此外,哲學家在研究時,忽略了哲學本身的中心任務,而將研究重點放在一些細枝末節上,造成了研究資源的極大浪費。為了有效整頓哲學研究,保證哲學研究的科學性和時效性,文德爾班對世界進行了重新劃分與歸類,它將世界劃分為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其中,事實世界是科學研究和其他門類科學研究的對象和重點,而價值世界則是哲學研究的重點領域,必須予以足夠重視。只有這樣,哲學才能重新煥發出其生機和活力,更好地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其學生李凱爾德在繼承其哲學理論學說的基礎上,將價值范疇作為其哲學研究的根本范疇進行分析與研究,這標志著價值哲學的創立與形成。
2 西方價值論的主要觀點
隨著西方價值哲學的不斷發展成熟,各派哲學家立足于其哲學理論的發展實際,提出了各自的主要觀點,并形成了較為系統完善的理論研究體系。各派別雖然研究的領域和方法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價值論,即主觀價值論、客觀價值論、過程價值論。
其中,主觀價值論的代表人物有文德爾班、美國的培里、奧地利的邁農、實用主義理論的先驅詹姆斯等。他們在進行價值論研究時,以主體需求為出發點,要求其研究必須符合主體的情感意志和道德追求,并根據其興趣所在去理解和闡釋價值的本質構成。
美國的培里是新實在哲學的代表者,他同樣認可主觀價值論觀點,要求將價值或善作為倫理學研究的出發點和目標,進行有計劃、有重點、有針對性的研究。他還認為價值是欲望依附性的一種本質表現與外在特征。在他看來,價值是興趣的集中反映,判斷一個事物是否具有價值,只要看它能夠引起人的興趣即可。一般地,越是有價值的東西就越能引起人的興趣,而無法引起人興趣的事物自然也就不具有價值。
杜威是實用主義價值論的代表,他認為價值是必然存在的,但要想對其直接定義則具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對價值定義的過程也是一個反省的過程,反省就必然會進行評價。在評價過程中,缺乏經驗的研究者常常會將評價與定義混為一談,從而無法準確定義價值。因此,為進一步明確價值的基本內涵,做到科學準確地定義,研究者必須根據事情的最終結果和內在性質進行定義和研究,更加注重研究的實際效果,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真理觀的體現。
薩特是存在主義價值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要求在進行價值論研究時應該將價值與存在聯系起來,進行對比性研究,深入研究和把握價值與存在的內在關系,認識即存在。他認為自我存在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必須不斷完善和整合,更好地追求其意識存在。他的存在主義價值論是由人的價值選擇所決定的,特別強調人的主觀性在價值發展中的作用。
現象學的價值論是由胡塞爾提出并發展起來的,是一種追求哲學科學性和絕對性的唯心主義學說。這一學說的形成和發展與歐洲的大陸哲學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系,它要求采用現象學的基本方法進行分析研究,以便將更好地解決價值論中的一些中心問題。舍勒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現象學的價值論,他承認價值研究的科學性,要求將這種客觀性提升到超驗性層面上來,學說帶有明顯的神秘主義和唯心主義痕跡。
第9篇:哲學的基本范疇范文
關鍵詞:過程哲學,價值與事實,無主體狀態,平面化靜態視角,社會個體生成論
“事實”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不僅從表面上看表現為強調價值的中國哲學與強調事實的西方哲學之間的差異[1],從學理上表現為有關西方哲學如何從“事實”出發推論出“價值”的問題,同時就作為當代西方哲學發展縮影[2]的懷特海過程哲學而言,也表現為如何使過程哲學的研究視角從靜態發展到動態、從對“過程”的平面化靜態描述發展到對“生成”的立體性動態描述、從竭力把“價值”客觀化發展到充分重視“價值”的主觀性社會文化維度[3]。
形象地說,懷特海的過程哲學就像一只正在蛻皮的蟬——在沒有完成這個蛻皮過程之前,它只能在平面上進行相應的觀察和研究論述,而只有完成了這樣的蛻皮過程,它才有可能“展翅高飛”,以更加廣闊的動態視角去考察和研究同樣廣闊的動態性研究對象,從而得出真正符合實際的結論。我認為,只有運用社會個體生成論[4]的研究立場和方法論視角,進行充分重視作為社會個體的主體的過程哲學研究,這只蟬才可能徹底蛻去它最后的硬殼而飛翔起來。
一、蟬與懷特海過程哲學的“破”與“立”
眾所周知,就一只蟬的完整生命歷程而言,它雖然命中注定會蛻掉最后束縛自己的那一層硬殼,擺脫只能平面爬行的狀態而飛翔起來,但在完成這個蛻皮過程之前,它的活動范圍基本上是平面的——也就是說,它只能在二維空間中爬到哪里算哪里;而且,這種生存狀態決定了它的視角的平面性,使它的感覺具有濃厚的“靜止”和“孤立”色彩[5]。而當它飛翔起來以后,它的生存狀態和視角顯然就完全是另一種境界了。我認為,作為西方哲學在20世紀發展縮影的懷特海過程哲學,與這種正在蛻皮的蟬有很多相似之處。為什么呢?
和西方歷史上任何一位哲學家一樣,懷特海創立的過程哲學不僅本身有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也體現了“不破不立”的基本傾向。就“破”的方面而言,他的批判矛頭主要針對的是分析哲學、心理主義、亞里士多德的主詞-謂詞分離學說、休謨的“孤立的簡單印象”學說,以及康德的“先驗圖式”論等[6]。而他之所以對這些學說提出批判,主要目的在于從根本上徹底消除西方哲學自古希臘以來一直存在的主體與客體、事實與價值分裂對立的困境——也就是說,他試圖通過徹底解決西方哲學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有關本體與現象、一與多、動與靜、永恒與流變、存在與生成、心與物、決定論與意志自由等形而上問題,以價值觀念為核心、以論述帶有生成色彩的[7]“過程”為手段,建構能夠融合英美語言分析哲學和歐陸思辨哲學這兩大陣營的過程哲學體系。
如果我們不滿足于國內曾經流行的、用所謂“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樣的標簽為懷特海所批判的這些學說定性的做法,而是進一步深入考察那些提出和擁護它們的(作為現實的社會個體而存在的)哲學家個體的主觀視角,我們似乎就可以看到,這些哲學家的學術研究視角與尚未完全蛻皮的蟬的視角確實具有相似之處[8],而懷特海的做法則似乎體現了蟬的這個蛻皮趨勢——努力擺脫原來僵硬刻板的主體-客體區分及其理論框架,通過論述“過程”打破原來非常僵硬的分裂對立狀態,并通過論述“價值”使上述所有這些分裂對立的方面能夠綜合、甚至能夠融合起來。
顯然,懷特海為自己確定的這個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它不僅意味著從“破”的角度徹底顛覆西方哲學自有史以來形成的各種各樣的哲學理論及其傳統,而且意味著要從“立”的方面建立起真正揚棄了這些理論、解決了它們的根本問題的哲學理論。那么,懷特海所“立”的是什么?他的基本愿望實現了嗎?
懷特海自己提出的哲學定義是:“哲學就是由關于它自己當初的主體性僭越的意識進行的自我修正”[9];而作為一個哲學家則應當“在存在的個體性和相關性之間保持平衡”[10]。就這種定義和要求而言,前者在顯示懷特海基本哲學觀強調對主體性僭越的批判反思意識的同時,表明了他試圖通過論述“過程”突破以往僵化的主體-客體框架的基本意向;而后者則以所謂“保持平衡”暴露了這種嘗試所具有的平面化傾向——因為我們即使僅僅就字面意思而言也可以看出,“保持平衡”的前提是承認有關的兩者的存在及其現狀,亦即認為它們存在于同一個時空階段、同一個層次或者平面之上,而不是在分別對兩者進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的基礎上,通過揚棄它們而取得突破性進展(亦即在此基礎上形成哲學理論和研究本身的生成過程),進而建立確實技高一籌的哲學體系。
另外,無論是出于強調糾正“主體性僭越”而矯枉過正,還是由于從根本上懼怕和回避主體的主觀性和任意性,懷特海在這里實際上都完全把自己的立足點放在追求純粹的客觀性上了[11],因而沒有給作為現實主體的社會個體留下存在的余地,更不用說對這種主體的主觀性精神境界在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之中的生成過程進行研究論述了。而這樣一來,他實際上就忽視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所有哲學家的論述基礎,因為這樣的論述基礎恰恰就是這種主體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以及他(她)的主觀性精神境界在這種傳統和環境之中的生成過程。
毋庸贅言,僅僅從懷特海對哲學的定義和哲學家應當做什么的論述出發,就肯定他的哲學是“一只正在蛻皮的蟬”,確實有論據不足之感。我們下面再結合他對過程哲學的說明,看一看實際情況究竟如何。
二、對過程哲學的說明的無主體狀態和平面化靜態視角
在《過程與實在》這部名著之中,懷特海對其過程哲學提出了二十七個范疇說明[12]。我認為,這些說明不僅比較直接地表現了他的過程哲學觀所包含的基本要點,同時也反映了這些要點所具有的無主體狀態和平面化靜態視角特征。
這里需要加以說明的是,這里所謂的“無主體狀態”并不是說懷特海這些論述不是以作為研究主體的他自己為前提,而是說他不僅由于竭力追求純粹的客觀性而把這樣的前提徹底隱藏起來,沒有加以任何論述,而且,即使在涉及作為其研究對象的各種主觀方面的時候,也把這些方面視為像客觀對象一樣[13]、與客觀對象毫無差別的靜態的東西,而加以“千人一面”式的論述。而所謂“平面化靜態視角”則是說,由于沒有涉及作為研究者的哲學家的論述所特有的主觀視角,更沒有涉及這種主觀視角的生成和變化過程,所以,這些說明都是以哲學家現成的靜態視角為依據的;而這樣一來,這樣的視角便由于追求共時性抽象依據的基本傾向而具有了平面化的特征。
因此,所有這些論述類型都是依據一位追求純粹客觀描述的哲學家的眼光表達出來的,既沒有涉及研究主體自己的視角是不是具有主觀性和動態性(即生成性)的問題,也沒有涉及作為其研究對象的主體諸方面是不是具有主觀性和動態性(亦即生成性)的問題,更不用說從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環境角度加以研究論述了。讓我們通過以下經過分類的范疇,具體看一看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
通過對懷特海這二十七個范疇說明進行未必完全適當的分類[14],我們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七類范疇說明:
第一類:關于存在物的基本類型——永恒客體(eternal object)和實際存在物(actual entities),實際存在物的功能、統一性和多樣性,以及實際存在物的“直接性”、“主體”與生成過程的關系(范疇v,xix,xx,xxi,xxii,xxiii等)[15];在這里,懷特海主要是對實際存在物的各個方面進行定義、描述和解釋,因此,這里并不存在對現實的個體性社會主體及其的精神世界的任何說明,更不用說涉及這種世界的社會維度和文化維度了。
第二類:關于世界和實際存在物作為造物都是過程、亦即都是生成過程,實際存在物的生成方式決定它們是什么(過程原理),以及有關它們的描述及其理由(范疇i, ix, xiv, viii,xviii)[16]。在這里,懷特海雖然強調了世界及其各種實際存在物都是過程或者生成過程,卻沒有(哪怕是非常簡略地)論及作為實際社會個體的現實主體是不是也包含在這樣的世界之中、也屬于這樣的實際存在物,他們在何種意義和層次上能夠成為這樣的過程、這樣的實際存在物,以及究竟處在何種生成層次之上的認識主體才能形成這樣的認識。
第三類:有關實際存在物的潛能與現實的關系(相對性原理),潛能及其與合生(concrescence)和永恒客體的關系(范疇iv,ii,vi,vii,x等)[17]。處于現實的社會世界之中的社會個體,也具有與這些實際存在物完全相同的潛能和現實性嗎?也許是。但是懷特海在這里同樣沒有做出任何有關的說明。所以我認為,他在這里的論述體現了與論述上面兩類范疇一樣的特征。
第四類:對于統一性、多樣性和客觀化的論述(范疇xvi,xxiv)[18]。就懷特海在這里所涉及的統一性和多樣性而言,究竟哪一種作為現實主體的社會個體能夠像懷特海本人這樣,做出有關某種統一性或者多樣性的陳述呢?一個兒童或者門外漢能夠這樣做嗎?而且,關于這里所論述的實際存在物的自我創造過程,現實的社會個體也同樣具有這樣的自我創造過程嗎?即使答案是肯定的,自我創造過程這個術語本身也表明,懷特海忽視了社會個體的創造過程所必然具有的社會維度和文化維度。
第五類:結合實際存在物的生成過程論述“攝入”(prehesion)及其構成和種類,由此轉入對于各種主觀方面的論述(范疇iii,xi,xii)[19]。我們在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懷特海是以和他描述客觀對象的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轉入對主體“攝入”的各個方面的描述的;而且,盡管主體這些有關方面在這里出現了,但主體卻同樣是靜態的、平面化的,基本上可以說沒有任何關于其生成過程的說明。
第六類:結合論述命題和包括情感、估價在內的各種主觀形式,繼而論述“感受”(feeling)及其滿足(范疇xiii,xv,xvii,xxv等)[20]。應當說,懷特海雖然在這里所涉及的純粹是社會個體主觀世界的各個方面,但他仍然竭力以完全客觀的方式進行論述;因此,他在這里也同樣是在竭力避免現實主體的主觀任意性。勿庸贅言,這種研究方式對于充分重視和研究主體及其各個有關方面來說,是不可能有多少益處的。
第七類:作為某種系列的合生過程,與整合以往的攝入過程、感受最終得到滿足的關系(范疇xxvi,xxvii)[21]。我認為這里的關鍵在于,這些所謂的攝入和滿足究竟屬于什么樣的主體?在懷特海這里的說明之中不存在有關這個問題的任何答案。
可見,即使我們只把懷特海對過程哲學的這些說明作為研究個案略加分析,而不詳細引用他的其他具體論述,我們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過程哲學所具有的無主體狀態和平面化靜態視角的特征。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我們對他這二十七個說明范疇的列舉和歸類,并沒有完全按照他原來的論述順序,而是參照西方哲學傳統流行的“客觀-主觀”模式進行的。這樣做雖然有掩蓋他的批判鋒芒之嫌,但卻有助于突出展示他的做法所具有的探索性和突破性。實際上,他對這二十七個說明范疇的論述順序也同樣帶有非常明顯的探索特征——從它們之間并不存在明確的邏輯遞進順序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嚴格說來,懷特海在這里表現出來的無主體狀態和平面化靜態視角特征,是與西方哲學傳統的惟理智主義主流一脈相承的[22];但另一方面,他對“過程”和“價值”的充分強調和研究論述,又體現出了對這種主流進行批判反思和揚棄的傾向和趨勢——除了這里的有關論述以外,他在其他地方對西方現代分析哲學所犯的“完善詞典的謬誤”的論述,也同樣非常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23]。 懷特海及其過程哲學基本上處于傳統與批判揚棄傳統這兩種基本趨勢之間,所以我們說,作為西方哲學目前的生長點之一的懷特海過程哲學就像一只正在蛻皮的蟬。那么,現在的關鍵在于,究竟進行怎樣的研究立場和視角的轉變,這只蟬才能把最后一層皮蛻掉?
轉貼于 三、作為西方哲學當代生長點的過程哲學與社會個體生成論
正像我們上面已經看到的那樣,懷特海的過程哲學一方面體現了非常強烈的、對西方哲學傳統的批判揚棄意識,另一方面也表現出非常明顯的無主體狀態和平面化靜態視角特征。那么,它究竟能不能成為西方哲學在當代的生長點?它怎樣才能完成這種蛻皮過程呢?
我認為,一種哲學能不能成為它從其中產生出來的哲學傳統的生長點,主要取決于兩點:第一、它是不是已經非常清楚和充分地意識到這種傳統的優長劣短?第二、它所采取的新的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能不能使它達到徹底揚棄這種哲學傳統的目的?這兩個方面顯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前者真正成為后者的前提,后者才有可能成為前者的結果。
就我們上面對懷特海過程哲學所進行的案例分析而言,由于它在第一點上既認識到這種傳統的某些根本性的致命弱點并力求加以克服,又由于竭力追求純粹的客觀性而具有“無主體狀態”和“平面化靜態視角”的特征,所以,它雖然因為試圖通過強調研究“價值”、通過以系統全面地論述“過程”揚棄這種傳統而有可能成為這種傳統的生長點,但是,它所秉承的這種傳統之強調“客觀性”、“抽象性”和“普遍有效性”的基本傾向,卻使它根本沒有辦法徹底完成這種揚棄工作。因此我認為,懷特海的過程哲學有可能成為現代西方哲學的生長點,但是,這種可能性并沒有完全變成現實,至少在他自己那里是如此——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他的過程哲學是一只正在蛻皮的蟬。那么,能不能“蛻皮”的關鍵在哪里?
我認為,就西方哲學傳統中一直存在的“事實”與“價值”的關系而言,西方哲學的傳統立場和方法論視角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由于竭力追求純粹的客觀性而徹底忽視了活生生的主體,亦即忽視了處于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之中的社會個體的主觀世界及其生成過程——無論這種個體是進行具體實踐活動的一般人,還是進行理論探討的哲學家,情況都是如此。顯然,無視這樣的主體、特別是無視他們作為個體在具體社會活動之中的所作所為和其主觀世界因此而出現的生成過程,不僅哲學家的主觀立場、方法論視角及其生成過程會處于哲學批判反思的領域之外,作為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也會因此而出現扭曲[24]。恰恰因為西方哲學傳統的主流竭力追求抽象結論的純粹客觀性和普遍有效性,所以,從這樣得出的所謂“事實”和關于“事實”的真理出發,根本不可能走向“價值”,因而根本不可能徹底解決有關本體與現象、一與多、動與靜、永恒與流變、存在與生成、心與物、決定論與意志自由等形而上問題——因為這樣的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已經使研究者“畫地為牢”,只能固守這樣的“事實”和及其真理,而不可能對包含主觀世界諸方面的生成過程有所覺察,更不用說加以必要的反思和研究論述了。
所以,我認為,能不能完成這種“蛻皮”,關鍵在于研究過程哲學的哲學家們有沒有能力在繼承懷特海過程哲學強調“價值”、強調“過程”、強調批判揚棄主體-客體二元分裂對立狀態的成果的基礎上,真正實事求是地看待和研究現實的社會個體——也就是說,取決于這些哲學家是不是真正能夠徹底地把過程哲學強調動態生成的基本觀點,全面落實成為使有關(包括作為哲學家的研究者在內的)社會個體主觀世界諸方面的研究,得到與對于客觀世界諸方面的研究同樣的地位,從而使所有主體的主觀世界、它們的生成過程和它們的歷史文化傳統背景和社會現實環境,都在過程哲學研究領域之中得到應有的地位和重視。毋庸贅言,懷特海雖然具有把所有研究對象都納入過程哲學的研究范圍、建立系統全面的過程哲學體系的宏偉抱負,但他最終并沒有實現這種抱負。
只有用社會個體生成論的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揚棄懷特海的過程哲學的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立足于社會個體及其主觀世界的生成過程的文化維度和社會維度,對社會個體的社會行動所涉及的(包括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在內的)各個方面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作為西方哲學在20世紀發展縮影的懷特海過程哲學才有可能真正實現自己當初的抱負,像蟬最后蛻掉了自己的硬殼那樣展翅飛翔起來。
注 釋
[1] 這是一個非常抽象的說法——一般說來,側重理智分析的西方哲學主流更加強調事實,并且以獲得關于事實的“真理”知識為歸依,而側重情感體驗的中國哲學和東方哲學則更加強調主體的感受,并且以對主體的規范和隨之而來的主體精神境界為鵠的,因而基本上可以說,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強調事實與強調價值這兩種做法之間的差異。當然,這個題目需要做我們在這里根本無法進行的廣泛的實證性研究。
[2] 參見陳奎德,《懷特海過程哲學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頁及以下部分。
[3] 當代西方哲學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出現的,逐漸重視研究日常語言、繼而逐漸重視研究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諸方面的趨勢,已經向我們表明了這一點。
[4] 這里所謂的“社會個體生成論”(the social inpidual growing-up theory),是本人在以往研究西方哲學、美學理論,現象學社會學等諸方面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基本思路;它具有以下四個要點: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內的每一個現實個體,都處于某種存在于具體社會文化環境之中的生成過程之中;
第二、這種生成過程具有兩個方面:一是個體通過相關的各種社會互動過程獲得越來越多的社會角色,二是個體的主觀世界因此而達到越來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人類社會生活包括學術在內的每一個方面,都是這種生成過程的結果,是由不同的社會個體通過這種過程建構的;
第四、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所有這些方面,都必須從有關這樣的社會個體主觀世界的生成過程的視角出發進行探討。
[5]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靜止”和“孤立”是作為主體的蟬的感覺所具有的,而并不是作為它的感覺對象的外部事物所具有的特性。
[6] 參見懷特海,《過程與實在》英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1929年版,第viii頁等。
[7]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懷特海在其論述過程中確實多處談到“生成”,并且把他對于“生成”的論述當作建構其過程哲學體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來處理;但是,他的論述側重點仍然是盡可能客觀地對過程加以描述——或者說,“生成”只是他對“過程”的形象描述,并沒有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過程”的涵義。然而實際上,“過程”恰恰應當是對“生成”的形象描述,也就是說,它所包含的意義只是“生成”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只是表面上的、從平面上看到的一部分,倒是“生成”包含了更加豐富的涵義。
[8] 囿于篇幅,我們在這里不可能對此進行詳細的論述,而只能強調指出,懷特海表現出來的非常強烈的批判傾向,主要針對的就是這種把所有研究對象都孤立化、抽象化、平面化的基本傾向。
[9]參見懷特海,《過程與實在》英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1929年版,第20頁。
[10] 參見《在世哲學家文庫·懷特海的哲學》英文版,紐約圖鐸出版社,1951年版,第680頁。也可參見陳奎德,《懷特海過程哲學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3頁。
[11] 因為顯而易見,哲學家只能根據某種客觀的情況和標準,才能認識到他(她)自己當初的主體性究竟是不是具有僭越性。
[12] 參見懷特海,《過程與實在》英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1929年版,第30-35頁。
[13] 實際上,懷特海之所以以有機體作為其研究對象,就是要以這種方式把所有作為其研究對象的客觀事物和主觀世界都統一起來。
[14] 囿于篇幅,我們不可能一一詳細引用懷特海的原文,只能以這樣非常概括的方式表達他的基本觀點。
[15]參見懷特海,《過程與實在》英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1929年版,第30頁和34頁。
[16] 參見,同上引書,第30頁,32頁,31頁和33頁。
[17]參見,同上引書,第30頁、31頁。
[18]參見,同上引書,第32頁,第34-35頁。
[19]參見,同上引書,第30頁,31頁和32頁。
[20]參見,同上引書,第32頁,32-33頁,第35頁。
[21]參見,同上引書,第35頁。
[22] 就西方哲學傳統主流而言,尋求客觀性、拒斥主觀隨意性的基本傾向一直處于主導地位,而這里指出的“無主體狀態”和“平面化靜態視角”則是這種傾向的兩個具體表現。
[23] 參見懷特海,《思想方式》英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1936年版,第235頁。
相關文章閱讀
相關期刊推薦
精選范文推薦
- 1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
- 2哲學理論論文
- 3哲學與人生
- 4哲學與人生教案
- 5哲學問題論文
- 6哲學社會科學論文
- 7哲學與人生的感悟
- 8哲學和政治的關系
- 9哲學博士論文
- 10哲學思想對人生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