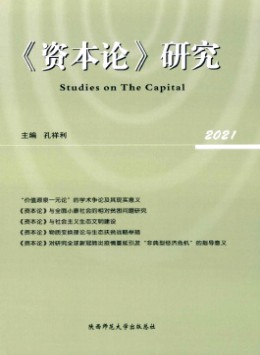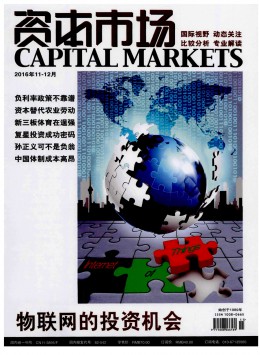資本利得稅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資本利得稅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關鍵詞】資本 資本利得 資本利得稅
一、資本利得和資本利得稅
資本利得稅是指對納稅人出售或轉讓資本性資產而實現的收益額課征的稅,常見的資本利得如買賣股票、債券和房地產等所獲得的收益。但在日本主要是指對股票、債券等金融商品收益所征收的稅。從稅種性質看,因其課稅對象為收益額,它是所得額的一種形式,所以國際上仍然將資本利得稅歸入所得稅類。因此,該稅種的目的除了籌集財政收入以外,還為了調節收入分配,實現多得者多納稅。資本利得稅可以針對所有企業與個人設計,如美國,英國等,也可以并入個人所得稅系中,如澳大利亞。
中國個人所得稅中的財產轉讓稅是指個人轉讓有價證券、股權、建筑物、土地使用權、機器設備、車船以及其他財產取得的所得。公司所得稅中也規定了對財產轉讓所得征稅的條例。因此,財產轉讓稅實際上相當于資本利得稅。在中國,資本利得稅并不是一個新稅種。
在新一輪的以簡化稅制,降低稅率,擴寬稅基為核心的稅制改革中,各國紛紛降低了所得稅的邊際稅率與累進檔次,其中資本利得稅的改革也集中體現了這一趨勢。在2006年,最大資本利得稅為5%,15%, 25% 或28%。
二、關于是否降低資本利得稅的爭議
然而目前,國際上對是否降低資本利得稅存在廣泛爭議。全球首席經濟學家Dri/Mc Graw和Allen Sinai認為資本利得稅是不公平的,意味著勤儉儲蓄的人比揮霍無度的人承擔更高的費用。這些經濟學家認為:降低資本利得稅能夠增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更加有益于中產階級,通常能夠鼓勵企業家的積極性,帶來技術突破,鼓勵儲蓄和投資等。然而,其他的經濟學家則認為資本利得稅一般能起到“多獲利者多交稅”的效果,對資本市場的貧富兩極分化能起到一定作用,同時能自發調節市場起落,對金融市場的穩定健康運行也有一定的效果。這種觀點認為降低資本利得稅將降低稅收收益,并導致資產大量出售,造成股票市場價格的下降。同時會造成財政預算赤字以及聯邦儲蓄與投資的減少。經濟的問題是缺少消費,并非缺少投資。因而降低資本利得稅并不能帶來經濟的增長。
盡管如此,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資本利得稅的改革絕對是稅制大范圍改革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對資本利得的征稅還未進行多大的改革與變化。
三、關于中外資本利得稅制的分析
1.目前,國際上比較多的采用分稅位。對不同收入的群體,不同投資期限的資產所得適用不同的稅率。美國從2003年起,長期投資的資本利得稅為15%(對于歸入最低和次低所得稅繳納人群的兩類人,資本利得稅為5%。短期投資的資本利得稅率較高,最高為28%。
在中國個人財產轉讓統一按20%的比例征收,公司財產轉讓所得按一般公司所得稅稅率計算。可見我國對資產轉讓所得實行一刀切的稅率,不同的收入者負擔相同的稅率,同時對不同投資期限的資產使用統一稅率,不利于資本利得稅的收入調節作用,以及對國內投資的調控。因此,從縱向公平角度和調控長短期投資上看,中國對資本利得征稅存在缺陷。
2.在中國,對于企業,所有的資本利得總額都被并入到企業應交所得稅計算總額中計算企業所得稅。對于個人,資本利得稅將被作為個人所得稅的最后一項來確定稅率。在個人資本利得方面,對于資本利得稅的主要來源股票轉讓收益,鑒于目前證券市場發育還不成熟,我國對個人股票轉讓收益暫不征稅。
3.各國對資本利得稅設計了各種的優惠措施,來加強本國資本利稅的競爭性,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優惠條件。這些優惠措施中最具特色的是各種豁免,減免與抵扣。
(1)各國都有各種資本利得抵扣措施,在美國如果投資損失超過了投資收益,凈損失可以被利用在一般所得稅的減免中。每年每個個人可以申報3000美元的凈投資損失,用來減免一般所得稅。剩余的投資損失還可以歸入下一年繼續用來計算下一年的資本利得凈值。企業還被允許將本年度的投資凈損失抵消上一年度投資收益,從而獲得一定的退稅。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資本損失不能抵扣其他的一般所得稅,增加了實際稅負。
(2)年減免額的規定;每年個人在出售資產時所獲得中有部分數額是可以免稅的。這一數額每年都有些變化,并不斷擴大。英國2003年個人的年免征額是£7900,而企業則不能獲得此減免。而在中國僅對個人轉讓自用5年以上住房并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個人所得稅。中國的資本利得減免只針對群體狹小,不具有一般的代表意義。
(3)各國政府均設計了各種減免措施,并允許企業與個人根據自身需要來組合各項減免政策,降低實際稅負。如為防止因通貨膨脹的指數減免措施;企業換購新的經營用資產時,可將出售的資產利得從新購置的資產原價中扣除,從而延緩當期繳稅的滾動減免措施。
中國資本利得在設計上缺乏有效的優惠措施,如在固定資產轉讓上,資本利得稅就不能發揮促進技術設備更新的作用,并使得目前中國通貨膨脹情況下,企業和個人實際負稅升高。
四、結語
在全球資本利得稅改革的浪潮下,為了增強我國的稅收競爭力,促進企業的發展,個人收入的調節,資本市場的宏觀調控。中國的資本利得稅都有進一步改革的必要。國際的資本利得稅的設計也給我們一些思考與借鑒。
參考文獻:
[1]The Impact of Capital Gains Tax Reductions on the U.S. Economy March,1997.
[2]李楚楠.資本利得稅――中國資本市場達摩克利斯之劍[J].經濟視角,2007.
第2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當我我國證券市場的交易成本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固定的、雙向征收的3.5‰傭金成本;二是固定的、雙向征收的2‰的證券交易印花稅。于是,在此種體系下,一筆交易的完成所需費用為5.5‰;與國際上傭金制度和稅收政策的變革趨勢相比較,我國證券市場交易成本明顯偏高。分析現行稅制的特點,我們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過高的交易成本損害了投資者對我國證券市場的信心,而如我們所知,證券市場是虛擬資本市場,維護投資者的信心和利益對于這個市場的穩定發展至關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競爭機制的培育;固定的高傭金制度實際上是對目前尚相當落后的證券行業的保護,不利于我國證券業的行業重組和業務創新,難以實現優勝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滯了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和難度;這不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競爭力,影響了現有企業的低成本重組,而且加速了我國資本的外逃。第四,現行稅制對交易活動本身征稅,而不論該筆交易的盈虧,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常常會起到拉大目前市場上已經十分懸殊的貧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稅收理論中的量能原則和公平原則。
與現行稅制相比較,資本利得稅的優越性是比較明顯的。
所謂資本利得稅,簡單而言就是對投資者證券買賣所獲取的價差收益(資本利得)征稅。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證券市場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極低的印花稅,代之以對資本利得征稅。在這樣的稅收體系下,一般能起到“多獲利者多交稅”的效果,對資本市場的貧富兩極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發抑制作用。不僅如此,當市場活躍時,由于獲利者的絕對數量和獲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稅收收入將隨之有一個較大的增幅,從而對正日漸升溫的市場起到持續自發“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場理性的維持和千衡發展的實現;當市場低迷時,獲利者給予數量(通常會)下降,但由于做空機制的存在,市場上仍不乏投機獲利者,此時對資本利得進行征稅,在客觀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機獲利空間、減輕(甚至免除)多方稅收負擔的作用,有利于市場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簡言之,資本利得稅體系及其內在的自發調節市場起落的機制有利于市場的穩健發展;當然,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市場也是經常起伏動蕩著的,那是因為決定市場升降趨勢的因素為數甚多,而稅收對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也有其客觀上的局限性。另外,資本利得稅制度下“多獲利者多交稅”的具體實施效果比之印花稅也更好地體現了稅收征管的量能原則和公平原則。
在我國,以資本利得稅代替印花稅作為資本市場的主體稅種,還具有特別的意義。
如我們所知,我國股票一、二級市場在實際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當大的價格差;并且一級市場資本利得收益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和單純性特點,因此單對一級市場的資本利得征稅,不但在現實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對解決目前市場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將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如果按20%的比例稅率計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漲幅在50%以上,則征收資本利得稅所得就會超過按10%籌資額減持國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現實意義是非常明顯的:通過對一級市場征收資本利得稅所獲取的新增收益補充社保基金,就可順勢降低國有股減持售價,從而為有關利益方在定價問題上達成共識創造關鍵性的條件。其合理性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其一,一、二級市場的割裂主要體現在二級市場價格水平遠高于一級市場,由此造成絕大多數新股上市都有相當可觀的漲幅,一些析股的漲幅甚至超過100%,一級市場普遍存在的這種超額收益與其所對應的風險是極不相稱的,也是非市場化取向的。從公平稅賦的角度看,應該對一級市場存在的這種低風險高收益征收資本利得稅,這有助于維護投資者財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有股暫不流通導致了兩個市場的割裂,那么對于由此在一級市場產生的超額收益,理應通過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形式來“彌補”國有股暫不流通的“損失”。在一級市場引入資本利得稅不僅是解開國有股流通難題的鑰匙,而且它將對整個資本市場的規范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首先,它實際上降低了一級市場的收益水平,對于申購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資者來說,征稅以后仍然能夠保證獲得較好的投資收益;但對于申購成本較高的融資申購來說,征稅將可能使其面臨虧損;因此,征稅將遏制融資申購行為,提高申購中簽率,從而保護一級市場投資者的利益。其次,根據所得稅制的超額累進原則,對于漲幅過大(往往是小盤股)的還可以在20%的基礎上實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擊“惡炒”小盤股的行為,加強價值型投資的市場主導地位。再次,它可以促進新股發行市場化的改革,為一、二級市場的接軌創造條件,最后,先行在一級市場試點資本利得稅可以為我國全面推行資本利得稅政策積累經驗;畢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來說新興證券市場征收印花稅,成熟的市場則以所得稅為資本市場主體稅種;免征印花稅、改征資本利得稅隨著各國證券市場的日漸成熟日益發展,將成為全球證券交易稅制演變的長期趨勢;從我國證券市場的長遠發展來看,以資本利得稅代替證券交易印花稅,也是大勢所趨。
二、我國二級市場推行資本利得稅的可行性分析
盡管單就理論分析,以資本利得稅替代印花稅作為我國證券市場(二級市場)的主體稅種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觀情況看,筆者認為立即推行這一稅收體系的替代時機尚未成熟。過去數年中,證券市場對開征資本利得稅時有議論,但最后都未能實施,2001年11月間,為扭轉股市連續數月的低迷態勢,財政部還調低了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而資本利得稅的推行則仍被排除在政府的決策選擇之外,足見政府對開征此稅的謹慎。就客觀情況看,目前在二級市場推行這一稅種存在如下困難;
1.技術方面的困難,也即“利潤確定”的困難性。是按當筆交易課征或是按當月累計交易所得課征?如果出現當期虧損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進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體的規定。同時,開征此稅需要有先進的稅務電子化系統和科學的稽查技術,才能對利潤進行及時準確的確定,而目前我國顯然還不完全具備這樣的科學技術條件。
2.就監管方面要求看,顯然對利得征稅有其合理性,但因為利得稅遠較交易印花稅復雜,核算利得困難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開來會對證券市場產生不利影響;從世界范圍來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稅的國家,均對交易的損失補償作了相應的規定,使得交易所得稅是在凈所得的基礎上進行征收,而這一環節的完善不但需要技術上的配套,同時還需要監管體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資者通過資產的轉移以規避交易所得稅。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監管機構要想做到這一步,短期內是有一定難度的。
3.開征資本利得稅必須充分估計到其對證券市場的沖擊力。我國曾于1994年底盛傳將開征證券交易稅和股票轉讓所得稅,引起軒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蕩。而同期臺灣證券市場也因擬開征資本利得稅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臺灣證券管理當局不得不宣布無限期擱置對資本利得稅的課征。因此在國內設立資本利得稅應持相當謹慎的態度,特別是在目前印花稅率本已較高的情況下,設立該稅種可能會使投資者產生增稅的印象,從而引發市場大幅振蕩。
第3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一、資本利得稅對比現行稅制的優越性分析
當我我國證券市場的交易成本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固定的、雙向征收的3.5‰傭金成本;二是固定的、雙向征收的2‰的證券交易印花稅。于是,在此種體系下,一筆交易的完成所需費用為5.5‰;與國際上傭金制度和稅收政策的變革趨勢相比較,我國證券市場交易成本明顯偏高。分析現行稅制的特點,我們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首先,過高的交易成本損害了投資者對我國證券市場的信心,而如我們所知,證券市場是虛擬資本市場,維護投資者的信心和利益對于這個市場的穩定發展至關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競爭機制的培育;固定的高傭金制度實際上是對目前尚相當落后的證券行業的保護,不利于我國證券業的行業重組和業務創新,難以實現優勝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滯了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和難度;這不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競爭力,影響了現有企業的低成本重組,而且加速了我國資本的外逃。第四,現行稅制對交易活動本身征稅,而不論該筆交易的盈虧,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常常會起到拉大目前市場上已經十分懸殊的貧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稅收理論中的量能原則和公平原則。
與現行稅制相比較,資本利得稅的優越性是比較明顯的。
所謂資本利得稅,簡單而言就是對投資者證券買賣所獲取的價差收益(資本利得)征稅。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證券市場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極低的印花稅,代之以對資本利得征稅。在這樣的稅收體系下,一般能起到“多獲利者多交稅”的效果,對資本市場的貧富兩極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發抑制作用。不僅如此,當市場活躍時,由于獲利者的絕對數量和獲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稅收收入將隨之有一個較大的增幅,從而對正日漸升溫的市場起到持續自發“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場理性的維持和千衡發展的實現;當市場低迷時,獲利者給予數量(通常會)下降,但由于做空機制的存在,市場上仍不乏投機獲利者,此時對資本利得進行征稅,在客觀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機獲利空間、減輕(甚至免除)多方稅收負擔的作用,有利于市場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簡言之,資本利得稅體系及其內在的自發調節市場起落的機制有利于市場的穩健發展;當然,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市場也是經常起伏動蕩著的,那是因為決定市場升降趨勢的因素為數甚多,而稅收對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也有其客觀上的局限性。另外,資本利得稅制度下“多獲利者多交稅”的具體實施效果比之印花稅也更好地體現了稅收征管的量能原則和公平原則。
在我國,以資本利得稅代替印花稅作為資本市場的主體稅種,還具有特別的意義。
如我們所知,我國股票一、二級市場在實際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當大的價格差;并且一級市場資本利得收益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和單純性特點,因此單對一級市場的資本利得征稅,不但在現實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對解決目前市場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將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如果按20%的比例稅率計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漲幅在50%以上,則征收資本利得稅所得就會超過按10%籌資額減持國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現實意義是非常明顯的:通過對一級市場征收資本利得稅所獲取的新增收益補充社保基金,就可順勢降低國有股減持售價,從而為有關利益方在定價問題上達成共識創造關鍵性的條件。其合理性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其一,一、二級市場的割裂主要體現在二級市場價格水平遠高于一級市場,由此造成絕大多數新股上市都有相當可觀的漲幅,一些析股的漲幅甚至超過100%,一級市場普遍存在的這種超額收益與其所對應的風險是極不相稱的,也是非市場化取向的。從公平稅賦的角度看,應該對一級市場存在的這種低風險高收益征收資本利得稅,這有助于維護投資者財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國有股暫不流通導致了兩個市場的割裂,那么對于由此在一級市場產生的超額收益,理應通過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形式來“彌補”國有股暫不流通的“損失”。在一級市場引入資本利得稅不僅是解開國有股流通難題的鑰匙,而且它將對整個資本市場的規范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首先,它實際上降低了一級市場的收益水平,對于申購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資者來說,征稅以后仍然能夠保證獲得較好的投資收益;但對于申購成本較高的融資申購來說,征稅將可能使其面臨虧損;因此,征稅將遏制融資申購行為,提高申購中簽率,從而保護一級市場投資者的利益。其次,根據所得稅制的超額累進原則,對于漲幅過大(往往是小盤股)的還可以在20%的基礎上實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擊“惡炒”小盤股的行為,加強價值型投資的市場主導地位。再次,它可以促進新股發行市場化的改革,為一、二級市場的接軌創造條件,最后,先行在一級市場試點資本利得稅可以為我國全面推行資本利得稅政策積累經驗;畢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來說新興證券市場征收印花稅,成熟的市場則以所得稅為資本市場主體稅種;免征印花稅、改征資本利得稅隨著各國證券市場的日漸成熟日益發展,將成為全球證券交易稅制演變的長期趨勢;從我國證券市場的長遠發展來看,以資本利得稅代替證券交易印花稅,也是大勢所趨。
二、我國二級市場推行資本利得稅的可行性分析
盡管單就理論分析,以資本利得稅替代印花稅作為我國證券市場(二級市場)的主體稅種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觀情況看,筆者認為立即推行這一稅收體系的替代時機尚未成熟。過去數年中,證券市場對開征資本利得稅時有議論,但最后都未能實施,2001年11月間,為扭轉股市連續數月的低迷態勢,財政部還調低了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而資本利得稅的推行則仍被排除在政府的決策選擇之外,足見政府對開征此稅的謹慎。就客觀情況看,目前在二級市場推行這一稅種存在如下困難;
1.技術方面的困難,也即“利潤確定”的困難性。是按當筆交易課征或是按當月累計交易所得課征?如果出現當期虧損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進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體的規定。同時,開征此稅需要有先進的稅務電子化系統和科學的稽查技術,才能對利潤進行及時準確的確定,而目前我國顯然還不完全具備這樣的科學技術條件。
2.就監管方面要求看,顯然對利得征稅有其合理性,但因為利得稅遠較交易印花稅復雜,核算利得困難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開來會對證券市場產生不利影響;從世界范圍來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稅的國家,均對交易的損失補償作了相應的規定,使得交易所得稅是在凈所得的基礎上進行征收,而這一環節的完善不但需要技術上的配套,同時還需要監管體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資者通過資產的轉移以規避交易所得稅。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監管機構要想做到這一步,短期內是有一定難度的。
3.開征資本利得稅必須充分估計到其對證券市場的沖擊力。我國曾于1994年底盛傳將開征證券交易稅和股票轉讓所得稅,引起軒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蕩。而同期臺灣證券市場也因擬開征資本利得稅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臺灣證券管理當局不得不宣布無限期擱置對資本利得稅的課征。因此在國內設立資本利得稅應持相當謹慎的態度,特別是在目前印花稅率本已較高的情況下,設立該稅種可能會使投資者產生增稅的印象,從而引發市場大幅振蕩。
第4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其一是美國奧巴馬政府在近期提出了要提高資本利得稅稅率的動議,可能會達至35%的水平。此前奧巴馬曾在一次講演中表示,巴菲特交的稅比自己交的還要少。雖然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稅種的比較―奧巴馬交的是單純個人收入所得稅,而巴菲特交的是資本利得稅―但這一政策建議也反映出后金融危機時代,美國政府希望借助稅收工具調整收入分配體系的意圖。
其二則是與國內PE行業此前數年間的高額盈利有關。近幾年來,國內的PE幾乎都在做Pre-IPO業務。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以Pre-IPO為目的的PE可謂賺得缽滿盆溢,但這種短期套利的PE投資策略本身也包含一些對實體經濟有害的成分。所以監管部門包括社會輿論也會認為應當對于這些負面效應進行規制。
但這種所謂“PE浮盈稅”或是某種形式的高額資本利得稅,在國內目前的環境下,實際上缺乏征收的合理性。首先,在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各國,資本利得稅本身是一種“額外”稅種。因為用于投資的資金和投資所獲利潤均是已被政府征過稅的,所以資本利得稅實際是一種“稅上稅”。而如奧巴馬政府所規劃,將這種“稅上稅”的稅率抬高至35%水平,等于是和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一級稅種持平,也是“前所未有”并引發極大爭議的。
其次,中國資本利得稅20%的稅率已處于各國同類稅種稅率的中上水平。而不同于美國,作為一個尚在成長中的新興經濟體,中國仍需要進一步提升包括PE在內的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但對資本利得征稅卻會直接阻礙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因此無論開征新的“PE浮盈稅”或是提高資本利得稅率,都違背了中國金融改革關于提高直接融資比例的基本目標。
第5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原因主要在于:
1、 即使整體上來看,A股與H股價差已經逐漸消失,但一些主要的藍籌股的A\H差價仍然存在;
2、 由于兩地資本利得稅稅收的不同,使得投資A股的投資者相比H股明顯享受了15%或16%的折價。根據香港的有關規定,法人和團體從買賣上市股票和其他上市證券獲得的利潤按16.5%征收,個人利得稅按15%征收。而投資A股則無需繳納資本利得稅。而資本利得稅是投資者應繳稅收所占比重最大的稅種。其他諸如印花稅和紅利稅率均較低,對投資者利潤的影響均沒有資本利得稅那么大。
3、 港股和A股兩地所面臨的無風險收益率的變化不同,亦會影響投資者的預期。由于香港采取的是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香港市場受美國貨幣政策影響大,受中國央行影響小。今年以來央行通過兩輪SLF注入7000億基礎貨幣,再考慮到支持房貸和接連下調正回購利率,中央定向穩增長的態度愈發明確。盡管不是過去形式上的降息與降準,卻是實質上的降息與降準。其實采取的方法雖然不是傳統性質的方法,但目的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又開始發力了。
4、 最近,隨著9月CPI回到“1”區間,創下了56個月新低,中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9月份的4.3%直落到10月16日的3.82%,降息的力度之大最近兩年罕見,降息信號明顯。相比之下,港股受美聯儲QE退出的影響,無風險收益率上升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當A股無風險利率正面臨不斷下降的前提下,A股相比港股的估值提升的可能性更大。
第6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關鍵詞:除息日套利;稅負效應;邊際投資者稅率;稅收客戶群效應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s the tax effect and tax clientele effect of Chinese stock markets during 2002 to 2007,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that price changes on ex-dividend days reflect the relative taxation of dividends and capitalgains for the “representative” investor,and there are tax clientele effect in Chinese stock markets.
Key Words:arbitrage opportunity on ex-dividend,tax effect,marginal stockholder tax rate,tax clientele effect
中圖分類號:F830.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6-0074-05
一、引言
Miller和Modigliani(1961)在無稅負或資本利得稅和紅利稅相等,及其他假設條件下得出股利無關理論。在資本利得和現金紅利利得課稅比率不同的情況下,Miller和Modigliani指出,市場將出現稅收客戶群效應,即高股利收益率(Dividend Yields)的股票將吸引股利稅負相對低的投資者,而股利稅負相對高的投資者則傾向于投資低分紅的股票。這時股利政策的制定就要考慮到公司投資者群體的稅負情況。
二級市場是否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關系到公司的股利政策是否能夠達到使得股東稅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標。如果能夠從實證數據中發現公司股利政策和邊際股東稅級的明確關系,就可以為Miller和Modigliani的理論提供一個佐證。同時,利用除息日的股價行為(除息日稅負效應)推導出公司的邊際股東所得稅率,是公司財務決策中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數據。另外,檢驗市場是否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也是對市場投資者是否理性的一個驗證。
Elton和Gruber(1970)提供了一個利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計算邊際投資者稅率,進而檢驗市場是否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的方法。在國內外股票市場上,普遍存在股權登記日股價與除息日股價之差小于每股分紅D的現象。對此Elton和Gruber認為是投資者在選擇投資或者變現一支股票時,會根據自己的稅負情況選擇在除息前還是除息后買入或賣出。這樣在達到均衡時,便可以推算出該支或者該類股票的邊際投資者稅率,從而可以驗證Miller和Modigliani提出的稅收客戶群效應。
Kalay(1982)指出,由于市場上在除息日前后套利的存在, 并不能反映某類股票投資者(區別于套利者)的稅負情況。即使 在不存在套利機會的范圍內,也不能用 的估計值來推導邊際股東的稅率。因為 是一個平均值。它可能是那些不存在套利機會范圍內的股票的值與在范圍之外的 值的均值。這樣,就包含了短期套利的交易結果和交易主體的稅負效應的混合作用。因此,邊際股東的稅率不能從除息日的股價變動中推出,除息日股價的變動不完全是由稅負效應引起的。
針對Kalay的批評,Elton和Gruber(1984)認為Kalay低估了交易成本,考慮到交易成本后,即使是市場中交易成本最低的證券經紀人也沒有可能進行短期套利,因此在除息日,不存在短期套利交易影響均衡價格的可能,均衡價格完全是稅負效應的結果。
目前A股市場這方面的研究有,毛端懿(2001)對滬市1994―1999年間的數據進行了分析,結論是:不能拒絕除息日股價相對于股權登記日股價下跌等于每股現金股利的假設;滬市不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不存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因此不能用除息日股價變動與每股股利的比值來推斷公司的邊際投資者稅率。徐麗(2004)對深市1995―2000年之間的數據進行了分析,其結論是:市場存在除息日股價的稅負效應,但是不存在因現金股利和資本利得的稅收差異而產生的稅收客戶群效應。
二、稅負效應及稅收客戶群效應的檢驗條件及檢驗方法
(一)確定A股市場是否存在除息日前后的套利機會
對投資者套利可能的檢驗:
如果一個交易成本為 、股利稅率為、資本利得稅率為 的投資者,在股權登記日買入,在除息日賣出以套利,則其將獲得 ,如果有:
即其獲利小于要付出的成本,則這種套利不可行。整理得:
如果一個交易成本為 、股利稅率為 、資本利得稅率為 的投資者,在股權登記日賣出,在除息日買入以套利,則其比一直持有相對多獲得資本利得收益 ,多交資本利得稅, 少獲得紅利收益 。如果該投資者根本沒有資本利得,即其最初的購買價高于 ,最終的出售價又低于,那么他的套利相對收益最大化,為
如果有:
則這種套利不可行。整理得:
總體的套利不可行的區間為:
其中
(二)對稅負效應和稅收客戶群效應的檢驗
如果A股市場的投資者由于交易成本的原因都無法在除息日套利,那么除息日的股價變動將取決于該股票的邊際投資者稅率,也即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
如果投資者在除息日前后賣出股票,他將面臨兩個選擇,在股權登記日賣出股票,或者在除息日賣出股票。前者,每股將獲得股權登記日的價格減去資本利得稅。后者,每股將獲得除息日價格
和每股現金股利D減去現金股利稅收,再減去資本利得稅收 。當投資者在這兩個選擇上沒有差異時,這兩種情況下的收益必然是相等的,即:
整理得:
當市場均衡時,將反映的是各種投資力量使其達到的均衡值,從此均衡值就可以推出各種投資者形成的一個邊際投資者的稅率的情況。
如果投資者決定在除息日前后買入股票,在股權登記日購買則相比除息日每股要增加現金流出
增加稅后紅利收入,減少未來的資本利得稅 。市場均衡時有:
其中,n是投資者股票預期持有期,k是風險調整后的折現率。
整理得:
當n=1時,其和(1)式是相當的。(1)式是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的已實現資本利得形式。
當投資者預期持有期足夠長,或者投資者無法確定未來是否總體上肯定會有資本利得,從而導致其不將資本利得稅納入當前考慮因素時,我們有:
這是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的未實現資本利得形式。同樣的,關于均衡值及邊際投資者稅率的分析也可以類比于這種形式。
在得出邊際投資者稅率后,可以對邊際投資者稅率和股利收益率進行相關性檢驗,如果結果顯著為正,那么稅收客戶群效應就得到驗證。
三、A股市場除息日是否存在套利機會檢驗
我們整理了2002―2007年只有現金紅利分紅的上市公司股價及分紅數據樣本。剔除分紅額很小(每股2分及以下)的數據,因為極端小的每股紅利將使得 的方差很大。剔除了2002年6月24日、2007年5月21日、2007年5月30日、2007年5月31日的數據,在這幾個交易日,由于政策的因素,市場振幅巨大,最終得到了2838個樣本數據。利用這些數據,對A股市場的除息日稅負效應、稅收客戶群效應進行實證檢驗。
國內稅收方面,個人在2005年6月12日前的現金股利所得稅率是20%,資本利得稅率為0%。2005年6月13日到2007年現金股利所得稅率是10%,資本利得稅率為0%。基金由于在收到現金紅利時已由發放企業代扣個人所得稅,而基金的投資收益無其他方面的稅收,所以基金面臨的稅負情況和個人投資者一致。一般企業所得稅情況是:特區或開發區內15%,其他地區33%,外資企業的所得稅是15%。金融企業(證券公司、保險公司)買賣股票的收益要先交營業稅(也是對資本利得的課稅),營業稅2002年為6% ,2003年以后5%。QFII的稅收在資本利得方面一直不明確,目前的實際稅負執行情況和國內基金是相同的。社保基金的稅收是最優惠的,免征所有所得稅,而且印花稅先征后返。
交易成本方面,我國投資者的交易成本主要是印花稅、證券交易經手費、證券交易監管費以及上交所方面的過戶費。基金、QFII、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沒有傭金費用。2002―2004年對應的是2‰的印花稅稅率,2005、2006年是1‰,2007年5月30日印花稅由1‰調整為3‰。經手費和監管費合計為0.1875‰,上交所的過戶費為每1000股1元。再考慮到會員的席位費和交易單元費用,交易成本比率可以認定為:印花稅+0.2‰。個人投資者稅負與基金相同,而交易成本比基金要高,基金如不能套利,個人投資者必然也不能套利,所以對個人投資者可不予考慮。一般企業的套利成本也高于證券保險等金融公司,所以也不予以考慮。
根據前面的計算方法,可以得出A股投資者的
無套利區間(見表1)。
可以看出,由于2003年進入市場的社保基金交易成本非常小,因此理論上其存在套利機會。但是另一方面,數據顯示,A股市場的除息日開盤價比除息價6年時間的均值在1.004,且統計上顯著大于1,如果1年進行100次這樣的套利,年化收益率將達到50%,這顯示社保基金并沒有進行套利。可能的原因是社保基金實行的管理人制度,其管理人的收益是占管理資金一定百分比(
其他投資者大部分情況下,由于印花稅成本的存在是無法套利的。少部分的套利機會存在,由于其不具有操作的統計基礎,也無法具體實施套利。這樣A股市場除息日均衡價格就完全是稅負效應的結果。
四、A股市場除息日稅負效應檢驗
我們先對2838個樣本數據進行計量分析。首先,檢驗除息日開盤價是否顯著異于除息價,結果如下:
作wald檢驗,發現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異于1,即除息日開盤價顯著異于除息價,且要大于除息價。其次,我們檢驗這種差異是否是由于指數當天的漲跌引起的,即檢驗“除息日開盤價=除息價+指數當日漲跌幅×除息價”是否成立。對數據作OLS估計得:
作wald檢驗,發現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異于1,無法用指數當日漲跌來解釋該差異。
可見,除息日開盤價是顯著異于除息價的,且不能用大盤的漲跌來解釋這種差異,說明市場存在除息日股價下跌小于每股分紅D的現象,即存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
下面,我們用 的值來估計邊際投資者稅率。由國內不同投資者的稅負情況,可以計算得到不同投資者的或數值(見表2)。
計算得到2002至2007各年及總體的
的統計均值及統計顯著性P值(見表3)。
從表3中可以看出,經指數調整的 數值除2005年較高外,其他年的與總體值比較接近,而且2002―2005年其值逐漸增大。也就是說,市場的邊際投資者稅率是基本穩定且在這段時期稍有下降的。
未經指數調整的 值在2007年有一個急劇的下降,但經指數調整后這個下降幅度變小。2007年由于股市處于一個單邊上漲期,導致對
的數值影響很大,因此2007年統計值的急劇下跌是一種偶然現象。
綜上,由于 顯著不為0并且小于等于1,A股市場在這一段時間存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通過表2和表3的對比可以看出,在總體上整個市場的邊際投資者稅率為33%。當然,這個總體的邊際投資者稅率對于單個公司沒有意義,單一公司應根據自己或和自己分紅收益率接近的公司除息日股價數據計算其邊際投資者稅率。
五、稅收客戶群效應的檢驗
我們將數據按照D/P數值從小到大分成10組(見表4),計算每組的均值,用spearman相關分析檢驗是否隨著D/P的增加,也相應增加。如果正相關性存在,則意味著高的D/P對應著低的 ,即市場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
對總體數據的D/P均值與均值作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745,P值為0.013。
另外對2002―2003年的D/P均值與 均值做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709,P值為0.022。對2004―2005年的D/P均值與
均值做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103,P值為0.777。剔除 方差最大的一組數據后的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517,P值為0.154。對2006―2007年的D/P均值與均值做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430,P值為0.214。剔除 方差最大的一組數據后的spearman相關分析得:相關系數為0.867,P值為0.002。
從結果可以看出,分別剔除了2004―2005年、2006―2007年的一組異常數據后(這兩組數據都是分紅很小而導致方差很大的數據),總體上和分階段的D/P與 都是顯著正相關的,說明A股市場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市場上不同類的投資者對股票分紅偏好不同,紅利稅相對低的投資者偏好高股利收益率的股票,資本利得稅相對低的投資者更傾向于獲得資本利得。與前面已有的關于國內市場的研究對照,可以看出,經過國內證券市場的逐步發展,投資者逐漸趨于理性,傾向于投資高分紅股票的投資群體逐步形成。
六、結論
由于市場交易成本的存在,A股市場除社保基金外,其他各類投資者不存在除息日套利的可能。除息日股價相對于股權登記日的下跌顯著小于每股分紅,A股市場存在除息日股價變動的稅負效應。由此可以推算每類股票的邊際投資者稅率,從而作為公司財務決策的一個參考依據。D/P與 都是顯著正相關的,說明A股市場存在稅收客戶群效應。A股市場不同稅負的投資者對不同分紅的股票具有偏好,因此股利政策對上市公司股票價值具有影響,上市公司需要制定合適的股利政策最大化其公司價值。與國內較早的研究結果相比,說明隨著國內證券市場的發展,投資者更趨于理性。另外,由于存在重視上市公司分紅的投資者群體,目前監管層提高對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的要求,對這一群體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毛端懿.滬市除息日股價變動的實證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2,(1)。
[2]徐麗.我國股票市場除息日股價行為的實證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
[3]Avner.Kalay, 1982, “The Ex-Dividend Day Behavior of Stock Pric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lientele Effec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37, No. 4 (Sep., 1982).
第7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1、跨國、跨地區、跨行業購并的稅收抵免
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之間均存在著稅收差異,這為企業購并的稅收籌劃提供了機會。如在跨國購并中,若購并企業與目標企業的經營是縱向聯系的,通過購并,一方面可達到加強各生產環節的配合,進行大協作生產的目的;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產品和勞務的轉讓定價,即高稅國一方降低對低稅國一方的轉讓價格,或低稅國一方抬高對高稅國一方的轉讓價格,實現納稅利潤由高稅國向低稅國的轉移,以達到減少集團總體稅負的目的。又如為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我國稅法規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從事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可以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我國對在經濟特區注冊經營的企業也實行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政策。這時可選擇能享受這些稅收優惠政策的企業作為購并的目標企業,從而獲得稅收減免。
2、經營虧損的稅收抵免
我國稅法規定:“納稅企業發生年度虧損的,可以用下一納稅年度的所得彌補,下一納稅年度所得不足彌補的,可以逐年延續彌補,但延續期限最長不超過五年。”對于有效高盈利水平且發展穩定的企業,可以選擇一家近年有大量經營凈虧損的企業為目標企業,通過購并使企業盈利與目標企業虧損相互抵消,獲得所得稅減免的利益。有時這還是某些企業實施購并行為的主要目的。但這類購并中,購并企業還必須充分預計虧損的目標企業將帶來的負面影響,如購并后企業整體效益滑坡可能導致股價下跌,股東財富受損,購并企業還需花費大量資金對虧損企業進行整合改造等。因此,如果虧損企業沒有其他方面可利用的價值,純粹的稅收抵免購并是不足取的。
3、債務融資的稅收抵免
購并企業通常需要籌措大量的資金來實施購并,其融資方式主要有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我國稅法規定:債務融資利息允許在稅前列支,而股權融資股息只能在稅后列支。為此,購并企業可以大量采用債務融資,以充分利用其利息抵免稅收的效用,在整體上降低企業的所得稅費用。但購并企業同時也必須考慮因大量債務融資給企業資本結構帶來的影響。如果購并企業原來的負債比率較低,通過債務融資適當提高負債比率是可行的;如果購并企業原來的負債比率比較高,繼續采取債務融資可能導致加權平均資金成本上升、財務狀況急劇惡化、破產風險增大等負面影響。此時,更好的融資方式也許是股權融資,或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并用,以保持良好的資本結構。
4、固定資產折舊的稅收抵免
企業通過購并取得了目標企業的固定資產。企業會計制度規定,固定資產應按其取得時的成本作為入賬價值,該歷史成本也是計提折舊的依據。企業購并時若固定資產重估的市場價值高于原賬面價值,購并企業以市場價值購入時則可按購入價值入賬。就同一項固定資產而言,購并企業計提的年折舊額將高于目標企業的年折舊額,故而可獲得增加的折舊成本的稅收抵免。但固定資產折舊的稅收抵免并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可獲得的。稅法規定:只有當接受的固定資產中隱含的增值或損失已經確認實現,才能按經確認評估的價值確定有關固定資產的計稅成本,否則,只能以固定資產在原企業的賬面凈值為基礎確定,即購并企業若是以股票換入的固定資產,則無法獲得該項稅收抵免。此外,如果目標企業使用加速折舊法,由于前期多提折舊使后期多形成的收益將被視為普通收益繳納所得稅,購并企業反而因后期少提折舊而增加稅負。
5、將經營收益轉化為資本利得的稅收抵免
大多數國家規定的股利所得稅要高于資本利得稅。有些企業的股東為避免繳納高額的股利所得稅而傾向于少分紅、多留存,企業保留了較多的盈余。通過購并,目標企業的保留盈余在股價中得到了補償,這部分經營收益即轉化為股東的資本利得,目標企業股東只需繳納資本利得稅,而免除了更高的股利所得稅。
二、企業購并出資方式的稅收籌劃
企業購并可以通過各種出資方式來實現,主要有現金收購、股票收購和綜合證券收購。它們給企業稅收帶來不同的影響。
1、現金收購
現金收購是企業購并活動中最簡單而又最迅速的一種出資方式。現金收購對企業稅負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①購并企業可享受到目標企業固定資產重估增值的折舊的稅收抵免;
②目標企業股東必須迅速確認因此獲得的資本收益并繳納資本利得稅,但如果采取分期支付現金的方式,既可以減輕購并企業一次性支付大量現金的負擔,也可以使目標企業股東獲得延期支付資本利得稅的好處;③目標企業的凈經營虧損將消失,任何相關方都無法獲得其稅收抵免。
2、股票收購
股票收購是購并企業以新發行的股票替換目標企業的股票或資產的出資方式。主要類型有吸收合并與新設合并、相互持股合并和股票換資產合并等。股票收購在購并活動中不發生任何稅費支出,但會影響企業將來的稅負。
①目標企業股東不需要立刻確認因換股所形成的資本收益,直到他們出售股票時才確認并繳納資本利得稅,即獲得了延期納稅的好處。
②股票收購的具體類型不同,適用的會計處理方法也不同,如采用權益匯總法和購買法對購并資產的確認、市場價值與賬面價值差額等的處理就有不同的規定,對購并后企業整體納稅情況也將帶來不同的影響。
③股票收購后,目標企業若是以購并企業的子公司形式存續,母子公司的所得稅是分開計算繳納的,子公司的經營凈虧損不能給母公司帶來稅收抵免;目標企業若是清償后成為購并企業的分公司,購并企業才可以獲得目標企業經營凈虧損的稅收抵免。但目標企業的清償將被迫收回過多的折舊及帶來其他不利的稅務后果。
④購并企業不能享受目標企業固定資產重估增值的折舊的稅收抵免。
3.綜合證券收購
綜合證券收購是以現金、股票、認股權證、可轉換債券等多種形式證券組合出資購買。其中采用可轉換債券收購對企業稅負的影響除與上述現金收購類似外,還有:
①可轉換債券在轉換前的利息支出可抵免所得稅;
第8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一、上市公司之間及上市公司內部各股東的平等稅收權力問題
平等負稅是稅收的一個基本原則,對股份制企業也不例外,但我國的股份制在平等負稅方面上還有許多問題亟待完善,主要表現在上市公司之間和上市公司各股東之間的稅負不盡公平合理。
無論是從公司平等競爭還是從稅法的嚴肅性來看,對股份制企業都要求統一稅制。但股份制企業實際執行中卻存在很大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1)實行新稅制后,已批準的在香港上市的股份制企業繼續執行15%的所得稅率。(2)各省市的滬深兩地的上市公司,除了少數執行統一的33%的法定稅率以外,許多省市出于地方本位利益考慮,為增強地方企業在股票市場上的競爭力,經省市人民政府批準,所得稅率有的按24%執行,既不統一,又不公平。(3)特區企業與內地企業在所得稅上存在較大差異,影響了內地股份制公司的競爭力。
這種不規范不公平的做法,其實質就是對上市公司實行稅收優惠,這一做法造成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1)一般來講,能夠允許上市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的生產規模和良好的經營管理基礎,而且在該公司股票發行、上市中,又可募集到一大筆資金,這樣的企業理應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如果一上市就較大幅度地減免所得稅收,勢必造成大幅度地減少國家財政收入。這種以減少國家財政收入為代價來換取企業內部轉機建制,可能使得受惠企業缺乏加強經營管理和提高效率的內在壓力,既不一定能真正促使企業實現轉機建制,又使得我國本來就十分困難的財政雪上加霜,擴大財政風險。(2)對上市公司大幅度地減免稅,對于非上市企業是一個極不公平的因子,上市企業原有的良好經營基礎和上市過程中吸收的大筆社會資金已為其提供了市場競爭中極大的優勢,這已是其他非上市企業望塵莫及的,加之稅收上的優惠,使非上市企業在競爭中的處境更加難堪。特別是在同一行業中,國家對企業上市有一個行業分布的選擇,同行業中,效益良好的企業未必都能上市,那么不能上市的企業實際上很難得到平等競爭的外部條件。因此,我們要執行規范統一的法人所得稅,改變上市公司與非上市公司之間以及各上市公司之間的企業所得稅不一致的局面,要求它們承擔相同的稅負,執行統一的33%的所得稅率,中央政府應統一掌握企業所得稅的減免,對省市級地方政府在企業所得稅減免問題上嚴格控制,只有這樣才能嚴肅稅法,進而促進股市的正常發展和公司之間的公平競爭。
稅收權力不平等的另一個方面則是股份企業的國家股、法人股和個人股的負稅要求不盡一致,對國家股、法人股的股利所得不征稅。這種只對個人股征稅的做法既違背了公平負稅的準則,也不符合“同股同利”的原則并且不利于國有股權的實現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目前,不少股份企業通過不公平的分配股利方案,侵占國有股,造成國有資產的隱性流失;同時還通過不規范的折股手段將國有資產增值部分計入資本公積金,使之成為全體股東享有的權益,導致國有資產被蠶蝕,其原因之一就是國家股的股東“缺位”。如果對國家股、法人股的股利也征稅,從而事實上把國家股作為國家所有的股權,這將有利于國有股權的實現和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為此,應根據稅收公平原則和股權平等的要求,所有因持有股份而獲得收益的股東,不論其本身是國家、法人還是自然人,他們的股利所得課征相同的稅收,并都由股份制企業代扣、代繳,實行源泉控制。也許有人會問,對國家股獲得的股息征稅不是國家自己征自己的稅嗎?就如把錢從自己的“左口袋”拿出又放進“右口袋”,這有必要嗎?其實這樣做在目前是非常有益的,有助于稅務部門代表國家行使對股份公司的利息分配的監督權,防止股份制企業通過少分或不分國家股息而造成國有資產和稅源的隱性流失,從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從更深遠的意義上看,對包括國家股、法人股在內的所有股東征收股息所得稅,有助于通過利益來驅動國家盡快形成一個實實在在的法人代表,并把國家股東、法人股東和個人股東擺在平等的法人地位上,在此基礎上促進國有股上市流通。國有股上市流通有利于削弱政府對資源的直接行政控制,有利于企業借助市場打破部門、地方行政隸屬關系,促使資源能夠真正合理流動起來,改變國有股的凝固狀況,并以此優化經濟結構,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二、證券交易過程中的稅收問題
目前我國在證券交易過程中征收的是印花稅,但問題較多,一是現行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實際上是就交易行為課征,與印花稅的名稱不符,理論依據不充分,法律上講不嚴謹,比較勉強;二是經濟學上的“馬太效應”所昭示的窮者愈窮,富者愈富的原理在股票市場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一般來說,機構、大戶容易獲利,這是小投資者所無可比擬的。但目前為股票交易行為設計的印花稅是不論交易數額大小,持券期限長短一律按同一比例對雙方征收的比例稅率,它雖然對控制股票交易頻率可發揮一定作用,但對于國家重點調控的資金大戶對股票市場的操縱現象卻無能為力,也不能采取免稅額度方式給中小投資者以適當的優惠,難以實現相對公平,對調節收入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這顯然是有悖于印花稅的設計初衷。
對證券交易行為的征稅方式改革已勢在必然。為了鼓勵投資、減少投機,應以證券交易稅取代目前的印花稅,但考慮到中國新舊稅制銜接以及兼顧兩家交易所所在地的地方利益,在目前情況下最適當的選擇是印花稅和證券交易稅兼征。不過,印花稅只對一級市場股票發行時訂立的產權轉移書據或合同課稅以改變目前對一級市場不征流轉稅的狀況,以調節一級市場股票發行價格,縮小一、二級市場的利益差距,也可以為國家獲得一筆財政收入。證券交易稅是對證券二級市場“零售”環節征收的流轉稅,而且規定只對賣方征收,借鑒國外對證券交易行為課稅的具體經驗,稅率不宜太高,最好不要超過5‰,在具體的實施措施上要明確持股時間長短與稅率差別的數量關系。另外,為了避免稅源流失,納稅方式應以“源泉扣除課稅”為主。考慮到國債在我國經濟發展和證券交易市場中的特殊地位,對國債轉讓收入宜從輕課稅。
三、證券投資收益分配過程中的稅收問題
我國證券收益分配中的稅收問題主要有二,一是缺乏避免對公司和股東個人股息紅利的重復課稅的機制;二是對證券交易的凈收益及資本利得的稅務處理不明確。
股息紅利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凈所得,稅后利潤在股東之間分配就成為股息。而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將企業獲得的股利作為企業所得一并征稅,我國《個人所得稅法》則規定個人取得股利、紅利所得應納20%的個人所得稅,不作任何扣除。這樣做雖然有利于加強控制稅源、擴大稅基,但毫無疑問形成了重復征稅,增加了股份公司的額外稅負。對股份公司的利潤和分派股息分別課征是不合情理的,它實際上是對股息收入的一種歧視性待遇,有悖于稅收的公平原則,也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我國現行的稅法將股份公司獲得的股利作為企業所得稅一并征稅,而股東在取得股息時還要繳納一次個人所得稅,形成了重復征稅,這在稅收理論上是說不過去的。為此,我們要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引入避免對股利雙重征稅機制。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在力爭避免重復征稅,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借鑒。西方發達國家主要采取兩種方式來消除或緩解重復征稅:(1)扣除制或雙率稅制。扣除制的做法是允許公司從稅收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比如美國為了減輕重復征收所得稅,就規定股東一年取得的第一個200美元股息可以免征所得稅。雙率稅制又稱為分率制,即對公司分配股息按低稅率征稅,對留存收益按高稅率征稅。這樣做也可以部分地減輕重復課稅,但公司的額外負擔并未觸及,故很少使用。(2)抵免稅和免稅制。抵免制的核心是通過將公司繳納的部分或全部稅款歸屬給股東所得股息中去,以抵免股東的個人所得稅。這一方法為西方大多數國家所采用。免征制是指股東個人所得的股息收入不作為個人一項所得,免除繳納個人所得稅,如希臘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都使用這一做法,它比較徹底地消除重復課稅。
隨著股份公司和證券市場的完善和發展,我國消除證券市場上股息重復課稅的問題也理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筆者認為,在我國比較理想的選擇是采用抵免制和扣除制。因為這種做法既能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能比較徹底地消除重復課稅,還與國家常規做法接軌,免稅制雖然可以徹底消除股息重復課稅問題,但是必然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流失,這在我國當前財政容易拮據的情況下不宜使用。由于股息相對穩定,確定其避免重復征稅的方法相對簡單。比如我們也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對個人股東取得的第一個200元實行免稅而對超過200元的股息按部分抵免制征收個人所得稅。這樣做既照顧了小投資者的利益,又方便了稅收征管,保證重點稅源不流失、不遺漏。
第9篇:資本利得稅范文
【關鍵詞】股利政策;除息日;追隨者效應;現金股利稅;市場微觀結構
1.引言
“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Clientele Effect)”是指當市場均衡時,投資者傾向于持有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司股票,即高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將吸引一群追隨者(邊際稅率低的投資者),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將吸引另一群追隨者(邊際稅率高的投資者);不同的股利政策會導致稅收導向的追隨者效應(Miller和Modigliani,1961)。根據“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由于在資本利得上的稅收優惠(相對低甚至為零的資本利得稅率和資本利得稅的可延緩交納),所以邊際稅率高的投資者往往偏好股利支付率低的股票。自Elton和Gruber(1970)首次對“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進行實證檢驗以來,“超過100篇的文章出現在財務經濟學頂尖期刊上檢驗除權除息日股價下跌幅度是否低于股利,如果是,這個現象是否緣于稅差效應(Elton,et al.,2005)”。
遺憾的是,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大部分文獻主要進行股利信號假說和股利成本的檢驗,對稅收這一制度變量缺乏必要的考慮。國內財務學研究主要追蹤國外當時的研究熱點,忽視了傳統經典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關研究缺乏對早期文獻涉及因素的考慮,后續研究結論恐難令人信服。本文旨在對國外相關理論進行比較系統的綜述,以期對展開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與稅收二者關系的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2.“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的證實
股價下跌幅度小于股利水平,這一除息日價格行為被眾多財務學家所證實。相當一部分研究從各個角度(不同國家、投資者賬戶數據或公開數據)利用各種天然純凈研究情景支持“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
早在Miller和Modigliani(1961)之前,Campbell和Beranek(1955)已注意到除息日股價跌落幅度小于股利額度,他們率先以399次分紅事件為樣本研究表明,除息日股價跌落幅度只有股利水平的90%;而Durand和May(1960)以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為個案分析表明,除息日股價跌落幅度約當于股利,即使兩者有差距也是微乎其微。
Elton和Gruber(1970)一文旨在通過除息日股價行為測算股東邊際稅率,指出早期的研究并未進行統計顯著性檢驗,并對除息日股價變化和股利的關系進行了正式的數學建模并實證檢驗。Elton和Gruber(1970)認為,市場處于均衡時,除權除息日股票的價格變動必須使股票買方和賣方無論是除權除息日之前或之后買賣股票都是無差別的(在邊際意義上)。他們通過對1996年4月1日至1967年3月31日所有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為樣本統計分析得出,除息日股價跌落幅度大約等于0.78倍的現金股利。
Elton和Gruber(1970)是第一份檢驗股利追隨者效應的實證研究。他們通過股利收益率和股利支付率兩個標準對樣本進行分組發現,股利收益率或者股利支付率與除息日股價跌落幅度顯著成正相關,這表明高股利收益率或者高股利支付率股票,其投資者處于低稅負等級,證實了Miller和Modigliani(1961)提出的“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
此后的大批文獻都試圖尋找各種純凈的研究場所證實“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比如,Barclay(1987)巧妙地通過比較美國引入個人所得稅前后的除息日價格行為,實證結果支持稅收追隨者效應。又如,Eades et al.(1984)不僅研究現金股利(現金股利稅大于資本利得稅)的股票,還研究優先股(現金股利稅低于資本利得稅)、進行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現金股利稅等于資本利得稅)的股票后發現,這些類型的分紅事件在除息日附近均存在異常報酬率,除稅收可以部分解釋現金股利事件除息日的超常報酬率外,日歷效應、股利公告效應、零交易效應以及證券收益的非正態性均不能解釋這種除息日異象。
不同于以往主要研究除息日的股票價格行為,Lakonishok和Vermaelen(1986)通過觀察除息日附近的交易活動來檢驗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Lakonishok和Vermaelen(1986)基于交易量視角來研究的理由有三。第一,Elton和Gruber(1970)假設相同稅差等級的投資者持有相似股利收益率的股票,那么不同稅差等級的投資者映射著不同股利收益率的股票,所以除息日附近不應該有超常交易量出現。但是,由于稅收原因,想快速變現且處于高稅差等級的投資者會在除息日前出手;反之,想購買且處于高稅差等級的投資者會在除息日后買入。第二,現實中各種各樣的股利收益率很難與稅差等級一一對應完美匹配。第三,如同Kalay(1982)指出的,并非所有投資者都是因為股利緣故才考慮買賣股票。因此,Lakonishok和Vermaelen(1986)證實除息日附近交易量明顯增加,尤其是協議傭金制度引入后和對高股利收益率的股票尤其如此,表明至少出于稅收緣故短期交易者對除息日股價有一定影響。
3.“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的駁斥
幾乎所有的財務學現象都會有支持或者反駁的雙面證據。部分學者從交易成本、風險、市場微觀結構等獨特視角進行反駁“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但是不同視角下的假說同樣受到來自“股利稅收追隨者效應”支持者的質疑。
相關文章閱讀
相關期刊推薦
精選范文推薦
- 1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 2資本市場論文
- 3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演變
- 4資本運營論文
- 5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 6資本市場培訓
- 7資本經營論文
- 8資本投資論文
- 9資本積累
- 10資本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