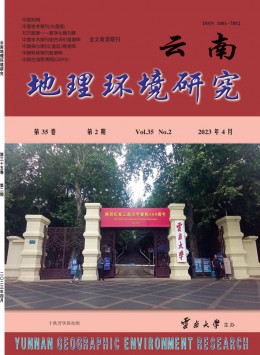地理環境對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影響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地理環境對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影響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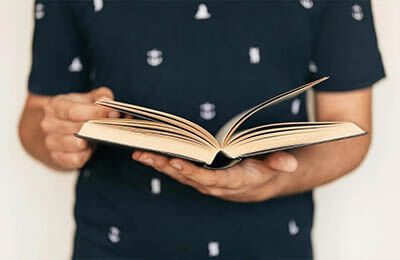
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架構
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類型除回族信仰伊斯蘭教外,其他各少數民族大都信仰原始宗教。原始宗教亦有學者稱為自然宗教,它是人類文明史以前的宗教形態,貴州各少數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大體上包涵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內容,這是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共性特點。
1.自然崇拜。自然崇拜是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形成基礎,早在原始社會時期,生活在貴州山地的各民族先民們把直接關系到與自己生存有關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加以神化,形成了萬物皆有靈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由于各民族所處地理環境不同,其崇拜的對象也不同。例如,為了祈求豐收而崇拜土地,有些部族對風、雨、雷、電的崇拜,都屬于大自然的崇拜。近山者則敬山神,近水者則祀水神,貴州少數民族普遍認為“萬物有靈”,天地間的事、物,都附有“靈”,與人們的生存禍福相關。無論是山川河流、古樹巨石、橋梁、水井等,都是崇拜對象。因此,有的山嶺不能挖掘,古樹不能亂砍,巨石不能開鑿、爆破,如果違反,則認為會敗壞“風水”,給村寨帶來“災難”。許多地方有新年初一,須敬祭“水神”,首次下河或到井里汲水之時,要攜帶神香紙錢插于河坎、井邊,或點火焚化,而后汲水回家。在榕江縣車江一帶的侗族,逢年春初,全寨的婦女要備酒菜到井邊“祭敬”,圍井“哆耶”,歌頌水井給人們帶來幸福,祝井水終年長流。許多地方出獵時,必須先敬“山神”,才能獲得野物,否則失利,甚至發生意外。
2.圖騰崇拜。原始宗教進一步發展,一些民族和部落出現了圖騰崇拜。圖騰崇拜是在自然崇拜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種形式的崇拜出現在原始社會的后期,其流行范圍相當普遍。被當成圖騰物的動植物被當作圖騰崇拜的直接對象,圖騰也是氏族或部落的標記和名稱。圖騰崇拜的崇拜物一般都是自然物,與各民族先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或為大樹巨石、或為珍禽猛獸、或日常可見之物,成為圖騰的自然物,往往被認為擁有某種神秘力量,并與本氏族有著某種親緣關系。貴州各少數民族由于生活環境的差異,其環境生活的動植物群落不一,而不同環境中的不同動植物對于人們生活的重要性也不同,因此不同民族、不同環境下作為圖騰物的選擇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圖騰崇拜中體現出一種紛繁復雜的圖騰信仰,反映了各族先民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的某些特征。
3.鬼魂崇拜。鬼魂崇拜比自然崇拜與圖騰崇拜有了進一步發展。這是原始人類進一步擺脫自然界與自我意識增強,強調自身存在的一種表現。貴州各少數民族普遍認為靈魂是與肉體伴隨在一起的,當靈魂脫離肉體時便形成了鬼魂。鬼魂生活在陰間,他監視著部落成員與家族成員的行動,他能左右人們的禍福,如果有人違反了人們約定的道德行為規范,鬼魂就會對其進行懲罰;如果陽世中人遇到困難祈求其幫助,鬼魂就會施以援手,但是事后當事人要對鬼魂答謝。各民族采取不同的葬禮,實際上亦反映著鬼魂崇拜,認為死者靈魂能單獨存在,所以要妥善處理好尸體,使死者感到舒適。一些民族甚至認為,人死之后靈魂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到陰間極樂之地,一部分前往墓地,一部仍留在家中,暗中保護家人。對于鬼魂認識,許多地方沒有鬼神之分,只有善惡之分,善的鬼能夠為人類帶來福,惡的鬼會給人類帶來災難。于是,很多地方產生了復雜的鬼神祭祀禮儀和驅鬼儀式。一方面通過媚神娛鬼,使陰間中存在的鬼神能夠為自己服務;另一方面,通過一定的驅禳鬼儀式,將惡鬼驅離,不給自己造成災害。因此,鬼魂崇拜中還包含許多巫文化的特點。
4.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以祖先亡靈為崇拜對象的宗教形式,它是宗教發展過程中,由圖騰崇拜發展而來,是從親緣意識中萌生、衍化出的是本族始祖先人的敬佩思想。祖先崇拜又分始祖崇拜、遠祖崇拜、家祖崇拜。祖先崇拜的出現,使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從自然崇拜向人為宗教轉變。
地理環境對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影響
(一)山地環境是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形成的基礎
自然地理環境,是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誕生的基礎,也是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產生之源。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十分低下,貴州各民族先民們對自然環境的依存度非常高,人類改造環境的能力遠遠不能與自然的力量抗衡,人完全被大自然所主宰。同時,人們的思維能力和智力水平都十分低下,不僅尚未形成獨立于自然的自我意識,還對自然界的許多自然現象不能做出科學的解釋,做出合理的闡述。在這種情況下,人類更多地借助于幻想和想象去解釋自然,解釋自己與自然的關系。這就導致了對于世界的虛幻反映和愚昧觀念,從而把許多事情都歸諸于神靈的力量,于是產生了最早的宗教意識。復雜的山地環境也決定了貴州宗教文化的內容。由于山地環境山高坡陡、葉茂林深、蟲豸出沒,加之地質災害、洪澇災害頻發,人們對自然界的依存度很高,為了適應環境,獲得食物,在復雜的自然環境中,不斷探索出適應自然的農耕經濟方式,在貴州主要有山地耕獵型、山地耕牧型、丘陵稻作型、刀耕火種型。由于沒有發達的農牧業,這里的居民大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此把對自然界的尊崇放在了第一位,偶然的災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瘟疫等等,人們都會幻想冥冥之中有神靈在主宰這一切。于是便產生了許多崇拜神祗的活動和行為,由于環境的復雜性,以及不同環境下人們操持的生產方式的不同,近水者祭水神,近山者,則祀山神;稻耕人群要祭田神、秧神、牛神;捕獵者則要祭獵神。于是產生了豐富多彩的多神信仰和崇拜。另外從貴州少數民族宗教信仰中的圖騰崇拜來觀察,作為圖騰物的對象,大多是自然環境中常見之物,或是與生活息息相關之物,因此,居于水邊的民族,多以魚、蛇、龍等為圖騰;以水牛為圖騰的,大都是從事稻作農耕的民族;以飛禽走獸為圖騰的,大都是山區耕獵民族。圖騰物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各民族居住的自然環境,這一點就有如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常以馬和狼為圖騰物,而貴州各民族種類繁多的圖騰物亦側面地證明了貴州山地環境的復雜。
(二)山地環境對貴州宗教文化發展的影響與地域性宗教文化的形成
山地環境對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發展與傳播起到的阻礙作用,使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在相對封閉的區域內獨自按規律發展,雖然它的發展速度緩慢,但這種發展從來沒有停止,最后各自都發展形成了一定的區域宗教文化,如都柳江流域的侗族薩歲崇拜,這是貴州都柳江流域侗族原始宗教中最為重要和神秘的內容,薩歲被當地侗族當成本民族的守護神加以崇敬,關于薩歲崇拜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純粹的土地崇拜,侗族是一個農耕民族,土地對侗族生存至關重要,侗族先民對土地的崇拜是首要的,因而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定居時,必先建立土地之神———薩的神祗和祭壇,正如侗族《祭祖歌》所唱的“未置門樓,先置地祗。未置寨門,先置‘柄地’”,證明了薩歲的崇拜起源于土地崇拜。第二階段,英雄崇拜色彩和祖先崇拜色彩加重,薩歲被具體指為古時候一名叫杏妮的侗族女英雄,薩歲被人格化并被尊奉為侗族保護神,衍成一種含有祖先崇拜、土地崇拜、英雄崇拜成分在內的復合崇拜。第三階段,薩歲被尊為至高無上的祖神(“薩歲”在侗語中表示至高無上的圣祖母),在薩神系列里位置最高。其發展歷程如部分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在研究人類宗教信仰的過程時所發現,宗教是由最低級演進至最高級———從拜物(如大川,大山,大樹之精靈)而至多神教,而至一神教(相信多神,但以一神為主),而至獨神教(只信獨一之神,即上帝或真主),例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雖然薩歲崇拜并沒有像其他宗教一樣形成獨神教,但是其已發展至一神崇拜的歷程清晰可見,已經成為一種區域性的宗教文化現象。除了都柳江流域薩歲崇拜,其他如雷公山、清水江流域苗族鼓藏(祭祖)文化;南北盤江流域布依族摩文化;武陵山、烏江流域土家族儺文化;都柳江流域水族牙娛崇拜;北盤江流域仡佬族山神崇拜;月亮山區域瑤族盤王崇拜等等,這些都是宗教文化區域性發展的結果。
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所顯現出的這種強烈的地域性,有時甚至超過了民族的特性,如雷公山、清水江區域苗族鼓藏文化,這種宗教文化現象在貴州苗族中部方言區非常普遍,許多寨子每隔幾年或十幾年甚至數十年就要舉行一次盛大的鼓藏祭祖活動,但是這種活動在貴州苗族的西部方言區和湘西方言區卻沒有發現,而在相鄰的錦屏與榕江的侗族中,卻存在與苗族吃鼓藏相似的習俗。另外如侗族南部方言區的祭薩活動是當地最隆重的宗教活動,但是祭薩活動在侗族北部方言區卻沒有,相反在都柳江流域的苗族和壯族中還存在相似的宗教活動。
貴州獨特的地理結構不僅對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傳播產生影響,也阻礙了其他宗教在貴州區域內的大范圍傳播,但是貴州山地所具有的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觀往往又是其他宗教所尋找的宗教圣地所在,世界上大的如山川、河流,小的如巖石、洞穴,都是一些宗教尋找的神圣場所。其中以山川圣地居多,究其原因之一,與山川的地理特色———高度有關,因為普遍認為神祗的居住地為人類不可及處,如天空,而山川曾是人類接近神祗的唯一自然途徑,所以山川被賦予神圣性。貴州的地理結構所造就的神奇山水便成了其他宗教尋覓的圣地,在佛、道教傳入貴州以后,在貴州山地上出現了很多古寺名剎與道觀,形成了許多有名的宗教景觀,如在武陵山麓形成的梵凈山佛教文化圣地,便是全國著名的五大佛教名山之一。
綜上,貴州山地環境決定了貴州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特點與屬性,嚴酷的山地環境是原始宗教產生的基礎,而山地環境的復雜性決定了貴州宗教文化的多樣性。貴州山地環境的封閉性使貴州宗教文化呈現區域化的特點,其他宗教進入貴州以后,在與地理要素相結合下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宗教景觀。(本文作者:吳嶸 單位:貴州省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