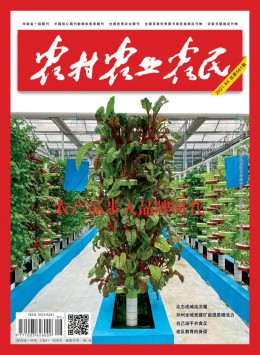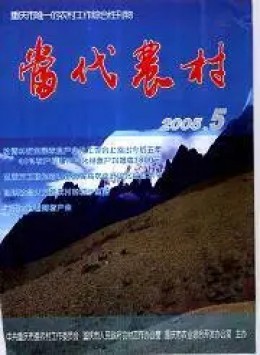農村文化建設模式的實踐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農村文化建設模式的實踐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內容提要: 農村公共文化建設,不僅是我國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關乎農村社會現代化的全局。伴隨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政策實踐,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多種創新性的建設模式,比較典型的有政府主導、精英引導、市場驅動等模式。這些實踐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更好地滿足了農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求。應理性地評估每種模式的價值,實現多元動力的有效組合,再造一種更有效率、更具活力的復合型文化發展模式。
關鍵詞: 農村公共文化; 文化事業; 文化產業
農村文化建設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文化是一種以鄉村社會為生成背景、以農村群眾為主體的文化形式。 農村文化表達的是農民的心靈世界、人格特征及文明開化程度。長期以來,以農民為主體的自然經濟、以農耕為主體的生活方式,使傳統中國社會形成了“倫理型”文化特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倫理、交換原則、資本邏輯滲透到鄉村社會,農村群眾的文化心理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逐漸向積極、主動、進取、理性的方向轉變,這是一種新的“文化規范”、“文化理性”。這種文化精神,既蘊含著獨立、自主、自律等主體性追求,又包含著平等、理性、民主等價值規范。在現代文明的熏陶下,農村文化在傳統與現代的激蕩中呈現出較為普遍的“二元結構”,即形成了進取性與保守性、開放性與封閉性、流動性與凝固性錯綜結合的復合體。農村文化的這種特質,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村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成制約。
一、問題的提出
長期以來,我國在農村文化建設上存在著“附屬論”、“靠后論”、“代價論”等認識,導致農村文化建設明顯滯后于經濟建設,公益性文化事業明顯滯后于經營性文化產業。“附屬論”是指用有利于經濟建設的功利觀點來衡量文化事業,導致農村文化建設的泛商業化。“靠后論”強調經濟發展之于文化建設的優先性,認為經濟發展是文化建設的基礎。“代價論”則認為犧牲文化建設是加快發展農村經濟所必需付出的一種代價。這些認識上的偏差甚至錯誤,在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導致精神文明建設明顯滯后于物質文明建設;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則阻礙了脫貧致富的進程,形成“經濟貧困”與“文化貧困”的惡性循環。特別是市場經濟資本邏輯的過度張揚,引發農村公益性文化活動的萎縮,商業性文化得以大肆擴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公益性文化的社會教化責任,一些農村地區文化建設出現“逆流”。
現代化是一個整體性的社會變遷過程。農村社會的現代化,絕不僅是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民的物質富裕,還包括農村的社會進步和農民的精神富裕。推動農村社會的全面發展和文明進步,需要審視農村文化建設的現實困境和緊迫性,并將其放在“五個建設”戰略格局中來考量。在“五個建設”的宏觀視野下,農村社會的文化生態令人擔憂:以倫理本位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逐漸消退,以感官娛樂為內容的大眾文化勃然興起,以政治認同為目的的主導文化面臨挑戰,農村社會呈現出多元文化混存的局面,農村文化在傳統與新潮互悖的迷惘中選擇。針對農村文化建設的滯后和困局,我國將農村文化建設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進行部署,推出了一系列有關農村文化建設和公共文化建設的政策,旨在促進農村文化事業健康有序發展。在農村文化建設中,公共文化建設至關重要,因為它擔負著核心價值引領和公共需求滿足的任務,關乎農民的文化權益保障和國家的文化整合。
二、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實踐模式
在國家公共文化政策的驅動下,各地組織實施了多項文化建設工程及常設性的文化活動,擴大了公共文化服務的領域,豐富了基層公共文化的內涵,并在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實踐中創造出多種模式。結合各地實踐經驗及其主導性特征,這里從理論上將其歸納為“政府主導”、“精英引導”、“市場驅動”三種模式。
(一)“政府主導+社會協同”模式
農村公共文化是一種社會公共產品,理應由政府來提供,政府要發揮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主導作用,充當起新農村文化建設領航者的角色。中央明確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作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任務,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營造環境,切實擔負起領導責任。”[1]政府擁有巨大的經濟資源、權力資源和民眾信任資源,能夠形成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長期以來在文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建設了相對完善的公共文化設施,創造出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促進了人民群眾文化權利的實現。政府主導模式,是基于政府在公共文化建設中的目標地位和職能界定,在實踐中形成的一種注重政府在資金、政策、管理等方面的主導作用的文化建設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政府主導文化建設,以縣、鄉、村文化陣地建設為基礎,構建公共文化服務的基礎平臺。近年來,甘肅臨澤縣按照“完善縣一級、鞏固鄉一級、發展村一級、延伸社一級、輻射戶一級”的文化發展思路,積極進行政策規劃,不斷加大財政投入,改善了縣級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的設施條件,加強了“三館”的規范化建設,推動其開展經常性的群眾文化服務活動。同時,著力推進基層公共文化服務陣地建設,全縣7個鄉鎮已全部建成高標準的鄉鎮綜合文化站;在行政村一級,建成農家書屋71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村級服務點71家、村級文化體育健身廣場64個。[2]目前,臨澤縣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已初具規模,在基層公共文化建設中,鄉鎮綜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動中心扮演著引導者、組織者的角色。
第二,文化活動形式以政府組織的“文化下鄉”活動為主。政府組織把農村短缺的、農民群眾喜愛的文化內容與文化服務送到農村,包括電影、戲劇、圖書、影碟、文化科技、醫療衛生信息等,也包括為農民提供文化服務的設備,如流動舞臺車、流動售書車、電影放映機等。2010年,湖南澧縣組織縣文化局、司法局、科技局、計生局、衛生局等單位,在澧縣澧南鎮開展了送文化、送圖書、送法律、送科技、送醫療“五下鄉”活動。澧縣文化局組織的澧州大鼓《查家底》、小品《包箱里的風波》以及戲曲、歌舞表演等精彩節目,受到了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澧縣圖書館為農家書屋和農民群眾贈送的圖書、圖書借閱卡受到了群眾的好評。通過“五下鄉”活動,農民群眾文化、科學、衛生、法律素質得到提高,農民群眾的文化生活日益豐富,生活質量得到提高。①《澧縣縣委、縣政府組織文化下鄉惠民演出活動》,http://www.hnqyg.com/a/zh/2010/0611/1065.html,2010-06-11。
第三,社會參與多以社區、村組、社團、自然人等為主體,形成一定的社會文化網絡。采取由政府牽頭主辦文化活動、文化項目,社會各單位積極承辦的形式,集結各方面的力量和優勢配合政府辦好農村文化。在公共文化建設中,深圳市寶安區制定了扶持和促進社會文化組織發展的政策,對活力強、影響大的優秀社會文化組織和民間文藝團體,在文化項目開發和文藝精品生產等方面給予資助和獎勵,充分調動社會辦文化的積極性。政府主導下的鄉村“文化大院”是這一模式的創新形式。內蒙古九原區從2003年開始“文化大院”創建以來,已有“歌舞大院”、“剪紙大院”、“秧歌大院”等40多個基層文化戶在開展活動。文化大院是以農家小院為活動場所,以每個村的文藝、文化愛好者和擁有活動設施、設備的農戶為組織者和參與者,自發組成的文化社團。他們利用農閑時間,經常開展文化活動。文化大院積極鼓勵支持廣大農民以自己的庭院為陣地,就地參與庭院文化建設,就地享受文化生活,最大限度拉近文化與農民群眾的距離,使廣大農民既成為庭院文化的參與者,又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使農民群眾真正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主人。[3]
(二)“精英引導+社團推動”模式
社會學理論表明,無論是野蠻社會,還是文明社會,任何社會中都存在著精英和民眾兩個群體,他們在意識、能力、權力與價值追求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在我國農村社會,鄉村精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群體。鄉村精英是那些在鄉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較高地位,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和社會威望,能夠對鄉村的事務和發展有一定支配能力的人。就農村公共文化建設而言,散布于廣大農村的“民間藝人”和“文化能人”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其藝術養分直接來自于農村,和農民有著天然的相通性,在民間文化的傳承和新農村文化建設中起著骨干和橋梁作用。這種以“民間藝人”和“文化能人”等鄉村精英主導農村文化發展主流、社區整合民間資源為基礎的農村文化發展模式,可稱為“精英引導”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鄉村精英協同、主導農村文化的發展走向。鄉村精英在文化發展方向的確定、文化重大決策的啟動和文化活動的策劃等方面發揮著規范、引導作用。在這一過程中,農村精英體現的是農村文化特質中代表社區、村落主流文化的先進因子,農村文化精英人物是農村文化的傳播者和倡導者。湖北宜昌三峽地區有個民間說唱藝人劉德方,能講400多個民間故事,會唱幾十首山歌民調,會表演一批花鼓戲和皮影戲劇目,會唱多部長篇喪鼓詞,被專家評價為“目前三峽地區最具活力的民間故事家和民間藝術家”。為發揮民間藝人在文化發展中的引領作用,當地成立了“劉德方民間藝術團”,開展經常性的民間文學演唱活動,并在活動中關注農民文化骨干的挖掘和培養,培養了新一代民間文化傳承人。[4]
第二,文化建設突出民間文化的傳承和鄉土特色的發揚。在陜甘地區的自樂班中,出現了一批農村文化的帶頭人。這些熱心民間文藝活動的中老年人,騰出自己的房子,作為文藝活動場所,集資“湊份子”購買演出服裝、道具,長年舉辦活動,農民活動農民辦,用市場運作手段來辦,使農村文藝活動富有生命力。在陜西眉縣青化鄉,當地村民集資組建了“大秦戰鼓社”等自樂班組織,這種組織“小型多樣”,活動以戲曲、歌舞、社火、快板等為主,農閑時自娛自樂,節慶日在周邊村鎮表演,很受群眾歡迎。浙江開化縣華埠鎮注重挖掘民間文化,把已經失傳和面臨失傳的民間表演藝術,如鑼鼓隊、秧歌舞、腰鼓舞、旱船、布龍、竹馬舞等通過整理和恢復全部展現出來,保持了文化建設的鄉土特色,促進了民間文化的多樣性發展。甘肅河西地區到處都有農民自發組織的劇團、戲社并常年活動在鄉村,使傳統的民間文化得到傳承。位于臨夏、甘南交界處的蓮花山民間花兒會,由于民間精英自覺組織,規模一年超過一年,吸引周邊數萬農民前來參加,活躍了當地群眾的文化生活。蘭州市永登縣苦水的“高高蹺”社火享有盛名,當地青年農民每年都籌劃組織 “高高蹺”社火表演,使這種民間技藝得以發揚和傳承。[5]
第三,政府適度的引導和扶持發揮著重要作用。山東省昌邑市不斷加大對基層文藝組織的扶持力度,注重提高農村各類文藝骨干的業務素質和工作水平,極大地滿足了農村群眾不同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該市85%的村(社區)擁有文藝隊伍,莊戶劇團、秧歌隊、合唱團等群眾性文化團體總數達500余支,農村文化能人300余人,每年自發演出達1萬余場。全市鄉村形成文明和諧的社會新風尚。[6]山東省臨清市在農村公共文化建設中,注重挖掘鄉土文藝人才的潛力和鄉村獨特的文化底蘊。通過政策幫扶,指導部分村莊成立了京劇戲迷協會、文藝俱樂部、農民詩書畫協會等民間組織,利用農閑開展書畫展示、文藝節目創作、文藝匯演等一系列活動。為給鄉土人才提供施展才華的舞臺,他們結合村莊文化大院建設,將小廣場、小戲臺等文體設施納入政府文化設施建設之列。①《臨清民間藝人扛起文化龍頭》,http://www.lcxw.cn/news/liaocheng/xianyu/20120824/253113.html,2012-08-24。同時,通過舉辦鄉土人才培訓班、文藝工作者下鄉指導等形式,鼓勵農民以身邊人、身邊事為素材,創作演出形式多樣的文藝節目,謳歌農村變化,教育感化群眾。
(三)“市場驅動+村企共建”模式
公共服務市場化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行政改革的核心主題,其基本思路是在公共服務供給領域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將原由政府承擔的部分公共職能推向市場,通過充分發揮市場優化配置公共資源的作用,達到改善和提升公共服務的目的。適應公共文化建設的需要,我國一些地方政府逐漸從“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思維中跳出來,嘗試通過市場機制為文化建設募集資金、資源并創新其運作方式,“文企聯辦”、“公辦民營”等市場化的運作模式逐漸發展起來。吉林長春市采取文企聯辦、民辦公助、公辦民營等方式,引導國有企業和民營資本積極參與到文化活動中。福建省長樂市積極探索文企聯辦、市場運作的文化建設路子,探索以民間資本“入股”方式發展農村公共文化,從而形成了形式多樣的“民資文化”格局。概括而言,“市場驅動”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依托企業投資和集體投資,創新文化投入機制。一是依托當地大型企業和企業集群興辦農村文化。由于籌資渠道便利,此類文化設施和文化活動具有規模大、設施全、層次高等特點,多集中在城郊和開發區的周邊,基本形成了文化生態園區,以河北省武安市東山文化公園和霸州市王疙瘩村的農民公園為典型。公園內設有劇場、圖書室、各類球場、農民健身中心、老年活動中心等,各類文體活動常年不斷,且活動內容較為豐富,村民們可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文體生活。二是依靠集體力量投資農村文化建設。這一類型主要集中在集體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以河北省辛集市的都大營村、新壘頭村為典型。都大營村投資60萬元建設的村民文化活動中心,每天都有村民舞會和文體活動,周圍十里八鄉的農民都來這里參加活動,成了當地一大亮點。文化活動還成了村“兩委”與村民溝通村情、共謀發展的有效載體。[7]
第二,嘗試市場化運作,創新公益文化運營模式。文化事業的繁榮離不開市場,也要在市場中找到自身的適當位置和生長點。目前,文化事業單位改革試點中的一些市場化運作,已經取得驕人的成績,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就是一個予人啟發的例子。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自1996年以來,擺脫了長期以來束縛文化館發展的桎梏和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經營觀念,經歷了館長聘任、全員聘任,引進機制、改變格局,開放辦館、多元發展等三個階段,進入到全面建設現代化文化館的新階段。①《略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http://www.ccmedu.com/bbs4_4573.html。蘭州市在2005年舉行了第三屆文化項目推介會,把蘭州各類文化活動和建設項目面向社會整體推介,為企業和社會各界關注文化、參與文化建設搭建服務平臺,借助市場機制對城鄉文化資源進行整合運作,為構建高層次的“文化圈”提供了動力支持。通過市場化運作和創新公益文化運營模式,項目推介會成為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生產主體、發展資金、消費受眾等各種要素整合配置的基礎平臺。
第三,政府創造環境,為“民資文化”發展助力。將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起來,在堅持公益性前提的情況下實現有限的市場化,是公共文化建設的路徑之一。政府需要適應這一發展要求,出臺推動“民資文化”健康發展的相關政策,在企業贊助、社會贈與、社會投資等方面,完善相關的配套政策;在文化活動場地、場所的建設用地等方面,給予相應的靈活政策;在農村文化骨干人才的培養和專門人才的文化支農方面,提供相應的扶持政策。2002年以來,福建省長樂市投資建成人民會堂、博物館、圖書文獻中心、金源科技大廈、廣播電視中心、新華書店、會堂廣場等多處基礎設施,為民資文化實體創造環境,提供演出的舞臺。每天清晨和傍晚,人民會堂廣場、南山公園、鄭和公園周邊地區,遍布數十個大小不等的扇子舞、彩帶舞、民俗舞方陣,都充滿歡聲笑語。同時,該市還堅持為民資實體“充電”、為書屋送圖書、為放映隊送電影拷貝、為演出戶送精品小戲等活動。[8]
三、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模式的檢視與重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快速轉型。經濟、社會變遷的過程伴隨著傳統文化的揚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孕育和形成。在這一社會轉型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時期,堅持文化秩序建構的社會主義方向,全面推進具有全民性和健康文化價值導向性的公共文化建設是必然的選擇。然而,考察我國社會文化發展的態勢,農村文化發展滯后是一個典型問題,尤其是公共文化建設更是滯后,存在著三個“不適應”:與全面實現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要求不適應,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要求不適應,與農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不適應。
近年來,在國家文化政策的驅動下,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并探索形成了一些創新模式,有效地提高了當地公共文化發展的質量和效率,更好地保障了農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滿足了農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求。但如果過分強調這些實踐模式的純粹性,往往又會使其自身缺陷得以放大:政府主導模式如果過分強調政府的主導地位,就可能忽略農村文化建設的主體——農民的文化權益和文化需求;精英引導模式如果過分依賴于少數精英人物,就可能漠視民眾作為農村文化建設主體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眾在文化建設和文化生活中的選擇權、參與權和創造權,不符合現代文化民主化發展的趨勢;市場驅動模式如果過度渲染市場化的發展取向,過度張揚市場機制的作用,就可能導致文化發展的商業思維和文化商業化的泛濫,削弱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價值導向性和社會公益性特征,就可能對人文精神和文化品位構成潛在威脅。
新農村公共文化的發展繁榮,需要遵循文化發展的基本規律,通過文化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綜合多種文化發展要素,吸納各種發展模式優勢,實現多元發展動力的有效組合和良性互動。[9]
為此,需要在借鑒吸納各種實踐模式優點的基礎上,探索一種更富活力、更有效率的文化發展模式,這種新型的公共文化發展模式應該注重以下方面:一是明確文化發展的基本宗旨,將保障公民的文化權利(包括享受權、參與權、選擇權、創造權等)作為公共文化發展的基本目標;尊重人民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話語權”,使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植根于民眾,發揮民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性地位。二是發揮政府在促進“文化民生”與“文化民主”中的關鍵性作用,堅持“弘揚主旋律”與“提倡多樣化”的辯證統一,切實履行政府的文化管理與文化服務職能,通過戰略規劃、政策支持和輿論引導,保證社會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維護社會文化秩序,優化社會文化生態。三是發揮文化精英在藝術創作、文化創新等方面的作用,鼓勵專業文藝工作者深入農村基層體驗農村生活,鼓勵他們創作農村題材的文藝作品;改善民間藝人生存與發展環境,通過政策引導和扶持、壯大民間文藝團體,發揮它們在優秀民族民間文化傳承創新、公共文化的生產供給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四是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實現文化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確立平等參與、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利用市場的競爭激勵機制,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供給,形成規范有序的競爭網絡,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在此過程中,應強化政府對市場化的管理能力,增強政府對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管理責任,保持公共文化服務的公共倫理意義。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人民日報》2006年1月13日
[2]馬鈺良:《臨澤逐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張掖日報》2012年6月19日
[3]阿勒得爾圖:《包頭市九原區引導扶持文化大院建設》,《中國文化報》2010年5月19日
[4][5]黃永林:《要重視民間文化在新農村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光明日報》2006年5月15日
[6]代選慶 李生濤 李洪帥:《昌邑民生為本譜寫文明和諧樂章》,《濰坊日報》2012年1月29日
[7]聶辰席:《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新模式——河北省發展“民資文化”的調查》,《黨建》2007年第8期,第 38~39頁
[8]蔡小偉余榮華:《小城大“文”章——福建長樂公共文化建設紀事》,《人民日報》2007年7月22日
[9]金民卿:《構建多種文化發展模式》,《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1月8日
作者:方曉彤 單位:蘭州城市學院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