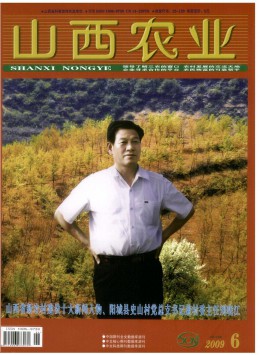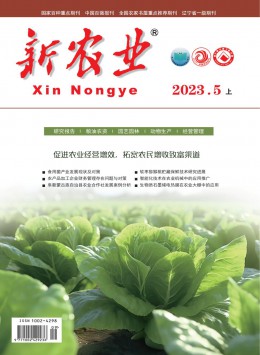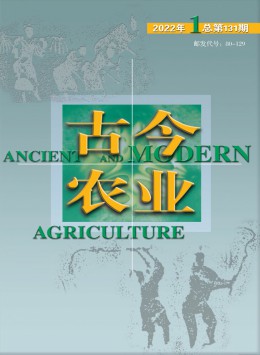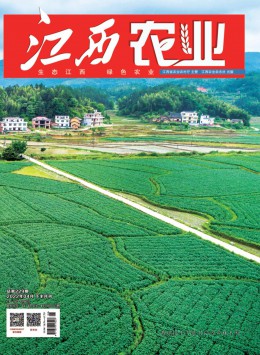農業財政支出及經濟增長的關聯性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農業財政支出及經濟增長的關聯性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引言及文獻回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農業經濟總量有了顯著的增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也有了很大提升。但由于經濟資源的稀缺性與生態環境的壓力,使得我國單純依靠要素投入增長來實現農業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我國的農業應向主要依賴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集約式增長方式轉變。財政支農支出是政府支持農業發展的主要手段,可以提供農業發展所必須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對于提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在“十二五”規劃中,我國政府將加大財政支農投入,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實現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將是未來工作重點之一。所謂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是指除了勞動力和資本之外,包含技術進步、公共服務效率提高等其他因素所帶來的農業產出增長率,通常用來考察一國或地區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在我國當前的惠農政策框架下,我們認為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TFP的拉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財政支農支出能提供農業發展所需要的經濟性公共物品和服務,通過形成物質資本增加私人部門獲得資源的便利性,提高現有農業資源的使用效率(Munnell,1996);第二,財政支農支出能提供農業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性公共物品和服務,通過形成人力資本或R&D資本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第三,財政支農支出有利于拉動私人投資,穩定私人投資預期。農業是一個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相交織的弱質產業,決定了農民私人投資對農村公共物品和服務的強烈依賴。因此,有必要通過完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供給為私人提供良好投資預期,增加私人投資和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從而帶動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政府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許多研究,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個方面:(1)探討財政支農支出總量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王文普(2008)基于VAR模型和VEC模型,選取1978~2005年的財政農業支出的數據,認為財政農業支出總水平對農業經濟增長有負向影響。(2)探討政府財政支農結構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陳燦煌(2009)在C-D生產函數框架下的分析認為,目前我國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結構性偏差。(3)探討財政支農支出的最優規模。郭玉清(2006)選取我國1981~2004年的財政支出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我國財政農業投入的最優規模占農業總產出的比重應達到8.26%。由此可見,已有的研究已經得出諸多重要結論,但仍可作出改進。首先,在研究視角方面,現有研究主要探討了財政支農支出總量和結構與農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對財政支農支出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關系卻鮮有研究,因此關于我國財政支農支出如何影響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推進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現有的文獻主要對該問題進行了“時間序列”和“截面”的研究,但鮮有考慮滯后變量的影響。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表明,技術進步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即當期技術水平受到前期技術水平發展的制約,因此應引入滯后因變量來控制農業技術進步的累積效應。綜上,本文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財政支農支出促進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行實證度量。我們首先采用超越隨機前沿生產函數估計1978~2009年間中國28個省份①農業TFP變動情況;然后采用1978~2006年間②省際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估算財政支農支出總量和結構與農業TFP之間的動態關系,考察了中長期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TFP的影響效應,以期為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的政策調整提供政策建議。
二、數據指標及說明
本文采用的是1978~2009年的28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面板數據。農業產出以國內生產總值中的第一產業產值(文中以Q表示)代替,并經過GDP平減指數換算為1978年不變價格。農業投入主要考察勞動力(LB)、土地(CD)、化肥(CH)和農業機械(MC)4種重要生產要素的投入。其中,勞動力投入以農林牧漁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代表,土地投入以農作物總播種面積代表,化肥投入以農業生產中實際投入的化肥數量代表,農業機械投入以農業機械總動力代表。上述原始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五十五年統計資料匯編》以及《中國財政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并根據實證分析的需要對相關面板數據進行歸類、整理和計算。財政支農支出即國家財政對農業的投入,是全部財政支出項目中支農資金的匯總和綜合,按照相似的支出功能和經濟性質,財政支農支出可以分為農村經濟性支出、農村社會性支出和農村轉移性支出。農村經濟性支出(FE1)是指具有政府投資性質的農業經濟建設支出,包含林業支出、農業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和支援農村生產支出等。農村社會性支出(FE2)是指具有政府消費性質的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支出。農村轉移性支出(FE3)是指具有政策性的政府補貼支出,包含農業生產資料價差補貼、糧食價格支持補貼、糧食風險基金、國家糧油安全儲備補貼等。
三、理論框架及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非中性技術進步的超越隨機前沿生產函數(FrontierProductionFunction)模型計算各省歷年農業TFP。由于我國各省份區域特征明顯、數據時間跨度較大,導致不同時期不同省份的TFP估計結果會有顯著的區別。而前沿生產函數基于DEA算法,不考慮隨機誤差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而隨機因素對結果的影響較小。
四、估計結果及分析
1.估計農業TFP。使用FRONTIER4.1工具,以最大似然法計算全國農業Malquist全要素生產率(TFP)。模型中的大部分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上是顯著的。勞動力的農業產出彈性為負值,很可能是由于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存在“過剩”,即進一步增加農業勞動力反而不利于農業產出的增加。耕地的產出彈性也為負值,表明在我國增加農業耕地投入對農業增長的影響同樣是反向。化肥和農業機械投入的產出彈性都是正值,說明增加二者的投入對農業產出起到了正向的影響。各個省份和區域的技術進步指數是用估計出的隨機前沿生產函數對時間求偏導得出的,再利用式(3)計算TFP。顯示了樣本區間內全國農業TFP的變動趨勢,限于篇幅,各個省份具體的農業TFP計算結果此處不再詳列。1978~2009年全國農業TFP呈波動上升趨勢,其變化周期與支農政策調整周期較為一致,大體分為五個階段:(1)1980~1985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我國對財政支農資金的有關分配和使用方法進行了改革,同時改進了農業稅的征收管理辦法。這些措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和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有力地推動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迅速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2.8%。(2)1986~1990年,中國改革的重點由農村向城市轉移,支農政策逐漸減少,導致這一階段中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迅速下降,年均增長率為-1.1%。(3)1991~1995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政府也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增加農業投入,促進農村經濟快速發展,使得糧食產量出現了大幅攀升,給農業TFP增長帶來了顯著正效應,全要素生產率保持了1.7%的年均增長率。(4)1996~2000年,由于宏觀經濟增長放緩、農產品需求受結構性買方市場的影響,我國農業增長再次進入低迷期。農民普遍出現“增產不增收”的問題,降低了農民增加新投資和采用新技術的積極性,使得這一時期的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緩慢,年均增長僅0.7%。(5)2001~2009年,21世紀以來農業生產的長期低迷使政府的財政支農政策開始實現戰略性轉變,相繼推出了一系列實質性的惠農政策,如稅費改革、增加農業補貼等,這些政策的實施重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全要素生產率再次迅速上升,年均增長4.0%。
2.估計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我們利用計算而得的1978~2006年全國28個省份的TFP及各類財政支農支出數據來估計式(4),以考察財政支農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影響。式(4)的因變量滯后項出現在方程式右邊,是一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傳統的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模型的OLS回歸方法,在估計這類動態面板數據模型時會導致內生性問題(當s<t時,lnyit-1與uit相關)和誤差項的移動平均過程,從而導致估計系數有偏。因此本文采用系統廣義矩法(SYSGMM)估計來克服上述問題,即先經過一階差分,然后采用t-2期前的因變量的滯后項及其一階差分的滯后項作為因變量滯后項的工具變量,以工具變量估計方法(IV)克服有偏的問題,從而得到一致且更為有效的估計結果(Arellano,Bover,1995;Blun-dell,Bond,1998)。,農業TFP滯后項(lnTFPit-1)的影響作用較大(彈性系數均顯著并大于0.6),即忽略農業技術水平的滯后因素會導致其他解釋變量估計有偏,說明我國農業技術水平的前期累積效應比較明顯。農村經濟性支出對三大區域的TFP均具有顯著正向效應,其中對中部地區影響最小,其次是西部地區,東部地區最大(東、中、西部地區影響系數分別為0.0552、0.0212和0.0355),出現了中部地區的政策“塌陷”。這是因為經濟性支出主要用于對交通和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可以有效地提高農業生產條件和改善市場環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技術的進步,提高我國農業的整體競爭力。東部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較強,可以提供的較為完善的農業基礎設施,極大地促進了區域內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此外,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增加了對西部地區的農業公共投資,極大地改善了西部落后的農業生產和技術條件,使經濟性支出對西部地區TFP的提升作用開始超過了中部地區。農村社會性支出對三大區域的農業TFP具有正向效應,但系數值較小(東、中、西部地區影響系數分別為0.0013、0.0009和0.0032)。這說明社會性支出對農業TFP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效率不高,因為從支出結構來看,我國農業各部門事業費居高不下,用于人員供養及行政開支的部分偏高,擠占了其他生產性項目所需要的支出。此外,現階段我國大部分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低下,部分農村社會性支出被消耗在行政管理的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公共資源閑置浪費的現象,對農業生產和技術進步直接推動作用相對較小。農村轉移性支出對三大區域的TFP具有負向影響,其中對中部地區的影響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區,東部地區最小(東、中、西部地區影響系數分別為-0.0095、-0.0129和-0.0104),表明我國現階段農業補貼并未達到理想的政策效果。這主要是因為2004年之前農業補貼主要是以促進糧食增產為目的間接補貼,一定程度上使農民的利益受損,其效果一直較差。雖然2004年后我國農業補貼轉向以促進農民增收為目的直接補貼,保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但由于近年來相對于農產品而言,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較快,無形中消減了農業補貼的政策效力,影響了農民的持續增收,使得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受到了抑制。此外,中西部地區作為糧食的主產區,地方政府要相應承擔配套的農業投資,無形中增加了其財政負擔,這使得中西部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財政能力大為減弱。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發現,1978年以來我國財政支農支出總體上提升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推動了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其中經濟性支出比社會性和轉移性支出對TFP的提升作用更大,而且不同類型的財政支農項目對TFP的提升作用在區域間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應提高政府財政對農業投入的總水平,并促進財政支農資金投入持續增長。嚴格按照《農業法》的規定,確保縣級以上各級財政每年對農業投入的增長幅度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同時各年新增的財政資金也應重點向“三農”領域傾斜。此外,應合理界定各級政府的財政支農職能,充分發揮中央政府的協調作用。對于經濟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地方財力相對充裕,地方政府應承擔更多的支農職能,建立以地方為主、中央為輔的財政支農體制;而對于經濟不發達而農業主產區相對集中的中西部地區,則要加大中央財政支農力度和政策傾斜程度。各級政府根據本地區的實際農業經濟發展狀況,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本地區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第二,積極優化財政支農支出結構,提高支農資金的使用效率。現階段應進一步穩定并增加農村經濟性支出,控制并降低農村社會性支出,加大農村轉移性支出,充分發揮各類支出對農業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推動作用。這里要特別提到的是國家應加大對中部糧食主產區的經濟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支持力度,努力減輕主產區因農產品生產而產生的財政負擔,支持主產區轉變農業增長方式。這對于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和糧油棉等居民基本必需品的供給,促進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