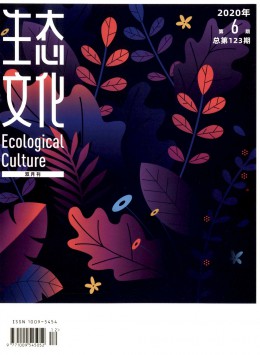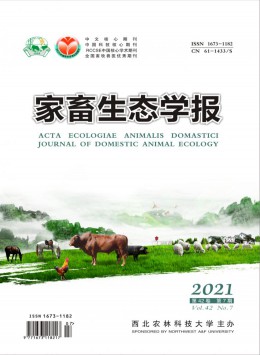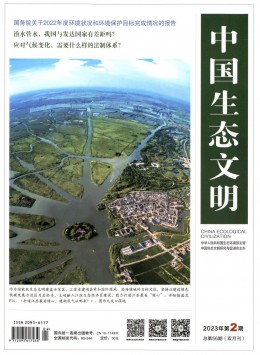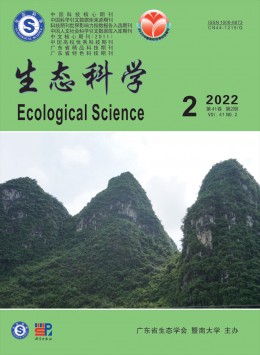生態美術和人與自然環境的融合發展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生態美術和人與自然環境的融合發展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以西方工業革命為起點,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開始加速惡化,特別是在科學技術賦予的力量作用下,人類社會從認識層面和行動層面自發地與自然環境剝離,將自身塑造成自然的統治者。一方面,人類在認識上逐漸否定了自身對自然的依賴性,正如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戈爾所言,“人們將面包的產地理解為超市而非麥田,這種潛意識中對自然的蔑視,無異于將人類定義成‘生態孤兒’的角色。”另一方面,人類在行為上破壞了自然環境的正常秩序,正如美國生物學家康芒納所言,“人類將生物圈的循環體系變成了資源型的線性消耗,潛意識中缺乏對自然環境的敬畏之心,依恃理性工具展開對自然的盲目征服。”但無論如何,人類始終無法擺脫作為自然界一分子的命運,人類社會在享有工業文明成果的同時,也必然要承受破壞自然環境導致的后果。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環保運動、生態思想、綠色理念等代表了當代社會對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深刻反思,也為生態文明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這一角度出發,“生態美術”正是人與自然關系演變的結果,既可以將它視為美學與生態學的融合形態,也可以看作是以美術這一藝術形式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批判,最終目標是生態美術和人與自然環境和諧關系的融合發展。《永恒的原鄉:中國當代生態美術研究》一書由彭肜、支宇主編,由四川大學出版社于2015年10月出版。全書以中國當代生態美術發展脈絡為依據,對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種種表現進行了全面且深入的探索。總覽全書,向讀者呈現出三個方面的特色。
緊扣主題,展開人與自然環境交惡結果的反思
《永恒的原鄉:中國當代生態美術研究》一書充滿了對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反思,其中兩者關系交惡既是反思重點,也是反思的起點。全書包括六個章節,按照人與自然環境關系表現差異可分成三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包含第一、二兩個章節,主要闡述人與自然環境關系交惡的結果。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五三個章節,主要闡述人與自然環境關系博弈的支點。第三部分為第六章“自然之美:重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主要闡述人與自然環境關系如何實現可持續性發展。本書中的“原鄉”是一個哲學概念,但可以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解釋和理解,全人類“原有的家鄉”無疑是自然環境,然而它不具備聚落地理學意義上的空間屬性。換言之,人類在物理層面從來都沒有脫離自然環境,但在心理層面對于自然環境的“鄉情”卻漸行漸遠,特別是在現代文明沖擊下,自然生態已經演變成精神家園,人們很難從原生態的自然環境中獲得歸屬感、依賴感,反而會面臨生命威脅和生存困難。這種人與自然環境關系交惡的現象,正是源于工業文明、科技文明、理性文明。在各種先進工具的使用過程中,人逐漸凌駕于自然之上,崇拜變成了征服,善待變成了破壞,祈求變成了占有,直到自然環境開始反噬人類社會,人們才意識到一味破壞、索取、利用的嚴重后果。作者指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交惡帶來兩種結果:其一是生態學研究立場的轉向,即從“以人為中心”轉向“以非人為中心”,這也是自然環境從外部施加壓力的結果,人們開始意識到人與自然是一個共同體,彼此之間并非權力關系而是自由關系,即人類有利用科學技術、現代工具破壞自然環境的自由,自然環境也有懲罰人類肆意妄為的自由。生態美術作為一種藝術表達介質,核心創作依據就是自由關系的正當性和對稱性。其二是生態美術話語及圖像表達范式的轉換,從對自然環境向人類無私饋贈的贊揚角度,轉換為人向自然環境進行戕害的批判角度,反饋到生態美術這一表現媒介上,涌現出大量以批判人類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為主題的作品。
導向明確,構建人與自然環境博弈競爭的支點
本書在論證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明確導向,即“博弈”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常態。在人類社會尚處于萌芽階段時,人類為了生存不得不和自然環境抗爭,此時人類處于博弈中弱勢的一方;而在人類社會處于工業文明、科技文明、理性文明高度發達階段時,人類基于私利需求而選擇向自然環境展開全面征服,此時人類處于博弈中強勢的一方。無論哪一種極端狀態出現,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都會失衡,關系交惡是必然結果,而要實現雙方博弈的和諧關系,人類必須在博弈中保持理性,并構建雙方博弈競爭的有效支點。綜合生態美術緣起、內涵及母題,本書將構建人與自然環境博弈競爭的平衡支點歸納為三個:第一,自然環境的異化。立足國內,自然環境的異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分別是城市景觀、鄉土重構、污染治理。城市景觀反映出人工力量與自然力量之間的博弈。能否在景觀場域下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主要取決于人能否因地制宜地創造。鄉土重構反映出人類發展與自然制約之間的博弈。能否在鄉土場域下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主要取決于自然環境條件、特色、資源價值,如果自然環境過于惡劣、嚴格,人們選擇放棄博弈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如出現集體遷移現象。環境治理則反映出人對自然環境的善意。能否在治理場域下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主要取決于環保技術的先進程度。第二,動物權利的保護。在人與自然關系范疇中,人與其他物種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雙方均具有動物的生命特征,如果將人與自然環境交惡視為“直接關系”,那么人對其他物種的生命剝奪則處于“間接關系”中,這與食物鏈、生態鏈意義上的殺戮完全不同。“生命之維”是當代生態美術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如羅中立的《繡花女孩》《夜歸》《影子》等作品,均體現出人與動物具有平等的生命權,而生命權已經上升至生態倫理、生態道德等層面,是人與自然環境博弈競爭中最牢固的支點。第三,工業文明的取代。工業文明是破壞自然環境的主要力量,作者強調克制欲望、簡約生存,助力推動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構建可持續發展模式。
與時俱進,重塑人與自然環境之間和諧的關系
本書指出,生態美學建構于生態學、美學兩個學術場域的交叉范圍內,而生態學研究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美學以社會文化為基礎,兩個“基礎”都處在動態變化之中,因此,重塑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系也要與時俱進。從人類破壞自然環境的方式來看,主要表現為人類社會對原生態自然環境的損毀,但人在人與自然關系場域內的地位,決定了對自然環境破壞的程度。以鄉土空間為例,人類生產能力有限、科技工具稀缺,只能在有限的自然環境空間中損壞原生態事物,如毀壞一部分森林、草原作為耕地,雖然破壞能力有限,但這不意味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和諧的,只是表明大自然的反撲能力超過人類的進攻能力,人類在自然修復過程中并沒有發揮積極作用。而在城市空間中,人類工業文明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彰顯,自然環境反而成為人類社會的點綴,如城市園林、交通綠化、公園景觀等,人們雖然竭盡全力保護這些自然環境要素,但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同樣不和諧,只是由于人工干預過多,自然環境中各物種在自組織能力下發揮的作用很小。因此,重塑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關系,要從更宏大的生態文明場域出發,讓人、自然同時參與到和諧關系的塑造中,如我國近年來推廣建設的海綿城市、生態城市等,不僅自然的力量得到了彰顯,且人類也重新回歸到對自然依賴的軌道。通讀全書,作者以平實易懂的文字、嚴謹簡約的表述,為讀者展現出生態美術和人與自然環境和諧關系的融合發展模式,不僅有助于引發人們對“原鄉”的心靈共鳴,喚起人們保護自然環境的意識,也為當代中國生態美術發展指明了方向,進一步豐富了其理論內涵與實踐方法。全書立意深遠、導向明確,研究思想與時俱進,具有重要的學術及應用價值。
作者:郝孝飛 單位:湖北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