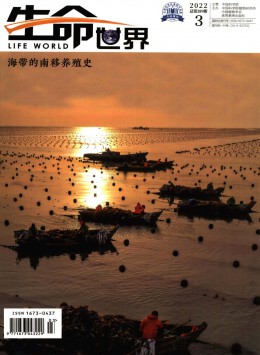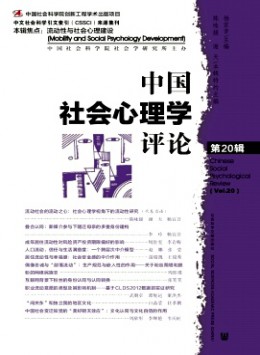建構主義研究范式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建構主義研究范式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關鍵詞:建構主義; 認識論;心理學
一、導言:作為一種新認識論的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觀點增長的表現在其研究角度的增多與地位的提高。現在,已經需要在不同的建構主義觀點中作出區分了。實際上,不同的人說的是不同的“范式”。曾經有人對建構主義作出了不同的區分,比如,社會建構主義、激進建構主義、控制論建構主義,等等。所有的這些范式都反對傳統認識論將知識作為是“實在”的客觀表征。他們的論證很少直接反對傳統認識論的固有概念,而是用另外的概念和觀點去替代原有的理論。建構主義者的“范式”之間也是互相爭論的。
建構主義的先鋒是恩斯特?格拉斯費爾德(Ernst von Glasersfeld),他的“激進建構主義”仍舊激烈地被人們討論。以皮亞杰的著作為基礎,格拉斯費爾德尤其關注個人自律和通過反射和抽象建立概念結構。根據他的觀點,“真正的”學習要將問題作為“一個人自己的問題”,作為阻礙一個人向目標進步的障礙。與這種關注個人的看法距離最遠的是發端于俄國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角度的建構主義。這種觀點強調意識活動中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位置,并且將學習定義為熟悉文化實踐。實際上,處于對立位置的觀點都有其合理之處,很長時間他們都不理會由他方提出的批評。這種現象就像庫恩所稱的“范式的不可通約性”。
在這個領域中,個人的(主體的)觀點與社會文化的(主體間的)觀點之間有著一種張力。這種不同范式尚無定論的紛爭,一方面使得在研究中有機會援引不同的觀點而不多考慮不同角度的一致之處;另一方面,近來它促使了整合不同立場的觀點的努力。實際上,在這場爭論中基本的問題被人們忽視了。為什么建構主義是一種新的認識論?在科學和哲學傳統中它處于什么位置?
對于知識的建構主義理論,人們首先應該澄清基本的觀念。可以確信,建構主義并非是相對主義、反實在論。它也不像懷疑主義那樣懷疑是否存在一個外在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大量的建立在建構主義觀點上的經驗論研究一直明白建構主義的實在論立場。建構主義在其反對長久以來的哲學和認識論傳統背景上有一定的說服力。它認為知識不是實在的表征而是建構。但是實際上,似乎特別難將建構主義與傳統涇渭分明地隔開,因為它的論證幾乎總是處在舊的認識論框架內,它始終沒有擺脫主客二分的傳統框架,而這恰好是建構主義竭力想拋棄的。
二、杜威對建構主義的貢獻
一位用畢生的時間從事知識的建構主義理論研究的哲學家就是約翰?杜威(1859―1952)。正如圖爾敏在杜威的《確定性的尋求》前言中所說的:杜威的著作“與知識論傳統是一個徹底的分離”,顯示出“那個時代幾乎不被認可的一種遠見、洞察力和原創性”。而且,“杜威的分析并不只是破壞性的。它也扼要地提供了對于‘知行關系’的一種積極的觀點。并且,這種觀點也被自然科學本身后來的發展所支持”。[1]在我們看來,杜威的論證也使得對知識的主體的(個人的)和主體間的(社會文化的)解釋能夠在同一個建構主義的框架下考慮。
杜威的著作一方面反對傳統的認識論,杜威將他的批評集中在傳統認識論共同的基礎上,即主體與客體、實在與知識、世界與意識的分離。杜威的知識理論表明以往討論仍然建立在實在和知識分離的基礎上。在更大的程度上,建構主義“范式”仍然與傳統的、二元論的框架緊緊連在一起。他的著作另一方面為建構主義知識論打下了基礎,它使得人們能夠對激進建構主義和社會文化建構主義的主張進行評價。它除了強調個體知識的“建構”,而且強調社會知識的“共建”。這使得對知識的主體的和主體間的解釋能夠在同一個建構主義的框架下考慮。
杜威的認識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的主客二分的模式。在杜威看來,認識論所關心的不只是知識問題,更重要的是認知問題。杜威認為,傳統的認識論在認知問題上是以“知識旁觀者”的理論(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出現的。這種認識論主張,知識是對實在的“靜態”把握或關注。杜威指出,這種認識論在認知上存在兩個缺陷:一是認知的主體與被認知的對象是分離的,認知者如同“旁觀者”或“局外人”一樣,以一種靜觀的狀態來獲取知識;二是認知被理解為一種認識對象呈現給認知者的事件,認知者在認識中是被動的。杜威指出,“知識的旁觀者”理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二元論”,在現代科學面前是站不住腳的。現代科學的發展表明,知識不是某種孤立的和自我完善的東西,而是在生命的維持與進化中不斷發展的東西。杜威指出,知識的獲得不是個體“旁觀”的過程,而是“探究”的過程。杜威認為,“探究”是主體在與某種不確定的情境相聯系時所產生的解決問題的行動。在行動中,知識不是存在于旁觀者的被動的理解中,而是表現為主體對不確定情境的積極反應。知識是個體主動探究的結果。
另一方面,除了強調個體知識的“建構”,杜威的認識論述強調社會知識的“共建”,這使得對知識的主體的和主體間的解釋能夠在同一個建構主義的框架下考慮,在研究中為建構主義增添了新的內容。
杜威的著作對“激進建構主義”做出了分析。在我們看來,激進建構主義的知識理論認為知識是非普適性的、去真理性的,知識不可能概括社會的法則,無個體之外的知識。在討論知識與實在的關系時,它既沒有說明實在與知識的一致得不到證明,也沒有在普遍上承認存在一個外部世界。而是在關于世界是在怎么樣的問題上采取了不可知論的立場。即使使用了像“可行性”或“可相容性”這樣的概念,但它應該指出從什么角度說不存在一致,從什么角度說沒有外在的“客體”。在認識論這方面,杜威的理論提到維果茨基的著作也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它沒有提供另一種解決方法,而是對理想激進建構主義的一種補充,仍是相同的根深蒂固的二元論的傳統。維果茨基的著作形成于笛卡兒和康德的認識論成為很多批評的靶子的時候,笛卡兒和康德知識論的不足在于他們只關注個人意識的自我分析。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引發了知識論理論中的社會維度的嘗試。維果茨基的心理學發展的文化―歷史理論集中于知識獲得過程中主體間向度的作用。在維果茨基看來,知識的獲得與環境的內化是相等的。社會建構主義的取向肯定難以包含個人文化的層次性、差異性以及個人成長史對個人認知的巨大影響力。而且,環境是客觀的結構,外在于獨立于內化過程。
面對建構主義令人不滿意的狀況,旨在協調激進建構主義和社會文化建構主義取向的“平衡”方案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
知識的個體性和公共性是相容的。杜威既認為知識是人不斷發展的活動的結果,又認為它是一種“公眾的”認識論,是一種每個人都可以利用的、公開的求知的方法。通過這種公眾的認識論,在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的過程中,人們自然就能夠獲得共識。由此,在杜威看來,知識雖然是每個個體自己從“做中學”得來的,但在一個民主的環境中,只要通過理性的、“實驗的”方法,每個個體就一個共同的問題是能夠獲得同樣的解答的,這個解答也就是公共的、客觀的知識。[2]
在解釋為什么人類會生活在一個“共同的世界”時,杜威的建構主義既沒有提出一個客觀世界,也沒有假設主體有合適的認知結構。他認為社會互動使得也迫使參與其中的每個人注意其他參與者的貢獻。為了能繼續這種社會互動,一個人不能不觀察和考慮其他人建構的客體和推論。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某種東西“在至少兩個不同的行為中心被共同地創造出來”。[3]有了這種人類的互動,就不難理解主觀實在的存在對共同理解的可能性不造成真正的威脅。彼此理解還意味著“在共同的追求中客體對雙方有共同的價值”。[4]杜威認為為了“在行為上達到一致”,有必要“達到態度上的相似”。他還認為個人實在也通過在共同的追求中獲得同樣價值的方式被改變。需要重點指出的是,雖然行為一致需要個人觀點的充分協調,但是這些觀點會趨于相同。人們繼續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實在中,雖然這種實在為了達到行為上可能的一致,現在已經被完全改變了。杜威認為,“個體通過參與公眾交流和社會生活能夠漸漸達成社會一致共識”。
三、總結
這種“理論實用主義”主要基于各個范式的不足,而不是他們的成就。這是一種協調相反觀點的嘗試。只是在知識與實在、主體與客體對立的二元論的框架中,這些相對的方面才似乎互相中立,協調認知建構主義和社會文化建構主義的取向似乎將兩者都包括了。建構主義理論應該能沿著這些線索詳細地闡述概念。在這點上,建構主義理論或許能證明它的成功。建構主義理論能證明沒有什么理論比建構主義更加實用和有效了。
參考文獻:
[1]John Dewey.The Quest for certainty[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8.
[2]趙 靜.試比較建構主義與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J].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5(03).
[3]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1.
第2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關鍵詞】建構主義;建構主義學前教育范式;物理知識活動;大范疇概念
【中圖分類號】G6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604(2007)04-0041-03
德弗里斯(Rheta DeVries)是當代著名建構主義認知心理學家與教育家,她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致力于把皮亞杰的建構主義理論應用于學前教育實踐,與凱米(Constance Kamii)一起成功構筑了建構主義學前教育范式①,對世界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她們建構的課程中,物理知識活動〔1〕作為兒童智力發展的必要途徑,在建構主義學前教育課程中受到了充分重視。但是,德弗里斯認為,并不是所有物理知識活動都適合作為課程,物理知識活動不僅要滿足對“良好物理知識活動”②的界定,而且要發揮其教育功能,還要符合認知心理學研究的結論。〔2〕如何把皮亞杰的建構主義理論轉化為教育實踐,這一直是德弗里斯關注的核心問題,她在學前教育中運用建構主義的案例為我們透析建構主義學前教育理論及其運用提供了一個思考平臺。
一、建構主義教育的經典案例――兒童對影子現象的研究
德弗里斯從1986年起開始關注兒童對影子現象的探索活動,影子案例成為一項將建構主義理論切實付諸實踐的典型研究。〔3〕在這個皮亞杰式的研究中,德弗里斯把影子的空間因果關系分解為若干變量之間的關系,它們分別是:物體―影子、物體―屏幕、影子―屏幕、光源―影子、光源―屏幕、物體―光源之間的關系。根據這六大關系,德弗里斯設計了26個相關問題(操作任務),然后運用皮亞杰的臨床觀察法和哥特曼量表,詳細剖析了兒童認識影子現象的若干個發展階段(見下表)。
根據對兒童影子認知的研究,德弗里斯確定了影子案例的教學原則:(1)精心選擇開展影子活動的導入性材料,選用的投影物體必須具有容易辨認的獨特外形特征,以便幫助兒童確立物體―影子的對應關系。(2)激發兒童的活動興趣,培養兒童好奇、探究、樂于實驗的品性。(3)創造機會讓兒童分享所知所得,在活動期間提供多種機會讓兒童分享在影子操作活動中的發現,甚至可以鼓勵兒童把自己的發現繪制成“影子讀本”。(4)鼓勵兒童思考如何以獨特的方式讓影子動起來,在挑戰性任務中不斷鞏固兒童對影子現象中蘊含的各種變量關系的理解。(5)接受兒童的錯誤觀念,也就是說要接受兒童的發展現狀,依據對兒童的發展性分析,適時評估并及時引導兒童。〔4〕
二、建構主義教育的發展――斜坡與軌道活動
從影子活動開始,德弗里斯對建構主義教育有了更為深刻的思考。尤其是在物理知識領域,德弗里斯一直在尋求一種比影子活動更具縱橫拓展力的活動,她把這種活動表述為大范疇概念(big ideas)。這一概念指的是活動設計要具有挑戰性和綜合性。從課程角度出發,建構主義的深層含義是具有發展意義的大范疇課程,即要將游戲和學科活動綜合起來,既能涵蓋語言、美術、數學與科學等學科知識,同時也能協調兒童知、情、意等方面的發展。在這個前提下,德弗里斯開始研究斜坡與軌道活動。〔5〕
1978年,凱米與德弗里斯兩人合著的《早期教育中的物理知識活動――皮亞杰理論的應用》一書中曾專門設計并論述過教室中的斜坡活動。在這個活動中,斜坡被做成很寬的固定高度的用具,兒童在同一或不同斜坡上試驗棒球的運動狀況。在后繼研究中,德弗里斯利用斜坡材料與形狀的多樣化、小球大小的多樣化以及目標容器形狀大小的多樣化,繼續發掘斜坡與軌道活動在促進兒童空間關系協調上的價值。
隨著德弗里斯研究思想的不斷深化,斜坡與軌道活動開始具有新的課程與教學涵義,活動內含的復雜程度大大增加,承載了建構主義教育的大范疇課程理念。
影子活動中的變量只有三個,即物體、屏幕與光源,而斜坡與軌道活動中蘊含的關系更為復雜。斜坡與軌道活動本身就是斜坡與軌道兩大物理活動的組合,斜坡的傾角、長度、斜坡的組合形式,場地的光滑程度,球的形狀、重量等都成為活動中的變量,再加上軌道的變化,兒童在活動中需要涉及與協調的關系千變萬化,比如斜坡斜度與小球滾動速度之間的關系,斜坡斜度與小球滾動距離之間的關系,軌道連接與物體運動持續性之間的關系,不同軌道組合或斜坡組合與小球運動方向之間的關系,在不同形狀或大小的軌道上滾動的小球與軌道/斜坡之間的關系,等等。在一個活動中能夠蘊涵如此多的關系,為兒童提供的建構空間也會更大,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兒童都能在斜坡與軌道活動中找到無數自我挑戰的機會。
三、從“影子”到“斜坡”――建構主義理論在學前教育中的發展變化
從影子活動開始,以德弗里斯為代表的建構主義理論流派開始重新強調結構論,而且隨著研究的深入,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德弗里斯日益強調在更廣泛的教學內容中應用建構主義理論。德弗里斯認為,更為廣泛的具體教學內容應該成為兒童建構認知和情感的豐富源泉。隨著對兒童社會道德氛圍研究的深入,德弗里斯越來越堅信,對兒童自主性的培養應該成為建構主義教育的核心,而自主性的培養不會只囿于材料,甚至不會囿于課程,它應該在生活中無處不在。
1987年,以建構主義理論為主要理論基礎的全兒教育協會(NAEYC)提出了 “發展適宜性方案”。這個方案在美國乃至世界學前教育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很多人批評NAEYC的建構式價值判斷僅停留在“應然”而非“實然”的狀態,最終促使NAEYC修正了對發展適宜性教育的某些解釋:發展適宜性教育不是課程,也不是一種僵死的期待;它并不意味著教師不要去教兒童,也不意味著讓兒童去控制教室活動;它并不排斥課程目標,課程也并不是必須由兒童生成;它并不適用于所有兒童;課程不等同于兒童發展。〔6〕NAEYC對發展適宜性教育的修正與德弗里斯對建構主義教育的反思不謀而合。在作為心理學家的“應然”與作為教育家的“實然”之間,德弗里斯最終朝后者跨出了一大步,這標志著以德弗里斯為代表的建構主義教育流派向更務實的方向發展,開始更多地考慮課程與活動的綜合性。德弗里斯承認,建構主義教育同樣需要兒童掌握基本的聽說讀寫技能,因此,她把數學、閱讀、寫作、繪圖、社會道德氛圍等納入了斜坡與軌道活動,大大提高了斜坡與軌道活動的課程價值與教育意義。
從“影子”到“斜坡”,反映了建構主義理論在學前教育中應用的發展軌跡,從中可以看出建構主義理論對時展需要的切實回應。但從另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到,建構主義理論并不容易讓人理解與實踐,“讓兒童自主建構”往往在實踐中會成為一種泛化的口號。對學前教育研究者和實踐者來說,真正理解并在學前教育中貫徹建構主義理論仍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參考文獻:
〔1〕C KAMII,R DEVRIES.Physical knowledge in preschool education〔M〕. 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3.
〔2〕DEVRIES,BETTY ZAN. Developing constructivist early childhood curriculum〔M〕.Teachers College Press,2002.
〔3〕DEVRIES R. Children’s conceptions of shadowphenomena〔J〕.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1986, 112 (4):479-530.
〔4〕DEVRIES,KOHLBERG L.Constructivist early education:Overview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programs〔R〕.NAEYC,1990.
第3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主題詞社會建構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代主義的產生體現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這種反思,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已進入后現代社會時期,在后現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及現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決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2.建構主義學者在地理分布上較為廣泛。建構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觀點、方法來源不同,很難像科學學(代表人物是英國的貝爾納)、傳統科學社會學(代表人物是默頓)追塑到某個國或某個代表人物,其成員分散在歐美不同國家。在英國,主要是愛丁堡學派,其成員是埃奇、布魯爾、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們從批判傳統知識社會學,特別是曼海姆思想出發,并從庫恩思想得到啟發,對科學知識的實質進行研究。在法國,拉圖爾、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爾、福柯的本土方法對科學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的考察。在美國,謝廷娜(一位建構主義女學者)、陳誠、瑞斯蒂等也進行著與拉圖爾類似的工作。另外,英國的馬爾凱、伍爾加,美國的平齊、休斯,荷蘭的比克,德國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學者都在從事不同的建構主義研究。當然,建構主義既然以一個思想學派出現,也存在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圖爾與伍爾加合作考察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共同發表《實驗室生活》一書,謝廷娜和馬爾凱一起主編《觀察到的科學》一書等等。
3.建構主義研究方法多樣化。盡管建構主義是建立在知識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一總觀點之上的,但其方法卻是經驗的。這樣,建構主義研究方法便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實驗室研究,由拉圖爾、伍爾加發起,像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保持一種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根據觀察日記進行研究;爭論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從微觀角度分析科學知識如何達成一致;話語分析(或稱修辭學方法),由馬爾凱等人發展而來,把科學活動參與者的“日常話語”作為主題,分析科學解釋是如何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在對技術的社會研究中,建構主義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會建構方法,這是平齊和比克把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引入技術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技術人工制品如何在社會、文化方面得到解釋;系統方法,休斯在技術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術看作一個系統(如電力系統),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的分析;操作子網絡方法,它與拉圖爾、卡隆、勞等人的研究工作相關,他們把技術、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看作整體的“異質操作子”網絡,分析技術在其中的作用。另外,愛丁堡學派早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以及隨后的弱綱領也都是建構主義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構主義這種經驗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特點,導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統一的理論凝聚。目前建構主義的各種觀點和學術成果,散見于有關學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種論文集里。拉圖爾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是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考察的結果,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也不過是對這種考察的進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觀察到的科學》以及平齊和比克主編的《技術系統和社會建構》等則均為集納諸多建構主義學者及相關學者經驗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因此,建構主義的學術觀點具有相當的分散性。
二
建構主義研究就其建構對象而言也呈現出某種復雜性。在建構主義的視野中,似乎借助行為者的互動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識、方法、學科、習俗和規則),科學家基于數據和觀察構造的理論和敘述,實驗室中由于物質參與而產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體都是建構成的。但是,從這種復雜性中仍可窺見出建構主義存在著強與弱的分野。
1.弱建構主義。弱建構主義強調的是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或社會原因,主要著重于宏觀社會學的把握,但并不否認其客觀性或邏輯性的原因。
這類建構主義觀點最早見于貝格爾和魯克曼的知識社會學論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現實的社會建構》一書中,他們提出現實是社會地建構成的,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社會建構過程。這里的現實是指主觀現實(即人們關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觀現實。所謂現實的社會建構就是這種主觀現實作為人工的產物雖然獨立于我們的意志,但都是在社會情景中發展、傳輸和保持的。[1]就是說,要建構其中某種主觀現實X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識,這種知識即便在X不存在時,也能產生某種行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識;(3)傳播X知識的手段。只要具備這些條件,X的知識便可在社會共同體“固定”或普遍存在下來。在貝格爾和魯克曼的建構意義上,社會中有許多東西如習俗、規則、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權力、科學等等都可看作是社會建構的。
當愛丁堡學派沖破傳統知識社會學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明顯區分后,巴恩斯、布魯爾、柯林斯等采取了與貝格爾和魯克曼相類似的方法來考察自然科學知識,即用社會背景來解釋科學知識內容。巴恩斯在論及庫恩對科學知識結果解釋的批評時說:“他所描述的科學中基本理論的變遷,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的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2]也即是說,既然自然科學并非以純結果的方式變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學知識的產生及其維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會背景。巴恩斯引進了“利益”概念,布魯爾認為除了一些社會原則外,還包括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物學的、認知的和感覺經驗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個“非科學”的標準清單:“基于從前合作對合作者實驗能力和忠誠的信任、實驗者的個性和智力、管理大實驗室的聲譽、科學家是否在工業界或學術界工作過、過去的失敗經歷、內部資料、科學成果的風格和表現、實驗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盡管愛丁堡學派的工作是建構主義的,但并沒有使用“社會建構”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會建構”一詞進行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孟德爾遜和達勒。他們的論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爾遜、魏因加特和懷特利主編的《科學社會學年鑒》第一卷,取名為“科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孟德爾遜和達勒認為,現代科學的建制、認知和知識主張并不能通過科學史論得到適當的說明,它們作為人工的產物必有其社會因果關系,因而是社會建構成的。
孟德爾遜等用“社會建構”批評科學史論的不適當性在今天看來雖然已無必要,但卻激起了對科學話語、文本的建構主義研究。以往的科學史論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學家的論著或談話錄、回憶錄為依據的。而馬爾凱則認為科學家的話語實際上變化很大,其內容和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談論者面對面的互動,因而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可以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建構的社會特性。馬爾凱和吉爾伯特通過對一個生物化學小組的34名有建樹的研究者的訪問,把科學家話語分成經驗性的和偶然性的兩種情況。結果發現,科學家在解釋正確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經驗性話語,而在說明錯誤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偶然性話語,即把科學家犯錯誤的原因歸于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偶然因素。[4]
邁耶斯在《寫作生物學: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的文本》一書中試圖表明,社會的考慮(主要是考慮讀者的鑒賞和興趣)怎樣“構成”科學主張、討論和論文或專著的寫作。他說:“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點是假定科學是在論文或見解修改和爭論反語重釋的聲言和協商的社會過程中建構的。對于這一基點,讀者將會感到驚異。”[5]這里,邁耶斯似乎指明,科學文本的社會建構是說它在公開發表之前就經過討論、協商、改變和削弱等,科學文本不僅源于客體素材,而且也經歷了科學家和評論者的審視。
可以看到,弱建構主義在探討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時,往往給科學的客觀性、理性和邏輯因素留有適當的余地。布魯爾的強綱領中的公平性、對稱性原則實際上要求對科學的真理和謬誤、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敗都做出說明,馬爾凱在歸納經驗性話語時則說明了實驗數據是在邏輯和時間優先情況下給出的。另外,愛丁堡學派并沒有回答在什么時機,讓社會背景因素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中。這就是有些強建構主義學者為什么并不把弱建構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研究的原因。
2.強建構主義。強建構主義是在微觀層次上對科學知識所做的經驗研究,認為科學知識或技術人工制品能夠顯示出其建構完全是社會性的。這類學者主要是謝廷娜、拉圖爾、伍爾加、平齊、比克等人。
謝廷娜將其工作貼上“建構主義”的標簽,而非“社會建構主義”。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將其研究同“社會背景”之類的東西聯系在一起,以示同愛丁堡學派的工作相區別。謝廷娜認為微觀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爭論研究,說明知識的一致性是如何達成的;其二是選擇科學工作的真實地點如實驗室作為研究對象,說明科學知識是怎樣建構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稱其研究成果為建構主義綱領。她歸納了科學建構的社會特征,即科學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現實”,而是指向陳述的操作,這種操作不僅使科學家進入大量面對面的協商和互動,還包括更廣泛的、超越處所的關系,與經紀人、工業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發生聯系。[6]
與謝廷娜一樣,拉圖爾也想避免將其建構主義研究同“社會背景”相提并論。他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標題是“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當1986年再版時把其中的“社會”一詞刪去了。但不管怎樣,該書的主題仍然指明:科學事實是一種建構的產物,是各種利益集團間協商的產物。通過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拉圖爾及其合作者伍爾加用整整一章專門論述了TRF(促甲狀腺釋放因子)的建構過程。[7]
在對《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合作之后,拉圖爾與伍爾加的研究綱領開始分道揚鑣了。拉圖爾轉向了操作子網絡,把其中的科學家當作“資源積累者”進行了“馬基雅維利”式的描述。[8]由于這一綱領不再具有明顯的建構主義風格,這里不加論及,與此不同,伍爾加卻對表象進行了建構主義的研究。
概括地說,客體(自然世界)與表現(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包含兩種圖式:
(1)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2)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第一種圖式認為客體獨立于表象,自然知識似乎與自然世界沒有多少關系;第二種圖式表明表象是客體的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識與自然世界之間沒有誰是第一性的、誰是本質的區別。伍爾加認為,前者是過去的科學社會學(包括愛丁堡學派)堅持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和本體論上的實在主義”圖式,后者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應遵循的模式。[9]對此,他提出兩條證據。首先,沒有表象,客體就是無用的,我們無法獨立于客體。其次是對同一客體的解釋存在著某種“柔性”,即科學陳述的多樣性,這導致人們去懷疑任何“假定”的客觀事物的存在。在這里,伍爾加是想說明表象構成或建構了客體,即世界是被建構著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學知識社會學已經成功地披上建構主義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標題或導言紛紛以“……的社會建構”而呈現于世。就是對技術進行社會研究的人們也未能逃脫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齊在《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一書中希望提倡一種新的建構主義研究綱領。
誠如前面所言,《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并不代表一種一貫的研究綱領。這里將集中考察平齊和比克的論文《事實與人工制品的社會建構:或者科學社會學與技術社會學怎樣得到互惠》。在該文中,他們提出了與布魯爾幾乎相近的“建構主義強綱領”:“在這一綱領里,所有知識和所有知識假設都將被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就是說,關于知識假設的起源、接受和拒絕的全部解釋都可以從社會世界領域尋找得到,而無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過,他們卻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的一些概念,并稱之為“技術的社會建構方法”:“這一方法的關鍵概念是‘解釋柔性’、‘終止機制’的‘相關社會群體’。其核心信條之一是技術人工制品對社會學分析是公開的,這不僅表現在技術的使用上,而且特別關及其設計和工藝‘內容’”。[11]平齊和比克用這種方法說明了自行車的歷史,表明了自行車是試錯的產物,新的嘗試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解決這個或那個社會群體提出的問題。因而每種技術產品都是“決定滲透”的結果,而非單向模式發展的邏輯程序。
總之,強建構主義雖然都標謗自己是完全的建構主義,但最終都是以對微觀社會學問題的關注來解釋宏觀社會學的構架。這一點從謝廷娜、伍爾加、平齊和比克的觀點可以明顯看出。特別是謝廷娜以實驗室活動為基礎來展示科學知識和建構與社會存在著的廣泛聯系,試圖消除科學知識發展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學知識發展的認識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數科學社會學家和“理想”,又說明強建構主義與弱建構主義不無兩致的“模糊性”。
三
簡單地說,建構主義尖銳地批判了個人主義的、觀念論的、實證論的和樸素實在論的科學或技術說明。他們對科學技術事業的因果解釋的社會資源的展示和說明,擴大了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但是,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傾向或理論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會偶然性因素。建構主義研究實際上是把科學技術的本體論相對化,以及把社會因素理性化。弱建構主義者,特別是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一方面想使它成為社會學乃至全部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成為理性和科學的體現,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否認科學知識與一般知識的區別,使科學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學。強建構主義者則是在強調科學或技術的社會建構的同時,把客觀的自然因素放置一邊。謝廷娜、拉圖爾等人提倡用參與式觀察對科學家的廣泛訪問來理解科學,但對自然界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的認識,卻僅僅停留在關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語言建構之上。而平齊、比克的研究則表明,技術社會學應著重于社會因素怎樣建構人工制品,而對技術的工藝內容可以置之不顧。建構主義這種對科學技術產生所做的過份的“社會學簡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殺了科學技術的本體論方面的因素,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物質基礎,從而把科學技術看成完全由各種社會偶然性因素組成的東西。
應該說,在當代有關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文化爭論中,建構主義有著強烈的后現代主義傾向。后現代主義者以對真理、客觀性、因果性、合理和進步等的懷疑和批判為特征。鑒于強建構主義堅決地解構了科學合理性觀念本身,那么強建構主義實際上就成了通往后現代主義一邊的橋梁。但對于弱建構主義,有的學者認為它致力于對科學的宏觀因果解釋,因而應被劃分到現代主義一邊。可是,如果考慮到并不是所有后現代主義都強調對現代科學的解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了繼承現代主義但又超越現代主義的“建構性后現代哲學”,[12]則恐怕弱建構主義也逃脫不了與后現代主義的干系。更何況弱建構主義也有著割裂科學與理性之嫌。
2.對于科學技術的解釋范圍較為狹窄。強建構主義研究過份強調實驗室、人工制品在理論上的重要性。如拉圖爾對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雖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家的行為,但這種微觀研究與科學的組織、結構、共同體等宏觀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平齊、比克在進行技術社會學研究時對相關社會的社會群體的關鍵作用給予了充分關注,但對技術發展有著強烈影響的經濟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觀條件均未被列入技術的社會建構研究的議事日程。至于弱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雖然貌似新鮮,其實在默頓的大部分科學社會學研究中都已論述過。早在1945年,默頓就描述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程序,說明了可以作為社會學分析的精神產品應包括信仰、意識形態、宗教道德及實證科學,還分析了精神產品的存在基礎,如群體結構、權力結構、競爭、沖突和利益等。
3.忽視科學技術后果及其評價。建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適合于解釋科學知識的起源和技術創新的動力,以致對于科技產品對人的自我意識、社區組織、日常生活、權力分布有何特別意義的問題很少給予關注。在許多建構主義者那里,關于科技成果的研究進入“死結”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學技術選擇的社會后果幾乎完全置之腦后。
與此相關,建構主義還貶低對科學技術的道德評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綱領在對待科學發現、科學理論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態度,即認為科學本身無所謂惡,是價值中立的。平齊、比克將柯林斯的綱領外推用于技術的社會研究時,對技術成果的最終善惡又采取了不可知論的態度,因而不去探討有關技術的地位、技術選擇的正誤這樣的問題。不管怎么說,建構主義開創的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新方向,對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技術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有著莫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P.L.BergerandTh.Luckmann.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inSociologyofKnowledge.Doubleday,1996,2—3.
[2]J.R.Brown(ed).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7.
[3]H.M.Collins.ChangingOrder,SagePublication,1985,87.
[4]J.PotterandM.Wetnerell.DiscourseandSocialPsych-ology,SagePublication,1987,chapter7.
[5]G.Myers.WritingBiology:TextsintheSocialConstr-uctionofScientificKnowledge,the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1990,141.
[6]K.D.Knorr—Cetina.TheManuf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7]B.LatourandS.Woolga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105—150.
[8]B.Latour.ThePasteurizationofFra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8.
[9]S.Woolgar.Science:theVeryIdea,EllisHorwood,1988,54.
第4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關鍵詞: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范式;本質主義;社會建構主義
教學與科研關系對于現代大學而言具有基礎性地位。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比喻說,傳統大學只是一個“村莊”,而如今的大學則是一個變化無窮的“城市”。作為變幻的“城市”的大學是一個多元的機構,它具有多種社會職能(這些職能還處于不斷地擴展之中),即“它標志著許多真、善、美的視野以及許多通向這些視野的道路;……標志著服務于許多市場和關注許多公眾”[1]。可是,不管“城市”如何地變幻無常與移形換影,其基本的元素和基本的框架構造依舊。這些最為基本的元素就是教學和科研。教學、科研構成了大學這座“城市”所有活動的基礎,而教學與科研之間的不同關系形態則是大學這座“城市”框架的基本景象。與克爾把大學看作是“城市”相類似,巴尼特(Ronald Barnett)認為,大學是一個活躍的變化的空間。大學空間中的教學、科研、管理和服務等是不斷變化的次級空間,這些次級空間的不同組合型構著大學空間的樣態。教學與科研是大學最主要的空間。教學與科研都是變動的,二者的關系也在變動。教學與科研這兩個大學的主要空間有時分離,有時結合,有時甚至重疊。作為大學空間的主要建筑材料,教學與科研關系的不斷變化使得大學空間的樣態呈現出多樣性。[2]因此,伯頓?克拉克(Burton R. Clark)說:“在現代大學教育中,沒有任何問題比教學與科研之間的關系更為根本。”[3]
正因為教學與科研關系之于現代大學的重要地位,這一問題引起了學者持久的關注。學界較為集中研究這一課題,大致是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研究的主要集中地是北美及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同樣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也已開始關注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問題。[4]到目前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可以被歸入兩種研究范式,即本質主義范式和社會建構主義范式。前者旨在發現教學與科研之間內在的確切關系,而后者則試圖描述與闡釋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社會建構性。
一、本質主義的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
本質主義是一個集合的概念,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都以普遍性、統一性和確定性為目標,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著一個深藏于內在的唯一的本質,這種本質是固定的和不變的。本質主義還假設,本質和現象的區分提供了人類觀察萬事萬物的基本圖式,人類認識特別是現代以來所謂科學認識的任務就是要透過現象揭示與發現事物的唯一本質。相應地,本質主義的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相信教學與科研之間存在精確的內在機制或結構,這些古老的機制深埋于地下并正等待著教育考古學家去挖掘。學者們所要做的就是要通過盡量科學的方法,去發掘這種確定的機制。
本質主義范式的研究主要有兩類: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相關性研究,以及關于師生教學與科研關系認識和感受的經驗研究。相關性研究多是以學生對于教師教學的評價作為教學效果的得分,以教師科研成果的數量及加權的引用率等作為科研得分,并計算它們的相關性。這種研究主要盛行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5]近幾年來,我國也出現了一些類似的研究。[6]但是,這些研究的結論并不一致,有的研究發現二者是高度正相關,有的則發現是微弱的正相關,有的是零相關,有的則是負相關。例如,瑞奇和羅什(Riech & Rosch)的研究結果為0.517,而拉姆斯登和摩西(Ramsden, P. and Moses, I.)的研究則發現科研和本科生教學之間存在負相關或者零相關。[7]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相關性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些局限,如對于“教學”和“科研”的界定過于狹窄――研究中的“教學”基本上指課堂教學,“科研”多指發表的論文或課題,其實真實的“教學”和“科研”都遠遠不止這些;相關性研究把教學和科研都作為靜態的事物來測量,與二者動態的本質是相悖的;等等。這使得人們開始關注師生對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認識和感受,以此試圖了解真實教育生活中的教學與科研關系。
同相關性研究的結果一樣,研究者同樣發現了多樣的教學與科研關系,教師對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認識和感受因學科、年齡、職稱等的差異而不同。羅伯遜和邦德(Robertson,J. and Bond,C.)的研究是此類研究的代表。他們在對澳大利亞9位大學進行半結構化訪談的基礎上,發現教師感受到了五種教學與科研關系,分別是:科研和教學是彼此矛盾的活動;教學與科研沒有或只有很小的聯系;教學是傳遞新的科研知識的方式;教師是科研或探究式學習的榜樣,鼓勵著探究性的學習;教學和科研在學習社群中存在一種共生的關系。[8]在之后的一項研究中,他們同樣發現了五種教學科研關系被感知的方式,并且這些關系與一定的學科相關(見圖1)。[9]國內學者的研究也發現,在教師的日常實踐中,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樣態呈現出四種模式:從教學與科研相關聯的形式上來看,存在著從內容、方法到精神文化等的變化,也就是說存在著一個從顯性聯系到隱性聯系的連續體;從教學與科研相關聯的程度上來看,存在著從很弱的聯系到比較強的聯系以至很強聯系的連續體(見圖2)。[10]
上述兩類本質主義范式的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性質上是存在著很大差異的:前者注重定量研究,后者注重定性分析;前者主要采用調查和數量統計的方法,后者主要采用現象圖式學和經驗場分析等質性研究方法;前者的研究樣本較大,后者多是小樣本;等等。但是,這些研究都假設教學與科研之間存在較為確定的關系,并試圖找出這種確定的關系。當然,相關性研究是最為極端的一類,它們相信教學與科研存在一種可以用數字精確表示的關系,并認為這種關系是確定無疑的。其他研究也確信存在某種一致的關系。可是,這些研究都沒有獲取確定的結論。大致來說,這些研究的結論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類觀點認為,教學與科研是一體的。這種觀點認為,在教師實際的日常生活中,教學與科研無法截然分開,它們是同時開展的,是同一過程的不同方面,也是同一水平能力的不同反映,是結合在一起的學術活動。經典的說法,是將教學和科研描述為“一個工作的兩個方面”[11],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這種觀點認為這兩種活動是無法分離的,在現實中是交織在一起的。
第二類觀點認為,教學和科研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這種觀點雖然承認二者是不同的活動,但強調二者之間存在微妙的、擴散的積極效應,一種活動的開展也必然帶來另一種活動的效果的提升。所以,里瑞(Leary, L.)說,“學術并不與教學的人不同”,并且“事實是,我們最好的教師幾乎毫無例外是最好的學者”[12]。這種觀點是一種最為普遍的觀點,即雖然承認教學與科研有區別,但堅信二者存在一種互惠的關系,彼此促進。
第三類觀點則認為教學與科研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教學和科研需要不同的智力特征和個性品質,教學和科研是不同的人所從事的工作。即使有少數人能兼顧教學和科研,但他們的教學和科研活動之間并不相干。巴尼特認為,作為研究者,學術人員居住于波普爾(Karl Popper)所謂的世界3;作為教師,他們卻在世界2中工作。[13]也就是說,教學和科研要么存在于不同的教師身上,要么是這些教師在一種情況下或者某些時段從事教學,而在另外的情況下或時段從事科研,而他們的教學與科研是沒有任何干預或者促進關系的。
第四類觀點認為教學與科研是相互沖突的活動,彼此干擾。這種觀點的理由有:(1)教學和科研具有不同的期望和義務。考慮到教師的傾向和投入,兩種角色被認為是持久的緊張關系,教學與科研是彼此矛盾的活動。(2)大學組織天生的激勵機制更重視科研而不是教學,所以這兩種活動存在內在的沖突,不存在相互促進的關聯。(3)以上理由都認為教學與科研之間的沖突是內在的――無論是教學與科研本身性質的還是組織自身的。但是,特恩斯(Turns,S.R.)認為這種沖突不是內在的而是外因造成的。他認為教師進行教學和科研的動機是同樣強烈的,但是,科研能帶來很高的聲望,而與教學相聯系的聲譽往往很少,這就可能會造成與教學的沖突。[14]
本質主義范式的研究,旨在發現教學與科研的本質關系,卻增添了諸多相互矛盾的經驗事實和更多的爭論。學者們逐漸認識到,也許教學與科研關系根本就不是某種確定性的關系,本質主義范式的研究也就此式微。
二、社會建構主義的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
近來的一些研究,則轉向了社會建構主義范式。社會建構主義范式的研究強調學術工作的社會適應性和歷史性,而反對本質主義所強調的客觀主義立場;社會建構主義的研究強調社會過程,而反對本質主義因過于關注個體的認識或感受而隱藏了這種經驗與感受的社會建構過程,以及個體觀點的變化;社會建構主義的研究在方法論上舍棄了本質主義的個體主義傾向,而轉向了整體主義。這些研究主要分析了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社會性”和“建構性”,強調教學與科研關系的變動性、社會制約性和建構性。
社會建構主義范式的研究,試圖揭示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社會性。通過研究,學者們也確實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結論。這些結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高等教育政策與體制對教學科研關系的影響深遠。泰勒(John Taylor)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了英格蘭和瑞典四所大學教學與科研的關系。他們發現環境因素尤其是不同的高等教育體系和政策環境,對于大學教學與科研的處理具有大的影響作用。在瑞典,沒有一個學術人員質疑二者的聯系及相互支持作用,并且教師們感覺自己有義務加強二者的聯結以吸引學生。在英格蘭,多數教師則認為教學與科研存在沖突,二者在時間和資源上相互競爭。教師也并沒有有意地加強二者之間無縫的、結合為一體的、互惠的關系的努力。[15]國內有研究發現,大眾化、功利性的大學評價體制和社會價值觀對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性質及其處理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很多老師抱怨說,現在的課堂過大,以至于教學效果很難提高,對于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也難以進行;多數教師認為,目前國家對于大學的評價體制,使得大學和教師必須極力重視科研產出,只有如此,學校才能在聲望、學科建設及經費方面取得優勢;一些教師還注意到,目前國家所處的發展時期,決定了功利性的科研受到重視,而忽視了長久的人才培養。[16]
第二,大學組織制度對教學與科研關系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國內學者的研究發現,四成以上的教師認為對教學科研關系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學校與院系的政策。也就是說,組織制度較之個人偏好、學科性質及國家政策與學生需求而言,對于大學的教學與科研關系具有更直接、更強大的影響。目前,我國大學由于存在對“一流”目標的盲目追求,以及教師評價考核機制和教學管理方式等方面的組織制度問題,已經導致教師背離了“教學與科研相統一”的信念。[17]
第三,組織和學科文化對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影響巨大。蒂姆和盧卡斯(Deem,R. and Lucas,R.)的研究發現,高等教育宏觀政策不僅影響了大學層面的制度,而且深刻影響了院系的教學文化和科研文化。這種院系的文化在教師的行為上得到了體現。[18]盧卡斯等人(Lisa Lucas, Mick Healey, et al.)使用多層次比較的方法,對英國3所大學共9個院系的教學與科研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組織或院系文化及學科對于教師教學、科研及二者關系的感受與經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19]院系文化多與學科有關。同院系文化對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影響相一致,學科不同,教學與科研關系有所差異。科爾貝克(CarolL. Colbeck)就發現,軟學科(如英語)的教師結合科研與課堂教學比硬學科(如物理)教師更容易。[20]
上述的研究發現,教學與科研關系受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影響。也正是基于這樣的發現,近年來,一些學者改變了思路,即從“被動的制約”到“主動的建構”。他們認為,不要再糾纏于教學與科研關系到底是什么及其歷史變化,與其這樣,我們不如基于一種更為實用的立場,那就是停止關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爭論,而去探究如何改善教學與科研關系。博耶(Boyer, E, L.)相信“是時候遠離令人厭倦的、陳舊的關于教學與科研的爭論了”[21]。他認為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擴大“學術”(scholarship)的范圍,將“綜合”、“應用”、“教學”的研究納入到“學術”的范疇之中,并且與經典的“發現”研究相提并論。博耶認為四種類型的“學術”,既有不同的性質與功能,又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諾依曼呼吁要“理清什么是教學、科研,以及二者的范圍,尤其是‘學術’的內涵及其與教學科研的關系”[22]。而布儒和邦德則認為只有強調“學習”這一中介,教學與科研關系這個越來越無結果的爭論(increasingly sterile debate)才將變得重新以有結果的方式被關注。[23]布儒和邦德的“學習”概念,在伯頓?克拉克那里則是“探究”。他指出“需要超越教學和科研的二分法”,要拒絕教學與科研不相容的理論,而呼吁探究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參與科研或探究也就是一種形式的教學。[24]
一些學者從國家層面以及國際學術社群的層面提出了一些具體的策略,如建構學術共同體、改變國家高等教育治理方式、改變資助與評估體制等等。我國學者李澤、曹如軍提出要建立高等教育分類撥款制度、建立高等教育多元評價制度并改革教師管理制度與學生培養制度。[25]而李健則從更廣泛的范圍內討論對策。他認為加強教學與科研的融合,不僅要加強高校內部科學研究與教學工作的互動,而且還要促進產業界、高等教育機構和科學研究機構的產學研合作,并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26]
更多的研究,則是從組織運作的角度,提出了改善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策略。詹金斯和赫利(Jenkins,A & Healey,M)提出了四類提升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策略:提升組織使命和意識;發展課程以提升聯結;改善科研政策和策略以提升聯結;改革教師發展制度并變革大學組織以提升聯結等。每類策略又分為多種具體的策略。[27]洛克(William Locke)則認為政策制定的核心在院系。因此要從院系入手,改善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如院系領導需要考慮能否及如何做到以下幾點:減少一方對于另一方的負面影響,時常是科研對教學的影響;一體化處理教學與科研策略;真正結合教學、科研等活動。當然,作者還認為,這最終需要國家在政策層面進行一些平衡二者的制度設計。[28]詹金斯等人也提出了從院系層面改善教學與科研關系的十個策略。這些策略包括院系的人事制度、評價制度、課程建設和文化建設等方面。[29]一些研究還專門關注到了課程設計這一點。赫利和詹金斯等人認為“課程應該處于教學與科研聯系的中心地帶”,并通過案例研究,得出了一些從課程角度提升教學與科研之間關系的策略。[30]我國學者則提出:要進行校內分工,教師可以側重教學或者科研;對教師在教學和科研上應有不同的要求,并應建立科學的教學與科研評價機制;建立學術本位的管理體制;實行研究性教學;等等。
三、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的深化
教學與科研關系是現代大學的根本問題,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關于教學與科研之間到底存在何種關系,以及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一直是高等教育界的重要課題。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大眾化、市場化的推進,教學與科研關系問題更是成為研究的熱點。到目前為止,相關研究已經很多,但可以從研究的思維方式和范式的角度劃分為本質主義的研究和社會學建構主義的研究。本質主義范式的研究試圖探尋教學與科研二者確切的、固定的本質關系,而社會建構主義的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則更多地把這一問題放在特定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中,進而去分析其社會建構性,是關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社會學研究。
本質主義范式的研究持有很強的基礎主義,傾向于用簡單的方式看待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很多人所使用的“nexus”一詞本身就潛在地假設了具體的和單一的教學與科研關系。即使一些研究者并沒有假設存在一種特定的“關系”,而是發現了多樣性的聯系,但這些研究的結論多是顯而易見的。即它們常常發現:在一些情況下科研對教學有積極影響,在有些情況下沒有;學生有時歡迎教師科研,有時則抵制教師參與科研;一些最富有啟發性的教師可以是研究者,但并非都是如此;一些最為出色的研究者是好教師,但并非所有都是。[31]可見,本質主義范式的研究,并沒有獲取所謂的“本質”,研究并沒有普適的解釋力。
因此,更多的學者已經逐步舍棄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進而轉向了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社會建構主義,更多地運用社會學的思維和方法進行研究。在未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需要更多地進行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社會學研究。可是,目前已有的社會學取向的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至少存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大多研究缺乏理論,存在理論匱乏的現象。在已有的文獻中,少有文獻基于某種理論開展研究,而是僅僅直接運用訪談和文本分析等方法進行經驗研究。經驗研究雖然增添了事實材料,但這些材料越來越多,且相互之間存有矛盾,這使得逐漸匯集起來的材料雜亂地堆積在一起,而不能解釋現實和指導未來。因此,需要找出一些解釋力較強的理論去分析和處理這些材料,并且建構未來的實踐。
第二,多數研究都持有常規的思維方式,即假設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可以而且應該更好地結合起來,卻沒有涉及為何要結合二者。基于此,很多研究都試圖尋找出提升教學與科研聯結的方式。但是,分離可能帶來的益處卻很少涉及。結合二者所帶來的問題以及這項工作的困難也沒有涉及。
第三,多數研究都采取了一種“制度―實踐”的分析框架和思維路徑,而且,這種分析框架強調的是“強社會、弱行動”,即一般都是分析國家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大學組織制度和文化、院系制度和文化等如何改變了教師的認識和行動,而較少涉及教師如何從行動上建構制度。可以說,已有的研究更多地強調了社會對個體行動的制約,而忽視了個體的能動性。
基于已有研究的成果及其局限,本文認為,應該以社會建構主義為研究范式,不僅要細致地闡釋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社會性,更要分析行動者的行動和學校制度的變革如何影響并改善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樣態。在深刻理解教學與科研關系的主體建構和社會制約的雙重性的基礎上,去建構理想的教學與科研關系。教學與科研關系也就成為了更為實際的、以制度和行動變革為導向的院校研究課題。這就要求大學要清楚教學、科研及二者關系運作的現狀,獲取大量的數據,在此基礎上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善的方略。而各類型院校甚至各個院校都有自身獨特的現狀,面臨獨有的問題,大學管理者和全體教師需發揮自身的創造力和想象力,進行制度重建和實踐革新。通過不斷地摸索,真正使得教學與科研的相互關聯成為師生真實的經驗。
參考文獻:
[1][美]克拉克?科爾.大學之用[M].高■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77.
[2]Barnett,R(Ed.)(2005) .Reshaping the university: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teaching, Pp2-6, Maidenhead: McGraw-Hill/Open University Press.
[3]Clar k, B.(1997). The modern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8(3): 241―255.
[4][10]劉獻君,吳洪富.非線性視域下的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5):77-87.
[5]吳洪富.國外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的四種路徑[J].江蘇高教,2011(4):65-68.
[6]吳洪富.國內教學與科研關系研究的歷史脈絡[J].江蘇高教,2011(1):62-65.
[7]Ramsden, P. and Moses, I. (1992). Associations betwee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23(3):273-295.
[8]Robertson, J. and Bond, C. (2001). Experience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what do academics valu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 (1):5-19.
[9]Robertson, J.(2007)Beyond the‘research/teaching nexus’: exploring the complexity of academic experience,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32 (5):541-56.
[11]Parsons,T.,Platt,G.M.(1970). Ag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oci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3(1):1-37.
[12]Leary,L.(1959).The scholar as teacher. School and Society,87 (January-December): 214-215.
[13]Barnett, R.(1992).Link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a critical Inquir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3(6): 619-636.
[14]Turns,S.R.(1991). Faculty research and teaching―a view from the trenches. Engineering Education, 81 (1):23-25.
[15]Taylor,J.(2008).The Teaching-Research Nexus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and and Sweden. Comparative Education, 38 (1): 53-69.
[16]劉獻君,張俊超,吳洪富.大學教師對于教學與科研關系的認識和處理調查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2):35-42.
[17]張俊超,吳洪富.變革大學組織制度,改善教學與科研關系[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119-124.
[18]Deem,R.and Lucas,L.(2007).Research and teaching cultures in two contrasting UK policy contexts: Academic life in Education Departments in five English and Scottish universities, Higher Education,54 (1):115-133.
[19]Lucas L, Healey M, Jenkins A, and Short C, Scott K and Deem R(2007). Academics’experiences and perceptions of‘research’&’teaching’: primary findings o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SRHE Annual Conference, Brighton, December 11-13.
[20]Colbeck, C L (1998). Merging in a seamless blend,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9(6):647~671.
[21]Boyer, E L(1990).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for the professoriate, Pp16, Princeton N J.: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2] Neumann, R(1996). Researching the teaching-research nexus: a critical review, Australian Journal of Education, 40 (1):5-18.
[23]Brew, A and Boud, D(1995).Research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Smith, B and Brown, S (eds.) Researc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Kogan Page.
[24] Clark, B R(1997). The modern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8 (3):242-55.
[25]李澤,曹如軍.大眾化時期大學教學與科研關系審視[J].高等教育研究,2008(3):51-56.
[26]李健.培養創新型人才必須強化教學與科研的融合[J].中國高等教育,2008(9):14-15.
[27]Jenkins,A and Healey, M(2005).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to link teaching and research. York: The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heacademy.ac.uk/assets/York/documents/ourwork/research/Institutional_strategies.pdf.
[28]Locke,W(2004).Integrating research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Implic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in the United Kingdom,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Policy, 16 (3):101-120.
[29]Jenkins,A,Breen,R,and Lindsay,R with Brew, A(2003). Reshaping higher education: Link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Falmer.
第5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一、從“外鑠”走向“內發”:教師專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在教師專業發展動因的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即“外鑠論”和“內發論”。“外鑠論”者主張教師專業發展受外部力量的控制,主張通過以知識、技術為主要內容的訓練式培訓來實現教師的專業發展。“內發論”者主張個體發展的動因源于內在力量,主張激發教師的自主發展意識,通過反思、對話等途徑來實現教師的專業發展。實踐已經向我們證明,教師專業發展必須從外部主導式培訓向教師專業自主成長范式轉換,即從“外鑠”走向“內發”。
第一,從教師專業化發展的歷程來看,從“外鑠”走向“內發”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必然選擇。教師專業化運動已經經歷了300百多年,它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組織發展”階段和“專業發展”階段。在“組織發展”階段,存在兩種不同的取向:一種是謀求整個專業社會地位提升的工會主義取向,這種取向是以罷工為主要形式以謀求社會對教學專業的認可和其成員經濟地位、工作條件的改善;另一種是強調教師入職的高標準的專業主義取向,這種取向則指向教學專業人員,通過制定專業標準和規范,要求專業人員改善對社會的專業服務水平。在“專業發展”階段,出現了教師專業發展的理智取向、實踐―反思取向和生態取向。在這一階段,教師專業化已從對外要求轉向通過自身教師素質的提高獲得社會的認可。從“組織發展”階段到“專業發展”階段的轉變,就預示著教師專業發展從“外鑠”到“內發”的范式轉變。
第二,從哲學的“內外因”原理來看,從“外鑠”走向“內發”亦是歷史必然的選擇。在教師專業發展中,教師自身的力量應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因,具有決定作用。教師專業發展必須從依靠外部力量轉向依靠教師的自身力量。我們必須樹立這樣的理念:教師是專業發展的主體,教師擁有專業發展的自。而綜觀中國教師職業的發展歷程,教師一直處于被剝奪權利和主體地位的境況。教師專業發展的自掌握在各級教育部門和各類教師教育機構中。教師主體地位的喪失,專業自的缺失是外部主導式培訓模式的必然結果。這正是教師專業發展長期處于低效狀態的根源所在。幸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外部主導式培訓逐漸讓位于“教師自主成長”模式。實踐已經向我們證明,沒有教師主動參與的教師培訓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理論基礎的轉變:從“行為主義”到“建構主義”
從國際教師專業化的發展歷程看,教師的專業化歷程經歷了“專業化”、“反專業化”、“新專業化”的過程。與此相應,教師研修的范式經歷了行為主義、認知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發展階段。“外部主導式培訓”范式是以行為主義為理論基礎的。行為主義學習理論強調刺激與行為反應之間的聯結,認為學習行為是可以訓練的。它只關注外部可觀察到的行為表現,而忽視行為主體的內部活動。在行為主義學習理論指導下教師專業發展著眼于技術訓練和能力本位。“教師專業自主成長”范式以認知主義特別是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認知主義心理學專注于個體內部心理的加工過程的研究。它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指導意義突出表現在元認知策略對教師專業自主成長的意義。元認知是對認知的認知(Flavell,1985),即是關于個人自己認知過程的知識和調節這些過程的能力。教師反思能力及反思性教學等概念的提出就是以元認知策略為基礎的。建構主義是在認知主義心理學的基礎上引入了人本主義和社會文化歷史的觀點。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對教師專業發展的理論指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教師是專業發展的主體,教師專業發展要建立在教師的主體性、自覺性、主動性即自主學習基礎上。建構主義理論強調學生是主動的學習者,強調學生在學習中的主動作用。(2)教師專業發展要基于教師已有的經驗,并提倡教師合作學習,建立學習型組織,營建合作的教師文化。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習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即社會文化背景下通過相互作用而實現意義建構的過程。“情景”、“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是學習環境中的四大要素。“教師專業自主成長”要扎根于認知主義和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實現教師專業的自主成長。
三、基本觀念的轉變:本質觀、知識觀、實踐觀
(一)本質觀:從“知識”本位轉向“人”本位
教師專業發展是一種尋求教師的“人格化”、“個性化”、“文化化”的過程。而傳統的教師專業發展僅局限于對教師知識的灌輸與技能的訓練。在教師專業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后,必須從“知識”本位轉向“人”本位。將教師專業發展定位在“人”的發展上,尊重教師的主體地位,關注教師的身心發展。實踐證明,沒有教師主體的自我實踐、反思意識的覺醒和能力的增強,只是靠行政手段或教育專家的“學術報告”,難于實現教師的教育教學觀念、教育教學行為和能力本質性的更新。幸運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模式開始出現轉向,逐漸考慮到教師是一個有意識的“人”,而非“知識的容器”。只有將教師專業發展的本質定位在“人”的發展,只有從依靠外部力量轉向依靠教師內部動力,才能順利實現教師的專業發展。
(二)知識觀:從“理論性知識”轉向“實踐性知識”
陳向明教授認為“實踐性知識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知識基礎”。實踐性知識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源泉。中小學教師是有著豐富實踐性知識的個體。尊重教師的實踐性知識,就是尊重中小學教師的主體地位,尊重中小學教師作為“人”的存在價值。美國心理學家波斯納提出了教師成長的公式:成長=經驗+反思。教師的實踐性知識就是這里“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這里的“反思”其實質應該是對教師自身教育教學實踐的反思――對教師自身實踐合理性的考察。教師的專業發展必須緊緊圍繞教師的實踐性知識,重視對教師實踐性知識的發掘。瑞吉歐的創始人馬拉古齊曾說過:“幼兒教師專業素養的形成與發展必須在與幼兒一起工作的過程中同時進行。”對于中小學教師的成長而言亦是如此。
那么如何挖掘教師豐富的實踐性知識呢?Stenhouse,L.的“教師成為研究者”、Elliot,J.的“教師成為行動研究者”、Kemmis,S.的“教師成為解放性行動研究者”理論的提出,為教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也為廣大中小學教師找到了一條適合他們的專業發展道路。
(三)實踐觀:從“訓練”轉向“對話與反思”
在“外部主導式培訓”模式中,主要的實踐方式有兩種:集中授課與課堂教學技能訓練。在集中授課中,教師培訓機構通過邀請知名學者來講學和一些優秀教師(如特級教師)來講授自己經驗的方式進行培訓。課堂教學技能的訓練主要通過觀、評課來實現。這兩種方式貌似以教師為主體,但實則主導權掌握在外部專家、培訓機構的手中。在“教師自主成長模式”中,對話與反思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主要方式及有效途徑。對話與反思的突出特點在于教師自主性的發揮。
四、運行機制的轉變: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群
教師專業發展是一種生態現象,教師個體的專業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所謂教師專業發展群是指建立一個以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為追求目標,以教師為主體,以教師自主成長為主要方式,各級政府、各教師教育機構、教師任職學校、社區、家長等協作參與的全方位、協作式群落(community)。這個群體的顯著特點有五個:(1)教師是中心,而非其他各類機構。教師的自主發展意識與自主成長是這個群落生命的主線。(2)教師的專業發展自的教師自主成長的權利保障。這里的教師專業自是特指教師在專業發展過程中的“發展自力”,而非普遍意義上的“教育教學自”。它包括教師自主選擇和自主決定專業發展目標、專業發展內容、專業發展階段與專業成長方式等權力。(3)各機構間相互合作,構成協作教師實現專業發展的生態圈。(4)教師任職學校是教師專業成長的基質。(5)在教師任職學校內部或教師任職學校間組成若干個教師專業發展合作小組。這些教師專業發展合作小組為教師合作學習提供了平臺。
第6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主題詞 社會建構 建構主義
一
建構主義研究目前日趨龐雜,其特點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建構主義研究來源于眾多思想和方法的影響。就建構主義研究的興起而言,它實際上是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知識社會學和哲學思潮匯流的結果。后現代主義的產生體現了人類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化工程(包括科學技術工程)的負面效應,如環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這種反思,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奧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維等人認為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已進入后現代社會時期,在后現代社會,知識成為社會斗爭的焦點,科學成為政治的工具,其客觀性和權威性將會受到懷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他們提倡對社會進行微觀研究、多元化理論視角、話語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識社會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揭示特定的知識和信念實體怎樣受到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只不過,知識社會學長期以來將信念分成數學和自然科學與包括諸如宗教信仰、道德哲學體系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認為前者是質樸的,不為任何利益考慮所玷污,而社會科學等學問則是意識形態的、受主觀思想和利益影響的,因而常常將數學和自然科學置于知識學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現代主義那里科學的客觀性已受到懷疑,而傳統知識社會學又置科學技術知識于不顧,那么,建構主義來考察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建構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當然,建構主義研究也從哲學中的反實證主義流派、新及現象學、人種學的研究方法獲得了啟示。 具體說來這些觀點是:(1)科學理論的證據非決定性,即在原則上總有幾個可供選擇利用的理論與有關的證據一致;(2)觀察滲透著理論, 即理論的附屬成份包含著各種形式的測量理論,有關的觀察結果是由用來檢驗的理論范式決定的,觀察在某一理論中得出,在與之競爭的和繼承的范式中其含義不同。更為具體地說,約定主義的哲學本體論和相對主義認識論肯定是直接促進了建構主義的研究。特別是庫恩、漢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蘭細菌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學事實、科學評價標準和科學理論范式都是相對的,不可通約的或非中性的,這樣用單純的理性邏輯就不足以說明科學認知的真實情況。于是,從庫恩等人思想中獲得靈感的建構主義學者們,大膽地對默頓科學社會學、傳統知識社會學等進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問題范圍之廣,觀點、命題之深,聲勢之大,以致許多人認為科學社會學已進入“后庫恩時代”。后來,出于對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發展是自主的,它影響著社會變遷,但不受社會影響)的不滿,技術社會學也被卷入到了建構主義研究中。
2.建構主義學者在地理分布上較為廣泛。建構主義作為一個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觀點、方法來源不同,很難像科學學(代表人物是英國的貝爾納)、傳統科學社會學(代表人物是默頓)追塑到某個國或某個代表人物,其成員分散在歐美不同國家。在英國,主要是愛丁堡學派,其成員是埃奇、布魯爾、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們從批判傳統知識社會學,特別是曼海姆思想出發,并從庫恩思想得到啟發,對科學知識的實質進行研究。在法國,拉圖爾、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爾、福柯的本土方法對科學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的考察。在美國,謝廷娜(一位建構主義女學者)、陳誠、瑞斯蒂等也進行著與拉圖爾類似的工作。另外,英國的馬爾凱、伍爾加,美國的平齊、休斯,荷蘭的比克,德國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學者都在從事不同的建構主義研究。當然,建構主義既然以一個思想學派出現,也存在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圖爾與伍爾加合作考察科學家之間的交流,共同發表《實驗室生活》一書,謝廷娜和馬爾凱一起主編《觀察到的科學》一書等等。
3.建構主義研究方法多樣化。盡管建構主義是建立在知識是社會地建構成的這一總觀點之上的,但其方法卻是經驗的。這樣,建構主義研究方法便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實驗室研究,由拉圖爾、伍爾加發起,像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保持一種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根據觀察日記進行研究;爭論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從微觀角度分析科學知識如何達成一致;話語分析(或稱修辭學方法),由馬爾凱等人發展而來,把科學活動參與者的“日常話語”作為主題,分析科學解釋是如何隨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在對技術的社會研究中,建構主義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會建構方法,這是平齊和比克把相對主義經驗綱領引入技術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技術人工制品如何在社會、文化方面得到解釋;系統方法,休斯在技術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術看作一個系統(如電力系統),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的分析;操作子網絡方法,它與拉圖爾、卡隆、勞等人的研究工作相關,他們把技術、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看作整體的“異質操作子”網絡,分析技術在其中的作用。另外,愛丁堡學派早期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以及隨后的弱綱領也都是建構主義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構主義這種經驗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特點,導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統一的理論凝聚。目前建構主義的各種觀點和學術成果,散見于有關學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種論文集里。拉圖爾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是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考察的結果,拉圖爾的《行動中的科學》也不過是對這種考察的進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觀察到的科學》以及平齊和比克主編的《技術系統和社會建構》等則均為集納諸多建構主義學者及相關學者經驗研究成果的論文集。因此,建構主義的學術觀點具有相當的分散性。
二
建構主義研究就其建構對象而言也呈現出某種復雜性。在建構主義的視野中,似乎借助行為者的互動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識、方法、學科、習俗和規則),科學家基于數據和觀察構造的理論和敘述,實驗室中由于物質參與而產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體都是建構成的。但是,從這種復雜性中仍可窺見出建構主義存在著強與弱的分野。
1.弱建構主義。弱建構主義強調的是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或社會原因,主要著重于宏觀社會學的把握,但并不否認其客觀性或邏輯性的原因。
這類建構主義觀點最早見于貝格爾和魯克曼的知識社會學論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現實的社會建構》一書中,他們提出現實是社會地建構成的,知識社會學關心的主題是社會建構過程。這里的現實是指主觀現實(即人們關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觀現實。所謂現實的社會建構就是這種主觀現實作為人工的產物雖然獨立于我們的意志,但都是在社會情景中發展、傳輸和保持的。[1]就是說, 要建構其中某種主觀現實X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識,這種知識即便在X不存在時,也能產生某種行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識;(3)傳播X知識的手段。只要具備這些條件,X 的知識便可在社會共同體“固定”或普遍存在下來。在貝格爾和魯克曼的建構意義上,社會中有許多東西如習俗、規則、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權力、科學等等都可看作是社會建構的。
當愛丁堡學派沖破傳統知識社會學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明顯區分后,巴恩斯、布魯爾、柯林斯等采取了與貝格爾和魯克曼相類似的方法來考察自然科學知識,即用社會背景來解釋科學知識內容。巴恩斯在論及庫恩對科學知識結果解釋的批評時說:“他所描述的科學中基本理論的變遷,不再是對增長的關于實在知識的簡單響應,而是用關于推理的評價的背景負荷才能表達的。”[2]也即是說, 既然自然科學并非以純結果的方式變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學知識的產生及其維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會背景。巴恩斯引進了“利益”概念,布魯爾認為除了一些社會原則外,還包括精神的、人類學的、生物學的、認知的和感覺經驗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個“非科學”的標準清單:“基于從前合作對合作者實驗能力和忠誠的信任、實驗者的個性和智力、管理大實驗室的聲譽、科學家是否在工業界或學術界工作過、過去的失敗經歷、內部資料、科學成果的風格和表現、實驗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盡管愛丁堡學派的工作是建構主義的,但并沒有使用“社會建構”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會建構”一詞進行建構主義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的是孟德爾遜和達勒。他們的論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爾遜、魏因加特和懷特利主編的《科學社會學年鑒》第一卷,取名為“科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孟德爾遜和達勒認為,現代科學的建制、認知和知識主張并不能通過科學史論得到適當的說明,它們作為人工的產物必有其社會因果關系,因而是社會建構成的。
孟德爾遜等用“社會建構”批評科學史論的不適當性在今天看來雖然已無必要,但卻激起了對科學話語、文本的建構主義研究。以往的科學史論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學家的論著或談話錄、回憶錄為依據的。而馬爾凱則認為科學家的話語實際上變化很大,其內容和真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談論者面對面的互動,因而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可以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建構的社會特性。馬爾凱和吉爾伯特通過對一個生物化學小組的34名有建樹的研究者的訪問,把科學家話語分成經驗性的和偶然性的兩種情況。結果發現,科學家在解釋正確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經驗性話語,而在說明錯誤信念時,通常依據的是偶然性話語,即把科學家犯錯誤的原因歸于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偶然因素。[4]
邁耶斯在《寫作生物學:科學知識社會建構的文本》一書中試圖表明,社會的考慮(主要是考慮讀者的鑒賞和興趣)怎樣“構成”科學主張、討論和論文或專著的寫作。他說:“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點是假定科學是在論文或見解修改和爭論反語重釋的聲言和協商的社會過程中建構的。對于這一基點,讀者將會感到驚異。”[5]這里, 邁耶斯似乎指明,科學文本的社會建構是說它在公開發表之前就經過討論、協商、改變和削弱等,科學文本不僅源于客體素材,而且也經歷了科學家和評論者的審視。
可以看到,弱建構主義在探討科學知識的社會原因時,往往給科學的客觀性、理性和邏輯因素留有適當的余地。布魯爾的強綱領中的公平性、對稱性原則實際上要求對科學的真理和謬誤、真實信念和錯誤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敗都做出說明,馬爾凱在歸納經驗性話語時則說明了實驗數據是在邏輯和時間優先情況下給出的。另外,愛丁堡學派并沒有回答在什么時機,讓社會背景因素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中。這就是有些強建構主義學者為什么并不把弱建構主義納入建構主義研究的原因。
2.強建構主義。強建構主義是在微觀層次上對科學知識所做的經驗研究,認為科學知識或技術人工制品能夠顯示出其建構完全是社會性的。這類學者主要是謝廷娜、拉圖爾、伍爾加、平齊、比克等人。
謝廷娜將其工作貼上“建構主義”的標簽,而非“社會建構主義”。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將其研究同“社會背景”之類的東西聯系在一起,以示同愛丁堡學派的工作相區別。謝廷娜認為微觀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有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爭論研究,說明知識的一致性是如何達成的;其二是選擇科學工作的真實地點如實驗室作為研究對象,說明科學知識是怎樣建構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稱其研究成果為建構主義綱領。她歸納了科學建構的社會特征,即科學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現實”,而是指向陳述的操作,這種操作不僅使科學家進入大量面對面的協商和互動,還包括更廣泛的、超越處所的關系,與經紀人、工業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發生聯系。[6]
與謝廷娜一樣,拉圖爾也想避免將其建構主義研究同“社會背景”相提并論。他和伍爾加的《實驗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標題是“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當1986年再版時把其中的“社會”一詞刪去了。但不管怎樣,該書的主題仍然指明:科學事實是一種建構的產物,是各種利益集團間協商的產物。通過對索爾克研究所格列明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拉圖爾及其合作者伍爾加用整整一章專門論述了TRF (促甲狀腺釋放因子)的建構過程。[7]
在對《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合作之后,拉圖爾與伍爾加的研究綱領開始分道揚鑣了。拉圖爾轉向了操作子網絡,把其中的科學家當作“資源積累者”進行了“馬基雅維利”式的描述。[8] 由于這一綱領不再具有明顯的建構主義風格,這里不加論及,與此不同,伍爾加卻對表象進行了建構主義的研究。
概括地說,客體(自然世界)與表現(科學知識)之間的關系包含兩種圖式:
(1)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2)表象客體或者科學知識自然世界
第一種圖式認為客體獨立于表象,自然知識似乎與自然世界沒有多少關系;第二種圖式表明表象是客體的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識與自然世界之間沒有誰是第一性的、誰是本質的區別。伍爾加認為,前者是過去的科學社會學(包括愛丁堡學派)堅持的“認識論上的相對主義和本體論上的實在主義”圖式,后者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應遵循的模式。[9]對此,他提出兩條證據。首先,沒有表象, 客體就是無用的,我們無法獨立于客體。其次是對同一客體的解釋存在著某種“柔性”,即科學陳述的多樣性,這導致人們去懷疑任何“假定”的客觀事物的存在。在這里,伍爾加是想說明表象構成或建構了客體,即世界是被建構著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學知識社會學已經成功地披上建構主義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標題或導言紛紛以“……的社會建構”而呈現于世。就是對技術進行社會研究的人們也未能逃脫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齊在《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一書中希望提倡一種新的建構主義研究綱領。
誠如前面所言,《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并不代表一種一貫的研究綱領。這里將集中考察平齊和比克的論文《事實與人工制品的社會建構:或者科學社會學與技術社會學怎樣得到互惠》。在該文中,他們提出了與布魯爾幾乎相近的“建構主義強綱領”:“在這一綱領里,所有知識和所有知識假設都將被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就是說,關于知識假設的起源、接受和拒絕的全部解釋都可以從社會世界領域尋找得到,而無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過,他們卻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的一些概念,并稱之為“技術的社會建構方法”:“這一方法的關鍵概念是‘解釋柔性’、‘終止機制’的‘相關社會群體’。其核心信條之一是技術人工制品對社會學分析是公開的,這不僅表現在技術的使用上,而且特別關及其設計和工藝‘內容’”。[11]平齊和比克用這種方法說明了自行車的歷史,表明了自行車是試錯的產物,新的嘗試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們沒有解決這個或那個社會群體提出的問題。因而每種技術產品都是“決定滲透”的結果,而非單向模式發展的邏輯程序。
總之,強建構主義雖然都標謗自己是完全的建構主義,但最終都是以對微觀社會學問題的關注來解釋宏觀社會學的構架。這一點從謝廷娜、伍爾加、平齊和比克的觀點可以明顯看出。特別是謝廷娜以實驗室活動為基礎來展示科學知識和建構與社會存在著的廣泛聯系,試圖消除科學知識發展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學知識發展的認識和社會因素結合起來。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數科學社會學家和“理想”,又說明強建構主義與弱建構主義不無兩致的“模糊性”。
三
簡單地說,建構主義尖銳地批判了個人主義的、觀念論的、實證論的和樸素實在論的科學或技術說明。他們對科學技術事業的因果解釋的社會資源的展示和說明,擴大了社會學研究的視野。但是,建構主義作為一種研究傾向或理論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會偶然性因素。建構主義研究實際上是把科學技術的本體論相對化,以及把社會因素理性化。弱建構主義者,特別是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一方面想使它成為社會學乃至全部社會科學研究的典范,成為理性和科學的體現,同時在另一方面卻又否認科學知識與一般知識的區別,使科學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學。強建構主義者則是在強調科學或技術的社會建構的同時,把客觀的自然因素放置一邊。謝廷娜、拉圖爾等人提倡用參與式觀察對科學家的廣泛訪問來理解科學,但對自然界在科學活動中的地位的認識,卻僅僅停留在關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語言建構之上。而平齊、比克的研究則表明,技術社會學應著重于社會因素怎樣建構人工制品,而對技術的工藝內容可以置之不顧。建構主義這種對科學技術產生所做的過份的“社會學簡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殺了科學技術的本體論方面的因素,忽視了科學技術的物質基礎,從而把科學技術看成完全由各種社會偶然性因素組成的東西。
應該說,在當代有關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文化爭論中,建構主義有著強烈的后現代主義傾向。后現代主義者以對真理、客觀性、因果性、合理和進步等的懷疑和批判為特征。鑒于強建構主義堅決地解構了科學合理性觀念本身,那么強建構主義實際上就成了通往后現代主義一邊的橋梁。但對于弱建構主義,有的學者認為它致力于對科學的宏觀因果解釋,因而應被劃分到現代主義一邊。可是,如果考慮到并不是所有后現代主義都強調對現代科學的解構,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了繼承現代主義但又超越現代主義的“建構性后現代哲學”,[12]則恐怕弱建構主義也逃脫不了與后現代主義的干系。更何況弱建構主義也有著割裂科學與理性之嫌。
2.對于科學技術的解釋范圍較為狹窄。強建構主義研究過份強調實驗室、人工制品在理論上的重要性。如拉圖爾對實驗室的人類學考察,雖然有助于我們理解科學家的行為,但這種微觀研究與科學的組織、結構、共同體等宏觀研究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平齊、比克在進行技術社會學研究時對相關社會的社會群體的關鍵作用給予了充分關注,但對技術發展有著強烈影響的經濟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觀條件均未被列入技術的社會建構研究的議事日程。至于弱建構主義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雖然貌似新鮮,其實在默頓的大部分科學社會學研究中都已論述過。早在1945年,默頓就描述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程序,說明了可以作為社會學分析的精神產品應包括信仰、意識形態、宗教道德及實證科學,還分析了精神產品的存在基礎,如群體結構、權力結構、競爭、沖突和利益等。
3.忽視科學技術后果及其評價。建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適合于解釋科學知識的起源和技術創新的動力,以致對于科技產品對人的自我意識、社區組織、日常生活、權力分布有何特別意義的問題很少給予關注。在許多建構主義者那里,關于科技成果的研究進入“死結”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學技術選擇的社會后果幾乎完全置之腦后。
與此相關,建構主義還貶低對科學技術的道德評價。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和柯林斯的經驗相對主義綱領在對待科學發現、科學理論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態度,即認為科學本身無所謂惡,是價值中立的。平齊、比克將柯林斯的綱領外推用于技術的社會研究時,對技術成果的最終善惡又采取了不可知論的態度,因而不去探討有關技術的地位、技術選擇的正誤這樣的問題。不管怎么說,建構主義開創的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新方向,對于人們從內部理解科學技術及其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有著莫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 P.L. Berger and Th.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Doubleday,1996,2—3.
[2] J. R. Brown(ed). Scientific Rationality:the Sociologi-cal Tur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4,7.
[3] H.M. Collins. Changing Order, Sage Publication, 1985,87.
[4] J.Potter and M. Wetnerell.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Sage Publication, 1987, chapter 7.
[5] G. Myers. Writing Biology: Text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 1990, 141.
[6] K. D. Knorr—Cetina. 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Pergamon Press, 1981.
[7] B. Latour and S.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5—150.
[8] B. Latour.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S. Woolgar. Science: the Very Idea, Ellis Horwood, 1988,54.
[10][11] W. E. Bijker, Th. P. Hughes and T. J. Pinch. The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e MIT Press,1987, 17—50.
第7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關鍵詞:教師質量;學生成就;教學實踐;專業發展
美國自頒布《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后,出現了大量研究教師質量與學生成就的關系的文獻。許多學者調研了影響學生成就的各種因素,發現教師是決定學生成就的核心因素,學生測驗分數的差距能夠直接歸因于教師質量。教師質量由許多因素構成,哪些是最重要的呢?考察這一問題不僅有助于教育者和決策者反思當前的教育教學改革,還能夠為教師教育以及教師專業發展指明方向。
一、教師對學生成就的影響模式考察
根據已有的大量研究,教師對于學生成就的作用主要由四個方面綜合而成:教師培訓、教學經驗、教學實踐、和專業發展經歷。教師的作用模式如圖1所示:
教師培訓:學歷――執照等級――教育學知識――內容知識
教學經驗:教齡
教學實踐:教學范式――教學動機――教學方法――評價方法
專業發展:內容――目的――類型――頻率
對學生成就的影響主要通過學生的數學成績來考察。
(一)教師培訓
美國的《中小學教育法》和《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要求,到2006年為止,每個教室中都要有一位高質量的教師。《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對“高質量的教師”是這樣界定的:在任一科目中取得學士學位、教師執照或者資格證書、成功地通過內容知識測驗或者完成科目內容專業課的學習。這一界定存在著含混性,許多州將“高質量”與教師執照等同起來,認為獲得教師執照的教師就是高質量的教師。這顯然沒有抓住“高質量教師”的本質。
教師培訓不能只為了獲得一個文憑或者教師資格證。更重要的是對教育學知識和科目內容知識的學習和掌握,這兩種知識相輔相成,對于教師日后的專業發展非常重要,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教學有效性的提升。
教師對科目知識的掌握與學生的表現存在正相關關系。而教師培養計劃,尤其是小學中低年級的教師培養計劃忽視了教師科目知識的重要性。在教師培訓中,對科目內容知識的重視程度要遜色于教育學知識。許多教師在小學教育培訓中主要接受教育學方面的學習,對于科目內容方面的知識,只接受了一般性的訓練,因而他們的數學和科學知識較為欠缺。
教師培訓的另一個方面是教師獲得的執照的等級。研究指出,教師資格證書的等級與學生的數學成就存在正相關關系。依據執照的等級,教師執照可分為三類:第一級是教師完成四年的大學教育,并獲得數學教育的初級執照。第二級是教師獲得高級的(或者碩士)數學教育資格證書,并取得了碩士學位。第三類執照是教師獲得額外的資格認證,這是國家根據學生的優秀表現頒發給他們的。
(二)教學經驗
第二種影響學生成就的變量是教師的教學經驗。教學經驗對學生成就的影響趨于正相關。研究表明,教師多年的教學經驗對學生的學業表現有積極的影響,然而,這種關系并非總是呈線性增長關系,隨著教齡的增長,增長趨于穩定。這通常是教師在職業生涯結束時,不再繼續學習,停止進步的結果。
在數學教育方面,教學經驗尤其會影響學生成就,
但是影響的程度是不確定的。盡管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其成就也存在影響,但菲特(Felter )發現,教師的經驗與學生的數學成就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三)教學實踐
教師教學實踐是影響學生成就的重要因素。教師在課堂中的教學實踐受其教學范式的影響。教師的教學信念體現在他們的教學方法中。傳統的教學方法建立在行為主義思想基礎上,學習被看做是累積性的,表現為結構性知識和技能的發展。學生的學習主要依賴于教師的指導。相反,皮亞杰主張的建構主義教育學,將學習視為學習者主動投身于真實世界,并在與以前的知識進行比較和聯系的基礎上所建構的。學習情境的創設推動著學生提問、質疑、并解決問題。
教師的教學實踐分為行為主義和建構主義兩類。蓋爾斯和燕(Gales and Yan )所做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當教師只給出一種正確答案或者解題方法,并讓學生獨立學習時,教師的行為主義教學法與學生成就之間呈顯著負相關。相反,當學習內容與真實世界相關,正確答案不唯一,學生在合作性的環境下學習數學時,教師的建構主義教學法對學生成就的影響是積極的。
(四)專業發展
許多新教師沒有做好準備應對課堂的現實、挑戰和教學難題。通過學區和學校提供的專業發展,新教師學習如何應對教學的復雜性。已有研究證明,學區采取措施支持新教師的發展是提高教師保持率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學區不僅注重支持新教師發展,還不斷推動老教師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老教師通過優質的、全面的專業發展來加強科目內容知識的學習,提升教學實踐,以更好地滿足學生的認知需求。NCLB也認識到繼續專業化對于提升教師質量的價值,將“高質量”界定為“持續、強化、以課堂為中心”。
持續的教師專業發展是提高教師質量的有力保證。然而,盡管各州意識到了教師專業發展重要性,但是基于資金的問題,學校不斷的減少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同時,大多數教師都是依賴于教齡的增長,而不是專業發展來提供學生成就的。他們認為,專業發展的培訓課程效果較差,因而,對花在專業培訓上的時間抱有怨言。學校對教師的評價不是參考其課堂表現,而是考察他們是否參加了專業培訓課,這種評價方式存在一定的有限性,并不能有效地督促教師改進教學,提升學生成就。
二、 個案研究
2006年,“北卡羅來納州提高學生數學和科學成就聯合組”,在國家科學基礎和教育部的資助下,做了一項為期五年的研究,旨在通過教育政策、教師專業發展、家長計劃提高學生數學和科學成就。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數學教學和數學成績上。研究數據取自北卡羅來納州東部一個縣,調查了46名小學的骨干教師與933名學生的年級末數學考試成績之間的關系。下面分別闡述教師的四個方面對學生數學成就的影響。
(一)教師培訓
教師培訓包括五個變量:學歷程度、執照類型、執照等級、教育學知識、科目內容知識。除了執照的類型,其他變量對學生成就的影響沒有重大差別。執照類型分為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數學教育或者其他的知識領域的資格證。有43名小學骨干教師在該州獲得資格認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獲得的是小學教育的執照;有兩名獲得的是中學教育的認證;有四名在小學教學的教師獲得的是高中教育執照,但不是數學方面的資格證;還有四名在小學工作的教師取得的是高中數學教育的資格證。
研究發現,中小學教師執照在科目內容知識儲備上有很大差別。中學教師執照要求教師在科目內容培訓更為嚴格。對科目內容知識準備的越充分,越能夠對學生成就產生積極影響。該發現與以前的教師的知識與學生學習的關系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小學教師的數學知識要求主要教數學基礎原理、計算和應用方面的知識;因此,對于小學教育而言,提高性的數學知識訓練不很重要,重點在于提高小學教師對基礎知識和教學方法的掌握和運用。
學歷層次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所有教師都通過傳統方案的認證,并且教師執照就是他們學歷中的組成部分。碩士學歷在提升教師作用方面沒什么影響,這引起人們對高學歷的質疑。這與以前的研究是一致的――已有研究表明碩士學歷不是影響學生數學成就的關鍵因素。
(二)教學經驗
教學經驗是決定學生成就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研究顯示,教學經驗與學生學習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教師的教學年限越長,他們越有機會增加知識內容儲備、改進教學方法、重新界定他們對學生品質和認知能力。因而,教學經驗越豐富,越有利于提高學生成就。這一發現與以前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
(三)教學實踐
教學實踐非常復雜,它由許多變量綜合而成。首先,教師的教學受其教學范式的影響。教學范式主要包括傳統教育學和建構主義教育學兩種。教師所持的教學理念大多介于二者之間。對教師的教學范式的考察通過兩個方面來進行:教學方法和評價方式。研究結果顯示,傳統或建構主義教學方法對學生成就的影響沒有明顯差別。這表明,不存在一種最好的教學方法,教學應綜合應用這兩種策略。在評價方面,傳統的評價方法表現為客觀測試題,只有一個標準答案;而建構主義的評價方法傾向于拓展性的考察,如讓學生做項目、課堂展示和示范等,對學生進行系統的考核。兩種評估策略沒有顯著差別,二者結合使用是最適當的。
教師的動機和教學目的影響到教師教什么和怎么教,它由五個要素構成:課程標準、標準化測試、教材、個性化課程以及教育學培訓。教材和教育學培訓在塑造教師教學決策方面不是重要的變量。對學生影響有重大的差異的因素是以下三項:課程標準、標準化測試以及個性化課程,這些因素左右了教師的動機和教學目的。外部的壓力對課程具有決定性影響,比如《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或者州的責任系統,極大地影響了教師教育決策制定。教師在課程上所做的決策圍繞提高學生學習成績而展開。由于對學生的評價主要以內容知識和技能為主,因此,課程和評價緊密結合起來。這反映出美國近年來以標準化為基礎的教育教學改革對教師責任感的影響,標準化的課程和測試成為教師教學的指揮棒。
教學技術是數學教學中的一項重要資源,它有助于加強學生對數學的理解;因此,要評價教師對計算機、電腦以及其他教學工具的使用對于學生學習的影響。結果顯示,數學測驗分數的重大差別是由骨干教師對教學技術的運用而產生的。較頻繁和廣泛的使用教學工具對學生成就具有積極的影響。因此,教師的專業發展需要集中在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和采用教學工具的技能上。鑒于教學技術在提高學生學習上的優勢,學校需要支持教師發展適當的教學綜合技術,這一發現為以前的內同研究提供了支持。
(四)專業發展
第四方面考察了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教師參加專業發展的目的以及參加的頻率。教師有效性極大地受到他們在教育學和科目知識培訓中的成長經歷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專業發展的內容和教師參與專業發展的動機對學生成就的影響甚微,最重要的是參加專業發展活動的頻率。學生成就隨著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增多而得到提高。這說明教師參加的專業發展機會越多,越有利于他們加深對數學教學的理解。孤立性和斷裂性的教師專業培訓不利于提高教師的水平,《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已經意識到了這點,必須建立持續性的教師專業發展制度。
三、啟示與借鑒
根據學生學習結果來評價教師質量,突顯美國以學生成就為中心的教學改革方針。教師作用模式便于我們從各個側面理解教師對于學生所起的作用,從而指引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向。
(一)人們通常易于忽視小學數學教育中的科目知識的學習,實際上,提高教師有效性需要教師深化對數學知識的認知、改進教學策略。至于碩士學歷在我國是否無益于教學質量的提高需要做更多的實證研究。
(二)教師教齡的增長確實為他們改進教學提供了機會,留住經驗豐富的老教師對學校而言意義重大。但這里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前提:即這必須是建立在老教師不斷反思自己的教學,并積極進行專業發展的基礎之上。
(三)在教學實踐中,建構主義教育學近年來沖擊很大,我國各地積極提倡建構主義的教學方法。同時,教師教學也遇到傳統教學理念和建構主義教學理念的沖突。其實“教無定法”,教師采取何種教學策略應因材施教。如果一味追求西方新的教學范式,并不能保證教學質量的提高,就容易導致教師的倦怠感和失落感。此外,教師的責任感仍是我們提高教學質量不可忽視的驅動因素,因而培養并保護教師的責任意識至關重要。
(四)我國對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性已達成共識,在改善專業發展時,不僅要注重教師參加專業發展的頻率,還要兼顧專業發展的內容。
參考文獻:
[1]Learning Point Associates. Critical issue: Us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student achievement[R]. North Central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2006.
[2]Terry Ackerman,Tina Heafner,Debra Bartz.An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Qualit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DB/OL].hub.省略/index.cfm/13389,2006.
[3]Cooney, S. A highly qualified teacher in every middle grades classroom: What states, districts and schools can do. 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 Atlanta, GA.[EB/OL] Available online:省略/programs/hstw/publications/pubs,2003.
[4]Blank, Rolf K.Using surveys of enacted curriculum to advance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relation to standards[J].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 77(4), 86-121,2002.
第8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1.對國際法產生與發展的詮釋。首先,理想主義認為國際法可以保證世界和平并規范國家行為。在此推動下,戰后簽訂了一系列國際條約并成立了國際聯盟,為國際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突出貢獻。其次,新自由主義主張國際機制、規則、制度是解決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有效手段,強調經濟因素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并且注重國際制度,促成了國際經濟立法的繁榮,WTO的成立,各種經濟合作協定的制定都與此有關。再次,建構主義認為國際法屬于一種規范,即社會認同,該理論把國際法上升到觀念的高度,超越了國際法是否為法的爭論,從而使國際法作為一種規范的國際地位被廣泛接受。
2.對國際法的地位與作用的詮釋。理想主義理論認為國際法可以保證世界和平,把國際法提升到一個很高的地位來看待,這帶來了戰后國際立法的繁榮。建構主義理論提升了國際法的地位。該理論認為國際法屬于各國共同意志的表達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會規范”,它將對各國的國際行為模式與價值選擇產生一定的強制性效果。各國對國際法的觀念和意識,屬于“文化”范疇,是具有權威效果的非物質力量,應充分重視國際法在現代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建構主義將國際法視為觀念,超越了國際法是否為“法”的爭論,使國際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對國際法發展動力問題的詮釋。國際法發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于國際社會對國際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諸如觀念、利益等國際因素也可能促進國際法的發展。新自由主義認為觀念因素能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觀念幫助治理世界,原則化觀念指導國際法的具體領域的制度建構,可見,觀念對國際法的發展起到一種理念性的動力作用,國際法就是由觀念上升而來的。任何一項國際制度首先都是一種觀念,當它被國際社會接受后,上升為制度,才成為有約束力的國際法。
可見,利用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等國際關系理論來分析國際法的一些宏觀問題,可以使人們對國際法有一個清晰的認識。
二、具體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對國際法的詮釋
1.博弈論詮釋了國際法的產生過程。博弈論是研究利益沖突的雙方在競爭中制定最優化策略的理論。博弈論認為國際法是各國博弈后所達成的一致,關鍵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夠達到平衡,國際法便確立;如果不能達到平衡,國際法無法確立。這在WTO國際立法中顯得比較明顯。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討價還價,如果最終達成一致,則可以消減關稅以及各種補貼等;而在農產品市場準入、國內補貼等方面各方無法達成一致,所以無法確立規則。可見,國際法的產生就是博弈的過程,是各方利益協調的過程。
2.相互依存理論詮釋了國際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該理論認為國際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國際社會對國際制度的渴求。國際法并非是一個獨立存在的自給自足的獨立體,它受國際社會需求的制約。晚近國際經濟立法的勃興乃是出于各國發展經濟,迎合經濟全球化的需要。而國際法立法范圍也朝著諸如向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現議題多元化的趨勢。相互依存理論之所以可以解釋國際法存在的原因是因為它道出了國際法存在的國際社會基礎,任何制度不是無端憑空存在的,它必須有依存于當下的社會建構,制度的供給要受社會需求的制約。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國際法是根據國際社會的需要而存在的。”
3.國家利益理論詮釋了國際法的最終目的所在。國家利益意指國家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維護本國和本民族免受外來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則。無論哪種國際關系理論,都認為國際制度(國際法)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對國際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對國家利益范疇的不同觀點,對國際法作為利益實現的工具這一點并沒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說,國際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說,國際制度(國際法)是實現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因素。
國家利益理論可以解釋國際法最終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國家利益是達成國際立法的動力,一國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國際制度來作為手段,這使得國際法得以產生;其次,以國際法為手段追求國家利益已經成為當下的主要趨勢,例如在WTO的體制中,各國利用WTO規則,要求他國消減關稅、放開市場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進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開拓殖民地等傳統手段;再次,沒有國家利益的需要,國際法便沒有存在的基礎。即使國際法還具有維護國際秩序之類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的,因此沒有利益存在,國際法也就不會存在。
第9篇:建構主義研究范式范文
一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基本內涵
建構主義強調學習是學生自我建構意義的過程,認為學習不僅是一種學習結果、學習方法,而且還是了解世界的方式。這一理論以全新的視角看待知識、學生和教學,給教育教學實踐提供了一種新的參照。
1.建構主義的知識觀
建構主義強調,知識并不是對現實的準確表征,它只是一種解釋、一種假設,它并不是問題的最終答案。相反,它會隨著人類的進步而不斷地被“革命”掉,并隨之出現新的假設;而且,知識并不能精確地概括世界的法則,在具體問題中,需要針對具體情境進行再創造。根據這種觀點,課本知識只是一種關于各種現象較為可靠的假設,而不是解釋現實的模板,因為經過篩選與提煉的知識不可能把現實具體而復雜的背景涵蓋進去。
2.建構主義的學習觀
建構主義認為,知識不是通過教師傳授得到的,而是學習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會文化背景下,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借助他人(包括教師和學習伙伴)的幫助,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源,通過意義建構的方式獲得的。因此,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情境”“協作”“會話”和“意義建構”是學習環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屬性。
3.建構主義的教學觀
建構主義認為,教學不能無視學生的經驗,而是要把學生現有的知識經驗作為新知識的生長點,引導學生從原有的知識經驗中“生長”出新的知識經驗。教學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知識的處理和轉換。教師不是簡單知識的呈現者,他應該重視學生自己對各種現象的理解,傾聽他們的看法,洞察他們這些想法的由來,以此為根據,引導學生豐富或調整自己的理解。這需要教師與學生共同針對某些問題進行探索,并在此過程中相互交流和質疑,了解彼此的想法,彼此做出某些調整。由于經驗背景的差異,學習者對問題的理解常常各異,在學習者共同體中便構成了一種寶貴的學習資源。
二 軍事基礎理論課程教學的困境
軍事基礎理論課程是軍事院校的主干課程,課程開設質量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未來軍官的素質,即軍官專業化的水平。但軍事院校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教學現狀仍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來自多個方面:
1.教員教學觀念落后,忽視學員學習的主體性
目前,許多教員基于行為主義和認知主義的學習理念,以傳統的教學模式進行教學。這種教學模式有利于發揮教員的主導作用,便于教員組織、監控和管理教學活動的整個過程,便于師生面對面的認知交流,因而有利于系統的軍事理論知識的傳授,但由于課堂完全由教員來主導和控制,學員的認知主體作用被忽視,處于一種被動接受的地位。因此,學員學習的積極性受到壓制,學習能力、創造精神的培養受到限制,導致學員無法利用已有的經驗去建構軍事理論與實踐知識。
2.學員課程學習目標不明確,學習動力不足
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一些學員缺乏對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理解,因而沒有明確的目標定位,學習動力不足。因為只有學習者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學習目標并形成與獲得所希望的成果相應的預期時,學習才可能是成功的。學習目標不是從外部由他人制定的,而是形成于學習過程的內部,由學習者自己制定的。如果學員缺乏管理自己學習的能力,他們就不可能成為自主的思考者和學習者,學員應在教員的幫助下,發展自己控制學習過程的能力。在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教學中,很多教員沒有意識到指導學員明確學習目標的重要性,導致學員學習動力不足。
3.課程體系僵化陳舊,缺乏生成性
建構在知識客觀主義基礎上的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課程體系陳舊僵化,過分強調間接經驗的學習和掌握。課程的設置是封閉式的,缺少發散性和開放性,并且過分注重基本理論的介紹,把知識看成是純客觀的、一成不變的,忽視知識的生成性,因而使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教材缺乏啟發性、可讀性,沒有生長點,沒有提供多種學習可能性供學員選擇,因而無法激發學員學習和探究的興趣。
4.教學過程情境缺失,教育資源單一
目前在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教學過程中,學員是在情境缺失的狀況下學習,他們沒有更多的對戰爭環境、軍事各要素之間的關系、軍事實踐的了解,缺少實踐機會,學習過程中缺乏“認知沖突”,只能是機械記憶書本上的理論,而無法進行知識建構。學員如果能在復雜真實的情境中,充分利用豐富的教育資源來完成學習任務,就會對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和深入探究的動力。
三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對軍事基礎課程教學改革的啟示
1.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軍事基礎課程教學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
首先,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傳統教學帶來了一場新的革命,使教學的中心由教師向學生轉移。根據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教學首先要使學員明確自己學習的目標,給予學員解決問題的自。學員不僅應確定所要學的問題,而且必須對問題解決的過程擁有自,教員應該刺激學員的思維,使他們參與學習目標的制定,激發他們自己解決問題。傳統的教學計劃特別強調學習目標,但學員通常并不接受這些目標,而只是關心能否通過考試。因而,我們的教學目標應該與學員學習的目標相符合。我們可以從學員那里獲得問題,并用這些問題作為學習活動的推動力,教員確定的問題應該使學員感到就是他們本人的問題,從而調動學員學習的積極性。
其次,結合軍事理論或實踐設計真實的學習任務和學習情境。建構主義認為,教師應該在教學中使用真實的任務和學習領域內的一些日常活動或實踐。這些接近生活真實的、復雜的任務整合了多重的內容或技能,它們有助于學生用真實的方式來應用所學的知識,也有助于學生意識到他們所學知識的相關性和意義。因此,結合學員的興趣讓他們選擇當代社會中的軍事問題進行探究,才會有利于他們軍事理論與實踐知識的積極建構。
再次,教員應成為學員學習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指導者和合作者,而不是單純的教授者。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不僅要求學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動接受者和知識的灌輸對象轉變為信息加工的主體、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同時也要求教師的教學主體理念發生變化,即教師要由知識的傳授者、灌輸者轉變為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組織者、促進者、幫助者。建構主義注重知識的生成性,認為學習不是由教師向學生傳遞知識,而是學生建構自己知識的過程。因此,在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教學中,教員就應當特別注意引導學員通過交流,自己來解決軍事理論與實踐的相關問題。
2.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軍事基礎理論課程教學改革提供了實踐范式
目前,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影響下形成的教學模式主要有:拋錨式教學(Anchored Instruction)模式、認知學徒(Cognitive Apprenticeship)模式、隨機訪取教學(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模式等。
拋錨式教學的主要目的是“使學生在一個完整、真實的問題背景中,產生學習的需要,并通過鑲嵌式教學以及學習共同體中成員間的互動、交流,憑借自己的主動學習、生成學習,親身體驗從識別目標到提出并達到目標的全過程”。這種教學要求創設有趣的、真實的情境以鼓勵學習者積極地進行知識建構。學徒式是一種“做中學”的最早形式,這種置于真實情境中的任務,提供了學習的有組織的和統一的作用和目的。“認知學徒制”就是要改變傳統的脫離現實生活的教學。隨機訪取教學使學習者可以隨意通過不同途徑、方式進入同樣教學內容的學習,從而獲得對同一事物或同一問題的多方面的認識和理解,這就是隨機訪取教學。
這些模式都強調教學的情境性和充分調動學生自主探究的積極性,在軍事基礎理論課程的教學中,目前比較能體現這一特點的就是研究性教學。研究性教學強調主動探究、自主學習,通過引導學員質疑、調查、實踐和參與,培養學員的問題意識,讓學員親身經歷解決問題的過程,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研究性教學主要是以問題為載體設計實施,注重知識的生成性,是師生共同構建知識和經驗的過程;研究性教學在內容、方法等方面都具有充分的開放性,注重情境性和實踐性,較充分地體現了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思想。這種以學員為主體的教學模式由于強調學員在認識過程中的主體性,強調學員在意義建構中的主動性,因而有利于學員自主學習意識的養成,發揮學員的學習積極性,有助于培養創新精神、創新能力和適應能力,改變學員被動學習的現狀。
參考文獻
[1]毛新勇.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在教學中的應用[J].課程·教材·教法,1999(9)
[2]蘇華.論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與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J].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