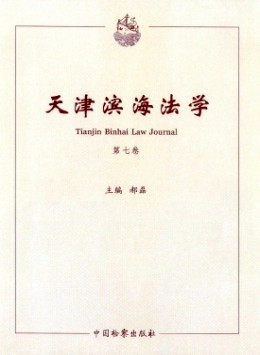民法典的條款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民法典的條款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關(guān)鍵詞:民法總則 必要性
一、各國模式
民法總則就是統(tǒng)領(lǐng)民法典并且民法各個(gè)部分共同適用的基本規(guī)則,也是民法中最抽象的部分。民法典作為高度體系化的成文立法,注重一些在民事領(lǐng)域中普遍適用的規(guī)則是十分必要的。傳統(tǒng)大陸法系國家大都采取潘德克頓體例,在民法典中設(shè)立總則。也有一些大陸法系的民法典中沒有設(shè)立總則,在民法中是否應(yīng)當(dāng)設(shè)立總則以及其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包括那些,是一個(gè)值得探討的問題。為了盡快制定一部體系完整、內(nèi)容充實(shí)、符合中國國情的民法典,首先必須討論民法典總則的設(shè)立問題。
綜觀大陸法系各國民法典編纂體系,具有代表性的不外乎羅馬式與德國式兩種。一是羅馬式。該體系是由羅馬法學(xué)家蓋尤斯在《法學(xué)階梯》中創(chuàng)設(shè)的,分為“人法、物法、訴訟法”三編。這種三編的編纂體系被法國民法典全盤接受,但法國民法典剔除了其中的訴訟法內(nèi)容,把物法分為財(cái)產(chǎn)及對(duì)所有權(quán)的各種限制和取得財(cái)產(chǎn)的各種方法。由于采納了此種體系,法國民法典沒有總則,缺少關(guān)于民事活動(dòng)的一般原則。有關(guān)民法的一般規(guī)則、原則體現(xiàn)在學(xué)者的學(xué)理中。瑞士、意大利等歐洲大陸國家民法、以及受法國法影響的一些國家的民法典也不采納總則編的設(shè)置或僅設(shè)置宣示性的“小總則”。二是德國式。總則編始于18世紀(jì)日爾曼普通法對(duì)6世紀(jì)優(yōu)士丁尼大帝所編纂的”學(xué)說匯編”所做的體系整理;該體系最早被胡果(Hugo)在1789年出版的《羅馬法大綱》一書中采用,最后由薩維尼在其潘德克頓教程中系統(tǒng)整理出來,并為《德國民法典》所采用。因?yàn)榭倓t的設(shè)立,進(jìn)一步增進(jìn)了其體系性。因此,許多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qū)民法,都采取了潘德克頓體例。?
然而一些學(xué)者對(duì)總則的設(shè)立提出異議,否定設(shè)立總則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總則的規(guī)定是學(xué)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一種抽象,更像是一種教科書的體系。而法律的目的不是追求邏輯體系的圓滿,而是提供一種行為規(guī)則和解決紛爭的準(zhǔn)則。而且總則的規(guī)定大多比較原則和抽象,缺乏具體的實(shí)用性和可操作性。第二,總則的設(shè)定使民法的規(guī)則在適用上的簡易性和可操作性反而降低,把原本統(tǒng)一的具體的生活關(guān)系割裂在民法中的各個(gè)部分。在法律適用時(shí),要尋找關(guān)于解決某一法律問題的法律規(guī)定,不能僅僅只查找一個(gè)地方,所要尋找的有關(guān)規(guī)定,往往分處于民法典的不同地方。這對(duì)法律的適用造成了麻煩。第三,由于設(shè)立總則必須要設(shè)定許多民法共同的規(guī)則即一般條款,但在設(shè)定一般條款的同時(shí)必須設(shè)立一些例外的規(guī)定。但哪些規(guī)則應(yīng)當(dāng)屬于一般規(guī)定置于總則,哪些規(guī)則應(yīng)當(dāng)作為例外規(guī)定,一般規(guī)定和例外規(guī)定的關(guān)系是什么,在法律上很難把握。
二、設(shè)立民法總則的理由
盡管民法典總則的設(shè)立遭到了許多學(xué)者的非難,但德國民法典設(shè)立總則的意義和價(jià)值是絕不可低估的。我認(rèn)為,從法國民法典未設(shè)總則到德國民法典設(shè)立總則,本身是法律文明的一種進(jìn)步。在我國民法典制訂過程中,對(duì)是否應(yīng)當(dāng)確立總則的問題,也有不同看法。有些學(xué)者主張我國民法典應(yīng)當(dāng)采用“松散式”或“匯編式”模式制訂,從而無需設(shè)立總則。但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贊成設(shè)立總則。我認(rèn)為民法典設(shè)立總則是必要的,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總則的設(shè)立增強(qiáng)了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可避免重復(fù),使法典更為簡潔。因?yàn)槊穹ǖ涞膬?nèi)容過于復(fù)雜,條文過多,通過總則的設(shè)定,可以避免重復(fù)規(guī)定。德國馬普研究所的卓布尼格教授即認(rèn)為,設(shè)立總則的優(yōu)點(diǎn)在于:總則條款有利于統(tǒng)領(lǐng)分則條款,確保民法典的和諧性;總則條款有助于減少分則條款,從而加快立法步伐;總則條款有利于民法典本身在新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情勢(shì)面前作出必要的自我調(diào)整。總則的設(shè)立使各個(gè)部分形成一個(gè)邏輯體系,將會(huì)減少對(duì)一些共性規(guī)則的重復(fù)規(guī)定,有利于立法的簡潔明了。盡管沒有民法總則并非不能形成民法典,但沒有民法總則,法典的體系就必然會(huì)淡化、削弱。除了商事特別法以外,民法的內(nèi)容本身是非常豐富的。如果將一些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從共同適用的規(guī)則中抽象出來,形成為總則,那么民法的內(nèi)在體系將更為嚴(yán)密,否則,將是散亂的。不可否認(rèn),民法總則并非適用于各項(xiàng)民事制度,但只要它能夠適用于大多數(shù)民事制度,那么它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價(jià)值。總則的設(shè)立使民法典形成了一個(gè)從一般到具體的層層遞進(jìn)的邏輯體系。
第二,總則增強(qiáng)了法典的體系性。凡是有總則的法典,體系性更強(qiáng)。潘德克頓學(xué)派設(shè)立總則的意義在于使人法和物法二者銜接起來,形成一個(gè)有機(jī)的整體。因?yàn)樵谌朔?或稱身份法)和物法(或稱財(cái)產(chǎn)法)兩部分里,確實(shí)存在著共同的問題,從而應(yīng)當(dāng)有共同的規(guī)則。例如主體(權(quán)利主體),客體(權(quán)利客體),權(quán)利的發(fā)生、消滅與變更,權(quán)利的行使等。這樣,在人法和物法之上,設(shè)一個(gè)總則編,規(guī)定人的能力、法律行為等,是可能也是應(yīng)該的。 同時(shí)避免和減少了重復(fù)規(guī)定,達(dá)到立法簡潔的目的。在設(shè)置了總則之后,德國民法典把性質(zhì)不同的民事關(guān)系分別獨(dú)立出來由分則各編加以規(guī)定。并在此基礎(chǔ)上構(gòu)建了兩個(gè)嚴(yán)密的邏輯體系,按照王澤鑒先生的看法,總則最主要的優(yōu)點(diǎn)在于,將私法上的共同事項(xiàng)加以歸納,匯集一處加以規(guī)定,具有合理化的作用,避免重復(fù)或大量采用準(zhǔn)用性規(guī)定。黑克(Heck)將總則編的這一作用比喻為“列車時(shí)刻表符號(hào)說明”:前面已經(jīng)說明過的東西,后面就沒有必要再作重復(fù)了。反之,如果不設(shè)立總則,而立法者要達(dá)到既全面又不重復(fù)的目的,就必須運(yùn)用參引的技術(shù)。
第2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將環(huán)境規(guī)范的抽象化內(nèi)容納入民法總則
在民法總則中納入環(huán)境規(guī)范中的一般化規(guī)范,提取環(huán)境規(guī)范中的公因子內(nèi)容。民法總則作為對(duì)民法分則各部分提取公因式的產(chǎn)物,是高度抽象化的結(jié)果。目前《民法總則草案》共分為n章,包括基本原則、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民事權(quán)利、民事法律行為、、民事責(zé)任、訴訟時(shí)效和除斥期間、期間的計(jì)算、附則等。從部分條款來看,該草案納入了部分環(huán)境規(guī)范的條款,具備鮮明的時(shí)代特征。其中,第七條規(guī)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dòng),應(yīng)當(dāng)保護(hù)環(huán)境、節(jié)約資源,促進(jìn)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該條文在民法學(xué)界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反對(duì)論者認(rèn)為該條款的加入徒然增加了民法典的不當(dāng)負(fù)擔(dān),屬于應(yīng)當(dāng)刪去的條款,也有觀點(diǎn)認(rèn)為此類無害條款不會(huì)對(duì)整個(gè)民法典產(chǎn)生損害,可予以保留,并不會(huì)發(fā)揮規(guī)范作用。實(shí)際上,在民法典中的基本原則部分加入環(huán)境保護(hù)的基本原則,不僅宣示了民法典的基本價(jià)值取向,對(duì)日后所產(chǎn)生的環(huán)境相關(guān)糾紛同樣具備重要的指導(dǎo)價(jià)值,應(yīng)當(dāng)在未來的民法典中予以保留。此外,該草案第一百六十條第(五)項(xiàng)增加了修復(fù)生態(tài)環(huán)境作為民事責(zé)任的承擔(dān)方式,從責(zé)任端融入了環(huán)境保護(hù)的規(guī)范因子。
盡管《民法總則草案》在前兩個(gè)條文中納入了一定環(huán)境保護(hù)規(guī)范的內(nèi)容,但是在實(shí)質(zhì)體系上仍然存在諸多缺失。首先,在民事主體與客體部分,未能反映環(huán)境法律主體與客體內(nèi)容,仍然停留于主體客體的二元區(qū)分層面。從主體層面而言,可考慮納入完全主體之外的非完全主體(準(zhǔn)主體),并由此避免將非人物種人類化或者保護(hù)不足的困境。在客體層面,環(huán)境法客體雖然與民事客體存在明顯區(qū)別,但通過類型化的方式仍然可以確定為物與行為,并由此構(gòu)建起交易客體與權(quán)利客體范疇,搭建起完整的環(huán)境法律關(guān)系鏈條,以回應(yīng)業(yè)已出現(xiàn)的環(huán)境交易制度。其次,在基本民事權(quán)利部分中,應(yīng)當(dāng)納入環(huán)境權(quán)利的基本范疇,并通過具體規(guī)范明確環(huán)境權(quán)的法典地位。目前,總則草案遵循人格權(quán)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基本劃分思路,并進(jìn)一步區(qū)分為物權(quán)、債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繼承權(quán)等權(quán)利類型,構(gòu)建了較為開放的權(quán)利體系。環(huán)境權(quán)利作為環(huán)境保護(hù)的權(quán)利基點(diǎn),應(yīng)當(dāng)將其與民法制度進(jìn)行整合銜接,可采取對(duì)現(xiàn)行民法制度中關(guān)系到環(huán)境法的部分進(jìn)行生態(tài)化解釋或?qū)樱蛘邔?duì)于現(xiàn)行民法制度中沒有的環(huán)境規(guī)范建立起新的制度回。將環(huán)境權(quán)作為人格權(quán)的一部分,雖然具有財(cái)產(chǎn)性內(nèi)容,但實(shí)質(zhì)意義上更加關(guān)涉?zhèn)€人的生存權(quán)以及自然地位。通過構(gòu)建明確的權(quán)利條款有助于為環(huán)境私法提供請(qǐng)求權(quán)基礎(chǔ),避免保護(hù)空自。
妥善處理環(huán)境規(guī)范與物權(quán)法的關(guān)系
在物權(quán)法中,與現(xiàn)有環(huán)境規(guī)范存在緊張關(guān)系的主要是動(dòng)物、植物、生態(tài)環(huán)境等的規(guī)范地位問題。譬如,在動(dòng)物的法律地位問題上,《德國民法典》第90a條規(guī)定,“動(dòng)物不是物。動(dòng)物受特別法律的保護(hù)。除另有規(guī)定外,關(guān)于物的規(guī)定準(zhǔn)用于動(dòng)物。”該條雖然出現(xiàn)在《德國民法典》的總則部分,但其規(guī)范對(duì)象是動(dòng)物的法律地位問題。在我國未來的民法典中,即使總則部分不能予以明確涉及,在物權(quán)法部分也不應(yīng)忽略。進(jìn)一步而言,動(dòng)物的法律地位問題反映了既有的物權(quán)制度與環(huán)境資源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包括陽光、水、土地、空氣等在內(nèi)的資源。其一方面關(guān)涉到所有權(quán)人的福社,另一方面又關(guān)系到社會(huì)福社。作為物質(zhì)性的存在形態(tài),環(huán)境資源應(yīng)當(dāng)在物權(quán)規(guī)范中予以體現(xiàn),包括物權(quán)法的一般規(guī)定以及具體的保護(hù)規(guī)范。常紀(jì)文建議將環(huán)境作為特殊的民事權(quán)利客體進(jìn)行規(guī)定,并且對(duì)一些生態(tài)功能具有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的環(huán)境資源確認(rèn)其財(cái)產(chǎn)權(quán),將其視為動(dòng)產(chǎn)囚。
妥善處理環(huán)境規(guī)范與合同法的關(guān)系
在合同法中,應(yīng)當(dāng)擴(kuò)充合同規(guī)范的廣度,將其從簡單的債之關(guān)系擴(kuò)充至包括各種環(huán)境合同在內(nèi)的范圍之上。近年來,包括排污權(quán)交易、碳交易等環(huán)境交易類型方興未艾,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作用日漸重要。這些新型的環(huán)境交易不僅要求明確的概念界定、政府監(jiān)管以及具體制度設(shè)計(jì),也需要與合同規(guī)范進(jìn)行對(duì)接,以明確其交易標(biāo)的、主體制度、交易行為、交易平臺(tái)等內(nèi)容回。這些交易雖然對(duì)象特別,管制需求強(qiáng)烈,但仍然是當(dāng)事人意思自治的產(chǎn)物,在規(guī)范適用上需要合同法的資源供給。在放棄制定債法總則的立法思路背景下,在合同法中反映環(huán)境合同交易勢(shì)在必行,否則將導(dǎo)致立法負(fù)擔(dān)轉(zhuǎn)向司法負(fù)擔(dān)的消極后果。
第3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二十世紀(jì)中葉以后的民法典制定-無論是越南、俄羅斯聯(lián)邦,還是中國-進(jìn)入環(huán)境問題非常嚴(yán)重的時(shí)代,它既不同于《德國民法典》制訂之時(shí),也不同于《法國民法典》制訂之時(shí),更不同于《羅馬法大全》編纂之時(shí)。作為世界上最新的民法典,《越南民法典》、《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都很有勇氣地貼近時(shí)代背景,產(chǎn)生了《德國民法典》、《法國民法典》、《羅馬法大全》所沒有的新類型條款(主要集中在物權(quán)法部分),為環(huán)境資源保護(hù)開辟了新的私法途徑。我國民法典中的相鄰關(guān)系立法應(yīng)與民法典中的其他部分一起,回應(yīng)“綠色”的歷史境遇。
一、相鄰關(guān)系立法宗旨之檢討
綜觀相鄰關(guān)系立法宗旨,至少應(yīng)包括兩個(gè)階段:
(一)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為主,環(huán)境負(fù)擔(dān)最小
相鄰關(guān)系法的目的是為了相鄰不動(dòng)產(chǎn)的“便宜”,包括經(jīng)濟(jì)便宜和環(huán)境便宜。從相鄰他方的角度來看,這種“便宜”實(shí)即“負(fù)擔(dān)”,即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和環(huán)境負(fù)擔(dān)。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設(shè)定的原則是益本(收益和成本)比較,即相鄰一方因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的設(shè)定所帶來的收益大于其為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的設(shè)定所支付的成本。環(huán)境負(fù)擔(dān)是指為了環(huán)境的保全而對(duì)相鄰不動(dòng)產(chǎn)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所施加的限制,最常見的例子是:為了日照、通風(fēng)、采光而對(duì)相鄰方建筑行為的限制,即使受限的經(jīng)濟(jì)利益很大。從古羅馬法到《德國民法典》,是環(huán)保需求低的階段,所以,全部相鄰關(guān)系的立法重點(diǎn)在于將相鄰權(quán)盡可能多地賦予經(jīng)濟(jì)便宜需求,盡可能少地賦予環(huán)境便宜需求。
(二)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為主,環(huán)境負(fù)擔(dān)擴(kuò)張
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環(huán)保需求較高的階段,理應(yīng)改變以往的立法宗旨,將相鄰權(quán)更多地賦予環(huán)境便宜需求,即承認(rèn)在某些環(huán)境資源保護(hù)情形下,相鄰一方不動(dòng)產(chǎn)可以對(duì)相鄰他方不動(dòng)產(chǎn)享有相鄰權(quán)。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程度不同的國家或同一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程度不同的時(shí)期,環(huán)境負(fù)擔(dān)擴(kuò)張的范圍是不同的,但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仍將在相鄰關(guān)系中占有相當(dāng)?shù)谋壤T跉v史的將來階段,完全可能出現(xiàn)“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縮小、環(huán)境負(fù)擔(dān)擴(kuò)張”,“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最小、環(huán)境負(fù)擔(dān)最大”這兩個(gè)較高級(jí)階段。
二、相鄰關(guān)系立法體系之重構(gòu)
(一)公法相鄰關(guān)系與私法相鄰關(guān)系
公法相鄰關(guān)系立法主要有環(huán)保法、建筑法、都市計(jì)劃法。它們的功能主要在于保護(hù)生活環(huán)境、預(yù)防火災(zāi)、追求布局上的美感。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些公法相鄰關(guān)系將本應(yīng)由私法相鄰關(guān)系調(diào)整的生活事實(shí)包括進(jìn)來。例如,《德國民法典》、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民法典等就沒有將通風(fēng)、眺望、日照納入,而是由公法調(diào)整,但上述生活事實(shí)較多地涉及到單個(gè)人的私益(尤其在農(nóng)村),或人數(shù)較多人的共同利益(尚難稱為公益,如公寓住戶),由公法來調(diào)整,在法理上缺乏根據(jù),也損害了“私益處分主義”的私法自治原則。對(duì)于人稠地少的小國或大國(如中國)來講,私人放棄相鄰環(huán)境利益可以節(jié)約土地,意義非淺。所以,在民法典制定之際,應(yīng)仔細(xì)分析不同的利益形態(tài),環(huán)保法等公法中屬于私法自治范圍的應(yīng)納入民法典中,屬于公益范圍的應(yīng)留在公法中。
(二)私法相鄰關(guān)系: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地役權(quán)合同等合同相鄰關(guān)系法和社區(qū)相鄰關(guān)系法
私法相鄰關(guān)系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第一,地役權(quán)客體應(yīng)不僅限于土地,尚應(yīng)擴(kuò)及工作物和空間,這樣,在土地、工作物、空間這三個(gè)客體之間通過排列組合,可以形成多項(xiàng)役權(quán)。應(yīng)通過諸如“以環(huán)境保護(hù)為目的之役權(quán)”等例示規(guī)定,來引導(dǎo)提示民眾,為環(huán)境資源保護(hù)提供更多的交易選擇。例如,奧地利民法典就規(guī)定可在鄰人屋檐上設(shè)定役權(quán)以澆灌己地花園等,這是土地對(duì)工作物的役權(quán)。第二,債權(quán)性環(huán)境保護(hù)合同應(yīng)當(dāng)列為有名合同,并通過調(diào)查研究確定典型條款,以起到減省交易成本、提高裁判預(yù)見度、提供公平尺度等功能,為相鄰環(huán)境保護(hù)提供新的交易工具。第三,社區(qū)相鄰關(guān)系法的性質(zhì)為自治規(guī)則,應(yīng)在民法典中用專條承認(rèn)其地位、制定條件及程序等。
建議在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中增列兩條:一是規(guī)定地役權(quán)合同等合同相鄰關(guān)系法可以為了環(huán)保目的(環(huán)保合同)、營業(yè)目的(營業(yè)地役權(quán))等,改變或改善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中的絕大部分條款。二是規(guī)定社區(qū)(建筑物區(qū)分所有人團(tuán)體、農(nóng)村的村民小組)可以為了環(huán)保目的、其他目的制定規(guī)約。這樣,體系就很清晰。
(三)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本身的體系重構(gòu)
是否可能在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內(nèi)單列一節(jié)規(guī)定環(huán)保相鄰關(guān)系,是一個(gè)值得探討的問題。目前各國民法典尚無此立法例。由于技術(shù)上高度困難,筆者不贊成單列,如果民法典總則或物權(quán)法總則中沒有一般環(huán)保條款,可在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內(nèi)增設(shè)一個(gè)一般環(huán)保條款,如:相鄰各方處理相鄰關(guān)系,應(yīng)遵循不損害或有利于環(huán)境資源保護(hù)原則。以此作為環(huán)境負(fù)擔(dān)(即環(huán)境相鄰權(quán))的生長點(diǎn),并統(tǒng)轄所有的環(huán)境相鄰關(guān)系。
三、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的制度變遷
(一)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的制度變遷的方式
主要有三種方式:其一是新制度的建立;其二是舊制度的功能增多;其三是舊制度的調(diào)整對(duì)象擴(kuò)張。這三種方式是不動(dòng)產(chǎn)相鄰關(guān)系法自身對(duì)環(huán)保理念的回應(yīng),具體分析如下:
(二)鄰地?fù)p害防免規(guī)則
可增加的新規(guī)則有:第一,對(duì)《德國民法典》第906條加以修改,形成新的規(guī)則。比如,規(guī)定在不可量物侵入輕微的情形下,亦可要求鄰地負(fù)最佳防免義務(wù)或損害賠償?shù)鹊取_@是一種高水平的環(huán)保,對(duì)于我國尚無可能。第二,臺(tái)灣等地區(qū)民法典及我國民法通則都沒有規(guī)定工作物、植物建造、種植的距離規(guī)則以及界墻規(guī)則來促進(jìn)環(huán)保或防火。王利明教授主持的我國民法典草案中就設(shè)定了這些新的規(guī)則(但《法國民法典》早有規(guī)定)。
舊規(guī)則的功能增多,表現(xiàn)在:第一,越界植物枝根規(guī)則最初立法意圖僅是排除對(duì)土地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的妨害,后來民眾日益重視日照、通風(fēng)、采光等生態(tài)價(jià)值,則此規(guī)則就同時(shí)儲(chǔ)存了兩種價(jià)值保護(hù)機(jī)能,這樣的讀解是從規(guī)則的歷史語境出發(fā)的,并可貫徹到全部相鄰規(guī)則中。第二,就《法國民法典》中的分界物規(guī)則而言,最初的意圖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所有權(quán)的絕對(duì)性,并表達(dá)了對(duì)封建領(lǐng)主自由進(jìn)入土地狩獵的厭惡心態(tài)。但實(shí)際上分界物既可促進(jìn)環(huán)保(防止臭氣、濕氣、暗響、熱氣等),也可以破壞環(huán)境(過高的分界物會(huì)影響通風(fēng)、采光、日照),所以其環(huán)保功能是當(dāng)初立法者不可能預(yù)料得到的。
舊規(guī)則的調(diào)整對(duì)象擴(kuò)張,主要是“不可量物及類似物”這兩個(gè)概念內(nèi)涵小外延大,將來出現(xiàn)的、未來民法典中列舉的新類型不可量物悉可包攬無遺。
(三)鄰地利用規(guī)則
目前立法通例僅承認(rèn)管線安設(shè)、營建、通行等情形方可利用鄰地。應(yīng)當(dāng)新增一條規(guī)則:基于環(huán)境資源保護(hù)目的,相鄰一方可以利用他方不動(dòng)產(chǎn),但應(yīng)以最小損害的方法使用之,并給予相應(yīng)的補(bǔ)償。我國自然保護(hù)區(qū)等環(huán)保區(qū)域眾多,與其毗鄰的不動(dòng)產(chǎn)上存在著私人權(quán)利,除了管線安設(shè)、營建、通行等以外,完全可能出現(xiàn)許多難以預(yù)料的需要利用鄰地的情形。如:珍稀動(dòng)物進(jìn)入鄰地,但又不能立即取回,需在鄰地上喂養(yǎng)較長時(shí)間;珍稀植物生長蔓延,大片越至鄰地,此時(shí)應(yīng)排除越界植物枝根規(guī)則的適用以保護(hù)生物多樣性;魚類等水生動(dòng)物因季節(jié)性產(chǎn)卵,游至某設(shè)定了水權(quán)的水域,亦應(yīng)限制水權(quán)的行使。管道安設(shè)規(guī)則涉及排污問題,其自始至終發(fā)揮著環(huán)保功能。
(四)水之相鄰關(guān)系規(guī)則
我國水法規(guī)定水資源屬國家所有,這對(duì)傳統(tǒng)水之相鄰關(guān)系規(guī)則產(chǎn)生了較大的沖擊,使之發(fā)生了變化。如自然流水的相鄰使用規(guī)則就被水權(quán)的優(yōu)先權(quán)規(guī)則所取代。但在異地水域上享有水權(quán)的人仍需在鄰地上設(shè)定引水權(quán)等,自然水(如雨、雪、冰)的排放規(guī)則也仍應(yīng)保存,所以傳統(tǒng)水之相鄰關(guān)系規(guī)則既有應(yīng)保存的部分,也有應(yīng)舍棄的部分。
水之相鄰關(guān)系規(guī)則最初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促進(jìn)土地資源的開發(fā)、利用,這與當(dāng)時(shí)的經(jīng)濟(jì)政策是吻合的。到環(huán)保意識(shí)較強(qiáng)的階段,該規(guī)則很大程度上又起到了保護(hù)土壤資源的作用,這是一個(gè)功能轉(zhuǎn)換的過程。
筆者以為應(yīng)增設(shè)新的規(guī)則:為防止土地沙化、鹽堿化、退化等緊急事情,相鄰一方可以優(yōu)先于他方行使水權(quán),或者可以使用他方土地上的儲(chǔ)水,但應(yīng)以不對(duì)他方土地資源造成重大損害為限,并應(yīng)予以相應(yīng)的補(bǔ)償。
(五)權(quán)利收購規(guī)則
第4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提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法在價(jià)值與體系方面均取得進(jìn)步,具體表現(xiàn)為人的私法主體地位的逐步確立、私法自治基石性地位的奠定、私人利益與私人權(quán)利得以確立并獲確實(shí)保障、民法的科學(xué)性得到長足發(fā)展等。不過,現(xiàn)行民法在形式理性化的程度上仍有改進(jìn)的空間。對(duì)中國社會(huì)而言,堅(jiān)持民法的自主性、形式化發(fā)展方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時(shí),也必須通過保持民法一定程度的開放性來克服形式理性法的某些內(nèi)在缺陷。
一、民法形式理性化:未竟的事業(yè)
韋伯認(rèn)為,近代以來法律的發(fā)展趨勢(shì),就是從"實(shí)質(zhì)"理性發(fā)展到"形式"理性、法律中的形式性逐漸呈現(xiàn)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過程,他進(jìn)而指出,此種構(gòu)成西方法律特色的形式理性法,是作為一種同樣理性的經(jīng)濟(jì)制度的資本主義的運(yùn)行的一個(gè)近乎必要的條件,對(duì)西方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fā)展具有決定性貢獻(xiàn)。
羅伯特昂格爾進(jìn)一步闡發(fā)了韋伯的觀點(diǎn)。他詮釋了一種與法制相關(guān)的"自主性"概念。自主性的特征尤其關(guān)鍵,正是它使得"法律秩序"成為一種形式性的規(guī)則體系。自主性是指表現(xiàn)在實(shí)體內(nèi)容、機(jī)構(gòu)、方法與職業(yè)上的一種自我運(yùn)作的邏輯,它包括區(qū)別于宗教、道德以及政治的實(shí)體自主性、司法獨(dú)立的機(jī)構(gòu)自主性、秉具獨(dú)特推理與論證方式的方法自主性以及自律性律師業(yè)的職業(yè)自主性。其中,實(shí)體自主性是指政府制定和強(qiáng)制執(zhí)行的規(guī)范并不是其他非法律觀念(如政治的、經(jīng)濟(jì)的或宗教的觀念)的再現(xiàn)和重復(fù)。以此來檢視30年來中國民法發(fā)展的軌跡,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中國民法的發(fā)展其實(shí)也經(jīng)歷了一個(gè)類似的從非形式法向形式法(自治法)轉(zhuǎn)變的過程。不過,中國現(xiàn)行民法距一個(gè)成熟的形式理性法仍有相當(dāng)?shù)牟罹唷?/p>
(一)內(nèi)在價(jià)值存在一定沖突
在當(dāng)前價(jià)值多元的開放社會(huì)中,除了應(yīng)遵循一些業(yè)已達(dá)成共識(shí)的價(jià)值觀念外,立法者完全可以根據(jù)自己的內(nèi)在價(jià)值判斷作出不同的價(jià)值選擇。"民事規(guī)范牽涉到的價(jià)值決定,如交易安全與意思自由間(無權(quán))或與財(cái)產(chǎn)權(quán)間(善意取得)的權(quán)衡,意思自由與利益衡平間的權(quán)衡(無因管理),創(chuàng)新與守成間的權(quán)衡(動(dòng)產(chǎn)加工),未成年人保護(hù)與交易安全間的權(quán)衡(成年制度),親情與公共利益間的權(quán)衡(死亡宣告)等等,是可以也應(yīng)該因社會(huì)而異的。"但是,一旦立法者選定了某種主導(dǎo)性價(jià)值,就應(yīng)將這一價(jià)值取向一以貫之,不要?jiǎng)虞m創(chuàng)設(shè)例外,或者隨意擴(kuò)張其他價(jià)值的適用空間,否則就會(huì)加劇價(jià)值之間的沖突。如中國民法原則上堅(jiān)守了抽象人格、形式平等的價(jià)值。而《合同法》第229條規(guī)定,"租賃物在租賃期間發(fā)生所有權(quán)變動(dòng)的,不影響租賃合同的效力。"由此建立了"買賣不破租賃"制度。"立法上之所以要強(qiáng)化租賃權(quán)的效力,主要是認(rèn)為承租人為經(jīng)濟(jì)上的弱者,為避免其于所有權(quán)變換時(shí)遭受權(quán)利之受損,故特設(shè)不破租賃的規(guī)定,以保障其權(quán)利。"因此,"買賣不破租賃"顯然是建立在具體人格與實(shí)質(zhì)平等的價(jià)值之上。不過,"承租人"的概念所涵蓋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主體的范圍是極其廣泛的,不動(dòng)產(chǎn)的租賃,至少在大多數(shù)情形下,確實(shí)可說涉及基本生存保障問題,不論假設(shè)承租一方為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弱者,或在契約訂立與履行上處于交易的弱勢(shì),都還不算離譜,但動(dòng)產(chǎn)的承租人則不存在類似的問題。因此,該條不當(dāng)擴(kuò)張了抽象人格、實(shí)質(zhì)平等等價(jià)值的適用空間,由此造成抽象人格與具體人格、形式平等與實(shí)質(zhì)平等之間的劇烈沖突。
雖然人格尊嚴(yán)、私人自治等價(jià)值觀念在中國獲得普遍的弘揚(yáng),但民法在落實(shí)這些價(jià)值方面仍有若干可議之處,從而產(chǎn)生了內(nèi)在價(jià)值實(shí)踐程度偏弱的現(xiàn)象,這也不符合形式理性法的要求。
如關(guān)于平等的價(jià)值要求,民法應(yīng)忽略各個(gè)社會(huì)個(gè)體的異殊性,無一例外地賦予他們成為民法上"人"的資格,從而使得各個(gè)個(gè)體得以毫無差別地進(jìn)入市民社會(huì)從事民事活動(dòng)。然而,《合同法》第52條第1款規(guī)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為無效合同。
第54條規(guī)定"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duì)方在違背真實(shí)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quán)請(qǐng)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jī)構(gòu)變更或者撤銷。"由此表明,當(dāng)被欺詐、脅迫方為國有企業(yè)時(shí),合同應(yīng)被確認(rèn)為無效;而當(dāng)被欺詐、脅迫方為非國有企業(yè)時(shí),受害人只能請(qǐng)求法院或仲裁機(jī)構(gòu)變更或撤銷合同。這種主體立法思想,使不同主體受到不同的法律對(duì)待,不符合平等的價(jià)值原則。
(二)規(guī)則存在一定漏洞與沖突
"法典不可能沒有縫隙",囿于人類認(rèn)識(shí)能力的局限性與法律的滯后性等原因,法律漏洞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在應(yīng)當(dāng)而且能夠?qū)⒂嘘P(guān)事項(xiàng)加以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就沒必要保留法律漏洞,讓法律存在調(diào)整的飛地。在中國民法中,還存在著大量的法律空白現(xiàn)象,如《民法通則》尚未確立社團(tuán)法人、財(cái)團(tuán)法人、意思表示、隱私權(quán)等制度;《合同法》尚未規(guī)定情更原則等制度,未確立借用、實(shí)物借貸、儲(chǔ)蓄等轉(zhuǎn)讓財(cái)產(chǎn)使用權(quán)或所有權(quán)的合同,以及雇用、演出、培訓(xùn)、郵政、醫(yī)療、出版等提供服務(wù)的合同;《物權(quán)法》未確立取得時(shí)效、添附、先占等制度。
規(guī)則的沖突,表現(xiàn)為各種規(guī)則之間存在理念上、內(nèi)容上和邏輯上的矛盾或者抵觸。中國現(xiàn)行民法中存在著部分規(guī)則沖突的現(xiàn)象。如《民法通則》第106條確立了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但是《民法通則》第132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對(duì)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cuò)的,可以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由當(dāng)事人分擔(dān)民事責(zé)任。"該條將原本只能扮演例外角色的衡平確立為侵權(quán)法的一項(xiàng)基本歸責(zé)原則——"公平責(zé)任原則".由于該條并未將公平責(zé)任類型化,在適用上對(duì)過錯(cuò)責(zé)任造成巨大的沖擊。"這樣的法律條文以及法庭行為是違反邏輯的。法律既然已經(jīng)規(guī)定過錯(cuò)賠償,怎么能夠同時(shí)規(guī)定即使無過錯(cuò)也有賠償責(zé)任呢?"畢竟"嚴(yán)格的形式主義立場,只能恪守邏輯一致性作出非此即彼的單一選擇。"而且財(cái)產(chǎn)的有無、多寡成為了判斷加害人應(yīng)否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的基本依據(jù),這在近代以降的世界民法史上恐怕都是絕無僅有的。再如,《民法通則》規(guī)定了這一來源于傳統(tǒng)大陸法系民法的制度,該制度貫徹了所謂的公開性原則,因此它被稱為顯名或直接。
從直接的內(nèi)涵來看,它顯然不包括某人以自己名義但為授權(quán)人利益而與他人為法律行為的情形,但《合同法》借鑒了英美法系的制度,并在第403、404條對(duì)隱名與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作出了較詳細(xì)的規(guī)定,由于《合同法》沒有限制間接的適用范圍,從而導(dǎo)致了該制度與《民法通則》所確立的直接制度的沖突。
(三)民法中公法規(guī)定有失泛化
公私法相互獨(dú)立乃是法治的基本原則,因此,"公法的歸公法,私法的歸私法。"除非為實(shí)現(xiàn)規(guī)范目的所必備,私法中不應(yīng)容留公法規(guī)范。現(xiàn)行民法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公法規(guī)定泛化的問題。如《合同法》第38條規(guī)定,"國家根據(jù)需要下達(dá)指令性任務(wù)或者國家訂貨任務(wù)的,有關(guān)法人、其他組織之間一方依照有關(guān)法律、行政法規(guī)規(guī)定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訂立合同。"該條并非創(chuàng)設(shè)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負(fù)有依指令性計(jì)劃或國家訂貨任務(wù)訂立合同的義務(wù),因?yàn)樵摿x務(wù)原已存在,而民事主體違反該義務(wù)訂立的合同,倘未達(dá)到違反強(qiáng)制性規(guī)范的程度就不應(yīng)使之無效,因此,本條的"訓(xùn)示"并無多大意義。第127條規(guī)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和其他有關(guān)行政主管部門在各自的職權(quán)范圍內(nèi)對(duì)的違法行為,負(fù)責(zé)監(jiān)督處理;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該條只是對(duì)行政機(jī)關(guān)的訓(xùn)示,置入《合同法》中對(duì)當(dāng)事人與裁判者并無多少規(guī)范意義。再如《合同法》第128條、《物權(quán)法》第32、33條很多處規(guī)定了爭議解決程序,教導(dǎo)人們?nèi)绾芜M(jìn)行爭議解決程序的選擇,這其實(shí)并非民法所應(yīng)發(fā)揮的功能。
(四)民事單行法之間存在沖突與不協(xié)調(diào)
截止到2008年3月,中國現(xiàn)行有效的法律總共229件,涵蓋憲法、憲法性法律、民商法、經(jīng)濟(jì)法、社會(huì)法、刑法、訴訟及非訴訟程序法等,其中,民事法律共32件。除此之外,現(xiàn)行有效的行政法規(guī)近600件,地方性法規(guī)約7000多件,其中大量涉及到民商事制度。從內(nèi)容上看,這些民商事法律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涉及傳統(tǒng)民法典的內(nèi)容的法律,如《婚姻法》、《繼承法》、《合同法》和《物權(quán)法》等。第二類是涉及傳統(tǒng)商法范疇的單行法,主要包括《公司法》、《票據(jù)法》、《海商法》、《保險(xiǎn)法》、《破產(chǎn)法》等。第三類是其他性質(zhì)的部門法律中所包含的民事規(guī)范,主要包括行政法、經(jīng)濟(jì)法、社會(huì)法等法律部門中所包括的民事規(guī)范,如《土地管理法》、《房地產(chǎn)管理法》、《反壟斷法》等法律之中的民事規(guī)范。由于單行法是在沒有民法典統(tǒng)轄的情況下制定的,這些單行法并沒有統(tǒng)一貫徹民法的價(jià)值,也沒有按照民法典的體系來構(gòu)建,相反,它們各有自己的價(jià)值傾向,事實(shí)上已自成體系,且各個(gè)單行法相互之間存在著較嚴(yán)重的重復(fù)、沖突與矛盾的現(xiàn)象。此外,某些重要的制度沒有由單行法加以規(guī)定,導(dǎo)致現(xiàn)行立法格局存在著嚴(yán)重的缺漏。
當(dāng)然,或許有學(xué)者會(huì)提出,對(duì)上述部分立法瑕疵,裁判者可以通過運(yùn)用各種法律適用的規(guī)則來竭力化解,不過,這顯然不能成為立法者于民法創(chuàng)制之際無視法的邏輯性與體系性的遁詞。
作為理性法首要的內(nèi)在要求,規(guī)則的內(nèi)在一致性并不是針對(duì)法律的高標(biāo)準(zhǔn),它其實(shí)是人類社會(huì)的法律制度所應(yīng)普遍具備的一項(xiàng)基本標(biāo)準(zhǔn),是一項(xiàng)底線的要求。"邏輯上的無矛盾性或一致性是邏輯系統(tǒng)的基本要求。"「王洪:《司法判決與法律推理》,北京:時(shí)事出版社,2002年,第88頁美國大法官霍姆斯說,法律的生命在經(jīng)驗(yàn),不在邏輯。這句話對(duì)裁判者或許管用,但對(duì)立法者來說卻完全用不上,對(duì)立法者而言,民法的生命當(dāng)然就在邏輯,其內(nèi)容一定不能前言不對(duì)后語。
二、法典化與民法的開放性
(一)通過制定民法典實(shí)現(xiàn)民法的形式理性
體系化是大陸法系法律形式理性的必然要求。大陸法系國家的經(jīng)驗(yàn)已經(jīng)表明,法典化是實(shí)現(xiàn)私法體系化的一個(gè)完美方法。如前所述,無論是在價(jià)值層面還是在規(guī)范層面,我國民事立法都還存在著諸多不足,而法典化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條最佳的路徑。其原因在于:第一,通過民法法典化可消除價(jià)值之間的沖突。價(jià)值是法律的靈魂,任何法律規(guī)范都要體現(xiàn)和保護(hù)一定的價(jià)值。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由于價(jià)值是主觀的、多元的,因此,民法上存在著彼此構(gòu)成矛盾從而形成沖突的價(jià)值,如私法自治與國家干預(yù)、形式平等與實(shí)質(zhì)平等、靜的安全與動(dòng)的安全、抽象人格與具體人格、形式正義與實(shí)質(zhì)正義等。采納不同的價(jià)值理念將會(huì)直接決定民法典的規(guī)范和制度的不同取向。民法典的編纂能確定整個(gè)市民社會(huì)領(lǐng)域應(yīng)采取的價(jià)值基調(diào),即"確立反映時(shí)代精神的價(jià)值概念,奠定法律體系的共同倫理基礎(chǔ)",并在整個(gè)民法領(lǐng)域?qū)⒃搩r(jià)值貫徹下去,使得圍繞著其核心價(jià)值形成協(xié)調(diào)一致的價(jià)值體系,由此建立民法的內(nèi)在體系,即實(shí)現(xiàn)法律原則的內(nèi)在一致性。在此基礎(chǔ)上,民法典通過兼顧、維護(hù)與上述價(jià)值形成沖突的其他價(jià)值,從而使整個(gè)社會(huì)能夠維持一種和諧共存的狀態(tài)。如在堅(jiān)守私法自治的基礎(chǔ)上,協(xié)調(diào)其與藉國家干預(yù)所欲達(dá)致的實(shí)質(zhì)正義、社會(huì)福利等目標(biāo)。"大自然給予人類的最高任務(wù)就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與不可抗拒的權(quán)力這兩者能夠最大限度地結(jié)合在一起。"再如在堅(jiān)守形式平等、抽象人格等價(jià)值的基礎(chǔ)上,協(xié)調(diào)其與實(shí)質(zhì)平等、具體人格等價(jià)值的關(guān)系,而加強(qiáng)對(duì)消費(fèi)者、承租人、受雇人等弱者的保護(hù)。
第二,通過民法法典化可消除規(guī)則之間的沖突。法典化實(shí)際上就是體系化,體系是民法典的靈魂與生命。"體系為一種意旨上的關(guān)聯(lián)。其在同一時(shí)空上的意義為,基于法律義理化的要求,自然趨向系統(tǒng)化,以排除或防止其間在邏輯上或價(jià)值判斷上的矛盾,此為基于理性尋求正確性的努力。"民法典可通過體系的構(gòu)建消除規(guī)則與規(guī)則之間的沖突、抵觸與矛盾之處,確保民法的確定性與行為結(jié)果的可預(yù)測(cè)性。
第三,通過民法法典化可建立單行法之間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實(shí)現(xiàn)民法整體的統(tǒng)一性。民法典的邏輯自洽表現(xiàn)在,其諸組成部分各得其所,且彼此之間可形成一般規(guī)范與特殊規(guī)范、普通法與特別法的關(guān)系。如買賣合同與合同法總則、合同法與債法、債法與民法總則之間就具有一般規(guī)范與特別規(guī)范的關(guān)系。在中國,由于立法機(jī)關(guān)對(duì)民法典的制定采取的是分階段、分步驟制定這一較為務(wù)實(shí)的方式,《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quán)法》等一系列法律是先后出臺(tái)的,各個(gè)單行法自成系統(tǒng),并無統(tǒng)一的主線貫串,相互間不可能有自洽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自然也無從形成合理的邏輯體系,甚至在價(jià)值、制度等方面還存在著抵牾之處;此外,由于尚未制定民法典,《合同法》、《物權(quán)法》等民事基本法與《公司法》、《保險(xiǎn)法》等商事特別法之間的關(guān)系也一直處于糾纏不清的狀態(tài),只有通過制定民法典進(jìn)行系統(tǒng)整合,才能建立民事法律整體的統(tǒng)一性。在法典化實(shí)現(xiàn)后,就可通過民法典總則來統(tǒng)轄上述民事單行法與商事特別法。民法典"具有清楚建構(gòu)且一致的法律規(guī)則與原則(外在體系),有助于達(dá)成法律內(nèi)在的一致性(內(nèi)在體系),并且對(duì)于將來法學(xué)理論、司法及立法發(fā)展提供概念架構(gòu)的成文法。"
第四,通過民法法典化可盡量減少法律漏洞。法典都具有全面性或完備性的特點(diǎn),即將同一領(lǐng)域同一性質(zhì)的法律規(guī)范,按照某種內(nèi)在的結(jié)構(gòu)和秩序整合在一起,能夠覆蓋社會(huì)生活的基本方面,從而為市民社會(huì)中需要法律調(diào)整的主要社會(huì)關(guān)系提供基本的法律規(guī)則。"法典編纂是一系統(tǒng)性的表述,是以綜合和科學(xué)方法,對(duì)特定國家內(nèi)一個(gè)或若干法律部門諸普遍和永久規(guī)則加以組織的整體"。若規(guī)則殘缺不全,基本素材的缺乏必然阻礙民法體系化的實(shí)現(xiàn)。法典化不同于一般的立法在于法典體現(xiàn)了各種有效控制主體的法律規(guī)則的完整性、邏輯性、科學(xué)性。通過法典化竭盡所能實(shí)現(xiàn)對(duì)民事基本制度的全面規(guī)定,可以有效減少民事領(lǐng)域的法律漏洞。裁判者大體上能在法典中發(fā)現(xiàn)所要的規(guī)范,而無假外求。
第五,通過民法法典化可消除各種法律淵源的沖突和矛盾,促進(jìn)私法規(guī)范的統(tǒng)一。"編纂法典有很多原因,但是最主要的還是人們懷有使法律明確和使全國的法律保持統(tǒng)一的愿望,這些國家曾依政治的標(biāo)準(zhǔn)結(jié)為一體。"18世紀(jì)開始的歐陸民法典運(yùn)動(dòng),正是以民法典取代了原來散見各地的習(xí)慣法、領(lǐng)地法、宗教法等,由此宣示和穩(wěn)定其統(tǒng)一的至上的。
在中國,因缺乏民法典,民法的規(guī)則未臻健全與完善,從而留下了法律調(diào)整的空白,這些空白多是通過國務(wù)院各部委的規(guī)章甚至地方性規(guī)章予以填補(bǔ),而規(guī)章的制定常受到部門和地區(qū)利益的主導(dǎo),難以全面照顧到全社會(huì)的利益;而且這些規(guī)范多是從管理社會(huì)成員而非為社會(huì)成員設(shè)定自由的角度來制定的,與民法在價(jià)值取向上判然有別。民法典的制定可有效地改變此類政出多門,法令不一的現(xiàn)象,實(shí)現(xiàn)市場規(guī)則的一致化與法制的統(tǒng)一化,從而為當(dāng)事人帶來確定的預(yù)期、保障市場經(jīng)濟(jì)的正常運(yùn)行。
(二)保持民法的開放性
制定一部形式理性的民法典是必不可少的,不過,人類法律的發(fā)展史已經(jīng)證明,立法者企圖通過一部法典而預(yù)見一切情況、解決一切問題的愿望是難以實(shí)現(xiàn)的。誠如拉倫茨所言,"沒有一種體系可以演繹式的支配全部問題;體系必須維持其開放性。它只是暫時(shí)概括總結(jié)。"因此,為了使法典能夠不斷適應(yīng)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需要,在保持法典的穩(wěn)定性的同時(shí),又要保持一定的開放性以容納新的社會(huì)情形。"法律必須穩(wěn)定,但又不能靜止不變。因此,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圖使有關(guān)對(duì)穩(wěn)定性的需要和變化的需要方面這種互相沖突的要求協(xié)調(diào)起來。我們探索原理……既要探索穩(wěn)定性原理,又必須探索變化原理。"總之,中國民法要盡可能為未來的發(fā)展預(yù)留空間,藉以保持其長久的生命力。
在協(xié)調(diào)法律的穩(wěn)定性和開放性關(guān)系方面,《物權(quán)法》提供了良好的經(jīng)驗(yàn)。簡言之:第一,它保持了權(quán)利客體范圍的適度開放性。如《物權(quán)法》第2條第2款規(guī)定,"本法所稱物,包括不動(dòng)產(chǎn)和動(dòng)產(chǎn)。法律規(guī)定權(quán)利作為物權(quán)客體的,依照其規(guī)定。"據(jù)此,在法律有特別規(guī)定的情況下,權(quán)利本身也可以成為物權(quán)的客體。第二,它保持了用益物權(quán)客體范圍的開放性。《物權(quán)法》第117條規(guī)定,"用益物權(quán)人對(duì)他人所有的不動(dòng)產(chǎn)或者動(dòng)產(chǎn),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quán)利。"該條承認(rèn)動(dòng)產(chǎn)用益物權(quán),動(dòng)產(chǎn)用益物權(quán)為將來居住權(quán)等人役權(quán)的設(shè)立預(yù)留了空間。第三,它協(xié)調(diào)了擔(dān)保物權(quán)的法定性與開放性。如《物權(quán)法》第180條第1款第7項(xiàng)規(guī)定,"法律、行政法規(guī)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財(cái)產(chǎn)"都可以抵押,將來法院可根據(jù)該條解釋出一些新的擔(dān)保形式。總之,物權(quán)法在體系的構(gòu)建上是開放的,這使得物權(quán)法不僅能夠滿足現(xiàn)實(shí),而且能夠適應(yīng)未來社會(huì)發(fā)展的需要。這一有益的經(jīng)驗(yàn)值得中國今后的民事立法借鑒。我們認(rèn)為,中國民事立法在保持開放性時(shí)應(yīng)當(dāng)注意如下幾個(gè)方面的問題:
第一,保持民法淵源的開放性。法典化具有一種"排他性"的傾向,即認(rèn)為法典為法律的唯一法源,將"法"等同于"成文法".不過,嚴(yán)格意義的排他性永遠(yuǎn)都只是一種無法企及的理想。面對(duì)紛繁蕪雜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有限的民法典條文終究會(huì)捉襟見肘。因此,法國與奧地利民法典雖未賦予成文法外其他規(guī)則的法源性,但習(xí)慣法在這兩部法典制定后即開始扮演重要角色,有時(shí)甚至違反法律明文規(guī)定而適用。德國民法制定時(shí),將法源問題留給學(xué)界解決,并未排除成文法外其他任何法源的適用。在立法上,以《瑞士民法典》第1條為嚆矢,現(xiàn)代各國民法典大都明確承認(rèn)習(xí)慣、判例、學(xué)理的法源性,甚至允許法官在法律無具體規(guī)定時(shí),依其自我判斷作出判決。因此,"法典化的排他性意義,在于建立成文法的優(yōu)越性,至于其他法源,并非全然排除,不予適用。"中國未來民法典也應(yīng)承認(rèn)成文民法外其他規(guī)則的法源性,使其他規(guī)則能像涓涓細(xì)流浸潤民法的根底,從而使得民法典的大樹長久地枝繁葉茂。
第二,處理好法條抽象性與具體性的關(guān)系。民法典只能確立社會(huì)生活中普遍性的基本規(guī)則,而不宜規(guī)定過分具體、瑣碎、細(xì)節(jié)性的內(nèi)容。據(jù)此,民法典應(yīng)保持法條的適度抽象,以適應(yīng)未來社會(huì)發(fā)展之需。保持法條的抽象性不僅是立法技術(shù)問題,更是民法典體系設(shè)計(jì)時(shí)所應(yīng)當(dāng)遵循的一般規(guī)律。其原因在于:其一,民法典為市民社會(huì)的基本法,并非單行法,它確定社會(huì)的基本規(guī)則,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般性和抽象性。其二,民法典作為私法,應(yīng)遵循私法自治的精神,不能過度干預(yù)人們生活。其三,民法典對(duì)社會(huì)生活的調(diào)整應(yīng)保持某種必要的節(jié)制。立法者在立法時(shí),有必要保持某種謙卑的心態(tài),不能認(rèn)為自己具有預(yù)見一切的能力,而要承認(rèn)認(rèn)知力的局限,從而給未來的發(fā)展預(yù)留空間。若一部法典事無巨細(xì)地進(jìn)行規(guī)定,則必然會(huì)在社會(huì)的演進(jìn)中頻繁更改,由此損害其穩(wěn)定性,從而削弱其生命力。特別是當(dāng)社會(huì)處于變動(dòng)不居的轉(zhuǎn)型期時(shí),過于具體更易使法典滯后于社會(huì)。總之,民法典可采取"原則法-特別法"的立法架構(gòu),以民法典規(guī)制常態(tài)的、普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而以目的導(dǎo)向的特別民法調(diào)整異態(tài)的、特殊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只有這樣,才可既維持其自主性于不墜,又可實(shí)現(xiàn)國家干預(yù)的政策目標(biāo),使得其與政治經(jīng)濟(jì)體制的其他部分不僅可和平共存,更是相互包容。
第三,在民法典中架設(shè)必要的管道,實(shí)現(xiàn)私法與公法的接軌與溝通。面對(duì)著現(xiàn)時(shí)代對(duì)社會(huì)公正的追求凸現(xiàn)的局面,民法典可通過設(shè)置"轉(zhuǎn)介條款"或"引致條款"來溝通民法與公法的方式來實(shí)踐對(duì)社會(huì)正義的追求。即在民法中仍堅(jiān)守私法自治的基本價(jià)值,同時(shí)在民法內(nèi)適當(dāng)?shù)牡胤郊茉O(shè)通往其他法律領(lǐng)域的管道,如規(guī)定法律行為不得違反"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所有權(quán)行使不得違反"法律"、不得實(shí)施違反"保護(hù)他人法律"的侵權(quán)行為等。"立法者必須在法典內(nèi)適當(dāng)?shù)牡胤郊茉O(shè)通往其他法律領(lǐng)域的管線,甚至區(qū)隔主線、支線,從而把常態(tài)民事關(guān)系和特別民事關(guān)系,把民事關(guān)系和前置于民事關(guān)系或以民事關(guān)系為前置事實(shí)的公法關(guān)系,連接起來。"這些條款的設(shè)置,增強(qiáng)了民法的伸縮性,使得民法典能在社會(huì)巨大變遷之下巋然不動(dòng),同時(shí)又能沖突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完成實(shí)踐社會(huì)正義的使命。
第四,處理好具體列舉與設(shè)置必要的一般條款的關(guān)系。具體列舉,是將某一類法律現(xiàn)象中的各種具體情況進(jìn)行詳細(xì)規(guī)定,此種立法技術(shù)能夠增強(qiáng)法的安定性,但因其視野的限制以及適用范圍的有限性,使其在實(shí)際的運(yùn)用上可能流于僵化,從而難以適應(yīng)不斷發(fā)展的社會(huì)情況,為此需要采納一般條款來彌補(bǔ)其局限性。一般條款,是未規(guī)定具體的適用條件和固定的法律效果而交由法官根據(jù)具體情勢(shì)予以確定的規(guī)范。由于其內(nèi)涵具有不確定性、較高的抽象性與普遍性,從而能夠滿足民法時(shí)刻跟進(jìn)社會(huì)生活變化的需要。將具體列舉的方式與設(shè)置必要的一般條款的方式結(jié)合起來,通過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等一般條款在一定限度內(nèi)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quán),既有助于實(shí)現(xiàn)個(gè)案正義,也可使民法典適應(yīng)社會(huì)的變遷。
三、結(jié)語
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民法逐步繁榮發(fā)展的30年,也是民法的理念漸次增強(qiáng)的30年。正如孫憲忠所說:改革開放初期深受其影響的蘇聯(lián)民法理論,以階級(jí)斗爭學(xué)說徹底否定了近代以來民法所接受的人文主義革命、工業(yè)革命和啟蒙運(yùn)動(dòng)的核心價(jià)值,即人文主義為核心的思想和價(jià)值體系;其計(jì)劃經(jīng)濟(jì)學(xué)說,徹底否定了近現(xiàn)代民法的基本觀念,如所有權(quán)理論、意思自治理論,也完全否定了民法建立的規(guī)范市場以及交易的制度體系。近30年來中國民法的實(shí)踐,就是一個(gè)價(jià)值重拾與規(guī)范重建的過程。其間,民法的形式性逐步累積,科學(xué)性亦逐步增進(jìn)。雖然中國民法最近30年的發(fā)展之于西方民法幾百年的發(fā)展只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是,觀諸中國僅以30年之功即獲西方社會(huì)百余年發(fā)展之所成,引致中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社會(huì)巨變與進(jìn)步,其成就是無論如何不能小覷的。wWw.gWyoO
確立人的私法主體地位,注重保障人的尊嚴(yán)、意思自治,穩(wěn)步推進(jìn)民法的科學(xué)化、體系化等等,這都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民法的歷程留給我們的豐厚而寶貴的遺產(chǎn)。繼承這些遺產(chǎn),并孜孜努力不懈,則完全可以期待,作為最近30年的民法發(fā)展在未來的標(biāo)志性成果的民法典,不僅將是一部垂范久遠(yuǎn)的民法典,更將會(huì)引領(lǐng)中國社會(huì)邁入一個(gè)"個(gè)人的自治、有尊嚴(yán)的生活"獲得全面實(shí)現(xiàn)的美好社會(huì)。
注釋:
[1]參見馬克斯。韋伯:《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下卷,第199頁以下
[2]參見昂格爾:《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法律》,吳玉章、周漢華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4年,第47頁
[3]蘇永欽:《走入新世紀(jì)的私法自治》,第48頁
[4]陳春山:《契約法講義》,臺(tái)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84頁
[5]參見蘇永欽:《走入新世紀(jì)的私法自治》,第338頁
[6]參見劉楠:《變法模式下的中國民法法典化——價(jià)值的、邏輯的與事實(shí)的考察》,《中外法學(xué)》2001年第1期
第5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關(guān)鍵詞〕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形式理性;民法典
〔中圖分類號(hào)〕D913.4〔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0-4769(2018)01-0106-13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的形式理性是尚待證立的命題。從筆者與同行交流的情況來看,不少人對(duì)此命題抱有如下疑問:其一,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領(lǐng)域是否存在形式理性的問題?其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的形式理性究竟為何含義?它較之法的形式理性的一般命題有何特殊規(guī)定性?其三,討論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的形式理性有無意義?這一課題對(duì)于我國法律實(shí)踐有無價(jià)值?本文將圍繞上述問題展開討論。
一、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形式理性命題的確立
形式理性是現(xiàn)代法共通的特征。以此推論,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欲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則須具備形式理性的品質(zhì)。韋伯的相關(guān)論證,雖不限于私法,但其討論常以歐陸民法為范例展開。依學(xué)界通說,“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是私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屬于民法的范疇”。〔1〕以此觀之,民法的形式理性亦應(yīng)體現(xiàn)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領(lǐng)域。上述由一般及于特殊的推論自有其道理,但我們的討論不能停留于此。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有其特殊性,對(duì)形式理性命題持懷疑態(tài)度者也多強(qiáng)調(diào)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與一般民法之區(qū)別。欲去除此類疑慮,則須梳理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與民法典、形式理性與實(shí)質(zhì)理性兩對(duì)范疇之間纏雜不清的關(guān)系。
形式理性并非法典法獨(dú)有的性格。雖然韋伯常以法德等歐陸國家的民法典為形式理性法的注腳,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法典法才具備形式理性,或者只有采用民法典的立法形態(tài)才能體現(xiàn)民法的形式理性。我們應(yīng)區(qū)分形式理性法與法的形式理性兩個(gè)不同范疇。形式理性法為虛構(gòu)的“理念型”,它剔除了一切實(shí)質(zhì)性考慮的“贅肉”,是完全以形式合理性標(biāo)準(zhǔn)取舍結(jié)構(gòu)的無血無肉的骨架。此種“理念型”純?yōu)橛^念上之構(gòu)造,沒有任何實(shí)定法能夠完全滿足形式理性法的要求,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也只是與其較為接近而已。法的形式理性則不然。歷史上出現(xiàn)過的法律包含理性的因素,也包含非理性的因素;有形式理性的面向,也有實(shí)質(zhì)理性的面向。法律人——立法者、司法者或者法律學(xué)者——總是會(huì)傾向于以一種更有概括力、更為體系化和更能體現(xiàn)邏輯自洽性的方式來組織法律材料和展開法律思維。形式理性可謂一切法律的內(nèi)在訴求。
對(duì)于業(yè)已存在的各種法律形態(tài),無論是單行法還是法典法,也無論是制定法還是判例法,或多或少都體現(xiàn)出某些形式理性的品格,只不過韋伯認(rèn)為法典為法律邏輯形式理性的最高形式。對(duì)于歷史上曾經(jīng)歷的不同法律階段,無論是羅馬法還是教會(huì)法,也無論是盎格魯-撒克遜法還是近代歐陸法律,或多或少都體現(xiàn)出某些“形式主義”的特征,只不過近代歐陸法律將此種形式合理性的追求演繹到了極致。因此,那種將形式理性與法典法劃等號(hào)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在民法典之外的民事單行法中同樣存在形式合理性的訴求,并且也包含形式合理性的因素。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是否納入民法典,與其是否具備形式理性,為兩個(gè)不同的命題。民法典要不要規(guī)定以及如何規(guī)定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系我國民法典制定體系之爭中的焦點(diǎn)問題。就此已積累了不少研究文獻(xiàn),學(xué)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和建議。按照張玉敏教授的概括,處理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與民法典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存在三種可能的方案:其一是鏈接式,即在民法典總則中以概括性規(guī)定確認(rè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為民事權(quán)利之一種,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規(guī)范則作為民事特別法存在于民法典之外,或保留專利、商標(biāo)、著作權(quán)等單行法形式,或編纂統(tǒng)一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典,或制定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基本法。其二是納入式,在民法典分則中與物權(quán)、債權(quán)等相對(duì)應(yīng)設(shè)專編對(du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加以規(guī)定,專利法、商標(biāo)法、著作權(quán)法等主要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中的實(shí)體權(quán)利義務(wù)規(guī)范全部整合至民法典中。其三是雙重立法模式,“即主張?jiān)诿穹ǖ渲幸?guī)定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共同規(guī)則,同時(shí)保留民法典外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特別法”。〔2〕
上述編纂體例之爭事關(guān)重大,以筆者淺薄學(xué)識(shí)不敢妄加評(píng)論。但依愚見,如果說有什么動(dòng)因推動(dòng)學(xué)者不斷思考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納入民法典的問題,其實(shí)就是一種內(nèi)在的對(duì)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追求和沖動(dòng)。“民法典供使用者便于檢索的信息統(tǒng)合功能,基本上已經(jīng)不大,因?yàn)闅v史經(jīng)驗(yàn)告訴我們完整法典只是神話,而現(xiàn)代越來越普及的各種電子數(shù)據(jù)庫也已經(jīng)可以充分滿足快速檢索的需求”。〔3〕以當(dāng)代信息技術(shù)條件,傳統(tǒng)紙質(zhì)傳播媒介中將法律融匯一爐以便利查詢的需求已經(jīng)淡化。即便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分散于各種單行法,“找法”也未見太多困難。此種情況下我們?nèi)宰巫我郧筇接懼R(shí)產(chǎn)權(quán)進(jìn)入民法典的可能性,主要系基于民法典體系完整性的考慮:“民法典雖然不能也不必囊括一切民事法律規(guī)范,但潘德克吞體系的基本思維模式卻要求民法典對(duì)基本的民事權(quán)利做出無遺漏的規(guī)定。既然肯認(rè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為基本的民事權(quán)利類型,將其納入民法典,并獨(dú)立成編就是必然的結(jié)論。誠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民法典的結(jié)構(gòu)和編排,只能以邏輯性、體系性為標(biāo)準(zhǔn)’。那么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在民法典中取得獨(dú)立成編的地位正是合乎邏輯和民法發(fā)展方向的安排。”〔4〕
對(du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與民法典之間關(guān)系的理解可謂見仁見智,但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法典化并非討論其形式理性的前提。即便民法典中不規(guī)定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仍然包含形式理性化的訴求。除了上世紀(jì)個(gè)別國家有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典化的嘗試,過去的數(shù)百年間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一直以民法典之外的單行法形態(tài)出現(xiàn)。這并未消解專利、商標(biāo)、著作權(quán)等法律不斷提升其形式理性程度的努力。雖然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有區(qū)別于一般民法的特殊性,但其發(fā)展歷史同樣印證了韋伯所揭示的規(guī)律:“以形式合理性的不斷增長為特征的法律理性化過程”。〔5〕依照謝爾曼和本特利的研究,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出現(xiàn)于19世紀(jì)50年代左右的英國。即便在這個(gè)被韋伯認(rèn)為“私法的理性化仍然十分落后”的國家〔6〕,專利和版權(quán)等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也正是憑借一種“形式主義”的技術(shù)和方法大幅提升其理性化程度,實(shí)現(xiàn)從前現(xiàn)代法向現(xiàn)代法的轉(zhuǎn)換。
以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的發(fā)展歷史觀之,法律的關(guān)注點(diǎn)從哲學(xué)基礎(chǔ)向形式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這一過程被本特利稱為“閉合化”——也是“不得不然”的選擇。從18世紀(jì)下半葉“關(guān)于文學(xué)財(cái)產(chǎn)的爭論”開始直至今日關(guān)于“文學(xué)財(cái)產(chǎn)的爭論”,參見〔澳〕布拉德·謝爾曼、〔英〕萊昂內(nèi)爾·本特利《現(xiàn)代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的演進(jìn):1760-1911英國的歷程》,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11頁以下。,對(duì)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對(duì)象本質(zhì)的探討從未停歇。盡管無數(shù)的聰明才智之士殫精竭慮,就此問題貢獻(xiàn)遠(yuǎn)見卓識(shí),但歧見紛呈的現(xiàn)象并未改變,沒有什么學(xué)說能成為一錘定音、令人信服的共識(shí)。以至于兩個(gè)世紀(jì)前辯論的問題、提出的見解,在今時(shí)今日又經(jīng)改頭換面,被重新提起。例如,“巴洛關(guān)于數(shù)字化財(cái)產(chǎn)而提出的問題,其中許多就與18世紀(jì)針對(duì)文學(xué)財(cái)產(chǎn)提出的問題是相似的”。參見〔澳〕布拉德·謝爾曼、〔英〕萊昂內(nèi)爾·本特利《現(xiàn)代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的演進(jìn):1760-1911英國的歷程》,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6頁。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甚至因此被稱為“玄學(xué)”。〔7〕如果我們將法律建筑于此種形而上學(xué)的基礎(chǔ)之上,等待關(guān)于無形財(cái)產(chǎn)本質(zhì)的哲學(xué)認(rèn)識(shí)獲得澄清后再及于具體規(guī)范,那么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可能至今還止步不前,處于原始蒙昧的狀態(tài)。專利、版權(quán)等法律能達(dá)成從前現(xiàn)代法到現(xiàn)代法的躍進(jìn),恰恰是因?yàn)槠潢P(guān)注點(diǎn)從權(quán)利的哲學(xué)基礎(chǔ)轉(zhuǎn)移至權(quán)利的取得程序、記載方法以及法律的組織方式等形式問題,通過法技術(shù)巧妙回避了“法律在授予無體物以財(cái)產(chǎn)地位時(shí)所面臨的根本性、并且在許多方面看來難以克服的問題”。〔8〕具言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能完成此種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端賴其下述方面的形式理性化:
其一,表述性登記制度的建立。所謂表述性登記(representativeregistration),是指用圖示或文字方式表現(xiàn)保護(hù)對(duì)象,而不是提交實(shí)物或模型,據(jù)此在官方機(jī)構(gòu)登記以明確其要求保護(hù)的權(quán)利范圍。當(dāng)代的專利和商標(biāo)申請(qǐng)程序采用的都是表述性登記方式。歷史上首先引入此種制度則可追溯至1839年6月14日英國通過的《外觀設(shè)計(jì)登記法》。法律給予任何制造品的外形和結(jié)構(gòu)以12個(gè)月至3年不等期限的保護(hù),條件是申請(qǐng)人必須向登記機(jī)關(guān)交存其外觀設(shè)計(jì)的三個(gè)復(fù)制件或者三幅圖片。〔9〕
較之既往做法,表述性登記的特點(diǎn)在于:(1)以文字表述或圖片替代了實(shí)物;(2)由行會(huì)登記轉(zhuǎn)為公共資金支持的政府集中登記;(3)登記成為取得權(quán)利的條件。這不僅帶來了便利信息存儲(chǔ)和傳輸?shù)膬?yōu)點(diǎn);更重要的是,它讓申請(qǐng)人自己陳述“權(quán)利要求保護(hù)的是什么”,并以此確定其保護(hù)范圍。奇妙之處在于,法律竟以此種程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知識(shí)財(cái)產(chǎn)的本質(zhì)和邊界這一難題。“根據(jù)19世紀(j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而形成的由公共資金支持的集中登記制度,變成了一個(gè)重要場所,許多由無體財(cái)產(chǎn)所產(chǎn)生的問題在那里得到了排遣。特別是,就登記制度要求申請(qǐng)人交存其創(chuàng)作物的表述而非該創(chuàng)作物本身(這是以往的通常情形)而言,確認(rèn)財(cái)產(chǎn)所有人以及財(cái)產(chǎn)邊界的任務(wù)就以官僚方式(bureaucratically)獲得了解決。重要的是,這些變化雖然強(qiáng)化了財(cái)產(chǎn)的封閉性,抑制了法律的創(chuàng)造性,但它們讓法律避免了確認(rèn)被保護(hù)財(cái)產(chǎn)的本質(zhì)這個(gè)艱難的任務(wù)”。〔10〕
其二,立法從具體到抽象。1839年之前的相關(guān)法律是按照瑣細(xì)的行業(yè)領(lǐng)域劃分,以一種條件反射式的方式直接映射需要調(diào)整的生活事實(shí)和具體問題,如1735年的《雕工法》、1787年的《白棉布印花工法》,甚至有為綢緞式樣或花邊式樣專門提出的法案。當(dāng)這種立法累積到一定數(shù)量,自然會(huì)產(chǎn)生合并、整理、歸納的理性化訴求。亞麻布、棉布或者平紋細(xì)布式樣上的權(quán)利為何不能擴(kuò)展至羊毛制品、絲織品、地毯甚至金屬制品?難道我們準(zhǔn)備為每一種制品的式樣都各自制定一部法律?1839年的《外觀設(shè)計(jì)著作權(quán)法》和《外觀設(shè)計(jì)登記法》的出現(xiàn)正是基于下述推論:適用于任何制造品的新式樣均應(yīng)予以保護(hù)。立法方式在此發(fā)生質(zhì)的變化:以更加體系化和規(guī)則化的法律制度來“替代那些形成普通法的粗俗、不適宜和虛偽的雜陳混合和制定法的混雜的經(jīng)驗(yàn)主義”。“前現(xiàn)代法對(duì)諸如白棉布、平紋細(xì)布和亞麻布外觀設(shè)計(jì)的印染這樣的東西給予保護(hù),所以它的保護(hù)是按對(duì)象而具體化的(subjectspecific),是回應(yīng)性的(reactive)。亦即,它趨向于對(duì)當(dāng)時(shí)向法律所提出的特定問題做出回應(yīng)。相反地,現(xiàn)代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傾向于更為抽象(abstract)和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特別是,前現(xiàn)代法的形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是對(duì)法律的運(yùn)行環(huán)境作出被動(dòng)回應(yīng)而確定的,而在現(xiàn)代法的立法起草過程中,則不僅考慮到其所調(diào)整的對(duì)象,而且也關(guān)注在實(shí)現(xiàn)這些任務(wù)時(shí)自身所采取的形態(tài)”。〔11〕
其三,法律范疇趨于明晰。直至19世紀(jì)前期,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還充斥著各種混亂的概念。專利、商標(biāo)和著作權(quán)這些基本的范疇并未得到清晰的劃分,各種權(quán)利的邊界具有不確定性和開放性。下述今天聽來令人費(fèi)解的說法在當(dāng)時(shí)卻常常出現(xiàn)于法律專業(yè)人士之口“發(fā)明上的著作權(quán)”“藝術(shù)品的專利”“商標(biāo)的著作權(quán)”“著作權(quán)或者式樣的專利”。就立法而言,遲至1835年,英國也沒有出現(xiàn)所謂“版權(quán)法”“專利法”或者“商標(biāo)法”。以專利為例,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專利法的內(nèi)容,大多包含于名為《技術(shù)和制造品法》和《形式法》(LawofForm)的兩部法律之中。專利權(quán)甚至被理解為一種復(fù)制權(quán)(copy-right)。〔12〕這說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的組織結(jié)構(gòu)和表達(dá)方式當(dāng)時(shí)尚未定型,各種概念和規(guī)范不能以一種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的思想為紐帶結(jié)為體系。
“法律教科書的發(fā)展、進(jìn)行立法改革的意圖以及不斷增強(qiáng)的對(duì)一種更理性和更有組織的法律制度的期望”等因素促成了法律范疇固定化的努力。至19世紀(jì)50年代,專利、版權(quán)和外觀設(shè)計(jì)三個(gè)法律領(lǐng)域逐漸分流,并且“被看作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這個(gè)更為一般性標(biāo)題之下的組成要素”。〔13〕商標(biāo)法則在19世紀(jì)下半葉被承認(rèn)為獨(dú)立的法律部門。其調(diào)整范圍原來交叉、重疊、雜混的部分逐漸得到梳理和澄清。不僅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的范疇逐漸固定化,而且這些范疇的組織方法也發(fā)生變化。前現(xiàn)代的法律將理解無體財(cái)產(chǎn)的核心放在“智力勞動(dòng)”和“創(chuàng)造性”概念之上,因此總是糾結(jié)于保護(hù)對(duì)象的本質(zhì)這樣的哲學(xué)思辨,而現(xiàn)代法經(jīng)歷了“從創(chuàng)造到對(duì)象”的轉(zhuǎn)換〔14〕,轉(zhuǎn)而關(guān)心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的對(duì)象本身,考慮表述此種對(duì)象的語匯和邏輯,以及不同對(duì)象之間的區(qū)際和聯(lián)系。到19世紀(jì)80年代,工業(yè)產(chǎn)權(quán)/文學(xué)產(chǎn)權(quán)的二分法漸被接受,并成為統(tǒng)領(lǐng)和支撐上述各種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的架構(gòu)。英國在主要領(lǐng)域進(jìn)行的法典化努力形成了下述立法成果:1852年的《專利法修訂法》、1883年的《專利、外觀設(shè)計(jì)和商標(biāo)法》、1862年的《商品標(biāo)記法》和1911年的《版權(quán)法》。
民法上親屬和繼承的一般規(guī)則未必適用于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鄭成思教授曾特別強(qiáng)調(diào)離婚財(cái)產(chǎn)分割和遺產(chǎn)繼承涉及版權(quán)時(shí)不能直接適用婚姻法和繼承法的一般規(guī)定。“更多的國家沒有簡單地援引其他單行法或民法一般原則來處理版權(quán)繼承問題,而是在版權(quán)法中對(duì)版權(quán)繼承作出專門的、具體的規(guī)定。有些國家甚至在版權(quán)法別指出民法關(guān)于繼承的某些一般性原則,不能適用于版權(quán)繼承。”他甚至認(rèn)為,處理離婚案件時(shí)不能視版權(quán)為夫妻共同財(cái)產(chǎn)。〔53〕因此,立法宜于婚姻法、繼承法中對(duì)涉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繼承或夫妻財(cái)產(chǎn)分割做出特別規(guī)定。
(三)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單行法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合理化
即便不考慮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與民法的關(guān)系,也不考慮各種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專利法、商標(biāo)法、著作權(quán)法等單行法也各自存在體系化的任務(wù)。就我國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單行法而言,由于立法技術(shù)不成熟和法律的起草大多由行政部門牽頭組織等原因,制定法律時(shí)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其實(shí)質(zhì)合理性方面的問題,對(duì)于法律的結(jié)構(gòu)、用語等法技術(shù)層面的問題研究不充分;注重對(duì)于外國法律和國際公約個(gè)別條款的借鑒,卻忽視不同條文之間的層次和邏輯。《著作權(quán)法》等現(xiàn)行法律給人的印象是“想到哪寫到哪”,立法者對(duì)于概念、規(guī)范、章節(jié)之間的關(guān)系似乎并沒有清晰的認(rèn)識(shí),也不能呈現(xiàn)出組織法律材料的思路和脈絡(luò)。不同條款之間雖不至于彼此矛盾,但多重疊和疏漏。這種粗糙的法律表達(dá)方式與德國等先進(jìn)國家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律形成鮮明對(duì)比,與形式理性法的要求相距甚遠(yuǎn)。其結(jié)果不僅不利于法學(xué)教育的開展,也給法律適用帶來困難。這方面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
例如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第十條列舉12項(xiàng)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包括復(fù)制權(quán)、發(fā)行權(quán)、出租權(quán)、展覽權(quán)、表演權(quán)、放映權(quán)、廣播權(quán)、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攝制權(quán)、改編權(quán)、翻譯權(quán)和匯編權(quán)等。法律的創(chuàng)制者就其所能想到的作品的各種具體使用方式,一一對(duì)應(yīng),分別設(shè)定不同的權(quán)利。這是理性化程度較低的“條件反射式的立法方式”。過于具象化的思維不具備形式理性法的抽象性品質(zhì)。過度細(xì)分、簡單對(duì)應(yīng)的權(quán)項(xiàng)設(shè)置造成的結(jié)果是,一方面語言張力不足,其語意不能涵攝某些新的作品利用方式,逼迫司法者不得求助于兜底條款或做擴(kuò)張解釋;另一方面各權(quán)項(xiàng)之間疊屋架梁、界限不清、關(guān)系不明,必有重復(fù)之處。更重要的是,十余項(xiàng)權(quán)利近乎隨機(jī)排列,不顯邏輯關(guān)聯(lián),對(duì)閱讀者來說如同一團(tuán)亂麻,難以掌握。教授法律者只有做歸納整理、分門別類的工作,尋找不同權(quán)項(xiàng)之間的聯(lián)系,提煉更具概括力的上位概念,揭示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體系結(jié)構(gòu),才能滿足受眾的理性思維需求,也才能為司法者準(zhǔn)確理解法律提供幫助。
第6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內(nèi)容提要: 請(qǐng)求權(quán)是請(qǐng)求他人作為或不作為的權(quán)利。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屬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我國法上侵權(quán)責(zé)任的概念,涵蓋了大陸法系中的侵權(quán)責(zé)任和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兩個(gè)概念。在絕對(duì)權(quán)受到侵害的不同時(shí)期或不同狀態(tài)都應(yīng)有相應(yīng)的、有效的救濟(jì)措施,對(duì)其集中規(guī)定更有利于絕對(duì)權(quán)的保護(hù)。絕對(duì)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應(yīng)適用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
侵權(quán)責(zé)任的承擔(dān)是對(duì)民事權(quán)利受到侵害的救濟(jì),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違約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侵權(quán)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都具有救濟(jì)民事權(quán)利的功能,那么,侵權(quán)責(zé)任與這些請(qǐng)求權(quán)是什么關(guān)系?民法應(yīng)該如何規(guī)定民事權(quán)利的救濟(jì)?關(guān)于違約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應(yīng)該屬于合同法中違約責(zé)任的內(nèi)容、侵權(quán)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由侵權(quán)責(zé)任法來規(guī)定已無爭議,那么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則等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是否要單獨(dú)分別加以規(guī)定呢?下文先來考察一下各國關(guān)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和侵權(quán)責(zé)任的立法模式。
一、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立法模式
(一)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立法
在立法上,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由《德國民法典》創(chuàng)設(shè)。《德國民法典》關(guān)于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規(guī)定非常詳盡和細(xì)致,其核心是關(guān)于所有權(quán)保護(hù)的規(guī)定。wWw..cOM該法典的物權(quán)法編第三章所有權(quán)專設(shè)第四節(jié)基于所有權(quán)而發(fā)生的請(qǐng)求權(quán),基本條款是第985條和第1004條;他物權(quán)則準(zhǔn)用關(guān)于所有權(quán)保護(hù)的規(guī)定;占有人也得基于占有提起各種請(qǐng)求權(quán)。在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立法上,《德國民法典》規(guī)定最為全面,所有權(quán)、他物權(quán)和占有都適用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有三種表現(xiàn)形式,即物權(quán)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妨害排除請(qǐng)求權(quán)和妨害防止請(qǐng)求權(quán)。
在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立法上,《德國民法典》規(guī)定最為全面,所有權(quán)、他物權(quán)和占有都適用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有三種表現(xiàn)形式,即物權(quán)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妨害排除請(qǐng)求權(quán)和妨害防止請(qǐng)求權(quán)。
《日本民法典》對(duì)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沒有作一般規(guī)定,只是對(duì)占有之訴作了規(guī)定,如第198條、第199條、第200條;在他物權(quán)中,對(duì)動(dòng)產(chǎn)質(zhì)權(quán)規(guī)定了準(zhǔn)用占有之訴的規(guī)定。但日本判例上承認(rèn)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認(rèn)為基于所有權(quán)的效力得請(qǐng)求排除侵害或防止其危險(xiǎn),而且理論上都一致承認(rèn)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1]
(二)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立法
近代以來的民法典并沒有“人格權(quán)”的規(guī)定,所有的人格精神利益或者倫理價(jià)值都是在“人之保護(hù)”模式下實(shí)現(xiàn)的,而不是“權(quán)利保護(hù)”模式。[2]因此, 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在“人法”中規(guī)定了 自然 人,同時(shí)又規(guī)定了人的住所等,但并沒有確定為人格權(quán),目的僅僅在于確定自然人的身份。對(duì)于人法中的人格精神利益或者倫理價(jià)值等內(nèi)在于人的價(jià)值,以及財(cái)產(chǎn)和所有權(quán),統(tǒng)一適用《法國民法典》第1382條、第1383條的侵權(quán)法一般條款加以保護(hù),將“權(quán)利保護(hù)”與“人的本體保護(hù)”統(tǒng)一于一般條款。其實(shí),《法國民法典》的立法者當(dāng)時(shí)根本就不知道所謂人格權(quán)理論,當(dāng)時(shí)的立憲委員會(huì)從未想過要就人格權(quán)提出什么宣言。《法國民法典》只是將個(gè)人承認(rèn)為抽象 法律 人格并只保護(hù)到不同人之間實(shí)行自由平等這個(gè)層次,而沒有涉及更深的個(gè)人人格的層次。[3]《法國民法典》沒有確認(rèn)人格權(quán),當(dāng)然也就不可能有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規(guī)定了。直到20世紀(jì)初,法國才借助德國的學(xué)說對(duì)人格權(quán)有了基本的共識(shí),并進(jìn)一步區(qū)分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和侵權(quán)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后來,《法國民法典》修正委員會(huì)吸收了這一研究成果,在民法典草案的第165條規(guī)定:“對(duì)人格權(quán)施加的不法侵害,被害人有中止侵害請(qǐng)求權(quán)。這并不妨礙加害者應(yīng)承擔(dān)損害賠償責(zé)任。”類似的條文在1970年和1994年分別被通過,正式成為《法國民法典》的組成部分。[4]
《德國民法典》除了將姓名權(quán)(第12條)規(guī)定為權(quán)利外,對(duì)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未規(guī)定為權(quán)利,只是說它們受到侵犯時(shí)受法律保護(hù)。在“侵權(quán)行為”一節(jié)中,對(duì)于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時(shí)負(fù)損害賠償義務(wù)(第823條第1款)。姓名權(quán)的規(guī)定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其為主體制度服務(wù),只有姓名才能固定主體身份,如同住所一樣;另一方面,姓名是外在于人的,不存在人的內(nèi)在倫理價(jià)值的困境。但生命、身體、健康、自由等就可同日而語了。德國學(xué)者霍爾斯特·埃曼在論及《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之所以沒有規(guī)定人格權(quán)的一般條款的原因時(shí),將其歸結(jié)為三個(gè)方面:其一,不可能承認(rèn)一項(xiàng)“對(duì)自身的原始權(quán)利”,否則就會(huì)得出存在一項(xiàng)“自殺權(quán)”的結(jié)論。薩維尼認(rèn)為,自然人對(duì)于他自身的合法權(quán)力是毋庸置疑的,這種權(quán)力是一切真正權(quán)利(如所有權(quán)與債權(quán))的基礎(chǔ)和前提。但是,這一“自然權(quán)力”不需要實(shí)定法予以承認(rèn),它受到旨在保護(hù)名譽(yù)免受侵害、免受欺騙及暴力等損害的刑法以及尤其是的民法規(guī)范的保護(hù)。薩維尼早就認(rèn)識(shí)到,只能通過具體的保護(hù)性條款而不能通過某項(xiàng)絕對(duì)的權(quán)利,來保護(hù)人格的“原始權(quán)利”。其二,債的產(chǎn)生以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受到侵害為前提,而人格中沒有財(cái)產(chǎn)利益;其三,人格權(quán)的內(nèi)容與范圍無法予以充分的、明確的規(guī)定。[5]與《法國民法典》未規(guī)定人格權(quán)的自發(fā)性不同,《德國民法典》的規(guī)定具有自覺性。
《德國民法典》沒有規(guī)定人格權(quán),但有姓名權(quán);沒有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但有姓名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其第12條(姓名權(quán))規(guī)定:“權(quán)利人的姓名使用權(quán)為他人所爭執(zhí)或權(quán)利人的利益因他人不經(jīng)授權(quán)使用同一姓名而受到侵害的,權(quán)利人可以請(qǐng)求該他人除去侵害。有繼續(xù)受侵害之虞的,權(quán)利人可以提起停止侵權(quán)之訴。”該規(guī)定與《德國民法典》第1004條第1款的表述幾乎完全相同,學(xué)者稱之為姓名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
《日本民法典》沒有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但是,日本通過判例確認(rèn)了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北方雜志案”是日本最高法院就存在名譽(yù)侵害之嫌的表達(dá)行為可否事先停止侵害而表明立場的第一個(gè)判例。日本最高法院1986年6月11日的判決認(rèn)為,名譽(yù)遭受違法侵害者,除可要求損害賠償及恢復(fù)名譽(yù)外,對(duì)于作為人格權(quán)的名譽(yù)權(quán),出于排除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的侵害行為或預(yù)防將來會(huì)發(fā)生的侵害的目的,應(yīng)解釋為還可以要求加害者停止侵害。日本的學(xué)說總體上傾向于支持該判例,承認(rèn)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獨(dú)立性。[6]
《瑞士民法典》是立法史上第一次規(guī)定一般人格權(quán)和專章規(guī)定人格權(quán)的民法典,也是該法典第一次完整地確立了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7]幾經(jīng)修改,不僅將原來的第28條作了修改使之完善,而且增加了第28條a至第28條l共11個(gè)條文進(jìn)行完善,建立了全面的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包括禁止即將面臨的妨害、請(qǐng)求除去已經(jīng)發(fā)生的妨害和請(qǐng)求消除影響,同時(shí)確立了侵害人格權(quán)的損害賠償制度。第29條和第30條是關(guān)于姓名權(quán)的規(guī)定。
近年來制定的民法典都傾向于規(guī)定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如《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第152條規(guī)定:“公民有權(quán)通過法院要求對(duì)損害其名譽(yù)、尊嚴(yán)或商業(yè)信譽(yù)的信息進(jìn)行辟謠、除非傳播這種信息的人能證明它們屬實(shí)。”《越南民法典》更是全面地規(guī)定了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該法第27條規(guī)定:“當(dāng)公民的人身權(quán)受到侵犯時(shí),該公民有權(quán): 1.要求侵權(quán)行為人或請(qǐng)求人民法院強(qiáng)制侵權(quán)行為人終止侵權(quán)行為、公開賠禮道歉、改正; 2.自行在大眾通訊媒介上更改; 3.要求侵權(quán)行為人或請(qǐng)求人民法院強(qiáng)制侵權(quán)行為人賠償物質(zhì)、精神損失。”《阿爾及利亞民法典》也全面規(guī)定了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該法第47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基于人格享有的固有權(quán)利遭受不法侵害時(shí),得請(qǐng)求停止侵害和損害賠償。”這個(gè)條文雖然簡單,但其內(nèi)容非常全面,是迄今為止規(guī)定的最為完整的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
綜上,各國民法關(guān)于人格權(quán)及人格權(quán)保護(hù)的規(guī)定經(jīng)歷了從無到有,從片面到全面的 發(fā)展 過程。對(duì)于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一般是將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害人格權(quán)的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同時(shí)作出規(guī)定。
(三)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立法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包括專利權(quán)、商標(biāo)權(quán)、著作權(quán)等被法律賦予獨(dú)立民事權(quán)利的地位,與物權(quán)、人格權(quán)一樣,同屬于絕對(duì)權(quán)的范疇,任何民事主體都負(fù)有不得侵犯的法律義務(wù)。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同樣為各國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所確認(rèn)。[8]因?yàn)橹R(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已在相關(guān)法律中作了明確規(guī)定,并且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獨(dú)立于民事基本法,故本文暫不探討。
二、侵權(quán)責(zé)任的立法模式
自羅馬法以來,在大陸法系,侵權(quán)行為始終是作為債的發(fā)生根據(jù),與損害賠償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可以說,侵權(quán)責(zé)任就是損害賠償責(zé)任。《法國民法典》第四編第二章侵權(quán)行為與準(zhǔn)侵權(quán)行為第1382條至1386條共五個(gè)條文都是規(guī)定各種侵權(quán)行為的責(zé)任,但都是負(fù)損害賠償責(zé)。《德國民法典》第二編第八章第27節(jié)第823條至第853條的規(guī)定也是以損害賠償為中心的。《日本民法典》、我國 臺(tái)灣 地區(qū)民法以及近年來制定的各國民法典,無不認(rèn)為侵權(quán)責(zé)任就是損害賠償責(zé)任。
根據(jù)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3款的規(guī)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cuò)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cái)產(chǎn),侵害他人財(cái)產(chǎn)、人身的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沒有過錯(cuò),但法律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的,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第134條規(guī)定了十種民事責(zé)任的承擔(dān)方式,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除(六)修理、重作、更換和(八)支付違約金外,都是侵權(quán)責(zé)任的承擔(dān)方式。即侵權(quán)責(zé)任除了損害賠償外,還可以適用返還財(cái)產(chǎn)、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xiǎn)、恢復(fù)原狀、消除影響、恢復(fù)名譽(yù)、賠禮道歉。可見,與大陸法系國家將侵權(quán)責(zé)任僅視為損害賠償責(zé)任不同,我國法上的侵權(quán)責(zé)任以損害賠償為主,以其他民事責(zé)任方式為輔。如上文所述,這些其它民事責(zé)任方式大多是大陸法系其它國家法律中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或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等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也就是說我國侵權(quán)責(zé)任的概念,涵蓋了大陸法系中的侵權(quán)責(zé)任和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兩個(gè)概念。
我國于2007年制定了《物權(quán)法》,該法第34條至第37條規(guī)定了物權(quán)的保護(hù)方法是請(qǐng)求返還原物、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險(xiǎn)、恢復(fù)原狀或損害賠償,其中請(qǐng)求返還原物、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險(xiǎn)是大陸法系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需特別說明的是,消除危險(xiǎn)相當(dāng)于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中的防止妨害請(qǐng)求權(quán),這從《物權(quán)法》第35條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妨害物權(quán)或者可能妨害物權(quán)的,權(quán)利人可以請(qǐng)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險(xiǎn)。”其中“可能妨害物權(quán)”也就是說有妨害物權(quán)的危險(xiǎn),相當(dāng)于大陸法系中“有妨害其所有權(quán)之虞者”;“消除這種危險(xiǎn)”相當(dāng)于大陸法系中的“得請(qǐng)求防止之”。這與大陸法中關(guān)于排除妨害請(qǐng)求權(quán)和防止妨害請(qǐng)求權(quán)的規(guī)定是一致的。只是我國《物權(quán)法》對(duì)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規(guī)定更為簡潔、全面,將所有權(quán)、他物權(quán)、占有的請(qǐng)求權(quán)統(tǒng)一規(guī)定,一體保護(hù)。除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外,《物權(quán)法》還規(guī)定了在大陸法系傳統(tǒng)民法中屬于侵權(quán)責(zé)任范圍的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這種模式對(duì)于民事主體物權(quán)的保護(hù)是有利的,應(yīng)該值得肯定。
但因?yàn)椤肚謾?quán)責(zé)任法》的制定,關(guān)于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規(guī)定與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或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規(guī)定的協(xié)調(diào)問題更加突顯。在《侵權(quán)責(zé)任法》制定的過程中,《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15條將《民法通則》第134條關(guān)于民事責(zé)任的承擔(dān)方式(除(六)修理、重作、更換和(八)支付違約金外)原文錄入,作為侵權(quán)責(zé)任的承擔(dān)方式,引發(fā)了學(xué)界積蓄已久的不滿[9]和擔(dān)憂。一是認(rèn)為侵權(quán)責(zé)任法應(yīng)該像大陸法系的侵權(quán)責(zé)任制度一樣,只規(guī)定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而不應(yīng)該規(guī)定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或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二是認(rèn)為如果將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置于侵權(quán)責(zé)任法中,將會(huì)導(dǎo)致侵權(quán)責(zé)任適用情形下的困境。[10]三是認(rèn)為如果侵權(quán)責(zé)任法將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或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作為侵權(quán)責(zé)任承擔(dān)的方式,將會(huì)產(chǎn)生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或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請(qǐng)求權(quán)的競合從而導(dǎo)致法律適用上的困惑。[11]下文主要對(duì)我國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立法模式形成的原因進(jìn)行分析。
三、我國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立法模式形成的原因
(一)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的內(nèi)容
如前文所述,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包括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包括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妨害除去請(qǐng)求權(quán)和妨害防止請(qǐng)求權(quán);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包括妨害除去請(qǐng)求權(quán)和妨害防止請(qǐng)求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包括妨害除去請(qǐng)求權(quán)和妨害防止請(qǐng)求權(quán)。總的來看,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包括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妨害除去請(qǐng)求權(quán)和妨害防止請(qǐng)求權(quán)。這些內(nèi)容與侵權(quán)責(zé)任的承擔(dān)方式(侵權(quán)責(zé)任的內(nèi)容)有什么區(qū)別呢?
《民法通則》和《侵權(quán)責(zé)任法》中關(guān)于侵權(quán)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是八種,[12]即賠償損失、返還財(cái)產(chǎn)、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xiǎn)、恢復(fù)原狀、消除影響、恢復(fù)名譽(yù)、賠禮道歉。[13]從請(qǐng)求權(quán)的角度觀察,返還財(cái)產(chǎn)就是返還財(cái)產(chǎn)請(qǐng)求權(quán),與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中的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同義;停止侵害、排除妨害都屬于排除妨害的方式,屬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中的妨害除去請(qǐng)求權(quán);消除影響則相當(dāng)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中的妨害防止請(qǐng)求權(quán)。另外四種侵權(quán)責(zé)任承擔(dān)方式則不屬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范疇。但這是否意味著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必須單獨(dú)立法,這四種責(zé)任方式就不可以與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一起規(guī)定呢?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絕對(duì)權(quán)保護(hù)的立法模式的發(fā)展趨勢(shì)。
(二)絕對(duì)權(quán)保護(hù)立法模式發(fā)展趨勢(shì)的回顧
關(guān)于物權(quán)的保護(hù),雖然大陸法系國家一般只在民法典的物權(quán)編中規(guī)定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而將損害賠償交給侵權(quán)行為編,但我國《物權(quán)法》既規(guī)定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第34、35條),又規(guī)定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第36、37條),似乎沒有人指責(zé)《物權(quán)法》“多管閑事”,規(guī)定了《侵權(quán)責(zé)任法》的內(nèi)容。
關(guān)于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法國、德國、日本等較早制定民法典的國家沒有規(guī)定人格權(quán)和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其關(guān)于人格權(quán)保護(hù)或者委之于侵權(quán)行為法,或者委之于判例。而在規(guī)定了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立法例中,無一不是將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一起規(guī)定,如《瑞士民法典》第28條a不僅規(guī)定了通常所說的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內(nèi)容,而且還規(guī)定了損害賠償;《越南民法典》第27條規(guī)定了終止侵權(quán)行為、公開賠禮道歉、改正、賠償物質(zhì)損失和精神損失等責(zé)任方式《阿爾及利亞民法典》第47條也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基于人格享有的固有權(quán)利遭受不法侵害時(shí),得請(qǐng)求停止侵害和損害賠償。”
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更是都與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一起規(guī)定的。如德國著作權(quán)法第97條第1款規(guī)定:“受害人可以訴請(qǐng)對(duì)于有再次復(fù)發(fā)危險(xiǎn)的侵害行為,即刻就采用下達(dá)禁令的救濟(jì);如果侵害人系出于故意或過失,則還可以同時(shí)訴請(qǐng)損害賠償”。德國商標(biāo)法第14條規(guī)定:“(5)任何人違反第(2)款至第(4)款的規(guī)定使用一個(gè)標(biāo)志,該商標(biāo)所有人可以起訴要求禁止這種使用。(6)任何人故意或過失侵權(quán),都應(yīng)當(dāng)負(fù)責(zé)賠償商標(biāo)所有人因此受到的損害。……”
可見,對(duì)于絕對(duì)權(quán)的保護(hù)應(yīng)該是全面的,在絕對(duì)權(quán)受到侵害的不同時(shí)期或不同狀態(tài)都應(yīng)有相應(yīng)的、有效的救濟(jì)措施,對(duì)其集中規(guī)定更有利于絕對(duì)權(quán)的保護(hù)。并且一個(gè)國家的立法體例的形成是與社會(huì)生活的實(shí)際和法律的發(fā)達(dá)史密切相關(guān)的。我國很多學(xué)者都在呼吁制定單獨(dú)的人格權(quán)法或民法典中的人格權(quán)編,理由是人格權(quán)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前提條件,很重要,應(yīng)予以特別保護(hù)。這是因?yàn)槲覈鴽]有民法典,我們需要制定民法典,存在制定人格權(quán)法或人格權(quán)編的契機(jī),對(duì)于早已制定民法典的國家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它們只能在關(guān)于修改“自然人”或“民事權(quán)利”一章的規(guī)定,對(duì)人格權(quán)的保護(hù)予以完善,或者是交由判例來彌補(bǔ)立法之缺漏。即使是近年來制定民法典的國家,也沒有單獨(dú)制定人格權(quán)編,只是對(duì)人格保護(hù)進(jìn)行了全面的規(guī)定,如《越南民法典》、《阿爾及利亞民法典》,并且這些立法例還有侵權(quán)損害賠償責(zé)任的規(guī)定。這也就是說,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能夠和諧相處。那為什么在我國法律中,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會(huì)存在沖突(競合)呢?這是由我國民事立法的特殊性所決定的。
(三)我國關(guān)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立法模式的原因分析
《物權(quán)法》關(guān)于物權(quán)的保護(hù)既規(guī)定了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又規(guī)定了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這種體例與《侵權(quán)責(zé)任法》中的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的規(guī)定就會(huì)產(chǎn)生沖突,這已經(jīng)不僅僅是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競合的問題,而可以說是物權(quán)法的保護(hù)與侵權(quán)法保護(hù)的重合了。如果只是物權(quán)法如此規(guī)定,而侵權(quán)法不規(guī)定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也許不會(huì)產(chǎn)生如此嚴(yán)重的問題。為什么會(huì)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呢?這是與我國民事立法的現(xiàn)狀密切相關(guān)的。我國法上沒有專門規(guī)定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如果不在侵權(quán)責(zé)任法中規(guī)定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人格權(quán)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hù)。筆者認(rèn)為,不管是有意還是無心,侵權(quán)責(zé)任法全面保護(hù)的規(guī)定是必要的。如果到時(shí)我們制定了人格權(quán)法或者是編纂了民法典,可以對(duì)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作專門規(guī)定,也可以對(duì)人格權(quán)的侵權(quán)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作宣示性的規(guī)定。如果我們有了人格權(quán)法或民法典,侵權(quán)責(zé)任法也可以只規(guī)定損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因此,在人格權(quán)法或民法典制定以前侵權(quán)責(zé)任法對(duì)絕對(duì)權(quán)保護(hù)進(jìn)行全面的規(guī)定是合理的。我們所需要做的是澄清絕對(duì)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的適用。以下就以《侵權(quán)責(zé)任法》為基礎(chǔ)來探討絕對(duì)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
四、絕對(duì)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的適用
《侵權(quán)責(zé)任法》規(guī)定的八種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中,返還財(cái)產(chǎn)、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影響是通常所說的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恢復(fù)原狀是賠償損失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形式,因此恢復(fù)原狀和賠償損失都是大陸法系侵權(quán)責(zé)任的內(nèi)容。那么消除影響、恢復(fù)名譽(yù)和賠禮道歉屬于什么規(guī)范呢?其實(shí)這兩種責(zé)任方式主要是對(duì)人格權(quán)侵權(quán)的救濟(jì),雖不是人格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內(nèi)容,但屬于侵權(quán)責(zé)任的方式,盡管大陸法系民法都只是將損害賠償作為侵權(quán)責(zé)任承擔(dān)的方式。這是我國民事立法的創(chuàng)造。《越南民法典》第27條在規(guī)定人格權(quán)保護(hù)時(shí),也規(guī)定了“公開賠禮道歉、改正”。其中,“改正”相當(dāng)于我國的消除影響、恢復(fù)名譽(yù)。
學(xué)界關(guān)于絕對(duì)權(quán)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適用上的困境主要是指如果將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置于侵權(quán)責(zé)任法中,那么侵權(quán)責(zé)任的構(gòu)成要件、時(shí)效限制不適用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行使,因而無法及時(shí)、有效地保障受害人的權(quán)益。而且侵權(quán)責(zé)任的一般歸責(zé)原則即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也不適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14]筆者不以為然。
首先,傳統(tǒng)民法主張一般侵權(quán)責(zé)任的構(gòu)成要件有四,即違法行為、損害事實(shí)、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shí)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以及行為的過錯(cuò)。其中,損害事實(shí)是關(guān)鍵要件,如果沒有損害事實(shí),則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shí)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要件也不可能存在。而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行使則不需要考慮是否有損害,當(dāng)然也就不需要考慮因果關(guān)系的要件了。過錯(cuò)要件也是不需要的。這是一個(gè)不言自明的道理。當(dāng)違法行為人的行為對(duì)權(quán)利人的權(quán)利構(gòu)成現(xiàn)實(shí)威脅之時(shí)起,權(quán)利人就有權(quán)要求侵權(quán)人停止其不當(dāng)行為、消除危險(xiǎn)、排除妨害而不論行為人是否有過錯(cuò)和損害事實(shí)是否存在。難道因?yàn)橐粋€(gè)實(shí)施違法行為的人沒有過錯(cuò),權(quán)利人就無權(quán)要求排除對(duì)其權(quán)利的侵犯嗎?難道要等到違法行為造成了損害后果才可以要求行為人停止侵害嗎?如果侵權(quán)法不分具體情況一律以過錯(cuò)( 法律 明確規(guī)定的幾種情形除外)和損害后果為要件,無疑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不過,這又與侵權(quán)法的立法傳統(tǒng)密切相關(guān),因?yàn)閭鹘y(tǒng)的侵權(quán)法只是規(guī)定侵權(quán)損害賠償責(zé)任。以傳統(tǒng)侵權(quán)法學(xué)理論為指導(dǎo)的我國侵權(quán)法律規(guī)范卻突破了傳統(tǒng)侵權(quán)法的立法體例,除了規(guī)定損害賠償責(zé)任外,還規(guī)定了其它的責(zé)任形式。那么,我們就不能一味地遵循傳統(tǒng)侵權(quán)法理論而要求侵權(quán)責(zé)任的構(gòu)成要件必須是違法行為、損害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和過錯(cuò),而是不同的責(zé)任形式適用不同的構(gòu)成要件。
在這個(gè)問題上,《侵權(quán)責(zé)任法》已有一定程度的解決,主要體現(xiàn)在第二章責(zé)任構(gòu)成和責(zé)任方式中。第6條、第7條[15]關(guān)于侵權(quán)責(zé)任構(gòu)成的規(guī)定不再要求“損害”,這也就意味著無損害的過錯(cuò)責(zé)任和無過錯(cuò)責(zé)任都可以成立。第21條更是對(duì)無損害的侵權(quán)責(zé)任適用情形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16]但這種侵權(quán)責(zé)任的構(gòu)成是否需要考慮過錯(cuò)則不明確。無損害的侵權(quán)責(zé)任在第五章產(chǎn)品責(zé)任中也有體現(xiàn),第45條規(guī)定:“產(chǎn)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財(cái)產(chǎn)安全的,被侵權(quán)人有權(quán)要求生產(chǎn)者、銷售者承擔(dān)排除妨礙、消除危險(xiǎn)等侵權(quán)責(zé)任。”雖然從第45條的規(guī)定可以得出我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規(guī)定了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侵權(quán)責(zé)任的結(jié)論,但還是美中不足,即《侵權(quán)責(zé)任法》沒有以一般條款的方式規(guī)定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可以考慮在《侵權(quán)責(zé)任法》的司法解釋中予以明確規(guī)定。[17]
其次,關(guān)于時(shí)效限制。有學(xué)者認(rèn)為怎么能因時(shí)間的經(jīng)過,就任憑借行為人侵害權(quán)利人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名譽(yù)、隱私等,而無權(quán)令其停止?在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物權(quán)遭受侵害的情況下,因時(shí)間的經(jīng)過,侵權(quán)人就可以永續(xù)地侵害他人的物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真無效益、正義可言,違反社會(huì)秩序的要求。[18]其實(shí),正如該學(xué)者所言,侵害行為正在進(jìn)行中,屬于一個(gè)侵權(quán)行為尚未結(jié)束,訴訟時(shí)效不開始起算,[19]那么也就不會(huì)出現(xiàn)因時(shí)間的經(jīng)過,而使權(quán)利人無權(quán)令侵權(quán)人停止侵害、讓其永續(xù)地侵害他人權(quán)利等無效益、不正義的后果了。因此,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作為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也就不存在訴訟時(shí)效方面的困惑了。
最后,關(guān)于侵權(quán)責(zé)任的歸責(zé)原則對(duì)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適用。如前所述,實(shí)質(zhì)上屬于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侵權(quán)責(zé)任形式是無需考慮過錯(cuò)和損害的,那么其歸責(zé)原則應(yīng)該是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但現(xiàn)有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只適用于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幾種情形,并且是針對(duì)已經(jīng)造成了損害的侵權(quán)行為。那么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的歸責(zé)原則就只能是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這種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與作為特定領(lǐng)域適用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有明顯的區(qū)別,具體表現(xiàn)在:第一,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作為整個(gè)侵權(quán)責(zé)任歸責(zé)原則的基本原則,原則上適用于侵權(quán)的一切領(lǐng)域;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只適用于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幾種情形。第二,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不把損害事實(shí)作為認(rèn)定對(duì)侵權(quán)責(zé)任是否成立的要件;對(duì)于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而言,如無損害事實(shí)的存在,就不能認(rèn)定行為人的侵權(quán)責(zé)任。第三,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適用不需要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適用必須有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另外,在具體司法實(shí)踐中,多數(shù)情況下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與其他原則在適用時(shí)往往會(huì)發(fā)生競合,但不能據(jù)此就否認(rèn)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獨(dú)立性。[20]
在適用于侵權(quán)領(lǐng)域的八種責(zé)任方式中,除了要求侵權(quán)人承擔(dān)賠償損失、賠禮道歉侵權(quán)責(zé)任適用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或特定情況下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外,對(duì)于其它的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完全可以適用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根據(jù)《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15條第2款的規(guī)定,上述的八種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可以單獨(dú)適用,也可以合并適用,具體適用何種形式,取決于權(quán)利人的具體訴訟請(qǐng)求的內(nèi)容。那么,在合并適用時(shí),只要有賠償損失或賠禮道歉在內(nèi),就須和這兩種責(zé)任方式單獨(dú)適用時(shí)一樣適用相同的歸責(zé)原則。依據(jù)上述原則,在具體的侵權(quán)訴訟中,法院應(yīng)根據(jù)權(quán)利人訴訟請(qǐng)求中要求侵權(quán)人承擔(dān)的具體侵權(quán)責(zé)任方式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歸責(zé)原則。這個(gè)原理可以通過《物權(quán)法》或《侵權(quán)責(zé)任法》的司法解釋來表達(dá)。這樣,也就解除了在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與侵權(quán)責(zé)任競合時(shí),在物權(quán)侵害之訴中,訴訟當(dāng)事人選擇物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而使《侵權(quán)責(zé)任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可能淪為“具文”的憂慮。[21]
五、結(jié)論
在我國現(xiàn)有的立法體例之下,承認(rèn)侵權(quán)責(zé)任形式的多樣性,將絕對(duì)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置于侵權(quán)責(zé)任法之中,是有必要的;關(guān)于這種體例的困惑通過無損害的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引入即可解決,即對(duì)于絕對(duì)權(quán)的不同的救濟(jì)方式適用不同的歸責(zé)原則。
第7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一) 人權(quán)主義
所謂人權(quán)主義, 是指以人權(quán)保障為最高理念, 體現(xiàn)以人為本位、以權(quán)利為本位的價(jià)值觀念, 將私權(quán)利作為人權(quán)的基礎(chǔ)權(quán)利。人權(quán)主義是21 世紀(jì)的人文主義。人權(quán)主義的民法典, 實(shí)際上就是私權(quán)神圣的民法典, 它是民法權(quán)利法性質(zhì)的必然要求, 即民法典全面確認(rèn)民事主體的平等性及其民事權(quán)利, 確保民事權(quán)利非經(jīng)法定程序不受限制或剝奪。具體而言, 民法典首先要構(gòu)建、全面的民事權(quán)利體系, 堅(jiān)持除物權(quán)、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實(shí)行權(quán)利法定主義外, 其他民事權(quán)利尤其是人身權(quán)利, 嚴(yán)格實(shí)行任意主義, 摒棄權(quán)利必為法律明文確認(rèn)的僵化觀念; 其次, 對(duì)不同主體的民事權(quán)利給予同等的保護(hù), 確認(rèn)私力救濟(jì)制度, 完善公力救濟(jì)制度, 實(shí)行徹底的全部賠償規(guī)則; 再次, 明確規(guī)定類推適用在民法上的價(jià)值及其司法適用; 最后, 確認(rèn)法院(法官) 不得以法無明文規(guī)定或法律規(guī)定不明確而拒絕審判。
(二) 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 即私法自治, 是指民法范疇內(nèi), 民事主體自由地決定自己的行為, 不受任何的非法干預(yù)。換言之,民事主體得依自主的意思作出判斷, 自主選擇、自主參與、自主行為、自己負(fù)責(zé), 在法律所不禁止的范圍內(nèi), 可以自由地依照自己的意思設(shè)立、變更、終止種種民事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 在因彼此間的權(quán)益發(fā)生糾紛時(shí)可以選擇糾紛的解決方式。意思自治理念實(shí)質(zhì)上就是私法上的自由理念、自由原則。意思自治原則是市場方式對(duì)法律提出的要求。在市場經(jīng)濟(jì)中, 當(dāng)事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 他利用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和知識(shí), 自主地進(jìn)行民事活動(dòng), 對(duì)自己的行為負(fù)責(zé)、享受自己行為帶來的利益, 承擔(dān)自己行為的風(fēng)險(xiǎn)。意思自治能確保民事主體進(jìn)行民事活動(dòng)的意思自由, 使之既不受其他當(dāng)事人的非法干預(yù), 也能抵御不當(dāng)或者越位的國家權(quán)力的干擾, 從而使市場的各種資源配置趨向優(yōu)化, 保障市場經(jīng)濟(jì)的順利進(jìn)行。貫徹這一理念, 民法典應(yīng)當(dāng)將協(xié)議、合同、契約三個(gè)概念統(tǒng)一, 恢復(fù)《民法通則》中的合同概念, 使一切民事法律行為皆受意思自治規(guī)則的調(diào)整, 全面落實(shí)契約(合同、協(xié)議) 自由; 在調(diào)整契約(合同) 關(guān)系方面, 盡可能多地設(shè)置任意性規(guī)范, 使當(dāng)事人意思表示的效力優(yōu)于任意性規(guī)范和法律推定條款。當(dāng)然, 這里的自由不是絕對(duì)的自由, 而是受法律和公序良俗限制的自由。
第8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關(guān)鍵詞:俄羅斯;大眾傳媒;誹謗法
中圖分類號(hào):D951.2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8―0961(2009)03―0038―04
按照西方學(xué)者的說法,1990年6月12日《宣言》的通過,標(biāo)志著俄羅斯“第一共和國”的成立,因?yàn)檫@份宣言規(guī)定了立法、執(zhí)行、司法三權(quán)分立的原則,由此俄羅斯整個(gè)社會(huì)的制度變遷從形式上說有了法律依據(jù)。但事實(shí)上,只是到1993年12月12日新憲法確立之后,整個(gè)社會(huì)制度創(chuàng)設(shè)才開始顯得有規(guī)可循,才初步具有了“革新”而非“應(yīng)急”的性質(zhì)。1993年《俄羅斯聯(lián)邦憲法》第一章“體制基礎(chǔ)”中第1條明確規(guī)定:“俄羅斯聯(lián)邦是一個(gè)民主、法制的以共和國形式統(tǒng)治的聯(lián)邦國家”。自此,俄羅斯開始制定大量法律對(duì)社會(huì)生活各個(gè)領(lǐng)域進(jìn)行調(diào)整,其中包括大眾傳播領(lǐng)域。使用法律的手段對(duì)大眾傳播領(lǐng)域中的傳播關(guān)系進(jìn)行規(guī)范和調(diào)整,最終形成了俄羅斯聯(lián)邦大眾傳播法體系。它主要由幾個(gè)部分組成――聯(lián)邦憲法、聯(lián)邦民法、聯(lián)邦刑法、大眾傳媒法、總統(tǒng)令、聯(lián)邦政府決議、國家杜馬決議與聲明以及其他與傳播相關(guān)的聯(lián)邦法律,其中《大眾傳媒法》為調(diào)整大眾傳播關(guān)系的專門法。對(duì)大眾傳媒誹謗行為進(jìn)行規(guī)制是大眾傳播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俄聯(lián)邦《憲法》對(duì)誹謗的限制
為了保障公民和媒體行使言論與新聞自由,俄《憲法》第29條第1款規(guī)定,保障每個(gè)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第4款規(guī)定,每個(gè)人都有權(quán)利以任何合法方式自由搜尋、取得、傳遞、生產(chǎn)、散布信息;第5款規(guī)定,保障大眾信息自由,禁止新聞審查。《大眾傳播媒法》重申了上述《憲法》對(duì)公民和媒體行使言論與新聞自由的保護(hù)。該法第1條規(guī)定,在俄境內(nèi)搜尋、獲得、制造、傳播信息以及籌設(shè)大眾傳播媒體不應(yīng)受到限制,除非其他關(guān)于傳播的相關(guān)聯(lián)邦法律規(guī)定不得違反之。但是,《憲法》同時(shí)認(rèn)為其所保障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并非絕對(duì),應(yīng)該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對(duì)公民和媒體在行使言論和新聞自由時(shí)侵犯他人名譽(yù)權(quán)的行為,即誹謗行為進(jìn)行限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憲法》第21條第l款規(guī)定,人格尊嚴(yán)受國家法律保護(hù),任何東西均不得成為詆毀人格的理由;第23條第1款規(guī)定,每個(gè)人都有私生活、個(gè)人和家庭秘密不受侵犯、維護(hù)自己榮譽(yù)和良好聲譽(yù)的權(quán)利。這些憲法條款構(gòu)成了俄政府對(duì)誹謗行為進(jìn)行規(guī)制與處罰的憲法基礎(chǔ)。
二、俄羅斯聯(lián)邦刑事誹謗法
俄羅斯有悠久的刑事誹謗法傳統(tǒng)。現(xiàn)行俄《刑法典》有五項(xiàng)罪名涉及誹謗行為。《刑法典》第129條規(guī)定,所謂誹謗是指“故意散布不實(shí)消息詆毀他人榮譽(yù)和尊嚴(yán),或是損毀他人名譽(yù)的行為”。俄《刑法典》和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法律一樣,把侮辱當(dāng)作是一項(xiàng)單獨(dú)的罪名。《刑法典》第130條規(guī)定,侮辱指“以下流方式貶損他人榮譽(yù)和尊嚴(yán)的行為”。《刑法典》第129條還區(qū)分了三種不同的誹謗:公開演說(public speech)中的誹謗、經(jīng)大眾媒介傳播的誹謗(第129條第2款)以及指控他人犯有嚴(yán)重或特別嚴(yán)重罪行的誹謗(第129條第3款)。如果誹謗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而實(shí)施或該誹謗性言詞的內(nèi)容系指控他人犯罪,則對(duì)該行為的處罰要比一般誹謗重――可能最多會(huì)判處三年監(jiān)禁。《刑法典》第297條規(guī)定了“藐視法庭罪”,該罪實(shí)際上是一項(xiàng)特別誹謗罪,因?yàn)樗?guī)定了在法庭審理案件過程中,不得誹謗參加旁聽的人。其他兩項(xiàng)罪名分別為第298條的誹謗法官、陪審員、檢察長、偵查員、調(diào)查人員、法警、法院執(zhí)行人員罪以及第319條的侮辱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代表罪,這兩項(xiàng)誹謗罪本質(zhì)上都屬于對(duì)公共官員名譽(yù)權(quán)的特別保護(hù),極易導(dǎo)致公眾,陡于對(duì)公共官員的批評(píng),從而與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煽動(dòng)性誹謗法聯(lián)系在一起。在俄羅斯,如果對(duì)刑事誹謗被告人提起公訴,公訴機(jī)關(guān)須舉證被告?zhèn)鞑サ臑椴粚?shí)信息,并且在主觀上是出于惡意。1997-2001年,俄羅斯所有的誹謗案件中,刑事侮辱和誹謗案件占5%~9%,其余案件均為民事誹謗案件。
三、俄羅斯聯(lián)邦民事誹謗法
(一)《民法典》對(duì)誹謗行為規(guī)制的主要內(nèi)容
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有數(shù)個(gè)條款對(duì)民事誹謗行為進(jìn)行規(guī)制,以保護(hù)公民和法人的名譽(yù)。《民法典》第150條列舉了大量的非財(cái)產(chǎn)性權(quán)利(non―property rights)和非物質(zhì)性利益(Non―material val―lies),其中包括了對(duì)人格尊嚴(yán)和名譽(yù)的保護(hù)。如果個(gè)人認(rèn)為自己受到不實(shí)和誹謗性信息的損害,有權(quán)向法院提訟以保護(hù)自己的榮譽(yù)、尊嚴(yán)和商譽(yù)。這說明民事誹謗法保護(hù)的客體不僅包括名譽(yù),還包括人格尊嚴(yán)。第151條則規(guī)定了針對(duì)包括損害個(gè)人名譽(yù)在內(nèi)的精神損害賠償責(zé)任,而法典第1099-1101條則為針對(duì)包括損害個(gè)人名譽(yù)在內(nèi)的精神損害賠償?shù)某绦蛐砸?guī)定。第152條規(guī)定了“反駁權(quán)”以及“答復(fù)權(quán)”等民事誹謗救濟(jì)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和《大眾傳媒法》都明確規(guī)定對(duì)死者的名譽(yù)與尊嚴(yán)進(jìn)行保護(hù)。《民法典》第152條第1款規(guī)定,根據(jù)當(dāng)事人的請(qǐng)求,死亡公民的名譽(yù)和尊嚴(yán)應(yīng)該得到保護(hù)。這與西方資深民主國家為了維護(hù)新聞自由,而拒絕提供對(duì)死者名譽(yù)權(quán)進(jìn)行保護(hù)的做法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
(二)民事誹謗行為的構(gòu)成要件
根據(jù)《民法典》第152條的規(guī)定,構(gòu)成民事誹謗一般須具備以下要件:1.相關(guān)信息已公開傳播;2.公開傳播的信息具有誹謗性;3。公開傳播信息的虛假性;4.公開傳播的信息屬于失實(shí);5.公開傳播的誹謗性信息指向原告。只要這五個(gè)要件都具備,作為被告的新聞?dòng)浾呋蛎襟w就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誹謗的侵權(quán)責(zé)任。司法實(shí)踐中,大多數(shù)法院對(duì)民事誹謗的構(gòu)成作狹義解釋,也就是并不要求五個(gè)要件都具備,只要具備其中三個(gè)就可判定構(gòu)成民事誹謗。法院通常很少關(guān)注公開傳播信息的特性,如這些信息是事實(shí)還是意見,這些誹謗性信息是否直接指向原告。在許多民事誹謗案件中,新聞?dòng)浾吖_的其實(shí)是對(duì)某件事實(shí)的評(píng)論或批評(píng),但當(dāng)事人向法院就此提起民事誹謗訴訟時(shí),法院往往會(huì)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決。這對(duì)新聞媒體行使新聞自由構(gòu)成了很大的威脅。
(三)民事誹謗法中的舉證責(zé)任
根據(jù)俄羅斯《民法典》的規(guī)定,民事誹謗的原告承擔(dān)最輕的舉證責(zé)任,卻給被告(如新聞?dòng)浾?設(shè)置了過重的舉證責(zé)任。原告應(yīng)該承擔(dān)的舉證責(zé)任是被指控的誹謗性陳述已公開并指向自己,但實(shí)際上,法院常常并不要求原告在法庭上明確證明自己就是那個(gè)被誹謗的對(duì)象,只要向法官說明有誹謗自己的材料公開,比如在法庭上給法官帶來一份載有被指控帶有誹謗內(nèi)容的報(bào)紙復(fù)印件即可。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即使在涉及公共利益
的情況下,被告都要承擔(dān)舉證被指控的誹謗性陳述是虛假的責(zé)任(《民法典》第152條第1款)。當(dāng)然,按照《民法典》第152條的規(guī)定,被指控的誹謗性陳述必須指向某特殊的個(gè)人或法人,并且很容易辨別。這些規(guī)定顯然對(duì)名譽(yù)權(quán)的保護(hù)有利,而對(duì)媒體行使新聞自由極為不利。
(四)民事誹謗法中的抗辯理由
俄羅斯民事誹謗法的主要目標(biāo)似乎就是用來對(duì)付那些犯錯(cuò)的被告。因?yàn)椋睹穹ǖ洹分械南嚓P(guān)規(guī)定只強(qiáng)調(diào)在民事誹謗訴訟中,原告如何反駁被告以及如何獲得賠償,而對(duì)于被告在面對(duì)原告的指控如何保護(hù)自己,也就是被告的抗辯權(quán)卻極少提及。《民法典》第152條第1款規(guī)定:“如果民事誹謗訴訟中的被告不能舉證被控信息符合事實(shí),公民可以要求法院為其提供機(jī)會(huì)反駁這些損害自己榮譽(yù)、尊嚴(yán)和商譽(yù)的信息。”因此,按照上述規(guī)定,似乎在俄羅斯,被告如果能在法庭上證明其所公開的信息的真實(shí)性,就不該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也就是真實(shí)性抗辯在民事誹謗訴訟中是有法律依據(jù)的。但是,實(shí)際情況并非如此。首先,被告舉證責(zé)任重。《民法典》規(guī)定,不管訴由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也不管原告是否為公眾人物或公共官員,被告(媒體和作品的作者)都要承擔(dān)舉證其公開信息真實(shí)性的責(zé)任,如果其舉證不成功,法院會(huì)自動(dòng)推定該信息為虛假。其次,大量不利因素的存在導(dǎo)致被告舉證艱難。按照俄羅斯法律的規(guī)定,只有原始文件或經(jīng)證實(shí)的文件才能提交法庭,這一點(diǎn)對(duì)作為被告的新聞?dòng)浾呋蛎襟w來說是幾乎不可能做到的。俄羅斯法律還規(guī)定,當(dāng)訴訟雙方當(dāng)事人試圖獲得證據(jù)被阻時(shí),可請(qǐng)求法院協(xié)助,條件是舉證當(dāng)事人已請(qǐng)求過并已被請(qǐng)求人拒絕,這對(duì)于民事誹謗訴訟的被告來說舉證也是很困難的。還有重要的一點(diǎn),作為被告的媒體和記者,如果盡了舉證的義務(wù)很有可能會(huì)暴露那些可靠的秘密的消息源,這種做法是違背其職業(yè)道德的。
(五)民事誹謗法中的救濟(jì)方式
俄羅斯民事誹謗法針對(duì)民事誹謗訴訟中的原告主要提供了三種救濟(jì)方式:
1 反駁權(quán)(right to refutation)
《民法典》第152條第1款規(guī)定,如果傳播者不能證實(shí)損害公民名譽(yù)、尊嚴(yán)或商譽(yù)的信息與實(shí)際相符,公民有權(quán)要求法院為其提供反駁機(jī)會(huì);第2款規(guī)定,如果損害公民名譽(yù)、尊嚴(yán)或商譽(yù)的信息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進(jìn)行的,那么,反駁這些信息可同樣使用大眾傳播媒介;如果上述信息載于某組織的文件中,該文件應(yīng)該修改或撤銷;其他情形下的反駁方式由法院裁定。《大眾傳媒法》第43條對(duì)“反駁權(quán)”也作了類似的規(guī)定,公民個(gè)人或組織有權(quán)要求傳播不實(shí)信息,并損害其名譽(yù)和尊嚴(yán)的大眾傳播媒介編輯部提供反駁機(jī)會(huì)。如果其本人無法行使反駁權(quán),可授權(quán)其人行使。如果該大眾傳播媒介編輯部沒有關(guān)于其所傳播的消息符合事實(shí)的證據(jù),則其有義務(wù)在本媒介上對(duì)該信息進(jìn)行反駁。如果公民或組織提供了反駁的文本,且該文本符合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應(yīng)該給予公開。有義務(wù)提供反駁權(quán)的廣播、電視節(jié)目編輯部,可向行使反駁權(quán)的公民或組織代表提供在其節(jié)目中宣讀文本或?qū)⑵湮谋句浺纛A(yù)播的機(jī)會(huì)。《大眾傳媒法》第44、45條分別規(guī)定了行使反駁權(quán)的程序以及拒絕提供行使反駁權(quán)的理由。
2 答復(fù)權(quán)(right to reply or answer)
《民法典》第152條第3款規(guī)定,當(dāng)大眾傳播媒介損害公民受到法律保護(hù)的權(quán)利或其他利益時(shí),公民享有答復(fù)權(quán)。《大眾傳媒法》第46條對(duì)答復(fù)權(quán)也作了相同的規(guī)定,大眾傳播媒介傳播了有關(guān)公民或組織的不實(shí)或者侵害公民權(quán)利和法律利益的消息,公民或組織有要求在該大眾傳播媒介中回復(fù)(解釋、反駁)的權(quán)利。有關(guān)答復(fù)和拒絕答復(fù)的規(guī)則適用本法律第43-45條的規(guī)定。對(duì)答復(fù)權(quán)的回復(fù)不早于大眾傳播媒介下期(次)的出版(或播出)。本規(guī)則不適用編輯部評(píng)論。
3 精神損害賠償
在民事誹謗救濟(jì)方面,民事誹謗法一貫傾向于優(yōu)先適用損害賠償金作為民事誹謗訴訟的主要救濟(jì)方式,《民法典》第19條、151條和152條第5款對(duì)此均作了規(guī)定。《民法典》第152條第5款規(guī)定,公民受法律保護(hù)的名譽(yù)、尊嚴(yán)或商譽(yù)受到大眾傳播媒介損害時(shí),其不僅享有反駁權(quán),同時(shí)可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大眾傳媒法》第62條重申了大眾傳媒如果傳播了損害公民名譽(yù)與尊嚴(yán)的信息,應(yīng)該承擔(dān)精神損害賠償責(zé)任。在《民法典》第151條和第1101條中,對(duì)賠償金額度做了規(guī)定。《民法典》第151條規(guī)定,在確定精神損失的賠償額度時(shí)應(yīng)參照違法者過錯(cuò)程度和其他值得注意的情況。法庭還應(yīng)當(dāng)考慮與遭受損失者個(gè)人特點(diǎn)相關(guān)的身體上的以及精神上的傷害的程度。第1101條規(guī)定,精神損失的賠償額度由法庭依照受害人所遭受的身體和精神上的傷害性質(zhì)、以及實(shí)施傷害者的過失程度來確定。在確定損失賠償?shù)念~度時(shí)應(yīng)當(dāng)考慮到明智性與公平性的要求。身體和精神上的傷害的性質(zhì)由法庭在考慮精神損失發(fā)生的事實(shí)情況以及受害者個(gè)人特點(diǎn)的情況下進(jìn)行裁定。
四、《反極端主義活動(dòng)法》與對(duì)誹謗行為的規(guī)制
2007年7月,俄羅斯國家杜馬修訂了《反極端主義活動(dòng)法》。修訂后該法把傾向于對(duì)公共官員執(zhí)行公務(wù)活動(dòng)進(jìn)行公開批評(píng)的行為看作是誹謗行為,并把這種行為當(dāng)作是一種極端活動(dòng)來打擊。該法第1條規(guī)定,“極端活動(dòng)”包括:公共協(xié)會(huì)、宗教協(xié)會(huì)、其他協(xié)會(huì)、媒體和個(gè)人,計(jì)劃、組織、準(zhǔn)備、并實(shí)施針對(duì)……在俄羅斯聯(lián)邦或其自治區(qū)內(nèi)擔(dān)任公職的人員,在其執(zhí)行公務(wù)或執(zhí)行與其公務(wù)有關(guān)活動(dòng)期間的公開誹謗活動(dòng)。該規(guī)定本質(zhì)上是以保護(hù)國家安全的名義對(duì)言論自由的限制,也是對(duì)公共官員所提供的一種特殊保護(hù)。同時(shí),該法還禁止各種“極端主義材料”的發(fā)行,以及禁止在媒體上出現(xiàn)極端主義的標(biāo)志(可能含有誹謗性內(nèi)容)。如果媒體在收到有關(guān)部門警告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進(jìn)行補(bǔ)救并一意孤行,或其行為對(duì)公民或法人造成損害,法院可以命令終止其行為(《反極端主義活動(dòng)法》第8、11條)。盡管截至2007年10月,上述特別規(guī)定仍未被適用,但它對(duì)于言論與新聞自由已造成很大沖擊。
第9篇:民法典的條款范文
民法論文5400字(一):民法概括條款適用的方法論論文
摘要:我國民法學(xué)界對(duì)于概括條款的一些基礎(chǔ)性問題尚缺乏深入研究,其在具體的司法適用中存在誤用現(xiàn)象。概括條款是一種不同于具有明確構(gòu)成要件與法律效果的法律規(guī)范,在規(guī)范結(jié)構(gòu)上包含無法通過法律解釋來確定的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本質(zhì)上是立法者授權(quán)法官造法的規(guī)范基礎(chǔ)。在法學(xué)方法論中,法律解釋的各種方法對(duì)于概括條款沒有適用余地,概括條款屬于法內(nèi)漏洞的范疇,在適用上劣后于類推、目的性限縮以及目的性擴(kuò)張等法學(xué)方法。在概括條款具體適用方法上,應(yīng)立足于我國《民法總則》關(guān)于目的條款以及基本原則部分的規(guī)定,遵循“案例-案例群-類型”的路徑以實(shí)現(xiàn)概括條款的教義學(xué)化。
關(guān)鍵詞:不確定法律概念;概括條款;法內(nèi)漏洞;類型化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民法總則》第7條、第8條、第153條第2款以及我國《合同法》第42條第3項(xiàng)、第60條是關(guān)于誠實(shí)信用和公序良俗的規(guī)定,被認(rèn)為是民法上兩個(gè)主要的概括條款(也稱一般條款)。①此外,我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6條也被認(rèn)為是概括條款,②該條在構(gòu)造上區(qū)別于德國侵權(quán)法“三個(gè)小概括條款”(dreikleineGeneralklauseln)的模式,一般被稱為“大概括條款模式(einegroβeGeneralklausel)”。③從這些條款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其僅停留在具體列舉的意義之上,并未清楚地界定出概括條款的規(guī)范結(jié)構(gòu)特征。
總之,概括條款所涉及的問題眾多,但是圍繞概括條款的研究有三個(gè)最為基礎(chǔ)的問題尚未得到徹底澄清:一是對(duì)于什么是概括條款尚缺乏一個(gè)清楚的界定;二是概括條款在什么樣的條件下適用沒有得到明確說明;三是概括條款具體適用的方法缺乏一個(gè)系統(tǒng)的闡述。筆者于本文中的任務(wù)就圍繞這三個(gè)問題展開,并基于我國民法特有的規(guī)定闡述概括條款具體適用的方法論,即概括條款在司法適用中所遵循的具體方法。
二、概括條款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
德國的權(quán)威法學(xué)詞典對(duì)概括條款的解釋是:“概括條款是一種法律規(guī)范,它僅設(shè)立了一個(gè)一般準(zhǔn)則,其在個(gè)案中的具體含義則委托法官在學(xué)說的幫助下去確定(例如德國民法典第242條、第138條)。”12從這一界定可以看出,概括條款屬于語言上不確定的規(guī)范,13其內(nèi)容完全空洞而需評(píng)價(jià)加以補(bǔ)充。14在此背景下,概括條款經(jīng)常被理解為不確定法律概念(unbestimmteRechtsbegriffe)、規(guī)范性概念(normativenRechtsbegriffe)、需要價(jià)值填充的概念(ausfüllungsbedürftigenBegriffen)以及空白規(guī)范(Blankettnormen)等。15因此,需要先從規(guī)范結(jié)構(gòu)上厘清概括條款與上述不同種類概念之間的關(guān)系,然后進(jìn)一步從概括條款本身所蘊(yùn)含的功能來認(rèn)識(shí)概括條款。
(一)需要價(jià)值填補(bǔ)的法律概念作為概括條款的形式特征
在法學(xué)上所使用的概念可以分為描述性概念以及規(guī)范性概念。16描述性概念指的是被描述為“真實(shí)的或現(xiàn)實(shí)的,基本上可感知的或其他有形物體”,17如民法中關(guān)于物、期間的概念。描述性概念,大多對(duì)應(yīng)于現(xiàn)實(shí)生活,具有確定性的含義。規(guī)范性概念指的是需要價(jià)值填充的概念或者價(jià)值概念,它暗示了一個(gè)價(jià)值授權(quán),18如民法中關(guān)于“婚姻”、“權(quán)利能力”、“故意過失”、“重大誤解”、“必要”、“重要”、“比例”、“合理”、“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等概念。規(guī)范性概念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法律已經(jīng)作出清楚界定的概念,不依賴于個(gè)人的主觀評(píng)價(jià)而獨(dú)立存在,如前述的“婚姻”、“權(quán)力能力”,也稱為規(guī)范確定性概念;另一類是要求法律適用者自己在個(gè)案中具體判斷的概念,如上述的“必要”、“重要”、“比例”、“合理”等概念,也稱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19
由此觀之,能夠與概括條款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的至少有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兩者的不同很清晰,從適用范圍上來講,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僅僅是一個(gè)構(gòu)成要件,但概括條款是一個(gè)完整的法律規(guī)范,20如我國《民法總則》第7條、第8條規(guī)定從事民事活動(dòng)應(yīng)遵守誠實(shí)信用以及公序良俗,并且在第153條規(guī)定違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為無效。從這個(gè)意義上講,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是作為概括條款的構(gòu)成要件而存在的。然而,這可能僅僅是界定概括條款的一個(gè)必要而不充分條件,因?yàn)樵诜梢?guī)范的構(gòu)成要件中,至少在非概括條款的普通的法律規(guī)范中也會(huì)用到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如我國《合同法》第119條所規(guī)定的“守約方采取適當(dāng)?shù)拇胧乐箵p失的擴(kuò)大,否則不得就擴(kuò)大的損害要求賠償”,何為“適當(dāng)?shù)拇胧本褪且?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因此,并非所有包含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法律規(guī)范均屬概括條款。在此,需要對(duì)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作進(jìn)一步的界分。
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在內(nèi)容以及范圍上都極其不確定的概念,21因?yàn)樗磉_(dá)的多義性以及概念沒有給出嚴(yán)格的界限。22通說認(rèn)為,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主要分為三種,即歧義、模糊與評(píng)價(jià)開放。23所謂歧義就是這個(gè)概念與多種不同的含義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需要結(jié)合不同的適用情況來確定這個(gè)概念的準(zhǔn)確含義。如我國《物權(quán)法》第5章所規(guī)定的“國家所有權(quán)”與憲法上“國家所有”的爭論,24這里的關(guān)鍵就在于澄清適用的背景。所謂模糊就是概念的內(nèi)涵不明確,外延過于寬泛,以至于某個(gè)對(duì)象是否能被涵攝于概念不確定。某一法律概念所涵蓋的領(lǐng)域,可被區(qū)分為三個(gè)領(lǐng)域,即肯定領(lǐng)域、否定領(lǐng)域以及中立領(lǐng)域。25在概念的肯定領(lǐng)域與否定領(lǐng)域,含義清晰,不存在模糊地帶,只有在中立領(lǐng)域,才存在模糊的情形。正是在這一領(lǐng)域,體系、目的等各種法律解釋的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如此,在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模糊領(lǐng)域,運(yùn)用法律解釋方法也能確定規(guī)范的清晰含義,典型例子如對(duì)于我國《物權(quán)法》第243條“必要費(fèi)用”的界定,即哪一類費(fèi)用屬于“必要費(fèi)用”。26所謂評(píng)價(jià)開放的領(lǐng)域,如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等,并無明確的界限,在適用方面存在價(jià)值上的偏好,需要價(jià)值補(bǔ)充。此外,在民法中還存在大量的如“酌情”、“顯著的”、“實(shí)質(zhì)性”、“相對(duì)的”及“合理的”等兼具模糊性與價(jià)值開放性的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如我國《合同法》第68條“經(jīng)營狀況嚴(yán)重惡化”、第110條第2款后段“履行費(fèi)用過高”、第195條“贈(zèng)與人的經(jīng)濟(jì)顯著惡化,嚴(yán)重影響生產(chǎn)經(jīng)營及家庭生活的”等。這種類型的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雖然較模糊,且均需要一定的評(píng)價(jià)因素方能確定,但無論如何不能離開規(guī)范目的的約束,即必須在規(guī)范目的之內(nèi),27通過體系或者目的解釋的方法就能確定其精確含義。
(二)概括條款的實(shí)質(zhì)含義
在形式構(gòu)造上概括條款是由需要價(jià)值補(bǔ)充的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來界定的,但是這種解釋方式僅僅停留在規(guī)范構(gòu)造上,并未揭示出概括條款的真正內(nèi)涵。概括條款的實(shí)質(zhì)含義必須從“適用的主體”與“適用的對(duì)象”兩個(gè)層次理解。所謂“適用的主體”,就是在制定法或者法典中表現(xiàn)為概括條款的規(guī)范由誰來適用;所謂“適用的對(duì)象”,就是指承擔(dān)具體功能的概括條款所處理的對(duì)象是什么。
在概括條款的具體適用時(shí),由于其開放性,其并未提供具體的適用指示,也未包含相關(guān)的評(píng)估標(biāo)準(zhǔn),因此必須通過價(jià)值補(bǔ)充才能實(shí)現(xiàn)其功能(AusfüllungsbedürftigkeitoderWertausfüllungsbedürftigkeit)。33在此意義上,其他法律和可能的法外評(píng)價(jià)將作用于確定概括條款的內(nèi)容,34比如有學(xué)者就認(rèn)為概括條款是將社會(huì)科學(xué)引入教義學(xué)的主要渠道。35民法并非單一價(jià)值的體現(xiàn),隨著社會(huì)的變遷,由民法所秉持的價(jià)值絕對(duì)的個(gè)人主義演變?yōu)閭€(gè)人主義與整體主義、合作主義的相互交錯(cuò),36即相互沖突的價(jià)值在相互的妥協(xié)中實(shí)現(xiàn)動(dòng)態(tài)平衡。37如何將不同的價(jià)值沖突從理論層面落實(shí)到實(shí)踐層面,概括條款將起到轉(zhuǎn)介作用。38因此概括條款的教義學(xué)化并不能單純依靠民法自身完成,39其所凸顯的價(jià)值并非“私法自治”所獨(dú)自涵蓋,即對(duì)其適用需要橫跨不同的法域或價(jià)值。
托依布納(Teubner)就將概括條款描述為“多次無限地援引社會(huì)價(jià)值”,基于社會(huì)規(guī)范(接收功能),基于價(jià)值觀的轉(zhuǎn)化(轉(zhuǎn)換功能)以及將規(guī)范形成完全授權(quán)給法官(授權(quán)功能)來具體化概括條款。40在此意義上,概括條款不但具有傳統(tǒng)意義上接收和轉(zhuǎn)介功能,而且也逐步發(fā)展成為授權(quán)法官自我評(píng)價(jià)和自我創(chuàng)造的發(fā)展功能,41如通過《德國民法典》第823條這一概括條款的“其他權(quán)利”所發(fā)展出的一般人格權(quán)、框架權(quán)等權(quán)利。
綜上所述,概括條款是對(duì)于法院以及法官在私法不同價(jià)值之間相互權(quán)衡以實(shí)現(xiàn)各價(jià)值動(dòng)態(tài)平衡的授權(quán)規(guī)范,具體表現(xiàn)為只要在某一規(guī)范的構(gòu)成要件中包含有無法通過解釋確定,而需要法官進(jìn)行價(jià)值補(bǔ)充的規(guī)范性不確定法律概念。
(三)民法領(lǐng)域中的概括條款
民法領(lǐng)域的概括條款體現(xiàn)為誠實(shí)信用與公序良俗。無論是誠實(shí)信用還是公序良俗均無法通過解釋來確定,均包含有價(jià)值開放且需要價(jià)值填補(bǔ)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兩者分別作為民事主體之間“特別關(guān)聯(lián)領(lǐng)域”以及“陌生領(lǐng)域”兩大領(lǐng)域概括條款的構(gòu)成要件,同時(shí)也是這兩大領(lǐng)域教義學(xué)發(fā)展的規(guī)范基礎(chǔ)。誠實(shí)信用僅適用于民事主體的“特別關(guān)聯(lián)”領(lǐng)域,是較高的行為標(biāo)準(zhǔn),通常針對(duì)特殊、非典型的情形適用以及權(quán)利行使行為的“行使審查”。以合同為例,權(quán)利的產(chǎn)生、變更、行使以及消滅各個(gè)階段均離不開誠實(shí)信用的“行使審查”功能,在此功能發(fā)揮過程中,在教義學(xué)上產(chǎn)生一系列成熟的法律制度并進(jìn)一步被法典化,如“禁止權(quán)利濫用”、“締約過失”、“保護(hù)義務(wù)”、“情勢(shì)變更”、“權(quán)利失效”等法律制度。公序良俗常用于保護(hù)第三人及公眾利益,是一個(gè)較低的行為標(biāo)準(zhǔn),通常針對(duì)一般、典型情形適用,針對(duì)法律行為內(nèi)容進(jìn)行“內(nèi)容審查”,在此功能發(fā)揮的過程中,在教義學(xué)上也產(chǎn)生出一系列成熟的法律制定并被法典化,如最為典型的“暴利行為”。
有“大概括條款”之稱的我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6條,采用對(duì)于“權(quán)利與利益的一體保護(hù)”模式,50不但對(duì)“權(quán)利與利益”無法進(jìn)行準(zhǔn)確界分,而且即使對(duì)于利益進(jìn)行保護(hù)也缺乏明確的適用標(biāo)準(zhǔn),這也無怪乎該法通過后,諸多學(xué)者還是采用德民的三個(gè)小概括條款模式進(jìn)行解釋論分析。51雖然德民的三個(gè)小概括條款模式依舊是概括條款,但是與我國侵權(quán)法上的大概括條款相比,已經(jīng)是較為成熟的教義學(xué)作品,具有更高程度的清晰性。由此也可看出,所謂的“大”與“小”并非是質(zhì)上的區(qū)別,而僅僅是量的差異。
三、概括條款適用的方法論位階
概括條款處于法學(xué)方法論的邊緣地帶,57扮演了帶有特殊任務(wù)的方法論意義上的輔角色(alsHilfsfigurderMethodelehremitspezialenAufgaben)。58按照傳統(tǒng)法學(xué)方法論所主張的法律適用步驟,可以把法律適用分為兩個(gè)階段,即法律解釋(Auslegung)和制定法漏洞(Gesetzeslücke)的填補(bǔ)。59概括條款的適用在傳統(tǒng)法學(xué)方法論體系中居于何種地位?這個(gè)問題可以轉(zhuǎn)換為,概括條款與法律解釋以及法律漏洞分別是什么關(guān)系?其進(jìn)一步可以轉(zhuǎn)換為,概括條款與法律解釋的各種方法以及法律漏洞填補(bǔ)各種方法之間是什么關(guān)系?
四、概括條款的具體適用方法
概括條款在法學(xué)方法論適用中已經(jīng)超出了法律解釋以及制定法漏洞中各種漏洞填補(bǔ)方法的強(qiáng)約束,具有準(zhǔn)立法性質(zhì),在適用時(shí)需考量社會(huì)政策層面的因素,93包括自然理性、社會(huì)本質(zhì)、衡平、應(yīng)受承認(rèn)裁判的整體脈絡(luò)、現(xiàn)行法的基本原則等因素,94并對(duì)上述各種因素進(jìn)行利益衡量,95本質(zhì)上是立法者授權(quán)法官造法的規(guī)范基礎(chǔ)。在具體適用上,一般認(rèn)為需要將概括條款通過具體化(Konkretisierung)的方法實(shí)現(xiàn),而具體化最重要的目標(biāo)就是類型化(Typus)。96“具體化”和“類型化”表明了概括條款法教義學(xué)化的兩個(gè)步驟。第一步,法官對(duì)于概括條款的直接適用,形成個(gè)案裁判(Fallentscheidung),這些既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的個(gè)案裁判一并作為案例類型形成的素材。第二步,法律工作者對(duì)于如上所形成的豐富的案例進(jìn)行歸類整理,形成案例群(Fallgrupp),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概括條款的法教義學(xué)化,97即類型建構(gòu)(Typologie)。這也說明了類型建構(gòu)與個(gè)案裁判之間的關(guān)系:類型的形成不應(yīng)先于個(gè)案裁判,而應(yīng)從屬于個(gè)案裁判。個(gè)案裁判是類型形成的基礎(chǔ),隨著個(gè)案裁判所傳遞出的一個(gè)個(gè)“參考點(diǎn)”,類型逐漸通過體系化和普遍化而產(chǎn)生。
五、代結(jié)論:法學(xué)方法的新思維
伴隨著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我國的民法學(xué)必將開啟一個(gè)全面的解釋論時(shí)代,我國學(xué)者除了對(duì)于普通民法規(guī)范的解釋闡明之外,還必須一并關(guān)注民法典中概括條款適用的特殊性。對(duì)于概括條款的適用而言,無法像普通的規(guī)范一樣通過涵攝適用,此時(shí)法官必須依照案件的具體事實(shí)、社會(huì)情境,于個(gè)案中發(fā)展出概括條款適用的具體規(guī)范。如果說涵攝模式所體現(xiàn)的是形式法治的要求,則概括條款的適用模式所體現(xiàn)的就是實(shí)質(zhì)法治的要求,它無疑是一種以問題為導(dǎo)向的思考方式,筆者的初步分析就是嘗試在傳統(tǒng)的民法適用方法之外,關(guān)注法學(xué)關(guān)于法律適用方法的另一個(gè)面向,即在體系思考的民法典中,如何融入問題導(dǎo)向的思維方式。至少就民法概括條款具體化而言,應(yīng)當(dāng)在方法論上秉持開放立場,使之與傳統(tǒng)的法學(xué)方法協(xié)調(diào)適用,作為民法典與法理論之間的溝通管道,保持民法典的包容性與適應(yīng)性,實(shí)現(xiàn)法律規(guī)范的合法性適用以及個(gè)案正義的有機(jī)統(tǒng)一。在此意義上,這也可以被視為法學(xué)方法論發(fā)展的一次新的嘗試。
民法畢業(yè)論文范文模板(二):民法適用中的價(jià)值判斷論文
內(nèi)容提要:脫胎于法理學(xué)研究范疇的價(jià)值判斷問題,在民事實(shí)體法上同樣體現(xiàn)其理論意義和實(shí)踐價(jià)值。在民事法律適用層面,價(jià)值判斷不僅是衡量當(dāng)事人利益關(guān)系的工具,而且會(huì)對(duì)事實(shí)認(rèn)定的形成以及價(jià)值共識(shí)的尋求產(chǎn)生重要影響。文章所選取的對(duì)于“批評(píng)的尺度”的探討、“知假買假能否請(qǐng)求懲罰性賠償”的判斷、“夫妻共同債務(wù)清償規(guī)則”的分析以及對(duì)于“民刑交叉案件中價(jià)值共識(shí)的尋求”等問題的論述,都是佐證前述觀點(diǎn)的實(shí)例。
關(guān)鍵詞:民法方法論價(jià)值判斷知假買假夫妻共同債務(wù)民刑交叉
一、從法理(學(xué))開始
這是一個(gè)從法理學(xué)出發(fā)的部門法探索之旅。按照“法理學(xué)是法學(xué)的基礎(chǔ)理論或法學(xué)體系的基礎(chǔ)”的主流觀點(diǎn),法理學(xué)屬于法學(xué)知識(shí)體系的最髙層次,擔(dān)負(fù)著探討法的普遍原理和根本原理,為各個(gè)部門法學(xué)和法史學(xué)提供理論根據(jù)和思想指導(dǎo)的任務(wù)。1民法學(xué)的理論和實(shí)踐難題,也當(dāng)然應(yīng)當(dāng)從法理學(xué)當(dāng)中尋求答案和指引。雖說作為一個(gè)“搞民法的人”,我一直堅(jiān)持認(rèn)為民法根本就不僅僅是部門法和制度法意義上的。民法的理念和其中許多設(shè)計(jì),幾乎直接就是法哲學(xué)的研究課題;民法的轉(zhuǎn)變,也大致可以充當(dāng)整個(gè)法學(xué)發(fā)展的向?qū)А?然而作為部門法的民法,由于其太過務(wù)實(shí)的學(xué)科氣質(zhì),在公眾的認(rèn)知里總還是會(huì)被認(rèn)為是一門技藝型的學(xué)問,在解決具體糾紛的法律適用當(dāng)中,這種感覺尤為明顯,以至于當(dāng)現(xiàn)代科技足以令人工智能進(jìn)入社會(huì)生活時(shí),所謂“電腦判案”立即就在民事案件的裁判當(dāng)中引發(fā)無盡遐想。按照這樣一種理想主義所刻畫的未來,法官將會(huì)由一臺(tái)電腦勝任,這一端輸入事實(shí)證據(jù)和法律條文,那一端就會(huì)打印出司法判決。最終,司法裁判的過程變得像工業(yè)化生產(chǎn)一樣全部或大部分由機(jī)器來完成,機(jī)械化的生產(chǎn)將取代人工的操作和人腦的思考。如此科幻的場景在民事法部門中之所以被人津津樂道,與公眾對(duì)于民法的“非法理”屬性的認(rèn)知不無關(guān)系。
法律中的價(jià)值判斷之所以必要,源于其實(shí)質(zhì)理性品格。關(guān)于法律的實(shí)質(zhì)理性的提法,出自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劃分,按照韋伯的界定,實(shí)質(zhì)理性具有價(jià)值的性質(zhì),是關(guān)于不同價(jià)值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的判斷。與之相對(duì)的形式理性主要被歸結(jié)為手段和程序的可計(jì)算性,是一種客觀理性;實(shí)質(zhì)理性則基本上屬于目的和后果的價(jià)值,是一種主觀的合理性。就法律的制定和施行而言,形式理性體現(xiàn)為法律本身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而所謂實(shí)質(zhì)理性主要指立法者將其主觀認(rèn)定的社會(huì)公認(rèn)的實(shí)體價(jià)值固定于法律規(guī)范之中,并在司法當(dāng)中根據(jù)主觀的社會(huì)正義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來解決糾紛。5在以立法為終極目標(biāo)的時(shí)代里,民法理論的研究也始終繞不出立法的主題,這使學(xué)者們?cè)诿穹▽W(xué)的研究上更愿意以對(duì)策性的制度研究為重點(diǎn),而一些基礎(chǔ)理論的研究則往往受到忽視。另外,理論的發(fā)展也主要依靠立法任務(wù)的催生和拉動(dòng)。當(dāng)然,這種發(fā)展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時(shí)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然而,必須明確的一點(diǎn)在于,法學(xué)理論的作用固然在于為規(guī)范的生成奠定基礎(chǔ),為制度的構(gòu)建提供平臺(tái),為價(jià)值的遵循樹立指向,這是由法學(xué)的規(guī)范與價(jià)值屬性所決定的;但是,法學(xué)也不單單只是一門關(guān)涉理論的學(xué)問,法學(xué)還具有實(shí)踐性,其歸根結(jié)底是一門以解決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訴愿紛爭為目的的實(shí)用性學(xué)科。
二、三個(gè)追問
在談及民法中的法理,尤其是使用法理學(xué)的方法和技術(shù)去分析屬于實(shí)體法的民法問題時(shí),總難免追溯到一個(gè)終極性的提問:法學(xué)究竟是不是一門科學(xué)?以及,在司法論的視域下,如何看待裁判中出現(xiàn)的法律以外的判斷因素。
(一)法學(xué)究竟是不是一門科學(xué)9
“就現(xiàn)代人文社會(huì)學(xué)科而言,能否具有‘科學(xué)’的本質(zhì),已然成為該學(xué)科是否正當(dāng)化的標(biāo)志,若某一學(xué)科被貼以‘不科學(xué)’抑或‘偽科學(xué)’的標(biāo)簽,那么該學(xué)科也難以在學(xué)術(shù)圈之內(nèi)占據(jù)一席之地。”10然而,要把“科學(xué)”的內(nèi)涵說清楚,特別是回答一門學(xué)科何以成為科學(xué)的問題,又談何容易。若按照傳統(tǒng)的邏輯經(jīng)驗(yàn)主義的解說,科學(xué)必須具有可驗(yàn)證性,即能夠借助實(shí)證性的方法,為事物間的因果關(guān)系提供論證,同時(shí)為人們預(yù)測(cè)相關(guān)的社會(huì)現(xiàn)象提供準(zhǔn)則。德國著名法學(xué)家基爾希曼(JuliusVonKirchmann)即提出了“作為科學(xué)的法學(xué)的無價(jià)值性”這一命題,他在柏林法學(xué)會(huì)的演講中認(rèn)為:“法學(xué)盡管是一門科學(xué),卻不像其他科學(xué)那樣能夠并且應(yīng)當(dāng)對(duì)現(xiàn)實(shí)以及人們的生活產(chǎn)生影響;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法學(xué)作為‘科學(xué)’從理論上說是無價(jià)值的,它并非‘科學(xué)’,不符合‘科學(xué)’一詞的真正定義。”他進(jìn)而認(rèn)為,“法學(xué)系以偶在現(xiàn)象為研究對(duì)象,自身也難免淪為偶在,只要立法者修改三個(gè)字,所有的法學(xué)文獻(xiàn)便將因此變成一堆廢紙”。11基爾希曼對(duì)于法學(xué)的科學(xué)性的批評(píng)可謂一針見血,“在日常的法律語言習(xí)慣中,人們很少說法學(xué)是科學(xué),而是說法律信條學(xué)”。
(二)裁判能不能采用法律以外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20
這個(gè)話題肯定要從概念法學(xué)——更確切地說——從對(duì)于概念法學(xué)的批判說起。民事法律規(guī)范的適用,必須針對(duì)個(gè)案依價(jià)值判斷予以具體化。法律規(guī)則背后有其潛在的文化、理念和價(jià)值,亦有其鑲嵌于特定時(shí)空下的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的要求。作為法律文本的法條,當(dāng)其在法律適用的三段論演繹中出現(xiàn)時(shí),不過僅僅只是“法源”而已,真正作為大前提的是相互聯(lián)系的規(guī)范整體。法官在具體案件中依據(jù)的裁判規(guī)范,其實(shí)是結(jié)合自己的智識(shí)、前見、體系化法律思維以及客觀情勢(shì)而形成的綜合判斷。幾乎可以認(rèn)為,所有規(guī)范性的概念都是必須具體化或予以價(jià)值補(bǔ)充的概念,無論是立法抑或法律運(yùn)作,都不只是一個(gè)純?nèi)患夹g(shù)性的、僅靠形式理性化即能解決的問題。“貌似一種極富操作性的‘以事實(shí)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zhǔn)繩’的司法運(yùn)作,事實(shí)上亦體現(xiàn)著多向度的價(jià)值沖突、博弈和協(xié)調(diào)。”21
法官進(jìn)行法律續(xù)造的根本動(dòng)力在于,法官不僅要依法裁判以滿足合法性的要求,還要追求個(gè)案正義來為判決提供正當(dāng)化基礎(chǔ),依法裁判與個(gè)案正義兩個(gè)目標(biāo)之間并非每每和諧無礙,而是時(shí)常出現(xiàn)沖突。理論家們關(guān)心的問題遠(yuǎn)不止于判決是否有法律依據(jù),更讓他們感興趣的是,判決的法律依據(jù)能否經(jīng)得起道德哲學(xué)關(guān)于正當(dāng)性標(biāo)準(zhǔn)的檢驗(yàn),以及標(biāo)準(zhǔn)本身能否經(jīng)得起進(jìn)一步的追問。尤其是,當(dāng)不同判決方案所依據(jù)的正當(dāng)性標(biāo)準(zhǔn)發(fā)生沖突時(shí),又如何根據(jù)更高的正當(dāng)性標(biāo)準(zhǔn)來決定取舍。22
(三)究竟能不能對(duì)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判
我同意這樣一種說法,所謂“概念法學(xué)”也不過是一種標(biāo)簽,沒有人真正堅(jiān)持純粹的概念法學(xué)或“法條主義”,即使是德國概念法學(xué)派的代表性人物普赫塔(Puchta)也并沒有拒絕一切現(xiàn)實(shí)的思考。問題的實(shí)質(zhì)其實(shí)在于對(duì)待法律、法官的裁判能力以及自由裁判權(quán)的態(tài)度:是否相信立法者會(huì)制定出符合法律原本精神的規(guī)則;是否相信法官會(huì)在一般理性的支配下做出公正的裁量。26法官與立法者一樣,都必須去界定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相對(duì)立相沖突的利益,但不同的是,法官必須受到制定法中所包含的價(jià)值判斷的拘束。27在“法官受制定法拘束”這個(gè)原則下,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問題就在于:法官應(yīng)該以何種方式正確地探知制定法的價(jià)值判斷。28
三、作為方法論的價(jià)值判斷
“法學(xué)兼具理論的認(rèn)識(shí)及實(shí)踐的價(jià)值判斷兩方面的因素,系一種具有實(shí)踐性質(zhì)的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故如何正確地解釋法律,不僅系理論認(rèn)識(shí)的問題,亦為一種實(shí)踐的活動(dòng)。”31在方法論層面,當(dāng)我們討論價(jià)值判斷問題時(shí),主要有以下幾個(gè)核心論點(diǎn)。
第一,尋求價(jià)值共識(shí)。從法理上看,民法適用的根本依據(jù),來自正義以及社會(huì)價(jià)值的共識(shí)。毋庸諱言,法官對(duì)法律規(guī)范和案件事實(shí)的理解當(dāng)中不可避免地會(huì)夾雜法官的個(gè)人成見。正如拉倫茨所指出的,法律之所以是制度,主要是它的安定性和普遍性。所以,在具體的民事裁判中追求個(gè)案特別的具體的公正的意圖,對(duì)人類的實(shí)踐活動(dòng)而言,不僅是極沒有效率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不可能的。與此相對(duì),法規(guī)范的普遍性,是我們不得不采用的規(guī)范模式。因此,現(xiàn)代法學(xué)研究的主題不在于其他,而就在于法學(xué)方法論的研究,從而去尋找使價(jià)值判斷客觀化的方法,以保證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安定性在契合時(shí)代主題的前提下得以客觀地實(shí)踐。32
第二,法典的體系效應(yīng)。盡管價(jià)值判斷、利益衡量是司法中非常重要的一種方法,然而并非在每個(gè)案件中都須使用價(jià)值判斷和利益衡量來解決問題。這是因?yàn)椋⒎ㄕ咴诹⒎ㄟ^程中已經(jīng)先行做了一部分利益衡量工作。可以說,法律上的利益,并不是社會(huì)生活中利益的全部,它是以法定形式存在的利益,因此只有合法利益或權(quán)益才是法官在司法判斷中需要關(guān)注的利益。“立法作為利益沖突調(diào)整的最為重要的工具,必須置于特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或者法律關(guān)系的環(huán)境之中。法律是以國家的名義出現(xiàn)并要求全體社會(huì)成員普遍遵守的一種行為準(zhǔn)則,它為人們追逐利益的行為提供了一系列的評(píng)價(jià)規(guī)范,努力為各種利益評(píng)價(jià)問題提供答案。”33如果對(duì)特定的利益沖突已有法律規(guī)定,立法者已作出取舍,司法者就不應(yīng)也不能隨意利用自有裁量權(quán)進(jìn)行利益判斷和利益衡量;換言之,司法者必須尊重立法者體現(xiàn)在實(shí)定法中的價(jià)值取向。34
當(dāng)然,這也就對(duì)法典編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法典不僅需要為裁判機(jī)關(guān)妥善處理民事糾紛提供規(guī)范支撐,更要讓裁判者在面對(duì)那些無法通過法律解釋、類推適用和法學(xué)通說來處理的價(jià)值判斷問題時(shí),能夠在法典中找得到立法者的結(jié)論。35
第三,以一般條款作為價(jià)值傳遞的路徑。為了減少抽象概括式立法的缺點(diǎn),立法者在法典中規(guī)定了一些“一般條款”,一般條款在私法中大多是以法律原則的形式出現(xiàn),如誠實(shí)信用、禁止權(quán)利濫用等。這些條款具有指令的特點(diǎn),屬于判斷標(biāo)準(zhǔn),其外延應(yīng)是開放的,本質(zhì)上是賦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權(quán),為個(gè)案的裁判指引方向。36
成文法中廣泛使用的一般條款往往包含直接的價(jià)值判斷因素。以憲法和民法關(guān)系為例,憲法所確定的基本權(quán)利對(duì)民法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民事立法的方式使基本價(jià)值體系在民法規(guī)范中得到反映。憲法作為民法典的效力基礎(chǔ),兩者的關(guān)系主要在于基本權(quán)利,即通過民法典來具體化或者實(shí)踐憲法上的基本權(quán)利。37但是由于立法本身的局限性,仍然可能出現(xiàn)民法對(duì)基本價(jià)值體系貫徹不徹底的情形,此時(shí),基本權(quán)利對(duì)第三人產(chǎn)生效力主要是通過法官對(duì)民法一般條款(基本原則)的解釋將基本權(quán)利這一客觀價(jià)值秩序注入民法體系。
價(jià)值判斷是無處不在的。當(dāng)面對(duì)具體案件時(shí),依照前述價(jià)值判斷方法的核心要點(diǎn),價(jià)值判斷的形成與適用大致遵循以下路徑:首先應(yīng)明定所處理的問題的本質(zhì),即明確對(duì)待當(dāng)事人雙方的糾紛時(shí),裁判者緣何會(huì)在此利益與彼利益之間糾結(jié)往復(fù);其次,厘清案涉糾紛所糾葛的利益關(guān)系并作出價(jià)值判斷,這樣做同時(shí)也是為了使問題的討論能夠遵循一以貫之的價(jià)值徑路,從而增強(qiáng)論證的說服力;再次,結(jié)合價(jià)值判斷的結(jié)論對(duì)法教義學(xué)上的各種判斷方法做出選擇;最后,基于前述論斷得出能夠平衡各種利益的裁判模式。
四、四個(gè)標(biāo)本
實(shí)體法當(dāng)中的法理從來不會(huì)僅僅停留于高堂講章的敘述,我接下來更愿意通過實(shí)例而不是抽象理論來顯示:在處理具體的司法案件時(shí),基本的價(jià)值判斷如何形成;價(jià)值判斷在裁判中如何具體適用;(甚至試圖表明)必要的價(jià)值判斷對(duì)于“客觀的”案件事實(shí)的形成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以及,不同部門法之間價(jià)值判斷的交匯和干擾對(duì)于裁判思維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