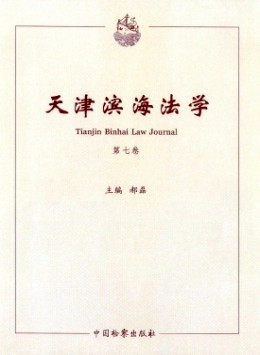民法典的由來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民法典的由來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關鍵詞:財產權 民法典總則 無形財產 人身權
引 言
自法典化運動以來,權利是民法無可爭辯的核心概念。沒有這個概念,將會引起很多困難,對此人們的意見是一致的。[①]在以形式理性和體系建構為特征的近現代民法中,民事權利和法律行為成為民法最基本的工具,若缺少其中之一,傳統民法體系便很難建立。事實上,各國民法典無不以權利為線索來進行體系建構,自羅馬法以來的物權和債權二分法在近現代各國的民法典中發揮了中樞作用,這種權利立法結構至今仍牢如磬石。在權利思維模式下,民事法律關系的興變無疑也是以權利的擴展為標志的,如隨著社會的發展,諸如知識產權和人格權等權利的出現,使民法的觸覺進一步深入現實生活,此一現象仍日益激增。在此過程中,關于民事權利的分析和描述成為人們了解和研究新的民法領域的鑰匙。但由于權利是法律的創造物,因此在法律上必須對權利作出詳細的規定,以獲得正當的定證法基礎。其原因在于,“雖然人們存在著實定法之外的權利,亦即這些權利并不取決于人類的規范活動,但是權利的具體內容卻總是由實定法確定的。”[②]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采傳統潘德克頓式立法模式國家的民法總則中,僅在權利的行使和保護的相關規定中涉及到權利,除此之外,我們很難在民法典總則中找到關于民事權利的一般界定,至于有關權利的形態和權利沖突解決的相關規定更是付之闕如。[③]通行的做法是,民法總則不規定各種具體的民事權利,而是將其放入各編中予以規定(如物權法規定物權關系,債權法規定債權關系等)。這樣的立法編排模式導致大量新型民事權利缺少與民法典連接的紐帶,不得不以單行法的形式游蕩在民法典周圍。單行法與民法典之間、民法和商法之間以及民法典內部的權利制度之間缺少一個整合的空間和過渡地帶,物權和債權的頑固性擋住了其他民事權利進入民法典的路徑。
上述現象使人們產生了疑惑,民法總則為何對權利的規定力盡微薄?民事權利在技術上的整合是否可行,其限度在哪里?關于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結構,目前學界已有充分的討論。權利體系問題與日前流行的人法與物法的爭論、以及民法和商法合一原則如何體現等重大理論問題密切相關。基于此,作者擬對傳統民法總則和權利體系進行一番審視和檢討,試提出在我國未來民法典中設立財產權總則編的建議,并闡述其理由和基本構想,以供同仁商榷。
一、 權利一般規范在民法典總則編的地位及其解釋
(一)民法總則中權利一般規定的缺失及其后果
民法總則立法模式肇始于德國的撒克遜民法典,是近代潘德克頓法學的產物。[④]總體來說,民法總則是法學家們基于概念法學的需要,為了得到普遍的、基本的原則和規則,利用非常抽象的推理方法得到的結果。相應地,民法典在結構上遵從先一般后特殊的原則,形成了總則、編、章、節的層次結構,從概念法學“提取公因式”這一特點出發,民法總則必然是概念層次結構的最終一環。依據這種邏輯體系,民法總則包含的是被提取和抽象的一般內容,并且體現為可適用于各編的規則。基于德國民法總則的“優越性”,其后許多國家的民事立法借鑒了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俄羅斯等國家都相繼采納。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民法典草案起草中,也是以德國民法典為藍本進行設計的,所涉及的問題也主要圍繞德國民法典的相關內容而展開。
盡管如此,民法總則設定的價值還是一直為學者所懷疑。[⑤]在此我們不從法律技術和法律適用上去探討,僅從內容上進行剖析。基于法律調整的是現實生活關系,民法總則的統領性也應著眼于法律關系,亦即真正的總則是對法律關系的各項要素進行最大限度的抽象,從而獲得普適效果。只有這樣,當新的民事關系出現以后,通過民法總則就能順利地進入民法典的調整領域。事實上,從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進行分析,它大致也是以法律關系為線索設計的,如法律關系的主體、內容、客體和變動等幾個必備要素,在總則中體現為人、物和法律行為制度,只是法律關系中最重要的民事權利制度卻付之闕如,其他各國的民法總則亦然。僅此一條,民法總則的統領性便令人懷疑。除此之外,人法、、物等制度均似民法的具體制度,并非“提取公因式”的產物,很難說有足夠的統領性,只有法律行為制度當之無愧地成為總則的內容,而成為民法總則的核心制度。[⑥]
權利內容的缺失影響了整個民法體系的統一性和完整性,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法各編與總則多有脫節。民法典主要是以權利為線索展開的,在此基礎上形成物法、債法和人身法等。但我們卻無法在總則里找到物權、債權和人身權對應的權利抽象物,總則與各部分之間沒有真切的聯系,使人產生民法總則僅為規定民事權利以外的法律規則這一感覺。
2、新型民事權利和民事關系很難通過總則進入民法典的領域。如知識產權制度、商事財產權制度只能在民法典之外以單行法的形式游弋;同樣,人格權制度的安排之所以爭論激烈,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總則對此沒有留下空間。在此前提下,甚至知識產權法和商法為民法的特別法這一說法都缺少有力的實體法依據。
3、沒有民事權利的抽象,財產關系法和人身關系法在民法典里無法整合。值得注意的是,總則的絕大多數內容并不適用于人格權法、家庭法和繼承法等人身關系法,我們只能從民法總則中嗅到濃厚的財產法的味道。因此,民法總則是否涵蓋了人身關系,值得探討。在體系上欲解決此一問題,必須在財產法和人身法上進行區分。
4、民法典對于財產權定位的缺失,使學界在新型財產權利的理解和設計上,往往陷入新型權利是“物權”抑或“債權”這一思維慣性的泥淖。以物權和債權來衡量新型財產權是民法理論的一貫作法,權利的“性質之爭”一直是中外法典化國家的通病。
上述四個方面的困境足以使我們對民法總則的內容產生困惑。民法是否存在一個真正完整的、邏輯意義上的總則?就目前各國民法典現狀來看,不采總則的占多數,包括修改過的荷蘭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也未采總則模式。有學者認為,民法總則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總則,分則中的許多內容并沒有能在總則中得到體現。反之,總則的內容也不能一以貫之地適用于分則。[⑦]如就人法而言,我們并不能從其中獲得一種適用于所有民事關系的人的形象,傳統民法的人的形象的設計是否完全適用于親屬法、人格權法甚至商法,存有疑問。如德國學者(Diter Medicus)梅迪庫斯認為:“民法典的人法部分僅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人們幾乎不可能從這些規定中推斷出一般性的結論。毋寧說,要研究這些規定,還必須考察我國法律制度中其他具有人法內容的領域,特別是《基本法》的基本權利部分、著作權法和商法。”[⑧]就物的規定而言,不難發現,“物”僅是民事法律關系客體的一部分,只是物權的客體,不能充當整個民事關系的客體。事實上,單獨就“物”作為客體進行規定在價值上、技術上也是值得推敲的,因為在法律上對物的規定與對物的歸屬的界定是同步的,與法律權利和義務相脫離談客體并沒有實際意義,民法總則中有關“物”的規定實際上全然屬于物權法的范疇。至于民法總則的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這種情況,這容易使人產生民法總則是融合抽象制度和具體制度的大雜燴這一感覺。另外,民事權利內容的缺失,使民法里常有的民事權利的界限、民事權利沖突的解決這些重要問題就缺少一個基本規則,而在民事權利日益受到限制以及權利沖突日益頻繁的今天,這一點尤為重要。應該認為,在民法總則中“法律行為”制度是最有價值的部分,人們對民法總則的肯定和溢美之辭也主要集中于此。
(二)傳統民法總則權利制度缺失的解釋
對于傳統民法總則的全面評價可能超出了作者的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事關系內容的缺失對總則的統領性構成了根本沖擊,民法總則在結構體系上并不全然是運用“幾何學方法”采取“提取公因式”途徑而得出的產物,其中多為相對獨立的民法制度規范,與其后各編中的具體法律規范之間并無統領和指導的關系。下面我們嘗試找出傳統民法總則結構形成的歷史因素。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當時德國人基于潘德克頓法學方法,對羅馬法進行創制的途徑和目標是建立徹底的、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的民法典。在此前提下,真正理想的結果是,民法典為運用法律邏輯對生活事實進行完全加工和制作的產物,歷史上基于生活事實而逐步發育的傳統法律體系將被摒棄。相應地,民法總則將成為人的總則、權利總則、行為總則、民事責任總則和人身關系總則的匯聚,民法具體制度則為人法、權利法、行為法、責任法和人身法等,這些內容對于有機的生活關系具有相當的普適意義。但可以發現,立法者并沒有采取這一理想的模式,而僅是對傳統民法體系進行適當的邏輯改造,即在保留物法和債法完整性的前提下,民法總則只是容納了物法和債法以外的其他規范。也就是說,除了法律行為制度外,德國民法上的人法、、物、時效等制度都主要是沿襲了傳統民法,只是以一般性規范的外在形式包容于總則之中。由于物法和債法則被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因此總則并不能直接對其有所指涉。
考察原因,不能忽視歷史傳統因素。首先從德國民法典制訂時的情形看,自古羅馬法至法國民法典,民法所調整的核心內容是一致的,即民法是以民事權利為中心的法律,民法典必須以權利為線索來構建,關于這一點理論上幾乎沒有爭議。基于羅馬法的核心制度表現為相對完整的物權和債權制度,并已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制度預設,德國立法者似乎很難拆解這一堅固的規范群體,無法對于物權和債權既定體系進行有效的抽象和改造,也無法在總則中進行規范。也就是說,無論設立總則與否,物權和債權仍是民法典體系的主干,總則是不能對此有所關涉的。因此,民法總則能夠包容的只能是游離在物法和債法之外的人法和行為法等制度了。
以法國民法典為參照進行分析也可獲得有益的結論。回顧德國歷史上有名的法典化大爭論可知,以蒂堡為代表的法學家曾一度想制訂與法國民法典相似的法典,只是薩維尼以立法技術不足為由阻擋了這一進程,薩維尼所說的立法技術其實就是概念體系,他并不完全反對制訂法典,只是認為缺乏嚴密的概念體系,法典不可能建立。因此,他回到古羅馬法,竭力找出適用于所有社會關系的概念體系,后經學者如溫德夏特等的發展,形成了概念法學。在此基礎上,后來的立法參與者開始嘗試以概念工具對古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予以改造。但顯然,前面述及的徹底的邏輯改造模式也許超出了德國學者的心理承受力,因為他們的概念源自羅馬法,所以自然不能背叛羅馬法的基本體系,不然自已所運用的概念的正當性將受到質疑。因而立法者在技術上適時地采取了第二種策略,即以概念法學為工具,對法國民法典進行了一番體系化和概念化的改造。但同時一個結構性的矛盾開始顯現:依潘德克頓理論體系,最終必然要有一個總則處于金字塔的頂端,以統領民法典其余各編,而依傳統羅馬法體系,物法和債法這一權利體系已經固定,學者對權利的抽象和物權、債權一般規則的創設受到極大限制。最終立法者通過將人法、物、行為、和時效等內容納入民法總則,完成了潘德克頓學派的使命。[⑨]
從理論基礎看,羅馬法固有的人法和物法結構也給德國民法典打上了烙印,這在民法總則規制的“人—物—行為”結構上表現得至為明顯。在羅馬法中,人法和物法是民法的主干,但羅馬人并不是從權利角度去理解財產,而是從物的角度來拓展,這從羅馬人將用益物權和債權都看作無形物這一規定上可見一斑。法國民法典仍沿襲了這一觀念,整個民法典也可描述為“人—財產”這一結構,其中財產仍是從物的角度去定義的,如債權、用益物權和其他財產權仍被定位為“無形物”。可見,物不僅充當了客體,在近代民法上對物的界定也一直充當著“權利界定”的角色。[⑩]德國民法典也不例外,盡管在理論上意識到民事權利與物是不同的概念,在總則第90條對物的界定中,將“物”限定為“有體物”,意識到了權利與物的區別,但羅馬法“人—物”結構仍未有突破,只不過在此基礎上創設了行為制度,而將法律關系意義上的權利和財產一定程度上仍置之度外。
綜上所述,民法總則中權利制度的缺失是具有其歷史原因的。自羅馬法以來關于財產的“物化思維模式”已根深蒂固,猶如頑固的堡壘,即使潘德克頓學說也無法拆解。與此相對應,物與財產的血緣聯系阻礙了無形財產的擴展,限制了民法科學權利體系的建立,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動、靈活的以行為為紐帶的生活關系世界。
二、設置民法財產權總則的基本理由
權利制度的缺失對我國目前民法典的體系設計提出了挑戰。但可否在立法技術上對所有民事權利作一有價值的抽象,將之歸于總則,以達到體系的統一?答案是否定的。民事權利本來就是法律關系類型化的產物,種類繁復,相互之間形態迥異(如物權、債權、人格權、身份權、無形財產權等),很難找到相通點。也就是說,權利本來就是關系概念,是法律關系的本體和實質,對權利的描述無異于揭示整個市民成員的生活。如基于權利形態的不同,民法自羅馬法以來發育出了涇渭分明的物法和債法;基于授予權利的社會關系基礎的不同,民法又形成了世人公認的財產法和人身法的分野;基于財產權配置和交易的市場化程度的不同,民法又形成了普通民法和作為特別民法的商法的格局。上述權利關系復雜的程度與民事關系的復雜程度是一致的,在民法總則中任何欲對權利進行本質的抽象無異于僅給民事權利下一定義,操作上的困難和抽象結果的價值不言自明。在這一問題上,總則和權利法律關系出現了兩難:如果制定一些非常一般的規則,那么一般規則的普適性必然受到限制,總則對具體關系的指導作用就很難實現,反之,如果對相對具體的關系進行次一級的較高程度的抽象,那么總則又會有許多例外。人們也許從權利一般制度的困境中,可以最好地理解民法總則是否真正能夠勝任統領民法的任務。[11]
這樣一來,《德國民法典》總則中民事權利制度的缺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立法上欲通過一般權利規范的界定來統領所有民事關系并不是理想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于權利關系的整合是不必要的,如果置當代民事權利的擴展于不顧,民法典不僅自身無法完整調整各類民事關系,而且是否可以統領特別法也令人懷疑。應當明確的是,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間,并非只是兩者選其一,非此即彼,在法典萬能主義和幾何學公式式的方法被打破以后,民事權利的適度整合是民法典在當代的發展要求,這種適度整合是法律碎裂化和法典功能保持兩者之間的緩沖地帶。關于適度整合對于未來民法典的重大意義在此不談,但對于法典中的權利關系問題,我們認為,設立財產權總則是適度整合的可行方案,對于民法典的體系化和發揮民法典制度的最大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下面擬從兩個方面提示財產權總則設立的必要性。
我們所稱的財產權總則主要是基于下列參照系,而構成財產權總則設計的基本理由。
(一)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的結構性分野
目前,關于民法的調整對象為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這一結論已為世界性的學術通說。但是迄今為止,在民法典結構上,卻很少看出這種區分的份量。物權制度和債權制度成為民法象征性的核心內容,而人身法卻大多蜷縮在民法典的最后部分或人法的云隙之間,甚至有時立法上將家庭法和親屬法的相關部分單行立法,不納入民法典。即便如此,這種分離的立法模式并沒能使人懷疑民法典的完整性。但是學者卻不能想象,如果現代民法缺乏法人制度、物權制度或者債的制度,民法典將會出現何種狀況。這似乎揭示出,自德國民法典以來,傳統民法的人法、物法和債法,具有內生的同質性,是在同一語境下對同一類社會現象的概括,從而形成一套穩固的、以邏輯為紐帶的規范群。[12]顯然,這種規范群體現的是一種財產邏輯關系,而非人身邏輯關系。可以認為,構成民法主體結構的概念體系,在近代實際上是以財產法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相反,概念法學所創立的概念系統對人身關系并沒有引起相同的重視。然而在學說上,學者卻大多傾向于將財產法的一套概念體系同樣用來套用于人身關系,以致顯得疑慮重重。簡言之,在社會關系多層化、復雜化的今天,能夠構成“民法”這一詞的特殊內涵仍是以財產法規則系統為標志的,如果缺少財產法上的人、行為和權利這一套話語系統,當代民法便會被徹底解構。
值得注意的是,對羅馬法的直接繼承和借鑒,之中貫徹了近代市民社會所要求的人格平等、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但在人身關系上則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義的等級性人格制度和家庭制度。直到上個世紀二戰以后,隨著世界人權運動的興起,各國才逐步進行了人身法的改革。由此可見,民法上的人格一律平等原則實際上是對財產關系主體的抽象,這在各國民法典中是一致的,而在人身關系主體地位的規定上卻存在著相當多的差異,這是因為人身關系與一個民族的道德觀念、民族習慣、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它不是單純由經濟因素決定的。所以在德國民法典中,幾乎完全脫離了家庭法而設計民法總則,家庭法只得退居到一種獨立地位。應該說,財產權與人身權的人格基礎、權利形態和調整手段具有質的區別。基于此,財產權和人身權應是民事權利系統最基本的分類,對于財產法和人身法在體系上應有一個明確的區分,并在民法典上直接體現出來。但實際上,立法者可能基于人人平等這一原則,忽視了此兩部分的人格基礎和運行邏輯互為不同這一事實,所以沒有加以深究。另外,由于民法在其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家庭法一是民法的基本組成部分,所以在設計近代民法結構體系時,各國民法典并沒有刻意將其與財產法嚴格分開。
從權利體系而言,財產權和人身權成為民法權利系統的基本界限。梅迪庫斯認為,親屬法和繼承法規定了相互之間具有聯系的、類似的生活事實。而物法和債法規則體系則不是基于生活事實的相似性,而是法律后果層面上的相似性。[13]換句話說,人身法的社會倫理性與財產法的形式理性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在此前提下,財產權與人身權具有諸多本質差異:就權利形態而言,財產權表現為是一種行為模式和外在資源的分配方式,而人身權主要表現為一種人身利益的認定,這種認定不是以物質載體為基礎的;財產權對所有主體是同等的,而人身權則主要因人而異;財產權可以轉讓,而人身權具有專屬性。近代以來的民法其實圍繞財產關系已形成了一套獨立的主體、權利和責任體系,這種體系的各項制度是同質的,并在整體上與人身法相區別。所以,在設計民法典體系時,應首先正視這一事實,在體系設計上應有嶄新的思路。
(二)民商合一的體現:財產法體系的整合
近代以來,民法和商法關系之微妙,難以言說。雖然在理論和立法上有兩種主張,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但兩者均缺乏實質意義上的說服力。就民商合一而言,倡導者雖然能列舉出數條切當理由,但無法提出有效的途徑使商法和民法在規則上相通,在立法上商法事實上并不完全顧及民法原理和制度而自行運作。比如,證券和票據的規則在民法制度上就無從歸宿;又比如,關于股權的性質,在民法上也是無法推斷。如果說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那么即使在具體規則上無法體現,至少在總則中也應為其留下一定發展空間。在此情形下,民商合一只能成為一種理論和名義上的解說。就民商分立而言,倡導者也很難抽象出商法獨立于民法的基本理論體系。雖然各國商法學者不乏努力草擬商法總則者,但都收效甚微。細言之,一則是由于商法本身是由相互不大關聯的、獨立的法律所構成,本來就不易從規則上找出共同的總則;二則是由于商人和商行為的本質界定,似乎又是建立在民法中人格假定和法律行為假定之上。至于其他如商業登記和商業帳簿的規定,似乎又是操作規程,不構成總則的本質內容。因此,民商分立之說也是一個理論和名義上的解說。
第2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我國的民事立法隨著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等的陸續出臺,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即一部系統民法典的各構成部分的立法基礎工作即將告竣,在此之后2002年曾經提上議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的編纂工作有可能再次提上議程。但是,在這一立法進程中還存在若干障礙需要克服,除有關當代民法制定理念、法典化必要性、民法各構成部分的內在聯系以及外在結構特點等存在研究的必要外,還有許多有關民法的新發展問題更需要加以研究,進行決斷。其中之一就是人格權立法問題,即當下是否有必要就人格保護問題果斷超越有關傳統民法的禁止加害式的保護性立法模式,以正面確認、規定人格權模式甚至使之單獨成編的方式為基礎進行立法。換言之,對于人格保護,民法上究竟是采取人格權立法方式,還是仍然采取限于將其作為禁止加害客體而保護的立法方式?
對此,目前在我國民法學界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部分學者不贊成在民法上對人格權采取確認式立法,反對在民法上正面設置人格權制度,建議仍然像有關傳統民法那樣,以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形式,通過將人格法益作為禁止加害客體加以規定的方式來處理人格保護問題。[1]但是,多數民法學者主張我國當下應從人格權確認的角度進行人格保護立法。[2]他們認為,在民法上將人格權實證權利化并無障礙,因為人格權本身雖然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但并不妨礙從民法上加以確認。這也是我國自從1986年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以來理論界的主流態度。《民法通則》第5章“民事權利”第4節“人身權”明確地以確認或曰賦權的方式規定了若干具體人格權。不過,關于人格權立法是否應單獨成編,則又存在分歧。贊成對人格權進行確認式規定的學者中,一部分學者反對人格權單獨成編,認為應將人格權確認及其一般保護規定歸入民法總則編的自然人項下作為主體屬性加以規定。他們認為,人格權與民事主體的主體(人格)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自然人人格與人格權不可分離,因此人格權確認規則只能置于民法總則編中的“人法”之下,《瑞士民法典》于第1編第1章第1節規定“人格法”的做法即為例證;而且此種模式也體現了人格權相較其他民事權利而言更具優越性的立法價值。[3]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人格權制度既不能為主體制度所涵蓋,也不能為侵權行為法所替代,而應該單獨成編。[4]
以上觀點分歧,可概括為“法益保護說”(“禁止侵害說”)、“人格權確認說”和“人格權獨立成編說”。上述觀念紛爭的出現絕非偶然。這是因為,人格保護問題與民法其他問題相比,其與自然人倫理本體在價值上緊密結合或不可分離的特點,使得它在立法上有著極為明顯的獨特性,尤其是與物權或債權及其保護問題明顯不同。人格保護立法因為不得不從其具有倫理化特點的角度加以區別考量,所以顯示出一種倫理化立法的特點,也就不可避免地體現出極為觀念主義的一面。從世界民法立法歷史來看,人格保護問題從來就難以決然歸入裁判的范疇,總是因為涉及倫理觀念紛爭而不可避免地陷入難以調和的重大分歧之中。
我國當前的人格權立法何去何從?與其說是徹底走出以上觀念的紛爭,還不如說在有關觀念紛爭或立法分歧中依據人格保護的歷史經驗和當今情勢,通過觀念比較和當下政策思考,選擇一個貼近當下實際和合理要求的人格保護立法方案。說到底,這仍然不過只是一個暫時的非終局決斷。
筆者即是在這樣一種意識下對當下人格保護特點和合理要求進行政策思考,以期對人格權立法提供有益的建議。
二、人格權的立法方式:應否民法實證化
我國當前的人格權立法面臨著立法模式選擇的分歧,首先是對民法應否正面確認人格權的分歧。
歷史研究是分析的重要基礎,但也僅限于此。我國的人格權立法何去何從,一方面應該認真研究既往的民法歷史,了解民法歷史上關于人格保護的做法和思想觀念;另一方面,更應該根據當下我們民法的時代定位以及目的加以權衡。
顯然,羅馬法人格保護的法律形式并不可取。從阿奎利亞法到后期的優士丁尼法典,羅馬法對人格保護都不過體現了一種自然主義式的處理,體現著與原始法律思維一脈相承的粗糙性。古羅馬學者的論述顯示出,當時雖然亦偶爾有權利的提法,但他們并沒有對人格權做出任何原理性的思考。
近代民法典,特別是1804年《法國民法典》的人格保護模式也不可取。天賦人格論可以在《人權宣言》中宣示,卻由于它本身拒絕將人格的地位降低——民法實證化,因此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大難題,特別是在如何突破其形式而在更大范圍、更深遠的基礎上進行人格保護上造成了難以跨越的實證法障礙——在主張法治國以及存在民法典的前提下,法官怎么可以依據法律外的理由來任意擴展侵權法上的這些簡陋的人格保護法律形式的司法基礎和范圍呢?
但是,從1896年《德國民法典》一定程度上隱約開始、在1907年《瑞士民法典》等明確規定、由1991年《魁北克民法典》和1994年《法國民法典》修正等全面細化的人格權實證化規定的立法模式卻大為不同。這種模式作為歷史的發展呈現了對既有模式的進步和修正。這種發展和修正本身存在堅實的現實基礎,亦有倫理觀念的支持。詳言之:首先,它與當下人格保護的現實合理性要求相合。這些民法典對自然人人格權基礎的確立不是實證主義的邏輯貫徹,而是現實主義的應對抉擇,是解決現實人格保護迫切要求之所急。隨著人權觀念日益深入并成為普識價值,人格隨時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脅,人格保護問題越來越凸顯出敏感性和現實迫切性。人們因此強烈要求,民法在個人關系中必須一開始就從法律上明確人格的范圍和法律界限,而不是僅僅到了受到侵害時才通過侵權法予以消極保護。那種法益保護式的立法模式,遠遠不能滿足復雜社會對人格關系保護的需要,只有深入到權利確認的深度,才能緩解社會復雜性與人格覺醒意識之間的張力。由此,就像當年的物權和債權一樣,人格保護立法突然獲得了權利化的現實基礎。[5]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私人權利原本屬于“不需要向外公布的法律的體系”,因為“權利的一切命題——作為法律上的命題——都是先驗的命題,因為它們都是理性的實踐法則”。[6]但是,人們還是要制定民法包括像《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這樣龐大的民法典去廣泛宣示和確認那些私人權利,確立一個龐大的權利體系。這是因為,只有通過將這些私人權利民法化,那種文明社會秩序才能夠真正穩定而持久地存續,這些私人權利才能由應然變成實然。康德對于物權制度法律化的必要性看得非常清楚。他說:“要使外在物成為自己的,只有在法律的狀態中或文明的社會中,有了公共立法機關制定的法規才可能。”[7]物的關系是這樣,人格關系又何嘗不是也有穩定確立的要求呢?總之,圓滿的人格法律狀態不能只是間接的,而應該是將直接的確認和間接的保護統一在一起的。其次,這也是非常關鍵的,當代這些民法典關于人格權利化的確認或修正,并沒有忽視人格倫理化的特殊性,仍然重視人格倫理化的要求。為此,他們創造性地運用一種兼顧人格關系倫理特點的新型權利確認方式,即將人格權設計為一種受尊重權。人格權作為一種受尊重權而設計,既可以很好地體現人格自身的倫理化品位,不會導致人格物化或客體異化的規范后果,即作為一種受尊重關系而不是對人格的排他支配關系,體現了人格權是基于人格交往的倫理需要而不是對特定客體的控制要求而生;又能夠很好地預定和明確那些人格關系的界限,即它通過應受尊重和基于應受尊重而具有的排他效力以及由此推論出來的某些獨特保護機制的規定,盡可能為現實關系中人們如何尊重人格和相互交往劃定可預見的范圍。這些規定,由于其正面確認的形式特點,不僅可以成為人格保護的法律基礎,而且更重要的意義是為人格積極交往提供了充分的依據和有效的保護機制。
我國的人格權立法,是在當代社會更趨復雜化的背景下進行的,應該更為強烈地感受到個人人格覺醒和人格關系日益敏感對立的現實壓力。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在民法上當然應該有一番新的作為來適應現實關于人格交往和人格保護的新的時代要求,人格權實證化是一種不容拒絕的現實選擇。因此,在如此時過境遷的背景下,如果還繼續援引羅馬法的自然主義法例,或者亦步亦趨步近代法國觀念主義的后塵,[8]顯然已不合時宜。一言以蔽之,今日我國民法上人格權之實證化是一種法律現實的要求。
《民法通則》曾經以專節從權利確認的角度規定了若干種人格權,如生命健康、名譽、榮譽、姓名等人格權。雖然我們已經在司法實踐中感受到其對于人格關系的明確界定作用以及對于我們這個發展中社會的個人人格意識的促進價值,但遺憾的是,《民法通則》采取了具體化人格權列舉這一掛一漏萬的不周延做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隱私權、身體權等的缺漏。此外,法律對當今人格交往中極為頻繁但又極為特殊的一些復雜情形,如涉及醫療、生物活動等時的那些特殊人格關系尚未作出必要的規范回應,因而缺乏針對性。因此,我國下一步的人格權立法,應該是在更為全面但也更為關注人格交往特殊情形的意識下加以完善和展開。
三、人格權的確認方式和內容構成:受尊重權及其展開
1.人格權通過受尊重權加以確認
在民法上將人格權利化的難點在于人格特有的倫理化品格。由此,人們提出,人格或其要素本身不可權利客體化,因此也就無法成立實證化權利,否則會導致許多倫理困境,如人格物化、自殺正當化等。
德國法學家薩維尼就明確從缺乏客體基礎的角度,否定人格或其要素可以權利實證化。他說:“這種觀點的邏輯一致的發展會導致對于自殺權利的承認。”[9]在這種前見下,如果仍然堅持將人格權實證化,就不能不形成一些扭曲的觀點,如將人格視為與權利并行的一種“秩序”,形成“權利-秩序”二元論,或者將人格視為一種“利益”,形成“權利-利益”二元論。[10]但是,這些思想說到底是受一種固定化的權利構造思維所影響,這種構造思維來自物權。根據傳統的權利觀,權利在技術構造上一般以物權為典型,被理解為“主體-客體”關系模式。事實上,權利概念本身可以是開放的,未必要限于“主體-客體”模式。其實,早期在對物權(后來的物權)、對人權(后來的債權)的簡單區分中,人們就注意到,對人權權能所指向的“特定行為”因具有請求的特點而很難說是一種客體化了的事物。[11]至于后來通過權能分類的發展而出現的形成權則更與客體問題疏遠起來,成為一種單純的作用方式。
對于人格權的民法確認,重要的是為人格交往和人格保護提供一種與人格倫理化品質相當的實證形式。這樣,轉換以支配權為原型的權利觀就極為必要。于是,受尊重權的構造形式就成為一種恰當的選擇。德國民法學家拉倫茨如是說:“人身權不是支配權……人身權根據它的實質是一種受尊重的權利,一種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12]無論是1907年《瑞士民法典》還是1991年《魁北克民法典》和1994年《法國民法典》修正,都是從轉換權利觀的角度通過構造受尊重權的方式,[13]來正面確立人格權制度,以調整倫理化的人格交往關系。除外在人格權如姓名權之外,這些民法典無論是對一般人格權還是特殊人格權均是以這種受尊重權方式加以確認的。
人格權作為一種受尊重權,其規定方式通常如下:首先正面確立自然人享有何種人格受尊重的權利;然后規定其排除效力,具體可體現為若干并列或不同層次的禁止行為,如1994年《法國民法典》修正后之第16-1條。當然,立法也可以采取更簡潔的方式,直接規定何種人格不受侵犯,或者對何種人格造成侵害或損害的行為受到禁止,同時還可以一并將特殊保護方法加以規定。前者如《瑞士民法典》第28條之規定,后者如《意大利民法典》第5條之規定。
《民法通則》關于具體人格權的規定并沒有達到這種理論自覺的高度,往往是從宣稱“公民享有”某種特殊人格權入手,如第98條之規定。不過,在條文具體展開時,《民法通則》有關規定最后還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主體-客體”關系模式,從排除效力入手對禁止行為作了規定。
2.人格權立法的內容構成
民法以權利確認的方式規定人格權時應規定哪些內容呢?這與是否應確認人格權的問題是一體的,最終體現為由立法者期望達成的制度功能來決定,因此存在一個追求立法功能與確定制度形式范疇的相互配合關系。
具體而言,人格權的內容構成應從以下方面著手:(1)從目前的人格交往和人格保護基礎應具有開放性來看,應該有關于人格尊重的框架性規定,即確立關于人格受尊重或保護的一般規范,相當于確立“一般人格權”,同時規定人格權一般保護方法。[14]如此可避免掛一漏萬,有助于開放地指引司法實踐。(2)對人格交往實踐中已經特別化了的應當加以明確受尊重界限的那些內在人格權逐個規定。這些人格權既有涉及身體、生命、健康、自由、性自主(也可一并合稱為身體完整)等物質性人格權,也有涉及名譽、隱私、信用等精神性人格權。其規定方式均應體現為受尊重以及由此產生的排除效力的表述,如《魁北克民法典》第10條之規定。這些條文應該同時規定特別人格權的排除效力(禁止行為)和具體保護方法。(3)應該對人格實踐中的某些極為特殊或者關系極為復雜的情形作針對性的延伸、細化規定,特別是針對新時期高科技應用、復雜社會管理帶來的特殊人格關系問題給予詳盡規定,以滿足社會實踐之需求。例如,在涉及醫療、器官移植、人體捐贈、生物實驗、遺傳檢查和鑒別、代孕、機構監禁、精神評估等活動時對身體完整權的特殊性問題予以立法應對,借鑒《法國民法典》第16-3條至第16-13條、《魁北克民法典》第11條至第31條的規定。(4)應對死后人格保護特別是死后身體的尊重作出規定,如《法國民法典》第16-1條和《魁北克民法典》第42條至第49條。(5)應對那些外在人格權如姓名權、個人數據等加以規定。這些具體人格與人格本體有一定的分離空間,甚至有商品化價值,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客體化。(6)立法至少還應該對人格、自由等的禁止讓與、放棄、限制等做出原則性規定。
四、人格權的立法體例:是否單獨成編
對于人格權應否單獨成編,目前我國民法學界也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撇開那些從根本上反對人格權確認式立法的觀點不談,[15]贊成人格權通過立法加以確認的學者中,也有不少學者堅決反對人格權獨立成編。他們主張應遵循《瑞士民法典》、1994年《法國民法典》修正、《魁北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等,將人格權立法在體例上歸于民法總則編的“人法”項下。[16]但是,目前一種更具影響的觀點是,我國目前制定人格權應當采取獨立成編,并以此為我國未來民法典結構體例的特色之一。[17]
那么,如何看待關于人格權是否單獨成編的爭論呢?筆者認為,人格權獨立成編這個問題,與先前兩個問題即民法上應否將人格權利化以及人格權的確認方式相比較,并非什么實質性問題。毋庸置疑,從體系上看,將人格權確認規范放在民法總則編“人法”項下確實具有形式與實質貼近的直觀性。這是因為,人格權與人格本體的不可分離性,體現的是它們在倫理上的一致特性,這就導致它們在價值上的同質性。而且,將人格權與主體一同規定,可以更好地從體例形式上凸顯人格權的更高位階性。在這種意義上說,把人格權在內在邏輯上等同于物權、債權,并且認為不將人格權獨立成編便是“重物輕人”的觀點恰恰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人格權獨立成編畢竟只是一個形式化的問題,而形式本身的問題均可以通過形式自身來解決。形式與實質的貼近不一定只有直觀性這一種方式。如果立法者打算達成某種特殊體例功能,必要時也可以采取不那么直觀的形式,創制一種編章結構獨特的形式美學。因此,盡管人格權與人格本體實質相連,但如果立法者愿意將人格權獨立成編而且處理得當,不損及人格權與人格本體的實質關聯,特別是其在倫理上的同質性,那么也是可以接受的。
人格權雖然不妨獨立成編,但也應特別注意人格權權利化絕對不能被簡單理解和論證為法律科學邏輯的產物,人格權編不能簡單地在內在邏輯上與物權編、債務關系編同等化;否則,必定損及人格權制度應有的價值和功能,特別是那些內在于人格權的“與生俱有”的倫理意義。由此,假設一定要使人格權獨立成編,那么就至少應該注意以下兩點:(1)人格權編的位置不能距離民法總則編中的“人法”太遙遠,以至于隔斷了它們之間的獨特關聯,正確的位置應該是緊接在民法總則編之后;(2)應該設置“架接條款”,將民法總則編中的“人法”與人格權編連接起來,使得人格權規定雖然在形式上分離,但在價值位階上卻與民法總則編中的“人法”依舊同齊,在功能上仍然可視為民法總則編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看作與后面其他各編地位相似。必要時,立法還應宣示人及其人格權的首要地位,即可以像《法國民法典》1994年修正后的第16條那樣規定:“法律確保人的首要地位(La primaurite),禁止對人的尊嚴的任何侵犯,保證每一個人自生命開始即受到尊重”。
五、結論:審慎的實證主義
社會發展到今天,隨著個人人格意識覺醒和人格交往關系的日趨復雜以及人格保護的課題更顯嚴峻,當前的人格權立法,不僅需要走出羅馬法人格保護的自然主義歷史軌道,而且也有必要走出過度理念主義的虛空,實現“從倫理領域向法律領域的移植”。[18]
為此,立法者應在保持對人格權的倫理特質具有清醒認識的前提下在法律形式上憑借法律實證主義外殼對人格權進行確認式立法,甚至還可以嘗試建立一個更具實證確定性的體系,以滿足現實生活對人格交往和人格保護的明確而細致的規范要求。當然,我們也應該時刻注意,這種實證主義不應該是毫無顧忌的,而應該抱著一種審慎的態度,時時警醒自己不能遮蔽人格權問題的規范實質,即人格權具有“與生俱來”且“揮之不去”的倫理特質。
注釋:
[1][8]參見尹田:《論人格權的本質——兼評我國民法草案關于人格權的規定》,《法學研究》2003年第4期。
[2]參見龍衛球:《論自然人人格權及其當代進路——兼論憲法秩序與民法實證主義》,《清華法學》2002年第2期;王利明:《人格權制度在中國民法典中的地位》,《法學研究》2003年第2期;徐國棟:《人格權制度歷史沿革考》,《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1期。
[3]參見梁慧星:《民法典不應單獨設立人格權編》,《法制日報》2002年8月4日。
[4]參見曹險峰、田園:《人格權法與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年第2期。
[5]《魁北克民法典》和1994年修正之后的《法國民法典》等當代民法典進行細化規定的人格權是人身完整權。這是因為現代社會醫療、生物實驗、機構監禁、精神評估等這些新事物使得人身完整權問題變得十分復雜:一方面這些事物的發展體現了技術和社會進步的一面,對于人類福利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但另一方面,這些事物的發展也存在對于“人身完整性”的不合理危險。因此,我們需要進行這兩方面的具體平衡,其結果是產生了許多特別的調整界定人身完整關系的規則。
[6][7]參見[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53-59頁,第67頁。
[9][德]薩維尼:《當代羅馬法體系I》,朱虎譯,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頁。薩維尼的這種思想應該是受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相關論述的影響。
[10]參見王晨、其木提:《21世紀人格權法的立法模式》,載渠濤主編:《中日民商法研究》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頁。
[11][12][18]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380頁,第379頁,第47頁。
[13]在日本法學界也存在類似主張。參見王晨、其木提:《21世紀人格權法的立法模式》,載渠濤主編:《中日民商法研究》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頁。
[14]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梁慧星研究員主持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第1編“總則”第2章“自然人”第5節對自然人的人格權進行了專門規定,共11個條文。筆者認為,該建議稿第46條的規定過于瑣碎,不如直接改為“自然人的人格應受尊重”。
[15]這些學者連對人格權確認立法都持否定態度,當然就更無從談起人格權獨立成編了。參見尹田:《論人格權獨立成編的理論漏洞》,《法學雜志》2007年第5期。
第3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關鍵詞】 誠實信用 道德規范 反思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在法律領域的適用范圍日益擴張,已由最初債務人履行債務的原則,逐漸確立為私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我國,學者對該原則的研究由來已久,將該原則作為《民法通則》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我國的立法中得到體現。“誠實信用”作為規范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道德規范,成為成文法國家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不僅從立法技術上成功地克服了成文法的局限,而且極大地推動了司法實踐走向真正的公平和正義。
一、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
我國古代典籍里出現過“誠信”一詞,其意義主要是一種道德規范,是對人的內心規制,而由于中國古代社會沒有民事法律,所以也就沒有誠實信用原則。法律意義上的“誠實信用原則”來源于西方,作為專門的法律術語,從現有的法律文獻來看,最初起源于羅馬法中的“一般惡意抗辯訴權”。它是指法官在裁判案件時,尋找當事人真意,以做出合理判斷的方法。法官從公平正義的理念出發解釋、補充當事人之間的合同內容,按交易習慣或一般人的觀念來增減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誠實信用雖說是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形成的道德規則,但在被立法者規定為民法典的一個法律條文之后,已經不再是單純的道德規則,而是一項法律規范。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
首先,就其宗旨而言,它是為了維持某種秩序,這種秩序或體現為一定的利益平衡性,或體現為一定的道德基礎性;其次,就其內容而言,它是以公平要求為內容規范的;再次,就其外延而言,它具有不確定性,可以補救法律漏洞;最后,就司法而言,它賦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權,允許法官在誠信原則的指導下進行創造性的司法活動。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歷史變革
在誠信原則的歷史發展中,誠實信用經過了從民法的補充規定到僅調整債權法律關系再到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過程。具體說,經歷了羅馬法―近代民法―現代民法三個階段。
1、羅馬法階段
誠實信用原則最早起源于羅馬法中的誠信契約和誠信訴訟。在羅馬法文獻中大量存在著“誠信”字樣,就誠信觀念興起的社會背景而言,古羅馬帝國的對外擴張使得古羅馬必須注重處理羅馬人與異邦人的關系,而羅馬帝國商品經濟的繁榮帶來合同法律關系的發展,基于信義而產生的誠實信用遂成為一種基本的社會道德規范。但是,他們發現無論多么周密的法律條款和合同,如果當事人心存惡意,總能找到規避之法,這就顯露出了羅馬法追求法律的絕對確定性而否定司法活動能動性的弊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羅馬法萌發了“誠信契約”和“誠信訴訟”。
這個時期的羅馬法規定的誠實信用原則并不十分清晰和完整,而且僅被限制在債權法領域內。在羅馬法中誠實信用還只是對某一類特定范圍內的契約在內容上的要求和對承審員就某一類特定范圍內的契約在內容上的要求,以及對承審員就某一類特殊的訴訟授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并未將誠實信用上升到具有普遍適用意義的基本原則的地位。盡管如此,它已具備了現代民法中誠實信用原則的兩個基本內容―“誠信要求”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在人類法制史上還是第一次。
2、近代民法階段
從歐洲近代史上法典編纂運動到德國民法典制定,為誠實信用原則發展的近代民法階段。誠實信用原則在這一階段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被剝奪殆盡,法官無論遇到多么復雜的情況,都能在龐大的法典中像查字典一樣找到現成的解決方案。沒有法官的自由裁量,誠實信用原則僅能對債權領域內的民事活動具有指導意義。誠信原則在近代立法中被定位為履行債務的原則,而且只要求債務人單方遵守,對債權人以及債權人以外的民事權利的行使并無約束力。盡管如此,誠實信用原則畢竟是法律公平公正的象征,立法者不能不尊重誠實信用原則所包含的價值取向,所以這一時期的成文法大都明文規定了誠實信用條款。
3、現代民法階段
二十世紀社會經濟飛速發展,新的經濟關系不斷產生。缺乏彈性的各國民事法律越來越難以適應經濟的飛速變化。經濟基礎的發展推動了法律的變革,于是立法開始采取嚴格規則和自由裁量相結合的新方式。
從瑞士民法典的制定(1907年)至今的時期是誠實信用原則所經歷的現代民法時期。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第2條中做出了如下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這一規定第一次在立法中將誠實信用原則提升到民法基本原則的高度,從而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
在這一時期,誠實信用原則回復到誠信要求和自由裁量權的統一。《瑞士民法典》中誠信原則的規定,作為一種能滿足現代社會需要的立法方式為大陸法系各國所仿效。至此,誠實信用原則完成了從道德規范到君臨民商法全法領域的“帝王條款”的轉變。
三、誠實信用原則的功能
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基本原則之一,其內容豐富抽象,但從一定意義上說,該原則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實際所包含的難以把握的規范性內容,而在于其功能。在現代民法時期,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法律解釋或理念的一種體現,不僅在司立法領域意義重大,在司法領域中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誠實信用原則具有誠信指導和衡平權授予的雙重功能,它打破了立法和司法兩權之間的僵硬劃分。具體而言,該原則的功能主要有三個方面。
1、指導當事人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功能
要求當事人在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時應兼顧對方當事人和社會的利益,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具體來說,在當事人雙方之間的利益關系中,誠信原則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對待自己事務之注意對待他人事務,保證雙方均能得到應得之利益,不損人利己;在當事人與社會的利益關系中,誠信原則要求當事人不得通過自己的活動損害第三人和社會利益,必須以符合其社會經濟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
2、彌補法律漏洞的功能
無論是司法還是法學研究,首先要尊重立法,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規則時都力求完善,以期能涵蓋社會所存在的一切法律問題。但是,“或因立法者的認識有限或思慮不周,或因情勢變更或立法技術和手段的局限,法律總是存在漏洞”。對于法無明文規定的案件,司法者可以根據民法基本原則特別是誠信原則來進行處理;同樣,對于守法者來說,當法律缺乏對某一事項的具體規定時,也應該把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個人的行為準則。
3、限制權利濫用,維護公序良俗的功能
誠信原則能兼用法律和道德手段限制權利人以迂回的方式規避法律來擴張自己的權利,同時使一些違反取締性規定、倫理道德以及正義觀念的行為得到限制,從而維護了社會的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公序良俗被視為誠實信用原則的一部分,因此,堅持誠信即維護了公序良俗。
四、誠實信用原則的現實反思
1、關于誠信原則與嚴格規則主義的矛盾
誠信原則具有內涵的模糊性和外延的不確定性,這就給法官留下了自由裁量的權利空間,官根據自己的判斷和社會生活的一般價值處理案件,法典化的要求則是法官嚴格依照法律行事,不得超越法律。這樣以來,造成的事實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與法律的嚴格規則主義相沖突。依法行事,則可能違背正義;依據誠信原則,又與法律相沖突。
2、關于誠信原則與經濟人假說的矛盾
現代民法是建立在一種基本的法律人格假說―經濟人假說―的基礎之上。此種法律人格乃是根植于啟蒙時代、盡可能的自由且平等、既理性又利己的抽象的個人,是兼容市民及商人的感受力的經濟人。經濟人的準則是“愛你自己,兼愛他人”,允許當事人最大化的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誠信原則的要求是“愛你的鄰人”或善待陌生人。這就造成了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違反了法治原則。
3、誠信原則強調義務與民法中權利的沖突
民法始終是以保護權利為己任,在任何時期民法都強調對私權的充分保護,民法的中心問題就是民事權利問題。龍衛球先生所著的《民法總論》在闡釋權利的概念時指出:“民法確認社會每個成員均以擁有一定范圍自身利益為法律生活的出發點,并將這種利益量化為一個人人享有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這就是權利。民法是權利法,它通過將個人利益單元化,創立了‘權利’這一法律細胞,并以權利本位予以貫徹。”民法的一切制度都以權利為軸心建立起來,民法的內容體系完全是一個以權利為中心的體系。而且民法的規范多為授權性規范,這類法律規范規定具有肯定內容的權利,被授權者有完成這樣或那樣的積極行為的權利。
誠信原則在我國的民法領域確立,正如博登海默所說的,“法律中還存在道德觀念并不起任何顯著作用的廣泛領域,專門的程序規則,流通的票據規則、交通規則的法令以及政府組織規劃的細節,一般都屬于這一類,在這些領域中,法律政策的指導觀念,乃是效用與便利,而不是道德信念”。在民法中,權利和義務作為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的。誠實信用原則對當事人屬義務性規范,側重于行使權利的適度,為權利劃定了界限,從義務的角度規定了權利,并且在現代民法中有較廣泛的具體運用。誠實信用原則的“擴張”并不表明這一原則在民法中占據了帝王之位。相反,這一原則的“擴張”從根本上正好說明了它在民法中的從屬地位。因為,在民事法律體系中這一原則的出現無不以某種權利為前提,并以權利的保障為目的。而它的擴張正好說明了人們對民事權利的認識加深,對民事權利保障的重視,表明了民事權利在民法中的基礎和核心地位。
【參考文獻】
[1] 龍衛球:民法總論[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
[2] 趙金山、劉同賀:論大陸法系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J].法學論壇,1997(4).
第4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關鍵詞:民間規范;法律規范;立法選擇;立法授權;司法選擇
中圖分類號:D920.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03—0067—04
一、引論:規范概念——“一個滑動著的刻度盤”
美國法社會學家羅斯科·龐德指出,宗教、道德與法律被視為人類進行社會控制的三種手段,只是不同的時期各自所發揮的作用不同。自近代以來,法律日益發展成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但人們不能、也不應將社會控制的全部活動納入法律的領域,而應注意發揮各自的功效。①“如果假定政治組織社會和它用來對個人施加壓力的法律,對完成目前復雜社會里的社會控制任務來說已經綽綽有余,那是錯誤的。法律必須在存在著其他比較間接的但是重要的手段——家庭、家庭教養、宗教和學校教育——的情況下執行其職能。如果這些手段恰當并順利地完成了它們的工作的話,許多本應屬于法律的事情將會預先做好。”②龐德看到了法律與宗教、道德、倫理等社會控制方式的不同作用機理,但依筆者之見,這其實只是事物本質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是:法律與其他社會控制方式之間存在著某種轉化機制,尤其是民間規范(民間法)向國家法律的轉化機制是世俗化了的現代法律在工商業社會中增強其規范效力與結果可接受性的一個關鍵問題。
若從龐德所言的“社會工程”角度講,法律當然是一種社會控制方式,而且是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社會控制”;③但從規范理論角度講,法律又是一個社會規范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一種特殊形式的社會規范,一種高度制度化了的社會規范。規范概念指涉兩個向度或要素:承認或曰認同;強制或曰制裁。強調前一種要素的規范更多是認知意義上的,可稱為“慣例”或“慣習”;強調后一種要素的規范更多是拘束性意義上的,最典型的莫過于“法律”。其實作為一種規范形式,“法律”也可能包含承認要素,而“慣例”或“慣習”也可能具有強制力。托馬斯·萊塞爾等德國法社會學家認同規范概念的程度差異性與內在轉換性,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個滑動著的刻度盤”,試圖“以制度化的程度(即規范的制定和實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組織的確認和保障)為標準,對社會規范和法律規范進行區分”。④規范概念因“刻度盤”和程度標準而獲得了類型化和等級化的直觀性,這也為不同類型或等級的規范之間的轉化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
德國法社會學家西奧多·蓋格爾認為,社會規范轉化為法律規范的三條路徑是:第一,通過“司法的選擇”即立法。社會規范通過法官的認可、尤其是職業共同體的普遍接受而變為法律規定。第二,通過“立法的選擇”即司法。社會規范通過立法者的立法行為而變為法律規范。第三,通過“立法的授權”即立法兼司法。“立法者指引準法律的習慣,例如交易習慣和商業習慣”⑤,由適用者在具體個案中加以援用。西奧多·蓋格爾所指出的這三條路徑,是對國內學者提出的“民間規范如何在國家法律中被吸收”這個問題的解答。韋至明教授曾經提出,習慣規范的法律化主要應通過納入和轉化兩種方式來實現。⑥不過,其論證內容基本上局限于西奧多·蓋格爾所言的第一條路徑,對于其他路徑,其并未進行詳細論述。筆者認為,應該接續西奧多·蓋格爾的上述理路,展開更為完整而細膩的分析。
二、通過“立法的選擇”
通過“立法的選擇”,將會使那些以習慣、慣例等形式存在的民間規范上升為國家法律規范。這是一條立法中心主義法學觀持有者所倡導的法人類學路徑、歷史法學派式的路徑,是最能體現民間法在一國立法機構受重視程度的一個標桿。在歷史法學派看來,法律從根源上講是奠基于民族性(“民族個性”)之上的,正是民族性孕育了法律;法學家只不過給法律增添了科學性要素,而立法者也不過是在民族性與科學性之基礎上賦予法律以制定法的形式而已。馮·薩維尼指出:“一切法律均緣起于行為方式,在行為方式中,用習常使用但卻并非十分準確的語言來說,習慣法漸次形成;就是說,法律首先產生于習俗和人民的信仰(popular faith),其次乃假手于法學。”⑦在社會法學派看來,法律是脫胎于社會生活的,法律規范是社會規范的特殊表現形式。社會規范的其他形式如習俗、道德、宗教、商業慣例等是“活的法”,與法律規范相互關聯、相輔相成。歐根·埃利希甚至斷言:“法的發展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學或司法判決,而在于社會本身。”⑧這似乎有過分貶低國家法與法學家(法律家)法的作用之嫌,但究其本意,乃在于對概念法學的“唯法律主義”和“國家實證主義”提出“矯枉必須過正”式的批判而并非抹煞立法、法學或司法判決的重要性,筆者認為其實際上是對立法前的準備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提升立法質量、保證立法效果,立法者應該充分尊重法律的民族性與社會性,充分尊重法學家對本土資源的挖掘和整理,使最終制定出來的法律兼具民主性與科學性,而不是片面強調其國家性與權力性,更不能憑借著法律的“有力武器”而大搞專制統治,走向法律的國家壟斷主義。
綜觀世界各國優秀的立法作品,無一不是通過“立法的選擇”路徑,將民族習慣加以充分吸收與合理編纂而形成的。在規制人們日常生活的私法領域,這一現象更為明顯。被譽為“金縷玉衣”般精致的《德國民法典》,正是法學家們將德意志“民族法”的民族性與羅馬法的技術性要素巧妙結合的產物。以馮·薩維尼為代表的德國法學界有識之士,秉持“民族法是制定法的內容、制定法是民族法的機體”⑨的立法理念,不盲目照搬《法國民法典》(薩維尼貶之為“一部只是為法國而制定的法典”),而是致力于“田野調查”即“考察民族的現實生活”以及對羅馬法的科學研究,最終締造出了“自家的、真正的、民族的、新的制度”。⑩作為判例法系典型代表的英美兩國,其立法作品的嬗變更值得玩味。普通法常被稱為“法官造法”,但在詹姆斯·卡特看來,法官并非在立法,而是在社會正義標準中或在此標準所由來的習慣、習俗中找到其判決的理由。徐國棟教授作了進一步闡發:法官立法表象的背后,“實質是不確定的人民在日常的互動中為自己立法”,普通法的“本質因而是習慣法”。20世紀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家盧埃林起草《統一商法典》時,巧妙地“融入到普通法的廣闊背景中去”,對商業慣例、判例等進行科學編纂,“有意追求使法典成為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法律體系”,從而獲得了巨大成功。
中國在清末民初,國家機構為了制定反映本國國情的民法典,進行了大規模的民商事習慣調查。謝暉教授對此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部民國初期在大陸、后來在臺灣地區施行的法典表明了“對通過習慣表達出來的民間規則的尊重”,也表明了“對以民間規則為代表的公民生活方式的尊重”,在一定意義上使今日“臺灣民眾的生活,更多地保存了中國固有文化與傳統習慣的火種”。筆者認為,清末民初國家處于轉型期,民俗習慣已經成為社會規范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時“國家機構開展了兩次全國性的民商事習慣調查運動,反映了統治者對民商事習慣的立法和司法價值的基本認同”。時至今日,我們的立法工作是否付出了比前人更多的習慣法之調研、科學分析之辛勞?我們的立法作品是否體現了前人的包容精神、達到了更高的水準?這是需要法律工作者深入反思的。
三、通過“立法的授權”
制定法通常情況下是靜止的、穩定的,而社會生活總是復雜的、多維度的。立法者既不可能、也無必要經常性地對民間習俗等進行大規模的調研,盡管從科學、民主地立法的角度講,他們應該組織相關的基礎性工作。立法者因應多變的現實生活的最省事、最節約成本的途徑之一,就是將職責推給法官,由其針對個案所涉社會生活事實進行“審慎的司法自由裁量”(judicial discretion),便宜處置。此即通過“立法的授權”。托馬斯·萊塞爾指出:“民法中規定了一些一般條款,這些條款使得在訴訟中可以適用一些法律規定以外的評判標準,交易習慣和貿易慣例就是其中的兩個代表。法律中使用這些概念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使法官在使用這些概念進行判決時必須以一定的社會規范為基礎,該社會規范必須適用于生活在特定地區的居民團體或者適用于某一經濟領域,而且相關的法律爭議也應該產生于該團體或者領域。這在今天已經得到了大家的公認。”通過“立法的授權”,實際上是立法者面對其意欲規制而又力有不逮的社會生活,所選擇的一種現實而又不失睿智的策略性退出機制。
在法律中,除了交易習慣和貿易慣例,地方慣例、道德習俗、宗教習俗等也常常被立法者以一般條款的方式加以確立,交由法官在個案中加以適用。謝暉在《大、小傳統的溝通理性》一書中,以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我國臺灣地區的民法典等為例,點評了此類“立法的授權”現象。筆者認為,更具代表性的是2004年修訂的《意大利民法典》。作為西方法典化運動的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律、西方現代法律的典范和重要參照系,《意大利民法典》的相關內容對于我們正確把握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提供了更多有益啟示。該法典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地確認了慣例的法源地位,第八條確立了慣例的效力層次,第九條確定了“慣例匯編”的資格——“未有相反證據的,推定機關和團體的正式匯編中公布的慣例為已存慣例”。尤其值得贊嘆的是,該法典關于慣例、習俗的授權性規定多達60余處,涉及家庭財產制、遺囑繼承、所有權、用益權、使用權和居住權、地役權、債的履行、契約、無因管理、勞動、企業勞動、自由職業和公司共12個領域,特別是集中了有關私權主體之間財產關系、人身關系的地方慣例與行業慣例,生動地展現了法律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內在聯系。該法典第三編第二章第二節之第六分節中,對“建筑物、植樹、溝渠之間的距離,土地之間的界墻、界溝和籬笆”事項作出了詳盡的規定,其中既包括國家法律的明確規范,也包括地方條例和慣例的大量吸納。多種類型的規范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套規范網絡,由法官在個案中具體適用。
四、通過“司法的選擇”
通過“司法的選擇”,即通過法官確信與認證的司法程序,把民間法轉化為針對個案的法律規范。議會機構的特點決定了立法者并不適合、也不擅長處理具體案件紛爭,其更多的時候是作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來協調政策分歧和利益沖突。法官職業共同體則具備了發現或創造針對個案的裁判規范的技能,其擅長將包括民間習慣在內的社會規范與法律規范加以區別和轉化。一般而言,“法律規范經常明確地用清晰、確定的語詞表達,以區別于其他規范。通過這種方式,它賦予那些以法律規范為基礎的團體的穩定性。因而那些不是建立在法律規范基礎上的團體,如政黨、宗教派別、親屬組織以及社交組織,總是具有某種松散的、不牢固的形式,直到它們采取法的形式。倫理規范、習俗規范和禮儀規范一旦喪失了其自身的普遍特性,用明確的詞語加以表述,并且對于社會法律秩序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其就經常會變成法律規范”。法官完全可以憑借司法權力和職業技能,將民間規范用法律話語加以概括后作為裁判的權威理由,以之化解個案糾紛。
當前,我國部分法院已經在探索“司法的選擇”路徑并取得了顯著成效。如江蘇省姜堰市人民法院大量搜集、歸類、總結和提煉本地區民間規則,通過審判指導的形式,為法官斷案提供實體和程序依據。2005年底至2007年3月,該法院相繼出臺了《贍養糾紛案件裁判規范意見》、《關于將善良風俗引入分割家庭共有財產的指導意見》、《關于將善良風俗引入民事審判工作的指導意見》等規范性文件,其基本做法是“根據一定原則、程序并經過認真論證,把民俗習慣或作為大前提(規范),或作為小前提(事實),運用到民事司法裁判中”。山東省青島市李滄區人民法院也曾通過“司法的選擇”路徑,運用當地民間規范成功審理了一起房產糾紛案件——“頂盆過繼”案。面對司法實務界的闊步探索,學界應進一步展開對民間法方法論的研究。
司法具有一些獨特的功能價值如具體性、中立性、判斷性、被動性、獨立性、權威性、程序性、最終性等。從法治邏輯上看,司法的具體性意味著法官的規范認知要在審理當事人的爭訟中進行,其所作出的裁判必須滿足“看得見的正義”。司法的中立性意味著法官擁有的更多是一種公共職能,其必須公正地裁量個案所涉權利義務的分配。司法的判斷性意味著法官必須深刻洞察當事人的沖突與糾紛背后的“規范違反”,分析個別行為對社會群體事實行為的偏離程度。司法的被動性意味著法官不能主動開啟解紛的法定程序,以避免公權力提前介入而對社會秩序造成更多紊亂。司法的獨立性意味著法官在處理案件中只服從法和法律(規范),不受其他力量的無端滋擾。司法的權威性意味著法官擁有高度職業化的技藝理性,能夠贏得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司法的程序性意味著法官處理案件過程的公開性,法官行為的可受監督性及其形式正義的可控性。司法的最終性意味著法官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的守護者和社會規范效力審查的終結者。司法的這些克制主義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具備審查民間規范效力的最佳機能。
當某一民間規范經過選擇、甄別而基本具備了適用的前提條件后,在司法過程中究竟如何具體地運用之?這是一個需要細膩處理的、專門化的、司法技術的問題,亦即一個法律方法論或司法方法論的問題。謝暉教授指出“必須給予法官個案裁判的能動性和構造裁判規范的自主性”,他大膽借鑒埃利希等西方法社會學家的理論,并嘗試運用現代法律方法論的知識資源和話語體系,對此作了富有原創性的學理闡釋和制度模型構建。埃利希提出了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二分法,將“人類行為的規則”(一種德國法學研究中流行的關于法的定義)與“法官據以裁決爭議的規則”(一種法官視角的關于法的定義)視為“大不相同的兩回事”,后者“只為法院適用”,并作為“一種特殊種類的法律規范”而“區別于包含一般行為規則的法律規范”。謝暉進一步主張:行為規范更多是為大眾制定的,可謂大眾規范;裁判規范主要是為裁判者制定的,可謂專家規范。裁判規范又可分為援引型與構造型兩類。援引型裁判規范意味著民間規范可以被法官直接用來作為裁判規范而定紛止爭(當然,這常常需要法律授權),而構造型裁判規范更多是指“當法官面對疑難復雜案件時,如果法律規定不能全部滿足、甚至完全不能滿足認定案件事實的要求,就需要法官結合案件事實、法律規定、其他社會規范、被人們接受的社會意識等,并結合法官自身的經驗、直覺和理性,構造出一種直接適用于當下案件的規范”,這其實就是法官在民間規范與法律規范之間進行司法方法論意義上的創造性轉化。筆者認為,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二元結構是和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結構相輔相成的。國家與社會的分野,形成了兩種秩序——國家推進型的建構主義秩序與社會培育型的自生自發秩序,這兩種秩序的有效運行和維系有賴于國家法律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有效支撐。同時,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二分,也暗示著規范之間的同質性與差異性并存。法律規范與民間規范等社會規范之間的同質性意味著其可轉換性,其互為替代性藉此成為可能。法律規范與民間規范等社會規范之間的差異性則意味著,規范之間的轉化需要特殊機制與專業技術支撐,其互為補充性藉此成為可能。
注釋
第5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一、關于合同自由原則的由來及其發展
在法律上,合同自由原則的真正確立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后。一般認為,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第1134條首次在法律上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該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在訂立合同的當事人之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這種合同,只能根據當事人間的合意或法律規定的原因撤銷之。”之后,各國民法典均予以效仿,紛紛確立了合同自由原則,該原則與私權神圣原則、過失責任原則被稱為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則。至今,合同自由原則仍是各國合同法奉行的最基本的原則。
合同自由原則強調社會關系的自我形成,主張把合同作為個人的自治范圍來對待,為此極大地激發了個人主觀創造能力,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該原則的形成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是密不可分的。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資產階級為鞏固革命成果,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法律上確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近代基本法律原則。這一原則體現在民法領域即是民事主體平等原則,而合同自由原則是主體平等的必然結果。在經濟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確立之初,自由競爭的模式更符合當時大規模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加之,在經濟理論上有亞當。斯密自由放任的經濟學主流的影響,這就要求資產階級國家在法律上確認合同自由的原則,最大限度地為當事人的行為自由提供空間。
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勞動者和雇主、大企業和消費者、出租者和承租者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合同自由受到挑戰。20世紀以來,兩次世界大戰和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導致了整個世界對合同的立法方針的變化。市場經濟完全依靠合同自由原則運行被實踐證明是失敗的。在經濟理論上,有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使得法律上的自由主義為逐漸增長的國家干預主義所代替。合同作為調整經濟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的手段,也不可能逃避這種變化。合同自由原則受到限制。當代合同法由于社會意志的侵入,個人意志的退縮,當事人的意愿和意志所起的作用已不象傳統理論所設想的那么大了,大多數法律學者認為,合同責任大小取決于所產生的合理預期值的多少,取決于允許對這種合理的預期值的實現進行阻撓是否公平,取決于社會政策對交易的影響。從以上觀點來看,當事人的承諾就變得不太重要了。那么,合同關系的大部分內容可以來源于習慣、公平觀念和政策,而不是被局限在合同所明示或暗示的內容之中。
二、合同自由原則的主要內容
合同自由原則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即合同訂立自由、合同內容自由及合同形式自由。關于這三方面的自由,立法者原則上不作具體規定,而是由合同雙方當事人自由決定。
1.合同訂立自由,即當事人雙方可以自由決定是否締結合同,自由地選擇合同的相對人。
2.合同內容自由,即當事人可以自由地決定合同的內容。合同法中大量的任意性規范使當事人得以選擇適用或排斥適用。
3.合同形式自由,即當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以何種方式訂立合同。
三、外國現代合同法對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
現代各國對合同自由原則的限制,在立法方面主要表現為:
1.強制訂立某些種類的合同。又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種為強制性合同取消了當事人不訂立合同的自由,但保留了當事人選擇合同相對方的自由。如根據其實施的行為或從事的職業,法律強制某些特定的當事人實施責任保險,象要求汽車駕駛員強制投保某些責任保險等。或者相反,保留當事人不訂立合同的自由,但不允許當事人對相對方進行任意選擇。如法國1972年546號法律規定,當事人拒絕雇傭某人,如果是基于“出身,或基于其屬于或不屬于某一種族、某一民族、某一人種及某一特定宗教”等,當事人將受到刑事制裁。另一種為當事人不訂立合同的自由和選擇相對方的自由都被取消,即當事人不僅必須訂立合同,而且只能與特定的人訂立合同。某些情況下,如果當事人拒絕與法律規定的相對方訂立合同,除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外,有時合同還被法律視為已經成立,即視當事人已和符合法律規定的相對方訂立了合同。
2.規定強制性合同條款,當事人不得排除其適用,或規定當事人相反的約定一律無效。
3.法律指定或專門設立具有準司法性質的行政機關,對合同進行監督、管理和控制。依據這些法律設立的行政機關,如美國的聯邦交易委員會、德國的卡特爾局等,在限制合同自由方面擁有廣泛的權利。但這種限制只是為反壟斷,維護自由競爭和保護中小企業及消費者的利益而進行的。
4.在合同法中引入公平、誠實信用等道德規范,制定具有極大彈性的原則性條款,通過對這些法律原則的適用,使法官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權。法官為調整合同當事人失衡的權利義務關系而介入的結果,使合同自由原則進一步受到限制。如前所述,法國對“經濟暴力”、“原因”等概念的引入。在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節第302條規定,可以拒絕履行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合同。1986年奇安尼體育用品公司訴格蘭茨公司一案就是依據該條法律起訴的。在此案中,零售商向生產商訂購服裝,后零售商向生產商提出取消訂貨。生產商提出以合同規定價格的一半將服裝賣給零售商,零售商對此表示接受,可是生產商在發售完全部貨物后,向法院起訴,要求零售商按合同規定的價格支付全部貨款。法院根據該條款,支持了生產商的請求。在日本,雖然民法中沒有情勢變更原則的規定,但在判例中適用了這一原則,賦予當事人以解除合同的權利,或者由法官在審判中對合同的內容進行修正或補充。在德國,民法典第138條規定:“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行為無效。”第152條規定:“合同的解釋,應當遵守誠實信用的原則,并考慮交易上的習慣。”第242條規定:“債務人應依誠實和信用,并參照交易上的習慣履行給付。”在英國,法律引入默示條款的概念,旨在維護社會公正和保護消費者的權益。默示條款不是當事人雙方協議達成的,而是來自法律或商業習慣,法律規定一些合同必須包含某些默示條款。1994年的消費者合同不公正條款規則規定,任何不公正的條款都對消費者沒有約束力。對于何為不公正從兩方面衡量:(1)不公正的條款必須與誠信的要求相違背;(2)不公正的條款必將導致當事人雙方合同權利義務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對消費者不利的。
通過各國的成文法和案例可發現,當今合同法的發展趨勢是合同的自由要更多地考慮公平觀念和習慣做法,合同自由的原則已經被弱化,這是與整個世界經濟形勢分不開的。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終究由經濟基礎所決定,并反過來為其服務,不斷調整以適應其不斷變化的需求。
第6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論文關鍵詞 德國民法 物權行為理論 獨立性 無因性
民法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市民社會的基本法以及確認權利和救濟權利的基本法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大陸法系的發源之處,德國民法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和瑞士,日本及我國民國時期(現為臺灣地區)的法律都屬于大陸法系范圍。中國自清末改制以來,繼受德國民法已經有一百余年,德國民法中的許多概念和制度都為我國所直接借鑒,從而使我國在短時間內形成了較為完善和能夠適應我國當前經濟體制的法律。但是,作為傳統民法中的重要理論之一的物權行為理論,我國立法對此卻持有保留的態度。其原因何在?物權行為理論在人們的實際生活中事實上到底能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一、民法中的物權行為理論
(一)物權行為的由來
物權行為理論肇始于德國普通法時期的普通法學。其創始人為歷史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德國學者薩維尼。19世紀初,薩維尼在講學時發表了其關于物權行為最初理論。物權行為的概念最早由薩維尼在其1840年出版的《現代羅馬法體系》一書中提出,但薩維尼在提出物權行為的概念后,并未明確界定其內涵。《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雖然采用了物權行為理論,并在其第一草案中曾使用了“物權契約”的用語,但后來認為其不夠精確,遂改用“物權合意”。關于物權的概念,至今仍然眾說紛紜。國內的主要學說有效果說,目的說,要件說和內容說。其中內容說較有說服力,認為“物權行為,為物權之設定,移轉為直接內容的法律行為。”①無論爭議如何,所能達成的共識是物權變動的合意為物權行為的基本要素。物權行為理論包括物權行為的獨立性,物權行為的無因性以及物權變動的形式主義原則。
(二)物權行為的獨立性
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即物權行為的“區分原則”,有學者亦成為“分離原則”。德國學者薩維尼關于物權行為獨立性的主張是通過觀察行人向乞丐的施舍而獲得的。當某人向乞丐贈與一枚硬幣時,正當原因與交付同時發生。此時,除所有權的移轉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事實,在某人與乞丐之間,既不存在先前的契約,亦不存在任何債權債務關系。純粹的、唯一存在的事實上的交付即使所有權發生轉移。認為“所有權的移轉并不以債權契約為必要,交付表達了所有權讓與的合意,是一真正的契約,一個物權法上的物權契約”。主張債權契約和物權契約是兩個不同的法律行為。要發生物權變動,必須依賴于債權契約之外的行為,即以直接發生物權變動為目的的法律行為,即物權行為。債權契約的效力只產生雙方當事人享有債權的負擔債務的效力,并不直接產生物權變動的效力。以買賣合同為例,民事主體雙方達成買賣合同,僅產生一方按照合同的約定給付標的物和另一方支付價金(對價)的效力,而不發生標的物和價金的所有權轉移的效力。要發生標的物和所有權轉移的效力,當事人雙方還應另行定義一個完全獨立的物權契約,此物權契約的內容為雙方主體轉移標的物和價金的所有權。至此,物權契約和債權契約截然分開。
(三)行為的無因性
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即物權行為的“抽象原則”。薩維尼認為,物權行為應當采取無因性,物權行為不受債權行為的影響。即物權行為成立后,不論其存在原因的債權行為無效或者被撤銷,都不影響物權行為的有效性。如在買賣合同中,當事人一方交付標的物,另一方支付價金以后,因債權合意有瑕疵或者合同內容違反法律或公序良俗原則而被確認無效或被撤銷,物權變動的效力不受影響,仍然有效。喪失所有權的出賣人不能以原物返還請求權請求買受人返還原物,而只能以不當得利的規則請求返還,因為在采物權行為無因性理論的前提下,此時買受人仍然享有標的物的所有權。物權行為的無因性與物權行為的獨立性一脈相承。至于物權行為的形式主義原則(亦可理解為公示公信原則的初始原則),動產以交付為轉讓生效要件,不動產以登記為物權變動生效要件。法律對此有明確的規定,并且在實踐中亦較為容易地適用,故對此問題不展開論述。
二、民法規定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及無因性的立法及在實踐上出現的問題
薩維尼及其他采物權行為理論的學者對物權行為理論的抽象,最初是薩維尼在解釋羅馬法的形式主義立法過程中提出來的。薩維尼采用歷史的研究方法,通過歷史的溯源而尋找法律的規則合理論。德國民法向來以概念精確,邏輯嚴謹和理論抽象之特點而著稱,而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理論更是極具抽象性。《德國民法典》第929條[合意與交付]規定:“轉讓動產所有權需由所有權人將物交付于受讓人,并就所有權的轉移由雙方成立合意。受讓人已占有該物的,僅需轉移所有權的合意即可。”《德國民法典》第873條[根據協議和登記取得]規定:“(1)轉讓土地所有權、對土地設定權利以及轉讓此種權利或者對此種權利設定其他權利,需有權利人與相對人關于權利變更的協議,并應將權利變更在土地登記簿中登記注冊,但法律另有其他規定的除外。(2)在登記前,雙方當事人僅在對意思表示進行公證人公證時,或者向土地登記局作出或者呈遞意思表示時,或者權利人已將符合《土地登記簿法》規定的登記許可證交付于相對人時,始受協議約束。“而《德國民法典》第877條規定,土地上權利的變更亦適用于第873條。通過對《德國民法典》具體條文的考察,可以明確的看到德國民法立法采取了物權行為理論。
民事立法的宗旨在于在交易秩序和民事權利的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使二者達到效益的最大化。民法不能只保護交易秩序,只關注交易的確定性和效益性而對交易主體的權利忽視,同時也不能只追求民事主體之內心真意而使民事交易秩序混亂效益低下。德國民法對于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理論的立法采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不可忽視的弊端。嚴重違背了民事交易活動中的公平正義,對權利人的權利無法真正加以保護,嚴重損害了出賣人的利益。以買賣合同為例,民事雙方主體在交付標的物和支付價金后,發現買賣契約未成立,無效或者被撤銷,此時因物權行為的無因性原理,物權行為的效力不受影響,買受人仍然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出賣人僅能以不當得利之規則請求返還(前已述及)。所導致的后果是出賣人由所有權人變為債權人,其權利由所有權變為債權,權利的效力下降,對出賣人的權利不能完全保護甚至是損害嚴重,以下對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進行分析:第一,如果買受人已經將標的物轉賣,第三人即使為惡意亦能取得所有權,出賣人不能對第三人主張任何權利,而只能向買受人請求返還轉賣所得價金。若不采物權行為理論,則出賣人可以直接對該惡意第三人起訴,請求返還標的物。第二,如果買受人已在標的物上設定擔保物權,由于擔保物權具有優先于債權的效力,則出賣人不能請求返還標的物,只能請求買受人賠償。若而不采物權行為理論,則買受人為第三人在無權處分之物上設定擔保物權的行為,應為無效,此時出賣人對此無權處分行為必然不追認。第三,如果買受人的其他債權人對該標的物為強制執行,由于出賣人處于一般債權人的低位,無法提起異議之訴。若不采物權行為理論,則出賣人作為所有權人,對于他人侵害自己財產的行為,當然可以提起異議之訴。第四,如果買受人陷于破產,出賣人不能以所有權行駛取回權從破產財產中取回標的物,而只能以一般債權人的地位,同其他債權人一起,按債權比例受清償。若不采物權行為理論,則出賣人的依法行使別除權,從破產財產中取回標的物,避免其財產減少,對出賣人的權利保護予以極大地幫助。第五,如果非因買受人的過失致使標的物毀損滅失的,買受人可以免責。若不采物權行為理論,則買受人不能免責,出賣人可以獲得賠償。總之,由于物權行為理論在司法實踐中有上述缺陷和弊端,德國判例學說通過解釋方法對物權行為的無因性理論之適用予以限制。使物權行為的效力受債權合意的影響,此為物權行為無因性之相對化的趨勢。
三、立法對物權行為理論的揚棄之思考
我國在2007年制定的《物權法》未采取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理論。《物權法》第15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效力。”《物權法》第23條規定:“動產物權的設立和轉讓,自交付時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物權法》第9條規定:“不動產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經依法登記,發生效力;未經登記,不發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依法屬于國家所有的自然資源,所有權可以不登記。”我國《物權法》對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并未規定,理論研究中葉飛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在我國的適用采取排斥態度。對此我們應當予以高度肯定。法律移植是快速提高本國法律水平的方法,大膽借鑒外國的先進立法理念和制度,但是,一定要立足于本國的歷史傳統和社會現狀,在總結本國的立法經驗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之上有選擇地對他國的法律制度予以借鑒,否則只能適得其反,對本國的法律現狀造成更大的損害。我國采取“債權合意+交付或登記”為物權變動方法,符合我國的民事立法傳統,易于執法者的理解和掌握。物權行為的獨立性和無因性理論過于抽象,遠離實際生活,并且在適用于司法實踐中產生了諸多弊端,故我國的立法模式能夠有效地平等地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和維護交易秩序和安全,兼顧出賣人和買受人的利益。并借助于善意取得制度,有效地保護善意第三人,達到了兼顧民事交易秩序和民事主體利益的效益最大化宗旨。是我國《物權法》理論和成文法中的一大亮點。
第7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關鍵詞:探望權;探望主體;強制執行
中圖分類號:D913.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23(C)-0228-01
婚姻的裂變是社會不安定的原因之一,隨著婚姻的解體使得越來越多的離異子女處于缺失父愛或母愛的家庭中。為了這些可能受到婚姻離異帶來傷害的未成年人的身心能得到健康發展,已經成為了當今社會立法者考慮的首要問題。為解決該問題,我國《婚姻法》增加探望權的規定。
一、探望權的由來和概念
(一)探望權的歷史沿革
探望權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系,是為處理離婚后父母及其他親屬探望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據,后被多數國家紛紛效仿。“探視權制度的設立正式為了考慮到兒童心理和感情的需要,使其雖然處于破裂家庭之中,但仍然能夠享有家庭成員的關愛”,故國家在制定探望權時首要考慮就是是否能給予兒童幸福和安全。可見立法設立之初是為子女利益考慮的,這也符合婚姻法的基本原則和憲法的相關規定。如德國《民法典》中明確規定:“不享有身體照顧權的父或母一方,有權與子女進行人身交往。不享有人身照顧權的父母一方和有照顧權權利人應當不做任何有損子女對另一方的關系或使教育產生困難的行為”。其次,家庭法院可以對交往權的范圍作出對第三人有效的詳細規定;澳門民法典規定在離婚時,法院得將未成年子女交由父母任一方照顧,同時須為不獲交托照顧子女之父親、母親或雙方訂立探訪。但基于對子女利益之考慮而不宜訂立者除外。我國《民法》,《婚姻法》沒有探望權,直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時,通過38條增加探望權的規定。
(二)探望權的概念和特征
我國學者認為探望權,又稱見面交往權,是指離婚后,不直接撫養子女的母或父一方享有的與未成年子女探望、聯系、會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權利。探望權是基于血緣關系產生,具有鮮明的特性:
1、探望權的權利主體為離婚后未撫養子女的夫妻一方。而探望權的義務主體是離婚后撫養子女的一方。
2、探望權是離婚后雙方的一項法定權利。離婚后不直接和子女生活的一方,可通過探望達到繼續教育子女的目的。
3、探望權產生的時間為離婚后。離婚后,由于缺乏家庭的關愛,就存在探望的必要。
4、探望權的行使必須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離婚對未成年人來說必造成心理傷害,為了讓其能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不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應通過與子女會面、交流或接觸,能增進彼此間感情,對孩子的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探望權的主體問題
我國法律明文規定,探望權的主體為未成年人的父或母并互為權利義務主體,其他人不享有該權利。對此學術界有兩種觀點,第一,離婚后不直接撫養子女的一方是唯一的探望主體;第二,除離婚后不直接撫養子女的一方為探視主體外,還包括不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外)祖父母。筆者贊同后者的觀點,探望主體限制過嚴,一旦其父母均無撫養能力,未成年子女通過指定撫養人,而與其他親屬形成了撫養關系,離婚后這些對未成年人成長過程起到撫養監護作用的第三人卻因無法律依據無探視權。1993年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案,號召各州立法,允許祖父母行使探視權,使得祖父母的監護權得到關注。之后,各州也承認了祖父母的探視權。德國民法典規定:“祖父母和兄弟姐妹有權與子女交往――尚若此種交往有利于孩子的幸福”。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實踐經驗使得探視主體大有擴大的趨勢,現在除了父母外,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其他第三人都享有探視權的可能,特別是實際中對未成年人已經履行一定的撫養教育義務的第三人。
三、探望權的行使問題
對探望權的行使問題上,有當事人協商或法院判決兩種方式,在實踐中采用協議優先原則。對于探望權的行使方式上,包括兩種方式:一種是探望性的探望,是指不直接撫養子女的一方到對方家或指定地點進行探望;還有一種是逗留性的探望,指探望人在約定時間接走子女,并按時送回。對于探望以何種形式實施,應著重考慮子女和當事人雙方的實際情形,以最適合子女利益的方式來實行。在探望權行使中,如果出現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損害其身心健康時,探望權的行使應中止。具體包括:(1)探望權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2)探望權人患有嚴重的傳染性基本或其他可能危及子女健康的疾病;(3)探望權人品行敗壞,甚至教唆、脅迫、引誘未成年子女實施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給子女帶來身心健康的傷害;(4)探望人在行使探望權時對子女有侵犯或犯罪行為,損害子女利益;(5)探望權人與子女感情惡化,子女拒絕探望的。對探望權中止按照我國法律規定,有權提出中止請求的是未成年子女,直接撫養子女的父或母以及其他對未成年子女承擔撫養教育義務的法定監護人,且必須按照法定程序向法院提出。對于探望權的中止,其他任何機關、個人包括雙方當事人均無權中止探望權,并且中止情節消失后,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決定恢復其探望權。
探望權是基于實際需要修訂增加的權利,該權利出現較晚,導致缺乏相關的明確規定,故我們需盡快完善立法,加大普法的力度,從而營造一個和諧科學的依法治國的氛圍,使得我國法律更適應時代的發展,為早日建立和諧社會努力。
作者單位:湖北咸寧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第8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關鍵詞: 消費者保護;消費者;撤回權;意思自由;合同嚴守;效力待定
前言
信息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與撤回權(Widerrufsrecht)屬于消費者保護領域的兩大傳統法律工具。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已確立了一般性的信息義務規則,但并無撤回權制度。目前,我國學界對消費者撤回權制度的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多為介紹德國撤回權制度以及英美冷卻期制度者,[1]而從消費者撤回權與合同自由關系角度論及撤回權制度正當性基礎的研究成果甚為少見。[2]要在既有的民法體系中加人撤回權制度,首當其沖的就是需要考量其正當性,保護消費者這一口號就足以構成撤回權的正當性理由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直接決定了撤回權制度調整的范圍,是建立一般性的撤回權制度,還是確立某些撤回權類型。與既有的撤銷權、解除權等形成權不同,撤回權有一個特殊的撤回期間制度,如何確定撤回期間的起算點?如何保護經營者信賴合同應被遵守的利益?撤回權制度是對既有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發展,二者的關系如何,也值得研究。針對這些問題,本文首先闡明消費者撤回權制度的規范目的,其次探討契約自由與契約嚴守之間的平衡,最后嘗試將消費者撤回權歸入既有的民法體系,以明確其特別法之地位。
一、消費者撤回權制度的規范目的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歐盟、德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等都陸續規定了消費者撤回權制度(Widerrufsrecht)或者與其類似的冷卻期制度(cooling-off period),使消費者在訂立合同后仍有機會修正其可能比較倉促的法律行為決定。[3]在我國既有的法律法規中,亦規定有消費者撤回權制度。如2002 年修訂的《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即首次規定了該項制度,[4]2005年國務院頒布的《直銷管理條例》第25條規定,直銷經營者應當建立并實行完善的換貨和退貨制度,并且將無因退貨期限定為30日。
這些制度的共同特點在于,即在特定的事實構成被立法詳細描述(類型法定)的情況下,消費者于一定期限內可以通過單方意思表示且無需給出原因地從與經營者簽訂的合同中擺脫出來。[5]而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立法者要賦予消費者以“無因”撤回權。
雖然消費者撤回權的引入深受消費者保護運動的影響,但其正當性基礎并不在于保護消費者。實際上,在法律交易中不存在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而使其享有優于經營者地位的一般原則,私人與經營者同樣都享有私法自治與合同自由,立法無論偏向哪一方都是違反平等原則的,故消費者保護本身并不能成為規定消費者撤回權的正當性理由。
還有學者認為,談判地位不平等是消費者撤回權的正當性基礎,撤回權之目的在于使消費者在撤回期限內有機會再次進行考慮或者自合同中脫身,從而使消費者受到妨害的談判地位平等性(Verhandlungsgleichgewicht)得以回復。[6]該種觀點的不足之處在于,消費者不能因為其在合同中體現的意思內容少于經營者就撤回其意思表示,故該觀點亦缺乏說服力。
早在1891年,德國學者Heck就建議規定分期付款買賣(Abzahlungskauf)情況下的后悔權(Reurecht)制度。[7]他認為,在分期付款買賣的情況下,顧客可能被勸誘購買非必需的以及超出其財產能力的標的物,其原因在于心理上的因素,即與目前的享受相比,將來才履行的義務往往被低估。[8]這一建議在當時并未被德國立法者所采納。直到1969年,在消費者運動浪潮的影響下,德國立法者才在《外國投資份額銷售法》[9]中規定了撤回權制度。雖然Heck的建議已經觸及問題的實質,但僅有經營者的勸誘因素,尚不足以構成消費者享有撤回權之正當理由。問題的關鍵在于消費者的意思是否受到了影響,是否具有勸誘行為反而并非問題的關鍵所在。
(一)意思形成障礙
立法者一般不會在法律中規定一般性的消費者撤回權,通常只針對特定情形或者具體合同類型規定消費者撤回權制度,而每種情況下的規范目的又各不相同。
1.上門交易情形下的消費者撤回權
在立法政策上,消費者撤回權實際上是與直銷(Direktvertrieb)等特殊銷售形式進行斗爭的結果。[10]現代社會,由于貨物與服務銷售形式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其中直銷模式以及網絡交易模式頗為興盛。歐盟于1985年針對直銷模式頒布了《上門交易撤回指令》(85/577/EWG),德國于 1986年制定了《上門交易法》。[11]德國立法者認為,在交易場合不適宜的情況下,如在消費者工作場合以及私人住宅訂立合同的情況下,存在對消費者突襲的危險并阻礙了其決定自由。[12]在歐盟《上門交易撤回指令》的立法理由中,亦認為其基礎在于“突襲之要素”,該突襲使得消費者喪失了比較價格與質量的機會。[13]因此,在此種交易情形下,消費者通常沒有表示出其在適當考慮情況下本應作出的表示。
2.特定合同類型情形下的消費者撤回權
頒布于1894年的德國《分期付款買賣法》原先并無消費者撤回權制度,1974年修改時[14]增設了分期付款買賣情況下的撤回權制度。1990年,該法為《消費者信貸法》[15]所取代,撤回權制度被擴張適用到其他類型的消費者信貸以及分期交貨合同情形。立法者認為,在消費者信貸合同情況下,賦予消費者以撤回權的原因在于:消費者無法完全判斷合同條款的整體,在談判這一很短的時間內無法對其有充分的理解。[16]消費者信貸合同的內容較為復雜,若無專門知識無法理解,且所貸款項金額巨大、期限較長,消費者有可能無法正確判斷貸款內容及自己的貸款能力,往往會陷入到長期債務負擔之中,目前的“房奴”稱謂恰是這一情況的“寫照”。
在德國《分期付款買賣法》之后,德國又相繼于1976年頒布了《遠程授課保護法》,[17]于1990年頒布了《保險合同法》,[18]于1996年頒布了《分時使用住宅法》,[19]于2000年頒布了《遠程銷售法》。[20]這些法律均規定了消費者撤回權制度。在遠程銷售情形下,立法者認為,于訂立合同前,消費者與供貨者并無個人接觸,且無法親眼看到商品或仔細了解服務的質量,也無從向其他自然人了解相關信息。[21]在遠程金融服務、分時度假以及消費者信貸合同情況下,消費者無法完全判斷合同條款的整體,在談判這一很短的時間內無法對其有充分的理解。[22]分時度假合同具有長期合同的性質,消費者于訂立合同時可能無法理解合同的長期約束力意味著什么,故應給予消費者一定期間以更好地檢查其權利與義務。[23]
綜合而言,在前述第一種情形下,消費者處于精神上的弱勢,突襲之情形導致其不能充分考慮和形成意思;在第二種情形下,消費者處于信息上的弱勢,信息不完全導致其無法自由形成意思。所以,消費者撤回權的基礎在于其意思形成受到了妨礙(Beeintrachtigung der Willensbil-dung)。[24]而這種妨礙并不必真正形成,只要具有潛在的妨礙意思形成之可能性即可。[25]實質上,立法者已推定在該法定情況下,消費者的意思形成受到了妨礙,而該推定是不可以被推翻的。
有爭議的是,是否將撤回權的類型限定于特定的合同類型,如僅限于買賣合同類型。德國學者梅迪庫斯在為債法委員會出具的鑒定中認為,不應根據合同類型規定撤回權制度,而應根據交易場景以及其他不當銷售形式確定撤回權制度。消費者撤回權的正當性理由與合同類型并不相關,而是在于其銷售形式使消費者可能過于匆忙作出決定。如果根據合同類型確定撤回權,則如何選擇合同類型往往會陷入任意性的危險。[26]
(二)意思形成障礙的救濟
意思形成障礙在本質上是屬于意思瑕疵的一種,但經營者妨礙消費者意思形成的情況,并不總是符合詐欺或者脅迫的構成要件,如二者均需具備主觀故意之要件,但經營者妨礙消費者的意思形成在大部分情況下均非出自故意,而證明經營者具有主觀故意的難度較大。根據法律上的“錯誤”理論,動機錯誤一般不構成可撤銷之事由,而消費者意思形成障礙的情況大部分屬于動機方面的問題,而證明動機問題亦十分困難,故不能通過錯誤制度解決意思形成障礙問題。在法律規定消費者撤回權之前,德國法院通常通過公序良俗條款救濟消費者意思的形成障礙問題,主要涉及合同價款的合理性以及對所提供的給付是否有個人需要的問題。[27]在消費者被迫倉促作出決定的情況下,法院還運用締約過失制度給予救濟。[28]根據締約過失制度,在合同談判時,一方當事人有過錯地違反咨詢和解釋義務的情況下,相對人可以請求損害賠償。
通過背俗規則或者締約過失規則對意思形成障礙固然可以部分地予以救濟,但根據此兩項規則無法構建“考慮期規則”,即通過賦予消費者一定的考慮期來保障法律行為上的決定自由,只有立法特別規定的消費者撤回權制度才能容納“考慮期規則”。[29]經過考慮期后,消費者決定是否撤回意思表示或者讓意思表示有效,而不是一概否認其效力。
(三)意思真正的形成
在立法者確定的法定情形或者法定合同類型下,消費者的意思形成被推定受到了妨礙。在邏輯上,該妨礙被排除后,消費者即應受其意思表示約束,那么如何判斷消費者的意思不再受到妨礙呢?在立法技術上,法律特別規定了撤回期間,以便使消費者真正地進行考慮并形成意思。
在德國法上,撤回期間為兩周,自經營者履行撤回權告知義務之后開始起算。只有在撤回期間起算后,消費者才能在沒有精神壓力的情況下思考是訂立合同還是行使撤回權。[30]
對于告知義務,法律的要求比較嚴格,除要求必須以書面形式作出外,尚須明確告知撤回權的行使、行使的相對人、期限開始起算時點以及消費者的權利。[31]在實踐中,糾紛最多的就是經營者是否正當地履行了撤回權的告知義務問題。
根據《德國民法典》第355條第2款和第3款的規定,如果經營者事后方履行撤回權告知之義務,則撤回期限為1個月,如果經營者未履行撤回權告知義務或者貨物沒有到達,則撤回期限為6個月。與撤回權期間關聯的并非經營者意思表示的作出,而是消費者意思表示的作出。[32]
撤回權期間一般都比較短,德國法上的規定為14天。對于消費者撤回權理論問題而言,如此短的期間似乎不那么具有實踐意義,但如果考慮到撤回權期間的起算點是從經營者履行告知義務之后起算的,就會發現上述問題的實踐意義是很大的。在經營者不履行告知義務或者告知不適當的情況下,德國的撤回權期限為6個月,而根據歐盟指令則為無期限,二者在此方面的規定發生了沖突。由于德國的這一規則被認為是違反歐洲法的,其于2002年予以修改。[33]這一修改對于消費者撤回權而言,其實踐意義就更大了。
根據《德國民法典》第312條的有關規定,在遠程銷售的情況下,撤回權期間的起算還與其他信息義務之履行以及貨物是否到達受領人有關,期間之開始不得早于其他信息義務之履行[34]以及貨物到達受領人之時。消費者即使獲得了相關信息,消費者的撤回權亦不立即消失,因為消費者被告知相關信息后,仍需消化這些信息,并與同類產品進行比較。[35]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修訂應引人經營者告知撤回權之義務以及說明義務的規定,使消費者清楚自己的權利狀況,并區分銷售合同、提供服務合同或者信貸合同等情況規定撤回權期間的起算點。
(四)撤回與退回
消費者撤回權不同于消費者退回權,德國法除了規定一般性的消費者撤回權以外,還規定了消費者退回權。在法律規定的特定情形下,如上門交易與遠程交易情形,消費者撤回權可以為返還權(Riickgaberecht)所替代,實質上是對撤回權的限制,即只能通過寄回貨物行使撤回權,[36]而且在利益衡量上作出了有利于經營者的安排。首先,其減輕了經營者的撤回權告知義務,只要消費者從出賣廣告單上推斷出必要的信息以及撤回權告知信息即為已足。[37]減輕經營者告知義務的理由在于,在大規模交易中要求經營者履行嚴格的告知義務過于苛刻,也會增加交易成本,經營者也會通過提高商品價格而將風險分散給消費者。其次,消費者于此情形下負擔了先履行義務,其只能通過寄回標的物行使退回權,經營者只有在標的物被寄回后才負有返還義務。[38]
消費者行使退回權的,其費用與風險由經營者承擔,如果貨物不適合寄送,則可以要求經營者取回。將撤回權行使方式限定在返還上是有利于經營者的,故要求在要約邀請性質的宣傳冊中必須明確告知返還權,并且必須保障消費者在經營者不在場的情況下已詳細地了解了該權利。
在消費者撤回權情況下,消費者可以文本形式或寄回原物的方式作出撤回之意思表示,但在以后者方式作出意思表示時,經營者并無退回權情況下的特權。在撤回期限內,只要消費者發送貨物(Absendung)于經營者,即為遵守撤回之期限,對于撤回意思表示之遲延風險以及損失風險,消費者并不承擔責任。[39]
二、消費者撤回權與契約嚴守原則
(一)消費者撤回權的構成前提
是否構成消費者撤回權,通常要經過兩個層次的考察,首先須是構成消費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對于何為消費者、何為經營者,立法上有兩種模式:一種是動態體系模式,即只規定若干判斷因素,但并不對其進行類型化;另一種是類型化模式,其或根據人的因素作出類型化規定,或根據特定情形下、基于交易目的產生的保護必要性作出類型化規定。[40]《德國民法典》第13條和第14條分別規定了消費者與經營者的定義,其模式屬于基于交易目的的類型化模式。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但對于何為經營者其并未作出規定。從其表述方式來看,該條規定采取的也是基于交易目的類型化之模式。即是否為消費者,關鍵是看其是否有生活消費之目的,至于其是否為企業或商人則非關鍵性要素。
其次,必須有法律規定的情況。如《德國民法典》第312條與第312a條規定的上門交易行為、第312b條以下規定的遠程銷售合同等。[41]而在法定類型情況下,其又有不同的構成前提。
1.上門交易。以上門交易情況下的撤回權為例,其構成前提首先必須是上門交易。而所謂上門交易,是指在法定情況下,消費者對于簽訂或者拒絕簽訂合同的決定自由受到妨害的情形。[42]所謂法定情況,具體包括消費者在其工作場所或住宅范圍內與經營者口頭協商而訂立合同的情況,在經營者或者第三人舉辦的、含有經營者利益的閑暇活動之際,消費者被促使訂立合同的情況,在交通工具或公用交通場所突襲攀談之后,消費者被促使訂立合同的情況。在這些情況下,決定自由受到妨害主要是指使人吃驚或者遭突襲產生了心理壓力,從而影響意思形成過程。[43]在《歐洲合同法原則》以及《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中并無消費者撤回權制度,但歐洲《一般參考框架草案》(DCFR)第5:201條以及第5:202條規定其適用于所有在交易場所以外訂立的合同以及分時度假合同,但并未進一步地予以類型化和給出正當性理由,其有過分保護消費者之嫌。其次,上述特定情形或場合必須被限定于作出意思表示,所謂限定于作出意思表示不等于作出意思表示,而是弱于作出意思表示,只要上門交易對于意思表示的作出構成共同原因即可。[44]最后,如果在上述場合下,訂立的合同是消費者事先制定的,則不存在突襲因素,故不構成撤回權;在磋商后立即給付以及給付對價,且價格不超過40歐元的情況下,亦不得撤回;在消費者意思表示為公證員公證的情況下,亦不存在意思形成被妨礙之情形,其意思表示不得撤回。
2.遠程交易。在遠程銷售情況下,消費者撤回權的構成要件中并沒有上述特定場合之要素。《德國民法典》第312b條規定,其在構成上僅要求具備“消費者與經營者僅使用遠程通訊手段訂立貨物供應或服務(包括金融服務)合同”這一要件。貨物與服務的概念甚廣,貨物指的是動產,而服務包括任何指向行為的合同,如勞務合同、承攬合同、游戲合同以及有償的事務管理。[45]而所謂使用遠程通訊手段,是指在消費者與經營者沒有同時出現的情況下談判、簽訂合同之情形。 [46]
縱觀消費者撤回權的構成前提,作為撤回權人的消費者并不需要給出撤回之理由甚或證明其撤回之理由。其既不需要具有對意思決定的真實妨礙,也不需問及撤回動機,實質為任意之撤回權(willkilrliches Widerrufsrecht)。在上門交易的情形下,尚需要特定場合與契約訂立之間的“因果關系”這一構成要件,而在遠程銷售情形下則僅需一些客觀的構成前提。問題是立法者賦予消費者以如此強大的撤回權,其是否構成了對契約嚴守原則的違反。
(二)任意撤回權與契約嚴守原則
為了保障契約將來產生效力,當事人須受其曾訂立的合同之約束,此即契約嚴守原則。契約嚴守原則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護交易以及信賴,賦予合同以將來之效力。合同當事人允諾給付,約束自己,在經濟上互為“犧牲”,即使在事后利益狀況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也應受其約束。[47]
合同嚴守與合同自由都是個人自決(Selbstbestimmung)的表達。所謂意思自由,即個人自由的行使,也即表示人實際上的、在自由中形成以及行使的意思。[48]沒有意思自由的合同拘束力是不可想象的,[49]只有在意思表示人有意識地、無瑕疵地做出允諾的情況下,嚴守合同才有其正當性。 [50]在實質之意思自由無法被保障,反而為他人決定所妨害的情況下,被妨害之人存有解銷利益。
但從合同對立關系來看,消費者具有解銷利益,即不受約束的利益,但其相對人享有存續以及受約束的利益,并且對合同的存在與約束力存有信賴利益。[51]如要否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通常除須具備意思表示瑕疵之前提外,尚需有可歸責于相對人的事由,如欺詐或脅迫情況下的“故意”要素。
消除利益與意思瑕疵以及可歸責事由是成正比的,意思瑕疵越嚴重、允諾人的表示瑕疵越可歸責于允諾受領人,在利益衡量上越有利于消除利益人,如欺詐的情況;如果意思瑕疵不可歸責于允諾受領人,那么就須嚴守契約,如立法政策上允許撤銷,則應給出補償,如錯誤的情況。
在上門交易場合,經營者的歸責基礎并不僅僅取決于特定場合對決定自由的威脅,而是取決于經營者制造、利用該場合而產生該威脅的因果關系。[52]經營者制造和利用這些場合對消費者構成特別危險,經營者應對消費者的意思形成承擔更高的責任,況且經營者具有控制意思表示瑕疵危險的能力。另外,經營者是交易的最大受益者,將行為風險分配給獲利者有其正當性基礎。經營者在本質上承擔的是行為責任。
在消費者撤回權的情況下,經營者負有告知撤回權之義務,故亦不得對訂立合同之存續產生信賴。
基于上述理由,賦予消費者任意之撤回權,有其正當性理由,并沒有危及經營者的信賴利益乃至法律的安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修訂時應設置經營者告知撤回權之義務,在利益衡量上應考慮經營者信賴嚴守合同的利益。
(三)法律效果上的利益平衡
在消費者合同被撤回的情況下,為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德國立法者決定對消費者撤回權適用解除權之法律效果。也就是說,意思表示或合同被撤回后,合同關系轉化為清算關系(Ab-wicklungsverhaeltnis)。當事人原則上相互返還受領之給付;在不能返還等情況下,得進行價值賠償;在特定情況下,解除權人的價值賠償義務得被免除;就用益以及費用通常也得返還。
由于利益狀況不同,消費者撤回權的法律效果也有很多不同于解除權法律效果之處,在消費者僅負有寄回義務的情況下,其費用原則上由經營者承擔。消費者行使撤回權返還自經營者處獲得之物的,由經營者承擔貨物毀損滅失之風險。
另外還有一點與解除權的法律效果不同,即消費者對于合理使用而產生的價值減損,亦須承擔賠償責任,但經營者必須在簽訂合同時就以書面方式告知該法律效果,而且要明示避免價值減少之可能性。對此規則還存在一個例外,即如果價值減少是因為檢驗貨物而造成的,消費者即不負賠償責任。
在解除權情況下,權利人對于偶然或者盡到通常注意義務仍產生的毀損滅失不承擔價值賠償責任,該規則不適用于撤回權之情況。其原因在于,撤回權并不以經營者客觀違反義務為構成前提,而且在消費者被告知享有撤回權的情況下,并無理由信賴其可以最終保有該標的物。[53]如果經營者沒有依法告知撤回權,消費者僅就其故意或者重大過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三、消費者撤回權的體系歸屬
在德國,消費者撤回權制度產生于民法之外,其出現在特別立法中。而在我國,存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這一基本法律,有關消費者撤回權制度應在這一基本法律中予以規定。但從德國法經驗來看,其采取了體系化之思路,即將特別法上的撤回權統一納入民法典之中。2000年,德國立法者將消費者撤回權并入民法之中,統一規定在《德國民法典》第361a條中,[54]并廢除了《消費者信貸法》、《上門交易法》、《分時使用住宅法》以及《遠程銷售法》等單行法。在 2002年1月1日德國債法現代化之后,《德國民法典》第361a條被擴展為5條,即第355條至第359條,分別規定了撤回權的構成前提、效力以及法律后果等。《德國民法典》第312條、第312a條規定了上門交易規則,第312b條以下規定了遠程銷售合同,第495條、第499條、第503條、第 505條規定了消費者借貸合同、融資輔助以及分期交貨合同。[55]盡管適用撤回權的具體類型不同,但在撤回權的構成前提、行使與消滅上都是共同的,即統一適用《德國民法典》第355條至第359條之規定。
為什么要將消費者撤回權這一特別法的規定歸入民法典呢?其主要理由在于明確一般法與特別法之關系。若特別法獨立于民法體系之外,在法律適用時,應多考慮特別法之適用,而不考慮一般法之適用。長此以往,一般法的規則將如同“具文”,并無用處。同樣是合同被解銷,在合同被解除的情況下,其法律效果是合同清算關系,而在撤回權的情況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若不考慮民法或合同法的一般規則而另行規定的,并不符合同樣情況同樣處理的一般正義之要求。消費者撤回權制度適用于所有的以消費者為一方當事人的合同,這幾乎占據了合同關系的半壁江山,其適用領域日益增大,而一般法的適用范圍反而有限,何為特別,何為一般,易生異議。所以,若要將消費者撤回權歸入民法典,就須澄清其在民法體系中的位置。
(一)效力模式
有爭議的是,在撤回期間,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如何,合同是待定有效還是待定無效?在撤回期間,當事人是否享有合同的履行請求權?
根據撤回期間意思表示以及合同狀態,法律上構建了兩種效力模式的撤回權。[56]
1.無效模式。消費者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甚或整個合同在撤回期限屆滿之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撤回權之行使阻止合同因沉默而產生效力。在2000年6月 30日之前,即消費者撤回權沒有被統一歸入《德國民法典》之前,單行法中均采此效力規則。在此之后,《外國投資份額銷售法》和《投資公司法》中仍規定有此種模式的撤回權。其典型表述為:指向買賣的意思表示僅在買受人未在兩周內書面撤回時才具有約束力。就經營者方面而言,其受意思表示約束,并無撤回權。在撤回期間,意思表示乃至合同是待定無效的(schwebende Unwirksamkeit)。
2.有效模式。根據《德國民法典》第355條規定(原《德國民法典》第361 a條第1款規定),消費者的意思表示自始有效,即只要雙方約定在合同訂立時雙方的履行請求權即產生,但在消費者于法定期限內撤回該意思表示,則其就不再受其意思表示約束。就經營者方面而言,其受意思表示約束,并無撤回權。在撤回期間,意思表示乃至合同是待定有效的(schwebende Wirksamkeit)。
兩種模式的區別在于,根據無效模式,在撤回期間,雙方是沒有履行請求權以及瑕疵擔保請求權的;[57]在有效模式下,雙方享有履行請求權以及瑕疵擔保請求權。在利益衡量上,后者比較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在無效模式下,撤回權具有權利阻礙功能,即阻礙意思表示具有效力;而在有效模式下,撤回權具有權利廢止之功能。[58]
(二)法律行為效力上的體系歸屬
在合同法上,作為表示人法律行為約束力標準的并非實質意思(materialer Wille),而是所謂的形式意思(formaler Wille),該形式意思是向外的、自受領人角度觀察的意思。而之所以形式意思對法律行為的約束力是決定性的,其原因并非在其自身,而是基于這樣一種推定,即形式意思是表意人真實、實質意思的表現。所以,若形式意思偏離了實質意思,或者作為表示基礎的意思不自由,法律就會阻止其效力。[59]
根據意思瑕疵程度以及瑕疵表示的對外效力,法律上提供了四層保障形式意思受真實意思約束的機制:(1)意思表示的主觀事實構成制度,如表示意思是否是意思表示的必要構成要件,如是則不具有表示意思,意思表示即不成立。(2)無效制度,如違反法律或善良風俗而無效。(3)效力待定,如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之行為,其效力待定。(4)撤銷,如欺詐或錯誤行為。
如上所述,消費者撤回權的效力有兩種模式,在這兩種效力模式下,撤回權在體系歸屬上各有不同。
1.無效模式下的體系歸屬。無效模式可以歸人效力待定類型。此時,意思瑕疵是比較重大的,故法律規定其對于表意人自始并無約束力,但事后可經過追認或其他方式而有效。
與消費者撤回權可以類比的是限制行為能力人法律行為的效力待定狀態。在精神弱勢與信息弱勢類型中,消費者于合同訂立時都出現了“無能力”的情況,這種能力是經濟上的行為能力(wirtschaftliche Geschaftsfahigkeit)。[60]
但與限制行為能力情況下的效力待定規則不同,意思表示發生效力并不是經過第三人追認,而是在撤回期間經過后,先前的意思表示才會發生效力。時間經過的效力是通過沉默的方式表現的,而通過可推斷之沉默確認負載真實意思的原始意思表示,該意思表示是立法者類型化的、不可推翻的并推遲到期間經過才發生效力的意思表示。[61]撤回期間屆滿時,即思考期間經過后,消費者獲得了向經營者表達意思之能力。
有學者認為,該推定之沉默并非法律行為,而是法律上行為(Rechtshandlung),并不適用法律行為制度中的行為能力以及以行為能力為前提的規則。因為即使意思表示的主觀構成前提不滿足,撤回亦發生法律效果,即擊破沉默的權利表象,使合同確定無效。[62]故并不適用法律行為制度中的行為能力以及以行為能力為前提的規則。
沉默是對原意思表示的確認,具有表示效力,具有可撤銷性,如基于對沉默法律意義的錯誤而撤銷該沉默,但由于法律規定了經營者之告知義務,故幾乎不存在錯誤之可能。
有疑問的是,沉默是否具有溯及效力。在行為性質上,沉默是一種確認(Bestatigung),故其并無溯及力,對于過去并無效力,因為確認在法律性質上是新的行為。[63]
在無效模式下,撤回權本身為形成權,通過單方的表示即可排除已經作出的意思表示,即變更了權利狀況。在理論上,即使合同未完全有效或者待定無效,也可以具有形成權效力。比如,無效的法律行為也可以被撤銷。[64]
2.有效模式下的體系歸屬。有效模式可以歸入可撤銷類型。在立法者看來,其意思瑕疵并不十分嚴重,故規定其自始有效,但可以事后撤回,該撤回具有溯及力。消費者撤銷權與可撤銷制度類似,與解除權制度并不類似,解除權制度的規范目的并不在于保護表示人的實質意思自由。[65]
撤銷權以意思瑕疵為前提,而撤回權的行使并不需要說明任何理由。這一點并不能否認撤回權類似于撤銷權,因為二者在功能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保護自由意思的形成。在撤回權情況下,雖然不需要意思瑕疵這一要件,但需要法定類型這一前提,法定類型免除了消費者證明意思形成瑕疵的義務。在法定類型情況下,意思表示瑕疵為法律所推定,且不可推翻。[66]
根據《德國民法典》第355條第1款第1句的表述,行使撤回權后,消費者不再受其整個意思表示的拘束,而非不再受約定的給付交換約束。故類似于撤銷權的消費者撤回權,具有溯及既往地廢止意思表示之效力。[67]
根據《德國民法典》第144條的規定,撤回權是不可被拋棄的,因為拋棄在法律性質上類似于可撤銷意思表示的確認,[68]其前提是撤銷權人有可能知道撤銷以及作為撤銷原因的錯誤。由此,在確認可撤回的意思表示時,其前提也是表示人有能力自己決定,但在撤回期限經過前,根據法定的評價,表示人并無自決能力,故在撤回期間屆滿前,不能放棄撤回權。[69]
(三)消費者撤回權并非解除權
關于撤回權的性質,在德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消費者撤回權是解除權的特別類型。合同自始有效,消費者行使撤回權后,合同關系轉化為類似合同的返還之債(vertragsahnliches Ruckgewahrschuldverhaltnis)。[70]
我國有學者認為,消費者可以對已作出的要約或承諾的意思表示予以單方面撤銷,即使合同已經成立,消費者也可以單方面解除合同。[71]根據該表述,撤銷權的實質是解除權。主張消費者撤回權為解除權的主要理由為,在撤回意思表示之前,雙方當事人均具有合同上的履行請求權,單方的意思表示可以排除雙方履行請求權,并確立返還之債的關系。在體系上,《德國民法典》將其規定在“解除權”一節,十分類似于雙方合意約定解除權之情形。[72]
筆者認為,消費者撤回權并非解除權。解除權針對的是履行障礙之情況,而消費者撤回權針對的是合同成立階段意思實質不自由的情況。合同解除權所針對者,是合同有效成立后履行階段出現的障礙,與合同階段的意思表示是否具有瑕疵并無關聯,而且在消費者行使撤回權前,合同效力并非確定有效,而是待定有效(schwebende Wirksamkeit),[73]但在解除權情況下,合同是完全和確定有效的。撤回權的行使情況不限于合同情形,在經營者沒有對消費者要約進行承諾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撤回,但此時并無解除之可能。
雖然撤銷的法律效果是不當得利之返還,但規定消費者撤回權的法律效果為不當得利返還關系,卻存在不合理之處。例如,在不當得利人善意的情況下,其僅負有返還既存利益之義務,在消費者撤回權情況下,通常企業須履行告知義務,并不存在善意不當得利的情況。有鑒于此,德國立法者將消費者撤回權的法律效果規定為解除權的法律效果。
但這里似乎存在一個矛盾,撤回權在法律性質上類似于撤銷權,但在法律效果上,《德國民法典》明文規定其不適用于不當得利之規定,而同于解除權的法律效果。據此,能否認為撤回權是一種特別的解除權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德國聯邦政府認為撤回權規則比較類似于效力待定法律規則,即將其規定在《德國民法典》第 130條以下,但并沒有將其規定在總則部分,因為其法律效果為解除權的法律效果,如果將撤回權的構成和行使規則與法律效果分別規定,會增加理解與適用的難度,故將其規定在解除權之后、債法總則之中。[74]也就是說,德國立法者即使規定撤回權的法律效果與解除權的法律效果相同,也沒有認為撤回權的法律性質就是解除權。其次,從解除權法律效果的歷史發展來看,其本身不過是不當得利法律效果的特別規定,在合同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分配以及在用益返還與費用返回上作了不同于不當得利法律效果的規定。在規則結構上二者是一致的,即起決定性作用的都是給付受領人與返還債權人是否已經知道具體合同失敗的可能性,以及受領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返還之標的物的毀損滅失有過錯。[75]
四、結論
消費者撤回權之規范目的在于救濟消費者意思形成之障礙,在其于精神上或信息上處于弱勢的情況下,給予消費者一定期間予以思考,由其決定撤回意思表示還是使意思表示產生效力。
撤回期間制度為消費者撤回權制度中的核心內容,其應當以經營者告知撤回權、收到貨物或者獲取信息等時點開始起算,起算點之確定應以其能夠真實形成意思為準。
消費者撤回權不同于消費者退回權,后者較有利于經營者,不僅告知義務有所減弱,而且消費者存在先履行之義務,故僅在特定領域中存有特別理由情況下方才應予允許,還是應以消費者撤回權為一般之原則。
在消費者撤回權的構成前提上,作為撤回權人的消費者并不需要給出撤回之理由甚或證明其撤回之理由,既不需要有對意思決定的真實妨礙,也不需要考慮撤回動機,其實質為任意之撤回權。在利益衡量上,消費者解銷契約的自由與經營者信賴契約嚴守的利益相沖突。要否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除了須具備意思表示瑕疵之前提外,尚需要有可歸責于相對人的事由,于上門交易或遠程銷售情況下,可歸責事由來自于經營者的行為,其為行為責任,并不根據過錯歸責。由于經營者負有告知撤回權以及信息提供之義務,其并無信賴契約將來有約束力之根據,故賦予消費者撤回權有其合理根據。
消費者撤回權的效力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無效模式,一種是有效模式。無效模式下的意思表示處于待定無效狀態,有效模式下的意思表示處于待定有效狀態。在前者,推斷之沉默具有確認待定無效意思表示有效的功能,而撤回權具有阻礙意思表示有效的功能;在后者,撤回權可以歸入可撤銷之類型,一旦行使撤回權,意思表示即為確定無效。
注釋:
[1]參見遲穎:《論德國法上以保護消費者為目的之撤回權》,《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6期;周顯志、陳小龍:《試論消費信用合同“冷卻期”制度》,《法商研究》2002年第5期;嚴歡歡:《冷卻期制度研究》,《河南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4期。
[2]參見張學哲:《消費者撤回權制度與合同自由原則—以中國民法法典化為背景》,《比較法研究》2009年第6期。
[3]Vgl. HKK zum BGB/Schmoeckel, § § 312 if.,Rn.75; 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I, AllgemeinerTeil,18.Auflage,2008, S.282, Rn.585.
[4]《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第28條規定:“經營者以上門方式推銷商品的,應當征得被訪問消費者的同意。上門推銷時,推銷人員應當出示表明經營者授權上門推銷的文件和推銷人員的身份證件,并以書面方式向消費者告知推銷商品的性能、特性、型號、價格、售后服務和經營地址等內容。經營者上門推銷的商品,消費者可以在買受商品之日起7日內退回商品,不需要說明理由,但商品的保質期短于7日的除外。商品不污不損的,退回商品時消費者不承擔任何費用。”
[5]Vgl.G. Reiner, Der vebraucherschtltzende Widemif im Recht der Willenserkdanmg, AcP 2003, S.4.
[6]Vgl.Wolf/I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2004,§39, Rn.20, S.718.
[7]Vgl. Heck, Wie ist den Mi(3brauchen, welche sich bei den Abzahlungsgeschliften herausgestellt haben, entgegenzuwirken 131, 180f.,192.
[8]同上注,第148頁。
[9]Vgl. Gesetz tlber den Vertrieb auslandischer Investmentanteile und fiber die Besteuenmg der Ertrgge aus auslandischen Investmentan-teilen v. 28. 7. 1969. BGB1 1986.
[10]Vgl. Lorenz, Der Schutz vor dem unerwtlnschten Vertrag, 1997, 5.123.
[11]Vgl.Gesetz fiber den Widerruf von Haustargeschaften mid hnlichen Geschliften v. 16.1.1986, BGBI 1122.
[12]Vgl.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355, Rn.6; Wolf/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2004, § 39, Rn.11, S.715.
[13]Vgl. H. Eidenm(Mer, Die Rechtfertigung、Widernifsrechten, AcP 210, S.68.
[14]Vgl.Gesetz betreflend die Abzahlungsgeschaftev.16. 5.1894, geandert durch Gesetz v. 15.5.1974, BGB1 I 1669.
[15]Vgl.Verbraucherkreditgesetz v. 17.12.1990, BGBI 2840.
[16]Wolf/Larenz, ABgemeiner Teil des BGB, 2004,§39, Rn.18, S.717.
[17]Vgl.Gesetz zum Schutz der Teilnehmer am Femunterricht v. 24.8.1976, BGB1 12525.
[18]Vgl. Gesetz Ober den Versichemngsvertrag v. 30.5.1908, getndert durch Gesetz zur Andening versichemngsrechtlicher Vorschriftenv. 17.12.1990, BGB12864.
[19]Vgl. Gesetz fiber die Verauβerung.Teilzeitnutzungsrechten an Wohngebauden v. 20.12.1996, BGBI 12154.
[20]Vgl. Femabsatzgesetz v. 27.6.2000, BGB1 I897.
[21]Vgl.Staudinger/Kaiser, BGB,Neubeatbeitung 2004, § 355, Rn.7;同前注[3], Medicus、 Lorenz書,第285頁,邊碼592。
[22]Vgl.Wolf/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2004,§39, Rn.18, S.717.
[23]同前注[13], H. Eidenmaller文,第68頁。
[24]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9頁。
[25]同前注[13], H. Eidenmttller文,第71頁。
[26]Vgl. Medicus, Verschulden bei Vertragsverhandlungen, in Gutachten und Vorschlage zur Uberarheitung des Schuldrechts, Band I,2000, S.519 ff.
[27]上門與剛成年的、無收入、無財產的高中生簽訂“嫁妝置辦合同”,價款12000馬克,該合同被法院認定違背善良風俗(BGH NJW 1982, 1457);誘導精神、身體殘疾老人倉促決定簽訂超出其履行能力并無需要的房屋粉刷合同,價值14000馬克,該合同也被宣布違背善良風俗(OLG Frankfurt NJW-RR 1988, 501).
[28]Vgl. LG Oldenburg MDR 1969, 392; AG Nttrtingen NJW-RR 1996, 392.
[29]Vgl. Begr. BR-Entwurf, BT-Drucks.7/4078, S.8.
[30]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10頁。
[31]Vgl. BGH NJW 2007, 1946;同前注[3], Medicus/Lorenz書,第288頁,邊碼600。
[32]同前注[3], Medicus/Lorenz書,第288頁,邊碼599。
[33]Vgl. EuGH NJW 2002, 281, in 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4. Aufl.,S.192.
[34]針對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德國法規定了經營者的信息提供義務。經營者對于合同標的的重要細節要提供信息,如果經營者沒有提供相關信息給消費者,或者導致消費者意思表示無效,或者導致撤回期間不起算。
[35]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10頁。
[36]Vgl. Brox/Walker, ABgemeines Schuldrecht, 34. Aufl.,S.192.
[37]Vgl. 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 § 356, Rn.2.
[38]Vgl.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355, Rn.3.
[39]同前注[3], Medicus/Lorenz書,第288頁,邊碼598。
[40]Vgl. HKK zum BGB/Duve,§§1-14, Rn.78.
[41]Vgl.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355, Rn.5;同前注[36], Brox、 Walker書,第189頁。
[42]同前注[36], Brox/Walker書,第181頁。
[43]同前注[3], Medicua/Lovenz書,第283頁,邊碼586。
[44]同上注,第283頁,邊碼587。
[45]同前注[3], Medicus/Lorew書,第283頁,邊碼592。
[46]同前注[36], Brox/Walker書,第186頁。
[47]同前注[10], Lorenz書,第29頁。
[48]Vg1.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 Auflage, 1979, II, S. 49.
[49]Vgl. Stathopoulos, Probleme der Vertragsbindung und Vertragsltsung in rechtsvergleichender Betrachtung, AcP 194, S.543, 552.
[50]同前注[10], Lorenz書,第28頁以下。
[51]同上注,第38頁。
[52]同上注,第164頁。
[53]同前注[3], Medicus/Lorenz書,第290頁,邊碼604。
[54]Vgl. Gesetz ttber Femabsatzvertrage und andere Fragen des Verbraucherrechts sowie zur Umstellung.Vorschriften aus Eum am 30.6. 2000, BGBI I897.
[55]《德國民法典》的一般性規定可以適用于遠程授課之情形,但不能適用于《外國投資份額銷售法》、《投資公司法》以及《保險合同法》規定之情形。
[56]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4頁以下。
[57]Vgl. B. Boemke, Das Wiedemifarecht in allgeniinen Verbraucherschutzrecht, AcP 2003,S.165; Certa, Widemrf und Schwebende Umwirksamkeit, 2000, 33.
[58]同上注,B. Boemke文,第166頁。
[59]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15頁。
[60]同上注,第19頁。
[61]同上注,第20頁。
[62]同上注,第21頁。對于無效行為確認的理論,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頁以下。
[63]同上注,迪特爾·梅迪庫斯書,第405頁。
[64]此即Kipp的法律上雙重效果說,參見前注[57],B.Boemke文,第178頁。
[65]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27頁。
[66]同上注,第28頁。
[67]同上注,第30頁;Gernhuber, WM 1998,1797,1804.
[68]對于無效行為確認的理論,參見前注[62],迪特爾·梅迪庫斯書,第407頁
[69]同前注[5], G. Reiner文,第36頁。
[70]Vgl. HKK zum BGB, § 355, Rn.46.
[71]參見金福海:《消費者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頁。
[72]Vgl. Staudinger/Kaiser, BGB, Neubearbeitung 2004, § 355, Rn.18.
[73]Vgl. Mankowski, WM 2001, 793, 794.
第9篇:民法典的由來范文
一、關于物權請求權范圍、性質的爭議及其評析
(一) 物權請求權范圍的爭議
對于物權請求權的具體范圍,理論上存在分歧意見。多數學者認為,其應包括三種,即“返還原物請求權”、“妨害除去請求權”、“妨害防止請求權”;[20]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除前述三種之外,物權請求權還應包括“恢復原狀請求權”。[21]
查有關學者介紹的資料,傳統民法理論一般不認為恢復原狀請求權屬于物權請求權之一種,但臺灣學者對此有所爭論。一些學者認為,由于恢復原狀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難以區分,故應僅采用損害賠償請求權:當發生所有物遭受他人侵害時,鑒于物的效用主要體現在經濟價值上,賠償損失即可使受害人利益得到滿足,對加害人亦較便利,故受害人只能請求金錢賠償而不能請求恢復原狀。物如遭受侵害,受害人得請求賠償全部價值,物如僅喪失部分經濟價值,則受害人只能請求賠償物因損毀所減少的價值。[22]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96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應向背害人賠償其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這一規定,顯然否定了恢復原狀請求權的成立,即臺灣地區立法上系將恢復原狀請求權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所替代。
但對此觀點其他學者并不贊成,其認為物的毀損與物的滅失有所不同,如果造成滅失應當以金錢賠償,但如果僅造成毀損則應當恢復原狀。[23]尤其當被毀損之物并非可替代物時,加害人應當負修繕責任,不能夠通過金錢賠償的方法而請求受害人讓與其物的所有權,故承認被害人對恢復原狀或價格賠償由選擇權,其主動在于被害人,所有權失其保障之顧慮,不復存在。[24]
對上述觀點,內地也有學者響應,認為在所有人的物受到他人侵害且可修復的情況下,不應以金錢賠償代替恢復原狀。并據此證明恢復原狀應當成為一項獨立的物權請求權。[25]
而一些反對恢復原狀請求權應列為物權請求權的內地學者所持理由是:恢復原狀是侵權責任或違約責任的救濟方式,如《德國民法典》關于恢復原狀的規定位于債編之下(第249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也將其規定在債編之下(第213條),即使在我國《民法通則》,也是在侵權責任之下加以規定的(第117條)。因此,其為債權性質的請求權,而不是物權請求權。[26]
上述就恢復原狀請求權是否為物權請求權的爭議極有意義,但所見爭者的論據卻使人不得要領。前述就此持“贊同論”的臺灣及內地學者侃侃而談之所及,僅為恢復原狀請求權不應被損害賠償請求權(金錢賠償)所替代,此言甚是,但并不能說明此種請求權應當屬于物權請求權而非債權請求權。而持“反對論”的學者則單純以某些立法上將恢復原狀請求權列入民法典債編規定來說明其非為物權請求權,顯然也難成其道理。
我認為,物權的保護方法中,恢復原狀當然是一種獨立的請求權(在物被部分損毀的情況下,禁止受害人在請求加害人修復還原或者賠償損失之間進行選擇是毫無理由的)。而此種請求權是否為物權請求權,應當看其是否符合物權請求權的特征。
“恢復原狀”(或回復原狀)在立法和理論上有不同含義,有時指恢復受侵害的權利之原來狀態(如物的返還或損壞物的修復),有時則還包括以非貨幣之等價物填補損害。[27]但此處之“恢復原狀”,僅指對遭受損害的物之部分或者全部修復還原。從與物權的關系上看,恢復原狀請求權因物權之保護所生(基于物權發生),與物權同命運(物權不存在,恢復原狀請求權也不存在;物權轉移,此項權利隨之而轉移,并且,不得脫離物權而單獨轉讓),同時,與損害賠償請求權全然有別,此種請求權之目的大體上也可視為對物權圓滿狀態的恢復。因此,如果純粹予以技術上的分析,恢復原狀請求權完全符合物權請求權的一切特征,當屬物權請求權之一種無疑。
然而,如果物權請求權本身的存在即非純粹邏輯分析的結果,那么,恢復原狀請求權是否為物權請求權之一種,便須打上問號。這一問題,留待下文探討。
(二)物權請求權性質的爭議
物權的請求權效力之效果為物權人對于妨害物權行使的特定人享有請求權利。對此種請求權利,理論上稱為物權請求權或者物上請求權。
依通說,在立法上,物權請求權制度為1900年《德國民法典》所創設。[28]其原因,與德國民法將物權與債權嚴格區分有直接關系。但在此之前,羅馬法及法國民法訴訟法上有關保護所有權的各種訴權,實際上早已形成了物權請求權的基本內容。[29]《德國民法典》以后,《瑞士民法典》[30]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31]均對物權請求權作了明確規定。《日本民法典》雖然沒有對物權請求權做出一般性規定,[32]但這一制度在司法實務上和理論上均得到承認。[33]
作為對物權之直接支配效力的保障,與物權的排他效力、優先效力及追及效力一樣,物權請求權也是基于物權人對標的物的直接支配權而產生,此點在現今學說上并無爭議。[34]但就此種請求權的性質,日本民法理論上卻有“債權說”、“物權說(物權作用說)”、“準物權說”、“物權效力所生請求權說”以及“物權派生的請求權說”等不同解釋。[35]歸納起來,或認其為債權(其為請求特定認為特定行為的獨立權利,純屬債權),或認其為“不純粹之債權”(其為類似于債權的一種獨立請求權,但從屬于基礎物權并與之同命運),或認其為依附于物權的一種請求權(其基于物權的作用而生,依存于物權而存在、消滅,非獨立的權力)。上述觀點中,認為物權請求權“雖是一種獨立的請求權,欲并非是一種純粹的債權”的理論在日本占上風。[36]
依德國民法理論的通說,物權請求權“是一種附屬性權利而不是獨立的權利”,其理由是:物權請求權基于保障物權的完滿狀態而生,并無獨立的存在目的,且更重要的是,此種權利完全不可以與本權脫離,不可以獨立地被讓與第三人(凡獨立的財產權利,必可予以獨立轉讓),同時,此種權利具有消極性,僅在物權的積極權能的行使受到妨礙時方可有行使的機會。[37]
而我國學者則多認為,物權請求權既不同于債權,也不同于物權,而是一類獨立的請求權。[38]爭議不可謂不大。
圍繞物權請求權的性質所展開的爭議于立法模式的選擇有重大意義。其爭議的主題是“物權請求權是否為債權之一種”?如其為債權或者“準債權”,則應納入債權的體系(侵權所生之債),適用債法的一般規則;如其非為債權而為物權之組成部分(物權支配效力之當然結果)或者為既非債權亦非物權的一種“獨立權利”,則可以納入物權法的體系,得不適用或不完全適用債法的一般規則。
無論如何,物權請求權不是物權之一種,此當無可置疑。而依德國民法將物權與債權作為財產權類型的基本劃分之后所形成的通常觀念,一項實體性的財產權利,[39]如非物權,即為債權。既然如此,物權請求權為什么不是債權呢?就主張物權請求權非為債權或者應獨立于債權的眾多學者所持理由來看,其主要之點在于:
1.物權請求權基于物權產生,與物權不可分離。其雖以要求特定人為特定行為為權利內容,但此種權利旨在保護物權,其來自于物權的支配內容,目的在于使物權恢復圓滿狀態和支配力。只有當物權人的支配權利所到他人侵害時,為恢復物權的圓滿狀態,物權人才能行使此項請求權,故物權請求權與物權同其命運,此與債權之完全獨立并不相同。
2.物權請求權基于對有體物的保護而生,其產生根據在于物權是對客體進行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權利。返還原物、排除妨害、恢復原狀均是針對有體物的保護而創設,此與債權產生的原因亦不相同。
3.物權請求權的產生原則上不考慮相對人是否有過錯,受害人只須證明侵害或妨害的存在,即可提出請求,不須就侵害人的過錯承擔舉證責任。而侵權行為所生之債權的產生一般以侵權行為人的過錯為要件。
4.物權請求權的效力優先于債權請求權,當二者并存時,前者優先于后者。如在破產程序中,所有人對其物享有取回權,此種取回權實際上是由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派生的,而此種權利當然應優先于一般債權而受到保護。
5.物權請求權不適用消滅時效,而債權請求權適用消滅時效。物權請求權系因與物權相依存,只要物權存在,則于物權受侵害時,物權請求權即行發生,亦即與物權同在,故應非消滅時效之客體。[40]
前述理由又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物權請求權之獨立性源于其與物權的緊密聯系(產生基礎為物權;不可脫離物權而單獨轉移;以保護“有體物”為目的等);二是其產生條件(相對人有無過錯)及其效力(是否具有優先性及是否適用消滅時效)不同于一般債權。
(三)評析
物權請求權本質上究竟是不是既區別于物權,又區別于債權的一種“獨立權利”?這個問題,顯然涉及到權利的基本分類方法和分類目的。
就權利的分類而言,至少需要遵循兩項游戲規則:一是權利分類的根據(角度)必須同一;二是用于分類的權利(分類所針對的權利)必須處于同一位階。現依據這兩項標準分析如下:
1.依據權利的實質內容進行分類:物權請求權本質上應當屬于債權。
物權與債權的區分,其依據的是財產權利的基本特性。而財產權利基本特性的區分根據,則應是財產權利的實質作用和具體內容(權能)。由此,自德國民法以來,實體財產權利被區分為物權(對物的直接支配權)和債權(對特定人以財產給付為內容的請求權)。毫無疑問,債權是對一類請求權最為抽象的高度概括:就債權而言,盡管存在其他請求權(如身份上請求權、訴訟請求權等),但凡為特定民事主體之間請求為特定財產給付者,應均屬債權。換言之,物權之所以是物權,關鍵在其對物的直接支配性,債權之所以是債權,關鍵在其對人的請求性(限于財產給付)。至于物權或者債權產生的根據、目的等等,均不影響其權利本身的屬性:不同的債權自有不同的產生依據以及不同的設立目的,如果說物權請求權因基于物權產生或基于物權保護之目的而不屬債權,則不當得利和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同樣得因物權之保護而產生。因此,前述以“物權請求權基于物權產生,基于保護有體物而產生,旨在保護物權,使物權恢復圓滿狀態和支配力”為理由,證明其性質上不屬于債權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前述理論以“物權請求權的產生無須當事人有過錯”否定其債權性質的理由亦難成立。債權的產生是否與債務人的過錯有關,應依不同情形對待:損害賠償之債固然一般以債務人(侵權行為人)的過錯為生成條件,但其他各類債權的產生(不當得利、無因管理以及契約之債)則根本不存在債務人有無過錯的問題。
至于強調物權請求權與物權不可分離、物權請求權不可單獨轉讓(而債權具有獨立性,亦可單獨轉讓),并以此說明物權請求權與債權存在本質差別的理由,亦不能成立。某種權利能否轉讓或者能否脫離其依附的其他權利而為轉讓,只是表現了該種權利與某一特定人格或者其他某種權利的相互聯系而已,與其權利之性質應無關系。事實上,與此種論述相反,債權亦并非全為獨立存在的權利,例如保證擔保權,其債權性質無可置疑,但此種權利既不因其必須依附于被擔保的主債權的存在而存在而不成其為一種債權,亦不因其不得單獨轉讓而不成其為債權。如果說物權請求權因不得脫離物權而單獨存在或者轉讓,從而便成為該物權之效力的一部分,或者因此而不能成為一種債權的話,那么,抵押權是否也應因不得脫離主債權而單獨轉讓從而成為主債權效力的一部分,或者因此而不能成為一種物權呢?人身傷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因其專屬性而成為人身權效力的一部分,或者因此而不能成為一種債權呢?
因此,以物權請求權的產生基礎、保護目的、相對人有無過錯以及能否獨立存在以及單獨轉讓來否定其債權性質的理由,不能成立。
至于物權請求權在實現上是否具有優先于其他債權的效力,以及是否不適用于一般債權均得適用的消滅時效及其原因,以下將作專題討論。但即便此兩項結論能夠成立,仍不足以從根本上否定物權請求權本身的債權性質:
首先,在實現上優先于普通債權的權利并不一定都不屬于債權。除物權優先于債權之外,如前所述,某些債權(企業破產清算時職工的工資、勞保福利等債權等)在特定情況下也有可能優先于其他債權。事實就是,權利的優先性的來源十分復雜,一項權利是否具有優先性,與該種權利的基本屬性并必然聯系。我們不能說凡優先于債權的權利就肯定是物權,也不能說其肯定就不是債權。因此,以物權具有優先于一般債權的效力作為否定其為債權之一種的理由,本身所設前提就是錯誤的。
其次,某種權利是否適用某種時效,亦非判斷該種權利之屬性的依據。就物權而言,盡管取得時效專為物權而設,但并非一切物權均得適用。如經過登記的不動產物權,依法即不適用取得時效(取得時效僅適用于未經登記或者錯誤登記的不動產及),但不能就此證明其不是物權。而雖然消滅時效專為債權而設,但一項債權是適用普通消滅時效還是特別消滅時效,甚至根本不適用消滅時效,也并不等于該項債權就當然成為債權之外的另一種“獨立權利”。如依我國《擔保法》的規定,主債權人因保證合同而對保證人取得的擔保權,得因除斥期間而非消滅時效而消滅,[41]這并不否認保證擔保權屬于債權。
結論就是,物權請求權作為一種特定當事人之間為特定給付之請求權,其性質上當屬債權無疑。
2.根據權利分類的角度或者標準:物權請求權無資格與債權“分庭抗禮”
為了進一步揭示財產權利的各種屬性,在物權與債權分類的基礎上,伴隨分類角度的轉換,物權與債權在各自的領域繼續被予以分類:根據物權人與所支配的財產的關系的聯系緊密程度(是支配屬于自己的財產或者支配屬于他人的財產),物權被區分為自物權與他物權;根據他物權設定的不同目的,他物權則又被區分為用益物權與擔保物權,等等。而根據債權所生之不同根據,債權又被區分為契約之債權、侵權之債權、無因管理之債權以及不當得利之債權等等。而“請求權”作為一種權利類別的出現,卻與物權和債權的區分毫無關系:當以權利的作用(法律上之力)作為分類標準并將分類的對象擴張于實體財產權之外時,權利被劃分為“支配權、請求權、形成權與抗辯權”。其中,除形成權與抗辯權屬程序性權利之外,[42]支配權和請求權分別為物權、債權、人身權以及知識產權等實體權利所包含或者派生。其中,請求權的“發現”,被認為是民法理論研究的重大成果。
請求權(Anspruch)的概念系由德國法學家溫德賽(Winscheid)由羅馬法上的Actio發展而來,認為于訴權((公權)之外,尚存在實體法上的請求權(私權)。基于其不同發生基礎,請求權被進一步區分為物權請求權、債權請求權、人格權上的請求權以及身份權上的請求權等。對于請求權的性質,學者有十分確切的說明:請求權系由基礎權利而發生,為“權利的表現,而非與權利同屬一物”。[43]換言之,任何請求權均為權利產生的權利:債權請求權為債權的基本權能,由債權本身所包含;物權請求權、人格權上的請求權以及身份權上的請求權等則多因權利受第三人侵害時發生。
這里,我不能不指出,既有理論在請求權分類問題上并未嚴格遵守邏輯規則:
就實體權利的分類而言,在“財產權”與“人身權”的分類基礎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與人格權、身份權等應當屬于下位概念的同一位階,而在前述權利存在之基礎上派生出來的各種權利(包括各種請求權),則應當屬于再下位的同一位階。因此,當物權、知識產權及人格權和身份權被指明為“支配權”時,與此相對應,就“請求權”的范圍,則只應指明債權。與此同時,由既存權利而派生出來的請求權,也應當按其應有位階予以排列,否則,分類的角度、標準和位階就會發生混亂。
如依照嚴格的邏輯規則,有關實體權利的分類應如下圖:
分類I: 財產權 人身權
物權 債權 知識產權…… 人格權 身份權……
分類II: 支配權 請求權
物權 知識產權 人格權 身份權…… 債權……
分類III: 權利被侵害所產生的請求權
物權請求權 “債權請求權” 人格權上請求權 (某些)身份權上請求權[44]……
返還原物請求權…… 違約金請求權…… 損害賠償請求權…… 妨害排除請求權……
分類VI: 債權
契約所生之債權 無因管理所生之債權 侵權行為所生之債權……
物權請求權 人格權上之請求權 (某些)身份權上之請求權……
分析上述分類列表,可以發現,既有理論在將所謂“債權請求權”定義為債權本身所包含的請求權的同時,將之用以對應物權請求權,是完全違背邏輯規則的。
當我們言及“物權為支配權,債權為請求權”時,系從權利本身的內容出發(參見上述分類II)。在這里,請求權為債權的基本權能(債權還包括受償權能等),支配權為物權的基本權能(還包括排他權能等)。[45]因此,以債權的“請求權能”去對應物權的“支配權能”是適當的。就權利的作用而歸納出“請求權”與“支配權”等的類別,具有重大價值。可是,既有請求權理論將作為債權本身所包含的權能(請求權)去對應物權等絕對權受侵害之后所派生的請求權,便不可能不發生權利位階上的錯亂,并進而導致權利性質歸屬上的錯亂:例如,如果將與物權請求權屬同一位階的“人格權上的請求權”理解為人格權遭受侵犯以后所生之請求權,那么,此種請求權無疑屬于侵權行為所生之債權。而因其為債權,故應屬于所謂“債權請求權”之一種。此時,人格權上的請求權顯然為債權請求權所包含,不得與之并列(基于身份權遭受侵犯而產生的身份上請求權以及知識產權上請求權等亦同樣如此)。而將所謂債權請求權(實際上就是債權本身)與人格權上請求權等相提并論,無異于確認了后者并非前者。如此一來,有關權利的屬性將自相矛盾,成為亂麻一團(參見上述分類III及分類VI)。
在這里,我無意試圖否定民法理論上有關請求權基礎及其體系研究成果所存在的重大價值,但在這一體系中,所謂“債權請求權”實際上被斷定為與債權相聯系(或者基于債權而產生)的一種權利而非債權本身(債權的基本權能),卻無論如何令人難以接受。
總之,物權與債權為對有體財產權的一種基本分類。任何有體財產權,如非物權,則為債權,原本并不存在“第三者”。而物權請求權無論多么特別,其必須基于物權遭受侵犯而產生,其并非某種權利之固有的權能。因此,在請求權體系中,物權請求權當與身份上請求權等相互對應,但卻無法與所謂“債權請求權”相互對應。而從權利分類的角度和標準來講,物權請求權絕無資格與物權、債權相并列。質言之,如果承認物權請求權完全是一種實體權利、財產權利的話,那么,就必須承認其沒有資格成為“獨立于”物權與債權的一種權利。物權請求權要么是物權,要么是債權,二者必居其一。
綜上所述,如果采用嚴格的也是機械的邏輯分析法,物權請求權無論從性質上還是權利分類的規則上,都應當列入債權的范圍,與契約之請求權、侵權行為之請求權、無因管理請求權以及不當得利請求權等一起,從屬、并列于“債權”這一觀念之下。但《德國民法典》以及后來的許多重要法典都將此種請求權規定與物權法之中,民法理論也長篇累牘論證此種請求權在物權法上應當自成一體的必要性,顯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在這里筆者必須申明的是:筆者斷言物權請求權性質上應屬債權,只是想從方法論或者實證的角度,指出既有理論的某些缺陷,并非認為物權請求權應由債權法來規定,甚至并非否定此種請求權“應當”被視為一種獨立于債權的請求權。筆者認為,物權請求權是否應當脫離債權體系而成為一類特殊的、獨立的請求權并規定于物權法,關鍵并不在于其權利性質本身如何,而在其是否具有脫離債權體系的必要性即法律價值。對此必要性的判斷,則完全取決于對有關選擇之利弊所作的實證分析而非嚴格的邏輯推理。
二、物權請求權獨立于債權體系的必要性
某些學者對于物權請求權與契約所生之請求權及不當得利所生之請求權的某些重要區別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以證明其非為債權之一種。[46]但此種論述不僅變換了比較的標準(如果以產生債權的法律事實為基礎,則與契約、不當的利等相對應的債權的產生依據,應為侵權行為,而物權受侵害后產生的請求權,應歸入侵權所生之請求權范圍。因此,將物權請求權與其他侵權所生之請求權相比較,論證其非為侵權所生之債權之一種,才是應有的角度),而且意義不大:產生基礎完全不同的請求權(債權),自然會有種種不同(正如在契約之債和不當得利之債之間,我們照樣會尋找到許多重要區別一樣)。問題僅僅在于,如果將物權請求權納入債權體系,其所處的地位及其由此導致的弊端如何?
很顯然,如果將物權請求權視為債權,則其應屬侵權行為所生之債權的一種(我國《民法通則》即采用這一立場)。[47]
因侵害物權而發生的請求權主要有返還原物、排除妨害(其包括傳統理論上之“妨害除去請求權”以及“妨害防止請求權”兩種)、恢復原狀、損害賠償等四種。前三種請求權的目的為回復物權圓滿狀態,自不待論,而第四種請求權則為價值補償即填補損害。從嚴格意義上講,所謂物權請求權制度,實際上就是要把前三種請求權(或者前兩種請求權)獨立出來,首先使其脫離侵權之債,然后進一步使其脫離整個債權體系,最后將之作為一種與物權有關的獨立權利進入物權立法體系。因此,應當首先分析物權請求權脫離侵權所生之債權的必要性,然后再分析其進一步脫離債權體系(或者真正意義上的“債權請求權”體系)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