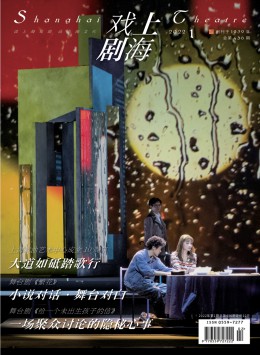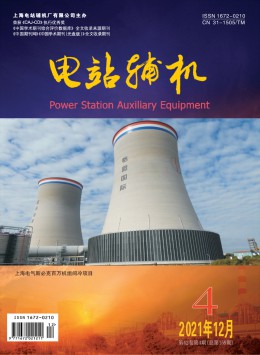關于中國夢的詩歌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關于中國夢的詩歌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關鍵詞:新月詩學 傳統詩學 西方詩學 中西合璧 “治病”
新月派在中國詩歌歷史中光彩奪目,然而不無遺憾的是它又轉瞬即逝。但是新月派詩人留下的詩歌在今天這個追新求異的時代卻仍然具有讓人看后不忍釋卷的魅力,新月派詩人兼詩論家所倡導的詩學在今天這個躁動不安的年代仍能給予人們諸多啟示。
對于新月詩歌的研究,文獻頗多并且深刻,本文暫不涉足。本文的興趣在于立足史料,挖掘出新月詩學的一些特質,讓新月詩學更加豐滿地呈現出來。
一、相關研究
黃昌勇把新月派的格律理論分為前后兩期,分別以對音節的討論[1]77和具有較強的理論色彩[1]80-81為特色;李思清評析了新月詩人的詩學探索及其文學史地位,點明新月詩人“在理性原則之下的詩學追求”[2]11,客觀地指出聞一多“三美”理論的局限性。其實,對新月派詩學的探討還可以從別的角度切入,如新月詩學的淵源等等。陳偉華較為全面地總結了前人研究,認為之前研究對新月派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探討不夠深入,提出“新月派的詩歌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割不斷的聯系”[3]22,從“人工論”、“三美原則”、“審美鑒賞”以及“‘健康’和‘不辱尊嚴’的原則”幾個方面論證了“新月派的整個詩論體系都繼承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神韻”[3]25。公允地說,新月詩學不僅僅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還有諸多證據表明它實際上還汲取了西方詩學的營養,可以算是中西合璧的寧馨兒。此外,自倡導新月詩學之初,新月派標榜的就是要治愈病態的中國文壇,從中也可以窺知新月詩論家的抱負。
由于“詩學”一詞指涉曖昧,本文在正式剖析新月詩學之前,對該詞進行簡單的界分。
二、“詩學”釋義
在西方語境下,“詩學”(poetics)一詞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同名著作《詩學》。《詩學》現存26章,主要討論了悲劇和史詩,在給出了悲劇的定義之后,詳細討論了其情節、性格、言詞、思想、形象與歌曲;之后又對史詩的原則、語言和韻律作了探討。“詩學”最初的含義便是關于詩歌的專門著作,尤指亞里士多德的著作[4]1043。當然,隨時間的推移,該詞逐漸獲取了更為豐滿的涵義,可以廣泛地指涉及詩歌的那些文學批評[4]1043,甚至是廣義地指向文學,尤見于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以及法國結構主義的相關論述中;或是指一種準則,而這種準則使得作者與讀者的交流成為可能[5]229;關于文學應該被(被允許)是什么的主要觀念[6]14。Lefevere進一步將詩學劃分為兩個組成部分:一是一個總目錄,包括文學手法、文類、主題、原型人物、場景和象征物;二是對文學所扮演的角色的觀念[6]26。Baldick一個晚近的定義倒是涵蓋了以上各義,認為詩學是“詩歌的基本原則,或文學的基本原則,抑或是對這些原則的理論研究”[7]172,并且詩學所關心的是詩歌(或文學)的突出特征,涉及其語言、形式、文類和創作方式[7]172。
“詩學”一詞出現在中國文化語境中時,從其誕生的元代[8]172直至近現代大家似乎都不約而同地取了它與詩歌相關的狹義定義,“‘詩學’概念從研究《詩經》之學,發展為泛指詩歌創作和詩藝,至元代范《詩學禁臠》以后逐漸專指關于詩論、詩體、詩法、詩評的研究”[8]176。
也正是由于“詩學”這個詞指涉曖昧,一般會把它再作界分,劃為“狹義詩學”,專指關于詩歌的研究[9]107,和“廣義詩學”,指稱文藝理論[9]108。若按照詩學在中國傳統中的定義以及在Baldick定義中與詩歌相關的部分,中國在1926年也可以稱出現了一支詩學:新月社諸位詩人兼詩學家,于1926年左右主要以《晨報副鐫―詩鐫》(以下簡稱《詩鐫》)為平臺提出了他們自己作詩的一些基本原則并進行了理論探討。這里的新月詩學顯然屬于狹義詩學,它與中國傳統文化、詩學自然有著割舍不斷的聯系,但同時它又極大地吸收了西方詩學的營養,可以稱得上是中西合璧的產物。新月詩學還有一個常為世人所忽略的特色――致力于治愈當時病態的中國文壇,這也是新月同人的宏大抱負。
三、新月詩學
新月社諸位詩人兼詩學家,于1926年左右主要以《晨報副鐫―詩鐫》為平臺提出了他們自己的詩學,既明顯地承襲了中國古典詩學,又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詩學的烙印。新月詩學從其誕生之日起,還肩負著沉重而又偉大的“責任”:治愈病態的中國文藝界。
(一)中西合璧新月詩學
陳偉華立足于新月詩學理論,論述了中國傳統文化是新月詩學的淵源所在[3]。值得補充說明一點的是,新月詩學在作詩的具體原則方法上也有明顯沿襲中國古典詩學的痕跡,詩歌的平仄和押韻就是很好的例子。新月詩學提倡詩歌要有“音節”,而韻腳和平仄則也屬于構成音節的要素[11]19,[12]49,[13]30。
中國古典詩學是講究押韻的,押韻是在句尾,出現過好些韻書,如呂靜的《韻集》,孫怖刊定的《唐韻》,陳彭年修的《廣韻》等等。特別是《廣韻》中,作詩允許“同用”,相近的韻可以通押。新月派詩論家也注意到韻的重要作用,一般認為要構成詩歌調和的音節(即現在所說的詩歌的音樂性)需要有韻等因素[11]19,[12]49,[13]30。新月派主力干將之一饒孟侃專門強調韻在詩歌中的重要作用,也主張“凡是同音的字,無論平仄,都可以通用”來押韻[12]50。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新月詩學講求押韻,是明顯地沿襲舊法。
此外,中國古典詩學講求詩歌的平仄,注重通過字音聲調的區別,平仄有規律地交替和重復,形成節奏,以實現詩歌音調的和諧。自梁代沈約的“四聲八病”說,尤其是他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的“八病”說以來,平仄逐漸成為中國古典詩學中的要素之一。而在新月派詩論家的論述中,平仄也是構成詩歌音樂性的要素之一,不容忽視[11]19,[12]49,[13]30。尤其是聞一多,他條分縷析地論證屬于聽覺方面的格律“有平仄”[13]30,通過詩歌的語言的平仄以實現其音樂性。于此,也可以窺知新月詩學講究平仄也不失為對于中國古典詩歌理論的一大繼承。
然而,新月詩學在作詩的原則方法上除了從中國古典詩學汲取的營養以外,還廣泛地吸收了西方詩學中營養,可謂中西合璧的寧馨兒。
新月詩學的旗手之一饒孟侃就曾經以聞一多的《天安門》為例,談及詩歌的節奏,認為可以分為“自然的節奏”和“作者依著格調用相當的拍子(Beats)組合成一種混成的節奏”[12]50。姑且不論第一種節奏,顯而易見的是,新月詩學所謂的第二種節奏,即在西方詩學中的Beats的觀照下由詩人精心刻意磨練出來的節奏,明顯地借鑒了西方詩學中作詩的原則和方法。此外,新月詩學的又一領軍人物聞一多也是沿用西方詩學的原則,認為詩歌的音節還要靠音尺來構成[13]30。這里所強調的“音尺”其實本來是在創作英詩時要遵循的。在這樣的作詩原則指導下進行的詩歌創作,難怪朱自清也要說他們寫成“西洋詩”了。
綜上所述,新月詩學在具體的作詩原則方法上兼容并蓄,繼承了中國詩學的傳統,同時又不失時機地借鑒西方詩學,是中西合璧的產物。
(二)治病救人新月詩學
以《晨報副鐫―詩鐫》為陣地,新月派詩人兼詩論家新月派注重發展他們以強調“格律”為特色的詩學,高舉“理性”的大旗,無疑是對初期新詩散文化弊端的匡正,要造就新詩形式重建的氛圍。在為鄧以蟄的《詩與歷史》寫的附識中,聞一多為當時中國文藝界把脈,確定它患上了“血虛癥”[11]17,于是開出藥方,極力推薦鄧以蟄的文章。時隔兩年,在新月同人的眼中似乎中國文壇尤其是詩壇仍然在遭受病魔的折磨,致使徐志摩在其執筆的《新月的態度》中痛斥時代的“變態”與“病態”,高呼要“健康”[14]8-9,認為在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創作中“感情不經理性的清濾是一注惡濁的亂泉”,要求在“這頭駿悍的野馬的身背上”“謹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14]7。新月派詩論家始終堅守著他們的陣地,到1931年陳夢家在為《新月詩選》撰寫序言的時候,還一如既往地強調寫詩“他[它]有規范,像一匹馬用得著韁繩和鞍轡”[15]10,重申新月同人關于寫詩的主張:“本質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15]17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新月派試圖治愈中國文壇的宏偉抱負。
四、結論
本文立足史料,試圖挖掘出新月詩學的一些特質,使其更加豐滿地呈現出來。新月詩學不僅僅是在理論和具體的作詩原則上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它實際上還汲取了西方詩學的營養,應該可以算是中西合璧的寧馨兒。此外,自倡導新月詩學之初,新月派就標榜要治愈病態的中國文壇,并且一以貫之堅持不懈,從中也可以窺知新月詩論家的抱負。
參考文獻:
[1]黃昌勇.新月派:詩藝探索與文化訴求[J].浙江學刊,2003(2):75-83.
[2]李思清.論新月詩人的詩學探索及其文學史地位[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6):9-14.
[3]陳偉華.“新月”理論家們的“硬譯”――論新月派詩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J].中國文學研究,2005(1):22-26.
[4]Murray,James A. H. et al.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Z].Vol. VII. Oxford: Oxford Press. 1933.
[5]Lefevere, André. “Why Waste Our Time on Rewritings?―The Trouble with Interpretation and the Role of Rewriting in an Alternative Paradigm”[A]. In Theo Hermans (ed.). 1985.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C].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985.
[6]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7]Baldick,Chris.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8]謝桃坊.中國詩學辯――關于“詩學為何”答楊義與高建平先生[J].社會科學研究,2006(1):170-177.
[9]楊乃喬.論中西學術語境下對“poetics”與“詩學”產生誤讀的諸種原因[J].天津社會科學,2006(4):106-111.
[10]朱自清.導言[A].朱自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八集詩集[C].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1935.(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
[11]鄧以蟄.詩與歷史[N].晨報副鐫―詩鐫(2).1926.(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下同).
[12]饒孟侃.新詩的音節[N].晨報副鐫―詩鐫(4).1926.
[13]聞一多.詩的格律[N].晨報副鐫―詩鐫(7).1926.
[14]徐志摩.“新月”的態度[J].新月,1928(1):3-10.
第2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關鍵詞:詩,畫,虛實相生,詩畫交融
錢鐘書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1]一文中確認了一種很有趣的事實:“中國傳統文藝批評對詩和畫有不同的標準:評畫時,賞識王士禎所謂“虛”以及相聯系的風格,而評詩時卻賞識“實”以及相聯系的風格”因此,“畫品居次的吳道子的畫風相當于最高的詩風,而詩品居首的杜甫的詩風只相當于次高的畫風。,虛實相生。。”于是,“用杜甫的詩風來作畫,只能達到品位低于王維的吳道子,而用吳道子的畫風來作詩,就能達到品位高于王維的杜甫。”在這里,錢鐘書先生用詩品、詩風、畫品、畫風肯定了詩和畫作為兩種不同藝術形式而具有的不同藝術特質─詩歌崇實,繪畫尚虛。
從《詩經》開始,詩歌便注重意象的實體性,相對于畫而言,較少以虛化境,用有限襯無限,在現實主義的詩歌道路上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如《氓》,《碩鼠》,即使具有朦朧性象征意蘊的《蒹葭》仍離不了以蒹葭的具體物象為媒介。之后的漢樂府古樸沉重,詩人們深感人生如夢,生命短促,因而或主張追求功名富貴,或宣揚及時行樂,在他們的詩中,時常發出絕望的哀鳴與怨憤,流露出難以掌握自身命運的不安情緒,這種情緒在魏晉南北朝的詩歌中又被進一步放大,如阮籍、嵇康、左思、伏挺等人的詩。詩歌至唐朝大放異彩,然其現實主義仍占主導地位,陳子昂、王昌齡、杜甫、韓愈、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皮日休等無不把“文以載道”作為自己詩歌創作的理想追求。宋詩主理、多玄機,元明清詩無甚成就,多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做著為封建政教服務的原地踏步。再看屈原開創的浪漫主義道路,其陣容遠遠小于現實主義大軍。他們或借景抒懷,或歌詠自然,多想象、夸張,情感濃烈,但不管其形式如何變幻,總體來說,也不過在詩歌的畫面中讓人看到的是一整套排列整齊的直線和勻稱劃一的對照,也不過在運用著韻腳的所有色調,對比的一切表達能力和同位語的各種策略。他們使用的工具的確巧妙,令人贊嘆稱奇,驚目惶然,但最終也脫不了“充實之謂美”的傳統窠臼,意象繁復,重疊鋪排,有的甚于現實主義之實。
與之相對應的繪畫,卻漸漸走上虛的軌道。中國畫從繪畫記事開始至東晉,人物畫成熟,宋山水畫占主導地位,且日益繁榮完備。,虛實相生。。宋之前多以實入畫,宋及其后開始注重虛的成分,并有意通過留空白,剪裁部分景物入畫等形式來充實虛的內涵。實際上,繪畫尚虛的理論在南朝時就已初見端倪。謝赫在《六法論》[2]中綜合畫學理論,輯成繪畫六法:曰氣韻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象形,曰隨類賦彩,曰經營位置,曰傳移模寫。他將氣韻生動放在首位,從而奠定了以后繪畫向虛發展的理論基礎。但宋元山水畫多擷取整座大山,整個大水充斥畫面,所以有人認為這是最寫實的作品。這樣認為固然有其一面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它同時也是最空靈的精神表現,心靈與自然的完全合一。畫家的心靈特性早已全部化在筆墨里面,寄托于一二人物,渾然坐忘于山水之間,如樹如石如水如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虛實相生。。氣韻可以籠罩萬物,而空靈又無跡可尋,所以在畫中表現為空虛與流動。中國畫最重視空白處,但空白處恰巧是靈氣往來生命流動之處。“ 中國繪畫所表現的最深心靈精神是一種‘深沉靜默地與這無限的自然,無限的太空渾然融化、體合為一。”[3]。
由此觀之,詩和畫追求上的差異使得二者難以融合。“以有詩之畫作畫,畫不能佳;以有畫意之詩為詩,詩必不妙。”[4]實際上,倘若將充實與空靈看作一個相對性概念,詩和畫在守宙觀、情趣、哲思等眾多方面仍具有共通之處,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相融的。而要想解決詩畫難以相融之尷尬境地,實現詩畫交融,則必須相應地降低詩的實度,向空靈轉化,同時減少畫的虛度,向充實靠攏。當然,這里的轉化與靠攏,必須以不降低詩畫藝術為前提。營造詩意的空靈,豐富畫意的內涵,讓二者在表現手法和意境上得到溝通和互補,故而虛實相生成為詩畫交融的契點與解決方式,所以張岱也就此提出“故詩以空靈才為妙詩,可以入畫之詩尚是眼中金銀。畫如小李將軍,樓臺殿閣,界畫寫摩,細入亳發。自不若元人之畫,點依稀,云不沒,反得奇趣。,虛實相生。。由此觀之,有詩之畫,未免板實,而胸中丘,反不若匠心訓手之為不可及也。“[5]粗看之下,似乎張岱主張詩畫分離,兩不搭界,其實若細看,則是張岱主張詩的虛化。倘以詩意為“空靈”,為不能畫之“咽”,“冷”等感覺,則“畫中有詩”仍可稱妙,只有可以入畫之詩才是“眼中金銀屑”。宗白華先生也說:“畫中靜境最不易達到。靜不是死亡,反而倒是甚微妙的潛隱的無數的動,在藝術宋超脫廣大的心襟里顯示了動中有和諧有韻律,因此雖動卻顯極靜。這個靜里,不但潛陷著飛動,更是表示著意境的幽深。”[6]宗白華先生結合詩論畫,卻正道出了詩畫交融中虛實相生的本質和精髓。
因為一首詩(一幅畫)的詩意(畫境)是欣賞者感受到的,所以虛實相生只解決了詩畫交融的創作層面,其接受層面,將作者心中表達出來的詩畫交融景面有效地傳達給欣賞者,還必須借助欣賞者與作者的心靈共鳴或欣賞者與物象的情感感應。,虛實相生。。沒有這種心靈共鳴或情感感應,詩畫交融也只能停留在創作層面,因而創作者必須創造出虛實相生而又情景交融的具體物象,方能使詩人或畫家在寄情于景、借景抒情中,將其幻象作用于觀者的回憶或幻象,使觀者自詩(畫)生情,寄情于詩(畫)之景,并因此情此景而誘發和開拓出更寬更厚的審美想象空間。如此創作者與觀者的心靈在交流中達成一致,形成共鳴,觀者與物象在接受中產生感應,進而完成詩畫交融的全過程。,虛實相生。。
中國詩與中國畫在判斷標準與價值取向上的不同,造成了詩畫交融的困難,但在深層次上,二者又具有許多共通之處,使得詩畫交融成為可能,其契合點與解決方式就是詩畫虛實相生,情景交融,拓展審美想象空間,以形傳神,以靜襯動,以有限達無限。
參考文獻:
[1]錢鐘書.錢鐘書散文[Z].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
[2]謝赫.古畫品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宗白華.從介紹兩本關于中國畫學的書并論中國的繪畫[A].劉英士.圖書評論第2期[Z].南京:南京評論社.
[4]屈興國.古典詩論集要[M].濟南:齊魯書社,P186.
[5]屈興國.古典詩論集要[M].濟南:齊魯書社,P186.
[6]宗白華.鳳凰山讀畫記[A].林同華.宗白華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3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關鍵詞:趙執信;詩文有別;詩文相通;以文為詩
詩文關系,是中外詩家、文家都感興趣的話題,朱光潛先生在《詩論》中曾專辟一章加以論析,相當細致地揭示了這一問題復雜的內涵。{1}朱先生的討論,在中外兩方面都留下繼續推進的空間,從中國古典詩學和文章學來看,對詩文關系的討論,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理論問題傳統,無論是詩文一律,還是詩文互異的認識,都與詩文創作及理論的發展變化有復雜的聯系。本文即希望從清代著名詩人趙執信對詩文關系的思考入手,立足趙氏的詩學淵源與創作格局,反思其詩文關系理論的獨特用心以及在文論史上的意義。
一、飯與酒:趙執信的詩文關系思考
趙執信無論是在創作,還是詩學思考上,都有鮮明的個性,他的《談龍錄》特別載錄了吳喬關于詩文關系的一個獨特的比喻,并深表贊同:
修齡又云:“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啖飯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哉言乎!{2}
飯與酒的比喻,凸顯了文與詩的差異,強調了詩的抒情性質。吳喬此說,見于《答萬季詩問》,該書所載吳氏之論,對這一比喻的意涵,言之更詳:
又問:“詩與文之辨?”答曰:“二者意豈有異?唯是體制辭語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盡變;啖飯則飽,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為人事之正道;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詩其可已于世乎?”{1}
在這個著名的比喻之外,對詩文差異的強調,吳喬于論詩之際,曾三致意焉,《答萬季詩問》又云:
又問:“命意如何?”答曰:“詩不同于文章,皆有一定之意,顯然可見。蓋意從境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鑒》、稗史,知其時事,知其處境,乃知其意所從生。如少陵《麗人行》,不知五楊所為,則‘丞相嗔’之意沒矣。‘落日留王母’之刺太真女道士亦然。馬嵬事,鄭畋云;‘終是圣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與少陵‘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正同,此命意之可法者也。”{2}
吳喬于此,強調了詩文命意方式的差異,認為文之命意,顯然可見,而詩之命意,則非顯然可知,需在知人論世的基礎上,“知其時事,知其處境”而“意從境生”。
吳喬之外,馮班亦是趙執信論詩規摹取法,不遺寸步的偶像,而馮班也很堅明詩文之異,其《鈍吟雜錄》云:“詩之為文,一出一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唯在達其志耳。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西涯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③這里,馮班批評李東陽議論太重,非詩之體,而議論是文最常見之手段,詩運用議論,倘若不能斟酌于輕重之間,便失去了詩特有的達意之道。
趙執信繼馮、吳之軌轍,強調詩文之異,而他對差異的堅持,似乎比馮、吳走得更遠。吳喬認為詩歌的章法布局,與“古文”有接近之處,而趙執信對長篇詩作章法的認識,則從未有詩文相近的說法。吳喬的意見,仍見于《答萬季詩問》:
又問:“布局如何?”答曰:“古詩如古文,其布局千變萬化。七律頗似八比:首聯如起講、起頭,次聯如中比,三聯如后比,末聯如束題。但八比前中后一定,詩可以錯綜出之,為不同耳。”{4}
吳喬這種將詩之章法與古文章法相比附的做法,在明清詩論中十分常見,例如清人施補華《峴傭說詩》云:“《奉先詠懷》及《北征》是兩篇有韻古文,從文姬《悲憤》詩擴而大之者也。后人無此才氣,無此學問,無此境遇,無此襟抱,斷斷不能作。然細繹其中,陽開陰合,波瀾頓挫,殊足增長筆力。百回讀之,隨有所得。”{5}清方東樹《昭昧詹言》云:“學歐公作詩,全在用古文章法。”{6}“不解古文,不能作古詩。”{7}“詩與古文一也,不解文事,必不能當詩家著錄。”{8}
趙執信也十分關注詩之章法,其《談龍錄》特別提到長篇的做法:“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9}這里,趙執信論長篇“體裁”,無一語涉及詩文章法之接近,不取吳喬詩文比附的意見,這其中也透露出詩文互異的論詩旨趣。
二、趙執信與詩文關系理論言說的歷史變遷
在中國古典文論史上,詩與文的關系構成一個理論問題,始自中唐。先秦時期,《詩經》是儒家文教的重要內容,魏晉南北朝時期,詩被視為“文”之一體,陸機《文賦》討論為“文”之道,其中論及“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10},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在論文敘筆中,也分別討論“詩賦”、“碑傳”、“論說”等各種文體。在這里,“文”是廣義的“文章”概念,包括一切用語言文字寫成的文章,詩是其中之一體,因此,詩與文的關系并不構成一個內涵復雜的理論問題。
中唐以后,詩文關系越來越受到文論家的關注,這里的“文”是一個狹義的“文章”概念,它與廣義“文章”概念的差別,在于不包括“詩”在內。中唐古文運動的代表柳宗元,曾經非常自覺地將“比興之作”與“著述之文”作出區別,其《楊評事文集后序》云:“作于圣,故曰經;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于《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于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于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于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于謠誦也。”{1}柳宗元認為“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2}這里所謂“比興之作”與“著述者流”的“乖離不合”,即是對詩文之異的一種揭示。晚唐著名詩論家司空圖,論詩精微獨詣,他在《與李生論詩書》中,特別提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③。這里面也體現出在詩文之差異中探論詩之三昧的用心。北宋的詩論家也明確提出詩文之不同,陳師道《后山詩話》云:“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4}
與中唐到北宋的文論家注目于詩文之差異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的詩文關系討論,則更加側重詩與文的相通。《杜工部草堂詩話》就記載了南宋人對陳師道詩文互異之說的批評:
《捫虱新話》云:“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玄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觀子美到夔州以后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5}
當然,在詩文相通的討論中,大量的還是對詩法、文法做統合的觀照。南宋著名的文章學著作《文則》,經常參照詩法來討論文法,體現了詩文一律的用心,例如將文中的比喻,比之于詩之比興:“《易》之有象,以盡其意,《詩》之有比,以達其情。文之作也,可無喻乎。”{6}李涂《文章精義》云:“《堯典》命羲和才數句耳,《七月》便詳似《堯典》,《月令》又詳似《七月》,而節病極多。然《堯典》分時,《月令》分月,其為文也易;《七月》顛倒月分,而以衣食為脈絡,其為文也難(此詩與周人之文不同類)。”{7}此處完全以文法觀察《七月》之章法,是詩文互參的又一例證。
明清文論中,關于詩文相通的討論,更為常見,例如:
詩文家不可重復說。此最為俗論。如“行行重行行”,下云“與君生別離”,又云“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又云“道路阻且長”,又云“相去日以遠”,在今人必訝其重復。“昭昭素明月,光輝燭我床”,曰“昭昭”,又曰“素”,又曰“明”,又曰“光輝”。《滿歌行》亦重疊言之;他詩不可枚舉。漢人皆不以為病。自疊床架屋之說興,詩文二道皆單薄寡味矣。{8}
又如:
詩猶文也,忌直貴曲。少陵“今夜州月,閨中只獨看”,是身在長安,憶其妻在州看月也。下云“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用旁襯之筆;兒女不解憶,則解憶者獨其妻矣。“香霧云鬟”、“清輝玉臂”,又從對面寫,由長安遙想其妻在州看月光景。收處作期望之詞,恰好去路,“雙照”緊對“獨看”,可謂無筆不曲。{9}
又如云:
詩文以氣格為主,繁簡勿論。或以用字簡約為古,未達權變。善用助語字,若孔鸞之尾,不可少也。太白深得此法。予讀《文則》、《冀越記》、《鶴林玉露》,皆謂作古文不可去助語字,俱引《檀弓》“沐浴佩玉”為證。余見略同。{1}
至于前面提到的,《昭昧詹言》所謂“詩與古文一也,不解文事,必不能當詩家著錄”;“不解古文,不能作古詩”等種種議論,更是對詩文相通之說的高度概括。
當然,明清時期也時時可以見到詩文相異的議論,例如《麓堂詩話》云:“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為文,韓退之以文為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為詩,則毫厘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2}《藝苑卮言》云:“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絕,句字殊,聲韻各協。下迨填詞小技,尤為謹嚴。《過秦論》也,敘事若傳。《夷平傳》也,指辨若論。至于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丑。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并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③
但總的來看,明清時期對詩文差異的關注,遠遜于詩文相通的討論。在這樣一個大的理論興趣歷史變化的背景下,趙執信上承吳喬、馮班,強調詩文之間的顯著差異,其理論之個性,就體現得很清楚。然而要體會其理論的獨特用心,我們還要理解詩文關系的理論思考,何以自中唐北宋以來,直到明清,呈現出從強調詩文差異,到側重詩文相通的轉變,這一問題需要聯系古典詩歌在中唐到北宋時期發生的巨大變化來回答。
中唐詩歌新變的顯著特征之一,就是“以文為詩”,作為中唐詩壇的代表人物,韓愈和白居易的詩作,都體現出“以文為詩”的特點,韓愈的某些古詩,借用古文的句式、技法,而白居易的近體詩,也包含了許多散文的句法。韓白的藝術探索,對宋初詩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歐陽修、蘇軾的詩作,在句法、章法上,都上承韓白,而有許多“以文為詩”的特色。在“以文為詩”的影響持續擴大的同時,對這一趨勢的反省與反撥,構成了中唐到北宋詩壇詩藝演變的重要動力,晚唐賈島、姚合、杜牧、李商隱都表現出對“以文為詩”之道路的反撥,而北宋以黃庭堅為代表的江西詩派,則在詩歌表現藝術上全面深刻地超越了“以文為詩”,突出了詩歌語言與表現藝術的獨特性。江西詩派對詩歌字句的推敲,是對詩化語言的探索,南宋嚴羽《滄浪詩話》批評宋人作詩之弊,是“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4},這里的“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的確是自中唐詩歌新變以來,伴隨著“以文為詩”越來越深入地進入詩歌,但“以文字為詩”與“以文為詩”并不相同。前者是指江西詩派對詩歌語言的推敲錘煉,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是對“以文為詩”之忽視詩歌獨特性的一種反撥,是詩歌藝術探索的深化。因此,當“以文為詩”在中唐到北宋的詩歌創作中不斷發展,“詩”與“文”在創作中的交融越來越深入,出于對這一大趨勢的反省以及追求詩歌獨立性的要求,中唐到北宋的文論中,反倒出現了許多強調詩文差異的聲音。例如,江西詩派代表詩人之一的陳師道所提出的“詩文各有體”,就是這些聲音的代表。
隨著江西詩派的詩壇影響日趨顯著,詩歌語言的獨立性得到強化,“詩”與“文”不再如韓、白、歐、蘇的某些作品,呈現復雜的糾葛,創作上離析詩文的需要已經不再強烈,因此,詩文相異的論調也隨之大為減少。人們更為關注的,是在“詩”、“文”這兩種互不相同的文體之間,是否存在彼此溝通借鑒的可能,因此,南宋以后大量關于詩文關系的言說,都集中于詩文在表現技法、藝術特色上如何相通,而關于詩文如何不同的討論,日見式微。
詩文關系理論言說與詩史演變這一微妙的聯系,也十分有助于我們理解趙執信何以在明清不重詩文之異的環境中,堅持對這種差異性的強調。
三、取意于江西之前:趙執信的詩歌格局與其詩文關系思考
趙執信一生吟詠不輟,其傳世作品數量頗多,創作上表現出取徑宋詩的顯著特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對江西詩派所代表的宋詩工于錘煉、詩境內斂的藝術追求,較少取法,更多地繼承了中唐到北宋,以韓、白、歐、蘇為代表的“以文為詩”、詩境偏于揮灑豪放的藝術道路。這種“取意于江西之前”的藝術格局,是理解其詩文關系思考的重要創作基礎。
如前所述,從中唐韓、白,到北宋歐、蘇,這一藝術脈絡在宋詩形成中具有核心的地位,韓、白、歐、蘇在藝術上體現出鮮明的“以文為詩”的特色,即引散法以入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詩歌的體式,但在詩歌語言的錘煉上,尚未發展到江西詩派的“以文字為詩”;在精神內涵上,將士大夫豐富的精神世界,通過詩歌進行表現,極大地擴展了詩歌的內容,從韓愈的怪奇雄杰、白居易的人生世事感喟,到歐陽修縱橫復雜的思致,以及蘇軾揮灑與豪放的詩風,唐宋轉型過程中士人精神的多樣面貌,在這一脈的詩作中得到全面的呈現,其中雖然白居易、歐陽修、蘇軾都表現出沉思內斂的一面,但并未像江西詩派那樣單一地專注于內斂。趙執信的詩歌,在藝術手法和精神內涵上,都與韓、白、歐、蘇非常接近。
五古與七古是趙執信傾注心力極多,也十分自信的體裁,傳世佳制甚多。從體式上講,自盛唐以來,七古就追求與歌行的分野,而中唐韓愈之“以文為詩”,則將古文章法引入七古,更進一步明確了與歌行的分殊。趙執信的七古創作,也表現出對歌行氣味的鮮明排斥,《談龍錄》:“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并得名,日事唱和。會有得諸葛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余繼作四十韻,盛傳于時,皆為閣筆。江都汪主事蛟門懋麟,王門高足也,內崛強。阮翁適得浯溪磨碑,蛟門亟為四十韻以呈,阮翁贊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狐。’遽擲之地。曰:“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堪作爾語乎?”阮翁為之失色者久之。”{1}
趙執信之所以對汪懋麟之作如此毫不留情,很可能就在于“楊家姊妹顏妖狐”一句,完全是歌行的語調,而七古豈“堪作爾語”。這種鮮明的臧否,于作詩并非通達之論,卻是自身創作追求最好的表白。
趙執信之五古與七古,最多取法于韓愈與蘇軾,韓愈語言上怪怪奇奇,精神上雄奇縱恣;蘇軾則思致揮灑、飄逸縱橫。趙執信的古詩與此十分接近,他在語言上拗峭雄杰,但意趣上則更接近蘇軾,例如《觀斗促織》:
金商動殺氣,惴氣一王。俄然角翅完,自喜牙須壯。草間分蟻穴,水次雜蛙唱。豈有勢必爭,群以力相尚。幽人洞物情,羅取就盆盎。無聲出指揮,快意見跳浪。初合猶兩疑,再鼓乃齊抗。猛士心,奮迅良馬狀。大鳴類號呼,小利增跌宕。遞進恍尋仇,獨勝欣得將。旁觀識強弱,萬事有得喪。一笑天地間,孤懷足閑暢。{2}
此詩用語不無狠重之意,但“旁觀識強弱,萬事有得喪。一笑天地間,孤懷足閑暢”又帶有蘇軾灑脫超然的氣質。
趙詩用語之怪奇狠重,《題搜山圖卷》是很好的代表:
深山窮壑妖所都,帝遣丁甲行天誅。飛廉屏翳豐隆俱,鬼獰神怒爭前驅。戈矛霜耀森旌旆。彼主者誰提鹿盧?金甲錯落須眉粗,前伏帖息為於菟。何不乘之趨亦趨,卻跨兩鬼如愁胡?雜萬眾飄風徂,蟻視蛇虺鼠熊。胸碎首不須臾,立使幽險成夷涂。窈窕巖洞中紆徐,猿猱狐貍相與娛。炫服麗質人無殊,新妝盈盈施粉朱。狙公醉倒笑語扶,峨冠墮地猶狂呼。大罰降矣何其愚,死且不悔可嘆吁!巨蟒修鱗千丈軀,舉頭倏忽排云衢。掉尾已斷將焉逋?黑螭拳縮甘就拘。潛飛無計空牙須,俯視水羞蝦魚。禹鼎象物良非誣,烈山焚林勞朕虞。未抵神力工掃除。閶闔巍巍臨太虛。清問下逮知民,山川永奠人安居。麒麟鳳凰豈竟無,問君胡然為此圖?③
這首詩如果與韓愈之《陸渾山火》、《調張籍》對讀,就可以看出兩者的用語特點十分接近。當然,趙執信性情豪放,因此,他將韓愈之怪奇與蘇軾之飄逸灑脫融合而形成的新境界,則更能反映他的個性,例如《觀漲二十韻》:
積陰歸山南,風日啟清麗。午景浮前川,奄忽水大至。初聞聲震蕩,澗壑助遠吹。漸見勢漫,坡隴各易位。前奔如有程,橫潰遂無際。擺簸困喬林,崩騰坼厚地。荒涯牛馬迷,吼沫兒童悸。空村走若狂,余亦曳杖出。半生放浪游,動與潮濤會。濁河千丈波,八月夜掉臂。來臥山陬,每愛沙水細。消長固有時,變更或失計。乞假潦資,依倚岡戀勢。造次快狹中,蒼黃逞雄氣。蛟龍羞蹙縮,魚鱉縱凌厲。小利欲何成,暴興恐難恃。大海在宇宙,終古不涌沸。一瞬泛濫流,只遺元冥愧。褰裳謹漫投,濯足存深致。高詠《秋水》篇,斜陽斂晴翠。{1}杜甫亦有類似題材的作品,《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云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蹙。蓊川氣黃,群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禿。乘陵破山門,回斡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黲黷。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云雷屯不已,艱險路更。普天無川梁,欲濟愿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眾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2}
兩相對照,趙執信命筆用意,多有胎息杜詩之處,但并沒有在驚心動魄一面做更大的鋪張,而是將河水之漲,與大海的平靜做對比,歸結于“高詠《秋水》篇,斜陽斂晴翠”的境界。這正是與蘇軾頗為接近的意趣。又如《雪晴過海上,適海市見之罘下,自亭午至晡,快睹有述,時十月十日》:
今晨雪乍晴,寒日升扶桑。出門邀河伯,東向同洋。昨日之罘山,紫翠點水如鴛鴦。未至二三里,見人欲飛翔。坐來忽復不相識,回峰疊嶂皆摧藏。赫然煙靄中,城郭連帆檣。疑是秦樓船。歸來閱千霜。又疑瑤宮與貝闕,神山倒影滄流長。飛仙驂虎豹,晃漾凌波光。招招不得語,目極天蒼黃。同游競指是海市,對之使我神揚揚。歲序閉冰雪,魚龍走顛僵。非時出瑰麗,此遇超尋常。當年蘇夫子,雄詞自炫驚海王。慚予本凡才,未敢縱筆相頡頏。不請亦得睹,失喜欲發狂。巨川細流兩無拒,信知大海真難量。準擬還家詫鄉黨,詎肯此地辭杯觴。天窮人厄總莫問,微塵大地俱荒唐。客散境變滅,半山還夕陽。醉歸卻聽暮潮上,浩浩天風吹面涼。③
此詩之聯翩浮想,飛揚意氣,這是蘇軾的“雄詞”,而非昌黎之險怪,類似的風格,又見于《平度州道中望東北諸山》:
秋風吹倦客,縹緲凌紫霞。赤松仙人要我去,為駕白鹿青龍車。羽輪飄飛不自制,始計已失秦瑯邪。大勞小勞遠相待,回馭又復成參差。明霞碧落杳夢寐,玉女有爪羞搔爬。北行度膠水,惟見塵與沙。晴嵐百里豁心目,高望一點青于鴉。眾山肩隨出,戢戢木末爭槎椏。天柱孤標倚蕭爽,下笑兩髻魯始。東萊岱華列,首室不敢加。譬人名既成,無事相矜夸。大澤東來獨雄杰,森然列仗排高牙。云峰飛瀑落千尺,煙光蜃氣無由遮。臺殿嵯峨布空曲,浮金炫碧生。我今矯首意惝恍,況于抗策窮幽遐。人生能幾何,引領白日斜。海山有約易錯迕,此中便可終來家。{4}
這樣的作品充分展示了“以文為詩”為詩歌帶來的寬廣篇制,以及縱橫的才思。趙執信于此游刃自如,正體現了其詩學的趣尚。趙執信最為親密的詩友馮廷也取法韓、蘇,而于長篇古體,浸頗深,趙執信與馮在京城以長篇并名,日事唱和,足見其詩學上的相投。這些長篇古詩,是趙氏創作中最引人注目的內容,也可由此見出其詩學上的根基所在。
對于中唐詩人白居易在近體詩中“以文為詩”的做法,趙執信也有深入的取法。與韓愈不同的是,白居易對“以文為詩”的嘗試,主要體現在近體詩中,趙執信的七律就大有“白體”的特點,像“眼已逢人混青白,心猶和月變盈虧”(《記夢》){1}就很有白體的腔調,還有不少作品更為典型:
青山風景久來真,白紙榮華換后新。無復堪容位置處,漸多不識姓名人。易驚畢弋憐高鳥,終托江河羨細鱗。只似丹青曹陸手,眼前涂抹一回春。(《覽仕籍戲成》){2}
童稚情親五十年,浮沉蹤跡兩茫然。經過初見霜生鬢,相望長如月在川。貧久原思兼抱病,醒多蘇晉本逃禪。海山他日期攜手,何必求歸兜率天。(《得天津書,知滄州同年劉師退健在》)③
世事圍棋敗尚爭,塵心流水淺逾鳴。天高神自張威福,歲旱人難料死生。大夢暗隨蝴蝶化,小詩輕擲鷓鴣名。海棠猶弄春姿態,剩向東風落滿城。(《晚春有感》){4}
這些作品,無論語言,還是情感書寫的特點,都是典型的“白體”。
韓白歐蘇“以文為詩”的藝術道路,容易帶來詩歌藝術特性的削弱,趙執信還是非常講求通過語言上的雕琢來避免詩意的平滑流易,例如《與馮信州躬暨夜話感舊》:
空村萬木號,寒雨坐來歇。秋燈照病顏,各已生華發。庭軒颯以清,壺樽偶然設。豈知故鄉親,有似天涯客。十年異出處,相望若秦越。心依玉山云,夢斷金門月。欣逢水聚萍,惜別風振葉。人生離合情,且與盡今夕。鵲驚三匝飛,鵬去六月息。何處與子期,神州有銀闕。{5}
此詩命意構思十分接近杜甫《贈衛八處士》,但用語明顯雕琢,例如,“十年異出處,相望若秦越。心依玉山云,夢斷金門月。欣逢水聚萍,惜別風振葉”,在用語上甚至有些流于雕琢。這樣的雕琢風格,與江西詩派以后的錘煉方式并不相同,而是更接近“晚唐體”的某些特點。自晚唐以來,詩壇就不斷有反撥“以文為詩”的努力,以賈姚為代表的五律,以許渾為代表的七律,工于錘煉,表現了對詩歌語言之獨特表現藝術的追求,這些作品被后世稱為“晚唐體”。趙執信的詩作,也體現出“晚唐體”的影響,例如:
十日山中汗漫行,山云作意變陰晴。連天細雪因風急,近郭空煙接日生。鞭影遠牽殘照色,馬蹄寒踏斷冰聲。定知此后相思處,贏得清樽夜夜傾。(《山行雜詩四首》其四){6}
煙披岳麓翠帷張,雨春疇細草香。人帶斷霞過小渡,鳥沖飛絮入斜陽。鞭絲帽影垂垂遠,日觀天門望望長。嶺半桃花隴頭麥,肯輸物色與江鄉。(《晚晴過太山下》){7}
兩詩的中二聯,都是雕琢工細,很接近“晚唐體”的風格。趙執信某些絕句,也很有“晚唐風調”,例如:
艇子飄搖似此身,深杯照影并無塵。閑評廊廟將煙水,何許堪容淡蕩人?(《泊吳閶,遇吳江徐電發,以小舟游虎丘,共飲話舊二絕句》其二){8}
有些絕句,以艷筆,寫風雅,也可見出“晚唐”體調,例如:
兩峰相憶不相識,中著茅亭定可憐。那更西湖似西子,橫陳日日小窗前。”(《為舒鳧題吳山草堂》){9}
趙執信的五律則接近賈姚,例如:
曉日不照地,群峰方障天。行人聽雞起,鳥道接河懸。遠樹猶藏雨,高城半出煙。秋來無限思,牢落付山川。(《獲鹿至井陘道中三首》其一){1}
雨腳背城見,前村開晚晴。近山風轉急,隔水月初生。樹杪懸燈火,煙中隱碓聲。今宵斷魂處,野館醉三更。(《晚行》){2}
這些詩句,極富錘煉之特點,但還缺少一些江西詩派平淡內斂的特色,含蓄的回味尚不及后者,更接近賈姚的詩作。賈島之作,尤其有求奇的傾向,而趙詩中“行人聽雞起,鳥道接河懸”,就近似賈作,而有聳然求奇之意。
總的來看,趙執信對“以文為詩”所可能產生的詩藝弊端,是以“晚唐”的方式來克服,他對詩歌語言獨特性的追求,與江西詩派的取徑還是有很大差異。這也在整體上使他的詩歌藝術在大的格局上是在韓、白、歐、蘇的框架中,沒有進入江西詩派的詩境。
在精神內涵上,趙執信對于平淡含蓄而內斂的趣味,始終沒有充分表達,其作品大量地呈現出縱橫豪放的風格。
內斂與自省,是宋詩逐漸成熟的精神品格,但趙執信的詩歌表達了大量的憤激嘲世的內容,他學習白居易新樂府而將譏世之義,傳達得更為透達無隱,例如:《道傍碑》:
道傍碑石何累累,十里五里行相追。細觀文字未磨滅,其詞如出一手為。盛稱長吏有惠政,遺愛想像千秋垂。就中行事極瑣細,齟齬不顧識者嗤。征輸早畢盜終獲,黌宮既葺城堞隨。先圣且為要名具,下此黎庶吁可悲。居人遇者聊借問,姓名恍惚云不知。住時于我本無恩,去后遣我如何思?去者不思來者怒,后車恐蹈前車危。深山鑿石秋雨滑,耕時牛力勞挽推。里社合錢乞作記,兔園老叟頤指揮。請看碑石俱磚,身及妻子無完衣。但愿太行山上石,化為滹沱水中泥。不然道傍隙地正無限,那免年年常立碑。③
此詩三字式的命題方式,以及內容,都與白居易新樂府十分接近,而在譏刺時事上,更為辛辣。中國傳統有為死者諱的傳統,而趙氏抓住長吏死后立碑虛美一點,大張譏刺,其內心之憤激時事,是超乎常情的。又如《贈徹禪師》諷刺僧人的種種“丑態”,也是筆下略無回護:“眼中數緇流,潦倒難位置。高者盛威容,出入陳軒騎。余者競壟斷,蠅營殉財利。文章竊皮毛,貴游倚聲氣。鄙夫多附和,市兒有吐棄。咄咄清凈門,到此土委地。”{4}
最令人驚異的,是趙氏為友人祝壽時,也嬉笑怒罵,不顧避忌:
人之有年歲,譬若影附形。上分日月光,下與爝火爭。觸景應明晦,過無減增。偶然積多寡,多者人艷稱。空余齒發變,豈有利欲并。所貴涉途寬,可以策修名。流欲泥干支,指日為所生。去日等逝波,所生焉足憑。況復信祝史,祈禳不暫寧。煩文苦妻子,奔走勞友朋。上古未聞此,往哲非自輕。行之經永久,欲止諒不能。計惟當斯時,置酒飛觥。四序各有適,百年其奚營。今年君四十,招我來前榮。束我雜賓中,開口殊可憎。不言官必高,不言仙可成。勸汝力飲酒,時事如沸鐺。(《同年曹蓼懷編修生日索贈》){5}
在祝壽時,反復申說人生之短暫,長壽之無憑,的確是“開口殊可憎”,其內心憤激時事的沸郁之情,亦了然可見。這種憤激,還流露在他對晚唐詠史詩的取法上,例如《三士墓》“石父曾令脫網羅,留將三士竟如何。孟嘗坐食三千客,拼盡園桃殺幾多。”{6}
在宋詩之平淡美學趣味形成的過程中,梅堯臣的古淡,是重要的藝術創造,趙執信也多有學梅之作,但他更多地是學習梅堯臣的“以丑為美”、“化俗為雅”,而于梅詩的“古淡”,并未有得。例如《秋熱》是學梅的典型之作:
西風不作力,大火張余威。雷雨呼莫應,毒熱來非時。七月月向盡,午汗已去肌。昨夜夢顛倒,謂是初炎曦。曉窗日潑眼,如臨洪爐窺。翻身欲起避,衾簟粘膠離,灑掃就隱,嬌兒啼相隨。藏冰日十市,怒詈來何遲。暑寒代有常,奚由失其宜。太寬以猛濟,遺愛傳良規。琴瑟忌專一,改弦待工師。敢持區區意,仰訴皇天慈。{1}
趙執信最近于宋人內省而理性的地方,也許就在與蘇軾之達觀以及自嘲諧謔之風的接近上,例如《陘陽驛雨甚,行橐皆濕,輿中聊述》:
欲知肩輿行遇雨,有似曳尾涂中龜。聳身延頸欲前去,四足不動如懸槌。窗欹枕雨腳入,紛斜一任西風吹。我既衣裳有沾濕,回視我仆嗟亦疲。幸余臟腑未湔濯,豈免涕淚同淋漓。無因天漏借石補,反思油衣以瓦為。人生有情每無厭,遨游謂樂居可嗤。請看行役足辛苦,他時枯坐無庸悲。{2}
此詩可以與蘇軾之《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泗州僧伽塔》對讀,既有對生活的達觀,也不無自嘲諧謔之意趣。類似的情感,在趙氏之作中,有許多表現,但整體上看,趙執信詩歌的情感內涵,還是以豪放揮灑為主,與江西詩派含蓄內斂的主調,有很明顯的差異。
第4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關鍵詞】李清照;王紅公;概念隱喻;《一剪梅》
一、理論介紹
Lakoff和Johnson(1980)的隱喻研究使得人們不再將隱喻僅視為語言的裝飾,不同學者采取不同方法從不同角度對隱喻加以探討和研究 ,如認知實驗方法下的隱喻研究,人類學角度的隱喻研究,語言習得與隱喻的發展等。隱喻不僅成為一個理論問題,也成為應用性的研究課題(Cameron & Graham,1999)。Lakoff和Johnson(1980)認為,人們賴以思維和行動的概念體系本質上是隱喻性的,這就是“隱喻概念體系”(metaphorical concept system)。人們以一個概念理解建構另一個概念,也以一個概念的詞語去談論和表述另一個概念,這就是“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Lakoff & Johnson,1980:3-6)隱喻普遍存在于各種文化和語言中(趙艷芳,2000:106),因此在認知語言學的框架內從語言對比的角度對英漢語中概念隱喻及其常見表達的異同進行分析有助于隱喻研究的深化。
Lakoff和Johnson將概念隱喻分為結構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位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及本體喻(ontological metaphors),這一分類成為認知語言學概念隱喻研究的基石。結構喻指隱喻中始源概念域的結構可系統地轉移到目標概念域中去,使得后者可按照前者的結構來系統地加以理解。通常是用源域 (source domain)中具體的、已知的或比較熟悉的概念去類比目標域(target domain)中抽象的、未知的或比較生疏的概念。方位喻運用諸如上下、前后、里外、深淺、中心―邊緣等表達空間的概念來組織另一概念系統。這與我們的身體構造、行為方式密切相關。將具體的空間方位概念投射于情緒、身體狀況、數量、社會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本體喻用關于物體的概念或概念結構來認識和理解我們的經驗。如可將抽象的概念喻說成具體的物體,可使后者的有關特征映合到前者上去,其中可分為三小類:(a)實體和物質隱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把經驗視作實體或物質,通過后者來理解前者,就可對經驗做出相應的物質性描寫,如指稱、量化、分類,使其帶上某類物質的特征,加以引申,進行推理,分析其相應的原因等。(b)容器隱喻(Container Metaphors)將本體(不是容器的事物、大地、視野、事件、行動、活動、狀態、心境等)視為一種容器,使其有邊界、可量化、能進、能出。(c)擬人隱喻(Personification)將事物視為具有人性就是一個明顯的本體隱喻。[1]
二、文本分析
1.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Red lotus incense fades on\The jeweled curtain. Autumn\Comes again. Gently I open \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On the orchid boat.
“香殘”一詞用“殘”字來表述“香”的消逝,可用本體喻下的實體和物質隱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對其進行分析,用有形的動作修飾無形的知覺,栩栩如生之感頓生。同時,這一機制也可用于解釋“玉簟”:通過玉的光澤來理解竹席的特征,可使其帶上玉石的色澤特征。“蘭舟”一詞也可作相似的解釋。譯文的“incense fades on the jeweled curtain”中“fade”一詞與原文的“殘”在意韻表達上似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將香譯為消逝在竹簾上與原文表達的意思有所不同。
“蘭舟”即木蘭舟,船的美稱,木蘭樹所制的舟船。“蘭舟”一詞被賦予性色彩始于《愛與流年:續漢詩百首》中《一剪梅》一詞。該詞譯文中融合了大量的元素。其中譯者將“輕解羅裳,獨上蘭舟”,“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譯為:“Gently I open\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On the orchid boat","Flowers, after their kind,flutter\And scatter.Water after\Its nature,when spilt, at last\Gathers again in one piece.\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Long for each other"。譯者將詞人在上闋中“輕解羅裳”演繹為詞人的訴求:“落花飄散循其類,流水溢聚因其性”,譯者據此隱喻詞人的性孤獨、,孤兒聯想到詞人乘蘭舟蕩漾。王紅公同時在注釋里稱“蘭舟:指詞人之性事,亦或確指其”。1971年王紅公與鐘玲合譯、出版《中國女詩人》時,他便將“蘭舟”與女性結合起來,取書名《蘭舟:中國女詩人》。他明知“蘭舟”是“Magnolia Boat”,卻為詩意起見,譯為“Orchid Boat”。他的詩人靈感將“蘭舟”賦予女性色彩,象征女性美,甚至暗喻成女性的性器官。重譯《一剪梅》時,王紅公明確注釋“‘蘭舟’是女性性器官的常用比喻。”在此后創作中,他也成功地將這一詞語納入主體詩歌中。“蘭舟”一次經過他的譯介,吸納了涵義,成功融入了美國本土文學,實現了經典化構建。[2]
2.云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Who can \Take a letter beyond the clouds?\Only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And write their ideograms\On the sky under the full\Moon that floods the West Chamber.
在中國古代,鴻雁可作書信的代稱,常見“鴻雁傳書”。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鴻雁比喻書信。王灣的《次北固山下》中有“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一句。此外,歐陽修在《戲答元珍》中也寫道“夜聞歸雁生鄉思,病入新年感物華”。由此可以看出,歸雁實際上是隱喻書信,并非真正的描寫大雁。中國古代自身的背景讓大家對這一隱喻并不陌生,但這一隱喻卻無法在譯文中體現出來。“wild geese”雖譯出“雁”這一字,但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翻譯對等詞的空缺,不僅對理解原文沒有幫助,可能會使讀者產生不解。且“雁字”是指雁群排列的形狀,而不是如譯文所說大雁在書寫某種符號。“月滿西樓”一處也進行了隱喻處理。將西樓作為一種容器,而月光則似裝在容器中的液體。譯文中選擇含義有一為“灌滿”和“淹沒”的“flood”一詞事實上也按照原文對月滿進行了隱喻處理。
3、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Flowers, after their kind, flutter\And scatter. Water after\Its nature,when spilt, at last\Gathers again in one place.\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Long for each other. But we \Are far apart and I have\Grown learned in sorrow.
徐炳昌曾將隱喻分為八類,分別為判斷式、偏正式、同位式、并列式、替代式、描寫式、迂回式和故事式隱喻。(轉引自王寅411-412)而此處的“花”和“水”因為只出現了喻體沒出現本體,以喻體代替本體,以二者來代替詞人自己與其丈夫,所以可歸為替代式。而且漢語中本身也有“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來表示一廂情愿的用法,同樣采用“流水”和“落花”來代替男女。隱喻一般都是從熟悉的、有形的、具體的、常見的概念域來認知生疏的、無形的、抽象的、罕見的概念域,從而建立起不同概念系統之間的聯系。王寅教授在其著作中對中國古人的“愁”的隱喻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而此處的“一種”和“兩處”這兩個量詞將“相思”、“閑愁”具體化、形象化了,以量詞代表的具體的熟悉的概念域來認知抽象無形的概念域。
4、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Nothing can make it dissolve\And go away. One moment,\It is on my eyebrows.\The next, it weighs on my heart.
中文中“眉頭”、“心頭”二詞本身就采用了實體和物質隱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s)這一隱喻機制,將“眉”和“心”都當做一個整體,通過人類這一整體形象的“頭”來理解“眉頭”和“心頭”可以對二者做出相應的物質性描寫。而“下”、“上”二字通過形容詞動詞化不僅將“情”這一事物形象化、生動化,視其為一種擬人隱喻,而且也可理解為一種方位隱喻。方位隱喻指參照空間方位而組建的一系列隱喻概念。空間方位來源于人們與大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概念,如:上――下,前――后,中心――邊緣等,人們將這些具體的概念投射于情緒、身體狀況、數量、社會地位等抽象的概念上,形成許多方位詞語表達抽象概念的語言表達。此處通過“下眉頭”、“上心頭”與前文相呼應,賦予“此情”一種不由自主的生命狀態,使其成為一種獨立的生命體,無論“下眉頭”或是“上心頭”都是“此情”自身發出的動作,突出了作者的“無計”之感。王紅公的英譯中更多的是將“此情”實體化,也就是實體物質隱喻,“dissolve”的解釋中含有固體溶解和消散之意,而此處作者選取“dissolve”也有可能是想造成一種模糊,因為后文的“on”和“weigh”都體現了“it”的重量和體積,或與古詩詞“載不動,許多愁”以及“不知心大小,容得許多愁”中將愁思物化的手法相似,因此可以看出譯者此處也采用了本體隱喻的機制。
三、王紅公的翻譯主張對其翻譯的影響
中西李清照詞英譯大致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國內中國譯者翻譯的李清照詞,譯者以弘揚民族文化為己任,以忠實于中國傳統文化為主要特點;而是英語世界西方譯者翻譯的李清照詞,以模擬漢語詩歌結構和意境表達為特點,努力保留異族文化特色,面向西方讀者;三是英語世界華裔學者翻譯的李清照詞,既忠實傳播祖國傳統的優秀文化,同時兼顧西方讀者的接受。
王紅公翻譯的李清照詞,一個總的特點是,譯詩本身是卓越的英語詩歌。按照美國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話來說,一是敏感超群,而是具有美國風格。雖然王紅公的譯詩以其簡潔明了的詩歌風格,極大地影響了一大批美國詩人。但所謂譯詩,他從不把忠實于字面意義的傳達作為其翻譯的目的。王紅公倡導的“同情”詩歌翻譯觀,強調譯者用譯入語進行再創造,譯文要傳達原作的神韻,要給讀者帶來沒的感受。在李清照詩詞英譯過程中,他實踐了“譯者是‘辯護律師’”的主張,彰顯了譯者的權利和自由。他運用創造性翻譯策略,給西方讀者展現了李清照詩詞的美和境界,其優美、典雅的譯詩得到了學界廣泛好評。William Lockwood稱“他(王紅公)再創了李清照充滿想象的詩歌之光輝,并因此把她明亮、豐富的個性待到我們生命之中。” [4]
王紅公提出詩歌翻譯是“同情”行為。他稱:“將詩譯成詩是一種同情行為--將自己與另一個人相認同,將他的話變成自己的話。我們知道,一位好的譯者是不會對照文本逐字翻譯的。他不是人,而是全力以赴的辯護律師。他的工作是一種特殊的請愿。詩歌翻譯是否成功的標準是同化,看陪審團是否被說服。”(Rexroth,1961:19)他強調譯者不應受到文本文字的羈絆,而應該積極向作者靠近,真切地體會作者的創作經歷和情感體驗,結合譯語的文化與習慣,適應譯語讀者的接受心理,然后用自己的語言傳達作者的情感。他認為,翻譯不僅停留在認知層面(理解原作),更是情感的投入(感受原作),是譯者和作者跨越時空的心靈交流。只有達到這樣的境界,譯者才可能譯出原作的精華。他的翻譯標準是“同化”,在歸化的情況下使譯文迎合讀者體味(taste)。雷氏的翻譯觀與當代西方文化學派翻譯理論家Andre Lefevere的觀點不謀而合:強調翻譯的“忠實”是不正確的,甚至它不是語言層面的對等的問題。實際上,翻譯涉及到由譯者在意識形態、詩學、文化體系的層面上所決定的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5]
王紅公譯介的李清照詩詞在譯者文化身份與時代特征中得以“再生”,譯文尋求的是一種異質文化語境中的“傳神”、“傳情”樣態。他生動的解讀與靈活的英譯打破了譯詩“忠實”與“誤譯”的二元對立,實踐了他的“同情”詩歌翻譯思想。譯文令英語讀者欣賞到了“異樣”的李清照。他跨越時空“邂逅”李清照后,憑借“易安詞”敘述了自我,豐富了自身的詩歌創作,締結了一段令人矚目的中美“詩緣”。
【參考文獻】
[1]王寅.認知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2]酈青.李清照詞英譯對比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3]李華.宋詞三百首詳注[M].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2.
[4]鐘玲.美國詩與中國夢[D].廣西師范大學,2003.
第5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關鍵詞:詩歌教學;文學教育;語文教學
中圖分類號:G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2851(2010)06-0140-01
一、與詩歌相關知識的傳授
詩歌教學中的相關知識可以分為有關詩歌的基本常識和詩歌鑒賞的基本知識。有關詩歌的基本常識的內容比較容易界定,學界間基本上沒有什么分歧。如關于中國古代詩詩詞曲賦的基本分類,像唐詩、宋詞、元曲等。唐詩又可分為古體詩和格律詩,格律詩又分為律詩和絕句,律詩和絕句又有五、七言之分;宋詞有不同的詞牌,根據長短又有慢詞和小令之分;現代詩歌也有其基本的體例和規范。這些知識,雖然沒有必要像大學中文系一樣進行深入的理解和研究,但中學生要學習它,對這些基本常識的了解是絕對必要的。正如方智范先生所言:“了解了一定的格律常識,有利于學生在鑒賞具體作品時,領悟中國古代詩歌在詩歌音律美方面比現代詩歌具有更精密細膩的特殊美感,對作品的意境和情韻的感受可以更深入一步。”
當然,教學中,這些基本常識的學習應該有多種途徑,但空對空的傳授必定是大忌,因為教學這些知識不是目的。有一位老師這樣教《沁園春?長沙》這首時,講到“沁園春”詞的格式,他結合《沁園春?雪》,引導學生了解掌心詞的有關知識:
(一)與學生同背《沁園春?雪》,并出示此詞全文
問題:仔細分析這兩首詞,談一談它們在結構上有什么相似點?
明確:字數相同,相應位置的結構相似,韻腳相同。
雙調,一百十四字。前段十三句,后段十二句。一般呈現出雅馴典重、曠達疏放、豪邁悲壯的風格。
(二)練習:根據有關詞的知識,從選項中選出恰當的一項:
沁園春 蘇軾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晨霜耿耿;云山離錦,朝露溥溥;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呤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尊前。
A、月華收練;此事何難
B、月華收練;此事有何難
C、漸月華收練;此事何難
D、漸月華收練;此事有何難
筆者以為,詩歌知識的這種教法是最值得肯定方法之一的,因為它做到了既形象實用又準確易懂。
二、詩歌的誦讀
詩歌教學中的誦讀慢慢被分析所取代,有的教師居然像分析散文一樣一句一句甚至一詞一詞地落實其中的微言大義,同時也沒忘了給詩歌分段,歸納中心思想。這種做法幾乎完全消解了詩歌獨特的文體特點,它的跳躍性,它的節奏感,它的音樂感,都被大量的意義分析給抹平了,詩歌教學成了應試教學的最大犧牲品。
我們漢字的詞匯量十分豐富,單單對文字,就有“讀、念、吟、誦、唱、看”等閱讀形態。一般的書信文稿是既可以“讀”也可以“看”的,也就是說既可以出聲,也可以不出聲的。而閱讀詩歌卻不能用“看”來表述,讀詩不能無聲。柳永的詞一寫出來就會在坊間傳唱,可見詞也不宜默讀。因此,詩歌不吟誦好比曲成不演唱一樣不可思議。
三、詩歌教學的人文熏陶
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追求實利的,中華民族始終缺少非功利的形而上的信仰,因此做什么事都得問一問:它有什么用處?科舉時代讀書人的所有目標就是中舉做官,書本只是他們入仕的敲門磚。封建王朝滅亡,廢科舉,興新學,總該有所改觀吧?我們先聽聽林漢達先生1941年在他的《向傳統教育挑戰》一書中一段話:
假如文字是礦工所用的鐵鋤,那么學問是用這鐵鋤所開出來的礦物。自然礦的種類不一,金礦銀礦也好,鐵礦煤礦也不錯。怕是怕工人們什么礦都不采,只在那是費了五年十年的光陰和精神,專在擦亮他們的鐵鋤。……這種開礦工人要他何用?這種讀書人,那是有什么教育?過去的讀書人是這樣,現在的學生還不仍是這樣嗎?學生在學校里干什么呢?還不是在他的鋤頭上做工夫嗎?誰叫他這樣干的呢?自然是他自己,他的父母和他的教員。一個學生若在作文簿上寫了幾個別字,或夾了幾句不通的字句,國文教員便批評他“不通”,“國文程度夠不上”,而他所寫的內容如何,卻不過問。反之,一個學生如能做詩,且做分平仄押詩韻的舊詩,那末,這管他所說是花呀,月呀,甚至是屁呀,他總是一個有國學根底的好學生。這樣的學生不但自己很高興,便是他的教員,他的家長,也很得意。
目前,“高中語文新課標”已經出臺,“人文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強調,在這教育改革的良好背景下,我們應該充分挖掘經典詩歌中審美意蘊和人文魅力,讓它化為學生的內在素養,使他們成為靈魂高尚、思想健全的人。
當然,我們反對這樣一種做法,即從作品的活生生的內容和形式中概括出理性的、抽象的中心思想或主題思想,再加以模式化的表達。“這種意蘊分析的教條化、圖解化傾向,熱衷于指向作品的社會政治意義”的做法只能是對詩歌本身的損害,對詩歌教學一點好處都沒有。從作家主體而言,作品中的意蘊,乃是其思想、意識、情感的綜合體。正如黑格爾所言:“意蘊總是比直接顯現的形象更為深遠的一種東西。”
四、詩歌創作的實踐嘗試
以寫詩來品詩,與以作文來賞文,其原理是一樣的,就是希望在做中學習,在做中體味。既體味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艱辛,又學習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境界。生活中常有這樣的現象,學過二胡,才會真切體會二胡演奏家的高超,挑過重擔,才會真切理解黃山挑山工的艱辛,同樣,寫過詩,對會真切洞察到經典詩作的萬丈光芒。
第6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關鍵詞:古詩詞 愛國主義 文學主題
引言
我國的文化源遠流長,古詩詞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的詩歌傳統歷史悠久,在古詩詞的發展過程中,愛國主義一直都是詩詞的重要主題。我國詩壇以及詞壇上出現了很多偉大的愛國詩人,他們留下的作品形成了一道壯麗的風景,愛國主義思想表達的是一種對祖國的熱愛忠誠,是牽絆著每一個國人最真摯的感情。在我國的發展過程中,經過了幾千年的發展,詩人以及詞人為國家的統一、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不僅使用文學之筆表達了愛國主義的情懷,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外國侵略,表達了中國人民骨子里擁有的一種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久而久之,這種精神便根植于中華民族的靈魂深處,形成了愛國主義傳統。古詩詞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對現代教育也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教學過程中加強對古詩詞的解析,有助于學生加深對詩詞主旨的理解,從而提升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
一、古典詩詞的愛國主義主題
愛國詩歌,是我國古典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詩歌作品中,作者表達了一種對祖國河山的熱愛之情,更表達了對國家以及民族的前途的關切之情。同時,在面對國家出現危難時會挺身而出親身參與到斗爭中,保家衛國、建功立業。古詩詞中的愛國主義情懷,主要有這幾個方面的體現。
(一)表達對祖國的熱愛
祖國的大好河山給詩人以及詞人很多的創作靈感,他們在進行詩詞創作時往往都會以祖國的山水為基礎,融入自己的情感,將祖國的山水也賦予了豐富的情感,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好像親身游覽了這些美麗的山水河流一樣,從而建立起對祖國的熱愛之情。
(二)表達對國家以及民族前途的關切
愛國主義詩人和詞人在創作時,往往將國家以及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國家的發展還是民族的發展,都是與自身的命運有緊密聯系的,國家的前途就是自己的前途。因此在詩歌中表達對國家以及民族的一種憂患意識。比如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三)表達保家衛國、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
國家遭遇危難之時也是詩人和詞人進行創作的高峰之時,當國家遭受外來國家的侵略時,很多具有愛國主義情懷的詩人以及詞人不僅會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憤慨,還會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比如陸游、辛棄疾,不僅創作了大量的愛國主義詞作,更是親身投入到戰斗之中,與金國對抗,為國立功。
二、愛國主義詩詞解讀
愛國主義一直都是古詩詞的重要組成部分,古詩詞中的愛國主義情懷也經歷了幾個階段的發展。
(一)古詩詞中愛國主義思想的萌芽
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詩經》,在《詩經》中有很多具有愛國主義情懷的詩篇,比如:《無衣》、《載馳》、《六月》等。“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是《無衣》的主要內容,其中表達了秦國人民希望可以團結一致共同抗敵的愛國主義精神,詩歌往往給人帶來一種十分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發展到戰國時期,出現了七雄紛爭,我國的大片土地上仍然彌漫著一種刀光劍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愛國主義文學達到了頂峰,當時著名的具有愛國主義情懷的詩人是屈原。他不僅熱愛自己的家鄉,也熱愛祖國的山河以及其他百姓,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順利,遭到了排擠,最后被流放到沅湘,他的治國抱負得不到相應的施展,卻一直在與黑暗的勢力斗爭。這才出現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等著名的詩句,表達了自己的一種氣節。在屈原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愛國主義情懷以及敢于為祖國獻身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二)古詩詞中愛國主義思想的發展
從東漢末年到南北朝,我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現象,在這種相互混戰的局面下,建安詩派的出現對詩歌的發展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建安詩歌抒發了詩人們渴望統一祖國、建功立業的抱負,建安七子的愛國情懷以及抱負得到了深刻的展現。比如曹植在《白馬篇》中刻畫了一個武藝高超、性情豪邁的游俠形象,他身上的那種愛國激情也是曹植身上的愛國情懷的體現。
發展到唐代之時,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強盛的國力對我國的文學發展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在太平盛世之下,越來越多的詩人開始對祖國的大好河山進行描繪,表現出一種豪邁的愛國主義情懷。比如李白就描寫了許多關于祖國山水的篇章,在他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秀美的江山,看到充滿了激情的生活。同時在邊塞詩人的筆下也可以看到愛國主義情懷,他們的愛國主義則是一種豪邁的殺敵必勝的情懷,比如“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愿將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等,這些詩句中都彰顯了豪邁的斗志以及豪氣。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唐朝也開始衰落,在這個時期,則出現了另一批憂國憂民的詩人,很多詩人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達治國的理念以及抱負,比如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體現了他的政治抱負,“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則表達了他愿意為國家獻身的精神。杜甫與李白同為唐代詩人,但是由于兩人生活的時代不同,在詩作中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情懷有很大不同。杜甫的愛國主義情懷是一種直面人生的憂國憂民的思想體現,比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等等。
我國古詩詞中的愛國主義思想得到深化是在宋朝時期。宋詞是我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愛國主義在宋詞作品中有十分深刻的體現。蘇軾、陸游、辛棄疾等都是豪放派的代表,他們在作品中將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等,都是膾炙人口的著名作品。在這個時代中也出現了很多愛國主義將士,他們不僅能在沙場上奮勇殺敵,也能在文壇上揮墨而作。其中陸游和辛棄疾的詞作,是宋代愛國主義詩歌中的杰出代表。
三、詩詞愛國主義教育價值
古詩詞是我國文化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產物,延續至今,在任何一個教育階段都有古詩詞的身影。古詩詞在現代社會中已經不單純地是作者的情懷以及思想的體現,更是一種重要的教學工具,是教材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部分。對古詩詞中的愛國主義情懷進行分析,對作者在進行創作時的心理進行剖析,有助于對學生的思想品德、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進行教育,從而幫助學生形成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對待國家以及民族具有責任感。比如辛棄疾的詞作對典故的運用是一個最大的特點,他所運用的典故,都與內心的情感是有很大關聯的,他是用典故在講述自己的人生,講述自己的故事。辛棄疾本身是一個具有高度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詞人,對于一些涉及到朝廷和政治的話題,很多時候不能直接描繪,因此只好隱晦地采用典故來表達內心世界。在對古詩詞進行解析時,需要對作者的生平、創作風格、作品主題等多方面進行分析,有助于從創作中得到靈感,便于學生領悟作者的情感,提升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
結語
古詩詞中的愛國主義情懷是古詩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古詩詞的創作過程中作者對社會現狀的反映,也是對自己的人生的真實寫照。只有對古詩詞進行深刻的分析,才能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以及傳遞的精神。
參考文獻
[1]張宏偉.“劍南詩萬篇,半灑神州淚”――試論陸游詩中的愛國主義思想[J].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11(08).
第7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關鍵詞:意境說 宗教思想 儒家 道家 佛家
意境說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核心范疇,內涵豐富、深刻且有著光彩奪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發生發展以至最終完成都離不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滋養。它深深植根于儒、釋、道對立互補共同作用積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結構中,是我國古典文化的精華,在形成過程中始終沐浴著中國特有的宗教思想的靈光,可謂中國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壯成長起來的一朵奇葩。
中國人的宗教意識很濃、很泛,卻也很隨意。一般中國人沒有嚴格的宗教信仰,也很少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對神靈的態度往往處于信與不信之間。無憂無慮時,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種神靈都不信;有災有難時,見到廟宇就燒香,見到神靈(塑像、畫像)就跪拜。大多數古代中國人盡管崇尚實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萬物有靈”觀念影響,在潛意識中還有對神靈的畏懼、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識也是很強的。另一方面,由于影響著中國人的儒、釋、道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彼此之間相對寬容,這就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同一個人可以既崇孔子為師,又求仙訪道、吃齋敬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成了文人們的人生信條。元代畫家兼詩人的倪贊表達更為鮮明,他說:“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禪。”
這種現象正透視出中國宗教思想的一大特點:“泛神”、“準教”。
中國人特有的這種宗教思想特點也影響到古代中國的文化藝術。儒、道、佛相互融合,積淀于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形成一種連續不斷的思想文化氛圍。意境說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理論的核心概念,也無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識的烙印。
而古代中國“泛神”、“準教”特點所帶來的儒、釋、道對立統一現象也決定了其影響意境說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單一的。
關于意境的概念與內涵盡管至今尚無一個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論,但通過文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對意境的內涵也已有許多共識。筆者在此將這種共識概括為:意境是藝術家創造出的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藝術整體,這個藝術整體能通過欣賞者的直觀把握和審美想象產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韻味。意境的內涵也可由此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虛實相生,三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
我國詩文自古就有寫景抒情的傳統。《尚書·堯典》中提出“詩言志”,強調詩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發,《詩經》所用“比興”則是通過言他物(寫景),來發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這也是一種景與情的結合,盡管景只是作為抒的媒介物出現的。人們真正將自然物象的“景”當作獨立的審美對象,則得益于道佛自然觀的影響。老莊主張回歸自然,他們把“心齋”的空明、虛靜當作對自然萬物做自由觀照的條件,認為只有通過這種非理性的直觀思維方式方可達到物我合一、物我兩忘的境界。如《莊子·齊物論》中所寫:“昔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老莊還認為,只有達到這種境界才能領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難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認為大自然的水流花開、鳥飛葉落,與其追求的那種淡遠任運的心境與“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瞬間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對大自然也倍加青睞。道佛對自然的鐘愛,引起了詩人對山水風景的關注,使田園風物自覺地走進詩歌,由詩中的背景升騰為主要審美對象。盡管早在《詩經》中就出現了情景交融的詩作,但那只不過是暗合了藝術創作的規律。有意識地將山水田園作為“主角”寫進詩歌,則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詩家對道禪自然觀的心領神會,使他們在對自然風景的抒寫中確實做到了情與景合、意與象偕,清新、自然,形神畢現,形成迥異于西方藝術再現自然的表現性山水風格,同時,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統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文論家將情與景統一起來,從而較為快捷地解決了情景關系問題。
詩家虛實之說也來源于道家的虛無論與佛家的色空觀。老子曾對“有”“無”關系作過說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認為“有無相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莊子說:“虛室生白”,“唯道集虛”。可見,道家“以虛無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實”。作為一種哲學的宇宙觀,道家將宇宙本體看作是虛實、有無的結合。佛教認為物質世界各種色相全是空幻不實的。修行者接觸色相時應“不于境上生心”(《壇經》),不迷戀、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觀,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實則以“中道”這一有著辯證思維特點的觀念又解除了這一危機。“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種“空”否定一切的同時,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這種虛無觀在魏晉之前已為文人重視,被當作玄學的核心。魏晉時,隨著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觀因其與道家虛無思想有著相通的精神,而強化了對文人們的影響。既然在道家與佛家眼里虛實并生、色空一體,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響的文論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虛實統一的可能性。虛可涵蓋少、情、隱、氣、神、意、主觀等,實則可含蘊多、貌、顯、骨、形、象、客觀等,既然通過直觀思維的“悟”,可以發現虛就是實,那么,通過直觀的藝術思維也會做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隱顯一體,氣骨合一,意與象合,形、神、理的統一。這樣虛實關系的解決,就帶動了這一系列概念之間關系的解決,虛實關系也就成了各關系的統帥與核心。
第8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李 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后各分散。永結無情游,相期邈云漢。
詩文解釋
在花叢中擺上一壺美酒,我自斟自飲,身邊沒有一個親友。舉杯向天,邀請明月,與我的影子相對,便成了三人。明月既不能理解開懷暢飲之樂,影子也只能默默地跟隨在我的左右。我只得暫時伴著明月、清影,趁此美景良辰,及時歡娛。我吟誦詩篇,月亮伴隨我徘徊,我手足舞蹈,影子便隨我蹁躚。清醒時我與你一同分享歡樂,沉醉便再也找不到你們的蹤影。讓我們結成永恒的友誼,來日相聚在浩邈的云天。
詞語解釋
獨酌:一個人飲酒。
成三人:明月和我以及我的影子恰好合成三人。
既:且。
不解:不懂。
徒:空。
將:和。
及春:趁著青春年華。
月徘徊:明月隨我來回移動。
影零亂:因起舞而身影紛亂。
交歡:一起歡樂。
無情:忘卻世情。
相期:相約。
邈:遙遠。云漢:銀河。
名家賞析
詩文賞析一
《月下獨酌》一共四首,這是第一首,是一首抒情詩,是作者抒寫他自己孤獨寂寞、以酒澆愁的苦悶心情。雖然是個人感情的抒發,但也是和當時現實有關的。
李白參加政治活動的時候,唐王朝已開始腐化,是李林甫、楊國忠和皇親貴宦們當權的黑暗時期。他們糾合黨人,排擠異己。李白既“非廊廟器”,又是性格傲慢,當然必為他們所不容。因而在政治上始終不得志,從而對現實不滿。但作為封建士大夫的李白,既無力改變現實,也看不到其他的前途,因而他感到孤寂和苦惱。本詩通過對月獨酌,集中反映了這種思想感情。
這首詩雖然以飲酒賞月為題材,但作者是通過這些題材來抒發他對當時現實的不滿的。它和那些幫閑文人所寫的風花雪月的詩作有根本的不同,在那狂歌醉飲后面隱藏著“愁多酒更少,酒傾愁不來”的憂郁、憤懣的情緒,這情緒多少體現著李白不與封建統治者合作的反抗精神。
詩文賞析二
這是一個精心剪裁出來的場面,寫來卻是那么自然。李白月下獨酌,面對明月與影子,似乎在幻覺中形成了三人共飲的畫面。在這溫暖的春夜,李白邊飲邊歌舞,月與影也緊隨他那感情的起伏而起伏,仿佛也在分享他飲酒的歡樂與憂愁。
從邏輯上講,物與人的內心世界并無多少關系。但從詩意的角度上看,二者卻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也正是中國詩歌中的“興”之起源。它從《詩經》開始就一直賦予大自然以擬人的動作、思想與情感,如“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愁月”“悲風”等等。李白此詩正應了這“興”之寫法,賦明月與影子以情感。正如林語堂所說:“它是一種詩意的與自然合調的信仰,這使生命隨著人類情感的波動而波動。”
但在詩之末尾,李白又流露出一種獨而不獨,不獨又獨的復雜情思,他知道了月與影本是無情物,只是自己多情而已。面對這個無情物,李白依然要永結無情游,意思是月下獨酌時,還是要將這月與影邀來相伴歌舞,哪怕是“相期邈云漢”,也在所不辭。可見太白之孤獨、之有情已到了何等地步!
斯蒂芬?歐文曾說:“詩歌是一種工具,詩人通過詩歌而讓人了解和嘆賞他的獨特性。”
李白正是有了這首“對影成三人”的《月下獨酌》,才讓我們了解和嘆賞他的獨特性的。
今天,無論男女老少,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他舉杯淺酌,都會吟詠“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以表他對所謂風雅與獨飲的玩味。而這首詩的獨特性,早已化入我們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之中了。
詩文賞析三
我歌唱時月亮徘徊,我起舞時影子零亂。清醒之時一起歡聚,酒醉以后各自分散。此詩通過奇妙的想象描寫了一個以月影為伴的詩人酣飲歌舞的奇特場面。詩人化無生命的自然物為有生命有情的人,和它們一同飲酒、唱歌、起舞,并且還要和月亮結成親密無間的好友,充分反映了詩人孤傲、清高、狂放不羈的情懷。當然,這正是詩人對世俗厭倦、對現實失望的反映,是一個具有遠大抱負的人不能施展才能,終生不得志的痛苦心情的流露。全詩以動寫靜,以熱鬧寫孤獨,取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
李白簡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亞碎葉。(今巴爾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時屬安西都戶府管轄)。幼時隨父遷居綿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蓮鄉。
他的一生,絕大部分在漫游中度過。天寶元年(742年),因道士吳筠的推薦,被召至長安,供奉翰林。文章風采,名動一時,頗為玄宗所賞識。后因不能見容于權貴,在京僅三年,就棄官而去,仍然繼續他那飄蕩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亂發生的第二年,他感憤時艱,曾參加了永王李的幕府。不幸,永王與肅宗發生了爭奪帝位的斗爭,兵敗之后,李白受牽累,流放夜郎(今貴州境內),途中遇赦。晚年漂泊東南一帶,依當涂縣令李陽冰,不久即病卒。
李白的詩以抒情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個真正能夠廣泛地從當時的民間文藝和秦、漢、魏以來的樂府民歌吸取其豐富營養,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獨特風貌。他具有超異尋常的藝術天才和磅礴雄偉的藝術力量。一切可驚可喜、令人興奮、發人深思的現象,無不盡歸筆底。杜甫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之評,是屈原之后我國最為杰出的浪漫主義詩人,有“詩仙”之稱。與杜甫齊名,世稱“李杜”,韓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調張籍》)。有《李太白全集》。
關于月的意象
“月”在中國文學中出現頻率成倍增長,至晚唐北宋達于巔峰。“月”自從進入人的審美視野,便不斷派生、衍播出介蘊不盡的象征喻指。
我們知道,月雖然只是自然界中一個純客觀的物象,但它卻逐漸成為華夏之邦人化自然的組成部分,成為詩人某些特定情感的信息載體。正是由于作者在創作時的處境情懷不同,從而導致了他們作品中“月”這一意象的不同思想內蘊,它們在規定的語境中,展示出了難盡言表的情感流程及其集中鮮明的價值取向。他們借月來抒懷言志,因而望月思鄉,望月懷人,望月感懷幾乎成了詩詞中的永恒主題。
下面從幾個不同側面歸納分析一下唐宋詞中“月”這一意象豐富而深刻的內涵:
(一)“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
月本無情,人卻有意。月亮的陰晴圓缺,其實只是普普通通的自然現象,但它卻映射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在以月破狀分離這一意象的詞作中,又可細分為兩小類:
(1)送別之作中的“月”。
“多情自古傷離別”,離別時的那種落沒與惆悵的心情是無以言表的,面對即將離去的親朋好友,只能是“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此時此刻的月亮也帶有幾分凄切傷感的色調。“楊柳岸,曉風殘月。”柳永《雨霖鈴》;以上送別詞中的詩句,具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即“月”的意象都并非“圓月”、“滿月”,而是“殘月”、“新月”。對于這一點,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是從自然科學角度分析,古人遠行,多啟程于黎明之前甚至夜半時分,此時月將西斜,月亮表現出來的特征便是殘缺 的、低垂的、朦朧的,因此,運用“殘月”、“隴月”等意象是符合實際的,是真實的客觀描寫。
(2)懷古、亡國之作中的“月”。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年年花開,歲歲月圓,但常常是物是人非,如今之明月,猶當時之明月,可如今的人事情懷卻已大異于當時了。面對依舊高懸于天的明月,此刻心中難免會涌上一種凄楚的感覺,那難以預料的世遷,只有明月才能作證,正如張若虛在其《春江花月夜》中所嘆:“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二)“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
愛情作為一個永恒的主題,在唐宋詞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描寫男女間純真愛情生活的作品,讀來讓人有一種純樸溫馨之感,余味無窮。在這類表達愛情的詞作中,“月”的意象除了用來烘托渲染幽會時那種恬靜溫馨、柔情蜜意的氛圍之外,也是借月亮的皎潔無瑕來象征青年男女間愛情的純真,給人以美的享受。
在這類詞中,“月”的意象變得美麗而朦朧,色調也較明朗,不再給人以憂傷的感覺,而且往往與“花”相映,充滿了詩情畫意。如“攜手看花深徑,扶肩待月斜廊。”(賀鑄《西江月》,這兩句極其生動地寫出了男女歡會時在花光月影環境中卿卿我我、情意綿綿的情態,給人以溫馨旖旎的印象。而“閑云歸后,月在庭花舊欄角。”由此可見,月與花的意象組合是男女愛情的象征。
(三)“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以月寫相思,自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胭,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后,代不乏人。因為千里共月最易引起相思之情。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然而對于漂泊在外的游子和戍邊的征人來說,淚卻是常流的,有誰能抵御那久別家鄉親人的孤獨之苦呢?
另外,再如:溫庭筠的《菩薩蠻》:“花落月明殘,錦裊知曉寒。”這里所舉的例子中的月大多是“殘月”、“斜月”的意象,這主要是想表現思婦們由于絲絲哀愁,縷縷離恨而整夜難眠,展轉反側,直到天明。真是獨處深閨,幽夢難尋,燈盡夢回,更覺寂寞難堪。這種以象表意,以景結情的“殘月”更有一種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
(四)“我寄愁心與明月” 。
我國是一個有著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那個時代,在森嚴的等級制和嚴格的家長制束縛中,連男子都要遵守許多封建禮法,就更不必說青春年少的女子,她們被綁縛在嚴格的“三綱五常”的道德倫理規范之中,幾乎被剝奪了最起碼的人生自由,她們無權隨意走出閨閣拋頭露面,無權自主愛情婚姻,從肉體到精神上都遭受著嚴重的摧殘。然而,她們畢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少女,對自由美好幸福的愛情婚姻的追求正是她們這個年齡的特征。可是她們隱密的“閨情”又能向誰傾訴?只有那輪天邊的明月才是知音,才是她們癡癡傾吐情愫的對象。正如韋莊在《女冠子》中寫道:“除卻天邊月,沒人知”。把明月引為知己,這倒更顯出了人間的孤獨,“明月不知離恨苦,斜光到曉穿朱戶”。
在這一類表達少女“閨情”的詞中,“月”是作為一個虛實結合的意象出現的,此時常常和“夢”的意象組合在一起,表達一種“覺來知是夢,無勝悲”的情感,說明少女們把月作為她們傾訴對象的空虛縹緲,迷茫惆悵。這樣便能達到虛實相間,相輔相成的藝術效果。
(五)“廬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唐詩宋詞中寫女子傷春惜別之情時,常常用“月”來比喻象征這些純結、美麗、多情的女子形象。如晏殊的《烷溪沙》中“鬢彈欲迎眉際月,酒紅初上臉邊霞。”他用“月”與“霞”來隱喻女子的眉和臉,從而讓人可以想象出這位姑娘的美艷。
(六)“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以上的五大類中,顯而易見“月”都是深深地打上了人的情感烙印的,有喜有悲,有著豐富的情感內蘊。但有時,月亮似乎又不那么多情,歐陽修在他的《玉樓春》中不是說:“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嗎?細細體味一下,其實不然,應該說此處的“月”的意象內涵更加深刻豐富。如果從情感上說,此處的否定正是對前面所分析的五大意象內涵的肯定,因為正是那些“有情之月”才使得歐陽修有了獨創新境的“無情之月”。他認為李后主之《虞美人》詞中的天邊明月與樓外東風,固原屬無情,何干人事?只不過就是有情之人觀之,則明月東風皆成為引人傷心斷腸之媒介了。事實上,他是從情感上轉入了一種理念上的反省與思考,是透過了理念才更見出深情之難解,是對離別無常之悲慨陷入極深之后發出的對人生乃至整個世事滄桑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嘆與。
第9篇:關于中國夢的詩歌范文
[關鍵詞] 黃庭堅;靜觀;真如;灑脫
[中圖分類號]I20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3-5595(2012)01-0082-05
在《五燈會元》、《續傳燈錄》等禪宗典籍中被列為臨濟宗黃龍派門人的黃庭堅,思想中包含大量的佛教思想,這對其思想及詩歌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佛禪觀照外部世界的方式,尤其是佛教“靜觀”的觀照方式對其影響甚巨。投映在其創作上,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具有靜穆之意象及境界的詩句屢次出現,而其許多詩歌中所要表達的亦是頓悟后內心的寂然不動、“離偽妄無遷改”的體驗,亦可稱之為“真如”①,這使黃詩呈現了靜穆的詩美特征;一是以真如之心性觀照外物,將自己理性深沉、抱道而居、超然灑脫的精神境界灌注于日常景物的描寫中,使其詩歌具有“以法眼觀,無俗不真”的灑脫超然之韻與悠然自得之趣。往昔,論者對黃庭堅與佛教之關系也頗為關注,然遍覽有關論文與專著,涉及佛禪“靜觀”與黃庭堅詩歌關系之方面,尚乏相關論述。本文擬從黃庭堅詩文的解讀入手,結合相關資料,力圖揭示佛禪“靜觀”與黃氏詩歌創作之關系。
一、反觀內視、淡泊自持――黃庭堅對佛禪“靜觀”之運用及在其思想層面之體現
黃庭堅的思想最大的特點是立足儒家,融攝佛禪。在黃庭堅關于人格、道德修養的論述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其對于禪宗修行方式的運用痕跡。
(一)反觀內視――黃庭堅對于佛禪“靜觀”的融攝
作為佛教觀照方式之一的“靜觀”,是主體以虛靜之內心、超越之精神體察外界的一種觀照方式,對此佛經中多有論述。《圓覺經》“威德自在菩薩”中曰:“善男子,若諸菩薩悟凈圓覺,以凈覺心,取靜為行。由澄諸念,覺識煩動,靜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于中顯現,如鏡中像。”②本章之偈亦曰:“寂靜奢摩他,如鏡照諸相。”②這種觀照、修行方式乃為“圓覺三觀”之一,亦可依宗密《圓覺經》之注,稱之為“靜觀”。 佛教認為這種靜觀的觀照方式能使修行者在修行中攝心住于緣,離散亂而趨禪定。后來的南宗禪雖然反對坐禪,但是從《壇經》、《宋高僧傳•唐鄴都圓寂傳》及《景德傳燈錄》卷二“南岳懷讓禪師”等禪宗典籍中屢次出現的對坐禪的批評來看,從反面說明了坐禪作為一種修行方式,其實一直是長期存在,并受到重視的。《宗門武庫》中載:“王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山曰:‘相公口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③“元禪師”即蔣山贊元,臨濟宗僧人。從其建議王安石坐禪來看,禪宗僧人其實并不反對坐禪,而其關于坐禪的諸多批評,著眼點乃在于反對“癡禪”及指出坐禪并非唯一修行方式。禪宗認為只要定心不散,行住坐臥皆為定,最重要的乃是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1]。
黃庭堅立足儒家融攝佛禪,發掘出了靜觀與儒家內省的修養功夫的相通之處,并將兩者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反觀內視的修養功夫。黃庭堅曾在《贈謝敞王博喻》中寫道:“道德無多只本心。”[2]1720他認為倫理道德是圣人依人之常情而制定的:“唯圣人能遂萬物之宜,通天下之志。萬物皆得宜,禮之實也;天下皆得志,樂之情也。”[3]1871因而要理解倫理道德,應該在心靈反省的基礎上進行。其《晁張和答秦覯五言予亦次韻》一詩中寫道:“士為欲心縛,寸勇輒尺懦。要當觀此心,日照云霧散。”[3]23表達對于“俗學”歪曲儒道,以致流傳失真的不滿。至于如何改變這種現象,其倡導“觀心”的方式,主張通過觀心、內省,除去妄念,達到萬物一家、彼我一體的最高道德境界。與此相類的論述還有很多,如《論語斷篇》中說:“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④《孟子斷篇》中說:“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思勉古人所以任己者。”④《君子亭》中曰:“君子藏器待時,盤桓于不中也,反身自觀。”④正如周裕鍇先生所言:“從思想淵源來看,黃庭堅接收得更多的是禪宗的心性哲學。”[4]72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月第28卷第1期左志南:靜穆與灑脫黃庭堅強調通過養心治性來達到最高的道德境界,關于養心治性的具體實踐方式,他概括為“反求諸己”、“反聽”、“內視”、“反觀”。其在《覺民對問》中寫道:“聰莫宜于反聽,明莫宜于內視,強莫宜于自勝。古之人能披折萬物,獨見本真。”④在《論語斷篇》中又說:“由學者之門地至圣人之奧室,其途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后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每鞭其后,積自得之功也。”④在《與胡逸老書》其九中寫道:“可試看《楞嚴》、《圓覺經》,反觀自足。”[3]1748黃庭堅強調通過自省,即對自我的省察來達到了悟的狀態,再用此了悟的心性來觀照自己的生活,從而達到為萬物之宰的境界。這種內省的修養功夫,與佛禪“靜觀”住心觀靜以體味真如心性的觀照方式,在方法上具有相通之處。不難看出,其自我省察極有可能是受到佛禪明心見性修行方式的啟發。
黃庭堅立足儒家、融攝佛禪的思想特點,決定了黃庭堅對于“靜觀”的運用是以禪入儒,他力圖將這種佛禪觀照方式運用到自己倫理道德的修養中。關于這一點,可以從“宴坐”一詞的使用中窺全豹之一斑。“宴坐”本是對佛教修行中坐禪方式的一種解釋,而這種坐禪的方式又是與“靜觀”的觀照方式互為表里的,因而考察其人對“宴坐”的使用與理解,可以窺見其人對“靜觀”理解之一斑。王安石詩中之“宴坐”均出現在與佛教有關的題材中,蘇軾詩中亦大多如是。而黃庭堅詩中的“宴坐”既出現在與佛教人物相關的題材中,又多次出現在與友人的寄贈詩文中,其含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佛教坐禪方式,也是主體內心澄明自在精神的一種體現。正如其在《宴坐室銘》中所言:“李子宴處,不惰不馳。觀宇觀宙,使如四肢。不動而動,不行而邁。萬物蕓蕓,則唯我在。”[3]1504雖是對友人的贊賞,實際上也是山谷的夫子自道。黃庭堅對“宴坐”的理解和運用,是置身于靜而觀動,更多的是主體理性精神充盈的一種外在體現。從對于“宴坐”的使用來看,黃庭堅是將“靜觀”作為人格修養的一種方式。
因而,黃庭堅對于靜觀的融攝,是著眼于靜觀與儒家內省學說的相通之處,將佛禪靜觀運用到其人格修養的具體實踐中。
(二)淡泊自持――黃庭堅在融攝佛禪“靜觀”過程中形成的思想特點
山谷之理想人格精神是一種至剛至大、獨立不倚的浩然精神,而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就是學以待世之用,但不以用與不用為意。其《楊概字序》中有言曰:“今夫學至于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耶!”④其詩中亦多相似之語:“文章不經世,風期南山霧。化蟲吟四時,悲喜各有故。吾獨無間然,子規勸歸去。”[2]1184 “無心經世網,有道藏丘山。”[2]71“寂寥吾道付萬世,忍向時人覓賞音。”[2]1070并且黃庭堅重視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自己的人格修養目標,反對空談,其有言曰:“今孺子總發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君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鐘鼓、宮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④此外,黃庭堅十分重視道德修養,具體說來即為“孝友忠信”。他在《答洪駒父書》中說:“自頃嘗見諸人論甥之文學,它日當大成,但愿極加意于忠信孝友之地。”[3]473其《戒讀書》一文中亦曰:“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3] 1683皆主張于日常生活的身體力行中實踐道德倫理的修養。
學以用世、但不以用與不用為意的思想特點,使黃庭堅少了前人或同時代其他人失志時的怨嘆與憤懣,卻多了幾分從容與灑脫。而這種從容與灑脫,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正是其以真如心性,靜觀人世所獲得的一種哲理上的超越;君子之道寓于日常生活中的思想特點,使他更加關注日常生活,并能以不同于常人的眼光看待日常生活,從而能從中發現別人不曾發現的美。前者可謂之淡泊,后者可謂之自持。
淡泊自持的人格境界,使黃氏靜觀的對象不僅是坐禪時內心的體悟,而更廣泛地擴展到其目光所及的各個領域。如“養生遺形骸,觀妙得骨”,“事常超然觀,樂與賢者共”,“蕓蕓觀此歸,一德貫真濫”,“團蒲日靜鳥吟時,爐一炷試觀之”,“志士仁人觀其大”,“隱幾惟觀化,開書屢絕編”,“天地入諭旨,芭蕉自觀身”,“我觀萬世中,獨立無介伴”,“蚊虻觀得失,虎豹擅文章”,“返身觀小丑,真成覆車犢”,“我觀諸境盡,心與古人同”,“萬水千山厭問津,芭蕉林里自觀身”,“觀水觀山皆得妙,更將何物污靈臺”等等。這也是黃氏多次強調“觀”的根本原因。
二、真如靜穆與超越灑脫――黃庭堅對“靜觀”之運用在詩歌創作中的體現
如前所論,黃庭堅著眼于靜觀與儒家內省學說的相通之處,將佛禪靜觀運用到其人格修養的具體實踐中,并形成了淡泊自持的人格特點。此獨特之人格特點與黃庭堅將創作視為人格修養之外在表現的文藝觀相結合,滲透到了其詩歌創作中。
黃庭堅在《奉答茂衡惠紙長句》中寫道:“羅侯相見無雜語,苦問溈山有無句。青草肥牛脫鼻繩,菰蒲野鴨還飛去。”[2]1176其用“露地白牛”、百丈懷海野鴨子事,所要說明的是自己禪學造詣低下,不能呵護佛性,對外部世界之認識也是隨著時空之流轉而變遷。從黃庭堅的自謙之詞中,可以看出其認識到了心隨物轉則會陷入迷誤的境地;只有本心不隨著時空變遷,方能達到更高的人格修養境界。因而黃庭堅多在詩中表現對于“離偽妄無遷改”之“真如”境界的體認與感悟。其有詩曰:“松柏生澗壑,坐閱草木秋。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抗臟自抗臟,伊優自伊優。但觀百歲后,傳者非公侯。”[2]501在詩中他選取松柏、金石兩個相對而言能超越時間空間流轉的意象,來“閱”草木秋凋,“看”萬物流走,以之來突出主體立足于靜以觀動的狀態。在他人伊優、抗臟之時自己卻保持真如不變之本心,從而不失本真。類似這樣的表述還有很多,如“萬物并流,金石獨止。”④“萬物,隨川而東。金石獨止,何心于逢。天地雷雨,草木爭長。松柏不春,以聽年往。”[3]1730
關于這一點,周裕鍇先生曾撰文指出:“黃庭堅詩中常見的意象往往具有堅固永恒或澄明高潔的性質。”并對此一現象之原因進行了比較細致的分析。同時,周先生還認為黃庭堅的詩“追求一種將道德和審美融為一體的人生藝術,道德不再成為外在的枷鎖,因人自心的覺悟而具有‘悠然自得之趣’”[4]75。但是對于這種“悠然自得之趣”,周先生并未進行進一步的探討。黃庭堅詩中具有“堅固永恒或澄明高潔的意象”是黃庭堅以“真如”之本心,靜觀外物時主體精神的體現,可以說是佛禪“靜觀”觀照方式的一種顯性的體現。除了這種顯性的體現外,“靜觀”作為一種與詩歌創作思維相通的觀照方式,對于黃庭堅產生的深遠影響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真如靜穆――理想精神境界的描寫
黃詩中有很多詩篇是對于在紛擾現實中,主體抱道而居、超然灑脫的精神狀態的描寫與贊賞。在這一類詩歌中,又可大致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黃氏寄贈友人之詩。這類詩歌中,其對友人的推崇與贊賞,往往多含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亦可看做是黃氏對自己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描寫。“牧牛有坦途,亡羊自多端。市聲鏖午枕,常以此心觀。”“仲蔚蓬蒿宅,宣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境勝失途窮。寒書萬卷,零亂剛直胸。偃蹇勛業外,嘯歌山水重。晨雞催不起,擁被聽松風。”“車馬氣成霧,九衢行滔滔。中有寂寞人,靈府扃鎖牢。”皆是對友人不為紛亂之外界所擾,保持內心虛靜澄明、甘于淡泊、超然物外之精神狀態的贊賞。“飛城東南,隱幾撫群動。……世紛甚崢嶸,胸次欲空洞”;“八方去求道,渺渺困多蹊。歸來坐虛室,夕陽在吾西”;“吾人撫榮觀,宴處自超然”;“室中凝塵散發坐,四壁矗矗見天下”;“得閑枯木坐,冷日下牛羊”;“觀物見歸根,撫時終宴坐”。這些詩句塑造的皆是以湛然不動之“真如”本心,以冷峻的目光看外界的紛紛擾擾的高潔友人形象。在這類寄贈詩中,黃氏對友人人格的贊賞看似與靜觀的觀照方式并無直接的聯系,但是詩歌中所塑造之形象,皆具有以真如之本心、冷峻之眼光去體察、觀想紛擾外界的超越特質。這是山谷對自己向往的人格、精神境界的具體描寫,而對這種人格、精神境界的體悟與認識,卻正是山谷在用靜觀方式觀照外部世界時所獲得的。
第二類是對于自己精神狀態的直接描述。與第一類在對友人人格境界的贊賞中道出自己的理想境界不同,在黃庭堅對自己精神狀態直接描述的詩歌中,靜觀這一觀照方式的使用痕跡更加明顯。其《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六言二首》其一:“一黃云繞幾,深禪想對同參。”其二:“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春閑。”《子瞻繼和復答二首》其二:“迎燕溫風旎旎,潤花小雨斑斑。一炷煙中得意,九衢塵里偷閑。”《寂住閣》:“莊周夢為蝴蝶,蝴蝶不知莊周。當處出生隨意,急流水上不流。”山谷的這類詩歌皆興象微妙,于一種境界的描述中,表達自己以真如本心靜觀外界時所感受到的無言之美。其《北窗》詩云:
生物趨功日夜流,園林才夏麥先秋。綠蔭黃鳥北窗下,付與來禽安石榴。[2]403
詩中,黃庭堅將自己瞬間所見所感作詩性之表達:萬物隨時而變、生生不息,園林草木皆綠之時,卻已至麥黃熟待收之際。然在語言之外卻隱含其一番感慨,即萬物如此,人世亦然。至于當如何應對此變化,其用閑臥北窗綠蔭之下,聽黃鳥吟唱,看石榴花發答之。乃聽其自然之意。因而任淵注曰:“末句蓋有所寄,言物化各用事于一時,姑聽其自然耳。”其在寫景的同時融入了自己冥心靜觀時所得的生命體驗,遂有悠游自得之味。
錢志熙先生曾指出:“山谷常借某種具體境界,傳達其內心所感悟到的那些無言之美。”[5]此“無言之美”正是黃氏以靜觀之方式觀照外物時,內心對真如心性之體驗的外在表現。
(二)超越灑脫――主體精神于景物描寫中的體現
《新華嚴經論》中有言曰:“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童女、仙人、外道五十三人,各各自具菩薩行,自具佛法。隨諸眾生見身不同,不云有轉。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間肉眼觀,無真不俗。”⑤《宗鏡錄》中亦云:“一切諸法中,皆有安樂性。所以云:若以肉眼觀,無真不俗;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⑥靜觀對黃詩之影響還體現在以靜觀之方式觀照外物時,“法眼”所到,無俗不真,即能于平常之處發現新的美,從而于常見之景的描寫中翻出新意。正如惠洪《冷齋夜話》中載:“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為我輩設。’”[6]如其《次韻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二之前半曰:“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青春白日無公事,紫燕黃鸝俱好音。”在世態千變萬化之際,真如之本心湛然自在,不受塵緣染污,以此心觀之,無公事之時即是良辰,鳥雀之鳴叫俱是悅耳之音。這正是靜觀外物時,真如之心性的體現。這也與《圓覺經》中強調觀照外界時覺性平等不動、遍滿法界的眼光有關,“由彼妙覺性遍滿故,根性塵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故,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遍滿無壞無雜。”②對于說過“可試看《楞嚴》、《圓覺經》,反觀自足”的黃庭堅來說,他對這種觀照方式肯定是極為熟悉的,其《題意可詩后》一文中就曾引用“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這也使得他在詩歌創作中實現了真如本心的灑脫表現:
打荷看急雨,吞月任行云。夜半蚊雷起,西風為解紛。
茗夢中覺,荷花鏡里香。涼生只當處,暑退亦無方。[2]636
山下三日晴,山上三日雨。不見祝融峰,還溯瀟湘去。[2]678
前兩首《和涼軒二首》作于崇寧二年,是黃庭堅寫自己用虛靜方式觀照外物之所見與所感。第一首描寫的是雨過天晴,皓月升空而后復被密云所蔽之過程,急雨灑落于荷葉之上,皓月為微云所慢慢吞沒,夜半雨勢將至空氣悶熱,蚊蟲聚集,嗡嗡作響,接著落雨前之涼風將其一掃而空。在此過程的描述中,聽、看的主體,就是內心寂然不動、超然物外的詩人本身。第二首寫自己于涼軒所見、所感,香茗一杯,芰荷十里,對此美景,不但世間之奔競可以忘卻,就連暑氣也被面對美景而生的灑脫胸襟所化解。第三首《離福巖》作于崇寧三年赴宜州貶所途中,山谷用寥寥數語淡然敘述了自己途中所歷,將自己內心湛然不動、不以遷謫為意的灑脫情懷現于言外。以上詩中皆寫自己日常所見之景物,然皆由“法眼”靜觀之角度出之,遂有迥異于流俗之超越灑脫之美。黃庭堅在經歷了貶謫的經歷和各種磨難后,用真如本心,靜觀外物之變遷,實現了對自己生命困境的灑脫超越,正如黃火火冖田《山谷年譜》中所引范廖之語:“先生雖遷謫處憂患而未嘗戚戚也,視韓退之、柳子厚有間矣。東坡云御風騎氣與造物游,信不虛語哉!”[7]
黃庭堅對于靜觀這一觀照方式的運用,與他推崇主體理性深沉、抱道而居、超然灑脫的精神境界是緊密相連的,這也使黃詩呈現了真如靜穆之美;而以真如之本心靜觀外物時,黃詩又呈現了“無俗不真”、超越灑脫之美。正是黃庭堅本自“真如”自性,將佛禪“靜觀”與詩歌創作思維相融,才使得黃詩呈現了真如靜穆與超越灑脫兩者深層次上的融合。
三、結語
《潛溪詩眼》中載:“山谷言學者苦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白。”[8]黃庭堅一直力求不蹈前人覆轍,自出機杼,主張在詩歌語言、境界上實現創新。這種創新精神與黃氏對靜觀之融攝相結合,造就了其獨特的詩學觀,即追求不俗與提倡苦思。關于前者,黃庭堅向往理性深沉、超然曠達的精神境界,以真如之心性,靜觀世遷而內心湛然自如。這種獨特、高邁的人格精神投映到其詩作中,使其作品迥異于流俗。關于后者,黃庭堅對靜觀的融攝,使其在創作思維上實現了革新。《文心雕龍•神思》云:“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9]黃庭堅融攝靜觀,為虛靜注入了新的意義。其用“法眼”靜觀外界,跳出前人窠臼,照見事理,從而做到了“以俗為雅,以故為新”。
注釋:
① 見子集《首楞嚴義疏注經》(《大正藏》第39卷89頁)。
② 見宗密略疏《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第39卷)。
③ 見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大正藏》第47卷)。
④ 見黃庭堅著《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⑤ 見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大正藏》第36卷)。
⑥ 見永明延壽《宗鏡錄》(《大正藏》第48卷)。
[參考文獻]
[1] 慧能.壇經校釋[M].郭朋,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31\|32.
[2] 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M].任淵,等注,劉尚榮,校點.北京:中華書局,2003.
[3] 黃庭堅.黃庭堅全集[M].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4] 周裕鍇.夢幻與真如――蘇、黃的禪悅傾向與其詩歌意象之關系[J].文學遺產,2001(3).
[5] 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36.
[6] 惠洪.冷齋夜話[M]//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34.
[7] 黃火火冖田.山谷年譜[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951\|952.
[8] 范溫.潛溪詩眼[M]//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317.
[9] 劉勰.增訂文心雕龍校注[M].楊明照,等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369.
Solemn and Natural: the Discussion between Huang Tingjians Study
of "Observing Calmly" and His Poetry Creation
ZUO Zhina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