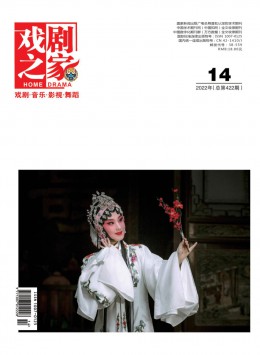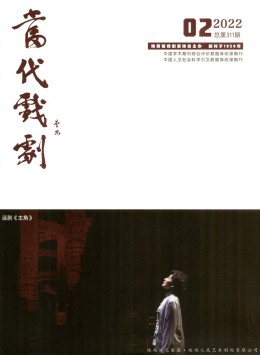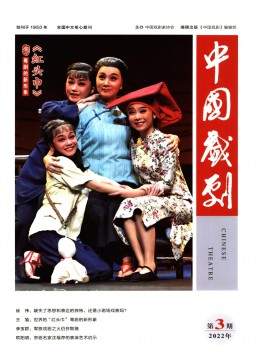戲劇影視文學文藝常識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戲劇影視文學文藝常識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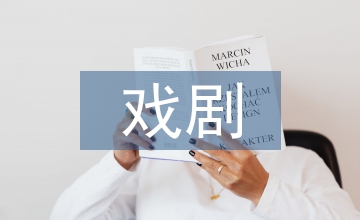
第1篇:戲劇影視文學文藝常識范文
作者簡介:康爾(1957- ),男,漢,江蘇鹽城人,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戲曲學博士,南京大學文化藝術教育中心主任,南京大學藝術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教育部戲劇、影視、廣播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普通高校藝術教育專家講學團成員。研究方向:藝術學,影視學,藝術文化學。
摘 要:把美酒釀成毒藥的是王彩玲;把追求變為成悲劇的是王彩玲;把落日認作朝陽的還是王彩玲。電影《立春》將一個烈女追日的故事演繹成了飛蛾撲火的悲劇,顯現出該片是一部典型的“他”敘事的作品。主創在向觀眾呈現那個年代的小城市的男權社會的特性的同時,也將主創內心的男性中心主義和父權主義的深層積淀,一不留神作了展陳。
關鍵詞:電影;《立春》;藝術特點;王彩玲;男性中心主義;父權主義
中圖分類號:J902
文獻標識碼:A
Pursuing the Sun or Plunging the Fire?
-Also on the Figure of WANG Cai-ling in And the Spring Also Comes
KANG Er
按說,最有資格談論王彩玲的,應該是顧長衛和蔣雯麗。因為前者是《立春》的導演,后者是王彩鈴的扮演者;因為對于王彩鈴,他們倆接觸得最早,揣摩的時間也最長。可是,看了《電影藝術》對他倆的訪談錄陸紹陽《夢猶在,理想不滅――顧長衛訪談》,林洪桐《應知秋實總有根――蔣雯麗訪談》,《電影藝術》,2008年第2期,第65-75頁。,筆者以為,無論是顧長衛還是蔣雯麗,都還沒有將王彩鈴這個人物形象的深層蘊意說到位,甚至令人產生了南轅北轍的感覺。
顯然,人物已經背叛了主創,結果也已背離了初衷。觀眾看到的王彩鈴,根本就不是顧長衛和蔣雯麗想象中的、言說中的王彩鈴。筆者不揣淺陋,也來談一談電影《立春》中的人物形象王彩玲。
一、把美酒釀成毒藥的,為什么是王彩玲?
電影《立春》是顧長衛執導的第二部故事片。在第一部影片《孔雀》的結尾處,主創為影片中不太爭氣的“弟弟”設計了這樣一段旁白:“那一年冬天,爸爸突然去世了,媽媽變老了,我們還好。我恍惚記得,爸爸走的那天,很快就是農歷立春了。”這段結束語,給人留下了期盼,留下了對于春天的遐想。《立春》問世之后,觀眾們驚訝地發現,顧長衛這一回向世人呈現的,仍然是在命運的隆冬里無奈掙扎的女人,其慘烈的程度較之于《孔雀》有過之而無不及。
《立春》所的表述故事,發生在一個名叫“鶴陽”的偏遠小城里。其時間跨度,依照顧長衛自己的說法,啟始于1986年,結束于1992年。陸紹陽《夢猶在,理想不滅――顧長衛訪談》,《電影藝術》,2008年第2期,第65頁。那段時期,中國的社會轉型已經開始,空洞的理想、僵化的信念、傳統的價值觀失去了昔日的光澤。每個人都想干點什么,但多數人并不知道應該干什么、究竟怎么干。在困惑、彷徨滋生蔓延、揮之不去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準確地說是小城居民對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想象,突然間成了年輕人追逐的對象。
影片《立春》,準確地展呈了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對于想象中的西方文化的追捧。音樂教師王彩鈴,特別癡迷西洋歌劇。唱進巴黎歌劇院,是她的追求與夢想。無業青年黃四寶,特別迷戀西洋繪畫。成為當代中國的凡高,是他的人生目標。群藝館的胡金泉,特別鐘情西洋芭蕾。能夠用腳尖跳舞,是他活著的價值與理由。就連五大三粗的工人周瑜,也特別崇拜西洋文學。對于普希金的詩作《紀念碑》,他居然能夠倒背如流。在這撥年輕人的心目中,西方文化是一壇美酒,令他們陶醉,令他們亢奮,令他們忘卻了小城生活的平庸與瑣碎。浸泡于其中的他們,鄙視庸俗,推崇高雅,以藝會友,時分時合地抵御著來自方方面面的非議,享受著幻想的。應該說,用天馬行空式的想入非非去慰藉青春的煩惱,并不是一個特別糟糕的生活策略,尤其是在影片所規定的那樣的時空中。
然而生活的法則是:現實必然驅散幻想,成熟必然取代幼稚。認清并無奈地接受這樣一條法則,是每一個年輕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可能遭遇的經歷。影片中的那幫年輕人,同樣也不能例外。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一個個都從陶醉中醒來了。黃四寶丟棄了畫筆,下海經商,開了間婚姻介紹所,日子過得似乎不賴。周瑜拋開幻想,找了個本分姑娘,結了婚也生了孩子。胡金泉的心理上雖然有些毛病,但他也在醒悟。當王彩鈴提出“等我有了娃就跟你學跳舞”時,胡金泉平靜地答曰:“你就別害他(她)吧”。貌似隨意的一句話,道出了他的大徹大悟。惟有王彩鈴,過了青春期之后依舊執迷不悟。縱然碰得鼻青臉腫,仍然癡心不改。她整日沉浸在普契尼的歌劇《托斯卡》所營造的藝術幻境中。由于她認定她就是“為了藝術、為了愛情”來到這個世上的;由于她堅持“寧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李一筐”的擇友、處世原則,結果,耽誤了戀愛結婚、生兒育女等許多人生大事,落得個等人來送女性棒的下場。由于王彩鈴在幻想中沉溺太久、陷得太深,她硬是把一壇美酒釀成了攻心的毒藥。而正是這味美酒釀成的毒藥,徹底地毀了王彩鈴的前半生。
看完了電影《立春》,筆者突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把美酒釀成毒藥的為什么不是別人?為什么不是曾經是同道者的那幫男性青年?為什么偏偏是王彩玲?從電影《立春》中,我們能夠解讀到的答案只能是:沉溺于幻想、墜落于虛榮而久久不能自拔,是女性,尤其是崇拜西方藝術的女性,天生的毛病。否則,確實無法解釋。
二、把追求變為成悲劇的,為什么是王彩玲?
在電影《立春》中,王彩鈴、黃四寶、胡金泉和周瑜等男女青年擁有相似的愛好,懷揣同樣的追求。依據評論界的主流觀點,他們都是“被所謂的藝術和所謂的愛情扭曲了的、懷抱理想主義的‘文藝青年’形象”。張民《立春:理想主義的墓志銘》,《電影藝術》,2008年第2期,第25頁。然而有所不同的是,黃四寶等三位男青年的追求,更多的具有喜劇色彩。換言之,他們都把對想象中的西方文化的追隨演繹成了一幕幕喜劇。例如,黃四寶在小城里找不到模特,只能畫的自己。知道母親不可能理解他的“下流”行為,在母親突然闖入時,赤身的他只能在床下躲藏。胡金泉的最愛,就是穿著一雙芭蕾女鞋翩翩起舞。為了證明自己的偉岸,他將一個女學生拖進了男廁所實施了“假”,“拔掉了卡在全市人民喉嚨里的那根刺”。周瑜在背誦普希金的《紀念碑》時,激情澎湃、才情飛揚。但因為用的是方言,其效果顯得非常滑稽,令人看后忍俊不禁。筆者注意到,在電影《立春》光碟的封面上,有“顧式幽默”四個字,估計是商家所為。我想,在電影《立春》中能夠體現“顧式幽默”的情節與細節,都與那幾個男青年有關,展現的也都是那幾個男青年的鬧騰。而作為女性的王彩鈴,她的追求、她的鬧騰,最終則演變成了一場典型的悲劇。
在師范學校的院子里,黃四寶當著許多學生的面,毆打、羞辱了前一天夜里與他同床的王彩鈴。這樣令人難堪、令人蒙羞的舉動,使得王彩鈴萬念俱灰。于是她選擇了自殺,從一座佛塔上跳了下去。從表面上看,是初戀的失敗,是黃四寶的絕情,導致了王彩鈴的自殺。其實,這些都是外部原因,都是引發悲劇的導火線。悲劇產生的內在原因,還是王彩鈴擬“洋”不化、一意孤行的所謂追求。
要想真正讀懂王彩鈴,還得從她鐘情的三幕歌劇《托斯卡》說起。歌劇《托斯卡》,講述了這樣一個浪漫的悲劇故事:1800年,羅馬畫家馬里奧?卡伐拉多西被當局逮捕了,其原因是他幫助政治犯安格洛蒂潛逃。歌劇女演員托斯卡,是畫家馬里奧的戀人。得知馬里奧正在獄中受刑,托斯卡心急如焚。心懷鬼胎的警察總監斯卡皮亞,以處死馬里奧來威逼利誘托斯卡,脅迫她就范。托斯卡將計就計謀,假稱愿意委身于斯卡皮亞。于是警察總監答應,搞一次假處決,讓馬里奧獲得自由。托斯卡在拿到了警察總監簽發的離境通行證之后,趁其不備殺死了他。黎明時分,馬里奧被押往刑場。托斯卡悄悄告訴她的戀人,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這只是一次假處決。不料,這是警察總監玩弄的計謀,畫家馬里奧被劊子手真的處決了。托斯卡悲憤欲絕,唱了一首肝腸寸斷的詠嘆調之后,從古堡上飛身而下,徇情自殺了。
在王彩鈴的白日夢中,落魄青年黃四寶就是羅馬畫家馬里奧?卡伐拉多西,而她自己則是美麗的歌劇演員托斯卡。王彩鈴曾經寬衣解帶為黃四寶當模特。這樣突兀的行為,在王彩鈴的想象中,是托斯卡為她的畫家戀人卡伐拉多西獻身。中國沒有古堡,于是,她選中了高高的佛塔。她縱身從塔上跳下,與其說是自殺,還不如說是在悲情演繹經典歌劇《托斯卡》。在人生的大舞臺上,王彩鈴一直在追隨、模仿著歌劇中的主人公托斯卡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生活模仿藝術,特別容易出現悲劇。更不用說被模仿的作品本來就是一出悲劇。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有人模仿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中的改革家喬廠長,有人模仿電視劇《新星》中的縣委書記李向南,結果都遭遇了失敗,甚至釀成了悲劇。有人曾經追問《喬廠長上任記》的作者蔣子龍:喬廠長的改革是成功的。我學他的樣子做了,為什么我沒有成功?蔣子龍的回答大意是:誰讓你學喬廠長了?誰讓模仿小說中的人物了?正因為有許多理想、許多美好的愿望在生活中不可能實現或很難實現,它們才會出現在文藝作品中的。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由于生活模仿藝術而導致的悲劇中最慘烈的當數了。唱完大戲就造反,穿著戲服舉義旗。一幫北方農民把自己都想象成了刀槍不入、所向披靡的劇中好漢。在焚燒了教堂、打劫了官府之后,被清軍剿殺得一敗涂地、血流成河,留下千古奇冤。
說王彩鈴把追求變成了悲劇,還不僅依據她曾經自殺過并摔壞了腿和腳。王彩鈴的悲劇還在于,在她自殺獲救之后,不再年輕的她容貌變得更加丑陋了。對于一個想當演員的女人來說,這可真是徹頭徹尾的悲劇。
筆者特別想知道的是,把追求變成悲劇的,為什么不是別人,為什么不是黃四寶、胡金泉、周瑜他們,而偏偏又是王彩玲?從電影《立春》中,我們發現,在主創的敘事中,暗含著一個預設:美麗的容貌是女性夢想成真的先決條件。女性永遠擺脫不了“被看”的地位,想當演員的女性更是如此。女性永遠是男性觀看、、發泄性想象的對象。因此,即便王彩鈴的追求不是當歌劇演員,她那臃腫、肥胖的身材和長有齙牙、痘疤的相貌,也決定了她的一生必將充滿悲劇性。
三、把落日認作朝陽的,為什么是王彩玲?
雖說,王彩鈴的終極夢想是唱進巴黎歌劇院。但是她也知道,從“鶴陽”去巴黎的路途非常遙遠,還得分幾步走。首先得有北京戶口,其次得躋身于中央歌劇院。為此,她不惜重金托人購買北京戶口。面對手段并不高明的騙局,她寧可相信機會還是存在的,也不愿意承認自己遇到了京城的混混。她死皮賴臉地去糾纏中央歌劇院的院長,并聲稱,即便是勤雜工,她也愿意干。王彩鈴年復一年地奔走、哀求與付出,換來的全是無效勞動。究其原委,除了自身的條件與歌劇演員的差距較大之外,還因為她所迷戀的西洋歌劇,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早就不再是朝陽藝術了。
西洋歌劇(opera in musica)誕生于16、17世紀之交,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加入音樂伴奏的悲劇。學術界通常把意大利的佛羅倫薩(而不是法國的巴黎)認定為歌劇的誕生地,將佩里擔任作曲的《達芙妮》(而不是普契尼的《托斯卡》)認定為有史以來第一部也是最經典的西洋歌劇。這種融音樂、戲劇、詩歌、舞蹈、舞美、雜耍為一體的豪華的、浪漫的藝術樣式,經過300年左右的發展,在20世紀初期已經顯現出衰落的跡象。人類有史以來最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驅散了世人延續了幾百年的浪漫情懷。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派思潮,徹底取代了文藝界的浪漫主義,使得以浪漫為特性的西洋歌劇,變成了一門即便在西方也不可能發生逆轉的夕陽藝術了。
在遠離意大利的中國,歌劇的命運同樣走過了由興盛到衰敗、從大紅大紫到無人問津的不可逆轉的歷程。共和國成立之后,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的催生下,在革命的浪漫主義情懷的烘托下,中國的歌劇(主要是民族化的歌劇)經歷過一個短暫的輝煌期,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創作出了《洪湖赤衛隊》、《江姐》、《劉三姐》等一批具有中國氣派的歌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后,滾滾而來的商品大潮,將中國的歌劇藝術沖上了危崖險灘。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沒人再愿意為特別燒錢的歌劇買單了。歌劇院的院長們,每天在思考的不是怎樣發展而是如何生存。正如片中的那位歌劇院的院長所言,“我們這里的演員,幾年也輪不上一個角色。怎么可能進人呢?”
可以對于這一切,王彩鈴卻渾然不知。固執地把落日認作朝陽,把困難重重、行將倒閉的歌劇院看作輝煌的、美妙的藝術殿堂。這個錯覺,決定了王彩鈴的命運必然具有悲劇性。生活的常識告訴我們,追求本身需要時間,需要經歷許多過程,而在這段時間和過程中,被追求的對象的性質與價值可能發生重大的變化。如果追求者一意孤行,不能及時調整追求目標,等待著追求者的必然是悲劇。這樣的道理應該誰都懂得,只有王彩鈴不知道。許多評論家,包括《立春》的主創,將這種無視現實、刻舟求劍式的追求視之為王彩鈴有理想、有抱負的依據,筆者實在不敢茍同。
對于在追求的名義下實施的愚蠢的行為,筆者想要追問的是,把落日認作朝陽的,為什么不是別人,不是迷戀過西洋藝術的黃四寶他們,而偏偏還是王彩玲?主創沒在影片正面回答。但是,從《立春》的敘事邏輯中,我們能夠解讀到的邏輯起點是:愛虛榮、見識短,無視現實、刻舟求劍,是小地方的女人與生俱來的弱點。
四、結語
依據上述三點追問與思考,我們發現,對于王彩玲這個人物形象的塑造,主創在敘事中遵循著這樣一個潛在的邏輯:由于沉溺于幻想是女性天生的毛病;由于美麗的容貌是女性夢想成真的條件;由于愛虛榮、見識短是女性固有的弱點;所以,只有王彩玲一個人,把美酒釀成了毒藥,把追求變為了悲劇,把落日認作了朝陽。結果,把一場貌似烈女追日的艱辛的馬拉松,演繹、表述成了注定要失敗的飛蛾撲火。
對于筆者的這番推導,顧長衛可能不愿意接受。因為他曾反復宣稱,他是在為“理想不滅”唱贊歌,他是在謳歌“理想主義者”。論及電影《立春》及主人公王彩鈴時,顧長衛曾經說道:“我想這個人如果能夠活下去,能夠一直與理想為伍,她的生命就是精彩的。”陸紹陽《夢猶在,理想不滅――顧長衛訪談》,《電影藝術》2008年第2期,第69頁。“我覺得這種理想主義的東西,或者是這樣的精神都會像接力賽式的傳遞下去。”同上,第66頁。蔣雯麗的觀點與夫君的幾乎一樣。但是,無論主創在影片之外如何表白,對于王彩鈴這樣的人物,是謳歌還是嘲諷,觀眾自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