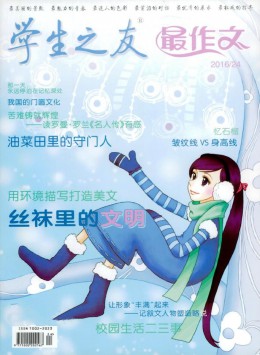紅樓夢作者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紅樓夢作者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1、曹雪芹,1715年至1763年,男,清代小說家。名沾,字夢阮,雪芹是其號,又號芹圃、芹溪;
2、祖籍遼陽,先世原是漢族,后為滿洲正白旗“包衣”人;
3、《紅樓夢》,原名《石頭記》,中國古典長篇章回體小說,中國四大名著之一;
第2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摘要】在《紅樓夢》里,人物的服飾也熠熠閃光,美不勝收。曹雪芹為他筆下人物設計的服飾,不管是在體制上,還是在款式、色彩上,都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我們透過那多姿多彩的服飾,看到了明清時期服飾方面的禮儀體制和審美理想。
【關鍵詞】紅樓夢;明清服飾;美學
服飾作為人的一種文化表征,必然成為社會文化的體現(xiàn)方式,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在《紅樓夢》這座金碧輝煌的藝術殿堂里,人物的服飾也熠熠生輝,美不勝收。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人物服飾的設計,無論是從款式還是從色彩上,都是經(jīng)過精心設計的,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可以說服飾是人的第二皮膚,也體現(xiàn)著對美的一種追求,是美的一種張揚和延續(xù),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很注重明清時期服飾的美學,賈府里面的人物服飾,一個個都是富麗堂皇,充分體現(xiàn)了人物的地位和命運,作者通過對服飾的描寫,把人物的心理和智慧的外在美充分體現(xiàn)出來。
一、紅樓夢中的服飾特點
首先,在《紅樓夢》中的人物服飾主要體現(xiàn)的是明清時期服飾的特點,在作品中描寫的《紅樓夢》的服飾和現(xiàn)實中朝代的服飾是不太相同的,可以說曹雪芹在描寫《紅樓夢》的服飾的時候是受到當時社會環(huán)境背景限制的,人物碰到正規(guī)的禮儀場合,就嚴格按照清朝的服飾制度穿戴的。但是作者又不完全按清制裝扮人物,以便給自己的藝術創(chuàng)造一個廣闊的天地,從客觀上看,清朝雖然廢除了明代服飾,但在有些方面還是沿用了明代的。由此可以看出,《紅樓夢》的服飾雖然有著曹雪芹自己的美學追求,但總的來說遵循的還是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審美標準。
其次,紅樓夢中的服飾大多以紅色為基調,而且多為描寫年輕美麗的女性服飾。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以紅色比喻美色,女子的服飾以紅為美,以紅為貴。比如,紅樓夢中對王熙鳳的服飾的描寫有三次,其中有兩次就以紅色為主。在當時,紅色不僅僅是美麗的代表,更是高貴吉祥的象征,而高貴就是美的表現(xiàn),書中所有的年輕女子個個美若天仙,所以都必須要有美的服飾與之搭配,而作者在設計時也是把美和高貴結合在一起了,同時也體現(xiàn)了明清時期封建社會把服飾禮儀作為當時重要審美標準。
二、《紅樓夢》中體現(xiàn)的明清時期服飾美學《紅樓夢》所展示的明清服飾是宏大和精微并存的。《紅樓夢》中的服飾大量運用許多蘊涵豐富意義的圖案,這些圖案都是祈求祥和,或者是權利和統(tǒng)治階層的象征,也或者是對長壽和生命健康的崇拜。
(一)代表了明清時期服飾文化的審美標準
我們可以從書中描述的賈府人物的服飾看出,它們代表了明清時期服飾文化最高的審美價值,顯示了極高的審美品味和美學追求。在《紅樓夢》中,人物的服飾描繪渲染出錯彩鏤金的輝煌之美的一面,也有體現(xiàn)芙蓉出水般的清雅之美的一面。《紅樓夢》中的服飾深刻展示出明清時代的服飾文化的特點:當時的社會更趨向于崇尚繁麗華美,趨于諸多粉飾太平吉祥的祝福之詞,將這些吉祥祝詞施之于圖案之上,增加華貴的審美氛圍。通過《紅樓夢》中對服飾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時代服飾特征表現(xiàn)為生動豪放、色彩濃重、簡練醒目,反映出了他們的審美形態(tài)。尤其是清代服飾,更加注重于繁縟的藝術樣式和風格,使得在服飾用料、飾物等方面突出強調精致細密。在《紅樓夢》中充分體現(xiàn)了由于滿漢服飾的融合,出現(xiàn)了清代服飾花樣豐富多彩的趨勢,它基本以明代服飾和清代服飾混合法來塑造人物。如紅樓夢中賈寶玉、王熙鳳、薛寶釵等主要人物的服飾都具有時代的代表性,是當時流行的時裝,他們的服飾都是富麗堂皇般的錯彩鏤金之美。在林黛玉的服飾上,主要體現(xiàn)的是清新淡雅,猶如芙蓉出水,與其他人的服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主要是形象塑造的需要,也是特定人物的審美需求。
(二)體現(xiàn)明清時期服飾自身美的規(guī)律
服飾不僅要符合明清時期一定社會、階級的審美標準,而更為關鍵的一點是要合乎服飾自身美的規(guī)律。在社會中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而其服飾也是不盡相同的。在《紅樓夢》中,每個人物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下穿戴的服飾,它的款式和顏色的搭配是不相同的。曹雪芹明白服飾的款式和色彩對人物角色描寫的重要性,因此按照美學的規(guī)律設計人物的服飾,為人物形象服務。比如說在林黛玉第一次進賈府看到賈母的丫頭的服飾,感覺她們穿紅著綠與別家不一樣。這主要是因為賈母的地位決定的,賈母以享受為主,所以她不僅需要像鴛鴦那樣善于體察迎合她的丫頭,也要求丫頭在外表上也要賞心悅目,所以這樣穿著的丫頭放在賈母房里實在是合適不過了。“穿紅著綠”既對塑造賈母的形象起了烘托作用,又合乎美的規(guī)律。
(三)體現(xiàn)明清時期人物形象性格
《紅樓夢》中的服飾是明清服飾的一個縮寫,體現(xiàn)著明清時期人們如何運用服飾美學來美化人的外貌,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服飾是人主動裝飾自己外貌的部分,它能夠有效地烘托人物外貌,這就是人類運用服飾進行裝飾的目的。好的服飾能夠使得人物外貌變得更美,就像我們通常所說的“三分長相,七分打扮”。因此,在《紅樓夢》中的服飾款式上,作者幾次描寫到寶玉穿箭袖衣,而箭袖衣是窄袖袍服,窄袖袍服是滿族游牧尚武的民族傳統(tǒng)流傳下來的,賈寶玉雖然不是習武的,但是穿上它可以顯得英俊干練、風流瀟灑。如果是變成穿寬袖長袍,那么就會顯得更適合讀書人,顯得老氣橫秋,這樣就不符合賈寶玉的形象和性格了。另外,服飾怎么打扮和什么樣的人喜歡什么樣的服飾,就要受到一定的思想引導了,這就能夠充分體現(xiàn)出一個人的內在修養(yǎng)、氣質和性格。因此,在明清社會中,服飾除了能突現(xiàn)人的外貌和性格以外,還可以體現(xiàn)出人的身份地位,上到帝王后妃、達官貴人,下到黎民百姓的衣冠服飾,這些都是有嚴格的區(qū)別,這種等級差別一直貫穿整個明清社會中,通過不同的服飾,我們可以看出人物經(jīng)濟狀況的好壞和身份地位的尊卑高下。
(四)體現(xiàn)明清時期服飾美學的環(huán)境背景
人物總是要在一定的環(huán)境中活動的,因此人物的服飾不僅要與人物相配,還要經(jīng)常變化,在更大的范圍內與周圍的環(huán)境、氣氛協(xié)調一致,才更具有美的效果。在《紅樓夢》中,作者能夠很好地利用服飾這個媒介,利用服飾的款式和色彩的變化來引出情節(jié)的變動,并推動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最終實現(xiàn)為揭示人物性格服務,為服飾增添了新的審美價值。比如說,在婚姻問題上講究姻緣的明清時期,在描述賈寶玉和薛寶釵的“金玉良緣”、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木石前盟”的問題上,作者通過人物的服飾來表達其思想,通過一個人穿什么服飾來表現(xiàn)他的性格,進而顯示出他們在處理問題上的差異,揭示人物命運,體現(xiàn)了當時社會的大背景環(huán)境。又如,在對晴雯服飾的描寫上,作者花的筆墨不少,通過她與服飾有關聯(lián)的情節(jié)鮮明地突現(xiàn)了她位卑而人不賤、剛義潑辣、愛憎分明的性格。服飾在紅樓夢中的審美價值不僅表現(xiàn)在人物的穿戴上,還在作品內容上是一個有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三、結語
綜上所述,《紅樓夢》中的服飾主要是在不違背清廷禁律的前提下,按照明清時期服飾的審美標準來進行的,遵循了明清時期美學的創(chuàng)造規(guī)律。《紅樓夢》通過運用服飾來塑造人物形象,渲染不同的環(huán)境氣氛,點綴大自然的景色,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同時體現(xiàn)封建的倫理道德。可以說,《紅樓夢》中的服飾是集明清時期社會服飾美之大成,是研究明清服飾美學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參考文獻:
[1]陳東生,甘應進,周麗艷,覃蕊.清代滿族風俗與《紅樓夢》服飾[J].太原大學學報,2006(3).
[2]崔榮榮.《紅樓夢》人物服飾——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的縮影[J].武漢科技學院學報,2004(6).
第3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關鍵詞:莊子;紅樓夢;好了歌;賈寶玉;浮生若夢
中圖分類號:I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2)15-0027-01
一、《紅樓夢》主題歌《好了歌》蘊含的主旨
莊子人生哲學的核心是追求精神的自由與絕對自由。莊子認為,人如果能順其自然之性,也就是縱情任性,便得自由,但這只是相對的自由。至于什么是絕對自由,如何獲得絕對自由,《逍遙游》作了詳盡的闡述:有所依賴的自由,只能算作相對自由,無所依賴的自由才是絕對自由。《紅樓夢》主題歌《好了歌》旨在指出若要人生好,須要“了”了“功名”、“金銀”、“嬌妻”、“兒孫”。而莊子主張“無名”“無功”“無情”,最終才能獲得精神的絕對自由。由此可見,兩者旨趣的完全相同。
《好了歌》主張了情,而《紅樓夢》開篇卻說此書“大旨談情”,二者看似相悖,其實則不然。從“開辟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可見,本書確實寫情。但是書到最后,幾乎所有情癡情種都以死退出了人生的舞臺,而寶玉最終無情,隨和尚道士離開了滾滾紅塵,復得“天下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的逍遙。可見《紅樓夢》用那“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讓人了解:人生最苦,情難了,無情最逍遙。在功名、金銀、情感中,不慕功名最易,不貪金銀次之,難舍者乃在“情”。若無情則無所不能“了”,如此便能逍遙。由此看來,《紅樓夢》“大旨談情”的真正目的在于勸勉世人“無情”,因此可以說莊子思想已深入《紅樓夢》骨髓了。
二、寶玉的命運與道家思想的聯(lián)系
對老莊人生哲學的認同,作者在塑造賈寶玉這個人物形象上尤見其功力。第三回寶玉首次登場亮相,作者用兩首《西江月》詞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這兩首詞將其縱情任性、蔑視功名富貴的超凡脫俗概括得淋漓盡致,生活中的寶玉也的確如此。寶玉蔑視功名富貴,縱情任性,因而也逍遙自在,這正是老莊所謂自由的境界,但它還未能達到絕對自由的境界。因為寶玉夢游“太虛幻境”時,警幻即道破寶玉本性:乃“天下第一人”。
寶玉無時無刻無事不記掛著黛玉,可他的真心往往不被黛玉理解。“金玉良緣”之說成了黛玉心中的一個魔咒,況且寶釵深得賈府上下人心,寶玉又有“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之嫌,因此黛玉總是不放心,常以“金玉良緣”之說嘲弄寶玉,以假意試真情,反惹出了不少口角之爭,致使兩人都為情而苦。寶玉為情而癡為情而苦的過程,也就是他漸漸轉向無情的過程。第二十一回寶玉看到《外篇·胠篋》“故絕圣棄知,大盜乃止”一段時,不禁提筆續(xù)曰:“……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減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由此續(xù)可見,寶玉似乎已隱隱地感覺到了閨閣之美給他帶來的煩惱。第二十二回“寶玉悟禪機”,聽到《寄生草》“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時,稱賞不已。可是這時的寶玉還無法做到“無牽掛”。直到黛玉離去,寶玉開始嘆人生,悲也喜也愛也恨也,一切都成空。癡情一生,苦一生,情不了,苦難盡,此時應了情,無情最逍遙。寶玉最終無情而返青埂峰,復得“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變無悲”的絕對逍遙。
三、道家“浮生若夢”思想在《紅樓夢》中的體現(xiàn)
追溯中國文學史,人生如夢的思想正是由莊子在《莊子內篇·齊物論》中首先提出來的。《紅樓夢》在第一回作了交代:“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這一番話暗示了作者人生若夢的感悟。“夢”可視為《紅樓夢》的精華、特色、靈魂,若將這些夢幻從《紅樓夢》中抽移出去,那么《紅樓夢》就沒了精髓。由此可見,《紅樓夢》通篇籠罩著“人生若夢”的感慨。聯(lián)系到莊周夢蝶的故事,二者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一回中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對頑石的勸語:“那紅塵中卻有些樂事”。但“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所以頑石化身的寶玉及仙界諸艷化身的紅樓眾女兒的人間情事糾葛以及四大家族的榮辱興衰,在全書的總結構中,則屬于一大幻夢,本身便是虛無的。
賈寶玉多次夢游太虛幻境,特別在第五回作者寫到寶玉夢中如神仙般愜意到了極致,可是美夢過后,萬事皆空,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人生一場,轉頭萬事皆空。這是一種典型的道家的浮生若夢的觀點。
其他人物的夢境,如秦可卿臨終前托夢鳳姐之言:“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賈元春給賈母托夢“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早。”等等,均反映出道家“人生若夢”的虛幻思想。
綜上所述,莊子道家的思想深深影響并貫穿于《紅樓夢》的始終,只有全面了解道家思想與《紅樓夢》的聯(lián)系,才能真正讀懂這部偉大的作品。
第4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那幾年我剛巧有機會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與柏克萊的加大圖書館借書,看到脂本《紅樓夢》。近人的考據(jù)都是站著看――來不及坐下。至于自己做,我唯一的資格是實在熟讀《紅樓夢》,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但是沒寫過理論文字,當然笑話一五一十。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根的散文最記得這一句:“簡短是雋語的靈魂”,不過認為不限雋語,所以一個字看得有巴斗大,能省一個也是好的。因為怕嘮叨,說理已經(jīng)不夠清楚,又把全抄本――即所謂“紅樓夢稿”――簡稱抄本。其實這些本子都是抄本。難怪“初詳紅樓夢”刊出后,有個朋友告訴我看不懂――當然說得較婉轉。
如今在這大眾傳播的時代,很難想象從前那閉塞的社會。第二十三回有寶玉四首即事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榮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錄出來各處稱頌。”看了使人不由得想到反面,著書人貧居西郊,滿人明義說作者出示《紅樓夢》,“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可見傳抄只限戚友圈內。而且從前小說在文藝上沒有地位,不過是好玩,不像現(xiàn)代蘇俄傳抄地下小說與詩,作者可以得到心靈上的安慰。曹雪芹在這樣苦悶的環(huán)境里就靠家里的兩三知己給他打氣,他似乎是個溫暖的情感豐富的人,歌星芭芭拉?史翠珊唱紅了的那支歌中所謂“人――需要人的人”,在心理上倚靠脂畸笏,也情有可原。近人竟有認為此書是集體創(chuàng)作的。
他完全孤立。即使當時與海外有接觸,也沒有書可供參考。舊俄的小說還沒寫出來。中國長篇小說這樣“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是剛巧發(fā)展到頂巔的時候一受挫,就給攔了回去。潮流趨勢往往如此。清末民初的罵世小說還是繼承紅樓夢之前的“儒林外史”。《紅樓夢》未完還不要緊,壞在狗尾續(xù)貂成了附骨之疽――請原諒我這混雜的比喻。
程本《紅樓夢》一出,就有許多人說是拙劣的續(xù)書,但是到本世紀等才開始找證據(jù),洗出紅樓夢的本來面目。我看見我捧著厚厚一大冊的小字石印本坐在那熟悉的房間里。“喂,是假的。”我伸手去碰碰那十來歲人的肩膀。這兩本書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紅樓夢》。《紅樓夢》遺稿有“五六稿”被借閱者遺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時間機器飛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來搶回來。現(xiàn)在心平了些,因為多少滿足了一部分的好奇心。
我這人乏善足述,著重在“乏”字上,但是只要是真喜歡什么,確實什么都不管――也幸而我的興趣范圍不廣。在已經(jīng)“去日苦多”的時候,十年的工夫就這樣摜了下去,不能不說是豪舉。正是:
十年一覺迷考據(jù),贏得紅樓夢魘名。
(選自《紅樓夢魘》,有刪改)
第5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雖是黃口小兒的浮光掠影,卻也水過地皮濕,對《紅樓夢》中的某些人物產生了數(shù)十年守恒不變的印象和評價:王熙鳳,夠毒的;賈璉,夠壞的;尤二姐,夠賤的;平兒,夠難的;寶釵,夠陰的;晴雯,夠俊的;尤三姐,夠硬的……
從9歲到眼下年近花甲,我自稱十讀紅樓,其實并無精確統(tǒng)計,但敢保讀過十遍以上。只是我讀《紅樓夢》不是索隱探密做“紅學”,而是為了從中偷藝寫小說。偷藝,也就是學以致用。
在中國寫小說的人不讀《紅樓夢》,我覺得就像基督徒不讀《圣經(jīng)》一樣,可算不通情理,說不過去。有一位“新潮”文藝理論家,拿《紅樓夢》跟西方現(xiàn)代派小說比較,說《紅樓夢》只夠初中水平。這就更加令人忍無可忍,惹得我多次寫文和發(fā)言反駁他。如今,此人到西方寄人籬下,“比較”來“比較”去,還是靠賣《紅樓夢》掙口飯吃。面對西方“藍眼睛”,大談《紅樓夢》比西方現(xiàn)代小說高出百倍、千倍、萬倍、萬萬倍,唬得那些“初中水平”以上的藍精靈如醉如癡,走火入魔。
閑言少敘,且說我向《紅樓夢》學習語言藝術,是重點進攻,條塊分割,全面推進。我的重點進攻對象是王熙鳳、林黛玉和晴雯。這三位女性的語言最有鮮明特色,個性最為突出。聞其聲如見其人,聽其言而發(fā)人深思。
條塊分割是對各系統(tǒng)(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和各單位(如怡紅院、瀟湘館、梨香院……)的不同人物進行個別和綜合對比研究。賈政、王夫人和趙姨娘的搭配,薛姨媽、薛蟠、薛寶釵一家的組合,真是虧他(曹雪芹)想得出,罵人不吐核兒。
凡在《紅樓夢》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哪怕微不足道,一閃而過,我也在“全面推進”中解剖“麻雀”。
深受賈寶玉的精神感染,全盤接收這位“無事忙”先生的高論,我對《紅樓夢》中的男性興趣不大,在女性中對已婚者也不太感興趣,而未婚少女,在丫頭身上下力多,小姐身上用心少。
通過我對《紅樓夢》的閱讀和思考,通過我在創(chuàng)作上借鑒和學習《紅樓夢》的深刻體會,我寫小說是追求以個性語言,來刻畫人物個性和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動。又以人物在動態(tài)中的準確的細節(jié)描寫,描繪人物形象。由于個人氣質和生活經(jīng)驗不同,我寫不出《家》《三家巷》那樣跟《紅樓夢》靠色的作品。但是,我在我的鄉(xiāng)土文學小說中,寫過不少“鄉(xiāng)土晴雯”“鄉(xiāng)土芳官”“鄉(xiāng)土金釧”“鄉(xiāng)土襲人”……只是沒有依樣畫葫蘆,不那么顯眼。
《紅樓夢》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際關系,我已十分熟悉,這幾年便不再通讀。出于個人情趣和創(chuàng)作需要,我對《紅樓夢》的閱讀改為“聽折子戲”的方法,也就是將《紅樓夢》的精彩片段,分割成若干中篇或短篇,類似《水滸》的宋10回、武10回、林6回、魯3回……凡以王熙鳳、林黛玉、薛寶釵、秦可卿、賈寶玉、劉姥姥、晴雯等為主角的章節(jié),或表現(xiàn)重大事件和復雜紛爭的段落,我都節(jié)選出來,反復精讀和尋思。如“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我節(jié)選了兩千多字。晴雯那多層次多側面的心理活動,完全從她那有聲有色、潑辣含蓄、豐富優(yōu)美的語言中流露表現(xiàn)出來。“不肖種種大承笞撻”一段,我前后節(jié)選了五千多字。在這五千多字里,或隱或現(xiàn)將賈府男女老幼、尊卑上下、親疏遠近、真假虛實的眾生相,暴露無遺。在這些“折子戲”里,每個人物的一言一笑,一動一靜,都話里有話,弦外有音,意猶未盡,令人回味無窮。
后40回的“折子戲”,我只看中黛玉之死和襲人之嫁兩節(jié)。
不僅對于《紅樓夢》我是如此重讀,而且對于過去閱讀的所有名著,我也是如此復習。
如此如此,我稱之為斷章取“藝”。
(選自《劉紹棠文集》)
第6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長久以來,關于《紅樓夢》之評論研究,有以為代表的索隱派,有以為代表的作者考證派……在紛繁多樣的重圍中,王國維與魯迅的見解獨具價值。
王國維與魯迅都經(jīng)歷過清末民初的國家轉型期,也都曾東渡日本留學深造,相似的時代、教育環(huán)境卻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學批評觀。下面,筆者就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說”一文及各篇雜論為例,從三方面來具體分析王國維與魯迅對《紅樓夢》評論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來源:集體還是個人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直接闡明了對賈寶玉真實身份的界定:“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可,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這種創(chuàng)新式的觀點將紅學的研究從傳統(tǒng)的索隱、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認為主人公是誰這個問題并非小說實質性問題,“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于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這種用西方美學的觀點來闡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創(chuàng)舉具有進步意義。魯迅則認為《紅樓夢》中的興榮衰敗之所以耐人尋味,是因為作者親身經(jīng)歷過世間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斷出這部小說是曹雪芹的人生傳記。“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他堅信賈寶玉的經(jīng)歷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實寫照。魯迅否定了王國維的觀點:“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庵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也……”筆者認為,王、魯二人之所以擁有相悖的觀點,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維方式不同。王國維借鑒西方的美學觀點,認為小說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復雜化的,作者所構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個人的形象,而是時代、社會的縮影。把小說主人公置于大的時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類的共性與人生的狀態(tài),這種宏觀的思維方式無疑是恰當?shù)摹t斞笇τ诖藛栴}的見解則稍顯不足,他認為《紅樓夢》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親身體驗,他把賈寶玉身上所有的特質都歸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說的包容性與虛構性,這種微觀思維方式略顯狹隘。在這一問題上,王國維的觀點更值得借鑒。
二、主題思想:消極避世還是積極進取
縱觀《〈紅樓夢〉評論》全文,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王國維的思想是悲觀避世的。他認可叔本華的觀念,認為生活的本質是欲望。王國維把世間所有的疾苦都歸為欲望作祟。“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對待生活的苦痛,他認為“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與此同時,他強調“出世”的力量,由此認為《紅樓夢》中唯惜春、紫鵑與寶玉三人達到了真正解脫的境界。在民族矛盾異常激烈的清朝末期,這種思想是消極且妥協(xié)的,同時也為他日后自盡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而魯迅則以清醒的民族意識在《紅樓夢》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階級的氣味。他見解獨到,從一個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從而論斷出“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個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同時,他把焦大所受的馬糞灌嘴的委屈與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論:“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將身份卑賤的仆人與受人敬仰的歷史偉人并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階級的先進思想。在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魯迅先進的思想覺悟更具有啟迪民智與指引方向的意義。
三、藝術價值:世界的還是民族的
在《紅樓夢》藝術價值問題上,王、魯二人的立足點迥異。王國維把《紅樓夢》的價值根基深植于西方美學與倫理學的土壤中,他認為《紅樓夢》的最大美學價值就在于它的悲劇意義——“徹頭徹尾之悲劇也”,進而把《紅樓夢》與叔本華所認為的第三種悲劇相連洽,“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紅樓夢》算得上是悲劇中的悲劇。同時,他又創(chuàng)造性地認為《紅樓夢》在美學與倫理學上的價值是相同的,“美學上之價值,亦與其倫理學上之價值相聯(lián)絡也。”雖有牽強附會之嫌,但也揭示出了人生與藝術的巧妙關系。而魯迅則認為《紅樓夢》真正的價值是突破了以往中國古典小說寫作的局限,“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的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tǒng)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種立足于民族傳統(tǒng)文化,以傳統(tǒng)小說思維來探討《紅樓夢》價值的方式同樣具有重大意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人對《紅樓夢》價值的觀點在一定意義上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側重于在世界文學體系中橫向探求,一個著眼于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縱向比較,雖不可否認二者的觀點都尚有不足之處,但其各自創(chuàng)新之觀念也著實為紅學開辟了嶄新的視界。
第7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從目前的關于《紅樓夢》的外文譯作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
1.1關于人名翻譯問題
1929年,我國譯者王際真的《紅樓夢》英文節(jié)譯本先后在美、英兩國出版。在這本譯作中,王際真采取男名音譯,女名意譯的做法,顯得十分混亂。比如將“平兒”翻譯成Patience(耐心),將“薛寶釵”翻譯成PreciousVirtue(寶德),將“鴛鴦”翻譯成Faith(忠信),這樣的翻譯方法使外國人認為這群姑娘不是《紅樓夢》中漂亮的少女,而是類似《天路歷程》這種“圣書”中虔誠的基督教徒。這樣的翻譯抹殺了《紅樓夢》中少女的天真無邪,而沾染了一絲國外的宗教氣息,實在不利于《紅樓夢》文化價值的傳播。此外,最令紅學專家吳世昌覺得荒謬的是將“林黛玉”翻譯成BlackJade,用我們中文來說,BlackJade是“、”的意思,此譯法完全扼殺《紅樓夢》的文學氣息,讓外國人對林黛玉這樣一個秀外慧中的女子產生誤解。
1.2關于習語翻譯存在的問題
在外文譯本翻譯中,《紅樓夢》中常用習語的翻譯也是存在問題較多的地方。在戴乃迭和楊憲益合作翻譯的《紅樓夢》中有一段譯文:His-feng,thoughhatingchiu-tung,waseargertouseherfirsttoridherselfofSecondSisterby“killingwithaborrowedsword”and“watchfromahilltopwhiletwotigersfight”.Foroncechiu—tunghadkilledSeeondSister,shecoulddothisnewconcubinein.原文是: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fā)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斗”。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第69回)我們都知道“借刀殺人”這個習語出自我國名作《孫子兵法》,意思是借助別人的力量打敗敵人,以節(jié)省兵力。在《紅樓夢》中,鳳姐因為討厭尤二姐,所以想借助秋桐的手除掉她,這也就是借刀殺人。戴乃迭和楊憲益將“借刀殺人”翻譯成“killingwithaborrowedsword”,雖然這樣的翻譯語言方式與我們漢語較為相似,但是其譯義卻會讓人產生誤解。導致英語讀者誤以為是王熙鳳用從別處借來的刀,親手去殺了尤二姐。毋庸置疑,這樣的譯文與原文意思就產生了偏差,不利于國外讀者理解王熙鳳的心理活動。
二、《紅樓夢》翻譯傳播中值得借鑒的地方
2.1關于書名的翻譯
關于《紅樓夢》書名,一直有很多種翻譯,比如TheDreamoftheRedChamber、TheDreamsoftheRedChamber、DreamoftheRedChamber、HungLouMeng、TheStoryoftheStone、ADreamofRedMansions、ADreamInRedMansions等,哪一種書名翻譯比較合適,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我國民族文化中,“紅樓”意指富貴人家的閨房,與“青樓”相對。“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如今無奈杏園人。駿馬輕車擁將去。”,這是唐朝詩人韋莊在《長安春》中對紅樓做出的描繪。可見“紅樓”二字有著豐厚的文化積淀,再加上一個“夢”字,更是透露出一種深邃的美學內涵。周汝昌先生認為《紅樓夢》這三個字是不可翻譯的,因為不管怎么翻譯,都無法傳達出其本身的豐厚韻味。英國人霍克思認為可將《紅樓夢》翻譯成“TheStoryoftheStone”,這是采用了《紅樓夢》的另一個書名《石頭記》,雖然這樣的翻譯屬于直譯,但可以避免可能引起的誤會,同時也符合作者曹雪芹最原先的創(chuàng)作構思,使國外讀者領略石頭的象征意義,不失為一種好的翻譯。
2.2關于中西方文化差異的翻譯
為了能夠向海外讀者真實無誤地傳達《紅樓夢》的文化內涵,譯者在翻譯《紅樓夢》的具體內容時,還照顧到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以此減少海外讀者的理解難度。《紅樓夢》原作中有這么一段情節(jié):馮紫英說:“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鉆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背地里細打聽,才知道我疼你不疼!”英國人大衛(wèi)•霍克思的譯文如下:You’resoexciting,andsoinviting;You’remyMaryContrary;You’remygoddess,butno!you’redeaftomyprayin;Whywon’tyoulistentowhatIamsaying?Ifyoudon’tbelieveme,makeasmallinvestigation;Youwillsoonfindoutthetruedepthofmyadmiration.如果將“刁鉆古怪鬼靈精”直譯,可能會使?jié)h語語言的神韻消失殆盡,還會顯得啰嗦,繁瑣。所以,大衛(wèi)•霍克思將其翻譯成MaryCon-trary。這是一首從18世紀開始流傳的英國童謠,講的是一個性格難以捉摸的女孩的故事,她的性格類似于“刁鉆古怪鬼靈精”。霍克思的翻譯到中西語言上的差異,并努力將兩種語言融合在一起,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三、結束語
第8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關鍵詞:選修課《〈紅樓夢〉欣賞》開放性
統(tǒng)一內容、統(tǒng)一手段、統(tǒng)一進度的統(tǒng)一化教學模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優(yōu)越性,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作為活生生個體存在的學生的個性需求。選修課的開設,從理論上講則恰好可以彌補這一不足。懷海特說:“教育改革的第一個要求是把學校看作一個單位,有它自己被批準的課程,這個課程建立在它自己的需要上,由它自己的教師來制訂。”①但是,由教師自己制訂的選修課到底怎么開、開什么?筆者以為,選修課的最大意義在于關注每一位學生的發(fā)展,滿足每一位學生的個性發(fā)展需求,所以,構建開放性的教學機制是關鍵。所謂開放性的教學機制,是指允許學生介入教師的備課過程,上課過程中給學生以充分的展示空間、足夠的思考時間,最后在師生多向評價中,使課程內容得以拓展、師生水平得以共同提高的教學機制。下面筆者將從自己《〈紅樓夢〉欣賞》選修課實踐出發(fā),對此問題進行具體闡述。
一、 課堂因我而精彩――開放的教學形式
選修課開課后教師首先發(fā)現(xiàn),相對于《紅樓夢》原著文字,學生其實對影視欣賞更感興趣。而教師開課的目的絕不是讓學生只關注影視內容就夠了,因為讓學生聰明起來的辦法不是欣賞影視,“而是閱讀,閱讀,再閱讀”②。其二,相對于原來固定班級的學生,這些參加《〈紅樓夢〉欣賞》選修的學生,除了對《紅樓夢》有更為濃厚的興趣外,90后的他們也很樂于展示自己、表現(xiàn)自己。面對這一現(xiàn)實矛盾和學生的這一特點,教師因勢利導,將影視欣賞與文字解讀相結合,將學生的注意力、興趣點慢慢拉回到原著上來。在這過程中,又給學生以充分的空間展示自我,提高學生自信力。
比如,在教學“身前身后事――判詞解讀”討論主題時,教師在學生研讀完判詞后,可布置學生一項任務:下載一段你認為最能體現(xiàn)原著人物特征的視頻,在課上播放交流,并說說你選擇該視頻的理由。這一任務既充分利用了年輕人嫻熟的網(wǎng)絡下載技術,又讓學生能在甄別、取舍的過程中關注原著、研讀原文,還可以讓學生在課堂上充分鍛煉、展示自己,可謂一舉多得。學生會下載、能播放、樂展示,學習信心和參與熱情自然提升。而學生下載的視頻定是五花八門的,講解理由也不乏獨到之處。教師在學生充分欣賞視頻之后,可讓學生自由討論87版和新版的林黛玉形象、87版的和新版的晴雯形象哪個更符合你心目中的形象、哪個更貼合原著形象等問題。學生視頻欣賞得認真,文字解讀得細致,問題討論得熱烈,原來的問題討論最后幾乎成了辯論會,學習效果甚佳。
比如,在教學“笑罵皆是情――《紅樓夢》說話賞析”專題時,為了讓學生對《紅樓夢》人物的說話藝術有更直觀、深刻的體驗,教師事先就布置了小組任務:選擇你們認為說話藝術最精彩的一個片段進行角色扮演,角色自定。小組角色扮演既滿足了90后學生愛表現(xiàn)的心理,又培養(yǎng)了他們的合作精神。或許學生的表演是倉促、稚嫩的,但學生參與的態(tài)度是真誠的,參與的經(jīng)驗是寶貴的。
再比如,在賞析人物形象之“任是無情也動人――寶釵”內容時,針對學生對寶釵的褒貶不一的態(tài)度,教師可設置辯論環(huán)節(jié),辯題可以是“你認為寶釵是賢惠還是虛偽?”“寶釵和黛玉,誰是妻子的更合適人選?”等等,讓學生既有充分發(fā)表自己觀點的機會,又有細讀原著文本的驅動力。
開放活躍的選修課堂,學生是絕對主角,選修課堂真正成了學生全方位展示自我的最好舞臺,學生與文本對話、與自我對話、與他人對話,樂在其中,因為“對話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實現(xiàn)”③。于是,看似枯燥無味的知識拓展類選修課《〈紅樓夢〉欣賞》自然而然就人氣爆棚。“語文教學應為學生創(chuàng)設良好的自主學習情境,幫助他們樹立主體意識”④,說的就是這個理吧。
二、 我要我的滋味――開放的教學內容
學生在課堂上發(fā)幾次言、辯幾次論、扮幾個角色,是否就意味著學生已真正成為課堂的主體了?答案是否定的。光是教學形式的開放,沒有思維的碰撞與契合,只能是花拳繡腿的表面功夫。甚至有時“表面興旺的背后隱藏著不可忽視的危機”⑤。只有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師的備課中來才能真正體現(xiàn)學生的有效參與。
初步構思《〈紅樓夢〉欣賞》選修課教學內容時,筆者設想的教學內容是四大專題,分別是“莫道是尋常――《紅樓夢》命名賞析”“哭紅悲艷處――《紅樓夢》人物賞析”“笑罵皆是情――《紅樓夢》說話賞析”“嘗仙桃一口――精彩情節(jié)導讀”,每專題又分別由若干討論主題組成。之所以在內容選擇上蜻蜓點水涉及人物、說話、命名等各方面,是因為想讓參加選修的初學者對《紅樓夢》的多方面藝術都有一定了解、興趣濃厚者對《紅樓夢》有進一步深入研讀的動力,從而對其未來閱讀生涯產生一定影響。
待學生報名后,教師在學生中作了簡單的調查,問題之一是:你最期望本選修課開設哪方面的學習內容?48位參加《〈紅樓夢〉欣賞》選修的學生,其中27人次提到對寶黛釵三人的關系、愛情、性格感興趣,21人次對《紅樓夢》中的詩詞尤其是十二釵的判詞感興趣,17人次提到對《紅樓夢》人物的說話藝術感興趣,12人次想了解《紅樓夢》與作者的關系,4人次想了解《紅樓夢》的飲食、服飾、建筑等其他方面知識。
基于此調查結果,教師及時地調整了自己的教學內容。在原來專題基礎上,增加了兩個新專題。為滿足學生希望了解《紅樓夢》與作者的關系的心理,新增設了專題“一把辛酸淚――走近曹雪芹”,專題由“都云作者癡――曹雪芹其人”“滿紙荒唐言――雪芹與石頭”“誰解其中味――序幕概賞”三個討論主題組成,以便學生對《紅樓夢》作者的生平遭際、創(chuàng)作緣由及作品基本思想內容有一個大致了解。在介紹作者與作品關系時,適當引入脂硯齋的評語,介紹等人的觀點,穿插學者劉心武的揭秘,讓學生在多種觀點面前,結合原著文字,對作者和作品的關系,自由下結論。
為滿足學生對《紅樓夢》飲食文化等方面的好奇,新增設了專題“茶語無限事――盞茶玄機”,本專題由“關乎命運”“關乎性格”“關乎處境”“關乎姻緣”四個討論主題組成,通過解讀楓露茶事件、櫳翠庵品茶、黛玉初進賈府飯后飲茶心理及鳳姐吃茶玩笑,明確飲茶關系茜雪命運、揭示妙玉性格、暗示黛玉今后處境、透露寶二奶奶人選信息,使學生對《紅樓夢》的飲食文化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培養(yǎng)學生一飯一茶皆關主旨、不可等閑視之的解讀意識。
另外,為了解決學生對《紅樓夢》人物判詞的疑問,在“哭紅悲艷處――《紅樓夢》人物賞析”專題下新增了討論主題“身前身后事――判詞解讀”,教師與學生共同解讀、討論寶玉夢游太虛幻境所讀判詞、所聽曲子,使學生對人物形象、命運等有一個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認知。
如此,教師根據(jù)學生的實際情況,及時調整教學內容,課堂學習的就是學生真正想要的,學生的困惑得以解疑,學生的興趣得到尊重,學生影響甚至支配教師的教學內容,學生豈有不興趣大增之理?而“興趣是生長中的能力的信號和象征”⑥。
三、 我的課堂我評價――開放的教學評價
開放的教學內容,就是學生參與教師的備課過程,教師根據(jù)學生知識儲備的實際情況隨時更新自己教學內容;開放的教學形式,就是教學過程中,把時間和空間還給學生,讓學生成為課堂的絕對主角。那開放的教學評價是什么樣的呢?開放的教學評價絕不是用一張試卷幾道題目解決的,也不是用點名簽到遲到早退來評判的。開放的教學評價應該包括師生相互評價、生生相互評價、學生自我評價、師生對課程的評價,其中尤其不可或缺的是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師生對課程的評價。
比如,在課程將近結束時,教師可以讓學生寫下自己在《〈紅樓夢〉欣賞》選修課中的收獲、向學生推薦本課程的推薦指數(shù)及一句話推薦語。收獲可以是知識、情感、做人等多方面的。推薦指數(shù)采用星級制,最高級別是五星級――非常值得推薦,最低級別是零星級――毫無推薦價值。教師據(jù)此既可了解學生的自我評價,又可由學生在《〈紅樓夢〉欣賞》這門課的收獲、對《〈紅樓夢〉欣賞》這門課的喜愛程度,而對《〈紅樓夢〉欣賞》這門課的價值有更科學、客觀的認識。教師還可以讓學生以不署名形式寫下自己對任課教師最想說的話,贊美或批評皆可。這樣,教師就可以根據(jù)學生的褒貶,反思自我授課得失,或為下一次選修課的開發(fā)、開設儲備經(jīng)驗和教訓,或進而深層思考本選修課程的存在價值。
而教師對學生的評價,教師也可以采用更新穎開放的評價標準來評價學生,例如,紅樓人物對應評價法:才情突出者,冠之黛玉;通古博今者,贊之寶釵;勤勉上進者,比之香菱;活躍能辯者,評之湘云;乖巧懂事者,謂之襲人……由此推開去,生生間的評價,教師也可以讓學生根據(jù)周圍同學上課表現(xiàn),為其找到大觀園中最相對應的人物,并注明理由。如此評價,既體現(xiàn)《〈紅樓夢〉欣賞》選修課課程特色,又讓學生耳目一新,還可讓學生重新審讀文本、審視自我,實現(xiàn)學生對原著文本的二次探究解讀目的。
開放的教學的內容、開放的教學形式、開放的教學評價,學生介入備課,支配上課,參與評價。對學生來說,內容是我要的,形式是我樂的,評價是我想的,選修課堂也就成了學生舒展性靈的空間。
以上便是筆者《〈紅樓夢〉欣賞》選修課開設實踐的一點思考,歡迎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
①[英]艾爾弗雷德?諾思?懷海特著《教育的目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
②[蘇聯(lián)]蘇霍姆林斯基著《給教師的建議》,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版
③[德]卡爾?雅斯貝爾斯著《什么是教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
④《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9篇:紅樓夢作者范文
關鍵詞:現(xiàn)代主義 紅樓夢 魔幻 現(xiàn)實
引言
曹雪芹的心血之作《紅樓夢》的橫空出世,不僅在我國古典文學史中產生無可估量的巨大影響,研究學界諸多著名專家也都認為:“西方上個世紀才展現(xiàn)的現(xiàn)代文學某些主要特點其實在我國18世紀文學巨典《紅樓夢》里面早已展露痕跡。”[1]所以,曹雪芹是現(xiàn)代文學創(chuàng)作諸多先行者當中的一員,《紅樓夢》中帶有現(xiàn)代文學的若干因素。在這點上,筆者借用博爾赫斯對韓愈等探索者評論的話來說:“這部作品當中稍微帶有一些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特點,這個特點至少在表現(xiàn)形式和基調這個層面上是相似的。”本文基于這一觀點,將現(xiàn)代主義文學表現(xiàn)形式和基調予以延伸,比較兩者的相似之處。
一、雜揉化
20世紀西方現(xiàn)代作品,尤其后現(xiàn)代作品里面通常有個很明顯的特點,即雜揉化。吳曉東先生在評論關于美國黑色幽默小說杰出代表人物托馬斯的代表作――《萬有引力》時,總結過有關雜糅化的特點,即作者在其著作里面“融匯許許多多的文藝種類,比如說滑稽小品、喜劇、偵探小說等,在著作內容中追尋的多元化內容穿插其中,這里面有物理、自然科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學科,著作中飽含著類似于百科全書式的企圖”。這樣融匯諸多領域與在著作中追尋多樣化的內容均包含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特點,以上特點在《紅樓夢》里面也有所表現(xiàn)。
首先,《紅樓夢》里面“融匯了許多西方現(xiàn)代小說所包含的文藝種類特點”,在這里面較為顯著的就是融入了神話內容。在《紅樓夢》第一回開篇,曹雪芹描述了兩則美麗動人的神話傳奇:其一是“女蝸補天”的故事;其二是“還淚”的故事。這兩則故事彼此獨立,甚至能夠單獨作為一則神話故事而存在。除去神話故事之外,這部作品里面還穿插了內容豐富的詩詞歌賦、燈謎、笑話等片段內容,以至于連中藥藥方、書籍筆記等都囊括其中。例如在第十回中提到的一例中醫(yī)藥方,第三十七回中提到的探春的“花箋”等,龐雜的涉足領域近乎囊括了那個時代全部的學科體系,像“百科全書”一般全部包容進了《紅樓夢》之中。 [2]《紅樓夢》里面的諸多文藝種類都可以歸屬于曹雪芹視角下的客觀描述內容,從根本上來說,不能完全歸類于文藝雜糅。
其次,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相近的是,《紅樓夢》也有著“大百科全書式”的追尋――故事內容上也將時代的方方面面囊括其中。《紅樓夢》從誕生之日起就被視為我國古代傳統(tǒng)社會的百科全書,書中的描繪涉及諸多領域,例如園林學、中醫(yī)甚至還有政治、經(jīng)濟、藝術等,全部被寫進小說里面,貫穿于賈府的興衰之間,這類似于西方現(xiàn)代主義小說中的表現(xiàn)特點。
基于以上兩點,作者曹雪芹的完成歷程具有特殊性,小說所構成的結構與涉足內容的多元化,初步展現(xiàn)出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作品里常有的雜糅化特點。
二、神話特點
神話化的特點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小說中的重要特點之一,這在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里面表現(xiàn)得尤為顯著。杰出代表作家馬爾克斯的著作《百年孤獨》里面囊括了數(shù)種流傳至今的神話原型,將神話故事的關鍵橋段重組融合其中。小說《紅樓夢》中存在同樣的手法,以神話的方式將小說內涵引申,展現(xiàn)出作家和小說里面各種人物角色之間生活與精神的聯(lián)系。[2]
《紅樓夢》中第一則神話是開篇伊始“補天”這個故事,曹雪芹并沒有直接引用這個神話,而是沒有拘束于原篇內容,對這個神話細節(jié)有所改動,更自然地融合于小說之中。這則神話故事最早來源于《淮南子?覽冥訓》,故事內容描述的是在遠古時期,支撐天與地的四根巨大的柱子一夜之間坍塌為虛無,大地破裂出了一條又一條巨大的縫隙;天空塌陷,不再覆蓋生活在大地上的蕓蕓眾生,大地也不再完全地承托住凡間的萬千生靈。[3]危機發(fā)生后,女媧把五色石拿來鍛造,利用其彌補天上的窟窿,然后斬斷螯的四條腿,用來當作支撐天地四極的支柱,從那以后天和地終于分離并恢復原貌。曹雪芹雖然套用此神話,但在描述時留有玄機,為小說后續(xù)情節(jié)做好鋪墊。將神話改為女蝸娘娘在補天后遺留了一塊石頭,這塊石頭經(jīng)過日月淬煉之后,通了靈性,看到其他諸石都能用作彌補天,而自己卻因無材被遺落,整天自怨自艾。后來遇到一個僧人和一個道士,經(jīng)由他們將這塊奇石帶到了人世間。經(jīng)過輾轉多年,最后遺落在大荒山下。這塊石頭上刻了一個故事,也就是《紅樓夢》里面的主要情節(jié)內容。在這里,有個地方特別需要關注:這個神話故事非常精準地描繪出曹雪芹和主人公賈寶玉內心世界的感受,表達出一種凄涼哀傷的情緒、無力回天的感觸。
《紅樓夢》里面的第二則神話是“還淚”。這則神話盡管是曹雪芹自己構思的,但有專家將這則神話故事稱作是一個作家別出心裁構思而出的“亞神話”創(chuàng)作,而不是直接引用我國某個古典神話里面的素材,“還淚”還稱作是“擬神話”。然而絕大多數(shù)專家仍然把它直接叫做神話。這則神話哀婉、凄美而動人,描述了于靈河岸上,神瑛侍者每天都用甘露來澆灌仙草,后來仙草修煉得成便用“眼淚”來報答侍者對其澆灌之恩德。這則神話簡單直白地暗含了賈寶玉與林黛玉之間的愛情故事,還尤為生動地描摹了他們倆人的個性特點。與此同時還為這部作品奠定了哀怨、糾纏而動人的感情基調,這個基調就好似看不見的手,暗暗地掌控著這部作品里面所有角色的命運,尤其是林黛玉的命運,暗示其將眼淚掉盡,最終逝去的悲慘結局。《紅樓夢》的神話使其蘊含了哲學道理與飄渺朦朧的文學美感,深化了人物特征的塑造。
三、魔幻化
“魔幻化”是西方魔幻現(xiàn)實文學的主要特點,“魔幻化”是將真實予以魔幻化或是將魔幻予以真實化,在小說中將真實的場景和幻想的場景融匯于一體,作品里面的是一個虛擬構建的世界。在這其中,一切發(fā)生之事均是真實存在的。這類小說的杰出代表作是《百年孤獨》,里面描寫了魔力無邊的磁鐵、不用燒水就會沸騰的水壺、沒有翅膀就可以飛行的搖籃、在生發(fā)過程中會有聲響的草兒等虛幻事物,均是真實和幻想的完美結合,這些內容讓人感到一切都有可能發(fā)生,一切發(fā)生之事均是真實存在。[4]類似這樣魔幻化的橋段在《紅樓夢》這部作品中也有類似的描述。例如男主人公賈寶玉的故事,“寶玉”名字由來是指賈寶玉自出生時起就將性命般要緊的玉石一直佩戴于身。這部作品里面對其魔幻化安排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地方:首先是賈寶玉“銜玉而生”。這個細節(jié)還描繪于第二回對其出生狀況說明里面。含著玉石降臨人間,這樣的事情是作者自己幻想出來而絕不可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玉石外面還刻有字跡,那更加不是真實世界會發(fā)生的事情。在《紅樓夢》里面,這個故事就是一個真正存在之事,這樣的寫作方法就是將幻想之事真實化了。其次,那枚玉石居然可以辟邪。這塊寶玉不但是主人公與生俱來就有的,更讓人感到驚奇的是這枚玉石跟主人公的性命相連,不但通靈,還可以驅邪避鬼。如果這塊玉石脫離了男主人公的身,那他就會有性命危險。作者將真實和幻想交融于一體進行寫作,因此,在《紅樓夢》虛擬構建的小說空間里,曹雪芹將魔幻化情節(jié)安置于真實場景之中,帶有現(xiàn)代主義文學色彩。
四、象征性
象征性寫作方式在歷來文學小說中屬于一種常見的方式,在現(xiàn)代文學小說里展現(xiàn)出來的特點一般都是集中、顯著的,其不僅只是寫作技巧,更是展現(xiàn)形式,它傳達了作者關于這個紛雜世界的更繁復、多義或是更朦朧的掌握與解析,呈現(xiàn)于作品里面的特別意象往往是一種主旨內涵的象征,這令作品有了復義性,小說中的這類因主旨級象征而得出復義性特點就是現(xiàn)代主義文學作品當中較為常見的特點。例如卡夫卡的杰出代表作《城堡》里面的“城堡”意象,均有著多重象征含義的主旨內涵,小說是整體與全方位的象征。這類主旨級的整體象征在《紅樓夢》這部作品里面也有所體現(xiàn)。[5]
這部作品里面的象征意象同樣是整個的、主旨級的。周思源在其論文中提到這部作品創(chuàng)立了全新的寫作方式――“象征現(xiàn)實主義”。李慶信更是討論這部作品當中的“本體象征、寓言象征與符號象征”。由此可知,這部作品里面使用了很多的象征手法。然而,身為主旨級的象征意象,筆者認為一定是作品里面小說所在之中心背景“大觀園”。這個地方是作家虛擬構建出來的地方,暗含了作家的愛恨情仇與自身人生經(jīng)歷,象征了曹雪芹期盼的完美境界。顯而易見,“大觀園”是作者內心中“理想世界”的象征,曹雪芹把這個地方象征化暗合了現(xiàn)代主義作品表現(xiàn)手法,兩者作品的主題都是通過里面的象征意象傳達的。
結語
綜上所述,就《紅樓夢》在表現(xiàn)形式、基調與思想等層面來說都和現(xiàn)代主義文學作品有非常類似的地方,其中微妙地帶有一些現(xiàn)代主義文學特點。不是說這部作品被現(xiàn)代主義所作用,或是這部作品是現(xiàn)代主義初現(xiàn)倪端的表現(xiàn),就像類似博爾赫斯可以將韓愈看作是卡夫卡的先行者、其作品稍微帶上了卡夫卡的某些特點那般,同樣可以將《紅樓夢》看作是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先行者,且?guī)в鞋F(xiàn)代主義小說的特點。
參考文獻
[1]曹雪芹,高鶚.紅樓夢[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郭孔生.《紅樓夢》手帕意象的解讀[J].語文建設,2014(29).
[3]蔡義江.紅樓夢詩詞曲賦鑒賞[M].北京:中華書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