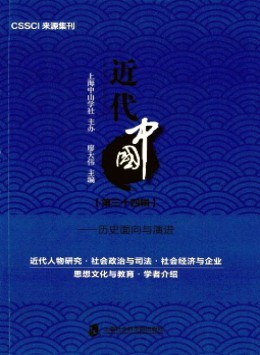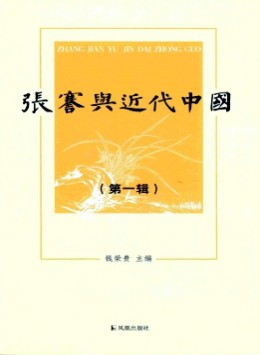近代中醫(yī)學校教育發(fā)展及特色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近代中醫(yī)學校教育發(fā)展及特色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江蘇是近代中醫(yī)學校教育的發(fā)源地之一,為近代中醫(yī)學校教育模式的確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通過介紹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形成的歷史背景、近代江蘇創(chuàng)辦的主要的中醫(yī)學校及辦學特色,研究探討和總結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發(fā)展的歷史經驗,探索其發(fā)展規(guī)律,為現(xiàn)代中醫(yī)藥高等教育的改革發(fā)展提供借鑒。
【關鍵詞】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
江蘇是我國中醫(yī)藥大省,歷史悠久,積淀深厚,中醫(yī)藥文化源遠流長。江蘇歷代名醫(yī)輩出,流派紛呈,在中醫(yī)藥界產生過極大的影響,在中醫(yī)藥發(fā)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近代以來,江蘇一大批中醫(yī)教育家面對中醫(yī)事業(yè)內外交困的局面,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發(fā)憤圖強,融會新知,為中醫(yī)的生存與發(fā)展積極抗爭、銳意改革,創(chuàng)辦中醫(yī)學校教育模式,探索中醫(yī)學術傳播的新途徑,開中國近代中醫(yī)教育之先河,為近代中醫(yī)學校教育模式的確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形成的歷史背景
由于西方文化的極速涌進,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生了急劇變化,猛烈地沖擊著近代中國的社會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這種急劇的變化不限于社會形態(tài)的轉變,也給中醫(yī)界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中醫(yī)教育被排除在國家教育體系之外,中醫(yī)界內部的分化,由此可以看出,中醫(yī)生存與發(fā)展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內憂外患,是中國醫(yī)學史上特殊的困難時期。近代以前,中醫(yī)學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醫(yī)學,中醫(yī)教育的主要模式是師承教育,近代中醫(yī)學校教育模式的形成具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第一,近代中醫(yī)學校教育的形成與中國傳統(tǒng)教育向近代教育轉化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密不可分。傳統(tǒng)教育向近代教育轉化的主要標志有二:一是產生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教育思想。近代思想家馮桂芬1861年在其政論集《校邠廬抗議》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哉者”,后被概括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變法圖強的依據(jù)。這也是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先進的思想家面對西方文明的涌入,深刻的觀察、分析、判斷而得出的思考,這一思想后來被世人普遍接受,成為此后半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對待中西文化教育沖突、交匯的指導方針[1]。二是產生了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教育機構。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設立京師同文館,通過同文館的翻譯、印刷出版活動了解西方世界。京師同文館“打破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教育模式,是中國近代最早按照資本主義教育建立起來的新式學校”[2],“是洋務學堂的開端,也是中國近代新教育的開端”[3],此后各種新式的學校、教學機構開始不斷涌現(xiàn),它們與傳統(tǒng)教育性質完全不同,開啟了中國教育的全面近代化的全新局面。第二,近代中醫(yī)學校教育的形成與西方醫(yī)學的傳入給中醫(yī)學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zhàn)密不可分。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門戶打開,由于通商口岸的增加和西方醫(yī)學的涌入,在一些重要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一大批傳教士和醫(yī)生在開始建教堂、開辦醫(yī)院、創(chuàng)立西醫(yī)學校,西醫(yī)發(fā)展呈現(xiàn)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近代中國出現(xiàn)了中西醫(yī)并存和碰撞的局面,“中醫(yī)該何去何從”開始在中醫(yī)學界的有識之士心中油然而生。中醫(yī)要發(fā)展并且后繼有人,而且必須舉辦適應時展的中醫(yī)教育,通過自身變革,才能保證中醫(yī)的薪火不斷,中醫(yī)才能發(fā)揚光大。在西方醫(yī)學傳入后,中醫(yī)教育發(fā)生了重要變化,教育模式迅速轉變,師徒授受和世襲家傳方式逐漸被中醫(yī)學校教育模式取代,成為我國醫(yī)學教育的主流。自清末民初以來,江蘇籍的中醫(yī)教育家們在全國率先創(chuàng)辦了第一批中醫(yī)學校,翻開了在實踐中嘗試與探索開展中醫(yī)學校教育的全新一頁。
2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的發(fā)展
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不管是辦學數(shù)量、辦學質量,還是社會知名度都始終處全國前列。1905~1948年,江蘇地區(qū)創(chuàng)辦的中醫(yī)教育機構多達30多所,其中一些中醫(yī)學校在中醫(yī)教育史上具有很大影響。這些中醫(yī)學校吸取近代教育的辦學理念,勇于突破傳統(tǒng)的中醫(yī)教育模式,借鑒西方醫(yī)學的學科體系、創(chuàng)新課程設置、教材編撰和教學內容與方法,在內外交困的大環(huán)境下,開辟出了中醫(yī)教育的發(fā)展道路,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中醫(yī)藥人才,為江蘇乃至全國中醫(yī)生存和發(fā)展作出了貢獻。近代江蘇地區(qū)創(chuàng)辦最早的中醫(yī)學校是1905年由李平書、張竹君創(chuàng)建的女子中西醫(yī)學院,這所學校專收女生,學習內容包括中西醫(yī)婦產科知識,由李平書講授中醫(yī)、張竹君講授西醫(yī)[4]。1916年夏,丁甘仁攜謝利恒、夏應堂等同道,自籌資金創(chuàng)辦了“在上海,乃至全國范圍,辦學時間最長,名醫(yī)造就最多,影響最大的中醫(yī)學校,”——上海中醫(yī)專門學校[5]。上海中醫(yī)專門學校在32年的辦學歷程中,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如丁濟萬、秦伯未、程門雪等皆為近現(xiàn)代中醫(yī)名耆。1929年,由陸淵雷攜章次公、徐衡之,創(chuàng)辦了中國國醫(yī)學院,由惲鐵樵擔任校長。該校力倡中醫(yī)科學化,對年青學生頗具吸引力[5]。1925年,由上海中醫(yī)專門學校畢業(yè)的學生王一仁、秦伯未、許半龍、章次公等創(chuàng)辦了上海中國醫(yī)學院。中國醫(yī)學院辦學21年,計畢業(yè)23屆,共906人[6]。上海中國醫(yī)學院是一所在全國較有影響的中醫(yī)學校,該校注重教學內容革新和教材編寫,最大的貢獻是倡議和組織召集了近代歷史上兩次全國中醫(yī)學校教材編輯會議,并統(tǒng)一和規(guī)范中醫(yī)教育教材,使之納入政府教育體系,使中醫(yī)教育更加系統(tǒng)化、正規(guī)化和現(xiàn)代化,盡管最終未能成功,但是在中醫(yī)教育發(fā)展史上意義重大。1934年,王慎軒在原蘇州國醫(yī)學社基礎之上創(chuàng)辦蘇州國醫(yī)學校,學校教學規(guī)模不斷擴大,學生大幅增加,1935年遷至蘇州長春巷內,成為當時國內設施和組織較為完善的中醫(yī)學校。蘇州國醫(yī)學校聘章太炎、謝利恒為名譽校長,社會名流唐慎坊為校長,王慎軒自任副校長兼學校總務主任,主持學校全面工作。蘇州國醫(yī)學校聘蘇滬名醫(yī)陸淵雷、葉橘泉、宋愛人等人負責各科教學,1936年又增設國醫(yī)研究院。1932年10月,承淡安在無錫創(chuàng)辦中醫(yī)針灸研究社,內附設實習科,5個月一期。由于密切結合臨床實踐,學員收益頗大,求學者日益增加。1935年,承淡安從日本留學歸國后創(chuàng)辦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針灸學校——中國針灸學講習所,即后來的中國針灸醫(yī)學專門學校。承淡安主張:“用科學方式闡明物理療法,發(fā)展中國固有醫(yī)學,造成針灸專門人才。”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中國針灸醫(yī)學專門學校培養(yǎng)的針灸專門人才(包括函授生)10000余人,該校為近代針灸學得以傳承與發(fā)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7]。由吳鶴齡、李晴生、王繼恒等主持的鎮(zhèn)江自新醫(yī)學堂創(chuàng)辦于1910年,任課教員則主要由當?shù)孛t(yī)吳子周、陳澤、楊燧熙等擔任。每期招生30名,分預科和正科,學制為四年。鎮(zhèn)江自新醫(yī)學堂于1912年更名為丹徒縣自新學校。這所醫(yī)校被研究者公認為清末標準的中醫(yī)學校,有明確的辦學宗旨和辦學方針,有規(guī)范嚴格的學制及合理的課程設置[8]。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以函授模式辦學的最早是丁福保于1910年創(chuàng)辦的中西醫(yī)學研究會,并附設該函授講習所,編輯發(fā)行《中西醫(yī)學報》作為函授教材,主要是向中醫(yī)介紹西醫(yī)[9]。惲鐵樵在教育史上是中醫(yī)函授教育的先行者,他兩度創(chuàng)辦鐵樵函授中醫(yī)學校,自編《鐵樵醫(yī)學函授講義》共22種。其他影響較大的中醫(yī)函授教育還有:1925年,由王一仁、秦伯未創(chuàng)辦的三益學社函授部,1929年,承淡安創(chuàng)辦中醫(yī)教育史上最早的針灸函授教育機構——中國針灸研究社,1932年,陸淵雷創(chuàng)辦的陸淵雷醫(yī)室遙從部,1933年,張贊臣創(chuàng)辦《醫(yī)界春秋》社函授部,1940年,時逸人創(chuàng)辦的時逸人國醫(yī)研究室等,這些辦學機構都是中醫(yī)學校函授教育的代表,曾經在國內外中醫(yī)界產生過重要的影響[5]。
3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的特色
3.1辦學宗旨
上海中醫(yī)專門學校的辦學宗旨為“昌明醫(yī)學,保存國粹”[10],以維護中醫(yī)及其教育的合法地位;中國國醫(yī)學院辦學宗旨為“發(fā)皇古義、融匯新知”,以求實踐其主張的“中醫(yī)科學化”[5];上海中國醫(yī)學院的辦學宗旨是“商量舊學,采納新知,不特欲自顯中醫(yī)獨立精神,且將別樹一中醫(yī)旗幟,由中國醫(yī)學而化為世界醫(yī)學”[6];新中國醫(yī)學院的辦學宗旨是“研究中國歷代醫(yī)學技術,融化新知,養(yǎng)成國醫(yī)專門人才,增進民族健康”[11];蘇州國醫(yī)學校的辦學宗旨是“發(fā)揚中國醫(yī)學的真理,吸收世界醫(yī)學的新知,造就一代適合新時代的新中醫(yī)”[12]。縱觀上述幾家中醫(yī)學校的辦學宗旨,無一例外都體現(xiàn)了當時中國中醫(yī)教育界的主流思想,即中醫(yī)教育要走以中醫(yī)為基,中西醫(yī)匯通發(fā)展之路,才能使中醫(yī)輸入新鮮血液,造就新時代的新中醫(yī)。這種中醫(yī)教育思想不僅是在當時,即使是在今天對于我們中醫(yī)學校教育仍然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3.2醫(yī)德教育
“醫(yī)乃仁術”,“以濟世為良,以愈疾為善,以活人為心”是中醫(yī)藥醫(yī)德與醫(yī)術的宗旨。近代江蘇中醫(yī)教育家非常重視學生的醫(yī)德教育,不僅要求學生在業(yè)務上要精益求精,對待患者更要始終懷有仁義博愛之心。上海中醫(yī)學院新落成的校門的門楣上,丁甘仁之長孫丁濟萬書寫了“痌瘝在抱”四個大字,時刻提醒在校的師生要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把患者的病痛當成自己的病痛,愛己及人,舍己為人[10]。蘇州國醫(yī)學校則是以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手書之“誠敬勤樸”為校訓,在德育方面就有十項德育標準,要求學生做到“誠以處世”、“敬以事人”、“樸以立己”、“慎以服務”、“陶冶向上之志趣”和“增進博愛的觀念”等[12]。強化學生的醫(yī)德教育是醫(yī)學教育的重要內容,反映了近代江蘇中醫(yī)教育者對醫(yī)德教育的高度重視,這種人才培養(yǎng)理念非常值得我們當代中醫(yī)教育者學習借鑒。
3.3附屬醫(yī)院
近代以來,西醫(yī)醫(yī)院相對成熟先進的醫(yī)療設備手段和模式對中醫(yī)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江蘇中醫(yī)學家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積極探索中醫(yī)醫(yī)院的發(fā)展模式之路。由于沒有政府的財政支持,他們自籌辦院經費,通過創(chuàng)立中醫(yī)學校附屬醫(yī)院,使培養(yǎng)的中醫(yī)人才能有更多的機會服務社會。江蘇中醫(yī)學校附屬醫(yī)院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918年,丁甘仁創(chuàng)辦的隸屬上海中醫(yī)專門學校的滬北、滬南兩所中醫(yī)醫(yī)院,1928年,秦伯未、王一仁創(chuàng)辦的隸屬上海中國醫(yī)學院的中國醫(yī)院,1936年,朱南山、朱鶴皋創(chuàng)辦的隸屬新中國醫(yī)學院的新中國醫(yī)院等[13]。這些醫(yī)院既承擔著治病救人的社會職責,還要承擔中醫(yī)教學的任務。江蘇中醫(yī)教育家創(chuàng)辦學校附屬醫(yī)院,堅持教學與臨床結合培養(yǎng)中醫(yī)人才,這也是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的又一重要特色。
3.4學術研究與交流
近代江蘇中醫(yī)醫(yī)家在中醫(yī)學校機構中設立研究社或研究院,用以開展中醫(yī)藥的現(xiàn)代化研究;發(fā)行中醫(yī)期刊雜志,用于開展學術交流。其中最有特色的當屬新中國醫(yī)學院,該院不僅設立了用于學術交流期刊發(fā)表的研究社,還特設新中國研究院。其他中醫(yī)學校均設有研究社,如上海中醫(yī)專門學校創(chuàng)立的上海中醫(yī)學會,創(chuàng)辦了《中醫(yī)雜志》、《國醫(yī)雜志》;中國針灸醫(yī)學專門學校設立中國針灸學研究社,創(chuàng)辦了《針灸雜志》,這是中國醫(yī)學史上第一份針灸雜志;上海中國醫(yī)學院創(chuàng)立《上海中國醫(yī)學院院刊》,上海中國國醫(yī)學院創(chuàng)立的《中醫(yī)新生命》,蘇州國醫(yī)學校還成立編譯館,出版了《蘇州國醫(yī)雜志》;上海新中國醫(yī)學院創(chuàng)立《新中醫(yī)刊》[14]等等。這些學社和雜志始終貫徹學術研究為教育服務的宗旨,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的這一特色對促進中醫(yī)學術的爭鳴、探討與交流,發(fā)揮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4結語
近代先進的江蘇中醫(yī)教育家積極順應時代的發(fā)展要求,創(chuàng)辦了一批具有一定規(guī)模和影響力的中醫(yī)學校,為中醫(yī)的生存與發(fā)展所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和貢獻。近代江蘇中醫(yī)教育,開始以學校教育為主導,不斷引入學校教育理念、原則和方法,在初步形成中醫(yī)學科體系的基礎上,在教學上引入了西醫(yī)知識,制定了較為全面和合理的課程以及教材體系,培養(yǎng)了一批具有扎實的中醫(yī)學理論與技能的,同時又有現(xiàn)代醫(yī)學知識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近代中醫(yī)學的生存危機,為近代中醫(yī)學的教學、科研和臨床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骨干人才。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在嘗試吸取先進教育理念的同時,依然能夠遵循中醫(yī)教育的傳統(tǒng)規(guī)律,堅持走教學與臨床相結合之路,堅持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之路,這是近代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盡管采取了規(guī)模化學校教育模式,但仍然名醫(yī)輩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對現(xiàn)代中醫(yī)藥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學習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宋建軍.中國近代教育史的分期與發(fā)展新論[J].合肥師范學院學報,2009,27(2):51-54.
[2]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育通史(第四卷)[M].2版.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27.
[3]孫培青.中國教育史(修訂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195.
[4]吳馨.上海縣續(xù)志[M].上海:南園志局,1918:9.[5]楊杏林,陸明.上海近代中醫(yī)教育概述[J].中華醫(yī)史雜志,1994,24(4):215-219.
[6]上海市中醫(yī)文獻館.上海中國醫(yī)學院院史[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5,8,15,115.
[7]徐建云.承淡安先生在針灸教育上的事跡[J].中醫(yī)文獻雜志,2000,18(3):36-37.
[8]車瑋.清末江蘇中醫(yī)學校教育概況及其述評[J].南京中醫(yī)藥大學學報,2007,8(4):211-212.
[9]高毓秋.丁福保年表[J].中華醫(yī)史雜志,2003,33(3):184-188.
[10]《名醫(yī)搖籃》編審委員會,上海中醫(yī)藥大學,上海市中醫(yī)文獻館.名醫(yī)搖籃:上海中醫(yī)學院(上海中醫(yī)專門學校)校史[M].上海:上海中醫(yī)藥大學出版社,1998:25,58,128.
[11]《杏苑鶴鳴》編審委員會.杏苑鶴鳴:上海新中國醫(yī)學院校史[M].上海:上海中醫(yī)藥大學出版社,2000:19,125.
[12]吳云波.蘇州國醫(yī)學校辦學精神和教育方針[J].中醫(yī)教育,1994,13(5):46-47,49.
[13]陸翔,戴慎.民國時期江蘇籍中醫(yī)醫(yī)家的歷史地位及影響[J].南京中醫(y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8(3):151-155.
[14]陸翔,朱長剛.民國時期江蘇籍中醫(yī)醫(yī)家教育思想探析[J].安徽中醫(yī)學院學報,2007,26(6):8-11.
作者:李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