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社會公平正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淺析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社會公平正義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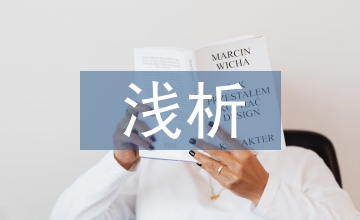
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認識到,關于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觀念不僅有著人類生命與意識的本體前提,同時也是在歷史中發展的觀念。馬克思說:“平等是人在實踐領域中對自身的意識,也就是人意識到別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它表明人的本質的統一,人的類意識和類行為、人和人的實際的同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8頁)恩格斯則進一步指出:“一切人,作為人來說,都有某些共同點,在這些共同點所及的范圍內,他們是平等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2頁)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進一步考察了人類平等觀念的演變與社會歷史中的人類平等與不平等的狀況,首先,他們指出,在人類的社會發展史中從來沒有實現真正的所有人的平等;其次,他們指出,平等觀念的演進發展到現代社會,“從人的這種共同特性中,從人就他們是人而言的這種平等中,引伸出這樣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43頁)同時,他們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抽象平等原則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馬克思說:“平等原則又由于被限制為僅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筆勾銷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說,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48頁)因此,不能囿于資產階級的眼界來看待平等問題,經濟與政治的不平等是最深刻的不平等,私有制社會中經濟的不平等表現為階級的對立與沖突。要真正實現人類的平等,必須消滅階級,解放全人類;只有消滅階級,消滅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或使人受屈辱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條件,才能有社會地位和權利的平等。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空想社會主義才真正變成了科學社會主義。
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觀點看,沒有平等也就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在以羅爾斯為代表的當代政治哲學的正義理論中,平等居于核心地位。沒有平等也就沒有社會正義。平等與正義是一個事情的兩面。雖然馬克思在他那個年代很少使用正義這一概念,并且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正義觀,但他對人類真正平等的追求,實質上代表了一種超越資產階級眼界的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因此,也可以說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在對立的階級已經消滅的社會條件下,從平等意義上理解的社會公平觀的要求是具體而多樣的。它強調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所應具有的平等基本權利,如生存權、受教育權、發展權等。它意味著人人享有社會可能提供給所有社會成員的基本資源和基本發展條件。社會公平觀強調每個人具有的平等權利,其根據在于每個人作為這一社會共同體的成員身份或資格。這是人類個體作為社會動物最根本的同一性。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來,我們消滅了剝削階級,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實現了最大限度的社會平等,即政治平等與經濟平等。回顧改革開放前所實行的社會分配制度,經濟平等是在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分配制度下實現的。它所導致的結果是社會生產力的低效率,“十年動亂”期間達到了經濟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進行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30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偉大成就。然而,在市場經濟和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條件下,社會生活的一個明顯變化則是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經濟平等是社會平等的重要方面,然而,平均主義的經濟平等導致社會生產力的低效率這一事實表明,這樣一種分配制度對于我國當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來說,是不適合的。它對于經濟發展缺乏激勵性,因為它保護了生產活動中的惰性。實際上,這意味著以往我們并沒有完整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并非認為在共產主義的初始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真正實現經濟的平等。在馬克思看來,社會主義社會還不能實行體現徹底平等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原則,而只能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前者是在更高級的社會階段———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馬克思設想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所實行的分配原則。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平等上雖然與資本主義社會有著質的區別,但仍然保留著“資產階級的法權”,承認不同貢獻的應得性。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不應空談抽象的道德和正義,而是應當把道德和正義問題與社會歷史發展階段聯系起來。因此,承認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差別,尤其是經濟上應得的差別,同樣是馬克思主義正義觀的內涵。從馬克思主義的正義觀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遵照鄧小平理論,讓一部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符合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歷史事實,同時也是向作為最終目標的“各取所需”的共同富裕的邁進。
不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經濟體制,并沒有預見到市場經濟的必要性。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市場經濟體制是現階段社會主義的生存與發展的必要體制。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社會實踐所產生的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卻是相當嚴峻的。這是因為市場本身有它的邏輯,如果不加以社會調節而完全按照市場的邏輯發展,在社會公平問題上就有可能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富裕的偉大愿景。市場經濟內蘊著一種經濟公平觀。這種經濟公平觀運行的結果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社會平等權利的社會公平正義觀有重疊的一面,但也有沖突的一面。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按照自己的邏輯運行,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經濟財富占有的不平等,貧富差距的拉大。一個公平合理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需要兩類公平:一是起點或機會的公平平等,二是應得的公平平等。就前者而言,是指所有進入市場中的經濟主體一律是平等的;如果某些主體有著優于其他主體的特殊權利,就是不公平的。這類公平平等也就是規則公平。就應得的公平平等而言,是指人們的勞動報酬是合法的收益所得,即符合“按勞動分配”的原則。然而,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按勞分配或按貢獻取酬的特點是拉開分配收益的檔次,從而激勵有能力的人,使他們有更大的勞動創造積極性或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并且,現代市場經濟的分配制度實行的是兩類分配制度,即按勞動力分配和按人力資本分配(包括股權或期權激勵),前者只有勞動力收益,后者則是智力或才能進入分配收益領域;兩者的差距可能高達千倍以上。
這里需要指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從非市場經濟的意義上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按勞分配原則,并且批判性地指出這里通行的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然而,馬克思所闡明的原理可以轉化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配原則。馬克思指出,由于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因此,勞動者領回作了各項社會扣除之后他的勞動“所給予社會的一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頁)。而這里的勞動所得并不表現為價值,即馬克思設想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消滅了商品交換,從而也就沒有貨幣,因此,個人從社會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從而領得與他的勞動量相當的消費資料。“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并且,“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同上,第11-12頁)然而,實踐表明在非市場的條件下,由于價值規律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從而不可能真正實行這一原則(結果是平均主義盛行)。這也就意味著,馬克思所提出的按勞分配原則只有在價值規律主導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才能真正起作用。不過,馬克思指出,這種平等的權利實際上是不平等的。他說:“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像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1-12頁)因此,雖然馬克思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在于真正的平等,然而他也意識到,由于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社會)剛剛從那個舊社會脫胎出來,因而權利不能超出那個社會的眼界,只能實行不平等的分配原則。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了理想社會的目標,馬克思對這一權利的批判表明他所追求的仍然是真正的社會平等。
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表明,隨著現代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財富占有的不平等現象也在發展,并將形成社會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分化。在現實中,由體制不健全、權錢關系等問題所導致的不公正的社會環境,使得社會財富占有上的不平等更為嚴峻。當前,我國社會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出現,并且基尼指數(0.46)已經超出了國際警界線。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已經拉開,并且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受阻,社會底層人員(如農民工)在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體制下難以改變其命運。如果一般社會成員的心理承受不了過分懸殊的收入差距,感受不到實際經濟利益的改善,尤其是社會底層人員感受不到生活的改善,那么就有可能危及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衡量利益關系是否和諧的一個基本尺度就在于社會公平是否得到了維護。一個財富占有嚴重不公平、利益分化嚴重的社會不是人民幸福的社會。同樣,一個貧窮的社會也不可能是人民幸福的社會。邁向共同富裕的經濟前提在于經濟的發展。沒有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沒有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要認識到社會公平正義觀和經濟生活的公平觀之間的不相容性,也要認識到它們在社會功能上的互補性。沒有市場經濟,中國不能經濟繁榮;而沒有社會和諧,中國不能長治久安。
重要的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并非是可有可無之舉,而是關系到中國走什么道路的根本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公平正義觀強調社會成員的生存權利、政治經濟權利的平等性,所指向的是未來人類社會的真正平等。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公平正義理想。我們必須意識到,市場經濟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它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樣一個歷史現實所規定的經濟必要性,但并不意味著我們的目的之所在。市場經濟內在有著偏離社會公平正義的趨向,因此,必須以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來加以制衡。制衡并不否定經濟生活的不平等,它在堅持平等的生存與發展權利的前提下,仍然承認一定范圍的應得財富的不平等的公正合理性。承認這類出發點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認可應得財富的不平等,是實行市場體制的現代經濟活動所需的公平觀,是現代生產效率的一個基本前提。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社會財富占有上的不平等有發生社會性質轉變的可能,即社會財富占有朝兩極分化發展,并引發社會的不穩定甚至社會的危機。因此,必須在特定意義上以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否定這種不平等,制約它的擴展,在財富分配上向平等方向傾斜,尤其是考慮那些最少受益者的利益。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不可能無限制地增加平等。增加平等在一定的社會認可范圍內可以增進效率;但超過了這個一定的范圍,就會產生負效率。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財富的分配既要體現市場經濟本身的特性,又要反映社會公平正義的呼聲,體現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本文作者:龔群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相關文章閱讀
- 1淺析宗教文化研究
- 2國外動畫藝術特征淺析
- 3所得稅會計淺析
- 4池塘養魚病害防治淺析
- 5服裝英語的翻譯淺析
- 6小學短跑訓練淺析
- 7奧運經濟淺析
- 8淺析金融會計
- 9淺析古籍句讀
- 10淺析美術課堂輔導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