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文學(xué)簡史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古代天文學(xué)簡史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古代天文學(xué)簡史范文
人類把地球繞太陽轉(zhuǎn)一圈確定為衡量時(shí)間的標(biāo)準(zhǔn)——年。但宇宙中所有天體的運(yùn)動(dòng)速度都是不同的,難道在宇宙范圍,時(shí)間真的沒有衡量標(biāo)準(zhǔn)?!或許,我們寧愿相信即使是在太空中,萬物也都有時(shí)間的長度,而時(shí)間也有細(xì)微的縫隙,“4度空間”——“蟲洞”就在我們四周,只是小到肉眼難以察覺,它存在于比分子、原子還細(xì)小的空間——“量子泡沫”之中。或許有朝一日人類的科技力量足以能夠抓住“蟲洞”并將它無限放大,抑或無中生有建造一個(gè)巨大的“蟲洞”,搭乘“時(shí)光機(jī)”即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自由穿越。只因自古以來,飛向太空,穿梭于宇宙空間就是人類最美好的遐想。
太空中飛上一個(gè)星期,等于地上100年,在時(shí)間中漫游,也就意味著飛進(jìn)未來,展開非凡的時(shí)空之旅。不止于觀賞太空旖旎的風(fēng)光,享受失重的樂趣。就像與宇宙心有靈犀的“小怪人”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Hawking)期望的那樣。
張開翅膀?qū)τ钪嬲归_充分的想象,閃念之間便會(huì)發(fā)現(xiàn)“世界”之外的“宇宙”竟是如此的神奇和美妙。而真理和幻想有時(shí)只是一線之差。“黑洞不黑”恰恰來源于一個(gè)閃念。誕生于1988年的《時(shí)間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以及2001年的《果殼中的宇宙》(The Universe in a Nutshell)可謂霍金對(duì)知識(shí)無限追求,對(duì)時(shí)空本質(zhì)之謎不懈探討之作。其背后是不斷求索的科學(xué)精神和勇敢頑強(qiáng)的人格力量。他的探索精神已然超越“臨界密度”,超越了相對(duì)論、量子力學(xué)、大爆炸等理論而邁入創(chuàng)造宇宙的“幾何之舞”。有關(guān)“黑洞”的探尋與定論,從而對(duì)于人類的觀念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第2篇:古代天文學(xué)簡史范文
關(guān)鍵詞:羊;綿羊;山羊;英譯
在中國農(nóng)歷羊年,全球華人會(huì)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慶祝羊年,甚至連老外們也想“摻和”一把。然而,他們很快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頭疼的問題:中國的羊年究竟是哪種羊?首先拋出問題的是英國曼徹斯特一家媒體,新聞的大標(biāo)題開宗明義:“曼徹斯特的中國春節(jié):究竟是哪一種羊?”糾結(jié)的不僅僅是英國人,美國媒體同樣“抓狂”,有些美國媒體直接就指定了一種羊,譬如華爾街日?qǐng)?bào)直接認(rèn)定是山羊,而今日美國則認(rèn)為是綿羊,最“聰明”的當(dāng)屬紐約時(shí)報(bào),他們避開了對(duì)究竟是哪種羊的討論,直接把羊年定義成了“any ruminant horned animal”(各種有角反芻動(dòng)物)。在此番討論中,“羊”年英譯的焦點(diǎn)集中在“sheep”(綿羊)和“goat”(山羊)之間。那么,羊年的“羊”究竟是“sheep”還是“goat”? 下面就此“羊”年英譯談?wù)勊娝搿?/p>
一、中國“羊”文化探析
1.生肖由來。生肖是華夏先民動(dòng)物崇拜、圖騰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學(xué)的結(jié)晶。和今天生肖說法完全一致的文獻(xiàn)出自東漢王充《論衡?物勢(shì)》:“……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論衡》提到生肖“羊”,但對(duì)“羊”的類別并無明確表述。但從文化淵源分析,“生肖屬相”歷來屬于漢文化的內(nèi)容,中國古代華夏文明主要生活的中原地區(qū),基本活動(dòng)的是山羊,綿羊則主要生活在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漠北、塞外。此外,綿羊主要為人們提供高質(zhì)量的毛皮,制作成寒衣。但在古代,生活在中原的人們以布衣、絲綢為主要衣料,在冬季,人們往往穿上好幾層單衣,而非一件“羊絨服”。當(dāng)時(shí)漢人對(duì)綿羊還比較陌生。從這點(diǎn)看,生肖羊應(yīng)是山羊。
2.“羊”型描述。古人對(duì)羊的造型描述,《論衡》中也有相關(guān)記載:“獬豸,一角之羊也……”。“獬豸”是中國上古傳說中一種羊型神獸,因其善斷是非曲直,所以獬豸又常被稱作“獬豸神羊”;神獸造型通常源于古人日常所見。所以,通過“獬豸”造型判斷,古人對(duì)羊的認(rèn)知至少應(yīng)是“有角羊”。眾所周知,山羊和綿羊的一個(gè)重大區(qū)別在羊角,山羊不論雄雌多有羊角,角多為直型鐮刀狀;而綿羊大部分無角,有角則多可能為雄性,多為螺旋形。獬豸的角趨直,更似山羊。那么,生肖羊跟獬豸同作為古人原始的動(dòng)物崇拜,也應(yīng)是山羊。
3.“羊”字解析。從漢字“羊”的演變來看,甲骨文是■;金文■承續(xù)甲骨文字形;篆文■基本承續(xù)金文字形,將金文的彎角■寫成■;隸書■則將篆文字形中類似“草頭”的羊角形狀■寫成了標(biāo)準(zhǔn)的“草頭”■。在甲骨文、大篆、小篆中,乃至簡化“羊”字中,“羊”都長著一對(duì)倒“V”型的角,這正像山羊那稍微有點(diǎn)彎的羊角。雖然在一些金文中又有類似綿羊角的■,但絕大部分古體“羊”字都依山羊角型而造,所以從漢字解析來看,生肖羊當(dāng)屬山羊。
4.考古發(fā)掘。從出土文物上看,絕大部分羊造型的文物,都是以山羊?yàn)樵停苌倏匆娋d羊的造型。譬如朝天宮博物館館藏的清代三陽開泰瓷瓶,圖案中的三只羊,就是長胡子、彎角的山羊,而故宮十二生肖銅首中的羊也是山羊造型。
二、“羊”的英語文化淵源
在英語文化中,山羊和綿羊有著迥異的象征意義。英語常用“the sheep and the goats”表示“好人與壞人”。同樣是羊,為何所受到的待遇如此懸殊?
英語“羊”的文化語境的淵源主要來自三個(gè)方面:生活勞動(dòng)、圣經(jīng)故事、希臘神話。
1.生活勞動(dòng)。首先,因?yàn)轲B(yǎng)羊業(yè)在西方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羊”對(duì)于英語文化的影響十分顯著。15世紀(jì)末由英國國內(nèi)養(yǎng)羊業(yè)引起的“圈地運(yùn)動(dòng)”甚至促進(jìn)了英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由于“羊”曾在西方人生活中扮演主導(dǎo)地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他們表達(dá)觀點(diǎn)的方式之一。綿羊性情溫和、毛質(zhì)好、肉鮮美、能換來財(cái)富,在以游牧為主的古猶太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因此綿羊(sheep)常被視為純潔、天真無邪的象征。在英語姓氏中,諸如Shepherd(牧羊人),Shephard以及Shepard等姓氏都衍生于sheep一詞。相比而言,山羊生性兇暴、雄性尾部散發(fā)異味,雖然人們也喝其奶食其肉取其皮,它仍然成了邪惡的象征。
2.《圣經(jīng)》淵源。綿羊與山羊成為“好人與壞人”(the sheep and the goats)的劃分最初來自《圣經(jīng)》馬太福音(Matthew 25:32)中的一段話:
“All the nations will be gathered before him, and he will separate the people one from another as a shepherd separates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
“世間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在《圣經(jīng)》里,上帝把他的臣民稱為綿羊,耶穌是牧羊人。他教誨信徒,牧羊人找到一只迷失的羊(sheep),得到的歡喜比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的歡喜還大。迷失的綿羊是耶穌的著名訓(xùn)誨辭,他認(rèn)為如果一個(gè)罪人改過自新,能帶來比九十九個(gè)無需悔改的義人更大的歡樂。因此,在英語里,用“迷失的綿羊”比喻“因誤入歧途而做錯(cuò)了事的人”“迷失正道的人”;因“綿羊”代表“善良的人”。
那么“山羊”為什么會(huì)被視為“惡”?在圣經(jīng)舊約中有這樣一則故事(《利未記》16:8 And Aaron shall place lots upon the two he goats: one lot “For the Lord”and the other lot,“For Azazel.”―Leviticus, Leviticus 16:8):上帝為了考驗(yàn)信徒亞伯拉罕的忠誠,要他把長子殺死祭奠,亞伯拉罕毫不猶豫舉刀就要?dú)鹤樱系叟商焓怪浦沽怂屗靡恢簧窖騺泶妫@就是“替罪羊”的由來。以后,每年的贖罪日,大祭司取山羊一只,把雙手按在山羊頭上,歷數(shù)猶太人的罪過,罪行就轉(zhuǎn)移到山羊身上,然后眾人把這只山羊驅(qū)趕到曠野之中,山羊就把眾人的罪過都帶走了,因此這只山羊叫scapegoat,scape即“驅(qū)趕”之意。山羊負(fù)罪至今,英語中許多表達(dá)方式說明了這一點(diǎn),譬如英語諺語有“You have no goats, and yet you sell kids.”(沒有老山羊,還把小羊賣了),再如英語修辭有“play the goat”有“做蠢事”一意。所以不論是諺語還是修辭,“goat”大都用在貶義語境下,這也體現(xiàn)了《圣經(jīng)》故事對(duì)英語“羊”的影響之大。
3.希臘神話。綿羊和山羊在古希臘神話中的地位也有較大的區(qū)別。在西方,人們會(huì)根據(jù)出生時(shí)太陽靠近天體黃道帶星座的位置來猜測(cè)一個(gè)人的性格。據(jù)說白羊座Aries(俗稱綿羊座)出生的人通常會(huì)被視為都是充滿活力而干勁十足的活躍者;而出生在摩羯座Capricorn(俗稱山羊座)的人相對(duì)而言則缺點(diǎn)較為明顯:缺乏改革創(chuàng)作精神,凡事猶豫不決。雖然星座玄學(xué)并無科學(xué)依據(jù),但也能略微窺覷出綿羊和山羊在英語文化中的差異。
文化是語言的基礎(chǔ),而語言是文化的延伸。在中西方文化中,“羊”實(shí)際上已經(jīng)脫離了其物質(zhì)構(gòu)架本身而被賦予了各種不同的寓意。在中國古代,“羊”用來指“綿羊”“山羊”皆可,雖然通過對(duì)文化資料的查考,農(nóng)歷“羊”年應(yīng)譯為“the year of goat”,但不論“山羊”“綿羊”,其意通“祥”,在漢語中的聯(lián)想意義基本相同。而在英語中“goat”卻是“邪惡”的代名詞,在具體翻譯時(shí)譯者需要考慮到“羊”的象征意義以及其背后的文化內(nèi)涵,所以綜合考量,“羊”年應(yīng)譯作“the year of sheep”為宜。當(dāng)然,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人們需要勇于超越自身文化的框架和約束,體會(huì)和接受外來文化,而譯者作為一種文化全球傳播的“媒介”之一,也理應(yīng)參與其中。畢竟,譯者只有在充分了解雙語文化背景后才能找準(zhǔn)兩種語言的契合點(diǎn),并最終實(shí)現(xiàn)傳遞文化之目的。
參考文獻(xiàn):
[1]鄭丕留,張仲葛,陳效華,等.中國養(yǎng)羊簡史[M].上海: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89-06.
[2]張黎艷,李宗成.十二生肖在英漢語言中的文化研究與對(duì)比[J].內(nèi)蒙古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2(03).
第3篇:古代天文學(xué)簡史范文
關(guān)鍵詞:漢代;唐代;歷法改革;傳統(tǒng)文獻(xiàn);文獻(xiàn)記載
《詩》、《尚書》、《春秋》、《國語》以及《管子》、《竹書紀(jì)年》、《家語》等文獻(xiàn)中有大量紀(jì)年紀(jì)日,冬至、朔望、日食等天象記載,這些記載連同《殷歷》、《周歷》等古歷法和歷代歷法專著,在后世各朝制定、改革歷法時(shí)都被給予了相當(dāng)?shù)闹匾暋5匾暡⒉灰馕吨鴮?duì)這些文獻(xiàn)記載持同一態(tài)度,他們?cè)诳隙ㄎ墨I(xiàn)記載的同時(shí),也會(huì)對(duì)其提出質(zhì)疑,進(jìn)而做出不同的解讀,甚至是否定文獻(xiàn)記載的正確性。本文欲以漢至唐代官修歷書為立足點(diǎn),考察歷法改革中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記載的態(tài)度,并試圖探討持有這些態(tài)度的原因。
1、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記載的重視、肯定與否定
古代在制歷、議歷、改歷時(shí),均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給予高度重視,以為自己的歷法或歷法觀點(diǎn)構(gòu)建優(yōu)勢(shì)。《后漢書》中記載:
劉歆研機(jī)極深,驗(yàn)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雒書乾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jìn)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yīng),少有闕謬。[1]
古代造歷者在鼓吹自己的歷法時(shí),極力將符合傳統(tǒng)文獻(xiàn)記載作為歷法的優(yōu)勢(shì)之一:
如后秦姜岌今治新歷……上可以考合于《春秋》,下可以取驗(yàn)于今世。[2]
如隋朝劉焯以開皇三年,奉敕修造……會(huì)通今古,符允經(jīng)傳,稽于庶類,信而有徵。[3]
力圖改歷的帝王和歷法家,也竭力引經(jīng)據(jù)典,從傳統(tǒng)中找尋佐證,為頒行新歷掃除障礙。東漢章帝在位期間,經(jīng)過一段歷爭(zhēng),欲改行《四分歷》時(shí),其詔書中就稱:
《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今改行《四分》,以遵堯順孔,奉天之文,同心敬授,倘獲咸熙。[4]
漢靈帝熹平年間,出現(xiàn)過一場(chǎng)“是否符合傳統(tǒng)文獻(xiàn)記載”的歷爭(zhēng)公案。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jì)掾陳晃上言,認(rèn)為歷法當(dāng)用甲寅元而不應(yīng)用庚申元,因?yàn)閳D讖中沒有以庚申為元者,庚申元是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隨意編造的虛妄之說。([1],235頁)之后議郎蔡邕提出以甲寅、庚申為元均可以在傳統(tǒng)中找到來源,只是古代的歷法各有不同而已。
令案情更加戲劇化的是,蔡邕還指出馮光、陳晃以甲寅為元的歷法雖然以《考靈曜》為基礎(chǔ),但其中參雜了與《考靈曜》、《甘石星經(jīng)》舊文均不相符的內(nèi)容,希望弄清其歷法的根據(jù),并以此來改造儀器,進(jìn)行實(shí)測(cè),說服持不同觀點(diǎn)的歷法家,但二人堅(jiān)持說自己的歷法來自傳統(tǒng)文獻(xiàn)。([1],237頁)之后該案以判處馮光、陳晃罰充鬼薪之刑,但靈帝頒書不必追究為終。這一公案可以充分體現(xiàn)古代歷法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重視。
另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在制歷、歷議時(shí),在人員上多要求儒家經(jīng)學(xué)人士參與其中:“尚書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經(jīng)史,…… 請(qǐng)此數(shù)人在秘省參侯。”[5]這也顯示了歷法改革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重視。
以上幾例古代歷法改革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記載的重視,均以對(duì)文獻(xiàn)記載的肯定為前提,這種肯定傾向在記載與歷法推算發(fā)生矛盾時(shí),表現(xiàn)尤為明顯,《春秋》中日食記載有日期的共有34條,《殷歷》、《魯歷》提前一天的有13條,晚一天的有3條;《周歷》提前一天的有22條,提前兩天的有9條。針對(duì)這種情況,《新唐書》評(píng)論道“其偽可知矣。” [6]這里的偽,并非指《春秋》的記載有誤,而是指這些歷法有問題。
但歷法家在重視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過程中,并非總是持同一的肯定態(tài)度,對(duì)不同的文獻(xiàn)可能持不同的態(tài)度,即使是同一文獻(xiàn),不同人的解讀也會(huì)完全不同,甚至有肯定與否定之別。
時(shí)有古歷六家,學(xué)者疑其紕漏,劉向父子,咸家討論,班固因之,采以為志。[7]
對(duì)于古代的傳統(tǒng)文獻(xiàn),并非所有人都全盤接受。
《春秋》中日食不書朔者有八條:《公羊》曰:“二日也。”《谷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6],597頁)
錢樂之因此認(rèn)為“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4],205頁)但“日蝕于朔,此乃天驗(yàn),《經(jīng)》《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圣人明文”([2],563頁)而劉孝孫“今以甲子元?dú)v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jīng)夫子,于理尤詳,《公羊》、《谷梁》皆臆說也”。([3],425頁)從中可看出不同人對(duì)同一事件的不同態(tài)度。
另一個(gè)例子是:《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對(duì)于房,有2種解讀,一種認(rèn)為是房星,即房宿的標(biāo)準(zhǔn)星,πSco[8]。另一種認(rèn)為是十二辰次之一。([6],601頁)
此外,《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水涸,本見而草木節(jié)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fēng)戎寒。”天根朝覿,《時(shí)訓(xùn)》也有記載:“爰始收潦”,《月令》也記載有:“水涸”。對(duì)于不同文獻(xiàn)對(duì)同一事物的記載,鄭康成的態(tài)度是“據(jù)當(dāng)時(shí)所見,謂天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為繆。”([6],602頁),而韋昭認(rèn)為“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皆非是。”([6],602頁)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顯示出了不同甚至是否定的態(tài)度。
由此可見,古人在對(duì)待傳統(tǒng)文獻(xiàn)時(shí),并非持單一的肯定態(tài)度,他們給予傳統(tǒng)文獻(xiàn)非常重要的地位,對(duì)其進(jìn)行不同的解讀,甚至是否定文獻(xiàn)的真實(shí)性或正確性。下文中我們將試圖探討古人持有這種態(tài)度的原因。
2、探討重視、肯定或否定文獻(xiàn)傳統(tǒng)的因素
2.1 傳統(tǒng)文獻(xiàn)自身的價(jià)值
傳統(tǒng)文獻(xiàn)記載著自先秦以來的許多天象記錄,歷法家認(rèn)為這些記錄為制定、改革、檢驗(yàn)歷法提供了很好的證據(jù)。后秦姜岌造《三紀(jì)甲子元?dú)v》,在其歷略中論述道:
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shí),時(shí)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shí)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huì)薄蝕可以驗(yàn)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有六……([2],566頁)
從中可以看出他對(duì)仲尼作《春秋》評(píng)價(jià)很高,特別指出其中的日食記錄對(duì)檢驗(yàn)歷法的重要性。對(duì)于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價(jià)值,杜預(yù)在《春秋長歷》中說到:“日蝕于朔,此乃天驗(yàn),《經(jīng)》《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可見至少在杜預(yù)心中,《經(jīng)》《傳》在記錄實(shí)際日食天象上,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對(duì)此,杜預(yù)有自己的觀點(diǎn):
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yùn)其舍,皆動(dòng)物也。物動(dòng)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有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shù),故歷無不有先后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言當(dāng)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yàn)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余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shù)術(shù)絕滅,遠(yuǎn)尋《經(jīng)》《傳》微旨,大量可知,時(shí)之違繆,則《經(jīng)》《傳》有驗(yàn)。學(xué)者固當(dāng)曲循《經(jīng)》《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明,以推時(shí)驗(yàn);而皆不然,各據(jù)其學(xué),以推春秋,此無異于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2],563-564頁)
這段文字至少包含兩點(diǎn)信息:一是《春秋》、《經(jīng)》、《傳》等傳統(tǒng)文獻(xiàn)是真實(shí)天象的忠實(shí)記錄者,歷法的制訂改革必須以此為依據(jù);二是歷法制訂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準(zhǔn)確預(yù)知天象——“順天”,因此對(duì)于傳統(tǒng)文獻(xiàn),必須把它當(dāng)成有力的工具,而不是死守文獻(xiàn)記載,杜預(yù)在此還用“度己之跡”“削他人之足”這一對(duì)比喻將“順天”與“推《春秋》”的關(guān)系作進(jìn)一步形象闡述。杜預(yù)的這一觀點(diǎn),既將文獻(xiàn)傳統(tǒng)置于高位,又揭示了歷法家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作出各自不同的解讀甚至背離傳統(tǒng)的部分原因。
對(duì)于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價(jià)值,比起杜預(yù),東漢蔡邕更注重與實(shí)際的結(jié)合。他在論及古代各歷的上元均有所不同時(shí),提及“他元雖不明于圖讖,各自一家之術(shù),皆當(dāng)有效于當(dāng)時(shí)。”([1],235頁)強(qiáng)調(diào)了不符合文獻(xiàn)傳統(tǒng)而與實(shí)際相符的意義,他甚至提出“且三光之行,遲速進(jìn)退,不必若一。術(shù)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當(dāng)時(shí)而已。故有古今之術(shù)。今術(shù)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猶古術(shù)之不能下通于今也。”([1],236頁)完全把符合實(shí)際放在第一位。
2.2 傳統(tǒng)文獻(xiàn)自身的多樣性
傳統(tǒng)文獻(xiàn),由于時(shí)代、地理、類型、作者等因素,每部文獻(xiàn)都有其自身的特點(diǎn),涉及到歷法,則有各自紀(jì)年系統(tǒng)的差異,《大衍歷議》中認(rèn)為:
《傳》所據(jù)者《周歷》也,《緯》所據(jù)者《殷歷》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6],592頁)
《隋書》中記載:若依《命歷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為錯(cuò)。([3],430頁)傳統(tǒng)之間也存在相互矛盾之處。
各代制定歷法定上元時(shí),都力圖在傳統(tǒng)中尋找根據(jù),如上文提及的東漢“歷元是否符合文獻(xiàn)傳統(tǒng)”公案,但傳統(tǒng)中的上元即已各不相同:
案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1],235頁)
天難諶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9]
對(duì)于建正,黃帝調(diào)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均以建寅為正,謂之“孟春”,到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為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為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10]“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huán),窮則反本。”([10],1258頁)
傳統(tǒng)本身具有多樣選擇性,后世歷法家在選擇文獻(xiàn)傳統(tǒng)時(shí),自然可挑選對(duì)自己有利的文獻(xiàn)記載進(jìn)行論證。《大衍歷議》之“中氣議”有如下論述:
《戊寅歷》月氣專合于《緯》,《麟德歷》專合于《傳》,偏取之,故兩失之。([6],592頁)
這種傳統(tǒng)的相異甚至延伸到了歷法家對(duì)傳統(tǒng)自身的解讀中,如對(duì)《春秋》的考證:
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shù)可傳于后。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2],566頁)
這種因文獻(xiàn)傳統(tǒng)自身的多樣性造成的矛盾加劇了歷法家對(duì)文獻(xiàn)傳統(tǒng)的不同解讀甚至是背離,可以以己之“矛”,攻彼之“盾”,為自己的歷法進(jìn)行辯護(hù),增加其可靠性的砝碼。
2.3 歷法家引用文獻(xiàn)傳統(tǒng)的最終目的是為自己的歷法或歷法觀點(diǎn)辯護(hù)
歷法家在改革、評(píng)論歷法時(shí),引經(jīng)據(jù)典,其最終目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歷法或歷法觀點(diǎn)優(yōu)于他者,以文獻(xiàn)的力量為自己增勢(shì)。歷法家們對(duì)待傳統(tǒng)文獻(xiàn)有三類方式:一是直接引用單個(gè)或同類文獻(xiàn),為自己的觀點(diǎn)作論據(jù);二是引用甲乙兩種文獻(xiàn),以甲文獻(xiàn)批駁乙文獻(xiàn);三是無論同類或異類文獻(xiàn),均運(yùn)用不同的觀點(diǎn)進(jìn)行解釋,以與自己的歷法或歷論相符合。對(duì)于第一、二類方式,前文論述中多有涉及,此處主要對(duì)第三種方式進(jìn)行討論。
劉宋時(shí)祖沖之和戴法興爭(zhēng)論歷法,祖沖之有一條論述:
日度歲差,前法所略,臣據(jù)經(jīng)史辯證此數(shù),而法興設(shè)難,征引《詩》《書》,三事皆繆。[11]
這段當(dāng)事人的話,鮮明地顯示出爭(zhēng)辯雙方均從傳統(tǒng)文獻(xiàn)中找尋依據(jù),為各自論點(diǎn)搖旗吶喊。其中一條爭(zhēng)議點(diǎn)是《尚書》中的“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法興議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則中宿常在衛(wèi)陽,羲、和所以正時(shí),取其萬代不易也。沖之以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
沖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jù)人君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準(zhǔn),流見之勢(shì),中天為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興以為《書》說四星,皆在衛(wèi)陽之位,自在巳地,進(jìn)失向方,退非始見,迂回經(jīng)文,以就所執(zhí),違訓(xùn)詭情,此則甚矣。([11],239-240頁)
戴法興和祖沖之對(duì)四星昏中的方位問題持不同意見,相互爭(zhēng)論,各自對(duì)其作出自己的解釋,并批判對(duì)方的觀點(diǎn)。
同樣以“昴仲”為基礎(chǔ),唐傅仁均的《麟德歷》遭到中算歷博士王孝通的發(fā)難: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耳。舉中宿,則余星可知。仁均專守昴中,執(zhí)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明昴中非為常準(zhǔn)。若堯時(shí)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余載,冬至昏翼中,日應(yīng)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yuǎn),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則《甲辰元?dú)v》為通術(shù)矣。[12]
縱觀王孝通的全部論述,他最終的落腳點(diǎn)在強(qiáng)調(diào)《甲辰元?dú)v》的通用性,其方法是對(duì)傅仁均的文獻(xiàn)傳統(tǒng)證據(jù)之一“星昴昏中”進(jìn)行批判,認(rèn)為傅仁均只選取《堯典》“四仲中星”中的一例作為論據(jù)這一作法有問題;同時(shí)以《月令》作為依據(jù),對(duì)“星昴昏中”這一記載的準(zhǔn)確性提出質(zhì)疑。然而事情至此,并沒有結(jié)束。
《大衍歷議》“日度議”中,著重闡述了“歲差”的概念,運(yùn)用“歲差”概念,歷議又對(duì)“王孝通的批判”進(jìn)行了批判:
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余載,……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于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shè)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fēng)以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為仲冬之侯,何必援昴于始覿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6],601頁)
這段論述雖然最終也以“水星昏正”作為論據(jù)對(duì)“星昴昏中”進(jìn)行了批評(píng),但其論述乃是運(yùn)用“歲差”觀念進(jìn)行辯護(hù),這里我們無需以現(xiàn)代的眼光評(píng)價(jià)王孝通和“大衍歷議”的觀點(diǎn)孰是孰非,僅把關(guān)注點(diǎn)放在對(duì)“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這一文獻(xiàn)的態(tài)度和做法上。從他們的論證中可以看出,歷法家絞盡腦汁,顛來倒去拿“日短星昴”來說事,無非是給自己推崇的《甲辰元?dú)v》或《大衍歷》增加優(yōu)越性的砝碼。
2.4 傳統(tǒng)在建設(shè)中逐漸成為傳統(tǒng)
傳統(tǒng),并非生來就成為衡量后世歷法優(yōu)劣的標(biāo)尺。傳統(tǒng)在第一次出現(xiàn)時(shí),與其同時(shí)存在或先于其存在的傳統(tǒng)并不在少數(shù),而為何唯獨(dú)這一傳統(tǒng)成為后世擁護(hù)的至高典籍,其他則成為旁門左道甚至逐漸失去傳承。這一點(diǎn)與傳統(tǒng)本身的建設(shè)密不可分,這一建設(shè)過程,是與后世歷法家不斷引用、解讀、肯定與否定傳統(tǒng)本身密切結(jié)合在一起的。
《舊唐書》中記載“暨秦氏焚書,遺文殘缺,漢興作者,師法多門,雖同徵鐘律之文,共演蓍龜之說,而建元或異,積蔀相懸” [13],歷法興建之初,制歷的方法多種多樣,歷法也各不相同,隨著各代歷法的發(fā)展,某部歷法或歷法中的某些部分逐漸發(fā)展為后世所遵循的傳統(tǒng)。
自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shí)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tǒng)改正朔,為歷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12],533頁)
后世歷法家在各自朝代制定歷法時(shí),因循時(shí)世,在運(yùn)用傳統(tǒng)的同時(shí),也逐漸改造傳統(tǒng),有時(shí)甚至將原有傳統(tǒng)棄之不用,建立新的傳統(tǒng)。
南北朝以前,各代歷法為了推合朔望,設(shè)置閏月,有設(shè)置月大小相間的傳統(tǒng)。到了何承天改歷法時(shí),為了使推算更精確,對(duì)這一傳統(tǒng)做法進(jìn)行了修改,其精良的歷法因此遭到批駁:
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余,于推交合時(shí)刻雖審,皆用贏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異。([4],205頁)
何承天的歷法在當(dāng)時(shí)未獲頒行,但后世皆認(rèn)為他的歷法優(yōu)良,并在隋朝得到應(yīng)用。對(duì)于“頻三大,頻二小”的做法,虞鄺認(rèn)為:
所謂朔在會(huì)合,茍躔次既同,何患于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于頻小也?([6],596頁)
傳統(tǒng)自身的建設(shè)過程,使得傳統(tǒng)文獻(xiàn)在不同時(shí)期、不同歷法家之間遭遇不同的經(jīng)歷,促進(jìn)傳統(tǒng)本身從非傳統(tǒng)向傳統(tǒng)轉(zhuǎn)化或進(jìn)一步成為經(jīng)典。《春秋》中日食有明確日期記載者共34條,日食是對(duì)朔日的最好考證。然而殷歷、魯歷、周歷都不能與朔日全合,各代歷法家都試圖以己之歷法對(duì)朔日進(jìn)行推合,以獲得與傳統(tǒng)相符的最精確歷法。
祖沖之考察《春秋》中日食有朔日的記載,以《周歷》和《魯歷》為范圍,認(rèn)為二者取其一([11],238頁)。到了唐代,《大衍歷議》“合朔議”認(rèn)為這些朔日記載并非出自同一歷法,對(duì)傳統(tǒng)的態(tài)度與前人迥異:
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皆與《周歷》合。其所記多周、齊、晉事,蓋周王所頒,齊、晉用之。……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原伯絞,與《魯歷》、《周歷》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楚人所赴也。……此則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shù)齊矣。([6],594-595頁)
此外,歷代官修史書中提及歷法時(shí),對(duì)文獻(xiàn)經(jīng)典的引用有一個(gè)從少到多的趨勢(shì)。漢人制歷議歷時(shí)少用文獻(xiàn)傳統(tǒng)作為佐證,《史記》中涉及文獻(xiàn)傳統(tǒng)僅1處《春秋》,《漢書》較之有10多處。自此以后,逐漸有增多的趨勢(shì),并在唐代達(dá)到一個(gè)高峰。雖然這涉及修書者以及歷法發(fā)展?fàn)顩r等因素,如《舊唐書》“歷”部分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引用很少。但在趨勢(shì)上可看出自漢至唐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關(guān)注越來越強(qiáng),這種重視除數(shù)量上的變化外,更表現(xiàn)為從對(duì)文獻(xiàn)的簡單引用,演變?yōu)閷?duì)文獻(xiàn)的反復(fù)解讀、考證。這一點(diǎn)充分顯示了傳統(tǒng)自身的建設(shè)過程。
2.5 外界因素的作用
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尊崇以及文獻(xiàn)自身地位的逐步建立,除傳統(tǒng)文獻(xiàn)自身的價(jià)值以及歷法家的目的性外,其他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動(dòng)作用。
一是自漢代以來儒家學(xué)說地位的確立。漢武帝時(shí)期,董仲舒建議實(shí)行“罷黜百家,獨(dú)尊儒書”,以加強(qiáng)皇權(quán)的統(tǒng)治地位。此后,儒家學(xué)說在漢代開始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詩》、《書》、《禮》、《易》、《春秋》被確立為“五經(jīng)”。以經(jīng)為中心,逐漸發(fā)展出經(jīng)學(xué),分為古文經(jīng)學(xué)和今文經(jīng)學(xué)。儒家經(jīng)學(xué)博士可以利用經(jīng)學(xué)權(quán)威干預(yù)國家政事,在國家政治制度如禮樂建制、刑法制度中發(fā)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是時(shí)上方鄉(xiāng)文學(xué),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qǐng)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bǔ)廷尉史,亭疑法。”[14]朝廷政事甚至可以直接依據(jù)儒家經(jīng)典裁決罪行,而且還能得到帝王和大臣們的贊同。[15]自漢代以后,儒家經(jīng)學(xué)得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成為后世歷代的正統(tǒng)思想,成為人才培養(yǎng)、國家制度建設(shè)的重要內(nèi)容。
二是教育和人才選拔制度的推動(dòng)。漢代建立官學(xué),發(fā)展興盛,分為中央官學(xué)和地方官學(xué)。中央官學(xué)和地方官學(xué)都教授儒家經(jīng)學(xué),太學(xué)的教學(xué)內(nèi)容主要是儒家經(jīng)典——《詩經(jīng)》、《書經(jīng)》、《禮經(jīng)》、《易經(jīng)》、《春秋經(jīng)》。[16]教授經(jīng)學(xué)的博士既是老師,又在朝廷為官,而這些儒學(xué)弟子則是官員的后備軍。此外,漢代統(tǒng)治者使用“察舉”和“征辟”并輔以考試的方法來選拔人才,這些方式都把儒家學(xué)說的內(nèi)容包含其中,甚至是直接作為考試內(nèi)容。漢代以后,教育和人才選拔制度逐漸發(fā)展并完善,到隋唐科舉制度趨于完善。知識(shí)分子若想進(jìn)入統(tǒng)治階級(jí),必須通過國家設(shè)立的教育制度或人才選拔制度,而這些制度均指定了學(xué)術(shù)的范圍甚至是教學(xué)、考試的范本。這些范圍的確定和范本的規(guī)劃必然將一些文獻(xiàn)推至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位置,成為知識(shí)分子乃至以后的國家官員夜習(xí)日用的工具。
本文在分析了古代歷法改革中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記載持有不同的肯定、否定態(tài)度后,從傳統(tǒng)文獻(xiàn)自身的價(jià)值及其多樣性,歷法家重視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目的,傳統(tǒng)文獻(xiàn)自身的建設(shè)過程以及儒家學(xué)說、教育及人才選拔制度的推動(dòng)等方面分析了古代歷法家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持以上不同態(tài)度的原因。這些因素的復(fù)雜性一方面影響了了古代歷法家對(duì)傳統(tǒng)文獻(xiàn)的不同態(tài)度,同時(shí)也提醒了現(xiàn)代學(xué)者在對(duì)待古代文獻(xiàn)和古代學(xué)者的文獻(xiàn)引用和研究時(shí)必須持謹(jǐn)慎的態(tài)度,從文獻(xiàn)本身及其外部環(huán)境多視角對(duì)其進(jìn)行關(guān)注和分析。
參考文獻(xiàn):
[1] [南朝宋] 范曄. 后漢書·律歷中[M]. 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
[2] [唐] 房玄齡等. 晉書·律歷[M]. 北京:中華書局,1974.
[3] [唐] 魏徵. 隋書·律歷下[M]. 北京:中華書局,2000.
[4] [南朝梁] 沈約. 宋書·歷上[M]. 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
[5] [北齊]魏收. 魏書·律歷[M]. 北京:中華書局,1974.
[6] [宋] 歐陽修, 宋祁. 新唐書·歷三上[M]. 北京:中華書局,1975.
[7] [唐] 魏徵. 隋書·律歷中[M]. 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367-368.
[8] 郭盛熾.《石氏星經(jīng)》觀測(cè)年代初探[J]. 自然科學(xué)史研究,1994,13(1).
[9] [南朝宋] 范曄. 后漢書·律歷下[M]. 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
[10] [漢]班固. 漢書·律歷[M]. 北京:中華書局,1975.
[11] [南朝梁] 沈約. 宋書·歷下[M]. 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
[12] [宋] 歐陽修, 宋祁. 新唐書·歷[M]. 北京:中華書局,1975.
[13] [后晉]劉昫等. 舊唐書·歷[M]. 北京:中華書局,1975,1151.
[14] [漢] 司馬遷. 史記·酷吏列傳[M].第2版. 北京:中華書局,1982.
[15] 周桂鈿,李祥俊. 中國學(xué)術(shù)通史·先秦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0.
[16] 謝蘭榮主編. 中外教育簡史[M]. 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14.
A Review about the Attitudes to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in the
Calendrical Debates and Reform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ies
SONG Shenm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Abstract: Fro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by governments from Han to Tang Dynastie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ttitudes to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in the calendrical debates and reforms. It is indicated that each dynasty had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they had the same attitudes. It is discussed that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were not only given affirmation but also were suspected, and even experience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What is more, some people had denied the validity of some of them. Some analyses will be given, a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attitudes will be explored in the paper.
第4篇:古代天文學(xué)簡史范文
【關(guān)鍵詞】科學(xué)共同體/非社會(huì)性/社會(huì)功能
【正文】
英國著名科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家約翰·齊曼認(rèn)為,元科學(xué)研究可以從三個(gè)層面進(jìn)行:研究科學(xué)家個(gè)體情感和價(jià)值的科學(xué)心理學(xué)、研究科學(xué)知識(shí)增長和演變的科學(xué)史以及研究科學(xué)共同體結(jié)構(gòu)和運(yùn)作的科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可見,科學(xué)共同體是科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研究中的一個(gè)核心概念。然而,這個(gè)概念在使用過程中卻存在著極大的混亂。因此,在討論科學(xué)共同體的非社會(huì)性之前有必要對(duì)其稍作解析。
一、科學(xué)共同體的三重含義
“科學(xué)共同體”(scientific community)一詞由英國科學(xué)家和哲學(xué)家米切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最早使用。他認(rèn)為科學(xué)家不是孤軍奮戰(zhàn),而是與他的專業(yè)同行一起工作,各個(gè)不同專業(yè)團(tuán)體合成一個(gè)大的群體,稱作“科學(xué)共同體”;“今天的科學(xué)家不能孤立地從事其行當(dāng)。他必須在某個(gè)機(jī)構(gòu)框架內(nèi)占據(jù)一個(gè)明確的位置。一位化學(xué)家成為化學(xué)職業(yè)中的一員;一位動(dòng)物學(xué)家、數(shù)學(xué)家或心理學(xué)屬于一個(gè)由專業(yè)科學(xué)家構(gòu)成的特殊群體。這些不同的科學(xué)家群體合起來形成‘科學(xué)共同體’”。[1]可見,波蘭尼意指的科學(xué)共同體是由不同專業(yè)的科學(xué)家共同組成的群體。
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哲學(xué)家?guī)於鲃t賦予了“科學(xué)共同體”以更為引人注目的意義和地位。在庫恩那里,科學(xué)共同體成了科學(xué)知識(shí)增長和科學(xué)革命發(fā)生的基礎(chǔ),其意義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按照庫恩的定義,科學(xué)共同體實(shí)際上是指一個(gè)專業(yè)的同行:“直觀地看,科學(xué)共同體是由一些學(xué)有專長的實(shí)際工作者所組成。他們由他們所受教育和訓(xùn)練中的共同因素結(jié)合在一起,他們自認(rèn)為,也被人認(rèn)為專門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標(biāo),也培養(yǎng)自己的接班人。這種共同體具有這樣一些特點(diǎn):內(nèi)部交流比較充分,專業(yè)方面的看法也較一致。同一共同體成員很大程度吸收同樣的文獻(xiàn),引出類似的教訓(xùn)。不同的共同體總是注意不同的問題,所以超出集團(tuán)范圍進(jìn)行業(yè)務(wù)交流很困難,常常引起誤會(huì),勉強(qiáng)進(jìn)行還會(huì)造成嚴(yán)重分歧。”[2]
在科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家中也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以李克特為代表,觀點(diǎn)同波蘭尼相近,認(rèn)為科學(xué)共同體即是所有科學(xué)家構(gòu)成的群體:“我們所謂的科學(xué)共同體,是由世界上所有的科學(xué)家共同組成的,他們?cè)谒麄冏约褐芯S持著為促進(jìn)科學(xué)過程而建立起來的特有關(guān)系。”[3]另一種以加斯頓為代表,觀點(diǎn)同庫恩相近,認(rèn)為科學(xué)共同體是一種專業(yè)團(tuán)體:“在某一領(lǐng)域進(jìn)行研究的科學(xué)家通常對(duì)另一個(gè)不同領(lǐng)域的研究工作并不了解。例如,物理學(xué)家的工作通常對(duì)化學(xué)的發(fā)展沒有什么重要性,而化學(xué)家的工作對(duì)生物學(xué)的發(fā)展通常也沒有什么重要性。因此,把所有實(shí)際的科學(xué)家想象為‘科學(xué)共同體’是不正確的。實(shí)際上有許多科學(xué)家的‘共同體’。在許多研究領(lǐng)域,這些共同體的數(shù)目為10-20個(gè),但極少多于200個(gè)。”[4]
由此可見,對(duì)于科學(xué)共同體有兩種基本的理解:一種將其理解為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科學(xué)共同體是指一個(gè)專業(yè)的同行),一種將其理解為科學(xué)職業(yè)共同體(科學(xué)共同體指所有以科學(xué)為職業(yè)的人)。然而,筆者以為,這兩種理解均不能完整反映科學(xué)共同體作為共同體存在的方式,還需要對(duì)其作第三種意義上的理解。
第三種意義上的科學(xué)共同體可稱作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即科學(xué)家們由于共同體的研究結(jié)合而成的群體。這是科學(xué)共同體更為普遍的存在方式。近代科學(xué)以專業(yè)化為特征,共同的研究基本上等同于共同的專業(yè)研究。因此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即等于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但在古代,嚴(yán)格的科學(xué)專業(yè)尚未成型。科學(xué)家只是憑著共同的興趣、研究內(nèi)容或僅僅是因?yàn)橛泄餐难芯炕囟Y(jié)合在一起,如古希臘著名的米都利學(xué)派(泰勒斯開創(chuàng))、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愛利亞學(xué)派、柏拉圖學(xué)園、呂克昂學(xué)園(亞里士多德開辦)等等。這種結(jié)合體只有共同的研究,而無所謂共同的專業(yè)。現(xiàn)代科學(xué)則以專業(yè)融合和交叉為特征,加斯頓所說“物理學(xué)家的工作通常對(duì)化學(xué)的發(fā)展沒有什么重要性,而化學(xué)家的工作對(duì)生物學(xué)的發(fā)展通常也沒有什么重要性”的現(xiàn)象早已為現(xiàn)實(shí)所否定。跨專業(yè)的交流和合作開始變得很平常。這時(shí),科學(xué)研究不能再以專業(yè)為劃分單位了,而只能以共同研究本身來度量。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近似于學(xué)派,但又比學(xué)派更為廣泛。它不像學(xué)派那樣要求有特殊的思想綱領(lǐng)和突出的科學(xué)成就,而只要求有廣泛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和接觸,并共同從事科學(xué)研究。一般而言,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具有共同的研究基地(實(shí)驗(yàn)室、學(xué)院、大學(xué)、研究所等)。
綜上所述,科學(xué)共同體的三重含義:以共同專業(yè)為特征的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以共同職業(yè)為特征的科學(xué)職業(yè)共同體以及以共同研究為特征的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
二、科學(xué)共同體具有非社會(huì)性
在科學(xué)觀中,對(duì)科學(xué)的社會(huì)性強(qiáng)調(diào)得比較多。自蘇聯(lián)學(xué)者黑森在第二屆國際科學(xué)史大會(huì)上(1931年)提交“牛頓《原理》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根源”一文后,科學(xué)的社會(huì)性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沖擊力進(jìn)入科學(xué)史家的視野。從此,科學(xué)史研究無論在方法上還是在內(nèi)容上都發(fā)生了根本性轉(zhuǎn)變:從內(nèi)史轉(zhuǎn)向了外史。這個(gè)轉(zhuǎn)向是如此徹底,以至于1970年代英國的“愛丁堡學(xué)派”提出了科學(xué)知識(shí)本身也是社會(huì)建構(gòu)的極端綱領(lǐng)。盡管人們對(duì)這一綱領(lǐng)遠(yuǎn)未達(dá)成共識(shí),但無論如何,社會(huì)性都已成為一道籠罩于科學(xué)之上的光環(huán),揮之不去了。但筆者以為,外史研究只是在傳統(tǒng)的科學(xué)史研究中打入了社會(huì)學(xué)的視角,它為我們提供的應(yīng)是一種新的觀察維度而不是現(xiàn)成的結(jié)論。在社會(huì)學(xué)視角的觀照下,科學(xué)應(yīng)該既有社會(huì)性的一面,也應(yīng)有非社會(huì)性的一面,而這種非社會(huì)性主要為科學(xué)共同體所體現(xiàn)。
科學(xué)共同體的非社會(huì)性具有表現(xiàn)為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的疏社會(huì)性、科學(xué)職業(yè)共同體的超社會(huì)性和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的抗社會(huì)性。
1.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的疏社會(huì)性
所謂疏社會(huì)性,簡言之,即疏遠(yuǎn)社會(huì)需求和評(píng)價(jià)的性質(zhì)。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在兩方面顯示出疏社會(huì)性。第一,在科學(xué)研究的出發(fā)點(diǎn)上,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中的科學(xué)家在很大程度上考慮的不是社會(huì)的實(shí)際需要,而是專業(yè)上的可能、發(fā)展以及自身的興趣、愛好。沃爾夫在《十六、十七世紀(jì)科學(xué)技術(shù)和哲學(xué)史》中對(duì)英國皇家學(xué)會(huì)評(píng)述道:“皇家學(xué)會(huì)早期會(huì)員對(duì)一切新奇的自然界現(xiàn)象普遍感到好奇,……他們把研究的網(wǎng)撒得太寬,因此喪失了統(tǒng)一地長期集中研究一組有限的問題所會(huì)帶來的好處。”[5]如果英國皇家學(xué)會(huì)的科學(xué)家主要從社會(huì)實(shí)際需要出發(fā)考慮研究范圍,那么他們決不至于“把研究的網(wǎng)撒得太寬”。美國著名科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家默頓用定量方法證明了此點(diǎn)。他依據(jù)英國《皇家學(xué)會(huì)史》備忘錄,統(tǒng)計(jì)了1661、1662、1686、1687四年英國皇家學(xué)會(huì)會(huì)員的科研選題情況,結(jié)果表明:“在四年中所進(jìn)行的各種研究的不到一半(41.3%)是致力于純科學(xué)的。如果我們?cè)谶@個(gè)數(shù)字上再加上只與實(shí)際需要有間接聯(lián)系的項(xiàng)目(海上運(yùn)輸7.4%,采礦17.5%,軍事技術(shù)3.6%),那么差不多有70%的研究與實(shí)際需要沒有直接聯(lián)系。”[6]默頓進(jìn)一步指出:“在本總結(jié)考察的以后年代,在純科學(xué)領(lǐng)域中的研究比例日益增加。”([6]3,259)
即使在純科學(xué)研究中,有些科學(xué)家甚至也不是為了解決某個(gè)具體問題才從事科學(xué)研究,而是為了滿足好奇心或?yàn)榱藢?duì)外在世界有一個(gè)全面透徹的了解。如果說前者還與社會(huì)有一定聯(lián)系(為解決社會(huì)實(shí)際問題打下理論基礎(chǔ),如DNA的發(fā)現(xiàn)有助于醫(yī)學(xué)治療),那么后者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就相當(dāng)疏遠(yuǎn)了。美籍印度天體物理學(xué)家、諾貝爾獎(jiǎng)得主錢德拉塞卡說道:“我想,我的動(dòng)機(jī)與許多科學(xué)家的不一樣,沃森(James Watson)說,當(dāng)他還是年輕人時(shí),就想到要解決一個(gè)問題,使他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獎(jiǎng)。他努力向前干下去,后來發(fā)現(xiàn)了DNA。很明顯,這種方法對(duì)沃森是很適合的,但我的動(dòng)機(jī)不是為了解決一個(gè)單一的問題,我需要的是對(duì)整個(gè)領(lǐng)域有一種透視的看法。”[7]在科學(xué)史上,像錢德拉塞卡這樣的科學(xué)家并非鳳毛麟角。開普勒在饑寒交迫下“為天空立法”,愛因斯坦在孤立無援中構(gòu)建“大統(tǒng)一論”,他們都是錢德拉塞卡式的人物。情況正如貝爾納指出的:“我們可以認(rèn)為,科學(xué)作為一種職業(yè),具有三個(gè)彼此互不排斥的目的:使科學(xué)家得到樂趣并且滿足他天生的好奇心、發(fā)現(xiàn)外面世界并對(duì)它有全面的了解、而且還把這種了解用來解決人類福利的問題。可以把這些稱為科學(xué)的心理目的、理性目的和社會(huì)目的。”[8]在貝爾納概括的科學(xué)的三個(gè)目的中,只有社會(huì)目的直接與社會(huì)相關(guān),其他三分之二則明顯遠(yuǎn)離社會(huì)。
第二,在科學(xué)研究的落腳點(diǎn)上,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有獨(dú)立于社會(huì)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科學(xué)水平的高低在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內(nèi)得到評(píng)判,而不是交由社會(huì)評(píng)價(jià)的。科學(xué)家的聲望、地位主要由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決定。科學(xué)家看重的也主要是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而不是整個(gè)社會(huì)對(duì)他(她)的認(rèn)可。在這一點(diǎn)上,科學(xué)共同體與其他共同體有著明顯的不同。例如,在體育中,運(yùn)動(dòng)員的成績是由裁判來評(píng)價(jià)的,而一名好的裁判未必是一名好的運(yùn)動(dòng)員,而且也不必是一名運(yùn)動(dòng)員;但科學(xué)家的成績則必須由科學(xué)家而且是專業(yè)同行來評(píng)價(jià),非科學(xué)家以及外專業(yè)的科學(xué)家都無權(quán)也無力對(duì)之作出評(píng)判。換言之,對(duì)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成員及其成就的評(píng)價(jià)可以在該專業(yè)共同體內(nèi)部進(jìn)行,而無需交由社會(huì)由其他共同體來完成。這也正是為什么同是精神生產(chǎn),在文學(xué)藝術(shù)上有專職評(píng)論家而在科學(xué)上并無類似對(duì)應(yīng)者的原因。
2.科學(xué)職業(yè)共同體的超社會(huì)性
所謂超社會(huì)性,即超越社會(huì)責(zé)任和界限的性質(zhì)。這首先表現(xiàn)在,一種職業(yè),一般而言都須對(duì)該職業(yè)群體之外的其他某個(gè)社會(huì)群體或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即都要負(fù)擔(dān)一定的社會(huì)責(zé)任,如,醫(yī)生要對(duì)病人負(fù)責(zé),教師要對(duì)學(xué)生負(fù)責(zé),工人要對(duì)雇主負(fù)責(zé)、軍人(職業(yè)軍人)要對(duì)政府和國家負(fù)責(zé)等等,但科學(xué)作為一種職業(yè)卻并無明顯可見的社會(huì)責(zé)任,它無須對(duì)任何人負(fù)責(zé)。當(dāng)然,對(duì)一名具體的科學(xué)家來說情況有所不同,因?yàn)樗赡苁鞘芄陀谡推髽I(yè)的科學(xué)家,因而必須對(duì)其負(fù)責(zé)。但對(duì)整個(gè)科學(xué)職業(yè)共同體而言,卻并無正式的法律或社會(huì)條文對(duì)其社會(huì)責(zé)任作出規(guī)定。1660年英國皇家學(xué)會(huì)成立時(shí),其章程中就只有權(quán)利而并無責(zé)任規(guī)定:“朕獲悉,一個(gè)時(shí)期以來,有不少一直愛好和研究此項(xiàng)業(yè)務(wù)的才智德行卓著之士每周定期開會(huì),……探討事物奧秘,以求確立哲學(xué)中確鑿之原理并糾正其中不確鑿之原理,……因此,朕決定對(duì)這一杰出團(tuán)體和如此優(yōu)異且堪稱頌之事業(yè)予以皇室恩典、保護(hù)和一切應(yīng)有的鼓勵(lì)。”([8],p.61)
另一方面,科學(xué)職業(yè)共同體又表現(xiàn)出超越某個(gè)具體社會(huì)的責(zé)任感,一種對(duì)整個(gè)人類以至整個(gè)世界和宇宙的關(guān)懷。正因?yàn)檫@一點(diǎn),在世界各國,許多杰出科學(xué)家的國家觀念都非常淡薄。天文學(xué)家第谷在1597年寫道:“當(dāng)政治家或其他人使他不勝煩勞的時(shí)候,他就應(yīng)該堅(jiān)定地帶著他的財(cái)產(chǎn)離去。人在各種條件下都應(yīng)該昂然挺立,無論至何處都是上有青天,下有大地,對(duì)一個(gè)具有活力的人來說,每一個(gè)地方都是他的祖國。”[9]法國哲學(xué)家和科學(xué)家笛卡爾則毫不猶豫地為一個(gè)荷蘭將軍和瑞典克里斯蒂納女王所雇用。荷蘭物理學(xué)家惠更斯在他的國家與法國發(fā)生戰(zhàn)爭(zhēng)的時(shí)候生活并工作在巴黎。當(dāng)英國科學(xué)家戴維就要接受法國的一枚獎(jiǎng)?wù)聲r(shí),英國和法國還發(fā)生著戰(zhàn)爭(zhēng)。愛因斯坦在1915年寫道:“我多么想把我們處于不同‘祖國’的同行們團(tuán)結(jié)在一起。這個(gè)學(xué)者和知識(shí)分子的小集體不就是值得像我們這樣的人去認(rèn)真關(guān)懷的唯一的‘祖國’嗎?難道他們的信念竟要僅僅取決于國境這個(gè)偶然條件嗎?”[10]1926年的蘇聯(lián)正是國家意識(shí)興盛之時(shí),然而蘇聯(lián)科學(xué)院常務(wù)秘書奧爾登堡院士在一次工作會(huì)議上卻警告說:“別忘了科學(xué)不是國家的,它不是哪個(gè)政府的,而是整個(gè)世界的。”[11]1942年和1943年,正值蘇德戰(zhàn)事如火如荼、蘇聯(lián)愛國熱情空前高漲、祖國利益高于一切之際,蘇聯(lián)科學(xué)家卻先后為兩位早已去世的外國科學(xué)家舉行了熱烈慶典——紀(jì)念伽利略逝世300周年和牛頓誕辰300周年。[12]這些都是科學(xué)職業(yè)共同體超社會(huì)性的表現(xiàn)。
3.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的抗社會(huì)性
所謂抗社會(huì)性,即抗拒社會(huì)干預(yù)和控制的性質(zhì)。社會(huì)心理學(xué)的主要?jiǎng)?chuàng)始人愛德華·羅斯曾指出,那些希望按照一定行為準(zhǔn)則行事的人傾向于限制社會(huì)控制。[13]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的成員即屬此列。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內(nèi)部自然形成的準(zhǔn)則、規(guī)范以及氣質(zhì)、偏好等(由于共同的研究活動(dòng)形成)使得共同體成員本能地排斥外在的社會(huì)控制和標(biāo)準(zhǔn),因?yàn)樗鼈兛赡芘c共同體自身的價(jià)值觀念、追求目標(biāo)和協(xié)調(diào)方式相沖突。對(duì)于這種沖突,德國社會(huì)學(xué)家斐迪南·滕尼斯有敏銳洞見。他認(rèn)為,共同體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礎(chǔ)之上的聯(lián)合體(如家庭、宗族),或者歷史形成的聯(lián)合體(如村莊、城市)以及思想的聯(lián)合體(如友誼、師徒關(guān)系)。維系這些聯(lián)合體的,是共同的習(xí)慣、風(fēng)俗、愛好、信仰等非正式的感情因素。與此相反,社會(huì)則產(chǎn)生于眾多個(gè)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有計(jì)劃、有組織的理性協(xié)調(diào)。個(gè)人預(yù)計(jì)從共同實(shí)現(xiàn)某一種預(yù)定的目的會(huì)于己有利,因而聚合在一起共同行動(dòng)。因此,“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huì)只不過是一種暫時(shí)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共同體本身應(yīng)該被理解成一種生機(jī)勃勃的有機(jī)體,而社會(huì)應(yīng)該被理解為一種機(jī)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4]正是共同體與社會(huì)的這種異質(zhì)性使得它們相互之間產(chǎn)生一定程度的對(duì)抗。雖然滕尼斯在這項(xiàng)研究中并未涉及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這一概念,但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完全可以劃歸到滕尼斯所說的“思想的聯(lián)合體”之列,因而具有一般共同體的特點(diǎn)。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只要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仍然是共同體,它就會(huì)本能地抗拒社會(huì)對(duì)它的調(diào)節(jié)和控制。
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的抗社會(huì)性在蘇聯(lián)科學(xué)院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由于缺少與外界的交流,蘇聯(lián)科學(xué)院的內(nèi)部交流頗為頻繁,并且往往打破專業(yè)界限。對(duì)此,美國的彼得·克寧(peter Kneen)博士評(píng)論到:“一位美國科學(xué)家如果不能打電話、寫信或經(jīng)常參加遠(yuǎn)處的討論班和會(huì)議,他(她)就會(huì)覺得缺少一個(gè)研究共同體,而相應(yīng)的,一位蘇聯(lián)科學(xué)家卻只需穿過一條走廊或者從一幢房子走至它相鄰的另一幢房子就能完滿解決問題。”[15]這種緊密交流和聯(lián)系使得蘇聯(lián)科學(xué)院中的科學(xué)家結(jié)成一個(gè)非常強(qiáng)的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這樣,盡管蘇聯(lián)建國后社會(huì)上一直提倡科學(xué)與工業(yè)相結(jié)合、理論與實(shí)踐相結(jié)合、科學(xué)必須面向國民經(jīng)濟(jì)主戰(zhàn)場(chǎng)服務(wù),但科學(xué)院的科學(xué)家們一直固守純粹科學(xué)立場(chǎng),并強(qiáng)烈反對(duì)國家和社會(huì)對(duì)科學(xué)的干預(yù)和控制。例如,1955年科學(xué)院院長涅斯米揚(yáng)諾夫就曾對(duì)政府接連不斷地以解決生產(chǎn)問題的要求來干擾科學(xué)院各研究所的工作表示不滿。諾貝爾獎(jiǎng)得主謝苗諾夫亦爭(zhēng)辯說,科學(xué)并不像許多斯大林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工業(yè)的附屬品,而是有它獨(dú)立的任務(wù),這就是“對(duì)自然界的徹底研究”。[16]20世紀(jì)20年代以后,蘇聯(lián)多次試圖成立一個(gè)中央機(jī)關(guān)(例如1965年成立的國家科學(xué)技術(shù)委員會(huì))對(duì)科學(xué)技術(shù)進(jìn)行全面控制,但由于科學(xué)院的抵制(實(shí)際是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的抵制),這一設(shè)想一直沒有完全得到落實(shí)。“經(jīng)過一番權(quán)力較量,科學(xué)院與國家科學(xué)技術(shù)委員會(huì)達(dá)成一項(xiàng)妥協(xié),即科學(xué)院繼續(xù)充當(dāng)基礎(chǔ)科學(xué)的主要機(jī)構(gòu),而國家科學(xué)技術(shù)委員會(huì)專管技術(shù)政策和技術(shù)轉(zhuǎn)讓。”([16],p.203)
三、科學(xué)共同體非社會(huì)性的社會(huì)功能
科學(xué)共同體的非社會(huì)性有著極為重要的“社會(huì)功能”(并非對(duì)社會(huì)的功能,而是社會(huì)學(xué)視角下對(duì)科學(xué)自身的功能)。一方面,它使科學(xué)有著超越人為界限的可能,使科學(xué)不僅是一種具有特殊目的和指向的活動(dòng),更是一種超越個(gè)人、社會(huì)、民族和國家的普世活動(dòng);另一方面它又在科學(xué)與非科學(xué)之間豎起了一道屏障,將科學(xué)家與外部社會(huì)相對(duì)隔絕,使之不為外部力量所輕易左右。這樣,科學(xué)研究就不會(huì)像軍隊(duì)或工業(yè)公司那樣完全受官僚機(jī)構(gòu)的支配,從而保持相對(duì)的獨(dú)立、自主和自由。馬克思說:“只有在共同體中,個(gè)人才能獲得全面發(fā)展其才能的手段,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gè)人自由。”[17]在個(gè)體力量微弱的條件下,具有非社會(huì)性的共同體既是個(gè)人抵抗國家和社會(huì)強(qiáng)力直接干預(yù)和控制的保護(hù)和依托,也是化解個(gè)人和社會(huì)之間矛盾和沖突的緩沖和中介。更重要的是,科學(xué)共同體的非社會(huì)性還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各種偽科學(xué)和學(xué)術(shù)腐敗的發(fā)展。
偽科學(xué)和學(xué)術(shù)腐敗的發(fā)生機(jī)制如下:一、科學(xué)對(duì)社會(huì)有用,即科學(xué)具有功利性和有效性;二、因?yàn)榈谝稽c(diǎn),科學(xué)在社會(huì)上受到尊重和重視,政府、企業(yè)等非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開始有目的地控制、利用和扶持科學(xué),從事科學(xué)研究變得有利可圖;三、由于第二點(diǎn),社會(huì)上出現(xiàn)大量試圖通過科學(xué)獲取利益的人,同時(shí),科學(xué)評(píng)價(jià)權(quán)部分轉(zhuǎn)移到非科學(xué)人員手上;四、由于上述原因,許多科學(xué)成果的優(yōu)劣、真?zhèn)蔚貌坏接行цb定,于是各種打著科學(xué)旗號(hào)的假冒偽劣行徑便乘機(jī)而起。
科學(xué)共同體的非社會(huì)性則能有效地避免上述發(fā)生機(jī)制的生成。首先,科學(xué)專業(yè)共同體的疏社會(huì)性減弱了科學(xué)的功利性,在科學(xué)研究的動(dòng)機(jī)上弱化了實(shí)用性要求,從而減少了因其造成的負(fù)面效應(yīng)。齊曼曾指出“當(dāng)研究成為一種‘責(zé)任’和‘職業(yè)’,顯然是在為雇主和薪金出力時(shí),就難以保持一種獻(xiàn)身的精神了。科學(xué)家對(duì)高尚目標(biāo)的獻(xiàn)身,保持了他的純粹,捍衛(wèi)了他個(gè)人的正直。當(dāng)研究成為‘同其他任務(wù)職業(yè)一樣’時(shí),對(duì)科學(xué)上杰出成就的追求會(huì)被奢望、虛榮和權(quán)術(shù)所代替。”[18]從這個(gè)意義上說,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的非社會(huì)性首先從道德上減少了偽科學(xué)和學(xué)術(shù)腐敗發(fā)生的可能。其次,科學(xué)職業(yè)共同體的超社會(huì)性增強(qiáng)了科學(xué)的開放性。當(dāng)科學(xué)家成為世界一體時(shí),要想在某個(gè)國家內(nèi)保存?zhèn)慰茖W(xué)或劣質(zhì)科學(xué)就變得更加困難了。中國清朝楊光先的歷法和蘇聯(lián)李森科的“春化論”等偽科學(xué)和劣質(zhì)科學(xué)就是在科學(xué)共同體超社會(huì)性的作用下瓦解的。最后,良好規(guī)范的競(jìng)爭(zhēng)是杜絕一切假冒偽劣的有效機(jī)制,在經(jīng)濟(jì)上如此,在學(xué)術(shù)上亦是如此。在經(jīng)濟(jì)上要保證良好規(guī)范的競(jìng)爭(zhēng)就必須充分發(fā)揮市場(chǎng)的作用,減少非市場(chǎng)因素的干擾;在學(xué)術(shù)上要保證良好規(guī)范的競(jìng)爭(zhēng)則必須充分發(fā)揮科學(xué)家主體的作用,即科學(xué)共同體的作用,減弱非科學(xué)因素的干擾,而科學(xué)研究共同體的抗社會(huì)性正好具有這種功能。它最大限度地強(qiáng)化了科學(xué)共同體的機(jī)能,使各種學(xué)說能夠按照科學(xué)本身的要求和規(guī)范展開競(jìng)爭(zhēng),進(jìn)而淘汰那些偽科學(xué)和劣質(zhì)科學(xué)。在這個(gè)意義上,科學(xué)共同體的非社會(huì)性又在體制上減少了偽科學(xué)和學(xué)術(shù)腐敗發(fā)生的可能。
總之,科學(xué)共同體的非社會(huì)性在保證科學(xué)良好運(yùn)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社會(huì)功能。正是因?yàn)檫@一點(diǎn),韋伯強(qiáng)調(diào)的“學(xué)術(shù)與政治相分離”的原則有其永恒的價(jià)值和意義。
四、結(jié)論
20世紀(jì)以來,科學(xué)正如齊曼所描述的“正在喪失作為社會(huì)整體中具有自主性的一部分的地位及其獨(dú)立的標(biāo)準(zhǔn)與目標(biāo),并且被納入‘合作’的控制之下。它已被逐漸當(dāng)作有目的的社會(huì)活動(dòng)的一種工具,而不再被認(rèn)為是不可預(yù)測(cè)的社會(huì)力量的獨(dú)立來源。這樣科學(xué)就從社會(huì)的邊緣進(jìn)入了權(quán)力的中心,在先進(jìn)的工業(yè)化國家,明顯地成為國家機(jī)器、統(tǒng)治階級(jí)、軍事—工業(yè)聯(lián)合體、或者種種支配我們生活的社會(huì)勢(shì)力的一種機(jī)構(gòu)。”([18]199-200)在科學(xué)已經(jīng)愈來愈社會(huì)化的今天,談?wù)摽茖W(xué)的非社會(huì)性似乎有些不合時(shí)宜。然而,科學(xué)的社會(huì)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世俗化”的一種表現(xiàn),它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科學(xué)的品位,而且使科學(xué)淪為各種權(quán)力爭(zhēng)奪的對(duì)象和犧牲品。半個(gè)多世紀(jì)前默頓曾指出:“在十七世紀(jì),對(duì)科學(xué)的最有效的支持是功利標(biāo)準(zhǔn);今天,它卻時(shí)而對(duì)科學(xué)起著一種壓制的作用。”([6],287)同樣,科學(xué)的社會(huì)化也曾一度對(duì)科學(xué)和社會(huì)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今天,在科學(xué)的社會(huì)性已經(jīng)被過分強(qiáng)調(diào)并且實(shí)際上對(duì)科學(xué)構(gòu)成了某種損害的時(shí)候,回過頭來探討一下科學(xué)的非社會(huì)性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發(fā)展科學(xué)。
【參考文獻(xiàn)】
[1] Michael Polanyi.The Logic of Ligerty[M]:the Reflections and Rejoinder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1951.53.
[2] (美)托馬斯·庫恩著.必要的張力[M].紀(jì)樹立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2。
[3] (美)李克特著.科學(xué)是一種文化過程[M].顧昕,張小天譯,北京:天聯(lián)書店,1989.138。
[4] (美)杰里·加斯頓著.科學(xué)的社會(huì)運(yùn)行[M].顧昕等譯.北京: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88.18。
[5] (英)亞·沃爾夫著.十六、十七世紀(jì)科學(xué)、技術(shù)和哲學(xué)史(上冊(cè))[M].周昌忠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202-203。
[6] (美)羅伯特·金·默頓.十七世紀(jì)英格蘭的科學(xué)、技術(shù)與社會(huì).范岱年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0.256。
[7] (美)S.錢德拉塞卡.莎士比亞、牛頓和貝多芬——不同的創(chuàng)造模式[C].楊建鄴,王曉明等譯.長沙:湖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6.191。
[8] (英)J.D.貝爾納.科學(xué)的社會(huì)功能[M].陳體芳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2.150。
[9] (美)莫里斯·戈蘭著.科學(xué)與反科學(xué).王德祿,王魯平等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14。
[10] (美)愛因斯坦.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許良英等編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79.5。
[11] Loren R.Graham.The soviet Acacemy of Science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1927-1932[M].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176.
[12] Alexander Vucinich.Empire of Knowledge: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1917-1970)[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204.
[13] (美)E.A.羅斯.社會(huì)控制[M].秦志勇,毛永政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48。
[14] (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體與社會(huì)[M].林榮遠(yuǎn)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9.54。
[15] Peter Kneen.Soviet Scientists and the State:An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Science in the USSR[M].London:Macmillan Pr.Ltd.,1984.44.
[16] (美)洛倫·R.格雷厄姆著.俄羅斯和蘇聯(lián)科學(xué)簡史[M].葉式@①,黃一勤譯.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0.204-205。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相關(guān)熱門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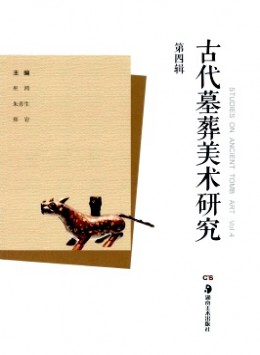
古代墓葬美術(shù)研究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CJF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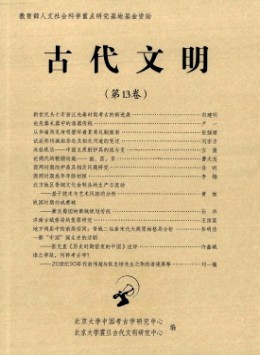
古代文明·輯刊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CJFD)
-

古代文明·中英文
級(jí)別:CSSCI南大期刊
榮譽(yù):中國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
-

古代文學(xué)前沿與評(píng)論
級(jí)別:部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CJFD)
-

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CJ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