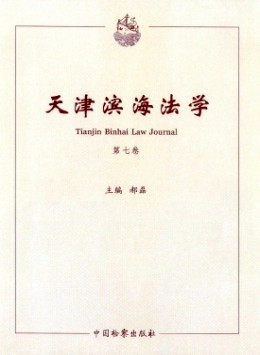民法典的說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民法典的說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關 鍵 詞人文主義,物文主義,民法典的倫理基礎,市場,人
一
2001年,徐國棟教授發表了《兩種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義對物文主義》一文,提出在中國民法典的起草過程中存在著物文主義的思路,并且對這一思路進行了批評。 文章一發表就引發了激烈的爭議。
論爭的焦點在于:究竟是否存在著物文主義的民法觀念?反對者通過論證不可能存在物文主義,回答了徐國棟教授的提問。既然民法規范都是以人為出發點,圍繞人而展開,其所調整的也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么,容納這些規范的民法典也都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被認為是人文主義的民法典。在人與物的關系上,始終是作為主體的人控制和支配著作為客體的物,不可能出現人與物的沖突。
延續這種思路,尹田教授于2004年又以《無財產即無人格——法國民法上廣義財產理論的現代啟示》為標題發表文章,否認物文主義民法觀念的存在。 但是,物文主義真的不存在嗎?那么就讓我們從“無財產即無人格”這樣的觀念談起。無
論尹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賦予“財產”以何種獨特的——在我看來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內涵,他的文章標題本身就揭示了“財產”能夠決定和支配“人格”的地位。如果把“財產”置換為“物”,把人格——按照通常的理解,就是指法律上的主體資格——置換為“人”,這不正是“物”反客為主,支配和凌駕于“人”之上嗎!物文主義何處尋?“無財產即無人格”的觀念就是其入門。
二
“無財產即無人格”的說法,在嚴格的法律意義上可以被處理為關于法律主體資格的一條規范:擁有財產是獲得法律上的主體資格的前提,沒有財產就無法成為法律上的主體。就現代民法而言,這顯然是個錯誤的說法。現代民法的基本原則是自然人因出生而成為民事主體,此外別無財產性的資格要求。從法律邏輯的角度看,“無財產即無人格”的說法中隱含著一個悖論。“有財產”,在嚴格的法律意義上應該表述為“享有財產性的權利”,而享有權利必須以具有法律上的主體資格——也就是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為前提。所以,“有人格”在邏輯上應該是“有財產”的前提。如果執著于“無財產即無人格”,那么就會導致一個邏輯上的循環悖論:無人格就無法獲得財產,而無法獲得財產本身又導致無法獲得人格。以羅馬法上的例子來說,奴隸不享有人格,并不是因為奴隸沒有財產,相反,是因為奴隸沒有人格,導致其不能擁有財產。
具體地分析民事主體的財產狀況與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們最多可以認為,財產是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所可能產生的給付義務的一般擔保。民事主體的財產狀況發生變化,會導致其履行債務的一般擔保的變化,進而間接影響到其交易相對方的交易安全。從實踐來看,民事主體的財產狀況會在事實上影響其在市場上從事交易活動的可能的規模和性質。但是,財產狀況不可能一般性地影響到民事主體的法律主體資格。這是因為:
(1)民事主體的財產狀況對民事主體從事不承擔義務的純獲利性質的行為沒有影響;
(2)民事主體的財產狀況對民事主體從事非市場交易性質的民事活動沒有影響;
概言之,即使民事主體由于沒有財產,因而沒有所謂的商業資信而被排斥在市場交易之外,這也不意味著他被一般性地排斥于所有的民事活動之外。
但是,“無財產即無人格”這樣的命題卻以一種絕對的方式將財產與人格相勾連,把廣義上“成為市民社會之一員”的“人格”,狹義地處理為“進入市場之地從事交換的資格”的意思,并且流露出以下的基本判斷:
(1)市民社會的基本社會生活關系是一種商業交換關系。因為它把不為市場所承認的人也看作是不為市民社會所承認的人;
(2)市民社會中的行為主體是有財產的商人。因為它把無財產的人排除在民法的主體之外, 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它把民法的領域限制于調整市場交換關系;
(3)作為結果,它把市民的存在化約為一種具有交換價值的純粹物質性的存在。
這是一種市場交易倫理主導下的民法觀念。在市場交易體系中,人與人之間聯系的紐帶就是需求關系。人在市場上的存在沒有自在的目的和意義,其意義只在于市場上的交換價值。在這樣的背景下,不難理解“無財產即無人格”這樣的說法。因為,無財產的人不具有市場交換價值,對于他人沒有什么用處,所以當然就不是人了! 在市場交易體系中,人格依附于財產,或者干脆可以說,市場上的人格就是財產。與你交易的人,并不把你看作一個本來意義上的人,而是把你看作是一個財產的符號。在這里,我們終于看到了“物”對“人”的取代和遮蔽。
因此,“無財產即無人格”描述和宣揚的正是一種市場交易倫理,一種見物不見人,以物度量人,將他人看作實現自己需求的物質性手段的商業觀念。馬克思將這樣的觀念總結為“貨幣拜物教”。徐國棟教授出于漢語的修辭習慣,為了與“人文主義”相對仗,將之總結為“物文主義” ,使用的術語雖然是新的,但是概括卻是非常精確的。
三
但是,“無財產即無人格”還存在著另外的一種可能的理解:“一個毫無財產、一文不名的人,連生存都難以維持,能算是真正的人嗎?……人只在享有財產權時,才能成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也才有所謂人權和人的尊嚴、人的自由”。此論暗合于傳統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觀念,強調的是物質保障對人的精神性質的社會存在所具有的根本意義,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以此論為依據,在處理法律上的利益衡量的時候,認為財產權保障具有優越的地位,那么也會導致物對人的凌駕和僭越。
就民法具體制度層面而言,在民法所規范和調整的社會關系中,在一定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人格性質的利益與財產性質的利益的沖突。法律在對這些相互沖突的利益進行選擇時,必須遵循一定的標準。人文主義的民法價值觀念所堅持的原則就是人格性質的利益要優先于財產性質的利益。比如說,對不能清償債務的債務人的人身不得強制執行,雖然這以犧牲債權人的利益為代價;與之相類似,一些具有人身性質的債務不可強制執行;在債的抵消制度上,故意侵害人身所導致的損害賠償之債不能抵消;關于消費者的個人信息資料,未經過消費者本人同意,其擁有者不得進行商業性的利用。客觀而言,現代民法理論在這一層次上的基本價值判斷并不存在很大的爭議。
但是,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重要的是,在“無財產即無人格”這樣的市場交換倫理觀念的主導下,近代民法構建出一種以財產權保障為核心的理論,并且通過民法典的編纂將之落實在實在法中。在這樣的觀念下,所有權被認為是“所有的立法的普遍的靈魂”,是一種“神圣的權利”。以財產權保障為中心而構建的民法體制毫無疑問在促進財富的迅速增長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它也導致了許多的負面效益。首先,社會總財富的增加并不自然導致普遍福利的增加,它只是使得資產者的福利增加;其次,以它為基礎形成了一種將手段與目的倒置的所謂的“異化”的現象:追求財富本來是為了人,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原本為目的的“人”被忘記了,追求財富本身成為了目的,并且形成了財產決定和支配人的現象。所謂“人為財(物)死,鳥為食亡”,就是這種觀念的寫照;再次,人的存在中的精神性質的一面被忽視,人的多樣性的存在被簡單地物質化了。人的生活被理解為一場為擁有得更多(to have more)而進行的斗爭,而不是使得人本身更加具有內涵(to be more)。近代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特別強調財產權的保障。這不是因為立法者考慮到財產占有是人格保障的前提和基礎,而是因為保障財產權的規范中體現的是有利于市場上的強者的社會基本經濟結構。在這樣的體制下,少數市場上的強者能夠以追求經濟效率為名,運用其財產的力量去壓迫大多數的普通民眾。這種現象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形式的物對人的壓迫:犧牲大多數人的基本人格利益,去保護少數人對財富的享有。我們知道,在美國憲法史上,曾經認為限制工人最長工作時間的法律剝奪了工廠主的財產權。因為財產權本身就包括了追求財富最大化的權利。
從這個角度而言,不能否認以財產權為核心的傳統民法體制表現出鮮明的“物文主義”的特征。人文主義的民法觀念所反對的就是這種把財富放在民法的核心位置的思想,主張的則是“始終以人為目的”的民法基本價值取向。為此,它反對GDP崇拜,不把物質財富的增加當作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唯一標志;它認為,以犧牲公民身體健康,犧牲環境質量而獲得的財富增加是忽視人的存在,以把財富本身當作目的來追求的產物;以犧牲人格尊嚴,在非人的工作條件下,通過超負荷的勞動時間而獲得的產出是一種非人道意義上的產出;以追求效率的名義,犧牲大多數弱者的利益,來保障強者財富的加速積累而獲得的經濟效率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效率。人文主義的財富觀點認為:財富只有在服務于人,并且是有效地服務于人的基本價值的保障和實現的時候,才獲得其重要性,財富始終是人的保障的工具,而不應該成為目的本身,抽象地強調財富的重要性,把財富本身當作目的本身來追求,這就是“物文主義”,而不是“人文主義”。
四
對物文主義的民法觀念的清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對人類社會生活關系的本質的反思,是對人的社會性的吁求,是對人的存在中的精神屬性的提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本意上乃是市民之間的合伙。個人結合為團體在最根本上是為了協作互助。不可否認,協作互助的方式很多,市場交換是實現社會協作的一種重要方式,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它的界限之所在。既然市民社會并非只是市場交換關系的總和,那么我們就應該避免讓市場的法則成為市民社會的唯一準則。市民 (合伙人)不只是商人,雖然他在市場上追富逐利,但是離開市場之地,他在家庭中養老撫幼,在非商業的社會生活中扶弱濟困、互助合作。總而言之,必須承認民法觀念中的人是一個具有健全的社會倫理觀念的“社會人”,而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
第2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過去,西方人信奉一句格言:“知識就是力量”。如今,國人形成一個共識:“知識就是財富”。從“Power”(力量)到“Wealth”(財富)反映了人們對知識價值的認知在不斷的深化。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諸要素中,知識要素較之資金、資源和勞動力等要素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出于這種探索與追求,筆者從90年代中期以來,提議建立一個大于知識產權范圍的無形財產權體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質形態所產生的權利,從而回應現代科學技術與商品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法律需求。
一、私權領域的非物質化革命與知識產權制度的構建
知識產權法是近代社會商品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知識產品財產化與知識財產法律化帶來了財產權的“非物質化革命”,這是羅馬法以來私法領域中的一場深刻的制度創新與變革。可以說,傳統的物與物權制度,即是物質化的財產結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的構成中,出現了所謂抽象化、非物質化的財產類型,即表現為知識、技術、信息的無形財產。黑格爾認為,上述知識產品,“可以成為契約的對象,而與買賣中所承認的物同一視之。此類占有雖然可以像物那樣進行交易并結契約,但它又是內部的精神的東西。”因此,知識產品是獨立于傳統意義上的物的另類客體,對此類財產的保護,無法簡單采用羅馬法以來的現存權利形式。知識產權制度的出現,為人們提供了“獲得財產的新方式”(馬克思語),它以知識、技術、信息等精神產品作為其保護對象,是一個屬于私法范疇但又獨立存在的嶄新的財產權制度。概言之,知識財產是一種新的財產,它不是以往對物進行絕對支配的財產,而是“非物質化的和受到限制的財產”。“非物質化”的結果,極大地拓寬了財產法的適用范圍,在很多情況下,法律保護的對象不是有形的財富,而是無形的財富,財產遂被定義為“對價值的權利而非對物的權利”。“非絕對性”的意義在于對新財產權利的適當限制,其目的是防止權力過于壟斷,以保證知識的正當傳播。在現代社會里,以知識為對象,以產權為表現形式的無形財產在社會財富的構成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二、知識產權體系的窘境與新的無形財產權范圍的建立
知識產權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知識產權,即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三個主要組成部分。廣義的知識產權,除上述權利外,還包括商號權、商業秘密權、產地標記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植物新品種權等各種權利。廣義的知識產權范圍,目前已為兩個主要的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即《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與《知識產權協議》所認可。上述廣狹義之知識產權體系,主要包括兩類權利,一是智力性成果權。這類權利保護的對象都是人們智力創造活動的成果,一般產生于科學技術、文化知識領域。創造性是此類客體獲得權利保護的必要條件;二是經營性標記權。這類權利保護的對象概為標示產品來源和廠家特定人格的區別標記。可區別性是該類客體的主要特征。由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與社會財富形態的變化,財產越來越多地變為無形的或非物質的,其中主要涉及知識產權,但不限于知識產權。因此,筆者主張,可以考慮建立一個大于知識產權范圍的無形財產權體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質形態所產生的權利。
“無形財產權”的概念系由德國學者科拉于1875年率先提出。他批判了以往的學說將無形產品之權利說成是一種所有權的錯誤,而將其看作為區別所有權的權利,即“無形財產權”(Immateriagiiterrecht)。此學說發表后即風靡于歐洲大陸。在一些西方國家,相關立法與學說曾以無形財產權來概括有關智力成果的專有權利。直至20世紀60年代,知識產權成為國際上通告的法律術語,仍有西方學者繼續采用無形財產權的說法。此外,還有一些國家在典型知識產權領域之外又創制了“商品化(形象)權”,按照鄭成思教授的說法,這是一種關于人及動物形象被付諸商業性使用所產生的權利。上述情況表明,知識產權一詞在眾多非物質性財產面前已力不從心,在現代社會財富構成中,確實存在著一種具有無形財產屬性又不能歸類于知識產權范疇的某些權利,并且隨著社會生活的日益發展,還可能出現其他一些更新的權利形態,筆者將其中一些權利稱之為經營性資信權。筆者主張,以客體的非物質性為權利分類標準,概括出與一般財產所有權有別的無形財產所有權。
三、經營性資信權的本質屬性與基本形態
經營性資信權,是指人們對經營活動的資格、信譽所享有的專有權利,該類權利所保護的對象系工商企業所獲得的優勢或信譽,這種專營優勢與商業信譽形成了特定主體高于同行業其他一般企業獲利水平的超額盈利能力,權利客體所涉及的資格或能力,包含有明顯的財產利益因素,但也有精神利益的內容。資信是一種非物質性利益,對此人們長期拘泥于人格屬性的認識。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與人們權利觀念的進化,有必要將這種資信從一般人格利益分離出來,賦予其應有的財產意義,并以獨立的無形財產權的名義給予保護。
在經營性資信權范疇中,主要有以下幾類權利:
一是商譽權。商譽(goodwill)即商業信譽與聲譽,它是特定主體商業文化的一種特殊價值形態。在我國的法學著述中,商譽是一個內涵廣泛的概念。而在經濟學理論中,商譽是公眾對企業經濟能力所產生的肯定性評價。對此,《牛津法律大辭典》及英國法院的相關判例對商譽的表達也是褒義性的。筆者認為,目前法學界對商譽的通說有失精確。商譽的基本屬性可以兩個方面把握:第一,它源于企業自身的經濟能力,包括經營狀況、生產能力、產品質量、服務水平、履約態度等,這是商譽的客觀要件。第二,與傳統的知識產權不同,商譽權表現為非確定的地域性、非法定的時間性、非定型的專有性。因此它是一種特殊的無形財產權。
二是信用權。在英國《牛津法律大辭典》和美國《布萊克法律辭典》中,信用(credit)與賒購、信貸等交易活動有關,是當事人特殊經濟能力(即償付債務的能力)的表現,來源于社會對特定主體的評價。我國法學界通說對信用的詮釋與國外相關理論不同。其實,信用有別于商譽,前者是關于償付能力的客觀的一般性評價,任何主體都可成為信用的主體;后者是關于一般經濟能力的綜合的積極性評價,其主體僅限于經營主體。同時,信用不僅是人格利益,它是能夠通過信用交換而獲得交易利益,雖不具有物質形態,但以信用證、資信文件等為載體的財產利益。因此,信用權應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一種資信權。
三是特許經營權。特許經營或專營(franchise)是權力機關所授予的從事特種行業、生產或經銷特定商品的資格。從性質上講,它是一種行政權的延伸,是一種能產生特殊經濟效益的權力的授予,它包括特種行業經營權、壟斷經營權、許可證經營權、資源開采經營權及其他特許經營權。政府授予特許經營權是特定企業獲得從事特種商品經營的資格,其權利取得方式的特殊性絲毫不會影響該項權利的基本屬性。換言之,特許經營權是一項以專營資格為客體的無形財產權。
四是形象權。形象(publicity)是人或社會組織所擁有的各種形象,往往與姓名、肖像、形體等人格因素相聯系。這些人格因素的某些特征,具有“第二次開發利用”的價值,即將此種形象進行商品化利用的價值。他人以合理的對價受讓或許可使用該形象,其目的并不在于該形象的創造性程度,而在于該形象與特定商品的結合對消費者帶來的良好影響。這種影響能給形象所附載商品帶來廣泛的認識度,能給形象的利用者帶來一定的經營優勢。因此,筆者有理由說,形象權也是一種經營性資信權。
四、知識產權立法選擇與無形財產的制度模式
從世界范圍說,關于知識產權的立法體例大致有三種情形:少數國家將知識產權編入民法典;個別國家將知識產權單獨編纂法典;大多數國家則對知識產權采取單行立法的方法。盡管有上述立法差異,現代各國并不諱言知識產權的民事權利或私人財產權利的基本屬性。正因如此,世界貿易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在其序言中強調有效保護知識產權的必要性時,要求締約方確認知識產權是一項“私權”。
第3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一、 關于侵權行為一般條款和侵權行為一般化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涉及到一個一般化、一個類型化,實際上說到底說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陸法系侵權行為法編制的方法和英美法系侵權行為法編制的方法,現在我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大陸法系關于侵權行為一般化的最基本的做法。中國民法現在的侵權行為法的基本思路的大陸法系的思路,集中表現在《民法通則》當中關于侵權的民事責任這一部分,法律立法的思想還是大陸法系,走的還是侵權行為一般化這樣一個套路。那么什么是侵權行為一般化這樣一個民法侵權行為法的編制方法?它基本表現在侵權行為法當中首先要有一個侵權行為一般條款。大陸法系在制定侵權行為法是按照侵權行為一般化的方法來編制,它首先要有一個侵權行為的一般條款,這個侵權行為的一般條款概括了主要的或者全部的侵權行為,然后對侵權行為的具體規則再做一個規定,它對侵權行為不作類型化的規定。《法國民法典》在1804年起草的時候,侵權行為法一共是五個條文,在這五個條文當中,1382條、1383條規定了過錯侵權責任;然后在1384條、1385條、1386條規定了特殊侵權行為;這五個條文把社會生活當中形形的侵權行為都概括進去了,它的立法就是侵權行為一般化的做法。大陸法系從《法國民法典》以后,大多都采用這樣的方法來立法,大陸法系侵權行為法一般化的立法方法就是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是從頭開始往后算,我把它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比較古老的成文法,在這些古老的成文法當中,比如兩河流域等,這樣一些古老的立法,它們都規定了非常多的侵權行為法的規范,但是它們都是對具體侵權行為的描述,沒有一個概括性的侵權行為的條文,它的特點就是具體規定。
第二個階段就是向侵權行為法的一般化前進了一步,這個時候就到了羅馬法的后期,羅馬法后期關于侵權行為羅馬法有一個新的規定,把它規定叫做“私犯”。在羅馬法上出現了“私犯”和“準私犯”的概念,這就把所有具體的侵權行為分為兩個類型,一類是一般的種類叫做私犯,另一類叫做準私犯。一種是對人或財產的私犯,一個人實施了行為侵害了他人的人身、侵害了他人的財產,這個時候就要承擔責任,把這種行為歸納到一起叫做私犯,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一般侵權行為;對侵權行為雖然沒有概括的條文和一般的條文來描述這種抽象的侵權行為,但是把這些侵權行為概括到一起成為一個類型。另一個類型就是“準私犯”,準私犯在羅馬法上描述了六種具體的情況,比如說法官錯判案件、建筑物上懸掛物品造成他人的損害、學徒造成他人的損害由他的師傅來賠償、家子造成的損害要有他的父親來賠償,在羅馬法上講的私犯和準私犯盡管不是對侵權行為作出一個一般化的進展,但是向著侵權行為的一般化發展了一步,在所有的侵權行為的兩種類型中私犯以后用來概括成為一般侵權行為,是進行侵權行為一般化的一個基礎。
第三個階段就是《法國民法典》,它在1382條作了一個非常概括性的規定。《法國民法典》侵權行為法這一部分規定了一般侵權行為和準侵權行為,一般侵權行為就是對侵權行為作了條文化的、概括化的、一般化的規定,把絕大多數的侵權行為概括成一個過錯、損害、因果關系,然后只要是符合這些要求的就構成了侵權行為,按照這個條文就要承擔賠償責任。這就把具體的侵權行為統統都抽象化,抽象出一個概括的條文,拿出這個條文應對所有的侵權行為。《法國民法典》在法律發展的歷史上完成了侵權行為從具體化到一般化的過程,它創造了1382條也就是民法侵權行為的一般條款。這里面我要補充一點,1382條、1383條講的都是過錯責任原則,由過錯造成損害就構成侵權行為,這是講的侵權行為的一般化,它是從羅馬法里面私犯演變過來的,《法國民法典》侵權行為所講的準侵權行為就是來源于羅馬法的準私犯。《法國民法典》的侵權行為的一般化和準侵權行為之間的界線在那里呢?侵權行為的一般化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我自己實施了侵權行為就由自己來承擔責任;準侵權行為就是對他人的行為負責以及對他所管轄之下的物件造成的損害負責,比如父母對子女,師傅對學徒這一些他人對別人造成的損害后果,要由你來負責,就是我們所講的替代責任。然后就是自己所管轄的物件造成的損害,物造成的損害就由物的主人來承擔責任,在《法國民法典》完成了一般化這樣一個過程,同時也把侵權行為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一般侵權行為,一部分是準侵權行為。
第四個階段就是《德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把侵權行為也分為兩類,一類叫一般侵權行為,一類叫特殊侵權行為;基本上還是沿襲《法國民法典》的做法,但是《德國民法典》對侵權行為的概念的界定以及構成和法國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們講法國的一般侵權行為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有過錯,第二要有損害,第三要有因果關系;德國按我們現在的理解要有四個要件,除了法國侵權行為的三個要件以外,還加了一個就是行為違法性的要件,《德國民法典》在規定侵權行為一般條款和一般侵權行為具體的表現和違法性的表現強調三個方面:
一、違反法定義務,就具有違法性。一個人存在市民社會當中,都存在一個具體的法律關系當中,他人是權利的主體,那么你作為絕對權的義務主體,你要承擔相應不進行侵害的義務。比如財產權、所有權,他人有這個財產的所有權,其他的所有人都是他的義務人,一個人享有人身權,其他的人都有對他不得侵害的義務,都是義務主體。
二、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這一種情況和我們目前的情況來看,比如說我們的《消費者保護法》中的18條,有一個關于保護他人的法律,經營者在提供經營、銷售服務過程中,要注意他人的安全,違反了這樣的法律,也具有違法性。比如說我們在商店購物,經銷商在通道安裝了一個玻璃門,玻璃門上面沒有放置任何的標志,看起來象沒有一樣,要是顧客在購物的時候撞上去了,把頭撞壞了,這也違反了保護義務。還有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就是一個人在賓館住宿,晚上進來一個小偷偷東西,結果把這個住宿的人打死了,打死以后他的親屬就向法院提訟,請求賓館承擔賠償責任。賓館也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義務。最典型的、最可笑的就是今年上半年討論的一個案件:一個人在家里地位很低,和太太的關系強弱對比很懸殊,家里面屬于陰盛陽衰的局面,一旦和太太動氣手來,吃虧的總是他;后來有一天又和太太打起來了,被太太打的頭破血流躺在醫院住院,住院以后,太太就帶了一些東西來看他,他還挺高興以為太太回心轉意了、安慰他來了,結果到了病房以后,拿出一個瓶子里面裝的是硫酸,朝他的臉上就潑過去了,造成臉部和胸部部分燒傷,后來傷勢好了出院以后,他就憤起到法院,的被告是誰呀!不是他的太太而是醫院,他說醫院沒有保護好我的安全,所以要由醫院來賠償,但是醫院是不是盡到安全保護的義務?應當說已經盡到了,如果說他的太太來了,醫院還要進行搜身檢查,才能準許探望的話,那就變成了監獄了。這樣一些都是保護他人的一些法律,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也就構成了違法性。
三、《德國民法典》里面提到違背善良風俗,這個行為的本身來講不違法,但是他要是故意的以違背善良風俗為目的來造成他人的損害也構成侵權,也構成違法性。史尚寬經常在他的書里面提到一個事情,他說什么是故意違背善良風俗造成他人的損害,比如說有一個村莊只有一個面包房,他要是不賣給別人面包別人就會餓死,大家都以面包為生。本來賣面包這個人賣給誰面包或者不賣給誰面包應當是買賣自由調整的范圍,賣給你或不賣給他是他的權利,買賣自由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但是如果他知道不賣給這個人面包,這個人就會餓死,他如果是以故意不賣面包給別人這樣的一個方法,要造成他人的損害,也是違背善良風俗的,雖然這個行為本身不違法,但由于他故意違背善良風俗造成他人損害,也具有違法性。德國法關于違法性的問題作了這三個方面非常好的規定,具備了這三個方面的違法性造成損害,要有過錯就構成一般侵權行為。同時它又規定一些特殊侵權行為作為補充,一個侵權行為的一般條款規定一般侵權行為,然后加上其他的一些具體的侵權行為,這兩部分加到一起,就是德國法和法國法對侵權行為一般化立法方法的一個基本的表現。
第五個階段,就是60年代初《埃塞額比亞民法典》。埃塞額比亞是一個很封建、很落后的國家,有的同學可能就不禁會問,埃塞額比亞是一個既封建又落后的國家它的民法有什么可學的呀?不對,埃塞額比亞的民法典是一個非常好的民法典,為什么說它好呢!因為它的民法典是法國最偉大的當代比較法學家勒內•達維德給他們起草的民法典。大家知道法國的民法典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法典之一,也是實現民法現代化一個基本標志。法國人對法國民法典的感情是無與倫比的,至今已經一百九十八年了法國民法典沒有作大的改動,很多人形容法國民法典的一件千瘡百孔的百衲衣,但是他們還是在修修補補不對它進行根本的手術。拿破侖說我們的多少戰功隨著硝煙都可以消滅掉,但是我們的民法典永存。法國人自己也知道他們的民法典存在著問題,二百年了隨著社會的發展能沒有問題嗎!他們每每都進行小的修補,解決不了大的問題,但又不想作大的變動。有這樣一個機會起草埃塞額比亞的民法典,他們就把法國民法典的理想全部體現在埃塞額比亞的民法典當中,把埃塞額比亞的民法典當作自己的民法典來制定,所以制定得非常好。埃塞額比亞民法典在成文法國家當中侵權行為法條文是最多的,一百多條,從法國民法典的五個條文到埃塞額比亞民法典的一百多個條文就說明了侵權行為法發展變化的情況。埃塞額比亞民法典也制定了侵權行為一般條款,它也講侵權行為的一般化。但是埃塞額比亞民法典的侵權行為一般條款和法國的、德國的都不相同,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都規定了侵權行為的一般化立法方法,都有一個基本的特點就是侵權行為一般條款它概括了絕大多數的侵權行為,但還有一部分沒有概括進去,這一部分就是特殊侵權行為,把侵權行為的一般條款和特殊侵權行為加到一起才構成全部的侵權行為。但是到了埃塞額比亞民法典它的侵權行為的一般條款就把全部的侵權行為概括到一起,不再分特殊侵權行為和一般侵權行為。現在歐洲在起草歐洲統一侵權行為法,它也有一個一般條款,他的一般條款和埃塞額比亞民法典的一般條款是一樣的,也概括了全部的侵權行為。
大陸法系立法通過我所講的五個階段的變化基本上實現了侵權行為一般化的發展方向,目前為止大陸法系侵權行為一般化立法方法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另一種就是埃塞額比亞民法典,這就是大陸法系侵權行為一般化發展的一些轉變的情況。
二、侵權行為類型化
侵權行為類型化也是一個立法方法,主要是英美法的做法。英美法的侵權行為法它是一個判例法,沒有成文的法典,盡管如此在理論上來概括侵權行為以及在實務當中來處理侵權行為,它還是分為具體的類型,對侵權行為作一些類型的劃分。法官在審理具體的案件一看這個案件是什么類型,就按什么樣的規則來處理。是誹謗,就按誹謗的規則來處理;是侵害債權涉及到經濟侵權、商業侵權,就放到相應的規則中去,沒有侵權行為一般化的概念。到了英美法系國家要講侵權行為的時候,他們會講每一種具體的侵權行為,絕對不會講侵權行為一般問題。
他們的判例法具體體現在哪些類型、立法情況我簡單介紹一下;
英國法分為七種典型的侵權行為,1、非法侵入,2、惡意告發,3、欺詐,4、其他經濟侵權,5、私人侵擾,6、公共侵擾,7、對名譽和各種人格權的保護。除了這七種以外,還有第八種就是無名侵權,就是我們說的有名合同和無名合同一樣。
美國法把侵權行為分為十三種類型,1、對他人身體、土地及動產的傷害,通常在理論上叫做故意侵權;2、過失,我們講過失是一種心理狀態,他們講過失是一種侵權行為;3、嚴格責任,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動物造成的損害,一個是危險活動造成的損害;4、虛假陳述;5、誹謗,就是我們講的侵害名譽權;6、侵害的虛偽不實;7、侵害隱私權;8無正當理由的訴訟,我們講的惡意訴訟;9、干擾家庭關系;10、對有約的經濟關系的干擾,這是商業侵權;11、故意過失以外其他方式侵犯土地利益;12、是干擾各種不同保護的利益;13、產品侵權。英美法的侵權行為是按照類型化的方法來處理的,以具體的類型來考慮侵權行為的情況,這是關于侵權行為類型化基本的情況。
大陸法系在制定侵權行為法一般化這種方法的時候,其實也考慮類型化這種方法,法國和德國在講侵權行為的時候,講一般侵權行為的同時也講特殊侵權行為。在埃塞額比亞民法典當中,它規定了全部的侵權行為抽象出一般條款以后,也規定一些類型化的侵權行為,一些特殊的侵權行為還需要有特殊的規則來處理,在一般化的基礎上它也采用類型化這種方法。臺灣的民法理論上是這樣說,他講侵權行為類型的時候,先講一般侵權行為,特殊侵權行為,然后還講共同侵權行為。其實這個劃分方法不是很有道理,因為一般侵權行為和特殊侵權行為他們講到規則不同,一個是對他人的行為負責、對物件造成的損害負責,而一般侵權行為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用這種方法來劃分這兩種侵權行為應當能講出道理來,把共同侵權行為也作為其中的一種,共同侵權行為也可能是一般侵權行為,也可能是特殊侵權行為,這樣劃分從邏輯上是亂的,劃分的標準不是一個標準。臺灣有些學者在書當中把侵權行為分為三種,一般侵權行為、特殊侵權行為加上共同侵權行為,這種方法我覺得是不可取的。從我們《民法通則》在強調民事責任這一部分從117條到119條分成了四種類型,117條是侵害財產,118條是侵害知識產權,119條是侵害人身,120條是侵害人格權造成精神損害。我們中國《民法通則》當中也分為一般侵權行為和特殊侵權行為,然后用另外一種方法再把它分為四種類型。
這部分我其中主要介紹的是英美法系侵權行為法立法的基本方法就是類型化。
三、侵權行為一般化和特殊侵權行為類型化的比較、優點和缺點
大陸法系侵權行為法立法一般化這種方法有一個侵權行為一般條款,這個條款概括主要的、幾乎是全部的侵權行為。采用這樣一種方法立法最大的特點就是:第一、立法簡潔,最典型的就是法國民法典五個條文規定了全部的侵權行為,直到今天,雖然增加了一些條文,但是基礎上還是原來的五個條文;第二,能給法官創造性,無論出現任何新型的侵權行為案件,法官都可以依照一般侵權行為的規定來處理這些案件,侵權行為一般化就有這個好處,給法官一個抽象的武器,只要符合這個抽象的規定,我都可以認定你是侵權行為,不用作什么具體的規定。但是侵權行為一般化也有弊端,它需要高素質的法官來真正理解這個條文、理解它的適用方法、理解它的立法精神,出現了這方面的問題他怎樣來適用這個一般條款來解決具體的糾紛。如果個別法官素質比較低,缺乏良知,他不懂得怎么樣運用法律和這個條款,他就不能作出合理的判決。事實上中國目前法官的整體隊伍的素質應當說是不高,在缺乏高素質法官隊伍的情況之下,一般條款在適用起來就有困難。大家可能就有疑問,沒有具體條文、沒有明文規定就不敢作出判決。象這樣的訴訟不只是一件、兩件,應當有很多。但是為什么法官不敢作出判決呢?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整體法官的素質不高,最大的問題就是太概括了,真正和實踐當中結合起來沒有高素質的法官是做不到的。中國的法官習慣于有具體的規定,拿著對號入座,一看這個案件違反這項條款,就按照具體的條文去判決。這是我對侵權行為一般化這樣一個分析,我不是全面的分析只是簡單的介紹一些主要的問題。
侵權行為類型化這種方法最大的特點就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確。侵權行為分那么多的類型,來了一個案件一看是什么類型的,然后就按照這個類型去做。大家可以看一看美國侵權行為法,它規定了侵權行為的十三種類型,然后每種類型都講了具體的方法。比如舉證責任怎么處理,法官主要掌握的要點是什么,它都作了非常清楚的說明。類型清楚、章法清楚,規則清楚便于適用,便于法官操作,這就是類型化侵權行為法的優點,法官拿過來一個案件就可以對號入座,除非有新類型的案件,原來類型當中沒有規定的侵權行為,出現以后需要法官來創造,這些除外,法官就按照原來判例提示的內容完全可以判決各類型的案件。這是侵權行為類型化的一種立法的方法。
它的問題是什么?缺點是什么?就是太復雜,不象侵權行法為一般化的方法有明確的條文,拿著這個明確的、抽象的條文法官就可以創造。英美法系他們講具體的類型,法官接過案件和作出判決以前,先把一些相關的案件的判例法調出來,然后分析這個案件具體適用哪一條具體的條文,要經過一個復雜的過程。另外一個就是它的體系比較亂,大家看一看英國侵權行為法分為七種類型,美國的侵權行為法分為十三種類型,他們的分類方法要按照大陸法系侵權行為法的立法方法來分析是講不出道理的,比如說美國侵權行為法第一種類型故意侵權和第二種類型過失侵權要按照大陸法系的立場來分析,故意侵權行為和過失侵權行為加上無過失侵權行為就等于全部的侵權行為,但是英美法系歷史上就是這樣一種分類方法。所以說英美法系體系比較亂,內容比較復雜,需要高素質的法官才能掌握。英美法系類型化的方法也存在著另外一個問題,大陸法系法官可以依照一般侵權行為的條款來創造性的適用法律,英美法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他們怎么樣來解決?除了他們規定的以外,再出現新的類型侵權行為怎么辦?英美法是最有辦法解決的,法官可以造法,再創造出一個新的判例,他們是用這種方法來補充立法不足的問題。
這部分我給大家介紹了一般化侵權行為法立法方法和類型化侵權行為法立法方法二者之間的差別和優點以及存在的問題。
四、中國的侵權行為法怎么辦
中國侵權行為法到底是走一般化的道路還是走類型化的道路?
象剛才分析的那樣,如果走一般化的道路那是我們的正統,大陸法系成文法國家應該走一般化的道路。但是大家又特別期望在立法的時候,一定要具體、明確、適用。大家經常講的能不能制定一個親民的侵權行為法。親民的侵權行為法最好規定的比較仔細、內容比較具體、法官也容易適用。
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來制定侵權行為法大概是個親民的侵權行為法。如果用三句話來概括就是,大陸法系為體,英美法為用,然后轉換吸收司法經驗,這三句話要是實現了大概能夠制定一個比較好的侵權行為法。大陸法系為體,怎么為體?要堅持大陸法系成文法的傳統,然后接受大陸法系侵權行為法嚴密的體系和理論,三要有一般條款。我想有了這三點大概體現侵權行為法大陸法系為體的這樣一個內容。以英美法系為用。在堅持大陸法系體例的基礎上,大量的借鑒英美法系關于侵權行為類型化的做法,在制定侵權行為一般化的同時也要規定侵權行為的類型,規定成為多少種侵權行為的類型,每一種侵權行為類型應當怎么去判斷,有什么樣的規則,也要把它規定出來,這樣就把英美法系類型化的侵權行為法的優點就借鑒過來了。此外還要大量的吸收司法實踐經驗。
從1986年至今,在這十幾年的時間中國的法律應當說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前幾天,臺灣一個高等法院的法官來北京我們聊了很長時間,他也承認中國大陸的民法在十幾年以前根本沒辦法和我們交流,因為我們也沒有什么基礎。在十幾年之后,現在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站在同一個等級上來對話。這就說明了我們在這十幾年中有著非常大的變化和發展,這樣大家就有共同對話的基礎。在這十幾年當中理論上有重大的發展,在實踐上也有非常大的進展。比如說大家現在再一起學習民法,你可以講什么是人身權,什么是財產權,你都可以講的很清楚。在1986年以前,你講人身權,大家懂嗎?你講隱私權,那個時間哪有隱私權這個概念,你要向黨坦白,對他人要忠誠,怎么可以隱瞞起來呢?觀念都不一樣。但是這十幾年的發展,大家對民事權利有著深刻的認識,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的權利不能受到侵犯,受到侵犯就知道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權利。在司法實踐當中積累的經驗也是非常寶貴的,所以在制定侵權行為法的時候,應當在實踐當中積累的豐富經驗都把它吸收進來。
我想我們在制定中國侵權行為法有大陸法系基本的基礎,把英美法系當中好的東西借鑒過來,再把我們實踐當中積累的經驗加進去,這樣的侵權行為法應當是一個比較全面的法律。我想這應該是一個理想,應當努力的去做。
第4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關鍵詞]人格權,一元理論模式,多元理論模式,權利的邊界,民法典編纂
一、問題的提出
在民法發展史中,法典編纂往往是各種理論的產生、發展和相互角逐的重要時刻。近來民法學界對人格權理論問題的高度關注以及圍繞人格權制度而展開的學術辯論就具有這樣的背景。①但是,在論戰中過于急切地得出自己的方案和反駁別人的方案,往往會導致理論說明的膚淺和空泛,所謂的學術論戰淪為一種“表態”和“站隊”性質的說法,這實際上不會推動理論研究的深入。為了避免這一弊端,就特別有必要在理論論戰中注重研究方法的嚴謹和說理的通透,只有這樣才能夠讓人格權的理論研究在民法典編纂中得到切實的發展和深化。人格權的基本理論研究自19世紀末期發軔于德國法學界以來,已經有了100多年的歷史,逐漸形成了自成格局的理論體系,有相應的論述路徑和分析方法。在這一研究中筆者就試圖運用這樣的路徑和分析方法對其理論脈絡進行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嘗試對中國的人格權立法問題給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形象地說,人格權理論的基本入口由一個選擇題構成:“存在一系列人格權還是一個統一的人格權”?答案可以是前者:“存在一系列人格權”,也可以是后者:“存在一個統一的人格權”。這兩個不同的答案就構成了人格權的兩種基本理論模式:多元模式和一元模式。
馬上有人會問:這有什么特殊,這不就是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的具體人格權和一般人格權的區分嗎?問題就在這里。不管是由于誤讀還是由于不了解,我們所習以使用的術語“具體人格權”和“一般人格權”在西方的法學語境中具有一種很特殊的,并沒有被我們所真正認識的內涵。在術語移譯中出于漢語的語用習慣所選擇的“具體-一般”這樣的對偶修辭法,導致我們對這兩個術語產生了望文生義的理解:認為這二者是具體與一般的關系,可以相互并存而不存在沖突,等等。其實這些說法都經不起推敲。在民法中,任何一種“權利”(dirittosoggettivo)都有其明確的邊界和內涵,這既為權利保護機制所要求,也是權利本身的一種基本特征。從權利的內涵-受到法律保護的利益來看,私法不可能對同一種利益采取賦予不同類型權利的方法來進行重疊式的保護。這不只是因為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而且是為了避免權利體系以及與之相關的請求權規范的混亂。難以設想,一種“權利”(甲)被包括在另外一種“權利”(乙)之內的同時,甲仍然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獨立的“權利”。我們對“所有權”這一術語的使用方法正反映了這一點。雖然在私法中也存在使用權、用益權等權利類型,但是當它們成為所有權的內容時,我們說的是所有權中包括了使用、收益等權能,而不是說所有權中包括了使用權、用益權等權利。如果某所有權人被妨礙使用自己的土地,是他的“所有權”受到侵害,而不是“使用權”受到侵害。②因此不能說所有權與使用權、用益權之間存在著一種一般與具體的關系,因為從民法規范的邏輯來看,所有類型的權利都是相互平行和獨立的。③同樣的邏輯也應該運用于人格權體系的分析中。如果接受一般人格權與具體人格權并存的說法,比如說,名譽權構成一種具體的人格權,那它與一般人格權的關系如何界定?如果它構成一般人格權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在一般人格權中就已經包括了名譽權所試圖保護的利益,當名譽受到侵害的時候,是一般人格權受到侵害,受害人可以援引一般人格權進行主張,這樣就沒有必要存在一個特殊的名譽權,名譽只是一般人格權保護的人格利益中的一個方面而已。如果我們認為名譽權獨立于一般人格權,也就是說,法律規定在名譽受到侵害的情況下,受害人必須依據名譽權的規定提出訴求,而不得依據一般人格權提出訴求,那么我們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一般人格權的客體中不包括名譽利益。④同樣的說法也可以針對所有的具體人格權,經過這樣一系列的排除之后,一般人格權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是一個一般性、概括性的權利,充其量只是一個補充性的權利。
這樣的推理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所謂一般人格權與具體人格權,在其原來的語境中,指的就是兩種人格權的基本理論模式。一元模式認為只有一個統一的、以整體的人格利益為客體的人格權,那些具體的人格要素,比如姓名、肖像、名譽等只構成這個具有統一性的人格利益的一個方面,因此也處于這個統一人格權的涵蓋之下。多元模式則認為不存在一個以統一的、整體的人格利益為客體的人格權,存在的是一系列的具體的人格權,這一系列的人格權保護的是特定的、具體的人格利益,正是這些作為客體的人格利益的不同構成了不同的人格權存在的基礎。這兩種理論模式產生于不同的歷史環境,有各自的價值取向和優缺點,在歐洲主要國家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⑤這正是下文所要詳細論述的內容。
二、多元理論模式與一元理論模式的產生與發展
(一)多元理論模式:民法傳統分析框架下的產物
從產生的時間來看,人格權理論上的多元模式是一種依循了傳統分析框架的理論,而一元模式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的新生事物。這里首先論述前者。
私法層面上的人格權理論研究始于19世紀末期的德國法學。⑥法學家基爾克(O.Gierke)在1895年出版的《德國私法》一書中,用了近200頁的篇幅詳細地論述了“人格權”(Pers nlichkeitsrechte)這一權利類型,認為它涉及生命、身體完整、自由、名譽、社會地位、姓名和區別性的標志以及作者和發明者的權利等。⑦這一著作被歐洲法學界認為是人格權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基爾克理論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他分別探討了人格在各個方面的具體體現(可以認為是一種多元論模式的起源),同時還在于他對人格利益的雙重性質的確認:他認為人格既具有精神性的價值,也具有物質性的價值。⑧
在私法體制中塑造人格權這一權利類型,在一開始就遇到一個法律邏輯上的難題。問題來自于人格利益的特殊性質與民法上的權利客體之間的兼容性。傳統民法中的權利構造的原型是所有權,它是一種財產性的權利,針對的是一個外在于主體的客體,權利主體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支配客體。⑨但是人格權所要保護的利益卻與此很不相同,人格利益并不處于外在于權利主體的客觀世界中,相反,它處于該主體自身之中,與主體內在地相結合,表現為主體獨特的身體、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經歷等等。⑩
由此產生的問題是:人格權的客體如何界定?按照形式邏輯的推理,既然人格利益內在于主體自身,那么人格權就是一種針對自己的權利(iusinseipsum)。這也就意味著人格權的主體與客體是同一的。但是,一種自己針對自己的權利從邏輯上來講是說不通的,[11] 而且在實踐中也會產生問題:如果說人格權的客體是主體自身,這也就意味著主體可以自由地處分其自身,甚至是自殺。既然自殺是不被允許的,那么也就必須否認存在著一種針對自身的權利。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傳統民法理論在很長的時間內拒絕人格權這一范疇的存在。[12]
難題是這樣得到解決的:擴大傳統民法概念中的“財產”(bene)范疇的內涵,無論是外在于主體,還是內在地與主體相結合,只要能夠滿足主體的某種需要,都可以被認為是一種財產(omniabonameamecumporto),并且即使財產是內在地與主體相結合也不意味著它不能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因此需要法律的外在保護。所以,人格利益可以采用賦予權利來進行保護的形式,人格利益可以成為權利的客體。[13] 在這樣的分析中并不存在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相互重合的問題。權利主體是一個法律上的抽象概念,是法律上抽象的人(Persona),但是人格權的客體針對的則是一個具體的人(Mensch,Uomo)的內在于自身的利益。[14] 人格權針對的不是一個人的自身的身體,而是針對一系列的典型的、個別性的、具體的人格利益。這種從受到保護的典型的、個別的人格利益的角度對人格權的理解,與傳統的權利理論相一致。在這樣的分析中,事實上就已經顯示出了多元論模式的輪廓。從理論邏輯來看,可以認為多元論模式是民法傳統分析框架下的必然產物,也自然是與傳統民法理論體系相契合的。
在傳統民法中,一種受到保護的利益要獲得“權利”這樣的民法制度上的外衣,一般要對它進行這樣的處理:(1)確定需要設立的權利類型的內涵和邊界,這就是確定該權利的客體的過程。根據利益法學的理論,這也是確定該權利所保護的利益的邊界。(2)將這樣的劃界結果反映在一定的法律規范條文中,使有關權利具有規范層面上的依據。由于受到保護的利益是典型的、具體的,所以保護該利益的權利也是典型的和具體的,它具體就表現為相應的確權條款以及救濟條款。
這種思路反映了傳統民法在法律價值上的選擇傾向。為了確保法律的確定性以及可預測性,任何行為或者利益的邊界都必須是確定的、可預測的。法律設立權利來保障個人利益的同時,限制了別人的自由空間,因此,只有當設立的權利的內涵和邊界是確定的,個人與他人的自由邊界才可能是清晰的,也只有這樣才可能產生一種具有可預測性的社會秩序。[15] 因此,一種內涵不確定、客體不清晰的權利是需要避免的。這種思路也反映了傳統的立法和司法職能分離的法制原則。一種內涵在立法上不明確的權利類型,勢必要求在司法過程中由法官來進行具體的判斷,這不符合傳統的立法-司法分離的原則。
以這樣的框架來分析人格權問題,必然要求建構一系列的、以特定的人格利益為保護對象的人格權。這些人格權所指向的客體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典型性,并且與一定的社會觀念相對應。這樣的對象包括姓名、肖像、名譽等。
不可否認,這樣的理論導致以下的后果:(1)人格權的客體范圍上的限制性傾向。根據前面提到的權利的典型性以及所保護的利益的典型性的特征,只有那些被典型化了的人格利益才能夠得到賦予權利這種方式提供的保障。那些剩余的、非典型的人格利益因此就處于人格權制度的保護范圍之外;(2)人格權的類型和范圍上的實證法傾向,也就是說,民法對人格權的保護以民法規范明文確認有關權利的存在為前提,對于法無明文規定的人格利益,在私法制度中不采用賦予權利的方式來進行保護。對于這些特征,筆者在下文將它們與一元論模式進行比較的時候再進行細致的分析。
(二)一元理論模式:憲法原則在民法體系中的衍生物
一元理論模式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格權理論中沒有所謂的一元論模式。在《德國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中都沒有條款規定一種統一的一般人格權。《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從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原則出發,為了追求法律規范的確定性,特別注意避免在法典中涉及一些內涵不容易確定的問題。[16]
就具體人格權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德國法并沒有提供一個完整的權利體系。《德國民法典》第12條規定的姓名權是《德國民法典》中惟一被明確確認了的人格權。另外一個特別法上規定的人格權是《德國藝術家和攝影家作品著作權法》第22條所規定的肖像權。至于《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四種典型利益,即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在受到侵害時可以給予損害賠償的保障,這并不是說,有一種生命、身體、健康和自由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它們不能與法律承認的人格權并列。《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甚至沒有明確指出人的名譽,因此,名譽原來只是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2款結合刑法中有關侮辱和惡意誹謗的規定而間接地受到保護。從這個角度看,具體人格權的規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民法中是非常粗疏的。
一元理論模式發展的最重要的推動力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于1949年通過的《基本法》。出于對納粹時期踐踏人權的極權統治的憎惡,《德國基本法》特別強調對人的基本價值的尊重和保障。該法第1條第1款規定,人的尊嚴不得被侵犯,保護人的尊嚴是國家的任務。第2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都有權自由發展其人格;第2款規定,任何人都有生命和身體完整的權利。第5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都有通過語言、文字和圖像的方式自由地表達和傳播其思想的權利;第2款規定,思想和信息自由不得造成對名譽權的損害;第3款規定,藝術、研究和教育是自由的。
其實不僅是德國,在歐洲別的國家也在憲法層面上強調對基本人權的保護。擺脫了法西斯統治的意大利,在1947年制定的新憲法中也確認了公民的一系列“不得被侵犯的權利”(dirittiinviolabili)以及尊重人格的原則。[17] 這種趨勢也具有國際性的特征。1948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都是其明確的表現。這種現象甚至被歸納為人格權的一種憲法化和國際化的趨勢。[18]
但是,有的學者因為這樣的說法就聲稱人格權是一種憲法上的權利,不是民法所能夠確認的。[19] 這樣的觀點其實是一種誤會。我們仔細考察《德國基本法》和《意大利憲法》有關條文的表述,所謂人格權的憲法化趨勢,更準確地是指憲法中出現的強調人格利益保護這一憲法原則和精神。這樣的原則,通過憲法(根本法)與民法(普通法)之間的上下位關系,可以滲透到整個民法的立法、司法和法律解釋活動中。至于民法以何種立法技術來落實這一憲法原則,那是在民法體系內部進行的事情。我們將看到,人格權基本理論上的一元論模式就是德國民法學界提出的一種解決方案。憲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在憲法文本中構造出圍繞某一民事權利的民事制度體系(它一般要包括概念構成、客體認定、救濟方法等)。雖然我們在公法和私法層面都同時使用“權利”這一概念,但是它們之間并沒有多少共通性。憲法上的權利概念更多地指向的是對國家權力的行使方式的限制(比如,憲法規定公民有健康權、受教育權、勞動權等,這些憲法規則指向的是國家有義務通過一定的財政資源、立法手段來使公民得到有效的治療,獲得教育資源,擴大就業機會等),但是,不存在與這些“憲法權利”相對應的可以供普通公民使用的普通的訴訟程序(普通公民不能因為憲法規定了勞動權就可以起訴要求國家給分配一個工作)。[20] 而民事權利則不同,它指向的是他人的確定的義務,并且有一種民事權利,就必然有一種與之相對應的采用普通訴訟程序的救濟方法。從這個角度看,辨析一種權利是民法上的權利還是憲法上的權利沒有什么意義。它們之間的聯系更多的是表現在,對民法基本原則的解釋要根據憲法的精神來進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法官們發現自己處于這樣的一個處境中:民法典中以權利形態進行保護的人格利益的類型十分狹窄;通過侵權行為進行間接保護的大門又不對一些非典型的人格利益敞開;指望立法對民法典的規定進行干預顯得遙遙無期;但是《基本法》確定的尊重人格的原則又必須在司法活動中得到貫徹。在這樣的情況下,法官發揮了司法能動性,試圖來彌合社會需要與立法滯后之間的鴻溝。為了獲得判決的說服力,德國法官援引德國《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作為判決依據,實現人格保護的目標。這是一個精彩的創造性司法的例子,其中經過已為中國學界熟悉,在此不再重復。[21]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德國民法學理論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人格權的一元論學說。一元論模式仍然借用傳統的民事權利的制度構造,認為人格權不是一組以典型的人格利益為客體的權利,而是一個統一的、普遍的權利類型,它被稱為一般人格權,它的客體所指向的是無所不包的人格的整體。那些個別的人格利益,比如說肖像、名譽、姓名等,只是這個整體人格中的一個方面,人格利益的所有方面在這樣的一個權利范疇中得到完整的、全面的保護。
馬上可以看出,這一模式以一種絕對的方式在民法上落實了人格保障的憲法原則。與前面提到的多元理論模式相比,它具有這樣的特征:(1)放棄了人格利益確認和保護上的典型性原則,從而潛在地將人格權的客體進行了巨大的擴展。[22] 因為在這樣的理論模式下,這個統一的人格權的客體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內涵和邊界,一切取決于如何解釋“人格利益”這個概念。(2)它以犧牲法律的確定性為代價,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實證法在人格利益保護上的難以避免的滯后性。在這樣的理論下,不會存在某種人格利益在民法的保護上“法無規定”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認為它克服了法律形式主義和權利實證化的傾向。(3)因為它放棄了一種必要的事先的規范構成,因此在人格保護的問題上,它永遠要依賴于司法活動中的法官對案件的個別解釋和判斷。換言之,這一領域不可避免地將呈現出判例法化的傾向。
在建構了這樣一個統一的一般人格權的范疇之后,必然要拋棄原來的多元論模式。因為與其說這些仍然是獨立的權利,不如說它們只是一般人格權的一些要素,對它們的考慮只是一種依據一般人格權的思路所進行的個案考察而已。相對于一般人格權,這些曾經作為獨立的權利類型的具體人格權,已經失去了法律上的獨立性。[23]
經過戰后半個世紀的發展,現在德國法律界認為一般人格權已經成為法律體制中的一個確切無疑的部分,屬于“法律認可的其他權利”,因此,某些涉及一般人格權的司法判決就只引用《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而不再援引《德國基本法》的有關原則了。[24] 但是,習慣了嚴謹的法律邏輯的德國法學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不斷嘗試為這樣的一個一般人格權尋求一個實證法上的規范基礎,也就是說將一般人格權納入民法的實在規范體系中,但是直到現在這一嘗試仍沒有獲得成功。[25]
因此,我們在談論一般人格權的時候,必須注意,這樣的一個權利范疇,嚴格來講,即使在它的發源地也還沒有得到民法規范層面的確認,它只表現在一系列的司法判決和對這些判決進行理論整理的法學家的論述中。
三、對比與選擇:多元模式與一元模式
從前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在人格權的基本理論上,無論是多元模式還是一元模式都形成于一定的歷史時期,對應于一定的社會觀念和法律思想,因此都有其合理性的內核。這里所進行的對比和分析,并不是要判斷哪一種模式正確、哪一種錯誤,而是通過對比分析來進一步揭示它們的內涵。只有在對二者的理論內涵全面了解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進行正確的衡量,作出符合我們需要的選擇。
(一)個體權利與他人自由的邊界
正如德國有些法學家所指出的,德國司法界和學術界以《德國基本法》宣告的尊重和保障人格的憲法原則為依據,通過判例法發展出一般人格權理論,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對以前的立法者頑固地拒絕承認一些基本人權的傾向的激烈對抗。[26] 這種理論態度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社會輿論的強烈影響。
人格權的一元理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對人格利益在民法層面上的保障采取了一攬子解決方案。在這樣的理論中,人格權的客體-人格利益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一個開放的整體,它的內涵可以根據不同時代的觀念進行具體的解釋。因此,如果采用這樣一種理論模式,永遠不會存在民法層面上的人格利益保護的遺漏問題。相比之下,多元理論模式卻顯得相對保守,因為在這樣的理論中,只有那些具體的、典型的、被民法明文規定的人格利益才得到以賦予權利方式給予的保護,因此這是一種封閉的、固定的理論模式。由于立法不可避免的不周延性和滯后性,總是難免出現一些遺漏以及新的人格利益不能及時被歸納提煉為一種典型的權利而得不到保護的情形。正如卡爾?拉倫茨所指出的:“人們終究不可能在范圍上通過劃界將所有人性中值得保護的表現和存在方面無一遺漏地包括進來。因為人們不可能無遺漏地認識到可能出現的所有沖突。”[27] 這是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在遭遇到法典法的立法方式時無法避免的一個遺憾。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面性的特征。一元論模式也表現出明顯的缺陷。在社會生活中,對某個人的自由和利益的保護總是以對他人的自由和利益的限制為代價。一元論模式在實踐上的結果就是以整體的人格利益為客體形成一個針對所有其他人的概括性的絕對權,他人負有消極的不作為的義務。[28]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絕對權比喻為一種法律上的保護性屏障,對于這種性質的屏障,我們并不陌生。在物權法中,特別是在所有權制度上,也存在類似的保護性屏障。但是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個具有絕對權性質的一般性人格權與一個一般性所有權在界定權利邊界上所遇到的問題是根本不同的。[29]
對于一種針對外在的物而建構的權利來說,它所設立的自由與利益的邊界是相對清晰的,因為物是客觀的物質性存在,它的邊界基本上就是它在空間中所占據的范圍。正常的社會成員面對“不得侵犯他人所有權”這一規范,根據直觀的理解就可以知道這種權利的邊界在哪里,因此可以明確地預見自己的行為在法律上的后果,不太容易“誤踩雷區”。[30]
但是,對于“人”來說,情況就要復雜得多。因為人格權保護的利益不限于人的身體空間范圍,它還涉及人的活動在外界的投射、人的獨特心理感受。對人的侵犯不只是指侵犯人的軀體所占據的空間,也包括侵犯人的心理。由于人性的特征,人有生理的痛苦,也會有心理的痛苦。一組發表于受害人千里之外的文字并不觸動受害人一根毫毛,但是也許會導致其極度的精神痛苦。所以,大多數的人格權規范(針對身體保護的規范除外)所設立的邊界只是一種抽象的邊界,由這樣的規范建立起來的保護性屏障也是無形的、不直觀的。如果說以具體的、典型的人格利益為保障對象的人格權在進行權利類型化的時候借助了普遍的社會觀念(比如說一般的人都能夠認知名譽、隱私之類的典型人格利益),還可以使社會大眾從這些具體的規范中獲得相對直觀和清晰的對自己行為后果的預測,但是一個抽象的統一的一般人格權卻幾乎完全取消了進行這種預測的可能性。面對“不得侵犯他人人格”這一禁止性的規范,如果對這樣的人格內涵又沒有一個哪怕是相對具體的界定,[31]這樣的一種權利即使它是出于保護個體的自由和利益的目的而設計,它在實踐上的效果卻是導致所有人的自由和利益處于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中。
由于這樣的原因,有學者認為一元理論模式的支持者雖然受到了保護人格思潮的影響,卻簡單地對人格權采用了與所有權相同的處理方法,因此對于人格權與人性的獨特屬性之間的聯系關注不夠,對于蘊涵在人格權中的人性的多樣性需求與蘊涵在財產權之中的同質性的經濟需求之間的差別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32]
(二)人格權類型化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一元模式批評多元模式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對人格利益進行類型化的劃分是很困難的, [33]因為人格-它被一元論者解釋為使人成其為人的要素的總和以及作為它的承載者的人本來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不應該被看做是各種物的結合。而且即使進行類型化的劃分,由于立法者認識能力的局限性,也會產生許多的遺漏。
但是,多元論模式的支持者認為,對人格利益進行類型化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這就涉及二者對人格利益的看法上的根本分歧。多元論者認為,至少就民法層面而言,人之成其為民法上的人是一個已經由民事主體制度解決了的問題。人格權制度不是一個指向民事主體的資格構成的制度,因此人格權不是一種“針對人格的權利”(diritto alla personalita), [34]而是涉及人的社會性存在中所產生的需求的滿足問題。這種需求的滿足就表現為一定的人格利益。因此,并不存在一個先驗的整體的人格觀念,存在的只是一些具體的、產生于一般社會觀念,也受到一般社會觀念制約的人格意識,以及與這種意識相對應的人格利益的觀念。基于這樣的考慮,對人格利益進行類型化是可能的,因為它畢竟有一般的社會意識背景。
但是,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對人格利益進行類型化的保護是必須的。前面已經提到,從法律調整技術的角度看,對人格利益進行明確的劃界,有利于適用法律,提高法律的穩定性。這是一個方面,另外的理由在于,人格利益的保護涉及的問題非常復雜,不同的人格利益的性質和邊界都存在很大的差別。[35] 我們當然可以無條件地保護自然人的人身不受侵犯,但是在涉及名譽和隱私的問題上則要認真地考慮它與出版自由與公眾知情權的協調問題。因此不同性質的人格利益的保護需要法律上更為精細的調整。同時,傳統的人格利益觀念也在發生變化。當我們談到人格利益的時候,傳統的觀念主要考慮的是一種消極的不被他人侵犯的利益。人格權的傳統理論也反映了這樣的觀念,認為人格權具有不可轉讓性之類的特征。但是,社會觀念已經在發生轉變,人格利益在某些方面已經包含了一個積極的方面,也即利用它來獲取經濟利益。[36]這特別表現在對一些公眾人物的姓名權和肖像權的商業利用中。[37]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法的任務就不只是保護人格權不被侵犯的問題了,而是也要承認、調整和保護這種合理的商業利用。在遇到這一情況時,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出現了:如何來界定這種交易活動的客體?對多元模式來說,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它們涉及的正是某種人格權中典型化了的人格利益,但是對一元模式來說,問題就不太容易解決。
類型化的要求還來自于對不同的人格利益的民法保護方法并不相同。因為不同的人格利益來自于人的不同社會性存在所產生的需求,因此對不同的人格利益的侵害形態也是不同的,民法必須因應這樣的差別,對不同的人格利益施加不同的保護方法。即使采用同樣的保護方法,也要具體體現出法律上的利益衡量。比如,同樣的停止侵害的救濟,對于侵犯身體的行為來說,是停止一個行為,但是對于侵犯名譽的行為的禁止,對于出版業來說,就意味著禁止出版或者銷毀出版物的命令。如果沒有對救濟所要針對的利益的性質和特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那么也會導致適用救濟方法上的隨意和不可預測性。如果涉及人格受到侵害的損害賠償,問題則更加突出。因為人格利益既有財產性的方面,也有精神性的方面,這也就意味著人格利益的損害既可以是物質性的損害,也可以是精神性的損害。這二者在認定損害的存在、估算損害的程度上都有巨大的差別,對此民法必須針對具體的人格利益的特征和相應的損害形態來確定賠償方法。一元理論模式對此根本無法給出一個統一的答案。雖然可以辯解說,一元理論也要考慮具體的人格利益以及具體的侵害形態來進行具體的調整。如果這樣的話,那么一元論試圖確立的那個統一的人格權范疇有什么實踐上的價值呢?
(三)立法的取向還是司法的取向?
在這一方面,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在一元理論的起源地-德國,無論是在憲法文本還是在民法典或其他民事法律的文本中,都沒有明確規定一般人格權這樣的權利范疇。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德國法院運用《德國基本法》中確立的人格保護的憲法原則,進行創造性司法而保護一些新類型的人格利益的判例。一般人格權這樣的范疇只是法學上對能動司法的成果進行論證和說明的理論模式。
雖然德國的法律實踐中已經確認這樣的司法創造的結果,但是它仍然沒有獲得立法規范層面上的確認,一元理論模式仍然是建立在司法造法的基礎上。在這里撇開立法與司法的職能分離的政治原則不去討論(因為筆者認為這一政治原則與民法層面上對人格利益保護的關系不大,正如法典法和判例法都可以用來保護民事權利一樣),只討論這樣的解決方案所需要的特殊的法制環境。
因為抽象的人格利益需要根據具體的案件來進行解釋和確認,所以以司法的取向來落實對人格權的保護是一元理論模式的一個必然后果。德國法學家清楚地認識到,一般人格權的主要問題在于它的不確定性。因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早就指出,在對一般人格權作界定時,必須“在特別的程度上進行利益權衡”;聯邦國最高法院的另一項判例則表達得更為清楚:“一個人的一般人格權與另一個人的一般人格權具有同等的地位,一個人自由發展其人格恰恰旨在謀求超越其自身范圍的發展。考慮到這一事實可能產生的沖突,在發生爭議時,必須進行界定,而在界定時,利益權衡原則必須具有決定性意義。”[38] 如果這樣的利益衡量沒有一個形式上的法律規范的標準,那么法官就承擔著進行利益衡量的重大責任。
我們當然不能臆斷法官會濫用這樣的權力,但是如果沒有司法判決自我論證的深厚傳統,沒有學理對司法判決的密切關注甚至是苛刻的評判,更主要的是,如果法官根本不理睬來自法學共同體的其他部分的意見,那么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來懷疑這種方案的可靠性和安全系數。如果我們沒有所有這些前提條件,我們就不得不依靠傳統的“合法性”原則去制約司法權的可能任性。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把那些能夠確定的盡量在立法上給確定下來。這正是傳統的多元理論模式的出發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在人格權的保護問題上的這一發展趨勢并不說明德國法制產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50多年來,德國法學界曾經三次嘗試在民法典中修改和補充關于人格權的規定,為一元論模式尋求一個實證法上的基礎。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提出一個叫做“重新整理關于人格權和榮譽的民法保護”的法律草案,建議修改《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采用這樣的表述:“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的人格,或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的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的人必須賠償由此導致的損害。”同時廢除《德國民法典》第825條,簡化第824條,在第847條增加一項關于侵害人格權的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在第12條中增加一系列的關于人格權的各個具體方面的規定。這一草案受到大眾傳媒的猛烈抨擊,被認為會嚴重影響新聞自由,沒有被采納。在20世紀70年代的末期又進行了一次嘗試,修改的方案與前一種方案大同小異,也沒有獲得成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又進行了一次沒有結果的嘗試,這一次的主事者是聯邦德國司法部,修改的理由是,在這一領域過于依賴個案判斷的方法,而且沒有能夠將傳統絕對權的規定與一般人格權的規定區別開來。為此,提出的方案是修改《德國民法典》第823條以下的規定,并且在第825條規范有關侵害人格(Pers nlichkeitsverletzung)的問題。草案的內容是這樣的:“(1)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人格的人要賠償由此導致的損害;(2)對于人格的侵害只有根據對有關利益和財產的權衡后也表現為一種侵害時才具有不法性。在進行權衡的時候必須考慮侵害的方法、原因和動機以及侵害所要追求的目的與侵害的嚴重程度之間的關系”。[39]
第三個方案雖然失敗但無疑相對更為合適。不過,從其表述中我們還是看到,即使這一草案成為法律條文,實際上并不能對個案性的解決方法有什么實質上的改變。因為它的內涵仍然是非常不確定的,司法之路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德國的立法者不想多此一舉地修改現行法律。
(四)如何對待一些非典型的人格利益:兩種模式的差別
的確如此具有戲劇性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人格權理論上的兩種基本模式的對立已經是一個久遠的話題,現在仍然歷久彌新,這一方面是因為學者們對理論思辨的愛好,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不同國家的法學家在考慮這些問題時所面臨的制度環境并不相同。一元論模式在德國具有壓倒的優勢地位。[40] 但是在法國,這一理論模式則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在那里多元論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41] 在意大利,理論和判例的態度一直處于搖擺之中,但是多元論占據優勢地位。[42]
有學者認為,這兩種模式的對立可以概括為:在侵犯他人人格的問題上,是法無明文許可即禁止,還是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43]一元論模式以一般的方式設立了禁止侵犯他人人格利益的禁令,因此屬于法無明文許可即禁止,而多元論模式以列舉的方式設立了禁止侵犯他人人格利益的禁令,因此屬于法無明文禁止即自由。通過這樣的對比把二者之間的差別進行了戲劇性的渲染。
但是,二者之間的差別真是如此具有戲劇性嗎?如果的確可以進行這樣的歸納,那么我們甚至要來認真考慮多元理論模式的理論用意了。為什么如此頑固地試圖縮小人格權制度保護的范圍?為什么只保護那些典型的人格利益,而置非典型的人格利益的保護問題于不顧?不過,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實際上,大量的研究已經揭示,現代的民法典已經通過一定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的程度上放棄了原先的形式主義的法律觀。民法對不同利益的保護機制是多樣的。賦予權利只是保護方式的一種,它當然是最完備的保護。但是除此之外,仍然有其他的機制來對一些不表現為權利的利益進行直接的或間接的保護。比如說在侵權行為體制上如果采用概括的非典型化的侵權行為模式,那么許多非典型的人格利益也就可以受到侵權行為體制的有效保護。民法對行為的調整也不僅僅依據實證主義的“合法性”概念。在民法中,對行為的正當性的判斷標準不只是機械的合法性標準,也有彈性的誠實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則。所以不能說多元理論模式就意味著“法無禁止即自由”。如果某一涉及他人人格利益的行為違反公序良俗原則,它仍然是要被禁止的。通過這樣的方法也可以說是間接地保護了一種非典型的人格利益。面對這些一般條款,審理個案的法官也要發揮能動司法的功能,根據時代的觀念,通過適用民法中的一般條款和一般原則來保護一些非典型的人格利益。
從這個角度看,多元模式其實并沒有否認保護非典型的人格利益的必要性,只是訴諸其他的民法保護方法而已。在保護人格利益的態度問題上,兩種模式不存在戲劇性的對立。
至于多元論的支持者為什么仍要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就涉及更深層次的例行案件和疑難案件的劃分問題。從最絕對的意義來說,立法不可能預見社會生活的所有問題,因此,法無明文規定的“疑難案件”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通過立法活動對典型問題的規范,可以在最大的限度內將絕大多數案件轉化為“例行案件”,也就是說法官只需要根據法條進行形式性的推論就可以得出結論,而不必總是進行個案判斷。這既符合思維的經濟性原則,也有助于節約司法資源,而且能夠通過“例行案件”建立社會大眾穩定的法律預期。
在涉及人格利益的保護問題上,一元模式在相當的程度上模糊了“例行案件”與“疑難案件”的劃分,過于寬泛地授權法官進行個案的衡量(前面提到的《德國民法典》的第三個修改方案就是一個證明)。堅持多元理論模式實際上也就是仍然堅持“例行案件”和“疑難案件”的劃分,讓那些涉及典型的人格利益-涉及具體人格權的案件成為“例行案件”,限制法官進行個案衡量,讓那些涉及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案件成為“疑難案件”,允許法官根據法的一般原則基于利益衡量來進行靈活的保護。只有在這一模式下,法的適用上的“禁止向一般條款逃逸”的原則才是有效的。這一原則的深層用意是對法官運用一般原則來處理“疑難案件”施加更嚴格的控制。[44]
四、兩種理論模式與中國的人格權立法
如果能夠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所面臨選擇的性質和意義,做出合適的選擇就不會太難:適合于我們的選擇是多元理論模式以及與之相應的在立法上規定一系列的具體人格權類型。主要的理由如下:
(一)立法時代的考慮
我們正處在一個立法的時代甚至是更大規模的法典編纂時代。立法的時代就應該優先考慮采用立法的技術來解決問題。要形成一個富有邏輯性的權利體系,必須借助于立法。從立法可以借鑒的制度資源來看,人格權制度經過20世紀后半期以來的巨大發展,積累了許多實踐經驗,可以為建立一個相當完善的人格權權利體系提供借鑒。
(二)國情的考慮
一元理論模式對高質量的司法階層的要求以及法律共同體的良性互動,這些我們并不具備。更重要的是,也許在中國,民法典中的一系列具體人格權的規定,其目的并不在于限制司法的任性,而更多地在于一種人格保護的理念在民法上的具體闡釋和落實。通過憲法確定人格保護的憲法原則,然后通過合憲性審查機制落實到民法層面,這樣的機制對我們也許還過于遙遠,那么更為現實的選擇是通過民法保障的方法,為人格利益的保護提供明確的規范基礎以及與之相應的普通民事訴訟程序保障機制。我們的國情是,在中國,與其抽象地拔高某種權利(說它是什么憲法權利、基本人權、不可侵犯等)的性質,不如在具體的法律中把這種權利寫得詳細而又具體,讓普通的人主張權利時有明確的依據。
(三)配套民法制度的考慮
如果說未來中國民法典中的侵權行為體制是一種典型化的、列舉式的侵權行為體制,如果中國民法典采用嚴格的實證主義、形式主義的法律觀念,拒絕在民法典中通過一般原則和一般條款,對民法外的規范打開窗口,那么人格權的多元理論模式的確會導致人格利益保護上的重大缺陷。德國法上之所以發展出一個統一的“一般人格權”,并且想方設法把它界定為《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規定的“其他權利”,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國封閉的典型化侵權行為體制所造成的。法國的情況就是一個例子。《法國民法典》中的侵權行為體制是非典型的、開放的體制,因為其第1382條沒有要求相反的受到損害的必須是一種權利,所以在法國,人格權的一元理論模式就幾乎沒有什么影響。
但是,根據現在強有力的學說,我們的侵權行為體制將是一種一般條款模式,因此是一種開放的侵權行為體制,一些非典型的合法利益也會受到這一制度的涵蓋。由此也可以預見,我們未來的民法典不可能是一種嚴格的實證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民法典,通過一般原則與法外規范進行溝通和協調。由于這些因素的存在,可以認為多元理論模式在中國民法典中的運用不會產生人格利益保護上的重大缺陷。
(四)人格權立法上的原則宣告與具體權利規范的并存以及立法體例問題
經過前面的分析,可以澄清這樣一個問題:在人格權立法上,兩種模式不能并存,但是人格利益保護的原則宣告與具體人格權規范則是可以并存的。關于人格權的一般規定是可以存在的。一般規定可以涉及人格利益保護上的法律原則、利益衡量、可以適用的救濟方法等對各種人格權共通的規定,但是這樣的一般規定不能被混淆為一般人格權,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事情。
(五)立法體例問題
根據上面的分析,筆者認為關于人格權的規定在結構上設立為民法典的單獨一編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因為在中國民法典中,我們需要通過這一制度建立一個相對完整的權利體系,要通過人格利益保護之具體的、細致的規定來凸現民法典所張揚的尊重人格和保護人格的時代精神。人格權獨立成編,緊隨總則之后,這樣安排的用意就是出于這些考慮而做出的結構上的強調。
雖然在規范適用上,條文的先后并不重要,但是特殊的結構處理可以獨立地表達出一定的信息。并且通過前文對人格權基本理論脈絡的梳理應該能夠認識到這一誤解。人格權制度與民事主體制度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民事主體制度所解決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與責任能力, 什么時候視為已經出生、什么時候成年,在什么狀態下具有責任能力等,這些狀態不影響該具體的人所享有的人格權。民事主體制度關注的是什么人在具備何種條件時可以登上法律的舞臺,成為一個演員(法律上的人);人格權制度要解決的則是設定這些演員之間的某一類型的行為規則,調整他們之間的某一特殊類型的利益關系。這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聯系呢?另外需要考慮的因素是,法人在一定的情況下也可以享有人格權,所以從邏輯上看,把人格權問題僅僅處理為自然人的人格保護問題是不合適的。在前面的論述中,筆者還提到,現在人格利益的概念也在發展中,出現了商業利用的問題,這既說明人格權問題不只是在受到侵害時才有意義,也說明人格利益與主體不可分離的說法也不完全都是成立的。胎兒、死者的人格利益保護更是與傳統的權利主體制度理論不相容,如果一定要把人格權規定在權利主體制度中,那么這些問題都不太好處理。但是如果人格權制度單獨成編,在其中對這些問題做出例外和變通規范就顯然更順理成章一些。至于人格權獨立成編是否有先例可循,筆者認為,無先例不應該成為一個反對理由。在筆者正在組織的意大利學者關于中國民法典的筆談中,就已經收到的回答而言,均認為關于人格權的規定應該獨立出來,沒有必要放在主體制度中。有學者甚至認為,如果中國采取了這樣的立法模式,在將來會成為歐洲國家仿效的對象。
注釋:
[1]參見王利明:《人格權制度在中國民法典中的地位》,《法學研究》2003年第2期;尹田:《論人格權的本質-兼評我國民法草案關于人格權的規定》,《法學研究》2003年第4期;梁慧星:《民法典不應該單獨設立人格權編》,《法制日報》2002年8月4日。
[2]See C.Massimo Bianca,Dirittocivile.Vol.VI,laproprietá,Milano,1999,13ss.
[3]也許有人會問,難道物權與所有權之間不是一般與具體的關系嗎?問題是,物權是一種學理上的范疇,指的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一組權利,它不是一種規范層面上的權利。因此,我們不能以“我的物權受到侵害”為由提出請求,而必須明確指出是哪一種權利受到侵害。
[4]這里不涉及規范適用上的“禁止向一般條款逃逸”的原則,而是兩種不同的權利的選擇性適用問題。因為一般人格權不是關于人格利益受法律保護的一種原則性宣告,而是一種權利類型,具有權利的一切法律特征和要件,例如具體的權利客體。卡爾·拉倫茨也指出一個絕對權僅僅是依附于一個具體的權利客體才能存在,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
[5]SeeCfr.,Vincenzo Zeno-Zencovich,Personalitá(dirit tidella),inDig.disc.priv.,Sez.civ.,XIII,430ss.
[6]SeePietroRescigno,Personalit (dirittidella),inEnc.Giur.Treccani,XXIII,Romas.d.
[7]SeeO.Gierke,DeutschesPrivatrechtá,I,Leipzig,1895.
[8]SeeVincenzoZeno-Zencovich,op.cit.,p.432.
[9][10][13][22][28][32][33][35]See Adriano De Cupis,Idirittidella perosnalitá,second aedizione,Milano,1982,p.33,p.33,34ss,p.42,p.65,42ss,p.38,p.41.
[11]這個問題在19世紀德國法學中被反復討論。Cfr.,F.von Savigny,Sistemadeldiritto romanoattuale,trad.it.diV.Scialoja,I,Torino,1886,338ss;B.Windscheid,Ildiritto delle Pandette,I,trad.iteannotodiC.Fadda-E.Bensa,I,Tori no,1925,115ss.
[12][34]SeePietroRescigno,op.cit.,p.9,p.6.
[14]See G.F.Puchta,Vorlesungen über das heutiger mische Recht,I,Leipzig,1894,52ss.
[15]See Cfr.,Franceso Gazzoni,Manualedidirittoprivato,VIIIedizione,Napoli,2000,692ss.
[16]See Hattenhauer,Die GrundbegriffedesBürgerlichen Rechts,Müchen,1982,12ss.
[17]See Cfr.,Massimo Siclari(acuradi),La Costituzione della Repubblica italiana nel testo vigente,Roma,2001.《意大利憲法》第2條規定:“共和國認可和保障自然人的不得被侵犯的權利,無論是作為個體而存在還是處在發展其人格的社會團體中……”
[18] See Adriano De Cupis,op.cit.,26ss.;VincenzoZeno-Zencovich,op.cit.,p.435.
[19]參見尹田:《論人格權的本質-兼評我國民法草案關于人格權的規定》,《法學研究》2003年第4期。
[20]普通訴訟程序發生的必要前提是存在明確的義務人,并且存在明確的具體義務,但是在憲法上,與一種“權利”相對應的不是針對一個具體的人的具體義務,而是一系列國家行為必須符合“權利”宣告中所體現的指向。所以,在憲法上,“權利”的內涵更多地是對國家權力的制約。
[21] 參見[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05頁;[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
[23]See Hubmann,Das Pers nlichkeitsrecht,K ,1967,p.172.
[24]具體的例子可參見聯邦德國最高法院(BGH)1978年6月20日的判決。Juristenzeitung,1979,102ss.
[25]See Cfr.,Aless and roSomma,I diri tti della personalitá eildirittogenerale della personalitá nell‘ordina mento privatisticodellaRepubblica Federale Tedesca,in Rivis ta Trimestrale didi ritto eproce dura civile,1996,fasc.3,834ss.
[26]See Aless and roSomma,op.cit.,p.834.
[27][德]爾卡?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頁。
[29]See Paolo Vercellone,Personalitá(diritti della),inNNDI,s.v.1084ss.
[30]See Paolo Vercellone,loc.cit.
[31]卡爾·拉倫茨也認為,《德國民法典》之所以在法典中沒有規定一般人格權,是因為難以給這種權利劃界,而劃界則明顯地取決于在具體案件財產或利益的相互沖突,究竟哪一方有更大的利益。參見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頁。
[36]SeeCfr.,Zeno-Zencovich,ProfilinegozialidegliattributidellaPersonalitá,inDirittodell‘informazioneedell’informatica(DII),1993,545ss.
[37]See Cfr.,C.Scognamiglio,I ldirittoall‘utilizzazione economica del nomeedell’immagine delle persone celebri,in Diritto dell‘info rmazioneedell’info rmatica(DII),1988,1ss.
[38][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800頁。
[39]SeeSomma,op.cit.,834ss.
[40]SeeCfr.,Aless and roSomma,op.cit.,807ss.
[41]SeeCfr.,D.Tallon,Personnalitè(Droitsdela),inEnc.Dalloz,Droitcivil,VI,1981.
[42]SeeCfr.,Giovanni Giacobbe,Natura,contenutoestruttura deidi ritti del lapersonalitá,inIldi ritto privat onellagiurispru denza,acuradiPaolo Cendon:le persone(III)-dirittidellapersonalitá,Torino,2000,24ss.
[43]SeePaoloVercellone,op.cit.,1084ss.
第5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關鍵詞:民法的基本原則
民法的一般原則
補充性強制性公共秩序性
一、民法一般原則的兩種表現形式
(一)民法的一般原則包含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和非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
所謂民法的一般原則(lesprincipesgenerauxdudroitcivil),也稱為法律的一般原則(lesprincipesgenerauxdudroit簡稱為PGD)、民法的基本原則,是指能夠在一系列不確定的法律狀況(lasituationjuridiquementindefiniesituationsiuridiquementindeterminees)當中得到一系列不確定適用的法律規范。
民法的一般原則在性質上不過是一種民事法律規范。該種民事法律規范或者由立法者在民法中作出明確規定,或者由法官在其司法判例中發現。當民法的基本原則被立法者所規定時,它們被稱為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1esprincipeagenerauxdudroitecritslespeincipesgenerauxdudroitsecundumlegem);而當民法的基本原則經由法官在其司法判例中發現時,它們被稱為非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lesprincipesgenerauxdudroitnonecritslesprincipesgenerauxdudroitsupralegem)。
所謂能夠在一系列不確定的法律狀況當中得到適用,是指作為一種法律規范,民法的一般原則、基本原則的適用范圍并沒有受到其自身的限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和案件所面臨的具體情況,它們既可能會在民法的某一個領域加以適用,也可能會在民法的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領域加以適用,還有可能會在民法的所有領域加以適用。所謂能夠在一系列不確定的法律狀況當中得到一系列不確定的適用,是指作為一種法律規范,在民法的所有領域、部分領域,民法的一般原則、基本原則能夠適用于眾多不確定的人。
(二)大陸法系國家民法當中的非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和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
雖然法國早在1804年就已經制定了《法國民法典》,但是,除了在少數法律條款當中對某些基本原則的具體方面作出了規定之外,法國立法者并沒有對民法的一般原則作出規定。例如,雖然法國立法者在《法國民法典》第6條當中對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原則作出了規定,但是,他們僅僅將此種原則限定在契約領域,因此,除了在契約領域適用之外,該條的規定無法在其他領域適用。再例如,雖然法國立法者在《法國民法典》舊的第1134(3)條當中對誠實信用原則作出了規定,但是,他們也僅僅將該種原則限定在契約義務的履行領域,既沒有將其視為整個契約當中的原則,更沒有將其視為整個民法領域的原則。類似的情況在整個法式民法典和德式民法典當中均是存在的。因此,在大陸法系國家,立法者很少直接對民法的一般原則、基本原則作出規定。
在民法上,將法律的一般原則視為民法淵源的做法始于1811年的《奧地利民法典》(LeCodecivilautfiehien),其第7條明確規定:在案件仍然存在疑問時,在考慮案件所面臨的不同情況下,法官應當根據自然法的原則作出判決。在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3條也對此種淵源作出了規定,該條規定,在欠缺制定法的情況下,法官應當根據法律的一般原則作出判決。
在1935年的著名文章《法律的一般原則》當中,意大利著名學者G.DelVeeehio對法律的一般原則作出了詳細的討論,認為《意大利民法典》第3條所規定的法律的一般原則不等于意大利法律的一般原則,而是等同于《奧地利民法典》第7條所規定的自然法的一般原則。他認為,作為民法的一種淵源,法律的一般原則是法律的最高真理,是指法律的邏輯和道德因素,也就是指人的理性。因此,它們屬于全人類的公共財富,而不是每一個民族、國家的私物。
問題在于,無論是意大利民法典、法國民法典還是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典,它們均沒有對這些被視為人類最高真理和人的理性的一般原則作出明確規定。在處理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時,法官必須首先通過某種方法找到它們,之后才能夠將它們作為民法規范予以適用并因此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因為民法典沒有對法律的一般原則作出明確規定,所以,即便它們屬于民法淵源,它們也僅僅是非制定法上的民法淵源,這就是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學者普遍將它們稱為非制定法的一般原則的原因。
為了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在民法典存在法律漏洞的情況下,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和民法學者不得不采取各種各樣的方法發現法律的一般原則,以便通過所發現的這些原則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其中最常用的一種方法是,通過邏輯推論的方式,從民法典所規定的一個或者幾個分散的法律文本或者零碎的法律文本當中發現法律的一般原則的存在,也就是,從一個或者幾個法律文本的精神當中發現法律的一般原則。此種方法被稱為擴張解釋(Inductionamplifiante),實際上就是將一個或者幾個法律文本、法律條款的規定一般化、泛化。
例如,從《法國民法典》第6條的規定中,法官和民法學者發現了能夠在所有民法領域加以適用的一個原則即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原則。再例如,從《法國民法典》舊的第1134(3)條中,法官和民法學者發現了能夠在所有民法領域均加以適用的一個原則即誠實信用原則。同樣,從法國民法典舊的第1134條和舊的第1135條的規定中,法國最高法院發現和確認了契約自由的一般原則和契約有約束力的一般原則。
除了上述方法之外,人們還采取另外一種方法,這就是,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發現一般原則,因為法律的一般原則并不是由某種單一的事件產生的,而是多種多樣的事件(multiplicationdesfaits)和因素(facteurs)共同作用的產物(produit)。如果沒有這些事件或者因素的共同影響和相互作用,則法律的一般原則將無法產生。這些事件和因素多種多樣,不一而足,包括但是不限于以下事件和因素:“事物的性質”、宗教道德、歷史傳統、法律經驗、法律科學、潛在的法律意識(consciencejuridiquelatente)、立法者的默示意圖、法律的精神、公平正義的自然法理念、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等等。它們結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法律的一般原則的產生、發展和確立,這就是多因素理論。
通過上述方法,大陸法系國家的法官和民法學者發現了各種各樣的一般原則: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平等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原則、法律安全原則、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尊重原則,等等。這些原則均被視為非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也就是法律的一般原則。當然,在法官和民法學者發現了某種一般原則之后,立法者也會采取措施,將他們發現的某種原則規定在制定法當中,并因此讓該種原則從非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上升到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例如,在2016年2月10日的法令當中,法國法官和民法學者所發現的契約自由原則就被規定在《法國民法典》新的第1102條,該條規定:任何人均享有簽訂或者不簽訂契約的自由,享有選擇契約當事人的自由,享有確定契約內容和形式的自由,只要他們在制定法所規定的限制范圍行為即可。契約自由不得違反同公共秩序有利害關系的規范。
(三)我國民法中的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和非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
而在我國,情況則完全不同,在制定任何法律時,立法者不僅不厭其煩地對法律的一般原則作出規定,而且還將法律的一般原則視為最重要的部分,因為他們均將法律的一般原則規定在制定法的第一部分即第一章中。在公法當中是如此,在民法中也是如此。
在1986年的《民法通則》中,立法者在第一章即“基本原則”中即對民法的基本原則作出了規定。在1999年的《合同法》中,立法者在第一章即“一般規定”中對合同法的一般原則作出了規定。在2007年的《物權法》中,立法者在第一編第一章即“基本原則”中對物權法的基本原則作出了規定。在2017年的《民法總則》中,立法者在第一章即“基本規定”中對民法的基本原則作出了規定。因此,在我國,民法中的基本原則在性質上均屬于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
在我國,《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對民法的基本原則的類型作出了明確規定,根據這些規定,民法的基本原則包括:當事人的地位平等原則,為《民法通則》第3條和《民法總則》第4條所規定;自愿原則,也就是意思自治原則,為《民法通則》第4條和《民法總則》第5條所規定;公平原則,為《民法通則》第4條和《民法總則》第6條所規定;等價有償原則,為《民法通則》第4條所規定,不過,《民法總則》已經放棄了此種原則,《民法總則》之所以放棄此種原則,是因為等價有償并不能夠在所有民法領域加以適用;誠實信用原則,為《民法通則》第4條和《民法總則》第7條所規定;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原則,為《民法通則》第5條和《民法總則》第3條所規定;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原則,為《民法通則》第6條和第7條和《民法總則》第8條所規定;節約資源和保護生態原則,為《民法總則》第9條所新規定。此外,《民法總則》第132條也對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作出了規定,雖然它沒有在第一章即“基本規定”中規定。
問題在于,除了《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所規定的這些原則之外,我國民法領域是否還存在其他原則?對此問題,我國民法學者均沒有作出明確說明。筆者認為,除了我國《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所規定的上述基本原則之外,我國民法領域還存在立法者沒有規定的一般原則,這就是非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諸如:法律安全原則和外觀原則等。
所謂法律安全原則(principedesecuritejuridique),是指在不需要付出難以逾越的努力的情況下,民事主體就能夠知道什么行為是法律所允許的,什么行為是法律所禁止的。為了實現此種結果,所制定的法律規范應當是清晰的、易懂的,并且一旦制定,法律規范不應當做頻繁的修改、變更,尤其是不能夠讓民事主體無法預見。法律安全原則通過多種多樣的方式表現出來:法律應當具備應有的質量;法律應當具有可預見性;制定法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生效判決具有既判力;民事主體應當在訴訟時效期間內主張權利;占有人基于占有時效取得所有權人的所有物,等等。
所謂外觀原則(lesprincipesregissantl'apparencedesactesjuridiques),也稱為外觀理論(Latheoriedel'apparence)和“法律行為的外觀理論”,實際上就是“公眾的錯誤形成法律”(Errorcommunisfacitius)的法律格言、法律諺語,是指當真正的權利人通過自己的行為創造出某種明顯事實狀態(situationdefaitvisible)或者表面狀態(situationapparente)時,如果他們所創造出的此種明顯事實狀態或者表面狀態讓第三人(lestiers)產生錯誤信賴(lacroyanceerronee)或者合理信賴(Laconfiancelegtime),則第三人就獲得了原本無法通過正常的法律規范所獲得的權利,第三人能夠以其獲得的權利對抗真正的權利人。因為外觀原則建立在第三人的合理信賴的基礎上,因此外觀理論也被稱為“合理信賴”原則(Leprincipedeconfiancelegitime)、“合理信賴”理論、“合理期待”原則(legitimateexpectations)。
在我國,還有一種現象非常獨特,那就是除了少數民法學者對法律規范的一般理論作出了闡述之外,大多數民法學者均沒有對法律規范的一般理論作出說明。㈣那我國的民法學者為何普遍忽視法律規范的存在?答案在于,在討論民法總論的內容時,他們均受到了德國民法典、德國尤其是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學者的影響。在德式民法典當中,立法者幾乎完全忽視了法律規范的一般理論。民法學者也幾乎忘記了法律規范的存在。而法式民法典則不同,立法者在民法典的序編當中對法律規范作出了或者詳盡或者簡略的規定。
在我國,《民法總則》沒有對法律規范的一般理論作出規定。我國《民法總則》第153條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問題在于,什么樣的法律規定屬于該條規定的“強制性規定”?在民法上,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是相對于法律的“任意性規定”而言的,它們均是法律規范的組成部分,因為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就是強制性法律規范,而法律的“任意性規定”則是指任意性法律規范。在使用了“強制性規定”的同時,我國立法者既沒有對“強制性規定”作出界定,也沒有對“任意性規定”作出界定,更沒有對法律規范的一般理論作出說明。
二、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和強制性
(一)民法一般原則補充性的準確界定
在法國,雖然民法學者承認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earaeteresuppletif),但是,在一般原則補充性的含義方面,不同的民法學者所作出的說明并不相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理論。
1.PierreMarchal對一般原則補充性作出的界定
某些民法學者將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等同于民法一般原則的附屬性,認為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僅僅是指它們所起到的補充功能,這就是,在制定法沒有作出規定的情況下,或者說在制定法存在法律漏洞(lacunes)的情況下,民法的一般原則能夠起到填補(combler)制定法所存在的法律漏洞的作用。PierreMarchal采取此種理論。在其《法律的一般原則》當中,除了承認法律一般原則的一般性、獨立性和演變性之外,他也承認法律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在對一般原則的補充性作出說明時,除了將補充性等同于附屬性之外,他還對補充性作出了說明,認為法律一般原則的補充性是指它們在制定法沒有規定的范圍內起到規范和調整的作用。
他指出:“法律一般原則的補充性也構成它們的附屬性。在制定法以確定方式進行規范和調整的范圍內,法律的一般原則不會發揮規范和調整作用,但是,在制定法沒有以確定方式進行規范和調整的范圍內,它們會補充制定法而發揮規范和調整作用。比利時民法典舊的第4條,實際上就是比利時訴訟法典第5條,對法律的一般原則所具有的此種補充特征作出了規定和證明了其存在,因為它要求法官在制定法沒有規定的情況下、在制定法規定模棱兩可或者不充分的情況下要作出判決。因為法律的一般原則的適用范圍往往超過了制定法的適用范圍,因此,法律的一般原則能夠幫助法官對制定法作出解釋,能夠幫助法官填補制定法所存在的法律漏洞,甚至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制定法所存在的矛盾。”
2.AmaryllisBossuyt、AlbertFettweis和SteveGilson等人對一般原則補充性作出的界定
某些民法學者則認為,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不同于民法一般原則的附屬性,人們不應當將一般原則的補充性與一般原則的附屬性混淆。因為一方面,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并不會涉及它們與制定法之間的關系,而是會涉及它們與行為人實施的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這就是,行為人實施的法律行為是否能夠違反民法的一般原則,如果他們實施的法律行為違反了民法的一般原則,他們實施的行為是否會因此無效;另一方面,民法一般原則的附屬性會涉及它們與制定法之間的關系,這就是,在制定法與一般原則的關系方面,究竟是制定法的地位要高于一般原則,還是一般原則的地位要高于制定法。
AmaryllisBossuyt、AlbertFettweis和SteveGilson等人采取此種理論。在其《超越制定法:法律一般原則的現實性和演變性》當中,除了承認民法一般原則的一般性、獨立性之外,他們也承認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和非附屬性。他們認為,在比利時,雖然民法學者和法國最高法院經常混淆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和附屬性,但是,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和附屬性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涉及到不同的方面。這就是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涉及到民法一般原則在性質上究竟是一種強制性的法律規范還是一種補充性的法律規范,行為人是否能夠通過自己的契約違反民法的一般原則;而民法一般原則的附屬性則不同,它涉及到民法的一般原則與制定法之間的關系,也就是涉及到它們在法律規范的位階當中的地位問題。
他們指出:“在民法當中,更進一步而言,在其他法律當中,法律一般原則的最準確范圍是什么?對此種問題的回答,一方面要求我們探尋法律的一般原則究竟是有補充性還是沒有補充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我們探尋法律的一般原則究竟是有附屬性還是沒有附屬性?如果我們采取嚴格區別標準的話,則這兩類問題并不屬于同一層面的問題:(1)一般原則是否具有補充性,關乎一般原則與行為人實施的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涉及到這樣的問題:行為人是否能夠通過自己的契約違反一般原則,在欠缺相反意思表示的情況下,一般原則是否會適用于行為人,換言之,法律的一般原則是不是總是具有強制性的特征、公共秩序的特征?(2)一般原則是否具有附屬性,關乎原則與制定法即立法者實施的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涉及到這樣的問題:在立法者將某一個原則的具體適用條件限定在確定領域時,該原則是否可以超越此種限定范圍而得到適用?”
3.筆者對民法一般原則補充性作出的界定
筆者認為,在上述兩種不同的理論當中,第一種理論是存在問題的,因為一方面,它混淆了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和附屬性,將原本不同的兩個問題混為一談;另一方面,它也不符合一般法律規范的補充性理論。而第二種理論則是合理的,因為一方面,它明確區分了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和一般原則的附屬性,另一方面它也符合一般法律規范的補充性理論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的確不同于民法一般原則的附屬性,因為它們所面臨的問題風馬牛不相及。當我們論及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時,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行為人是否能夠通過自己的法律行為明確規避、排斥民法一般原則的適用?如果他們在其法律行為中明確規避、排斥民法一般原則的適用,他們實施的法律行為是否因此無效?而在民法上,當我們論及民法一般原則的附屬性時,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作為一種法律規范,民法的一般原則與其他法律規范尤其是制定法之間的地位、位階如何?究竟是民法的一般原則優越于制定法,還是制定法優越于民法的一般原則?
在討論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時,如果我們將一般原則的補充性理解為一般原則與行為人實施的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則我們這樣的理解符合民法學者對一般法律規范補充性的理解。因為,在對一般法律規范作出分類時,民法學者普遍根據行為人在行為時是否能夠規避、排斥法律規范的不同而將一般法律規范分為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和補充性的法律規范,關于這一點,筆者將在下面的內容中作出詳細的討論。雖然民法的一般原則在性質上不是一般法律規范,但是,它們仍然是法律規范,因此,它們也具有一般法律規范所具有的強制性和補充性。
基于此種考慮,筆者對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作出如下界定:所謂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是指作為一種法律規范,民法的一般原則也像一般法律規范那樣能夠起到補充行為人意思表示不足的功能,在行為人沒有作出意思表示的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沒有通過契約或者其他法律行為明確排除民法的一般原則,則民法的一般原則能夠自動適用于行為人。換言之,作為一種法律規范,并非民法的所有一般原則均是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因為,民法的某些一般原則在性質上也屬于補充性的法律規范。
(二)民法一般原則強制性的界定
所謂民法一般原則的強制性,是指行為人在行為時應當尊重、遵守作為法律規范的一般原則,應當按照民法一般原則的要求積極作出某種行為,或者應當按照民法一般原則的要求消極不作出某種行為。如果他們在行為時不尊重、不遵守一般原則的要求,沒有積極實施某種行為或者積極實施了某種行為,則他們所實施的行為或者無效,或者讓他們因此對他人遭受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在民法上,判斷民法的一般原則在性質上究竟是強制性的法律規范還是補充性的法律規范,其標準是行為人在行為時是否能夠通過自己相反的意思表示規避、排斥民法的一般原則:如果行為人在行為時不得通過自己相反的意思表示規避、排斥民法的某一個一般原則,則該原則在性質上屬于強制性的法律規范,筆者將其稱為強制性的一般原則,也稱為民法一般原則的強制性;反之,如果行為人在行為時能夠通過自己相反的意思表示規避、排斥民法的某一個一般原則,則該原則在性質上屬于補充性的法律規范,因為,在行為人的意思表示不明確或者欠缺時,如果行為人沒有通過意思表示明確排斥該種原則,則該種原則能夠自動起到補充行為人意思表示不足或者不清晰的功能,筆者將其稱為補充性的一般原則,也稱為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
作為一種法律規范,具有強制性的一般原則或者表現為禁止性的法律規范,或者表現為命令性的法律規范,這一點同一般法律規范沒有兩樣。當民法的一般原則表現為禁止性的法律規范時,它們就是禁止性的一般原則。所謂禁止性的一般原則,是指民法的某一個一般原則明確禁止行為人實施同該原則相反的任何行為。例如,平等原則明確禁止行為人實施歧視他人的行為,良好道德原則明確禁止行為人實施同道德相反的行為,公共秩序原則明確禁止行為人實施違反公共秩序的行為,等等。如果行為人違反此類原則的禁止性規定而實施某種行為,則他們實施的法律行為無效,在引起他人損害發生時,他們還應當賠償他人所遭受的損害。
所謂命令性的一般原則,是指民法的某一個一般原則明確要求行為人積極實施某種行為。如果行為人沒有按照該原則的要求實施該種行為,則他們的不作為行為構成非法行為,應當就其非法行為引起的損害對他人承擔賠償責任。
例如,物的行為引起的一般侵權責任原則要求物的所有權人或者控制權人采取措施,警告他人當心其所有物或者控制物所存在的危險。如果他們沒有采取措施警告他人,在他人因為其物而遭受損害時,他們應當賠償他人所遭受的損害。再例如,當行為人以犧牲他人利益作為代價而獲得不當利益時,他們應當將其獲得的利益返還給他人,否則,基于他人的訴求,法官有權責令他們返還。
在理論上,雖然民法一般原則的強制性既可以表現為禁止性的法律規范也可以表現為命令性的法律規范,但是,民法的一般原則大都屬于禁止性的法律規范,命令性的法律規范很少,因為民法的大多數原則的目的單純、單一,這就是,約束和限制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防止行為人無限擴張或者任意放大其意思自治和契約自由的范圍。例如,公共秩序原則、良好道德原則、權利濫用的禁止原則等均屬于禁止性的法律規范。
(三)民法一般原則的強制性與補充性之間關系的復雜性
在民法上,誠實信用原則(Leprincipedelabonnefoi)當然要求債務人積極履行協助義務,公平原則(Leprinciped’equite)當然要求旅館對其顧客提供人身或者財產保護義務,等等。問題在于,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究竟是強制性的法律規范還是補充性的法律規范?換言之,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究竟是命令性的法律規范還是補充性的法律規范?單純從這兩個原則要求債務人和旅館積極實施協助義務和提供保護來看,這兩個原則似乎在性質上屬于命令性的法律規范、強制性的法律規范,不屬于補充性的法律規范。不過,單純從原則對行為人提出要求的立場來分析,我們還無法明了這兩個原則的性質,因為,根據意思自治原則,如果契約當事人在其契約當中明確排斥了行為人承擔的某種義務,該種義務當然不能夠強加給行為人。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其契約當中,當事人是否能夠通過契約將這兩個原則所強加的協助義務、保護義務予以規避、排斥?如果契約當事人能夠在其契約當中規避、排斥這兩個原則所強加的義務,則這兩個原則在性質上就屬于補充性的法律規范,而如果他們不能夠在其契約當中規避、排斥這兩個原則時候強加的義務,則這兩個原則在性質上就屬于命令性的法律規范。
問題在于,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所強加的義務能夠由契約當事人通過契約條款予以規避、排斥嗎?對于這樣的問題,民法學者少有說明。雖然如此,筆者認為,對于這樣的問題,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原則上,這兩個一般原則所強加的義務是能夠通過契約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規避、排斥的,而在極端例外情況下,這兩個一般原則所強加的義務則是不能夠通過契約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規避、排斥的。換言之,原則上,這兩個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屬于補充性的一般原則,在極端例外情況下,它們在性質上屬于命令性的法律規范。
在民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在性質上之所以是補充性的一般原則,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它符合立法者規定這兩個一般原則的原本的目的。雖然早在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當中,法國立法者就已經對這兩個一般原則作出了規定,但是,在規定這兩個一般原則時,法國立法者僅僅將其視為一種意思表示的補充制度,并沒有希望以這兩個一般原則取代契約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因此,將這兩個一般原則視為補充性的,符合立法者的意圖。其二,如果將這兩個一般原則視為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則它們的實行會從根本上危及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會讓“契約當事人之間的契約等同于他們之間的法律”的名言被連根拔起,并因此讓契約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不再受他們自身的控制。
所謂在極端例外情況下這兩個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屬于命令性的法律規范是指,如果立法者明確規定,這兩個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則它們將會被視為命令性的法律規范,不再被視為補充性的法律規范,即便它們仍然起到補充契約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不足。在此種例外情況下,這兩個一般原則之所以被視為命令性的法律規范,是因為此種性質符合立法者的明示意圖。
根據此種判斷標準,在今時今日的法國,公平原則仍然在性質上屬于補充性的法律規范,而誠實信用原則則不再屬于補充性的法律規范,而屬于命令性的法律規范。根據公平原則,在契約當事人沒有對某種債務作出規定的情況下,如果公平原則要求債務人對債權人承擔此種債務,則該種債務對債務人有約束力,債務人應當按照公平原則的要求承擔此種債務。換言之,公平原則能夠補充契約當事人之間的意思表示不足。法國民法典舊的第1135條對此種規則作出了明確說明,它規定:協議不僅對當事人所明確表達的內容產生約束力,而且還對公平、習慣和制定法根據協議性質賦予的債所引起的所有后果均產生約束力。在2016年2月10日的法令之后,法國民法典新的第1194條仍然對此種規則作出了說明,它規定:契約不僅對當事人所明確表達的內容產生約束力,而且還對公平、習慣和制定法所產生的所有后果均產生約束力。
根據誠實信用原則,即便契約當事人沒有在他們的契約當中明確規定契約當事人在行為時要承擔忠實義務(devoirdeloyaute)或者協助義務(devoirdecooperation),他們在行為時也應當承擔這兩種契約義務。換言之,誠實信用原則也屬于能夠補充契約當事人意思表示不足的一般原則。法國民法典舊的第1134(3)條對此作出了明確說明,它規定:協議應當以誠實信用的方式加以履行。在2016年2月10日的法令之后,法國民法典新的第1104條仍然對此種原則作出了說明,該條規定:契約應當經過協商、成立并且應當以誠實信用的方式得以履行;此條規定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規定。
總之,除非制定法明確規定或者法官通過司法判例明確認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法律效果在性質上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否則,行為人有權通過自己的意思表示規避或者排斥它們所產生的法律效果,當他們通過自己的意思表示規避或者排斥這些原則所產生的法律效果時,他們的意思表示仍然有效;在意思表示不清或者欠缺的情況下,這些原則產生的法律效果自動補充他們的意思表示。
三、法國民法學者對民法一般原則的公共秩序性和強制性之間的關系作出的說明
在民法上,如果民法的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屬于補充性的法律規范,則它們當然不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就像具有補充性的一般法律規范在性質上不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一樣,這一點毫無疑問。問題在于,如果民法的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屬于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包括禁止性的法律規范和命令性的法律規范,它們是否一定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對此問題,大多數民法學者均沒有作出明確說明,僅少數學者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認為并非所有具有強制性的一般原則均具有公共秩序性,包括PatrickMorvan、AmaryllisBossuyt、AlbertFettweis、SteveGilson和Jean-PierreGridel等人。
(一)PatrickMorvan就一般原則的公共秩序性和強制性之間的關系作出的說明
根據這些少數學者的意見,判斷民法的一般原則在性質上究竟是不是具有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其標準既不在于民法的一般原則是否具有強制性、約束力,也不在于行為人是否能夠通過自己的意思表示將其加以規避或者排斥,而在于民法的一般原則所維護的利益:如果民法的某一個一般原則所維護的利益屬于公共利益、一般利益,則它屬于公共秩序性的法律規范;反之,如果民法的某一個一般原則所維護的利益屬于私人利益、個人利益,則它屬于非公共秩序性的法律規范。
在其《私法的原則》當中,PatrickMorvan就采取此種態度,他指出,在私法領域,雖然“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是存在的”(L’existencedeprincipesd’ordrepublic),但是,“并非所有的原則均是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Touslesprincipesnesontpasd’ordrepublic)。一方面,在私法領域,民法的某些一般原則的確具有公共秩序性質、公共秩序特征(lecaract6red’ordrepublic),因為,“為了規避行為人實施的與一般原則有沖突的意思表示行為,最高法院在眾多的案件當中鄭重宣告,某些私法原則具有公共秩序的特征。”另一方面,在私法領域,并非民法的所有原則在性質上均具有公共秩序性質或者公共秩序的特征,因為大量的私法原則并不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而僅僅是為了維護私人利益(interetprive)。
PatrickMoran指出,雖然民法的一般原則多種多樣,但是,大多數一般原則都不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僅少數一般原則屬于公共秩序性的。例如,有關占有訴訟(l’actionpossessoire)方面的原則就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因為法國最高法院在其判決當中認定,此種原則關乎社會秩序和公共和平的維護。再例如,破產清算程序當中的債權人平等原則也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因為法國最高法院在其判決當中認定,債權人之間的平等原則是公共秩序性的,無論是在國內法當中還是在國際法當中都是如此。
不過PatrickMoran認為,最典型的范例即是人的身份的不得處分性原則和人的身體的不得處分性原則,因為這些原則隨著近些年來所出現的代孕契約和性別變更(transsexuels)而“活化”(reactivation),在針對這些問題作出說明時,法國最高法院強調,人的身份的不得處分性原則和人的身體的不得處分性原則屬于公共秩序性的。
(二)AmaryllisBossuyt、AlbertFettweis和SteveGilson等人就一般原則的公共秩序性和強制性之間的關系作出的說明
在其《超越制定法:法律一般原則的現實性和演變性》當中,AmaryllisBossuyt、AlbertFettweis和SteveGilson等人也采取此種態度,雖然他們明確將強制性等同于公共秩序性,但是,他們所說的強制性僅僅是指狹義的,這就是以維護公共利益、一般利益為目的的一般原則,而不是一般民法學者所謂的廣義的強制性。他們指出:“人們可以認定,法律的一般原則具有補充性,因為它們能夠補充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不足,并且當事人也能夠通過自己的法律行為違反法律的一般原則,除非在例外情況下,引起爭議的原則具有強制性或者公共秩序性。因為法律的一般原則既具有補充性也具有強制性,因此,在判斷行為人是否能夠違反法律的一般原則時,我們應當仔細分析每一種原則的具體情況,以便判斷行為人是否存在能夠違反該原則的理由。”
AmaryllisBossuyt、AlbertFcttweis和SteveGilson等人認為,在債法和契約法當中,契約等同于制定法的原則,契約的合意主義原則以及契約履行的誠實信用原則不應當被視為強制性的、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而應當被視為補充性的原則;在法國,雖然民法典第1382條所規定的一般過錯責任原則被視為公共秩序性質的,但是,在比利時,該條所規定的一般過錯責任原則則不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即便該條仍然禁止行為人間接免除故意過錯和欺詐所產生的后果;當我們將誠實信用的一般原則看作具有強制性特征或者公共秩序特征的原則時,我們的此種講法同樣言過其實;當我們說權利濫用原則、無過錯的外觀原則、鄰人滋擾的禁止原則和不當得利的禁止原則具有強制性的特征時,我們這樣的講法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雖然這些原則在法律制度當中是重要的,但是,它們還沒有重要到能夠否定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的地步。當法律行為的客體消滅時法律行為無效的原則也不是強制性的或者公共秩序性的。事實上,在民法或者私法當中,雖然法律的一般原則眾多,但是,大量的一般原則均不是強制性的或者公共秩序性的。
如果立法者在規定法律的一般原則時明確賦予某一個一般原則以強制性和公共秩序性,則該原則當然具有強制性和公共秩序性。雖然在產生時某些非制定法上的一般原則具有強制性、公共秩序性,但是在當下它們是否具有強制性、公共秩序性,則不無疑問,例如,在產生時,欺詐使一切行為無效的原則當然具有強制性、公共秩序性,但是,在今時今日,人們則可能不會這樣看,因為它們可能會認定該原則不具有強制性、公共秩序性。
(三)Jean-PierreGridel就一般原則的公共秩序性和強制性之間的關系作出的說明
在其《法國最高法院在私法一般原則的創設和承認當中所起到的作用》當中,Jean-PierreGridel認為,在承認民法一般原則的過程當中,法國最高法院面臨諸多難題(lesdifficult6s),其中就包括民法一般原則的公共秩序性和一般原則的強制性之間的關系:如果說民法的一般原則具有強制性的話,那么,民法一般原則的強制性是否等同于民法一般原則的公共秩序性?對于這樣的問題,Jean-PierreGridel認為很難回答,因為,除了民法一般原則的觀念(lanotion)模糊不清(floue)之外,有關法律規范強制性的淵源和后果(souFeesetdescons6quencesdel’impdrativit6d’unenorme)方面的觀念也是含含糊糊的。
Jean-PierreGridel認為,雖然人們將法律規范的強制性理解為人們不得違反所涉及到的法律規范,但是,在作出此種理解時,人們有時將其理解為制定法所表達的意圖(制定法的規定是禁止性的,違反制定法禁止性規定的行為是無效的;同制定法所規定的內容相反的條款被視為沒有規定),有時則理解為非制定法上的規范,在欠缺制定法的規定時,這些規范對司法判例認為不可侵犯的利益提供保護,這些利益關乎急迫的集體需要(uneexigencecollectiveimpefieuse)。這就是同公共秩序有利害關系的法律規范,包括制定法所規定的法律規范和非制定法所規定的法律規范。在1929年的著名案件當中,法國最高法院認定:禁止行為人實施某些法律行為的公共秩序能夠在制定法的規定之外存在。
Jean-PierreGridel指出,雖然非制定法上的某種一般原則能夠成為行為人不得違反的公共秩序,但是,民法的一般原則并非在所有情況下均能夠成為行為人不得違反的公共秩序,即便它們在性質上屬于強制性的,因為,行為人在行為時能夠違反排斥民法的某些一般原則。雖然民事責任的完全賠償原則(1eprincipedelareparationintegraleenresponsabilitecivile)屬于強制性的規范,但是,根據契約自由原則,契約當事人完全可以通過契約方式違反民事責任的完全賠償原則,這就是,除非存在故意過錯(fauteintentionnelle)、重大過錯(fautelourde)或者不可寬恕的過錯(fauteinexcusable),否則,契約當事人所簽訂的限責條款(lesclauseslimitatives)、免責條款(lesclauseselisives)和加則條款(lesclausespenales)是有效的,一旦存在這些法律條款,則契約債務人將不會根據完全賠償責任原則賠償契約債權人承擔的民事責任。
在侵權責任領域,民事責任的完全賠償原則更是如此。一方面,在行為人對他人實施侵權行為之后,他人既可以與行為人達成和解協議,就賠償范圍做出明確約定,也可以放棄所享有的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另一方面,在他人因為行為人實施的侵權行為而遭受損害之后,只有他人能夠向法院起訴,要求法官責令行為人對其遭受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他人不得通過檢察官提起此種訴訟,因為此種侵權訴訟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他人的私人利益。
四、民法一般原則的公共秩序性和強制性的區分理論
筆者認為,在法律規范方面,我們不應當將法律規范的強制性等同于法律規范的公共秩序性,或者反之,將法律規范的公共秩序性等同于法律規范的強制性。因為,雖然我們能夠說法律規范的公共秩序性一定屬于法律規范的強制性,但是,我們不能夠說法律規范的強制性一定屬于法律規范的公共秩序性。在一般法律規范領域是如此,在民法的一般原則領域也是如此。在民法的一般原則領域,我們之所以應當區分一般原則的強制性和一般原則的公共秩序性,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民法的一般原則所維護的利益存在差異。在民法上,法律規范的強制性既可能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也可能是為了維護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而法律規范的公共秩序性則不同,因為法律規范的公共秩序性僅僅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它們不會維護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因此,雖然同樣具有強制性,如果法律規范僅僅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則法律規范的強制性等同于法律規范的公共秩序性。
除了能夠在一般法律規范當中適用之外,此種理論當然也能夠在民法的一般原則當中適用。因為,作為一種法律規范,民法的一般原則所實現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某些一般原則僅僅是為了補充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不足,不是為了限制行為人的意思表示的,這就是補充性的一般原則,或者被稱為民法一般原則的補充性,已如前述。而某些一般原則則是為了禁止或者要求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的,這就是強制性的一般原則,或者稱為一般原則的強制性,包括一般原則的禁止性和一般原則的命令性,已如前述。
在民法上,民法的一般原則為何禁止或者要求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筆者認為,就像制定法禁止或者要求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是為了實現不同的目的一樣,民法的一般原則也是基于不同的目的禁止行為人實施或者要求他們實施某種行為。在某些情況下,民法的一般原則基于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的維護而禁止或者要求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而在某些情況下,民法的一般原則則是基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的維護而禁止或者要求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
例如,同樣是民法的一般原則,權利濫用的禁止原則和人的身體的不得處分性原則所維護的目的顯然不同。在民法上,權利濫用的禁止原則僅僅是為了維護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防止行為人過度行使自己的主觀權利而損害他人的利益,尤其是防止不動產所有權人過度行使其不動產所有權而損害其不動產相鄰人的利益。而在民法上,人的身體的不得處分性原則則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防止行為人通過處分自己身體的行為侵犯人的尊嚴、人的至高無上性。
當民法的一般原則是為了維護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時,它們就不具有公共秩序性,即便它們具有強制性;而當民法的一般原則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時,它們就具有公共秩序性,雖然它們同時也具有強制性。
其次,在違反民法的一般原則時,行為人實施的法律行為的命運并不完全相同。在民法上,雖然法律規范的強制性均要求行為人在行為時要尊重和遵守法律規范,不得通過自己的意思表示規避、排斥法律規范,但是,如果行為人在行為時違反了法律規范,他們所實施的法律行為的命運并不完全相同,這就是,如果行為人實施的行為違反了具有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則他們實施的法律行為絕對無效(nulliteabsolue);反之,如果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沒有違反具有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則他們實施的法律行為相對無效(nulliterelative)。
除了能夠在一般法律規范當中適用之外,此種規則也能夠在民法的一般原則當中適用。在民法上,除了寥寥無幾的幾個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屬于補充性的法律規范之外,大多數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均屬于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尤其是屬于禁止性的法律規范,命令性的一般原則較少,已如前述。作為強制性的法律規范,民法的一般原則當然對行為人有約束力,行為人不得通過自己的意思表示規避、排斥一般原則的適用,已如前述。問題在于,如果行為人在行為時違反具有強制性的一般原則,他們實施的法律行為的命運是否相同?答案是否定的,雖然行為人的行為違反了具有強制性的一般原則,它們實施的行為的命運是不同的,這就是,在行為時,如果行為人違反了具有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則他們實施的法律行為絕對無效,反之,如果他們違反了不具有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則他們實施的法律行為相對無效。
例如,同樣是違反了欺詐使一切行為均無效的原則和人的身體的不得處分性原則,行為人與他人之間的契約命運迥然不同。如果行為人在行為時違反了前一個原則,則他們與他人簽訂的契約相對無效,如果他人不主張無效,則他們之間的契約仍然有效。而如果行為人在行為時違反后一個原則,則他們與他人簽訂的契約絕對無效,即便他人不主張,他們之間的契約也不可能轉化為有效契約。
最后,此種理論符合立法者明確區分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和公共秩序性的法律規范的做法。在當今社會,雖然民法仍然貫徹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但是,基于社會公共利益的考慮,除了在民法典當中規定大量的補充性的法律規范之外,立法者也規定了大量的強制性的法律規范,這些法律規范或者禁止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或者要求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法國大多數民法學者均認為,立法者在其民法典當中規定的所有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均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因為他們直接將強制性等同于公共秩序性,已如前述。不過,這些民法學者的此種看法顯然違反了法國立法者的意圖,同他們在其制定法當中明確區分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和公共秩序性的法律規范的做法不符。
在法國民法典當中,法國立法者就明確區分法律規范的強制性和法律規范的公共秩序性,因為他們認為,除非具有強制性的法律規范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否則,它們并不具有公共秩序性。換言之,如果法律規范僅僅是為了維護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即便它們是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它們也不是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筆者僅以法國民法典第9條和第16-1條為例對此作出說明。
在法國,民法典第9條對私人生活受尊重權(Ledroitaurespectdelavieprivee)作出了明確說明,該條規定:任何人均享有私人生活受尊重的權利。為了阻卻行為人實施侵犯他人親密私人生活的行為,為了責令行為人停止實施侵犯他人親密私人生活的行為,除了能夠責令行為人賠償他人遭受的損害之外,法官還能夠采取一切措施,諸如查封、扣押或者其他措施。在緊急情況下,法官可以通過簡易程序決定采取這些措施。在法國,民法典第16-1條規定對身體的受尊重權(ledroitaurespectducorpshumain)作出了說明,該條規定:任何人均享有身體的受尊重權;人的身體是不能夠受到侵犯的;人的身體、身體的組成部分和身體的產物均不得成為財產權的客體。
在法國,民法典第9條和第16-1條均對自然人的人格權提供保護,均禁止行為人通過各種各樣的非法手段侵犯他人的人格權。因此,它們在性質上均屬于強制性的法律規范。問題在于,它們是否均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對此問題,法國立法者明確規定,法國民法典第16-1條的規定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因為在法國民法典第16-9條當中,法國立法者明確規定“本章的規定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其中就包括第16-1條在內。而在法國民法典第9條當中,立法者則沒有明確規定該條的規定屬于公共秩序性的。
同樣是對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權提供保護,同樣是強制性的法律規定,法國立法者為何直接將第16-1條的規定視為公共秩序性的而沒有將第9條的規定視為公共秩序性的?答案不言而喻,因為這兩個法律條款的目的不同:法國民法典第16-1條的目的在于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而法國民法典第9條的目的則僅僅在于維護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
為了防止行為人或者法官將他們規定的某一個或者某幾個法律條款、法律文本解讀為非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條款、法律文本,在規定這些法律條款、法律文本時,法國立法者近些年來采取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做法,這就是,他們直接在法國民法典當中宣告所規定的這些法律條款、法律文本在性質上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無論是在規定一般法律條款、一般法律文本時還是在規定民法的某一個一般原則時,均是如此。
在法國,民法學者將法國民法典第16條、第16-1條至第16-9條所規定的全部內容看作民法的一個一般原則的主要內容,這就是“自然人的受尊重原則”(leprincipedurespectdelapersonnehumaine)。該種原則所包含的內容眾多,諸如: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尊重原則(Leprincipedurespectdeladignitedelapersonnehumaine)、人的身份的不得處分性原則(Leprinciped'indisponibilitedel'etatdespersonnes)和人的身體的不得處分性原則(Lepnciped'indisponibiliteducorpshumain)等。除了在性質上屬于強制性的法律規范之外,這些原則在性質上也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因為它們的目的在于維護人的尊嚴(dignite)、人的至高無上性(laprimautedelapersonne)和確保人受到應有的尊重。法國民法典第16條對該原則所維護的公共利益的目的作出了明確說明,該條規定:制定法確保人的至高無上性,禁止一切損害人的尊嚴的行為,擔保人自生命開始之日起就受到尊重。
在法國民法典新的第1104條當中,法國立法者也采取了此種做法,除了認定誠實信用原則能夠在契約的談判過程、契約的成立過程和契約的履行過程當中適用之外,他們還認定該原則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原則。在法國民法典新的第1104條當中,法國立法者之所以將誠實信用原則明確看作公共秩序性質的,是因為在誠實信用原則的問題上,民法學者之間存在不同的意見,某些民法學者認為,誠實信用原則在性質上并不是公共秩序性質的,例如AmaryllisBossuyt、AlbertFettweis和SteveGilson等人,已如前述。為了防止民法學者再將誠實信用原則視為非公共秩序性質的,在修改法國民法典時,法國立法者明確規定,契約法和民法領域的誠實信用原則在性質上不再是補充性的法律規范,而是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
五、具有公共秩序性的一般原則的類型
總之,就像所有的強制性法律規范在性質上并不都是公共秩序性質的法律規范一樣,所有具有強制性的一般原則在性質上也不都是具有公共秩序性的一般原則。判斷民法的一般原則在性質上究竟是不是公共秩序性的,其標準是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
根據此種判斷標準,民法的大多數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均不屬于公共秩序性的法律規范,僅少數一般原則在性質上屬于公共秩序性的法律規范。屬于公共秩序性的一般原則主要包括:平等原則自由原則、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人的受尊重原則、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原則、適用最有利于勞動者規范的原則、立法者明確規定為公共秩序性的一般原則以及法院在其司法判例當中明確認定為公共秩序的原則。這些一般原則之所以在性質上屬于公共秩序性的,是因為它們均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
在民法上,當我們說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在性質上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原則時,人們可能會心存疑慮,甚至完全不以為然,因為他們認為,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維護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然而,如果我們僅僅將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的維護看作該種原則的目的,則我們的此種看法顯然是錯誤的,同該種原則在民法一般原則當中的真正地位相差十萬八千里。
在歷史上,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地位顯赫,沒有任何其他原則能夠與其相提并論,包括平等原則、自由原則和人的受尊重原則。這些原則之所以無法與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相提并論,是因為這些原則均源自意思自治原則,是意思自治原則的派生物和應有的、必然的結果:人之所以是自由的,人之所以是平等的,人之所以是應當受到尊重的,是因為人不同于物、動物,他們有自己的“內心”,有自己的智識能力和個人意志,能夠抑制自己的激情,能夠支配和控制自己的沖動,在客觀法律限定的范圍內,他們完全能夠隨心所欲,按照其個人意志實施任何行為;因為他們能夠自由的作出行為,因為他們作出的行為是經過他們理智思考的結果,是他們深思熟慮之后作出的自愿選擇,因此,他們應當對自己作出的行為負責,這就是所謂的意志自由、意思自治。
在19世紀之前,人們普遍重視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認為它是民法的首要原則、最重要的原則。20世紀以來,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權利社會化現象的加劇,尤其是隨著立法者和法官對這一原則的限制越來越多,人們開始鼓噪此種原則的衰敗。不過,無論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是否真的衰敗過,迄今為止,該原則仍然是民法最重要的一般原則,因為其他的一般原則基本上均是建立在此種一般原則的基礎上,均是從該種原則當中派生出來的。所不同的是,這些派生出來的一般原則或者是該種原則的延伸,或者是該種原則的限制。例如,民法的自由原則和平等自由就是該種原則的延伸,權利濫用的禁止原則和公共秩序和良好道德原則就是該種原則的限制。
在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并不僅僅關乎私人秩序、私人利益或者個人利益,它也關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一般利益,因為,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達和商事的繁榮均是建立在該種原則的基礎上:因為民法實行意思自治原則和契約自由原則,人們就能夠憑借此種原則積極作為、努力進取,除了借此實現個人的功成名就之外,也借此實現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達和商事的繁榮。事實上,如果沒有該種原則,人類的文明和社會的進步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是該原則被PatrickMorvan視為公共秩序性原則的原因,已如前述,也是法國民法學者GhestinJacque、LoiseauGregoire和Yves-MarieSerinet認定該種原則具有憲法價值的原因。
在民法上,某些一般原則的目的究竟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還是私人利益,人們做出的回答可能與最高法院做出的回答大相徑庭。例如,對于利益的享有而言,沒有出生的胎兒被視為已經出生的人的一般原則就是如此。在討論該原則的性質時,人們可能會將該原則視為非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因為他們可能會認為,民法之所以實行此種原則,其目的在于保護胎兒的利益:讓胎兒在出生之前就能夠享有遺產繼承權、遺贈繼承權,讓他們在出生之前就能夠享有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等等。不過,在1985年10月10日的司法判例當中,法國最高法院認定,此種原則在性質上并不屬于非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而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因為它認定,保險契約的當事人不得通過自己的契約排斥胎兒所享有的遺產繼承權。
法國最高法院的此種做法無疑是適當的,因為表面上看,此種原則的確是為了保護私人利益即未出生的胎兒利益,但實質上,此種原則并不僅僅是為了保護私人利益,它同時還保護公共利益,因為胎兒的利益關系到自然人的法人格問題:如果胎兒的利益無法受到保護,則胎兒將無法享有法人格,而一旦胎兒的利益獲得保護,則他們就享有法人格。在民法上,自然人的法人格問題在性質上當然屬于公共秩序的問題,不屬于私人利益的問題。這是法國最高法院認定該原則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最主要原因。
在民法上,適用最有利于勞動者規范的原則似乎也不屬于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而僅僅屬于非公共秩序性質的原則,因為該原則的目的似乎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個人利益。不過,情況并非如此,因為該原則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個人利益,它也同時保護公共利益。因為這樣的原因,雇主與其勞動者所簽訂的勞動契約不得排除該種原則,無論是他們之間的個人勞動契約還是集體勞動契約,均是如此。也因為這樣的原因,民法學者普遍將勞動者與其雇主之間的勞動秩序稱為公共秩序性質的秩序,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公共秩序(lordrepublicsocial),以便與政治公共秩序和經濟公共秩序相對應。
除了這些一般原則之外,民法的其他一般原則均為非公共秩序性的,諸如:一般過錯責任原則、權利濫用的禁止原則、不當得利的禁止原則、欺詐使一切行為均無效的原則、時效不得對無法行為的人適用的原則,等等。因為這些一般原則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一般利益,而是為了維護私人秩序、私人利益、個人利益。
例如,一般過錯責任原則當然不是公共秩序性的,因為它的目的在于保護因為行為人實施的過錯行為而遭受損害的人的利益,當他人因為行為人實施的任何過錯行為而遭受損害時,他人均有權根據該原則要求法官責令行為人賠償其遭受的損害,如果行為人符合一般過錯責任的構成要件的話。再例如,權利濫用的禁止原則在性質上也不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因為它的目的在于保護因為行為人濫用其主觀權利而遭受損害的人的利益,當他人因為行為人濫用主觀權利的行為而遭受損害時,他人有權根據該原則要求法官責令行為人賠償其遭受的損害。
在民法上,欺詐使一切行為均無效的原則究竟是公共秩序性的還是非公共秩序性的,人們在不同時期所作出的回答并不完全相同。歷史上,此種原則被視為公共秩序性的,而近代以來,此種原則則逐漸被視為非公共秩序性的。在今時今日,民法學家對此種原則的性質存在不同看法,例如AmaryllisBossuyt、AlbertFettweis和SteveGilson等人就認為,該原則在性質上屬于公共秩序性的,已如前述。
第6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一、從物的角度分析動物的主客體地位
(一)物的概念
民法學上所稱為“物”,必須具有能為私權客體的屬性,既涉及一般意義上的有體物;也涉及某些法律規定的權利,如可以轉讓的不動產使用權、債權、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利等由法律確認的適用物的規則的財產權利。這是廣義的物的概念,狹義的物,即實物,被認為是物權法上的物,即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夠為人力所支配,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具有一定物質形體的物。
從物權法中對物的定義中我們就能能得出動物在民法中的客體地位,且動物應為客體中的物。首先,動物為人體之外的客觀存在物,不為人體的一部分;其次,動物能被人支配與控制,我們可以利用動物為我們的生產生活提供一定的服務,比如,利用牛耕地、馬拉車、狗拉雪橇等;再次,動物能滿足人的需求,例如,動物的肉蛋奶可以為人類食用,我們還可以利用動物的皮毛制成工藝品,供人們欣賞等等;其四,動物具有經濟價值,如前所述,我們可以利用動物的產品進行交易,獲得經濟價值;最后,動物可以獨立成一體,動物不依賴于人人而獨立存在。以此種種我們可以說動物為民法中的物。
(二)分析動物為民法中客體中的物
在民法典草案第一章的第1條明確規定了立法目的是“為了保障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團體合法的民事權益,正確調整民事關系,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根據憲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總結民事活動的實踐經驗,制定本法。”換言之,民法典所承認的法律主體仍然不包括動物。而在第111條中明確規定:“對動物尤其是野生動物的處分,不得違反自然資源法和動物保護法的規定。”與我們現行的《民法通則》相比,民法典更為強調對動物的保護,但是對其的規定仍然是放在了“權利客體”這一章,由此也看出了立法者對動物地位的態度。
另外,從民事主體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以及責任能力來講,動物在民法中的主體地位的說法是應予否定的。首先,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是法律賦予自然人得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適于出生終于死亡。法律并未賦予作為物的哦那個物享有這種資格。其次,動物不具有民事行為能力。從哲學上講,人區別于動物是因為人有大腦會思考,可以以自己的意識改造客觀世界,但動物卻不能。動物不可能依據其意思表示進行民事活動,而意思表示是民事行為的核心要素。我們更不能根據動物的年齡、發育水平來劃分其行為能力,不可能說一只2歲的狼不能捕捉食物,而3歲的就可以,如果2歲的狼捕到一只羊的行為屬于效力待定的行為,還需要受到其父母的追認,你不覺得這很荒謬嗎?還有就是,動物還能行使權嗎?難道動物也要享有姓名權、榮譽權、隱私權、財產權、著作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嗎?顯然這是很荒誕的!我認為,無論是從社會觀念還是在法律規定中,動物只可能是民法中的客體。
二、典型案例分析
既然動物為民法中的客體,動物加害該如何處理,能否得到精神賠償?國外有許多案例說明了這一點。例如,法國有這樣一個判例:被告的狼犬把原告名貴的短腿鋼毛犬咬死,因原告對被害動物具有重大感情利益,法院除判給原告購買新犬費用1400法郎外,另給精神損害賠償2000法郎。不過這個問題在歐洲引得法律界的爭論很大,沒有定論。
在我國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對此有規定:“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因侵權行為而永久性消滅或者毀損,物品中所有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請求精神損害的,法院應予以受理。”據此能引發精神損害賠償的物是特定紀念物,必須還要具有人格象征意義,寵物很難說具有“人格象征意義”,因此寵物主人無法以此條款規定為依據主張精神損害賠償。但對于野生動物為害鄉里,則要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特別保護區域內的動物屬于國家或者保護區域組織所有或者管領,當期侵害附近區域內的居民的人身或者財產安全時,應由國家或者保護區予以賠償。發生在四川熊貓保護區域內熊貓損害居民莊稼就屬于這種情況。但不受法律保護的動物就為無主之物,既然沒有主人,受其之害就只能歸天災啦,受害之人就只能買保險啦。
三、動物客體地位確立的意義
《德國民法典》第90a條后兩句規定:“動物非物。動物受特別法律保護。對于動物,在未有特別規定時,準用關于物的規定。”我國有學者依此規定認為,既然動物不是物,不是客體就只能是主體,此種觀點顯然“是荒謬的”。此項規定并不是將動物人格化或當成權利主體,而是指在表示對有生命的“物”的尊重,動物的所有人不得任意處分動物。在民法上,動物仍屬物,只是對動物的支配,應收特別法的規范,受到限制[11]。據此,除非有特別法規定,動物仍然受民法中關于動物的規定,表面上這似乎提高了動物的法律地位,但實際不然。這只是從政策上引起人們對動物的保護,維護生態平衡和物種的多樣性以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卻遭到垃圾大的破壞。特別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人們以破壞生態平衡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繁榮,實際上這是極不科學的,不符合自然規律不利于人類的可持續性發展。
雖然動物在法學地位上不斷提高,但其客體地位是不容動搖的。當今動物生存環境的惡化,絕大部分是由于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合理性造成的,人類只從自身利益出發,而忽視了其與動物的聯系,割裂了二者的統一性。所以我們應該從法律層面上對動物加以保護,但這種保護是完善對動物的立法保護,而非改變其客體地位。我們只需約束人類的行為,而無需創設法律主體這種復雜的法律關系來保護動物。創建動物的法律主體地位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效率的,這不符合當今高速發展的社會。
肯定動物在民法中的客體地位不僅對當今社會生活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完善我國立法工作、司法實踐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當然也是對人類作為萬物之主的尊重!
第7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內容提要: 作為典型合同體系例外和特別規則存在的無償合同,無論在成立(生效)要件、終止方式,還是在債務人承擔的義務標準等方面,其制度設計都與有償合同迥異。制度差異的背后隱藏著對不同價值功能的追求。有償合同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需要的行為規則,無償行為則是人們維系團結合作的渠道。即使是借助商業化的形式,無償行為也能在商業社會中創設出某種利他的、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從而實現促進財產交易和提升社會團結等多元價值。
現代合同立法以有償為原則,無償合同只是作為各國民法典典型合同體系中的例外和特別規則存在;理論上對具體有名合同的研究往往也集中于有償合同,尤其以買賣為范本展開,無償合同從未獲得過足夠的關注。既然現代市民已全盤“商人化”,法律行為以營利性為圭臬,而各國民法典仍對無償合同進行規制,其意義何在?民法對無償合同與有償合同究竟是如何區別對待的?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交往方式,無償合同在整體的社會交往中又具有何種價值?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嘗試展開一次民法學和社會學之旅。
一、無償合同與有償合同的區分
自羅馬法以來,各國民法中一直存在一些在本質上為無償的合同,如贈與、無利息消費借貸、使用借貸、委任、保管以及終身定期金等。這類合同的特點是,一方對另一方完全不負對待給付義務。此類單務、無償合同也被稱為“恩惠契約”或“好意型契約”[1](P.162),以示其與典型的交易行為之間的差別。
有償契約與無償契約劃分的哲學起源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關于交換正義和慷慨美德的倫理學說,基于這種學說,羅馬法中的合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交換正義行為,另一類則是慷慨行為。大部分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都沿襲了這一分類方案,其中,被視為在歐洲私法向近代的世俗理性法轉型過程中發揮承上啟下關鍵作用的格老秀斯的體系更接近常見的羅馬法類型。根據格老秀斯的看法,人們有時出于“施惠”(即無償地)而給予利益,有時為“互惠”(即為獲得利益)而給予利益。無償授予的利益有時立即轉讓,有時在將來轉讓(如贈與允諾);有時也會創設受領人方面的義務,如使用借貸和無償委托等[2](P.90-91,130-131)。這一分類直接影響了《法國民法典》,法典區分了有償合同與無償合同,并把作為契約效力基礎的原因(cause)理論建立在這一劃分的基礎之上。包塔利斯對此有下述描述:“什么是契約的原因?恩惠(行善)契約的原因就是恩惠自身。但在利己契約中,原因就是利益,也就是說,當事人簽訂契約所追求的好處。”[3](P.293)《法國民法典》第1105條規定了“恩惠契約”,即“當事人的一方無代價給與他方以利益”的契約;第1106條規定了有償合同:“當事人雙方相互負擔給付與作為的債務時,此種契約為有償契約。”對二者的區分標準,即如何判斷雙方的給付是否符合“均衡”(equivalence)的要求,法國民法學界歷來存在爭議,目前學術界占主流的觀點認為,認定一個合同有償還是無償,應綜合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來判斷。無償合同欠缺一般有償合同給付均衡的客觀“原因”,作為主觀原因的“恩惠意圖”在認定上存在明顯的不確定性,因此應施加嚴格的形式要求予以補充[4](P.98-99)。
德國學者認為,有償合同與無償合同是根據一方是否負有財產上的對待給付義務作出的劃分[5](P.303)。債務人負有的行為義務不屬于對待給付的范圍,如在附義務贈與中,受贈人為獲得贈與所從事的義務(一般為勞務或某些行為限制)并不被認為是獲得贈與的對價。雖然受贈人所負的義務僅影響到贈與人瑕疵擔保責任范圍,即其應在受贈人所負義務的范圍內承擔與出賣人相同的瑕疵擔保責任(《日本民法典》第551條第2款、《德國民法典》第524條、《瑞士債務法》第248條第2款),但這并不改變對贈與合同的單務無償性質的認定。基于此種標準,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給付有無對價意義,應主要根據當事人的主觀意思加以判斷。日本學者亦有采取此項標準者,如我妻榮教授指出,無論價金如何便宜,只要當事人認為其交易屬于買賣,其價金就具有對價意義;而贈與中,無論受贈人所負的負擔如何沉重,只要當事人認為是贈與,負擔就不具有對價的意義[6](P.44)。在我國臺灣地區,對“無償”的界定,史尚寬先生也持主觀標準,認為“無償謂不受任何對價。是否為無償,應主觀的決定之。縱令使相對人負擔多少之義務,如其負擔較其所取得之利益為微小,當事人不以為有對價之意義,仍為贈與。”[7](P.120)
無償合同具有如下特點:第一,無償合同僅限于民事行為。商法學者認為,“無償的行為與商法完全絕緣”。雖然商人也通過贈送禮品或者同意給予某種優惠條件,但依照“贈品回報理論”(theorie ducontre-don),其期待的是更加牢固地“拴住”顧客[8](P.49)。也正因如此,各國法律都對各種優惠銷售行為施加嚴格的規范,如法國 1986年12月1日法令對“有獎銷售”、“郵購買賣”的規制、1989年9月22日條例規范的“打折銷售”等。第二,無償合同的“無償”僅限于“不支付金錢價值的對價”。例如,在附義務贈與中,其中的“義務”不構成贈與的對價。當受贈人請求贈與人履行其義務時,贈與人不能以受贈人未履行義務為由進行抗辯,附義務的贈與不影響對贈與行為在民法上“無償”的定性。只是贈與人向受贈人給付贈與物以后,受贈人不履行所負義務的,贈與人有權請求其履行或者撤銷贈與。一般而言此處的“義務”,須為“人的行為”,不得為物之給付。
二、無償合同的民法學之維:制度梳理
無償合同與有償合同的機理極為不同,其要在民法中安身立命,必然要體現為一系列特殊的制度構造。以下對民法典或合同法中諸具體無償合同的微觀規則進行梳理,以期在宏觀上把握無償合同相對于有償合同的特殊品性。
(一)無償合同一般為要式合同或要物合同
1.無償合同的要物性
在無償合同中,由于作出給付的一方當事人并不能從對方獲得對待的財產給付,因此,就存在著優待該給付方以實現雙方當事人之間利益平衡的問題。對此,各國法律大多規定要么其意思表示必須采取特定形式,要么交付標的物方能使合同成立或生效。如合同法第210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第367條規定:“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464條規定:“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于無償使用后返還其物之契約。”
要物行為在羅馬法上是作為契約拘束基礎從特定形式到當事人意志演進中的過渡階段而出現的[9](P.84)。與古代法中的那些要式契約相較,要物契約的當事人即使不履行特定手續,只要交付標的物,債的關系亦屬有效。用梅因的話說,要物契約“第一次把道德上的考慮認為‘契約’法中的一個要素”,“在倫理觀念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10](P.187)現代契約法中契約自由原則的確立,使要物契約在古代法中所負有的將契約效力從程式中解放出來的作用當然不復存在,其在現代合同法中的存在價值就依存于保護無償合同中的利益出讓方。“要物合同之緣起,主要在于避免契約義務之發生,以保護無償契約當事人中只負擔義務的一方。因為在無償契約,例如使用借貸、無償消費借貸、無償寄托契約等,契約成立后的權利義務,片面地有利于契約當事人一方(例如借用人、借貸人、寄托人等),因此有特別規定‘非至完成標的物之交付,契約不成立’之必要,法律憑借要物契約的理論來緩和只負擔義務一方的不利益。”[11](P.50)
2.無償合同的要式性
無償合同的要式性在贈與合同上體現得最為典型。自羅馬法以來的大陸法系民法典幾乎都肯定形式對贈與效力發揮的作用。如優士丁尼《法學階梯》規定:“……當贈與人表示他的意思時,不問是否采取書面方式,贈與即告成立。聯的憲令規定這些贈與應以買賣為范例,轉讓是必要的;但是即使沒有轉讓行為,轉讓也有完全的效力,并使贈與人負有轉讓的義務……聯的憲令提高到五百個索拉杜斯,因此不超過此數的贈與,無須登記,又規定某些贈與,根本不需要登記,其本身完全有效……。”(注:[羅馬]查士丁尼:《法學總論—法學階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68頁。該條中所言“根本不需要登記”是指對于婚前贈與或贈與用于贖回戰俘的,雖超過限額,也可免于登記。)根據《法國民法典》第931條、《德國民法典》第518條、《意大利民法典》第782條第1款、第783條第1款的規定,(注:《法國民法典》第931條規定:“一切生前贈與行為應以通常契約的形式,在公證人前作成之,且應在公證人處留存契約的原本,否則贈與契約無效。”《德國民法典》第518條第1款前段規定:“為使以贈與的方式約定履行給付的合同有效,約定須經公證人公證。”同條第1款規定:“缺少前款規定的方式的,可以通過履行約定的給付加以補救。”《意大利民法典》第782條第1款規定:“贈與應當以公證的方式作出。如果贈與的標的是動產,則只有贈與人在公證書中指明該動產的價值,或者在另外一份由贈與人、受贈人和公證人共同簽署的文書中指明該動產的價值情況下,贈與才有效。”第783條第1款規定:“即使未依公證的方式進行,但只要進行了交付,則價格低廉的動產的贈與有效。”)贈與人與受贈人達成合意后,要么公證,要么履行,否則贈與合同不發生效力。因此不論在德國法上,還是在意大利法上,贈與合同均為要式合同。當然,該特征并不具有絕對性,公證形式的欠缺,可通過履行來加以彌補,此時贈與合同又具有了實踐合同的性質。根據《瑞士債務法》第242條第1項以及第243條第1項之規定,贈與合同必須采用書面形式始發生效力,如果動產贈與未采用書面形式,則贈與人將動產交付給受贈人也可補正贈與合同的效力。此立法例與上述法國、德國、意大利民法之規定并無不同。而對于不動產或不動產權利之贈與,依《瑞士債務法》第243條第2項之規定,經公證方發生法律效力。并且依第242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此公證具有嚴格性與絕對性,如欠缺此方式,即使將不動產或不動產權利登記于土地登記簿,贈與亦不發生效力。
日本民法與我國臺灣地區“民法”采取了另一種立法思路,雖未賦予贈與合同以要式性,但要式的贈與相較于不要式的贈與合同亦具有更強的法律效力。根據《日本民法典》第549條,贈與人與受贈人達成合意,贈與合同即發生效力。贈與合同顯然為諾成合同。并且,根據第550條的規定,對書面贈與,贈與人不得撤銷;而對非書面贈與,在合同履行前,贈與人得行使任意撤銷權撤銷贈與。(注:書面雖非贈與合同之成立要件,即贈與非要式行為,但書面形式采納與否,對贈與合同有重大影響。即采用書面形式的贈與不得任意撤回,反之則可任意撤回。因此,書面贈與較非書面贈與,其效力更為強大。學者因此稱贈與合同為準要式行為。參見[日]四宮和夫:《日本民法總論》,唐暉、錢孟珊譯,朱柏松校,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52頁。)日本民法上述規定對我國臺灣地區“民法”有重大影響。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408條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其一部已移轉者,得就其未移轉之部分撤銷之。”該條則不再區分動產贈與與不動產贈與,凡贈與合同,不論以動產抑或不動產為標的,均為諾成合同。只是除經公證之贈與或為履行道德義務之贈與外,在贈與物權利移轉前,贈與人可撤銷贈與。
(二)無償合同的拘束力較弱,債務人一般依法享有履行拒絕權
依照合同拘束力原則,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合同,但在無償合同中,普遍存在著允許當事人任意終止合同效力的現象。(注: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權分為兩類,一是一方當事人享有的任意解除權,包括:(1)承攬中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權(《合同法》第268條);(2)旅客運輸合同中旅客的任意解除權(《合同法》第295條);(3)旅游合同中旅客的任意解除權(我國臺灣地區“民法”);(4)勞動合同中勞動者的任意解除權(《勞動合同法》第37條);(5)保管合同中寄存人的任意解除權。(《合同法》第376條)。二是合同雙方都享有任意解除權,包括:(1)委托合同中雙方的任意解除權(《合同法》第410條);(2)不定期租賃中雙方當事人的任意解除權(《合同法》第232條)。對于第二類任意解除權的適用,學界認為應予以限縮解釋。如崔建遠教授認為,如果一個合同既包含委托的因素,又包含其他合同類型的因素而構成無名合同時,即不得適用《合同法》第410條來解除合同。參見崔建遠、龍俊:“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權及其限制—‘上海盤起訴盤起工業案’判決的評釋”,載《法學研究》 2008年第6期。
)這一設置使得無償合同的實質拘束力較有償合同明顯減弱,具體體現在:
1.贈與合同中贈與人的任意撤銷權
一如上述,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民法對贈與合同做出諾成性而非要物性的設計,但為保護無償出讓利益的贈與人,特賦予贈與人在作出贈與允諾后的不履行權,即贈與人享有任意撤銷權。如我國合同法第186條規定:“贈與人在贈與財產的權利轉移之前可以撤銷贈與。”大陸法系如此,英美法系亦如是。在美國合同法上,贈與人同樣可以撤銷其作出的贈與允諾。有學者指出,法律允許撤銷贈與允諾顯示了一種讓無償行為的當事人保持其既有狀態的政策,“如果不存在交易性質的交換(這種交換通常會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那么設置相應的法律機制就可能缺乏正當性。”[12](P.51)
2.無償委托合同中雙方當事人的任意解除權
各國民法均賦予無償委托合同的雙方當事人以任意解除權:大陸法系自羅馬法開始,委托合同即以無償為原則,(注:保羅《論告示》第32編:“如果不是無償的,則不存在委托。因為,委托契約的締結是基于幫助他人和友誼。收取報酬不符合委托的本意。”參見[意]桑德羅·斯契巴尼選編:《契約之債與準契約之債》,丁玫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隨后的《法國民法典》第1986條、《德國民法典》第662條均為如此。《日本民法典》第648第1款規定:“受任人除非有特約,不得對委任人請求報酬。”隨后在第651條規定委任雙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權。(注:該條規定:“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于不利于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因非可歸責于該當事人之事由,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不在此限。”)對于規定如此寬泛的解除權的原因,日本學者大村敦志指出,一是因為委任合同要求雙方具有高度的人身信賴關系。一旦這種信賴關系遭到破壞,當事人當然可以解除合同。此外,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是以委托合同的無償性為基礎的,而在雙方約定為有償的委任關系中,這一任意解除權當然應受到限制[1](P.138-139)
雖然有學者認為,任意解除權與委托雙方的信任關系相關,但縱觀各國立法,將委托合同規定為無償合同的立法例,一般會同時配合規定任意解除權。如《法國民法典》第2003條前段規定:“委任人得任意解除其委任”,第2007條規定:“受任人即以其拋棄通知委任人,而拋棄其委任。但拋棄如對委任人發生不利時,受任人對委任人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但受任人非受顯著的損失即不能繼續其委任時,不在此限。”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547條規定:“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雖然學界對此條的性質認識不一,但少數觀點認為,依此條委任雙方未約定報酬的,委任原則上為無償[14](P.523)。第549條同樣也配合以規定雙方的任意解除權。
3.無償消費借貸預約中貸與人的任意撤銷權
修正前的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475條規定,“消費借貸,因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交付而生效力。”該條明確將物之交付作為消費借貸的生效要件。不過將有償的消費借貸規定為要物契約是否適當,在臺灣學界一直遭受質疑,黃茂榮指出,消費借貸應區別其有償無償給予不同對待,即直接將有償的消費借貸規定為諾成契約;而無償的消費借貸則應回歸一般無償契約的基本立場,容許債務人任意撤銷[15](P.110)。對此,修正后的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475-1條規定,“消費借貸之預約,其約定之消費借貸有利息或其他報償,當事人之一方于預約成立后,成為無支付能力者,預約貸與人得撤銷其預約。消費借貸之預約,其約定之消費借貸為無報償者,準用第465條之一之規定。”即無償消費借貸預約中貸與人可隨時撤銷其約定。
4.使用借貸預約中貸與人的任意撤銷權
《德國民法典》第598條將使用借貸規定為諾成契約,但解釋上仍肯認貸與人交付借用物后享有任意終止權,這實際上即賦予了出借人享有毀約權[16](P.91)。我國臺灣地區“民法”修訂后刪除了原第465條,增設第465-1條規定,“使用借貸預約成立后,預約貸與人得撤銷其約定。但預約借用人已請求履行預約而預約貸與人未實時撤銷者,不在此限。”事實上也是采納此種做法。
(三)無償合同債務人的義務與責任較有償合同中債務人的義務與責任為輕
德國學者梅迪庫斯指出,基于“利益主義”(Utilitaetsprinzip)的原則,只有因合同而獲得利益的人才應負完全的責任,因此,無償行為的行為人往往是被減輕的,而且其負擔的義務往往也比較容易得到解脫[16](P.5)。由此看來,契約的有償無償其實涉及到法律對當事人的保護,并非無足輕重之事實[17](P.129)。具體體現在:
1.債務人僅例外承擔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在有償契約如買賣中,當事人所為之給付系為換取具有對價關系之對待給付,如一方給付不符合對價平衡,即應負瑕疵擔保責任(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354條、合同法第157條)。但在贈與、使用借貸、無償消費借貸等無償合同中,贈與人或貸與人原則上對標的物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如根據我國合同法第191條的規定,只有對附義務的贈與,贈與人才在附義務的限度內承擔與出賣人相同的責任以及只有贈與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證無瑕疵,贈與人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消費借貸中債務人的瑕疵擔保責任也因借貸是否附有利息而有所不同。依《日本民法典》第590條的規定,消費借貸只有在有附利息約定時,出借人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無利息的消費借貸中,借用人可以以有瑕疵之物的價額返還。只有在出借人明知借用物有瑕疵而不告知借用人時,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對使用借貸,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466條的規定,貸與人故意不告知借用物之瑕疵,致借用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即除此情形外,出借人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2.降低債務人所負注意義務的標準
(1)保管人的注意義務
傳統民法區分有償保管與無償保管而異保管人的注意義務。無償保管中,保管人對保管物盡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的注意義務即可。但對于有償保管(如倉儲合同),保管人則應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法國民法典》第1927條、《德國民法典》第690條、《日本民法典》第400條與659條、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590條、《意大利民法典》第1927條)。合同法也秉承了此立法精神,只是把保管人的注意義務降到更低的程度。第374條規定,“保管期間,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毀損、滅失的,保管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保管是無償的,保管人證明自己沒有重大過失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基于嚴格責任的一般歸責原則,對此條可作如下理解:第一,對于有償保管,在保管期間保管物損毀滅失的,保管人即應承擔除法定免責事由外的違約責任,無論是否具有過失。第二,對于無償保管,保管人僅需盡普通人的注意義務,保管人盡一般人所應盡的注意即無重大過失,從而可免責,但舉證責任由保管人承擔。因此,此處采納的是過錯推定責任。(注:基于此,保管人的法定免責事由包括:(1)《合同法》第117條規定的“不可抗力”;(2)《合同法》第394條規定,因倉儲物的性質、包裝不符合約定或者超過有效儲存期造成倉儲物變質、損壞的,保管人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根據“舉重以明輕”的法解釋規則,既然專事倉儲業務的倉管人可因這些事由而免責,則有償保管合同的保管人也應可因這些事由而免責。)
(2)受托人的注意義務
與其他無償合同類型不同,委托合同以人身信任關系為基礎,因此,無論有償委托還是無償委托,受托人均應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對此,《德國民法典》第161條、《日本民法典》第644條、《瑞士債務法》第398、328條均訂有明文。當然,也有立法基于委托有償性與無償性的不同仍然采取了區別對待的做法,如依《法國民法典》第1992條第二項的規定,受托人雖均負過失責任,但無償的受托人應較受領報酬的受托人為輕。因此,與有償的委托人相比,立法對無償的委托人應更為寬容(moins rigoureusement)。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535條規定,“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并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即要求有償委托人承擔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無償委托人只需負與處理自己事務同樣的注意即可。我國合同法第406條規定,“有償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過錯給委托人造成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無償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給委托人造成損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賠償損失。”與上述立法相比,該條進一步拉大了無償受托人與有償受托人所負注意的標準,即相較于有償受托人承擔善良管理人的抽象輕過失責任,無償受托人只承擔重大過失責任。
3.債務人承擔較輕的債務不履行責任
基于贈與合同的無償性,各國立法往往規定贈與人僅承擔較輕的債務不履行責任。如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409條規定,“贈與人就前條第二項所定之贈與給付遲延時,受贈人得請求交付贈與物;其因可歸責于自己之事由致給付不能時,受贈人得請求賠償贈與物之價額。前項情形,受贈人不得請求遲延利息或其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第410條規定,“贈與人僅就其故意或重大過失,對于受贈人負給付不能之責任”。第411條規定,“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不負擔保責任。但贈與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或保證其無瑕疵者,對于受贈人因瑕疵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義務”。這些規定從三個方面減輕了贈與人的債務不履行責任:首先,降低贈與人的責任標準。如第410條規定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責。其次,免除贈與人的責任。如贈與人給付瑕疵給付遲延,無論其為故意重大過失抑或輕過失,均不承擔債務不履行責任。非故意不告知瑕疵以及未保證無瑕疵,也不承擔加害給付責任。再次,縮減贈與人的責任范圍。如贈與人履行遲延時,受贈人不得請求遲延利息或其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我國合同法于第189條規定,贈與人就其故意或重大過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四)法律對某些無償合同存續期限保護的程度低于有償合同
1.定期贈與
定期贈與是指贈與人在一定期間內繼續向受贈人為贈與的贈與,其在性質上不僅為無償合同,而且屬于繼續性合同,具有人格信賴關系,因此當贈與人死亡或受贈人死亡時,除贈與人有反對的意思表示外,定期贈與消滅。如《日本民法典》第552條規定,“以定期給付為標的贈與,因贈與人或受贈人死亡而喪失其效力。”
2.委托合同
《法國民法典》第2003條規定,委托可因委任人及受任人的自然死亡(或民事死亡)、禁治產或非商人的破產而終止;《德國民法典》第673條也規定,委托關系因受托人死亡而消滅。合同法第411條也規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或者破產的,委托合同終止,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根據委托事務的性質不宜終止的除外。”委托特別是無償委托建基于當事人之間的信賴,無論一方當事人還是雙方當事人同時死亡,因此種信賴關系不復存在,委托合同皆隨之消滅。
3.使用借貸
借用人死亡,借用合同當然終止[1](P.164-165);[13](P.25)。如《日本民法典》第599條規定,“使用借貸因借用人死亡而喪失其效力。”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472條第4款規定,“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貸與人得終止契約:……四、借用人死亡者。”而在作為有償合同的租賃合同中,承租人死亡的,合同并不當然終止,而是由其同居人取得承租人地位,如合同法第234條規定,“承租人在房屋租賃期間死亡的,與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賃合同租賃該房屋。”依照我國臺灣地區學說及實務上見解,房屋租賃未以書面形式訂立的,除有“土地法”第100條所規定之事由的,出租人并不能收回房屋[18](P.259)。究其區別對待之緣由,是因為“無償之債的當事人間有高度之屬人的恩給考慮,因此,借用人死亡時,應讓貸與人有重新考慮的機會。”[15](P.97)
(五)無償合同相較于有償合同的其他明顯差異
1.有償合同的規定不能類推適用于無償合同
例如,各國法律均在租賃合同中規定了“買賣不破租賃”以特殊保護不動產特別是房屋承租人,但此項制度并不適用于房屋借用合同。我國臺灣地區“最高法院”1970年臺上字第2490號判例中曾明確指出,“使用借貸,非如無償的租賃之有‘民法’第425條之規定。”不能類推適用的原因在于:第一,承租人使用的物來自于對價的給付,而借用人則無償使用出借人提供的標的物,二者地位不具有類似性,對承租人予以特殊保護的政策并不能直接推及于借用人。第二,與無償行為相比,法律一貫對有償行為的受益人給與較高程度的保護,法律對有償的租賃合同中承租人的保護也并不能當然擴及于無償的借用合同中的借用人。第三,如果賦予借用人的債權以對抗力,將會對出借人的處分權構成過分限制,從而妨害物的使用效率的發揮,不符合經濟原則。
2.作為有償合同典范的買賣的規定可準用于其他有償合同,但作為無償合同典范的贈與的規定不能當然準用于其他無償合同
買賣合同在有償合同中居于“總則”地位,各國法一般設有對其他有償合同的準用條款(如《日本民法典》第559條、合同法第174條等)。由于各種無償合同各自有不同的配置,其獨立性較為明顯,法典中并不存在所謂關于無償合同的一般性規定,前述分析也只是為了精確地理解各個無償行為中配置的特別制度,并不是對無償合同一般規定的抽象化。可以說,有償合同具有共性,而無償合同則各不相同。贈與是無償、單務合同的典型代表,并非無償合同的一般規則,關于贈與的規定不能準用于其他無償合同。一如德國學者梅迪庫斯所言,“并非對任何提供某種無償給付的人,都可以減輕其責任。”[19](P.151)如在客運合同中,合同法第303條第一款關于乘客自帶行李的毀損滅失的過錯責任不適用于無償客運合同,而第302條關于旅客人身傷害賠償的嚴格責任歸責原則就不論客運合同是否有無償而一體適用。這一區別對待的基礎在于規范背后隱藏的債務人義務的不同,而非合同是否為有償。[20](P.113)。
三、無償合同的社會學之維:主要以贈與為例
上述論說只是從民法學視角揭示了有償與無償合同之間的制度差異,但這尚不能對無償行為的設定及存在原因給出更為深刻的解釋。無償行為在表面上與理論上關于交易本質和人性標準的“利己”原則這一基本預設并不相符,不過,它不但未因為與商業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不符而式微,相反卻歷久而彌新,有時還以更加宏大的敘事出現在現代生活中,如企業社會責任、慈善等都是在贈與、捐助等無償行為的基礎上才得以可能。這些都意味著無償合同在市民社會中具有促進交易之外的其他社會功能。
古典合同法理論從人類的社會行為中抽象出各個典型的交易關系并加以標準化,同時進行細密的法律規制,從而建構了典型合同體系。但在社會學的視野中,交換不限于“片斷式”的個體行為,也不限于確定的可折算成金錢的交換。契約不僅包括經濟上的交換,還包括其他的互動行為。各個具體的法律上的締約行為都只是廣義社會交換鏈條中的一個片斷而已。那些在民法中的被定性為“無償”的行為,也并非真的無“償”,無償行為中給予財產或價值的一方,同樣可能懷有某種互惠的動機和需求。只不過這些需求被“不用支付對價或報酬”的表面現象掩藏起來,行為人真正追求的東西其實在合同之外。各國民法中普遍允許贈與人撤銷對“忘恩負義”受贈人已做出的贈與行為,甚至不顧該贈與已履行公證、書面等形式的事實。(注:《法國民法典》第955條規定:“生前贈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始得以有負義行為為理由而予以取消:一、如受贈人謀害贈與人的生命時;二、如受贈人對贈與人成立虐待罪、輕罪或侮辱罪時;三、如受贈人拒絕撫養贈與人時。”《德國民法典》第519-532條、《瑞士債務法》第249-250條都有類似規定。我國合同法第192條規定:“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如果把視野放寬,就會發現贈與人同樣存有希望得到某種回報的期待。對此,大村敦志指出,贈與行為盛行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但其目的并不相同:那些在各種節日進行各種社交性贈與是互酬的,在社會學上具有“對待給付”的性質;在此情形中,贈與的“目的”不達即意味著合同的基礎喪失,贈與人當然可以撤銷其贈與表示。只有那些向公益團體的捐贈,才屬于真正無對待給付的贈與。(注:[日]大村敦志:《債権各論》,有斐閣2003年版,第166頁。我妻榮教授也認為,“人無償給予財產,不一定僅限于利他的動機,也有可能是出于回報以前接受的利益,為了期望對方將來作出貢獻,為了獲得名譽,其他各種有對價的或利己的動機。”參見[日]我妻榮:《債權各論》(中卷一),徐進、李雙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徐國棟教授的評價則更為直接,“就贈與合同而言,多數人通過把它界定為一種無對價的合同隱晦地歸人利他合同,但另一些學者認為,從長期來看,受贈人必定要對贈與人提供的恩惠作出回報,從而否定贈與合同的利他性。”(注:Peter M. 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US, 1964, pp. 93 ss.轉引自徐國棟:《人性論與市民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頁。)正因如此,美國學者Jane B. Baron將贈與稱為“贈與型交易”(gift-change)。不過,他也承認其與一般的商業交易行為存有一些差異,如贈與人不追求給付與獲取之間的準確均衡;由于贈與的目的一般在于建立人際關系和情感紐帶,因此,成本—收益理論不適用于贈與所依存的情感與道德世界等。(注:Jane B. Baron, Gifts, Bargains and Form, Indiana Law Journal, Spring, p. 196(1988/1989).)Melvin Aron Eisenberg則進一步指出,即使贈與涉及交易與互惠性,但它也與普通的市場交易存在根本的不同,這是因為,首先,贈與行為并不明確建立于交易之上,因此,即使它關涉互惠性,但也并非以此為條件;更重要的是,贈與所涉及的交易一般都建立于愛或道德的動機之上,即贈與必須體現情感關系或道德義務。如果說在普通交易中,物品是人們追求的目的,而贈與中,物品只是人們達到最終目的的手段而已。(注:Melvin Aron Eisenberg, The World of Contract and The World of Gift, California Law Review July, p. 844(1997).)
(一)贈與的社會功能
在現代生活中,贈與首先是人們社會交往的重要手段,一般人都喜歡通過互贈禮物來建立和培養良好的社會關系,贈與也是家庭成員之間表達親情和財產流轉的主要手段。贈與行為以及作為贈與行為后果的禮物的流動也一直是人類學家關注的對象。在他們看來,饋贈是一種具有二元性和通融性的行為和制度,其理想的實踐和發展條件存在于那些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基本關系是生產和再生產,人既是個體又是自身所屬群體代表的社會中。……這一行為幾乎見于所有的人類社會,從完全市場化的社會到與之相反的中央集權制社會中的某些行業或領域。簡而言之,只要是以人際關系解決事情的場合,便有饋贈[21](P.6)。法國社會學家莫斯曾開創性地提出,贈與與回禮之間的時間間隔正是商業借貸的原型。此外,通常情況下,回禮的價值必須高于所受贈品,而回禮中超過贈品的這部分價值就是利潤的起源。再者,接受贈與而讓回禮延后,懂禮節的人這時應該將某些替代品暫存到對方那里以示謝意,由此很容易聯想到這就是擔保的起源。總而言之,禮節性的贈與與回禮中包含著嚴格的義務與名譽感,從而形成了“信用”觀念,并為此后商業交易的公正性奠定了基礎[22](P.138)。這些研究表明,贈與與交換可能是同源的,并且同時發生。據此推測,人類在起始階段就有著進行物品互酬的欲望。我們只能這樣推定,最初存在的既不是進行贈與的名譽欲望,也不是希望進行交換的物質欲望,而是贈與和交換未被分離前的無償的互酬情感[22](P.140)。莫利斯·戈德列認為,一個社會的再生產需要三項原則和三個基礎的組合方可實現。那就是必須饋贈一些東西,出售或交換一些,再就是總是保留一些。在我們生活的社會里,買賣交易成了占主要地位的社會活動。賣意味著將東西與人徹底脫離;饋贈總是使贈出的東西保留著原主人的某種特性;而保留則是不讓有些東西與人分離,因為這些東西與人之間的聯系代表著人的歷史和認同,是應當傳承下去的,至少應傳承直至這一認同感不再產生之時[21](P.22)。饋贈的這一特性在現代有關饋贈的法律規定中仍有鮮明體現:
第一,目的性贈與。目的性贈與,是指自然人或法人接受一定財產,這些財產是作為與接受人的其他財產在經濟上相分離的特別財產而被管理,且為一定的目的而使用。如大學以法人的名義接受捐款,且款項只能用于安排獎學金或其他類似目的。這些財產就成為“管理這些財產且按照既定的目的使用其權益的受托人的財產”,拉倫茨稱之為“非獨立財團”,適用德國民法典第525條以下關于“附負擔贈與”的規定[23](P.249)。
第二,財團法人。有學者指出,大陸法系的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的區分,最終集中于是否承認社員可以改變公司的權利能力這一點上。社團法人(如公司)自然可以改變自己的經營范圍,但財團法人(如寺院、學校、醫院、基金會)則不能輕易改變章程和經營范圍[24]。財團法人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得人民可以超越個人的生存界限,以組織體的形式來完成一些長期或者永續存在、有意義的社會目的,促進公益事業,帶動社會發展,而不必因為捐助人的死亡或者捐助人財產的增減而受影響。”[25](P.1-2,219)“財團法人是財團設立者的契約延伸,這種契約不能被社員所改變。”[26](P.97-98)
對于這些做法,也許莫利斯·戈德列的說法頗有啟發意義,“我們今日的道德原則以及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行為都與饋贈、義務以及自由有關。所幸的是并非所有的人際關系都只限于買賣關系,凡物除去市價之外還有感情上的價值,而這還不是物的所有價值。我們還不至于完全落入商業道德的羈絆,今日社會中還有那么一些人,那么一些階層,他們還保留著過去的某些傳統,而我們自己,至少在某些場合,某些時候還在遵循這些傳統[21](P.131)。“任何社會及其分支群體和個體的進步在于懂得穩定社會關系靠饋贈給予、接受和回贈之道”[21](P.153),莫斯研究了原始社會的饋贈習俗之后得出結論說,是西方社會在最近時期把人變成“經濟動物”的,所幸我們還未完全如此行事。無論精英或平民,非理性的純粹消費行為俯首皆是,這些習慣甚至見于貴族階層,就像有道德、責任、科學性和理性的人一樣。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不像現在這樣,人變成機器,變成復雜而又斤斤計較算計的機器是近代的事[21](P.145)。日本社會學家山崎正和曾不無嘲諷地指出,“20世紀的人雖然試圖證明比過去任何時候的人都更真正誠實,但揭開表面就發現其中空空如也。”[22](P.257)
(二)其他無償合同的社會功能
羅馬法學家保羅《論告示》中就曾指出,“使用借貸更多的是出于自愿和方便他人,而不是出于對金錢的需要。”[27](P.95)這類合同在家庭和熟人社會中適用得較為廣泛。自然人間的借款合同多以無償、互助為其特征,立法者正是以此為出發點,才鍵入了要物性要件,使得當事人可以多加斟酌,在交付之前可取消意思表示。(注:張谷:“借款合同:諾成契約還是要物契約?—以合同法第210條為中心”, civillaw. com. cn/qqf/weizhang. asp? id=24212,最后訪問日期:2011 -02 -29)
結語
明確民法中有償行為與無償行為的界限,其意義不只是更加鮮明滿足商事生活的需求,同時也應當全面凸現市民社會的多元本質。現代商業社會中,“工業化就是竭盡全力地置換人們的行為模式”,“讓人們變得無名無姓”[22](P.275)。有償契約發揮著財產流轉增值的重要作用,契約基礎理論以“買賣”為范本加以創設,民法的商法趨勢等,提供了人成為“經濟人”所需的技術手段,使得現代私法視野中,主體“人像”已走上普遍商化的不歸路。同時,這也給以“個人主義”為標簽的現代性肇致了深刻的危機,人類學家所描述的那種田園牧歌式的社會團結與協作圖景已為個體的、冷冰冰的經濟人圖像所取代。在此背景下,有的民法學者甚至稱無償合同既不符合“公平”,也不符合“人性”。(注:如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謝哲勝教授認為,在有償合同中,各主體地位具有互換性且主體間相互支付對價,法律只需賦予各個主體基于其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實現主體的利益平衡。而在無償合同中,僅一方當事人即利益出讓方負給付義務,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義,亦不符合人性。參見謝哲勝:“贈與的生效要件”,載《臺灣法研究參考資料》1998年第8期。)但是,到底哪些人性才最接近真實的人性?在眾多關于人性的爭論中,哪種人性標準最具可信性?對此,莫斯的回答是:人們應當重新回到法律的堅實基礎,回到正常的社會生活的原則上來。既不能以為公民太善良、太主觀,也不能把他們想得太冷酷、太實際。人們對他們自己、對別人、對社會現實都會有一種敏銳的感覺。他們的行為舉止既會考慮到.自己,也會考慮到社會及其亞群體。這種道德是永恒不變的;無論是最進化的社會、近期的未來社會,還是我們所能想象的最落后的社會,都概莫能外[28](P.233)。
從法社會學家的角度,個人實際上從來就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他登記、加人、融人和受制于一系列群體,因此,對他而言,脫離這些團體生存是難以接受的”,這是“人類情緒和情感生活的基本事實”[29](P.64-65)。如果說以商事行為為代表的有償合同是為專門以獨立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人(商人)設計出的行為規則,那么將贈與等無償行為看作是為人們欲實現合作和關懷的那些人性而設計出的規則并無不當。鑒于法律行為“動機無涉”的特點,我們在目前的合同法體系所提供的這種“片斷”式架構中無法找到無償給予方所獲得的對待給付。無償行為或許能使人們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也維系了團結合作的觀念,培養人們維持共同生活所必須具有的互助品格。即使是借助商業化的形式,無償行為也能在商業社會中創設出某種利他的、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注:如法國最高法院認為,公司向顧客分發禮品這樣的無償行為,雖然表面上與商法相對立,但實際上仍是一種“從屬的商事行為”。因為任何一家公司都不是受‘贈與意圖’所推動,而是受發展商務的愿望所驅動。公司通過贈送禮品,創造出一種有利的氣氛,所以這并不屬于民法上的贈與。參見[法]伊夫·居榮:《法國商法》(第1卷),羅結珍、趙海峰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頁。)正因無償契約的存在,使得本具工具理性的合同法,也能同時實現促進財產交易和提升社會團結的多元價值。
注釋:
[1][日]大村敦志:《債權各論》,有斐閣2003年版。
[2][美]詹姆斯戈德雷:《現代合同理論的哲學起源》,張家勇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3]李中原:《歐陸民法傳統的歷史解讀—以羅馬法與自然法的演進為主線》,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4][日]大村敦志:《典型契約と性質決定》,有斐閣1997年版。
[5][德]迪特爾施瓦布:《民法導論》,鄭沖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6][日]我妻榮:《債法各論》(上卷),徐慧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7]史尚寬:《債法各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8][法]伊夫居榮:《法國商法》(第1卷),羅結珍、趙海峰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9]朱慶育:《意思表示解釋理論—精神科學視域中私法推理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0][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11]劉宗榮:《新保險法—保險契約法的理論與實務》,臺灣三民書局2007年版。
[12][美] E艾倫范斯沃斯:《美國合同法》(第3版),葛云松、丁春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3][日]加藤雅信:《契約法》,有斐閣2007年版。
[14]黃立主編:《民法債編各論》(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5]黃茂榮:《債法各論》(第1冊),中國政法大學2004年版。
[16][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7]林誠二:“買賣不破租賃規定之目的性限縮與類推適用”,載《中國法律評論》(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18]姜炳俊:“未訂書面之不動產租賃無期限限制”,載黃茂榮主編:《民法裁判百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9][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0]王雷:“客運合同中乘客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研究”,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4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21][法]馬賽爾莫斯:《論饋贈—傳統社會的交換形式及其功能》,盧匯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2][日]山崎正和:《社交的人》,周保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
[23][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4]鄧峰:《作為社團的法人:重構公司理論的一個框架》,載《中外法學》2004年第6期。
[25]陳惠馨等:《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探討》,我國臺灣地區“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5年印。
[26]張維迎:《產權激勵與公司治理》,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27][意]桑德羅斯契巴尼選編:《契約之債與準契約之債》,丁玫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第8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內容提要: 2002年《德國民法典》第253條修改后,以違約責任為基礎的非財產損害撫慰金請求權在一定的法益范圍內得到了一般性的肯定,但違約非財產損害的 法律 救濟僅以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遭受侵害為前提。德國法上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對其傳統的非財產損害賠償保護模式帶來了 歷史 性的變革;另一方面,囿于非財產損害法益范圍的局限性,該項變革的實際效果又非常有限。德國法上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的 發展 演進,為
隨著 經濟 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非財產損害[1]的法律保護日趨完善,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許多國家均強化了對人的非財產利益的救濟,從而彰顯人的主體價值和尊嚴,體現人這一法律主體的特殊地位。通常而言,非財產利益的私法救濟主要存在于侵權行為法領域,通過對人身權的法律保護加以實現;而伴隨著的法律的演進,在合同法領域也逐步出現了非財產損害的救濟渠道,即將非財產利益納入違約責任的保護范疇之中。就中國民事立法和司法現狀而言,非財產損害的侵權法救濟水平已經達到了比較高的程度,而違約責任的非財產利益保護則似乎仍舊停滯不前,尤其在思維意識方面,尚未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因而,以比較法為視角,從認識外國法律制度著手,或許能為完善我國相關制度提供有益的參考。本文以德國法上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的變革為實例,通過對德國法上相關制度變遷的考察,旨在為我國民法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鑒。Www..COM
一、德國民法對非財產損害的傳統保護模式
傳統的《德國民法典》對非財產損害的法律保護主要體現在兩個條文之中。首先,依《德國民法典》原第253條的規定:損害為非物質上的損害時,僅在法律有規定的情形下,始得要求以金錢賠償損害。[2]這里所指的金錢賠償,即撫慰金請求權。根據原第253條的規定,撫慰金僅得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形下才可被賦予。其次,依照《德國民法典》原第847條第1款的規定:在侵害身體、健康以及剝奪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受害人所受損害即使不是財產上的損失,亦可以因受損害而要求合理的金錢賠償。然而,依原第847條在法典中所處位置,其列于侵權行為的相關規定中,即此處所謂侵害身體、健康以及剝奪自由均應建立在侵權行為的基礎上。又因為侵權責任與合同責任在歸責原則、賠償范圍、消滅時效等方面存在相當的差別,以侵權行為為基礎保護受害方的身體、健康及自由等非財產利益的重要前提是侵害行為符合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并依侵權行為法應承擔相應責任。如果嚴格依照《德國民法典》上的這種傳統的保護非財產利益的模式,將會嚴重妨害非財產利益的保護。因為原第253條所設置的最主要的法定例外情形即是原第847條之規定,而后者所指乃侵權行為,因而非財產利益的保護主要放置于侵權行為法之下,合同法上幾乎不提供任何有效的保護。
顯然,這樣一種過于狹隘的立法模式給司法實踐帶來了長期的困擾。法院在實踐操作中無法完全遵守《德國民法典》之原有規定,特殊案件中它們往往規避原第253條的規定,發展出一些規則,以符合強化非財產權益保護的趨勢。在對既有規定進行規避時,德國法院主要采取兩種方向的努力:一方面,以《德國基本法》上保護基本人權的第2條、第3條為基礎,創造性地發展出了“一般人格權”的概念,從而突破了原第253條法明文規定之限制,而“一般人格權”最大的特點是其內涵的廣泛性及不確定性。[3]當然,以“一般人格權”的方式強化對非財產權益的保護仍然是在侵權行為法的框架內進行的,它以侵權責任作為“一般人格權”的保護基礎;另一方面,將一些非財產權益“商業化”,即將某些實質上為非財產性質的損害視作“商業化”后的財產來看待。[4]原第253條調整的范圍僅限于非財產損害,而非財產利益被“商業化”后即不再受原第253條的限制,從而實質上擴大了非財產權益的保護范圍。并且,這種“商業化”的方法并非僅以侵權責任為基礎,還包括了其他責任基礎如合同責任,因為財產損害是整個民法主要保護的對象。盡管法院在實踐中作出了種種努力,立法者也在局部進行了一定的變革,但尚不足以實現對非財產損害的充分保護,由此產生了對相關法律進行改革的現實需求。
這項變革需求最終在2002年4月18日德國議會頒布的于2002年8月1日生效的《關于修改損害賠償法規定的第二法案》[5] (以下簡稱《第二法案》)中得以實現,該法案對《德國民法典》原第253條及第847條作出了重大調整。原第253條的內容仍得以保留,但在此后增加了一款,即現第253條第2款:因侵害身體(body)、健康(health)、自由(liberty)或性的自我決定(right of sexual self-determination)而須賠償損害的,也可以因非財產損害而請求公平的金錢賠償。[6]《第二法案》同時取消了原第847條,即關于非財產損害金錢賠償法定性要求的撫慰金條款。這樣,在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方面,非財產權益的保護不再以侵權責任為唯一基礎,包括合同責任在內的其他責任同樣可以為非財產權益的保護提供依據,這被稱為《德國民法典》上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的一次“劃時代變革”。 [7]下文以違約的非財產損害賠償為研究對象,以合同責任為主要分析基礎,來探討德國法變革前后合同責任在非財產損害方面的地位和功能演變。
二、《德國民法典》傳統的突破:以 旅游 合同、雇傭合同為例
依《德國民法典》最初的規定,非財產損害的保護須以法律有明文規定為前提,而相關規定主要集中于侵權法領域。在合同法領域,違約的非財產損害賠償沒有法律上的明文規定,因而是完全被禁止的。然而,這樣一種過于僵硬的保護模式,導致了相當的非財產損害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護。
(一)旅游合同
具有代表性的非財產權益遭受損害的例子是旅游合同項下的假期利益。原則上,旅游合同中的假期利益(因旅游而帶來精神上的享受)屬于非財產權益,但《德國民法典》上最初并不保護此類利益。若死守此種思維定式,勢必會導致相關當事人的非財產權益無法得到適當保護。事實上,法院在處理相關案件的實踐中,逐漸發展出一套規避原第253條規定的方法,即通過假期商業化,使旅游合同下的假期利益具有財產性質,因而不再受到第253條對非財產損害賠償的特殊限制。[8]所謂非財產損害的商業化,是指凡是交易上可以支付金錢方式“購得”的利益(如享受娛樂、舒適、方便),依據交易觀念,此種財產即具有財產價值,從而對其侵害而造成的損害,屬于財產上的損害,被害人得請求金錢賠償。[9]
旅游合同項下以違約責任為基礎的案件,系追究違反旅游合同者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包括對“商業化”假期的賠償責任。顯然,將假期商業化是規避第253條規定限制的有效方法,但其在理論構成上(即方法論上)卻過于勉強。將事實上屬于非財產損害性質的假期視作具有財產性質,人為擬制的色彩過于濃重,實為應對法律之舉。同時,假期過分商業化也會引起法律上保護利益的失衡。前已指出,假期商業化的后果使得此種非財產損害可以獲得賠償,其所依據的基礎并不限于合同責任,理論上并不必然排除侵權責任。但倘若在侵權責任之下,使假期過分“商業化”,可能會引起侵權責任不適當地擴張,反過來,打破了法律上的均衡,有矯枉過正之嫌。事實上,法院對以侵權責任為基礎,使假期過分商業化的做法表示了反對,拒絕以假期商業化作為承擔侵權責任的依據。由此可見,盡管假期商業化為旅游合同上的非財產利益提供了強化保護,符合社會發展之需要,但該理論本身在構成上具有相當的缺陷,受到了學者的強烈批評。
1979年《德國民法典》修正時,增列了旅游合同,并在第651 f條第1項規定:游客在不影響其減少費用或者預先解約權的情況下,可以要求因不履行的損害賠償,但旅游瑕疵是基于不可歸責于旅游舉辦人的事由的除外;第2項規定:旅游無法進行或者明顯受損害時,游客也可以因無益地使用休假時間而要求以金錢作為適當賠償。通說認為,此種立法規定已不采取商業化的理論,將假期視為一種財產價值;此條文乃第253條所謂“雖非財產上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金額”之特別規定,[10]即遭受損害的旅游合同當事人可僅因符合該第253條之特殊規定,而得到假期這種非財產損害的賠償,無需再以假期商業化理論為基礎,請求賠償商業化的假期。一般認為,第651f條第2項規定了第253條第1款的其他法定例外情形,即對于非財產損害的金錢賠償不以身體或健康損害(修訂后第253條第2款)為要件。基于這樣的認識,衡量金錢賠償額度時不應只考慮勞動收入這一尺度,相反還應考慮其他情形,特別是應當考慮瑕疵造成侵害的程度。此時,個人的抵抗能力(如抵抗噪音的能力)也是應當考慮的因素。另外,對于無勞動收入的人,也要考慮其損害賠償請求權。[11]德國立法上的這種轉變值得關注。
(二)雇傭合同
除了旅游合同之外,雇傭合同也是明確可以請求賠償非財產損害的合同法領域,它主要體現在1998年《德國民法典》修訂時增加的第611a條第2款和第3款,即因雇主性別歧視而請求適當的金錢賠償這一特殊的賠償問題。[12]2006年8月18日,德國《平等待遇法》(allgemeines gleichbehandlungsgesetz)在長期討論后終于生效,該法是一部專門反歧視的立法,涉及勞動法、一般合同法及公法領域,其影響深遠。它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反歧視立法體例,并對現有的相關立法作出了一定的調整。該法生效的同時,《德國民法典》原第611a條、第611b條被廢除。《平等待遇法》對非財產損害賠償給予了更為一般性的規定。[13]該法第15條主要規定了雇傭關系下的歧視性損害賠償,包括財產損害及非財產損害的賠償;第21條規定了該法所涉及的其他私法關系(如針對一般大眾提供的貨物及服務的私法合同、 教育 、醫療治理)情形下的歧視性損害賠償,其中同樣包括非財產損害。[14]
(三)其他情形盡管如此,在旅游合同及雇傭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中,違約的非財產損害賠償仍然受到第253條的嚴格限制,幾無取得賠償之可能。這表明,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的突破僅限于旅游合同等極為特殊的合同領域,在其他合同中,即便也涉及合同當事人重大的非財產損害,這些損害仍然無法獲得賠償。以下這則發生于1998年的案件可以清楚說明德國法傳統上對違約非財產損害排斥之態度。
在預訂婚禮房間案[15]中,原告尋求在其針對被告提起的關于精神痛苦和折磨的損害賠償訴訟中得到法律支持。本案中,原告新娘與被告賓館締結了一份合同,約定被告在1997年6月27日晚上(也就是新娘結婚當天)為原告提供一個帶壁爐的能容納12人的房間。由于被告的過失,該房間在那天晚上已經被其他人提前預訂并使用了。由于未能獲得適當的替代房間,原告晚上計劃的婚禮慶祝儀式未能舉行。因為這場“災難”,原告連續數日以淚洗面,她的精神壓力達到了極限,并且遭受了心理上的打擊(psychologicalshock)。原告于是對其遭受的痛苦及折磨請求賠償3,000馬克。初審法院拒絕了原告的請求,理由是由于原告未遭受物質上的損失且不能對違約引起的痛苦、折磨給予賠償,原告的訴求不會得到支持。高等法院對此表示贊同。
聯邦最高法院在判決中論述道:“本案中,原告針對被告提起的賠償精神痛苦的訴訟請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47條不會被考慮,除非被告在違反合同未能保留房間之外,同樣給原告造成了符合823(1)條形式的身體上的或健康上的損害。然而,原告提起的訴訟并不構成此種訴求。
在此,我們不應考慮因違約引起的合同當事人精神狀態的干涉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包含在823條的保護性目的范圍內。即便該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初審法院對此并不認同),原告仍然未能對痛苦及苦難造成的損害賠償提供足夠的事實基礎。
首先,原告未能提起正確的訴訟,即原告以被告的違約行為造成了原告身體上或健康上的傷害為由提起訴訟欠準確。的確,給他人造成損害的當事人必須對其應負責的行為所造成的精神狀態的損害承擔責任,但需該行為引起的受害方精神上的損害足以構成身體上或健康上的損害。然而,諸如本案的一類案件中,因一方當事人的行為給受害方造成的精神上的損害如果能夠成為可以請求對方承擔責任的損害形式,該精神損害的種類、強度及持續期間必須明顯超過日常生活中不欲事件的正常反應,至少可以將其與疾病的效果相比較。本案中,原告聲稱她因為‘這場災難終日以淚洗面’且‘數周未能正常與人談論此事’,原告認為其承受的精神壓力達到了極限值并遭受了精神上的折磨(該觀點在沒有進一步事實證據證明的情況下不能被支持)的事實,未能顯示被告違反合同的結果達到了上述要求。
無論如何,即便根據原告的主張,該精神上的挫折達到了相應的嚴重性要求的程度,原告的請求仍不能成立,因為被告并不存在過錯。這里必須清楚的是,被告的過錯不僅應包括被告未能保留房間的違約行為的過錯,還必須包括該違約行為造成精神上損害結果的過錯,而這正是承擔責任的基礎。當然,在應用適當程度的注意時,酒店店主必須認識到由于其過錯未能為新娘的婚禮慶祝儀式保留預訂的房間會給新娘造成消極的心理反應,甚至是嚴重的傷害。然而,在沒有相反表示的情況下,被告不能預見的是在通常情形下,原告反應的種類、強度以及持續期間是如此嚴重以至于可以構成身體上或健康上的損害。”
其實,在其他國家的合同法上,與婚禮相關的合同糾紛案件往往較為可能獲得非財產損害賠償,因為與婚禮合同緊密相連的是重大的非財產利益,法律如果對這些重要的精神利益完全漠視,勢必會造成合同正義的落空,無法為合同當事人提供足夠的保護。而《德國民法典》原有的規定恰恰體現了一種完全悖離于現實的規則,法律與社會之間過分的脫節也必然會引起法律改革的呼聲,從而使法律規定跟上社會發展的實踐,有效地保護合同當事人的正當利益。這種改革一定程度上在2002年的《第二法案》中得以實現。
三、《德國民法典》2002年修正后的情形
(一)條款的變化
《德國民法典》原第847條位于第二編(債務關系法)第八章(各種債務關系)第二十七節(侵權行為)中,屬于債法分則中一般侵權行為的規定,因而,相關的非財產損害僅得以一般侵權行為為基礎請求賠償。修正后的《德國民法典》將原第847條的主要內容轉移到了第253條第2款之中,該條在民法典中的地位處于第二編(債務關系法)第一章(債務關系的內容)第一節(給付義務),屬于債法總則,其規定適用于債法調整范圍內的所有情形。盡管原第847條第1款與第253條第2款在內容上大體相似,但由于編排體例的變化,使得符合相關條件取得損害賠償的依據不再局限于侵權行為,而是擴大到包括合同責任、危險責任在內的整個債的范圍。另外,《德國民法典》第249條至第255條涉及的是一般性的損害賠償的規定,它們不僅調整債法分則中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內容,也調整其他各編中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內容,甚至還調整《德國民法典》之外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內容。由此可見,修正前后的變化異常重大,致使原來適用非常狹隘的條款,在相當廣泛的范圍內得以適用。
(二)修正理由
關于撫慰金條款修改的理由,德國聯邦司法部在《關于修改損害賠償法規定的第二法案草案》中給予了充分的說明。第一,這種調整是為了消除法律上的不一致狀態。修正之前,撫慰金請求權僅存在于一般侵權行為的過錯責任中,而在不取決于過錯的危險責任以及合同責任的范圍內(除少數例外情形)均不存在撫慰金請求權。由于在危險責任與合同責任范圍內排除了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因此,在這些領域內發生的身體、健康和自由受到嚴重侵害而造成的非財產損害均無法獲得賠償。另外,從受害人的角度看,同樣是非財產損害,由于責任基礎不同,在侵權行為領域得到賠償,但在其他領域則無法獲得賠償,造成了法律上的差別。修正后的法律正是創設了一個統一的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在身體、健康、自由或性的自我決定受到侵害時,不再區分責任基礎,而均可給予金錢賠償。第二,這種調整也是為了與其他歐洲國家的法律相適應。如在法國和英國,并沒有將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限制在合同之外的明確規定。[16]
事實上,上述理由并不充分,就第一點理由而言,考慮到各個法律領域自身的特點,尤其是侵權法與合同法之間的種種差異,對同樣的損害在不同的責任基礎上予以區別對待實乃常事。比如,懲罰性賠償在侵權法領域大量存在,但在合同法領域則一般認為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侵權法除了補償受害方的損失外,有時還兼有懲罰、阻嚇侵權行為人的功能,而合同法救濟的目的主要是恢復雙方當事人利益的平衡,因而不具備懲罰的功能。這里恰當的問題似乎應該是:同樣的非財產損害在不同的責任基礎上絕對的賠或不賠是否符合債法相關部分的目的,這樣的區分是否過于絕對,尤其是在侵權責任與合同責任日益融合的今天。因此,第一點理由在理論上絕非完全不存在可議之處。[17]就第二點而言,《德國民法典》大幅度修正的目的之一便是與歐盟其他國家的法律更為接近,從而在歐洲法律統一化的進程中扮演更為重要和積極的角色。然而,就違約的非財產損害賠償而言,歐盟各主要國家的立法和實踐差異相當大,例如修正前的德國民法除極少例外,完全排斥違約的非財產損害賠償;而法國法上的做法則恰恰相反,法國法非常慷慨地在合同法領域給予非財產損害賠償,而與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不加區分;英國法上,早期著名的addis v.gramophone co ltd案[18]確立了違約非財產損害一般不予賠償的原則,但隨著社會的演進,逐步發展出了一系列的例外,主要包括合同的重要目的在于提供精神上的利益以及違約行為引起了身體上的不便或不適的情形。因此,就一定情形下給予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而言,德國法修正后與法國法、英國法較從前更為接近,但由于英、法之間模式的總體上的對立,德國法的修正很難說推進了歐洲合同立法的統一化進程,德、法、英三國之間違約的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仍存在相當的差異。
另外,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教授所著《侵權行為法》一書中,在論述《第二法案》對危險責任下非財產損害賠償改革時提及了兩點立法理由:第一,對于立法者來說,協調與歐洲鄰國的法律規定也很重要,因為在這些規定中,在保證痛苦撫慰金時,一般未根據過錯而有所區別。第二,立法者還強調了這一新規定對審判程序合理化的效果。現行法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在一定的領域內,創設一個以簡單客觀的風險分配為基礎的補償機制,而這一目的在原法中實際上卻無法實現,因為原法對痛苦撫慰金的規定,總是會涉及侵權行為法的過錯責任。[19]前述第一點理由前文已提及,但是,此處換了一種說法,即非財產損害的賠償不應以過錯為基礎(侵權責任),在非過錯的情形下,應同樣給予保護。《第二法案》的改革的確減少了德國與其他歐盟國家在非財產損害賠償領域的差距,但僅僅這樣的改革力度,離統一化還有過于遙遠的距離。并且,如果單從協調與歐洲其他國家的相關立法出發,德國的立法者完全可以放開手腳,而不是畏畏縮縮地將保護法益限定于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領域。德國法改革后對非財產權益的保護水平,實際上并不一定達到英國的水平。比如婚姻相關合同,葬禮合同等情形,德國法似乎仍然無法給予足夠的保護。就第二點理由而言,“創設一個以簡單客觀的風險分配為基礎的補償機制”的確是一個具有相當說服力的理由。但是,由此產生的問題是,為何立法者不可以將這樣一種簡單客觀的補償機制推廣到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領域之外的所有領域呢?如果將現有的機制擴張到任何非財產損害的情形,似乎更符合這種簡化的思維模式。
《德國民法典》上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的立法理由尚有可議之處,僅上述理由似乎并不能充分充分說明立法上顛覆式修正的理由,尤其是在思維嚴謹的德國法上,這樣大幅度的變革顯得尤為不成熟。[20]
(三)新條款適用條件
依據《德國民法典》第253條第2款,獲得非財產損害賠償的前提是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遭受了侵害。由于修正后的法律體例的變化,撫慰金賠償義務建立的法律基礎不再局限于侵權行為,而是擴展到了其他領域。與原第847條內容相比,第253條第2款除將適用條件擴大到“性的自我決定”上,并無明顯變化。而第253條第2款所涉及的身體、健康、自由的內涵亦與第823條第1款中之相關概念一致。[21]
1.關于侵害身體與健康。對身體的侵害是指對外部身體完整性的損害。與侵害身體相反,侵害健康是指對內部身體完整性的損害(即造成身體內部功能的紊亂)。侵害身體就是指損害身體的完好性。侵害健康是指任何身體機能不利的反常狀況的產生或加重,而是否導致痛苦或身體狀況的重大改變則并不重要,簡而言之,就是侵擾了一個人生理、心理或者精神的正常狀態,使其產生了病態。按照通說,只要損害了身體的完好性,為 治療 疾病而實施的手術也是侵害身體的行為,但通常這種行為都是免責的。
2.關于侵害自由。第253條第2款保護法益的自由,并非與一般的行為自由意義同一,通說將其理解為身體的活動自由,或者說是離開某一地點的可能性。實踐中,侵害自由最重要的案例是對人進行監禁,以及以違反法治國家原則的方式促使國家機關對人進行拘捕。如果某人因過錯引起 交通 堵塞,則其行為并不構成侵害他人自由,因為交通堵塞而受到影響的當事人僅僅是不能開動其機動車,其身體活動的自由并沒有受到妨害。[22]
3.關于侵害性的自我決定。《德國民法典》原825條的規定為:以欺詐、威脅或者濫用從屬關系,誘使婦女允諾婚姻以外同居的人,對該婦女因此而產生的損害負有賠償義務。原第847條第2款規定:對婦女犯有違反道德的犯罪行為或不法行為,或者以欺詐、威脅或者濫用從屬關系,誘使婦女允諾婚姻以外的同居的,該婦女享有相同的請求權(撫慰金)。修訂后的第825條為:因欺詐、脅迫或濫用從屬關系而誘使他人實施或容忍其(性)行為的人,負有向該他人賠償因此而發生的損害的義務。修訂后的第825條保護的對象有所擴大,即受害方主體不受年齡、性別及婚姻狀態的限制。原第847條被廢除,其主要內容移轉到修訂后的第253條第2款中,其保護的主體與第825條保持一致,亦有相應的擴展。因此,違反第825條造成非財產損害的,受害人可以第253條第2款作為依據,請求賠償非財產損害。事實上,法律修訂前后的變化,主要反映在保護對象范圍的寬窄上,具體內容并無實質性變化。值得注意的是,侵害性的自我決定現在并不限于婚姻之外,而是延伸到婚姻之內,受到侵害的配偶一方同樣享有請求權。
盡管依第253條第2款,非財產損害的可賠償性是以身體、健康、自由或性的自我決定遭受侵害為前提條件,但這并不意味著只要身體、健康或自由遭受了侵害,即可主張撫慰金請求權。依照德國法院的司法實踐,如果受害人的健康只是短時間且微不足道地受到損害,則不能請求撫慰金。對此,德國法院在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案例。并且,一般而言,只有在其他救濟方式不能為受害人提供有效保護的情況下,法院才會給予非財產損害賠償。[23]
(四)制度分析
2002年德國法上相關制度修正后,在一定的法益范圍內肯定了一般性的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因而,可將其稱之為“有限的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根據《德國民法典》修正后的第253條第2款,在身體、健康、自由以及性的自我決定的法益范圍內,承認以違約責任為基礎的精神損害撫慰金請求權,在一定范圍內,實現了“劃時代變革”。然而,與法國法的模式相比,修正后德國法的違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顯然要“吝嗇”得多,法國法上無論何種合同何種法益受到侵害,均得請求非財產損害救濟;而修正后的德國法則明文限定于“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受侵害的情形,只有在此范圍內才不考慮救濟的責任基礎。除此之外,即便存在嚴重的非財產損害,囿于第253條法定性的限制,很難得到 法律 上的救濟。
德國法上的這種模式并非首創,在2002年德國法修正之前,其他國家、地區已有類似的立法例,如瑞士、荷蘭及我國的 臺灣 地區等。《瑞士債法典》第九十九條(責任程度及賠償范圍)規定:“1.債務人一般應當對其任何過錯行為承擔責任。2.責任的程度依交易的具體性質而定,特別是在欠缺為債務人謀利益的故意時,應當考慮減輕責任。3.對上述問題,侵權法中有關責任 計算 的規定在適用范圍之內同樣適用于合同過錯行為。”根據該條第3款之規定并結合法典上的其他規定,均體現了在一定的法益范圍內,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同樣可以成立。[24]《荷蘭民法典》第6:095條規定:“根據損害賠償的法定義務應當予以賠償的損害包括財產損害和其他損害,后者以法律賦予獲得相應賠償的權利為限。”第6:106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權要求財產損害以外其他損害的公平賠償:a、該責任人有加害的故意;b、受害人遭受身體傷害、榮譽或名譽的損害或者其人身遭受了其他侵害;c、對死者未分居的配偶或者二等以內血親對死者的懷念造成傷害,但以該傷害在死者在世的情形下會產生他對榮譽或名譽損害的賠償請求權為條件。”[25]我國臺灣民法典中有關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條文,包括第18條第二項、第194條關于侵害他人生命權、第195條第一項(不法侵害他人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或其他人格法益的情形)、第977條第二項、第979條第一項、第999條第二項、第1056條第二項關于婚約、婚姻之解除或撤銷而對無過錯方所造成的精神損害賠償。但1999年修訂后的臺灣民法典于“債之效力”一節中增加了第227-1條,增訂“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人格權受損害者,準用193條至195條及第197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在債務人違約造成債權人人格權受損害的情況下,應當認為債權人可以請求精神損害賠償。[26]由此可見,盡管瑞士、荷蘭及我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具體法律規定上有所不同,但總體來看均與修正后的德國法模式大體相似。
修正后德國法模式的優點之一在于可以避免全面性的顛覆,將此種變革的影響力控制在一定的法益范圍內(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這對于傳統上排斥違約非財產損害撫慰金賠償的德國法來說顯得相對較為容易接受。換言之,在有限的法益范圍內肯認違約非財產損害的賠償請求權,而除此之外的其他非財產損害情形則加以否定,此種“中間路線”式的進路實乃妥協的產物,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緩減了持傳統觀念的人們的擔憂。
違約行為造成非財產損害的情形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其一,引起非財產損害的違約行為同樣符合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在此情形下,存在所謂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尤其是當違約行為侵害了合同當事人的人身權時,這種責任上的競合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前述 旅游 合同之下,旅客遭受了身體傷害的情形。按照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觀點,此種情形下,可由受害的當事人選擇以違約責任,抑或以侵權責任尋求法律上的救濟。其二,違約行為造成了非財產損害后果,但違約行為本身并不符合侵權行為的相關要件,無需承擔侵權法上的責任,而只需對違約引起的損害后果承擔責任,本文將此種情形稱為“單純由違約引起的非財產損害”類型。由于不存在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因而此類情形并不涉及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競合問題。比如,旅游合同下,并未造成人身傷害時的,無益度過假期的損害即為適例。由于不存在侵權責任,此類情形下的非財產保護途徑僅為違約責任,因而,當違約責任下不包括非財產損害救濟,相關精神損害將無從得到法律的保護。
分析修正后德國法上的違約非財產損害的制度模式,其重要意義在于:德國法上確立一般性的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的領域是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等法益遭受侵害的情形,除此之外的其他領域,一般并不承認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而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大致上可以對應于身體權、健康權、自由權及性自主權等人身權,換言之,違約行為引起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損害時,往往也可能構成了侵犯相關人身權的侵權行為。從而在多數場合下,德國法修正后的非財產損害保護大都可以歸類于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相競合的情形,在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存在競合的情形下,引入違約非財產損害的實際影響主要在于,為受害人提供不同救濟渠道的選擇,拓展在此類情形下非財產損害的救濟方法。由于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在構成要件、舉證責任、時效期間等方面存在著相當的差別,對于受害的合同當事人而言,選擇不同的責任基礎當有重大的實際意義。比如,前文所述旅游合同下,違約責任對痛苦和折磨形式的非財產損害不提供保護,而侵權法上則予以救濟;未伴有人身傷害的旅游合同下,可由當事人約定賠償損害的限額為旅游費用的三倍(第651h條);時效期間上,合同下的時效期間較短(一個月或者兩年),而侵權法上的時效期間往往較長,一般為三年。如此一來,便可以解釋緣何聯邦最高法院傾向于在旅游合同之中加入侵權法的責任。
然而,在單純由違約行為引起非財產損害的情形下,修正后的德國法尚難提供法律上的有效救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在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等法益受侵害時,往往存在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的競合,而極少出現單純由違約引起非財產損害的場合;同時,這些法律保護利益的范圍僅僅構成整個法律保護非財產利益的一個組成部分,加上這些法益的涵蓋范圍相對有限,相當部分的非財產權益無法納入這些法定保護利益的范圍,因而在單純由違約行為引起非財產損害的情形下,修正后德國法模式的效用仍顯得非常有限。實際上,越是單純由違約行為引起的明顯精神損害的情形,其對于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的需求度越高。德國法此次修正所采用的立法模式與現實保護非財產利益的強烈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
此外,德國法的修正模式還帶有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即如何有效地確定受違約責任保護的非財產法益的范圍,換言之,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的保護范圍是否具有理所當然的內在合理性?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一結論可以通過將德國法與瑞士法、荷蘭法、臺灣地區法進行比較后得出。瑞士法主要以人身及名譽為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保護的對象,就保護的范圍而言,仍然顯得比德國法更富于彈性;荷蘭法上,以“身體、榮譽、名譽或其人身”為違約非財產損害救濟制度的保護對象,由于立法上采用了較為靈活的語言,因而在法律適用中具有較大的解釋空間,比德國法的法益保護范圍要靈活寬泛得多;臺灣地區法保護利益的范圍系侵害人格權,范圍亦較德國法為寬。由此可見,德國法將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一般性的限定于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受侵害的范圍內,而將名譽、隱私等人身權利排除在外,其內在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五)案例適用分析:預訂婚禮房間案
由上分析可知,當出現身體、健康、自由或性的自我決定遭受侵害等非財產損害情形時,修正后的《德國民法典》不再固守原有的以侵權行為為依據的窠臼,而是將撫慰金請求權的基礎擴大到合同責任及危險責任,從而實現了德國債法上撫慰金制度的一次“ 歷史 性變革”,徹底變更了非財產損害賠償取得的依據,進而在合同責任、危險責任領域引入了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然而,應當注意到,德國法上的撫慰金制度的變化嚴格局限于身體、健康、自由以及性的自我決定法益范圍內,除此之外的其他非財產利益仍無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而且,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無論如何靈活地加以解釋,其所涉及的非財產利益只是眾多非財產利益中有限的一部分,大量非財產利益由于受到第253條第1款的限制而無法得到相應的保護。因此,從實踐的角度看,德國民法上撫慰金制度變化的“歷史性”意義也要大打折扣。尤其與英、法等國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相比,德國法上的變革仍然是謹小慎微的。
以前述預訂婚禮房間案為例,修正前的德國法院實踐不支持原告的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假定該案的發生時間是在2002年8月1日《第二法案》生效之后,原告提出的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能否得到支持?在前述法院的判決中,已經論證了侵權責任無法成為取得撫慰金請求權的基礎,加之其與危險責任無涉,此處需詳加分析的主要是合同責任。根據修正后的第253條規定,如果原告的身體、健康、自由或性的自我決定遭受侵害并存在非財產損害,原告即可以合同責任為依據請求非財產損害賠償。結合該案案情,新娘所受到的損害主要表現為“終日以淚洗面”、“達到了承受壓力的極限值”、“數周未能正常與人談論此事”等,作為婚禮的相關案件,新娘所遭受的這些精神上的損害完全屬于正常人可以理解的范疇。然而,除非有證據表明新娘的精神損害達到了侵害身體、健康及自由的程度,否則無法取得非財產損害賠償。對照上述關于侵害身體、健康、自由的界定,新娘遭受的感情上的痛苦很難納入相關保護利益范圍之內,即便擴張解釋也很難達到此種效果。因此,《第二法案》修正后的第253條盡管將責任基礎從侵權責任擴展到合同責任及危險責任領域,但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以外的其他非財產法益仍然游離于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外,本案即為例證。原告新娘所遭受的精神損害為社會上一般人所公認,而近乎“吝嗇”的立法模式使其精神撫慰金之請求幾無實現之可能,此與實質公平與正義明顯有違。環顧德國左鄰右舍,無論是一般性肯定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的法國法,抑或例外情形下給予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的英國法,毫無疑問都會在類似情形下支持原告的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以彌合其遭受的精神痛苦。以此視角觀之,盡管第253條的修正是歷史性的,但其重要意義更多體現在理論蘊味上,而非司法實踐中。換句話說,德國的立法者在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領域邁出的只是“理論上的一大步,事實上的一小步”。
四、結論
《德國民法典》頒布實施百余年來,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即撫慰金請求權)原則上僅存在與侵權行為法領域。盡管在旅游合同和雇傭合同領域,司法和立法均先后為撫慰金請求權開啟了有限的例外,但原則性的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并未得到法律的承認。在危險責任領域同樣如此。2002年《第二法案》生效實施后,在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遭受侵害的情況下,無論是以侵權責任,還是以合同責任、危險責任為基礎,受害方均可以請求非財產損害賠償。因此,在“身體、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決定”這些非財產利益范圍內,一般性的撫慰金請求權得以確立,而無需考慮其責任的依據,實為此百年法典在撫慰金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變革。經由這樣的變革,撫慰金請求權適用的標準得到了統一,法律不再區分合同與非合同、過錯與非過錯,使得相關法律的適用更為清晰流暢;同時,該變革使確認撫慰金請求權的基礎從侵權責任延伸到合同責任與危險責任,大大擴展了撫慰金的適用范圍,撫慰金請求權的主體在性的自我決定方面也有所擴大。法律上的變革強化了對受害人非財產利益的保護,簡化了對非財產損害的保護程序,適應了社會 發展 與進步的需要。德國法采用的此種變革模式不失為一種值得效仿且行之有效的法制漸進模式。目前,我國法學界對違約責任下非財產損害賠償的定性尚存在不同的認識,有完全排斥者,有完全肯認者,亦有有限承認者,因而,德國法上的變革為我們從觀念上認同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的合理性奠定了思想基礎,至少,違約的非財產損害賠償不再是天方夜譚式的空想。作為 中國 法主要借鑒對象之一的德國法經歷了如此的變革,勢必可以更新我國學者和司法者的觀念,消除他們心理上的障礙。德國法上的變遷為中國相關法律制度的演進提供了具體的 參考 模式:即我國亦可以嘗試首先在亟待保護的法益范圍內對非財產損害實施救濟,進而推進全面建立一般性的違約非財產損害賠償制度。如是,則既可以為相關法益的保護提供現實的渠道,又能夠避免全面變革可能帶來的震蕩與不安。
注釋:
[1]本文中所謂之非財產損害(non-pecuniary damage、non-financial damage、non-economic damage、non-patrimonial loss),與精神損害(mental sufferings、intangible loss)以及非物質損害(immaterial damage)在同一意義上使用,均指受害人的非財產性質的損害。對于“非財產損害”的內涵界定,參見程嘯:《違約與非財產損害賠償》,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2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3頁。
[2]《德國民法典》,鄭沖、賈紅梅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頁。本文所引用之《德國民法典》條文,除另有說明外,均以該翻譯版本為參照。
[3]關于德國法上一般人格權發展較為詳盡的論述,參見p.r.handford,moral damage in germany,27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49,1978.關于一般人格權的內涵界定,參見[德]迪特爾•施瓦布:《民法導論》,鄭沖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9頁。
[4]關于商業化的理論,參見下文旅游合同部分的相關案例和論述。
[5]bgbl.2002 i 2674.
[6]《德國民法典》,陳衛佐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頁。
[7]韓赤風:《精神損害賠償的劃時代變革》,載《比較法研究》2007年第2期。
第9篇:民法典的說法范文
內容提要: 基于意思自治原則,大陸法系傳統制度奉行顯名主義,故僅指直接,間接被稱為“行紀”。我國《合同法》第402條的規定系對“以被人名義”的擴張解釋運用之結果,但其第403條則借鑒英美法中的規則,承認間接在一定條件下得發生本人與第三人之間相互的違約責任請求權。這一做法,并非承認間接在任何情況下均得在本人與第三人之間發生直接的效果歸屬關系,故其并非對顯名主義的否定,且對既有制度具有補充和完善之功效。我國《合同法》所規定的“行紀”應解釋為行紀經營者所從事的商業活動,故該法第402條對之不得適用,而該法第403條則僅適用于非行紀的間接而不適用于行紀。
一、的立法安排
大陸法系民法上的制度所反映的,是實際生活中借助于他人行為而直接實現自己利益追求目的的現象。而人之行為的效果直接歸屬于被人這一法律安排,卻是在近代民法上才出現的。
理論上,將行為的效果直接歸屬于被人的被稱為“直接”。而“直接作為一種思維形態,直到19世紀才清晰地顯現出來。它的對立物,是間接。”{1}有關資料表明,基于“任何人之所為,均是為其自己作為”的原則,早期羅馬法完全不承認,{2}直到羅馬法后期,通過各種例外規定,才出現某些觀念的萌芽。{3}至歐洲中世紀,間接在商事活動中逐漸被廣泛運用。間接的特點,是法律效果首先直接歸屬于行為人,然后通過物權或者債權讓與以及債務承擔或者免除而轉移給本人。1804年《法國民法典》關于“委任契約”的規定,奠定了近代民法上(直接)的基礎。該法典第1988條規定:“委任人對于受任人依授予的權限所締結的契約,負履行的義務。委任人對于受任人權限外的行為,僅在其為明示或默示追認時,始負責任。”盡管這部法典并沒有確定獨立的概念,但該法典對于委任契約獨立性的承認,實際上也承認了包含在委任中的的觀念。也就是說,如無觀念的存在,委任契約便缺乏獨立存在的基礎。而法律允許某個法律行為可以在實際參加者的范圍之外發生效力,當然意味著法學上的一個重大進步,表明了契約從原始的極端形式主義中獲得了解放。
被德國民法設計為一種獨立制度的,僅為直接。而人以被人名義實施行為,則是行為效果之所以能夠直接歸屬于本人的邏輯根據:依據意思自治原則,僅在本人有直接承受行為效果的意思且為相對人明知的情況下,本人與相對人之間才存在真正的“合意”,行為的效果方可在本人和第三人之間直接發生法律效力。因此,人的身份必須為相對人所知曉和認可,而此種知曉和認可,則表現為人“以被人的名義”與第三人為法律行為。對此,《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句明確規定:“人于權限內,以被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被人發生效力。”后來繼受德國法上的制度的國家或者地區,莫不把“以被人名義”(理論上稱為“顯名主義”)作為區分行為與其他相似行為的主要標志。如《日本民法典》第99條第1款規定:“人于其權限內表示為本人而為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意大利民法典》第1388條規定:“由人以被人的名義并為其利益,在授權的范圍內締結的契約,直接對被人產生效力。”“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103條第1款規定:“人于權限內,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
依合同約定,受托人為委托人利益但以自己名義所實施的行為,構成所謂“間接”。間接中,受托人行為的效力直接在受托人與第三人之間發生,然后再由受托人將取得的權利義務轉讓給委托人,因而間接不會在委托人與第三人之間直接設定任何權利義務關系。雖然在間接中,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存在“委托”關系,委托人亦向受托人進行“授權”,但在德國法上,間接非為真正的,不會產生的三方關系,由于受托人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所為行為的效果由受托人自己承受,故該行為的效力并不受制于受托人的身份(權的享有及其權限),由此,制度中有關授權行為獨立性、無因性的設計,對之毫無意義。《德國民法典》未規定間接,但《德國商法典》對之進行了規定:“以自己的名義為他人買賣貨物或有價證券并以此為職業的人”稱為“行紀人”。(《德國商法典》第383條)盡管作為間接主要發生依據的契約具有委任契約的性質,但被稱為“行紀合同”,行紀人以自己名義實施的行為稱為“行紀行為”。
上述(直接)與行紀(間接)的立法模式,為多數大陸法國家和地區所繼受。
二、我國《合同法》對顯名主義的突破
我國民法理論整體上繼受了德國民法理論,將“以被人名義實施行為”作為的基本特征。《民法通則》第63條第2款規定:“人在權限內,以被人的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被人對人的行為,承擔民事責任。”間接被稱為“行紀”,適用行紀合同的相關規則。
但上述原則,似乎被1999年《合同法》第402條和第403條的規定所突破。該法第402條規定:“受托人以自己名義,在委托人的授權范圍內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403條規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的關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托人不履行義務,受托人應當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對第三人的權利,但第三人與受托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該委托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除外。”(第1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托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第2款)前述規定的出現,就筆者參加《合同法》立法過程來看,直接起因是為了解決我國外貿的需要。其內容與《國際貨物銷售公約》和《歐洲合同法原則》的規定基本一致。由于其規定并未限定適用范圍,故后來引起諸多討論及批評。
《合同法》的上述規則,大體上來源于英 美法及有關國際條約中的規則。
關于英美法上的制度,我國存在一些理論介紹,也有人將之與德國法上的進行比較研究。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其研究尚不算深人。比如,已有學者正確地指出,人們人云亦云地將所謂“區分論”(授權行為與基礎關系的區分)與“等同論”(人的行為視為本人的行為)作為兩大法系在制度上的基本區別,{4}但并未注意到此種來源于原聯合國法律顧問、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主席施米托夫有關文章{5}中提出的理論及其介紹上的模糊性和邏輯錯位。{6}又如,英美法上所謂“隱名”究竟是僅指人公開本人的存在但并不以本人名義實施行為,還是包括不公開本人的存在并以人自己的名義實施行為?有關研究也未達成共識。
事實上,在注重效果而不注重形式的英美法上,“”是一個包容廣泛的法律用語,一切受他人之托而為行為的人(包括經紀人、居間人等)均可稱為“人”。采用一種直觀而非抽象的思維方法,英美法原則上將視為一種契約的產物,{7}根據各種具體的“”行為設定不同的具體規則,除了形式多樣而且靈活的形式之外,英美法最重要的特色在于,無論人是否公開被人的存在或其姓名,其行為均有可能在委托人與第三人之間發生效力。在所謂“agent for an unnamed principal”(人公開本人之存在,但未公開本人之姓名,并在合同上寫明“本人”之類字樣)的情形,英國法認為,其合同責任應由本人承擔,而美國《法重述》則認為,除非人與第三人另有約定,否則人應承擔合同責任。{8}而在所謂“agent for an undisclosed principal”(人既未公開本人之存在,也未公開本人之姓名,而以自己的名義簽訂合同)的情形,本人在一定條件下享有所謂“介入權”(對第三人的請求權),第三人也享有所謂“選擇權”(選擇人或者本人行使請求權)。英美法的上述規則,為《國際貨物銷售公約》等國際條約所采納并對具體適用條件作出了一些更改。{9}
事實上,我國《合同法》第402條的規定并非是對“顯名主義”的突破。
我國《民法通則》僅規定“人以被人名義實施民事法律行為”,但并未就“以被人名義”的具體形式做出規定,理論上對此亦甚少討論。通常認為,“以被人名義”不僅要求人對相對人公開其人身份,而且必須明確將被人作為法律行為的一方主體(如本人為人與相對人簽訂的合同的一方當事人)。這一做法,似乎嚴格遵循了德國民法所確定的“顯名主義”原則。但實際上,《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在規定人“以被人名義”為意思表示的同時,明確指出“其意思表示不以明示被人為之者為限,依情況可斷定系以被人名義而為之者,亦適用之。”這就是說,“以被人名義”可以采用明示方法,也可用推定方法予以確定。在德國司法實踐中,根據客觀情況判斷“應以他人的名義發生效力的意思表示”的判例,比比皆是。甚至于在公開事實之時,人可以暫不公開被人亦即保留事后指明行為當事人的權利,只不過如果人事后無法指明被人,則必須根據《德國民法典》第179條有關無權人的責任的規定,自行承擔責任。{10}
從“顯名主義”的價值目標來講,這一原則意在保護與人為法律行為的第三人:在人未公開其人身份時,如其行為效果歸屬于本人,則不免使第三人在“意料之外”而與本人之間建立法律關系,明顯違背意思自治原則且有損第三人利益。但在人明示其人身份,或者存在足以使第三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人身份的情況下,雖人未指明被人是誰,或者人以自己的名義簽訂合同,則無相反意思表示的第三人顯然知道自己“身居何處”,故行為仍應有效成立。據此,“以被人名義”應采寬泛解釋,不僅包括人既公開其人身份亦公開被人姓名,而且包括人僅公開其人身份但未公開被人姓名。在法律行為的實施方式上,無論人以被人名義實施行為,或者人以自己的名義簽訂合同但標明其人身份,或者人以自己名義簽訂合同且未標明其人身份,只要有證據證明第三人明知或者應知行為的存在,且第三人在合同中未作相反約定,則行為均可成立,但在人未以被人名義實施行為的情形,如果依法律規定或者交易習慣不得在本人與第三人之間發生權利義務關系者(如作為營業的行紀行為—參見后文),則應除外。
對于人僅公開其人身份但未以被人名義實施行為的情形,我國理論界歷來存在認定其發生效果的觀點,司法實踐中也出現過相應判例,《合同法》第402條的規定不過是肯認了這一規則,其法律條文的表達從形式上看似乎是對英美法以及相關國際條約的移植或者借鑒,但就其內容實質,>:請記住我站域名/
但《合同法》第403條的規定,則有可能被認為是對“顯名主義”的根本性突破。
如前所述,顯名主義的立法根據在于意思自治原則的貫徹,由此,在行為為第三人所不知曉的情況下,法律不應當將受托人行為的效果強加于第三人,亦即不應當背離第三人的意志在本人與第三人之間強行建立權利義務關系。但依《合同法》第403條的規定,即使第三人在簽訂合同時對于人的身份一無所知,在第三人違約而導致受托人對委托人違約的情形,委托人享有“介入權”,得直接對第三人行使合同請求權,而在委托人違約而導致受托人對第三人違約的情形中,第三人享有“選擇權”,即可選擇直接對委托人行使合同請求權,如此一來,在“未露面”乃至對第三人一無所知的本人與同樣對本人一無所知的第三人之間,便發生了效果的直接歸屬關系,所謂“顯名主義”似乎就此不復存在。
但仔細分析,可以發現,所謂“間接”在我國立法上之被承認“可發生與直接相同的效果”的說法,其實是不準確的。與此同時,這一立法選擇,并非對“顯名主義”所欲達之宗旨的背離,而恰恰是對該原則的必要補充,同時順應了經濟生活發展的潮流,有助于減少訟爭,維護社會經濟秩序:
其一,直接最重要的特點在于行為可在本人與第三人之間直接發生效果歸屬關系,但《合同法》第403條的規定并未承認間接在任何情況下均得發生直接的效果。依照該規定,僅在本人違約且導致受托人違約以及第三人違約而導致受托人違約的情形,方可賦予本人以“介入權”以及賦予第三人以“選擇權”。如不具備法定條件即未出現法定的違約事實(不僅受托人對第三人違約,而且系因委托人違約而違約;或者,不僅受托人對委托人違約,而且系因第三人違約而違約),在本人和第三人之間根本不可能發生任何權利義務關系。由此,在特定情況下,法律賦予本人以“介入權”及賦予第三人以“選擇權”,其功能和目的僅在發生違約的情況下對本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救濟,而并不在于讓間接人的行為在本人與第三人之間發生直接的效果歸屬關系。故如認為該規定使顯名主義限于崩潰,并不屬實。由此,該規定非為制度的一般規則而純屬例外規定,由于其規則僅適用于間接中本人或者第三人違約的特定情形,故不構成對行為“須以被人名義進行”之基本特征的背離。
其二,鑒于間接的情形,本人與受托人之間存在關系,受托人系為本人利益而活動,受托人行為的效果最終將歸屬于本人,故本人對于因其自身的原因(對受托人違約)而對第三人直接造成的損害,自應當承擔責任。而在受托人向第三人披露本人的 情形,如果第三人依法繼續選擇受托人行使請求權,顯然尊重了第三人不予承認關系的意志,而如果第三人選擇本人行使請求權,則無異于第三人對實際存在的關系的事后認可。由此,法律賦予第三人以“選擇權”,完全符合意思自治的要求。相反,在因第三人違約而導致受托人對本人違約的情形,經受托人向本人披露第三人,如本人行使介入權,由“幕后”轉至“前臺”,有利于其正當利益保護而無損于違約的第三人。反之,如以僵化的方式堅持所謂“顯名主義”,無視本人與受托人之間實際存在的關系,則在本人違約而導致受托人對第三人違約的情形,第三人僅能追究受托人(表面上的當事人)的責任,于第三人不公平,而在第三人違約并導致受托人對本人違約的情形,本人只能依賴于受托人對第三人的請求權的實現而間接獲得救濟,于本人亦不公平。
由上可見,我國《合同法》第402條和第403條的規定,均有其合理性。在這里必須強調的是:承認間接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可以產生本人與第三人之間相互的違約責任請求權,完全不等于承認間接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在本人與第三人之間發生直接的效果歸屬關系。由此,該第403條的規定是對既有制度的有益補充和完善,不僅沒有破壞既有制度的規則體系和基本法理,而且有助于交易秩序的維護。
三、《合同法》第403條與有關行紀合同的規定的沖突與化解
《合同法》第414條對行紀合同所下定義是:“行紀合同是行紀人以自己的名義為委托人從事貿易活動,委托人支付報酬的合同。”這一定義及以下各條文就行紀合同所作規定,大體上相同于大陸法系民法有關行紀合同的基本規則。但在該法第403條有關間接規定的條件之下,行紀行為與該條文所規定的“受托人以自己名義實施的行為”發生了明顯的雷同。于是,有關“間接與行紀”的關系,便成為理論上討論的問題。
《合同法》第403條的規定是否與行紀合同的規定之間存在沖突?問題在于:①既然受托人以自己名義為行為應屬“行紀”,那么,此種行為何以被規定于“委托合同”而不規定于“行紀合同”?②行紀行為是否適用第403條之規定?
很顯然,有關“間接”與“行紀”的關系,必須重新加以清理。
有關資料表明,行紀制度因國際貿易的發達而產生于15至16世紀,其基本特征在于受托人為委托人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為商業上之交易。從立法上看,大陸法系各國家或地區均在其商法典或者民法典中對之進行了規定,只是在行紀活動適用范圍以及行紀人資格方面似乎有所不同。就行紀的適用范圍,有的限定為“物品”的買賣(《日本商法典》第551條),或“商品或有價證券”的買賣(《德國商法典》第383條及以下),或“動產或有價證券”的買賣(《瑞士債法典》第425條及以下),或“動產買賣及其他商業上之交易”(“我國臺灣地區民法”第576條),或未作明確限定(《意大利民法典》第1731條、《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990條);就行紀人的資格,不少立法將之明確限定為“以行紀為常業者”(日本、德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等)。與此同時,行紀合同準用委托合同的規定,為多數立法所肯定。
從理論上講,行紀合同實質上是委托合同的一種類別,亦即如單純看行紀合同之雙方的關系(委托人與行紀人),其無疑具備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但因行紀合同的受托人只能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為交易行為,故真正使行紀合同在多數國家的立法中被列為獨立于委托合同的一種合同類型的根本原因,在于行紀行為而非行紀合同本身。{12}至于行紀制度在商業活動中的價值,有學者將之歸納為六個方面:①委托人得享受與他人進行交易的利益而不暴露其身份,從而保護其商業秘密;②第三人只需信賴行紀人而無需慮及幕后的委托人的信用及支付能力,有利于交易的安全和便捷;③委托人得利用行紀人的信用、資產及知識經驗;④行紀人以自己的責任從事行紀活動,能夠靈活行使其權利;⑤由于行紀人對第三人直接承擔責任,故委托人不會因人之過失或者濫用權而遭受損害;⑥委托人和行紀人之間的關系準用委托合同的規定,故能發生于權的授予相同的功效。{13}
縱觀其他國家和地區有關行紀制度的立法以及相關理論闡述,行紀其實存在三個極為重要的基本特征:
1.行紀行為主要是受他人之委托而為他人利益從事動產(包括有價證券等)之交易。
如前所述,多數國家的立法將行紀行為限定為動產交易。鑒于行紀人須以自己名義直接與第三人為交易行為并取得標的物或者貨幣,而后將權利轉移給委托人,而不動產因其物權變動多須采用登記方法,如通過行紀活動從事交易將成本巨大且手續繁瑣(當事人將不得不完全不必要地進行兩次不動產物權變動登記),難以采用行紀的方法進行交易。為此,即使未將行紀行為明文限定于動產的立法,也未必具有允許將之適用于不動產交易的意圖。
2.行紀人須為“常業者”。
行紀起源于國際貿易的需要,為一種重要的商業中介業務營業,需有營業資本、商業資源、商業信用及專門經驗,并形成諸多商事習慣,故但凡采“民商分立”的國家(德國、日本等),均將行紀制度規定于商法典,為商行為中之一種,并明定行紀人僅以行紀為營業的商事主體(商人)方可充當。唯采“民商合一”的國家(意大利等)多未作此限定,但我國臺灣地區除外。
3.行紀人與第三人為交易行為的效果在任何情況下只能直接歸屬于行紀人。
行紀是一種專業經營業務,具有固定的經營模式和交易規則,故行紀人僅能以自己名義與第三人為交易行為并直接承受交易效果,行紀人亦可行使其所謂“介入權”即自己直接成為買受人或者出賣人,但在委托人與第三人之間,任何情況下均不可能發生直接的請求權關系。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傳統大陸民法理論將“行紀”等同于“間接”,其實是不確切的:如果將“間接”的概念用以描述受托人以自己名義實施行為且行為效果間接歸屬于本人的現象,而將“行紀”限定于“常業者”所從事的商業行為的話,那么,“行紀”僅為間接中的一種,凡不以行紀為“常業者”所實施的間接行為,非為行紀。由此,行紀行為應適用商法典或者民法典有關行紀合同的規定,而非行紀的間接行為,應適用民法典有關委托合同的規定。
據此,我國《合同法》第403條與其有關行紀合同的規定之間的沖突便可化解:前述我國《合同法》第414條將行紀合同定義為“行紀人以自己的名義為委托人從事貿易活動,委托人支付報酬的合同”,其中,依行紀的特點,將“貿易活動”按照慣例解釋為“動產買賣或其他交易”而不包括不動產交易,自可成立。而該條文雖未對“行紀人”的含義作出闡明,但根據其“為委托人從事貿易活動并收取報酬”的行為性質,并基于“貿易”一詞在我國通常指商業經營行為而非一般民間交易,也可將“行紀人”解釋為“以行紀為營業的企業或者個體商人”。由此得出的結論便是: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的規定僅適用于非行紀的間接,反之,行紀行為不適用該第403條的規定。
與此同時,我國《合同法》第402條有關“受托人以自己名義實施行為而為第三人所明知,得成立關系”的規定也不適用于行紀行為,自不待言。
注釋:
{1}[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1 ~ 672頁。
{2}參見[意]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317頁。
{3}參見周枏:《羅馬法原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616~618頁。
{4}參見鄭自文:《國際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第4頁;張艷:《商事法》,人民 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第8頁;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頁、第50頁。
{5}參見[英]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趙秀文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頁、第381頁。
{6}參見李錫鶴:“兩大法系之法理根據比較”,《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7}關于的理論基礎,英美法學者存在“合意說”、“權限說”和“權力說”等不同觀點。有學者認為,在英美法系,盡管“合意”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判斷關系存在與否的關鍵性因素,盡管被人和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大多因其相互之間的協議而產生,但現實生活中,既存在因合意而產生的,也存在不容否認的,還有法律自動構成的。參見徐海燕:《英美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頁。
{8}參見周林彬等:《比較商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頁。
{9}參見吳清旺:“范式比較研究”,《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
{10}參見前注{1},[德]迪特爾·梅迪庫斯書,第699頁。
{11}據此,筆者認為,可將人明示被人名義而實施的稱為“顯名”,將人未明示被人名義但其人身份為相對人所明知或應知的稱為“隱名”,隱名產生與顯名相同的法律效果。同時,將第三人不知也不應知人身份的情形稱為之“間接”。
{12}也有國家將行紀合同明文列為委托合同之一類,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705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