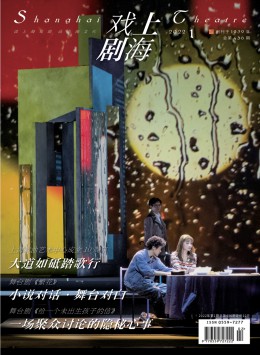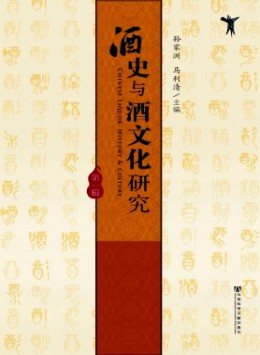關于經濟糾紛的起訴書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關于經濟糾紛的起訴書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關于經濟糾紛的起訴書范文
基金項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廳2013年高等學校訪問學者專項發展項目“恢復性司法理念指導下的社區矯正運作模式研究——一個功能主義的視角”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FX2013256。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非監禁處遇的社區矯正代表著犯罪矯正的未來走向,體現了刑罰的輕緩化、人道化和行刑的社會化、經濟化。截止2013年8月底,全國實行社區矯正的罪犯占全國罪犯總數的四分之一。①隨著兩院、兩部聯合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正式實施,人民法院不斷擴大非監禁刑的適用率,判處緩刑、管制和裁定假釋的比例越來越高。人民法院應當如何確保對被告人采用社區矯正的正確性,理論與實務界普遍認為,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是一項行之有效的保證措施。
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擬適用社區矯正前,由專門機構對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人格特征、社會評價、犯罪行為后果和影響等情況進行專門調查,并對其人身危險性和是否具備社區矯正的監管條件進行系統評估,從而為人民法院提供書面調查評估報告并提出是否適用社區矯正建議的制度。通過科學的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分析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使人民法院對犯罪人是否適用社區矯正的評判能夠建立在與犯罪人有關的、體現其再犯可能性的所有因素的綜合評價上,以降低社區矯正的適用風險,為社區矯正執行機構開展個性化的預防犯罪和矯正犯罪提供科學依據,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社區服刑人員再犯罪的風險。所以,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在社區矯正的適用階段扮演著“身先士卒”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步驟和過程,調查評估報告則為社區矯正執行階段開展個性化預防與矯正提供了科學依據。
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起源于美國的緩刑資格調查制度,到1930年,緩刑資格調查演變成為整個量刑提供判決前的調查報告,從而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審前社會調查制度。1950年在海牙召開的第12屆國際刑法及監獄會議積極倡導了這一制度,之后被許多國家效仿。我國的社會調查評估制度最早運用于審理未成年人犯罪領域。為貫徹《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北京規則》)的公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率先于2001年4月出臺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其中第21條明確規定審判機關在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前可以進行社會調查。隨后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于2002年、2007年頒布《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為辦案提供參考。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68條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未成年人審前社會調查制度。
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普遍適用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少年司法改革對這一制度的探索,給社區矯正的適用帶來了啟發。人民法院對“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適用緩刑、管制的比例越來越大。但“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社會危害不大”都屬于量刑情節,只有通過審前社會調查獲得較為充分的量刑信息,法官才能準確地判斷能否適用緩刑、管制,將罪犯放置于開放的社區環境接受社會矯正。在《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出臺以前,就有不少省市如江蘇、浙江、安徽、四川、湖北①等對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進行了探索和實踐。2012年,“兩院兩部”聯合下發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啟動程序、工作主體、調查內容等問題,這標志著我國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的正式確立。
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在當下的社區矯正實踐中被廣泛運用和實施,也取得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這一制度的形成和實施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還存在著諸多問題:因《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4條對相關部門進行調查評估的權力所設置的是“可以委托”的“授權性”規范,而不是“應當型”的“義務性”規范,導致了調查的隨意性;啟動主體主要為人民法院的單一性導致了啟動時間的滯后性;調查內容的不統一有可能會造成部分關鍵調查項目和調查環節的缺失,導致了調查報告就事論事、膚淺空洞、對犯罪原因的深層剖析和人身危險性的綜合判定的嚴重不足;調查報告的低質量無法為人民法院適用社區矯正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進而導致了調查評估報告效力上的不確定性。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對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的程序構建提出一些設想,先將整個程序設計為啟動階段、調查階段和調查評估報告的使用階段,然后分別進行程序構建。筆者從適用案件范圍、啟動主體和啟動時間三個要素來構建啟動程序;從調查主體、調查內容和調查方式方法三個要素來構建調查程序;最后從檢察院和監獄機關兩個方面構建調查評估報告的使用程序。
二、啟動程序的構建
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啟動程序是指由什么主體在什么時間針對哪些案件開始著手社會調查工作,其中適用案件范圍、啟動主體和啟動時間是啟動程序最重要的三個要素。
在英美,刑事審判分為“定罪裁判”和“量刑聽證”兩個相對分離的階段。在大部分案件中,一般是在法院判定被告人有罪之后、開始量刑之前,法院才委托內部具有相對中立性的緩刑官進行量刑前調查。少年被告人案件則由社會工作者單獨或者會同緩刑監督機構一起調查。究竟哪些案件需要進行量刑前調查,在美國,聯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在一些州當中,要對所有被宣告犯有重罪的案件都進行量刑前調查;在另一些州當中,僅要求對可能判處一定時間(如1年)以上刑罰的案件進行量刑前調查;還有的州規定對21歲以下或18歲以下的犯罪人和初次犯罪的犯罪人必須進行量刑前調查。需要注意的是,在進行量刑前調查的案件中,并不必然要判處犯罪人緩刑。而在不可能被判處緩刑的案件中,是否進行量刑前調查,由法官自己決定。[1](p104)
我國目前 普遍的做法即在人民法院立案經由承辦法官初步閱卷后,認為有可能被判處非監禁刑的案件,委托社區矯正執行機構——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社會調查,這是一種模仿英美的做法。仔細比較我國與英美國家在刑事審判模式、制度安排、機構設置等方面的不同,這種模仿和借鑒在我國存在著“水土不服”的情況。
(一)案件范圍
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的適用范圍主要是建議被判處緩刑和裁定假釋的案件。《刑法修正案(八)》明確規定緩刑和假釋前需要“考慮罪犯對社區的影響”、“不致再危害社會”,這為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但是對于判處管制和決定暫予監外執行前是否需要考慮罪犯對社區的影響,法律并沒有作出規定。筆者認為,人民法院判處管制是《刑法》等相關法律明文規定具有相應的量刑情節時就應當適用的刑罰,而且管制本身就是一種非監禁刑,不需要考慮社區影響,應當適用社區矯正。《刑事訴訟法》、《監獄法》明確規定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條件。是否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決定主體不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問題,而且監外執行的條件消失后,社區服刑人員就應回監獄服刑。因為社區矯正期間主要是強化監管,教育矯正和幫助其再次融入社會的作用不明顯。所以,判處管制和決定暫予監外執行,是因符合法定量刑情節而依法獨立作出相應的裁判,管制中的酌定情節也只對量刑期限有影響,人民法院作出這兩種形式的裁判,審前社會調查的重要性不大。而法律對于裁判緩刑、假釋的條件只有原則性的規定,審判人員需要更多地考慮犯罪人自身的具體情況,在專門調查的基礎上,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評估,應在全面綜合的前提下作出裁判。這些罪犯的具體情況大多數屬于酌定的量刑情節,所以,筆者認為,裁判緩刑、假釋的審前社會調查程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應作為裁判的前置性程序。
另外,筆者需補充兩點。第一,我國《刑法》規定緩刑的適用條件為:一是適用對象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構成累犯者;二是犯罪分子確有悔改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這說明緩刑只適用于主觀惡性不大、社會危害較小的輕微刑事案件,只有被判緩刑才能適用社區矯正避免監禁刑。然而緩刑的條件限制排除了那些法定刑期為三年以上,但被告人悔罪態度非常好、再犯罪可能性非常小的案件。筆者認為這部分案件如果通過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發現被調查人確實一貫表現很好,只是過失犯罪或激情犯罪,且悔罪態度好,積極賠償被害人,再犯可能性極小,本著修復被傷害的關系的目標,可以考慮借鑒適用國外的嚴格監督性緩刑。當然這需要修改緩刑的條件,增加屬于社區矯正性質的非監禁刑種(措施)。第二,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本身就是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發展而來。本著“教育、感化、挽救”的理念,對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論是否可能被判緩刑,應一律開展審前社會調查。
(二)啟動主體和啟動時間
因啟動主體的單一性造成了啟動時間的滯后性問題,已成為目前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制度的詬病之一。根據《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2002年《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和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我國針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啟動主體可以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辯護人和人民法院。而《社區矯正實施辦法》也規定可以啟動審前社會調查的主體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和監獄部門。
《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是刑事案件的偵查機關,有權依法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犯罪行為及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有觀點認為,公安機關在偵查案件時,就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所處社區群眾、單位職工都有接觸,因而公安機關可以在辦案的同時就啟動審前社會調查程序開展調查,還可以節約訴訟成本。[2]然而,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往往是本能地逃避制裁,認罪態度不一定好,被害人正處于憤怒期,在此階段開展社會調查,恐怕難以收集到真實可靠的信息。公安機關的走訪調查是為了偵破案件的需要,更為重視那些能夠證明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證據,對于那些涉及嫌疑人罪輕或罪重問題的量刑證據,公安機關并沒有足夠強大的動力開展調查和收集。[3]所以,公安機關的偵查職能和審前社會調查的性質目的不同,公安機關不適宜作為審前社會調查的啟動主體。
目前,全國檢察機關開展量刑建議改革,檢察機關完全可以通過量刑建議權提出適用非監禁刑的建議,提供法庭采信,而量刑建議的提出有待于調查收集豐富的量刑信息。所以,檢察機關啟動社會調查活動是為了在量刑建議中提出酌定量刑情節進而建議法官能否適用緩刑。刑事審判中的簡易程序一般是針對輕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自愿認罪,并對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而僅對被告人量刑的過程。所以檢察機關是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的前提下,啟動審前社會調查程序,以獲得豐富的量刑信息。對此,已有地區嘗試了此做法。如上海市浦東區人民檢察院與人民法院、司法局協商,主動承擔起審前社會調查工作,對可能適用緩刑的被告人、由人民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進行調查,并作為量刑建議材料提交給人民法院。[4]人民檢察院作為啟動主體將社會調查工作提前到審查起訴階段,也體現了人民檢察院對社區矯正的監督職能,避免了事后監督①的不及時和效果不佳的弊端。
辯護人則根據自身辯護職責的需要開展社會調查工作,制作書面材料提交法庭,以便法庭在量刑辯論時有充分的調查信息與公訴人(檢察機關)相抗衡,法庭將重點審理發生爭議的量刑事實。
人民法院啟動審前社會調查,容易造成先入為主、未審先定、合而不議的偏差,無法保證審判的公正和實質化的審理。而人民法院自行開展社會調查,會與人民法院的中立地位、司法被動性和證據裁判規則產生沖突。[5]英美國家是由人民法院內部的緩刑官開展調查,緩刑官地位獨立,有著較高的職業素養、職業操守和敬業精神,能夠保證調查信息的真實性和全面性。但是,我國的人民法院內部并沒有設置這種專職的“緩刑官”,也沒有設立作為司法行政機構的“緩刑官辦公室&rdq uo;。若由人民法院的法官擔任社會調查員開展社會調查,會存在因權力過于集中而濫用的可能。同時,基層人民法院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工作量本來就非常大,讓法官親自從事“審前社會調查”,不僅法官普遍不支持,而且也沒有基本的可操作性。[6]但是,有的案件人民檢察院認為不可能適用緩刑,而人民法院在審理階段又出現了新的證據,認為可能適用緩刑;或者一審判決實刑,但到二審認為可能適用緩刑。在上述兩種情況下,應賦予人民法院審前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權,但不是自行調查權。所以,人民法院不適合作為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但是必要時可以委托專門調查機構進行社會調查。
監獄管理機關是罪犯的管理部門。監獄根據罪犯的改造情況,對于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部分犯罪人,在執行一定刑罰之后,認為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就可以向中級以上人民法院提交假釋建議書。而罪犯的悔罪態度、改造表現、社會危害性才是決定能否假釋的實質條件。因為,監獄在管理過程中對罪犯的各方面情況比較了解,賦予監獄對擬假釋的罪犯調查“對社區的影響”,可以將調查結果與罪犯的悔罪表現、社會危害性評估等綜合考慮,制作假釋建議書,提交人民法院裁定。所以,監獄管理機關是適用假釋案件的審前社會調查啟動主體。
綜上分析,筆者認為,對于人民法院判處緩刑等適用社區矯正刑罰和相關措施的,審前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主體主要應為提出量刑建議的檢察機關和為被告人辯護的辯護人,其中檢察機關的審前社會調查是一種職責,辯護人的審前社會調查是一種權利。必要時,審判機關可以啟動審前社會調查程序。對于人民法院裁定假釋適用社區矯正的,審前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主體應為建議假釋的監獄管理機關。一般啟動時間應為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或監獄準備提交假釋建議書階段。啟動時間的前移是為了確保調查主體有充裕的時間開展調查,而不是匆忙應付了事。
三、調查程序的構建——關注被害人的權利
(一)調查主體分析
根據《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規定,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被委托主體)是縣級司法行政機關。但在實際工作中,真正進行審前社會調查的主體往往是基層司法所。筆者認為,制度設計由社區矯正的執行主體即基層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英美國家的量刑前報告是由緩刑官根據法官的要求準備的,而緩刑官負責緩刑犯的監督執行。我國借鑒了國外的做法。第二,由社區矯正執行主體開展審前社會調查可以使其提前了解擬適用社區矯正犯罪人的基本情況,有利于今后對其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和矯正,實現刑罰的個別化,提升社區矯正的效果。第三,可以實現社區矯正的適用主體(審判機關)和社區矯正的執行主體(司法行政機關)的無縫對接,有利于及時接收、管理、防止脫管、漏管的現象發生。但是,從學理上來說,該制度設計存在著不合理的因素;從實施的實際效果上看,也存在著諸多問題與不足。
第一,由社區矯正執行主體司法行政機關作為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違反了職能相分離的原則。審前社會調查是社區矯正適用階段的重要程序,調查評估結論對人民法院決定是否適用社區矯正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而英美國家規定由社區矯正執行主體緩刑官準備量刑前報告,那是因為緩刑官是法院內部相對獨立的司法調查員,法院內部又設立作為司法行政機構的“緩刑官辦公室”作為緩刑執行監督機構,他們都屬于法院系統。在我國不具備這樣的機構,我國社區矯正的適用主體和執行主體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國家機關,根據職能相分離的原則,司法行政機關不適合成為審前社會調查的調查主體。
第二,基層社區矯正機構的人員配備緊張、知識結構不合理、專業性不強等因素影響了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結論的客觀性和中立性。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工作是一項專業性非常強的工作,按照規定,每份評估報告需走訪調查評估對象的家庭、社區、鄰居、單位,聽取被害人、所在村(社區)的意見,非常費時費力(人力、物力)。另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動頻繁,異地犯罪的現象日漸增多,人戶分離情況嚴重,在客觀上加劇了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難度。基層社區矯正機構的工作人員大都缺乏法學、社會學等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人員素質較低,有時為了應付工作臨時組合,甚至社工、志愿者也加入到審前社會調查的隊伍中,導致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報告往往膚淺空洞、主觀傾向明顯,質量無法保證。
因此,筆者認為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調查主體應與啟動主體同一,即誰啟動誰調查,這種設計既能夠保證調查的時效性,又能夠保證調查質量。但人民法院作為啟動主體例外。社區矯正機構可以對是否具備社區矯正的監管條件進行調查,同時還應當作為調查的參與主體發表自己的意見。據筆者的實際調研發現,社區矯正機構開展審前社會調點關注的就是是否適合社區矯正的外部監管條件,而對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調查,因受制于工作人員的素質,調查評估結論簡單粗糙。
我國目前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從事“社會調查”的主體有:未成年人保護組織,如共青團、婦聯、青少年保護委員會、關系下一代委員會等;專職社會工作者或青年志愿者;社區矯正機構。[7]但問題是這些被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在從事本職工作之外兼職從事社會調查,難以保證其全身心地投入到調查中,因而也就無法保證調查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所以,社會團體組織不足以承擔社會調查的重任。從長遠考慮,我國應該設立專門從事審前社會調查的機構,以確保調查評估結論的中立性和專業性。筆者建議在人民法院系統內部設立專門的刑事案件審前社會調查委員會(或者專職的調查員),同時建立兼職調查員專家庫(具有一定心理學和教育學知識的人),讓其提供專業方面的指導和幫助。
(二)調查內容
緩刑前的社會調查評估內容和假釋前的社會調查評估內容是有所區別的,但總體來說應包括以下兩方面內容。其一是犯罪人自身情況的調查,其二是是否適合社區矯正外部條件的調查。
對犯罪人自身情況的調點首先應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在人身危險性調查中最重要的是被告人或罪犯的認罪悔罪表現,包括對犯罪行為的認識、悔過 態度和賠償損失情況。如果認罪態度好,悔罪表現突出,表明行為人犯罪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較小。其次是犯罪前的平時表現(包括工作學習表現、業余生活、鄰里關系、社會交往以及違紀違法情況)、主觀思想動態和個性特點。再次是家庭、單位、鄰居對其的社會評價。社會危害性調查包括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環境因素、被告人造成損害的社會影響、被害人的諒解等內容。
是否適合社區矯正外部條件的調查,包括家庭背景情況和社區公眾被害人的態度(社區環境)。家庭背景調查包括家庭關系情況(如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的基本情況,是否是離異家庭,配偶、子女、父母是否有違法犯罪情況,家庭關系是否存在經濟糾紛等)、家庭經濟狀況、家庭成員的態度。社區公眾被害人的態度主要調查被害人的心理承受狀況、社區(村)基層組織的意見、公安派出所的意見,未成年人還需調查學校的意見。
而那些被告人實施犯罪時的情況,如犯罪人的年齡、職業、精神狀態,犯罪動機、犯罪目的、故意過失、是否預謀、犯罪手段、犯罪時間、地點等內容,不應該是審前社會調查的內容,而是公安機關在刑事偵查時就應調查的內容,是作為定罪的證據。
辯護人的調查內容則是在全面研讀公訴方的案卷筆錄,洞悉公訴方的量刑建議的前提下,對起訴書所記載的量刑情節進行必要的調查核實,調查收集各種被公訴方所忽略的酌定量刑情節。
(三)調查的方式方法
當前,我國對審前社會調查評估的具體方式沒有明確的規定,社會調查評估應當如何實施還是一個空白。但調查方式是否科學合理直接關系到所獲取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全面性。[8]筆者在走訪調查時發現,實踐中的審前社會調查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填寫表格式的審前社會調查表,表格中內容的獲取采取個別約談、查閱資料、召開座談會、走訪等形式,如《浙江省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表》;另一種是直接以調查筆錄的形式出現,調查筆錄中有若干預設的問題,包括被告人、社區居民、派出所、所在村(社區)等調查筆錄,如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司法局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審前調查表》。兩種調查方式大同小異,但調查的具體過程我們無法知曉。
對此,美國緩刑官的量刑前調查過程為:首先,緩刑官要與被定罪的犯罪人進行一次面談,被稱為“最初面談”。這種最初面談通常是在緩刑官的辦公室中進行(如果犯罪人已經被拘留或逮捕的,就在看守所中進行)。在犯罪人未被拘留或者逮捕的情況下,最初面談也可能在犯罪人的家中進行,這樣的面談給緩刑官提供了了解犯罪人的家庭狀況等信息的機會。家庭面談不僅可以讓緩刑官通過實地觀察證實某些信息,還可以通過與犯罪人的其他家庭成員面談來證實有關信息。該面談的內容包括犯罪人的犯罪歷史、兒童時期的成長經歷、受教育程度、就業情況、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家庭情況等。其次,緩刑官試圖通過醫療記錄、雇傭記錄、社會服務部門的記錄、學校記錄等來核實這些情況。如果時間允許,緩刑官應與所有的有可能了解犯罪人情況的人進行面談,并核實信息的準確性。在一些案件中,緩刑官還應該到犯罪案件發生的地方,現場了解與犯罪案件的發生有關的情況。[9](p105)
但是上述調查過程并沒有反映出犯罪人的悔罪態度問題。筆者認為,犯罪人對被害人的真誠道歉并積極賠償的行為能較好地體現其悔罪態度,同時也能夠體現犯罪人不再犯罪乃至回歸社會的意愿,使其人身危險性大大降低;犯罪人積極賠償被害人,努力幫助被害人擺脫困境,這也是降低犯罪社會危害性的標志。被害人接受道歉和犯罪人給予的賠償并對犯罪人表示諒解,這意味著雙方的矛盾有所化解,因犯罪所破壞的社會關系得到一定的修復。此類信息的調查收集將對法官量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調查主體在對犯罪人面談后,應再與被害人進行面談,了解雙方和解的可能性。被害人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社區矯正的社會效果,因此,有必要在社區矯正審前社會調查過程中引入刑事和解程序,以使社區矯正盡可能得到被害人的認同,從而實現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增進社會和諧。[10]因此,關注被害人的權利和意見是調查程序中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
四、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使用程序的構建
(一)檢察機關使用社會調查評估報告的程序
檢察機關根據社會調查評估報告向法庭提出是否適用非監禁刑的量刑建議,連同起訴書、案卷材料一并提交法庭,作為量刑參考依據。檢察機關作為公訴機關,檢察官受刑事追訴地位的影響,其提出的量刑建議一般會具有程度不同的偏向性。[11]近期一些基層人民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即簡易程序審理已出現檢察官出庭支持公訴,法官則對控辯雙方存有爭議的量刑情節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查,引導雙方就量刑發表辯論意見的情況。[12]這種量刑模式的改革,改變了以往人民法院對簡易程序的“辦公室操作”模式,①有效地規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同時也糾正了檢察官的偏向性。在這種量刑模式下,法官必須充分考慮雙方提出的量刑建議,對雙方提供的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中有爭議的內容展開質證和辯論,兩造對抗的模式確保了量刑的公正性。需要注意的是,檢察機關通過量刑建議的方式適用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不能總是強調“法律監督”,而應從行使訴權的角度來對待審前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以使得辯護方的“量刑建議”與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具有同等的影響力。[13]
(二)監獄機關使用社會調查評估報告的程序
監獄機關根據社會調查評估報告,向人民法院提出是否適用假釋的建議書。實踐中的操作往往是人民法院對假釋建議書進行書面審理,人民法院只對監獄報送的材料進行審核即作出裁定。有的人民法院甚至會以罰金的繳納情況作為裁定假釋的決定性因素,而完全忽視罪犯在監獄的悔罪表現和對被害人的補償等因素。近年來,人民法院也出現了對一些特殊的假釋案件召開聽證會,進行公開、公正的審理,以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但哪些假釋案件需要召開聽證會還需進一步論證。若人民法院對假釋案件召開聽證會,那么社會調查評估報告中有爭議的內容就會被質證和認證,從而確保人民法院裁定假釋的公正性。
【參考文獻】
[1][9]吳宗憲.社區矯正比較研究(上)[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周立琴.淺議審前社會調查制度的不合理性[EB/OL].http://hubei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3820,2014-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