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論文關(guān)鍵詞 沖突法 沖突規(guī)范 法律規(guī)范 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
沖突法是國(guó)際私法的特有研究范疇,是國(guó)際私法的核心和靈魂。國(guó)際私法是調(diào)整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關(guān)系的,而沖突法就是一種主要的調(diào)整方法,通過(guò)適用沖突法規(guī)范找到該民商事法律關(guān)系應(yīng)受何國(guó)實(shí)體法調(diào)整,從而確定當(dāng)事人具體的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之所以稱之為沖突法,是因?yàn)樗倪m用在于解決各國(guó)之間(包括各區(qū)域之間)的民商事法律沖突問(wèn)題。在國(guó)際私法發(fā)展的歷史進(jìn)程中,沖突法理論的重要地位和深厚基礎(chǔ)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若將沖突法納入整個(gè)法學(xué)體系中,它的法理學(xué)基礎(chǔ)似乎就不那么清晰明確了,以至于法學(xué)界各學(xué)者觀點(diǎn)莫衷一是。本文通過(guò)對(duì)現(xiàn)有的關(guān)于沖突法性質(zhì)的理論觀點(diǎn)進(jìn)行再認(rèn)識(shí),旨在探尋沖突法真正的法理學(xué)基礎(chǔ),明確其法理地位,以求拋磚引玉,求教于專家。
一、問(wèn)題的提出與現(xiàn)有觀點(diǎn)
傳統(tǒng)沖突法理論認(rèn)為,沖突法是一種特殊的法律規(guī)范,是指明某一國(guó)際民商事法律關(guān)系應(yīng)適用何國(guó)法律的規(guī)范,因此又被稱為法律適用規(guī)范或法律選擇規(guī)范。它具有特殊的邏輯結(jié)構(gòu),由“范圍”和“系屬”兩部分要素構(gòu)成。
而傳統(tǒng)的法理學(xué)理論認(rèn)為,法律規(guī)范是一種社會(huì)規(guī)范,是由國(guó)家制定或認(rèn)可,具有特定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并以法律條文或其他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一般行為規(guī)則。法律規(guī)范包括實(shí)體規(guī)范和程序規(guī)范兩大類,規(guī)范本身通常由三個(gè)部分組成,即假定、處理、制裁,它們構(gòu)成法律規(guī)范的邏輯結(jié)構(gòu)。
可見(jiàn),傳統(tǒng)的沖突法理論雖然把沖突法界定為法律規(guī)范,但是沖突法本身的特征卻沒(méi)有一樣是符合法律規(guī)范的,甚至是相左的。試問(wèn)如此認(rèn)定沖突法性質(zhì)的法理學(xué)基礎(chǔ)何在?一個(gè)沒(méi)有法理基礎(chǔ)的沖突法理論又如何能在博大的法學(xué)體系里站住腳跟,在理論乃至實(shí)踐中發(fā)揮它應(yīng)有的作用呢?有鑒于此,筆者也查閱了許多相關(guān)資料,越來(lái)越多的學(xué)者開(kāi)始關(guān)注這一問(wèn)題,并形成了如下幾種主要的觀點(diǎn):
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法律規(guī)范所包含的范圍已經(jīng)不全面。在法理學(xué)中,應(yīng)該把法律規(guī)范分為法律規(guī)則和特殊的法律規(guī)范。法律規(guī)則就是那些包括規(guī)定權(quán)利、義務(wù)、責(zé)任標(biāo)準(zhǔn)和準(zhǔn)則的規(guī)范,而特殊的法律規(guī)范則包括法律選擇規(guī)范、法律適用規(guī)范,還有一些定義性、解釋性的法律規(guī)范,沖突規(guī)范就是其中的法律選擇規(guī)范。
另一種觀點(diǎn)雖然也否認(rèn)現(xiàn)有法理學(xué)理論的不足和相對(duì)滯后,但是卻認(rèn)為沖突法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法律規(guī)范,而就是一般法律規(guī)范中的法律規(guī)則。作為邏輯上周延的沖突規(guī)范,仍然具備法律規(guī)范邏輯結(jié)構(gòu)的三要素:“假定”體現(xiàn)在“范圍”部分,同時(shí)還包括隱含的“涉外因素”;“處理”體現(xiàn)在“系屬”部分;“后果”則體現(xiàn)在其他法律條文之中。
最近幾年,似乎又有一種新的認(rèn)識(shí)日趨成為主流觀點(diǎn)。這種觀點(diǎn)認(rèn)為沖突法的性質(zhì)不是法律規(guī)則,而是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范。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范是指那些不能單獨(dú)調(diào)整某一社會(huì)關(guān)系,即本身并不規(guī)定權(quán)利和義務(wù),但為調(diào)整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法律規(guī)則適用所需的那些法律規(guī)范的總稱。也就是說(shuō),這種觀點(diǎn)并不否認(rèn)沖突法是法律規(guī)范,只是不是法律規(guī)則或者什么特殊的法律規(guī)范,而明確其為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范。
二、質(zhì)疑與再認(rèn)識(shí)
綜合以上幾種主要的關(guān)于沖突法性質(zhì)的理論論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理論上的糾纏不清是源于學(xué)界并未深入研究有關(guān)沖突法的一些法理學(xué)基礎(chǔ)問(wèn)題,比如究竟沖突法到底是一種什么法?是法律規(guī)范?法律規(guī)則?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范?抑或是其他性質(zhì)?只有搞明白了這些基本問(wèn)題,才能為沖突法找到其法理學(xué)基礎(chǔ),從而更加完善我國(guó)的國(guó)際私法乃至整個(gè)法學(xué)體系。而若只一味關(guān)注部門(mén)法內(nèi)部關(guān)系,卻忽略整個(gè)法律體系框架內(nèi)法律之間關(guān)系,則自然阻礙了我們對(duì)沖突法性質(zhì)的法理思考。因此,我們有必要先從法理學(xué)的角度來(lái)認(rèn)識(shí)這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然后再更好地重新認(rèn)識(shí)沖突法的性質(zhì)問(wèn)題。
(一)法律概念的再認(rèn)識(shí)
在現(xiàn)代漢語(yǔ)詞典中,規(guī)范一詞的含義是明文規(guī)定或約定俗成的標(biāo)準(zhǔn),如技術(shù)規(guī)范、行為規(guī)范。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規(guī)定的標(biāo)準(zhǔn),即為法律規(guī)范。由于法律對(duì)于一般人的行為的規(guī)范性、普遍性以及強(qiáng)制性等特征,人們往往把法律稱之為法律規(guī)范,并用法律規(guī)范來(lái)代指整個(gè)法律。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沖突法與沖突規(guī)范往往被人們等同視之。然而從法的構(gòu)成要素角度來(lái)說(shuō),簡(jiǎn)單地把沖突法視為沖突規(guī)范的表述是不盡嚴(yán)謹(jǐn)合理的。筆者認(rèn)為,學(xué)者們習(xí)慣將沖突法表述為沖突規(guī)范,僅僅是在肯定沖突法的社會(huì)規(guī)范作用,但這并不代表沖突法在性質(zhì)上就是法律規(guī)范。因?yàn)榉梢?guī)范是一個(gè)法理學(xué)概念,它有自己的法理意義和邏輯構(gòu)成。
規(guī)則的含義則是規(guī)定出來(lái)供大家共同遵守的條例和章程,如行為規(guī)則,游戲規(guī)則。以法律的形式規(guī)定出來(lái)的規(guī)則就是法律規(guī)則。從漢語(yǔ)本意上,法律規(guī)則和法律規(guī)范表達(dá)的基本是同一個(gè)意思,甚至在我國(guó)的相關(guān)法學(xué)著作中,這兩個(gè)詞語(yǔ)也往往是相互通用的。而在西方法理學(xué)中,法律規(guī)范則是法律規(guī)則的上位概念,西方法學(xué)界不僅將這兩個(gè)概念加以區(qū)分,而且認(rèn)為法律規(guī)則僅僅是法律規(guī)范中的一個(gè)要素。凱爾森就提出:最好不要把法的規(guī)范與法的規(guī)則混淆起來(lái),因?yàn)榉ǖ膭?chuàng)制權(quán)威所制定的法的規(guī)范是規(guī)定性的;法學(xué)所陳述的法的規(guī)則卻是敘述性的。近年來(lái),受現(xiàn)代西方法理學(xué)的影響,我國(guó)學(xué)者也多主張法律規(guī)范是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則和法律規(guī)則三要素構(gòu)成。
(二)法律性質(zhì)的再認(rèn)識(shí)
在法理學(xué)上,沖突法并不符合法律規(guī)范的定義和構(gòu)成,因?yàn)樗炔皇且粋€(gè)單純的法律概念,也不是抽象的法律原則,更不屬于法律規(guī)則,它應(yīng)該是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
首先,沖突法一定不是一個(gè)單純的法律概念或一個(gè)僅具有指導(dǎo)性意義的法律原則。法律概念只是對(duì)法律用語(yǔ)所進(jìn)行的立法解釋,法律原則是調(diào)整某一領(lǐng)域或全部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概括性的,穩(wěn)定性的法律原理和準(zhǔn)則,而沖突法則是源于不可避免的法律沖突,一般來(lái)說(shuō),只要兩個(gè)法律對(duì)同一問(wèn)題做了不同規(guī)定,而當(dāng)某種事實(shí)又將這些不同的法律規(guī)定聯(lián)系在一起時(shí),法律沖突便會(huì)發(fā)生。經(jīng)濟(jì)和科技的飛速發(fā)展,加劇了人們?cè)诜缮系慕煌吐?lián)系,同時(shí)也加劇了這種法律沖突的凸顯。為了解決法律沖突帶來(lái)的法律適用上的難題,法學(xué)家們?cè)缭?3世紀(jì)的時(shí)候就創(chuàng)造出了這種特殊的解決方式——沖突法,即規(guī)定當(dāng)出現(xiàn)法律沖突時(shí)應(yīng)如何選擇適用法律的法。因此,沖突法遠(yuǎn)不是一個(gè)法律概念或法律原則所能涵蓋的,它是法學(xué)家們創(chuàng)造性地應(yīng)用法律的具體體現(xiàn),反映著法學(xué)本身的發(fā)展變遷。
其次,沖突法也不是法律規(guī)范中的法律規(guī)則。法律規(guī)則是對(duì)某種事實(shí)狀態(tài)的法律意義或法律效果作出的明確規(guī)定,是具體規(guī)定當(dāng)事人的某種權(quán)利、義務(wù)或責(zé)任的產(chǎn)生、變更或消滅的法律規(guī)范,具有極強(qiáng)的明確性和普適性。法律規(guī)則還有一套嚴(yán)密的邏輯結(jié)構(gòu),盡管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有“三要素說(shuō)”(假定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兩要素說(shuō)”(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新三要素說(shuō)”(假定、處理、法律后果)等不同見(jiàn)解,但都不外乎承認(rèn)法律規(guī)則有其特定嚴(yán)謹(jǐn)?shù)倪壿嫿Y(jié)構(gòu)。比如《合同法》第107條:當(dāng)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wù)或履行合同義務(wù)不符合約定的,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繼續(xù)履行、采取補(bǔ)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zé)任。這就是一條包含完整的三要素邏輯結(jié)構(gòu)的法律規(guī)則,其中當(dāng)事人雙方存在合同關(guān)系是假定條件),一方不履行合同或履行不合約定是行為模式,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是法律后果。而在沖突法理論里,沖突法是知名某一國(guó)際民商事關(guān)系應(yīng)適用何種法律的法,是選擇適用法律的法。以我國(guó)為例,2011年新出臺(tái)的《涉外民事關(guān)系法律適用法》就是我國(guó)的沖突法,它用以指導(dǎo)我國(guó)在涉外民事關(guān)系存在法律沖突時(shí),如何選擇適用法律的問(wèn)題。如該法第23條規(guī)定:夫妻人身關(guān)系,適用共同經(jīng)常居所地法律;沒(méi)有共同經(jīng)常居所地的,適用共同國(guó)籍國(guó)法律。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法官處理涉外夫妻人身關(guān)系案件時(shí),在法律適用方面,首選的應(yīng)該是夫妻的共同經(jīng)常居所地法律,其次才是共同國(guó)籍國(guó)法律。至于法律如何規(guī)定夫妻雙方的具體權(quán)利義務(wù)則不在本法的調(diào)整范圍之內(nèi)。沖突法里類似這樣的法條占絕大多數(shù),從性質(zhì)上說(shuō),它更像是為法官設(shè)立的裁判準(zhǔn)則,缺少法律規(guī)則具有的普遍性,同時(shí)多了一些專業(yè)性,這也是《涉外民事關(guān)系法律適用法》的普及性遠(yuǎn)不及《民法》、《刑法》等法律規(guī)范的原因所在。從結(jié)構(gòu)上說(shuō),它是由“范圍”和“系屬”兩部分構(gòu)成,前者是該法條所要調(diào)整的國(guó)際民商事法律關(guān)系或所要解決的法律問(wèn)題,如上例中的“夫妻人身關(guān)系”;后者是該法律關(guān)系或法律問(wèn)題所應(yīng)適用的法律,如上例中的“共同經(jīng)常居所地法律”和“共同國(guó)籍國(guó)法律”。這和法律規(guī)則的“兩要素”或“三要素”的邏輯結(jié)構(gòu)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說(shuō)“假定”體現(xiàn)在“范圍”部分,同時(shí)還包括隱含的“涉外因素”還勉強(qiáng)說(shuō)的過(guò)去的話,那么在沖突法的法條里實(shí)在找不到所謂的“行為模式”或者“法律后果”部分。
最后,沖突法應(yīng)該屬于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是指創(chuàng)制和適用法律規(guī)范時(shí)必須應(yīng)用的專門(mén)技術(shù)知識(shí)和方法,是法律文件中的技術(shù)性事項(xiàng),涉及的內(nèi)容主要有法的生效時(shí)間、法的溯及力問(wèn)題、法律解釋權(quán)、憲法中有關(guān)國(guó)旗國(guó)徽國(guó)歌等的規(guī)定。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是法的構(gòu)成要素之一,它不同于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范。雖一字之差,但它們二者所屬的法理學(xué)范疇已大不相同。在法理學(xué)中,法的概念要高于法律規(guī)范的概念,而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是與法律規(guī)范一樣,同屬法的構(gòu)成要素之一,但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范則是法律規(guī)范的下位概念,僅屬于法律規(guī)范的一種。之所以說(shuō)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是法的要素之一,是因?yàn)槿绻麤](méi)有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法律規(guī)范在執(zhí)行和適用時(shí)就會(huì)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有損法律的尊嚴(yán)。比如幾乎每部法律的附則部分都會(huì)規(guī)定該法的生效時(shí)間,這種法條當(dāng)然不是什么法律概念、法律原則或法律規(guī)則等法律規(guī)范,但是如果沒(méi)有這樣的規(guī)定也會(huì)使該部法律的適用出現(xiàn)各種問(wèn)題,因此它也是法的構(gòu)成要素之一,只是法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而已。這種條文一般在一部法律里面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往往會(huì)被人們忽略,并不足以影響整部法律里大多數(shù)法條法律規(guī)范的性質(zhì)。所不同的是,在沖突法里,這種規(guī)定技術(shù)性事項(xiàng)的法條則是占絕大多數(shù)的,因?yàn)闆_突法本身就是通過(guò)“系屬”中的“連結(jié)點(diǎn)”的指引,指導(dǎo)和輔助法官找到該“范圍”所應(yīng)適用的規(guī)定當(dāng)事人具體權(quán)利義務(wù)的法律規(guī)范的法。正是“連結(jié)點(diǎn)”的這種橋梁和紐帶作用使沖突法素有“橋梁法”之稱,而這也更體現(xiàn)了沖突法法條的技術(shù)性特點(diǎn)。因此,沖突法的性質(zhì)應(yīng)當(dāng)由其中的大多數(shù)法條的性質(zhì)決定,它是法的要素中的技術(shù)性規(guī)定。
第2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1.1 職務(wù)犯罪初查的概念界分
“初查”按其字面意思可解釋為:初步調(diào)查、初步偵查或者初步審查,我國(guó)刑事訴訟法對(duì)職務(wù)犯罪初查的概念并沒(méi)有做出立法性的規(guī)定,但最高人民檢察院于 1999 年頒布的《關(guān)于檢察機(jī)關(guān)反貪污賄賂工作若干問(wèn)題的決定》第 6 條規(guī)定:“初查是檢察機(jī)關(guān)對(duì)案件線索在立案前依法進(jìn)行的審查,包括必要的調(diào)查。”這一司法解釋對(duì)初查在某種意義上進(jìn)行了定義。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第 110 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于報(bào)案、控告、舉報(bào)和自首的材料,應(yīng)當(dāng)按照管轄范圍,迅速進(jìn)行審查,認(rèn)為有犯罪事實(shí)需要追究刑事責(zé)任的時(shí)候,應(yīng)當(dāng)立案;認(rèn)為沒(méi)有犯罪事實(shí),或者犯罪事實(shí)顯著輕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責(zé)任的時(shí)候,不予立案,并且將不立案的原因:請(qǐng)記住我站域名通知控告人。”從這條規(guī)定中提煉出的“迅速進(jìn)行審查”是在刑事訴訟法中能夠找到的關(guān)于初查的籠統(tǒng)的、模糊的法律定義。法律概念是否能夠反映法的本質(zhì)屬性,法律概念之間能否協(xié)調(diào)一致,是影響一項(xiàng)法律制度能否有效運(yùn)行的重要因素。但是就初查而言,由于種種原因,不管是在實(shí)踐中還是在理論中,都沒(méi)有形成一個(gè)正式的法律概念,相反對(duì)于此概念的界定,學(xué)術(shù)界一直是爭(zhēng)議不斷,觀點(diǎn)分歧一直存在。具有代表性的幾種觀點(diǎn)可以概括如下:其一,職務(wù)犯罪初查是指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前通過(guò)初步調(diào)查的方法,對(duì)本院管轄范圍內(nèi)的犯罪案件線索進(jìn)行審查,以獲取證據(jù),確定是否需要對(duì)案件立案?jìng)刹榈脑V訟活動(dòng)①;其二,職務(wù)犯罪初查是審查的一種方式,是對(duì)管轄范圍內(nèi)的線索進(jìn)行調(diào)查,以判明是否符合立案條件的訴訟活動(dòng)②;其三,職務(wù)犯罪初查是檢察機(jī)關(guān)職務(wù)犯罪偵查部門(mén)在獲取職務(wù)犯罪線索后,為進(jìn)一步判明是否需要立案?jìng)刹?而對(duì)已有材料進(jìn)行分析辨別所做的必要調(diào)查活動(dòng),是職務(wù)犯罪案件進(jìn)入刑事訴訟程序之前的專門(mén)的調(diào)查活動(dòng)③;其四,職務(wù)犯罪初查是指人民檢察院為了確定是否需要將案件立案?jìng)刹?通過(guò)初步調(diào)查的方法,對(duì)自己管轄范圍內(nèi)的犯罪案件線索進(jìn)行審查,以獲取證據(jù)的訴訟活動(dòng)①。從上述觀點(diǎn)分析可得出,對(duì)于職務(wù)犯罪初查概念的爭(zhēng)議焦點(diǎn)主要集中在兩個(gè)方面:一是職務(wù)犯罪初查究竟是一種訴訟外的司法調(diào)查活動(dòng)還是一種訴訟程序中的偵查活動(dòng);二是職務(wù)犯罪初查僅指對(duì)線索相關(guān)書(shū)面材料的審查還是包括對(duì)事實(shí)的實(shí)踐調(diào)查。要想提煉出一個(gè)權(quán)威性的概念,就必須抓住各定義之間的共性,從中加以提煉,從而概括出概念的本質(zhì)。
1.2 職務(wù)犯罪初查制度法律性質(zhì)
性質(zhì)是一事物區(qū)別于另一事物的顯著標(biāo)志,我們要深入研究某事物,必須要弄清它的性質(zhì),才能抓住其本質(zhì)。所以,我們要對(duì)職務(wù)犯罪初查制度進(jìn)行系統(tǒng)的研究,就必須首先認(rèn)清初查的性質(zhì)。但是,由于我國(guó)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并沒(méi)有規(guī)定初查制度,更沒(méi)有明確其性質(zhì),即使相關(guān)司法文件中有對(duì)職務(wù)犯罪實(shí)踐的操作規(guī)定,但同樣沒(méi)有對(duì)其性質(zhì)進(jìn)行界定。所以,職務(wù)犯罪初查一直面臨著性質(zhì)不清的困惑,理論上眾說(shuō)紛紜,對(duì)此爭(zhēng)論不斷,至今沒(méi)有形成統(tǒng)一的認(rèn)識(shí)。對(duì)于職務(wù)犯罪初查的性質(zhì),目前學(xué)術(shù)界有如下三種不同的觀點(diǎn)①:(1)職務(wù)犯罪初查行為是一種行政行為。持此種觀點(diǎn)的人認(rèn)為“訴訟行為是在立案后才開(kāi)始的,立案之前的行為應(yīng)當(dāng)是行政行為”②。立案是我國(guó)刑事訴訟程序的開(kāi)端,是刑事訴訟展開(kāi)的標(biāo)志,因此初查作為立案前行為當(dāng)然被排斥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外,初查不具有刑事訴訟的法律性質(zhì),而應(yīng)被界定為行政行為。(2)職務(wù)犯罪初查行為是一種偵查行為。持這種觀點(diǎn)的人認(rèn)為,職務(wù)犯罪初查活動(dòng)在本質(zhì)上與正式偵查沒(méi)有實(shí)質(zhì)的區(qū)別,如前所述,二者在調(diào)查的主體、內(nèi)容、措施上都有重疊,盡管所要求的調(diào)查程度不同,但從實(shí)質(zhì)上看初查就是初步的偵查。(3)職務(wù)犯罪初查行為是一種非偵查性質(zhì)的調(diào)查行為。持這種觀點(diǎn)的人認(rèn)為“這種立案前的調(diào)查工作是非偵查性質(zhì)的調(diào)查活動(dòng),理由是偵查活動(dòng)只有在刑事訴訟開(kāi)始后,也就是立案后才能進(jìn)行”。所以,一般意義上的偵查行為是在立案后才可以進(jìn)行的,在立案前就適用違反了我國(guó)規(guī)定的法律程序,根據(jù)我國(guó)現(xiàn)行的規(guī)定,發(fā)生在立案前的初查行為不可能具有偵查性質(zhì),它只是在為偵查做鋪墊的前期調(diào)查行為。
第 2 章 職務(wù)犯罪初查制度的域外考察與評(píng)析
2.1 英美法系國(guó)家的職務(wù)犯罪初查制度
在英美法系國(guó)家,無(wú)論是刑事訴訟理論還是立法,刑事訴訟程序通常從逮捕或傳訊犯罪嫌疑人開(kāi)始的,即訴訟行為始于偵查程序的啟動(dòng),所以英美國(guó)家沒(méi)有立案程序,也沒(méi)有偵查程序之前的初查行為。而且,在英美法系一般沒(méi)有將職務(wù)犯罪劃歸為檢察機(jī)關(guān)自偵案件的習(xí)慣,檢察機(jī)關(guān)不直接參與偵查活動(dòng),因此也沒(méi)有類似于中國(guó)檢察機(jī)關(guān)職務(wù)犯罪偵查的程序。雖然,在這些國(guó)家的司法實(shí)踐中一般是逮捕后才正式進(jìn)入刑事訴訟程序,但是,在逮捕前警察要做大量的調(diào)查工作,例如警察在接到公民、被害人舉報(bào)的線索,或是自己在執(zhí)行公務(wù)中發(fā)現(xiàn)情況后就開(kāi)始偵查。警方通常采用現(xiàn)場(chǎng)勘查和會(huì)見(jiàn)見(jiàn)證人等方式了解情況,當(dāng)掌握了一定數(shù)量的證據(jù)材料后,認(rèn)為確有必要提起公訴時(shí),才對(duì)犯罪嫌疑人實(shí)行正面接觸,包括逮捕、拘留。此后,才開(kāi)始正式進(jìn)入刑事訴訟程序。可見(jiàn),英美法系國(guó)家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沒(méi)有初查的明確規(guī)定,但是這種偵查行為包含了與我國(guó)初查相似的功能,實(shí)際上發(fā)揮了初查制度的作用。在英國(guó),司法警察是偵查行為的獨(dú)立實(shí)施者。一般而言,除了那些法律允許采用“無(wú)證逮捕”或“無(wú)證搜查”的情況外,警察對(duì)任何公民實(shí)施的逮捕或者對(duì)任何公民實(shí)施的搜查和扣押行為,都必須事先向治安法官提出申請(qǐng),并說(shuō)明實(shí)施逮捕和搜查的正當(dāng)理由。這實(shí)際上是對(duì)偵查程序的限制,因而,從程序合法性來(lái)看,也不得存在犯罪初查行為。在美國(guó),與英國(guó)一樣,也建立了針對(duì)警察逮捕、羈押、保釋、搜查、扣押、竊聽(tīng)、訊問(wèn)等項(xiàng)權(quán)力的司法審查機(jī)制。除了在法律規(guī)定的例外情況以外,警察對(duì)任何人實(shí)施逮捕、搜查都必須首先向一名中立的法官提出申請(qǐng),
第3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海南大學(xué)法學(xué)院,海口 570028)
摘 要: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指真正繼承人所繼承的遺產(chǎn)被部分或者全部被無(wú)正當(dāng)權(quán)原侵占時(shí),真正繼承人可以直接向無(wú)本權(quán)人或者請(qǐng)求人民法院,確認(rèn)繼承人的繼承資格并返還所繼承遺產(chǎn)的概括性的權(quán)利。我國(guó)《繼承法》等相關(guān)民事法律對(duì)此制度并未作出明確規(guī)定,有規(guī)定的地方也有很大不足之處。本文從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概念、價(jià)值、特征和訴訟時(shí)效角度分析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性質(zhì),結(jié)合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中的規(guī)定,旨在為《繼承法》的修訂過(guò)程中提供制度完善的建議,從而更加有效的維護(hù)繼承人的合法權(quán)益,促進(jìn)交易安全,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能夠發(fā)揮一定作用。
關(guān)鍵詞 :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性質(zhì);訴訟時(shí)效;除斥期間
中圖分類號(hào):D923.5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文章編號(hào):1000-8772(2014)25-0140-03
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可以追溯到古代羅馬法,在近代許多國(guó)家的法律幾乎對(duì)其都有明文的規(guī)定。然而受法律傳統(tǒng)、法律習(xí)慣以及分屬不同法系等因素的影響,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表達(dá)也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表達(dá):繼承訴,遺產(chǎn)請(qǐng)求權(quán),返還遺產(chǎn)請(qǐng)求權(quán),遺產(chǎn)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等等。我國(guó)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還沒(méi)有明確上升到法律層面,只是在法學(xué)界進(jìn)行廣泛的討論,并且借鑒國(guó)外法律將其稱之謂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但是隨著我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司法實(shí)踐的發(fā)展,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的確立越來(lái)越具有現(xiàn)實(shí)迫切需要。
一、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概念和意義
(一)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概念
我國(guó)法學(xué)界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概念主要存在“資格說(shuō)”和“財(cái)產(chǎn)請(qǐng)求權(quán)說(shuō)”兩種爭(zhēng)議。資格說(shuō)認(rèn)為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指繼承權(quán)受到侵害時(shí),真正繼承權(quán)人以訴訟方式直接請(qǐng)求人民法院判令回復(fù)繼承人的地位。[1]財(cái)產(chǎn)請(qǐng)求權(quán)說(shuō)認(rèn)為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指真正繼承人在繼承權(quán)受到侵害時(shí),通過(guò)訴訟的方式確認(rèn)其繼承人地位,并請(qǐng)求判令遺產(chǎn)占有人返還所侵占的遺產(chǎn)。
綜合以上兩種學(xué)說(shuō)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概念描述,我認(rèn)為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指真正繼承人所繼承的遺產(chǎn)被部分或者全部被無(wú)正當(dāng)權(quán)原人侵占時(shí),真正繼承疼可以直接向無(wú)本權(quán)人或者請(qǐng)求人民法院,確認(rèn)繼承人的繼承資格并返還所繼承遺產(chǎn)的概括性的權(quán)利。
(二)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特征
1、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一種概括性的權(quán)利
據(jù)上文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真正權(quán)利人不僅請(qǐng)求確認(rèn)其真正繼承人地位,而且要求請(qǐng)求返還被侵占的遺產(chǎn),也即身份權(quán)的資格確認(rèn)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
2、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實(shí)體性權(quán)利,而非程序性權(quán)利
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身份法上的請(qǐng)求權(quán),是民事法律賦予民事主體所享有的一項(xiàng)實(shí)體性權(quán)利,屬于實(shí)體法所規(guī)定的范疇,并不是訴訟法上規(guī)定的程序性權(quán)利。
3、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獨(dú)立的請(qǐng)求權(quán)
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行使的最為直接的權(quán)源是繼承人的繼承地位,是一種基于身份的原因法律所賦予的一項(xiàng)特殊的、獨(dú)立的權(quán)利,并不是法律所賦予的繼承人對(duì)繼承財(cái)產(chǎn)享有的財(cái)產(chǎn)性權(quán)利這樣的間接權(quán)利基礎(chǔ)。繼承身份地位的獨(dú)立性,決定了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一項(xiàng)法律確認(rèn)和保護(hù)的獨(dú)立的權(quán)利。
4、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行使的最終目的是獲得遺產(chǎn)
通過(guò)行使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以確認(rèn)真正繼承人的繼承地位,所要達(dá)到的真正目的是去的所爭(zhēng)議的遺產(chǎn),可謂確認(rèn)之訴是前提和手段,給付之訴才是最終目的。[2]
(三)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意義
法律制度的設(shè)計(jì)和構(gòu)建是為了更好地實(shí)現(xiàn)法律價(jià)值。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的構(gòu)建對(duì)于從根本上維護(hù)繼承人的合法權(quán)益,保護(hù)繼承法律關(guān)系的穩(wěn)定,保障市場(chǎng)交易的安全,市場(chǎng)交易能夠順利進(jìn)行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shí)和理論意義。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的構(gòu)建主要具有以下意義和功能。
1、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能夠促進(jìn)觀念的繼承權(quán)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shí)的繼承權(quán)[3]
在我國(guó)繼承法理論界對(duì)繼承權(quán)的性質(zhì)理論研究主要存在主觀說(shuō)和客觀說(shuō)兩種學(xué)說(shuō)。客觀說(shuō)視繼承權(quán)是繼承人享有的一項(xiàng)期待性的權(quán)利,指的是在繼承開(kāi)始前繼承人在繼承法律關(guān)系中所處的法律地位,是自然人依法或者依照遺囑繼承遺產(chǎn)的資格,是繼承人繼承遺產(chǎn)的能力。主觀說(shuō)認(rèn)為繼承權(quán)是指繼承人在繼承法律關(guān)系中實(shí)際享有的繼承人繼承被繼承人的遺產(chǎn)的具體的權(quán)利。[4]在這兩種學(xué)說(shuō)中我國(guó)理論界更傾向于客觀說(shuō)。然而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不僅包括繼承人的繼承地位的身份權(quán),也包含繼承人在繼承法律關(guān)系中享有的請(qǐng)求返還無(wú)權(quán)占有的部分或者全部遺產(chǎn)的請(qǐng)求權(quán)。在繼承發(fā)生時(shí),開(kāi)始繼承時(shí)因?yàn)槔^承法律關(guān)系和物權(quán)法律關(guān)系處于復(fù)雜和不穩(wěn)定性中,繼承人的期待性的權(quán)利未必能夠得到切切實(shí)實(shí)的實(shí)現(xiàn),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的建立,就是為了在真正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受到損害時(shí)能夠快速的到救濟(jì)。因此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在順利實(shí)現(xiàn)觀念的繼承權(quán)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shí)的權(quán)利的過(guò)程中起到法律制度保障。
2、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為了保障真正繼承人的利益而設(shè)
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社會(huì)新型財(cái)產(chǎn)的出現(xiàn),越來(lái)越多的財(cái)產(chǎn)納入到遺產(chǎn)的范圍中是一種必然的趨勢(shì),從而造成遺產(chǎn)內(nèi)容更加復(fù)雜,標(biāo)的物種類越來(lái)越多。當(dāng)真正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受到侵害時(shí),如果繼承人根據(jù)對(duì)所爭(zhēng)議的個(gè)個(gè)遺產(chǎn)享有的權(quán)利,單獨(dú)請(qǐng)求法院保護(hù),真正繼承人陷入極大地訴累中,必然也會(huì)為其付出更大的代價(jià),增加了維權(quán)成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的建立能夠讓真正繼承人概括性地行使權(quán)利,從而減少訴訟成本,能夠減少繼承人的訴累,維護(hù)真正繼承人的利益。
3、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能夠節(jié)約司法資源,減少當(dāng)事人訴累[5]
如上所述,如果繼承人依據(jù)個(gè)個(gè)請(qǐng)求權(quán)一一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會(huì)因一個(gè)爭(zhēng)議受理許多不同的案件,對(duì)司法資源是一種極計(jì)大的浪費(fèi),如果有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法院可以以此合并審理,起到節(jié)約司法資源的效果。如果當(dāng)事人依據(jù)個(gè)個(gè)請(qǐng)求權(quán)一一起訴,根據(jù)民事訴訟證據(jù)的基本理論“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的原則,當(dāng)事人因此要各個(gè)所爭(zhēng)議的事實(shí)舉證,更需要溯及既往地證明此權(quán)利真實(shí)的歸屬于被繼承人。如果有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只需證明繼承發(fā)生時(shí)只要有其權(quán)利這樣的事實(shí)就可以完成舉證責(zé)任,大大減輕了繼承人的舉證責(zé)任。
4、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有利于快速確定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維護(hù)交易安全
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對(duì)其權(quán)利的行使有訴訟時(shí)效的規(guī)定,有利于迫使真正繼承人盡快行使權(quán)利,明確產(chǎn)權(quán)關(guān)系,明確對(duì)所爭(zhēng)議的遺產(chǎn)權(quán)利歸屬的法律關(guān)系,在所有人與第三人處分權(quán)利的交易中保護(hù)善意第三人,也維護(hù)了法律關(guān)系的穩(wěn)定。
5、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性質(zhì)
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法律性質(zhì)的論爭(zhēng),民法學(xué)界由來(lái)已久,但最具有權(quán)威性的觀點(diǎn)主要有以下三種:繼承人地位回復(fù)形成權(quán)說(shuō)、遺產(chǎn)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說(shuō)和繼承資格確認(rèn)以及財(cái)產(chǎn)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說(shuō)。
(1)繼承人地位回復(fù)形成權(quán)說(shuō)
該說(shuō)認(rèn)為,通過(guò)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使表見(jiàn)繼承人的資格溯及既往地消滅以及使請(qǐng)求權(quán)人的繼承資格溯及既往地恢復(fù)效力。繼承人繼承的是被繼承人的人格或者地位,不是為了方便起見(jiàn),允許繼承人通過(guò)一個(gè)訴求而實(shí)現(xiàn)數(shù)個(gè)訴求,而是在繼承權(quán)被他人侵害時(shí)請(qǐng)求回復(fù)繼承人的繼承帝位。[6]
該說(shuō)僅僅突出了形成權(quán)的性質(zhì),強(qiáng)調(diào)繼承人資格和地位的回復(fù),但是與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設(shè)立的最終目的即通過(guò)回復(fù)繼承資格而獲得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相背離。如果以此學(xué)說(shuō)理解,并沒(méi)有解決繼承人所真正關(guān)心的實(shí)質(zhì)性問(wèn)題——獲得爭(zhēng)議遺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這與該制度的設(shè)立目的不符。另外形成權(quán)受除斥期間限制,一旦把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性質(zhì)理解為形成權(quán),如果除斥期間過(guò)去,亦或在除斥期間中真正繼承人因客觀不能或者不可抗力等事由不能及時(shí)行使此權(quán)利,勢(shì)必給真正繼承人造成財(cái)產(chǎn)上的損失,不利于維護(hù)真正繼承人的合法權(quán)利。
(2)遺產(chǎn)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說(shuō)
該學(xué)說(shuō)認(rèn)為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就是真正繼承人請(qǐng)求無(wú)權(quán)占有遺產(chǎn)人返還所占的部分或全部遺產(chǎn)的權(quán)利。此學(xué)說(shuō)包括集合權(quán)利說(shuō)和獨(dú)立權(quán)利說(shuō)兩種。[7]
1)集合權(quán)利說(shuō)
集合權(quán)利說(shuō)認(rèn)為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是對(duì)所爭(zhēng)議的各個(gè)繼承財(cái)產(chǎn)的請(qǐng)求權(quán)的集合。我認(rèn)為此學(xué)說(shuō)把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和物權(quán)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有混淆之意。如果把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理解為數(shù)個(gè)物權(quán)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的集合,又為何單獨(dú)設(shè)立其制度,并且物權(quán)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不受訴訟時(shí)效的限制,與繼承法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也相互矛盾。另外在法律沖突時(shí)有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的規(guī)則,在繼承糾紛和物權(quán)糾紛上,我們應(yīng)該首先選擇適用繼承法。基于以上愿意我認(rèn)為集合權(quán)利說(shuō)有一定不妥之處。
2)獨(dú)立權(quán)利說(shuō)
獨(dú)立權(quán)利說(shuō)認(rèn)為繼承回去請(qǐng)求權(quán)是繼承人在遺產(chǎn)被他人無(wú)權(quán)占有一部分或者全部繼承權(quán)受到侵害時(shí)所享有的特別、獨(dú)立的和包括的原狀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也即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不是多個(gè)物上請(qǐng)求權(quán)的集合,是在繼承發(fā)生時(shí)對(duì)被繼承人的占有的一切物或者享有的權(quán)利,得請(qǐng)求占有人概括的回復(fù)。
3)繼承資格確認(rèn)及財(cái)產(chǎn)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說(shuō)
該說(shuō)認(rèn)為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不僅具有對(duì)真正繼承人的繼承地位的確認(rèn)而且還要求無(wú)權(quán)占有人返還所占有的遺產(chǎn)。由此得知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不僅具有人的請(qǐng)求權(quán)性質(zhì)還包含物的請(qǐng)求權(quán)性質(zhì)。對(duì)于確認(rèn)繼承人的繼承地位具有人的請(qǐng)求權(quán)性質(zhì),相對(duì)于要求返還所占有的遺產(chǎn)來(lái)說(shuō)具有物的請(qǐng)求權(quán)的性質(zhì)。
我認(rèn)為此說(shuō)相對(duì)于前兩個(gè)學(xué)說(shuō)來(lái)說(shuō),更符合立法目的,并且也與司法實(shí)踐相吻合。設(shè)立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就是要保護(hù)繼承人的繼承權(quán),進(jìn)而對(duì)所爭(zhēng)議的財(cái)產(chǎn)明確歸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之訴發(fā)生的原因就是因?yàn)榇嬖趯?duì)真正繼承人地位的爭(zhēng)議,但是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之訴的最終目的是要返還所占有的遺產(chǎn)。可見(jiàn)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之訴包括確認(rèn)之訴和給付之訴的雙重性質(zhì),確認(rèn)之訴是前提條件和手段,給付之訴是確認(rèn)之訴的目的。
繼承資格確認(rèn)及財(cái)產(chǎn)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說(shuō)把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理解為資格確認(rèn)和財(cái)產(chǎn)返還請(qǐng)求權(quán),進(jìn)而把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之訴分解為確認(rèn)之訴和給付之訴,兩訴合并在一塊,不僅節(jié)約了司法資源,而且可以減少當(dāng)事人的訴累,快速認(rèn)定繼承法律關(guān)系和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維護(hù)交易的安全,保護(hù)真正繼承人的合法權(quán)益。
二、從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性質(zhì)評(píng)析我國(guó)法律對(duì)其制度的規(guī)定以及不足
(一)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規(guī)定
縱觀我國(guó)現(xiàn)行的法律法規(guī),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的規(guī)定僅僅限于《繼承法》第八條和《執(zhí)行繼承法意見(jiàn)》第十五條。繼承法第八條明確規(guī)定了繼承訴訟提起的訴訟時(shí)效期間為兩年,以及超過(guò)訴訟時(shí)效的法律后果即不得再提起訴訟。執(zhí)行繼承法意見(jiàn)第十五條規(guī)定了繼承訴訟時(shí)效期間中止、中斷的事由情形,也確定了超訴訟時(shí)效期間的法律后果。
(二)對(duì)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中規(guī)定評(píng)析
1、對(duì)“兩年期間”性質(zhì)認(rèn)定
根據(jù)繼承法第八條超過(guò)訴訟期間不得再提起訴訟的規(guī)定,我們不難看出對(duì)兩年期間的認(rèn)定是除斥期間而不是訴訟時(shí)效期間。除斥期間適用于形成權(quán),請(qǐng)求權(quán)適用訴訟時(shí)效期間,但是通過(guò)上文分析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性質(zhì)應(yīng)為繼承資格確認(rèn)及財(cái)產(chǎn)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因此此條款有一定的不合理之處。另外從司法實(shí)踐來(lái)看,即便訴訟時(shí)效經(jīng)過(guò),權(quán)利人不是不可以提起訴訟,只是權(quán)利人喪失了勝訴權(quán),繼承人的實(shí)體權(quán)利并沒(méi)有因?yàn)樵V訟時(shí)效期間的屆滿而喪失,真正權(quán)利人的訴權(quán)并沒(méi)有喪失,法院還是要受理案件。[8]
因此從我國(guó)的立法目的和司法實(shí)踐的情況來(lái)看,繼承法第八條的規(guī)定都與其相互矛盾,對(duì)法律系統(tǒng)完整統(tǒng)一并不協(xié)調(diào)一致,故對(duì)繼承法第八條的修改應(yīng)該充分明確時(shí)效的性質(zhì)。
2、把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和繼承權(quán)糾紛的關(guān)系混淆
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中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并沒(méi)有做出明確規(guī)定,繼承法第八條只是從訴訟時(shí)效視角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做出規(guī)定,并且用繼承糾紛取代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這樣的做法混淆了繼承糾紛和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制度,有偷換概念之嫌,并未理清兩者內(nèi)涵和外延的問(wèn)題。如前所述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作為一種特殊的請(qǐng)求權(quán),是實(shí)體權(quán)利,這種以訴訟的方式體現(xiàn)實(shí)體權(quán)利,不符合法律的精神,為了充分保護(hù)繼承人的合法權(quán)益應(yīng)該在繼承法中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明確規(guī)定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另外繼承糾紛是大概念,繼承會(huì)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之訴是子概念,繼承糾紛包含方方面面,涉及范圍廣泛,不只局限在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糾紛。
3、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訴訟時(shí)效認(rèn)定
如果把繼承法第八條和《執(zhí)行繼承法意見(jiàn)》第15條訴訟期間的規(guī)定理解為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訴訟期間,那么二十年的期間過(guò)長(zhǎng),不利于快速解決繼承糾紛,不利于明確繼承法律關(guān)系,也不利于維護(hù)市場(chǎng)交易關(guān)系。訴訟期間的首要作用就是督促權(quán)利人盡快行使權(quán)力,解決糾紛,明確法律關(guān)系,促進(jìn)交易,而現(xiàn)行法律對(duì)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訴訟期間的規(guī)定過(guò)長(zhǎng),容易使繼承財(cái)產(chǎn)處于不穩(wěn)定的關(guān)系,造成社會(huì)資源的浪費(fèi)。[9]
筆者認(rèn)為在繼承法修訂過(guò)程中,應(yīng)該充分體現(xiàn)促進(jìn)市場(chǎng)交易的原則,維護(hù)第三人的利益,可以適當(dāng)縮短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訴訟時(shí)效期間,促使真正繼承人盡快行使權(quán)利,提高民事交易的效率。
4、超訴訟時(shí)效期間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分析
依據(jù)繼承法第八條和《執(zhí)行繼承法意見(jiàn)》第15條的規(guī)定,超過(guò)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訴訟時(shí)效的,真正繼承人不得再提起訴訟,也即喪失起訴權(quán),但是遺產(chǎn)的無(wú)權(quán)占有人能否取得所爭(zhēng)議的所有權(quán)?在我國(guó)現(xiàn)行法律中,并沒(méi)有規(guī)定取得時(shí)效,因此遺產(chǎn)占有人并沒(méi)有取得遺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只是取得了對(duì)抗繼承人返還遺產(chǎn)的抗辯權(quán)。這勢(shì)必不利于財(cái)產(chǎn)流通,不利于交易關(guān)系的穩(wěn)定。但是基于繼承人的繼承地位,并不會(huì)因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的訴訟時(shí)效而消滅,我國(guó)繼承法實(shí)行概括繼承,繼承人也要繼承被繼承人的債務(wù),這就會(huì)產(chǎn)生繼承人只繼承了被繼承人的債務(wù)而沒(méi)有的繼承財(cái)產(chǎn)的法律結(jié)果,與民法的公平原則相背離,無(wú)益于保護(hù)繼承人的合法權(quán)益。
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可以借鑒國(guó)外立法,確立取得時(shí)效制度,從而保護(hù)交易安全,同時(shí)也能通過(guò)取得時(shí)效的確立,督促真正權(quán)利人行使繼承回復(fù)權(quán)。
參考文獻(xiàn):
[1] 張玉敏.繼承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 劉悅.倫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J].遼寧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1,(6):14-17.
[3] 史尚寬.繼承法論[M].北京: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0.
[4] 郭明瑞,房紹坤,關(guān)濤.繼承法研究[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7):16—17.
[5] 余延滿,冉克平.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研究[J].重慶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3,(5):105- 107.
[6] 郭明瑞,房紹坤.繼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 金錦城,宋建民.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之性質(zhì)研究[J].行政與法,2002,(2).
[8] 王燕軍.論繼承回復(fù)請(qǐng)求權(quán)[J].山西經(jīng)濟(jì)管理干部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9,(3).
第4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關(guān)鍵詞:違法性/出罪根據(jù)/犯罪理論體系
目前,與“違法性”有關(guān)的討論成為中國(guó)刑法理論界的熱點(diǎn)。但是,在筆者看來(lái),有關(guān)的討論之所以會(huì)存在很多爭(zhēng)議和懷疑,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對(duì)“違法性”這個(gè)概念以及這個(gè)概念在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與功能有不清楚的認(rèn)識(shí)。“違法性”這個(gè)概念在德國(guó)刑法理論(或者以德國(guó)刑法理論為淵源的刑法理論中,例如,在日本刑法理論中)、英美刑法理論和前蘇聯(lián)的刑法理論中,都得到了使用。但是,在不同的理論體系中,這個(gè)概念的含義,不僅有相似之處,而且存在很大的區(qū)別。筆者認(rèn)為,厘清刑法中“違法性”的概念及其在理論體系中的功能,對(duì)于促進(jìn)中國(guó)刑法基本理論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違法性的概念
對(duì)語(yǔ)言的理解,需要語(yǔ)境。對(duì)重要法律概念的理解,更需要一個(gè)恰當(dāng)?shù)纳舷挛摹R虼耍瑢?duì)“違法性”這個(gè)概念的考察,只能在其所產(chǎn)生的各國(guó)法律體系中進(jìn)行考察。
(一)德日刑法理論中的“違法性”概念
現(xiàn)代德國(guó)和日本的刑法理論,都使用“違法性”這個(gè)概念。日本刑法理論使用的“違法性”,雖然與德國(guó)理論有一些不同,但是,從這個(gè)詞的詞源上看,它是來(lái)自德語(yǔ)和德國(guó)刑法理論。
在德國(guó)刑法理論中,“違法性”這個(gè)詞的德文原文是Rechtswidrigkeit,它的字面含義是“違反法的”,①它的一般法律含義是“對(duì)抗法制度(die Rechtsordnung)的行為”所具有的性質(zhì)。②在德國(guó)刑法理論語(yǔ)境下的“違法性”,具有兩個(gè)重要的特點(diǎn):一是,這里所說(shuō)的法,不是指具體的法律條文,甚至不是指具體的哪一部法律,而是指整個(gè)法律制度或者全部有法律約束力的條文的整體;二是,與前一個(gè)特點(diǎn)緊密聯(lián)系,這里的“違法性”必須是根據(jù)整個(gè)法律體系得出的整體性判斷。在德國(guó)“違法性”概念中所說(shuō)的“法(Recht)”,嚴(yán)格地說(shuō),指的不僅是制定法,而且還包括在長(zhǎng)期實(shí)踐中產(chǎn)生出來(lái)的習(xí)慣性規(guī)則。根據(jù)一些德國(guó)學(xué)者的意見(jiàn),這些規(guī)則和規(guī)范還包括在各國(guó)法律制度中都存在的法律思想。③也就是說(shuō),德國(guó)刑法語(yǔ)境下的違法性,指的是根據(jù)在實(shí)際上具有拘束力的法律和非法律(自然法、習(xí)慣法)對(duì)一個(gè)具體行為所做出的正確性或者錯(cuò)誤性評(píng)價(jià)。
當(dāng)然,在對(duì)具體行為進(jìn)行違法性判斷時(shí),其根據(jù)本來(lái)應(yīng)當(dāng)是具體的,但是,在“違法性”中得出的評(píng)價(jià),并不是為了指明這個(gè)具體行為所違反的規(guī)范,而是為了指明這個(gè)具體行為在符合具體刑事法律規(guī)定的情況下,是否仍然具有從法秩序的整體方面進(jìn)行判斷之后可能得出的“正確”性質(zhì)。Recht這個(gè)德語(yǔ)詞,從字面上看,不僅具有“法”的意思,而且具有“正確”的意思。在德國(guó)刑法理論中,在“違法性”這個(gè)階段中得到“正確”評(píng)價(jià)的行為,就不需要進(jìn)入下一個(gè)階段的評(píng)價(jià);只有不能得到“正確”評(píng)價(jià)的行為,才能進(jìn)入下一階段的評(píng)價(jià)。
在日本刑法理論中,雖然學(xué)者們對(duì)“違法性”的表現(xiàn)和功能存在著許多爭(zhēng)論,但是,在這個(gè)詞的基本概念上仍然沿用德國(guó)理論的說(shuō)法。從詞源上看,日本刑法理論中的違法性就是德國(guó)刑法理論中的Rechtswidrigkeit這個(gè)詞。④日本刑法理論中的“違法性”通常就是指行為違反法或者不被法所允許的性質(zhì)。⑤應(yīng)當(dāng)特別注意的是,日本刑法理論一般也都把“違法性”中的“法”指向法秩序的整體。⑥雖然在理論中存在著對(duì)形式違法性和實(shí)質(zhì)違法性的爭(zhēng)論,但是,日本刑法理論中并沒(méi)有人主張,對(duì)“違法性”僅僅應(yīng)當(dāng)從形式或者實(shí)質(zhì)的一個(gè)方面進(jìn)行考察,而完全不必進(jìn)行另一個(gè)方面的考察。也就是說(shuō),在日本刑法理論中,“違法性”中的“法”的含義,也不僅包括制定法而且包括倫理規(guī)范的整體;“違法性”的判斷也是以符合刑事法律規(guī)定的行為是否具有正確性為理論任務(wù)的。
(二)英美刑法理論中的“違法性”概念
在英美刑法理論中,由于新近的理論發(fā)展,尤其是由于美國(guó)學(xué)者對(duì)德國(guó)刑法原理的比較性研究,使得中國(guó)學(xué)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英文表述與德文表述之間的關(guān)系:德文Rechtswidrigkeit這個(gè)概念,就是指英文中以“wrong”為詞根的一些詞,例如“wrongful”,“wrongfulness”,“wrongdoing”等。⑦在英文的法律詞匯中,“wrong”⑧或者“wrongful”⑨的基本意思就是指具有“不公正或者不正義”的特征,與此相適應(yīng),“wrong”這個(gè)詞所表達(dá)的意思,就不僅可能以法律規(guī)定為根據(jù),而且可能以道德上的要求為根據(jù),⑩當(dāng)然,這種狀態(tài)與英美法系中侵權(quán)法與刑法的密切關(guān)系有關(guān)。從基本意思上說(shuō),“wrong”指的是一個(gè)行為或者某種事件所具有的錯(cuò)誤性。至于把“wrong”翻譯成“違法性”(11)還是“錯(cuò)誤”(12),則完全是在中文翻譯上可以討論的問(wèn)題。
(三)前蘇聯(lián)與我國(guó)刑法理論中的“違法性”概念
在前蘇聯(lián)的刑法理論中,由于犯罪實(shí)質(zhì)概念的作用,違法性在相當(dāng)一段時(shí)間里,并不被認(rèn)為在犯罪的成立或者犯罪的概念上具有重要意義。在犯罪概念意義上,最早提出把違法性作為犯罪實(shí)質(zhì)特征的前蘇聯(lián)刑法學(xué)者是杜爾曼諾夫。他認(rèn)為,犯罪是“危害社會(huì)的、違反刑事法律的、有責(zé)任能力的和依法應(yīng)受懲罰的作為或不作為。”(13)前蘇聯(lián)的刑法理論在使用違法性或者刑事違法性這個(gè)概念時(shí),主要是為了區(qū)分犯罪與其他違法行為之間的界限,“按照違法行為的社會(huì)危害程度把它們分為刑事違法行為、違反紀(jì)律行為和行政過(guò)失行為”。(14)這樣看來(lái),前蘇聯(lián)刑法理論使用的違法性指的就是刑事違法性。
在前蘇聯(lián)刑法理論中使用的“違法性”(пpотивоправность)這個(gè)詞,意思是與法相矛盾或者相抵觸的性質(zhì)。(15)不過(guò),在前蘇聯(lián)刑法理論中的“違法性”中的“法”所使用的Пpaво這個(gè)詞根,雖然它的基本含義仍然是“法”、“權(quán)”、“權(quán)利”,(16)但是,如果把這個(gè)詞放在前蘇聯(lián)主張犯罪實(shí)質(zhì)概念、長(zhǎng)期不采納“罪刑法定原則”、允許類推的語(yǔ)境下來(lái)理解,就會(huì)有新的發(fā)現(xiàn)。在前蘇聯(lián)的法律詞匯中,雖然這個(gè)“法”首先是指制定法與成文法意義上的刑法,但是,并不排除法律沒(méi)有規(guī)定時(shí)可以適用的不成文法意義上的“法”。也就是說(shuō),在前蘇聯(lián)刑法理論中,法與對(duì)錯(cuò)是不加區(qū)分的,在不主張罪刑法定原則和主張類推的情況下,在認(rèn)定犯罪時(shí),甚至成文法與不成文法也是進(jìn)行入罪性適用的。Право也是一個(gè)整體!
在蘇維埃刑法分則的內(nèi)容中,有的刑法學(xué)者可能在特定的語(yǔ)境下使用這個(gè)概念。例如,特拉伊寧在說(shuō)明“表明違法性的特征”時(shí),以《蘇俄刑法典》第182條第4款為例:“沒(méi)有按規(guī)定程序取得……許可,而制造……刀劍的……”,指出“在這種具體場(chǎng)合,違法性(未經(jīng)許可)……正是與作為刑事責(zé)任的一般前提的違法性不同的那種違法性的具體形式。”(17)很明顯,在這里,“違法性”雖然有一般和具體之分,但指的都是刑事違法性,也就是違反刑事法律的性質(zhì)。
在我國(guó)的刑法理論中,1979年以前的刑法教材常常不提犯罪具有違法性這一特征。這主要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我國(guó)只有刑事單行法規(guī),沒(méi)有刑法典,“很多犯罪的定罪判刑主要依據(jù)政策和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因此,強(qiáng)調(diào)犯罪必須具有違反刑法的特征,不僅不符合實(shí)際,而且還可能束縛同犯罪進(jìn)行斗爭(zhēng)。”(18)在1979年刑法典通過(guò)之后,根據(jù)“以法律為準(zhǔn)繩”的要求,“危害社會(huì)的行為必須同時(shí)是觸犯刑法規(guī)定的行為,才能構(gòu)成犯罪”,因此,違法性也就是刑事違法性,就成為我國(guó)刑法界公認(rèn)的犯罪特征。
不過(guò),我國(guó)刑法理論對(duì)于違反(雖然是在刑法中規(guī)定的)國(guó)家(法律或者法規(guī))規(guī)定的行為性質(zhì),一般并不清楚地認(rèn)定為是刑事違法性,而是一方面認(rèn)定為社會(huì)危害性的表現(xiàn),另一方面又把對(duì)這種規(guī)定的無(wú)認(rèn)識(shí)或者錯(cuò)誤認(rèn)識(shí),認(rèn)定為“法律上的錯(cuò)誤”。(19)在這一點(diǎn)上,我國(guó)刑法學(xué)者保留了一個(gè)不是違反刑法的“違反法律的性質(zhì)”,雖然概念還不清晰,但是與前蘇聯(lián)的理論有所不同。
(四)小結(jié)
通過(guò)對(duì)以上這些概念的比較,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結(jié)論:
第一,關(guān)于“違法性”概念的根據(jù)。德日英美刑法理論對(duì)于“違法性”中的“法”,雖然在表述的清晰性上有區(qū)別,但是基本上都認(rèn)為,“違法性”中的“法”指的不僅是刑法,而且包括其他法,其中,德國(guó)刑法理論明確指出要根據(jù)整個(gè)法律制度來(lái)對(duì)違法性作出評(píng)價(jià)。在前蘇聯(lián)和我國(guó)的刑法理論中,基本上主張“違法性”就是“刑事違法性”,也就是說(shuō),“違法性”中的法指的就是刑法,盡管我國(guó)刑法理論在“刑法上的認(rèn)識(shí)錯(cuò)誤”部分,還使用了不清晰的“違反法律”的概念。簡(jiǎn)言之,在我們討論的“違法性”這個(gè)語(yǔ)境下,“法(Recht)”和“法律(Gesetz)”在中文中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卻涉及是否包括不成文法、有關(guān)的基本含義是什么等重大問(wèn)題。
第二,關(guān)于“違法性”概念的表述。由于根據(jù)的不同,為了敘述便利和準(zhǔn)確表述,如果沒(méi)有特別說(shuō)明,下文使用的“違法性”是不包括“刑事違法性”的,也就是說(shuō),“違法性”和“刑事違法性”是有著重大區(qū)別的兩個(gè)概念。中國(guó)刑法學(xué)者在“法律上的錯(cuò)誤”項(xiàng)下保留的那個(gè)不清晰的“違反法律”所指向的內(nèi)容,在本文中將予以特別說(shuō)明。
第三,關(guān)于“違法性”概念的基本含義。“違法性”的基本含義是(由于違反整體法律制度而)無(wú)法得到具有正確性的評(píng)價(jià),“刑事違法性”的基本含義是違反了刑事法律的規(guī)定。
二、違法性概念的體系性功能
對(duì)違法性概念的體系性功能進(jìn)行考察,需要結(jié)合違法性的體系性位置來(lái)一并考慮。
在前蘇聯(lián)和我國(guó)一般的刑法理論中,刑事違法性和社會(huì)危害性“具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凡是具有嚴(yán)重社會(huì)危害性的行為,也必然具有刑事違法性”。(20)刑事違法性和社會(huì)危害性的并列或者跟隨關(guān)系,在前蘇聯(lián)和我國(guó)使用“社會(huì)危害性”作為犯罪本質(zhì)的刑法理論中,基本上得到了承認(rèn)。在這個(gè)犯罪理論體系中,刑事違法性概念所起的作用,是與社會(huì)危害性一起,為刑法規(guī)定犯罪的正當(dāng)性和合理性提供理論支持。
在英美刑法理論中,違法性的總則性理論位置還不清晰。英美學(xué)者不僅可能在立法階段上使用違法性(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行為所具有的錯(cuò)誤性),用以論證刑事立法進(jìn)行犯罪化的根據(jù),(21)而且更普遍的是在司法階段,在自我防衛(wèi)和正當(dāng)化根據(jù)部分中,使用違法性和與之相關(guān)的過(guò)錯(cuò)(fault)概念,來(lái)說(shuō)明排除刑事責(zé)任的根據(jù)。與德國(guó)的理論體系相比較,英美刑法中的違法性概念雖然還沒(méi)有獲得“總則”性地位,但是,它所發(fā)揮的基本理論功能,在立法階段是試圖為規(guī)定犯罪的正當(dāng)性和合理性作出輔說(shuō)明,在司法階段是為說(shuō)明排除刑事責(zé)任的根據(jù)服務(wù)的。
在德國(guó)刑法理論中,違法性的理論位置在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也被日本學(xué)者翻譯為行為構(gòu)成該當(dāng)性)之后,在罪責(zé)之前,它的理論任務(wù)是說(shuō)明一個(gè)行為在具有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之后,是否具有根據(jù)整體法制度可以得出的正確性判斷,從而為罪責(zé)性評(píng)價(jià)提供前提。在這個(gè)理論位置和理論任務(wù)方面,困擾中國(guó)學(xué)者的問(wèn)題主要是:
第一,違法性概念與法益概念的關(guān)系
違法性與法益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它們?cè)诶碚撐恢煤屠碚摴δ苌隙加泻艽蟮膮^(qū)別。在德國(guó)刑法理論中,對(duì)法益的概念曾經(jīng)存在過(guò)很大的爭(zhēng)論,法益理論仍然“還屬于刑法中最不精確地得到說(shuō)明的基礎(chǔ)問(wèn)題”。(22)但是,如果人們把具有違法性的行為理解為“對(duì)法益的侵害或者危害”,(23)那么,法益就成為違法性概念指向的對(duì)象。如果人們同意把法益區(qū)分為先法性法益、憲法性法益和后刑法法益,(24)那么,我們就可以看到:后刑法法益,也就是在刑事立法規(guī)定之后在刑法中表現(xiàn)出來(lái)的那種法益,是為說(shuō)明行為具有違法性的(形式和)內(nèi)容服務(wù)的;而憲法性法益,也就是處于刑法之前但是位于憲法之后的法益,以及先法性法益,也就是法律尚未明確規(guī)定的那種法益(如果我們承認(rèn)的話),都可以成為“批評(píng)法理的”工具,用來(lái)測(cè)量已經(jīng)寫(xiě)好的刑法,(25)也就是說(shuō),用來(lái)作為說(shuō)明現(xiàn)行法律規(guī)定的恰當(dāng)性以及作為排除刑事責(zé)任根據(jù)的基礎(chǔ)。“實(shí)質(zhì)違法性”的概念,只有在“一種法益的侵害或者危害,與規(guī)范共同生活的法律制度的目的相沖突時(shí)”,(26)才被提出來(lái)。應(yīng)當(dāng)注意,法益概念本身甚至法益受到侵害的具體事實(shí)和現(xiàn)象,并不當(dāng)然說(shuō)明“違法性”和“實(shí)質(zhì)違法性”本身。這里的思路是:不正確的行為會(huì)使法益受到侵害,但是,使法益受到侵害的行為并不絕對(duì)是不正確的!
第二,違法性概念與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概念的關(guān)系
在違法性和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這兩個(gè)概念之間,雖然曾經(jīng)有理論主張,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不是獨(dú)立的犯罪要素,其存在于違法性之中”,(27)但是,在現(xiàn)代主張區(qū)分違法性和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的理論中,這兩個(gè)概念是有明顯區(qū)別的。一個(gè)行為由于違反了一種法律禁令或者法定要求而在形式上成為違法時(shí),雖然有可能將兩者聯(lián)系在一起,但是,違法性,或者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是形式違法性,與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在體系性位置和體系性功能上仍然有著區(qū)別。形式違法性“只是在形式上表示該行為在法律上不被允許而已”,(28)而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僅僅指出了這個(gè)行為符合刑法的禁止性規(guī)定,這種符合刑法規(guī)定的性質(zhì)還完全不涉及這個(gè)行為是否在法律上不被允許的問(wèn)題!在這里的思路是: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說(shuō)明了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guī)定;形式違法性說(shuō)明的是“符合行為構(gòu)成的、在實(shí)質(zhì)性違法上不能通過(guò)排除不法的根據(jù)來(lái)包括的違法的行為”。由于脫離實(shí)質(zhì)違法性的形式違法性在理論體系上的位置和功能上與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非常相近,并且,形式違法性與實(shí)質(zhì)違法性之間本來(lái)應(yīng)當(dāng)存在的緊密聯(lián)系,因此,現(xiàn)代德國(guó)刑法理論中有重要影響的理論已經(jīng)認(rèn)為:“這樣一種概念的形成不僅是多余的,而且是誤導(dǎo)性的”。(29)由于這個(gè)原因,筆者認(rèn)為,單獨(dú)研究違法性與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之間的關(guān)系,尤其是研究形式違法性的概念和功能,需要認(rèn)真考慮其中的必要性和意義問(wèn)題。
第三,違法性概念與刑事違法性概念的關(guān)系
如前所述,違法性在德日英美刑法理論體系中的基本含義是行為具有從法秩序看來(lái)的“不正確性”,也就是“錯(cuò)誤性”,刑事違法性在前蘇聯(lián)和我國(guó)刑法理論體系中的基本含義是“違反刑法性”。因此,兩個(gè)概念在體系性位置和理論功能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區(qū)別。簡(jiǎn)言之,前者的思路是:在認(rèn)定行為符合刑法規(guī)定之后,還必須進(jìn)行對(duì)錯(cuò)判斷,錯(cuò)的不一定有罪,對(duì)的一定無(wú)罪;后者的思路是:符合刑法規(guī)定的行為就是錯(cuò)的,錯(cuò)的就是有罪的。
第四,違法性概念的理論功能到底是什么
在德國(guó)刑法理論中,違法性的理論位置是安排在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之后和罪責(zé)之前的。對(duì)一個(gè)行為的評(píng)價(jià),只有在得出具有違法性的評(píng)價(jià)之后,才能進(jìn)入下一階段的考察(罪責(zé)問(wèn)題),否則,刑事責(zé)任問(wèn)題就被排除了。這就是說(shuō),在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之后安排的違法性,就為更嚴(yán)格地限制刑事責(zé)任提供了一個(gè)機(jī)會(huì)。雖然通過(guò)違法性考察的行為是具有違法性的,但是,這個(gè)概念的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通過(guò)確認(rèn)不具有不正確性來(lái)排除刑事責(zé)任。因此,筆者認(rèn)為,違法性的理論功能是出罪性的。相比之下,刑事違法性不是一個(gè)單獨(dú)的判斷過(guò)程,嚴(yán)格地說(shuō),對(duì)于刑事違法性的符合性進(jìn)行判斷的過(guò)程,就是認(rèn)定犯罪構(gòu)成成立的過(guò)程,而“犯罪構(gòu)成是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的唯一根據(jù)”,因此,筆者認(rèn)為,刑事違法性的理論功能是入罪性的。更準(zhǔn)確地說(shuō),違法性是在確定了行為符合刑法規(guī)定的要求這個(gè)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解決這個(gè)行為是否仍然具有錯(cuò)誤性的問(wèn)題;刑事違法性僅僅解決的是行為是否符合刑法規(guī)定的問(wèn)題,這個(gè)行為是否由于不具有錯(cuò)誤性而應(yīng)當(dāng)被排除刑事責(zé)任的問(wèn)題,在這個(gè)概念所存在的特定體系中,甚至主要的不是通過(guò)這個(gè)概念(而是通過(guò)社會(huì)危害性)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
對(duì)于違法性的理論位置和理論功能,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總結(jié):違法性處于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構(gòu)成要件該當(dāng)性)之后的體系性地位,在入罪性考慮之后安排了出罪性考慮,使得犯罪的成立,不僅必須具備法律所要求的要素,而且必須具備整體法律所否定的錯(cuò)誤性,這種理論安排可以使對(duì)犯罪的設(shè)立性思考達(dá)到更加準(zhǔn)確的程度。相比之下,刑事違法性的概念,先被認(rèn)為是社會(huì)危害性所決定和派生的,后被認(rèn)為是社會(huì)危害性的法律基礎(chǔ),(30)也就是說(shuō),它僅僅作為決定犯罪能否成立的特征之一,承擔(dān)的主要是入罪的功能。由于刑事違法性一般不在“正當(dāng)防衛(wèi)”或者“排除犯罪性的行為”部分運(yùn)用,因此,在刑事責(zé)任成立之后,不使用刑事違法性而直接使用社會(huì)危害性進(jìn)行排除刑事責(zé)任的思維模式,在思路的簡(jiǎn)明清晰性和邏輯的一貫性方面,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三、中國(guó)刑法理論對(duì)違法性概念的借鑒問(wèn)題
中國(guó)刑法理論對(duì)借鑒違法性概念表現(xiàn)了極大的興趣。筆者也主張,中國(guó)刑法理論應(yīng)當(dāng)借鑒并采納違法性的概念。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改善中國(guó)刑法的犯罪論體系;
第二,確立更準(zhǔn)確的關(guān)于成立犯罪的思維方式。
在使用“刑事違法性”(其實(shí)是社會(huì)危害性)概念的體系中,從犯罪的成立條件來(lái)說(shuō),具有“簡(jiǎn)明易懂”和“比較容易地直接得到特定的意識(shí)形態(tài)觀念的支持并為之服務(wù)”的特點(diǎn),因此,這種體系“在革命勝利初期”,對(duì)于爭(zhēng)取民眾的支持是十分有利的。(31)危害社會(huì)的就是違法的,因而也就是有罪的!這個(gè)思路在什么是“危害社念”有(尤其是基于階級(jí)性而取得的)基本共識(shí)的前提下,的確簡(jiǎn)單明了。然而,從犯罪的排除條件方面看來(lái),使用刑事違法性的理論體系就不僅喪失了這種簡(jiǎn)單明了的特征,而且處于邏輯不清的處境之中。排除犯罪的條件是在犯罪成立之后進(jìn)行考慮的,因?yàn)椤胺缸飿?gòu)成是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的唯一根據(jù)”,而排除犯罪的條件又沒(méi)有包括在犯罪構(gòu)成之中,因此,在犯罪已經(jīng)構(gòu)成的情況下去討論犯罪的不構(gòu)成(至少?zèng)]有超過(guò)必要限度的正當(dāng)防衛(wèi)是完全不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的),不僅在理論上要使用同一個(gè)“社會(huì)危害性”概念,既進(jìn)行入罪性評(píng)價(jià),又進(jìn)行出罪性評(píng)價(jià),至少在形式上產(chǎn)生了那種既賣(mài)矛又賣(mài)盾的尷尬問(wèn)題,而且導(dǎo)致實(shí)踐中,在已經(jīng)入罪的情況下再進(jìn)行出罪性辯護(hù)面臨重大的困難,刑法理論的發(fā)展所追求的克服司法任意的問(wèn)題也難以避免。應(yīng)當(dāng)指出,在這個(gè)理論體系中,刑事違法性在排除犯罪的評(píng)價(jià)中基本上沒(méi)有發(fā)揮什么重要作用,充其量是在防衛(wèi)過(guò)當(dāng)?shù)那闆r下再次發(fā)揮入罪的法律根據(jù)的作用。在中國(guó)社會(huì)和中國(guó)刑法的語(yǔ)境下,這個(gè)思維方式和法律規(guī)定在起刑點(diǎn)比較高,也就是犯罪的危害性比較明顯的情況下,還不容易暴露出特別嚴(yán)重的弱點(diǎn),但是,在改革開(kāi)放使中國(guó)進(jìn)入高速發(fā)展期,整個(gè)國(guó)家進(jìn)入“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社會(huì)呼喚更嚴(yán)密的法律保護(hù)和刑法保護(hù)時(shí),這個(gè)理論體系就難以處理用以往的觀點(diǎn)看來(lái)比較細(xì)微、但是在今天又具有重大社會(huì)價(jià)值的那些問(wèn)題了,例如,環(huán)境犯罪、腐敗犯罪、金融犯罪、證券犯罪、犯罪、交通犯罪、食品衛(wèi)生安全犯罪、生產(chǎn)安全犯罪,乃至輕微的侵犯人身權(quán)的犯罪。很明顯,以刑事違法性概念為代表的思維方式已經(jīng)明顯難以滿足社會(huì)的要求了。
在使用違法性概念的體系中,犯罪的成立必須由兩步(或者三步)組成,沒(méi)有完成全部評(píng)價(jià)步驟,犯罪就不能成立。這樣,雖然在第一步中考慮的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是以入罪性為基本特征的,但是,即使在符合行為構(gòu)成的情況下,在這個(gè)理論體系中,入罪也是沒(méi)有完成的。在違法性判斷的過(guò)程中,符合行為構(gòu)成的可以根據(jù)整體法律制度的要求進(jìn)行判斷而排除刑事責(zé)任。這里的思路是:符合刑法規(guī)定的不一定有罪,符合法律制度要求的一定無(wú)罪。這個(gè)思路雖然具有法律技術(shù)要求性高、結(jié)構(gòu)比較復(fù)雜等不利于法治后進(jìn)國(guó)家掌握的要素,但是也具有多方面的明顯好處。一是整體理論體系比較合理,犯罪不僅必須具備刑法所規(guī)定的入罪條件,而且必須不具備法律制度所允許的出罪條件;二是思維方式比較合理,有利于實(shí)現(xiàn)準(zhǔn)確的思考,違法性和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乃至法益,都各有各的理論位置,各有各的理論功能;三是便于滿足社會(huì)和法治的進(jìn)步,面對(duì)日益增長(zhǎng)的社會(huì)和個(gè)人對(duì)安全和自由的需要,完善的理論體系和準(zhǔn)確的思維方式,有望為社會(huì)提供符合法治要求的刑法理論產(chǎn)品。
筆者認(rèn)為,可以考慮在中國(guó)犯罪論體系的改革過(guò)程中,借鑒違法性的概念,通過(guò)逐步改革的步驟,改進(jìn)現(xiàn)有的體系。在目前的階段上,與違法性概念直接有關(guān)的改革有兩個(gè)要點(diǎn):一是明確犯罪構(gòu)成不是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的唯一根據(jù);二是把正當(dāng)防衛(wèi)和緊急避險(xiǎn)部分改造成“正當(dāng)化與免責(zé)”部分,并使之成為評(píng)價(jià)刑事責(zé)任的一部分,即犯罪的成立,不僅必須以犯罪構(gòu)成的成立為條件,而且必須以沒(méi)有正當(dāng)化(或者免責(zé))根據(jù)為條件。當(dāng)然,這個(gè)改造任務(wù)的完成并不是這么簡(jiǎn)單的,還需要進(jìn)行大量的研究工作。
不過(guò),在這個(gè)研究工作中,如何看待中國(guó)刑法理論應(yīng)當(dāng)使用的違法性概念的名稱,以及如何看待違法性認(rèn)識(shí),是目前中國(guó)學(xué)者關(guān)心的緊迫問(wèn)題。
筆者認(rèn)為,對(duì)于中國(guó)刑法理論應(yīng)當(dāng)使用的違法性名稱,可以使用兩個(gè)辦法:一是直接使用德國(guó)刑法理論中的違法性概念,就像現(xiàn)在使用的刑事違法性是來(lái)自前蘇聯(lián)的理論一樣;二是改變名稱,例如,改稱錯(cuò)誤性或者其他能夠更準(zhǔn)確說(shuō)明Rechtswidrigkeit含義的譯法。筆者認(rèn)為,使用諸如形式違法性或者實(shí)質(zhì)違法性的概念,或者仍然沿用刑事違法性的概念,由于其在原有體系中已有的確定意思,因此,用這種名至實(shí)不至的方法加以命名,很容易造成思維的混亂和交流的困難。
在違法性認(rèn)識(shí)方面,根據(jù)前面對(duì)違法性概念和功能的分析,筆者認(rèn)為,中國(guó)刑法理論應(yīng)當(dāng)采取謹(jǐn)慎分析的態(tài)度。由于違法性的理論位置在行為構(gòu)成符合性之后,并且,其基本理論功能是出罪性的,因此,違法性認(rèn)識(shí)應(yīng)當(dāng)也是為出罪服務(wù)的。但是,由于違法性中指向的“法”所具有的廣泛性,因此,在改造中國(guó)刑法理論的過(guò)程中,就應(yīng)當(dāng)顧及其中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
首先,行為人在行為時(shí),對(duì)自己行為違反刑事法律規(guī)定的性質(zhì)認(rèn)識(shí)錯(cuò)誤,以及對(duì)自己的行為的對(duì)錯(cuò)性或者在整體法律制度上的評(píng)價(jià)的認(rèn)識(shí)錯(cuò)誤,在前蘇聯(lián)和我國(guó)刑法理論中屬于“對(duì)犯罪客體的認(rèn)識(shí)錯(cuò)誤”或者屬于“對(duì)刑事違法性的認(rèn)識(shí)錯(cuò)誤”。(32)從國(guó)內(nèi)外的研究看來(lái),把這部分內(nèi)容列入罪過(guò)的意識(shí)因素之中,要么“對(duì)于刑事責(zé)任的有無(wú)不發(fā)生作用”,(33)要么主張“不得以不知法律而無(wú)犯意或免除刑事責(zé)任”。因此,把這部分內(nèi)容列入違法性認(rèn)識(shí)的范疇沒(méi)有什么實(shí)際意義,在理論上的意義也不明顯。
其次,對(duì)于在刑法中規(guī)定的作為犯罪成立條件的其他法律法規(guī)的認(rèn)識(shí),例如,走私罪所要求的“海關(guān)法規(guī)”,交通肇事罪中的“交通管理法規(guī)”等等,筆者曾經(jīng)主張它們屬于“表明這些犯罪的客觀要件的重要事實(shí)”,(34)也就是說(shuō),在對(duì)這些非刑事法律和法規(guī)發(fā)生認(rèn)識(shí)錯(cuò)誤時(shí),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對(duì)事實(shí)上的認(rèn)識(shí)錯(cuò)誤”來(lái)處理。中國(guó)刑法理論引入違法性概念,現(xiàn)有的犯罪構(gòu)成的體系性位置和功能也有可能發(fā)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對(duì)于這些非刑事法律法規(guī)的認(rèn)識(shí),是否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德國(guó)刑法理論發(fā)展為“行為構(gòu)成錯(cuò)誤”和“禁止性錯(cuò)誤”,則是有待研究的問(wèn)題。不過(guò),筆者認(rèn)為,中國(guó)刑法理論不一定需要以這種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為條件,來(lái)決定是否采納違法性概念。
總之,在采納違法性概念之后的中國(guó)刑法理論,在犯罪論部分有望實(shí)現(xiàn)思維方式的根本改變,這就是:人罪的根據(jù)不是行為具有社會(huì)危害性,而是行為屬于刑法所禁止的(行為為什么被刑法所禁止以及這種禁止是否妥當(dāng)?shù)膯?wèn)題,則成為一個(gè)刑事立法的正當(dāng)性和合理性問(wèn)題,而不再是入罪的根據(jù)問(wèn)題);出罪的根據(jù)不是法益不受侵犯(不是以法益為根據(jù)),而是行為的無(wú)錯(cuò)誤性(雖然侵犯了法益,但是不具有違法性),行為的無(wú)錯(cuò)誤性根據(jù)不僅來(lái)自刑法和其他制定法,而且,在可以適用的情況下,來(lái)自非制定法,也就是說(shuō),來(lái)自整個(gè)法律制度可以作出的評(píng)價(jià)。相信人們會(huì)同意,這個(gè)思維方式會(huì)更有利于人權(quán)的保護(hù),更有利于我國(guó)社會(huì)和個(gè)人的安全和自由的發(fā)展。
注釋:
①See Wahrig Deutsches Wrterbuch, 6. Auflage, Bertelsmann Lexikon Verlag.
②參見(jiàn)Creifelds,Rechtswrterbuch, 11. Auflage,C. H. Beck中的相關(guān)詞條。
③同注②。
④參見(jiàn)[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說(shuō)(總論)》,馮軍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頁(yè)。
⑤同注①。
⑥參見(jiàn)[日]大谷實(shí)著:《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175頁(yè)。
⑦參見(jiàn)喬治·P·弗萊徹著:《刑法的基本概念》,王世洲主譯,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頁(yè)。
⑧See David M.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⑨See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8th Edition, Thomson/West, 2004.
⑩同注⑤,David M.Walker書(shū)。
(11)同注④,弗萊徹書(shū),第97頁(yè)。
(12)參見(jiàn)[英]戴維·沃克著:《牛津法律大詞典》,北京社會(huì)與科技發(fā)展研究所組織翻譯,光明日?qǐng)?bào)出版社1988年版。
(13)[前蘇]A·A·皮昂特科夫斯基等著:《蘇聯(lián)刑法科學(xué)史》,曹子丹等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頁(yè)。
(14)[前蘇]A·H·特拉伊寧著:《犯罪構(gòu)成的一般學(xué)說(shuō)》,王作富等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58年版,第139頁(yè)。
(15)參見(jiàn)“БОЛЪШОЙ ТОЛОВЪЙ СЛОВАРЪ РУССОГО Я3ЪКА”,Санкт-пeтepбуpr,“НОРИНТ”,2000 r.(俄羅斯科學(xué)院,《大俄語(yǔ)詳解詞典》,2000年版)。
(16)同注①。
(17)[前蘇]A·A·皮昂特科夫斯基等著:《蘇聯(lián)刑法科學(xué)史》,曹子丹等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頁(yè)。
(18)參見(jiàn)楊春洗、甘雨沛、楊敦先、楊殿升著:《刑法總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頁(yè)。
(19)例如,高銘喧主編:《刑法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173頁(yè);肖揚(yáng)主編:《中國(guó)新刑法學(xué)》,上海科技文獻(xiàn)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頁(yè)。
(20)楊春洗、甘雨沛、楊敦先、楊殿升著:《刑法總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頁(yè)、第33頁(yè)。
(21)參見(jiàn)Andrew Ashworth,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4th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至少參見(jiàn)第42頁(yè)以下,在那里討論了被犯罪化的行為是否只應(yīng)當(dāng)以道德為基礎(chǔ)的問(wèn)題。
(22)[德]克勞斯·羅克辛著:《德國(guó)刑法學(xué)總論》(第一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yè)以下,第26頁(yè)。
(23)李斯特語(yǔ),參見(jiàn)前注③,第390頁(yè)。
(24)參見(jiàn)劉孝敏:“法益的體系性位置與功能”,載《法學(xué)研究》2007年第1期。
(25)同注③,第391頁(yè)以下。
(26)同注③,第390頁(yè)。
(27)[日]曾根威彥著:《刑法學(xué)基礎(chǔ)》,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頁(yè)。
(28)[日]大谷實(shí)著:《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177頁(yè)。
(29)[德]克勞斯·羅克辛著:《德國(guó)刑法學(xué)總論》(第一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頁(yè)。
(30)參見(jiàn)肖揚(yáng)主編:《中國(guó)新型法學(xué)》,上海科技文獻(xiàn)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頁(yè)。
(31)參見(jiàn)王世洲、劉孝敏:“關(guān)于中國(guó)刑法學(xué)理論體系起點(diǎn)問(wèn)題的思考”,載《政法論壇》2004年第6期。
(32)參見(jiàn)王世洲著:《從比較刑法到功能刑法》,長(zhǎng)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頁(yè)以下。
第5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法律的概念分析作為法律哲學(xué)的一種研究方法是隨著現(xiàn)代分析哲學(xué)和語(yǔ)言哲學(xué)在法律哲學(xué)中的應(yīng)用而出現(xiàn)的,是哈特《法律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Law) 開(kāi)創(chuàng)了自覺(jué)地對(duì)法律進(jìn)行概念分析的先河。 在論證的結(jié)構(gòu)上,本部分首先介紹Scott J. Shapiro 關(guān)于law、the law 和law的明確區(qū)分,然后再分析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及其后記( Postscript) 中所隱含的區(qū)分,以此來(lái)總結(jié)法律是什么?這個(gè)提問(wèn)方式或概念分析指的是什么。下一部分再討論德沃金語(yǔ)義學(xué)之刺的論證及法律實(shí)證主義的回應(yīng),主要是哈特的回應(yīng)。這兩部分內(nèi)容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分別討論概念分析是什么和不是什么。首先從《法律的概念》開(kāi)始討論關(guān)于law 的各種用法的微妙含義。
二、概念分析與語(yǔ)詞分析: 對(duì)德沃金語(yǔ)義學(xué)之刺的回應(yīng)
Brian Bix 認(rèn)為,概念性定義( conceptual definitions) 瑐瑥可以指向三個(gè)不同的對(duì)象: ( 1) 追蹤并解釋語(yǔ)言用法( linguistic usage) ; ( 2) 發(fā)現(xiàn)一個(gè)概念的重要性( significance) ,而這個(gè)重要藏在我們關(guān)于用法的實(shí)踐與制度中; ( 3) 概念性定義也能夠強(qiáng)加一個(gè)道德的標(biāo)準(zhǔn),而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有可能也基于我們的用法。瑐瑦第一種僅僅是探尋語(yǔ)詞的意義; 第二種主要涉及到對(duì)實(shí)踐的總結(jié)與判斷,在道德上至少是有可能( 或意圖) 中立的; 而第三種則對(duì)道德判斷是開(kāi)放的。Brian Bix 指出,概念分析與用法相連,但是這個(gè)聯(lián)系是松散的。盡管如此,但是也會(huì)導(dǎo)致混淆,即認(rèn)為討論法律是什么?就是探尋語(yǔ)言的用法,這就是德沃金語(yǔ)義學(xué)之刺的論證。這個(gè)論證實(shí)際上就是認(rèn)為,實(shí)證主義把What is law?與What is thelaw?等同起來(lái),而德沃金認(rèn)為這樣是行不通的,它無(wú)法解釋并解決法律中的理論分歧。瑐瑧德沃金的看法是對(duì)的,但實(shí)證主義提出過(guò)這樣的主張嗎?
( 一) 德沃金語(yǔ)義學(xué)之刺的論證
德沃金為論述的需要而建構(gòu)了一種他所批評(píng)的靶子,即法律的單純事實(shí)觀點(diǎn)( the plain-factview of law) ,他把其描述為: 法律只是依賴于單純歷史事實(shí)( plain historical fact) 的事物,關(guān)于法律的唯一明智的分歧是關(guān)于法律機(jī)構(gòu)在過(guò)去實(shí)際上所做之決定的經(jīng)驗(yàn)分歧( empirical disagree-ment) ,而我稱之為理論分歧( theoretical disagreement) 的東西被認(rèn)為是虛幻的,且最好被理解為關(guān)于法律應(yīng)當(dāng)是什么而非關(guān)于法律是什么的看法。德沃金還認(rèn)為,他在《法律帝國(guó)》中所舉的四個(gè)樣本案例似乎構(gòu)成了單純事實(shí)觀點(diǎn)的反例: 在這些案件中的論證似乎是關(guān)于法律的,而非關(guān)于道德或忠誠(chéng)或修補(bǔ)( not morality or fidelity or repair) 。因此我們必須提出關(guān)于單純事實(shí)觀點(diǎn)的如下挑戰(zhàn): 為什么這一觀點(diǎn)堅(jiān)持[理論分歧的]出現(xiàn)( appearance) 在此僅是一種幻覺(jué)呢? 某些法律哲學(xué)家提出了一個(gè)令人驚異的回答。他們認(rèn)為,關(guān)于法律根據(jù)( the grounds of law) 的理論分歧必定是一種托詞,因?yàn)檎欠蛇@個(gè)語(yǔ)詞的意義( the very meaning of the wordlaw) 使得法律依賴于某些特定的標(biāo)準(zhǔn),而且他們還認(rèn)為,拒絕或挑戰(zhàn)這一標(biāo)準(zhǔn)的任何法律人都將是在自相矛盾地胡言亂語(yǔ)。在德沃金看來(lái),他提出的關(guān)于法律的理論分歧也是關(guān)于法律是什么的爭(zhēng)論,而非關(guān)于道德、忠誠(chéng)或修補(bǔ)的爭(zhēng)論。
他基本上是在提出一種新的概念框架在對(duì)法律進(jìn)行解釋,但引起爭(zhēng)議的并不在此,而是在這段引文的最后他對(duì)法律的語(yǔ)義學(xué)理論所做的一種概括。德沃金在語(yǔ)詞的意義( themeaning of the word) 、標(biāo)準(zhǔn)( criteria) 、共享規(guī)則( the shared rules) 和單純歷史事實(shí)之間建立了關(guān)聯(lián),這四者構(gòu)成了對(duì)德沃金意義上之法律語(yǔ)義學(xué)理論的完整說(shuō)明。標(biāo)準(zhǔn)提供了語(yǔ)詞的意義,我們共享的規(guī)則設(shè)定了這些標(biāo)準(zhǔn),而這些規(guī)則( 在上述那些法律哲學(xué)家看來(lái)) 又是和單純歷史事實(shí)聯(lián)系的一起的。對(duì)于這些規(guī)則和標(biāo)準(zhǔn),我們也許會(huì)有分歧,也許并不能完全意識(shí)到它們的存在,但這些都不影響一個(gè)共同的預(yù)設(shè),即我們確實(shí)共享著關(guān)于語(yǔ)詞之用法的標(biāo)準(zhǔn)。對(duì)于這種法律的語(yǔ)義學(xué)理論,德沃金做了這樣的概括: 某些哲學(xué)家堅(jiān)持認(rèn)為,法律人都遵循著判斷法律命題的某些特定的語(yǔ)言標(biāo)準(zhǔn)( certain linguistic criteria for judging propositions of law) ,他們也許是在無(wú)意中提出了確認(rèn)這些標(biāo)準(zhǔn)的理論。德沃金把這些理論統(tǒng)稱為法律的語(yǔ)義學(xué)理論,在他的概括中,似乎法律的語(yǔ)義學(xué)理論的標(biāo)志是判斷法命題的語(yǔ)言標(biāo)準(zhǔn)。
結(jié)語(yǔ)
在《法律的概念》的序言中,哈特指出他的這本書(shū)可以視為一個(gè)描述社會(huì)學(xué)的嘗試( an essayin descriptive sociology) ; 并指出,這是因?yàn)榫驼Z(yǔ)詞而探究其意義的做法是錯(cuò)誤的,諸多類型的社會(huì)情形或社會(huì)關(guān)系之間的重要區(qū)分,通過(guò)檢視相關(guān)表述的標(biāo)準(zhǔn)用法和這些表述依賴于通常未言明的一個(gè)社會(huì)語(yǔ)境的方式,就能得以澄清。這段表述帶有明顯的語(yǔ)言哲學(xué)色彩,提出了一個(gè)引起很大爭(zhēng)議的主張,即他的研究既是描述社會(huì)學(xué)的,又是概念分析的。
第6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一、光船租賃合同概念的再界定
光船租賃法律關(guān)系是一種租賃合同法律關(guān)系,對(duì)于光船租賃合同的理解,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多采用我國(guó)《海商法》第144條所下的定義,[2]252將光船租賃合同界定為:“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不配備船員的船舶,在約定的期間內(nèi)由承租人占有、使用和營(yíng)運(yùn),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從內(nèi)容的表述上看,這個(gè)概念與合同法上的租賃合同概念沒(méi)有本質(zhì)區(qū)別,①只是對(duì)租賃物進(jìn)行了特定化。同時(shí),這個(gè)概念與海商法其他租船合同的概念相比,主要在于強(qiáng)調(diào)出租人提供的船舶不配備船員以及船舶由承租人占有、使用和營(yíng)運(yùn)。在租船合同下,出租船舶是否配備船員的問(wèn)題,究其實(shí)質(zhì)就是確定由誰(shuí)來(lái)合法地占有和控制船舶的問(wèn)題。正如美國(guó)學(xué)者G.吉爾摩和C.L.布萊克所言,“以上所討論的租船合同(指定期租船合同和航次租船合同),都與貨物運(yùn)輸有關(guān),是仍舊控制船舶航行的一方與另一方簽訂的運(yùn)輸合同。而光船租賃合同在實(shí)際的作用和重要的法律后果上,船舶的占有權(quán)和控制權(quán)從一方當(dāng)事人轉(zhuǎn)移給了另一方當(dāng)事人,就像岸上不動(dòng)產(chǎn)的出租,出租人把附屬于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的許多權(quán)利和義務(wù)都已轉(zhuǎn)給了承租人”[3]。可見(jiàn),出租人提供的船舶是否配備船員只是光船租賃合同與其他租船合同在法律外延上的差別,而并未觸及到其法律概念的內(nèi)涵,因此不能揭示光船租賃合同概念的內(nèi)容。我們認(rèn)為,在界定光船租賃合同的概念時(shí)應(yīng)以探求其法律內(nèi)涵為宗旨,而不能僅停留在對(duì)法律外延的概括上,以《海商法》第144條的法律規(guī)定來(lái)詮釋光船租賃合同概念顯然并不確切。在此,筆者想引用英國(guó)學(xué)者S.Drury的論述來(lái)重識(shí)光船租賃合同的法律概念。“光船租賃合約,顧名思義,是一個(gè)船舶出租合約。依據(jù)該合約,租船人從船東那里取得了約定期限內(nèi)具有排他性的占有、控制船舶的權(quán)利。”[4]
二、合同法理論下的光船租賃權(quán)法律屬性
光船租賃合同屬于財(cái)產(chǎn)租賃合同,故就其權(quán)利屬性而言,光船租賃權(quán)應(yīng)屬于財(cái)產(chǎn)租賃權(quán),依民法學(xué)界的觀點(diǎn),一般財(cái)產(chǎn)租賃權(quán)的法律性質(zhì),概括起來(lái)主要有三種學(xué)說(shuō),[5]即債權(quán)說(shuō)、物權(quán)說(shuō)和債權(quán)物權(quán)化說(shuō)。目前,“債權(quán)物權(quán)化說(shuō)”的觀點(diǎn)為世界上多數(shù)國(guó)家的立法所采納。依此學(xué)說(shuō),一般財(cái)產(chǎn)租賃權(quán)的性質(zhì)為債權(quán),但法律為強(qiáng)化其效力,使其具有物權(quán)化的趨勢(shì)。這種趨勢(shì)帶來(lái)的法律效力上的一個(gè)顯著效果就是使租賃權(quán)具有對(duì)抗效力。從債權(quán)的一般理論上講,債權(quán)人不得以其債權(quán)對(duì)抗對(duì)標(biāo)的物享有物權(quán)的人。但在租賃關(guān)系中,承租人在租賃合同存續(xù)期間,可以其租賃權(quán)對(duì)抗取得租賃物所有權(quán)或其他物權(quán)的人,而對(duì)租賃物進(jìn)行使用和收益。這是租賃權(quán)“物權(quán)化”的最集中體現(xiàn)。在我國(guó)海商法學(xué)界,對(duì)光船租賃權(quán)法律性質(zhì)的認(rèn)識(shí)多與一般財(cái)產(chǎn)租賃權(quán)的性質(zhì)相同,認(rèn)為光船租賃權(quán)的性質(zhì)屬于債權(quán),但具有某些物權(quán)的特點(diǎn)。[2]93有觀點(diǎn)進(jìn)一步指出,[6]357-358光船租賃合同成立后,即使出租人將船舶讓與第三人,原光船租賃合同繼續(xù)有效,新的船舶所有人必須尊重承租人對(duì)船舶的租賃權(quán),即構(gòu)成合同法意義上的“買(mǎi)賣(mài)不破租賃”。該觀點(diǎn)主張光船租賃權(quán)本身具有對(duì)抗效力且對(duì)抗效力的發(fā)生時(shí)間始于光租合同成立。對(duì)此,筆者有不同意見(jiàn)。筆者認(rèn)為,光船租賃權(quán)有別于一般財(cái)產(chǎn)租賃權(quán)的“債權(quán)物權(quán)化”性質(zhì),其不具有物權(quán)對(duì)抗效力,故光船租賃權(quán)應(yīng)屬于“未被物權(quán)化”的債權(quán)。由此,光船租賃登記應(yīng)屬于債權(quán)登記。理由是:第一,未經(jīng)登記的光船租賃權(quán)不能適用“買(mǎi)賣(mài)不破租賃”規(guī)則。當(dāng)船舶被出租人讓與第三人時(shí),即便不會(huì)影響到光船租賃合同的效力,也并不意味著光船租賃權(quán)可以當(dāng)然對(duì)抗船舶買(mǎi)受人的權(quán)利。根據(jù)我國(guó)《船舶登記條例》第6條之規(guī)定,未經(jīng)登記的光船租賃權(quán),不得對(duì)抗第三人。這里的第三人,雖未指明包括哪些人,但也未排除船舶的買(mǎi)受人,因此對(duì)于已經(jīng)取得船舶所有權(quán)的買(mǎi)受人而言,未經(jīng)登記的光船租賃權(quán),顯然不能對(duì)抗船舶買(mǎi)受人的所有權(quán)。可見(jiàn),光船租賃權(quán)的對(duì)抗效力是在其依法履行了光船租賃登記程序后才具有的,而不是在光租合同成立時(shí)產(chǎn)生的。在光船租賃期間發(fā)生船舶的讓與時(shí),未經(jīng)登記的光船租賃權(quán)不能對(duì)抗船舶受讓人取得的船舶所有權(quán),因此不能構(gòu)成合同法意義上的“買(mǎi)賣(mài)不破租賃”。除了船舶買(mǎi)受人之外,“這里的第三人應(yīng)該是廣義的第三人,因?yàn)楣獯赓U不發(fā)生物權(quán)變動(dòng),未經(jīng)登記的光船租賃,僅在光船租賃合同當(dāng)事人之間發(fā)生效力,既不能對(duì)抗與船舶有系爭(zhēng)關(guān)系的第三人,也不能對(duì)抗與船舶無(wú)系爭(zhēng)關(guān)系的第三人”[6]69。因此,光船租賃權(quán)在沒(méi)有進(jìn)行光船租賃登記的情況下,不應(yīng)具有對(duì)抗效力,也不能適用“買(mǎi)賣(mài)不破租賃”的規(guī)則,其僅應(yīng)具有債權(quán)性質(zhì)。第二,未經(jīng)登記的光船租賃權(quán)不能對(duì)抗船舶抵押權(quán)。我國(guó)《海商法》第151條第一款規(guī)定,未經(jīng)承租人事先書(shū)面同意,出租人不得在光船租賃期間對(duì)船舶設(shè)定抵押權(quán)。有觀點(diǎn)指出,[7]該條款是間接地賦予光船租賃權(quán)對(duì)船舶抵押權(quán)的對(duì)抗效力。對(duì)此,筆者并不贊同。所謂光船租賃權(quán)對(duì)船舶抵押權(quán)的對(duì)抗效力,是以兩個(gè)權(quán)利的存在為前提條件的,當(dāng)兩個(gè)權(quán)利均已設(shè)定后,方可談及權(quán)利對(duì)抗問(wèn)題。顯然,《海商法》第151條第一款是對(duì)光船租賃合同雙方權(quán)利義務(wù)的規(guī)定,并不涉及光船租賃權(quán)與船舶抵押權(quán)的對(duì)抗效力問(wèn)題。因此,從《海商法》第151條中尚不能得出光船租賃權(quán)對(duì)船舶抵押權(quán)具有對(duì)抗效力的結(jié)論。如前所述,未經(jīng)登記的光船租賃權(quán)不具有對(duì)抗效力,不能對(duì)抗已經(jīng)設(shè)立的船舶抵押權(quán)。當(dāng)出租人未經(jīng)承租人事先書(shū)面同意而與第三人設(shè)定了船舶抵押權(quán)時(shí),該船舶抵押權(quán)也不會(huì)因《海商法》第151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而導(dǎo)致無(wú)效,此時(shí)光船承租人只能依據(jù)第151條第二款之規(guī)定“出租人違反前款規(guī)定,致使承租人遭受損失的,應(yīng)當(dāng)負(fù)賠償責(zé)任”,向光船出租人主張損害賠償。如前文所述,在英美法下,光租合同與期租、程租一樣都被認(rèn)為是“私人合約”而不要求進(jìn)行登記。由此,光船租賃權(quán)也是作為“私人合約”下的承租人權(quán)利而僅具有債權(quán)屬性的。出于立法淵源的考量,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海商法》下的光船租賃權(quán)是對(duì)英美法下光船租賃權(quán)的繼受,其法律性質(zhì)具有一致性。作為英美法下光船租賃合同的格式范本,波羅的海航運(yùn)公會(huì)制定的《標(biāo)準(zhǔn)光船租賃合同》(StandardBareboatCharter,租船合同代號(hào)“貝爾康”(BARECON))堪稱“私人合約”的典范。在《“BARECON”89》(1989年修訂版)第二部分(PARTⅡ)第10條中有這樣的約定:“船東只保證在未事前取得租船人的批準(zhǔn)時(shí),不得將船作任何(其他)抵押。”這一約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光船承租人的利益在光船出租人設(shè)定船舶抵押權(quán)時(shí)免受損失。因?yàn)樵谟⒚婪ㄏ拢@樣的法律風(fēng)險(xiǎn)是客觀存在的。由于光船租賃合同屬于“私人合約”,故光船租賃權(quán)僅能具有債權(quán)性質(zhì),而不存在“物權(quán)化”的表現(xiàn),因此船舶抵押權(quán)的實(shí)現(xiàn)就會(huì)直接影響到光船租賃權(quán)的行使,而這一點(diǎn)與大陸法下的一般財(cái)產(chǎn)租賃權(quán)完全不同。正是由于英美法中的光租租賃權(quán)的債權(quán)性質(zhì),承租人對(duì)船舶抵押權(quán)因?qū)崿F(xiàn)而產(chǎn)生的所有權(quán)等物權(quán)權(quán)利不能構(gòu)成任何實(shí)質(zhì)性的對(duì)抗力,所以在《“BARECON”89》中才將其設(shè)計(jì)成“事先同意”,以英美合同法規(guī)定的“保證條款”形式賦予光船承租人有權(quán)追究光船出租人違約責(zé)任的權(quán)利。①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格式條款與我國(guó)《海商法》第151條的規(guī)定完全吻合。由此可見(jiàn),我國(guó)光船租賃合同的立法設(shè)計(jì)與英美法下的光租合同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性,光船租賃權(quán)在“私人合約”的框架內(nèi)僅具有債權(quán)屬于,而不具有物權(quán)化的特征。這樣的認(rèn)識(shí)對(duì)于明晰光船租賃合同法律關(guān)系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同時(shí)對(duì)于澄清和捋順光船租賃合同與光船租賃權(quán)登記制度之間的協(xié)調(diào)適用關(guān)系具有指導(dǎo)意義。
作者:李偉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
第7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制度是現(xiàn)代民商事領(lǐng)域中一個(gè)技術(shù)性比較強(qiáng)的民商事制度,它是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尤其是商事關(guān)系的發(fā)展而逐步發(fā)展起來(lái)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于商品交換關(guān)系高度發(fā)達(dá),社會(huì)關(guān)系復(fù)雜多樣,人們不可能事必躬親,于是制度就產(chǎn)生并得到發(fā)展。無(wú)論是在國(guó)內(nèi)貿(mào)易和國(guó)際貿(mào)易中,制度都得到廣泛的應(yīng)用。尤其是在作為國(guó)際商事領(lǐng)域的國(guó)際貿(mào)易中,許多業(yè)務(wù)工作都是通過(guò)各種人進(jìn)行的,其中包括普通人、經(jīng)紀(jì)人、運(yùn)輸人、保險(xiǎn)人、廣告人等等。現(xiàn)代制度的一個(gè)基本發(fā)展趨勢(shì)就是人職業(yè)化。在資本主義國(guó)家這些人多數(shù)都是公司。如果離開(kāi)了這些人,國(guó)際貿(mào)易就無(wú)法順利進(jìn)行。因此,我們必須對(duì)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制度有所了解,并在對(duì)外貿(mào)易業(yè)務(wù)中靈活運(yùn)用。
我們?cè)诹私鈬?guó)際商事法律制度之前,首先要明確、商事、國(guó)際商事以及國(guó)際商事法的基本概念。
一、、商事與國(guó)際商事
(一)
的概念在學(xué)界已經(jīng)基本形成了通說(shuō)。所謂(Agency)制度,是指人(Agent)按照本人(Principal)的授權(quán)(Authorization),代表本人同第三人發(fā)生法律行為,由此而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直接對(duì)本人發(fā)生效力的法律行為。這里所說(shuō)的“本人”就是委托人,也就是被人;“人”就是受要人的委托替本人辦事的人;而“第三人”則是泛指與人打交道的人。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具有以下幾個(gè)特征:
1.是一種法律行為。從的定義來(lái)看,畢竟是人與第三人之間發(fā)生的法律行為,它以設(shè)立、變更、終止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為目的。所以,它在性質(zhì)上屬于法律行為。這是的本質(zhì)性特征。
2.是基于本人或者被人的授權(quán)行為而發(fā)生。如果沒(méi)有本人的授權(quán)而進(jìn)行的,屬于無(wú)權(quán),不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權(quán)本質(zhì)上是一種權(quán)利。這是的權(quán)利性特征。
3.行為的法律后果最終歸屬于本人(被人)。由本人對(duì)人或被人的行為負(fù)責(zé)。這是的效力性特征。
【觀察】:老劉是一家公司老板,業(yè)務(wù)繁忙,于是委托朋友小李去天津購(gòu)買(mǎi)電腦軟件,小李去天津與A軟件公司簽定買(mǎi)賣(mài)合同,并履行完畢。在這個(gè)關(guān)系中,老劉是委托人,也叫本人;小李是人;A公司是第三人。老劉與小李之間是關(guān)系。
(二)商事
是商事的上位概念,商事是的一個(gè)種類。所謂商事,主要是指發(fā)生在商事領(lǐng)域的由商事人按照本人(商事被人)的授權(quán),代表本人同第三人發(fā)生商事法律行為,由此而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直接對(duì)本人發(fā)生效力的。商事除了具備的本質(zhì)性特征、權(quán)利性特征和效力性特征之外,還具有“商事性”的個(gè)性特征。商事性通常是具有營(yíng)業(yè)性質(zhì),或者說(shuō)以營(yíng)業(yè)為主要目的,一般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發(fā)生領(lǐng)域?yàn)樯淌骂I(lǐng)域,比如金融領(lǐng)域中的票據(jù)領(lǐng)域、保險(xiǎn)領(lǐng)域等,貿(mào)易領(lǐng)域中的運(yùn)輸領(lǐng)域、廣告領(lǐng)域等。二是發(fā)生商事行為,比如上述諸領(lǐng)域里的票據(jù)、保險(xiǎn)、運(yùn)輸、廣告等。
(三)國(guó)際商事
如果說(shuō)商事是的下位概念,那么,國(guó)際商事又是商事的下位概念。所謂國(guó)際商事是指,人按照被人的授權(quán)或法律規(guī)定,代表被人從事同第三人簽定國(guó)際商事合同或者從事其他有法律意義的國(guó)際商事行為,由此產(chǎn)生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直接對(duì)被人發(fā)生效力的一種。從這個(gè)定義可以看出,國(guó)際商事除了具備商事的一般特征之外,還具有以下幾個(gè)個(gè)性化特征:
1.國(guó)際商事具有“國(guó)際性”特征。這主要是指國(guó)際商事行為中的人、被人或者第三人,營(yíng)業(yè)地不在同一個(gè)國(guó)家或者地區(qū),或者他們盡管營(yíng)業(yè)地在一個(gè)國(guó)家或地區(qū)但其國(guó)籍或者住所不在同一國(guó)家或者地區(qū)。
2.國(guó)際商事具有“商事性”特征。這主要是指國(guó)際商事行為發(fā)生在商事領(lǐng)域或者發(fā)生商事性質(zhì)的行為。如前所述,“商事性”中的商事領(lǐng)域或者商事行為表現(xiàn)就是,帶有營(yíng)業(yè)性質(zhì)的領(lǐng)域或者行為。
3.國(guó)際商事具有“性”特征。這主要是指國(guó)際商事從本質(zhì)上來(lái)說(shuō),畢竟是一種行為,完全符合的幾個(gè)特征。除此而外,還有一層含義是國(guó)際商事的行為在法律上必須具有可性,比如某跨國(guó)公司老板全體職工看望病中住院的東道國(guó)同事,就不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可性。
二、國(guó)際商事法
(一)概念
簡(jiǎn)單地說(shuō),國(guó)際商事法主要是調(diào)整國(guó)際商事關(guān)系的各種法律規(guī)范的總稱。國(guó)際商事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上的國(guó)際法主要是指,專門(mén)的調(diào)整國(guó)際商事關(guān)系的,且對(duì)各個(gè)國(guó)家普遍適用的部門(mén)法典,目前在國(guó)際法范圍內(nèi),針對(duì)所有國(guó)家和地區(qū)普遍適用并生效的國(guó)際商事法典還沒(méi)有。調(diào)整國(guó)際商事關(guān)系的,一般是廣義上的各種有關(guān)國(guó)際商事的法律規(guī)范的總稱,包括國(guó)際法律規(guī)范,也包括國(guó)內(nèi)法律規(guī)范。因此,通常所理解的國(guó)際商事法主要是從廣義角度來(lái)說(shuō)的。
(二)調(diào)整國(guó)際商事關(guān)系的法律規(guī)范
如前所述,從廣義上看國(guó)際商事法,調(diào)整國(guó)際商事關(guān)系的法律規(guī)范包括國(guó)際法律規(guī)范,也包括國(guó)內(nèi)法律規(guī)范。下面我們從這兩個(gè)方面來(lái)看歸納一下:
1.調(diào)整國(guó)際商事關(guān)系的國(guó)際法律規(guī)范
第8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論文摘要:股東代位訴訟作為一種訴訟形態(tài),既具有民商事訴訟的共性,又有其獨(dú)特的一面,明確其與相關(guān)概念之間的界限對(duì)其性質(zhì)的界定至為關(guān)健,股東代位訴訟在性質(zhì)上屬于派生訴訟和共益訴訟.對(duì)股東代位訴訟原告的資格不應(yīng)進(jìn)行過(guò)多的限制,被告的身份以公司的高級(jí)管理人員為主,同時(shí)包括其他人。
一、股東代位訴訟的概念
關(guān)于股東代位訴訟的概念,學(xué)界有不同的見(jiàn)解,有觀點(diǎn)認(rèn)為,“股東代表訴訟,又稱派生訴訟、股東代位訴訟,是指當(dāng)公司的合法權(quán)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卻怠于起訴時(shí),公司的股東即以自己的名義起訴,而所獲賠償歸于公司的一種訴訟形態(tài)。”,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所謂股東代位訴訟是指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經(jīng)理等在執(zhí)行職務(wù)時(shí)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或公司章程的規(guī)定,給公司造成損害并應(yīng)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但公司因故怠于追究其賠償責(zé)任時(shí),依法由股東代位公司提起追究董事、經(jīng)理等民事賠償責(zé)任的訴訟。”
上述第一種觀點(diǎn)將股東代位訴訟等同于股東代表訴訟的做法值得商榷,代表訴訟與代位訴訟是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訴訟形式,不可混為一談,關(guān)于兩者的關(guān)系,容下文詳述。另一方面,股東代位訴訟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不是只要發(fā)生公司的合法權(quán)益受到侵害且公司怠于起訴時(shí),都可以引起股東代位訴訟權(quán),只有在公司的合法權(quán)益受到董事、經(jīng)理等高級(jí)管理人員的侵害時(shí),才可能發(fā)生股東的代位訴訟。換言之,股東代為訴訟針對(duì)的僅僅是公司內(nèi)部管理層對(duì)公司權(quán)益的不法侵害行為。第二種觀點(diǎn)將股東代位訴訟僅僅限制在股份有限公司,似有不妥,因?yàn)闊o(wú)論是從英美法系商法還是大陸法系商法來(lái)看,股東代位訴訟均適用于有限責(zé)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yàn)椴徽撛谟邢薰具€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都可能存在董事、監(jiān)事等高級(jí)管理人員違反法律、法規(guī)或者公司章程侵害公司合法權(quán)益的情形,股東當(dāng)然享有代位訴訟權(quán),因此這種觀點(diǎn)其實(shí)是剝奪了有限責(zé)任公司股東的訴權(quán),同時(shí)也縱容了董事等高級(jí)管理人員肆意侵害公司利益的行為。
筆者認(rèn)為,股東代位訴訟,是指公司的董事、監(jiān)事、經(jīng)理等在執(zhí)行職務(wù)時(shí)違反法律、行政法規(guī)或公司章程的規(guī)定,給公司造成損害并應(yīng)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但公司因故怠于追究其賠償責(zé)任時(shí),依法由股東代位公司提起追究董事、監(jiān)事、經(jīng)理等民事賠償責(zé)任的訴訟。
二、股東代位訴訟的性質(zhì)
有關(guān)股東代為訴訟的性質(zhì),學(xué)界可謂眾說(shuō)紛紜.,莫衷一是。筆者認(rèn)為,要科學(xué)界定股東代位權(quán)訴訟的性質(zhì),首先必須厘清股東代位訴訟與相關(guān)概念之間的關(guān)系。
(一)股東代位訴訟與相關(guān)概念的界限
1.股東代位訴訟與債的保全之代位權(quán)訴訟的關(guān)系
所謂債的保全之代位權(quán)訴訟(以下簡(jiǎn)稱代位權(quán)訴訟),是指在債務(wù)人怠于行使其對(duì)次債務(wù)人的到期債權(quán),而危機(jī)債權(quán)人債權(quán)實(shí)現(xiàn)的情況下,債權(quán)人為了保全自己的債權(quán),而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提起的請(qǐng)求次債務(wù)人向自己履行債務(wù)的訴訟。
從兩者的概念來(lái)看,股東代位訴訟與代位權(quán)訴訟都屬于派生訴訟,即代位訴訟,詳言之,兩者都是原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的原本不應(yīng)由其享有訴權(quán)的訴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股東代位訴訟中的“代位”與代位權(quán)訴訟中“代位”的內(nèi)涵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
但是,這兩者在發(fā)生條件、法律效果等方面還是存有巨大的差別的。具體表現(xiàn)在:
其一,就發(fā)生條件而言,股東代位訴訟是在公司的董事、經(jīng)理等高級(jí)管理人員違法或者違反公司章程損害公司利益而公司怠于行使訴權(quán)的情況下始為發(fā)生,而代位權(quán)訴訟,是在債務(wù)人怠于行使其對(duì)次債務(wù)人的到期債務(wù),而危害債權(quán)人的債權(quán)實(shí)現(xiàn)時(shí)方可成立。
其二,就法律效果而言,股東代位訴訟的發(fā)生緣由是作為公司的受害人怠于追究侵權(quán)責(zé)任,股東雖是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并且最終目的亦旨在使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免受損害,但是畢竟股東對(duì)公司享有的是股權(quán),而非債權(quán)。另一方面,公司怠于訴訟的不作為對(duì)股東權(quán)益的損害也是間接地、潛在的,故法律規(guī)定股東代位訴訟的法律結(jié)果由公司而不是作為訴訟當(dāng)事人的股東承受。而代位權(quán)訴訟中,債權(quán)人、債務(wù)人以及次債務(wù)人之間在代位訴訟發(fā)生之前就存在三角債關(guān)系,債權(quán)人提起代位訴訟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實(shí)現(xiàn)自己對(duì)債務(wù)人的債權(quán)。由此看來(lái),代位權(quán)訴訟的法律效果直接及于作為訴訟當(dāng)事人的債權(quán)人。
2.股東代位訴訟與代表人訴訟的區(qū)別
代表人訴訟,是指一方或雙方人數(shù)眾多的,而由人數(shù)眾多方當(dāng)事人推舉的代表人代為進(jìn)行的訴訟。代表人訴訟是為解決群體性糾紛而設(shè)計(jì)的,其實(shí)質(zhì)是對(duì)具有相同或同一種類訴訟標(biāo)的的眾多當(dāng)事人糾紛進(jìn)行訴訟主體上的合并。現(xiàn)代公司法中,也存在代表人訴訟,是指某一類股東的合法權(quán)益受到侵害時(shí),由其中一個(gè)股東代表其本人和其他股東提起的訴訟。可見(jiàn),代表人訴訟與股東代位訴訟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具體表現(xiàn)在:
其一,訴訟標(biāo)的不同。代表人訴訟是針對(duì)包括代表人在內(nèi)的人數(shù)眾多的股東與侵權(quán)行為人之間的侵權(quán)責(zé)任法律關(guān)系。股東代位訴訟的訴訟標(biāo)峋是公司與其董事、經(jīng)理等高級(jí)管理人員之間的侵權(quán)責(zé)任法律關(guān)系。也就是說(shuō),公司乃作為實(shí)體法律關(guān)系的訴訟標(biāo)的的一方當(dāng)事人。股東欲成為訴訟當(dāng)事人須以公司怠于行使訴權(quán)為前提。
其二,訴訟當(dāng)事人不同。代表人訴訟的當(dāng)事人一方是多數(shù)股東,代表人僅是人數(shù)眾多一方當(dāng)事人的代言人,其他股東雖未參加訴訟,但并不影響其當(dāng)事人身份。而股東代位訴訟中,提起訴訟的股東既非公司的代表人,也不是其他股東的代表人,其本身就是一方訴訟當(dāng)事人。
其三,訴訟法律效果的歸屬不同。代表人訴訟的法律效果及于人數(shù)眾多一方的所有股東,代表人本人當(dāng)然也是訴訟法律效果的直接承受人。而股東代位訴訟的法律效果不由起訴股東直接承擔(dān),而是由公司承受。
(二)股東代位訴訟的性質(zhì)分析
我們分析一個(gè)事物的性質(zhì),其實(shí)就是對(duì)其進(jìn)行歸類,換句話說(shuō),性質(zhì)分析即是在被分析事物的上位概念中為其找到一個(gè)適當(dāng)?shù)淖鴺?biāo)。因?yàn)楣蓶|代位訴訟是股東訴訟的一種,故首先須對(duì)股東訴訟進(jìn)行一個(gè)類型化解讀。
現(xiàn)代公司法中,股東的訴訟形式主要有個(gè)人訴訟(personalsu-its)、代表人訴訟((representativesu-its)和派生訴訟((derivativesuits)三種‘按照這一分類標(biāo)準(zhǔn),股東代位訴訟屬于派生訴訟。因?yàn)楣蓶|代位訴訟不是股東因?yàn)樽约旱暮戏?quán)益受到直接侵犯而以自己的名義向法院提起的,其發(fā)生是有特定前提的,這一點(diǎn)前已論及。股東代位訴訟和股東代表人訴訟更不能混為一談,兩者之間的區(qū)別不再贅述。究其本質(zhì)而言,股東代為訴訟與代位權(quán)訴訟屬于同一類訴訟,那就是派生訴訟,這也恰能說(shuō)明兩者(股東代位訴訟與代位權(quán)訴訟)之間的區(qū)別,因?yàn)樗麄兪峭粚用娴膬蓚€(gè)彼此獨(dú)立的概念,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擁有同一個(gè)上位概念(派生訴訟)。
依股東行使權(quán)利的目的不同又可劃分為共益訴訟和自益訴訟兩種類型。所謂共益訴訟是指股東以行使參與公司經(jīng)營(yíng)的權(quán)利為目的的訴訟。股東參與公司經(jīng)營(yíng)的權(quán)利主要是表決權(quán)和監(jiān)督權(quán),具體體現(xiàn)為通過(guò)表決權(quán)參與公司重大事項(xiàng)的決策,并選擇公司的經(jīng)營(yíng)管理者:通過(guò)監(jiān)督權(quán)監(jiān)督董事、監(jiān)事、經(jīng)理、高級(jí)管理人員等的經(jīng)營(yíng)管理行為,規(guī)范公司的運(yùn)行機(jī)制,維護(hù)股東的整體利益。自益訴訟是股東以行使從公司獲得直接經(jīng)濟(jì)利益的權(quán)利一自益權(quán)一為目的的訴訟,股東的自益權(quán)包括知情權(quán)、利潤(rùn)分配請(qǐng)求權(quán)等。其中股東代位訴訟屬于共益訴訟,股東代表人訴訟與股東個(gè)人訴訟屬于自益訴訟范疇。
三、股東代位訴訟的當(dāng)事人
(一)原告
股東代位訴訟既然是股東代位公司追究董事等損害賠償責(zé)任的訴訟,那么,代位訴訟的原告應(yīng)是股東。值得注意的是,代位訴訟的股東應(yīng)滿足什么樣的條件才能以原告的身份代位公司對(duì)依法應(yīng)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的董事等向法院提起訴訟。股東資格限制條件分二種情況:一種是有限責(zé)任公司的股東;一種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對(duì)于有限責(zé)任公司的股東,一般無(wú)條件限制,這一點(diǎn)也被我國(guó)公司法所確認(rèn)。對(duì)于第二種情況,為了防止股東濫訴,各國(guó)和地區(qū)法律一般都對(duì)原告股東的資格從持股期限、持股的數(shù)量等方面對(duì)原告股東進(jìn)行了限制。
我國(guó)新《公司法》中規(guī)定:股東代表訴訟的原告資格是,有限公司的任何一名股東,股份公司連續(xù)180日以上單獨(dú)或者合計(jì)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代表公司提起訴訟。股份公司的股東由于取得股份和出售股份都比較容易,為了防止濫訴,新公司法在持股時(shí)間和持股比例兩個(gè)方面給予限制性規(guī)定。對(duì)于公司法的這一規(guī)定,筆者認(rèn)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和持股時(shí)間限制不甚妥當(dāng)。持股時(shí)間的限制意在防止有人在獲知公司遭受侵害之后故意買(mǎi)入股票而通過(guò)訴訟牟利的投機(jī)行為。而公司董事、經(jīng)理等高級(jí)管理人員侵害公司權(quán)益的侵權(quán)行為一般情況下是一個(gè)長(zhǎng)期延續(xù)的過(guò)程。所以公司法規(guī)定的180日以上在實(shí)踐中并不能很好的貫徹持股時(shí)間限制的立法目的。至于持股數(shù)的限制,筆者認(rèn)為沒(méi)有必要,反而有歧視小股東合法權(quán)益之嫌,其實(shí)立法者的初衷在于防止小股東濫用訴權(quán),影響公司的正常經(jīng)營(yíng)秩序,但是,在實(shí)際中,小股東往往并不太關(guān)心公司的經(jīng)營(yíng)狀況,而且由于其持股數(shù)量小的緣故,小股東也很難通過(guò)知情權(quán)了解公司董事、經(jīng)理等高級(jí)管理人員危害公司利益的侵權(quán)行為。所以實(shí)踐中小股東提起的代位訴訟非常少見(jiàn)。從維護(hù)公司合法權(quán)益的角度來(lái)看,賦予所有股東代位訴權(quán)也更加有利于公司權(quán)益的全面保護(hù)。
第9篇:法律概念的性質(zhì)范文
內(nèi)容提要: 通過(guò)邏輯分析方法和價(jià)值分析方法,常態(tài)下的好意同乘屬于情誼行為,不屬于無(wú)償客運(yùn)合同;好意同乘中的施惠方構(gòu)成侵權(quán)行為時(shí),其應(yīng)該承擔(dān)損害賠償責(zé)任,而非通說(shuō)認(rèn)為的適當(dāng)補(bǔ)償責(zé)任,只是根據(jù)社會(huì)學(xué)解釋方法其賠償范圍應(yīng)當(dāng)予以適當(dāng)減輕而已。
一、討論好意同乘問(wèn)題的意義
在當(dāng)前交通擁擠及汽車環(huán)境污染嚴(yán)重的背景下,好意同乘現(xiàn)象日漸普遍, 2007年12月28日北京市法學(xué)會(huì)環(huán)境資源法學(xué)會(huì)在《“節(jié)能減排,從我做起”倡議書(shū)》中也提出了“為減少機(jī)動(dòng)車排放,提倡從住宅到單位的私家車主動(dòng)安排車牌單雙號(hào)分日行駛,停駛?cè)蘸托旭側(cè)盏能囍飨嗷ゴ畛恕钡男袆?dòng)方案。實(shí)際上,不管是出于環(huán)保的還是日常生活便利的考慮,相互搭乘也越來(lái)越成為人們提倡的出行方式。在有的國(guó)家,順路搭乘甚至成為一種常態(tài)的主要交通方式。[1]人類是自私的,但好意同乘說(shuō)明在沒(méi)有利益關(guān)系下,人們也會(huì)關(guān)心其他人的生活和福祉,雖然這種關(guān)心不是經(jīng)常性的;而互相搭乘說(shuō)明人類找到了一種更高級(jí)的將利他和利己有機(jī)結(jié)合起來(lái)的行為方式。
與此同時(shí),近年來(lái)好意同乘糾紛越來(lái)越引起實(shí)務(wù)界和理論界的關(guān)注。好意同乘到底是純粹的生活事實(shí)還是民事法律事實(shí)?好意同乘與無(wú)償客運(yùn)合同的關(guān)系是什么?發(fā)生事故時(shí)車主對(duì)同乘人是否是一律“適當(dāng)補(bǔ)償”?在討論客運(yùn)合同中乘客人身?yè)p害賠償請(qǐng)求權(quán)的過(guò)程中,上述問(wèn)題難以回避,尤其是好意同乘問(wèn)題和客運(yùn)合同中的無(wú)償客運(yùn)合同又交織在一起,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屬于事實(shí)上的客運(yùn)合同關(guān)系,有學(xué)者認(rèn)為屬于無(wú)償客運(yùn)合同關(guān)系,[2]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屬于無(wú)名合同、可以類推適用客運(yùn)合同的規(guī)定。
二、好意同乘的概念、特點(diǎn)及性質(zhì)
(一)好意同乘的概念和特點(diǎn)
好意同乘是指乘車人在運(yùn)行供用者好意并無(wú)償?shù)匮?qǐng)或允許下同乘于運(yùn)行供用者之車的現(xiàn)象。[3]好意同乘是一種典型的生活互助行為,這種行為有助于弘揚(yáng)中華民族樂(lè)善好施、助人為樂(lè)的精神。好意同乘是理論界的通用說(shuō)法,在實(shí)踐中也稱為“搭便車”、“搭順風(fēng)車”、“免費(fèi)搭乘”等等,筆者認(rèn)為“免費(fèi)搭乘”的說(shuō)法容易與無(wú)償客運(yùn)合同混淆,本文的立場(chǎng)之一就是區(qū)分兩者,故不采“免費(fèi)搭乘”的說(shuō)法,仍用“好意同乘”的表述。
好意同乘中提供便利方的行為動(dòng)機(jī)是出于情誼,也就是為了增進(jìn)車主或者實(shí)際駕駛?cè)撕痛畛巳说那檎x,給予搭乘人一定的便利。好意同乘關(guān)系的特點(diǎn)主要有:第一、無(wú)償性,即車主或者實(shí)際駕駛?cè)瞬恢苯踊蛘唛g接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即放棄經(jīng)濟(jì)利益,單方面提供方便;第二、好意性,即提供方便的一方伴隨著利他性動(dòng)機(jī),是一種利己的過(guò)程中伴隨利他的行為;第三、不具有契約性,即雙方之間的好意協(xié)定關(guān)系是一種非法律行為的協(xié)定關(guān)系,在當(dāng)事人之間沒(méi)有法律性的意思表示,因而也不具有規(guī)范性的約束力,即使有給付行為的外觀,也不具有合同意義上的債務(wù)履行,而只是任意的給付。[4]上述特點(diǎn)必須同時(shí)具備,而核心特點(diǎn)是不具有契約性。不能單純以無(wú)償性推論系屬好意同乘,而非法律行為,因?yàn)榉缮弦渤姓J(rèn)無(wú)償客運(yùn)合同的存在。
就好意同乘的概念應(yīng)該明確的是:第一、好意同乘不以一方主動(dòng)提供為限,實(shí)務(wù)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搭乘人主動(dòng)請(qǐng)求對(duì)方給予便利的現(xiàn)象頗為常見(jiàn),其與主動(dòng)邀請(qǐng)同乘不應(yīng)有法律評(píng)價(jià)上的不同。[5]我國(guó)司法實(shí)務(wù)中也是采取類似態(tài)度。[6]第二、好意同乘不能包括強(qiáng)行性乘坐,也不能包括無(wú)償偷坐。[7]
“經(jīng)驗(yàn)的現(xiàn)實(shí)證明自身是一種茫無(wú)邊際的雜多”,[8]基于事實(shí)特征的此種無(wú)限性與人們對(duì)事實(shí)認(rèn)知有限性的矛盾,人們所采用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屬于“帶有開(kāi)放結(jié)構(gòu)的語(yǔ)言”,概念的核心地帶意義是清晰的,而越趨邊緣地帶意義越為模糊。[9]好意同乘概念亦然。符合前面三項(xiàng)特點(diǎn)的屬于“沒(méi)有疑問(wèn)的”好意同乘,結(jié)合前述特點(diǎn),有如下“模棱兩可的”情形應(yīng)予說(shuō)明:第一、好意同乘在搭乘者支付或者分擔(dān)汽油費(fèi)的情況下是否就成為有償客運(yùn)合同?對(duì)此種模棱兩可的情況,爭(zhēng)議很大,但是多數(shù)觀點(diǎn)采否定說(shuō),主張此時(shí)仍然屬于好意同乘。[10]這種情形下,分擔(dān)油費(fèi)等形式只是象征性地補(bǔ)償,不構(gòu)成對(duì)價(jià)給付,對(duì)駕車人的勞務(wù)仍屬免費(fèi),仍然構(gòu)成好意同乘。第二、好意同乘是否需要具備順路同乘的特點(diǎn)?即是否以搭乘人與司機(jī)或者車主的目的地相同而順路搭乘為必要?車主或者實(shí)際駕駛?cè)艘サ哪康牡夭皇谴畛巳耸孪戎付ǖ?是否就不構(gòu)成好意同乘?[11]有學(xué)者就認(rèn)為此時(shí)應(yīng)該以無(wú)償委托合同認(rèn)定。筆者認(rèn)為此種專程運(yùn)送仍然屬于單方施惠,除非雙方明示成立無(wú)償委托合同,否則不能當(dāng)然地認(rèn)為構(gòu)成事實(shí)上的契約關(guān)系。
(二)好意同乘的性質(zhì)
上述對(duì)好意同乘的分析一直是對(duì)此種生活現(xiàn)象的基本描述,而任何分析描述不論多么詳盡都不能窮盡現(xiàn)實(shí)在內(nèi)容上的多樣性。好意同乘實(shí)質(zhì)上的法律性質(zhì)如何?仍然需要進(jìn)一步討論。實(shí)際上對(duì)好意同乘中車主責(zé)任的分析,是建立在對(duì)好意同乘行為的民法定性的基礎(chǔ)上的。明確了好意同乘的民法性質(zhì),才能恰當(dāng)?shù)靥幚砑m紛,學(xué)界對(duì)此雖然討論不多,但是對(duì)此前提性問(wèn)題還是具有普遍共識(shí)的。
1.好意同乘屬于情誼行為
好意同乘是情誼行為的一種。實(shí)際上情誼行為也不是一個(gè)非常準(zhǔn)確和有確定含義的概念,它產(chǎn)生于德國(guó)判例,在《德國(guó)民法典》上對(duì)其無(wú)明文規(guī)定,是一種發(fā)生在法律層面之外的行為,不能依法產(chǎn)生后果,因此有學(xué)者將其稱為“社會(huì)層面上的行為”,[12]也有學(xué)者將其稱為“好意施惠關(guān)系”或者“施惠關(guān)系”,[13]其名異而實(shí)同。
作為情誼行為的好意同乘行為并非一種法律行為,也就不可能構(gòu)成客運(yùn)合同。[14]其主要原因是法律行為乃以意思表示為要素,其核心是意思表示,而好意同乘中的一方是處于增進(jìn)相互間的情誼而提供搭乘的方便,情誼增進(jìn)是其行為的動(dòng)機(jī)。“設(shè)立法律關(guān)系的意圖(效果意思)是構(gòu)成合同的實(shí)質(zhì)性因素,并非所有的協(xié)議都是合同”。[15]而如前所述,雖然一方有邀請(qǐng)或者允許的表示,但是情誼的考慮是其出發(fā)點(diǎn)。在事實(shí)層面上,同乘人和車主之間存在一項(xiàng)合意,但是這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合意,只是生活意義上的合意。此種合意不具有意思表示中基本的構(gòu)成要素——效果意思,即沒(méi)有受其拘束的意思,可見(jiàn)并不能構(gòu)成法律行為。司法實(shí)務(wù)上對(duì)法律行為和沒(méi)有拘束力的情誼行為的區(qū)分也是以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的。“一項(xiàng)情誼行為,只有在給付者具有法律上受約束的意思時(shí),才具有法律行為的性質(zhì)。這種意思,表現(xiàn)為給付者有意使他的行為獲得法律行為上的效力……,亦即他想引起某種法律約束力……,而且受領(lǐng)人也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受領(lǐng)這種給付的。如果不存在這種意思,則不得從法律行為的角度來(lái)評(píng)價(jià)這種行為。”[16]好意同乘只是基于情誼而發(fā)生的一般社會(huì)行為,而非法律行為。可見(jiàn)并非所有的合意都構(gòu)成合同行為,實(shí)際上合同內(nèi)容也不一定均須合意達(dá)成,只是合同中的要素須此而已。合同與合意并非完全一致,有法律意義的合意方可能構(gòu)成合同。
因?yàn)楹靡馔烁静粯?gòu)成一項(xiàng)法律行為,那么主張好意同乘關(guān)系類推適用客運(yùn)合同的觀點(diǎn)也就難以成立。我國(guó)《合同法》第124條規(guī)定:“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沒(méi)有明文規(guī)定的合同,適用本法總則的規(guī)定,并可以參照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最相類似的規(guī)定。”可見(jiàn),只有無(wú)名合同才可能適用與其最相類似的相應(yīng)有名合同的規(guī)定,好意同乘中不存在一項(xiàng)合同,甚至連法律行為都不成立,這項(xiàng)非法律行為和客運(yùn)合同不具有基本的性質(zhì)上的類似性。類推適用說(shuō)是沒(méi)有根據(jù)的。[17]
有觀點(diǎn)認(rèn)為好意同乘構(gòu)成事實(shí)行為。[18]筆者認(rèn)為這種觀點(diǎn)也值得商榷。事實(shí)行為是指行為人實(shí)施一定的行為,一旦符合法律的構(gòu)成要件,不管當(dāng)事人主觀上是否具有確立、變更或者消滅某一民事法律關(guān)系的意思,都會(huì)基于法律的規(guī)定,從而引起一定的民事法律效果的行為。事實(shí)行為與好意同乘、乃至與情誼行為的共同點(diǎn)是它們都不具有當(dāng)事人的意思表示。就事實(shí)行為而言,其法律效果的發(fā)生不問(wèn)是否為當(dāng)事人所意欲,法律對(duì)其采取法定主義的調(diào)控方式。但在好意同乘關(guān)系中,法律并沒(méi)有對(duì)當(dāng)事人之間的此種關(guān)系配置任何權(quán)利義務(wù),誠(chéng)如王澤鑒先生所言:“于此等行為,當(dāng)事人既無(wú)受其拘束的意思,不能由之產(chǎn)生法律上的權(quán)利義務(wù)。”[19]可見(jiàn),法律對(duì)好意同乘行為與事實(shí)行為采取的態(tài)度是根本不同的。
既然好意同乘根本不屬于事實(shí)行為,主張好意同乘屬于無(wú)因管理的觀點(diǎn)也就不能成立。[20]提供搭乘者根本不具有發(fā)生法律行為的意思,法律對(duì)其也保持沉默,此時(shí)更談不上管理意思的存在了。不能因?yàn)楹靡馔伺c無(wú)因管理同具有社會(huì)共同體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的特點(diǎn),就理所當(dāng)然地將其在性質(zhì)上歸為一類。
以上是從概念和規(guī)范出發(fā)對(duì)好意同乘性質(zhì)做的邏輯分析。更進(jìn)一步看,好意同乘的性質(zhì)本身屬于一個(gè)價(jià)值判斷問(wèn)題,因?yàn)橛懻撃芊駥⒑靡馔诉@一生活事實(shí)上升為民事法律事實(shí)的過(guò)程就是“一個(gè)面向生活世界進(jìn)行民法解釋的過(guò)程”,此種本體論解釋結(jié)論的不同直接影響對(duì)好意同乘的性質(zhì)界定,而不同的解釋結(jié)論直接關(guān)系到將好意同乘放在民法層面規(guī)范還是交由交往道德規(guī)范的問(wèn)題,這就“直接涉及當(dāng)事人之間利益安排”。[21]
好意同乘關(guān)系雖然屬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但是至少就今天的價(jià)值取向來(lái)說(shuō),該種社會(huì)關(guān)系“不具有可訴性”,[22]也就不能成為民事法律關(guān)系,好意同乘這一生活事實(shí)也不能上升為民事法律事實(shí)。可訴性究竟是做出這一價(jià)值判斷結(jié)論的依據(jù)還是該結(jié)論的當(dāng)然結(jié)果,尚存疑問(wèn),這也顯示了探討價(jià)值判斷問(wèn)題時(shí)避免循環(huán)論證的難度。一個(gè)更現(xiàn)實(shí)的路徑是交由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基于其所處社會(huì)的價(jià)值取向遵循法律認(rèn)可的表決程序和表決規(guī)則做出決定。[23]這一方法既可以彌補(bǔ)可訴性標(biāo)準(zhǔn)循環(huán)論證之弊,又可以因應(yīng)道德規(guī)則本身的變動(dòng)性及其與法律規(guī)則邊界的變動(dòng)性。
2.好意同乘并非一概屬于“法外空間”
上文對(duì)將好意同乘定性為情誼行為,并論證其不屬于法律行為、不構(gòu)成客運(yùn)合同;不屬于事實(shí)行為,也不構(gòu)成無(wú)因管理。但是是否好意同乘只能“由當(dāng)事人的私人友誼調(diào)整”,“不由法律調(diào)整”,“不能由法律救濟(jì)”呢?[24]好意同乘關(guān)系中的雙方不會(huì)對(duì)法律約束作實(shí)際思考,除非出了麻煩,麻煩一般出在同乘人在同乘過(guò)程中受到傷害的情形。
相關(guān)熱門(mén)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法律科學(xué)
級(jí)別:CSSCI南大期刊
榮譽(yù):Caj-cd規(guī)范獲獎(jiǎng)期刊
-

法律與金融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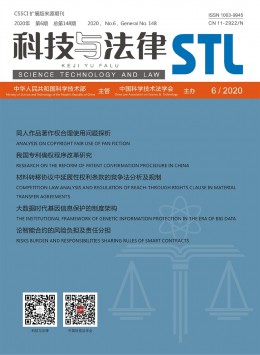
科技與法律
級(jí)別:CSSCI南大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法律適用
級(jí)別:CSSCI南大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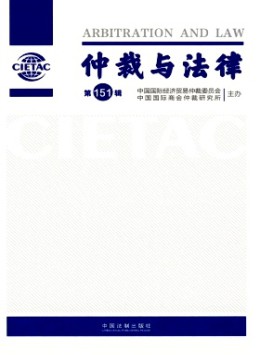
仲裁與法律
級(jí)別:部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