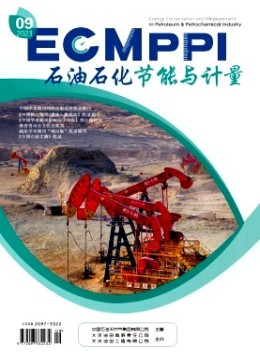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城鎮化 碳排放 STIRPAT模型 地區差異
一、引言
如今,自然資源日趨緊張,生態環境日趨惡劣,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全世界人民關注的焦點。加速城鎮化和促進低碳發展是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重點。城鎮化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的能源消費對碳排放量的影響也不同。江蘇省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顯著,蘇南、蘇中、蘇北目前正處于不同的城鎮化階段,因此對比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三個區域的能源消費碳排放量對我國在城鎮化進程中發展低碳經濟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已有學者對城鎮化和碳排放之間的關系做了相關研究。盧祖丹基于1995―2008年省域面板數據,通過建立STIRPAT模型對城鎮化和碳排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研究,得出城鎮化發展有利于實現碳減排,但未探討不同的城鎮化水平對碳排放的影響因素。林伯強、劉希穎用協整法探討城市化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但只針對中國這一主體進行研究,并未對不同區域進行對比分析。宋德勇、徐安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區域差異對碳排放的影響,并未對經濟發展水平和碳排放的內在聯系進行探討。
二、研究方法
經濟發展是碳排放增長的首要因素,本文結合York等提出的STIRPAT隨機回歸模型,來分析研究產業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該模型主要分析P(人口)、A(富裕度)、T(技術)、I(環境影響)之間的關系,公式為:
I■=?琢P■■A■■T■■e■ (1)
其中:?琢是常數項,b、c、d是人口、富裕度、技術的指數,e是誤差項。
在實際分析時,將模型先進性對數化處理:
lnIi=ln?琢+blnPi+clnAi+dlnTi+lnei (2)
式(2)中,P代表城鎮化水平,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表示(%),用來反映人口向城鎮聚集的程度;A代表人均工業生產總值,用工業生產總值與常住人口的比值表示(元/人);T代表工業能耗強度,選取工業能源消費量與工業生產總值的比重即工業能耗強度來表示(噸標準煤/萬元);I表示工業碳排放量(噸)。相關經濟數據均以2000年為基期做了不變價處理。
根據國家統計局編制的《能源統計報表制度》,本文的能源消費指能源的終端消費量。在計算碳排放量時,首先將能源消費量折算成標準煤,然后根據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給出的標準煤的碳排放系數為2.4567噸CO2/噸標準煤進行計算。
文中的能源數據來自江蘇省13市各自歷年的《統計年鑒》;經濟社會數據來自歷年《江蘇省統計年鑒》。
三、結果與分析
1、研究區域
江蘇省位于我國大陸東部沿海中心,地處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位于全國前列,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10%以上。江蘇省經濟發展區域差異大,蘇南、蘇中、蘇北的城鎮化發展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因此選擇江蘇省為研究樣本,研究其城鎮化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探究城鎮化進程中碳排放的影響因素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蘇南地區(南京、蘇州、無錫、鎮江、常州)與上海相鄰,經濟發展較快,是江蘇省經濟發展的主力,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2013年城鎮化率已達到73.5%;蘇中地區(揚州、泰州、南通)與蘇南地區隔江相望,位于長江中下游,經濟發展速度適中,城鎮化發展水平較落后,2013年城鎮化率為59.7%;蘇北地區(徐州、宿遷、淮安、連云港、淮安)相對蘇南和蘇中雖然自然資源豐富,但是接近內陸,經濟發展落后,城鎮化水平與蘇中地區較接近,城鎮化率在2013年已達到56.1%。
2、模型回歸結果
由于蘇中和蘇北地區2006年以前能源消費量數據缺失,故本文將主要研究2006―2013年間各區域的碳排放量。對式(2)利用SPSS進行線性回歸分析時,首先將數據進行Zscore一致性處理,避免各變量數量級不同對數據分析的影響,然后將處理后的數據帶入模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模型整體通過了一致性檢驗,但是在95%的置信區間,所有變量的t值都不顯著。進一步計算各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三個變量的VIF均遠大于10,證明模型中的城鎮化水平、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和工業能耗強度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因此不適合運用最小二乘法進行無偏估計。
為克服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采用SPSS軟件中的有偏估計嶺回歸函數對模型進行擬合。嶺回歸是一種改良的最小二乘估計法,通過放棄最小二乘法的無偏性,以損失部分信息、降低精度為代價獲得回歸系數更為符合實際、更可靠的回歸方法。其中k=0時,即為普通最小二乘估計。將式(2)進行嶺回歸分析,當k=0.1時,蘇南模型中各自變量回歸系數變化趨于穩定,當k=0.2時,蘇中和蘇北的模型中各自變量回歸系數變化趨于穩定,從而擬合方程分別為:
蘇南:lnI=0.2813lnP+0.4407lnA-0.2424lnT (3)
蘇中:lnI=0.4607lnP+0.2379lnA-0.2074lnT (4)
蘇北:lnI=0.1846lnP+0.3516lnA+0.4007lnT (5)
對嶺回歸擬合結果進行檢驗(見表1),結果顯示擬合結果能夠通過顯著性檢驗。
根據模擬結果可以看出,蘇南、蘇中和蘇北的模型在5%的置信區間都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所有變量的t值都大于1.96,R2值和調整的R2值都大于86%,說明P(人口)、A(富裕度)、T(技術)三個變量解釋了86%以上的碳排放量變動。
3、結果分析
(1)工業能耗對碳排放的影響。根據回歸方程可以看出,城鎮化水平和工業生產總值與碳排放量都呈正相關,與實際相符合。工業發展越快,能源消耗越多,碳排放量越大。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并沒有導致碳排放的減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城鎮化發展仍然離不開工業產業的發展。
蘇南是江蘇省經濟最發達地區,是江蘇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力。結合表2和圖1可以看出,2006年以來,蘇南地區的城鎮化水平較高,至2013年城鎮化水平已達到73.50%,且一直持續穩步增長。蘇南城鎮化水平對碳排放影響的彈性系數為0.28,說明該地區較高水平的城鎮化并沒有使碳排放量得到減少。相比蘇中和蘇北地區,蘇南地區的工業生產對碳排放的影響更大,彈性系數達0.44,說明該地區在發展工業的同時應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蘇中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慢,城鎮化水平由2006年的47.3%增長為2013年的59.7%,變動幅度是三個區域中最小的。回歸結果顯示,蘇中地區工業發展對碳排放量的影響較小,彈性系數為0.24,說明該地區工業發展并未造成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是城鎮化對碳排放量影響較大,彈性系數達到0.46,說明該地區在大力發展城鎮化的同時必須注重減少碳排放量。
蘇北地區城鎮化發展較快,至2013年,蘇北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已達到56.1%,超過蘇中地區。相對而言,蘇北地區的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發展潛力較大。對蘇北地區碳排放量影響較顯著的因素是工業能耗強度,彈性系數為0.40,說明該地區節能減排的關鍵是降低工業能耗強度。城鎮化水平彈性系數為0.18,對碳排放影響較弱,說明該地區大力提高城鎮化水平不會造成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
對比三個回歸方程,蘇南和蘇中的能耗強度與碳排放呈負相關,而蘇北地區能耗強度與碳排放呈正相關,且能耗強度每增加1%,碳排放量將增加0.4007%,比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對碳排放量的影響更大,原因在于,蘇南和蘇中地區的工業技術先進,能源利用效率高,而蘇北地區經濟落后,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性較強,能源利用效率較低。
(2)能源消費模式。2010年之前江蘇省的家庭能源消費主要是煤氣和液化石油氣,從2010年開始其家庭能源消費主要是天然氣。到2013年,除蘇州地區,全省其他12個市都已經不使用煤氣。根據IPCC《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提供的碳排放系數可知,天然氣的碳排放系數為0.4483×104,煤氣的碳排放系數為0.3548×104,液化石油氣的碳排放系數為0.5042×104。
由圖2可知,隨著經濟的發展,蘇南、蘇中、蘇北城鎮居民家庭消費的碳排放強度都在逐步減弱,且變動趨勢接近一致。這主要是由于煤氣和液化石油氣消費量的減少和天然氣消費量的增加,使得能源消耗導致的碳排放增長速度小于經濟發展的增長速度。2006―2013年,僅家庭能源消費,蘇南地區的碳排放強度下降38.27%,蘇中地區的碳排放強度下降38.04%,蘇北地區的碳排放強度下降50.46%。
至2007年,天然氣還尚未投入使用,而江蘇省13市中除蘇北的連云港和宿遷兩地外,其它各市氣化率均達到90%以上。到2013年,江蘇省13市的燃氣普及率已經達到95%以上,天然氣的使用使三大地區家庭能源消費模式趨于一致。不同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對于家庭能源消費模式的影響并不顯著,從2007年開始,三大地區的能源消費強度就逐漸接近,因此改善能源消費模式也可以大大減少碳排放量。
(3)能源政策。應綜合考慮三個地區不同城鎮化發展水平下的能源政策對碳排放的影響。從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資源稟賦可以看出,蘇南地區的能源主要依靠進口,但蘇南地區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蘇中、蘇北地區較多人口流入蘇南地區,推動蘇南地區的城鎮化發展。在“十二五”期間,蘇南地區基本已經實現能源消耗增長速度低于經濟發展速度。蘇南地區對于新能源產品和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使得蘇南地區的碳排放量基本得到了控制。相對于蘇南地區,蘇中地區城鎮化發展速度較慢,且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高耗能產業發展較快,在推動新能源發展的同時,重點發展石油化工產業的衍生產品,能源消耗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碳排放量持續增長。蘇北地區雖然城鎮化水平超過蘇中地區,但卻是江蘇省經濟發展最落后的地區,能源消耗高,對煤炭等傳統能源的依賴性高。但是蘇北地區利用自身的地理優勢,致力于新能源開發,主要研發太陽能和風能,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減少碳排放量。獨特的地理優勢和能源優勢,使蘇北地區的城鎮化建設發展較快,但同時也抑制了蘇北地區的經濟發展,促使蘇北地區仍停留在重工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階段。
四、結論和建議
1、結論
本文以處于城鎮化發展不同階段的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個地區為例,利用STIRPAT模型探討城鎮化發展進程和經濟發展水平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表明,不同的城鎮化發展進程和經濟發展水平對碳排放量的影響不同。城鎮化發展和經濟發展速度均較快的蘇南地區,碳排放量的增長速度(25.8%)已經低于工業經濟增長速度(156%),碳排放量基本得到了控制;城鎮化發展和經濟發展速度適中平穩的蘇中地區,城鎮化發展是現階段的發展重點,碳排放量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一致,持續穩步增長;城鎮化發展速度較快但經濟發展落后的蘇北地區,對傳統能源依賴性大,碳排放量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
蘇南地區,城鎮化水平由2006年的67.1%增長為2013年的73.5%,工業生產對碳排放的影響最大,彈性系數達0.44;城鎮化水平對碳排放影響的彈性系數僅為0.28,城鎮化建設的推動對碳排放量影響較小。蘇中地區,城鎮化水平由2006年的47.3%增長為2013年的59.7%,與蘇南地區相反,工業發展對碳排放量的影響較小,彈性系數為0.24,工業發展并未造成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但是城鎮化對碳排放量影響較大,彈性系數達到0.46,推動城鎮化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對蘇中地區的碳排放影響較大。蘇北地區,雖然經濟增長速度是三個地區中最快的,2013年蘇北地區工業生產總值是2006年的6.31倍,但是蘇北地區的城鎮化水平和工業生產的彈性系數分別只有0.18和0.35,而能耗強度對碳排放的影響最大,彈性系數為0.40,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強度才是蘇北地區節能減排的關鍵。
2、政策建議
(1)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優化升級。雖然蘇南地區正在逐步實現產業轉型,但是蘇中和蘇北地區的經濟發展仍舊以重工業為主,而且江蘇新能源資源匱乏,對傳統能源依賴程度大,僅鹽城地區風能資源較為豐富。因此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減少碳排放量最直接的方法。
(2)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優化能源消費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強度有助于節能減排。家庭能源消費對碳排放的影響體現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應改變能源結構,使用碳排放量較少的新能源替代傳統能源。例如,大力發展太陽能、風能發電,減少火力發電;早日實現江蘇省13市100%的燃氣普及率,減少煤氣和液化石油氣的使用。
(3)大力實施節能減排政策。政策與實踐相結合,在接下來的“十三五”期間,進一步降低碳排放強度,努力實現經濟與碳減排的同步發展。結合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不同的地理優勢和資源稟賦,制定不同的發展政策,因地制宜,使地區在經濟穩步發展的同時減少碳排放。
(注:基金項目:江蘇省實踐創新指導項目“城鎮化不同階段對區域碳排放影響研究――以江蘇省為例”201410299088X。)
【參考文獻】
[1] 盧祖丹:我國城鎮化對碳排放的影響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11(7).
[2] 林伯強、劉希穎:中國城市化階段的碳排放:影響因素和減排策略[J].經濟研究,2010(8).
[3] 宋德勇、徐安:中國城鎮碳排放的區域差異和影響因素[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1(11).
[4] York R,Rosa E A,Dietz T.STIRPAT,IPAT and ImPACT;Analytic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J]. Ecological Economics,2003(23).
第2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經濟增長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由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率的提高等原因,經濟規模在數量上的擴大,即商品和勞務產出量的增加。其衡量指標有國內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總量指標。近20年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根據經驗數據測算,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長速度為9·4%[3]。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GDP增長水平總體高于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這一時期,中國碳排放總量也呈現較快增長的態勢。從可以看出,1980—1997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快速時期,碳排放量增長也很快,到1997年后才逐漸降低。
由于碳排放受社會、經濟、自然、生態、技術等多方面的影響,因此,通過研究各主要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可分析未來中國的碳排放趨勢,并選擇合理的溫室氣體減排途徑。據徐玉高等[3]分析中國1970—1994年間各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經濟增長是中國20多年來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僅此一項引起的碳排放變化占總量的94%以上。采用相關分析方法對中國1980—2000年GDP和碳排放數據進行擬合,結果。可以看出,1980—2000年間中國碳排放量的變化和GDP的增長呈顯著相關(R2=0·9581)。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各因素中,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較大,與其他國家相比,投資在中國經濟增長中所占比重較大,這與中國剛進入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并長期以來實行的重工業發展戰略相關。這一方面造成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增加,投資的增加加快了重工業的發展,引起對能源、交通的需求也增加,碳排放隨之增加;其次,由于經濟的增長,人均GDP增加,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對碳排放的需求也增加,尤其在一些相對貧困的地區,工業化、城市化剛剛起步,碳排放增加速度很快;最后,由于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造成大片森林被砍伐,環境破壞,使得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而增加。
但是,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會引起技術、制度的變革和經濟結構的演進,由此引起的經濟發展可能使碳排放量在一定時期減少。張雷[4]研究了國家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結構多元化發展導致國家能源消費需求增長減緩,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發展則導致國家碳排放水平下降,兩者結構多元化的演進最終促使國家發展完成從高碳燃料為主向低碳為主的轉變。因此,為研究中國未來碳排放量隨經濟增長的變化趨勢,需要從經濟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出發,更深入地分析經濟增長各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
2中國經濟增長影響碳排放的原因
2·1經濟結構的影響
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但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著眼于短期經濟總量的增長,重視經濟增長的效率,而忽視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增長的可持續性,使得經濟增長的效率低下,結果是對資源、環境形成無形的巨大壓力。分析中國的經濟結構可以發現,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高速發展的成就,但經濟結構并未取得明顯改進,工業所占比重約為40%~50%,服務業(即第三產業)僅占33%,服務業比重低于巴西約20%,并低于發達國家約35%~40%(圖4)。因此,中國的經濟結構依然是比較低下的。這與中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并一度強調重工業發展戰略不無關系,而重工業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經濟目前仍為外延型和粗放型的增長,說明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還要走漫長的道路,未來經濟的發展對能源和CO2排放的需求還很大。
2·2能源結構的影響
從經濟增長必需的能源看,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并未改變。2001年,煤炭占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的62%,比世界平均水平24·7%高37·3%,而其他清潔能源如水能、核能、天然氣等所占比重不超過11%[5]。計算表明,單位標準煤炭燃燒產生的CO2是等標量石油排放的1·23倍,是等標量天然氣排放的1·75倍[3]。由于煤炭所占比重較大,故中國單位能源使用產生的CO2量高于其他國家。從能源利用效率看,雖然中國在過去20年取得了GDP翻兩番、能源消費僅翻一番的成就,但單位能源消費所產生的GDP仍低于其他主要國家(表2)。因此,改善能源結構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減少碳排放量,中國都將面臨極大的挑戰。
2·3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剛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如果不轉變目前高投入和高消耗的經濟增長方式,且繼續維持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碳排放量在未來還要持續增長,將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中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一般來說,根據庫茲涅茨(Kuznets)曲線,經濟增長與環境惡化間呈倒“U”型曲線關系(EKC曲線),說明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會伴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惡化,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環境惡化會得到遏止并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好轉[6]。但是,溫室氣體的排放在本質上是人們的生存需要所決定的,且受人們的消費偏好等因素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水平尚處于由溫飽向小康過渡的階段,地區增長不平衡,滿足基本發展需求是第一位的,碳排放的需求仍很大,因此,經濟增長遠沒有達到庫茲涅茨曲線的閾值點,碳排放還會隨經濟增長而增加。在分析各國統計數據的基礎上,錢振為[7]探討了能源消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認為在21世紀前20年,中國正處在能源需求增長較快的時期,單位GDP的能源消費難以大幅度下降,提高單位能源產生GDP的空間并不大,說明未來碳排放量還將繼續增長。
據Birdsall和Shafik以及Bandyopadhyay等人用更多的時序數據和截面數據估計,人均碳排放與經濟增長間的Kuznets曲線關系是很微弱的;或者,人們接受轉折點遠遠高于現實經濟發展水平的Kuznets曲線,那么經濟發展達到轉折點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已遠遠超過了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水平[3,8,9]。2003年,中國人均GDP為1090美元,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未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仍需要巨大的碳排放空間。盡管1997年后中國碳排放量有所減少,但要達到Kuznets曲線的碳排放量大幅下降的階段,仍然有一段距離。在不損害經濟發展的條件下,GHG(GreenhouseGases,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是衡量減排效果的最好方法。GDP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指每百萬美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溫室氣體排放量[10]。中國是世界上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最高的國家,1990年GDP的CO2排放強度為1·56kg碳/美元,達到世界平均水平0·24kg碳/美元的6·5倍,美國的6倍,日本的16倍[11]。這與中國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水平還比較低下不無關系,而中國外延型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是主要原因。但隨著經濟的增長,技術會得到改進,經濟增長依賴于大量投資和能源消耗的現狀會得到改善,在改進人們消費偏好的基礎上,選擇一條低碳發展的路徑,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高于能源消耗的速度,CO2的排放強度總體上會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由此形成經濟持續健康的增長。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間,中國的能源消費平均年增長率為4·3%,GDP的平均增長率為9·6%,能源消費的增長率遠低于GDP的增長率。在此期間,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強度基本未變。因此,1980—2000年,中國GDP的CO2排放強度平均年下降率為5·6%[12]。從這個意義上看,盡管未來中國經濟處于較快發展階段,對能源、交通的需求還很大,但單位GDP的能源消耗減少的空間還比較大。
3結論
按照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消費模式,中國碳排放量將隨經濟增長而增加,其中尤以工業增長排放CO2最為顯著。根據國際經驗,一國經濟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加快,交通、能源的消費需求增加,碳排放量將很快增長。如果不改變目前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沿著一些發達國家的老路去發展,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巨大挑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要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益,大力發展資源節約型產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單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這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減少未來碳排放量的首要選擇。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是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強度大的主要原因,這一方面是中國的自然社會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和中國的能源利用技術落后有關,因此,吸收國內外先進的能源利用和碳減排技術,改進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以減少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在中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3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EKC曲線;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權;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二氧化碳排放;碳減排義務;碳減排效果;京都議定書
中圖分類號:F064.2;F1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2-0066-06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Based on Fair Development RightsLI Jun-jun, ZHOU Li-mei
(Economics School,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 lot of controversies about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for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task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hich mak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uncertain for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ding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consturcts an international panel data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32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17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1971―200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s is increasing, that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continuously bigger than tha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not strictly fulfilled the obligation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anwhile, dual policy under “Kyoto Protocol” has not made abnormal transfer of industry.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s owned by each country, it is unfair to requir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ak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ligation currently,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sh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each country.
Key words:EKC Curv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s; glob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ligat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Kyoto Protocol
一、引言
溫室效應導致氣候異常變化,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正在不斷完善之中,以圖遏制碳排放量的過快增長。但世界工業發展方式還未實現根本性轉變,在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壓力下,各國都在繼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碳排放的增長趨勢短期內難以扭轉。同時,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受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不同,實施碳減排的經濟基礎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動機也不同,碳減排任務的分配將是一個長期的利益博弈過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規定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同責任,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就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碳減排壓力太大。2005起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進一步要求發達國家在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諾期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減少5.2%,大多數國家要求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8%,而澳大利亞、冰島和挪威則允許一定幅度的上升。但事實上,包括美國、日本等國在內的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沒有完成既定的碳減排目標,并企圖拋棄《京都議定書》,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承擔硬性碳減排義務,其理由是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總量迅速增長,占全球比重越來越高,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要求的雙重政策不公平。
李軍軍,周利梅:基于公平發展視角的碳減排國際比較按照“污染避難假說”,在不同國家的碳減排政策標準和實施力度有差距的情況下,碳減排壓力較大的國家,政策措施更為嚴格,對產業的影響就越大;同時,為了避免能源約束和碳稅等低碳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就會轉移到碳減排政策更寬松的國家,導致產業非正常轉移,二氧化碳排放也隨之轉移。為了吸引外資,低收入國家可能競相放松碳排放管制,從而破壞碳減排國際合作機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公共環境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共同選擇,如果不能建立各方都認可的碳減排國際合作機制,全球氣候環境就可能陷入“公地悲劇”。那么,《京都議定書》是否真的是約束了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而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增速?發展中國家是否由于寬松的碳減排政策而獲得額外經濟增長?
從公平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需要發展,都有保持經濟增長的權利,但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增長過程中碳排放量也不同,要正視這種差異。按照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收入之間存在一個倒U形曲線的關系:在相對較低的收入水平,隨著收入的增加,能源的消費量增加并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此時,兩者呈正相關關系;隨著收入增長到一定的高水平,因為環境保護意識增強,提高了環境政策的調控和傳導效果,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減少,兩者呈負相關關系。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過程中,應該考慮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科學評價各國經濟增長過程的碳減排效果。
自從Grossman 等(1991)較早發現空氣污染和人均GDP之間存在倒U曲線關系后,當前多用EKC曲線研究碳排放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如:Ang(2007)、Zhang等(2009)、Fodha等(2010)分別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RDL)或者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檢驗二氧化碳排放和GDP之間因果關系,Azomahou(2006)和Romero-ávila(2008)等人用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驗證EKC曲線。但這些研究大多數都基于單個國家或局部區域;也有一些文獻選擇經合組織或大量國家(Wang,2011)作為樣本的,但也都是側重于驗證EKC曲線,沒有從國際對比的角度分析不同碳減排義務的國家。有鑒于此,本文將從經濟發展對碳排放影響的角度分析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碳減排效果。
二、面板數據模型與數據分析
不失一般性,假設碳排放主要來自化石能源消耗,影響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據此建立雙對數面板數據模型:
如果β>1,說明碳排放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碳減排形勢惡化,碳排放強度上升;如果β
為了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可以把面板數據的樣本分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部分,分別估計以后比較彈性系數,根據彈性系數的大小來判斷碳減排政策的作用。如果發達國家的彈性系數小于發展中國家,說明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碳減排形勢好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2008年至2012年的強制性碳減排義務,但協議是從2005年開始生效,此后發達國家之間的碳排放交易非常活躍,清潔發展機制(CDM)也允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項目級的碳減排量的轉讓,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CDM項目數量和規模都增長迅速。因此,要判斷碳減排協議的簽訂對各國碳減排效果的影響,可以把2005年作為分水嶺,分別估計并比較前后兩個期間的彈性系數,如果彈性系數下降,說明碳減排政策取得實質性效果。
《京都議定書》規定41個發達國家具有強制性碳減排義務,由于9個國家缺失部分碳排放統計數據,本研究把具有完整數據的32個發達國家納入分析范圍,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意大利、日本、盧森堡、馬耳他、摩洛哥、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由于發展中國家較多,本研究選擇其代表性國家,選擇依據是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一億噸,符合這個標準的國家共17個,分別為中國、印度、伊朗、韓國、沙特、墨西哥、印尼、南非、巴西、泰國、埃及、阿根廷、馬來西亞、委內瑞拉、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基斯坦和越南。二氧化碳排放和GDP數據都采集自國際能源署(IEA)的能源統計年鑒,時間跨度為1971年至2009年。其中二氧化碳排放(CO2)單位是百萬噸;GDP以十億美元為單位,按匯率(GDPE)和按購買力評價(GDPP)兩種方法折算為2000年不變價格。
數據測算表明,2009年世界各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290億噸,是1990年的1.38倍,比1971年翻了一倍。樣本中49個國家碳排放總量為238.3億噸,占全球總量的82.2%,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其中,17個發展中國家碳排放總量從1990年的47.9億噸快速增長到2009年的126.9億噸,年均增長5.26%,占全球總量的比重從1990年的22.9%上升到2009年的43.9%。同期32個發達國家的碳排放總量則從108.1億噸上升到111.3億噸,上漲了3%,比重從51.6%下降到38.4%。據此來看,近年來全球碳排放總量的快速增長主要歸因于發展中國家,只有發展中國家實施嚴格的碳減排措施,才能有效控制全球碳排放總量的過快增長,這也是近年來在全球氣候峰會上,發達國家強硬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硬性碳減排義務的主要原因。但是從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來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大多處于工業化起步階段,增長速度普遍高于發達國家,碳排放增速較快是正常的;而發達國家基本完成工業化,經濟增長速度普遍放緩,碳排放增速理應降低。如果不顧這個事實,強行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嚴格的碳減排義務,不但忽視了發達國家碳排放的歷史責任,也會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權利,加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極不公平的。衡量發展中國家碳減排效果,重要的是看經濟增長過程中碳排放的收入彈性,如果彈性系數和碳排放強度下降,就說明其碳減排政策的有效性。
三、檢驗與參數估計
1.單位根檢驗
由于每個時間序列都是由多個國家組成,其檢驗方法要考慮到截面的差異。LLC方法是應用于面板數據模型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較早的方法,假設各截面序列具有一個相同的單位根,仍采用ADF檢驗形式(Levin et al,2002);而IPS檢驗則是對每個截面成員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后,利用參數構造統計量檢驗整個面板數據是否存在單位根(Im et al,2003)。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也是對不同截面進行單位根檢驗,利用參數的p值構造統計量,檢驗整個面板數據是否存在單位根。分別用四種方法對CO2、GDPE和GDPP三個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時的滯后階數都按AIC最小化準則確定,結果如表1所示。表1 面板數據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四種方法的檢驗結果非常接近,通過對原序列和一階差分的單位根檢驗結果進行判斷,在1%顯著性水平下三個變量都是非平穩序列,都有單位根,并且是一階單整。因此,可以對三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是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的方法,Engle和Granger最早提出的協整檢驗方法是判斷兩個或多個變量回歸后的殘差是否平穩,如果殘差是平穩的,說明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對于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Pedroni(1999)的檢驗方法是假設各截面的截距項和斜率系數不同,Kao(1999)的檢驗方法卻規定第一階段回歸中的系數相同;Maddala等(1999)提出根據單個截面序列的協整檢驗結果構建新的統計量,從而判斷整個面板數據的協整關系。表2列出了采用不同方法分別對CO2和GDPE、CO2和GDPP兩組變量協整檢驗的結果。檢驗結果一致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表明CO2和GDPE、CO2和GDPP兩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據此可以對模型(1)進行參數估計。
表2 面板數據變量的協整檢驗
CO2與 GDPECO2 與GDPPPanel v-Statistic-0.40-0.39Panel rho-Statistic-2.53**-2.53**Panel PP-Statistic-4.36***-4.36***Panel ADF-Statistic-5.27***-5.27***Kao(Engle-Granger)6.49***4.20***Johansen FisherTest trace statistic 163.00*** 163.30***Max-eigenvalue statistic 159.90*** 159.70***
3.參數估計
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碳排放水平有很大差異,參數估計應該選擇面板數據的變截距模型;至于選擇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盡管樣本國家只有49個,但僅僅用于分析這些個體,不涉及其他國家,因此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另外,截面隨機效應的Hausman檢驗p值為0.94,也不支持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考慮到存在截面異方差,采用加權廣義最小二乘法(GLS)估計參數,并處理序列相關性,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方程1的解釋變量是按匯率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E),方程2的解釋變量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P),方程擬合優度較高,除截距項外參數都能通過1%顯著性檢驗,兩個方程的系數比較接近,說明以不同方式換算的GDP對結果影響不大。考察不同期間的系數,1971―2009年碳排放的收入彈性系數0.607
D.W.2.0982.1362.571.8991.8741.759Chow-F1.72***0.79方程3的樣本由32個發達國家組成,方程4的樣本由17個發展中國家組成,方程擬合優度較高,除截距項外參數都能通過1%顯著性檢驗。方程3的系數0.712大于方程4的系數0.574,在兩個不同時期內,發達國家的碳排放的收入彈性系數都超過發展中國家。按照公式(2),方程3的分割點檢驗Chow-F值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也是明顯大于2005年以前的彈性系數。而發展中國家的彈性系數雖然也有上升,但沒有通過分割點檢驗。
四、結論
在環境和能源約束下維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無疑是各國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旨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能否發揮作用,關鍵在于碳減排目標的設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以及碳減排任務的分配能否得到各國認可。只有在碳減排任務合理、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兼顧到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承受能力,才能得到廣泛認可,形成合作的基礎。碳排放的收入彈性系數反映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彈性系數的大小和變化趨勢能夠說明一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程度和碳減排效果,也可以作為碳減排任務分配的依據之一。利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1971―2009年主要國家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彈性系數為0.6,碳排放增幅低于經濟增幅,碳減排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分割點檢驗判定彈性系數有明顯上升趨勢,說明近年來經濟增長過程中碳減排力度在減小。對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盡管發達國家的碳排放總量增長緩慢,部分國家的碳排放總量甚至下降,而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總量增長比較快,但發達國家碳排放的收入彈性系數在各個階段一直大于發展中國家,2005年以后也沒有明顯改變。這一方面說明發達國家碳減排政策實施力度不夠,效果還不甚明顯;另一方面也說明《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碳減排義務形成的政策差異,并沒有造成資本因為規避碳排放約束而發生明顯的非正常轉移。
因此,從各國公平擁有經濟發展權的角度來看,應該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明確發達國家碳排放歷史責任前提下,發揮發達國家良好經濟基礎和先進技術優勢,確實降低碳排放強度。同時,加強國際合作交流,加大技術轉讓和資金援助力度,擴大碳排放權交易范圍,完善清潔發展機制,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碳減排積極性,降低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增速。只有建立在公平、合理基礎上的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才能發揮各國碳減排的積極性,有效控制全球碳排放過快增長。
參考文獻:
ANG J B. 2007. CO2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utput in France[J]. Energy Policy(10):4772-4778.
AZOMAHOU T,LAISNEY F,VAN P N. 200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2 emissions: a nonparametric panel approach[J]. J Public Econ,90:1347-1363.
FODHA M,ZAGHDOUD O. 2010. Economic growth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in Tunisi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 Energy Policy,38:1150-1156.
GROSSMAN G M,KRUEGER A B. 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No.3914:1-38.
IEA.2011.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2011[EB/OL].省略.
IM K S,PESARN M H,SHIN Y. 2003.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J]. J Economet,115:53-74.
KAO C.1999. Spurious regression and residual-based tests for cointegration in panel data[J]. J Economet,90:1-44.
LEVIN A,LIN C F,CHU C. 2002. Unit root tests in panel data: asymptotic and finite-sample properties[J]. J Economet,108:1-24.
MADDALA G S,WU S.199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 root tests with panel data and a new simple test[J]. Oxford Bull Econ Stat,61:631-652.
PEDRONI P.1999. Critical values for cointegration tes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with multiple regressors[J]. Oxford Bull Econ Stat, 61:653670.
ROMERO-AVILA D.2008. Convergence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mong 37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revisited[J]. Energy Econ,30:2265-2282.
第4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碳幣碳排放權交易低碳經濟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沒有完全散去的背景下,世界各國在致力于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對碳排放問題的爭論不但沒有暫時放緩,更有著愈演愈烈的趨勢。尤其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對減排計劃似乎有著空前的熱情——在制定自己國家減排目標的同時,更是“積極”地制定出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目標,這似乎可以看作是發達國家為經濟復蘇和經濟轉型所做出的努力。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金融市場上對美國制定的減排計劃的高調反映,一些金融機構對此計劃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支持,這樣的態度不僅僅是因為減排計劃在給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的同時,也給金融市場帶來了新的盈利和創新空間;更是因為按照發達國家意志制定的減排計劃一旦實施,碳排放權的交易將會推動碳幣時代的到來。這樣一來,這些所謂的游戲規則制定者將會以碳幣為工具,迎接屬于他們的碳幣時代。因此,我們要看到減排計劃背后所醞釀的碳幣,在碳幣時代到來之前掌握先機。
一、碳幣及其生成的歷史條件
(一)碳幣
首先要明確的是,碳幣并不是一種像金屬幣、紙幣、電子貨幣等那樣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形態,它是一個意想中的貨幣體系,也可以說是一個衡量世界上各種貨幣幣值的新標準。甚至有人將其理解為一種貨幣本位,像金本位和虛金本位制那樣,使信用貨幣和“碳”關聯起來,進而影響到某一種貨幣在世界市場上的信用地位和幣值。目前我國對碳幣的定義為:碳額度與黃金額度可以互換并作為國際貨幣的基礎(戴星,2009),其在世界范圍內的準確定義和衡量標準還沒形成,不過很明顯的是,在“碳幣體系”下,除了一國的經濟實力和黃金儲備,碳排放額度將會成為影響該國貨幣地位和幣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二)碳幣生成的歷史條件
促成碳幣誕生的最直接因素是國家之間碳排放權的交易(CDM)。1997年通過了《京都議定書》之后,世界各國開始努力降低碳排放以達到該協議所規定的減排目標。但是短時間內降低碳排放量不僅需要大量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資源,更有可能由此引發社會各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置失衡。即便不會給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帶來嚴重的沖擊,但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這當然是發達國家不愿意面對的結果。《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從2005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則在2012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這個時間差便成了國家之間進行碳排放權交易的條件之一。
2005年《京都議定書》生效以后,世界各主要溫室氣體排放國就要在2012年之前完成該協議規定的減排目標(與1990年的碳排放量相比)。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各國家地區之間的減排任務差距較大,這主要是由于各國的歷史排放量、經濟和技術實力不同,所要承擔的減排任務也不盡相同。從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的舉動我們可以看出,這一目標對于一些國家來說并不是很輕松就能實現的,或者說要實現該目標勢必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而美國這樣的國家是不愿意用放松經濟發展的步伐來換得該目標的實現的。對于其他國家來說,要么通過采用新技術或者轉變能耗模式來實現這一減排目標,要么就向率先完成減排目標的國家或者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購買碳排放權力,即以付出貨幣的形式將自己的減排任務轉移出去。如果購買碳排放權的實際成本要小于該國在短時間內實行本土減排而付出的成本,那么碳排放權的交易無疑就成了這些發達國家的首選。
以歐盟為例,1990年歐盟的碳排放量約為4.57億噸,我們假設歐盟每年按1%的速度降低碳排放量,則2008年其減排任務在300萬噸左右。在歐洲市場上2008年的碳排放交易價格約為30歐元/噸,而在中國市場上大約為10歐元/噸,這就意味著如果歐盟將減排任務完全轉移到中國要比完全轉移到歐洲市場上節省6000萬歐元,而同樣完成了減排目標。對于中國來說,歐盟所支付的減排價格則可以轉化成中國的外匯儲備。當然這只是一個簡單假設的例子,不過足以說明在國家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碳排放交易空間。
隨著《哥本哈根協議》(草案)的制定,國際市場上的碳排放交易會越來越多,而碳排放的交易價格也會逐漸上漲。很明顯的,碳排放權的交易已經開始影響到國家或者地區之間的貨幣關系,但是這樣以碳排放權交易為紐帶的貨幣關系還不是“碳幣體系”。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斷創新和碳金融產品的出現,碳排放權交易將會逐步在金融市場上顯示出其對世界貨幣體系的影響力。
二、“碳幣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迫于緩解氣候問題和《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協議》等國際規則的壓力,世界各國將會逐步降低碳排放量。但是如前所說,并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可以或者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減排目標。這樣一來,世界市場上的碳排放權交易會越來越繁榮,碳排放權也會逐漸成為各國貨幣之間的一條紐帶。目前世界金融市場上的一些金融機構已經開始提議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來適應碳交易市場的發展,比如碳排放權期貨和現貨。這些金融產品使得各國在金融市場上可以直接進行碳排放權的交易。如我們所知,目前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影響各國貨幣的主要金融產品有黃金和石油,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創新以及碳排放權交易的日益繁榮,如果碳排放權也進入到金融市場,將會成為和黃金、石油并列的影響貨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這個時候,碳幣便基本上形成了雛形。
可見,在2012年以后隨著發展中國家也開始肩負起減排責任,碳排放權貨幣化的速度會進一步加快。即便是碳排放權擁有了貨幣職能,碳幣體系在發展過程中依然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
(一)碳幣體系下的貨幣本位問題
之前已提到,目前一些人將碳幣理解為一種新的貨幣本位,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對碳幣的片面理解。因為隨著金屬貨幣退出歷史舞臺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信用貨幣逐步占領了市場并且適應著經濟的發展,但是信用貨幣背后依然有著國家黃金儲備和國家信用的支撐,這也是信用貨幣的基礎。碳幣不同于黃金和國家信用,它最初是一種由部分國家制定出的規則而促成的交易,這種交易在未來的金融市場中又變成了一種金融產品,而最終這種金融產品被賦予了貨幣的職能。所以我們可以說,支撐碳幣的是由人為規定的碳排放目標和在碳排放權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關系”。更何況碳排放目標的制定和類似于《哥本哈根協議》之類的國際規則不可能代表所有國家的利益,所以這種信用關系本身就帶有著比國家信用更多的不確定性和不平等性。如果這種碳排放權交易的信用關系也充當了信用貨幣的貨幣本位,那么它在給世界金融市場帶來更大風險的同時,勢必也會給國際貨幣體系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使世界貨幣體系變得更加脆弱。在未來的碳幣時代,究竟什么會充當碳幣的貨幣本位——依舊是黃金,還是帶有碳排放權交易信用的參考一攬子貨幣幣值的多重本位制?這將是世界各國努力的方向之一。
(二)碳幣的發行權問題
無可厚非的,碳排放權的制定者可以根據自身狀況制定出更有利于該國的減排目標。以美國為例,假如《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目標到期以后,美國在2032年新的減排目標是比2012年降低10%。如果以其自身的實力來看,到2022年美國就有可能實現該減排目標,那么美國就可以將剩下十年的減排能力通過金融市場交易出去,這也就意味著美國擁有了十年的碳幣發行權,而其究竟有多少的碳幣發行量,就要看他自身的減排能力了,我們可以簡單的計算一下:
如果美國擁有著到2032年可以實現比2012年降低30%的減排能力,那么他額外擁有的碳排放權就是:2012年碳排放量×(30%-10%)=A;假設2022年到2032年的碳排放權交易的均價為P,那么A×P=Q,Q就是美國可以控制的碳幣發行數量。至于何時發放,發放多少,就要由其自己說了算了。
可見,碳幣的發行權問題主要在于減排目標的制定方面。誰在減排目標的制定上擁有著更多的主動權,誰就在碳幣體系下擁有著更多的選擇權,這對于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來說是很不平衡的。所以碳幣的發行權問題也將會是未來各國爭論的焦點。
(三)碳幣體系的影響
在碳幣體系下,各國的貿易商品、關稅和匯率水平都會受到碳排放量的影響。對于貿易商品來說,如果以碳幣衡量各國的貨幣幣值,那么世界市場上的貿易商品價格的形成除了受到目前已有的因素影響之外,還要受到該國減排目標的影響。對于擁有著較輕減排負擔的國家來說,在實現減排目標之后,可以通過賣出碳排放權來獲得額外的外匯儲備,并且節省購買碳排放權的貨幣,這樣就保障了這些國家的正常流動性和幣值穩定,也維持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即不會因為國內缺乏資金而導致商品生產萎縮或者落后,其產品可以用更低單位的碳幣價格表示出來,在國際市場上就有了更強的競爭優勢。相反,對于有著較重減排任務的國家來說,一方面需要支出額外的貨幣來購買碳排放權,另一方面也要在減排技術和設備方面花費資金,這將會影響到國內正常的經濟秩序,使這些國家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碳幣標價較高,從而降低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給經濟發展帶來惡性循環。
碳幣體系對關稅的影響類似于對商品價格的影響。擁有碳幣發行權的國家在制定關稅方面有著更多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其可以借用碳幣工具,對那些沒有碳幣發行權國家的商品征收更高的關稅;而對于沒有碳幣發行權或者較少碳幣發行權的國家來說,只能在關稅的制定方面處于被動的地位。至于各國關稅的變動水平,其中主要依據就是碳幣發行權的多少。
在外匯市場上,碳幣發行權所屬國的貨幣和碳幣之間有著更加緊密的聯系,因此其貨幣的幣值在碳幣體系之下會有著更加強勢的地位,幣值穩定且劇烈變動的風險較小;沒有碳幣發行權的國家的貨幣幣值就會由于缺少了碳交易信用而變得相對弱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強勢貨幣幣值的影響,缺少了變動的主動性就意味著存在著較大的匯率風險。
三、碳幣體系下規則的制定和作用途徑
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其擁有著先進的技術和資金支持,因此要實現他們自己制定的減排目標困難并不是很大,但是對于新型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完成發達國家為其制定的減排目標就比較困難了。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若要完成減排目標,途徑有三個:
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社會資源發展低碳技術來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能耗模式。不過如之前所述,這勢必會影響到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進一步加大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這樣即使完成了減排目標,在新一輪的減排計劃制定當中,發達國家又會重新針對這些沒有參與權的國家制定出新的減排目標,如此循環下去,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會越拉越大。
二是向發達國家購買先進的減排技術和設備。雖然說發達國家有義務對發展中國家提供減排資金和技術的支持,但是在未來的碳幣體系之下,出于對本國利益的考慮,發達國家不會無償無盡地向發展中國家伸出援助之手。而發展中國家就必須向發達國家購買技術和設備來完成自己的減排任務。
三是向提前完成減排任務的國家購買碳排放權。采取這條途徑就意味著正式的將本國貨幣納入到了碳幣體系之下,也就是說該國貨幣在碳幣體系中的地位受到“碳幣”的左右,被左右的程度就取決于所購買的碳排放權的多少,從另一方面來說就是購買碳排放權的國家的貨幣將受控于碳幣體系規則的制定者。
不管從哪一個方面來看,碳幣體系規則的制定者都擁有著絕對的主動權,碳幣將是這些規則制定者的工具,而不能參與制定規則的國家只能處于被動地位,將財富以“碳幣”的形式轉移到規則制定者的囊中。
因此,碳幣體系的規則制定勢必會成為各國爭取碳幣主動權的焦點。不過由于綜合國力不同,減排計劃的制定不可能顧及到所有國家的利益,這種規則最終也會向制定者的利益靠攏,維持著制定者的意愿。所以,發展中國家應該及早的認清減排計劃背后所掩蓋著的“碳幣”,在規則的制定中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
四、目前中國面臨的碳交易狀況和建議
作為一個碳排放大國,我們一貫堅持的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不過《京都議定書》并沒有規定2012年之前中國的減排目標,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卻積極的為中國制定著2050年的減排目標,甚至要中國和印度承擔全球減排總量的20%。如果以這個標準來衡量,那么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來實現這個減排目標。顯然,由西方發達國家制定出來的減排標準是不合理的,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參與未來減排計劃的制定,在碳幣時代到來之前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掌握主動權。
從目前的碳排放權交易情況來看,我國簽訂的碳排放權交易項目已經超過了印度,居于世界第一位(如圖1)。
目前我國擁有著數量眾多的碳排放交易項目,這一方面說明我國擁有著潛在的減排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國正在努力發展碳排放交易市場。碳排放交易既為我國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資金和活力,又發展了我國新興的碳排放交易市場,使我們逐步熟悉該市場上的交易規則,為以后碳幣時代的到來打下良好的基礎。但是從目前我國的碳交易市場來看,國內市場上的碳排放權交易價格要遠遠低于世界市場價格。雖然這樣可以為我國帶來更多的交易項目,但是并不能很好的為我國帶來應有的收益。因此,我們還應該合理的對碳排放權進行定價,使國內的交易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打造碳交易市場的宏觀經濟環境:
第一,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向綠色經濟轉型,努力將減排壓力轉化成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目前我國正處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也是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重要階段,如何將這個特殊的經濟時期同節能減排聯系起來,實現經濟發展和降低排放的雙重目標,將是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的工作重點。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既有利于我國在未來的碳幣時代擁有著更多的主動權,也有助于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碳幣時代到來之前,積極發展綠色經濟,將會穩步推動我國經濟向碳幣時代平穩地過渡。超級秘書網
第二,參與國際減排計劃的制定,維護自己的權益。碳幣體系的關鍵之一就是減排規則的制定,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掌握規則的制定權就意味著碳幣的發行權。若要在碳幣時代擁有更多的碳幣發行權,使我國在碳幣體系之下處于主動的地位,就必須參與到減排計劃的規則制定中來,通過參與規則的制定維護本國在碳幣發行方面的權益。
第三,加快金融市場的建設和完善,打好碳金融產品發展的基礎。碳幣一旦開始生成,必然首先出現在宏觀條件良好的金融市場上。所以我國應該從現在的碳排放權交易開始,努力熟悉碳交易的交易規則和發展趨勢,并且及時地改善宏觀金融市場環境,做到市場環境和經濟發展階段相協調,這樣才能在碳幣時代到來的時候,使碳幣在第一時間擁有良好的發展空間。
第5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碳排放 LMDI方法 能源消費
一、引言
湖北是典型的能源輸入型地區,如何在能源缺乏的條件下實現經濟增長、且做到低碳與減排這一目標,是湖北省現階段面臨的重要難題。因此,分析湖北省能源消費碳排放影響因素,有助于找到合適的減排措施,實現湖北經濟的長遠發展。
二、文獻綜述
關于碳排放及其影響因素的關系研究方面,Shi(2003)在基于對93個國家1975―1996年的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人口的變化對碳排放變化的作用比發達國家更加明顯。從經濟發展方面來說,Kim、Lee&Nam(2010)利用STAR模型,研究發現韓國的碳排放和經濟增長之間是相互依存的。經濟發展水平影響收入水平,進而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和偏好,從而會導致不同強度的碳排放。Lenzen(1998)和Weber(2000)的研究表明消費者的行為對能源的使用以及溫室氣體的排放有一定的影響。關于碳排放影響因素分解模型的研究方面,Hulten(1973)首次將指數分解方法應用于能源問題的研究。Boyd等(1987、1988)分別提出了算數平均的Divisia指數法的乘法和加法形式。Ang和Liu(2000)提出了對數平均Divisia分解法(LMDI),通過這種方法來計算出來的因素權重不存在殘查,計算結果更加準確。國內學者徐國泉等(2006)采用對數平均權重Divisia分解法,定量分析了我國1995―2004年,能源效率、能源結構及經濟發展等因素對人均碳排放的影響。宋德永等(2009)運用LMDI方法,引入產業結構因素分析了我國1990―2005年的碳排放影響因素。朱勤等(2009)引入了人口因素研究碳排放影響因素。秦翊、侯莉(2013)運用LMDI分解法對廣東省能源消費碳排放進行分解,量化各因素貢獻。許廣月(2011)采用面板數據的計量模型,認為影響我國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是產出規模、產業結構域及能源消費結構。綜上分析,本文認為采用LMDI方法分析湖北省能源消費碳排放影響因素是較為合理的。
三、湖北省能源消費與碳排放現狀
1、能源消費
從表1中數據可以看出,隨著湖北經濟的發展,湖北省能源消耗量不斷增長。2012年湖北省能源消耗總量高達18128.09萬噸標準煤,比2005年增加7546.74萬噸,其中煤炭消耗12237.57萬噸、石油112.86萬噸、天然氣389.42萬噸、電力2019.28萬噸,比2005年分別增加77%、42%、164%、89.5%。
由表2中相關數據可知,湖北省主要的消費能源為煤炭,2005―2012年間,煤炭消費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例總體維持在60%到70%之間,有較小幅度的上漲。石油消費所占比例先增后減,總體維持在20%到25%之間。電力消費所占比例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增長幅度較小,總體維持在9%到11%之間。天然氣消費所占比例上升趨勢明顯,2012年所占比例比2005年增加了54%,但從整體而言,湖北省天然氣消費規模非常小。由于同等質量條件下的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煤炭提供的熱量少于石油和天然氣,但碳排放要高于石油和天然氣,因此煤炭消費所占比例會直接影響到地區的碳排放水平,能源消費結構的不合理會影響碳排放量。
2、碳排放
在測算湖北省能量消費碳排放量時,采用國際上公認的比較合理的碳排放測算方法――IPCC清單法進行計算。按照煤炭、石油、天然氣三大類能源分類進行計算,將各小類化石能源按照折標準煤系數折算為煤炭、石油、天然氣并分別進行加總,再利用碳排放系數計算碳排放量。關于碳排放系數,采用國家發改委能源所推薦的系數。
由此可以得到湖北省2005―2012年碳排放總量數據如表5。
由表5相關數據可知,從2005―2012年,湖北省碳排放總量總體呈上升趨勢,2008年有所降低。2005年碳排放總量為6665.58萬噸,2012年碳排放總量為11349.7萬噸,是2005年排放量的1.7倍。2011年,湖北省碳排放總量首次突破億萬噸。從表3湖北省能源消費量相關數據可發現,2008年能源消費總量反增為減。這些數據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總量不斷增加,三者變動存在一定的相關性。由于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湖北省經濟形勢受到了影響,導致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總量出現同向波動的情況。
由圖2可知,2005―2012年間,由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的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都不同程度的呈現出上漲趨勢。在各種能源利用中煤炭產生的碳排放量最多,其次是石油,再次是天然氣。煤炭消費量的增加是湖北省能源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由于天然氣是一種比較清潔的能源,雖然由天然氣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不斷增加,但在總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較低。
四、基于LMDI方法的湖北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
1、LMDI方法的分解模型
構建碳排放影響分解模型的目的是分解出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因素,并通過計算這些因素的貢獻率來分析其影響程度。根據Johan.A等的分析框架,碳排放量的分解如下:
其中,C為第T年相對于基年的碳排放量的變化值;CT、C0分別指第T年,基年的碳排放量;CK、CS、CI、CR、CP分別為能源排放強度、能源結構、能源強度、人均GDP以及人口等因素變化導致的碳排放量的變化值。
按照LMDI方法,各個因素的分解結果如下:
因此,文中所需的數據有2005―2012年間湖北省碳排放量、各種能源消費量、能源消費總量、湖北省GDP及人口數據。通過計算后構成能源結構、能源強度、人均GDP數據。
各類能源消費量數據均來自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3》,需要說明的是,文中所統計的能源消費量是全社會能源消費量,而不是規模以上工業能源消耗量。此外,為了方便計算與分析,將統計年鑒中的8小類能源消費數據利用折標準煤系數換算后,加總歸類后得到煤炭、石油及天然氣三大類能源消費量;碳排放數據是在能源消費數據的基礎上,采用國家推薦的碳排放系數,利用碳排放量測算公式計算得到。湖北省人口及GDP數據均來源于湖北省統計局網站中公布的湖北統計年鑒。其中,為避免受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2005―2012年的湖北省生產總值數據采用2005年的不變價格。通過計算整理,本文進行實證分析所需的相關基礎數據如表7、8所示。
3、實證分析
(1)數據處理
在表7及表8的相關數據基礎上,利用對數平均指數分解法(LMDI)對湖北省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分解分析。由于能源碳排放強度是固定不變的,根據碳排放分解公式,可知影響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因素為能源結構因素、經濟發展因素、能源強度因素及人口因素,得到各分解因素的貢獻效應值如表9所示。
(2)因素分析
結合相關計算結果和湖北省經濟發展、人口規模、能源消費及能源結構的有關數據,對湖北省2005―2012年碳排放變化的影響因素作進一步分析。由表10可知,能源強度累積效應值為負數,能源結構、經濟發展及人口規模的累積效應為正數。
能源結構因素逐年效應存在較大的波動情況,在2005―2006年、2006―2007年、2007―2008年以及2011―2012年等期間內,能源結構效應為負值,其余期間為正值。由表8可知,2006年、2007年、2008年以及2012年,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均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天然氣及石油消費比重未出現該趨勢,且煤炭的碳排放系數在三種能源中是最高的。因此,能源結構效應與高碳能源消費比重保持同方向的變化,降低高碳能源的消費比重有助于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從累積效應值來看,能源結構累積效應為64.65,是湖北省碳排放量變化的正向影響因素,但效應貢獻率較低,僅為1.5%。
由表9可知,能源強度因素逐年效應均為負值。結合表8中能源強度數值變化情況,即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可知,能源強度因素逐年積累效應與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的變化趨勢一致,因此,能源強度上升,將促使碳排放量上升;能源強度下降,會抑制碳排放量的增長。從貢獻率來看,能源強度因素的貢獻率為-73.13%,對湖北省碳排放量的變化有較強的影響。“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2010年)湖北省能源強度不斷下降,該期間湖北省能源建設顯著,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湖北省碳排放的過快增長。
2005―2012年期間,經濟發展因素的逐年效應均為正值,累積效應值不斷增加,據表8中的人均GDP數據可知,經濟發展因素效應與人均GDP的變化趨勢保持一致,不斷上升,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湖北省碳排放量也在不斷增長。經濟發展因素的效應貢獻率高達167%,經濟規模的變化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2010―2011年期間外,人口規模因素的效應均為正值,根據表7中人口數據可知,2011年湖北省總人口為6164.1萬人,比2010年減少11.9萬人。人口規模因素逐年累積效應不斷上升,由此可知,人口規模對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增加具有拉動作用。人口規模的效應貢獻率為5.3%,相對于經濟發展因素和能源強度因素而言,影響作用較弱。
五、小結
通過運用LMDI方法對湖北省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結果如下:在2005―2012年期間內,湖北省碳排放量從2005年的6665.58萬噸,增長到了2012年的11349.7萬噸,年平均增長率為7.9%,低于同期GDP增長速度。在此期間,湖北省碳排放累積效應總體呈上升趨勢,而在2008年有所回落。這一趨勢是經濟發展因素、人口規模因素、能源強度因素以及能源結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四個影響因素中,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規模的擴大是湖北省碳排放量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經濟發展效應的貢獻值高達167%。同時,人口規模效應也對湖北省碳排放量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貢獻率為5.3%。雖然人口規模因素不是短期內可以調整的,但如果實施了有效的長期調控戰略,其驅動力也是不容忽視的。能源強度效應在很大的程度上抑制了湖北省碳排放量的增長,貢獻率達到-73.13%。“十一五”規劃期間,能源強度下降趨勢明顯,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能源強度由2011年的1.28噸/萬元,下降到2012年的1.15噸/萬元,同時,2011―2012年期間能源強度抑制效應高達-1140.57,這表明《湖北省低碳發展規劃(2011―2015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是指導今后一個時期湖北省低碳發展的總體藍圖和行動綱領。但從總體累積效應來看,湖北省碳排放量仍然保持著一定的增長速度。因此,湖北省要重視相關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從而減少碳排放量。2005―2009年,能源結構因素對湖北省碳排放量增加起到了一定的抑制,而此后轉變為拉動作用。總體而言,能源結構效應是湖北省碳排放量變化的正向影響因素,但影響效應變化不大,主要原因是湖北省能源消費結構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優化,仍是以煤炭等高碳能源為主。同時這樣說明湖北省通過調整能源結構來減少碳排放量的空間還很大。
因此,對于湖北省碳減排政策提出如下建議:(1)湖北省應增加清潔能源消費比重,整合利用水電資源,推動天然氣快速規范發展、高效利用風能資源、充分發展太陽能、有序開發生物質能,強化低碳能源生產與供應,減少煤炭消費量,逐步調整和優化能源結構,減少碳排放。(2)降低湖北省單位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可采用行政和經濟手段,從而有效地抑制碳排放量的增加。(3)利用科技創新,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能有效地降低湖北省碳排放量。政府應加強在能源領域的研發投入,鼓勵和引導企業增加能源技術研發投入,利用湖北省的人力資源優勢,組織動員產學研相結合進行重點課題攻關。(4)推行碳排放配額制度,建立健全湖北省碳交易市場。這是新時期湖北省發展低碳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課題來源: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鋼鐵產業集群低碳化發展與政策研究”(14G109)。)
第6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經濟增長;能源消耗;間接碳排放;面板數據模型
中圖分類號:F06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8409(2012)09—0001—06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Based on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the Sub—sector Panel Data from 1995 to 2007
CAO Guang—xi, YANG Ling—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The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are calculated by using Chinese input—output tables from 1995 to 2007.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s and short—term effec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ng—term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exists, and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s a positive short—term cause to carbon emissions, while energy consumption negatively causes carbon emission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energy consumption;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panel data model
近年來,碳減排相關問題受到各國政府和民眾的廣泛關注。目前,中國碳排放僅次于美國居于世界第二位。據國內外眾多研究機構預測,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前后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在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將積極加強對溫室氣體排放的控制,并且提出了“到2020年,萬元GDP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的節能減排新目標。因此,研究中國的能源消耗、經濟增長和碳排放之間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近年來,世界各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出發,應用時間序列分析和面板數據模型,對經濟增長、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三者的相互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但由于選擇的計量方法、研究對象發展水平和時間跨度的不同,許多相關研究的結果之間存一些分歧和差異。牛叔文等曾對此作過詳盡綜述[1]。
國外學者Shafik,Ban dyopadhyay發現,1960~1990年149個國家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收入水平兩者之間呈正向線性關系[2]。Grubb認為,在工業化初期,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逐漸增加,但是跨越一個特定的階段后,人均收入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會減弱[3]。國內學者李明賢和劉娟通過相關系數分析、回歸分析等相關關系分析,得出中國經濟增長是碳排放增長的推動原因,但是碳排放增長率明顯低于經濟增長率[4]。帥通和袁雯對近年來上海工業能源消耗和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進行分析,采用IPCC 2006年提出的各類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的計算方法,探討了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變動對碳排放的影響[5]。牛叔文等以亞太八國為對象,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1971~2005年亞太八國的能源消耗、GDP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關系,得出了三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結論,并且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基數和能源利用效率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1]。Chang對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經濟增長進行了多變量因果關系檢驗,認為經濟增長的需求將增加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6]。
第7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 脫鉤模型;經濟增長;低碳經濟;CO2排量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3-5595(2013)01-0017-05
低碳經濟概念是在全球氣候日益變暖、氣候變化日益無常的背景下由英國政府在其2003年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率先提出的,它是指經濟發展要著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逐步提高清潔能源使用比例,以減少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減少人類對化石能源的依賴[1]。發展低碳經濟既順乎世界潮流又合乎中國國情,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發展低碳經濟是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抓手,是應對氣候變化、開展國際合作的戰略選擇。山東省作為中國的經濟強省,應順應世界和國家節能減排的潮流,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研究山東省低碳經濟發展很有必要。
一、脫鉤理論文獻綜述
脫鉤概念首先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用來表示經濟發展過程中用較少的物資消耗產生較多的社會財富,是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對物資消耗高度依賴的敏感反應。該組織的初衷是破解經濟發展與環境損害的難題。OECD脫鉤概念的提出,促進了各類經濟活動脫鉤指標的建立[2]1。
縱觀國內外的研究,國外學者更多注重節約能源和減少排量兩方面研究,且將脫鉤指標運用在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和經濟發展的領域。OECD以30個成員國為代表,運用39個指標分析其環境與經濟脫鉤狀態,最后得出這30個國家總脫鉤率約為52%[2]2;Juknys以立陶宛(Lithuania)為例,分析其脫鉤情形[3];Herry Consult GmbH等學者以奧地利為例,分析在經濟增長過程中,運輸業需求情況與其脫鉤狀態[4];Tapio對歐洲的交通業經濟增長與溫室氣體之間的脫鉤情況進行了研究[5];David Gray、Jillian Anable、Laura Illingworth和Wendy Graham等分析了蘇格蘭地區經濟增長與二氧化碳排放的脫鉤情況[6]。
國內關于脫鉤研究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土地資源、循環經濟、能源消耗的測度及農業等領域。鄧華、段寧在其文章中介紹了西方“脫鉤”理論的兩種主流評價模式——IU曲線和總量研究,并提出物資消耗總量的研究應該成為經濟增長與物質消耗關系研究的主流方向[7]。王崇梅、王薦其將脫鉤理論應用到煙臺開發區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中,即“1.5-2倍數”發展戰略,并指出這種發展模式和中國的國情非常吻合[8]。劉建興、許肅分析了福建省19年的能源消耗和經濟增長關系,得出福建省能源生態壓力低于中國平均水平,所付出的自然生態成本高于中國平均水平,能源利用率有待改善提高[9]。馮艷芬、王芳采用總量比較法的脫鉤評價模式,設計了耕地消耗與經濟增長總量的脫鉤指標及脫鉤率,計算了1996—2002年廣州市耕地消耗與經濟增長總量的脫鉤關系[10]。王遠、陳潔等以江蘇省為研究區域,運用“脫鉤”和“復鉤”理論、協整分析技術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辨識和分析了能源消費總量、電力消費和地區生產總值之間的耦合關系[11]。 李忠民、慶東瑞運用OECD脫鉤指標和Tapio脫鉤指標對山西省工業部門工業增加值與其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脫鉤分析,得出作為山西省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之一的工業呈現GDP與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擴張連結狀態[12]。王虹利用相對“脫鉤”、“復鉤”的理論與測度方法,分析了中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之間的關系[13]。徐衛濤、張俊飚等用脫鉤理論,分析了化肥施用量與糧食生產之間的關系,得出二者之間的脫鉤類型[14]。楊璐嘉、李建強等對四川省的建設占用耕地與經濟發展分別進行了總量脫鉤評價和消耗強度脫鉤評價[15]。
第8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低碳經濟;財稅政策;措施
1碳排放過量對地球環境造成的危害及現狀
至今為止,人類活動造成的碳排放對生態環境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也給人類的社會和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1.1碳排放過量造成全球氣候變暖
經過近十幾年來科學家對全球海平面高度和全球平均溫度等數據的監測發現,兩極地區冰雪大范圍融化,全球氣候變暖十分明顯。很多數據表明,全球生態系統已經受到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這些影響在目前看來有好有壞,但從長遠來看,整體是弊大于利。
1.2碳排放過量主要由全球工業化導致
自英國等發達國家率先進入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造成的碳排放越來越多。研究表明,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紀末,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已經增加了近一倍,其中,主要是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甲烷等。而全球氣溫升高又導致全球氣候異常,如大旱、大澇、氣溫差異大等極端天氣,給人來生活造成很大不便。
1.3全球碳排放過量還將持續很久
科學家根據現有數據做出預測,如果世界各國仍沿用如今的做法,未來幾十年,全球氣候變化仍將持續下去。到二十一世紀中期,全球氣候將進一步變暖,并將進一步誘發全球氣候的很多變化,甚至比如今造成的影響更加嚴重。
2實行低碳經濟對我國發展的積極意義
人類活動造成了全球碳排放過量問題,給人類帶來很多負面影響,甚至影響到人類的生存安全。因此,全球各國應該團結起來,控制碳排放,減緩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對此,我國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戰略目標,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發展低碳經濟,建設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國家。
2.1發展低碳經濟可以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科學發展觀
我國雖然地大物博,自然資源豐富,然而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數量很少,因此實現低碳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十分重要。我國目前的能源結構仍以煤炭等化石能源為基礎,而這些能源的使用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這也是我國如今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因此,我國想要發展低碳經濟,首先應該做的就是提高我國能源使用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如風能、潮汐能等,從而改變我國目前的能源結構,減少碳排放。除此之外,我國還應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我國工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資源利用率,實現經濟的綠色增長和低碳發展。另外,還應發展我國的科學技術,依靠技術進步帶動資源利用率的提高,大力發展低碳技術,推動整個社會的科學技術的進步。
2.2發展低碳經濟可以改善居民生活條件
環境的好壞對我國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比如,最近我國很多城市都頻繁出現霧霾天氣,導致空氣能見度降低,空氣中充滿大量的有害顆粒,人類呼吸了這樣的空氣后,很容易導致呼吸器官疾病。另外,很多地區的酸雨天氣造成建筑等腐蝕,莊稼顆粒無收,給人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損失。因此,發展低碳經濟,保護環境已經成為我國目前迫切解決的問題之一,黨和國家為了改善民生,保證我國人民的健康安全,改善我國人民的生活質量,必須將科學發展觀落實到黨和國家工作的每一步上,從各個方面解決氣候變化和高碳經濟帶來的民生問題。
2.3發展低碳經濟有助于提高我國的國際形象
氣候變化如今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它不僅需要我國的努力,更需要全球各國的大力支持。氣候變化不僅僅關乎一國,它關系到各國的社會經濟的發展,關系到世界人民的生存與發展。如今,世界各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簽訂了許多公約,使世界各國得以公平合作。在這種環境下,為了滿足我國的長遠發展,必須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碳排放量減少迅速的國家也將獲得世界各國人民的尊敬,有助于樹立我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
3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
從財稅政策方面,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主要有以下措施:
3.1完善與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相關的法律法規
目前,我國與碳排放以及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然而這些法律法規已經不能適應如今社會中追求低碳經濟的目標,因此,黨和相關部門應該積極行動起來,完善與低碳經濟發展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定和低碳經濟發展有關的法律法規,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
3.2政府應出臺相關的政策來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政府除了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還有在政策上給予低碳企業一定的優惠措施,具體到財稅政策上就是減免一定比例的稅收,從而鼓勵企業實行低碳經濟,體現國家對低碳經濟的重視。同時,國家應該在總體上制定相關的碳排放控制目標,并鼓勵全社會企業來積極完成。在宏觀上,國家應積極主導經濟的發展方向,給我國工業化企業指明道路,幫助其改變自身高碳排放的發展方式,使其轉變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企業。
4總結
因此,為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首先應在法律制度方面給予支撐,并在國家政策上給環境友好型企業適當的支持,其次國家應對其起到宏觀調控作用,牢牢把握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給全社會制定出相應的目標,給我國企業指明發展方向。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為我國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郭代模,楊舜娥,張安寧,等.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基本思路和財稅政策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09(58):2-8,40.
[2]王順敖.對我國低碳經濟背景下財稅政策的思考[J].前沿,2010(16):67-70.
第9篇: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范文
關鍵詞:二氧化碳;減排成本;減排技術;減排對策
一、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基本狀況分析
隨著經濟發展,溫室效應不斷加劇,已嚴重影響到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溫室氣體,對溫室效應的作用可達66%。大部分的溫室氣體與人類活動有關,特別是進入工業化后,溫室氣體的濃度急速上升。
1.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體特征
我國能源主要是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這類能源是二氧化碳的主要能源。而且,由于我國是上升期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能源消耗大,導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很大。我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以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對較小,在21世紀之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速緩慢。從2003年開始,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迅猛的增長,增長率達到了13%。在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超過了美國。
歐盟的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美國的碳排放量也一直是處于穩定的高水平狀態。中國與日本的碳排放量從1980年到2007年都出現增長,日本增量較小,中國增量較大,總體碳排放量超過了美國。發達國家,已度過了工業化初期高耗能的時期,碳排放量趨于穩定并緩慢減少。中國由于經濟的發展,碳排放量大增,減排任務極重。而且由于技術的不到位,強制性減排會造成很大的經濟代價。
2.我國不同地區及不同行業碳排放量的現狀
我國不同省區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很大的差異。2007年,絕對碳排放量最多的省份是山東,最少的省份是海南;碳排放量增長速度最快的是寧夏和內蒙古,最少的黑龍江。從分布區域看,東部地區二氧化碳排
放量占到了全國排放量的一半,而且增長最快,達到9.8%;中部地區占到26.72%,增長率分別為8.85%;西部相對最少,增長率為7.45%;從行業分布來看,工業碳排放量占到全國的70%以上,高耗能行業碳排放量增長了一倍。其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碳排放增長最快。電力碳排放系數總體呈下降趨勢。
二、溫室氣體減排成本分析
減排成本是一個關鍵制約因素,發展中國家短期內無法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減排目標,只能是通過限制、關閉高排放部門來實現,這就需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
1.減排成本的基本概述
對二氧化碳減排成本可以從不同視角、層次對二氧化碳的減排成本的定義和估算。總體來說,可以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進行界定。
從微觀角度,二氧化碳減排成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了實現減排目標而直接投入的技術和資金。從宏觀角度,二氧化碳減排成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了實現減排目標采取措施從而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即通過強制性減排造成的國家GDP損失。這種損失主要是因為在短期內無法依靠技術進步而達到減排目標,只能通過限制高耗能企業的發展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這樣抑制了經濟的發展,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本文主要從宏觀角度分析,還涉及到邊際減排成本,邊際減排成本是指每減少一單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所引起的GDP的減少量。
2.我國二氧化碳減排成本分析
經濟發展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的一種矛盾的關系,如何做出一個適當的權衡非常重要。通過考察中國經濟發展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運用投入產出分析及多目標規劃理論,建立了中國宏觀經濟成本估算模型。通過對模型的求解,對其結果的分析,建立了下圖。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與潛在GDP之間的關系,從而對中國減排宏觀經濟成本做出粗略的計算。不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對應不同的GDP值,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大時,GDP值也最大。當GDP值為最大值35.30萬億元時,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達到最大值97.01噸。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對二氧化碳的限制將以降低GDP的增長率為代價。通過對上圖數據的計算分析得出下表。
從表中可以看出,當二氧化碳減排的力度越大,減排的宏觀經濟代價就越大,GDP的年增長率就會越低,二氧化碳的宏觀經濟成本就越高,而且在不同的減排力度下,成本的上升幅度也不同。在
減排量在4.42億噸到7.59億噸的區間內,減排量每增加1%,宏觀經濟成本就上升0.20%;在7.59到9.84這個區間內,減排量每增加1%,宏觀經濟成本就上升0.46%。同時也可以看出,碳強度降低的彈性較小。二氧化碳減排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十分顯著,我國2010年二氧化碳減排的宏觀經濟成本約為3100―4024元/噸二氧化碳。
然而由于溫室效應的消極影響越來越大,國際對中國溫室氣體減排的要求越來越高,中國目前必需節能減排,由于技術的不到位只能強制性減排,造成了很大的經濟損失。如表2中所示為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650ppmv,550ppmv,450ppmv情景下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可以看出在450ppmv穩定情景下,發展中國家在2010年減排,會出現經濟損失。減排率越大經濟損失就越大。所以大規模的二氧化碳減排會對我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對二氧化碳濃度要求越低,我國的經濟損失就越大。如圖中所示在450ppmv情景下,2100年損失可達到4.8%,在650情景下損失就小的多;有長期準備的減排其損失要小于突然快速減排;技術是實現減排的核心。
因此,在設定限排目標時應充分考慮到二氧化碳減排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程度,根據實際的潛力和承受力確定合理目標。減排要依靠長期的技術進步,短期內碳排放強度下降的空間彈性不塌,因此不宜把目標設的太高。
參考文獻:
[1]范英.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路徑與政策研究[M].科學出版社,2011(7):112-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