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數(shù)額”在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金融詐騙犯罪進(jìn)行立案認(rèn)定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數(shù)額是決定是否作為詐騙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責(zé)任的標(biāo)準(zhǔn)。現(xiàn)行的法律文件對(duì)于數(shù)額的規(guī)定不夠具體、明確,從而給司法實(shí)踐的適用帶來混淆。本文分別金融詐騙個(gè)人犯罪和共同犯罪兩種類型就“數(shù)額”的認(rèn)定、適用問題闡明看法。在金融詐騙個(gè)人犯罪中,應(yīng)當(dāng)區(qū)別犯罪既、未遂兩種情形,在既遂犯中,應(yīng)當(dāng)以所得數(shù)額作認(rèn)定,適用中注意對(duì)具有返還、非法使用處分、行政機(jī)關(guān)已經(jīng)單獨(dú)處理過等情形的具體適用。犯罪在預(yù)備、未遂、中止的情況下,以指向數(shù)額為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在金融詐騙共同犯罪中,則應(yīng)當(dāng)分別定罪和量刑兩種情形作認(rèn)定。
「關(guān)鍵詞金融詐騙 所得數(shù)額 指向數(shù)額 認(rèn)定 適用
“數(shù)額”在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金融詐騙犯罪進(jìn)行查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數(shù)額是決定是否作為詐騙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責(zé)任的標(biāo)準(zhǔn)。200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聯(lián)合的《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以下簡(jiǎn)稱《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對(duì)于金融詐騙犯罪和經(jīng)濟(jì)犯罪中涉及到“數(shù)額”的犯罪基本都作了具體的規(guī)定,達(dá)到這一數(shù)額的,才能構(gòu)成刑事犯罪立案、追訴,追究刑事責(zé)任;未達(dá)到《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中的數(shù)額的,不構(gòu)成刑事犯罪,只能作為一般違法行為追究相應(yīng)的民事或行政責(zé)任。《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意在解決由于缺乏對(duì)一些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在立案?jìng)刹椤⑴丁⑵鹪V工作中出現(xiàn)掌握尺度不盡一致的情況,影響到案件的查處工作,從而給辦案實(shí)踐提供一個(gè)明確、統(tǒng)一的執(zhí)法規(guī)范。 但是,這一規(guī)定對(duì)于金融詐騙數(shù)額和其他經(jīng)濟(jì)犯罪追訴數(shù)額的規(guī)定,仍然有含糊之處,使得實(shí)踐中仍然不宜操作。舉例來說,在陳淑蘭、陳淑英集資詐騙案件中,“二陳”涉及到的詐騙數(shù)額共達(dá)8877萬元,用后吸收的集資款兌付先前的集資款本息為6467萬元,無法返還的集資款共計(jì)2400萬元,如果適用《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究竟適用哪一個(gè)數(shù)額進(jìn)行認(rèn)定,該規(guī)定沒有說明,從而給實(shí)踐中的適用帶來混淆;而這一問題在金融詐騙犯罪,乃至經(jīng)濟(jì)犯罪的認(rèn)定中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在下文中分別金融詐騙個(gè)人犯罪和共同犯罪兩種類型就“數(shù)額”的適用問題闡明看法,為公安機(jī)關(guān)司法實(shí)踐作一參考。
一、金融詐騙個(gè)人犯罪
對(duì)于金融詐騙個(gè)人犯罪的犯罪數(shù)額具體所指,在學(xué)理上有多種認(rèn)識(shí),包括:指向數(shù)額,是指詐騙犯罪的指向的公私財(cái)物數(shù)額,即行為人主觀上希望騙得的數(shù)額;所得數(shù)額,是指詐騙犯罪人通過實(shí)施詐騙行為想實(shí)際得到的財(cái)物數(shù)額;交付數(shù)額,是指詐騙行為的被害人由于受騙而實(shí)際交付的財(cái)物數(shù)額;侵害數(shù)額,是指詐騙行為直接侵害的實(shí)際價(jià)值額, 我們認(rèn)為,對(duì)認(rèn)定金融詐騙罪的數(shù)額問題應(yīng)當(dāng)首先分別犯罪是否既遂的情形。因?yàn)樾袨槿嗽陬A(yù)備、未遂、中止的狀態(tài)下,可能只存在指向數(shù)額,所得數(shù)額、交付數(shù)額、侵害數(shù)額都無從談起。
(一) 金融詐騙犯罪既遂的情況
在金融詐騙犯罪既遂的情況下,我們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以上述的所得數(shù)額予以認(rèn)定。理由如下:
首先,指向數(shù)額雖然反映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但在具體實(shí)施詐騙犯罪中,由于種種客觀因素,行為人主觀上希望騙得的數(shù)額可能沒有全部得以實(shí)現(xiàn),以指向數(shù)額作為定罪量刑的標(biāo)準(zhǔn),失之過嚴(yán)。同時(shí),以指向數(shù)額為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在司法實(shí)踐上缺乏可操作性,行為人主觀上的意圖,在取證上存在難度:行為人的主觀意圖,最直接的證據(jù)應(yīng)當(dāng)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但是根據(jù)我國(guó)刑事訴訟法第46條的規(guī)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jù)的,不能認(rèn)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如果希冀通過口供發(fā)現(xiàn)線索,獲取其他間接證據(jù)來認(rèn)定,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過口供縮小、隱瞞自己的罪責(zé),司法機(jī)關(guān)同樣難以順利取證、追究犯罪。何況,在許多犯罪中,行為人對(duì)于自己主觀上希望詐騙所得的數(shù)額,并沒有明確的意圖,這樣,在司法認(rèn)定上,就會(huì)陷入數(shù)額不明、無法認(rèn)定的尷尬局面。
其次,就交付數(shù)額來說,也不宜成為認(rèn)定的犯罪數(shù)額的標(biāo)準(zhǔn),這是由于在詐騙犯罪實(shí)施過程中,行為人為達(dá)到最終非法占有公私財(cái)物的目的,往往會(huì)有先期兌現(xiàn)的行為,有時(shí)甚至是高于本金的高額返還。如在以“標(biāo)會(huì)”方式進(jìn)行的集資詐騙犯罪中,行為人為引誘更多的社會(huì)公眾的參與,會(huì)對(duì)先期參與的被集資者兌現(xiàn)高息(并還本)的許諾,在犯罪實(shí)施的過程中,行為人也會(huì)定期進(jìn)行返還,這些返還的數(shù)額不應(yīng)當(dāng)計(jì)算在對(duì)行為人進(jìn)行定罪量刑的犯罪數(shù)額中,但在交付數(shù)額中就無法得以體現(xiàn)。
再次,就侵害數(shù)額來說,一些論者主張將其作為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的標(biāo)準(zhǔn) ,我們認(rèn)為采納侵害數(shù)額在司法實(shí)踐中難以操作,以侵害數(shù)額作為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的標(biāo)準(zhǔn),除了會(huì)將行為人非法所得計(jì)算進(jìn)去,還會(huì)將行為人的侵害行為所造成的其他直接損失計(jì)算在內(nèi),這樣一來,認(rèn)定的標(biāo)準(zhǔn)就難以界定。尤其是在被害者為社會(huì)不特定公眾的詐騙犯罪中,如集資詐騙犯罪,由于涉及面廣,人數(shù)眾多,被害者自身情況多種多樣,造成的直接損害就多種多樣,有的家庭生活難以維持,有的企業(yè)瀕臨破產(chǎn),所以,以侵害數(shù)額為標(biāo)準(zhǔn)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在理論上說得通,在實(shí)踐中并不具有可行性。
最后,根據(jù)有關(guān)司法解釋的精神,也應(yīng)當(dāng)以所得數(shù)額作為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的標(biāo)準(zhǔn)。最高人民法院在《關(guān)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中規(guī)定:“利用經(jīng)濟(jì)合同進(jìn)行詐騙的,詐騙數(shù)額應(yīng)當(dāng)以行為人實(shí)際騙取的數(shù)額認(rèn)定”,金融詐騙中可以視為合同詐騙的特殊類型,根據(jù)《合同法》第10條的規(guī)定,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第11條規(guī)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shù)據(jù)電文(包括電報(bào)、電傳、傳真、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xiàn)所載內(nèi)容的形式。在金融詐騙中,犯罪行為人與受騙方仍然表現(xiàn)為合同交易的形式,而且大部分是書面合同的形式,如集資詐騙中的有價(jià)證券、融資憑證、貸款詐騙中的貸款合同、票據(jù)詐騙中的金融票據(jù)、信用證詐騙中的附隨合同、單據(jù)、文件等,保險(xiǎn)詐騙中的保險(xiǎn)合同等。所以,針對(duì)以經(jīng)濟(jì)合同形式實(shí)施詐騙犯罪其數(shù)額以所得數(shù)額認(rèn)定的這一司法解釋,其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貫徹于金融詐騙犯罪中。
所得數(shù)額,如上所述,是指詐騙犯罪人通過實(shí)施詐騙行為而實(shí)際得到的財(cái)物數(shù)額。在具體認(rèn)定所得數(shù)額時(shí),有以下幾種情況需要注意:
第一,犯罪人有返還情節(jié)時(shí)應(yīng)當(dāng)據(jù)實(shí)扣除返還的數(shù)額。一般地,在詐騙行為中,行騙人非法占有受害者的財(cái)物,或大肆揮霍,或席卷而逃,在案發(fā)前并不存在返還的問題。但近年來發(fā)展起來的一些詐騙形式中,行騙人為使自己的詐騙得逞,手段更加隱蔽,形式更為復(fù)雜,在實(shí)施詐騙行為中的過程中,為了騙取更多公眾的信任,以便將數(shù)目更大的款物據(jù)為己有,在詐騙行為開始之初,往往會(huì)兌現(xiàn)自己高額回報(bào)的許諾,向先期的投資者支付高額本息。實(shí)際上,犯罪人仍然不會(huì)自己受損,用以返還的資金是后期受害者的資金。如陳淑蘭、陳淑英集資詐騙中,先期自己掏錢墊付20%的月息,以蒙騙更多的群眾參與。在一些貸款詐騙中,也會(huì)出現(xiàn)詐騙犯罪人有返還的情形。根據(jù)所得數(shù)額的涵義,犯罪人用以返還的部分不屬于實(shí)際騙取得到的部分,不應(yīng)被認(rèn)定進(jìn)來。
由此,對(duì)于連環(huán)詐騙的情形中,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時(shí)也應(yīng)當(dāng)將返還的數(shù)額累計(jì)后排除在外。所謂連環(huán)詐騙,是指行為人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連續(xù)多次實(shí)施詐騙行為,期間多次以后一次詐騙所得返還給前一次的受騙者。這種連環(huán)詐騙的行為,如果從形式上把每一次詐騙行為孤立起來看,其每次行為都能單獨(dú)構(gòu)罪,如果以此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必然得出按累計(jì)詐騙所得計(jì)算的結(jié)論。但是,由于這種“拆東補(bǔ)西”式的連環(huán)詐騙行為是在行為人統(tǒng)一的主觀故意支配之下進(jìn)行的,這種前后連環(huán)的單個(gè)詐騙行為,是一個(gè)詐騙犯罪整體行為的組成,所以對(duì)此類案件犯罪數(shù)額的認(rèn)定,其實(shí)際所得的數(shù)額應(yīng)將累計(jì)詐騙所得總額減去累計(jì)歸還的數(shù)額,以實(shí)際騙取的所得額,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jù)。有關(guān)的司法解釋也是肯定這種做法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9條規(guī)定,“對(duì)于多次進(jìn)行詐騙,并以后次詐騙財(cái)物歸還前次詐騙財(cái)物,在計(jì)算詐騙數(shù)額時(shí),應(yīng)當(dāng)將案發(fā)前已經(jīng)歸還的數(shù)額扣除,按實(shí)際未歸還的數(shù)額認(rèn)定,量刑時(shí)可將多次行騙的數(shù)額作為從重情節(jié)予以考慮。”
第二,犯罪人非法使用、處分的部分應(yīng)當(dāng)計(jì)算在內(nèi)。在詐騙犯罪中犯罪人實(shí)際占有他人款物后,往往有非法處分他人款物的行為,包括個(gè)人的揮霍,為掩蓋詐騙實(shí)質(zhì)而進(jìn)行的虛構(gòu)性的投資經(jīng)營(yíng),付行賄等好處費(fèi)、用于其他違法犯罪活動(dòng),等等,這部分資金應(yīng)當(dāng)計(jì)算在犯罪數(shù)額之內(nèi)。有論者反對(duì)以所得數(shù)額作為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的標(biāo)準(zhǔn),主要理由之一就在于認(rèn)為所得數(shù)額不能包括犯罪人對(duì)集資款非法進(jìn)行使用的部分 .我們認(rèn)為對(duì)于“所得”的理解并不能從字面上狹隘地理解,不能將“所得”只限定為尚未使用處分的占有狀態(tài),行為人占有、使用、處分集資款都是“所得”的當(dāng)然含義,一般地,行為人占有他人財(cái)物,最終目的仍是為了使用、處分,所以,犯罪人非法使用、處分詐騙來的財(cái)物部分應(yīng)認(rèn)定為犯罪數(shù)額,這也是所得數(shù)額所涵蓋的部分。以陳淑蘭、陳淑英集資詐騙案為例,二陳共詐騙金額8877萬元,還本付息6467萬元,其余的2400萬元都被“二陳”用于個(gè)人揮霍,則以2400萬元揮霍用款認(rèn)定“二陳”集資詐騙犯罪所得。
第三,已經(jīng)被行政機(jī)關(guān)單獨(dú)處理過的部分不再計(jì)算。實(shí)踐中,犯罪人在實(shí)施集資詐騙等金融犯罪時(shí)需要一定的時(shí)間,有些還表現(xiàn)為徐行犯、連續(xù)犯等,如果在這一過程中,行為人的一些違法行為已經(jīng)被行政機(jī)關(guān)作為行政違法行為處理過,并進(jìn)行了對(duì)違法所得的追繳。行為人因?yàn)榧Y詐騙等犯罪案發(fā),在未超過追訴時(shí)效的期間內(nèi),其實(shí)施的行為都應(yīng)當(dāng)被追訴,這時(shí)已經(jīng)被行政機(jī)關(guān)處理過的部分是否應(yīng)當(dāng)計(jì)入,有不同的觀點(diǎn),有主張應(yīng)當(dāng)計(jì)入,因?yàn)樾姓幚砼c刑罰處罰性質(zhì)不同。我們認(rèn)為,不應(yīng)當(dāng)再次計(jì)算在內(nèi)。因?yàn)楸M管行政處理在性質(zhì)上不同于刑罰處罰,但都是一種否定的法律評(píng)價(jià),根據(jù)“一行為不再罰”的法理,不應(yīng)當(dāng)對(duì)同一個(gè)違法行為進(jìn)行重復(fù)評(píng)價(jià),所以不應(yīng)再次計(jì)算在內(nèi)。
(二) 在金融詐騙預(yù)備、未遂、中止的情況下
在金融詐騙預(yù)備、未遂、中止的情況下,只有指向數(shù)額最齊備,這時(shí)以指向數(shù)額為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在具體犯罪中,指向數(shù)額有不同的體現(xiàn),如貸款金融詐騙犯罪中體現(xiàn)為行為人申請(qǐng)的貸款數(shù)額,票據(jù)金融詐騙犯罪體現(xiàn)為票面數(shù)額。當(dāng)然,在案件的具體處理中,如果綜合全案,情節(jié)輕微,危害不大的,可以根據(jù)刑法總則的原則規(guī)定,不作為刑事案件立案處理。
二、金融詐騙共同犯罪
在金融詐騙共同犯罪中,如何適用《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中的數(shù)額,也是理論和實(shí)踐上急待解決的問題。因?yàn)樵诮鹑谠p騙共同犯罪中,也存在多個(gè)數(shù)額,如各犯罪人分贓所得的數(shù)額、在實(shí)施犯罪中參與分擔(dān)的數(shù)額、共同犯罪所得的總額等,在理論上對(duì)于這一數(shù)額的認(rèn)定也有分贓數(shù)額說、分擔(dān)數(shù)額說、參與數(shù)額說、犯罪總額說、綜合說等不同的觀點(diǎn),莫衷一是;目前司法實(shí)踐主要參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關(guān)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在第1條中所作的規(guī)定,即“對(duì)共同詐騙犯罪,應(yīng)當(dāng)以行為人參與共同詐騙的數(shù)額認(rèn)定其犯罪數(shù)額,并結(jié)合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數(shù)額等情節(jié)依法處罰。”但在這一司法解釋中,詞義也很模糊:“以行為人參與共同詐騙的數(shù)額認(rèn)定其犯罪數(shù)額”究竟是指參與的共同犯罪總額還是指行為人所實(shí)行的犯罪的數(shù)額,含義不清。如果是指參與的共同犯罪總額,以此作為對(duì)行為人處罰的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有違罪責(zé)自負(fù)和罪刑相適應(yīng)的刑法原則。因?yàn)楦鞴餐缸锶嗽诠餐缸镏械牡匚弧⑺鸬淖饔谩⒕唧w實(shí)施犯罪行為的社會(huì)危害性可能會(huì)不同,如為集資詐騙犯罪提供方便、進(jìn)行幫助的犯罪人與組織并直接實(shí)施集資詐騙的犯罪人在主觀惡性和客觀危害上都有差異,都以犯罪總額作為處罰標(biāo)準(zhǔn),就不能體現(xiàn)出刑罰與所犯罪行相適應(yīng)。如果是指行為人實(shí)行犯罪的數(shù)額,以此作為認(rèn)定犯罪的標(biāo)準(zhǔn)又有不妥。因?yàn)楣餐缸锝^不是各個(gè)犯罪人行為的簡(jiǎn)單相加,在共同犯罪中,盡管各個(gè)行為人分工可能不同,但都圍繞著詐騙這一共同目標(biāo)進(jìn)行活動(dòng),各個(gè)行為人的行為與犯罪結(jié)果之間都存在因果關(guān)系。按照我國(guó)刑法關(guān)于共同犯罪的規(guī)定和共同犯罪理論,毋庸置疑,共同犯罪行為人均為對(duì)犯罪的結(jié)果負(fù)責(zé),而不是只對(duì)各人實(shí)行犯罪的數(shù)額負(fù)責(zé)。否則,共同犯罪與單人犯罪就沒有區(qū)別了。
我們認(rèn)為,解決金融詐騙共同犯罪的數(shù)額認(rèn)定問題,應(yīng)當(dāng)分別定罪和量刑兩種情形(其中定罪上與適用《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有更直接的聯(lián)系)。首先,在認(rèn)定犯罪時(shí),應(yīng)當(dāng)以共同犯罪所得總額作為標(biāo)準(zhǔn),而不應(yīng)當(dāng)以各個(gè)犯罪人所參與實(shí)行的犯罪所得數(shù)額為標(biāo)準(zhǔn)。例如,數(shù)人共同實(shí)施集資詐騙罪,共同犯罪總額達(dá)到“數(shù)額較大”,即所得數(shù)額在10萬元以上,而其每個(gè)人各自實(shí)行的犯罪數(shù)額部分都不夠該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這種情況下對(duì)每個(gè)犯罪人構(gòu)成犯罪,并應(yīng)在“數(shù)額較大”的基本構(gòu)成的法定刑檔次內(nèi)量刑。其次,在對(duì)共犯各犯罪人量刑時(shí),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共同犯罪總額所達(dá)到的量刑幅度和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數(shù)額等情節(jié)綜合考量,依法認(rèn)定。如共同犯罪的數(shù)額達(dá)到“數(shù)額巨大”或“數(shù)額特別巨大”,而每個(gè)共犯實(shí)施犯罪的數(shù)額都不夠“數(shù)額巨大”或“數(shù)額特別巨大”,而僅達(dá)到“數(shù)額較大”或“數(shù)額巨大”,這種情況下對(duì)每個(gè)共犯認(rèn)定犯罪時(shí)都在“數(shù)額巨大”或“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加重構(gòu)成范圍內(nèi)定罪量刑,而不應(yīng)在“數(shù)額較大”或“數(shù)額巨大”的范疇內(nèi)定罪量刑。同時(shí),刑法總則中對(duì)主犯、從犯、脅從犯和教唆犯的處罰原則,都是應(yīng)當(dāng)參照的法定標(biāo)準(zhǔn)和法定依據(jù)。如刑法第26條第3款規(guī)定,“對(duì)組織、領(lǐng)導(dǎo)犯罪集團(tuán)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tuán)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第4款規(guī)定,“對(duì)于第三款規(guī)定以外的主犯,應(yīng)當(dāng)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
「注釋
參見《最高檢、公安部有關(guān)負(fù)責(zé)人就〈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答記者問》[N],載法制日?qǐng)?bào)2001年4月30日第3版
參見趙秉志主編:《侵犯財(cái)產(chǎn)罪研究》[M]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4頁(yè)
第2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一、犯罪成本的含義
關(guān)于犯罪成本,有廣義說和狹義說兩種。廣義說認(rèn)為:犯罪成本是指一個(gè)國(guó)家或社會(huì)在犯罪問題上的所有損失、浪費(fèi)、開支、花銷的總和。而狹義說則認(rèn)為:犯罪成本僅僅指犯罪人因?qū)嵤┓缸锒冻龅奈镔|(zhì)成本,即犯罪者實(shí)施犯罪行為的全部支出,也可稱作個(gè)人成本。![1]
本文所探討的是狹義的犯罪成本,即嫌疑人為實(shí)施犯罪而付出的物質(zhì)成本。多數(shù)犯罪中都需要有成本支出,特別是在詐騙犯罪中,犯罪成本更為常見,其表現(xiàn)形式多樣,如嫌疑人為實(shí)施犯罪購(gòu)買作案工具、偽裝道具、租用場(chǎng)地、交通工具甚至雇傭他人等。詐騙罪以非法獲取他人財(cái)物為目的,嫌疑人為此而付出的經(jīng)濟(jì)成本應(yīng)否從犯罪數(shù)額中扣除呢?本文以詐騙數(shù)額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為基礎(chǔ),圍繞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這一核心,就犯罪成本的扣減問題展開探討。
二、能減輕被害人損失的犯罪成本可以扣減
對(duì)于詐騙罪中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害,目前理論界存在著整體財(cái)產(chǎn)損害說和個(gè)別財(cái)產(chǎn)損害說的對(duì)立。整體財(cái)產(chǎn)損害說認(rèn)為,使用欺騙方法騙取財(cái)物,但同時(shí)交付了相當(dāng)價(jià)值的財(cái)物的,應(yīng)當(dāng)將財(cái)產(chǎn)的喪失與取得作為整體進(jìn)行綜合評(píng)價(jià),被害人財(cái)產(chǎn)的整體并未受到損害的,則不成立詐騙罪,該說以被害人的“凈財(cái)富”損失額度作為詐騙罪能否成立的前提條件。個(gè)別財(cái)產(chǎn)損害說認(rèn)為,財(cái)物因交付而喪失就是財(cái)產(chǎn)損失的內(nèi)容,只要存在個(gè)別的財(cái)產(chǎn)損失就認(rèn)定為財(cái)產(chǎn)損失,即使被害人取得了財(cái)產(chǎn)也對(duì)詐騙罪的成立沒有影響。[2]
在我國(guó),并沒有犯罪成本扣除的相關(guān)規(guī)定,詐騙罪財(cái)產(chǎn)損害數(shù)額的認(rèn)定,刑法理論和實(shí)務(wù)部門爭(zhēng)論較大。綜合考察各家關(guān)于詐騙犯罪數(shù)額認(rèn)定的觀點(diǎn),共有六種:主觀說,所得說,損失說,交付說,雙重標(biāo)準(zhǔn)說,折衷說。[3]在這幾種觀點(diǎn)中,所得說符合個(gè)別財(cái)產(chǎn)說的觀點(diǎn),而損失說符合整體財(cái)產(chǎn)說的觀點(diǎn)。
損失說認(rèn)為應(yīng)以被害人的實(shí)際損失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筆者認(rèn)為此觀點(diǎn)更為可取,因?yàn)閾p失說符合刑法打擊侵財(cái)犯罪保護(hù)公民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本來目的。我國(guó)《刑法》第1條和第2條共同揭示了我國(guó)刑法的目的:保護(hù)法益,法益是指應(yīng)當(dāng)由刑法保護(hù)的利益。犯罪的本質(zhì)是一定的社會(huì)危害性,而社會(huì)危害性的內(nèi)容是對(duì)合法權(quán)益的侵犯。[4]因此,被害人被侵害的法益也就是實(shí)際損失應(yīng)當(dāng)是認(rèn)定詐騙罪犯罪數(shù)額的根本,該損失額表征了詐騙犯罪社會(huì)危害性的嚴(yán)重程度。被害人有實(shí)際的財(cái)產(chǎn)損失,其法益受到侵害,才有成立犯罪的可能性。相反,則無成立犯罪之虞。因此,被害人的實(shí)際財(cái)產(chǎn)損失是衡量詐騙罪是否成立以及量刑輕重的標(biāo)準(zhǔn),損失說是可取的。
既然被害人的實(shí)際損失是認(rèn)定犯罪數(shù)額的標(biāo)準(zhǔn),那么,被害人被詐騙的財(cái)產(chǎn)損失因嫌疑人犯罪成本的支出而部分得到彌補(bǔ),則應(yīng)將該部分被彌補(bǔ)的損失從詐騙數(shù)額中扣除,這才是最終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的定罪量刑的犯罪金額,貫徹了刑法的“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原則。司法解釋[5]的規(guī)定也采納了損失說:其一,詐騙數(shù)額應(yīng)當(dāng)以行為人實(shí)際騙取的數(shù)額認(rèn)定;其二:對(duì)于多次進(jìn)行詐騙,并以后次詐騙財(cái)物歸還前次詐騙財(cái)物的,在計(jì)算詐騙數(shù)額時(shí),應(yīng)當(dāng)將案發(fā)前已經(jīng)歸還的數(shù)額扣除。司法解釋明確了詐騙罪的詐騙數(shù)額就是被害人的實(shí)際損失額,且歸還被害人的財(cái)物應(yīng)當(dāng)扣除,肯定了嫌疑人的犯罪成本可以扣除。
雖然詐騙罪中可以扣減犯罪成本,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成本都要扣除,只有那些能彌補(bǔ)被害人財(cái)產(chǎn)損失的犯罪成本才能扣減。以下,筆者分三個(gè)層次論述可扣減的犯罪成本范圍。
三、可扣除犯罪成本的范圍
(一)犯罪成本應(yīng)交付給被害人或使被害人實(shí)現(xiàn)權(quán)利
嫌疑人的成本中,只有交付給被害人或能使被害人實(shí)現(xiàn)權(quán)利的那部分犯罪成本才能考慮扣減。占有財(cái)產(chǎn)是實(shí)現(xiàn)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的前提和基礎(chǔ),詐騙罪中被害人就是失去了對(duì)財(cái)物的占有和控制才造成損失,所以,嫌疑人的犯罪成本只有被被害人占有和控制,才能減輕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程度,抵消嫌疑人犯罪行為的部分社會(huì)危害性。如典當(dāng)金條案中,嫌疑人將價(jià)值15000元摻有非貴重金屬的金條冒充足金金條,典當(dāng)30000元,該金條具有一定的價(jià)值,能減輕被害人的損失,在認(rèn)定嫌疑人的詐騙金額時(shí)應(yīng)扣減15000元的成本。
除了直接交付給被害人的犯罪成本,還有一些雖然沒有直接交付給被害人,但代替被害人履行了部分義務(wù),使被害人減輕了財(cái)產(chǎn)損失,也應(yīng)從詐騙金額中扣減。如嫌疑人支付3個(gè)月租金租一套公寓,后以房東的名義租給被害人,并收取六個(gè)月房租。該案中,嫌疑人支付的3個(gè)月房租使被害人實(shí)現(xiàn)了3個(gè)月的住房需求,這3個(gè)月的租金應(yīng)當(dāng)從被害人的被騙數(shù)額中相應(yīng)扣減。
(二)可扣除的犯罪成本在客觀上應(yīng)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
在形式多樣的詐騙案件中,犯罪成本也以不同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因此,必須區(qū)分嫌疑人付出的犯罪成本是否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沒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犯罪成本不能減小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不在扣減之列。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判斷以財(cái)物本身的屬性為基礎(chǔ),以一般人的認(rèn)識(shí)能力為判斷準(zhǔn)則,凡是能夠在社會(huì)上流通和交換,具有市場(chǎng)價(jià)值的都應(yīng)認(rèn)為有客觀價(jià)值。如典當(dāng)金條案中,嫌疑人交給典當(dāng)行的金條具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能夠減少典當(dāng)行的經(jīng)濟(jì)損失,應(yīng)當(dāng)從予以扣減。
有成本價(jià)的物品不一定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嫌疑人在詐騙過程中提供的某些物品雖然也需付出成本價(jià),但卻不能進(jìn)入市場(chǎng)流通和交換,在客觀上沒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不能減輕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如嫌疑人謊稱以某國(guó)家級(jí)機(jī)構(gòu)的名義評(píng)獎(jiǎng),要求被害人繳納若干費(fèi)用,被害人得到了獎(jiǎng)杯和證書以及所謂的國(guó)家級(jí)榮譽(yù)。這些獎(jiǎng)杯和證書的制作雖有成本價(jià),但不具有使用價(jià)值和交換價(jià)值,對(duì)被害人來講與廢品無異,不能減輕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因此該成本不能從犯罪金額中扣減。再如,嫌疑人謊稱被害人家中有災(zāi),為其做法事、念經(jīng),并交給被害人一些所謂消災(zāi)避邪的“法物”,這些“法物”沒有市場(chǎng)價(jià)值,無法用金錢來衡量,因此也不能抵消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
(三)可扣除的犯罪成本對(duì)被害人有主觀價(jià)值
主觀價(jià)值的判斷以被害人的利用目的為標(biāo)準(zhǔn)。嫌疑人交付給被害人的犯罪成本如果有可能被被害人利用,對(duì)被害人有價(jià)值,則該部分犯罪成本可在詐騙金額中扣減。主觀價(jià)值的判斷應(yīng)以具體被害人的個(gè)人情況為基礎(chǔ),同樣的財(cái)物對(duì)不同的人意義不同,利用可能性也完全不一樣。但判斷時(shí)也應(yīng)參酌一般人對(duì)財(cái)物的利用、使用情況。
如夏某與白某合伙低價(jià)購(gòu)買《中國(guó)政府全書》、《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新編勞動(dòng)人事政策法規(guī)全書》等書,然后以市委紀(jì)律檢查委員會(huì)、市勞動(dòng)和社會(huì)保障局等名義,向多個(gè)街道辦事處、鄉(xiāng)政府等單位推銷。夏某與白某按定價(jià)出賣了書,但是被害單位并不需要這些書,只是不得已接受上級(jí)單位攤派才購(gòu)買。這些書對(duì)被害單位并無利用可能性,所以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被害單位存在財(cái)產(chǎn)損失。再如,嫌疑人以義診的名義在小區(qū)為老年人看病,謊稱多名老年人頸椎、腰椎等有病,讓老年人購(gòu)買其攜帶的按摩治療儀,但有些老年人未患該病,并不需要治療儀。雖然治療儀有一定市場(chǎng)價(jià)值,但因?qū)Ρ缓θ藷o主觀價(jià)值,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已經(jīng)造成。
上述3個(gè)案例中,嫌疑人交付給被害人的財(cái)物都有市場(chǎng)價(jià)值,但由于這些財(cái)物對(duì)被害人沒有主觀價(jià)值,不能減輕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損失,所以這些犯罪成本不能從詐騙金額中扣減。
綜上,關(guān)于詐騙罪犯罪成本的扣減問題,筆者的結(jié)論是:嫌疑人實(shí)施詐騙行為時(shí),交付給被害人的有客觀經(jīng)濟(jì)價(jià)值且對(duì)被害人有主觀價(jià)值的犯罪成本可以從犯罪數(shù)額中扣減。
注釋:
[1]參見張福成:《經(jīng)濟(jì)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載《公安學(xué)刊》2004年第4期。
[2]參見朱志斌:《論誘價(jià)概念在詐騙罪中的獨(dú)立性價(jià)值》,載《刑事法雜志》2012年第8期。
[3]參見丁天球:《侵犯財(cái)產(chǎn)罪重點(diǎn)疑點(diǎn)難點(diǎn)問題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38 頁(yè)。
[4]張明楷:《新刑法與法益侵害說》,載《法學(xué)研究》2000年第1期。
第3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構(gòu)成詐騙罪是不是一定要有財(cái)產(chǎn)損害的存在,不同國(guó)家的刑法存在分歧。有些國(guó)家明文規(guī)定必須要有存在財(cái)產(chǎn)損失,如德國(guó)的刑法中則規(guī)定,這種行為要使他人陷于錯(cuò)誤中,因而損害其財(cái)產(chǎn)才可以成立詐騙罪。但有些國(guó)家則沒有這方面的要求,如日本刑法僅規(guī)定欺騙并使他人交付財(cái)物的或者獲取財(cái)產(chǎn)上的違法利益,或者使他人獲取的,成立詐騙罪。盡管我國(guó)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未將財(cái)產(chǎn)損失作為詐騙罪成立的要件,但條款中表明了了數(shù)額較大的這個(gè)要件,通常我們就認(rèn)為這是導(dǎo)致了被害人數(shù)額較大的財(cái)產(chǎn)損失了。所以能夠認(rèn)定,財(cái)產(chǎn)損失是財(cái)產(chǎn)法益被侵犯的表現(xiàn),最少應(yīng)該是不成文性質(zhì)的構(gòu)成要件因素。
二、財(cái)產(chǎn)法益界定
既然要有財(cái)產(chǎn)損失的存在,那就要明確界定財(cái)產(chǎn)。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刑法的理論中主要存在三種學(xué)說:經(jīng)濟(jì)的財(cái)產(chǎn)說、法律的財(cái)產(chǎn)說和折中說。法律的財(cái)產(chǎn)說的理論中,所有的財(cái)產(chǎn)犯罪都對(duì)財(cái)產(chǎn)方面的權(quán)利造成了侵害,刑法之所以規(guī)定財(cái)產(chǎn)罪是對(duì)民法上的權(quán)利進(jìn)行保護(hù)。因?yàn)樗鲝埿谭▽儆诿袷路桑?0 世紀(jì)30 年代開始,人們不再認(rèn)為刑法屬于民事法律,而這一理論基本上已經(jīng)沒有人支持。經(jīng)濟(jì)的財(cái)產(chǎn)說理論中,財(cái)產(chǎn)是一個(gè)利益總體,具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因此它是財(cái)產(chǎn)犯罪所保護(hù)的法益;經(jīng)濟(jì)價(jià)值與金錢價(jià)值劃上了等號(hào),金錢的收益和損失是判斷損害是否存在的標(biāo)準(zhǔn)。侵犯了具有金錢價(jià)值的利益,并且導(dǎo)致總體價(jià)值的降低,才存在刑法所說的損害。刑法的獨(dú)立性越來越受到重視,一度使經(jīng)濟(jì)的財(cái)產(chǎn)說成為有力學(xué)說,但這仍然難以被人接受。將法律與秩序的統(tǒng)一、實(shí)質(zhì)主義和結(jié)果無價(jià)值的理論作為基本理念,折中說則認(rèn)定財(cái)產(chǎn)是受法律秩序所保護(hù)或不受其駁詰并且有經(jīng)濟(jì)上的價(jià)值的利益總體。刑法中的法益不是民法上的法益,但也不是不受民法的非法利益。在我國(guó),我們面臨著對(duì)這種保護(hù)利益的認(rèn)識(shí)的轉(zhuǎn)型。在過去,許多學(xué)者覺得,詐騙罪是對(duì)公有、私有財(cái)產(chǎn)的所有權(quán)的侵害。事實(shí)上這是一種法律的財(cái)產(chǎn)說。但自20 世紀(jì)30 年代以來,人們已不認(rèn)為刑法屬于民事法律,這一理論已經(jīng)失去了理論基礎(chǔ),基本已經(jīng)沒有人支持。令人關(guān)注的是,在司法解釋中,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對(duì)設(shè)置圈套誘騙他人參賭又向索還錢財(cái)?shù)氖茯_者施以暴力或暴力威脅的行為應(yīng)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fù)》(1995 年11 月6日)同意設(shè)置圈套誘騙他人參賭獲取錢財(cái)者,成立賭博罪而非詐騙罪。這里所采的不是純粹的經(jīng)濟(jì)財(cái)產(chǎn)說。而對(duì)非法獲得的財(cái)物,比如甲偷了乙的手機(jī),如果丙又去偷了甲偷取的手機(jī),丙也成立詐騙罪。而如果乙將被偷的手機(jī)偷回,因?yàn)橐也皇腔诜欠ㄕ加械哪康模砸也粦?yīng)構(gòu)成詐騙罪。但是對(duì)于和槍支彈藥等違禁物品的占有則不應(yīng)用詐騙罪加以保護(hù),因?yàn)閷?duì)此類違禁物品的持有和出賣都是能夠處罰的。假如從非法持有者或出賣者手里騙得違禁物品構(gòu)成詐騙罪,那么會(huì)出現(xiàn)刑法也在懲罰犯罪的同時(shí)也在縱容犯罪。同樣,對(duì)違法交易的金錢的主張,也無法得到刑法的支持。綜上,較之經(jīng)濟(jì)的財(cái)產(chǎn)說,法律的、經(jīng)濟(jì)的財(cái)產(chǎn)說更為可取。
三、捐款、補(bǔ)助詐騙分類和財(cái)產(chǎn)損失的認(rèn)定
雖然折中說被多數(shù)學(xué)者支持,但是這一理論在面對(duì)特定的某些詐騙案件時(shí),有時(shí)仍顯得心余力絀。而捐款、補(bǔ)助詐騙案件就是一類可以促進(jìn)折中說改良的特定案件。首先,一般的詐騙案件,大多是經(jīng)濟(jì)業(yè)務(wù)上的往來這一類。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均基于獲得經(jīng)濟(jì)上相稱的對(duì)待的目的,是以,只要對(duì)照財(cái)產(chǎn)處分前后的大體情況,可以發(fā)現(xiàn),財(cái)產(chǎn)損失即表現(xiàn)為財(cái)產(chǎn)價(jià)值的減少。在此種情境下,不管采取何種學(xué)說,通常不會(huì)有結(jié)果上的差異。而經(jīng)典的捐款、補(bǔ)助案件就是單方面地給以財(cái)物。比如,德國(guó)一高等法院曾經(jīng)審理過一起這樣案子:被告人在募捐時(shí),向被害人出示了假造的別人的捐獻(xiàn)數(shù)額的清單,以此激發(fā)被害人的攀比欲,被害人果然捐獻(xiàn)大量金錢(攀比捐款案)。法院判決,這個(gè)案子構(gòu)成詐騙罪,因?yàn)楸缓θ擞胸?cái)產(chǎn)損失,假如被告人沒有出示該清單,被害人將不付出如此高額的款額。這個(gè)判決以經(jīng)濟(jì)的財(cái)產(chǎn)說為基礎(chǔ),主流學(xué)說的支持者們幾乎一致反對(duì)。
例如,德國(guó)的學(xué)者拉克內(nèi)則認(rèn)為,財(cái)產(chǎn)所有權(quán)人的攀比欲是不受詐騙罪保護(hù)的,被害人在此案中完全是自我負(fù)責(zé)的。所以,只有款項(xiàng)未被用于救濟(jì)目的,而被被告人占有,即它的客觀目的未能實(shí)現(xiàn),繼而使客觀上這種捐款行為的意義落空,詐騙罪才成立。這就是德國(guó)的客觀目的論(Zweckverfehlungslehre)。根據(jù)這種理論,即便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的價(jià)值有所減少,也不一定不成立詐騙罪,因?yàn)檫@種減少對(duì)被害人來說是意料中的,惟有當(dāng)捐款的客觀目的沒有實(shí)現(xiàn)時(shí),才能否定被害人的自我負(fù)責(zé),繼而認(rèn)為詐騙罪成立。如此,詐騙罪的財(cái)產(chǎn)損失就不僅是單純的經(jīng)濟(jì)上的價(jià)值的減少,此時(shí),再采取經(jīng)濟(jì)的財(cái)產(chǎn)說就很難解釋通。我國(guó)刑法學(xué)界,也有學(xué)者這樣認(rèn)為。還有一種新的案件,是當(dāng)捐款、補(bǔ)助的詐騙和經(jīng)濟(jì)業(yè)務(wù)結(jié)合時(shí)出現(xiàn)的混合類型的案件。例如,被告人通過銷售明信片并且在明信片上提醒本次銷售會(huì)將過半的收入捐給眼疾患者。但實(shí)際上,被告將收入都收入囊中,不曾捐獻(xiàn)。被告人被起訴后,稱明信片價(jià)格與市價(jià)符合。這樣的情況下,盡管確實(shí)有募捐的意思表示,但明信片的購(gòu)買者沒有承擔(dān)任何經(jīng)濟(jì)損失,德國(guó)學(xué)界大多認(rèn)為,純粹的處分自由不是詐騙罪保護(hù)的法益,財(cái)產(chǎn)才是。在沒有財(cái)產(chǎn)損失的情況下,不適用客觀目的理論,而由被害人自己承擔(dān)不利后果,不以詐騙罪論。但是,假如明信片的價(jià)格顯著高于市場(chǎng)價(jià)格,那么超過的價(jià)格成立詐騙罪。在我國(guó),因?yàn)閿?shù)額到不了入罪門檻,幾張明信片當(dāng)然不會(huì)成立詐騙罪。但如果碰到轉(zhuǎn)移數(shù)額較大的財(cái)物時(shí),完全有可能在案件中使用這一理論。比如,演唱會(huì)舉辦方宣稱將演唱會(huì)的所以收入捐給慈善組織,但觀眾買票后,舉辦方卻將收入占為己有(演唱會(huì)案)。就這個(gè)案件而言,我國(guó)學(xué)者指出主辦者欺騙觀眾收益將捐獻(xiàn)給慈善機(jī)構(gòu),觀眾因公益目的而購(gòu)買門票,主辦者卻將收入占為己有,沒有為觀眾實(shí)現(xiàn)公益目的,所以主辦者的行為構(gòu)成詐騙罪。然而,一概構(gòu)成詐騙罪,這種做法要先權(quán)衡經(jīng)濟(jì)上的得失。只有經(jīng)濟(jì)損失必定存在,才能運(yùn)用客觀目的論得以成立。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這種一概成立詐騙罪的處理辦法是不合理的:要是演唱會(huì)門票的價(jià)格明顯低于正常市場(chǎng),而且演出的十分熱門的歌手,出錢聽一場(chǎng)這樣的演唱會(huì)對(duì)觀眾來說完全符合成本效益的,即使有個(gè)別觀眾出于慈善的目的購(gòu)票,但絕大部分觀眾并不存在認(rèn)識(shí)上的錯(cuò)誤,而是理性消費(fèi)。在這種理性消費(fèi)情況下,如果這些觀眾僅遭受較小的經(jīng)濟(jì)損失,則在我國(guó)的體系下成立詐騙罪是完全可以否定的。反之,如果把這類理性消費(fèi)認(rèn)定為詐騙罪,那么刑法會(huì)不謙抑,詐騙罪的保護(hù)法益也成了單純的處分自由。
第4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關(guān)鍵詞:集資詐騙 犯罪原因 防控
2007年,犯罪嫌疑人劉某、殷某以做茶油生意需大量資金為名,許諾月息2%到20%,向120余人非法集資2800余萬元。2010年4月,法院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劉某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cái)產(chǎn)五十萬元,判處被告人殷某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十萬元。筆者擬以劉某、殷某集資詐騙犯罪案件為藍(lán)本,分析集資詐騙案件的特點(diǎn)、發(fā)案原因,并對(duì)如何有效防控該類案件,提出自己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集資詐騙犯罪案件的特點(diǎn)
1.涉案金額巨大,損失一般難以挽回。集資詐騙的涉案金額往往比一般的經(jīng)濟(jì)犯罪要大的多,并且犯罪嫌疑人將集資詐騙得來的款項(xiàng)大部分或者全部用于個(gè)人揮霍,導(dǎo)致涉案款物難以追繳。如本案中涉案金額高達(dá)2800多萬元,相當(dāng)于當(dāng)時(shí)案發(fā)所在國(guó)家級(jí)貧困縣財(cái)政收入的1/5。其中除了返還給集資人部分本息及購(gòu)買庫(kù)存茶油外,大部分都被兩被告人用于購(gòu)買住房、高檔轎車和其他個(gè)人開支,導(dǎo)致1400多萬元難以歸還給受害人。
2.受害人數(shù)眾多,中老年人受騙突出。由于集資詐騙的對(duì)象是不特定多數(shù)人,一件案件往往涉及眾多受害人。如本案中兩被告人先后向120余人非法集資,共打出了200多張借條。另外,從集資詐騙對(duì)象的年齡來看,以45歲左右中老年人居多,其中既有個(gè)體戶,也有企事業(yè)單位職工和少數(shù)黨政干部。這類人員往往具有一定積蓄和經(jīng)濟(jì)能力,防騙意識(shí)薄弱,對(duì)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違法犯罪活動(dòng)了解不多,易被表面假象所迷惑,基本上沒有考慮投資風(fēng)險(xiǎn),從而給不法之徒可乘之機(jī)。
3.作案方式誘惑性大,隱蔽性和欺騙性強(qiáng)。該類案件犯罪嫌疑人通常利用人們追求高額投資回報(bào)心理,采用欺騙的方法獲取受害人信任,讓受害人相信其還款能力,致使一般民眾很難判斷其真假,從而使受害人步入其“圈套”。有的犯罪嫌疑人隱匿真實(shí)身份,有的通過虛構(gòu)業(yè)務(wù)項(xiàng)目,有的虛假?gòu)V告,贏得好感、騙取信任,同時(shí)承諾低投入高回報(bào),獲得集資款,然后采取后續(xù)集資款支付前期集資款利息的“拆東墻補(bǔ)西墻”方式兌現(xiàn)承諾,一旦資金鏈一斷或?qū)⒁獢啵R上逃匿。如本案中的被告人劉某就對(duì)受害人謊稱自己是湖南某茶油廠副董事長(zhǎng),并先期組織部分投資人到某茶油廠考察,通過這些假象,騙取受害人信任。而另一被告人殷某明知?jiǎng)⒛吃谕顿Y茶油生意過程中虧損,購(gòu)買的綠海茶油及好恰茶油均未銷售出去,并無盈利收入的情況下,仍偽造與寶鋼后勤保障部等大型單位簽訂了大量供應(yīng)茶油的合同、印章,虛構(gòu)銷售茶油的事實(shí)。在兩人獲得受害人的信任后,以做“茶油生意”急需資金周轉(zhuǎn)為由,以月息2%到20%不等分紅或高利息的方式向受害人借款。
4.作案時(shí)間長(zhǎng),社會(huì)危害大,容易引發(fā)。由于該類案件往往要經(jīng)歷犯罪嫌疑人產(chǎn)生犯意、選擇作案方法,到取得受害人的信任、獲取大額資金、資金鏈斷裂等過程,大多數(shù)集資詐騙案件作案時(shí)間超過1年,有的持續(xù)時(shí)間長(zhǎng)達(dá)3—5年。由于受害人員多,涉案金額大,損失一般難以挽回,處置及善后工作難度較大,案件一旦發(fā)生,給人民群眾的正常生產(chǎn)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嚴(yán)重影響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安全和社會(huì)穩(wěn)定。如本案中兩被告人在長(zhǎng)達(dá)3年多的時(shí)間里非法集資2800多萬元,由于有1400多萬元難以歸還給受害人,導(dǎo)致受害人經(jīng)常聚集到公安機(jī)關(guān)上訪,引發(fā)群體性上訪事件。
二、集資詐騙案件多發(fā)的原因
1.受害群眾法律意識(shí)淡薄,具有貪財(cái)和盲目的心理。部分受害群眾不能正確辨別合法與非法、違法與犯罪的界限,都希望尋找到一種投資快、成效大的投資模式,在求富心理的驅(qū)動(dòng)下,一見到高利率的誘惑就盲目產(chǎn)生投機(jī)行為。有的受害人為貪財(cái),明知是騙局也故意參與,充當(dāng)非法集資活動(dòng)的“幫兇”。
2.政府相關(guān)部門監(jiān)管不力,信息資源共享不夠。政府金融監(jiān)督、工商管理等部門對(duì)非法集資犯罪的社會(huì)控制力不高,對(duì)市場(chǎng)監(jiān)管存在漏洞。如由于工商部門對(duì)公司的設(shè)立條件審查不嚴(yán),使得不法分子得以披上合法外衣進(jìn)行集資詐騙活動(dòng)。同時(shí),由于相關(guān)部門溝通不夠、信息傳遞不及時(shí),缺乏統(tǒng)一的協(xié)調(diào)、配合,未能及時(shí)取締和打擊集資詐騙行為,直到給群眾造成的損失不斷擴(kuò)大,達(dá)到構(gòu)成刑事犯罪標(biāo)準(zhǔn)后,犯罪分子才受到打擊。
3.司法認(rèn)定存在分歧,影響打擊效果。司法實(shí)踐中,集資詐騙案件案情復(fù)雜,加上集資詐騙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并不明朗,部分辦案人員難以準(zhǔn)確劃清集資詐騙案件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比如對(duì)非法集資與合法融資的界限認(rèn)識(shí)不一,難以準(zhǔn)確認(rèn)定非法集資行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又比如存在將集資詐騙行為混淆為合法借貸或者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的現(xiàn)象,等等。這種認(rèn)識(shí)上的分歧,使得辦案人員不能在第一時(shí)間掌握集資詐騙犯罪事實(shí),準(zhǔn)確打擊集資詐騙犯罪,削弱了打擊此類犯罪的威懾作用。
三、防控集資詐騙犯罪的對(duì)策
1.提高執(zhí)法能力,加大打擊力度。及時(shí)學(xué)習(xí)新進(jìn)頒布的法律法規(guī)和司法解釋,提高準(zhǔn)確認(rèn)定集資詐騙案件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能力。特別是要注意準(zhǔn)確界定集資詐騙罪的“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應(yīng)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認(rèn)真分析借款人無法返還的原因,避免僅憑被告人自己的供述,將集資詐騙罪簡(jiǎn)單認(rèn)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等相對(duì)較輕的罪名,做到不枉不縱。同時(shí),從重打擊那些給受害人造成巨大損失無法挽回、對(duì)當(dāng)?shù)亟?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造成重大影響的集資詐騙案件,提高刑罰威懾力,遏制該類犯罪的發(fā)生。
2.加強(qiáng)法制宣傳,引導(dǎo)公眾增強(qiáng)風(fēng)險(xiǎn)防范意識(shí)。在做好打擊該類犯罪案件的同時(shí),更加注重做好預(yù)防犯罪工作。結(jié)合集資詐騙典型案例,在電視臺(tái)、報(bào)紙等新聞媒體預(yù)防集資詐騙犯罪公告,加強(qiáng)輿論宣傳,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增強(qiáng)人民群眾的投資風(fēng)險(xiǎn)意識(shí)、防范犯罪能力,切實(shí)維護(hù)好自身權(quán)益。
第5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合同詐騙罪立案標(biāo)準(zhǔn)的第2種情形,“單位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以單位名義實(shí)施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數(shù)額在5萬元至20萬元以上的”,應(yīng)當(dāng)立案追究。
根據(jù)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guān)于經(jīng)濟(jì)犯罪案件追訴標(biāo)準(zhǔn)的規(guī)定》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duì)方當(dāng)事人財(cái)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yīng)予追訴:
1.個(gè)人詐騙公私財(cái)物,數(shù)額在5000元至2萬元以上的;
2.單位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以單位名義實(shí)施詐騙,詐騙所得歸單位所有,數(shù)額在5萬元至20萬元以上的。
合同詐騙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設(shè)的罪名。
刑法第224條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duì)方當(dāng)事人財(cái)物,數(shù)額較大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shù)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yán)重情節(jié)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cái)產(chǎn):
(1)以虛構(gòu)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2)以偽造、變?cè)臁⒆鲝U的票據(jù)或者其他虛假的產(chǎn)權(quán)證明作擔(dān)保的;
(3)沒有實(shí)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duì)方當(dāng)事人繼續(xù)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對(duì)方當(dāng)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yù)付款或者擔(dān)保財(cái)產(chǎn)后逃匿的;
第6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關(guān)鍵詞:金融機(jī)構(gòu);新型詐騙;犯罪特點(diǎn);防范措施
一、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的主要分類
現(xiàn)階段,我國(guó)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所出現(xiàn)的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類型相對(duì)較多,可從詐騙技術(shù)手段、冒充身份、犯犯罪嫌疑人、實(shí)施方式等方面分類。比如,根據(jù)詐騙嫌疑人所在地,可將其分為這樣兩種:第一種,在境外借助網(wǎng)絡(luò)電話的形式詐騙。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團(tuán)伙在非洲、東南亞、歐洲等地設(shè)置詐騙窩點(diǎn),從大陸招收大量話務(wù)員,借助網(wǎng)絡(luò)渠道和公眾取得聯(lián)系,并冒充公檢部門的工作人員,虛構(gòu)事實(shí),獲得公眾信任,從而實(shí)施詐騙。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這種類型的案件占全部詐騙案件的22.0%左右,但經(jīng)濟(jì)損失占全部損失的62.0%;第二種,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團(tuán)伙在自己生活的鄉(xiāng)鎮(zhèn),借助短信、電話的形式向全國(guó)公眾實(shí)施詐騙。這種類型的詐騙具備相對(duì)顯著的地域性,占全部詐騙案件的80.0%左右,經(jīng)濟(jì)損失占全部損失的41.0%。
二、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頻發(fā)的原因
1.受害人防范意識(shí)不足
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發(fā)生率的提高、成功詐騙率的提高和受害人防范意識(shí)不足相關(guān),從犯罪心理學(xué)角度來講,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是可以有效預(yù)防的,只需受害人充分了解詐騙手段,就能有效預(yù)防詐騙案件的發(fā)生。但從實(shí)際情況來講,盡管相應(yīng)部門做好了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的宣傳和防范工作,比如:通過媒體宣傳的方式對(duì)涉及詐騙的號(hào)碼實(shí)施停機(jī)處理,這種方式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最終結(jié)果并不理想。一般來講,詐騙分子詐騙手段千變?nèi)f化,單純性的防范宣傳是無法趕上詐騙手段變化速度的。同時(shí),公安機(jī)關(guān)還存在單打獨(dú)斗的情況,無法調(diào)動(dòng)各力量參與其中,影響最終的防范結(jié)果。
2.案件偵破打擊效果不佳
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案件偵破普遍存在技術(shù)不合理、查證困難等情況,再加上相應(yīng)部門協(xié)作機(jī)制相對(duì)滯后,無法形成相對(duì)合理、有效的打擊能力,間接增加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發(fā)生率,主要包括這樣幾種:①主動(dòng)破案意識(shí)薄弱。因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的特殊性,多為跨地域作案,具有犯罪手法變化快速、空間跨度大等特征,任何一起詐騙案件需很長(zhǎng)的時(shí)間偵破,線索的取證工作相對(duì)困難,需投入相對(duì)較多的人力、物力,甚至需輾轉(zhuǎn)多個(gè)國(guó)家,雖工作時(shí)間相對(duì)較長(zhǎng),但最終的效果并不理想,導(dǎo)致各公安部門習(xí)慣性的將優(yōu)勢(shì)資源放在相對(duì)較大的案件上,對(duì)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案件存在不愿打擊心理;②未形成部門共同治理模式。公安部門在打擊犯罪過程中未充分結(jié)合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造成犯罪案件的偵破工作處于被動(dòng)狀態(tài)。公安部門在發(fā)現(xiàn)受害人后,賬戶凍結(jié)的處理時(shí)間相對(duì)較長(zhǎng),無法在第一時(shí)間凍結(jié)相應(yīng)賬戶,增加資金的流失總量;通信部門接收到公安部門提供的信息后,未及時(shí)處理、回應(yīng)相關(guān)問題,導(dǎo)致公安部門無法及時(shí)、快速的找尋犯罪窩點(diǎn),間接增加犯罪率。
3.犯罪成本、刑罰成本不相稱
①低成本。所謂的低成本主要表現(xiàn)為這樣幾個(gè)方面:一方面,經(jīng)濟(jì)成本低。現(xiàn)階段,大多數(shù)的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分子借助電腦、手機(jī)等工具作案,這些工具購(gòu)買價(jià)格相對(duì)較低,所獲得的經(jīng)濟(jì)效益也比較低;另一方面,犯罪懲罰成本低。網(wǎng)絡(luò)詐騙不存在犯罪現(xiàn)場(chǎng)證據(jù),加大偵破取證難度,降低案件偵破、犯罪分子抓獲率;②高回報(bào)。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具備作案手段集團(tuán)化、隱蔽性特征,致使網(wǎng)絡(luò)詐騙犯罪發(fā)生率明顯高于相對(duì)傳統(tǒng)的搶劫率,促使諸多犯罪分子使用自認(rèn)為安全的手段作案。
4.部門監(jiān)管不力
伴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使電信行業(yè)在管理、經(jīng)營(yíng)等方面相對(duì)落后,存在大量問題。再加上日常經(jīng)營(yíng)中過于追求經(jīng)濟(jì)效益,缺乏責(zé)任心,從某種程度上提高犯罪率。一般來講,部門的O管不力主要表現(xiàn)為這樣幾點(diǎn):第一點(diǎn),電信部門監(jiān)管不到位。在新型技術(shù)、新型應(yīng)用大力推廣的過程中,未充分考慮安全因素,導(dǎo)致典型網(wǎng)絡(luò)電話成為虛假信息的主要渠道。并且,手機(jī)卡實(shí)名制未落實(shí)到底。用戶在購(gòu)買手機(jī)卡時(shí),通常不用自己身份證開具,或直接在街頭、網(wǎng)絡(luò)購(gòu)買不記名的手機(jī)卡;第二點(diǎn),互聯(lián)網(wǎng)監(jiān)管不到位。先進(jìn)技術(shù)的發(fā)展在提高國(guó)民經(jīng)濟(jì)水平的同時(shí),也給犯罪團(tuán)隊(duì)提供相對(duì)較多的工具,犯罪分子在淘寶商店中購(gòu)買大量犯罪工具,或借助現(xiàn)有工具開發(fā)屬于自己的工具詐騙。同時(shí),網(wǎng)絡(luò)實(shí)名制未落實(shí)到底,造成門戶網(wǎng)站、論壇等存在大量欺詐性的信息,為詐騙活動(dòng)的開展提供便利。
三、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防范新型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的措施
為更好地識(shí)別、控制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維護(hù)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聲譽(yù),為客戶提供相對(duì)安全、高效的服務(wù)透析,應(yīng)根據(jù)網(wǎng)絡(luò)詐騙的實(shí)際情況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在降低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發(fā)生率的同時(shí),實(shí)現(xiàn)最終的防范目的。
1.樹立反欺詐理念
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經(jīng)營(yíng)過程中,對(duì)各業(yè)務(wù)、管理?xiàng)l線詐騙交易進(jìn)行監(jiān)測(cè)、調(diào)查,建立機(jī)構(gòu)內(nèi)部的風(fēng)險(xiǎn)報(bào)告制度、詐騙監(jiān)測(cè)預(yù)警機(jī)制,將各業(yè)務(wù)產(chǎn)品作為基礎(chǔ),以實(shí)現(xiàn)最終的詐騙預(yù)警目的。同時(shí),還需根據(jù)金融機(jī)構(gòu)的實(shí)際情況評(píng)估詐騙預(yù)防情況。
2.加大宣傳力度,強(qiáng)化防詐騙意識(shí)
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可借助宣傳欄、顯示屏等宣傳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風(fēng)險(xiǎn),按時(shí)或不按時(shí)的在重要場(chǎng)所、集市等開展宣講活動(dòng),提醒客戶這種詐騙的表現(xiàn)形式、詐騙的潛在性風(fēng)險(xiǎn)。并且,還可借助防詐騙手冊(cè)發(fā)放的形式幫助客戶更好的了解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類型、防范重要性,以提高客戶的防詐騙能力。
3.加大金融機(jī)構(gòu)員工防詐騙培訓(xùn)力度
要想從根本上預(yù)防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的發(fā)生,應(yīng)加大基層金融機(jī)構(gòu)員工的培訓(xùn)力度,主要表現(xiàn)為:培訓(xùn)金融機(jī)構(gòu)員工的基礎(chǔ)性的金融業(yè)務(wù),培訓(xùn)金融機(jī)構(gòu)管理人員相應(yīng)制度,以反詐騙、法律法規(guī)為主。另外,加大金融機(jī)構(gòu)業(yè)務(wù)人員的教育、培訓(xùn)力度,比如:根據(jù)業(yè)務(wù)人員的工作職責(zé)、工作崗位進(jìn)行信用卡、貸款欺詐的識(shí)別和預(yù)防;開展重點(diǎn)培訓(xùn)活動(dòng),對(duì)不同時(shí)期的突發(fā)詐騙行為進(jìn)行反欺詐培訓(xùn)。
4.打擊網(wǎng)絡(luò)黑產(chǎn)源頭
現(xiàn)階段,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的主要源頭是編寫釣魚網(wǎng)站代碼的黑客,其處于犯罪金字塔最頂端,雖人數(shù)少,但卻能影響整個(gè)網(wǎng)絡(luò)產(chǎn)業(yè)鏈,可從這樣幾點(diǎn)進(jìn)行:第一點(diǎn),建立網(wǎng)絡(luò)黑產(chǎn)數(shù)據(jù)庫(kù)。目前,網(wǎng)絡(luò)黑產(chǎn)商業(yè)化已處于成熟階段,黑客們存在相對(duì)復(fù)雜、精巧的產(chǎn)業(yè)鏈,無法估測(cè)黑產(chǎn)網(wǎng)絡(luò)規(guī)模。針對(duì)這種情況,國(guó)家政府應(yīng)盡快了解網(wǎng)絡(luò)組織結(jié)構(gòu),掌握黑客的主要來源、聯(lián)系方式、從事行業(yè)等;建立網(wǎng)絡(luò)數(shù)據(jù)庫(kù),以在全面掌握黑產(chǎn)情況的同時(shí),幫助公安部門更好打擊犯罪團(tuán)伙;第二點(diǎn),引導(dǎo)黑客轉(zhuǎn)型。現(xiàn)階段,因大多數(shù)黑客在社會(huì)中找不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再加上學(xué)歷、年齡等因素的影響,得不到社會(huì)認(rèn)可。因此,國(guó)家政府應(yīng)根據(jù)網(wǎng)絡(luò)的發(fā)展情況建立人才的吸引機(jī)制,將其引導(dǎo)到相對(duì)正常的生活軌道上,便于成立紅色黑客組織,共同對(duì)抗黑客,加快黑客的轉(zhuǎn)型速度。
此外,還需完善立法。從立法層面著手,適當(dāng)修改相關(guān)規(guī)定,將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從犯罪案件分離出,并將其納入社會(huì)管理秩序罪中,降低網(wǎng)絡(luò)詐騙的入刑門檻,增加電信網(wǎng)絡(luò)犯罪成本,提高法律威懾力;完善和電信網(wǎng)絡(luò)詐騙相關(guān)的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加大金融機(jī)構(gòu)監(jiān)管機(jī)制的建設(shè)力度,強(qiáng)化筋肉機(jī)構(gòu)的法律責(zé)任。比如:針對(duì)手機(jī)號(hào)碼不實(shí)名制的問題,應(yīng)在相應(yīng)條例中規(guī)定手機(jī)號(hào)碼開具用戶提供真實(shí)信息,明確設(shè)定未履行義務(wù)的處罰措施,促使金融機(jī)構(gòu)員工、公眾自覺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
第7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關(guān)鍵詞:詐騙罪;犯罪既遂;失控說
關(guān)于詐騙罪既遂的問題古老而又常青,兩大法系各國(guó),尤其是德日兩國(guó)的學(xué)者因?yàn)榉ㄖ蜗刃卸鴮?duì)此問題研究已較為深入,我國(guó)目前也形成了諸多關(guān)于詐騙罪既遂的細(xì)致分析,“占有”、“控制”、“失控”、“損失”、“失控加控制”、“控制加數(shù)額較大”這六種學(xué)說在理論界爭(zhēng)論較大。但從整體上說,理論界目前對(duì)詐騙罪既遂的問題尚未形成共識(shí),而且司法實(shí)踐中所采的占有說已經(jīng)明顯不能適應(yīng)高速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需要。司法實(shí)踐中很多問題尚未引起理論界足夠的重視,有些問題甚至才剛剛引起實(shí)踐部門關(guān)注。下面將從詐騙罪既遂認(rèn)定現(xiàn)存的學(xué)說開始進(jìn)行分析研究,并從犯罪客觀方面、刑法機(jī)能等方面論證失控說的合理性,結(jié)合司法實(shí)踐對(duì)詐騙罪的既遂認(rèn)定進(jìn)行探討。
一、詐騙罪既遂標(biāo)準(zhǔn)學(xué)說
(一)占有說
占有說。周光權(quán)教授認(rèn)為,占有說是合理的,因?yàn)椤靶谭ㄒ员Wo(hù)法益為目的,認(rèn)定是否成立犯罪要考慮有無法益侵害存在”;占有說有時(shí)又被稱為取得說。該說認(rèn)為,對(duì)詐騙罪基本犯的既未遂形態(tài)的區(qū)分應(yīng)該以行為人是否已經(jīng)實(shí)際占有公私財(cái)物,對(duì)公私財(cái)物無合法根據(jù)的占有達(dá)成的同時(shí)即構(gòu)成詐騙罪的既遂。否則,就是詐騙未遂。占有說是目前司法界所采的主流學(xué)說,也是司法實(shí)踐中的詐騙罪既遂認(rèn)定的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周光權(quán)教授也支持占有說。然而此種學(xué)說目前已經(jīng)難以適應(yīng)因科技進(jìn)步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而迅速變化著的實(shí)踐,因?yàn)殡S著結(jié)算方式的變化,行為人有可能在控制某物的同時(shí)卻并未占有它,占有與控制的脫離使得占有說難以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詐騙罪既遂的認(rèn)定起到應(yīng)有的作用。比如當(dāng)公私財(cái)物雖處于行為人的控制之中,但卻為第三人所占有時(shí),行為人并未直接占有其所騙得的公私財(cái)物,以占有說來判定,難道要因此認(rèn)定行為人為詐騙未遂?可是此時(shí)被騙走財(cái)物的當(dāng)事人已經(jīng)實(shí)際失去了對(duì)財(cái)物的控制,認(rèn)定為未遂明顯不妥。
(二)控制說
控制說。控制說認(rèn)為,詐騙罪的既遂應(yīng)該以行為人實(shí)際取得對(duì)所欲騙取的公私財(cái)物的實(shí)際控制為準(zhǔn)。控制說的提法從行為人對(duì)財(cái)物取得實(shí)際控制出發(fā),而不僅僅限于表面上的占有。控制說的問題在于受害人喪失對(duì)自己財(cái)物的控制與行為人取得控制兩者并不同步,行為人取得對(duì)財(cái)物的控制等于或者晚于受騙人喪失對(duì)財(cái)物的控制,控制說將行為人實(shí)際控制財(cái)物作為法益受到侵害的認(rèn)定點(diǎn),不利于對(duì)受害人利益的保護(hù),因?yàn)槭芎θ说睦嬖趩适?duì)財(cái)物控制的那一刻就已經(jīng)受到侵害。
(三)失控說
失控說。熊選國(guó)認(rèn)為應(yīng)該采失控說,他認(rèn)為“財(cái)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是否失去其對(duì)財(cái)物的控制為詐騙罪既遂與未遂標(biāo)準(zhǔn)”。該學(xué)說主張對(duì)詐騙罪既遂的認(rèn)定應(yīng)該以財(cái)物的所有人失去對(duì)財(cái)物的控制為準(zhǔn),也即失去對(duì)財(cái)物的實(shí)際支配權(quán)作為認(rèn)定詐騙罪既遂與否的界限。如果財(cái)物的所有人因行為人的欺騙行為而實(shí)際失去了對(duì)自己財(cái)物的控制,那么此時(shí)詐騙既遂,否則為未遂。
二、失控說作為詐騙罪既遂標(biāo)準(zhǔn)的合理性
(一)從詐騙罪客觀方面分析失控說的合理性
研究詐騙罪的既遂認(rèn)定,離不開對(duì)犯罪本身、對(duì)犯罪構(gòu)成的研究。目前學(xué)界對(duì)詐騙罪的四個(gè)構(gòu)成要件一般無爭(zhēng)議,但對(duì)于詐騙罪的客觀方面應(yīng)該包含幾個(gè)基本要素,有著四要素和五要素之爭(zhēng)。“四要素說”認(rèn)為,詐騙罪客觀方面的構(gòu)成要素包括:欺騙行為、使他人產(chǎn)生錯(cuò)誤認(rèn)識(shí)、處分財(cái)產(chǎn)、獲取財(cái)產(chǎn);“五要素說”認(rèn)為,除了上述四個(gè)要素之外,詐騙罪客觀方面的基本構(gòu)造還應(yīng)該包括財(cái)產(chǎn)損失,這樣才是完整的詐騙罪的客觀方面的構(gòu)造。可以說,對(duì)本罪客觀方面的不同認(rèn)識(shí)直接會(huì)對(duì)詐騙罪基本犯既遂形態(tài)的認(rèn)定產(chǎn)生影響。
從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上來講,犯罪行為人實(shí)施欺騙行為,使被害人陷入錯(cuò)誤認(rèn)識(shí)從而喪失對(duì)財(cái)產(chǎn)的控制這一事件是早于或者與受有損失同時(shí)發(fā)生,也即是說,“失去控制”這一時(shí)間點(diǎn)至少不會(huì)晚于“受有損失”。相比損失說來講,失控說采取的是“四要素說”,更有利于公私財(cái)產(chǎn)的保護(hù)。同時(shí)由于“五要素說”比起“四要素說”多了“受有損失”,其時(shí)間點(diǎn)也是滯后于“四要素說”的,因此,基于“四要素說”的失控說更為合理。
(二)從刑法機(jī)能方面分析失控說的合理性
1.刑法機(jī)能的種類:談到詐騙罪的既遂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不得不提起刑法的機(jī)能。刑法的機(jī)能實(shí)質(zhì)上是指刑法所具有的作用,是刑法可以發(fā)揮的作用和人們希望刑法所能起到的作用。目前的主流學(xué)說認(rèn)為刑法有三種機(jī)能,分別為:保護(hù)法益、行為規(guī)制、自由保障。
2.契合刑法的保護(hù)機(jī)能:保護(hù)法益機(jī)能在刑法的三種機(jī)能中位居前列,甚至可以說刑法的機(jī)能就是保護(hù)法益。關(guān)于詐騙罪判斷的關(guān)鍵點(diǎn)在于被害人是否喪失了對(duì)財(cái)物的控制,而不在于行為人是否取得了控制,因?yàn)闊o論行為人取得與否,被害人均已喪失了其本來?yè)碛械膶?duì)財(cái)物的控制,法益已然受到了侵害。從這個(gè)方面來講,刑法的保護(hù)法益機(jī)能位居前列,為了更好的發(fā)揮刑法的機(jī)能,從而更好地保護(hù)法益,采用失控說是最符合保護(hù)法益這一機(jī)能的,所以是合理的。
三、司法實(shí)踐中新型詐騙犯罪的既遂認(rèn)定
(一)短信詐騙犯罪的既遂認(rèn)定
相比普通詐騙犯罪,短信詐騙型犯罪有著特殊的行為過程,具體表現(xiàn)為,被害人一般并非直接將財(cái)物交付給行為人,而是通過匯款或者轉(zhuǎn)賬等方式交付,在財(cái)物流轉(zhuǎn)的過程中加入了第三方。從受害人收到詐騙短信,到基于錯(cuò)誤認(rèn)識(shí)而處分財(cái)產(chǎn),中間由于第三方比如銀行的介入,導(dǎo)致財(cái)產(chǎn)并非直接轉(zhuǎn)移至行為人。財(cái)物喪失控制的節(jié)點(diǎn)應(yīng)該從被害人基于錯(cuò)誤認(rèn)識(shí)向銀行等第三方發(fā)出通知時(shí)較為適宜。
(二)虛擬財(cái)產(chǎn)詐騙犯罪的既遂認(rèn)定
“虛擬財(cái)產(chǎn)不會(huì)因?yàn)槿藗兊母惺苋绾味a(chǎn)生變化”,虛擬財(cái)產(chǎn)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的產(chǎn)物,它具有:非實(shí)體性、客觀性、價(jià)值性、流通性、依附性等特點(diǎn),然而我國(guó)法律目前沒有對(duì)虛擬財(cái)產(chǎn)作出明確的界定。對(duì)虛擬財(cái)產(chǎn)進(jìn)行詐騙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特點(diǎn),“其行為階段為:行為人詐騙他人虛擬財(cái)產(chǎn)前的準(zhǔn)備,其次以各種方法使對(duì)方相信自己能夠滿足他的要求,再次使對(duì)方自愿交出財(cái)產(chǎn),最后對(duì)虛擬財(cái)產(chǎn)進(jìn)行控制”。對(duì)于虛擬財(cái)產(chǎn)詐騙犯罪,其既遂認(rèn)定應(yīng)該根據(jù)不同情節(jié)進(jìn)行具體認(rèn)定。其一,當(dāng)行為人對(duì)被害人的賬號(hào)本身進(jìn)行操作時(shí),比如修改密碼,則應(yīng)以行為人修改密碼之時(shí)為犯罪既遂之時(shí),因?yàn)榇藭r(shí)被害人已經(jīng)喪失了對(duì)自己電子賬號(hào)的主導(dǎo)權(quán),同時(shí)也對(duì)賬號(hào)內(nèi)的一切物品失去了控制權(quán);其二,當(dāng)行為人并未對(duì)被害人賬號(hào)本身進(jìn)行動(dòng)作,而僅將賬號(hào)內(nèi)的虛擬物品進(jìn)行轉(zhuǎn)移,應(yīng)該以該特定虛擬物品實(shí)際離開原主時(shí)為既遂的時(shí)間點(diǎn),而該虛擬物品是否已經(jīng)轉(zhuǎn)移至另一賬號(hào)之下則在所不問。
四、結(jié)語
作為多發(fā)性犯罪――詐騙罪,對(duì)于它的既遂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的研究在理論和實(shí)務(wù)上都是有著重要意義的。現(xiàn)今理論研究還在不斷深入,實(shí)踐也在不斷發(fā)展,對(duì)于詐騙罪既遂的研究并不會(huì)終止,在進(jìn)行理論研究的同時(shí)我們需要立足于現(xiàn)實(shí),與時(shí)俱進(jìn),不斷深入對(duì)于詐騙罪既遂認(rèn)定的研究,找出現(xiàn)有不足與缺陷,讓詐騙罪的既遂認(rèn)定更加完善。(作者單位:河北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法學(xué)院)
參考文獻(xiàn):
第8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關(guān)鍵詞:電信詐騙;實(shí)質(zhì)客觀理論;失控說
中圖分類號(hào):D924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589(2013)32-0134-03
常見的電信詐騙類型如下,即虛構(gòu)電信欠費(fèi)以及涉嫌洗錢罪的虛假事由,被告人假冒中國(guó)電信以及公檢法人員欺騙被害人的身份資料和賬戶被犯罪集團(tuán)利用,涉嫌洗錢罪,謊構(gòu)“安全監(jiān)管賬戶”誘使被害人將銀行賬戶內(nèi)的資金轉(zhuǎn)賬至所謂的“安全監(jiān)管賬戶”,騙取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
何謂犯罪既遂,當(dāng)行為人既已著手實(shí)行,且將行為實(shí)行完成,或已發(fā)生結(jié)果者,則犯罪即屬既遂,而成立既遂犯[1]299。電信詐騙犯罪應(yīng)屬結(jié)果犯,已發(fā)生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結(jié)果方成立犯罪既遂,若未發(fā)生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結(jié)果則屬于犯罪未遂。然而,認(rèn)定行為人的電信詐騙是否已著手實(shí)行,則是論證成立電信詐騙犯罪既遂與否的前提,故而對(duì)“著手”的學(xué)說作深入探究實(shí)屬必要。
一、電信詐騙犯罪形態(tài)的著手標(biāo)準(zhǔn)學(xué)說薈粹
(一)關(guān)于認(rèn)定著手的學(xué)說
關(guān)于認(rèn)定著手實(shí)行的理論,其一,形式客觀理論,認(rèn)為行為人唯有已經(jīng)開始實(shí)行嚴(yán)格意義的構(gòu)成要件該當(dāng)行為,始可認(rèn)定為著手實(shí)行。其二,實(shí)質(zhì)客觀理論,該理論有兩類見解,較為合理的見解認(rèn)為,行為人必須開始實(shí)行足以對(duì)于構(gòu)成要件所保護(hù)的行為客體形成直接危險(xiǎn)的行為,始得認(rèn)定已達(dá)著手實(shí)行的行為階段。其三,主觀理論,認(rèn)為行為是否已達(dá)著手實(shí)行的行為階段,應(yīng)就行為人的主觀意思以為斷。若依據(jù)行為人的犯意及其犯罪計(jì)劃,而可判斷犯罪行為已經(jīng)開始實(shí)行者,則可認(rèn)定為著手實(shí)行。其四,主觀與客觀混合理論,認(rèn)為行為人直接依其對(duì)于行為的認(rèn)識(shí),而開始實(shí)行足以實(shí)現(xiàn)構(gòu)成要件的行為,即可認(rèn)定行為已達(dá)著手實(shí)行的行為階段[1]307。林山田教授認(rèn)可主觀與客觀混合理論。
(二)各學(xué)說的合理性基礎(chǔ)之探究
電信詐騙犯罪案件中的行為人常利用電話、電腦等通訊工具作為詐騙手段,行為人購(gòu)買電話、電腦等工具即是為實(shí)施犯罪做準(zhǔn)備,此時(shí)即可反映出行為人的危險(xiǎn)性格。若采用主觀理論認(rèn)定電信詐騙犯罪的“著手”,可能使著手時(shí)期過于提前。依此理論,行為人開始購(gòu)買專門用于詐騙的電話、電腦等工具時(shí),已經(jīng)反映行為人犯意,并可判斷行為人已經(jīng)開始實(shí)行其犯罪計(jì)劃,此時(shí)認(rèn)定行為人已著手實(shí)行電信詐騙。此理論過早認(rèn)定著手,不當(dāng)?shù)財(cái)U(kuò)大實(shí)行行為的范圍,必然導(dǎo)致擴(kuò)大處罰范圍,故擯棄之。
關(guān)于形式客觀理論,該理論將行為人實(shí)行嚴(yán)格意義的構(gòu)成要件該當(dāng)行為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作為認(rèn)定著手實(shí)行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而在時(shí)間上接近構(gòu)成要件行為的行為方可認(rèn)定為嚴(yán)格意義的構(gòu)成要件該當(dāng)行為,此理論可能導(dǎo)致實(shí)行的著手時(shí)期過于推遲。例如:在一則電信詐騙犯罪的案件中,某公司的財(cái)務(wù)會(huì)計(jì)甲,接到分別冒充公安人員、檢查人員、法院人員的犯罪嫌疑人的電話,對(duì)方稱甲在財(cái)務(wù)往來中所利用的工商銀行賬戶曾被販毒集團(tuán)使用,受騙的甲到ATM機(jī),邊聽該詐騙電話邊將該賬戶內(nèi)的財(cái)產(chǎn)轉(zhuǎn)賬至對(duì)方提供的“安全監(jiān)管賬戶”,在甲按下“確定鍵”的前幾秒,被識(shí)破騙局的銀行工作人員拉住而未按下此鍵。若按照形式客觀理論,在時(shí)間上接近構(gòu)成要件行為的行為應(yīng)指行為人在電話里“指示”甲按“確定鍵”的行為,因?yàn)榇诵袨榕c甲處分財(cái)產(chǎn)的處分行為在時(shí)間上比較接近,故而被認(rèn)定為嚴(yán)格意義上的構(gòu)成要件該當(dāng)行為,行為人實(shí)施此行為時(shí)方可認(rèn)定為“著手”,過于推遲了電信詐騙犯罪著手實(shí)行的時(shí)間,使電信詐騙犯罪的未遂范圍過于狹窄,故擯棄之。
若采用實(shí)質(zhì)客觀理論,有利于正確認(rèn)定電信詐騙犯罪著手實(shí)行的時(shí)間點(diǎn)。張明楷教授在其著作《未遂犯論》亦主張此理論,該書中主張的實(shí)質(zhì)客觀說中的結(jié)果說,認(rèn)為侵害法益的危險(xiǎn)性達(dá)到了具體程度(一定程度)時(shí),才是實(shí)行的著手[2]61。張明楷教授在其新著《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亦主張此理論,即“只有開始實(shí)施直接使受騙者陷入處分財(cái)產(chǎn)的認(rèn)識(shí)錯(cuò)誤的欺騙行為,具有導(dǎo)致他人遭受財(cái)產(chǎn)損失的緊迫危險(xiǎn)時(shí),才是金融詐騙罪的著手。”[3]426刑法的任務(wù)在于保護(hù)法益,“實(shí)質(zhì)客觀說”中的結(jié)果說將“具有侵犯法益的緊迫危險(xiǎn)性”作為判斷“著手”問題的標(biāo)準(zhǔn),通過懲罰已“著手”實(shí)行犯罪的被告人從而保護(hù)法益,同時(shí)又不過早地提前認(rèn)定“著手”的時(shí)期,亦不過遲地認(rèn)定“著手”的時(shí)期,采用此說認(rèn)定電信詐騙犯罪的著手問題,頗為合理。在上述例子中,當(dāng)甲準(zhǔn)備前往銀行ATM機(jī)轉(zhuǎn)賬時(shí),此時(shí)已經(jīng)具有導(dǎo)致甲遭受財(cái)產(chǎn)損失的緊迫危險(xiǎn),因此,當(dāng)犯罪嫌疑人欺騙甲并使甲相信“安全監(jiān)管賬戶”這事情時(shí),已是電信詐騙犯罪的著手實(shí)行,具備使其自身負(fù)刑事責(zé)任的客觀基礎(chǔ)。
二、界定電信詐騙犯罪既遂形態(tài)的學(xué)說
(一)如何界定電信詐騙犯罪既遂形態(tài)的學(xué)說薈粹
如何區(qū)分詐騙罪既遂形態(tài)與未遂形態(tài),有以下諸多學(xué)說。其一,占有說,該說認(rèn)為,區(qū)分詐騙罪基本犯的既遂與未遂形態(tài)應(yīng)當(dāng)以公私財(cái)物是否為行為人實(shí)際占有為標(biāo)準(zhǔn)。如果行為人已經(jīng)取得本欲占有的公私財(cái)物,就是詐騙罪基本犯的既遂。其二,控制說,此學(xué)說主張,應(yīng)以行為人是否實(shí)際取得對(duì)公私財(cái)物的控制或支配為界限,對(duì)詐騙罪基本犯的停止形態(tài)進(jìn)行劃分。如果行為人實(shí)際取得了對(duì)公私財(cái)物的控制或支配,則為詐騙罪基本犯的既遂。其三,失控說,認(rèn)為應(yīng)以財(cái)物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是否失去對(duì)其財(cái)物的控制,即以財(cái)物所有人或占有人是否實(shí)際失去對(duì)財(cái)物的實(shí)際支配權(quán)為界限作為詐騙罪基本犯既遂與未遂形態(tài)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其四,損失說,該學(xué)說為林山田教授所提倡。被騙者受騙而處分財(cái)產(chǎn)造成其本人或者第三人之財(cái)產(chǎn)損失,即為本罪之既遂,至于行為人是否已獲得財(cái)物,則與本罪之既遂無關(guān)。其五,失控加控制說,認(rèn)為應(yīng)以被詐騙的公私財(cái)物是否脫離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控制并實(shí)際置于行為人的實(shí)際控制之下為標(biāo)準(zhǔn),對(duì)詐騙罪基本犯的既遂與未遂形態(tài)加以區(qū)分[4]73。
(二)上述既遂標(biāo)準(zhǔn)學(xué)說合理性之探究
失控說與損失說相比,損失說要求行為人的行為不但使被害人失去了對(duì)財(cái)產(chǎn)的控制權(quán),亦須因行為人的詐騙行為造成了被害人實(shí)際的財(cái)產(chǎn)損失才能構(gòu)成詐騙罪既遂。該損失說似乎過于推遲了詐騙罪既遂的時(shí)間點(diǎn),電信詐騙犯罪利用快捷通信技術(shù)作案,若采用損失說認(rèn)定電信詐騙犯罪既遂與否,似乎不利于打擊此類作案速度快的犯罪。“失控說、控制說、損失說”三種學(xué)說在被害人喪失財(cái)產(chǎn)與行為人取得該筆財(cái)產(chǎn)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不一致時(shí),采取不同的學(xué)說得出的結(jié)論不同。設(shè)被害人喪失財(cái)產(chǎn)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為A,行為人取得財(cái)產(chǎn)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為B,在時(shí)間軸上A點(diǎn)在B點(diǎn)之前發(fā)生,且當(dāng)A點(diǎn)、B點(diǎn)的時(shí)間段距較長(zhǎng)時(shí),采取“失控說”抑或是采納“控制說”反映了成立電信詐騙犯罪既遂時(shí)間的快慢,亦反映了刑罰處罰范圍的大小以及其背后的刑法思想。若采用“失控說”,在A點(diǎn)即成立犯罪既遂,較早地認(rèn)定電信詐騙犯罪既遂,在處置發(fā)案率頗高的電信詐騙犯罪方面體現(xiàn)了擴(kuò)大此類犯罪的處罰范圍的發(fā)展趨勢(shì),這與當(dāng)前電信詐騙犯罪案件激增并嚴(yán)重侵害公民財(cái)產(chǎn)安全、嚴(yán)重影響社會(huì)秩序密切相關(guān),司法機(jī)關(guān)采用此學(xué)說認(rèn)定電信詐騙既遂形態(tài),反映了“亂世用重典”的刑法思想。但被害人喪失財(cái)產(chǎn)之后,行為人取得財(cái)產(chǎn)之前,若涉案財(cái)產(chǎn)被警方通知銀行凍結(jié),行為人并未因此獲利,被害人財(cái)產(chǎn)最終亦未因此受損,此時(shí)讓行為人承擔(dān)詐騙罪既遂的刑事責(zé)任,似乎頗不公平,亦有違刑法的謙抑性理念,此一點(diǎn)頗手學(xué)者詬病。然而,若采用“控制說”,于B點(diǎn)(即行為人取得財(cái)產(chǎn)的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方成立電信詐騙犯罪既遂,其不合理之處更顯而易見。上海警方專案組在偵破電信詐騙案件的工作中發(fā)現(xiàn),由于當(dāng)今社會(huì)信息化程度很高,被害人錢款一旦轉(zhuǎn)賬到犯罪嫌疑人賬戶,往往犯罪嫌疑人會(huì)在幾十分鐘、甚至幾分鐘內(nèi)就能將錢款通過網(wǎng)上銀行或者電話銀行轉(zhuǎn)移,而這段時(shí)間內(nèi),被害人甚至都沒有發(fā)現(xiàn)自己已受騙上當(dāng),待發(fā)現(xiàn)后再去報(bào)案,這筆錢款已經(jīng)被取出。電信詐騙犯罪的財(cái)產(chǎn)轉(zhuǎn)移軌跡往往體現(xiàn)為銀行的轉(zhuǎn)賬記錄,但一旦犯罪嫌疑人銷毀該賬戶或銀行卡,且此銀行卡往往又是從黑市中購(gòu)買,并非犯罪嫌疑人的真名賬戶,此時(shí),警方將難以取證證明犯罪嫌疑人實(shí)際控制贓款的數(shù)額,若如此,則難以認(rèn)定其犯罪既遂的數(shù)額,進(jìn)而可能導(dǎo)致過于縮小電信詐騙犯罪的處罰范圍,不利于抑制電信詐騙犯罪以保護(hù)社會(huì)公民的財(cái)產(chǎn)。針對(duì)以上難題,假若警方以被害人實(shí)際轉(zhuǎn)賬的數(shù)額作為認(rèn)定電信詐騙犯罪既遂的數(shù)額,無異于重回“失控說”的認(rèn)定思路。
三、采用失控說的理由分析
依據(jù)上述關(guān)于電信詐騙犯罪既遂標(biāo)準(zhǔn)的論述,采納“失控說”認(rèn)定電信詐騙犯罪既遂形態(tài),而不采用“控制說”、“損失說”、“占有說”,應(yīng)是權(quán)衡之后的合理之選,采用“失控說”的論證理由有如下幾個(gè)方面。
(一)刑法的保護(hù)機(jī)能的論證角度
刑法所具有的機(jī)能當(dāng)中,其保護(hù)機(jī)能應(yīng)位居前列。由于刑法以保護(hù)法益為目的,懲罰詐騙罪的目的無非是要保護(hù)財(cái)產(chǎn)所有者、占有者對(duì)財(cái)產(chǎn)的權(quán)利,并且詐騙罪社會(huì)危害性的大小,也主要不在于行為人是否控制了財(cái)物,而在于被害人是否喪失了對(duì)財(cái)物的控制。從此種意義上而言,行為人即使沒有取得(或控制)財(cái)物,但如果被害人失去了對(duì)財(cái)物的控制,視為詐騙罪既遂亦是情理之中[5]193。總而言之,從刑法的目的在于保護(hù)法益的論證角度而言,采用“失控說”是合理的。
(二)利益衡量或者價(jià)值平衡的論證角度
利益衡量的方法論認(rèn)為,法官應(yīng)通過利益衡量的方法,綜合把握案件的實(shí)質(zhì),結(jié)合社會(huì)環(huán)境、社會(huì)秩序、價(jià)值觀念等,對(duì)雙方當(dāng)事人的利益關(guān)系做比較衡量,做出本案當(dāng)事人哪一方應(yīng)受保護(hù)的判斷,然后再?gòu)姆蓷l文中尋找根據(jù),以便使結(jié)論正當(dāng)化或合理化。電信詐騙中較為典型的案例為,行為人謊稱被害人的賬戶涉嫌洗錢罪,謊構(gòu)“安全監(jiān)管賬戶”誘使被害人將銀行賬戶內(nèi)的資金轉(zhuǎn)賬至所謂的“安全監(jiān)管賬戶”,騙取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當(dāng)行為人取得上述部分詐騙財(cái)產(chǎn)的支配權(quán)或者控制權(quán),若將全部轉(zhuǎn)賬財(cái)產(chǎn)的數(shù)額認(rèn)定為既遂數(shù)額,對(duì)行為人而言似乎不公平,其未取得相應(yīng)的非法經(jīng)濟(jì)利益卻要為此付出相應(yīng)的成本(即承擔(dān)該部分?jǐn)?shù)額的刑罰),損害了其對(duì)法律公平對(duì)待自己的心理預(yù)期。另一方面,從被害人的角度分析之,其被詐騙的財(cái)產(chǎn)曾經(jīng)因行為人的詐騙行為一度失控,且被警方追回的概率極其微小,該部分財(cái)產(chǎn)的安全受到高度威脅。刑法的目的在于保護(hù)法益,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安全免受詐騙行為侵害的法益應(yīng)受到刑法的優(yōu)先關(guān)注。論述至此,兩對(duì)相互沖突的“價(jià)值”顯現(xiàn)出來,“價(jià)值一”即被害人的財(cái)產(chǎn)安全免受高度威脅的法益,“價(jià)值二”即行為人對(duì)法律的合理的公正預(yù)期。運(yùn)用價(jià)值平衡的方法論,結(jié)合當(dāng)今電信詐騙犯罪案件頻發(fā)的社會(huì)環(huán)境、該類嚴(yán)重?cái)_亂財(cái)產(chǎn)安全的社會(huì)秩序、犯罪嫌疑人運(yùn)用高端的電信設(shè)備與被害人的相對(duì)弱勢(shì)等情況,對(duì)雙方當(dāng)事人的利益關(guān)系作比較衡量,且行為人的公正預(yù)期產(chǎn)生于詐騙行為之后,依據(jù)“任何人不能從其違法行為中獲益”的法理,對(duì)基于實(shí)施詐騙行為之后的行為人的公正預(yù)期的這一價(jià)值,不應(yīng)受到法律的保護(hù)。因此,司法的天平應(yīng)傾向于保護(hù)“價(jià)值一”,此即為進(jìn)行價(jià)值平衡得出的判斷。
(三)“結(jié)果無價(jià)值論與二元違法論”的論證角度
結(jié)果無價(jià)值論認(rèn)為,違法性的實(shí)質(zhì)在于行為所引起的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的危險(xiǎn),而“二元違法論”這一學(xué)說以結(jié)果無價(jià)值論為基礎(chǔ),同時(shí)作為對(duì)結(jié)果的違法的限定也考慮行為無價(jià)值(社會(huì)相當(dāng)性的逸脫)。日本刑法學(xué)界幾乎已不再有人主張“行為無價(jià)值一元論”,主要是“結(jié)果無價(jià)值論”與“二元違法論”之間的對(duì)立[6]96。以“結(jié)果無價(jià)值論”作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當(dāng)被害人將銀行卡內(nèi)財(cái)產(chǎn)轉(zhuǎn)賬至行為人的賬戶時(shí),已經(jīng)失去了對(duì)該筆財(cái)產(chǎn)的控制權(quán),其財(cái)產(chǎn)安全的法益已受到行為人詐騙行為的侵害,該法益被侵害的危害結(jié)果在時(shí)間維度上具有不可逆轉(zhuǎn)性,即使后期警方將部分財(cái)產(chǎn)追回返還給被害人,亦是如此。因此,以“結(jié)果無價(jià)值論”判斷之,行為人詐騙該財(cái)產(chǎn)的行為具有違法性。以“二元違法論”判斷之,行為人的電信詐騙行為在客觀上違反了我國(guó)刑法第266條關(guān)于詐騙罪的規(guī)定,主觀上具有犯罪故意,其行為因違反規(guī)范而無價(jià)值,在具備“結(jié)果無價(jià)值”的基礎(chǔ)上亦符合“行為無價(jià)值”,符合“二元違法論”進(jìn)而肯定其行為違法。總而言之,無論是以結(jié)果無價(jià)值論抑或是二元違法論皆可論證行為人詐騙財(cái)產(chǎn)的行為具備違法性,其有責(zé)性更顯而易見,已經(jīng)具備處以刑罰的客觀基礎(chǔ)。詐騙罪為結(jié)果犯,肯定該財(cái)產(chǎn)的犯罪數(shù)額為既遂數(shù)額,進(jìn)而成立結(jié)果犯使行為人負(fù)刑事責(zé)任,自是情理之中,畢竟其已具備科處刑罰的客觀基礎(chǔ)。而采用失控說認(rèn)定該部分財(cái)產(chǎn)數(shù)額為既遂數(shù)額,在結(jié)論上是符合上述論證結(jié)果的,此即為采用失控說的合理之處。
參考文獻(xiàn):
[1]林山田.刑法通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2.
[2]張明楷.未遂犯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3]張明楷.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6.
[4]趙秉志.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中詐騙犯罪司法疑難問題[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
第9篇:經(jīng)濟(jì)詐騙的標(biāo)準(zhǔn)范文
網(wǎng)絡(luò)詐騙超過3000元構(gòu)成犯罪。
【法律依據(jù)】
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guān)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詐騙公私財(cái)物價(jià)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上的,應(yīng)當(dāng)分別認(rèn)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guī)定的“數(shù)額較大”、“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高級(jí)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可以結(jié)合本地區(qū)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fàn)顩r,在前款規(guī)定的數(shù)額幅度內(nèi),共同研究確定本地區(qū)執(zhí)行的具體數(shù)額標(biāo)準(zhǔn),報(bào)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備案。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相關(guān)熱門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 1奧運(yùn)經(jīng)濟(jì)淺析
- 2低碳經(jīng)濟(jì)下的旅游經(jīng)濟(jì)發(fā)展及特征
- 3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下醫(yī)院經(jīng)濟(jì)管理研究
- 4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與低碳經(jīng)濟(jì)綠色包裝探索
- 5金融經(jīng)濟(jì)與實(shí)體經(jīng)濟(jì)良性互動(dòng)研討
- 6低碳經(jīng)濟(jì)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優(yōu)勢(shì)探討
- 7小議虛擬經(jīng)濟(jì)與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的良性互動(dòng)
- 8低碳經(jīng)濟(jì)下工程經(jīng)濟(jì)論文
- 9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論文
- 10實(shí)體經(jīng)濟(jì)流動(dòng)下的虛擬經(jīng)濟(jì)發(fā)展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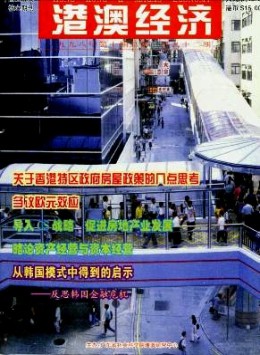
港澳經(jīng)濟(jì)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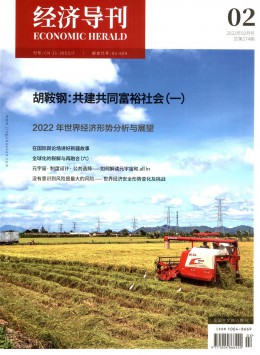
經(jīng)濟(jì)導(dǎo)刊
級(jí)別:部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CJFD)
-

商展經(jīng)濟(jì)
級(jí)別:部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金融經(jīng)濟(jì) · 下半月
級(jí)別:部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港口經(jīng)濟(jì)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