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一、建立行政訴訟和解制度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行政訴訟是一種社會(huì)糾紛的解決機(jī)制,和解協(xié)調(diào)無(wú)疑是一種解決糾紛的有效手段。同時(shí),這種協(xié)調(diào)制度建立在法院依法核準(zhǔn)的基礎(chǔ)上,能確保國(guó)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實(shí)得到維護(hù)。所以,在當(dāng)前城市拆遷、征地補(bǔ)償?shù)刃姓讣罅吭黾樱罕娦允录蜕嬖V上訪案件不斷,行政糾紛錯(cuò)綜復(fù)雜的情況下,構(gòu)建和完善行政訴訟和解協(xié)調(diào)機(jī)制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1、降低成本,節(jié)約資源。行政審判判決耗時(shí)耗力,并且容易引起上訪、申訴等現(xiàn)象,浪費(fèi)各種資源。在行政訴訟中通過(guò)和解協(xié)調(diào)好“官民”糾紛,更易化解當(dāng)事人之間的矛盾,使“官民”握手言和,徹底平息糾紛,節(jié)約了訴訟成本和司法資源,做到案結(jié)事了,雙方滿(mǎn)意。這一點(diǎn)在原告人數(shù)較多的共同訴訟方面更為典型。
2、緩解對(duì)抗,自糾不足。行政主體通過(guò)改變不合理的具體行政行為使行政相對(duì)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其對(duì)行政機(jī)關(guān)的抵觸情緒,增進(jìn)人民群眾和行政機(jī)關(guān)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有瑕疵的情況下,行政和解可以使行政機(jī)關(guān)意識(shí)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進(jìn)完善,為行政機(jī)關(guān)提供了一個(gè)自查自糾的平臺(tái)。
二、行政和解應(yīng)注意的問(wèn)題
一是要堅(jiān)持合法原則,增強(qiáng)解決糾紛的公正性。每一起行政案件,法院都應(yīng)查明案件事實(shí),對(duì)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作出明確判斷,在分清各方是非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協(xié)調(diào)。即不損害原告的合法利益,也不放縱被告的違法行為。對(duì)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只能審查,而不能協(xié)調(diào)。
二是要堅(jiān)持自愿原則,增強(qiáng)當(dāng)事人地位平等意識(shí)。行政訴訟協(xié)調(diào)應(yīng)建立在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的權(quán)力或權(quán)利能互諒互讓?zhuān)?dāng)事人地位平等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無(wú)論是管理方或被管理方,在法律地位上均是平等的。因此,當(dāng)事人之間協(xié)調(diào)處理糾紛必須出于自愿,協(xié)調(diào)意見(jiàn)必須是當(dāng)事人的真實(shí)意思表示。法院不能強(qiáng)制任何一方當(dāng)事人協(xié)調(diào)處理案件。:
第2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關(guān)鍵詞:爭(zhēng)議順序沖突處理
自199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行政訴訟法》施行后,法院須依不同的訴訟法,分別適用行政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qū)﹃P(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進(jìn)行審理。如何處理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的審理順序,即優(yōu)先審理何者,是理論和實(shí)踐均必須予以規(guī)范與明確的問(wèn)題。隨著我國(guó)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的建立和進(jìn)一步完善,為了更有效調(diào)整紛繁復(fù)雜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和合理配置資源,行政權(quán)的進(jìn)一步擴(kuò)大,已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行政權(quán)時(shí)刻影響著大量的民事法律關(guān)系,行政法律關(guān)系與民事法律關(guān)系相互滲透、交叉;同時(shí),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法律意識(shí)尤其是行政訴訟意識(shí)的增強(qiáng),唯權(quán)、唯上思想的擯棄,一旦行政行為侵犯其民事權(quán)益時(shí),已不再聽(tīng)之任之,而是充分行使提起行政訴訟的權(quán)利,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的案件將有增無(wú)減。因此,從理論上,對(duì)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的審理順序進(jìn)行探討,為以后立法提供更加科學(xué)的理論依據(jù),規(guī)范、統(tǒng)一目前司法操作方式,均具有積極意義。
一、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的概念、特征與表現(xiàn)形式
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是指在案件的審理過(guò)程中,同時(shí)存在均需解決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二爭(zhēng)議內(nèi)容上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處理結(jié)果互為因果或互為前提條件的一種爭(zhēng)議形式。
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具有如下特征:1、法院已立案受理至少一爭(zhēng)議,但未審理終結(jié)。當(dāng)二爭(zhēng)議均被訴至法院,法院就必須解決二訴訟的審理順序;法院在審理一訴訟的過(guò)程中,出現(xiàn)另一須適用其它的訴訟程序?qū)徖淼臓?zhēng)議時(shí),不能置之不理,也要處理優(yōu)先解決何者。爭(zhēng)議均未被訴至法院和一爭(zhēng)議或二爭(zhēng)議均已被審理終結(jié),不存在審理順序的沖突。2、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必須是緊密型的,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關(guān)聯(lián)性是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的本質(zhì)特征。本文所指的關(guān)聯(lián)性不是哲學(xué)意義上的普遍聯(lián)系性,其條件有二方面:一是內(nèi)容上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行政爭(zhēng)議因民事?tīng)?zhēng)議產(chǎn)生或民事?tīng)?zhēng)議因行政爭(zhēng)議產(chǎn)生;二是處理結(jié)果上具有因果性或前提條件性,一爭(zhēng)議判決本身依賴(lài)于另一爭(zhēng)議的解決,后一爭(zhēng)議雖不構(gòu)成前一爭(zhēng)議的主要標(biāo)的,但決定前一爭(zhēng)議的判決結(jié)果。3、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的當(dāng)事人基本具有吻合性,民事?tīng)?zhēng)議的原、被告是行政爭(zhēng)議的原告、第三人,反之亦然。雖然行政爭(zhēng)議必然有行政主體的參與,行政主體在行政訴訟中充當(dāng)被告的角色,但行政爭(zhēng)議的其他當(dāng)事人基本是民事?tīng)?zhēng)議的原、被告。任一爭(zhēng)議的當(dāng)事人不是另一爭(zhēng)議的當(dāng)事人,該二爭(zhēng)議就不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4、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的當(dāng)事人均已向法院提出主張。法院在審理案件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存在當(dāng)事人未向法院主張的關(guān)聯(lián)的另一爭(zhēng)議,依照“不訴不理”的民事、行政訴訟基本原則,法院無(wú)職權(quán)審理未被當(dāng)事人主張的另一爭(zhēng)議,故無(wú)需解決優(yōu)先審理何爭(zhēng)議的問(wèn)題。
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的表現(xiàn)形式有二種:一是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即理論上的本訴與他訴。依法院立案受理的時(shí)間的先后可分為行政訴訟受理在先和民事訴訟受理在先,但法院立案受理的時(shí)間的先后,不能決定何者應(yīng)優(yōu)先審理。二是關(guān)聯(lián)的訴訟與爭(zhēng)議。在訴訟的過(guò)程中,出現(xiàn)關(guān)聯(lián)的、當(dāng)事人已向法院主張的另一須依其它訴訟程序?qū)徖淼闯稍V的爭(zhēng)議。若后爭(zhēng)議已被訴至法院且法院已立案受理,即轉(zhuǎn)化為第一種形式,本文所指的第二種形式是未將爭(zhēng)議轉(zhuǎn)化為訴訟的情形。
二、本訴與他訴的優(yōu)先關(guān)系的處理原則
本訴與他訴的優(yōu)先問(wèn)題,學(xué)者傾向性的觀點(diǎn)是行政訴訟優(yōu)先于民事訴訟。其理由是:1、從行政法理論上講,是行政權(quán)優(yōu)先原則在訴訟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①。行政優(yōu)先權(quán)原則要求行政權(quán)與社會(huì)組織或公民個(gè)人的權(quán)利在同一范圍內(nèi)相遇時(shí),行政權(quán)具有優(yōu)先行使與實(shí)現(xiàn)的效力。2、從二訴訟保護(hù)的社會(huì)利益價(jià)值大小看,行政訴訟保護(hù)的權(quán)益既有行政利益,又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quán)益;民事訴訟保護(hù)的主要是公民和組織的人身權(quán)益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益②。3、從二訴訟的審理結(jié)果看,行政訴訟的審理結(jié)果可能是行政機(jī)關(guān)履行法定職責(zé)或行政賠償,民事訴訟的審理結(jié)果是民事權(quán)益得以實(shí)現(xiàn),民事義務(wù)得到履行,主要體現(xiàn)了各方在財(cái)產(chǎn)利益上的增加或減少,一般不涉及生命權(quán)和人身自由權(quán)等基本人權(quán)③。
在司法實(shí)踐中,處理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優(yōu)先關(guān)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種:1、各自獨(dú)立式。法院不同的審判庭對(duì)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獨(dú)自審理,他訴的是否存在和審理結(jié)果,不理不睬,僅對(duì)本訴的所有證據(jù)材料效力予以審核認(rèn)定并直接據(jù)此作出裁判。2、行政訴訟優(yōu)先式。行政訴訟具有優(yōu)先性,民事訴訟讓位于行政訴訟;中止民事訴訟的審理,待行政訴訟審理終結(jié)后,并以行政訴訟的處理結(jié)果為依據(jù)繼續(xù)審理民事訴訟。該式是行政訴訟先于民事訴訟觀點(diǎn)的典型的司法操作模式。3、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式。當(dāng)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并存時(shí),在立案審查階段,把民事訴訟作為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形式予以立案,移交行政審判庭審理;在審理階段,由民事審判庭把民事訴訟移送到行政審判庭作為行政訴訟附帶民事訴訟形式一并予以審理。
上述三種方式,固然有其合理的方面,如第一種方式能及時(shí)、快捷審結(jié)案件,第二種方式簡(jiǎn)單明確、易于操作,第三種方式體現(xiàn)訴訟的效益原則。但是,如果繼續(xù)探究上述三種方式的利弊,似有形而上學(xué)和機(jī)械論的嫌疑,其缺點(diǎn)或不足之處顯而易見(jiàn)。
根據(jù)行政法的理論,行政行為一經(jīng)行政主體作出和被行政相對(duì)人知曉,即具有公定力。否定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或使行政行為失效的機(jī)關(guān)只能是行為機(jī)關(guān)、行為機(jī)關(guān)的上級(jí)機(jī)關(guān)或人民法院。行政訴訟法第3條第2款規(guī)定,人民法院設(shè)行政審判庭,審理行政案件;行政審判庭是對(duì)行政行為進(jìn)行合法性審查并作出評(píng)價(jià)的唯一合法主體;民事審判庭無(wú)權(quán)對(duì)作為民事訴訟中的證據(jù)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jìn)行審查,更無(wú)權(quán)對(duì)行政行為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獨(dú)自審理民事訴訟,違背行政行為的效力原則。因此在民事訴訟中,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以查證屬實(shí)的行政主體超越職權(quán)作出的行政行為、行政相對(duì)人已喪失提起行政訴訟的時(shí)效的權(quán)利等為由對(duì)行政行為作出評(píng)價(jià)并據(jù)此作出裁判的行為,是錯(cuò)誤的。但法院在審理民事訴訟的過(guò)程中,可對(duì)作為證據(jù)的行政行為的客觀性和關(guān)聯(lián)性進(jìn)行審核認(rèn)定并據(jù)此對(duì)訴訟直接作出裁判,如法院對(duì)作為民事訴訟的證據(jù)的“行政”行為系偽造,不是行政主體作出的“行政”行為,不能直接或間接導(dǎo)致行政法律關(guān)系的產(chǎn)生、變更與消滅的“行政”行為,因上述“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行為,不受行政行為的公定力效力原則的約束;也因上述“行政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不可能以行政訴訟方式進(jìn)行司法審查,因此法院可直接予以審核認(rèn)定。在民事訴訟中,法院無(wú)權(quán)否定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同樣因?yàn)楸粻?zhēng)議的行政行為可能屬于可撤銷(xiāo)的行為,也無(wú)權(quán)肯定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并據(jù)此作出裁判結(jié)果,否則,在行政訴訟中,法院作出撤銷(xiāo)行政行為、確認(rèn)行政行為違法的裁判時(shí),將由于法院的過(guò)錯(cuò)出現(xiàn)相互矛盾的裁判。各自獨(dú)立式無(wú)視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關(guān)聯(lián)性的客觀存在,違背了客觀決定主觀的認(rèn)識(shí)規(guī)律,其裁判結(jié)果的錯(cuò)誤就在所難免了。因此,各自獨(dú)立式的處理方式不僅違背法學(xué)和哲學(xué)的基本理論,實(shí)踐證明極易破壞司法統(tǒng)一原則,損害國(guó)家司法權(quán)威,降低司法公信度。
從訴訟法律關(guān)系角度而言,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是相互獨(dú)立的,不存在效力大小、誰(shuí)先誰(shuí)后的問(wèn)題。優(yōu)先審理行政訴訟不屬于行政優(yōu)先權(quán)的內(nèi)容,優(yōu)先審理行政訴訟不符合主體是行政主體、是為了實(shí)現(xiàn)行政目的所必需的、必須有法律依據(jù)等行政優(yōu)先權(quán)的成立條件。行政優(yōu)先權(quán)與優(yōu)先審理行政訴訟無(wú)必然的聯(lián)系,行政優(yōu)先權(quán)的理論并不能推理出優(yōu)先審理行政訴訟的理論。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是通過(guò)對(duì)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司法審查,最終保護(hù)受違法行政行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quán)益,民事訴訟也保護(hù)全民所有制主體的合法權(quán)益;同時(shí),很難說(shuō)行政權(quán)益大于經(jīng)濟(jì)利益,實(shí)際上,保護(hù)行政權(quán)益的目的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更大的經(jīng)濟(jì)利益,不能也算不清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各所保護(hù)的社會(huì)利益的大小。雖然行政訴訟審理的對(duì)象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權(quán),但民事訴訟的審理對(duì)象中包括人格權(quán)、身體健康權(quán)、名譽(yù)權(quán)等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從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審理結(jié)果而言,孰輕孰重,實(shí)難辨清。在司法實(shí)踐中,多數(shù)的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案件的審理順序,確應(yīng)是行政訴訟優(yōu)先于民事訴訟。但是,在審理行政機(jī)關(guān)以申請(qǐng)與事實(shí)、主體不符或法律規(guī)定為由的行政不作為的行政案件時(shí),就不應(yīng)優(yōu)先審理行政訴訟④。
為了方便當(dāng)事人,節(jié)約訴訟成本,避免“官了民不了”⑤的現(xiàn)象,徹底解決糾紛,提高行政審判效果,理順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審理順序,合理利用司法資源,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式是極其科學(xué)的方式。民事訴訟法第6條第1款規(guī)定,“民事案件的審理權(quán)由人民法院行使”,行政審判庭審理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如同刑事審判庭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一樣,是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在理論上,法院在不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前提下,可決定適用何種程序?qū)徖戆讣?dāng)事人無(wú)權(quán)選擇案件的審理程序與審判庭。遺憾的是,行政訴訟法對(duì)此未作任何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行政訴訟法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第63條規(guī)定了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可惜的是該條款規(guī)定的行政附帶民事訴訟范圍過(guò)于狹窄,且規(guī)定了必須由當(dāng)事人要求一并解決的前提條件與法院可以(并不是必須)一并審理;同時(shí),內(nèi)容簡(jiǎn)單、缺乏操作性,所以該規(guī)定形似建立了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制度,實(shí)質(zhì)上是基本采納了行政不能附帶民事訴訟的觀點(diǎn)的產(chǎn)物⑥。目前,在司法實(shí)踐中,能以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糾紛的案件是極為少數(shù)的。筆者認(rèn)為,建立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已是迫在眉睫的立法任務(wù),如刑事訴訟法中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編一樣,修改現(xiàn)行行政訴訟法,設(shè)立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專(zhuān)章或編,規(guī)定建立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及其原則性問(wèn)題;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行政附帶民事訴訟受理范圍、立案、證據(jù)規(guī)則、審理程序等作出司法解釋。如在短期內(nèi)不能修改行政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應(yīng)立即修改與完善關(guān)于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司法解釋?zhuān)绕涫橇阜秶贫ㄈ缱罡呷嗣穹ㄔ骸蛾P(guān)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問(wèn)題的規(guī)定》,其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關(guān)于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進(jìn)一步擴(kuò)大是必要的、迫切的。建議將行政主體頒發(fā)權(quán)證的行政行為引起的民事訴訟納入必要的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將行政處罰引起的民事訴訟納入普通(可以)的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受理范圍,這樣才能真正發(fā)揮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應(yīng)有作用。
筆者認(rèn)為,目前,除可以依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與國(guó)行政訴訟法>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第63條規(guī)定,適用行政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審理的案件外,正確處理關(guān)聯(lián)的本訴與他訴的審理順序的原則,應(yīng)是優(yōu)先審理決定另一訴訟裁判結(jié)果(內(nèi)容)的訴訟,即優(yōu)先審理屬于原因、前提條件的訴訟。該方式既不違反現(xiàn)行法律的有關(guān)規(guī)定,又是對(duì)上述三種方式揚(yáng)長(zhǎng)避短的結(jié)晶。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款第(5)項(xiàng)規(guī)定,本案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jié)果為依據(jù),而另一案尚未審結(jié)的,中止訴訟,和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與國(guó)行政訴訟法>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第51條第1款第(6)項(xiàng)規(guī)定,案件的審判必須以相關(guān)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案件的審理結(jié)果為依據(jù),而相關(guān)案件尚未審結(jié)的,中止訴訟,是筆者主張的方式的法律依據(jù)。雖然有人認(rèn)為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款第(5)項(xiàng)規(guī)定中的“另一案”僅指另一民事案件,但筆者認(rèn)為應(yīng)包括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否則,該法律應(yīng)明文規(guī)定是另一民事案件。
三、審理關(guān)聯(lián)的訴訟與爭(zhēng)議的處理原則
業(yè)已進(jìn)行的訴訟與在訴訟中出現(xiàn)的須適用不同的訴訟程序解決的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雖不存在訴訟優(yōu)先的問(wèn)題,但如何處理該爭(zhēng)議和如何中止訴訟,是司法實(shí)踐中不可回避的問(wèn)題。在司法實(shí)踐中,主要做法有以下幾種:1、直接認(rèn)定和裁判式。法院在訴訟中對(duì)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直接予以審核認(rèn)定并據(jù)此對(duì)訴訟直接作出裁判。2、建議式。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出現(xiàn)關(guān)聯(lián)的行政爭(zhēng)議時(shí),建議行政機(jī)關(guān)復(fù)查糾正并提供復(fù)查結(jié)果或建議當(dāng)事人另行行政機(jī)關(guān),同時(shí),中止民事訴訟的審理。3、內(nèi)部移送式。法院在訴訟中出現(xiàn)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時(shí),將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以?xún)?nèi)部移送方式移送至相關(guān)審判庭進(jìn)行審理,同時(shí),中止訴訟的審理。
直接認(rèn)定與裁判式,雖然可以減少繁瑣的訴訟程序,但其不合理的原因與上述的各自獨(dú)立式基本相同,不再贅述,因此是不可取的。
建議式,是建立在理想化的法制環(huán)境上,不僅沒(méi)有法律依據(jù),且極可能損害當(dāng)事人的合法權(quán)益,破壞程序公正。現(xiàn)行法律、司法解釋均未規(guī)定法院向行政機(jī)關(guān)或當(dāng)事人提出建議時(shí),可中止訴訟的審理。行政機(jī)關(guān)對(duì)于法院要求復(fù)查行政行為的建議,因無(wú)法定復(fù)查和答復(fù)的義務(wù),而不作任何回應(yīng),已是司空見(jiàn)慣的事。當(dāng)事人有權(quán)處分其實(shí)體權(quán)利和訴訟權(quán)利,有權(quán)決定是否將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提交法院依不同的訴訟程序予以解決。因此法院的建議可能無(wú)任何積極的意義,相反極易延長(zhǎng)甚至超過(guò)法定審理期限和結(jié)案不能。
行政訴訟法第56條規(guī)定,只有法院認(rèn)為行政機(jī)關(guān)的主管人員、直接責(zé)任人員違反政紀(jì)的和有犯罪行為的,才能將有關(guān)材料移送有關(guān)部門(mén)處理,但未規(guī)定將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移送相關(guān)審判庭進(jìn)行審理;民事訴訟法亦未規(guī)定有關(guān)內(nèi)部移送的內(nèi)容,可見(jiàn),內(nèi)部移送式缺乏法律依據(jù);同時(shí),內(nèi)部移送式違反了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中的不訴不理的基本原則,屬于公權(quán)不當(dāng)干涉私權(quán)。法院在審理被移送的其他爭(zhēng)議時(shí),若原告不提出訴訟請(qǐng)求、不出庭、不舉證等,將使該爭(zhēng)議的審理無(wú)法進(jìn)行與終結(jié)。
筆者認(rèn)為,正確處理關(guān)聯(lián)的訴訟與爭(zhēng)議的辦法是已審理訴訟的審判庭代表法院履行告知義務(wù),告知提出爭(zhēng)議方應(yīng)對(duì)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另行提訟;提出爭(zhēng)議方收到告知書(shū)后,將承擔(dān)相應(yīng)的法律后果。行政訴訟法第34條第1款和民事訴訟法第64條第1款均規(guī)定,當(dāng)事人有責(zé)任向法院提供證據(jù),包括主張和反駁證據(jù);同時(shí),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第3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行政訴訟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第8條均規(guī)定,法院應(yīng)當(dāng)向當(dāng)事人告知舉證范圍、舉證時(shí)限和逾期提供證據(jù)的法律后果,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實(shí)質(zhì)是決定訴訟結(jié)果的證據(jù)的效力認(rèn)定問(wèn)題,屬于當(dāng)事人提供主張或反駁證據(jù)的范疇,據(jù)此法院應(yīng)履行告知提出爭(zhēng)議方以另行方式完成舉證責(zé)任的義務(wù)。告知書(shū)向提出爭(zhēng)議方送達(dá)后,即可產(chǎn)生法律效力。當(dāng)事人在告知的期限內(nèi)未行使訴權(quán),法院可以對(duì)作為訴訟的證據(jù)的爭(zhēng)議的證明力予以認(rèn)定,并對(duì)訴訟作出裁判。該方式克服了拖延訴訟時(shí)間、無(wú)法律依據(jù)等弊端。該方式在司法實(shí)際操作中,還須解決以下問(wèn)題:1、告知應(yīng)以書(shū)面形式作出,并向當(dāng)事人送達(dá),告知書(shū)的內(nèi)容為當(dāng)事人應(yīng)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內(nèi)就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另行提訟,否則,將承擔(dān)對(duì)其不利的法律后果。2、告知另行提訟的時(shí)間,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嚴(yán)格執(zhí)行案件審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規(guī)定》第9條第5項(xiàng)規(guī)定,以一個(gè)月為宜。因?yàn)閰⒄丈鲜鲆?guī)定,該期限不計(jì)入審理期限。3、法院履行告知后,因無(wú)法律依據(jù),不能立即中止訴訟的審理,當(dāng)事人另行并被法院立案受理后,才能中止訴訟。4、若當(dāng)事人未在告知的期限內(nèi)另行,但在法院對(duì)訴訟作出裁判后,在法定的期限內(nèi)對(duì)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另行的,法院對(duì)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的,仍應(yīng)予以立案受理并依法作出裁判。因關(guān)聯(lián)的爭(zhēng)議的裁判結(jié)果致使前一訴訟被改判或再審的,應(yīng)依照或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第46條規(guī)定,前一訴訟的裁判不屬于錯(cuò)誤裁判,且由被告知方承擔(dān)因此增加的有關(guān)訴訟的合理費(fèi)用以及因此而擴(kuò)大的一當(dāng)事人的直接損失,以懲罰被告知方怠于行使權(quán)利。
注釋?zhuān)?/p>
①黃江:《行政法理論與審判實(shí)務(wù)研究-全國(guó)法院系統(tǒng)第十二屆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論文選》中的《行政、民事關(guān)聯(lián)訴訟的法律思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420頁(yè)。
②張步洪、王萬(wàn)華:《行政訴訟法律解釋判例述評(píng)》,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1版,第555頁(yè)。
③同②。
④同①,第422頁(yè)。
⑤江必新:《中國(guó)行政訴訟制度之發(fā)展-行政行政訴訟司法解釋解讀》,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96頁(yè)。
⑥甘文:《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解之評(píng)論-理由、觀點(diǎn)與問(wèn)題》,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第174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關(guān)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行政訴訟法﹥?nèi)舾蓡?wèn)題的解釋》,中國(guó)城市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李國(guó)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行政訴訟證據(jù)若干問(wèn)題的規(guī)定﹥釋義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3、江必新:《中國(guó)行政訴訟制度之發(fā)展-行政訴訟司法解釋解讀》,金城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4、甘文:《行政訴訟司法解釋之評(píng)論-理由、觀點(diǎn)與問(wèn)題》,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
5、張步洪、王萬(wàn)華:《行政訴訟法律解釋與判例述評(píng)》,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北京第1版。
6、全國(guó)高等教育自學(xué)考試指導(dǎo)委員會(huì)組編(羅豪才主編):《行政法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3月第3版重排版。
7、劉善春:《行政訴訟原理及名案解讀》,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北京第1版。
8、方世榮主編:《行政訴訟法案例教程》,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第3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一、案例引出問(wèn)題:舉證責(zé)任如何分配
案情簡(jiǎn)介某公安局公安人員到某小區(qū)調(diào)查偷稅情況時(shí)與小區(qū)經(jīng)警李某發(fā)生爭(zhēng)執(zhí),公安局即派出干警到場(chǎng)拘傳李某,在拘傳過(guò)程中,公安人員與經(jīng)警發(fā)生糾纏,后把李某帶到公安局辦公室訊問(wèn)一直到下午,李某由于感覺(jué)不適被公安人員帶到骨科醫(yī)院檢查為頸椎骨質(zhì)增生及C6,椎體隱裂,該醫(yī)院給李某出的疾病證明為“頸部挫傷”。第二天,李某到省醫(yī)院檢查,診斷結(jié)果為:1.頸椎間盤(pán)突出并脊髓不完全性損傷;2.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李某當(dāng)即住院一個(gè)月后以被公安人員毆打致傷為由訴至法院,請(qǐng)求判令公安局賠償。訴訟過(guò)程中,公安局認(rèn)為其公安人員未毆打李某,李某的頸椎間盤(pán)突出是慢性病,并非毆打所致,并出示當(dāng)時(shí)在場(chǎng)的公安人員證詞,認(rèn)為李某無(wú)證據(jù)證明是公安人員毆打李某。李某認(rèn)為行政訴訟應(yīng)由被告舉證,其只要出示傷情即可。法院曾委托鑒定,鑒定部門(mén)無(wú)法作出頸椎間盤(pán)突出是或不是外傷所致的肯定性結(jié)論。
法官的推理和處置法官的結(jié)論性意見(jiàn)為:公安局承擔(dān)全部賠償責(zé)任。理由如下:
1.公安機(jī)關(guān)違法行政致傷李某的可能性推定。李某是在被公安人員帶去訊問(wèn)的當(dāng)天下午即感覺(jué)不適,脖子不能動(dòng),且醫(yī)院有“頸部挫傷”、“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的證明,這些情況都表明存在公安機(jī)關(guān)違法行政致傷李某的可能性;
2.不排除李某傷(病)并非由公安機(jī)關(guān)違法行政所致的可能性。由于李某住院治療是因頸椎間盤(pán)突出,但頸椎間盤(pán)突出一般是一種慢性病,它有可能是李某本身就有這種病,碰巧此時(shí)發(fā)作。由于原告未對(duì)此舉證,被告又無(wú)法提供這方面的證據(jù),所以無(wú)法查清。
3.公安機(jī)關(guān)負(fù)舉證責(zé)任,未很好履行即敗訴。行政訴訟法第32條明確規(guī)定,行政訴訟中的舉證責(zé)任由被告行政機(jī)關(guān)承擔(dān)。在行政執(zhí)法中,公民和行政機(jī)關(guān)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李某為何頸部挫傷、頸椎間盤(pán)突出,原告不能提供證據(jù),只能靠被告舉證。而被告舉不出李某不是因公安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違法行政行為致傷的證據(jù),故應(yīng)承擔(dān)敗訴責(zé)任。
舉證責(zé)任由誰(shuí)負(fù)鑒于原告的訴訟請(qǐng)求,事件的終極性爭(zhēng)議點(diǎn)在于,公安機(jī)關(guān)應(yīng)否承擔(dān)賠償義務(wù)。可是,這個(gè)法律問(wèn)題的解決依賴(lài)于一個(gè)事實(shí)認(rèn)定,即李某是否系公安機(jī)關(guān)的違法公務(wù)行為致傷。為澄清此事實(shí)上的疑問(wèn),法官需要圍繞兩個(gè)方面的若干證據(jù):其一,公安機(jī)關(guān)有沒(méi)有在執(zhí)行職務(wù)過(guò)程中實(shí)施違法行為;其二,若答案是肯定的,違法行為是否導(dǎo)致李某頸椎間盤(pán)突出的直接原因。這一點(diǎn)法院無(wú)法查清。于是問(wèn)題轉(zhuǎn)化為,訴訟兩方當(dāng)事人究竟哪一方必須提出充足的證據(jù)以說(shuō)服法官支持其主張,否則,該方當(dāng)事人就要承擔(dān)最終敗訴的后果。這亦即我們通常所理解的舉證責(zé)任的分配問(wèn)題。
法官在本案中的選擇是把舉證責(zé)任配置到行政機(jī)關(guān)一方,主要理由有兩個(gè):其一,《行政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其二,行政機(jī)關(guān)與公民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不平等,李某的傷情只有被告才能提供。暫且不論《行政訴訟法》第32條規(guī)定在立法技術(shù)上的缺陷。就第二個(gè)理由而言,行政機(jī)關(guān)與公民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不平等具有相當(dāng)程度的普遍性,如果由此推論被告負(fù)舉證責(zé)任,這一配置原則豈不成為絕對(duì)的?針對(duì)行政賠償訴訟中的舉證責(zé)任問(wèn)題,不少人認(rèn)為原告應(yīng)負(fù)擔(dān)損害事實(shí)的舉證責(zé)任,包括損害事實(shí)的存在、損害由被告違法公務(wù)引起、損害的程度等。最高人民法院也在《關(guān)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的若干規(guī)定》中作出規(guī)定,“原告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對(duì)自己的主張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被告有權(quán)提供不予賠償或者減少賠償?shù)臄?shù)額方面的證據(jù)。”根據(jù)1999年11月24日通過(guò)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行政訴訟法>若干問(wèn)題的解釋》(以下簡(jiǎn)稱(chēng)《若干解釋》)第27條第3項(xiàng)規(guī)定,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必須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證明因受被訴行為侵害而造成損失的事實(shí)。就是說(shuō),根據(jù)學(xué)理和最高權(quán)威的司法解釋?zhuān)景傅脑鎽?yīng)對(duì)法院所需要的上述兩方面證據(jù)負(fù)擔(dān)舉證責(zé)任。如何說(shuō)學(xué)理、司法解釋與本案審判實(shí)踐的這一矛盾?在舉證責(zé)任問(wèn)題上,學(xué)理、司法解釋和本案的審判實(shí)踐是否都有值得檢討之處呢?
二、舉證責(zé)任的分配模式
任何法制社會(huì)所追求的最高價(jià)值都是社會(huì)秩序的良性穩(wěn)定。社會(huì)秩序的良性穩(wěn)定意味著社會(huì)成員在法律不禁止的范圍內(nèi)自由地工作、生活并以此享受自己的那份快樂(lè),社會(huì)成員之間沒(méi)有沖突和爭(zhēng)執(zhí)。在正常狀態(tài)下,每個(gè)人都應(yīng)當(dāng)被推定為是自由的,即不存在對(duì)他人特定的責(zé)任或義務(wù),誰(shuí)對(duì)這種推定提出挑戰(zhàn),誰(shuí)就應(yīng)當(dāng)提供充分的根據(jù),即負(fù)舉證責(zé)任。通常,對(duì)被推定的自由狀態(tài)提出挑戰(zhàn)者所提出的事實(shí)是一種積極的事實(shí),即認(rèn)為他人應(yīng)對(duì)他承擔(dān)特別義務(wù)或責(zé)任的一個(gè)事實(shí)是存在的。如果我們把挑戰(zhàn)者提出的一個(gè)事實(shí)存在的主張稱(chēng)為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把否定這個(gè)積極主張的事實(shí)存在的主張稱(chēng)作消極性事實(shí)主張。那么,最初提出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人在法律程序中就應(yīng)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就法律所推定的事實(shí)進(jìn)行爭(zhēng)執(zhí)者,對(duì)其主張事實(shí)負(fù)舉證責(zé)任,積極性事實(shí)如果無(wú)特別的推進(jìn)情形,應(yīng)認(rèn)為消極性事實(shí)受推定而存在,主張消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人免除舉證責(zé)任,其舉證責(zé)任由主張積極性事實(shí)的人承擔(dān)。
提出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人應(yīng)當(dāng)就其主張?zhí)峁┏浞值淖C據(jù),但這并不意味著,對(duì)積極性事實(shí)持否定意見(jiàn)者就沒(méi)有任何舉證責(zé)任。在訴訟中,如果一個(gè)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被充分的證據(jù)所證實(shí),如果對(duì)積極性事實(shí)持否定意見(jiàn)的當(dāng)事人只能提出簡(jiǎn)單的否定意見(jiàn)而不能提供相應(yīng)的反駁證據(jù),那么敗訴的后果將由對(duì)積極性事實(shí)持否定意見(jiàn)的一方當(dāng)事人承擔(dān)。從提供反駁證據(jù)的必要性及其與訴訟結(jié)果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上看,對(duì)積極性事實(shí)持否定意見(jiàn)的當(dāng)事人也負(fù)有相應(yīng)的舉證責(zé)任。比如說(shuō),公安局提出了當(dāng)事人王五毆打他人、應(yīng)受拘留處罰的積極性事實(shí),并向法庭提供受害人的陳述、旁觀群眾的證詞及醫(yī)院診斷證明等充分的證據(jù),這時(shí)公安局的舉證責(zé)任已初步履行,只在王五不能以有力的證據(jù)否定公安局提供的證據(jù),王五就要承擔(dān)敗訴后果,王五的這種如不提供證據(jù)就要承擔(dān)敗訴后果的責(zé)任與公安局的不能提供相應(yīng)證據(jù)就要承擔(dān)敗訴后果的責(zé)任在性質(zhì)上是一樣的,也是一種舉證責(zé)任。
但是,在上述情況下,即使同樣為舉證責(zé)任,提出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當(dāng)事人與提出消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當(dāng)事人的舉證責(zé)任所要達(dá)到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同。提出“王五實(shí)施了毆打他人的違法行為”這一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當(dāng)事人必須提供“充分的”即足以說(shuō)服人的證據(jù),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證明體系,類(lèi)似于證明“所有的天鵝都是白色的”這樣全稱(chēng)判斷,只要他的證據(jù)不能達(dá)到充分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能構(gòu)成足以使人信服的證明體系,他的舉證責(zé)任就沒(méi)有完成,其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就不能成立,因而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敗訴后果而無(wú)需對(duì)方當(dāng)事人再承擔(dān)什么舉證責(zé)任。但是,如果提出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當(dāng)事人提供了充分的證據(jù)并形成足以讓人信服的證明體系,持消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當(dāng)事人的舉證責(zé)任也就相應(yīng)產(chǎn)生了。只是應(yīng)達(dá)到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同罷了。既然持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當(dāng)事人提供證據(jù)應(yīng)達(dá)到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是證據(jù)充分、令人信服;那么持相反意見(jiàn)的當(dāng)事人只要打破對(duì)方的證明體系,使對(duì)方的證據(jù)不能達(dá)到令人信服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他的否定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就達(dá)到了,這個(gè)證明標(biāo)準(zhǔn)類(lèi)似于只要能夠證明有一只天鵝是黑的或黃的不是白的,駁倒“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這個(gè)全稱(chēng)判斷的任務(wù)就完成了。所以說(shuō),上述兩種舉證責(zé)任的不同在于應(yīng)達(dá)到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同,在訴訟中控訴方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要達(dá)到事實(shí)清楚,證據(jù)確實(shí)充分;而辯護(hù)方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則只要對(duì)控方的指控提出合理的懷疑,起到說(shuō)明控方的指控沒(méi)有達(dá)到相應(yīng)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的功效,從而使指控不能成立,以達(dá)到辯護(hù)的目的。由于對(duì)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舉證責(zé)任應(yīng)達(dá)到使人信服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所以在西方證據(jù)法學(xué)上把這種舉證責(zé)任叫“說(shuō)服責(zé)任”;而持消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當(dāng)事人的舉證責(zé)任只限于能夠使對(duì)方“令人信服”的證明標(biāo)準(zhǔn)不能達(dá)到,并以此逼迫持積極性事實(shí)主張的當(dāng)事人繼續(xù)提供證據(jù),推動(dòng)對(duì)事實(shí)的證明向深層次發(fā)展,所以這種舉證責(zé)任在西方證據(jù)法學(xué)上叫“推進(jìn)責(zé)任”。說(shuō)服責(zé)任是對(duì)于裁判結(jié)論的要求而言的,既是初步的,也是根本的,同時(shí)也是推進(jìn)責(zé)任的基礎(chǔ);推進(jìn)責(zé)任對(duì)裁判結(jié)論而言是關(guān)鍵性的,只要這種責(zé)任不再“推進(jìn)”,裁判結(jié)論將根據(jù)說(shuō)服責(zé)任的履行情況產(chǎn)生,同時(shí),推進(jìn)責(zé)任也是逼迫對(duì)于進(jìn)一步履行說(shuō)服責(zé)任的內(nèi)在動(dòng)力。當(dāng)然,雙方當(dāng)事人的舉證責(zé)任均不限于一次或兩次完成,而是按照“說(shuō)服責(zé)任-推進(jìn)責(zé)任-說(shuō)服責(zé)任-推進(jìn)責(zé)任……”的循環(huán)方式不斷向前推進(jìn)的。可以說(shuō),在法律程序中,沒(méi)有哪一方當(dāng)事人可以不負(fù)舉證責(zé)任的,除非他愿意接受不利訴訟后果。
我國(guó)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的被告對(duì)其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dān)的舉證責(zé)任,就是說(shuō)服責(zé)任。說(shuō)服責(zé)任是推進(jìn)責(zé)任的基礎(chǔ)。但是,我國(guó)行政訴訟法沒(méi)有關(guān)于推進(jìn)責(zé)任的規(guī)定,而推進(jìn)責(zé)任不僅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實(shí)踐中根本無(wú)法回避的。立法不完善的問(wèn)題給實(shí)踐中的法官正確把握千變?nèi)f化的舉證責(zé)任帶來(lái)了很大困難。
三、行政訴訟舉證責(zé)任的分配是否“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
當(dāng)前,關(guān)于行政訴訟舉證責(zé)任與“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原則之間關(guān)系的討論頗多,主要有三種不同觀點(diǎn):第一種觀點(diǎn)是主導(dǎo)觀點(diǎn),即在行政訴訟中“被告負(fù)舉證責(zé)任”;第二種觀點(diǎn)認(rèn)為被告只對(duì)其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負(fù)舉證責(zé)任,其他問(wèn)題仍采取“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原則;第三種觀點(diǎn)則認(rèn)定行政訴訟舉證責(zé)任是“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一般原則在行政訴訟中的體現(xiàn)。下面對(duì)三種觀點(diǎn)作評(píng)價(jià),以闡明筆者觀點(diǎn)。
首先,批評(píng)“行政訴訟被告負(fù)舉證責(zé)任的觀點(diǎn)是片面的,其理由如下:1.《行政訴訟法》并未規(guī)定行政機(jī)關(guān)應(yīng)對(duì)其不作為負(fù)舉證責(zé)任;2.被告為其具體行政行為舉證達(dá)到一定程度之后,原告還是要負(fù)舉證責(zé)任,否則只能是敗訴,訴訟中舉證責(zé)任在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的轉(zhuǎn)移不容否定;3.行政案件立案之前,行政相對(duì)人必須負(fù)證明其符合一定程序要件之舉證責(zé)任,否則,原告必然被裁定駁回起訴或判決駁回訴訟請(qǐng)求;4.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如不舉證,只能是敗訴。
那么,是否可以把《行政訴訟法》的規(guī)定解釋為:被告對(duì)具體行政行為合法性負(fù)舉證責(zé)任是“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的倒置,而其他問(wèn)題仍遵循這一原則呢?第三種觀點(diǎn)的答案是否定的。因?yàn)椋趯?duì)被告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提起行政訴訟案件中,起訴雖然由行政相對(duì)人提起,但法院要審查的卻不是行政相對(duì)人行為的合法性,而是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而具體行政行為是由被告作出的,是被告“主張”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由被告為之舉證正是“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的一般舉證原則的體現(xiàn)。行政爭(zhēng)議與民事?tīng)?zhēng)議不同。民事?tīng)?zhēng)議中,主張實(shí)體請(qǐng)求的一方若被對(duì)方拒絕,只能提起民事訴訟;在訴訟中,舉證責(zé)任最初應(yīng)由實(shí)體請(qǐng)求的主張方承擔(dān),被主張方提出的是對(duì)主張方實(shí)體請(qǐng)求的抗辯,此時(shí)不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行政爭(zhēng)議中,若實(shí)體請(qǐng)求由行政相對(duì)人提起(包括申請(qǐng)行政機(jī)關(guān)作為和要求行政賠償),則情況同于民事訴訟;若實(shí)體請(qǐng)求由行政機(jī)關(guān)提起,行政機(jī)關(guān)可自行實(shí)現(xiàn)其實(shí)體主張。在行政訴訟中,原告實(shí)質(zhì)上是對(duì)被告在行政爭(zhēng)議中提出的實(shí)體請(qǐng)求的抗辯,被告應(yīng)首先為其實(shí)體請(qǐng)求舉證,具體行政行為本來(lái)就是行政機(jī)關(guān)的主張。以上理論借鑒及假設(shè)的適用已經(jīng)表明,“行政訴訟中被告負(fù)證責(zé)任”的觀點(diǎn)是片面的,但與第三種觀點(diǎn)的論證過(guò)程不同,筆者更傾向于針對(duì)具體爭(zhēng)議點(diǎn)的具體分析,即深入其個(gè)性化的具體情境。例如,第三種觀點(diǎn)以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負(fù)舉證責(zé)任為由,批評(píng)單一的被告負(fù)舉證責(zé)任模式。可是,正如前文具體分析所示,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和被告都可能負(fù)擔(dān)說(shuō)服責(zé)任。第三種觀點(diǎn)把行政管理過(guò)程和行政訴訟過(guò)程聯(lián)系起來(lái),作為分配行政訴訟舉證責(zé)任的基礎(chǔ),的確有獨(dú)到之處。不過(guò),以為在行政管理過(guò)程中是行政機(jī)關(guān)主張并自行實(shí)現(xiàn)其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jī)關(guān)在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shí)負(fù)責(zé)舉證,因而在行政訴訟中的主張方和舉證方就是行政機(jī)關(guān)這樣的論證是否過(guò)于簡(jiǎn)單?首先,在行政程序中,并非除了申請(qǐng)行政機(jī)關(guān)作為和要求行政賠償之外的情形都是由行政機(jī)關(guān)負(fù)擔(dān)說(shuō)服責(zé)任。這可以參考一下美國(guó)法院的判例:“在一個(gè)牽涉內(nèi)陸礦場(chǎng)運(yùn)營(yíng)申訴委員會(huì)的案件中,該行政機(jī)關(guān)負(fù)責(zé)提供表面上確鑿的證據(jù),來(lái)證明以不安全運(yùn)營(yíng)為由下令一家煤礦停業(yè)是合理的,但是,證明煤礦運(yùn)營(yíng)是安全的責(zé)任則由業(yè)主承擔(dān)。在此案中,法院的部分推理是:該煤礦業(yè)主最熟悉煤礦的運(yùn)營(yíng)情況,在象這樣的案件中,對(duì)事實(shí)有特殊了解的人負(fù)擔(dān)舉證責(zé)任是適當(dāng)?shù)摹!逼浯危姓芾磉^(guò)程和行政訴訟過(guò)程在相當(dāng)程度上是彼此獨(dú)立的。經(jīng)歷行政程序之后,行政訴訟程序完全是由原告認(rèn)為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侵犯其合法權(quán)益所引起的。原告在提起訴訟請(qǐng)求時(shí)要求法官認(rèn)定具體行政行為違法,難道不是一種主張?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對(duì)人反駁行政行為的理由,提出自己的證據(jù)要求行政機(jī)關(guān)考慮,此時(shí)他處于抗辯方的境地;進(jìn)入行政訴訟程序后,他已經(jīng)轉(zhuǎn)而處于請(qǐng)求方的地位,行政機(jī)關(guān)則成為抗辯方。不能否認(rèn)行政訴訟原告是請(qǐng)求方,其也是在主張對(duì)自己有利的事實(shí),假如再簡(jiǎn)單套用“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原則幾乎是絕對(duì)的。但是,由此強(qiáng)調(diào)“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原則,我們豈非也可以得出原告要承擔(dān)舉證責(zé)任的結(jié)論?最后,無(wú)論是原告還是被告,為了獲得勝訴,都會(huì)在訴訟過(guò)程中主張對(duì)自己有利的事實(shí),都必須就此負(fù)舉證責(zé)任。只是在不同的特定爭(zhēng)議點(diǎn)上,基于政策和公正的考量,兩方當(dāng)事人的舉證負(fù)擔(dān)輕重不同。
任何一方當(dāng)事人,只要提出一種事實(shí)主張,都至少必須承擔(dān)推進(jìn)責(zé)任(提證責(zé)任),否則其主張被法官或任何有理性人承認(rèn)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而且總有一方當(dāng)事人要為其主張承擔(dān)說(shuō)服責(zé)任。如果從這個(gè)意義上而言,“誰(shuí)主張,誰(shuí)舉證”原則,對(duì)于理論發(fā)展和法律實(shí)務(wù)都沒(méi)有什么重要價(jià)值而言,因?yàn)槲覀冞€是無(wú)法弄清:在某個(gè)特定爭(zhēng)議點(diǎn)上,哪一方當(dāng)事人只需為其主張的事實(shí)承擔(dān)推進(jìn)責(zé)任,而哪一方當(dāng)事人必須為其主張的事實(shí)承擔(dān)說(shuō)服責(zé)任?
第4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關(guān)鍵詞:行政程序理性原則正當(dāng)性
在中國(guó)法治國(guó)家建設(shè)中,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已經(jīng)沒(méi)有爭(zhēng)議。依法行政不僅要求政府權(quán)力的行使受實(shí)體法規(guī)范的制約,在更大程度上意味著政府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公正、公平、公開(kāi)的行政程序行使其權(quán)力。從這一意義上看,行政程序法制度的改革與完善乃是目前法治國(guó)家建設(shè)所面臨的一項(xiàng)迫切要求。在實(shí)踐中,行政程序法制度的改革已經(jīng)逐步展開(kāi),制定統(tǒng)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呼聲越來(lái)越高。但是在我國(guó)行政程序的改革中,程序理性不論作為一項(xiàng)原則還是相應(yīng)的程序制度,都沒(méi)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本文試對(duì)這一問(wèn)題進(jìn)行探討。
一、程序理性的中心問(wèn)題
程序理性亦即程序的合理性。程序的合理性不僅僅指通過(guò)法律程序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從實(shí)體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實(shí)體正義的,而且更主要的指一個(gè)法律程序產(chǎn)生該結(jié)果的過(guò)程是一個(gè)通過(guò)事實(shí)、證據(jù)以及程序參與者之間平等對(duì)話(huà)與理性說(shuō)服的過(guò)程。換言之,程序在結(jié)構(gòu)上應(yīng)當(dāng)遵循通過(guò)理性說(shuō)服和論證作出決定的要求,不是恣意、專(zhuān)斷地作出決定。因此可以認(rèn)為,程序理性是程序正義的一項(xiàng)基本要求。
就行政程序而言,程序理性的中心問(wèn)題是通過(guò)一系列的程序機(jī)制(包括程序原則和程序制度)限制自由裁量權(quán),盡可能地保證自由裁量權(quán)行使的理性化。美國(guó)著名的行政法學(xué)者K.C.戴維斯曾經(jīng)指出,在行政活動(dòng)過(guò)程中,行政機(jī)關(guān)所擁有的自由裁量權(quán)可以說(shuō)是無(wú)所不在的。不論是行政機(jī)關(guān)對(duì)事實(shí)的認(rèn)定還是對(duì)法律規(guī)范的理解,都存在不同程度自由裁量的空間(注:戴維斯教授在他的《自由裁量的正義》一書(shū)中,對(duì)行政過(guò)程中存在自由裁量的語(yǔ)境進(jìn)行了詳細(xì)分析。在這一基礎(chǔ)上,他進(jìn)一步探討了對(duì)自由裁量權(quán)進(jìn)行制約的法律途徑。參見(jiàn)K.C.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APreliminaryInquiry,UniversityofllinoisPress1969,chpter1.)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只要有自由裁量權(quán)的存在和行使,就有產(chǎn)生恣意的可能性。(注:SeeRobertE.Goodin,ReasonsforWelfare:ThePoliticalTheoryofWelfareStat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p.p.193~204.)正因?yàn)槿绱耍杂刹昧繖?quán)的問(wèn)題總是伴隨著權(quán)力應(yīng)當(dāng)理性行使的要求。“福利國(guó)家”和積極行政的興起,使現(xiàn)代國(guó)家的行政權(quán),包括自由裁量權(quán)大大增強(qiáng)。自由裁量權(quán)的中心是選擇,而選擇的基礎(chǔ)總是與判斷相聯(lián)系,選擇與判斷又總是以一定的程序進(jìn)行的。因此通過(guò)法律程序的機(jī)制使自由裁量權(quán)的行使理性化,對(duì)于程序公正而言就顯得更為重要。
依其“自由裁量”程度的不同,我們可以將自由裁量權(quán)概括地分為三種。根據(jù)羅納德。德沃金教授的分析:(1)某人擁有自由裁量權(quán),假如他在作出決定時(shí)必須先要對(duì)某一事實(shí)或狀態(tài)作出判斷的話(huà),(注:SeeRonaldDworkin,TakingRight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p.31~32.)這種意義上的自由裁量權(quán)筆者稱(chēng)之為“判斷型自由裁量權(quán)”。例如,當(dāng)某人被要求從一棵果樹(shù)上摘下“最熟的一個(gè)蘋(píng)果”時(shí),他必須先判斷哪一個(gè)蘋(píng)果是最熟的。(2)某人擁有自由裁量權(quán),假如他可以在某個(gè)被準(zhǔn)許的范圍內(nèi)進(jìn)行選擇的話(huà),(注:RonaldDworkin,TakingRights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32.SeealsoK.C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1972,P.91.)筆者將這種自由裁量權(quán)稱(chēng)為“弱選擇型自由裁量權(quán)”,因?yàn)檫@是一種受特定標(biāo)準(zhǔn)限制的選擇。例如,如果某人被要求從樹(shù)上摘下一個(gè)熟蘋(píng)果,那么他可以在若干個(gè)蘋(píng)果之間進(jìn)行選擇。(3)某人擁有自由裁量權(quán),假如他可以不受限制地作出選擇或判斷,(注:RonaldDworkin,TakingRight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32.)這種自由裁量權(quán)可以被稱(chēng)為“強(qiáng)選擇型自由裁量權(quán)”,因?yàn)樗鼪](méi)有給出對(duì)選擇進(jìn)行限制的任何具體標(biāo)準(zhǔn)。例如,如果某人僅僅被要求從樹(shù)上摘一個(gè)蘋(píng)果,他實(shí)際上可以選擇摘任何一個(gè)蘋(píng)果。
以上對(duì)自由裁量權(quán)種類(lèi)的簡(jiǎn)要分析表明,隨著對(duì)自由裁量中判斷和選擇之標(biāo)準(zhǔn)的具體化和細(xì)致化,我們可以從實(shí)體方面對(duì)自由裁量權(quán)的行使進(jìn)行控制。但是這種控制是相當(dāng)有限的,因?yàn)樽杂刹昧繖?quán)設(shè)定的本來(lái)目的就是容許判斷和選擇的空間,如果標(biāo)準(zhǔn)越具體,判斷與選擇的空間就越小,當(dāng)標(biāo)準(zhǔn)具體到一定程度時(shí),從邏輯上講,選擇實(shí)際上是唯一的。因此,從實(shí)體方面對(duì)自由裁量權(quán)進(jìn)行控制盡管是必要和可行的,但也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兩難。法律程序的控制可以消解這種兩難困境。程序允許選擇,同時(shí)又限制恣意。法律程序可以滿(mǎn)足選擇理性化的基本要求。(注:從法律程序的結(jié)構(gòu)上看,程序所要限制的是選擇的恣意,而非選擇本身。法律程序要求程序主持者和程序的參與者通過(guò)理性對(duì)話(huà)、說(shuō)服和論證而為他們的選擇與判斷提供證明,從而可以使選擇或決定更加合理。在這一過(guò)程中,恣意和專(zhuān)橫可以得到抑制。關(guān)于法律程序促進(jìn)選擇過(guò)程理性化的進(jìn)一步討論,參見(jiàn)季衛(wèi)東:《程序比較論》,《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1期,第5頁(yè)。)其最主要的機(jī)制可以歸結(jié)為兩個(gè)方面:第一,給出所作決定的理由;第二,程序在結(jié)構(gòu)上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以下對(duì)這兩方面的問(wèn)題作扼要探討。
二、說(shuō)明理由
當(dāng)裁判者通過(guò)一個(gè)程序活動(dòng)而作出決定時(shí),他應(yīng)當(dāng)說(shuō)明作出該決定的理由。說(shuō)明理由的必要性首先可以從決定的實(shí)體合理性角度來(lái)進(jìn)行闡釋?zhuān)划?dāng)某個(gè)決定是由一系列的理由而可以從邏輯上得到證明時(shí),決定的實(shí)體合理性也可以得到證明。但是說(shuō)明理由的要求并不僅僅是實(shí)體合理性的要求。從法律程序的運(yùn)作過(guò)程看,理性的人們?cè)谧鞒鰶Q定之前必然將考慮一系列的事實(shí)和法律因素,這些因素構(gòu)成決定的理由,如果裁判者在作出決定的程序中沒(méi)有說(shuō)明這些理由,人們就可能認(rèn)為已作出的決定沒(méi)有理由,缺乏客觀和理性的考量,甚至只是權(quán)力恣意行使的結(jié)果-不論該決定在實(shí)體上是否合理。可以想象,假如一個(gè)法律程序不要求決定者說(shuō)明所作決定的理由,人們將不可避免地對(duì)該程序的合理性并進(jìn)而對(duì)公正性喪失信心。
(一)說(shuō)明理由的意義
對(duì)于程序正義的實(shí)現(xiàn)來(lái)說(shuō),說(shuō)明理由的核心意義在于,對(duì)程序操作過(guò)程中的自由裁量權(quán)進(jìn)行一種理性的控制,促使人們建立起對(duì)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的信心。具體說(shuō),說(shuō)明理由有以下意義:(1)增強(qiáng)人們對(duì)決定合理性的信心,因?yàn)橹辽僭谛问缴纤砻鳑Q定是理性思考的結(jié)果,而不是恣意。人們對(duì)這樣的程序有理由予以信任。(2)對(duì)于那些對(duì)決定不滿(mǎn)而準(zhǔn)備提起申訴的當(dāng)事人來(lái)說(shuō),說(shuō)明理由可以使他們認(rèn)真考慮是否要申訴,以何種理由申訴。特別是在決定非由全體一致同意的情況下,少數(shù)人的不同或反對(duì)意見(jiàn)更可以為當(dāng)事人提供關(guān)于決定形成的必要信息,可以使決定中可能存在的錯(cuò)誤暴露出來(lái);對(duì)主持復(fù)審的主體來(lái)說(shuō),情況也同樣如此。(3)讓將要受到?jīng)Q定影響的當(dāng)事人了解作出該決定的理由,體現(xiàn)了程序公開(kāi)這一價(jià)值,也意味著對(duì)當(dāng)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與尊嚴(yán)的尊重。一個(gè)針對(duì)當(dāng)事人的、拒絕說(shuō)明理由的決定等于把人當(dāng)做客體,而不是可以理性思考的平等的主體。(4)對(duì)于裁判者來(lái)說(shuō),為自己作出的決定說(shuō)明理由,意味著他在行使權(quán)力、作出決定的過(guò)程中,必須排斥恣意、專(zhuān)斷、偏私等因素,因?yàn)橹挥锌陀^、公正的理由才能夠經(jīng)得起公開(kāi)的推敲,才能夠有說(shuō)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說(shuō)明理由是對(duì)自由裁量權(quán)進(jìn)行控制的一個(gè)有效機(jī)制。(5)對(duì)于一個(gè)決定來(lái)說(shuō),說(shuō)明理由不僅使人們知其然,而且可以使人們知其所以然。人們可以因此而進(jìn)一步知道為什么自己的行為會(huì)得到肯定或否定,因而他們可以更好地調(diào)整自己以后的行為。
由此,對(duì)于一個(gè)程序過(guò)程來(lái)說(shuō),說(shuō)明理由是一項(xiàng)基本要求,是法律程序體現(xiàn)正義的必要條件之一。英國(guó)行政法學(xué)者韋德強(qiáng)調(diào),無(wú)論如何,如果某個(gè)行政決定沒(méi)有說(shuō)明理由,行政機(jī)關(guān)將很難使這樣的決定正當(dāng)化。(注:H.W.R.Wade,AdministrativeLaw,5thedition,Oxford:ClarendonPress1982,p.p.373~374.)提供了理由的決定固然未必是準(zhǔn)確或體現(xiàn)了正義的,但沒(méi)有任何理由加以支持的決定僅僅從形式上看就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換言之,由于這樣的決定總是更容易與恣意和專(zhuān)斷相聯(lián)系,其正當(dāng)性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質(zhì)疑。
(二)作為程序公正基本要求的說(shuō)明理由制度
與程序中立和程序公正等要求不同的是,盡管說(shuō)明理由的要求對(duì)于程序正義的實(shí)現(xiàn)非常重要,當(dāng)代主要的人權(quán)法典以及關(guān)于公民權(quán)的一系列憲法性規(guī)定中,都未直接對(duì)此要求加以規(guī)定。(注:SeeUntiedNations1966;andEuropeanConventiononTheProtectionofHumanRightsandFundamentalFreedulms,1950.)雖在刑事訴訟中,一系列主要的人權(quán)公約都規(guī)定被告人必須享有了解權(quán),這意味著作出決定之前,他們有權(quán)了解有關(guān)的事實(shí)和被指控的罪名,他們有權(quán)了解針對(duì)他們的判決或決定,但知道有關(guān)的事實(shí)或決定是一回事,知道這些事實(shí)和決定是如何被確認(rèn)和如何產(chǎn)生的是另一回事。前者只是告知有關(guān)的事實(shí)和決定;后者則進(jìn)一步要求告知為何會(huì)有這樣的事實(shí)和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的對(duì)抗制審判程序中,特別是在由陪審團(tuán)作出裁決的刑事訴訟中,并不需要對(duì)所作的裁決說(shuō)明理由;在行政法領(lǐng)域,普通法院也曾經(jīng)主張:就普通法的要求看,如同法院一樣,行政機(jī)關(guān)并不具有為自己的決定說(shuō)明理由的義務(wù)。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并不存在一種為司法或行政決定說(shuō)明理由的義務(wù)”,而且自然正義原則也沒(méi)有說(shuō)明理由的要求。(注:S.A.deSmith,JudicialReviewofAdministrativeAction,4thedition,London:StvensandSons1980,pp.148~149.)在英國(guó),直到20世紀(jì)70年代,法院在Rv.GamingBoardforGreatBritain一案中(1970年)仍然認(rèn)為,該委員會(huì)根據(jù)有關(guān)法律而作出拒絕向當(dāng)事人頒發(fā)證書(shū)的決定時(shí),無(wú)需說(shuō)明理由。(注:SeeR.v.GamingBoardforGreatBritain;ExparteBenaim(1970)2QBat417.)在其后的Breenv.AmalgamatedEngineeringUnion一案中,丹寧爵士堅(jiān)持:無(wú)論何時(shí),只要公平原則要求說(shuō)明理由,行政機(jī)關(guān)就必須對(duì)其所作的決定說(shuō)明理由。他進(jìn)一步認(rèn)為,當(dāng)某項(xiàng)特權(quán)被否認(rèn)時(shí),行政機(jī)關(guān)無(wú)需說(shuō)明理由;但是如果被影響的客體不是特權(quán)而是一項(xiàng)人身、財(cái)產(chǎn)或自由權(quán),行政機(jī)關(guān)必須在作出相關(guān)的決定時(shí)說(shuō)明理由。(注:SeeBreenv.AmalgamatedEngineeringUnion,(1971)1QBat175.)在1975年的Pepysv.LondonTransportExecutive一案中,審理該案的上訴法院開(kāi)始在裁決中聲稱(chēng):“說(shuō)明理由乃是良好行政的基本要素之一。”(注:SeePepysv.LondonTransportExecutive,(1971)2QBat191.)在1983年的一個(gè)案件中,法院甚至認(rèn)為:“任何沒(méi)有說(shuō)明理由的行政決定都意味著違背了正義的要求,而且構(gòu)成一項(xiàng)記錄中的法律錯(cuò)誤。”(注:SeeRv.ImmigrationAppealTrbunal;ExparteKham(1983)2ALLER420AT423.)在美國(guó),學(xué)者將制作決定的基礎(chǔ)分為兩個(gè)方面:事實(shí)和理由。前者涉及到?jīng)Q定的事實(shí)依據(jù),后者主要與法律的適用、對(duì)政策的理解以及自由裁量權(quán)的行使相聯(lián)系。(注:K.C.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mparry1982,p.236.)關(guān)于事實(shí),聯(lián)邦最高法院曾經(jīng)認(rèn)為,在制作決定時(shí)必須指出該決定所依據(jù)的有關(guān)事實(shí),乃是一項(xiàng)憲法性要求。(注:PanamaRefiningCo.v.Ryan,293U.S.388,431~432,55S.Ct.241,253(1995)。)但是由于法院自身在作出決定時(shí)往往也未能開(kāi)示有關(guān)的事實(shí),因此,對(duì)事實(shí)的開(kāi)示實(shí)際上并沒(méi)有成為正當(dāng)法律程序的一項(xiàng)要求。(注:1930年以前,即美國(guó)衡平法院規(guī)則(FederalEquityRules)修改之前,衡平法院在作出判決時(shí)并不需要說(shuō)明有關(guān)的事實(shí)依據(jù)。即使根據(jù)現(xiàn)行的規(guī)則,法院在對(duì)某些案件作出裁決時(shí),也無(wú)需說(shuō)明有關(guān)的事實(shí)。參見(jiàn)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mpany1982,p.319.)盡管如此,不論是法院還是國(guó)會(huì)的立法都要求行政機(jī)關(guān)在制作將要影響相對(duì)人權(quán)利義務(wù)的決定時(shí),不僅要說(shuō)明有關(guān)的事實(shí)依據(jù),而且必須說(shuō)明理由。根據(jù)美國(guó)聯(lián)邦行政程序法第557條(c)項(xiàng)的規(guī)定,所有的行政決定都必須附有關(guān)于“事實(shí)、理由、結(jié)論以及相應(yīng)的依據(jù)”的說(shuō)明,除非“某些理由是不言自明的”。(注:Davis,Administrat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mpany1982,p.320,326.)但經(jīng)過(guò)修改的標(biāo)準(zhǔn)州行政程序法(MSA)以及大多數(shù)州的行政程序法都沒(méi)有規(guī)定行政決定必須說(shuō)明理由,盡管這些法律都要求必須闡明有關(guān)的事實(shí)。從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對(duì)一系列案件的裁決的態(tài)度看,說(shuō)明理由可以被認(rèn)為是一項(xiàng)普通法上的程序要求,只要制定法沒(méi)有與其相反的規(guī)定,說(shuō)明理由的要求就是應(yīng)當(dāng)?shù)玫綕M(mǎn)足的。“行政機(jī)關(guān)對(duì)于其采取行動(dòng)所依據(jù)的基礎(chǔ)應(yīng)當(dāng)能夠提供清楚的說(shuō)明和足夠的理由支持。這是行政法一項(xiàng)簡(jiǎn)單的,但卻是基本的規(guī)則”。(注:SECv.CheneryCorp.,318U.S.80,94,63S.Ct.454,462,(1943)。)
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行政機(jī)關(guān)必須為其所作的決定說(shuō)明理由,從一定程度上講,意味著人們對(duì)行政機(jī)關(guān)的活動(dòng)提出了比對(duì)法院更高的程序要求。(注:SeeGeoffreyAFlick,NaturalJustice:PrincltplesandPracticalApplication,2ndedltion,Buterworths1984,p.115.)在我看來(lái),之所以對(duì)行政程序強(qiáng)調(diào)這一要求,乃是因?yàn)榕c法院以及訴訟程序消極的特征不同,行政機(jī)關(guān)可以主動(dòng)地對(duì)相對(duì)人行使權(quán)力,行政程序因而具有主動(dòng)性;同時(shí),與法院相比,行政機(jī)關(guān)擁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權(quán)。權(quán)力量的大小應(yīng)當(dāng)與其所應(yīng)當(dāng)受到的制約強(qiáng)度成正比。因此,筆者贊成一些學(xué)者的主張:普通法上的自然正義原則應(yīng)當(dāng)暗示了第三條關(guān)于程序正義的自然法原則-為自己所作的決定說(shuō)明理由。(注:SeeD.J.Hewitt,NaturalJustice,Sydney:Butterworths1972,p.10;SeealsoPaulR.Verkuil,Crosscurrent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WilliamandMaryLawReview27,p.p.685~715.)從程序性權(quán)利的角度看,這一要求實(shí)際上驗(yàn)證了當(dāng)事人在程序中有了解“充分信息”的權(quán)利。很少有哪些程序語(yǔ)境能夠有足夠的依據(jù)對(duì)當(dāng)事人的這種權(quán)利予以剝奪或限制,因?yàn)椋?dāng)事人要求對(duì)影響到他們利益的決定說(shuō)明理由的權(quán)利,可被認(rèn)為是體現(xiàn)程序正義的一項(xiàng)基本要求。(注:SeeR.A.Macdonald,JudiclalReviewandProceduralFatrnessinAdministrativeLaw,McGillLawJournal25,p.p.520~564.)
值得注意的是,從實(shí)踐方面看,行政決定必須說(shuō)明事實(shí)和理由的要求主要是在正式的行政程序中發(fā)展起來(lái)的。在沒(méi)有正式聽(tīng)證的非正式程序中,這一要求往往難以得到滿(mǎn)足。(注:Davis,AdministraviveLawText,WestPublishingCompany1982,p.318.)但事實(shí)表明:在非正式程序中,闡明事實(shí)和理由的要求往往顯得益發(fā)重要,因?yàn)樵诜钦匠绦蛑懈枰獙?duì)自由載量權(quán)的恣意和專(zhuān)斷進(jìn)行制約。假如行政機(jī)關(guān)對(duì)于某個(gè)當(dāng)事人的申請(qǐng)僅僅告知“申請(qǐng)被拒絕了”,但卻不需要說(shuō)明為什么,那么恣意和專(zhuān)斷的空間至少在形式上就令人難以接受。程序在這種情況下看起來(lái)成了一個(gè)“黑箱”。因此筆者主張,即使在非正式程序或簡(jiǎn)易程序中,闡明事實(shí)、標(biāo)準(zhǔn)與理由的要求都是不能被“簡(jiǎn)化”的。
行政機(jī)關(guān)必須闡明行政決定所依據(jù)的事實(shí)和理由,這是一項(xiàng)程序性要求。至于其所闡明的事實(shí)和理由是否正確、合理,則主要是實(shí)體性問(wèn)題。因此,對(duì)于說(shuō)明理由的要求來(lái)說(shuō),是否說(shuō)明了理由是程序合法性問(wèn)題;而理由是否合理是實(shí)體合理性問(wèn)題。對(duì)于后者,法院在進(jìn)行司法審查時(shí)有權(quán)就理由的“合理性”予以審查。這也表明,程序正義的要求并不是正義實(shí)現(xiàn)的“充要條件”,而僅僅是必要條件。
三、形式理性
說(shuō)明理由的程序制度側(cè)重于從實(shí)體的標(biāo)準(zhǔn)和依據(jù)方面來(lái)制約自由裁量權(quán),形式理性則側(cè)重于從形式上對(duì)自由裁量權(quán)進(jìn)行制約,要求通過(guò)法律程序而作出的決定至少應(yīng)當(dāng)在形式上或邏輯上符合理性的要求。
在法律程序的運(yùn)作過(guò)程中,一些程序制度并不直接要求針對(duì)給定的條件應(yīng)作出何種內(nèi)容的決定,但它們要求在作出這些決定時(shí)在步驟或形式上應(yīng)遵循什么樣的規(guī)則。例如,在正式程序中,作出決定之前應(yīng)該進(jìn)行聽(tīng)證;如果聽(tīng)證不是在作出決定之前而是在其后進(jìn)行,則不論該決定實(shí)體上是否合理,就其形式上看就是不公正的,因?yàn)檫@樣的程序步驟違背了形式理性的要求。同樣,如果對(duì)于兩個(gè)實(shí)質(zhì)上相同的情況作出了不同的處理決定,人們也有理由對(duì)產(chǎn)生這些決定的處理過(guò)程的公正性提出質(zhì)疑。實(shí)際上,法律程序的結(jié)構(gòu)和步驟安排對(duì)于決定的實(shí)體內(nèi)容并不發(fā)生直接的影響,正因?yàn)槿绱耍鼈兺环Q(chēng)為“形式理性的要素”。(注:DavidLyons,F(xiàn)ormalJustice,MoralCommitment,andJudicialPrecedent,1984JuourmalofPhilosophy81,p.582.)這些要素可以被認(rèn)為是保證法律程序獲得“工具理性”的必要條件,是實(shí)現(xiàn)法律程序“理性”價(jià)值的基礎(chǔ)。為了獲得程序理性,筆者以為,程序的操作或設(shè)計(jì)應(yīng)當(dāng)考慮以下三個(gè)方面的基本要求:(1)程序的步驟在運(yùn)行過(guò)程上符合合理的順序。(2)程序應(yīng)當(dāng)能夠保證在給定同樣的條件時(shí)產(chǎn)生相同的結(jié)果。在英美對(duì)抗制程序中,這一要求包括決定的一致性、遵守先例以及與法律規(guī)則的一致。(3)程序的操作應(yīng)當(dāng)遵循職業(yè)主義原則,主持或操作法律程序的主體應(yīng)當(dāng)是合格的。
(一)程序步驟的合理性
程序展開(kāi)過(guò)程在時(shí)間上應(yīng)當(dāng)遵循合理的順序,因?yàn)槿藗內(nèi)粘I畹慕?jīng)驗(yàn)足以表明,一個(gè)理性決定的產(chǎn)生步驟在時(shí)間上應(yīng)當(dāng)有一個(gè)合理的先后順序。合理的步驟一方面可以促進(jìn)結(jié)果在實(shí)體方面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它們還是對(duì)決定產(chǎn)生過(guò)程公正合理的形式上的要求。例如,從作出決定的過(guò)程看,收集和闡述事實(shí)、證據(jù)及理由的程序步驟應(yīng)當(dāng)在制作決定的步驟之前進(jìn)行;如果先有決定,再闡述事實(shí)和理由,不論這一決定多么正確,也不論所闡述的事實(shí)和理由多么客觀全面,這一作出決定之過(guò)程的公正性仍然應(yīng)當(dāng)受到挑戰(zhàn),因?yàn)榘凑者@樣的方式所作出的決定就給人一種恣意和專(zhuān)斷的印象。
(二)一致性
在給定的條件或前提相同的情況下,通過(guò)法律程序而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應(yīng)當(dāng)是相同的。為了保證一致性,英美法系的傳統(tǒng)中產(chǎn)生了同樣情況同樣對(duì)待、遵守先例等原則。如果行政機(jī)關(guān)對(duì)于同樣的情況作出不同的決定,從形式上看就是違背理性的。遵守先例的要求也可以類(lèi)似地得到說(shuō)明。但遵守一致性原則只是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并不必然地意味著符合了這些要求的決定或結(jié)果實(shí)體上就是合理的。有時(shí)候,所遵循的先例可能是錯(cuò)誤的,遵守先例則意味著重復(fù)錯(cuò)誤;有時(shí)候作出決定的機(jī)關(guān)對(duì)具備同樣情況的當(dāng)事人作出相同的處理,但可能都是不合理的。由此可見(jiàn),一致性的要求與程序正義的其它要求一樣,只是法律程序獲得理性的必要條件。
從法律角度講,一致性的要求主要是通過(guò)一種類(lèi)似“作繭自縛”的效應(yīng)而防止權(quán)力行使中的恣意。從個(gè)體的道德權(quán)利角度講,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一致性原則是個(gè)體應(yīng)當(dāng)享有的“平等對(duì)待權(quán)”的要求,因?yàn)閷?duì)同樣情況下的不同處理將會(huì)導(dǎo)致對(duì)個(gè)體的區(qū)別和歧視,導(dǎo)致不平等和不公平。(注:RichardPierce,SidneySharpiro,andPaulVerkuil,AdministrativeLawandProcess,NewYork:FoundationPress1979,p.127.)美國(guó)學(xué)者戴維斯在其《自由裁量的正義》一書(shū)中也指出,假如X和Y的情況是相同的,而行政機(jī)關(guān)要求X交稅,Y卻不用交稅,那么與Y相比較而言,X顯然受到了不公平的對(duì)待;或者雖然行政機(jī)關(guān)要求X和Y都必須交稅,但要求X比Y交得更多,X同樣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對(duì)待。(注:Davis,DiscretionaryJustice;APreliminaryInquiry,UniversityofminoisPress1969,p.p.167~168.)在這種情況下,決定的公正與否似乎可以通過(guò)比較的方式而被感受到。有的學(xué)者由此而提出了“比較的正義”這一概念,認(rèn)為其基本要求就是對(duì)同樣情況應(yīng)當(dāng)給予平等對(duì)待。(注;SeeM.D.Balyes,ProceduralJustice:AllocatingtoIndividuals,KluwerAcademicPublichers,pp.92~94.但是應(yīng)當(dāng)注意,對(duì)“比較的正義”這一概念,人們提出了很多質(zhì)疑。一個(gè)被指控的刑事被告人可以以他的同犯逍遙法外為理由而認(rèn)為對(duì)他的指控不符合正義嗎?一個(gè)負(fù)有納稅義務(wù)的個(gè)人X可以以與他情況相同的Y沒(méi)有納稅而指責(zé)對(duì)其征稅的行為不符合正義嗎?有的學(xué)者甚至認(rèn)為,從道德上看,強(qiáng)調(diào)“比較的正義”也是存在問(wèn)題的,因?yàn)檫@將鼓勵(lì)人性中“貪婪和妒嫉”等弱點(diǎn),SeeJohnE.Coon,Consistency,1987CaliforniaLawReview75,p.p.59~133.)
在行政法領(lǐng)域,遵循一致性的要求盡管是制約自由裁量權(quán)的一項(xiàng)原則,但由于行政活動(dòng)不能沒(méi)有必要的靈活性,因此對(duì)這一原則不能作僵化的理解。從某種程度上講,行政法對(duì)一致性、遵守先例等原則一般都有比較靈活的規(guī)定。從美國(guó)的情況看,對(duì)于復(fù)數(shù)以上的明顯相同的情況,行政機(jī)關(guān)要么予以同樣的對(duì)待,要么解釋它們之間的差別。(注:SeeContractorsTransportationCorporationv.UnitedStates,537F2d1160(4thCir.1976)。)如果行政機(jī)關(guān)對(duì)同樣情況沒(méi)有進(jìn)行同樣的對(duì)待,或?qū)Σ煌闆r同樣對(duì)待,但卻沒(méi)有解釋這樣做的理由,在某些情況下其中的一個(gè)決定可能會(huì)被認(rèn)為“濫用自由裁量權(quán)”而被法院撤銷(xiāo)。(注:SeeDelMundov.Rosenberg,341F.Supp345(C.D.Cal,1972)。)遵守先例原則與一致性原則緊密相關(guān),因?yàn)樽袷叵壤龑?shí)際上意味著一致性原則在時(shí)間上的體現(xiàn)-現(xiàn)在的情況與以前相同的情況同樣對(duì)待。美國(guó)標(biāo)準(zhǔn)州行政程序法規(guī)定,除非行政機(jī)關(guān)能夠給出“事實(shí)和理由”表明不遵守先例是“公平與理性的”,否則應(yīng)當(dāng)遵守先例。(注:MSA5-116(c)(8)(Ⅲ)。從理論上講,遵守先例原則也將可能導(dǎo)致一些問(wèn)題。例如,如果被遵守的先例是錯(cuò)誤的,或者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先例已經(jīng)不再適合現(xiàn)在的要求等,在這些情況下,一味地遵守先例可能意味著法律的保守和僵化。但是,即便如此,一些學(xué)者仍然認(rèn)為遵守先例還是有其不可否認(rèn)的意義。他們爭(zhēng)辯道:(1)遵守先例可以保證法的確定性和可預(yù)測(cè)性(predictablity);(2)人們?cè)谝欢ǔ潭壬弦蕾?lài)于過(guò)去的經(jīng)驗(yàn)來(lái)處理當(dāng)下的事情;(3)遵守先例符合效率的要求;(4)遵守先例可以促使法律的一致性(coherenceorconsistency)。參見(jiàn)DavidLyons,F(xiàn)ormal,JusticeandJudicialPrecedent,1985VanderbiltLawReview38,p.p.495~512.)
(三)職業(yè)主義原則
程序理性的另一個(gè)要求是程序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職業(yè)主義原則。雖然職業(yè)主義原則與控制自由裁量權(quán)并沒(méi)有直接的關(guān)系,但對(duì)于程序理性和自由裁量權(quán)的合理行使并非毫無(wú)關(guān)系。首先,職業(yè)主義意味著專(zhuān)業(yè)化,對(duì)于自由裁量權(quán)的行使而言,專(zhuān)業(yè)化的程序操作者比外行更有可能作出合理的判斷,至少?gòu)男问缴峡词侨绱恕o(wú)論是稅率的確定還是對(duì)交通事故中責(zé)任的區(qū)分,專(zhuān)家的意見(jiàn)都更為中肯。其次,職業(yè)主義原則有助于保證決定之間的一致性,因?yàn)閷?duì)于相同情況的判斷以及豐富的職業(yè)經(jīng)驗(yàn)都是非職業(yè)的程序操作者無(wú)法比擬的。
四、結(jié)論與建議
第5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關(guān)鍵詞:振興東北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
一、實(shí)施振興東北的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國(guó)地域遼闊,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無(wú)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經(jīng)濟(jì)政策的戰(zhàn)略選擇上,應(yīng)采取整體與區(qū)域既相互協(xié)調(diào)、相互促進(jìn),又講求實(shí)效、彼此有別的政策取向。
(一)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與宏觀的積極財(cái)稅政策比較
1.實(shí)施范圍不同。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僅實(shí)施于需要拉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特別區(qū)域,如東北老工業(yè)基地。而我國(guó)以往的積極財(cái)稅政策則是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實(shí)施,雖然也有優(yōu)先發(fā)展某一區(qū)域的特點(diǎn),但更加注重的是優(yōu)先發(fā)展某一行業(yè)領(lǐng)域,如基本建設(shè)領(lǐng)域。
2.理論依據(jù)不同。由于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是一種財(cái)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協(xié)調(diào)整個(gè)宏觀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因此,它的理論依據(jù)是公共物品理論。公共物品理論認(rèn)為滿(mǎn)足公共需要有兩個(gè)系統(tǒng):一是市場(chǎng),二是政府。市場(chǎng)提供私人物品滿(mǎn)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滿(mǎn)足公共需要。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振興的一個(gè)現(xiàn)實(shí)障礙之一就是長(zhǎng)期以來(lái)公共物品的缺乏。在東北地區(qū)實(shí)施積極的財(cái)稅支持政策用以滿(mǎn)足公共物品的供給,是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國(guó)以往實(shí)施的積極財(cái)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財(cái)政支持政策。雖然在實(shí)施近7年中,它順應(yīng)西部大開(kāi)發(fā)戰(zhàn)略和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戰(zhàn)略,并對(duì)這兩個(gè)區(qū)域進(jìn)行財(cái)政支持,但是它實(shí)施的初衷卻是為了克服通貨緊縮,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積極財(cái)政政策的理論基礎(chǔ)是有效需求理論。有效需求理論認(rèn)為如果經(jīng)濟(jì)正處于嚴(yán)重的蕭條時(shí)期,應(yīng)實(shí)施擴(kuò)張性財(cái)政政策,即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kāi)支和增加社會(huì)福利的辦法。我國(guó)以往實(shí)施的積極財(cái)稅政策主要是通過(guò)增發(fā)國(guó)債、擴(kuò)大政府開(kāi)支來(lái)刺激經(jīng)濟(jì),而沒(méi)有大規(guī)模地實(shí)施減稅政策,因而還不能?chē)?yán)格認(rèn)為是擴(kuò)張性財(cái)稅政策,只能謂之積極的財(cái)稅政策。
(二)在東北實(shí)施積極財(cái)稅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連續(xù)性的要求。到目前為止,實(shí)施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戰(zhàn)略?xún)H2年。國(guó)家推出的兩批振興東北的項(xiàng)目剛剛起步,擴(kuò)大增值稅抵扣范圍的改革也只是初見(jiàn)成效,如果不能繼續(xù)對(duì)東北地區(qū)采取財(cái)政政策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項(xiàng)目無(wú)法順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興東北整體戰(zhàn)略的擱淺。這將使東北老工業(yè)基地不能得到振興,而且國(guó)家前期投資也將付之東流。因此,從政策的連續(xù)性考慮,還應(yīng)該在東北地區(qū)繼續(xù)實(shí)施積極的財(cái)稅政策。
2.貫徹“有保有控”方針的需要。我國(guó)宏觀財(cái)政政策的轉(zhuǎn)變是向中性財(cái)政政策的轉(zhuǎn)變,其基本的政策含義是認(rèn)為宏觀經(jīng)濟(jì)運(yùn)行態(tài)勢(shì)變化之后,現(xiàn)階段還不宜采取“全面緊縮”的調(diào)控方法,既不能“不轉(zhuǎn)彎”,又不能“急轉(zhuǎn)彎”,而應(yīng)當(dāng)在穩(wěn)健把握之下著力協(xié)調(diào),在調(diào)減擴(kuò)張力度中區(qū)別對(duì)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則。政府資金使用的重點(diǎn),應(yīng)集中于國(guó)家發(fā)展規(guī)劃確立的戰(zhàn)略發(fā)展目標(biāo)和農(nóng)林水利、生態(tài)保護(hù)與國(guó)土整治、西部開(kāi)發(fā)與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振興的重點(diǎn)項(xiàng)目。
3.發(fā)展經(jīng)驗(yàn)和現(xiàn)實(shí)財(cái)力的保障。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我國(guó)先后實(shí)施了沿海發(fā)展戰(zhàn)略和西部大開(kāi)發(fā)戰(zhàn)略,積累了區(qū)域經(jīng)濟(j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和財(cái)稅宏觀調(diào)控的寶貴經(jīng)驗(yàn)。東南沿海地區(qū)在20年間成為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隆起”地帶,西部地區(qū)GDP增長(zhǎng)速度也明顯加快。在實(shí)施區(qū)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過(guò)程中,國(guó)債投資、一般轉(zhuǎn)移支付和專(zhuān)項(xiàng)轉(zhuǎn)移支付、財(cái)政貼息、稅收優(yōu)惠等作為宏觀調(diào)控的重要財(cái)稅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這些都是我國(guó)實(shí)施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戰(zhàn)略,采取積極財(cái)稅政策可資借鑒的寶貴經(jīng)驗(yàn)。此外,我國(guó)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和稅收收入的超額增長(zhǎng)也為振興東北,實(shí)施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現(xiàn)實(shí)財(cái)力空間。
4.消費(fèi)型增值稅制度的示范效應(yīng)良好。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固定資產(chǎn)更新財(cái)力不足問(wèn)題,是制約經(jīng)濟(jì)振興的關(guān)鍵問(wèn)題之一。擴(kuò)大增值稅抵扣范圍試點(diǎn)的實(shí)行,一方面為試點(diǎn)的行業(yè)的固定資產(chǎn)更新補(bǔ)充了資金;另一方面還對(duì)全國(guó)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區(qū)域外資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導(dǎo)向與示范作用。
二、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的制度安排
為了有效地實(shí)現(xiàn)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振興,在實(shí)施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時(shí)應(yīng)有所側(cè)重,點(diǎn)面結(jié)合。“點(diǎn)”即政策支持的行業(yè)領(lǐng)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區(qū)區(qū)域。
(一)擴(kuò)大財(cái)稅政策的支持范圍
1.應(yīng)加大對(duì)資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從東北地區(qū)的實(shí)際情況看,主要分為四種類(lèi)型:一是綜合性工業(yè)城市,如沈陽(yáng)、哈爾濱、長(zhǎng)春等工業(yè)城市;二是煤礦、石油城市,如阜新、雞西、大慶等資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區(qū),如伊春及其他林業(yè)局等;四是農(nóng)村地區(qū)。前兩類(lèi)主要是工業(yè)城市,后兩類(lèi)主要是農(nóng)林地區(qū)。從國(guó)家財(cái)政支持的區(qū)域來(lái)看,近2年來(lái)對(duì)東北地區(qū)的財(cái)稅政策支持主要傾斜在上述的前兩個(gè)區(qū)域,即綜合性工業(yè)城市和資源型城市,其中以綜合性工業(yè)城市享受到的優(yōu)惠最多。資源型城市則由于資源稟賦原因,直到21世紀(jì)初還承擔(dān)著國(guó)家計(jì)劃任務(wù),一直處于為國(guó)家;宏觀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作貢獻(xiàn)的地位。據(jù)統(tǒng)計(jì)僅黑龍江省自1952年以來(lái),由于初級(jí)資源品的低價(jià)調(diào)出與工業(yè)制成品的高價(jià)調(diào)入,形成的價(jià)差貢獻(xiàn)多達(dá)7000億元,而國(guó)家對(duì)該省的預(yù)算內(nèi)投資不足其貢獻(xiàn)額度的1/4.又因其;③產(chǎn)業(yè)進(jìn)入壁壘較高,非國(guó)有經(jīng)濟(jì)進(jìn)入難度較大,要實(shí)現(xiàn)資源型城市的振興,國(guó)家財(cái)稅政策方面的支持至關(guān)重要。
2.應(yīng)重視對(duì)基礎(chǔ)產(chǎn)業(yè)的政策支持。國(guó)家對(duì)東北農(nóng)村地區(qū)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財(cái)稅政策,即減免農(nóng)業(yè)稅;對(duì)東北林區(qū)的財(cái)政支持主要是繼續(xù)落實(shí)天然林保護(hù)工程資金。然而,這些政策和資金對(duì)森工林區(qū)和農(nóng)村地區(qū)的支持作用遠(yuǎn)未達(dá)到“振興”的目的。對(duì)于今后財(cái)稅政策支持區(qū)域的把握,我們認(rèn)為應(yīng)該向森工林區(qū)和農(nóng)村地區(qū)做進(jìn)一步的傾斜。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振興是全面的振興,不能片面地理解為對(duì)傳統(tǒng)工業(yè)城市的振興。前期支持工業(yè)城市的財(cái)稅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動(dòng)?xùn)|北的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但要使經(jīng)濟(jì)向深度發(fā)展,財(cái)稅政策必須惠及森工林區(qū)和農(nóng)村地區(qū),當(dāng)然也包括資源型城市。
(二)合理安排財(cái)稅政策的支持重點(diǎn)
已實(shí)施的財(cái)稅支持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對(duì)東北的裝備制造業(yè)、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的扶持力度。如首批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100個(gè)國(guó)債項(xiàng)目中,遼寧省的52個(gè)項(xiàng)目都是圍繞先進(jìn)裝備制造業(yè)和原材料基地兩個(gè)主題,總投資442億元;2003年國(guó)家還啟動(dòng)了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發(fā)展專(zhuān)項(xiàng)60個(gè)項(xiàng)目,總投資56億元,截至2004年底,國(guó)家共下達(dá)國(guó)債項(xiàng)目貼息資金8億元,安排東北高新技術(shù)項(xiàng)目118項(xiàng)。毫無(wú)疑問(wèn),裝備制造業(yè)和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都是拉動(dòng)?xùn)|北經(jīng)濟(jì)的增長(zhǎng)點(diǎn),東北經(jīng)濟(jì)的騰飛要靠這些優(yōu)勢(shì)項(xiàng)目來(lái)帶動(dòng)。但是,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振興從長(zhǎng)期著眼,還需要解決一些基礎(chǔ)的瓶頸問(wèn)題,以便從根本上全面振興東北地區(qū)。具體來(lái)說(shuō),新一輪的財(cái)稅扶持項(xiàng)目應(yīng)更加側(cè)重以下領(lǐng)域:1.減輕企業(yè)與地方的歷史包袱。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振興的一個(gè)重要內(nèi)容就是國(guó)有經(jīng)濟(jì)的戰(zhàn)略性調(diào)整。由于東北地區(qū)國(guó)有經(jīng)濟(jì)的比重高,形成時(shí)間長(zhǎng),這種調(diào)整需要非常高的體制轉(zhuǎn)型成本,這就需要政府的投入,以幫助企業(yè)減輕或甩掉歷史包袱。為此,建議國(guó)家設(shè)立東北老工業(yè)基地調(diào)整改造基金,專(zhuān)項(xiàng)用于東北地區(qū)衰退產(chǎn)業(yè)的退出、接續(xù)產(chǎn)業(yè)的培育,以保證穩(wěn)定的資金來(lái)源和渠道。
2.完善社會(huì)保障體系。東北地區(qū)的社會(huì)保障問(wèn)題與企業(yè)的歷史包袱問(wèn)題緊密相關(guān),且形勢(shì)依然嚴(yán)峻。以吉林省為例,到2002年末,全省下崗失業(yè)人員累計(jì)超過(guò)100萬(wàn)人,全省離退休人員105萬(wàn)人,每年養(yǎng)老保險(xiǎn)基金收支自然缺口近30億元,全省城鎮(zhèn)納入動(dòng)態(tài)管理的“低保”對(duì)象149.7萬(wàn)人。未來(lái)5年城鎮(zhèn)約有230萬(wàn)下崗失業(yè)人員和新生勞動(dòng)力需要就業(yè),農(nóng)村約有200萬(wàn)富余勞動(dòng)力需向城鎮(zhèn)轉(zhuǎn)移。另外,東北地區(qū)的失業(yè)保險(xiǎn)金也遠(yuǎn)低于全國(guó)平均水平。因此,需要國(guó)家加大對(duì)東北地區(qū)社會(huì)保障政策的支持力度,解決社會(huì)保障支出缺口巨大的問(wèn)題,使社會(huì)保障制度成為社會(huì)的穩(wěn)定器,為振興東北創(chuàng)造良好的環(huán)境。
3.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與建設(shè)。東北地區(qū)作為我國(guó)重化工業(yè)的基地,過(guò)去一直沒(méi)有重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生產(chǎn)粗放、污染嚴(yán)重、資源消耗大。作為世界三大黑土帶之一,東北大平原的黑土在近半個(gè)多世紀(jì)以來(lái),有2/3的耕地存在嚴(yán)重的水土流失,黑土層已由原來(lái)的60厘米~70厘米厚減到30厘米左右;在中南部地區(qū),特別是遼寧中部城市群地區(qū),鋼鐵、冶金、采礦、石油化工等產(chǎn)業(yè)集中,長(zhǎng)期以來(lái)“三廢”治理的欠賬較大,未經(jīng)處理或處理未達(dá)標(biāo)的城市和工業(yè)廢水大量流入農(nóng)業(yè)地區(qū),使一些農(nóng)業(yè)土地受到嚴(yán)重污染;而在約占東北大平原面積1/3的西部,與科爾沁沙地相鄰接,生態(tài)環(huán)境脆弱,分布有總面積達(dá)200萬(wàn)公頃的風(fēng)沙土,320萬(wàn)公頃草場(chǎng)已有80%以上的面積嚴(yán)重退化;還有,因大規(guī)模農(nóng)業(yè)開(kāi)墾,使東北大平原濕地面積急劇減少,濕地的生物種類(lèi)已減少了25%。因此在財(cái)稅政策上,除了擴(kuò)大國(guó)家財(cái)政對(duì)環(huán)境保護(hù)和治理的投入規(guī)模,還可在東北開(kāi)征生態(tài)稅收,以配合財(cái)政政策,調(diào)整產(chǎn)業(yè)布局。
三、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策略
我國(guó)實(shí)施了近7年的積極財(cái)政政策,在對(duì)整體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作出積極貢獻(xiàn)的同時(shí),也帶來(lái)一些負(fù)面因素和潛在風(fēng)險(xiǎn)。在東北實(shí)施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時(shí),需借鑒國(guó)際成功經(jīng)驗(yàn),盡量規(guī)避可能出現(xiàn)的風(fēng)險(xiǎn)。
(一)財(cái)稅政策實(shí)施過(guò)程中需考慮的問(wèn)題
1.國(guó)債資金的投資效率。由于國(guó)債資金配置存在嚴(yán)重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色彩,需防止預(yù)算軟約束在國(guó)債資金的安排使用中可能造成的浪費(fèi)和低效率現(xiàn)象。如由于國(guó)債項(xiàng)目前期準(zhǔn)備工作不足,不能按時(shí)開(kāi)工和竣工而造成國(guó)債資金閑置;或者由于國(guó)債項(xiàng)目設(shè)計(jì)、施工出現(xiàn)嚴(yán)重失誤,致使工程量大增,拖延工期或形成半拉子工程等失誤浪費(fèi)現(xiàn)象。
2.對(duì)民間資本的擠壓效應(yīng)。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乏力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就是,國(guó)有經(jīng)濟(jì)比重過(guò)大,缺乏市場(chǎng)活力。據(jù)統(tǒng)計(jì),東北地區(qū)的國(guó)有企業(yè)大體上占企業(yè)總數(shù)的70%左右。前期振興東北的國(guó)債項(xiàng)目主要是加大對(duì)國(guó)有企業(yè)的扶持,這就有可能對(duì)民間資本產(chǎn)生擠壓效應(yīng),而民營(yíng)經(jīng)濟(jì)比重過(guò)低,會(huì)導(dǎo)致市場(chǎng)化程度低,經(jīng)濟(jì)發(fā)展內(nèi)在動(dòng)力不足。
3.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矛盾。東北地區(qū)現(xiàn)有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矛盾主要有二:其一,收入分配和消費(fèi)結(jié)構(gòu)性失衡。不同行業(yè)、地區(qū)間職工的收入差距在拉大。1998年以來(lái)農(nóng)林牧漁業(yè)總產(chǎn)值沒(méi)有實(shí)質(zhì)性增長(zhǎng),農(nóng)村和林區(qū)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緩慢。其二,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仍不均衡。雖然加大了財(cái)政轉(zhuǎn)移支付力度,但國(guó)債項(xiàng)目的安排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使得區(qū)域不平衡狀況更加嚴(yán)重。
4.國(guó)際成功經(jīng)驗(yàn)的借鑒。東北地區(qū)的老工業(yè)基礎(chǔ)(遼寧起始于1894年的京沈鐵路時(shí)期;黑龍江起始于抗美援朝遼寧省北遷項(xiàng)目及“一五”時(shí)期國(guó)家重點(diǎn)建設(shè)項(xiàng)目;吉林起始于“一五”時(shí)期國(guó)家的9個(gè)重點(diǎn)建設(shè)項(xiàng)目),主要是以資源為依托形成的重工業(yè)格局,其特點(diǎn)與德國(guó)的煤炭主產(chǎn)區(qū)魯爾區(qū)和法國(guó)的鐵礦主產(chǎn)區(qū)洛林區(qū)有相似之處,都是依托自然資源興起的老工業(yè)區(qū)。魯爾與洛林的振興均借助于國(guó)家的政策支持,如法國(guó)政府對(duì)洛林地區(qū)實(shí)行3萬(wàn)法郎以上的生產(chǎn)性新設(shè)備投資給予30%的補(bǔ)貼、服務(wù)性設(shè)備給予20%的補(bǔ)貼等,其成功經(jīng)驗(yàn)值得借鑒。
(二)有效實(shí)施區(qū)域性財(cái)稅政策的策略
為了能夠避免積極財(cái)政政策實(shí)施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我們總結(jié)了兩條策略性主張,以求能夠更有效地實(shí)施振興東北的區(qū)域性積極財(cái)稅政策。
1.建立省以下的轉(zhuǎn)移支付制度。我國(guó)現(xiàn)行的轉(zhuǎn)移支付辦法均在中央和省一級(jí)進(jìn)行,對(duì)省以下的轉(zhuǎn)移支付制度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東北地區(qū)不但整體上較東南沿海地區(qū)落后,而且在一個(gè)省內(nèi)也存在較大的地區(qū)差距。在這種客觀現(xiàn)實(shí)條件下,隨著公共財(cái)政的逐步建立,分稅制的不斷完善,建立完整的省以下的轉(zhuǎn)移支付制度就顯得非常迫切。省以下的轉(zhuǎn)移支付制度應(yīng)在考慮本省實(shí)際情況的基礎(chǔ)上,在財(cái)政管理體制目標(biāo)范圍內(nèi),盡量與中央對(duì)地方的轉(zhuǎn)移支付制度相協(xié)調(diào)。
2.政府投資引導(dǎo)民間資本。為了更有效地提高政府投資的效率,政府投資的一個(gè)基本原則是:政府投資先行,引導(dǎo)民間資本投入落后地區(qū)。落后地區(qū)的多數(shù)基礎(chǔ)設(shè)施投資只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屬于純公共物品。對(duì)此,政府投資雖是必要的,但更有效的辦法是通過(guò)項(xiàng)目融資的方式,鼓勵(lì)民間資本進(jìn)入。這不但可以緩解政府財(cái)政的壓力,還可以促進(jìn)民營(yí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
3.試行區(qū)域性生態(tài)稅收制度。我國(guó)現(xiàn)行稅收制度在計(jì)稅依據(jù)的確定上,均以?xún)r(jià)值決定理論為基礎(chǔ),沒(méi)有將資源品開(kāi)采過(guò)程中的生態(tài)價(jià)值折損納入計(jì)稅依據(jù)。資源品尤其是初級(jí)資源品的銷(xiāo)售價(jià)格在進(jìn)入市場(chǎng)時(shí),其價(jià)格決定均取決于供需狀況。導(dǎo)致資源主產(chǎn)區(qū)一方面產(chǎn)品低價(jià)外銷(xiāo);另一方面生態(tài)狀況急劇惡化,又得不到及時(shí)彌補(bǔ)。實(shí)施區(qū)域性財(cái)稅政策支持,可考慮配合稅收制度改革,調(diào)整稅收管理體制,在資源品主產(chǎn)區(qū)進(jìn)行生態(tài)型稅收制度的試點(diǎn),以現(xiàn)行排污收費(fèi)制度為基礎(chǔ),按照自然資源的稀缺程度,將生態(tài)價(jià)值折損量量化計(jì)入計(jì)稅依據(jù),稅收收入定向用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恢復(fù)與治理。
參考文獻(xiàn)
(1)陳共《財(cái)政學(xué)》,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
(2)楊君昌《對(duì)我國(guó)財(cái)政政策有效性的若干看法——?jiǎng)P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在財(cái)政政策上的分歧及其啟示》,《當(dāng)代財(cái)經(jīng)》2002年第1期。
(3)安體富、王海勇《振興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財(cái)稅政策取向》,《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年第6期。
第6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重慶市將行政失信要給補(bǔ)償?shù)葐?wèn)題納入政府信用建設(shè),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法治中的正當(dāng)期待原則。正當(dāng)期待原則是禁止突兀地改變已經(jīng)生效的法律規(guī)則,要求在撤銷(xiāo)或者變更行政決定之前進(jìn)行恰當(dāng)?shù)睦婧饬浚⒔o予必要的補(bǔ)償。
俗話(huà)說(shuō),“人無(wú)信而不立”。在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運(yùn)行中,“信任”被普遍認(rèn)為是除物質(zhì)資本和人力資本之外決定一個(gè)國(guó)家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社會(huì)進(jìn)步的主要社會(huì)資本。在某種意義上,信任作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劑,決定了經(jīng)濟(jì)實(shí)體的規(guī)模、組織方式、交易范圍和交易形式。而《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民法通則》第四條規(guī)定民事活動(dòng)應(yīng)遵循誠(chéng)實(shí)信用的原則,這被奉為民法學(xué)中的“帝王條款”,也為一切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參加者樹(shù)立了一個(gè)“誠(chéng)實(shí)”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當(dāng)政府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之中出現(xiàn),建設(shè)其信用體制,那么它也是民法主體-法人,也需遵守誠(chéng)實(shí)信用的原則。
在政府和公民之間的管理和被管理關(guān)系中,引入信任機(jī)制的作用,也同樣十分必要。在行政管理過(guò)程中,相對(duì)于勢(shì)單力薄的一個(gè)個(gè)散落于島嶼上的、缺乏足夠集體行動(dòng)和交涉能力的公民而言,政府掌握更多的相關(guān)知識(shí)、技術(shù)和信息,富有相對(duì)充裕的資源,相對(duì)低廉的成本。因此公民會(huì)對(duì)政府的行為存在某種信賴(lài),正因如此,政府失信,則會(huì)破壞公民和政府之間的信任與協(xié)作關(guān)系,動(dòng)搖法治政府的根基。因此,強(qiáng)調(diào)政府守信,打造誠(chéng)信政府,就顯得格外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第7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關(guān)鍵詞:法國(guó)行政法行政法治原則行政均衡原則
法國(guó)是大陸法系國(guó)家的典型代表,素有“行政法母國(guó)”之譽(yù),其行政法被許多國(guó)家奉為典范。法國(guó)最先從理念上承認(rèn)行政法是一個(gè)獨(dú)立的部門(mén)法,并通過(guò)行政法院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努力構(gòu)建了一個(gè)完整的行政法體系。支撐這一龐大的行政法體系的是隱藏在其背后的行政法基本原則。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使法國(guó)的行政法體系雖然規(guī)模宏大但不顯得雜亂無(wú)章,雖然范圍廣博但卻構(gòu)成一個(gè)和諧的整體。法國(guó)著名法學(xué)家勒內(nèi)。達(dá)維在談及法國(guó)行政法時(shí)自豪地說(shuō):“一系列行政法原則已經(jīng)形成,它完全可以和民法原則媲美,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勝一籌。”[①]深入研究集中體現(xiàn)法國(guó)行政法精神的基本原則可以使我們深刻理解和領(lǐng)會(huì)法國(guó)行政法的基本內(nèi)涵、主要觀念和規(guī)范體系,同時(shí),這對(duì)在國(guó)情上與法國(guó)有許多相同之處的中國(guó)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法國(guó)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與發(fā)展
法國(guó)行政法的產(chǎn)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guó)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為法國(guó)行政法的產(chǎn)生提供了政治、經(jīng)濟(jì)、思想準(zhǔn)備,大革命時(shí)期建立起來(lái)的獨(dú)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biāo)志著法國(guó)行政法的產(chǎn)生,并使以法國(guó)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duì)比。正是伴隨著法國(guó)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出現(xiàn)的法治國(guó)思想和獨(dú)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fā)展,在法國(guó)逐步產(chǎn)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行政均衡原則,這兩個(gè)原則被認(rèn)為是法國(guó)行政法的基本原則。
(一)法治國(guó)思想的影響
在法國(guó),法治國(guó)的思想產(chǎn)生于1789年資產(chǎn)階級(jí)大革命前的啟蒙時(shí)代。以孟德斯鳩、盧梭、伏爾泰等為代表的一大批資產(chǎn)階級(jí)啟蒙思想家以理性作為武器向宗教神學(xué)和君主專(zhuān)制發(fā)起了猛烈的攻擊。其中,作為古典自然法學(xué)派代表人物的孟德斯鳩和盧梭比較系統(tǒng)的闡述了法治國(guó)的思想。孟德斯鳩的“三權(quán)分立制衡論”、盧梭的“天賦人權(quán)論”、“社會(huì)契約論”、“人民論”都包含有豐富的法治國(guó)思想。他們傾向于個(gè)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認(rèn)為“國(guó)家權(quán)力不是絕對(duì)的,國(guó)家和個(gè)人都應(yīng)服從法律,法律保護(hù)個(gè)人權(quán)利,不受?chē)?guó)家權(quán)力的非法侵害。”[②]啟蒙思想家的法治國(guó)思想伴隨著法國(guó)資產(chǎn)階級(jí)大革命的爆發(fā)進(jìn)一步深入人心,并成為法國(guó)憲法的一個(gè)重要原則。1789年《人權(quán)宣言》第5條規(guī)定:“……凡未經(jīng)法律禁止的行為不得受到妨礙,任何人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未規(guī)定的行為”,該宣言的第6條規(guī)定:“法律表達(dá)普遍意志。所有公民皆有權(quán)親自或經(jīng)由其代表來(lái)參與法律之形成。不論保護(hù)抑或懲罰,法律必須對(duì)所有人一樣。……”。上述規(guī)定都是當(dāng)時(shí)法治國(guó)思想的表現(xiàn)。
個(gè)人的自然權(quán)利是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構(gòu)造其法治國(guó)思想的邏輯起點(diǎn),這種學(xué)說(shuō)對(duì)于弘揚(yáng)民主、平等、自由等價(jià)值觀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shí)也適應(yīng)了當(dāng)時(shí)資產(chǎn)階級(jí)革命的需要。但是,隨著法國(guó)的政治風(fēng)云變換和壟斷資本對(duì)加強(qiáng)國(guó)家權(quán)力的需要,建立在形而上學(xué)的個(gè)人主義之上的自然權(quán)利說(shuō)被實(shí)證主義社會(huì)法學(xué)派的學(xué)說(shuō)所取代。以狄驥為代表的實(shí)證主義社會(huì)法學(xué)不是從個(gè)人的自然權(quán)利出發(fā),而是以社會(huì)的連帶關(guān)系為邏輯起點(diǎn)對(duì)法治國(guó)的思想進(jìn)行了闡述。狄驥認(rèn)為:“法律的強(qiáng)制力量并不來(lái)源于統(tǒng)治者的意志,而是來(lái)源于法律與社會(huì)相互依存的一致性。由此,法律對(duì)統(tǒng)治者的約束同其對(duì)庶民的約束一樣嚴(yán)格,因?yàn)榻y(tǒng)治者與庶民一樣,也受建立在社會(huì)相互關(guān)聯(lián)性基礎(chǔ)上的法律規(guī)則約束。”[③]狄驥與啟蒙思想家的法治國(guó)思想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但在使國(guó)家的公權(quán)力受到法律的控制和約束方面是一致的。比如,狄驥認(rèn)為:“國(guó)家必須遵守它所制定的法律,只要該法律未被廢除。國(guó)家可以修改或取消某項(xiàng)法律;但只要該法律存在,國(guó)家限制行為,行政行為和司法行為都必須在該法律法定范圍之內(nèi),而正是因?yàn)檫@一點(diǎn),國(guó)家才是法治國(guó)家。”[④]
法治國(guó)思想的傳播為法國(guó)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與發(fā)展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思想基礎(chǔ)。首先,法治國(guó)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使國(guó)家公權(quán)力從屬于法律,這種精神在行政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就是行政法治原則,即作為國(guó)家公權(quán)力之一的行政權(quán)也應(yīng)當(dāng)?shù)椒傻闹洹F浯危ㄖ螄?guó)思想不僅要求公權(quán)力服從于法律特別是制定法(形式法治國(guó)),而且進(jìn)一步要求公權(quán)力的行使必須符合公平、正義的觀念(實(shí)質(zhì)法治國(guó))。二戰(zhàn)后,隨著從經(jīng)濟(jì)自由主義向國(guó)家干預(yù)主義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行政權(quán)更加廣泛地深入到法國(guó)社會(huì)之中。為了應(yīng)對(duì)層出不窮的社會(huì)問(wèn)題,法律賦予了行政機(jī)關(guān)更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quán),在這種情況下,體現(xiàn)形式法治國(guó)思想的行政法治原則的局限性日益明顯。為了加強(qiáng)對(duì)行政自由裁量權(quán)的控制,行政法院通過(guò)判例發(fā)展出了行政均衡原則。該原則要求,在法律沒(méi)有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行政行為必須合理、適度、均衡。而這正是行政法院根據(jù)公平、正義等實(shí)質(zhì)法治國(guó)的觀念對(duì)行政行為提出的要求。
(二)行政法院制度與判例的作用
法治國(guó)思想在行政法領(lǐng)域的應(yīng)用必須有制度性的保障才能使該思想變?yōu)樯鷦?dòng)的現(xiàn)實(shí)。在這方面,法國(guó)的行政法院制度與判例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對(duì)法國(guó)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的形成具有較大影響的另一重要因素。
“法國(guó)的行政法是由行政法院適用的特殊法律,而行政法院正是為適用行政法而創(chuàng)造的。”[⑤]大革命時(shí)期,法國(guó)人的一個(gè)共同信念是:最高法院代表舊制度,大革命的目標(biāo)之一就是要取消司法權(quán)對(duì)行政權(quán)的干預(yù)。至今仍然有效的1790年8月16日—24日的法令宣布:“司法機(jī)構(gòu)應(yīng)當(dāng)同行政職能相分離,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預(yù)行政人員的活動(dòng),違者以瀆職論處”。“這項(xiàng)規(guī)定意味著一個(gè)終點(diǎn),但它卻恰恰是法國(guó)行政法的起點(diǎn)的標(biāo)志。”[⑥]自此以后,法國(guó)行政法院從最初的保留審判權(quán)到后來(lái)的委托審判權(quán)直至1889年通過(guò)“卡多案件”正式取消部長(zhǎng)法官制,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發(fā)展過(guò)程才逐漸同實(shí)際的行政相分離。這個(gè)分離的過(guò)程是行政法院的獨(dú)立性逐步增強(qiáng)的過(guò)程,是行政審判權(quán)對(duì)行政權(quán)的監(jiān)督逐漸強(qiáng)化的過(guò)程,同時(shí)也是法國(guó)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逐步形成和發(fā)展的過(guò)程。
法國(guó)行政法院自創(chuàng)立以來(lái)已有二百年的歷史,在此期間它對(duì)推進(jìn)法國(guó)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的發(fā)展起到了獨(dú)特而卓越的作用。對(duì)此,美國(guó)學(xué)者莫里斯。拉朗熱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行政法院所發(fā)揮的卓越作用真正是法國(guó)獨(dú)創(chuàng)的。在這個(gè)國(guó)家里,政府經(jīng)常變動(dòng),憲法也并不持久而來(lái)回更改,行政法院卻是主要的穩(wěn)定因素。它所賴(lài)以建立的原則,越過(guò)成文的憲法,構(gòu)成一個(gè)真實(shí)的不成文的憲法。……在這個(gè)多次發(fā)生革命的國(guó)家里,行政法院以漸進(jìn)的方式發(fā)揮作用,它做事既謹(jǐn)慎,又有效,有時(shí)也被急風(fēng)暴雨所顛覆,但很快又達(dá)到恢復(fù),就這樣保持著國(guó)家的永久性和民族的連續(xù)性。”[⑦]法國(guó)行政法院在控制行政權(quán)濫用、保護(hù)公民合法權(quán)益方面所起的作用尤為顯著。在第五共和國(guó)創(chuàng)立憲法委員會(huì)之前,行政法院歷年所發(fā)展的案例法幾乎是唯一限制政府權(quán)力的法律。[⑧]行政法院通過(guò)判例的形式不僅率先發(fā)展了權(quán)力濫用理論,從而豐富了行政法治原則,而且在20世紀(jì)80年代,又發(fā)展了行政均衡原則。均衡原則與英國(guó)的合理性原則、德國(guó)的比例原則、日本的無(wú)瑕疵裁量請(qǐng)求權(quán)和裁量零收縮理論同屬對(duì)行政裁量權(quán)的有效控制手段,但更能體現(xiàn)法國(guó)行政法特色。在比較法國(guó)新舊兩個(gè)時(shí)代時(shí),托克維爾認(rèn)為二者唯一實(shí)質(zhì)性的區(qū)別在于“大革命之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專(zhuān)橫的手段才能庇護(hù)政府官員,而大革命以來(lái),它已能合法地讓他們違反法律。”[⑨]這種判斷在托克維爾所處的時(shí)代也許是真知灼見(jiàn),但是在后托克維爾時(shí)代,伴隨著獨(dú)立的行政法院制度的出現(xiàn)和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與發(fā)展,這種說(shuō)法已經(jīng)與法國(guó)當(dāng)代的現(xiàn)實(shí)顯得距離過(guò)于遙遠(yuǎn)。
法國(guó)本是一個(gè)成文法國(guó)家,“同至今仍以判例法為基礎(chǔ)的英國(guó)法相比,法國(guó)法則有以制定法為中心的法結(jié)構(gòu)這種大陸法的特征。”[⑩]因此,法院判案原則上以成文法為根據(jù),然而在行政法中起主要作用的卻是判例。這是由法國(guó)行政法的特點(diǎn)所決定的。因?yàn)椋环矫嬖诠ê退椒ㄏ嗷シ蛛x的傳統(tǒng)之下,行政法院對(duì)行政案件的審理不適用民法和其他私法的規(guī)定;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事項(xiàng)極為繁雜,法官經(jīng)常遇到無(wú)法可依的情況,不得不在判決中確定所依據(jù)的原則。在法國(guó),“行政法的重要原則,幾乎全由行政法院的判例產(chǎn)生。”[11]一位法國(guó)行政法學(xué)家用生動(dòng)的語(yǔ)言說(shuō),如果我們?cè)O(shè)想立法者大筆一揮,取消全部民法條文,法國(guó)將無(wú)民法存在;如果他們?nèi)∠啃谭l文,法國(guó)將無(wú)刑法存在;但是如果他們?nèi)∠啃姓l文,法國(guó)的行政法仍然存在,因?yàn)樾姓ǖ闹匾瓌t不存在成文法中,而存在于判例之中。[12]這幾句話(huà)雖然有些夸張,但卻十分生動(dòng)地說(shuō)明了判例對(duì)于法國(guó)行政法的重要性,也說(shuō)明法國(guó)行政法的特點(diǎn)。在法國(guó)行政法中,判例占據(jù)如此重要的地位,這或許有兩個(gè)原因:一是行政事務(wù)復(fù)雜多變,成文法難以適應(yīng)這種速度;二是判例出自具有較高素質(zhì)的最高行政法院法官之手,質(zhì)量比較高。[13]此外,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逐月逐年公開(kāi)發(fā)表,供學(xué)術(shù)界討論和研究,法學(xué)界對(duì)于判決的評(píng)價(jià),也能提高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的質(zhì)量。
法國(guó)行政法中的原則大都先由法官或法學(xué)家們?cè)诎讣l(fā)生后提出或創(chuàng)造出來(lái),經(jīng)過(guò)實(shí)踐的檢驗(yàn),有的成為普遍性的成文法原則,如行政法治性原則;有的則仍處于判例狀態(tài),僅僅出現(xiàn)在法學(xué)家們的學(xué)術(shù)研究中,行政均衡原則即屬此類(lèi)。這些原則由判例產(chǎn)生,經(jīng)過(guò)實(shí)踐的檢驗(yàn),所以具有高度的適應(yīng)性和靈活性,這正是法國(guó)行政法的優(yōu)點(diǎn)之一。
綜上所述,法治國(guó)思想的傳播為法國(guó)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產(chǎn)生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思想基礎(chǔ),獨(dú)特的行政法院制度為之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制度環(huán)境,而行政法院的法官則根據(jù)實(shí)踐需要通過(guò)高質(zhì)量的行政判例不斷對(duì)其進(jìn)行豐富和完善。正是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逐步推動(dòng)了行政法治和行政均衡兩項(xiàng)基本原則在法國(guó)的形成與發(fā)展。
二、行政法治原則
在法國(guó),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行政法是調(diào)整行政活動(dòng)的國(guó)內(nèi)公法。調(diào)整行政活動(dòng)是指行政活動(dòng)必須遵守法律,在其違反法律時(shí)受到一定制裁,例如引起無(wú)效、撤銷(xiāo)或賠償責(zé)任的結(jié)果。這就是法國(guó)行政法學(xué)上所謂的“行政法治原則”。具體而言,它是指法律規(guī)定行政機(jī)關(guān)的組織、權(quán)限、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后果,行政機(jī)關(guān)的行政行為必須嚴(yán)格遵守法律的規(guī)定并積極保證法律的實(shí)施。[14]該原則是法治國(guó)思想在行政法領(lǐng)域最為重要的體現(xiàn),是法國(guó)行政法的核心原則。
(一)行政法治原則的主要內(nèi)容
行政法治原則主要包含以下三項(xiàng)內(nèi)容:
1.行政行為必須具有法律依據(jù)。行政機(jī)關(guān)只能在法律授權(quán)的范圍內(nèi)采取行動(dòng),這是行政法治原則的根本要求。對(duì)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動(dòng),而無(wú)須法律授權(quán)。但是,對(duì)于行政機(jī)關(guān)來(lái)說(shuō),則沒(méi)有這種自由,而必須嚴(yán)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規(guī)則。這是行政行為與公民個(gè)人行為的最大區(qū)別。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機(jī)關(guān)職責(zé)清晰、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fù)其責(zé)。
行政機(jī)關(guān)的權(quán)限(包括事務(wù)、時(shí)間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規(guī)定在憲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當(dāng)成文法規(guī)定不明確時(shí),行政法院根據(jù)法的一般原則對(duì)成文法的規(guī)定進(jìn)行補(bǔ)充和解釋。行政機(jī)關(guān)不得超越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限范圍自由行動(dòng),否則,構(gòu)成“無(wú)權(quán)限”。無(wú)權(quán)限行為是最為嚴(yán)重的違法行為,在越權(quán)之訴中,“無(wú)權(quán)限”是行政行為被撤銷(xiāo)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無(wú)權(quán)限機(jī)關(guān)所作出的行為,屬于羈束行為,且該行為的內(nèi)容符合法律規(guī)定,有管轄權(quán)的機(jī)關(guān)在同樣的情況下也只能作出同樣的決定,行政法院對(duì)這種行為并不撤銷(xiāo),因?yàn)槌蜂N(xiāo)該行為“并不影響行政決定的結(jié)果和當(dāng)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費(fèi)訴訟時(shí)間。”[15]
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僅要求行政行為的存在須有法律依據(jù),而且進(jìn)一步要求行政行為的實(shí)施須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說(shuō),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過(guò)程必須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實(shí)現(xiàn)法律對(duì)行政行為全程的監(jiān)督和控制,使行政權(quán)在法律所設(shè)定的軌道上運(yùn)行。但是,我們不能把行政法治的這一要求,簡(jiǎn)單理解為行政機(jī)關(guān)只能機(jī)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則適用于具體事件而沒(méi)有任何斟酌選擇的余地。行政行為有羈束行為和自由裁量行為之分,它們受法律制約的程度上是有所區(qū)別的。但是,二者都必須受制于法律這一點(diǎn)是共同的,不可動(dòng)搖的。根據(jù)行政法治原則,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規(guī)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慮對(duì)行政行為規(guī)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條例的咨詢(xún)、討論和公布程序,行政處理的說(shuō)明理由和書(shū)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規(guī)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對(duì)人權(quán)利的考慮,因此行政機(jī)關(guān)必須遵守,否則行政法院將宣布該行為無(wú)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慮,行政法院對(duì)于形式違法的行政行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銷(xiāo),而是根據(jù)形式違法的具體情況分別作出撤銷(xiāo)、不予撤銷(xiāo)和補(bǔ)正等不同形式的靈活處理。
明確的管轄權(quán)與合法的形式共同構(gòu)成了控制行政權(quán)行使的主要條件,無(wú)權(quán)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國(guó)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銷(xiāo)行政決定的最初的兩個(gè)理由。在當(dāng)代的法國(guó),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因?yàn)椤笆掷m(xù)不僅限制每個(gè)公務(wù)人員的權(quán)力,也使每個(gè)公務(wù)人員受到其他公務(wù)人員的制約和補(bǔ)充。”[16]比如,法國(guó)在1978年公布實(shí)施了《改善行政機(jī)關(guān)與公眾關(guān)系法》,1979年公布實(shí)施了《說(shuō)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機(jī)關(guān)與公眾關(guān)系法》,1983年又公布實(shí)施了《行政機(jī)關(guān)與其使用人關(guān)系法令》等單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則的重要內(nèi)容。首先,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須以實(shí)現(xiàn)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黨派或者所屬團(tuán)體的利益。例如,當(dāng)某家旅館與市長(zhǎng)的某個(gè)親戚開(kāi)辦的旅館形成競(jìng)爭(zhēng)時(shí),該市長(zhǎng)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yàn)榻杩陉P(guān)閉該旅館。其次,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授權(quán)的特別目的。例如,在1875年的巴利塞訴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銷(xiāo)了省長(zhǎng)作出的關(guān)閉巴利塞先生的火柴場(chǎng)的決定,理由是該行為的目的不是法律與規(guī)章授予他權(quán)力時(shí)要保障的目的,而是為了維護(hù)國(guó)家財(cái)政部門(mén)的利益。[17]
行政行為的目的必須符合法律的規(guī)定是行政法治原則進(jìn)一步深化的表現(xiàn)。在法國(guó)行政法治進(jìn)程的初期,只要一種行政行為是由具備法定權(quán)限和資格的行政機(jī)關(guān)依據(jù)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會(huì)認(rèn)定該行為合法,而不問(wèn)該行為的目的和動(dòng)機(jī)是什么。隨著行政法治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行政法院發(fā)展了濫用權(quán)力的理論,根據(jù)該理論,行政法院可以審查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dòng)機(jī)。如果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dòng)機(jī)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該行為將被行政法院以濫用權(quán)力為由予以撤銷(xiāo),從而使每一項(xiàng)行政行為都處于行政法院的監(jiān)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對(duì)行政行為目的和動(dòng)機(jī)的審查極大地?cái)U(kuò)展了行政法治原則的內(nèi)容,狄驥認(rèn)為這導(dǎo)致了自由裁量行為概念在公法領(lǐng)域的消失。[18]
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還要求行政決定的內(nèi)容和法律根據(jù)合法。
3.行政機(jī)關(guān)必須以自己的積極行為來(lái)保證法律的實(shí)施。行政法治有兩層含義:消極的行政法治和積極的行政法治。消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規(guī)定的權(quán)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積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機(jī)關(guān)以自己的積極行動(dòng)保證法律的實(shí)施,這是法國(guó)行政法治原則的最新擴(kuò)展。
根據(jù)積極行政法治的要求,不僅行政機(jī)關(guān)拒絕作出實(shí)施法律的具體行政處理決定構(gòu)成不作為的違法,而且當(dāng)法律和上級(jí)機(jī)關(guān)條例要求行政機(jī)關(guān)必須制定條例,而行政機(jī)關(guān)不履行該義務(wù)的行為同樣也是違法的。法國(guó)最高行政法院在1959年的一個(gè)判決中聲稱(chēng),行政機(jī)關(guān)在情況需要的時(shí)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條例來(lái)維持秩序,就是違反法律。[19]1969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觀點(diǎn):當(dāng)制定行政條例為實(shí)施某個(gè)法律所必要時(shí),行政機(jī)關(guān)有義務(wù)制定這個(gè)條例。[20]
(二)行政法治原則的限制
行政法治原則是法國(guó)行政法的主要原則,行政法院利用該原則對(duì)行政行為進(jìn)行廣泛的監(jiān)督,對(duì)防止行政權(quán)的濫用起到了關(guān)鍵的作用。無(wú)論是行政處理行為還是行政條例都受到行政法治原則的支配。但是,該原則的適用是有限制的,不能適用于行政機(jī)關(guān)的某些行為,這類(lèi)行為主要包括以下兩種:
1.政府行為。行政法院出于避免與總統(tǒng)、議會(huì)和管理國(guó)際關(guān)系的當(dāng)局發(fā)生正面沖突的實(shí)際政治需要,對(duì)下列的政府行為提起的訴訟不予受理:
第一,涉及政府與議會(huì)兩院之間的憲法關(guān)系的行為,比如總統(tǒng)召集議會(huì)或推遲議會(huì)的命令,終止議會(huì)會(huì)議或解散眾議院或參議院的命令等。
第二,政府的外交行為,也就是涉及法國(guó)和其他國(guó)家之間的行為。比如政府對(duì)于國(guó)際條約的磋商、簽定、批準(zhǔn)、執(zhí)行等行為。
第三,總統(tǒng)根據(jù)1958年憲法第16條在國(guó)家遭到嚴(yán)重威脅時(shí),根據(jù)情況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另外,總統(tǒng)根據(jù)憲法第11條將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復(fù)決的行為。
政府行為制度主要是行政法院通過(guò)判例創(chuàng)造的,其范圍也主要是行政法院的判例所決定的。在法國(guó),先后有政治動(dòng)機(jī)理論、統(tǒng)治行為等理論對(duì)于政府行為的存在予以辯解。但是,無(wú)論如何解釋?zhuān)炔皇苄姓ㄔ罕O(jiān)督又不受普通法院監(jiān)督的政府行為畢竟是對(duì)行政法治原則的破壞。因此,隨著法律地位的鞏固和提高,行政法院通過(guò)判例逐漸縮小政府行為的范圍,從而擴(kuò)大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范圍。比如在1875年拿破侖親王訴戰(zhàn)爭(zhēng)部長(zhǎng)案中,行政法院拋棄了“政治動(dòng)機(jī)”理論,實(shí)質(zhì)上縮小了不受行政法院審查的政府行為的范圍。另外法國(guó)政府的外交活動(dòng)原則上不受法院的管轄,但是最近行政法院也通過(guò)案例減弱了這一原則性。[21]
2.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是指在發(fā)生了諸如戰(zhàn)爭(zhēng)、自然災(zāi)害等的特殊情況下,行政機(jī)關(guān)為了保證公共秩序和公務(wù)運(yùn)行的連續(xù)性而采取的特殊行動(dòng)。特殊情況在最初是指戰(zhàn)爭(zhēng),之后特殊情況的范圍越來(lái)越廣,擴(kuò)展到和平時(shí)期發(fā)生的危機(jī)和緊急情況,比如發(fā)生全國(guó)性的罷工或者是大規(guī)模的自然災(zāi)害等。
對(duì)于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行政法院不能用合法性原則進(jìn)行審查,否則,這類(lèi)行政決定可能都會(huì)因?yàn)檫`法而被撤銷(xiāo),這將使行政機(jī)關(guān)在面臨特殊緊急的情況時(shí),不能迅速采取行動(dòng)以消除現(xiàn)實(shí)存在的威脅,以維護(hù)公共利益和保證公務(wù)活動(dòng)連續(xù)進(jìn)行。但是,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對(duì)公民權(quán)利和自由是極大的威脅,必須對(duì)其加以制約和限制。因此,行政法院通過(guò)判例發(fā)展了行政法的另一項(xiàng)基本原則,即行政均衡原則。行政法院運(yùn)用均衡原則對(duì)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進(jìn)行監(jiān)督和制約,從而維系了公共利益和個(gè)人利益之間的平衡。
上述可見(jiàn),行政法治原則的適用存在著一定的限制,但是,隨著政府行為范圍的逐漸縮小,該原則的適用范圍正呈現(xiàn)出逐漸擴(kuò)大的趨勢(shì)。同時(shí),為了加強(qiáng)對(duì)自由裁量行為和特殊情況下的行政行為的監(jiān)督,行政均衡原則作為行政法治原則的補(bǔ)充應(yīng)運(yùn)而生。
三、行政均衡原則
在法國(guó),行政均衡原則(The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主要是適應(yīng)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quán)的需要而出現(xiàn)的,它是法國(guó)行政法院對(duì)具體行政行為的監(jiān)督逐漸強(qiáng)化的產(chǎn)物,是法治國(guó)思想進(jìn)一步深化的表現(xiàn)。二戰(zhàn)后,法國(guó)行政法院的權(quán)力迅速加強(qiáng),逐漸取得了獨(dú)立于行政機(jī)關(guān)的法律地位,到1970年代形成了對(duì)行政權(quán)力有效的監(jiān)督和制約,并建立起一整套以行政法治原則為中心的行政組織、行政行為、行政監(jiān)督和行政法院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隨著社會(huì)對(duì)公共服務(wù)需求的不斷增長(zhǎng),國(guó)家加強(qiáng)了對(duì)社會(huì)的干預(yù),行政事項(xiàng)迅速增多,行政自由裁量權(quán)出現(xiàn)了日益擴(kuò)大、難以監(jiān)督的趨勢(shì)。法院對(duì)自由裁量的行政行為和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難以直接運(yùn)用合法性原則進(jìn)行監(jiān)督和控制。在此情況下,行政法學(xué)家們根據(jù)具體案件總結(jié)出了一些在特定情況下適用的、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quán)的均衡原則。
(一)行政均衡原則的涵義及其主要內(nèi)容
“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duì)于行政機(jī)關(guān)的具體行政行為進(jìn)行司法監(jiān)督或?qū)彶榈脑瓌t,其含義目前仍沒(méi)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shuō)來(lái),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jī)關(guān)具有自由裁量權(quán)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wú)法依據(jù)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duì)行政行為進(jìn)行裁決的情況下,監(jiān)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xiāo)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shí)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2]該原則的本質(zhì)是行政法院通過(guò)對(duì)行政行為的均衡性審查,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權(quán)的濫用,維護(hù)行政機(jī)關(guān)和相對(duì)人之間,公共利益和個(gè)人利益之間的平衡。一般認(rèn)為,下列行為違反了均衡合理原則:[23]
1.判斷事實(shí)明顯錯(cuò)誤。在很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行政法院只審查行政決定的合法性而不審查行政決定的適當(dāng)性,以免以行政法院代替行政機(jī)關(guān),妨礙行政效率。事實(shí)問(wèn)題屬于行政機(jī)關(guān)自由裁量權(quán)的范圍,行政法院不評(píng)價(jià)行政機(jī)關(guān)事實(shí)上是否應(yīng)當(dāng)作出某項(xiàng)決定。但是,進(jìn)入二十世紀(jì)以后,為了加強(qiáng)對(duì)自由裁量權(quán)的監(jiān)督,行政法院在“越權(quán)之訴”中開(kāi)始審查作為行政行為根據(jù)的事實(shí)問(wèn)題,將“判斷事實(shí)明顯錯(cuò)誤”作為撤銷(xiāo)行政行為的理由之一。所謂“明顯錯(cuò)誤”是指不需要專(zhuān)門(mén)的知識(shí),任何通情達(dá)理的人根據(jù)一般的常識(shí)都能看出的錯(cuò)誤。當(dāng)一個(gè)行政行為存在這類(lèi)錯(cuò)誤時(shí),必然會(huì)造成事實(shí)和法律適用之間的失衡或者不相稱(chēng)。“當(dāng)行政決定的結(jié)果看起來(lái)有背良知、丑惡可恥、違背邏輯(例如,在公職部門(mén)中,一個(gè)小小的錯(cuò)誤導(dǎo)致解職)時(shí),法官將撤銷(xiāo)這個(gè)決定。”[24]而且,隨著地位的逐漸提高,行政法院以越來(lái)越靈活的方式來(lái)判斷“明顯”的特征。“判斷事實(shí)明顯錯(cuò)誤”是行政法院對(duì)自由裁量行政行為進(jìn)行均衡性監(jiān)督的最常見(jiàn)方式。通過(guò)這種均衡性監(jiān)督,行政法院力圖保持行政機(jī)關(guān)和行政相對(duì)人之間,公共利益與個(gè)人利益之間的平衡。
2.手段與目的不相稱(chēng)。行政機(jī)關(guān)有選擇達(dá)到行政目的手段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不是沒(méi)有限制的。在有多個(gè)手段可以達(dá)到法律所規(guī)定的目的情況下,如果行政機(jī)關(guān)所選擇的不是對(duì)行政相對(duì)人損害最少的手段,則屬于手段與目的不相稱(chēng)。手段與目的不相稱(chēng)造成了對(duì)個(gè)人權(quán)利的過(guò)度侵害,使公共利益和個(gè)人利益的關(guān)系失去了平衡。行政法院對(duì)行政行為手段和目的的均衡性監(jiān)督主要適用于兩個(gè)方面:第一,適用警察行政領(lǐng)域。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1933年的“本杰明”案。在該案中,本杰明先生要求舉辦一個(gè)藝術(shù)研討會(huì),但是,市長(zhǎng)擔(dān)心發(fā)生騷亂,因此以維持公共秩序?yàn)橛桑铝罱寡杏憰?huì)的舉行。最高行政法院認(rèn)為,市長(zhǎng)可以采取其他手段達(dá)到維持公共秩序的目的,如召集大量警察,既可以避免騷亂,又不至于對(duì)公民的自由構(gòu)成威脅。再如,在1953年的一個(gè)判決中,行政法院撤銷(xiāo)了市長(zhǎng)的一個(gè)命令,市長(zhǎng)規(guī)定集市上的流動(dòng)商販必須具有對(duì)第三人傷害保險(xiǎn)的保險(xiǎn)單,法院認(rèn)為為了保護(hù)公共安全,這項(xiàng)規(guī)定對(duì)進(jìn)行危險(xiǎn)表演的藝人來(lái)說(shuō)是必要的,但是對(duì)于販賣(mài)糖果和花卉的商販來(lái)說(shuō)是過(guò)分的。[25]第二,適用于監(jiān)督“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對(duì)于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法院無(wú)法進(jìn)行合法性監(jiān)督,但是,為了避免該類(lèi)行為造成對(duì)公民權(quán)利和自由的造成過(guò)度的侵害,行政法院仍然要對(duì)行政行為進(jìn)行均衡性審查,這包括審查特殊情況是否存在;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dòng)機(jī)是否是為了滿(mǎn)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其行政是否與當(dāng)時(shí)的情況相適應(yīng),是否超過(guò)了必要的限度。可見(jiàn),在上述的兩種情況中,行政法院同樣是致力于在公共秩序和公民的自由之間,公共利益和個(gè)人利益之間尋求合理的均衡以避免行政權(quán)對(duì)相對(duì)人的過(guò)度侵害。
3.損失與利益失衡。這是指行政決定所要實(shí)現(xiàn)的利益和所造成的損害結(jié)果之間不相稱(chēng),失去平衡的情況。行政法院對(duì)行政行為的這種均衡性監(jiān)督主要適用于計(jì)劃行政與公用征收相關(guān)的領(lǐng)域。如在計(jì)劃行政領(lǐng)域,行政法院曾經(jīng)以一個(gè)飛機(jī)場(chǎng)開(kāi)放計(jì)劃可能花費(fèi)的資金與有關(guān)市鎮(zhèn)可能提供的資金之間不成比例為由而宣告該計(jì)劃違法。[26]又如,在1971年的一項(xiàng)判決中,行政法院根據(jù)均衡原則拒絕了居民訴請(qǐng)撤銷(xiāo)某項(xiàng)市政工程計(jì)劃的要求。在該案中,法院認(rèn)為該工程計(jì)劃中修建一條公路的得益高于因此而征用拆除的90所房屋的價(jià)值。在類(lèi)似的另外一個(gè)案件中,盡管地方議會(huì)為了公共利益具有提供牙科診所的廣泛權(quán)力,行政法院仍然可以審核是否有必要在該地區(qū)設(shè)置診所以及公共投資與收益是否相稱(chēng)。[27]在上述案件中,由于行政機(jī)關(guān)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quán),行政法院難以應(yīng)用行政法治原則進(jìn)行監(jiān)督審查,同時(shí),由于這類(lèi)案件的專(zhuān)業(yè)性和技術(shù)性很強(qiáng),法官中也很難找出“判斷事實(shí)是否明顯錯(cuò)誤”,因此,法院往往審查公共工程計(jì)劃所可能得到的效益和可能引起的損害之間是否達(dá)到了平衡。法國(guó)法學(xué)家古斯塔夫。佩澤爾在談到法律對(duì)行政自由裁量權(quán)的限制時(shí)指出:“在為公益事業(yè)而進(jìn)行的行政征用方面,今天法官監(jiān)督是否存在對(duì)私有財(cái)產(chǎn)的損害,財(cái)政成本和可能對(duì)社會(huì)產(chǎn)生的不便,或征用是否損害其他公共利益,它所代表的利益是否過(guò)分。”[28]可見(jiàn),行政法院對(duì)這類(lèi)案件的審查是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權(quán)衡各方面利弊的結(jié)果。法國(guó)行政法學(xué)稱(chēng)這種權(quán)衡是“損失和利益對(duì)較表”。[29]由于損益平衡監(jiān)督實(shí)際上最接近于對(duì)行政行為進(jìn)行妥當(dāng)性的判斷,因此在實(shí)踐中的運(yùn)用受到嚴(yán)格的限制。
(二)行政均衡原則的限制與前景
在法國(guó),行政法院對(duì)行政行為的監(jiān)督主要表現(xiàn)為合法性審查,對(duì)行政行為是否合理、妥當(dāng)和均衡的監(jiān)督被嚴(yán)格限制在特定的范圍內(nèi)。目前,行政法院只能將該原則適用于對(duì)行政處理的審查而不適用于對(duì)行政條例的監(jiān)督。在實(shí)踐中,行政法官盡量不應(yīng)用均衡原則,而是采用行政法治等原則對(duì)行政行為進(jìn)行監(jiān)督和審查。因此,行政均衡原則是以行政法治原則的補(bǔ)充的面目出現(xiàn)的。
行政均衡原則的適用之所以有上述的限制,一方面是分權(quán)的需要。行政權(quán)和行政審判權(quán)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權(quán)力,有必要保持二者之間適當(dāng)?shù)姆蛛x和獨(dú)立,這在客觀上要求行政審判權(quán)對(duì)行政權(quán)的監(jiān)督應(yīng)當(dāng)保持在適當(dāng)?shù)姆秶鷥?nèi),以免行政審判權(quán)過(guò)分侵犯行政權(quán),妨礙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是歷史傳統(tǒng)的原因。“獨(dú)立的普通和行政法院為法國(guó)保持了基本法治,從而在動(dòng)蕩的政局背后為社會(huì)帶來(lái)了穩(wěn)定。但或許是大革命的沖擊,法國(guó)的法院至今堅(jiān)持著謙遜的外觀。”[30]大革命以后的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行政審判權(quán)依附于行政權(quán),因而行政機(jī)關(guān)也就放心地接受了行政法院的監(jiān)督。但是,隨著地位的逐步提高,行政法院對(duì)行政權(quán)實(shí)行了越來(lái)越廣泛和深入的監(jiān)督,這種情景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huì)喚醒法國(guó)人對(duì)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的回憶。因此,行政法院對(duì)行政權(quán)的監(jiān)督在富有創(chuàng)新性同時(shí)又是非常謹(jǐn)慎的。行政均衡原則的適用實(shí)質(zhì)上相當(dāng)于對(duì)行政行為是否適當(dāng)?shù)膶彶椋@已經(jīng)達(dá)到了行政權(quán)和行政審判權(quán)相互交叉的灰色地帶,稍有不慎,就有行政審判權(quán)侵犯行政權(quán),行政審判權(quán)代替行政權(quán)之嫌。因此,行政法院在適用均衡原則時(shí)也就格外小心謹(jǐn)慎,嚴(yán)格限制其適用范圍。
如上所述,由于分權(quán)和歷史等原因,行政均衡原則的適用存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應(yīng)當(dāng)看到的是該原則對(duì)控制行政自由裁量行為和政府日漸擴(kuò)大的特殊權(quán)力起到了獨(dú)特的作用。在很多情況下,行政法院對(duì)行政行為的監(jiān)督表面上是利用的行政法治原則,實(shí)則應(yīng)用的是行政均衡原則。可以預(yù)見(jiàn)的是,隨著行政法院獨(dú)立地位的進(jìn)一步鞏固和權(quán)力的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以及社會(huì)對(duì)行政自由裁量權(quán)和特殊情況下的行政決定加強(qiáng)監(jiān)督的需求的不斷增長(zhǎng),該原則在法國(guó)行政法中將發(fā)揮將越來(lái)越大的作用。目前,該原則已經(jīng)超越了行政法領(lǐng)域,為法國(guó)憲法委員會(huì)所繼承,用以審查法律的合憲性。[31]同時(shí),該原則也超出了國(guó)界對(duì)其他國(guó)家的行政法學(xué)產(chǎn)生了相當(dāng)?shù)挠绊憽1热纾?guó)上議院認(rèn)為,英國(guó)行政法將來(lái)有可能接受這一原則,作為審查行政行為的一項(xiàng)依據(jù),并承認(rèn)它相當(dāng)于英國(guó)的“溫斯伯里不合理性原則”(WednesburyPrincipleofUnreasonableness)。行政法學(xué)者約威爾和萊斯特爾也主張英國(guó)應(yīng)引進(jìn)和移植這一原則,以彌補(bǔ)英國(guó)行政法原則的缺陷。[32]從現(xiàn)實(shí)看,均衡性監(jiān)督在歐洲法中也已經(jīng)得到了實(shí)際的應(yīng)用,比如,歐洲法院在“超熱牛奶許可案”、“消毒牛奶進(jìn)口案件”、“產(chǎn)品國(guó)籍標(biāo)志案”以及“原油進(jìn)口案”等一系列案件中都運(yùn)用了該原則。[33]隨著歐洲一體化進(jìn)程的不斷推進(jìn),這一原則將不僅對(duì)歐洲大陸行政法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也將會(huì)被英國(guó)行政法所接受而帶來(lái)英美法系行政法的變化。
作者:武漢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
[①][法]勒內(nèi)。達(dá)維:《英國(guó)法和法國(guó)法:一種實(shí)質(zhì)性比較》,潘華仿等譯,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頁(yè)。
[②]沈宗靈:《現(xiàn)代西方法理學(xué)》,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頁(yè)。
[③][法]萊昂。狄驥:《憲法學(xué)教程》,王文利等譯,遼海出版社、春風(fēng)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yè)。
[④][法]萊昂。狄驥:《憲法學(xué)教程》,同前,第29頁(yè)。
[⑤][法]勒內(nèi)。達(dá)維:《英國(guó)法和法國(guó)法:一種實(shí)質(zhì)性比較》,同前,第102頁(yè)。
[⑥][法]勒內(nèi)。達(dá)維:《英國(guó)法和法國(guó)法:一種實(shí)質(zhì)性比較》,同前,第115頁(yè)。
[⑦][美]莫里斯。拉朗熱:《國(guó)政院》,《圖萊法學(xué)雜志》1968年第1期。轉(zhuǎn)引自袁曙宏、趙永偉:《西方國(guó)家依法行政比較研究-兼論對(duì)我國(guó)依法行政的啟示》,《中國(guó)法學(xué)》2000年第5期。
[⑧]張千帆:《西方體系》(下冊(cè)。歐洲憲法),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yè)。
[⑨][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2年版,第95頁(yè)。
[⑩][日]早川武夫等:《外國(guó)法》,張光博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5頁(yè)。
[11]王名揚(yáng):《法國(guó)行政法》,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yè)。
[12][法]弗德?tīng)枺骸缎姓ā罚?984年法文版,第107頁(yè)。轉(zhuǎn)引自王名揚(yáng):《法國(guó)行政法》,同前,第22頁(yè)。
[13]參見(jiàn)胡建淼:《比較行政法-20國(guó)行政法評(píng)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頁(yè)。
[14]這里涉及的“法律”,是指廣義上的法律,在法國(guó)包括:憲法、法律、歐共體的規(guī)則和指令、法的一般原則、判例和條例。
[15]王名揚(yáng):《法國(guó)行政法》,同前,第689頁(yè)。
[16][法]莫里斯。奧里烏:《行政法與公法精要》(上冊(cè)),龔覓等譯,遼海出版社、春風(fēng)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541頁(yè)。
[17]參見(jiàn)胡建淼:《外國(guó)行政法規(guī)與案例評(píng)述》,中國(guó)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616頁(yè)。
[18][法]萊昂。狄驥:《公法的變遷。法律與國(guó)家》,冷靜譯,遼海出版社、春風(fēng)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71頁(yè)。
[19]見(jiàn)法國(guó)最高行政法院1953年Doublet案件的判決。
[20]見(jiàn)法國(guó)最高行政法院1964年11月27日DameVreRenard案件判決。
[21]參見(jiàn)胡建淼:《外國(guó)行政法規(guī)與案例評(píng)述》,同前,第614頁(yè)。
[22]王桂源:《論法國(guó)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則》,《法學(xué)研究》1994年第3期。
[23]參見(jiàn)王桂源:《論法國(guó)行政法中的均衡原則》,同前。
[24][法]古斯塔夫。佩澤爾:《法國(guó)行政法》,廖坤明等譯,國(guó)家行政學(xué)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6頁(yè)。
[25]王名揚(yáng):《法國(guó)行政法》,同前,第472頁(yè)。
[26]趙娟:《合理性原則與比例原則的比較研究》,《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人文科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0年第5期。
[27]張千帆:《法國(guó)的國(guó)政院與行政行為的司法控制》,《中國(guó)法學(xué)》1995年第3期。
[28][法]古斯塔夫。佩澤爾:《法國(guó)行政法》,同前,第47頁(yè)。
[29]王名揚(yáng):《法國(guó)行政法》,同前,第699頁(yè)。
[30]張千帆:《西方體系》(下冊(cè)。歐洲憲法),同前,第6頁(yè)。
[31]張千帆:《西方體系》(下冊(cè)。歐洲憲法),同前,第98頁(yè)。
第8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行政處罰是國(guó)家特定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懲戒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個(gè)人、組織的一種行政行為,屬行政制裁范疇。行政處罰作為一種法律制裁,是對(duì)違反行政管理法規(guī)的行政相對(duì)人的一種懲戒、教育手段。目的是使相對(duì)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違法行為。
因?yàn)樾姓幜P本身所具有的強(qiáng)制力、直接影響相對(duì)人權(quán)利義務(wù)、對(duì)相對(duì)人的聲譽(yù)、財(cái)產(chǎn)、行為甚至人身自由產(chǎn)生不利后果的特點(diǎn),使得行政處罰必須嚴(yán)格依法設(shè)定、執(zhí)行、監(jiān)督與救濟(jì),并遵守法定的行政處罰原則與適用原則。筆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討論的,就是行政處罰適用中的“一事不再罰”原則在理論與實(shí)踐中的幾個(gè)問(wèn)題。
“一事不再罰”是行政法學(xué)界對(duì)行政處罰適用原則之一的一個(gè)概括性表述,其具體內(nèi)涵、定義依我國(guó)《行政處罰法》第二十四條為“對(duì)違法當(dāng)事人的同一違法行為,不得給予兩次以上行政罰款的行政處罰”。這一原則的規(guī)定主要是為了防止處罰機(jī)關(guān)對(duì)相對(duì)人同一違法行為以同一事實(shí)理由處以幾次行政處罰,以獲得不當(dāng)利益,同時(shí)也是為了保障處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對(duì)人法定的合法權(quán)益不受違法的行政侵犯,使一定的違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規(guī)的行為與一定的法律責(zé)任相互確定掛鉤,進(jìn)而體現(xiàn)法律制度與行政管理的可預(yù)見(jiàn)性與穩(wěn)定性?xún)r(jià)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關(guān)系中,處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體擁有以國(guó)家名義出現(xiàn)的行政管理權(quán),具先定力、執(zhí)行力與強(qiáng)制力。尤其是隨著現(xiàn)代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國(guó)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國(guó)民生活的各個(gè)領(lǐng)域,對(duì)行政權(quán)這一管理優(yōu)益權(quán)規(guī)范的必要性日益為人們所認(rèn)識(shí)并逐漸突出。而在行政管理法律關(guān)系中的相對(duì)人一方,由于與行政主體的地位的不對(duì)等性,其合法權(quán)益在國(guó)家公權(quán)力的沖突中便顯得尤為渺小。行政相對(duì)人即使是違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規(guī),受到一定的行政處罰,其作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屬性的合法權(quán)益的保障與事后救濟(jì)與保障是現(xiàn)代行政的價(jià)值理念之一。“一事不再罰”原則的背后所體現(xiàn)的,就是這種法理價(jià)值理念的追求。將其通俗化來(lái)表述,便是犯錯(cuò)一次就只能、只需承擔(dān)一次行政處罰,且這種處罰必須是先有的、法定的。
“一事不再罰”原則在我國(guó)理論研究與立法實(shí)踐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處,導(dǎo)致了行政管理實(shí)踐中的一些混亂、相悖狀態(tài)。以下筆者試述之:
一、《行政處罰法》對(duì)“一事不再罰”處罰主體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確定性。對(duì)幾個(gè)機(jī)關(guān)都有管轄權(quán)的違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規(guī)的行為該由哪個(gè)行政機(jī)關(guān)進(jìn)行處罰沒(méi)有明確的規(guī)定。例如有的規(guī)章法規(guī)規(guī)定對(duì)某一違法行為,可以由幾個(gè)機(jī)關(guān)去處理,與此同時(shí),無(wú)論是出于現(xiàn)實(shí)還是法理都不允許相對(duì)人對(duì)處罰的主體進(jìn)行選擇。因此,由于部門(mén)利益、權(quán)責(zé)劃分不清,機(jī)關(guān)間協(xié)調(diào)不盡充分等原因,在實(shí)踐中產(chǎn)生了由不同行政機(jī)關(guān)分別進(jìn)行一次行政處罰而在事實(shí)上產(chǎn)生“一事多次罰”的形式上合乎法律原則但卻悖離原則的內(nèi)在價(jià)值要求的合法、矛盾現(xiàn)象。筆者暫稱(chēng)為行政處罰主體的競(jìng)合。這無(wú)疑是不符合行政統(tǒng)一性、行政法治、行政管理價(jià)值的追求的。
二、《行政處罰法》的“一事不再罰”原則對(duì)適用法規(guī)時(shí)的沖突沒(méi)有提供合適的沖突適用規(guī)則。隨著行政法制的發(fā)展與法律法規(guī)的制定與對(duì)社會(huì)關(guān)系調(diào)整、保障的日益細(xì)化,一個(gè)違反行政管理法規(guī)的行為可能會(huì)導(dǎo)致侵犯了不同社會(huì)利益客體的后果,這時(shí)就可能會(huì)出現(xiàn)保護(hù)不同利益客體的特別法都對(duì)該行為競(jìng)相適用,而同時(shí)產(chǎn)生幾個(gè)不同的法律責(zé)任、法律后果的現(xiàn)象。筆者稱(chēng)之為法律法規(guī)適用的競(jìng)合。而此時(shí)如果對(duì)相對(duì)人依據(jù)不同的法律法規(guī)做出幾個(gè)不同的處罰決定,就明顯違反“一個(gè)行為,不得兩次以上處罰(此處亦可表現(xiàn)為幾份處罰,但處罰之間肯定會(huì)出現(xiàn)時(shí)間上的先后、客觀上的表現(xiàn)也是次序不同)”的原則。而如果只做出一項(xiàng)處罰決定,往往會(huì)面臨一般法與一般法之間、特別法與特別法之間互無(wú)優(yōu)位難以決定選擇適用的難為局面。這種情況給行政主體的處罰管理提出了行政執(zhí)法實(shí)踐上的難題。
三、《行政處罰法》的“一事不再罰”原則對(duì)都有處罰權(quán)、相同行政職能的不同行政主體由誰(shuí)處罰、是否排斥相同的處罰無(wú)提供法定指引。筆者認(rèn)為這是行政處罰主體競(jìng)合的另一種特殊表現(xiàn)形式。由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發(fā)達(dá),物流、人流、資金流與智力成果大流通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甚至世界范圍內(nèi)的出現(xiàn),一個(gè)違法行為在一地已被一個(gè)行政主體處罰后,是否還應(yīng)承擔(dān)另一地另一相同職能但主體資格不同的行政主體以相同理由、依據(jù)而做出的行政處罰決定呢?例如司機(jī)王某運(yùn)送西瓜由A省到C省,途中被A省道路行政管理部門(mén)認(rèn)定車(chē)輛超載并處以罰金。后途經(jīng)B省又被當(dāng)?shù)芈氛芾聿块T(mén)以超載為由處以罰金。最后進(jìn)入C省境內(nèi)再次受到C省路政管理部門(mén)的相同理由依據(jù)的第三次處罰。王某若以《行政處罰法》中的“一事不再罰”原則抗辯之,達(dá)到的答辯可能是“他主體的處罰并不代表本主體的處罰。本主體只要不對(duì)你進(jìn)行第二次處罰便不違犯該原則。”確實(shí),我國(guó)《憲法》與《行政組織法》都授權(quán)有關(guān)行政部門(mén)與行政主體資格與相應(yīng)的處罰權(quán)限。他們均以行政主體身份進(jìn)行行政規(guī)制、行政管理。其主體資格是法定的。以“一主體沒(méi)有實(shí)施兩次處罰,他主體并不代表本主體”的理由進(jìn)行抗辯似乎有其邏輯、法理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這種現(xiàn)象在現(xiàn)實(shí)行政管理處罰中廣泛的存在。“一事不再罰”原則對(duì)此似乎顯得無(wú)能為力。我們先且不論該抗辯理由是否成立,但單憑“一事不再罰”似乎無(wú)法判定其違法性與無(wú)效性。
出現(xiàn)這三種現(xiàn)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尚未充分完善、立法技術(shù)不夠成熟、行政理論研究還不夠細(xì)致等客觀因素,也有爭(zhēng)奪部門(mén)利益方面的主觀因素,筆者在此試結(jié)合法理學(xué)、憲法學(xué)與行政法學(xué)的一般理論、原則提出解決辦法。
一、對(duì)于前述第一項(xiàng)“一事不再罰”原則缺乏處罰主體法定唯一性的缺漏,首先應(yīng)該在立法上引起重視,進(jìn)而規(guī)范立法行為,減少不必要的“一權(quán)多授”、“多部門(mén)授權(quán)”,從而在立法設(shè)計(jì)上防止、杜絕此種不符合立法科學(xué)的缺陷。而在立法完全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之前,可以依照以下三個(gè)原則來(lái)解決。
1、專(zhuān)職部門(mén)優(yōu)于一般職能部門(mén)進(jìn)行管理、處罰的原則。這是考慮到現(xiàn)代行政的復(fù)雜性、專(zhuān)門(mén)性、技術(shù)性特點(diǎn)。由專(zhuān)門(mén)的職能部門(mén)管理、處罰更有利于行為性質(zhì)的認(rèn)定、違法行為后果的確認(rèn)與處罰幅度的統(tǒng)一性與科學(xué)性。
2、層級(jí)低的部門(mén)優(yōu)于層級(jí)高的部門(mén)進(jìn)行管理、處罰的原則。這是考慮到基層行政管理部門(mén)的分布面較廣,更有利于及時(shí)發(fā)現(xiàn)、處理違反行政法律法規(guī)的行為,也便利于當(dāng)事人依事后救濟(jì)程序提起行政復(fù)議、行政訴訟的管轄、處理與裁判。
3、通過(guò)行政程序法的規(guī)定,將法律法規(guī)中所有出現(xiàn)幾個(gè)行政處罰主體競(jìng)合的情形都整理規(guī)范歸結(jié)到由法律法規(guī)中規(guī)定的幾個(gè)機(jī)關(guān)組成的聯(lián)合執(zhí)法機(jī)構(gòu)以共同名義做出處罰決定。此方法可以作為上述兩個(gè)原則的補(bǔ)充。適用解決幾個(gè)專(zhuān)門(mén)職能部門(mén)之間、幾個(gè)一般職能部門(mén)之間、幾個(gè)同級(jí)行政機(jī)關(guān)之間的管理權(quán)確定的問(wèn)題。但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是現(xiàn)實(shí)中較難操作,要將法律法規(guī)中所有出現(xiàn)此種沖突的情形一一整理規(guī)范、再由法律規(guī)定授權(quán)聯(lián)合執(zhí)法機(jī)構(gòu)處理,實(shí)踐中將會(huì)導(dǎo)致增加立法整理的工作負(fù)擔(dān)與行政人員編制膨脹等弊端,所以只僅僅應(yīng)局限作為上述1、2兩個(gè)原則的補(bǔ)充。
行政法學(xué)界有學(xué)者提出可以通過(guò)重新定義“一事不再罰”原則來(lái)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其提出的定義為:“不得以同一事實(shí)和理由對(duì)同一違法行為罰兩次或兩次以上”,但筆者認(rèn)為這種表述在處罰主體的唯一性確定上還存有欠缺。而容易被默認(rèn)理解為“同一行政主體不得以同一事實(shí)和理由對(duì)同一違法行為出罰兩次或兩次以上”,而“由不同行政主體‘依法’同時(shí)以同一事實(shí)和理由對(duì)同一違法行為的處罰”則是符合“一事不再罰”的形式合法、實(shí)質(zhì)不合法現(xiàn)象,這就成了規(guī)避這一原則的“合法”情形。因此筆者認(rèn)為此種表述也不是十分嚴(yán)密的。
二、對(duì)于前述第二項(xiàng)“一事不再罰”原則對(duì)適用法律法規(guī)過(guò)程中的法律法規(guī)適用競(jìng)合沖突未能提供合適的沖突規(guī)則的問(wèn)題。在行政執(zhí)法實(shí)踐中,“之所以會(huì)有兩個(gè)以上法規(guī)、規(guī)章對(duì)同一行為從不同角度規(guī)定處罰,這是立法者從不同角度考慮問(wèn)題的結(jié)果。并不是這一行為變成兩個(gè)或兩個(gè)以上的行為。如果一個(gè)行為可按不同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定處罰兩次以上,隨著我國(guó)法規(guī)、規(guī)章的日益增加、規(guī)定日益細(xì)密,這一行為被處罰的次數(shù)將不斷增加,其后果不堪設(shè)想(引用1)。”這種幾個(gè)法律法規(guī)對(duì)同一違法行為進(jìn)行規(guī)制的情形似乎已超出“一事不再罰”的要求,但行政處罰所體現(xiàn)的是行政相對(duì)人在違反了行政管理法規(guī)后所應(yīng)依法承擔(dān)對(duì)己不利的法律責(zé)任,是一種對(duì)國(guó)家的責(zé)任、義務(wù)。這不同于有的刑事犯罪中還需負(fù)擔(dān)民事方面的賠償責(zé)任。既然只是一種責(zé)任形式,那就必須只能承擔(dān)一種責(zé)任后果。如果按照某些學(xué)者的意見(jiàn)認(rèn)為可以同時(shí)處以幾個(gè)不同的行政處罰,這無(wú)疑就給相對(duì)人設(shè)定了過(guò)重的不合理的法律責(zé)任負(fù)擔(dān);與此同時(shí),法律的行為規(guī)范指引性與責(zé)任后果的唯一確定性將被犧牲,穩(wěn)定性的存亡也會(huì)取決于執(zhí)法主體的意念之間。這就明顯是有悖于行政法治的行為規(guī)范、可預(yù)見(jiàn)性、穩(wěn)定性等基本價(jià)值要求的。所以這個(gè)法律法規(guī)適用競(jìng)合的問(wèn)題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并加以解決。在此,筆者試給出幾個(gè)沖突規(guī)則:
1、特別法優(yōu)于普通法(一般法)的原則。這是法理學(xué)中的一項(xiàng)基本原則,采用這一原則的原因與意義筆者在此不加累述。
2、新法優(yōu)于舊法的原則。這是因?yàn)樾姓芾砻鎸?duì)的是日新月異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新法往往更能體現(xiàn)立法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社會(huì)現(xiàn)象的把握、定性、調(diào)整的立法意圖與對(duì)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理念。從而實(shí)現(xiàn)行政管理與時(shí)俱進(jìn)的科學(xué)性與積極性,也有利于相對(duì)人對(duì)處罰理由、處罰依據(jù)、處罰方式與責(zé)任形式的接受與認(rèn)識(shí),避免出現(xiàn)使用過(guò)時(shí)的法律法規(guī)進(jìn)行處罰而導(dǎo)致相對(duì)人的逆反心理,導(dǎo)致降低行政效率與增加行政成本負(fù)擔(dān)。
3、對(duì)相對(duì)人處罰程度較輕的形式優(yōu)于對(duì)相對(duì)人處罰程度較重的形式的原則。這是因?yàn)樾姓幜P只是實(shí)現(xiàn)一定行政管理目的的具有教育、懲戒兩重性的手段,處罰不是目的,令相對(duì)人承擔(dān)不利的法律后果也不是目的。站在受處罰的相對(duì)人的角度而言,受到行政處罰本身在精神上已是一種不利的后果,責(zé)任形式、法律后果的輕重、制裁幅度的大小往往會(huì)影響、關(guān)系到相對(duì)人的認(rèn)識(shí)程度、重視程度與接受程度。所以,刻意地加重行政相對(duì)人的行政處罰負(fù)擔(dān)并不見(jiàn)得是絕對(duì)必要的。而站在行政處罰主體的角度而言,對(duì)相對(duì)人有意識(shí)、有選擇地適用制裁后果較輕的行政處罰形式,將無(wú)疑更能體現(xiàn)行政執(zhí)法、行政法治中“寓情于治”的成熟管理技巧,將會(huì)更容易實(shí)現(xiàn)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管理--反饋與意見(jiàn)的傳達(dá)與接受,有利于相對(duì)人對(duì)行政處罰行為的接受與理解,從而有助行政管理的順暢運(yùn)行與整體行政效率的提高。
4、絕對(duì)禁止同時(shí)對(duì)一行為適用多法、多種處罰的原則。同時(shí)適用多法、給予多種行政處罰的不利后果、于法于理的不成立前面已有論述。必須在行政處罰制度中強(qiáng)調(diào)這一原則,以免因?yàn)樾姓黧w故意或過(guò)失導(dǎo)致此種情形的出現(xiàn)。
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在適用上述三項(xiàng)沖突規(guī)則對(duì)相對(duì)人進(jìn)行處罰后,行政主體應(yīng)有義務(wù)對(duì)相對(duì)人進(jìn)行告知教育,使相對(duì)人了解自己的行為對(duì)社會(huì)關(guān)系造成的多種危害與在法律上的多種不利后果。從而在今后的行為中能提起應(yīng)有的注意,不致再違反他法而再受他種處罰。
三、對(duì)于《行政處罰法》的“一事不再罰”的原則對(duì)相同職能的不同行政主體該由誰(shuí)來(lái)處罰,是否排斥相同處罰無(wú)提供法定指引該如何處理。
筆者認(rèn)為在此之前還有個(gè)法理問(wèn)題需要明晰。舉上述王某運(yùn)輸西瓜的案例。對(duì)其進(jìn)行處罰的A、B、C三省路政管理部門(mén)都是合法、有權(quán)的、互無(wú)隸屬關(guān)系的三個(gè)獨(dú)立行政主體。他們?nèi)叩奶幜P行為似乎不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因?yàn)樗麄兙宰约旱闹黧w名義做出了“合法”的“一次”處罰,雖然理由依據(jù)是一樣的。然而這樣真的不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嗎?筆者認(rèn)為答案無(wú)疑是否定的。因?yàn)槿齻€(gè)互不隸屬的不同行政主體他們行政權(quán)均是來(lái)自于國(guó)家的授權(quán),也就是說(shuō)他們的權(quán)力均源屬于一個(gè)根本的主體--國(guó)家,而他們都只是國(guó)家設(shè)立在不同地區(qū)進(jìn)行行政管理的代表機(jī)構(gòu)。因此,這三個(gè)形似獨(dú)立的主體其實(shí)質(zhì)是一體的。
從法制的角度來(lái)考察,他們適用的是相同的法律法規(guī),而正是這套法律法規(guī)的原則要求他們“一事不再罰”。也就是說(shuō),相對(duì)人如果因違法行為被適用這套法律法規(guī)承擔(dān)了行政處罰不利后果,他們從法制統(tǒng)一的要求出發(fā)均應(yīng)予以確認(rèn)與保護(hù),而不能無(wú)視其他行政主體據(jù)此做出的處罰決定而冒違反“一事不再罰”之大不韙再次進(jìn)行處罰。這種行為本身就是違法與背離行政法制統(tǒng)一性要求的。
從相對(duì)人的角度來(lái)考察,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適用法律法規(guī)對(duì)相對(duì)人的違法行為進(jìn)行處罰是有絕對(duì)義務(wù)接受的,因?yàn)檫@種處罰是一種國(guó)家行為,反映的是國(guó)家對(duì)公共秩序的一種要求與調(diào)整,是國(guó)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與體現(xiàn),是由處罰機(jī)關(guān)代表國(guó)家意志做出的規(guī)制性的國(guó)家行為。而如果允許相同職能的不同行政主體對(duì)同一行為進(jìn)行多次處罰,就會(huì)使相對(duì)人產(chǎn)生“究竟哪一個(gè)處罰機(jī)關(guān)才代表國(guó)家?是不是一個(gè)處罰機(jī)關(guān)代表一個(gè)‘國(guó)家’?各個(gè)處罰機(jī)關(guān)是否各自代表‘各自’的‘國(guó)家’?”的疑問(wèn)。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疑問(wèn)是對(duì)國(guó)家(對(duì)外最高代表權(quán)、對(duì)內(nèi)最高統(tǒng)治權(quán))、行政權(quán)統(tǒng)一的疑問(wèn),其政治危害性是顯而易見(jiàn)的。會(huì)造成相對(duì)人對(duì)國(guó)家概念的理解、國(guó)家權(quán)力的行使、國(guó)家代表的唯一性等問(wèn)題的認(rèn)識(shí)混亂,甚至?xí)屜鄬?duì)人產(chǎn)生國(guó)家對(duì)內(nèi)表現(xiàn)形式之一的統(tǒng)一行政權(quán)被行政執(zhí)法機(jī)關(guān)故意割裂的認(rèn)識(shí),這對(duì)國(guó)家的統(tǒng)一、行政法制的統(tǒng)一、行政法制建設(shè)的破壞性無(wú)疑是致命的。
行政實(shí)踐中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大多是因?yàn)榈胤嚼嬷髁x、部門(mén)利益主義在作祟,行政管理不是一種獲利機(jī)制,我們更不能認(rèn)同“雁過(guò)拔毛”的合理性。行政管理是一個(gè)國(guó)家對(duì)公共秩序的要求、調(diào)整、規(guī)范,而不是某些人、某些機(jī)關(guān)牟利的機(jī)制。處理這個(gè)《行政處罰法》對(duì)相同職能的不同行政主體該由誰(shuí)來(lái)處罰,是否排斥相同處罰無(wú)提供法定指引的問(wèn)題,不是應(yīng)該設(shè)計(jì)出什么解決原則、方法機(jī)制的問(wèn)題,基于上述這個(gè)問(wèn)題的重大危害性,應(yīng)該在《行政處罰法》中予以明令禁止,只一律承認(rèn)肯定首次處罰的唯一合法性并賦予相對(duì)人對(duì)二次處罰的積極抗辯權(quán),以維護(hù)法制的整體統(tǒng)一性,制止濫用權(quán)力、爭(zhēng)奪利益亂法的不正常現(xiàn)象。
綜上所述,筆者認(rèn)為“一事不再罰”原則是必要與科學(xué)的,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等價(jià)值理念追求的。但在理論與實(shí)踐中,我們還須進(jìn)一步深入細(xì)致研究,以期盡識(shí)其真義,從而使其真正完備起來(lái),為行政執(zhí)法、行政處罰實(shí)踐提供更全面的理論指導(dǎo)與更強(qiáng)的依據(jù)性、可操作性。
(引用1)《行政法學(xué)》羅豪才主編,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205-206頁(yè)
主要參考書(shū)目:1、《行政法學(xué)》羅豪才主編,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修訂第一版
2、《行政法學(xué)》王連昌主編,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修訂版
第9篇:行政問(wèn)責(zé)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guò)將民訴中的證明責(zé)任概念引入刑訴,以從證明責(zé)任角度來(lái)加深司法工作人員對(duì)疑罪從無(wú)、疑罪從輕的理解。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孕育保障人權(quán)理念。為司法人員在實(shí)踐中把握疑罪從無(wú)原則提供一個(gè)可操作性的標(biāo)準(zhǔn)。
證明責(zé)任的分配是一個(gè)民事訴訟法上的概念,是指當(dāng)雙方當(dāng)事人窮盡一切手段都無(wú)法說(shuō)明某一個(gè)案件事實(shí)的真實(shí)情況,從而使得法官無(wú)法基于現(xiàn)有證據(jù)對(duì)該案件事實(shí)作出內(nèi)心確信時(shí),得判決主張對(duì)己有利事實(shí)之當(dāng)事人承擔(dān)該案件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髦C明責(zé)任,即承擔(dān)不利后果之責(zé)任,或說(shuō)敗訴責(zé)任。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案件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鞒龇ü僮杂尚淖C范圍時(shí),就進(jìn)入了證明責(zé)任的領(lǐng)域內(nèi)。自由心證和證明責(zé)任有各自作用的范圍。正是因?yàn)樽C明責(zé)任分配的存在,民事訴訟才得以獲得民眾普遍認(rèn)可的公正,盡管這種公正也許并不是真實(shí)情況的反映,但是程序公正為當(dāng)事人提供了公平的對(duì)抗平臺(tái),提供了有效的救濟(jì)手段,而敗訴是當(dāng)事人自己未能有效攻擊防御的結(jié)果,在情感上敗訴當(dāng)事人雖有不甘,但也是能夠接受的。從而平復(fù)了業(yè)已破壞的社會(huì)秩序。
在民事訴訟中證明責(zé)任分為主觀的證明責(zé)任和客觀的證明責(zé)任,主觀的證明責(zé)任又稱(chēng)為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客觀的證明責(zé)任則稱(chēng)為結(jié)果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主觀的證明責(zé)任又包含主張責(zé)任和提出證據(jù)的責(zé)任。結(jié)果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與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在民事訴訟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結(jié)果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是法院在案件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鳡顟B(tài)下,根據(jù)法律預(yù)設(shè)的證明責(zé)任分配規(guī)則進(jìn)行裁判的法律規(guī)范,對(duì)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鲿r(shí)如何判決具有實(shí)質(zhì)意義。它是由法律預(yù)先分配的,是不可轉(zhuǎn)移的,具有指導(dǎo)當(dāng)事人收集提供證據(jù),為法院在待證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鲿r(shí)提供裁判依據(jù)的作用。英美法系證據(jù)法又稱(chēng)之為“說(shuō)服責(zé)任”,即任何主張爭(zhēng)議事實(shí)的當(dāng)事人,不能以充分的證據(jù)說(shuō)服陪審團(tuán)和法官,或者爭(zhēng)執(zhí)的結(jié)果真?zhèn)尾幻鳎愠袚?dān)敗訴的風(fēng)險(xiǎn)。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是當(dāng)事人在訴訟過(guò)程中,都必須用證據(jù)證明其主張的事實(shí)的可信性和訴訟行為的正當(dāng)性。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根據(jù)訴訟進(jìn)行的情況動(dòng)態(tài)分配,在雙方當(dāng)事人之間動(dòng)態(tài)轉(zhuǎn)換。它具有引導(dǎo)案件事實(shí)的證明不斷深入的功能。因此在英美法系國(guó)家又稱(chēng)為“提供證據(jù)的責(zé)任”或“推進(jìn)責(zé)任”。
現(xiàn)在我們把證明責(zé)任的分配引入刑事訴訟中來(lái)討論:我們都知道刑事訴訟是一個(gè)追究犯罪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刑罰權(quán)的過(guò)程,其中有一項(xiàng)現(xiàn)代各國(guó)基本都已確立的原則被告人不得自證無(wú)罪原則。也就是說(shuō)如果要對(duì)被告人判處刑罰,那么控訴機(jī)關(guān)必須要有充分的證據(jù)來(lái)證明其對(duì)被告人之指控是真實(shí)可信的,否則就應(yīng)當(dāng)對(duì)被告人作無(wú)罪判決。而不得要求被告人自己證明自己的罪行,更不能為獲得被告人之口供而刑訊逼供。基于這點(diǎn)我們可以看出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在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之分配是絕對(duì)的不一樣的。民事訴訟行為意義上證明責(zé)任之分配是動(dòng)態(tài)的在當(dāng)事人之間轉(zhuǎn)換的,而刑事訴訟中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則完全由控訴機(jī)關(guān)來(lái)承擔(dān)。具體到案件中就是對(duì)于被告人的各項(xiàng)犯罪指控都是由控訴機(jī)關(guān)提出并收集提供證據(jù)進(jìn)行證明。所以從推進(jìn)訴訟進(jìn)程,引導(dǎo)案件事實(shí)證明不斷深入這點(diǎn)上,其責(zé)任幾乎都在控訴機(jī)關(guān)身上。所以可以這樣說(shuō)刑事訴訟不存在民事訴訟中所謂的動(dòng)態(tài)的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控訴機(jī)關(guān)承擔(dān)的是絕對(duì)的訴訟程序推進(jìn)責(zé)任。我們知道行為意義上的證明責(zé)任是包含主張責(zé)任和提出證據(jù)的責(zé)任兩部分的,在刑事訴訟具體案件中主張責(zé)任就是控訴機(jī)關(guān)對(duì)被告人之犯罪指控或說(shuō)指控罪名的提出。而后控訴機(jī)關(guān)必須圍繞其所指控之罪名提出充分證據(jù)來(lái)證實(shí)被告人確實(shí)犯該罪。那么控訴機(jī)關(guān)必須提出哪些事實(shí)呢?讓我們先分析一下民事訴訟的情況。在民事訴訟中將各種實(shí)體法律規(guī)范劃分為請(qǐng)求權(quán)規(guī)范和對(duì)立規(guī)范。對(duì)立規(guī)范又分為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權(quán)利受制規(guī)范、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是阻止權(quán)利的生效,比如合同雙方其中一方無(wú)行為能力,后又未被監(jiān)護(hù)人追認(rèn)。此時(shí)主張無(wú)行為能力就是主張一個(gè)妨礙規(guī)范。權(quán)利受制規(guī)范是指阻止權(quán)利的行使,比如同時(shí)履行抗辯、不安履行抗辯等。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是指權(quán)利被消滅已經(jīng)不存在。比如債務(wù)履行而消滅債權(quán)。在民事訴訟過(guò)程中主張權(quán)利的人必須證明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要件事實(shí)的存在,即對(duì)此事實(shí)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而針對(duì)此權(quán)利進(jìn)行抗辯提出妨礙規(guī)范、受制規(guī)范和消滅規(guī)范之當(dāng)事人則必須對(duì)其提出的以上三種規(guī)范承擔(dān)證明責(zé)任,也即當(dāng)以上規(guī)范要件事實(shí)無(wú)法證明時(shí)其要承擔(dān)敗訴的責(zé)任。那么在刑法中是否存在法律規(guī)范的如此劃分呢?我認(rèn)為是存在的。具體罪名之犯罪構(gòu)成要件即可看作是刑罰權(quán)規(guī)范(類(lèi)似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而刑法規(guī)定之正當(dāng)防衛(wèi)、緊急避險(xiǎn)等阻卻行為違法性之規(guī)范則為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刑事追訴時(shí)效則為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即一旦犯罪行為超過(guò)追訴時(shí)效就不再予以追究,刑罰權(quán)消滅。但是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證明之根本不同,在于后者對(duì)基本規(guī)范要件事實(shí)(權(quán)利形成規(guī)范)與對(duì)立規(guī)范之證明責(zé)任分配給雙方當(dāng)事人分別承擔(dān),而前者無(wú)論是基本規(guī)范還是對(duì)立規(guī)范都由控訴方承擔(dān)。也就是在刑事訴訟中,控訴方不僅要證明被告人行為符合具體罪名之犯罪構(gòu)成要件事實(shí),而且還要證明其不存在違法阻卻事由(權(quán)利妨礙規(guī)范)和未過(guò)追訴時(shí)效(權(quán)利消滅規(guī)范)。這一點(diǎn)恰是與被告人不得自證其罪原則一致的。因此我們得出的刑事訴訟證明責(zé)任分配結(jié)論是:對(duì)于基本規(guī)范和對(duì)立規(guī)范之案件事實(shí)之證明責(zé)任均分配給控訴機(jī)關(guān),當(dāng)這些案件事實(shí)真?zhèn)尾幻鲿r(shí)則由控訴機(jī)關(guān)承擔(dān)不利后果。
參考文獻(xiàn)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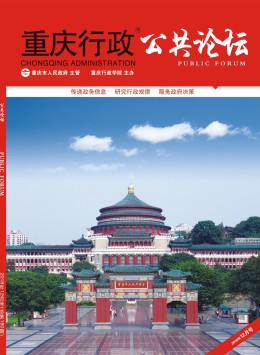
重慶行政 · 公共人物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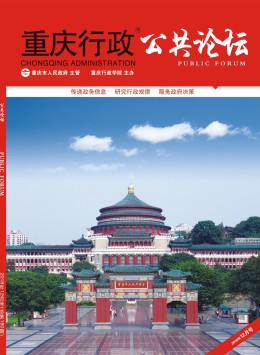
重慶行政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行政與法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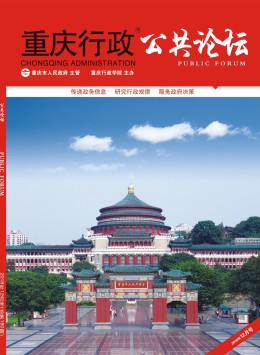
重慶行政 · 公共論壇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行政管理改革
級(jí)別:CSSCI南大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