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得其所的解釋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各得其所的解釋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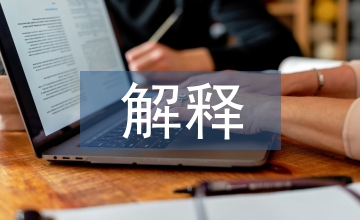
第1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關鍵詞:唐詩 宇文所安 李白 詩歌研究 中西文化
引言
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極具代表性的詩人,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一直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但同時作為世界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重視。早在十八世紀末,法國阿米奧就將李白介紹到西方。此后,經由埃茲拉?龐德、亞瑟?威利、維特?賓納、斯蒂芬?歐文的努力,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形象逐漸進入到了西方的視野。這個過程被呂福克總結為“起初是艱難的開始,爾后是盲目的崇拜,或是一絲不茍的逐字翻譯,以至于現今兼講內容正確、形式優美的翻譯嘗試。”[1]李白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凝聚了中國古代詩人的一種不羈的精神。在李白形象、作品向西方傳遞的過程中,李白也被賦予了更為豐富的內涵。
一、宇文所安對李白詩詞的解讀
斯蒂芬?歐文,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中文名宇文所安。1946年出生于美國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1972年獲得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言和文學的博士學位。留校任教。至1982年進入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擔任教授,教授中國文學。兩年后擔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中國文學教授和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他擅長的領域在于近代文學,以及比較詩學。他的許多作品集中關注三世紀到十三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中段。同時,他的專著《初唐詩》《盛唐詩》《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都反映出他對唐詩的熱愛和專注。宇文所安和保羅?克羅爾作為顧問編委,聯手另外五位編輯一起共同編撰了中國人文藏書系列。此系列中國人文藏書計劃將出版二十卷。歐文已經譯完杜甫詩歌全集,將于2015年初,作為中國人文藏書系列的開篇第一本呈現在讀者面前。
作為美國第三代漢學家,宇文所安不同于很多的中國學者,他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研治中國詩歌的方法。“中國學者可能起初是先聽課,讀一些別人的文章,然后再讀詩;我則是先讀詩,然后再讀別人的文章。”[2]宇文所安注重細讀,始于英國的“細讀法”,這種分析性的細讀,有助于克服由于過于熟悉所帶來的思維定勢或者障礙,避免過于受先驗印象的影響。宇文所安對歐洲文學甚至中亞文學涉獵甚多,在他廣泛的世界文化的閱讀基礎上,他對詩歌建立了一種客觀而理智的評判,他擯棄宋代以來形成的所謂文學正統觀。不應單純以選本或前人的評價來證明某些詩歌的價值,某些詩歌沒有價值。宇文所安將閱讀本身視為一種愉悅,同時他也將此作為對中國和西方古代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的唯一方法。
在涉及到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研究方面時,宇文所安認為遠比西方古代文學理論復雜。他眼中的中國文學批評強調多樣性和個別性,用不同的方式處理不同的問題。它不像西方那樣,形成完整的傳統意義上的概念系統。宇文所安特別關注唐代以來逐漸興盛的詩法、文法類的通俗理論,他認為“這些啟蒙性的東西已經深深沉淀在各個層面的文化之中。”宇文所安對李白的解讀建立在一個比較客觀和全面的背景下,他并沒有將后世盛贊的李白和杜甫等同于盛唐,而是采取一種較為謹慎的做法:將天才安置在其基本背景下。在宇文所安的《盛唐詩》中,就獨辟了第八章《李白:天才的新觀念》來解讀李白的詩歌作品和個性特征。
西方曾經有學者表示,寫李白的難度超過寫任何其他中國詩人,因為他具有最多面的特點,將李白與法國象征派詩人保爾?魏爾倫相比。宇文所安在理解李白的過程中,認為其“全力描繪和突出自己的個性,向讀者展示自己在作為詩人和作為個體兩方面的獨一無二”。[3]宇文所安曾經抱持一種觀點,“歷史研究必須用歷史敘述的方法。”但在寫作《初唐詩》《盛唐詩》過程中,歷史方法的局限性暴露了出來。于是他采用了一種更為靈活的方式來完成《傳統中國詩和詩學》,這本書中,不再像一般的論著,存在一個連貫且權威的主導的聲音,而是引入了一個對話模式中的敘述者,通過建立一個對話系統,展開一個基于歷史而又跨越歷史的批評空間,將中國文學史上一些現象,跨時空地放在一起討論。如在《李白:天才的新觀念》中,宇文所安就李白和王維的形象進行了比較,這兩者是同時代最著名的詩人。但宇文所安認為李白創作生涯的開端就大不同于其他詩人。在他看來,李白接受的詩歌教育和王維的大相徑庭,這導致他的詩歌呈現出不同于當時其他詩人的特點。
宇文所安以李白的《訪戴天山道士不遇》為例,展示了李白在開篇中沒有使用一般的場景,而使用了破壞全詩平衡的“犬吠”,這與當時任何經過京城訓練的詩人的手法大相徑庭,宇文所安認為李白大膽跨越傳統文學經驗,他這種刻意獲得的“奇”效,也為他贏得了讀者,這也進一步成為了他的詩歌標志。“在753年,殷[評價李白的《蜀道難》為‘奇之又奇’”。[4]同時,李白不同于京城詩人,他是個真正的“外來者”,宇文所安在對李白背景的描述中使用了非常謹慎的措辭,他認為李白的家庭背景含糊不清,真實的情況“可能在現實中黯淡無光”,李白在京城孤立無援。正因為如此,宇文所安對李白的理解有了一層更為深刻而現實的解讀。[5]通常批評家和傳記家持有一種觀點,即李白傾心于創作超現實的作品,他對神仙體裁的詩歌創作頗多,并在其詩詞作品中顯示出對這一現象的深刻理解,這于大多數詩人而言是罕見的。但宇文所安敏銳地認識到,當時社會背景中對于這一題材的扶持,使它成為“宮廷寵臣的迷人捷徑”,而這也成為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的李白所選擇的道路,因此,超現實的體裁都被李白作為馳騁想象力的對象,運用于詩詞創作之中。宇文所安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量極大,在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研讀之后,對回憶往事的心理狀態和寫作手法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于是他又完成了《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論述“在中國古代文學中,人們面對過去的東西,所產生的一種特定的創作心理和欣賞心理。”[6]
二、宇文所安對李白詩詞解讀中有待完善之處
宇文所安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以及作家個性化的解讀,給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為寬廣的思路和視角。但不可否認,在西方視角下的美國漢學家,解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時,也更易于產生一種基于西方人文觀念而產生的異讀。宇文所安在解讀王守仁的《旅文》時,認為王守仁同死者說話是“為了發泄他的怒氣,同時也是為了贖清他的罪責,他把責任推卸得一干二凈……他借此自夸,要死者對他感恩戴德,然而,就是這種隱而不宣的自我夸耀,削弱了他的訴訟的力量。”
宇文所安在對李白的解讀中,曾經留意到“在開元時期,率真狂誕的天才正在成為流行角色”。宇文所安并沒有認為這兩種類型的結合與蜀地有必然的內在關聯,不過他表示“蜀人經常以某種變化與這些價值標準聯系在一起。”進而他推測“蜀地可能事實上曾經是一個比中原較不穩定的地區,故暴力行為或暴力的夸言及變幻莫測行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再者,在宇文所安對李白和王維的比較中,以《盛唐詩》為例,他視王維為都城詩人的代表,將李白作為都城詩壇格格不入的外來者。[7]這種定位確實有一定道理,但宇文在論述李白與王維的差異時,單從兩人的作品中歸納出兩人不同的特點,未免稍顯草率。宇文所安認為李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的首聯“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里,由于“犬吠”太過破壞全詩的平衡,由此他得出兩位作者之間的不同差異,然而類似的現象在王維的作品中也不難發現:《贈劉藍田》首聯“籬間犬迎吠,出屋候荊扉。”由此可見,單從少量作品出發分析得出的結論也許不夠嚴密。不過這些微瑕不能掩蓋宇文所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對唐詩文化傳播所作出的創造性的貢獻。
結語
作為西方唐詩研究中首屈一指的美國漢學家代表的宇文所安,在對李白的解讀過程中,不僅言論新穎,且在研究視角、理論框架乃至具體結論等方面均使人耳目一新。他使用了與傳統詩歌詮釋不同的方法,不僅僅以知人論世的角度入手,還從句讀、音韻、修飾分析并最終完成體驗和思辨的結合。他常常因為一片現象激發靈感,捕捉一瞬間的獨到感觸,以文字為媒介,傳遞情感,抓住與讀者的共鳴。他憑借自己的歷史文化修養,深化了這一情感,將讀者帶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開拓了讀者的精神視野。更為不易的是,宇文所安跨越了不同語言的障礙,將李白的文學作品作為一種獨立的客觀事物來欣賞,而非作為社會或者歷史的附庸物來分析。這種既不按照中國歷來文學家所限定的框架,也不一定遵循現代文學批評家慣用的手法,卻反而向中國學者和讀者展示了一片新的天地,賦予了李白研究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呂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中國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
[2]郭娟.目的論視角下龐德《華夏集》語言意象評析[J].語文建設,2015(14).
[3]宇文所安.盛唐詩[M].北京:三聯書店,1998.
[4]唐旭.李白《蜀道難》的藝術表現特點探析[J].語文建設,2013(17).
[5]宇文所安.追憶[M].北京:三聯書店,2001.
[6]曹麗芳.李白《蜀道難》的創作時間問題――從一則注釋談起[J].語文建設,2011(9).
第2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知、情、行是彼此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轉化的。一般地說,“知”的培養是基礎;“行”的實現是關鍵和標志;“情”起中介和“催化劑”的作用。因此,學生思想品德的培養必須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導之以行、持之以恒”,促進四要素統一和諧地發展。
思想品德教育只考慮認識過程是遠遠不夠的,通過班會或團隊活動向同學們正面宣傳提倡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是需要的,但抓住時機,創設自然融洽環境,努力激發學生自身的“內應力”與道德情感則是另一回事。在校內、教室是學生接受思想品德教育的主要場所。教師在這兒,有的通過別開生面的班隊活動,有的挖掘學科自身的教育因素,有的則根據學生個性與心理特征,因勢利導,達到各種教育預期目的。但也應看到,由于對學生“主體需求是內化的原動力”這一點認識不足,在如何把社會首先規范內化為學生自己的品質方面研究得不夠,我們的某些方面教育就顯得脆弱與生硬。學生在那種正面教育場合,有時很難放開自己,他們經常只是首先意識的被動接受者,即使安排有學生在活動中發言,所說的也常是此刻我應該說此什么,而非內心真實所感,不能期望這種形成會達到很好的效果。其實,真能觸到學生靈魂的教育常常是不露痕跡。它不僅發生在操場上,發生在課間十分鐘,而且發生在事先無所準備的最自然的生活與情境中。因此,進行情感教育,是德育工作者打開學生心靈的啟動器,是“知”與“行”的中介和“催化劑”。
(一)以情育情,以情動人
情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感染性,也就是說,情能動情。即在一定的時間和范圍內,情感可以感染到其他的人,使之發生同樣的或與之相聯系的情緒。新組建的98級公關班,有兩位女同學因小事發生口角,繼而惡言相向,在班上掀起軒然大波。事后,我不是武斷地各挨五十板,而是找當事人心平氣各地了解情況,并打算抓住這個時機,召開一個主題班會。班會以小組為競賽單位,安排了學生喜聞樂道的歌曲、典故、諺語、名人名言等項目,圍繞著“團結、友情、親情”進行了緊張的比賽,學生們情緒高漲,竟相參與。當活動進行到時,我在黑板上寫了“大家庭中的你、我、他”幾個大字,緊著錄音機里傳出了《相親相愛》的歌曲,再一次引起了全班同學的情感共鳴。隨著如潮般的掌聲,那兩個同學不約而同地走上講臺,四只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通過這次班會,同學們認識到同學間,要互相“包容”,只有團結一心,班級這條“大船”才能順利到達成功的彼岸。而且,增強了集體的凝聚力,形成團結向上的班風。
(二)以知育情,以情促知
我們知道,單純地對學生說教是不會有好效果的,同樣單純地采用感化而不伴之以說理,也難以使學生產生有原則、有深度的道德情感。“知之深,愛之切”正是這個道理,因此,班主任應著力提高學生的道德認知,使他們知道應該怎么做、明白為什么要這樣做。如今年五月份,發生在美國轟炸南聯盟中國大使館的血腥事件,引起了全世界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我趁此機會讓學生觀看電視,收集有關新聞報道,激發他們的愛國激情,發出了“中國人民不可欺”的強烈心聲。同時,又讓他們認識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激勵他們“為中華崛起讀書”以實際行動來聲討美國的暴行。這樣,無疑對學生進行了一次有血有肉的愛國主義教育。也就是說,認知越豐富,明理越深刻,情感就會越深厚。
(三)以行育情,以情導行
情感的另一特點是實踐性。實踐是情感形成和轉變的基礎,也是搖動情感發展的動力。所以情感教育要從實踐開始,在實踐中,以行育情,越實踐,學生的情感就越深,反過來,情感越深,就越愿意實踐,從而形成自覺行為。
在以“愛心獻功臣”的活動中,我班學生紛紛捐款,奉獻了自己的一片愛心。錢雖不多,但卻體現了中國青少年對那些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出生入死的功臣的崇敬之情和愛國、愛民族的高尚情操。
第3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婚姻是組成家庭的基本形式,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一種必然的永遠不會消亡的現象。然而,人們在對婚姻進行解讀過程中往往只是知其大略而不得根本,甚而對中國的婚姻制度多有偏頗。筆者乃性情中人,亦屬好事之輩,閑暇中通過瀏覽中國文化要典,得之一二,故發文與同仁共享。
婚姻,古學謂之“昏姻”或“昏因”。《說文》曰:“禮,娶婦以昏時,故曰昏。”何以要在昏夜娶婦呢?原來,我國最初的婚姻是掠奪婚,掠奪的婦女要在黑夜里才能得手。后世結婚便沿用了這個習慣,都在夜里迎娶,由此逐漸形成了婚姻的概念,同時把婚姻之禮稱之為婚禮。
古代對婚姻解釋有三,其一,漢代鄭玄說:“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唐代孔穎達解釋:“男以昏時迎女,女姻男而來……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這里是從嫁娶的儀式來說的。其二,鄭玄說:“婿曰婚,妻曰姻。”孔穎達說:“……此據男女之身,婿則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古云婿曰婚,妻曰姻。”這是從夫妻的稱謂來說的。其三,《爾雅•釋親》中說“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為姻兄弟。”《鄭風孔疏》說:“婦黨稱婚,婿黨稱姻。”概而述之以上三種,意思為:婿于昏時娶婦,婦因婿而來,隨之定為夫妻的稱謂,建立兩家姻緣親屬關系,這些都是要通過婚姻儀式來實現的。由此,我們在明白了為什么要進行結婚儀式的同時,也明白了婚姻的概念時產生于嫁娶之后的。因為,嫁娶是專指掠奪、買賣的婚嫁行為,而婚姻是專指聘娶婚姻行為的。
依據《禮記》中的解釋,古時候的結婚原由大多是為擴大家族勞力的需要、為祭祀祖先、傳宗接代或固定人倫而結婚的,因此,中國古代社會的婚姻,是以家族需要為核心的,婚姻當事人的意志根本不在考慮范圍以內。嚴格說,實際上是兩個家族間的交換行為。所以一旦發生兩廂情愿的個人感情或者自由戀愛的行為,就會被視為行為,父母國人皆賤之。
我國古代封建制度下的婚姻,直至以后才逐漸瓦解。隨著歷史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自由戀愛成就了不少心有靈犀的男男女女,“有情人終稱眷屬”的幸福婚姻遍地皆是。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隨著改革開放的社會影響,逐漸富起來的一些國民開始肆意踐踏原本美滿的幸福與婚姻。演繹出了一目目“三角戀”、“婚外情”的丑劇。不少獲得了解放和自由的女性更是不知自重地拿著自己的肉體做著出賣靈魂的交易。好在人們的覺悟有所提高,盡管不少的人仍然在做著“路邊的野花不采白不采”的勾當,但“喜新不厭舊”不也成為了一種各得其所的時尚嗎?
第4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于是,在找過幾份工作無果之后,她也就一心一意地為他做起了全職太太,起初的日子是甜蜜溫馨的,因為有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她不必再每天手忙腳亂地買菜做飯洗衣拖地,她可以仔細研究食譜,把精挑細選的原材料變成一道道美味的菜肴,也可以自得其樂地把家里打掃得窗明幾凈,男人每天回到家里,都有可口的飯菜和舒適的環境,所以兩人都各得其所。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日子開始漸漸變了味道,首先是她自己開始厭倦這種仿佛與世隔絕般的主婦生活,做完了家務的她,常常對著空空的屋子發呆,茫然而無聊;而男人對她的態度也開始了微妙的變化,不僅理所當然地不做任何家務,向他要生活費的時候,也開始皺起了眉頭,嫌她花錢大手大腳,還對她抱怨現在經濟不景氣,掙錢艱難等等;兩人的對話越來越少,她發現自己已經開始跟不上他的思維,她的無知常得到他的奚落,偶爾想和他交流點什么,男人也常以“你懂什么”之類的話搪塞敷衍……
矛盾終于在一個夜晚爆發,那是緣于一道男人最愛吃的炒菠菜,剛坐上飯桌的時候,男人還是愉悅的,可剛吃了幾口,就聽他啊呀了一聲,她被嚇了一跳,問他怎么了,男人呸呸吐了幾口之后,才對她嚷道:“你怎么洗的菜?里面有沙子,硌了我的牙!”她趕緊解釋道:“我今天可能洗菜的時候匆忙馬虎了點,下次注意!”男人卻不依不饒了:“你知不知道我最怕吃到沙子啊?你每天班也不用上,全靠我養著,在家都忙什么呢?連菜都洗不干凈,你還會干什么?”說完惱怒地拂袖而去。
那一刻,她終于明白,那一粒沙背后掩藏的婚姻危機。
還好,她是個懂得自尊自愛的女人,那個夜晚過后,她拋棄了靠別人生活的想法,也放棄了那種無所事事的生活方式,開始了新的屬于自己的日子――讀書,充電,交友,擇業……半年之后,她重新成為一個人們眼中自信優雅的女人。
又是一個夜晚,她為男人做了一道清炒菠菜,而這一次,確實是因為時間緊張,菜洗得不夠徹底,男人再次被一粒沙硌了牙齒,她有些不好意思了:“算了,這菜別吃了,下次我一定洗干凈點!”不料男人并未生氣,反過來安慰她:“這有什么,不過一粒沙子嘛,再說你現在也挺忙的,能吃上現成飯我已經心滿意足了!”說著,把沙子吐掉,又大口大口地接著吃了起來。
第5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的確,回望歷史,我們發現以往人們需要數十年的苦心經營才可以積累起來的巨額財富到了今天可以縮短至幾年。姜奇平的感嘆還有下文,“運動員靠青春吃飯,財富創造無法持久,而互聯網卻沒有這種限制。”太多如馬云、李彥宏等人的創業故事不斷警示著我們,不論什么時代,只要卯足了勁在一個領域里深耕細作,揮灑青春堅持到底,就一定能夠做得優秀。這也是我今天中午與本刊年輕的COO季泓宇同志一起吃飯時達成的驚人一致。
21世紀已過完了它的第一個十年,十年于互聯網來說已是滄海桑田。站在2010年的節點上,我們看到了產業分工與升級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看到了因產業深入發展而必然產生的摩擦與博弈,如上半年的圖書新規、下半年的3Q大戰,我們看到了為創業者而生的互聯網新藍海。一切的一切,盡管是如此的粗暴甚至殘酷,然而卻又是那么的新鮮與生動。
如果一定要在這歲尾年初的時刻給即將過去的一年貼一個標簽的話,我想它一定是“和諧”。被譽為中華傳統文化核心的“和”是什么?戲謔的解釋是,“口”代表人,“禾”代表糧食,因此每個人都有飯吃就是和諧。巨頭騰訊與以網絡安全軟件為主業的小弟360爭利無異于斷了奇虎的糧,這當然不和諧。圖書新規也反映了國家相關部門欲置圖書網站于死地的不和諧之舉。兩大事件帶來的積極后果是引起了社會的反思,大中小企業各得其所、良性競爭的業界未來值得期待。
第6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關鍵詞:朱熹;《中庸章句》;“人-物”平等思想;生態觀
中圖分類號:B24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074(2013)01-0007-07
《中庸》開宗明義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并由此展開對于“中庸”、“誠”等概念思想的闡述;同時,《中庸》又講“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對于《中庸》所言,各家的解釋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朱熹《中庸章句》從人與物統一的層面作了獨特的詮釋,蘊含著人與自然萬物相互平等的思想;而這種“人-物”平等思想,與今天所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觀所必需的思想基礎。
一、人與物的統一
對于《中庸》所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漢鄭玄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效之,是曰‘教’。”唐孔穎達疏曰:“‘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兇,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人自然感生,有剛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于下,是‘修道之謂教’也。”[1]1625在鄭玄、孔穎達看來,《中庸》講“性”“道”“教”,只是就人而言的;講人之性源自于天,循性而有人道,修行此道而得以教化。
儒家重視人。據《論語?鄉黨》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應當說,孔子并不是不重視馬,而是認為,人比馬更為重要。雖然據《論語?述而》載: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但是,在孔子那里,魚、鳥之類肯定是不可與人相提并論的。《孟子?盡心上》講“仁民而愛物”,但更強調“愛有差等”,認為“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中庸》則明確講“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可見,在先秦儒家那里,人與物受到重視的程度是不同的。
與此同時,先秦儒家又講人之性與物之性的不同。《論語?陽貨》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講的是人之性。孟子講“性”,講人性之善,并且較多地講人之性與物之性的區別。據《孟子?告子上》載: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在孟子看來,人之性與動物之性有著本質的區別。又據《孟子?離婁下》載: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在孟子看來,人與動物的差異在于人之性與動物之性不同。
與此不同,朱熹《中庸章句》對于《中庸》所言“性”“道”“教”的詮釋,則從人與物統一的層面展開,指出: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相比于鄭玄、孔穎達,朱熹的詮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僅就人而言,后者則將人與物統一起來;具體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發明:第一,認為人與物都得自天所賦的共同之理,而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第二,認為人與物“各循其性之自然”而有各自的當行之道;第三,認為“修道”在于依據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對人與物作出不同品級的節制和約束。
二、人之性與物之性
朱熹從人與物統一的層面詮釋《中庸》所言“性”“道”“教”源自二程。二程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于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2]29-30認為《中庸》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通人、物而言”。
繼承二程的思想,朱熹也認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通人、物而言;并認為,人與物都有來自天之所賦的、共同的“天命之性”。他說:
“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為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物物各有這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3]1491
人與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則為人道,循馬牛之性則為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牛馳,則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3]1494-1495
朱熹還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3]1492明確認為,自然物也有與人一樣的仁、義、禮、智、信之性,所謂“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4]56。
朱熹甚至還認為,不僅牛馬、昆蟲之類有性,草木以及無生命之物也有性。他說:
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書燈便有書燈底道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5]2484
據《朱子語類》載: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階磚便有磚之理。……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焚灶,是無生意矣。然燒甚么木,則是甚么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4]61
朱熹還說:“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木燒為灰,人陰為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6]
朱熹《中庸章句》特別講“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不僅把仁、義、禮、智、信“五常”看作“性”,而且還增加了“健”、“順”。關于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朱熹說:“且如狗子,會咬人底,便是稟得那健底性;不咬人底,是稟得那順底性。又如草木,直底硬底,是稟得剛底;軟底弱底,是稟得那順底。”[7]375“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3]1490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講人與物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只是就人之性與物之性同出一源而言。朱熹講“性”,不僅講人與物共同的“天命之性”,還講人與物有氣稟的差異。朱熹說:“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4]58由于氣稟的差異,實際上又導致了人之性與物之性的不同。朱熹說:“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8]1378
關于氣稟的差異而導致人之性與物之性的不同,朱熹《孟子集注?告子上》注孟子所謂人之性不同于犬之性、牛之性,曰: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朱熹認為,人與物由于氣稟的不同,所得仁、義、禮、智之性就有全與不全的差別。所以,朱熹說: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后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于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9]507
在朱熹看來,人所稟之氣“正且通”,物所稟之氣“偏且塞”,因而造成人之性與物之性的差別,以至于貴賤的差別。另據《朱子語類》載: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4]957
朱熹認為,人之性只是明與暗的差別,可以由暗使之明;而物之性或偏或塞,“偏塞者不可使之通”。所以,在朱熹看來,人之性與物之性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很大的差異。
三、人之道與物之道
《中庸》講“率性之謂道”。在鄭玄看來,“率性”是指人“循性行之”;孔穎達認為,“率性”是“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認為人“率性”之后而有道。與此不同,二程說:“‘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10]10-11“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2]30認為“道”與“性”皆“通人、物而言”。
與鄭玄、孔穎達不同,朱熹認為,《中庸》“率性之謂道”不是人“率性”之后而有道,“率性”并非人為。他指出:
“率性之謂道”,性是一個渾淪底物,道是支脈。恁地物,便有恁地道。率人之性,則為人之道,率牛之性,則為牛之道,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后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3]1493
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于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于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9]551
在朱熹看來,人與物有“性”,就有相應的“道”,而與人為無關。
朱熹反對把“率性之謂道”的“率性”解說為人循“性”而為,認為“道”并非人為,而且特別強調“率性之謂道”,即“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3]1491。據《朱子語類》載:
安卿問“率性”。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率’字,亦只訓循。……曰:‘循牛之性,則不為馬之性;循馬之性,則不為牛之性。’乃知循性是循其理之自然爾。”
“率,循也。不是人去循之,……。程子謂:‘通人、物而言,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物物各有個理,即此便是道。”
問:“‘率性之謂道,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上說?”曰:“諸家多作行道人上說,以率性便作修為,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性是個渾淪底物,道是個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3]1491
在朱熹看來,“道”不是由于人循“性”而成,而是由“性”自然派生出來的;“率性”是指人與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循其理之自然”、“循吾本然之性”。因此,朱熹講“道即性,性即道”[11]82,認為“道”與“性”是同一的。
如前所述,朱熹雖然講人與物有共同的“天命之性”,但又認為,人與物所稟之氣的不同而造成人之性與物之性的差別。由于“道”是由“性”自然派生出來的,所以,人與物有其各自不同的“當行之路”,即“道”。這就是朱熹《中庸章句》所言:“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中庸或問》也說:“‘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9]550-551
四、“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
如前所述,朱熹《中庸章句》注“修道之謂教”曰:“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天下,則謂之教。”據《朱子語類》載:
問:“明道曰:‘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中庸》卻言‘修道之謂教’,如何?”曰:“性不容修,修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圣人于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誰能便于道上行!”[3]1495
問題是,什么是“品節”?呂大臨在解說“修道之謂教”時說:“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人稟于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于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于是,引《禮記?檀弓》孔子門人子游曰:“人喜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踴矣。品節斯,斯之謂禮。”接著又說:“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后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小不及者,不可以不修。此先王所以制禮,故曰‘修道之謂教’。”[12]271-272其中子游所言,說的是人的情感變化及其不同表達的各個層次:喜、陶、詠、猶、舞、慍、戚、嘆、辟、踴。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鄭玄注曰:“舞踴皆有節,乃成禮”;孔穎達疏曰:“品,階格也;節,制斷也。”[13]1304據此,人們把“品節”理解為“按品級而加以節制”(《辭源》)。
朱熹《中庸或問》在對“修道之謂教”作進一步解說中指出:
修道之謂教,言圣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于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于此者,亦或不能無失于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于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于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圣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范,以立教于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9]551
在朱熹看來,人與物有其各自不同的“道”,圣人能夠依據人與物各自不同的“道”對人與物作出不同品級的節制和約束,以立教于天下,這就是《中庸》所謂“修道之謂教”;而之所以只有圣人能夠做到,那是因為“圣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能夠克服“私意人欲”所造成的“乖戾舛逆”,能夠“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范”。
由此可見,在朱熹那里,“修道之謂教”中的“修道”,不是鄭玄、孔穎達的修治或修行“道”,而是指圣人依據“道”對人與物作出不同品級的節制和約束。對此,朱熹門人潘柄說:“‘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于人為,而實原于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朱熹后學饒魯說:“修,裁制之也。圣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也。”[14]在朱熹看來,所謂“修道之謂教”,是指人與物由于氣稟的不同而存在著差異,“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因此有可能背“道”而行;圣人則依據“道”而對人與物作出不同品級的節制和約束,立禮、樂、刑、政之屬,以教化天下。
在把“修道之謂教”中的“修”解說為“品節之”的同時,朱熹認為,“修道之謂教”也通人、物而言。據《朱子語類》載:
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修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夭殀’,‘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圣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范而及于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于人較詳,于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
問:“《集解》中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修道之謂教’,是專就人事上言否?”曰:“道理固是如此。然‘修道之謂教’,就物上亦有個品節。先王所以咸若草木鳥獸,使庶類蕃殖,如《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如周公驅虎豹犀象龍蛇,如‘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個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3]1495
在朱熹看來,“修道之謂教”不只是在倫理道德方面的教化,而且也包括在開發和利用自然物方面的品節防范,從而“使萬物各得其所”。
五、“與天地參”
《中庸》第二十二章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應當說,這段論述旨在強調圣人“至誠”對于“盡其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及“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重要價值。對于其中“與天地參”,朱熹注曰:“與天地參,謂與天地并立為三也。”顯然,在朱熹看來,“與天地參”,實現人與天地的和諧,是人類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標;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贊天地之化育”,也就所說,要通過人與自然的互動,并在輔助自然的過程中,達到與自然的相互補充、相互協調。
關于“與天地參”,戰國時期荀子也有過闡釋。《荀子?天論》講“明于天人之分”,但較多強調人對于天地的作用,指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愿其所參,則惑矣。”認為人與天地參,是指人能夠治天時、地財。所以,荀子反對放棄人力而順從天地,而要求“制天命而用之”。與荀子不同,朱熹則要求通過“贊天地之化育”。
關于“贊天地之化育”,程頤曾說:“‘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后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15]158朱熹贊同程頤的說法,指出:“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所為,各自有分’,說得好。”[16]1570而且,朱熹注《中庸》“贊天地之化育”曰:“贊,猶助也。”并指出: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卻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16]1570
在朱熹看來,天與人“各自有分”,有天所為之事,有人所為之事;而人所為之事,就應當是“贊天地之化育”。所以,他明確把“贊天地之化育”之“贊”詮釋為“贊助”。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還把“贊天地之化育”之“贊”,進一步詮釋為“裁成輔相”。所謂“裁成輔相”,源自《周易?泰》所引《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17]14關于“裁成輔相”,二程說:“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圣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圣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獲,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18]280可見,“裁成輔相”就是根據天地之道,教化百姓依道而行。朱熹說:
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卻須圣人為他做也。[19]259
天地之化無窮,而圣人為之范圍,不使過于中道,所謂裁成者也。[17]58
朱熹認為,天地間之萬事萬物固有其不完善之處,圣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使之完善。據《朱子語類》載:
問“‘財(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輔相者,便只是于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圣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圣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圣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20]1759
“財(裁)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圣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圣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20]1760
應當說,朱熹對“贊天地之化育”以及“裁成輔相”的詮釋,既是針對人類社會,也是針對天地自然;就后者而言,朱熹的詮釋包含了兩個重要思想:其一,由于“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應當積極主動地在與自然的互動中,通過彌補自然之不足,以滿足人的要求,而不是消極而被動地適應自然,甚至畏懼自然;其二,在與自然的互動中,人只是起到輔助自然的作用,只是補充自然的不足,而不是肆意破壞或“改造”自然。正是通過這種人與自然的互為補充,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需要指出的是,在朱熹那里,“贊天地之化育”并不是從人出發。朱熹說:
凡有形于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參天地、贊化育,然后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于外也。[21]141-142
在朱熹看來,“贊天地之化育”就是要對于不同的物,要給予不同的對待,應當“若其性、遂其宜”,也就是要根據自然物的特殊性,合理地予以對待,而不是外在的強加。他還說:“‘贊天地之化育’,皆是實事,非私心之仿像也。”[16]1570認為“贊天地之化育”不是依據人的主觀模仿和想象。為此,朱熹特別強調對于天地自然萬物的認識。他說:
圣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獺祭魚,然后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后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22]256
在朱熹看來,要使萬物各得其所,就必須“因其性而導之”,就是要根據自然物的不同物性,順其性而為,合理地加以開發和利用,“取之以時,用之有節”;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先要“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知得萬物之性。
顯然,朱熹講“贊天地之化育”,就是要求對自然物的“取之以時,用之有節”;從廣義上講,就是要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上,對自然物的合理開發和利用;“取之有時”,就是開發自然物須“有時”;“用之有節”,就是利用自然物須“有節”。他認為,能夠“贊天地之化育”,就可以“與天地參”,實現人與天地的和諧。
六、結語
綜上所述,朱熹通過對《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及“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的詮釋,從人與物統一的層面,討論了人之性與物之性、人之道與物之道的關系,進而要求“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并通過“贊天地之化育”,達到“與天地參”,實現人與天地自然萬物的和諧。顯然,其中蘊含著人與自然萬物相互平等的思想,即“人-物”平等思想。重要的是,這種“人-物”平等思想,不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是強調人與自然萬物在相互平等基礎上的互補與協調,與今天所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觀是一致的。
參考文獻:
[1][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M]//十三經注疏: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
[2][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M]//二程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3][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二[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一)卷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七)卷九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5.
[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徐子融(三)[M].四部叢刊初編本.
[7]黎靖德.朱子語類(二)卷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5.
[8][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五十九[M].北京:中華書局,1985.
[9][宋]朱熹.朱子全書:第6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0][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一[M]//二程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1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一)卷五[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2][宋]呂大臨.禮記解?中庸[M]//藍田呂氏遺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
[13][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九:檀弓下[M]//十三經注疏:下.北京:中華書局,1980.
[14][明]胡廣.四書大全?中庸章句大全上[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M]//二程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
[1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四)卷六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7][宋]朱熹.周易本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宋]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上[M]//二程集: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9][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一)卷十四[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五)卷七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5.
第7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從《尚書》、《周禮》到《說文解字》,“和諧”兩字都是指音樂的合拍與禾苗的成長,“和”即是“諧”“諧”即是“和”,引申表示為各種事物有條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協調,即《中庸》里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周禮》中說的“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所謂“執中至和”,就是通過正確方法,實現美好理想,達到事物發展的最佳境界。故此,和諧社會應該是社會的各種要素相互協調,社會結構合理,社會運行有序,人各得其所,地各得其用,物各得其流,社會中的各種事物具有良好的生長和發展環境的社會。
和諧社會不僅僅在于它的物質意義,更在于它的精神意義,不僅要物質豐富,更要讓每個社會成員之間互相認同和接納,身心愉快。儒家的社會倫理思想在尊尊、長長和男女有別的前提下,融入了親親意識,在身份和等級不能完全消除的情況下,不同身份、不同等級的人之間,用親情、友情、溫情連接著。所以從倫理的角度看,和諧社會又應該是一種充滿仁愛,到處洋溢著溫情、善良和互相幫助的社會。這就是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和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雖然這里的“和”沒有反對等級和差別,也沒有指望消滅不平等,反而在一定意義上肯定了等級和差別的合理性。但孔子又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和”與“同”的區別在于是否承認差異性,有差異性的統一謂之“和”,無差異性的統一謂之“同”。也就是說,君子善于協調、統一各種不同的分歧意見,達成新的共識。而小人則不能正確對待不同意見和分歧,只會對不同的意見加以排斥,將相同的意見簡單累加。”和”的實質是“包容”,“同”的實質是“排斥”。所以“和”又有反對絕對同一,反對簡單服從,主張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意義。因此,和諧社會應該是一個思想活躍,包容萬芳,多種文化共存的社會。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眾多的和諧社會模式,而尤以儒家描述的“大同社會”最具代表性。《禮記禮運》里說:“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所呈現的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氣象,人人相親相愛,沒有壓迫,沒有戰爭。
錢穆說:“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天人合一”代表著中國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統一。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道家認為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自然的法則主宰人世間的一切,所以人要敬畏自然、效法自然、順應自然。老子在《道德經》中反復強調“道”的功能和作用“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而以為天下正。”(《道德經》第三十九章)“道”既然是自然界的變化法則、規律,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經》第二十五章)就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之事。而在儒家的孔子那里,盡管“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論語公冶長》)但他又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意思是說,要治理好天下,必須效法天道。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的學說,并試圖在“天人合一”的思想體系中確立起一個道德本體,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在孟子看來,天人是相通的,而這個相通又是在存心、養性與修身等意義上的“天人合德”(天人皆有德)。“天人合一”的命題是在《易傳》中首先明確提出來的。原文是“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兇。為什么“天”與“人”能夠“合一”呢?就是因為“天”與“人”之間有“合其德”的關系。這種“天人合德”關系包括了四種相合關系:與天地同德,厚德載物;與日月同輝,普照一切;與四時同律,井然有序;與鬼神同心,毫無偏私。這實際是將“大人”的個人品格及其高尚行為作了全面概括,只有具備這四種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人”。孟子將這種“天人合德”的思想加以發揚光大,他進一步闡述道:“天之道”與“人之道”是有誠相通、相互感動的,主張“樂天”、“畏天”。他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并提出“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孟子梁惠王下》)的以德治國主張,認為“仁則榮,不仁則辱”,“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以“德”為橋梁,將天人、物我連接成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近而把德通過天人合德關系從個人品格修養拓展到治國理念與實踐上來,體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情懷。
古人的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還進一步表現為愛護資源,保護生態系統的生態倫理觀。《周易》特別提倡古代天子打獵用的“三驅法”,不主張對野生動物一網打盡。《比》卦九五爻辭說“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意即:最明顯的比附措施是用“三驅之法”,放走前面的野獸,使周圍的邑民百姓沒有戒備之心,這樣才是吉利的。什么叫“三驅之法”呢?《周義正義》解釋說:“凡三驅之禮,禽向己者則舍之,背己者則射之,故失其前禽也。”這樣可以保證野生動物資源不枯竭。孟子則進一步將這種生態倫理觀發揮為“王道之始”。他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撼也。養生喪死無撼,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把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否上升到人類生存發展和社會安危的高度。
修身養性——人與自我的和諧
儒家和諧社會的理想是建立在個人道德修養提高的基礎上,因此,儒家特別強調通過正心、誠意、修身來規范人的行為,強調由道德學養的提升以求身心內外的和諧。孔子認為人只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精神生活,特別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愛為中心,推演出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把培養有道德的人作為學問的根本,認為這是社會穩定和諧的根基。在為人處事、修身養性方面,孔子特別講究“允中”、“執中”。所謂“中”,是說凡事應該有一個適當的度,超過這個度,就是過,沒有達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處理事情,要合乎這個度,就是“執中”。關于中的含義,孔子自己解釋為“過猶不及”、“執兩用中”、“中立不倚”。《論語先進》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意思是說,子貢問孔子:子張與子夏哪個好一些?孔子說:子張有些“過”,子夏卻顯得“不及”。子貢說:那么,子張好一些吧?孔子說:“過猶不及”。可見,在孔子看來,“中”就是既“無過”,也無“不及”。同時,孔子又認為,作為衡量標準的“中”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時間和條件的改變而改變,必須靈活運用。在從政上,“邦有道,則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在行為上,他主張中行“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認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養境界。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張“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溫不厲…‥恭而安”(《論語述而》)在
審美判斷上,主張“樂而不,哀而不傷”。(《論語八佾》)
道家也主張以謙下不爭、清靜無為的方式達到人的身心和諧。“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老子第四章》)老子還強調修身養性要做到有自知之明、克服自身的弱點、堅持力行、人總要有精神等“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老子第三十三章》)莊子則在《大宗師》中為人們描繪出“真人”的精神境界,鼓勵人們去學習效仿,以求得心靈的寧靜與平和。“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直宜而莫知其極。”
推己及人——人與人的和諧
第8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關鍵詞:馬克思交往理論社會主義全面發展和諧社會
中圖分類號:C913.2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0)011(C)-0211-02
一、馬克思交往理論與人的全面發展
馬克思對于人的全面發展有著系統而深入的論述,馬克思認為,人自身的發展經歷三個階段:“人的依賴關系(最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
交往在人的全面發展得以實現的過程中起著基礎性作用。馬克思說:“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隨著交往的不斷擴大,社會對人的能力、素質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同時,社會交往的發展使人的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得以不斷張揚,人的個性才得以自由而全面發展。
人的全面發展是交往有效性實現的前提條件。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曾列舉了當今時代存在的三種合法性危機:
(1)當相互理解的需要無法從文化的知識儲備中得到滿足時,便會出現“合法性危機或信仰危機”,這時,“意義的儲備”發生短缺,無法對一些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
(2)當相互協調的需要無法從合法的制度中得到滿足時,便會在社會一體化方面出現障礙,“社會同情”的資源將發生短缺。
(3)當社會化進程中出現的障礙再也無法在傳統的、被承認的行為環境中被排除,當心理病態和異化成為普遍現象時,便會發生“自我同一性”資源短缺。
哈貝馬斯認為要解決當今時代存在的這三種合法危機,就必須實現交往的三個有效性的要求,即判斷、陳述的真實性,遵循規范的正當性和表達自我的真誠性。
然而,交往有效性要求能夠在人們的交往行為中實現,其內在的根源就在于:行為者需要有能力基于他們的生活世界,反思性地面對作為整體出現的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在這種反思關系中,行為者不再與三個世界中出現的事物發生直接的關系,而是把上述三個世界作為整個世界來理解,并依據解釋、商討的方式和原則,對事態做出相應的表達。行為者所需要形成的這種能力就不能不以人實現全面發展為前提。
因此,交往在為人的全面發展奠定基礎的同時,人的全面發展也為交往的進一步擴大提供了更加宏大的歷史背景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系
1、“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的內在邏輯。所謂“和諧’,就是協調,具體地說,就是事物的各個組成部分或組成要素之間的相互協調。因此,以協調來推動發展就成為和諧社會的基本發展模式。
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因此,社會主義社會是充滿創造活力的社會,體現為人的各方面潛能不斷得到充分發揮。在社會主義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中,促進人的潛能逐步得到發展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關鍵環節。與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前發展相適應,社會和諧程度與人的全面發展也表現為一個分層次、逐步實現的過程。在此過程中,隨著社會和諧程度的提升,人的各種素質將向著全面的方向發展。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要造就一代又一代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人,并以此來進一步推動社會主義的健康發展。
社會主義社會堅持以人為本,凸顯人的社會主體地位。我們黨從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把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培養“四有”公民,看作是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和諧、推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這表明,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要培養和依靠全面發展的人,從而在實踐上把提高人的素質、發揮人的作用問題融入到建設和諧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進程之中。
2、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雙向互動。
在建黨八十周年的“七一”講話中,著重提出人的全面發展的思想,既把它作為現實社會主義追求的人文價值取向,也把它作為孕育一個全新的執政理念和實踐目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邏輯起點。
一方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社會將使人更充分地獲得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人自身的和諧就是逐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它必然要求社會成員個性和諧、精神和諧,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心態以及豁達的生命情懷,能真正融入自然、融入社會。這樣,未來社會將把“創造著具有人的本質的這種全部豐富的人,創造著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作為這個社會的恒久的現實。”
構建和諧社會是真正從作為現實生活的具體人出發,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
另一方面,人的全面發展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主體保障。只有全面發展的人,才能駕馭生產力、科學技術和交往形式的巨大進步,“因為現存的交往形式和生產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發展的個人才可能占有它們”。而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全面發展,正是推進社會趨于和諧的動力。
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與實現社會和諧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和雙向互動的。這種一致性就要求我們要把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協調起來,不能以犧牲人和社會的發展為代價而單純追求經濟的一時繁榮,而是要具有長遠的戰略眼光,使經濟社會和人相互促進、和諧地發展。
三、交往理論與和諧社會的統一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成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尤其是以網絡為特征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我國公共領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泛交往。交往的不斷擴大和深入,為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帶來了不斷發展變化的各種問題。所以,我們要深入研究交往與和諧社會的關系,以交往促進和諧,以和諧規范交往。
第一,社會和諧的基礎條件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人的全面發展都必須在人與自然的協調與和諧中得以實現。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在發展變化。科學技術為人類創造出驚人的物質財富,使人們在征服自然中獲得了極大的解放。但人與自然的對立也隱含著巨大的危機,過度地開發征服自然、違背自然的規律,使當代人類面臨著嚴重的生態失衡、環境污染和人口膨脹等危機。如果人類不解決好這些問題,勢必會造成社會發展失去平衡、動蕩甚至災難。因此,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必須協調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使人們在優美的生態環境中工作和生活。
第二,建設和諧社會必須從根本上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社會和諧從本質上來說是人的不斷發展所形成和表現的一種社會存在狀態。而人在本質上是社會的人,人的不斷發展,離不開社會的和諧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各個方面的制度還不完善、不成熟。因此,必須高度重視人民民主,強調德治與法治的統一,關心社會的公平與公正,關注全民素質的提高,以求促進社會和諧,推進人的全面發展。
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個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統一。人類交往活動的目的是為了生存和發展,而社會的發展本質上是人自身的發展和人的本質的生成過程,因此,人的全面發展和人的本質的實現是一個與社會交往相統一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三種不同關系之上,同樣,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也統一于這三種關系之中。
第9篇:各得其所的解釋范文
隨著《刑法修正案八》將扒竊作為盜竊罪的一種寫入刑法,有關扒竊的司法難題也日益凸現出來,扒竊既遂標準的認定是其中之一。關于扒竊的既遂標準,司法實務中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扒竊是行為犯,亦即只要行為人完成了扒竊的行為,而不需要竊得任何的財物,行為人的行為就構成扒竊的既遂。另一種觀點認為,扒竊是結果犯,扒竊必須竊得財物才構成既遂,但其又認為竊得的財物沒有數額上的要求,哪怕只竊得一元錢也構成既遂,因為扒竊在一般情況下是一種以竊得不特定財物為概括目的的目的犯,竊得財物就達到了目的。
二、以法益為核心作出的分析
(一)通過文義解釋,我們發現,刑法第264條實際上將盜竊分成了兩大類:一類是普通盜竊,其必須滿足數額較大的條件;一類是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由此可以看出,第二種類型的盜竊犯罪肯定不需要達到數額較大才構成既遂,但我們是否就因此從表面上認定,扒竊是一種行為犯或者扒竊既遂的構成不需要犯罪結果達到特定的數額?試想,一個人在公共汽車上實施了扒竊行為,結果只竊得了5元錢,而另一個人將農民曬在場上的糧食偷走,糧食價值1000元,現在刑法要對這兩種行為作出同樣的評價,我內心感到強烈的不平等,我感到它既沒有遵循西塞羅的“各得其所”原則,亦未實現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然而純粹的情感不足以說服他人,必須進行論證說理。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該法律條文進行論理解釋,以探究其之精神。
(二)德國法學家認為,刑法之所以設立行為犯,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行為人雖僅著手于未遂階段,但幾乎已不可能對于由此產生的危險加以控制,如內亂罪;第二,未遂行為本身已對法益造成了破壞,因而有必要將未遂與既遂相提并論。對照這個標準,我們來觀察扒竊行為,首先扒竊不屬于一旦著手就難以控制由此產生的危險的犯罪類型;同時,扒竊竊得財物與未竊得財物應該還是有很大差別的,不能相提并論。因此,不宜將扒竊認定為行為犯。
(三)應該肯定扒竊是結果犯,這是由刑法設立此種罪名所欲保護的法益所決定的。刑法設立盜竊罪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護公民的所有權或占有(究竟是所有權還是占有尚有爭議)不受侵害,扒竊作為盜竊的一種也不例外。有人也許會認為,刑法既然將扒竊單列為盜竊的一種,其必然保護一種普通盜竊罪所不保護的法益。這種觀點并不錯,因為扒竊往往在公共場所實施,其給公眾心理造成了一定的恐慌,破壞了狹義的社會秩序。然而,這不能改變扒竊是結果犯的定性,因為設定扒竊型盜竊罪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公民的所有權或占有,保護公共秩序只能是其次要目的。那么,為什么說法益決定犯罪構成(我們亦可稱之為犯罪的既遂標準,行為犯、危險犯、結果犯都是具體的犯罪構造)?這是因為,法益的性質不同,重要的程度不同,決定刑法要采取不同的保護手段。對于保護一旦受侵危害結果就難以控制的法益,要采取行為犯的犯罪構造,亦即刑法要及早介入,對于實行完畢的危害行為,不待其產生危害結果,就將其視為完整的犯罪行為,并對其科以刑罰。而保護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或財產安全這種重要法益,刑法需要更加提前介入,而采取危險犯的犯罪構造,對于造成一定危險狀態的危害行為就要定罪科刑,以達到最大程度上保護法益的的目的。至于保護像財產權、公共秩序這樣的一般法益,出于對保障公民自由和維護社會安全的權衡,刑法采取結果犯的犯罪構造,亦即此類犯罪既遂的成立以危害行為引起一定的危害結果為前提。因此,設立扒竊型盜竊犯罪主要是為了保護公民的財產權,刑法的這一立法目的決定了扒竊是結果犯,扒竊既遂的成立必須以竊得一定得財產為前提條件。至于這一定的財產,其數量不可過于微量,因為扒竊中的這個“扒”字只是一種情節,而其真正決定扒竊性質的還是“竊”字。盡管偉大的法學家薩維尼教授說過,解釋法律不能如同做數學題那樣清晰明了,但此處我們還是要解一個簡易的方程。由于對兩種類型的盜竊犯罪,刑法所規定的法定刑是相同的,那么我們可以列出這樣一個等式:普通盜竊行為(a)·數額較大(b)=扒竊行為(c)·數額(x),已知條件為c>a。據此等式,我們可以解出b>x,然而這個解只給出扒竊既遂數額的上限,而沒有給出下限。我認為,這個下限數額應該參考多種因素,包括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居民對扒竊行為的容忍程度等。為了維護司法的統一,最高司法機關應該及早制定相應的司法解釋來明確扒竊既遂的數額標準。